中国传统儒家司法伦理道德探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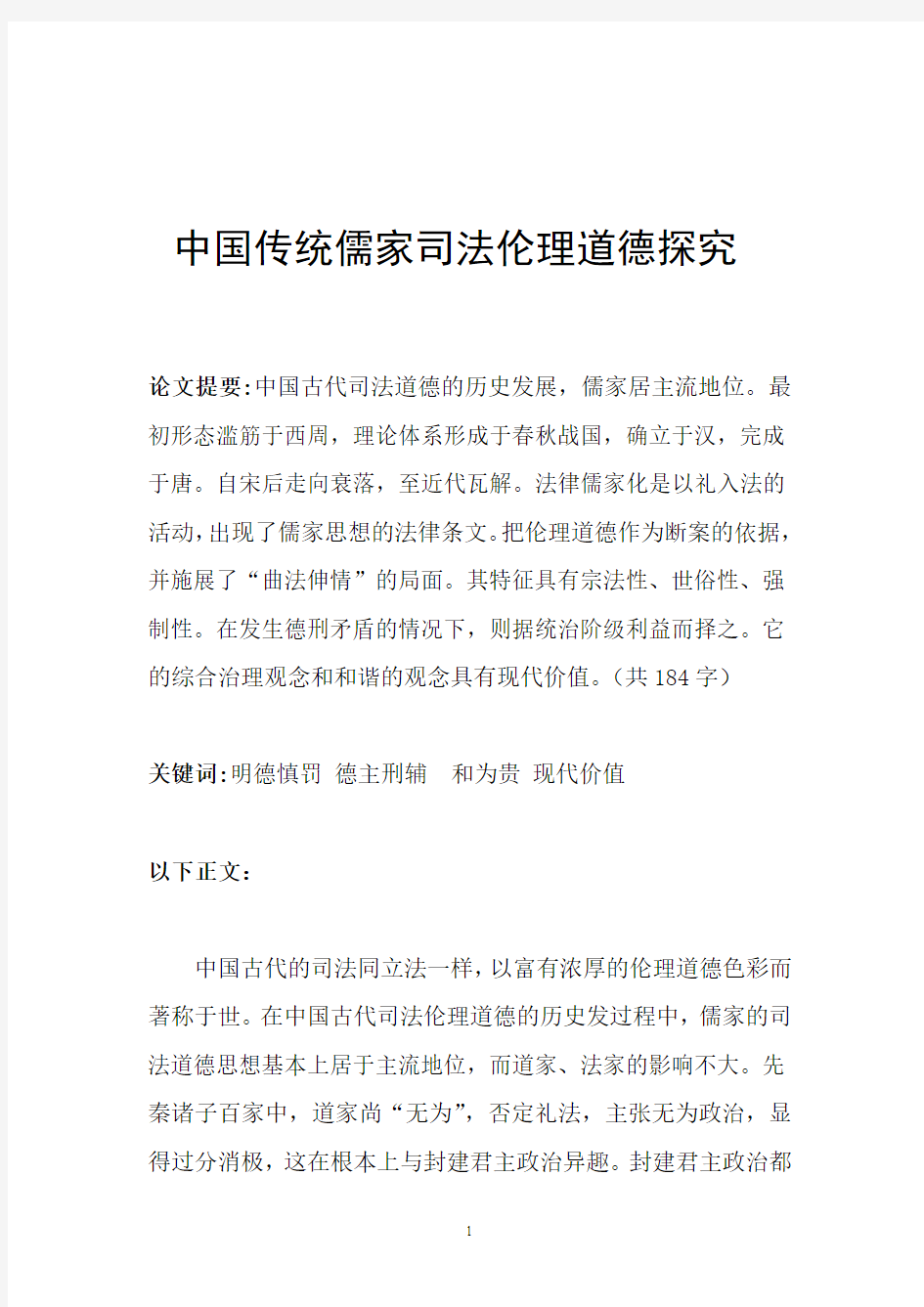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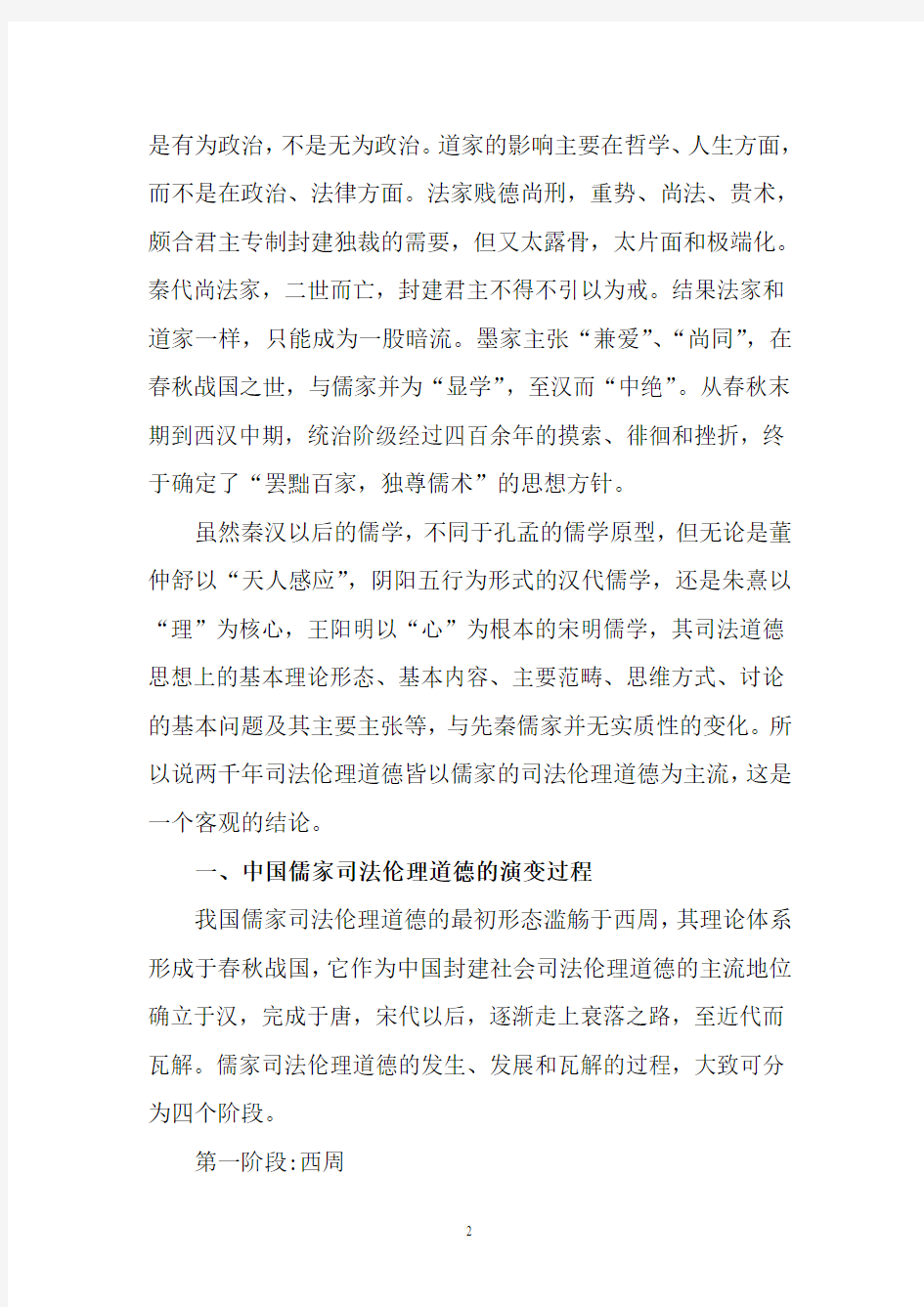
中国传统儒家司法伦理道德探究
论文提要:中国古代司法道德的历史发展,儒家居主流地位。最初形态滥筋于西周,理论体系形成于春秋战国,确立于汉,完成于唐。自宋后走向衰落,至近代瓦解。法律儒家化是以礼入法的活动,出现了儒家思想的法律条文。把伦理道德作为断案的依据,并施展了“曲法伸情”的局面。其特征具有宗法性、世俗性、强制性。在发生德刑矛盾的情况下,则据统治阶级利益而择之。它的综合治理观念和和谐的观念具有现代价值。(共184字)
关键词:明德慎罚德主刑辅和为贵现代价值
以下正文:
中国古代的司法同立法一样,以富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而著称于世。在中国古代司法伦理道德的历史发过程中,儒家的司法道德思想基本上居于主流地位,而道家、法家的影响不大。先秦诸子百家中,道家尚“无为”,否定礼法,主张无为政治,显得过分消极,这在根本上与封建君主政治异趣。封建君主政治都
是有为政治,不是无为政治。道家的影响主要在哲学、人生方面,而不是在政治、法律方面。法家贱德尚刑,重势、尚法、贵术,颇合君主专制封建独裁的需要,但又太露骨,太片面和极端化。秦代尚法家,二世而亡,封建君主不得不引以为戒。结果法家和道家一样,只能成为一股暗流。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在春秋战国之世,与儒家并为“显学”,至汉而“中绝”。从春秋末期到西汉中期,统治阶级经过四百余年的摸索、徘徊和挫折,终于确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方针。
虽然秦汉以后的儒学,不同于孔孟的儒学原型,但无论是董仲舒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为形式的汉代儒学,还是朱熹以“理”为核心,王阳明以“心”为根本的宋明儒学,其司法道德思想上的基本理论形态、基本内容、主要范畴、思维方式、讨论的基本问题及其主要主张等,与先秦儒家并无实质性的变化。所以说两千年司法伦理道德皆以儒家的司法伦理道德为主流,这是一个客观的结论。
一、中国儒家司法伦理道德的演变过程
我国儒家司法伦理道德的最初形态滥觞于西周,其理论体系形成于春秋战国,它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司法伦理道德的主流地位确立于汉,完成于唐,宋代以后,逐渐走上衰落之路,至近代而瓦解。儒家司法伦理道德的发生、发展和瓦解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西周
周公认为殷商王朝“早坠”,无怪乎天命,而是无德的必然。在总结封王酷刑毁政,乱刑亡国的惨痛教训时,提出“明德慎罚”的思想,针对武庚三监叛乱后的形势,如何对待处理殷民的归顺,关系到西周王权的存亡。周公便把明德与德用作为治国治政的手段,实行怀柔政策,重视教化,勿滥刑杀,于先教而后刑之中,体现宽严适当,德刑并施,从此中国古代对法的思维方式被导向了伦理型,周公开创的伦理与法律结合起来的先例,实为中国古代司法伦理道德的奠基者。
第二阶段:春秋战国
儒家尊重家族血缘基础以及由此产生的宗法礼教,并因袭和弘扬周公传统,创立了礼的体系,初步完成了司法伦理道德的理论建设。例如孔孟为代表的德治思想,就是反对苛政和严刑峻法,注重道德感化,强调统治人民不应单靠刑罚。在重德轻刑的前提下,当教化不起作用的时候仍可使用刑罚,以“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两手治理国家。
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是讲折狱持平,公正中直,不枉不纵,不潜不滥,不杀无辜,不诬无罪的意思。孔子提出的中庸主义的法律方法论原则,在儒家司法伦理道德中占极重要的位置,不仅指导刑事立法,刑事诉讼,而且贯穿于整个司法伦理道德之中。可是在当时,儒家这一套司法伦理道德的思想理论,不但不为统治者所重视,而且处处受到排斥。礼的精神在法律建设中的地位
远远不如法家学说来得重要。
第三阶段:两汉至清
秦王朝奉行法家政治的失败,加快了儒家司法伦理道德的振兴,经过贾谊,特别是董仲舒的理论论证和思想重建,以及贤良文学在“盐铁会议”上的努力,儒家司法伦理道德思想体系的主流地位初步确立。
西汉董仲舒把孔孟的“德治”思想发展和概括为“德主刑辅”。从此历代王朝都毫无例外地把“三纲五常”列为德治的主要内容,而且都明确要求立法和司法必须严守儒家伦理道德的信条。在这种情况下,推行由董仲舒提倡和汉武帝支持的“经义折狱”便成为封建王朝运用儒家伦理道德原则指导和改造司法活动的重要手段。除依法令断狱外,还可以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审判案件的根据。但是,所标榜的“原心定罪”实质上是既定法律不顾的罪行擅断主义,审判者可以按照自己理解经文的意思,随意为权贵们开脱罪责,镇压和陷害劳动大众。
自西汉后期起.对儒家司法伦理道德顶礼膜拜,并在司法实践中继承法律儒家化的传统,制定了许多以儒家司法伦理道德为指导的法典,大大推动了伦理道德的法律化。汉律规定“鞠狱不实”、“故纵故不直”等职务罪,提出“慎狱”就是司法官吏必须履行的职责和应遵循的司法道德。除此汉律中按儒家思想制定的法律条文还有:其一亲亲得相首匿,儒家把父为子隐叫“仁”,子为父隐为叫“孝”,认为这是一种正直的品德。其二定不孝为重
罪,儒家提倡幼辈对尊长的孝道,不孝不可容忍,所以加重了对不孝罪的处罪。其三先请制度,这是儒家“刑不上大夫”思想下,出现的贵族官吏的特权。其四秋冬行刑,是以儒家阴阳五行的理论为依据,进行刑罚顺应天时阴阳之变。
如果说两汉是揭开封建法典儒家化的序幕,那么魏晋南北朝推动了法律向儒家化的发展,以儒家思想为根据制定的刑法原则,基本上始创于这一时期。
魏律出自儒生之手,自然吸收了前代儒者所崇奉的理想制度。东汉后期,流行着儒家宣扬的“八议”,但未人律,曹魏改律,采纳了汉儒这一主张,制定了“八议”制度,进一步扩大了贵族的法律特权。
晋代修律之人,多为儒学大家,使晋律成为一部儒家化程度较深,对后世影响颇大的重要法典。首先是礼、律并重。儒家经典取得了与法律并驾齐驱的地位,其突出的标志是礼、律并等,人们常把礼与刑相提并论。其次法律规定父母死,吏民都要依礼居丧。对违者给予处置。太子洗马(官名)郤洗的母亲去世,因贪不能归葬,便在京城住所处置空棺安葬,三年服丧期满后继续在京作官。后因告发其为母假葬被弹幼。再次准五服治罪,按礼教之意,对冒犯尊长的亲族成员的刑法处罚要重于常人,被冒犯者与冒犯者的血缘关系越近,处罚也就越重。
南朝法律以儒家思想为依增设“官当”制度。北朝法律确立“重罪十条”,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君权和父权,所以将损害
君和父的犯罪被列为主要打击对象。此外,在儒家以孝治天下思想的影响下首创了“留养”制度。
在上述汉魏晋南北朝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儒家以礼入法的活动从汉代开始,陆续出现了一些以儒家思想为依据的法律条文。自曹魏至北齐,各王朝纷纷在吸收前代法律的基础上又不断创立新制,每一朝又加人若干新的儒家因素,内容越积越多,体系也越益精密。
到了隋唐,统治集团毫不迟疑地宣布儒家思想在立法、司法中的主导地位,使法律儒家化日趋完善。当时著名的儒学纯厚之辈都参加了法律的制定和注释。唐律标志着儒家司法伦理道德的统治地位最终确立,彻底改变了法律思想与法律条文两张皮的状态,将儒家司法伦理道德与法典有机地融为一体。史称唐律“一准乎礼”。说明唐律集前代儒家化法律之大成,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地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而又十分完备的封建法典。至此,从汉代起的法律儒家化活动,终于以其确立在中国封建法律中的正统地位而告完成。
宋代以后,儒家司法伦理道德经过统治者的极端化,被当作维护统治地位的法宝,越来越被推崇和强化。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如遇到德刑矛盾时,为了渲染礼教纲常,有时干脆舍弃法律,把伦理道德原则作为断案量刑的依据,这就是统治阶级贯用的“曲法伸情”的手段。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面对风俗教化每况愈下的危局,统治阶及对施展“曲法伸情”一招更为重视。
第四阶段:近代
随列强炮舰涌进中国的,不仅是鸦片,还有西法。这加速了儒家司法伦理道德的灭亡。值得一提的是著名法学家沈家本,由他主持的清末修律,宗旨之一是改重为轻,开创了中国近代法制的先河.他的法律思想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慎刑思想,比较全面地批判了古代繁刑严诛的重刑主义,抨击死刑的滥用和行刑之酷虐,彻底否定和坚决废除肉刑。当然靠沈家本的修律是无法改变封建专制,更何况清末修律,原本是预备立宪骗局。但客观上宣告了儒家司法伦理道德作为法律的指导思想和内在的历史终结。此后,儒家司法伦理道德只是作为历史上的法文化心理传统遗存在中华民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心理之中。
二、中国儒家司法伦理道德的特点
儒家司法伦理道德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中确实起到了法律的功能,中国古代的法律就是以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色彩著称于世的。儒家司法伦理道德作为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客观实在的法学结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宗法性。儒家司法伦理道德以血缘情感为心理基础,以宗法人伦为主要内容,其核心是“三纲五常”。宗法制度在西周演变而成,秦汉则成宗族制度,明清以后变为家族制度。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万变不离其宗,血缘纽带一直未受到根本的松动,以等级制度,亲属关系为社会核心组织的性质却坚实地固定下来。古人关于礼的定义有百种之多,探其本源,不外是宗法伦
常。由此而决定了血缘尊卑,身份贵践,权力和财产的分配。宗法家族伦理被视为法的渊源,并凌驾于法律之上,以朝廷和家族为本位,因此古代的法律最主要的精神仅有两条,孝于宗族和忠于王朝。
(二)、世俗性。中国古代法不完全表现为神权和宗教形式,而是法律与世俗伦理的直接靖合。儒家司法伦理道德植根于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的深厚土壤之中,其理论是实实在在的世俗伦理,不同于超凡的宗教,也有别于先验的理性。儒家的伦理不是神秘的信仰,而是安身立命的准则,生活实践的规范。同当时的法律一样都不是神权法,而是直接来源于君王权力之下的治民之术。
(三)、强制性。伦理道德与法律,两者作为外在的强制力量和行为规范,其社会价值和职能是一致的。在中国古代,道德本身就是法律。礼义道德脱离了原来的含义,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它从应该走向必须,从内在道德走向外在行为规范。即它在保存自身伦理道德特征同时,对自身内容进行外化、超越,从而具有法律约束功能。首先,是以国家系统的暴力为主要手段的直接政治性强制为手段的约束;其次,是以家庭强制、宗族强制、乡党强制;再次,是无视正当权利、完全以义务为本位的观念性强制。“饿死是小,失节是大”以放弃生存权利履行封建道德义务,以确保儒家司法伦理道德的作用。
三、对儒家司法伦理道德的辩证分析
儒家司法伦理道德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对推动废止肉刑、减少冤狱、创立恤囚制度曾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是维护特权、罪刑不一、腐朽的司法体系的辩护士。以封建统治阶级在司法活动中对待德、刑矛盾的态度,无非是两种情况。
(一)、在发生德刑矛盾的情况下,如果道德会带来弊大利小的后果,统治阶级就会置道德于不顾。在封建社会里,审案中的拷执之制,刑罚中的酷刑,残忍至极,同儒家标榜的“宽厚”等道德精神可谓谬之千里;族诛之法,与儒家倡导的“善善及子孙”的道德信条也大相径庭。可是这些严刑却被历代王朝奉为至宝,竞相使用。封建统治阶级一边说儒家道德的核心是“仁”,鼓吹“仁者爱人”,“先德后刑”,一边又肆意诛戮,残害百姓;一边宣扬要“守法行仁”,“秉公无私”,一边又带头贪赃枉法,毁坏法律,这种德行不一的矛盾,实质上不过是封建制度腐朽性和地主阶级残暴本性的表露而已,是君主专制主义自身固有的。
(二)、如果在司法活动中德刑相悖时,道德能带来利大弊小的结果,儒家伦理道德的作用就会受到重视。刑法属于次要地位,德教与刑罚的控制手段是不相同的.在表现形式上德教主要依靠内省、自觉的自我控制。调解制度便应运而生,依靠家族力量进行和解。调解又是对于司法诉讼的补充,它以儒家的“礼之用,和为贵”为原则,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依据,和睦无争即为“合礼”,告状即为“失礼”。息讼当然是以德教民而化争。在中国古代最初是民间调解,企盼将争端化解于成讼之前。但有些争端终
究化解不去,而非对薄公堂不可,当然和解精神与原则是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的,于是又有了法庭调解。在成讼之后,也希望尽快息讼,至于消除的手段,自然体现着“礼教”。注重维护宗法社会秩序,达到天下太平。实际上完全的“无讼”是办不到的,“出礼则人刑”,“刑禁已然”。
四、中国儒家司法伦理道德的现代价值
对于儒家司法伦理道德,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
其一是它的综合治理观念。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它强调法律与伦理的结合,惩罚与教化的互补。”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礼记·缁衣》)。这种立足于教化并强调刑罚力量的学说,表现出异常的清醒和理智的态度。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出现了不少新情况和新变化,人民内部矛盾日益增多,并体现出自身的特点,具有多发性、多样性、复杂性、多变性。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已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较难处理,单靠某一部门,采取某一手段,都是难以奏效的。必须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大力加强和改进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同时积极运用法律等手段的综合治理,才能及时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防止激化,促进社会稳定和人民团结。
其二是和谐的观念。儒家希望人类社会是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和睦大家庭,然而社会常常会出现不和谐的
局面,原因何在?儒家认为由残暴政治所造成,“苛政猛于虎”,所以儒家主张“仁政”,施行礼教,以最大限度减少摩擦,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还从心性层面来消除不和谐的根源。即通过“吾日三省吾身”的方法,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完善人格,以此来维护内心平衡,化解暴力与冲突。法律是他约,道德是自约,一个社会完全依靠他约,而没有自约,是难以健康发展的。在“德主刑辅”历史传统的国度里,更应注重道德教化作用。现行的人民调解组织,实际上是古代“和为贵”的沿袭,对民间纠纷的调解起了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同步推进,使道德规范化,各行各业都制订了文明公约。居民守则,乡规民约,具有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功能,按这些规范化解矛盾易于人们接受,矛盾双方心服口服,从根本上解决了矛盾产生的主观起因。
如今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里,要建立高度的文明,无视历史传统的影响是不行的,对传统的文化只能是扬弃,而不宜全部摒弃,儒家传统的司法伦理道德对于法制、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司法伦理的建设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
(2)朱熹:《春秋繁露》,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
(3)孙钦善:《论语注释》,巴蜀书杜1999年出版。
(4)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76年出版。
(5)司马迁:《史记》,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出版。(6)何勤华:《中国法学史》,法律出版社2000年出版。(7)张国华:《中国法思想史》,法律出版社1982年出版。(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美)博登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