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挠我的痒痒肉
爱笑的天使爱哭的恶魔挠小亮痒痒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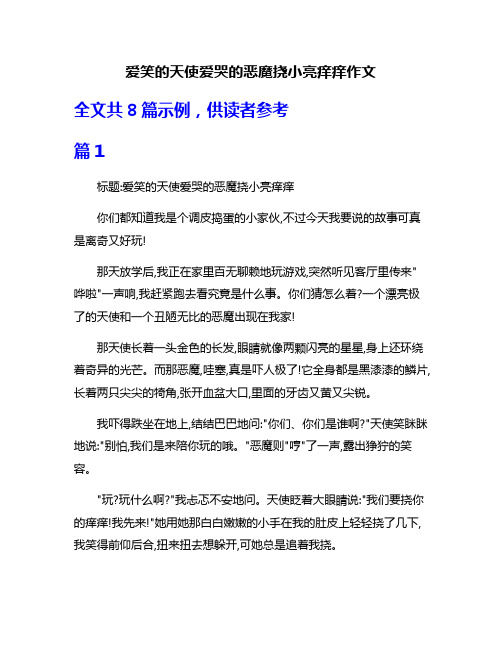
爱笑的天使爱哭的恶魔挠小亮痒痒作文全文共8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篇1标题:爱笑的天使爱哭的恶魔挠小亮痒痒你们都知道我是个调皮捣蛋的小家伙,不过今天我要说的故事可真是离奇又好玩!那天放学后,我正在家里百无聊赖地玩游戏,突然听见客厅里传来"哗啦"一声响,我赶紧跑去看究竟是什么事。
你们猜怎么着?一个漂亮极了的天使和一个丑陋无比的恶魔出现在我家!那天使长着一头金色的长发,眼睛就像两颗闪亮的星星,身上还环绕着奇异的光芒。
而那恶魔,哇塞,真是吓人极了!它全身都是黑漆漆的鳞片,长着两只尖尖的犄角,张开血盆大口,里面的牙齿又黄又尖锐。
我吓得跌坐在地上,结结巴巴地问:"你们、你们是谁啊?"天使笑眯眯地说:"别怕,我们是来陪你玩的哦。
"恶魔则"哼"了一声,露出狰狞的笑容。
"玩?玩什么啊?"我忐忑不安地问。
天使眨着大眼睛说:"我们要挠你的痒痒!我先来!"她用她那白白嫩嫩的小手在我的肚皮上轻轻挠了几下,我笑得前仰后合,扭来扭去想躲开,可她总是追着我挠。
渐渐地,我笑累了。
恶魔看我累了,就伸出它那黑乎乎的大爪子,在我身上乱挠一气,我被挠得又痒又疼,哇哇大叫。
就这样,天使用她柔软的小手挠我的痒痒,而恶魔则用它那锐利的爪子撕扯我的皮肤。
我笑着、哭着,在地上打滚。
爸爸妈妈回来时,看到这离奇的一幕,也被吓了一大跳。
后来天使和恶魔对我说:"小亮啊,你要记住,快乐和痛苦是并存的,就像我们一样,一个代表欢乐,一个代表痛苦。
你要学会欣赏快乐,但也不能畏惧痛苦,因为没有痛苦就体会不到快乐的珍贵。
"说完,它们就"哗啦"一下不见了。
我想了又想,终于明白了天使和恶魔的教导。
从那以后,我变得积极乐观,不再害怕生活中的痛苦和挫折。
因为我知道,只要有爱笑的天使在身边,就一定能战胜爱哭的恶魔。
篇2【爱笑的天使爱哭的恶魔挠小亮痒痒】你们知道吗?我家里有两个神奇的小人!一个是爱笑的天使,一个是爱哭的小恶魔。
不爱洗手的小猫读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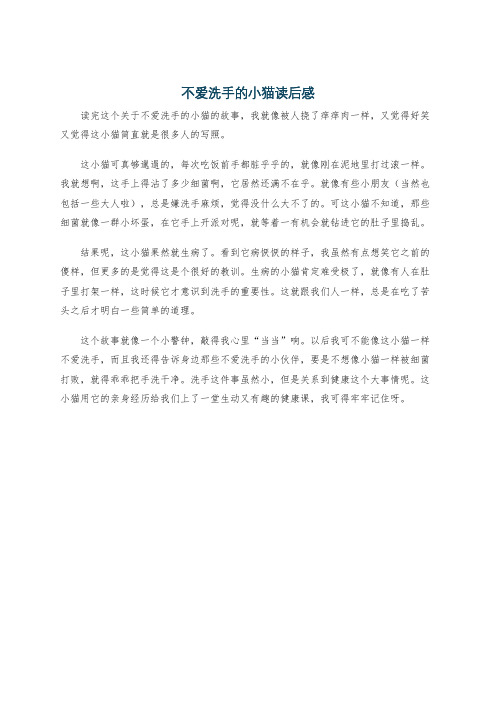
不爱洗手的小猫读后感
读完这个关于不爱洗手的小猫的故事,我就像被人挠了痒痒肉一样,又觉得好笑又觉得这小猫简直就是很多人的写照。
这小猫可真够邋遢的,每次吃饭前手都脏乎乎的,就像刚在泥地里打过滚一样。
我就想啊,这手上得沾了多少细菌啊,它居然还满不在乎。
就像有些小朋友(当然也包括一些大人啦),总是嫌洗手麻烦,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这小猫不知道,那些细菌就像一群小坏蛋,在它手上开派对呢,就等着一有机会就钻进它的肚子里捣乱。
结果呢,这小猫果然就生病了。
看到它病恹恹的样子,我虽然有点想笑它之前的傻样,但更多的是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教训。
生病的小猫肯定难受极了,就像有人在肚子里打架一样,这时候它才意识到洗手的重要性。
这就跟我们人一样,总是在吃了苦头之后才明白一些简单的道理。
这个故事就像一个小警钟,敲得我心里“当当”响。
以后我可不能像这小猫一样不爱洗手,而且我还得告诉身边那些不爱洗手的小伙伴,要是不想像小猫一样被细菌打败,就得乖乖把手洗干净。
洗手这件事虽然小,但是关系到健康这个大事情呢。
这小猫用它的亲身经历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又有趣的健康课,我可得牢牢记住呀。
冬季皮肤痒千万别乱挠

断 的瘙 痒 而 挠 抓 , 阴唇 部 常 有 皮 怒 发 冲 冠 。
肤 肥 厚 及 浸 渍 ,也 可 有 红 肿 及 糜
3 饮食 宜清 淡 、 消 化 , . 易 多
专 家提 醒 ,冬 季 人 体 皮 脂 腺 烂 。此 类 患者 常 存 在 白带 异 常 及 食 新 鲜 蔬 菜 和 水 果 ,保 持 大 便 通 和汗腺 分 泌 的皮脂 及汗 液减 少 , 对 卫 生 护 垫 过 敏 等 症 状 。 头 皮 瘙 畅 , 以将 体 内 积 聚 的 致 敏 物 质 和
刺激 性食 物 , 鱼 、 、 等 并戒 如 虾 蟹
掉烟酒 。
年 人 。皮 肤 瘙 痒 症 主 要 表 现 为 皮
1 合 理 的皮 肤 保 养 , 量 避 . 尽
4 冬 季 室 内采 暖 温 度 不 宜 . 过 高 ,被 褥 不 宜 太 厚 ,可 以用 加
肤 局 部 出 现 瘙 痒 , 也 可 以 是 全 身 免 挠 抓 。挠 抓 不 仅会 使 皮肤 破 损 ,
敏 使 部 常 见 。也 可 由 于 情 绪 激 动 , 度 复 刺 激 而 更 加 兴 奋 、 感 , 瘙 痒 发 。还 应 该 养 成 定 时 定 量 喝水 的 温 改 变 ,饮 酒 或 食 入 辛 辣 食 物 后 引 进 一 步 加 重 , 抓 越 痒 , 成 恶性 越 形 习惯 ,如 果 总 是 感 到 口渴 时 才 喝 松 内衣 选 水 ,人 体 就 会 处 于 缺 水 状 态 ,而 发 瘙 痒 加 重 。瘙 痒 可 为 持 续 性 或 循 环 。衣 服 宜 宽 大 、 软 , 阵发 性 , 度 轻 重 不 一 , 间长 短 用 棉 织 品 或 丝 织 品 , 不 要 穿 毛 织 人 体 一 旦 缺 水 就 会 从 皮 肤 中 汲 取 程 时
皮肤瘙痒千万别用“老头乐”挠

龙源期刊网 皮肤瘙痒千万别用“老头乐”挠作者:曾丽雄来源:《饮食与健康·下旬刊》2015年第02期不少老人都酷爱使用“老头乐”,殊不知。
这“老头乐”也藏着隐患。
侍亲心得老年人由于年龄的增长而导致了皮肤的老化萎缩、变薄和皮肤血液供应减少,皮肤变得更加粗糙,并易脱屑,瘙痒就因此发生了。
另外,人的皮脂在温度高时呈液体或半液体状,容易排出体外,冬天温度较低,人的皮脂呈固体状,就不容易排出体外,它也会刺激皮肤产生瘙痒感。
用“老头乐”抓痒,偶尔用几下也并无多大妨碍,但是奇痒之时,只恨手上力小,往往用力去抓,致使皮肤剥脱,出现损伤性丘疹。
经常这样做,还会使皮肤色泽变暗,局部皮肤呈苔藓样改变。
若抓破皮肤,继发感染,则易导致疖子、毛囊炎等。
特别是使用“老头乐”抓背部,盲目性较大,很容易损伤黑痣,可能诱发癌症。
其实,预防皮肤瘙痒,关键是要防止皮肤干燥,合理保护皮肤。
于是我建议父母平时多注意合理的皮肤保养,经常洗换内衣,衣服宜宽大、松软。
妻子给父母买衣服时,也一般选择棉织品或丝织品,特别是贴身穿的衣服,不要选择毛织品。
皮肤瘙痒多发生在冬季,我建议父母在冬季洗澡的次数不必过多,一般7天左右洗一次就行。
洗澡宜用温水和中性的洗浴用品,而不要用太热的水和碱性的洗浴用品。
水太热会造成皮肤血管扩张,皮肤充血,并刺激皮肤中的感觉神经末梢,短时间内可能有止痒作用,长期下去会加剧瘙痒感;碱性洗浴用品去污力强,同时也会把皮肤表面的皮脂洗掉,使皮肤更加干燥和易受刺激。
冬季应适量涂抹润滑油膏保护皮肤。
有些老人对鱼、虾、蟹等食物过敏,因此在饮食方面要特别注意,不吃会过敏或刺激的食物。
应戒烟酒,不喝浓茶、咖啡。
饮食宜清淡、易消化,多食新鲜蔬菜和水果。
大便通畅能有效地将体内积聚的致敏物质及时排出体外。
对已经证明有过敏的食品,包括同类食品均应绝对忌食。
当别人挠你痒痒肉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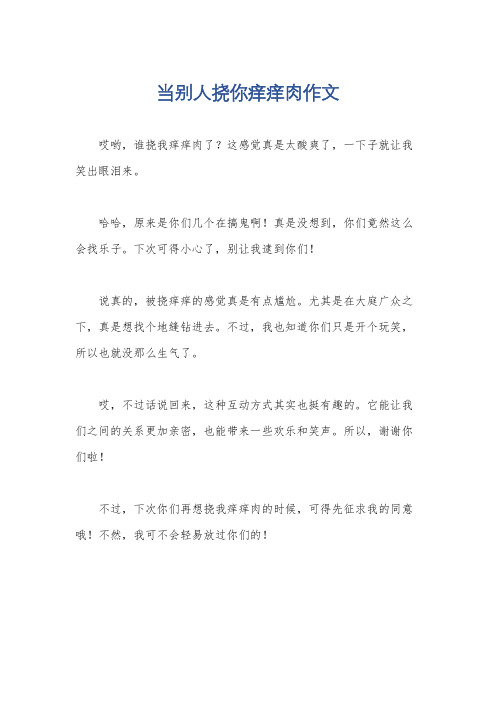
当别人挠你痒痒肉作文
哎哟,谁挠我痒痒肉了?这感觉真是太酸爽了,一下子就让我笑出眼泪来。
哈哈,原来是你们几个在搞鬼啊!真是没想到,你们竟然这么会找乐子。
下次可得小心了,别让我逮到你们!
说真的,被挠痒痒的感觉真是有点尴尬。
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真是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不过,我也知道你们只是开个玩笑,所以也就没那么生气了。
哎,不过话说回来,这种互动方式其实也挺有趣的。
它能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也能带来一些欢乐和笑声。
所以,谢谢你们啦!
不过,下次你们再想挠我痒痒肉的时候,可得先征求我的同意哦!不然,我可不会轻易放过你们的!。
挠小孩子的胳肢窝痒痒肉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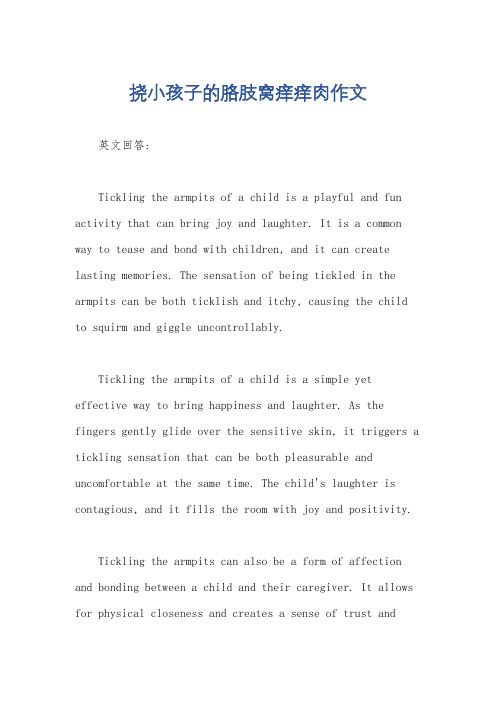
挠小孩子的胳肢窝痒痒肉作文英文回答:Tickling the armpits of a child is a playful and fun activity that can bring joy and laughter. It is a common way to tease and bond with children, and it can create lasting memories. The sensation of being tickled in the armpits can be both ticklish and itchy, causing the child to squirm and giggle uncontrollably.Tickling the armpits of a child is a simple yet effective way to bring happiness and laughter. As the fingers gently glide over the sensitive skin, it triggers a tickling sensation that can be both pleasurable and uncomfortable at the same time. The child's laughter is contagious, and it fills the room with joy and positivity.Tickling the armpits can also be a form of affection and bonding between a child and their caregiver. It allows for physical closeness and creates a sense of trust andconnection. The child feels loved and cared for, and it strengthens the emotional bond between them.However,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ickling the armpits should always be done with care and respect for the child's boundaries. Some children may not enjoy being tickled or may have sensory sensitivities that make it uncomfortable for them. It is essential to be attentive to their reactions and stop if they express discomfort or ask you to stop.In conclusion, tickling the armpits of a child can be a delightful and enjoyable experience for both the child and the caregiver. It brings laughter, joy, and strengthens the bond between them. However, it is crucial to be mindful of the child's comfort and boundaries. Communication and respect are key in ensuring a positive and enjoyabletickling experience.中文回答:挠小孩子的胳肢窝痒痒肉是一种有趣的游戏,可以带来快乐和欢笑。
哥哥别挠我痒痒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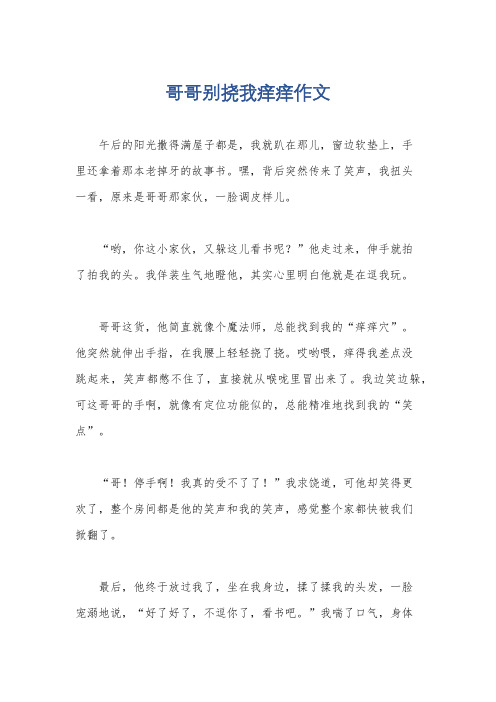
哥哥别挠我痒痒作文
午后的阳光撒得满屋子都是,我就趴在那儿,窗边软垫上,手
里还拿着那本老掉牙的故事书。
嘿,背后突然传来了笑声,我扭头
一看,原来是哥哥那家伙,一脸调皮样儿。
“哟,你这小家伙,又躲这儿看书呢?”他走过来,伸手就拍
了拍我的头。
我佯装生气地瞪他,其实心里明白他就是在逗我玩。
哥哥这货,他简直就像个魔法师,总能找到我的“痒痒穴”。
他突然就伸出手指,在我腰上轻轻挠了挠。
哎哟喂,痒得我差点没
跳起来,笑声都憋不住了,直接就从喉咙里冒出来了。
我边笑边躲,可这哥哥的手啊,就像有定位功能似的,总能精准地找到我的“笑点”。
“哥!停手啊!我真的受不了了!”我求饶道,可他却笑得更
欢了,整个房间都是他的笑声和我的笑声,感觉整个家都快被我们
掀翻了。
最后,他终于放过我了,坐在我身边,揉了揉我的头发,一脸
宠溺地说,“好了好了,不逗你了,看书吧。
”我喘了口气,身体
终于放松下来,心里暖暖的,全是感激和依赖。
阳光继续照在我身上,暖洋洋的。
挠痒审问间谍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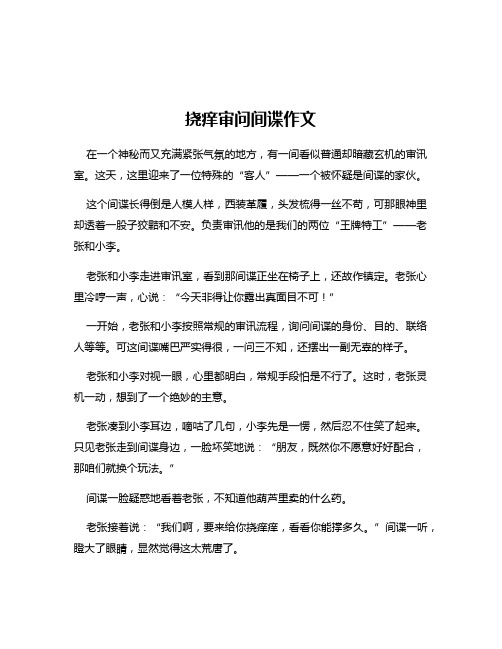
挠痒审问间谍作文在一个神秘而又充满紧张气氛的地方,有一间看似普通却暗藏玄机的审讯室。
这天,这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一个被怀疑是间谍的家伙。
这个间谍长得倒是人模人样,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可那眼神里却透着一股子狡黠和不安。
负责审讯他的是我们的两位“王牌特工”——老张和小李。
老张和小李走进审讯室,看到那间谍正坐在椅子上,还故作镇定。
老张心里冷哼一声,心说:“今天非得让你露出真面目不可!”一开始,老张和小李按照常规的审讯流程,询问间谍的身份、目的、联络人等等。
可这间谍嘴巴严实得很,一问三不知,还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老张和小李对视一眼,心里都明白,常规手段怕是不行了。
这时,老张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老张凑到小李耳边,嘀咕了几句,小李先是一愣,然后忍不住笑了起来。
只见老张走到间谍身边,一脸坏笑地说:“朋友,既然你不愿意好好配合,那咱们就换个玩法。
”间谍一脸疑惑地看着老张,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老张接着说:“我们啊,要来给你挠痒痒,看看你能撑多久。
”间谍一听,瞪大了眼睛,显然觉得这太荒唐了。
还没等间谍反应过来,小李已经上前按住了他的肩膀,老张则伸出了那双“魔爪”,朝着间谍的腰间挠去。
“哈哈哈哈……别……别挠了……”间谍瞬间就破功了,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老张可不停手,继续挠着,边挠边说:“快说,你的任务到底是什么?”间谍一边笑着一边喘着粗气说:“我……我真的……不知道……”老张加大了力度,间谍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哎呀,求求你们,别挠了,我说,我说!”听到这话,老张和小李才停了手。
间谍大口喘着气,开始交代他的罪行。
原来,他是被派来窃取重要情报的,已经把一些关键信息传递出去了。
老张和小李听着,脸色越来越严肃。
等间谍说完,老张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哼,早这样不就好了,非得受这挠痒的罪!”经过一番详细的审问,终于把这个间谍的底细摸得清清楚楚。
最后,老张和小李把间谍交给了相关部门,圆满完成了这次特殊的审讯任务。
挠小孩子的胳肢窝痒痒肉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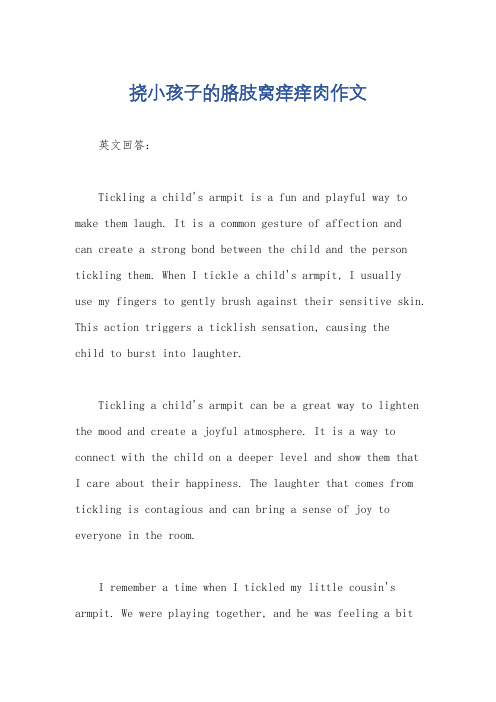
挠小孩子的胳肢窝痒痒肉作文英文回答:Tickling a child's armpit is a fun and playful way to make them laugh. It is a common gesture of affection andcan create a strong bond between the child and the person tickling them. When I tickle a child's armpit, I usuallyuse my fingers to gently brush against their sensitive skin. This action triggers a ticklish sensation, causing thechild to burst into laughter.Tickling a child's armpit can be a great way to lighten the mood and create a joyful atmosphere. It is a way to connect with the child on a deeper level and show them that I care about their happiness. The laughter that comes from tickling is contagious and can bring a sense of joy to everyone in the room.I remember a time when I tickled my little cousin's armpit. We were playing together, and he was feeling a bitdown. I decided to tickle him to cheer him up. As soon asmy fingers touched his armpit, he started giggling uncontrollably. His laughter filled the room and brought a smile to everyone's face. It was a beautiful moment of connection and happiness.Tickling a child's armpit is also a way to createlasting memories. It is something that they will remember and cherish for years to come. Whenever they think back to that moment, they will be reminded of the love and joy that was shared.中文回答:挠小孩子的胳肢窝是一种有趣的方式,可以让他们开心地笑出声来。
挠小朋友的胳肢窝痒痒肉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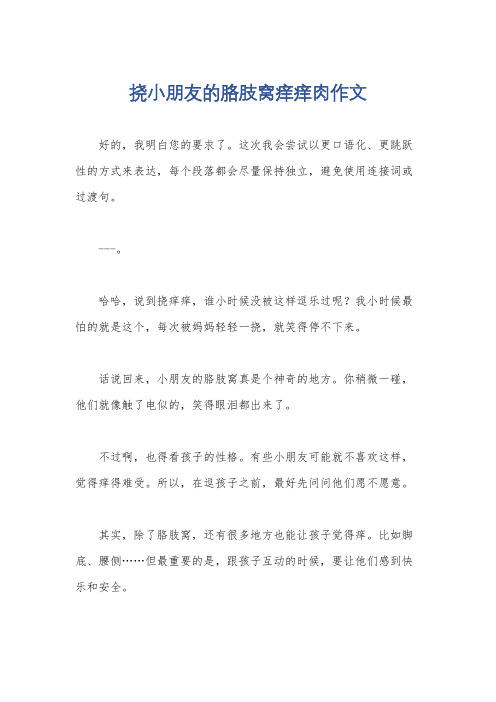
挠小朋友的胳肢窝痒痒肉作文
好的,我明白您的要求了。
这次我会尝试以更口语化、更跳跃性的方式来表达,每个段落都会尽量保持独立,避免使用连接词或过渡句。
---。
哈哈,说到挠痒痒,谁小时候没被这样逗乐过呢?我小时候最怕的就是这个,每次被妈妈轻轻一挠,就笑得停不下来。
话说回来,小朋友的胳肢窝真是个神奇的地方。
你稍微一碰,他们就像触了电似的,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不过啊,也得看孩子的性格。
有些小朋友可能就不喜欢这样,觉得痒得难受。
所以,在逗孩子之前,最好先问问他们愿不愿意。
其实,除了胳肢窝,还有很多地方也能让孩子觉得痒。
比如脚底、腰侧……但最重要的是,跟孩子互动的时候,要让他们感到快乐和安全。
总之,跟小朋友玩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分寸和方式。
别让他们觉得不舒服,也别让自己后悔。
---。
希望这样的回答能满足您的要求!。
炉子里的柴去哪儿了读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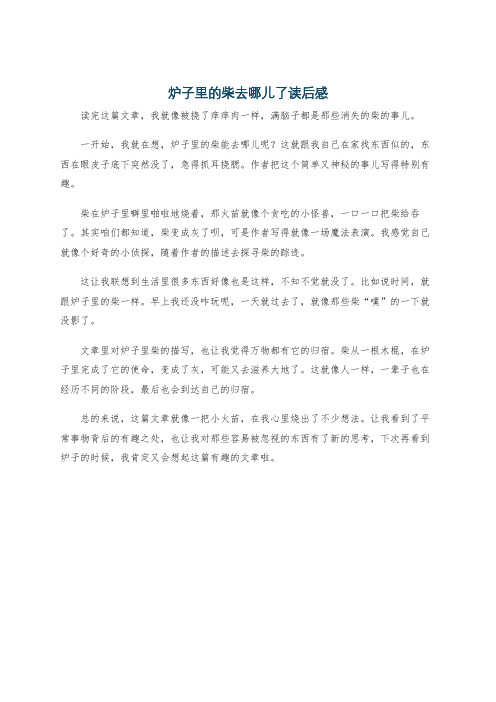
炉子里的柴去哪儿了读后感
读完这篇文章,我就像被挠了痒痒肉一样,满脑子都是那些消失的柴的事儿。
一开始,我就在想,炉子里的柴能去哪儿呢?这就跟我自己在家找东西似的,东西在眼皮子底下突然没了,急得抓耳挠腮。
作者把这个简单又神秘的事儿写得特别有趣。
柴在炉子里噼里啪啦地烧着,那火苗就像个贪吃的小怪兽,一口一口把柴给吞了。
其实咱们都知道,柴变成灰了呗,可是作者写得就像一场魔法表演。
我感觉自己就像个好奇的小侦探,随着作者的描述去探寻柴的踪迹。
这让我联想到生活里很多东西好像也是这样,不知不觉就没了。
比如说时间,就跟炉子里的柴一样。
早上我还没咋玩呢,一天就过去了,就像那些柴“噗”的一下就没影了。
文章里对炉子里柴的描写,也让我觉得万物都有它的归宿。
柴从一根木棍,在炉子里完成了它的使命,变成了灰,可能又去滋养大地了。
这就像人一样,一辈子也在经历不同的阶段,最后也会到达自己的归宿。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就像一把小火苗,在我心里烧出了不少想法。
让我看到了平常事物背后的有趣之处,也让我对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东西有了新的思考,下次再看到炉子的时候,我肯定又会想起这篇有趣的文章啦。
《安全教育---我的身体,别碰》_《我的身体,别碰》小班x幼儿园x教案微课公开课教案教学设计课件

《安全教育课一一我的身体,别碰》教案及反思
活动目标:
1.了解男生女生身体方面的不同;
2.知道自己身体中哪些是隐私部位;
3.自主有意识的保护自己的隐私部位;
4.对于有侵犯自己意向的行为知道拒绝,并采取措施;
活动过程:
首先,以提问的方式,引导幼儿自行说出自己的性别。
之后进行追问,引导幼儿说出为什么她是女生或男生,得出一些表面的关于男女区别的结论;
其次,突出主题——男生和女生在身体上根本性的不同有什么,这些不同这些都是隐私,是需要保护的;
最后,通过动画视频的形式表现如果有人侵犯了幼儿自身,幼儿应该怎么办?
活动反思:
1.此课程教育性强,知识点抽象。
在真实上课中,需要教师较高的渲染能力,亲和能力才能吸引幼儿,让幼儿理解其内容,达到教学目标;
2.课程最后的动画可以邀请幼儿进行情景演绎,更能吸引幼儿,强
化幼儿自我保护的意识;
3.此课程是针对小班,但其中的内容给其他年龄阶段的幼儿均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可以灵活运用于其他年龄阶段的孩子。
学校:XX幼儿园
教师:XXX
2019.8。
健康提醒:皮肤瘙痒别乱抓!(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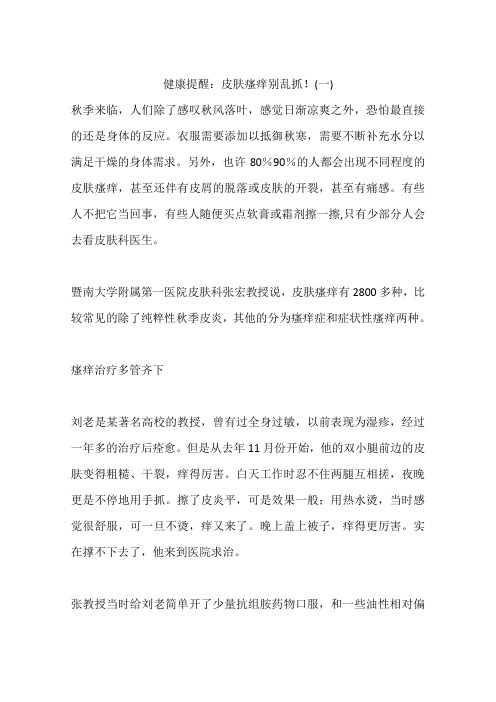
健康提醒:皮肤瘙痒别乱抓!(一)秋季来临,人们除了感叹秋风落叶,感觉日渐凉爽之外,恐怕最直接的还是身体的反应。
衣服需要添加以抵御秋寒,需要不断补充水分以满足干燥的身体需求。
另外,也许80%90%的人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皮肤瘙痒,甚至还伴有皮屑的脱落或皮肤的开裂,甚至有痛感。
有些人不把它当回事,有些人随便买点软膏或霜剂擦一擦,只有少部分人会去看皮肤科医生。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张宏教授说,皮肤瘙痒有2800多种,比较常见的除了纯粹性秋季皮炎,其他的分为瘙痒症和症状性瘙痒两种。
瘙痒治疗多管齐下刘老是某著名高校的教授,曾有过全身过敏,以前表现为湿疹,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后痊愈。
但是从去年11月份开始,他的双小腿前边的皮肤变得粗糙、干裂,痒得厉害。
白天工作时忍不住两腿互相搓,夜晚更是不停地用手抓。
擦了皮炎平,可是效果一般;用热水烫,当时感觉很舒服,可一旦不烫,痒又来了。
晚上盖上被子,痒得更厉害。
实在撑不下去了,他来到医院求治。
张教授当时给刘老简单开了少量抗组胺药物口服,和一些油性相对偏大的复方外用皮脂类固醇制剂涂抹,第二天症状就缓解了,过了二三天就好了。
张教授建议病人再吃35天药以巩固疗效。
同时,在生活上也需注意营养均衡,建议他可以补充一些脂溶性、水溶性的维生素(在安全剂量内可以经常服用);不吃刺激性的食物如烟酒、胡椒;不吃热气的食物如芒果、荔枝、榴莲、花生和煎炸的食物;不要吃发物尤其是海鲜类;不要用热水烫,(即使当时会舒服一些,但过后会加重);在肥皂、沐浴露的选择上,一定要选有明确的非碱性或中性标志的产品,因为碱性的洗浴用品会脱掉油脂,使皮肤更干;平时用稍有油性的护肤品;还需要注意的是要少用手抓,抓不可能止痒,而是变为其他的感觉,比如痛;最后需要做到的是尽量保持规律的生活,工作休息配合好,有张有弛,尤其是精神要愉快放松,紧张的精神会使对事物的敏感度高,更专注于痒。
皮肤干痒别乱挠,止痒妙招助缓解

文/董绍军秋冬时节,天气干燥,皮脂腺分泌少,对皮肤的保护不足,很容易皮肤干燥。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很多人皮肤瘙痒的情况也会加重,感觉皮肤痒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去抓挠,可有时会出现越挠越痒的情况,这可能是由皮肤瘙痒症引起的。
下面几个小妙招,能助你缓解皮肤瘙痒。
局部降温缓解瘙痒:在瘙痒的部位给予降温处理,比如用布包裹着冰块或使用湿冷的布局部外敷,持续时间控制在5~10分钟或直至瘙痒消退。
或者外用冷却剂,比如选用含有薄荷霜、炉甘石成分的产品,将其放于冰箱后,再涂在瘙痒处,可以达到降温止痒的效果。
皮肤干痒别乱挠 止痒妙招助缓解温水淋浴,切忌搔抓:瘙痒难忍时,洗澡就不要用热水淋浴或者泡澡了,水温过热容易破坏皮肤油脂,从而加重瘙痒,因此淋浴或泡澡时的水温控制在40℃以下,时间不超过10分钟。
如果皮肤已经被抓破或者有水泡渗出,可以用燕麦浴,对瘙痒能起到舒缓的作用。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治疗瘙痒的过程中切忌搔抓,因为搔抓会加重皮肤瘙痒。
形成瘙痒—搔抓—瘙痒加重的恶性循环,增加皮肤感染的风险。
勤剪指甲以减少搔抓对皮肤的刺激及感染风险,儿童或老年人若无法控制对皮肤的搔抓,可戴上棉质的手套。
需要提醒的是,冬季最好穿宽松、全棉衣物,紧身、羊毛或其他纤维的衣物容易刺激皮肤,引起剧烈瘙痒。
护肤止痒杏仁雪梨茶:杏仁富含健康脂肪以及维生素E,这些营养素具有修复受损肌肤及滋润的功效,此外,杏仁还富含β-胡萝卜素,它能在人体中转化成维生素A,维生素A 有助合成和修复上皮组织。
雪梨富含维生素C及果胶等成分,维生素C 可增加人体胶原蛋白的产生,让肌肤柔软光滑,果胶可维持皮肤弹性及光泽。
蜂蜜则有保湿、滋润肌肤的效果。
三者进行搭配,对缓解皮肤瘙痒有一定的效果。
取健康成长Healthy Growth青春期健康32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
张大爷为何扔了痒痒挠【精品-d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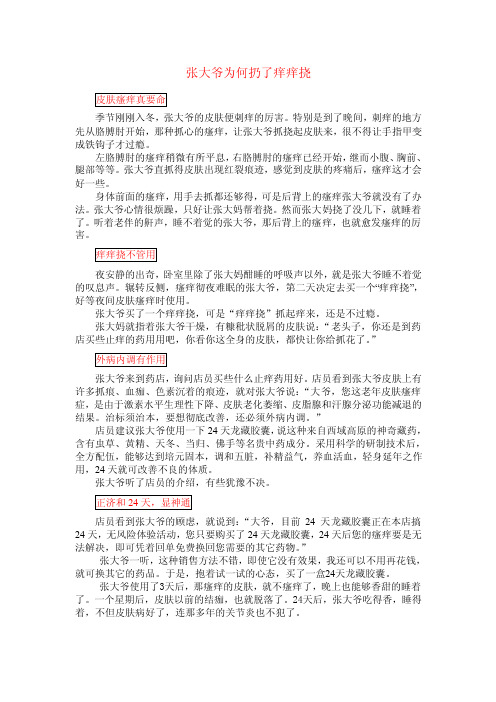
张大爷为何扔了痒痒挠皮肤瘙痒真要命季节刚刚入冬,张大爷的皮肤便刺痒的厉害。
特别是到了晚间,刺痒的地方先从胳膊肘开始,那种抓心的瘙痒,让张大爷抓挠起皮肤来,很不得让手指甲变成铁钩子才过瘾。
左胳膊肘的瘙痒稍微有所平息,右胳膊肘的瘙痒已经开始,继而小腹、胸前、腿部等等。
张大爷直抓得皮肤出现红裂痕迹,感觉到皮肤的疼痛后,瘙痒这才会好一些。
身体前面的瘙痒,用手去抓都还够得,可是后背上的瘙痒张大爷就没有了办法。
张大爷心情很烦躁,只好让张大妈帮着挠。
然而张大妈挠了没几下,就睡着了。
听着老伴的鼾声,睡不着觉的张大爷,那后背上的瘙痒,也就愈发瘙痒的厉害。
痒痒挠不管用夜安静的出奇,卧室里除了张大妈酣睡的呼吸声以外,就是张大爷睡不着觉的叹息声。
辗转反侧,瘙痒彻夜难眠的张大爷,第二天决定去买一个“痒痒挠”,好等夜间皮肤瘙痒时使用。
张大爷买了一个痒痒挠,可是“痒痒挠”抓起痒来,还是不过瘾。
张大妈就指着张大爷干燥,有糠秕状脱屑的皮肤说:“老头子,你还是到药店买些止痒的药用用吧,你看你这全身的皮肤,都快让你给抓花了。
”外病内调有作用张大爷来到药店,询问店员买些什么止痒药用好。
店员看到张大爷皮肤上有许多抓痕、血痂、色素沉着的痕迹,就对张大爷说:“大爷,您这老年皮肤瘙痒症,是由于激素水平生理性下降、皮肤老化萎缩、皮脂腺和汗腺分泌功能减退的结果。
治标须治本,要想彻底改善,还必须外病内调。
”店员建议张大爷使用一下24天龙藏胶囊,说这种来自西域高原的神奇藏药,含有虫草、黄精、天冬、当归、佛手等名贵中药成分。
采用科学的研制技术后,全方配伍,能够达到培元固本,调和五脏,补精益气,养血活血,轻身延年之作用,24天就可改善不良的体质。
张大爷听了店员的介绍,有些犹豫不决。
正济和24天,显神通店员看到张大爷的顾虑,就说到:“大爷,目前24天龙藏胶囊正在本店搞24天,无风险体验活动,您只要购买了24天龙藏胶囊,24天后您的瘙痒要是无法解决,即可凭着回单免费换回您需要的其它药物。
挠痒痒范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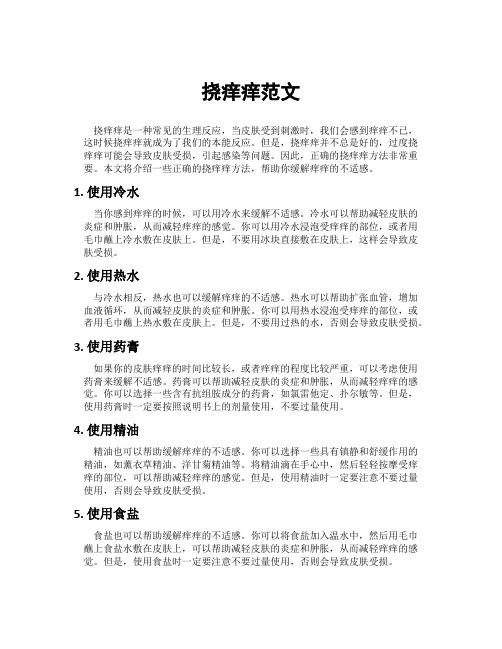
挠痒痒范文挠痒痒是一种常见的生理反应,当皮肤受到刺激时,我们会感到痒痒不已,这时候挠痒痒就成为了我们的本能反应。
但是,挠痒痒并不总是好的,过度挠痒痒可能会导致皮肤受损,引起感染等问题。
因此,正确的挠痒痒方法非常重要。
本文将介绍一些正确的挠痒痒方法,帮助你缓解痒痒的不适感。
1. 使用冷水当你感到痒痒的时候,可以用冷水来缓解不适感。
冷水可以帮助减轻皮肤的炎症和肿胀,从而减轻痒痒的感觉。
你可以用冷水浸泡受痒痒的部位,或者用毛巾蘸上冷水敷在皮肤上。
但是,不要用冰块直接敷在皮肤上,这样会导致皮肤受损。
2. 使用热水与冷水相反,热水也可以缓解痒痒的不适感。
热水可以帮助扩张血管,增加血液循环,从而减轻皮肤的炎症和肿胀。
你可以用热水浸泡受痒痒的部位,或者用毛巾蘸上热水敷在皮肤上。
但是,不要用过热的水,否则会导致皮肤受损。
3. 使用药膏如果你的皮肤痒痒的时间比较长,或者痒痒的程度比较严重,可以考虑使用药膏来缓解不适感。
药膏可以帮助减轻皮肤的炎症和肿胀,从而减轻痒痒的感觉。
你可以选择一些含有抗组胺成分的药膏,如氯雷他定、扑尔敏等。
但是,使用药膏时一定要按照说明书上的剂量使用,不要过量使用。
4. 使用精油精油也可以帮助缓解痒痒的不适感。
你可以选择一些具有镇静和舒缓作用的精油,如薰衣草精油、洋甘菊精油等。
将精油滴在手心中,然后轻轻按摩受痒痒的部位,可以帮助减轻痒痒的感觉。
但是,使用精油时一定要注意不要过量使用,否则会导致皮肤受损。
5. 使用食盐食盐也可以帮助缓解痒痒的不适感。
你可以将食盐加入温水中,然后用毛巾蘸上食盐水敷在皮肤上,可以帮助减轻皮肤的炎症和肿胀,从而减轻痒痒的感觉。
但是,使用食盐时一定要注意不要过量使用,否则会导致皮肤受损。
6. 注意个人卫生最后,要注意个人卫生。
保持皮肤清洁干燥,避免过度挠痒痒,可以帮助减轻痒痒的感觉。
同时,要注意饮食健康,避免食用过多刺激性食物,如辣椒、酒精等。
总之,正确的挠痒痒方法非常重要。
用羽毛挠腋窝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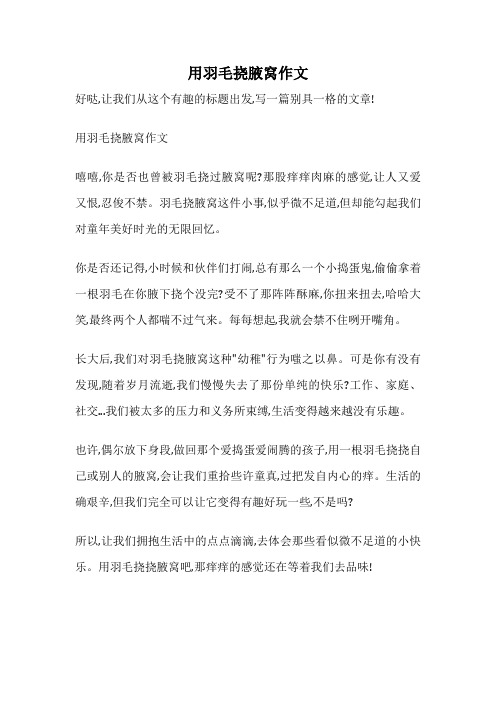
用羽毛挠腋窝作文
好哒,让我们从这个有趣的标题出发,写一篇别具一格的文章!
用羽毛挠腋窝作文
嘻嘻,你是否也曾被羽毛挠过腋窝呢?那股痒痒肉麻的感觉,让人又爱又恨,忍俊不禁。
羽毛挠腋窝这件小事,似乎微不足道,但却能勾起我们对童年美好时光的无限回忆。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和伙伴们打闹,总有那么一个小捣蛋鬼,偷偷拿着一根羽毛在你腋下挠个没完?受不了那阵阵酥麻,你扭来扭去,哈哈大笑,最终两个人都喘不过气来。
每每想起,我就会禁不住咧开嘴角。
长大后,我们对羽毛挠腋窝这种"幼稚"行为嗤之以鼻。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随着岁月流逝,我们慢慢失去了那份单纯的快乐?工作、家庭、社交...我们被太多的压力和义务所束缚,生活变得越来越没有乐趣。
也许,偶尔放下身段,做回那个爱捣蛋爱闹腾的孩子,用一根羽毛挠挠自己或别人的腋窝,会让我们重拾些许童真,过把发自内心的痒。
生活的确艰辛,但我们完全可以让它变得有趣好玩一些,不是吗?
所以,让我们拥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去体会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快乐。
用羽毛挠挠腋窝吧,那痒痒的感觉还在等着我们去品味!。
【中班安全教案】中班安全教育《别摸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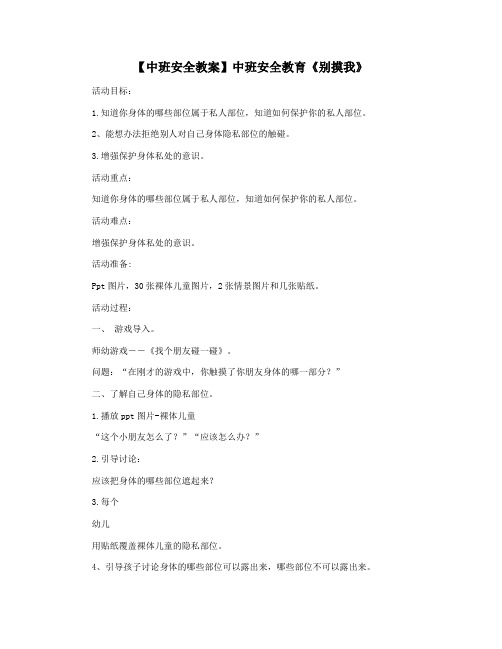
【中班安全教案】中班安全教育《别摸我》活动目标:1.知道你身体的哪些部位属于私人部位,知道如何保护你的私人部位。
2、能想办法拒绝别人对自己身体隐私部位的触碰。
3.增强保护身体私处的意识。
活动重点:知道你身体的哪些部位属于私人部位,知道如何保护你的私人部位。
活动难点:增强保护身体私处的意识。
活动准备:Ppt图片,30张裸体儿童图片,2张情景图片和几张贴纸。
活动过程:一、游戏导入。
师幼游戏――《找个朋友碰一碰》。
问题:“在刚才的游戏中,你触摸了你朋友身体的哪一部分?”二、了解自己身体的隐私部位。
1.播放ppt图片-裸体儿童“这个小朋友怎么了?”“应该怎么办?”2.引导讨论:应该把身体的哪些部位遮起来?3.每个幼儿用贴纸覆盖裸体儿童的隐私部位。
4、引导孩子讨论身体的哪些部位可以露出来,哪些部位不可以露出来。
5.播放ppt图片-穿泳衣的儿童被泳装遮起来的部位就是不能被别人看的,这些部位属于隐私部位。
三、知道如何保护身体的隐私部位。
1、讨论:怎么样才不会被别人看到我们身体的隐私部位?a、穿衣服B,站着时不要脱掉衣服和裙子c、坐着时、躺着时要把腿并拢、裤子裙子整理好d、换衣服和上厕所时,关上门,避开人群。
2、出示情景图片―a、你在这张照片上干什么?b、小女孩能答应吗?应该怎么办?c、引导孩子找到一种方法——告诉孩子只有父母才能看到和触摸隐私部分。
3、出示情境图片二a、医生在做什么?小女孩该怎么办?b、告诉孩子要让爸爸、妈妈在旁边陪同。
4.知道如何尊重他人的隐私。
每个人都要保护自己身体的隐私部位,对于别人的隐私部位我们应该怎样做?a、不要偷看、触摸、辱骂b、进别人房间前应先敲门,经过允许后才可进去。
(爸爸、妈妈)四、游戏师幼玩游戏――《找个朋友碰一碰》。
“在游戏中,我们不能触摸朋友身体的那些部位?”(注意:身体的隐私部位非常脆弱。
如果你在游戏中不注意,你会伤害游戏的隐私部位)。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别挠我的痒痒肉回到家时,妻还没有回来。
孟蓝抬眼看去,墙壁上的大挂钟已滴哒到十二点过八分了。
他连忙洗手摘菜,面是老家送的手工挂面,吃哨子面最妥了。
厨房墙角有几只黑塑料袋,袋里装着周日在南环路菜市上购买的菜类。
孟蓝翻开袋口,见剩了些红罗卜葱蒜苗,又有几根芹菜。
他选了几样急急在龙头下掏洗。
日子过得清汤寡味,像凝固结冰的湖面,根本泛不出一丝涟漪。
孟蓝是个有好口碑的男人,好到别人夸奖时感觉有些不好意思,羞羞地脸红发烧。
男人会的他会,女人会的他也会,当然除过坑蒙拐骗吃喝嫖赌生娃喂奶。
春雨过后,太阳软软飘浮着,好似烙个块油酥锅盔贴在了半空,晕糊糊的没有温暖。
光线仄着身子,斜斜地射进窗户,只有光的白亮,却难见光的辐线。
关中道的早春,空气依旧是凛冽地冒着寒意。
龙头里反弹的水花,还有些碜人骨头。
孟蓝是不怕冷的,即就是怯火也无济于事的。
照惯例儿子早该放学回家了。
他边拾掇被他水洗刀切的蔬菜,边惦记着儿子东东。
东东一撩下书包,总是嚷嚷着要吃饭的。
倒油,点火。
火苗在锅底翻卷着火舌,稍过几分钟,油在锅内滋滋地冒白泡。
珍珠般大大小小,簇簇拥拥地在油面奔涌,奔涌片刻,又偃息下去,腾起烟来弥漫开了。
孟蓝熟捻地倒菜搅菜,铁匙饮了油水,在锅底欢快地奏吟,象唱歌似的有韵律。
妻子惠芳进门时,孟蓝正把菜摆到饭桌上,准备下面。
饭桌实际是茶几,就在客厅中央。
孟蓝看妻子时,也瞅见了儿子东东。
妻子横眉冷眼的,矜持里散射着怒气。
儿子悲苦着圆脸,用小手背擦着眼睛,是种哭泣未了的式样,身上泥泥水水,粘得衣服尽是污糟。
“你乍搞的,回来这么迟?连东东都不管。
”妻子恼怒地嚷道。
见妻子有些发火了,孟蓝只是好脾气地一笑。
孟蓝己记不清楚,妻子惠芳从什么时侯开始,变成容易上火的女人。
神情日渐跋扈,泼得象干红辣椒。
往日的温顺贤淑荡然无存了,成了风干了的野菜,或者暗淡了的照片,只留给记忆里那一抹绿茵,那一抹色彩。
孟蓝懒得跟妻子争,自家人争来吵去实在乏味。
争过吵过依旧要在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床上睡觉,就像太阳每天从东山梁升起,傍晚又到西山梁跌落,第二天又周而复始,没有一点点变化。
孟蓝走到儿子跟前,揽住儿子问道:“跌倒啦?弄一身泥。
”“今天老师要看电影《无极》,我们放学早,路上王鹏老骂赵丽娜是跛子,我说要告老师,他就把我推倒了。
”儿子东东抬起胳膊,用袖口抹抹眼泪。
“你不会打他?用手抓他?爷儿俩都是蔫货。
真是啥蔓上结啥瓜。
”惠芳急急奔到了厨房,打开抽油烟机,排泄油烟气雾。
毕了便回过身来,给儿子边脱脏了的衣服边说。
“哎,你这是啥话?少儿不宜!”孟蓝见妻子数落得失了分寸,便说。
“不对呀?!现在这世道,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
你眼珠子瞪得象汽灯似的,朝我鼓啥闲劲,有本事找王鹏家长讨个说法去!”惠芳扬脸说着,给儿子换了身条绒新衣服,心疼地抚着东东脑袋。
儿子东东的满头乌发,水波浪般波动。
“今年署假,妈送你学武术去,看谁还敢惹我儿!”孟蓝无奈地直叹气,给儿子拾掇碗筷,伺侯儿子吃饭。
他心里压抑得气闷,胸口里象似塞满了砖头瓦碴,咯得发胀发疼。
大家心里都有事,饭也吃得仓促而又潦草。
吃罢,孟蓝便就出了门,想去透透气。
街道上还留下雨渍,大大小小的水洼在道旁林萌下滩着。
古城镇虽说连年建筑,楼房也鳞次节比,一座座地拔地而起了,渐渐有了城市的规模,但旧城依然遗留下岁月的痕迹,斑驳地混杂在新的建筑物之间,向人们述说往昔的风光和苍桑,孟蓝在财政局上班,工龄已快十年了。
十年,朝前想似乎很是遥远,返首回思却真象词语里所说:白驹过隙。
匆匆地抓不住有所骄傲的成效。
孟蓝想起大学时的踌躇满志,想起刚毕业时的意气奋发,所有的目空一切豪言壮语仿佛风中落叶,被吹刮得无影无踪了。
他考取了会计师,又连续考中注册会计师,多少次他想南下寻找适宜自身的地方,但每每一见儿子东东却心灰意散。
家象系在腰间的裤带,一旦松动随时都会绊倒的。
孟蓝走在街上,走得清闲而又悠忽。
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流如帜,熙熙嚷嚷的满街乱窜。
他来到十字路口,站在巨型广告牌下观看南来北往东西奔流的车辆和人流。
随着红绿灯一明一暗,车辆和人流便像决口的河流溢泄了。
他看见城区交警队的小刘,戴了双白手套正坐在岗楼里喝茶。
靠北侧的街巷里,停放着七八辆车,是违了章被截留下来的。
有四个轱辘的,也有三轮农用车。
旁边一位交警,正在指天划地的训斥吆喝。
离得远了,聒杂得听不见声音,只能看见交警满脸的恼怒和司机温驯的陪笑。
孟蓝本想走过去凑热闹,想想却又不好意思了。
只好讪讪地远眺。
正在此时,腰间的手机响了,是沙宝亮的《暗香》。
他打开一看,是单位老何。
他急忙赶到医院,老何正焦急在楼口张望。
见他来了,连忙迎了上去。
老何是办公室同事,年龄大,人也稳重。
他见孟蓝有些疑惑,便低声悄悄说:“刘科长出事了,中了毒,是老婆下的。
正在急救室里抢救,恐怕是救不下命的。
”刘科长与老婆关系一直不和。
刘科长家在农村,老婆是城里人,结婚时老婆就没有参加婚礼。
此后两人婚姻一直在疙疙瘩瘩的阴影里生活。
后来,老刘招干进了财政所,把全部心里用在工作上面,工作得很有一套章法。
被上调到财政局,熬成了科长。
熬成科长的老刘,却没把与老婆的关系熬出个和谐美满来。
老婆依旧如故,横眉冷对着不肯化敌为友,化敌为夫。
刘科长几次要离婚,老婆却死活不肯罢休,说是只有她死了,方才会随老刘的愿。
刘科长在外面有个女人,孟蓝知道,说实话就老刘的处境,孟蓝打心里支持老刘找个情人,也好嘘寒问暖,消解压抑烦闷。
谁知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纸里是包不住火的。
刘科长的事被老婆知哓了,与老刘大闹了几场,又与老刘的情人打了个一塌糊涂,撵到财政局嚎叫吵骂了一个礼拜。
最终竟然选择用毒药结束不堪的命运。
孟蓝与老何刚走到病房门口,医生己从急救室里出来了。
他走到孟蓝跟老何跟前,沉痛地说:“中毒太深了,人没救下。
估计是毒鼠强之类的三步倒。
唉,料理后事吧!”单位来了不少人,就连局长也驾车匆匆赶来了。
大伙们帮忙,用白床单把刘科长与老婆裹住,抬到推车上推到太平间里,安置到冰棺里。
太平间里管事的人,唤来专门给死尸擦洗换衣的民工。
当民工给刘科长擦洗面容时,孟蓝看见刘科长表情很是安祥,象似睡着了一般,脸上微微带着些笑意。
而刘科长老婆,却是黑风罩脸,脸上有股怒气,似乎要迸破面皮。
匆匆忙忙一下午,孟蓝觉得有些乏困。
这种乏不是来自身体,而是来自心里。
心里憋得慌,憋得难受。
神经也似乎一直在抽搐,抽搐得全身的经骨似被抽掏走了。
一个大活人,说死就死了,死得如此惨烈悲凄。
他不由得感慨起命运的多舛。
他感到头昏脑胀起来,头大得像五升斗,木楞楞地安置在肩膀上。
他走在街道上。
他不想回家。
孟蓝一想起回家,觉得头会愈发大起来的。
他来到红茶房。
红茶房己经热闹起来了。
散座己坐满客人。
近几年,大江南北,举国上下,喝茶己成了风尚,茶馆生意也兴盛得红火。
古城有几十家茶馆,孟蓝最喜欢来红茶房品缀饮茶。
孟蓝瞅准的是红茶房的环境和清雅素静的氛围。
他来到临窗靠墙角的位置坐下,吧台的服务生是熟识的了,不待他点定,便端来一壶冻顶乌龙,温和又有礼貌地放在茶桌上,斟满一杯,悄没声息地撤退下去。
孟蓝呷了一口,霎间有股清香沁入口腔,直浸透到肺腑里去了。
大厅磁盘里放了首古曲,他知道是《平沙落燕》。
“万里微茫。
鸿雁来也楚江空,碧云天净。
长空一色,万里动微茫,江涵秋影。
江涵秋影,风潇潇,送旅雁南归。
只见那一双双封,摆列头着字样儿在天际。
数声嘹唳也,不胜怨,谁知。
栖宿平沙,楚江秋老,萧疏两岸芦花。
和那千树丹枫,一轮明月,的也风波荡漾,吹动雁行斜。
又见雁行儿背流霞,向那水云落下。
呀呀的渐离的云汉路,而共立在那平沙。
相呼唤也吱喳,无羁绊的也堪夸。
惊飞不定,夜深人静也,底事又惊飞,栖止不定。
只听哑哑的也一声清,扑扑的乱攘波影,纷纷的嘈杂也恁悲鸣。
想只为江枫渔火相近了芦湖,怕受人机矰。
故不辞劳顿也,冥然避戈腾。
朴落江皋试看他飞上云端,扰扰攘攘,只在空际回旋。
猛可的又群然一声划剌江皋。
乍静也。
却又哀鸣转高。
声声也嗷嗷,以诉说劬劳也,怆然封月哀号。
余音娓娓,数声急骤,乍因何事侜张,却又从容作软商量。
鸣声渐缓,余音娓娓,直数到月移砧断,漏尽更长。
孤客不堪听,最可怜山高月冷。
”词曲甚长。
孟蓝听过几遍后便把词曲全都记了下来。
他觉得他的心灵与词曲相通似的,在震憾里感到十分爽快。
他陶醉在古曲音韵之中,一边啜饮品茶,一边静听欣赏。
他觉得灵魂得到了稳妥,浮澡和忧郁全被洗熨得适坦而安逸。
他摇头晃脑地合着节拍,俨然己到了物我两忘的境地了。
“今天闲着?”老板走过来了。
她穿了一身墨绿色套裙,细长的脖颈上随意用纱巾挽了一朵花,斜斜地倾在象牙色的锁骨上。
细细柔柔的长发一边绾在耳后,一边飘逸地垂了下来,宛若诗人笔下的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你好长时间没来了。
”老板又说道。
语音婉约得像李清照的词曲。
“忙得焦头烂脚,来享享清福。
”孟蓝说。
“你再迟来几天,便就物是人非了。
”老板说着,有一种自嘲的意味,夹杂着微微的颤音。
“乍的?”孟蓝有些疑惑。
“我要走了。
我男朋友在上海开了间公司,叫我过去帮忙。
”“那恭喜你了。
要去大地方了。
”“离开故土,有些舍不得的。
”“心随故土一起走吧。
”“前头的路黑灯瞎火,谁知道是光明,还是陷井。
”“爱情在召唤,是金光大道呢。
”“爱情是毒药。
我真有些害怕的。
”“欧洲中世纪有句格言,传颂至今了:‘一杯白开水,一口干粮。
只要爱人在我身旁,哪怕是沙漠,也会变成天堂。
’”“借你吉言,但愿是天堂。
”老板叹了口气,说道:“他若能像你这样有品味,我算是烧了八辈子高香了。
”猛地,老板突然伸过手来,把手压在孟蓝手背上,抚摸几下,又紧紧地握紧攥住。
他感到有股热流传递过来,象电波似的。
老板脸色发红,眼神迷乱,脸颊上浸润出细细的汗珠。
“今晚上别走了,陪陪我。
我想要你!”老板乞恋地请求。
孟蓝心里发痒,痒得似乎有无数毛毛虫在乱抓乱挠。
他血脉奔涌起来,有种欲望像要冲破禁固。
他看着老板,不知从哪里迸发出一股毅力,他决然地说:“对不起了,我妻子和儿子还在家里等我呢!”“你妻子真幸福啊!你也真幸福的。
我真羡慕你们。
”老板说着,两行泪滚落下来,滑过她俏丽的脸庞,顺着脸沟,跌进嘴里。
古城夜晚,己是万家灯火了。
孟蓝在路灯下走着,路灯投射到他身上,在地面反映出身影,随着他的步履移动。
夜风有些凛冽,抚过他的脸颊,硬硬地发疼。
他迷朦地感到前面似乎有人群列队瞅他。
站在前列的是刘科长和他老婆,随后的是妻子惠芳,再后面是红茶房老板。
孟蓝眼睛有些发涩,涩涩地酸楚,两滴泪便溢出眼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