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昆虫记
部编人教版八年级上名著阅读《昆虫记》知识点梳理及系列练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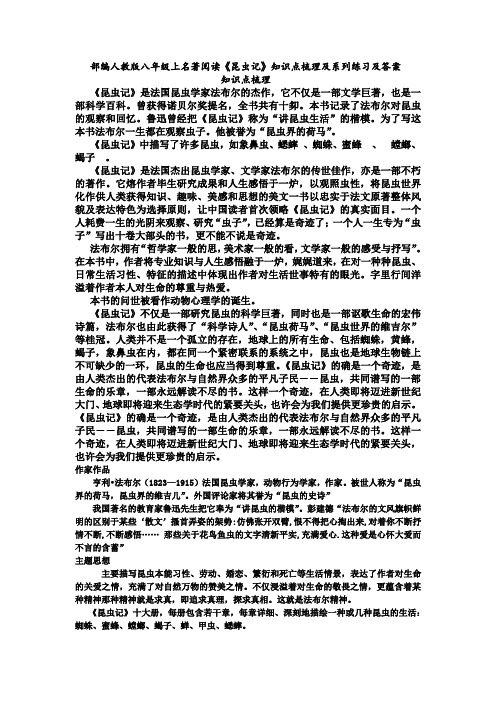
部编人教版八年级上名著阅读《昆虫记》知识点梳理及系列练习及答案知识点梳理《昆虫记》是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的杰作,它不仅是一部文学巨著,也是一部科学百科。
曾获得诺贝尔奖提名,全书共有十卶。
本书记录了法布尔对昆虫的观察和回忆。
鲁迅曾经把《昆虫记》称为“讲昆虫生活”的楷模。
为了写这本书法布尔一生都在观察虫子。
他被誉为“昆虫界的荷马”。
《昆虫记》中描写了许多昆虫,如象鼻虫、蟋蟀、蜘蛛、蜜蜂、螳螂、蝎子。
《昆虫记》是法国杰出昆虫学家、文学家法布尔的传世佳作,亦是一部不朽的著作。
它熔作者毕生研究成果和人生感悟于一炉,以观照虫性,将昆虫世界化作供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美文一书以忠实于法文原著整体风貌及表达特色为选择原则,让中国读者首次领略《昆虫记》的真实面目。
一个人耗费一生的光阴来观察、研究“虫子”,已经算是奇迹了;一个人一生专为“虫子”写出十卷大部头的书,更不能不说是奇迹。
法布尔拥有“哲学家一般的思,美术家一般的看,文学家一般的感受与抒写”。
在本书中,作者将专业知识与人生感悟融于一炉,娓娓道来,在对一种种昆虫、日常生活习性、特征的描述中体现出作者对生活世事特有的眼光。
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本人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
本书的问世被看作动物心理学的诞生。
《昆虫记》不仅是一部研究昆虫的科学巨著,同时也是一部讴歌生命的宏伟诗篇,法布尔也由此获得了“科学诗人”、“昆虫荷马”、“昆虫世界的维吉尔”等桂冠。
人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包括蜘蛛,黄蜂,蝎子,象鼻虫在内,都在同一个紧密联系的系统之中,昆虫也是地球生物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昆虫的生命也应当得到尊重。
《昆虫记》的确是一个奇迹,是由人类杰出的代表法布尔与自然界众多的平凡子民――昆虫,共同谱写的一部生命的乐章,一部永远解读不尽的书。
这样一个奇迹,在人类即将迈进新世纪大门、地球即将迎来生态学时代的紧要关头,也许会为我们提供更珍贵的启示。
《昆虫记》的确是一个奇迹,是由人类杰出的代表法布尔与自然界众多的平凡子民――昆虫,共同谱写的一部生命的乐章,一部永远解读不尽的书。
部编版统编版八上名著《昆虫记》名家评论式阅读题

《昆虫记》名人评价式阅读题1、鲁迅把《昆虫记》奉为“讲昆虫生活的楷模”,你认为鲁迅给予该书这么高评价的原因是什么?(1)《昆虫记》将昆虫鲜为人知的生活和习性生动地揭示出来,关注的是昆虫活生生的生命过程,使人们得以了解昆虫的真实生活情景。
2)《昆虫记》写作技巧高超。
行文活泼,语言诙谐,还常常以拟人的手法表现昆虫世界。
(3)《昆虫记》堪称科学与文学完美结合的典范。
2、有人说:“《昆虫记》是优秀的科普作品,也是公认的文学经典。
”你认同这一评价吗?请结合《昆虫记》内容简述理由。
认同。
作为昆虫学家,法布尔是严谨细致的,他根据观察得来的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将昆虫鲜为人知的生活和习性生动地揭示出来,使人们得以了解昆虫的真实生活情景,因此,《昆虫记》是优秀的科普作品;《昆虫记》行文生动活泼,语调轻松诙谐,字里行间情趣盎然,是公认的文学经典。
3、巴金说:“《昆虫记》熔作者毕生的研究成果和人生感悟于一炉,以人性观察虫性,将昆虫世界化作供人类获取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美文。
”请从“趣味”“美感…,思想”中任选一个关键词,结合《昆虫记》的内容谈谈你对这个词的理解。
(80字左右)【答案】答案示例:趣味——在《昆虫记》中,比如法布尔写蝉的幼虫,描述它们用自身的汁液在隧道的墙上涂抹“水泥”,使道壁坚固,写出了小生灵们的情态、智慧,让人读起来兴味盎然。
4、,鲁迅曾评价它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书”。
请结合书中具体情节谈谈“趣”在哪里?“益”在何处?示例:有趣之处:在昆虫学家法布尔的笔下,杨柳天牛像个吝啬鬼,身穿一件似乎“缺了布料”的短身燕尾礼服;小甲虫“为它的后代作出无私的奉献,为儿女操碎了心”;而被毒蜘蛛咬伤的小麻雀,也会“愉快地进食,如果我们喂食动作慢了,他甚至会像婴儿般哭闹”。
它行文生动活泼,语调轻松诙谐,充满了盎然的情趣。
有益之处:(1、该书让我们了解到昆虫的生活和习性2、该书让我们感受到作者对生命的尊重、对自然万物的赞美3、该书让我们体会到野外观察和实验的方法)法布尔细致入微地观察毛虫的旅行,他不顾危险捕捉黄蜂,他大胆假设、谨慎实验、反复推敲实验过程与数据,一步一步推断高鼻蜂毒针的作用时间与效果,萤的捕食过程,捕蝇蜂处理猎物的方法,孔雀蛾的远距离联络……一次实验失败了,他收集数据、分析原因,转身又设计下一次实验。
部编版八年级上册第五单元 昆虫记 专题探究(含答案和解析)

部编版八年级上册第五单元 昆虫记 专题探究 练习(含答案和解析)一、填空与阅读。
姓名: 得分:1.《昆虫记》,又叫,这一著作被誉为,其作者被称为。
作者是国的昆虫学家、文学家。
2.《昆虫记》总共有卷,既是一部又是一部。
《昆虫记》曾经获得奖提名,透过昆虫世界折射出。
3.《昆虫记》一书中描写了许多的昆虫,请任意举出四种,例如:、、、。
4.鲁迅把《昆虫记》奉为“讲昆虫生活的楷模”,你认为鲁迅给予该书这么高评价的原因是什么?5.阅读名著选段,请回答问题。
【甲】当那个可怜的蝗虫移动到螳螂刚好可以碰到它的地方时,螳螂就毫不客气,一点儿也不留情地立刻动用它的武器,用它那有力的‘掌’重重地击打那个可怜虫,再用那两条锯子用力地把它压紧。
于是,那个小俘虏无论怎样顽强抵抗,也无济于事了。
【乙】他拉上了个买卖,把车拉起来,他才晓得天气的厉害已经到了不允许任何人工作的程度。
一跑,便喘不过气来,而且嘴唇发焦,明知心里不渴,也见水就要喝。
不跑呢,那毒花花的太阳把手和脊背都要晒裂。
好歹的拉到了地方,他的裤褂全裹在了身上。
【甲】段文字选自名著《①》,作者是②,他为我们展现了大自然的小生灵们鲜为人知的生活和习性。
【乙】段出自名著《③》,作者是④,这里所写的是⑤(写出人名)在烈日下拉车的情景,细腻逼真,令人感同身受。
6.名著阅读。
①蝈蝈儿也存在着同类相食的现象。
诚然,在我的笼子里,我从来没见过像螳螂那样捕杀姐妹、吞吃丈夫的残暴行径,但是如果一只蝈蝈儿死了,活着的一定不会放过品尝其肌体的机会的,就像吃普通的猎物一样。
这并不是因为食物缺乏,而是因为贪婪才吃死去的同伴。
②撇开这一点儿不谈,蝈蝈儿是彼此十分和睦地共居在一起的,它们之间从没有发生严重的争吵,二、选择题。
顶多面对食物时有点儿敌对行为而已。
我扔入一片梨,一只蝈蝈儿立即占住它。
谁要是来要这块美味的食物,出于妒忌,它便踢腿把对方赶走。
自私心是到处都存在的。
吃饱了,它便让位给另一只蝈蝈儿,而另一只也立刻变得不宽容。
部编八上语文五单元名著导读《昆虫记》 科普作品的阅读

3.世界上第一次子午线实测工作,是 在我国__唐__代__(朝代)时进行的。
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
【作者简介】 蕾切尔·卡森,美国海洋生物学家、科普作
家,她的作品《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引发了美国以至于全世界的环境保护事业。1980 年被追授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主要内容】
专题三:跟法布尔学写作
1.从写作的角度精读《昆虫记》,摘抄若干 精彩片段,进行鉴赏、点评。
2.观察你喜欢的小动物,学习法布尔的写作 技巧,进行仿写。
第1题示例:
“沉默寡言、生活隐秘、天生无趣”的隐修 士——蝎子,是胆小鬼。不知是出于自私还是胆 小,它们不能容忍与同类共居。所以胜方吃掉败 方,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然而蝎子的猎食有时 并不是为了食欲。它们的饭量小得出奇,除了交 尾期,一年中有四分之三的时间不进食。它们不 吃死尸,只对滴血的猎物兴趣盎然。品行如斯的 蝎子在对待爱情时却另有行径。
【写作手法】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在讲求科学性、知识 性的同时,还兼顾了趣味性。该书用深入浅出的 语言,按照天文学的发展历史,从古到今,一步 步揭示了人类探索宇宙、揭示天体奥秘的过程, 呈现了科学发展的历程;书中不时穿插一些天文
发现的故事,极大地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把 人类对天空的遐想和科学的解读进行鲜明的对比, 在揭示、纠偏的同时,表现了作者对浩瀚宇宙的 探索和赞美之情。作者欲通过该书培养青少年学 科学、爱科学的精神,吸引更多的青少年投身天 文学的研究当中。
年累月辛苦劳作,侍奉蚁后,喂养幼蚁,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蚁后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这真是太不公平了。我不免为工蚁的命运鸣不 平,真希望有一天公平正义的阳光能照进黑暗 的蚁穴。
这就是我喜爱的黑色的小生灵——蚂蚁。
专题06《昆虫记》知识梳理-备战2024年中考语文名著阅读知识(考点)梳理+真题演练

专题06《昆虫记》知识梳理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法国昆虫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博物学家、昆虫学家、科普作家。
他是第一位在自然环境中研究昆虫的科学家,他以毕生的时间与精力,仔细观察昆虫的生活和它们为生存、繁衍所进行的斗争,然后将其观察所得写成详细确切的笔记,最后编写成巨著《昆虫记》。
《昆虫记》的成功为他赢得了“昆虫界的荷马”“昆虫界的维吉尔”的美名。
1880年,法布尔用积攒下的一小笔钱,在小镇附近购得一处坐落在荒地上的老旧民宅。
他用当地的普罗旺斯语给这处居所取了个风趣的雅号——荒石园。
此后,法布尔守着心爱的“荒石园”,开足生命的马力,年复一年,不知疲倦的从事昆虫学研究,把劳动成果汇成一卷又一卷的《昆虫记》。
1910年,《昆虫记》第十卷问世了,这时法布尔已是86岁高龄的老人了。
法国文学界推荐他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可惜诺奖委员们还没来得及做最后决定,便传来法布尔离世的消息。
1915年10月11日,这位“以昆虫为琴拨响人类命运颤音的巨人”与世长辞。
《昆虫记》是一部严谨的科学著作,一部关于昆虫的百科全书,同时也是一部讴歌生命的宏伟诗篇。
作者法布尔通过长时间的细致观察,获得了大量关于不同种类昆虫的特征、习性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将昆虫世界真实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昆虫记》分十卷,每一卷分17~25不等的章节,每章节详细、深刻地描绘一种或几种昆虫的生活,同时收入一些讲述经历、回忆往事的传记性文章。
在该书中,作者描述了小小的昆虫恪守自然规则,为了生存和繁衍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作者依据其毕生从事昆虫研究的经历和成果,以人性观照虫性,又以虫性反映社会人生。
重点介绍了他所观察和研究的昆虫的外部形态、生物习性,真实地记录了几种常见昆虫的本能、习性、劳动、死亡等。
《昆虫记》是一本讲昆虫生活的书,涉及蜣螂、蚂蚁、西绪福斯虫等100多种昆虫。
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现在已知的昆虫种类约100万种,占所有已经知晓的动物种类的5/6;并且仍有几百万的未知晓的昆虫仍待人类去发现和认知。
八年级上册语文第五单元名著导读:昆虫记

《昆虫记》
科普作品的阅读
阅读指导
1.借助前言、后记或附录中有关作家作品的介绍,了解作 家的生平事迹、科学成就和全书的大致内容,为阅读整本书做 些准备。
2.在阅读中,遇到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概念、术语,要查找 工具书或相关资料,把握其含义;要运用自己在课内外学到的 知识加强理解,深化认识;如果科普作品的内容是你非常感兴 趣或比较熟悉的,也可以质疑问难,拓展延伸,把阅读引向更 深层次。
(2)有人说“这种敬畏生命的情怀,给《昆虫记》这 部科学著作注入了灵魂和生气”,请以上面语段 为例,说说这段文字是如何体现作者“敬畏生 命”的情怀的。
示例一:“可怜做母亲的对此一无所知”,作者把面 临蚋对自己家族的毁灭性破坏而一无所知的蝉说成 “可怜的母亲”,还有“让自己牺牲”等词语,都体 现出作者对蝉的怜惜,字里行间充满悲悯情怀。 示例二:描写的对象是昆虫,但作者却把它们当作人 来写,体现了对生命的敬畏。
毛,通常黑色的鞘翅上有红色或黄色的斑纹,或红色、 黄色的鞘翅上有黑色的斑纹,但有些鞘翅却是黄色、红 色或棕色的,没有斑点,这些鲜艳的颜色具有警戒的作 用,可以吓退天敌。 (1)这段文字主要描写的对象是 瓢虫 。
(2)《昆虫记》是“公认的文学经典”,语言很有特 色,请结合文段加以分析。
《昆虫记》行文生动活泼,语调轻松诙谐,充满了盎 然的情趣。如,把瓢虫鼓鼓的身体比喻为“半粒豌 豆”,生动形象;对瓢虫鞘翅颜色的描写,细致入 微;“吓退”一词对其颜色作用的描写更是充满幽默 感。
织“罗网”方面独具才能; 螳螂 善于利用“心理战
术”制服敌人。
2.(湖北孝感中考)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几乎每次进餐后,它(蓝图拉毒蛛)都要整理一 下仪容。譬如用前腿上的跗节把触须和上颚里里外外 清扫干净。
2021年中考语文二轮专题复习_名著导读专题练习——《昆虫记》【含答案】

2021年中考语文二轮专题复习名著导读专题练习——《昆虫记》1. 走近名著。
一个人耗尽一生的光阴来观察、研究昆虫,已经算是奇迹了;一个人一生专为昆虫写出十卷大部头的书,更不能不说是奇迹。
这些奇迹的创造者就是法布尔,他的《昆虫记》被誉为“_______________”。
在这本书中,_______________在地下“潜伏”四年;_______________在编织“罗网”方面独具才能;_______________善于利用“心理战术”制服敌人。
2. 名著阅读。
《昆虫记》是优秀的科普读物,也是公认的文学经典。
鲁迅把它奉为“讲昆虫生活的楷模”。
在作者笔下,________像个吝啬鬼,身穿一件似乎“缺了布料”的短身燕尾礼服;“________”为它的后代作出无私的奉献,为儿女操碎了“心”;________会“愉快地进食,如果我们喂食动作慢了,它甚至会像婴儿般哭闹”。
3. 阅读下面文本,完成下面问题。
你们是把昆虫开膛破肚,而我是在它们活蹦乱跳的情况下进行研究;你们把昆虫变成一堆既恐怖又可怜的东西,而我则使得人们喜欢它们;你们在酷刑室和碎尸场里工作,而我是在蔚蓝的天空下,在鸣蝉的歌声中观察;你们用试剂测试蜂房和原生质,而我却研究本能的最高表现;你们探究死亡,而我却探究生命。
这里的“我”是_______________,他一反常规,用_______________和实验的方法来研究昆虫的本能和习性。
他的名著《昆虫记》,堪称_______________完美结合的典范,赢得了“_______________”的美誉。
4. 阅读下面文本,完成下列各题。
早已准备好的九寸长的空芦管可以阻止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
把这根空芦管插进差不多九寸长的隧道里面的时候,就形成了一根自动引水管。
于是石油可以顺着导管流入土穴中,一点儿也不会漏掉,而且,速度还很快。
然后,我们再用一块事先已经捏好的泥土,像瓶塞子一样,塞住出入的孔道口,断绝这些黄蜂的后路。
名著中考试题:《昆虫记》(含答案)

名著中考试题:《昆虫记》(含答案)1、法国有一个人耗尽了一生的精力来研究昆虫,并专为昆虫写出了十卷大部头的书,这个人是_________;这本书时《__________》,这本书又译为《昆虫物语》或《昆虫学札记》,全书充满了对生命的关爱之情,充满了对自然万物的赞美之情,被誉为“__________”。
法布尔昆虫记昆虫的史诗2、鲁迅把《昆虫记》奉为“讲昆虫生活的楷模”,你认为鲁迅给予该书这么高评价的原因是什么?(1)《昆虫记》将昆虫鲜为人知的生活和习性生动地揭示出来,使人们得以了解昆虫的真实生活情景。
(2)《昆虫记》是优秀的科普著作,也是公认的文学经典。
3、阅读《昆虫记》中《绿色蝈蝈》选段,回答问题。
①为了变换食物的花样,我还给蝈蝈吃很甜的水果:几片梨子,几颗葡萄,几块西瓜。
这些它们都很喜欢吃。
就像英国人酷爱吃用果酱作作料的带血的牛排一样,绿色蝈蝈酷爱甜食。
也许这就是它抓到蝉后首先吃肚子的原因,因为肚子既有肉,又有甜食。
②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吃到沾糖的蝉肉的,因此别的东西也得吃。
对于金龟子一类的昆虫,它毫不犹豫地都接受,吃得只剩下翅膀、头和爪。
③这一切都说明蝈蝈喜欢吃昆虫,尤其是没有过于坚硬的盔甲保护的昆虫。
它十分喜欢吃肉,但不像螳螂一样只吃肉。
蝈蝈这蝉的屠夫在吃肉喝血之后,也吃水果的甜浆,有时没有好吃的,甚至还吃一点儿青草。
④蝈蝈也存在着同类相食的现象。
诚然,在我的笼子里,我从来没见过像螳螂那样捕杀姊妹、吞吃丈夫的残暴行径,但是如果一只蝈蝈死了,活着的一定不会放过品尝其尸体的机会的,就像吃普通的猎物一样。
这并不是因为食物缺乏,而是因为贪婪才吃死去的同伴。
⑤撇开这一点不谈,蝈蝈是彼此十分和睦地共居在一起的,它们之间从不争吵,顶多面对食物有点儿敌对行为而已。
我扔入一片梨,一只蝈蝈立即占住它。
谁要是来咬这块美味的食物,出于妒忌,它便踢腿把对方赶走。
自私心是到处都存在的。
吃饱了,它便让位给另一只蝈蝈,这时它变得宽容了。
《昆虫记》读后感600字作文 昆虫记读后感600字(优秀8篇)

《昆虫记》读后感600字作文昆虫记读后感600字(优秀8篇)昆虫记读后感篇一历史的风沙蹉跎了往昔的岁月,掩盖住了曾经的荣光,却怎么也掩盖不住经典的辉煌。
暑假期间,我有幸读到法布尔的《昆虫记》,在作者的带领下,我看见一个生动有趣的昆虫世界。
《昆虫记》是法布尔的传世巨作,这本书是根据法布尔毕生精力和研究编写的一部作品。
书中详细观察了昆虫的生活和为生活以及繁衍种族所进行的斗争,以虫性反观社会人生,不但展现了法布尔科学观察研究方面的才华,同时向读者传达了她的人文精神以及对生命的无比热爱。
在这本书里,有许多我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昆虫,也有大家熟知、害怕的昆虫。
以前,我对昆虫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喜欢,甚至讨厌。
但是在法布尔的文字中,我看到了许多昆虫的庐山真面目,也感受到了昆虫的神奇与可爱,明白昆虫也是有感情的,它们是大自然的生灵,是人类的朋友,而不是令人厌恶的对象。
在法布尔的书中,我最喜欢的是萤火虫这一章。
以前我只是因为萤火虫能够发光便对它格外关注。
现在,我对萤火虫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萤火虫,又名流萤、宵烛、夜光;它有一个神秘的身份麻醉师;它是昆虫界不折不扣的肉食主义者;在它的身上有独特的玫瑰花瓣,这能帮助萤火虫牢牢得地吸附在某个物体的表面法布尔的笔触饱含感情,在他的心中,世间生灵皆平等,昆虫也可以像人类一样有自己的生活。
在他们的背后,也有许多的故事,我们应该像法布尔学习,养成善于观察的好习惯,去发现生活中的美。
看过这本书后,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更加热爱大自然。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为大自然的神奇而喝彩,为生命的多姿而喝彩!教师评语:经典在你笔下更为经典,你为昆虫所感动,为生命喝彩,老师为你的文字点赞!立意深刻,自然联系现实,条理清晰,浑然天成!名著《昆虫记》读后感400字篇二____是一位法国的昆虫学家。
今天,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读____所写的一部著作——《昆虫记》。
____是第一位在自然界中研究昆虫的科学家,在自然环境中对昆虫进行观察与实验,真实地记录下昆虫的本能与习性,写成了《昆虫记》这部昆虫学巨著,他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
《昆虫记》课外阅读知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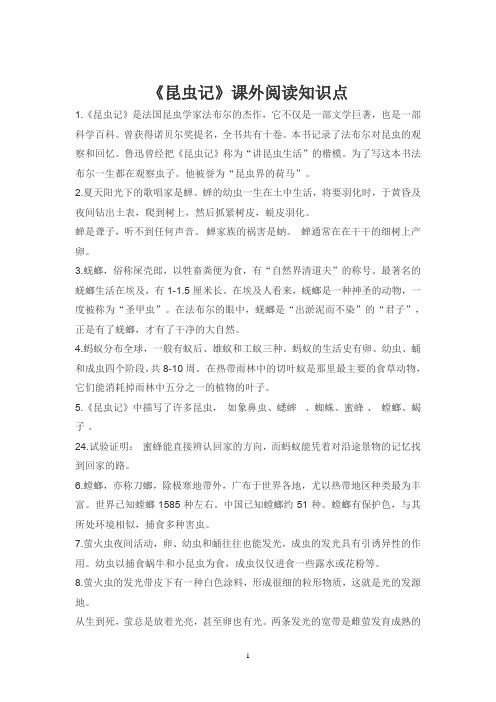
《昆虫记》课外阅读知识点1.《昆虫记》是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的杰作,它不仅是一部文学巨著,也是一部科学百科。
曾获得诺贝尔奖提名,全书共有十卷。
本书记录了法布尔对昆虫的观察和回忆。
鲁迅曾经把《昆虫记》称为“讲昆虫生活”的楷模。
为了写这本书法布尔一生都在观察虫子。
他被誉为“昆虫界的荷马”。
2.夏天阳光下的歌唱家是蝉。
蝉的幼虫一生在土中生活,将要羽化时,于黄昏及夜间钻出土表,爬到树上,然后抓紧树皮,蜕皮羽化。
蝉是聋子,听不到任何声音。
蝉家族的祸害是蚋。
蝉通常在在干干的细树上产卵。
3.蜣螂,俗称屎壳郎,以牲畜粪便为食,有“自然界清道夫”的称号。
最著名的蜣螂生活在埃及,有1-1.5厘米长。
在埃及人看来,蜣螂是一种神圣的动物,一度被称为“圣甲虫”。
在法布尔的眼中,蜣螂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正是有了蜣螂,才有了干净的大自然。
4.蚂蚁分布全球,一般有蚁后、雄蚁和工蚁三种。
蚂蚁的生活史有卵、幼虫、蛹和成虫四个阶段,共8-10周。
在热带雨林中的切叶蚁是那里最主要的食草动物,它们能消耗掉雨林中五分之一的植物的叶子。
5.《昆虫记》中描写了许多昆虫,如象鼻虫、蟋蟀、蜘蛛、蜜蜂、螳螂、蝎子。
24.试验证明:蜜蜂能直接辨认回家的方向,而蚂蚁能凭着对沿途景物的记忆找到回家的路。
6.螳螂,亦称刀螂,除极寒地带外,广布于世界各地,尤以热带地区种类最为丰富。
世界已知螳螂1585种左右。
中国已知螳螂约51种。
螳螂有保护色,与其所处环境相似,捕食多种害虫。
7.萤火虫夜间活动,卵、幼虫和蛹往往也能发光,成虫的发光具有引诱异性的作用。
幼虫以捕食蜗牛和小昆虫为食,成虫仅仅进食一些露水或花粉等。
8.萤火虫的发光带皮下有一种白色涂料,形成很细的粒形物质,这就是光的发源地。
从生到死,萤总是放着光亮,甚至卵也有光。
两条发光的宽带是雌萤发育成熟的9. 蟋蟀种类很多,最普通的为中华蟋蟀,体长约20毫米,年生一代。
蟋蟀生性孤僻,一般情况下都是独自生活,决不允许和别的蟋蟀住在一起,它们彼此之间不能容忍,一旦碰到一起就会咬斗起来,蟋蟀是以善鸣好斗著称的。
读《昆虫记》有感(10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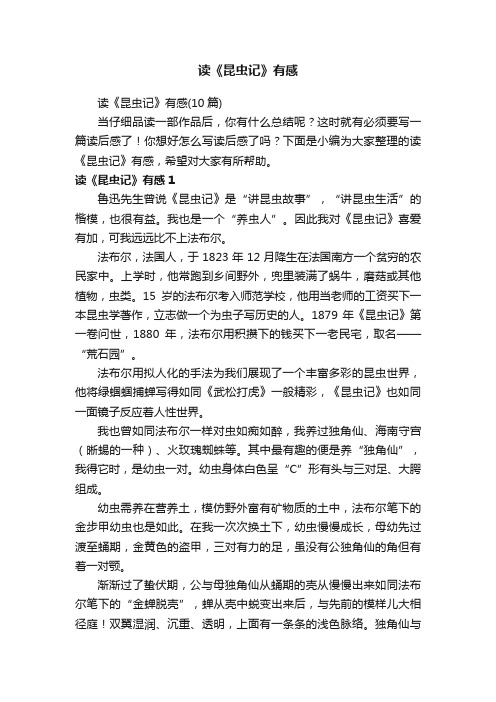
读《昆虫记》有感读《昆虫记》有感(10篇)当仔细品读一部作品后,你有什么总结呢?这时就有必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你想好怎么写读后感了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读《昆虫记》有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读《昆虫记》有感1鲁迅先生曾说《昆虫记》是“讲昆虫故事”,“讲昆虫生活”的楷模,也很有益。
我也是一个“养虫人”。
因此我对《昆虫记》喜爱有加,可我远远比不上法布尔。
法布尔,法国人,于1823年12月降生在法国南方一个贫穷的农民家中。
上学时,他常跑到乡间野外,兜里装满了蜗牛,磨菇或其他植物,虫类。
15岁的法布尔考入师范学校,他用当老师的工资买下一本昆虫学著作,立志做一个为虫子写历史的人。
1879年《昆虫记》第一卷问世,1880年,法布尔用积攒下的钱买下一老民宅,取名——“荒石园”。
法布尔用拟人化的手法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昆虫世界,他将绿蝈蝈捕蝉写得如同《武松打虎》一般精彩,《昆虫记》也如同一面镜子反应着人性世界。
我也曾如同法布尔一样对虫如痴如醉,我养过独角仙、海南守宫(晰蜴的一种)、火玫瑰蜘蛛等。
其中最有趣的便是养“独角仙”,我得它时,是幼虫一对。
幼虫身体白色呈“C”形有头与三对足、大腭组成。
幼虫需养在营养土,模仿野外富有矿物质的土中,法布尔笔下的金步甲幼虫也是如此。
在我一次次换土下,幼虫慢慢成长,母幼先过渡至蛹期,金黄色的盗甲,三对有力的足,虽没有公独角仙的角但有着一对颚。
渐渐过了蛰伏期,公与母独角仙从蛹期的壳从慢慢出来如同法布尔笔下的“金蝉脱壳”,蝉从壳中蜕变出来后,与先前的模样儿大相径庭!双翼湿润、沉重、透明,上面有一条条的浅色脉络。
独角仙与蝉有雷同,但独角仙有着蚴黑的盗甲如同出征战士的装备,不出意料独角仙是好斗者,如果你细心观察常常会在树上观察到两只公独角仙为争夺窃窕淑女而大大出手。
我的两只独角仙吃着昆虫果冻度过晚年,但他们却没有产生爱情的结晶;便一命呜呼了。
法布尔曾说:“你们探究死亡,而我却探究生命。
昆虫记读书笔记(15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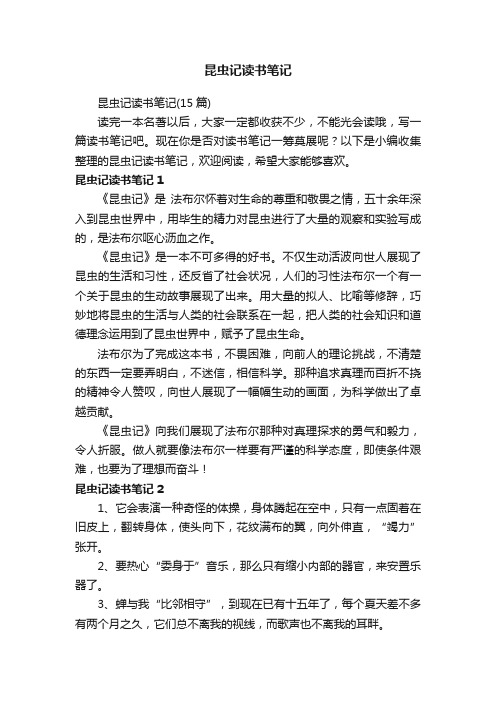
昆虫记读书笔记昆虫记读书笔记(15篇)读完一本名著以后,大家一定都收获不少,不能光会读哦,写一篇读书笔记吧。
现在你是否对读书笔记一筹莫展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昆虫记读书笔记,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昆虫记读书笔记1《昆虫记》是法布尔怀着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之情,五十余年深入到昆虫世界中,用毕生的精力对昆虫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实验写成的,是法布尔呕心沥血之作。
《昆虫记》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不仅生动活波向世人展现了昆虫的生活和习性,还反省了社会状况,人们的习性法布尔一个有一个关于昆虫的生动故事展现了出来。
用大量的拟人、比喻等修辞,巧妙地将昆虫的生活与人类的社会联系在一起,把人类的社会知识和道德理念运用到了昆虫世界中,赋予了昆虫生命。
法布尔为了完成这本书,不畏困难,向前人的理论挑战,不清楚的东西一定要弄明白,不迷信,相信科学。
那种追求真理而百折不挠的精神令人赞叹,向世人展现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为科学做出了卓越贡献。
《昆虫记》向我们展现了法布尔那种对真理探求的勇气和毅力,令人折服。
做人就要像法布尔一样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即使条件艰难,也要为了理想而奋斗!昆虫记读书笔记21、它会表演一种奇怪的体操,身体腾起在空中,只有一点固着在旧皮上,翻转身体,使头向下,花纹满布的翼,向外伸直,“竭力”张开。
2、要热心“委身于”音乐,那么只有缩小内部的器官,来安置乐器了。
3、蝉与我“比邻相守”,到现在已有十五年了,每个夏天差不多有两个月之久,它们总不离我的视线,而歌声也不离我的耳畔。
4、这样几下抖动便去掉了舍腰蜂刚刚初具规模的窠巢,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它的蜂巢居然已经有一个橡树果子那样大了,真让人始料不及。
它们可真是一些让人惊奇的小动物。
5、临近沟渠的时候,它当然就会注意到这件可喜的事情,于是就匆匆忙忙地跑过来取水边这一点点十分宝贵的泥土。
它们不肯轻意放过这没有湿气的时节极为珍稀的发现。
6、臂,其实是最可怕的利刃,无论什么东西经过它的身边,它便立刻原形毕露,用它的凶器加以捕杀。
部编版八年级语文上册第五单元名著导读《昆虫记》名家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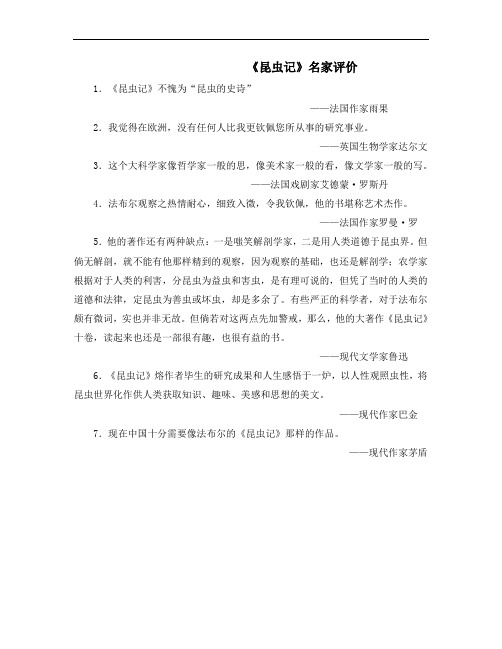
《昆虫记》名家评价
1.《昆虫记》不愧为“昆虫的史诗”
——法国作家雨果2.我觉得在欧洲,没有任何人比我更钦佩您所从事的研究事业。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3.这个大科学家像哲学家一般的思,像美术家一般的看,像文学家一般的写。
——法国戏剧家艾德蒙·罗斯丹4.法布尔观察之热情耐心,细致入微,令我钦佩,他的书堪称艺术杰作。
——法国作家罗曼·罗5.他的著作还有两种缺点:一是嗤笑解剖学家,二是用人类道德于昆虫界。
但倘无解剖,就不能有他那样精到的观察,因为观察的基础,也还是解剖学;农学家根据对于人类的利害,分昆虫为益虫和害虫,是有理可说的,但凭了当时的人类的道德和法律,定昆虫为善虫或坏虫,却是多余了。
有些严正的科学者,对于法布尔颇有微词,实也并非无故。
但倘若对这两点先加警戒,那么,他的大著作《昆虫记》十卷,读起来也还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书。
——现代文学家鲁迅6.《昆虫记》熔作者毕生的研究成果和人生感悟于一炉,以人性观照虫性,将昆虫世界化作供人类获取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美文。
——现代作家巴金7.现在中国十分需要像法布尔的《昆虫记》那样的作品。
——现代作家茅盾。
昆虫记读书笔记_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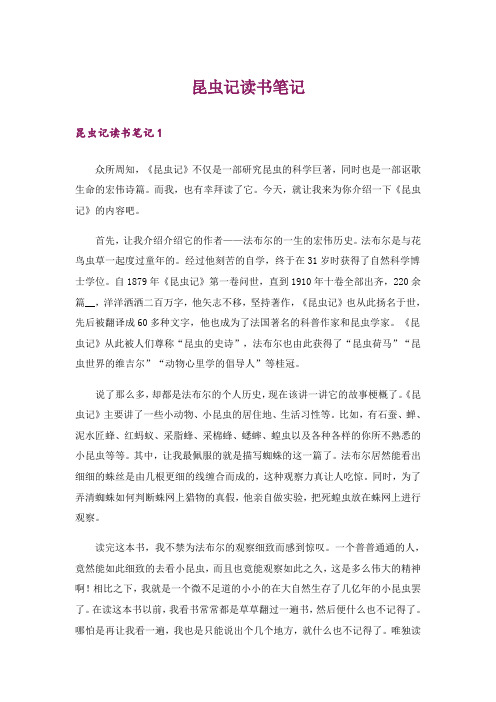
昆虫记读书笔记昆虫记读书笔记1众所周知,《昆虫记》不仅是一部研究昆虫的科学巨著,同时也是一部讴歌生命的宏伟诗篇。
而我,也有幸拜读了它。
今天,就让我来为你介绍一下《昆虫记》的内容吧。
首先,让我介绍介绍它的作者——法布尔的一生的宏伟历史。
法布尔是与花鸟虫草一起度过童年的。
经过他刻苦的自学,终于在31岁时获得了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自1879年《昆虫记》第一卷问世,直到1910年十卷全部出齐,220余篇__,洋洋洒洒二百万字,他矢志不移,坚持著作,《昆虫记》也从此扬名于世,先后被翻译成60多种文字,他也成为了法国著名的科普作家和昆虫学家。
《昆虫记》从此被人们尊称“昆虫的史诗”,法布尔也由此获得了“昆虫荷马”“昆虫世界的维吉尔”“动物心里学的倡导人”等桂冠。
说了那么多,却都是法布尔的个人历史,现在该讲一讲它的故事梗概了。
《昆虫记》主要讲了一些小动物、小昆虫的居住地、生活习性等。
比如,有石蚕、蝉、泥水匠蜂、红蚂蚁、采脂蜂、采棉蜂、蟋蟀、蝗虫以及各种各样的你所不熟悉的小昆虫等等。
其中,让我最佩服的就是描写蜘蛛的这一篇了。
法布尔居然能看出细细的蛛丝是由几根更细的线缠合而成的,这种观察力真让人吃惊。
同时,为了弄清蜘蛛如何判断蛛网上猎物的真假,他亲自做实验,把死蝗虫放在蛛网上进行观察。
读完这本书,我不禁为法布尔的观察细致而感到惊叹。
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竟然能如此细致的去看小昆虫,而且也竟能观察如此之久,这是多么伟大的精神啊!相比之下,我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的在大自然生存了几亿年的小昆虫罢了。
在读这本书以前,我看书常常都是草草翻过一遍书,然后便什么也不记得了。
哪怕是再让我看一遍,我也是只能说出个几个地方,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唯独读了这本书,一开始我也是草草翻过了几页,却被法布尔的写作功力深深的吸引住了。
从此,我便改变了看书、读书的习惯,也开始越来越认真地读所有的书籍。
有评论说:“法布尔的《昆虫记》是一般文学家无法企及的,因为它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
《昆虫记》中考习题训练及答案

名著《昆虫记》习题训练一、填空:1.法国有一个人耗尽了一生的精力研究昆虫,并专为昆虫写出了十卷大部头的书,这个人是;这本书是《》。
这本书又译为《》或《》,被誉为“”。
2.《昆虫记》的主题:。
3.(1)《昆虫记》中,法布尔不但仔细观察食粪虫劳动的过程,而且不无爱怜的称这些食粪虫为_________。
(2)它们扇动双翅,四足高高跷起,黑黑的肚子卷起触到黄色的足.用大颚仔细收察,从闪亮的淤泥表面挑选出精华.这是法布尔描写________从淤泥垒建巢穴时的情景。
(3)法布尔称赞_______的建筑才能,认为在这一点上_________远胜于卢浮宫的建筑艺术智慧。
(4)法布尔赞美昆虫的爱情,特别是在__________这一章中刻画的更是细致入微。
4.法布尔的《昆虫记》除真实记录昆虫的生活,还透过昆虫世界折射出。
全书充满了对生命的,充满了对自然万物的。
5.《昆虫记》在第三卷中写到的三种垒筑蜂分别是,,。
6.由于《昆虫记》中精确地记录了法布尔进行的试验,揭开了昆虫生命与生活习惯中的许多秘密,达尔文称法布尔为“”。
7.作者根据大量第一手资料,将昆虫的生活和习性揭示出,如在地下潜伏4年才能钻出地面,在阳光下歌唱5个星期;善建巢穴,管理家务;善于捕食、织网;善于利用“心理战术”制服敌人;可以不用任何工具“剪”下圆叶片做巢穴盖子。
8.在作者笔下,像个吝啬鬼,身穿一件似乎“缺了布料”的短身燕尾礼服;“为它的后代作出无私的奉献,为儿女操碎了心”;而被毒蛇蜘蛛咬伤的也会“愉快地进食,如果我们喂食动作慢了,它甚至会像婴儿般哭闹。
”9.《昆虫记》不仅是一部研究昆虫的科学巨著,同时也是一部讴歌生命的宏伟诗篇,法布尔也由此获得了“”、“”、“”等桂冠。
二、简答:1.《昆虫记》“是优秀的科普著作”,你从选文中获得了哪些科普知识?(3分)2.写出《昆虫记》中你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一种昆虫,并说明理由。
3.鲁迅把《昆虫记》奉为“讲昆虫生活的楷模”,你认为鲁迅给予该书这么高评价的原因是什么?(3分)4.《昆虫记》中写了不少昆虫的生活和习性,请你列举出3个5.《昆虫记》被誉为“昆虫的史诗”,这离不开作者法布尔的功劳,你从他身上得到哪些启示?(2分)6..《昆虫记》“透过昆虫世界折射出社会人生”,结合选文说说蟋蟀给你较大触动的有哪些方面?7.为什么称法布尔是昆虫学的荷马?8.《昆虫记》中昆虫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赋予了人的思想感情。
鲁迅与昆虫记

鲁迅与《昆虫记》王富仁《昆虫记》全集的出版,无疑是2001年中国书界的一大收获。
在本报和《Newton -科学世界》杂志社主办的年度“十大科普好书”评选中,该书榜上有名。
此外在《南方周末》、《中国图书商报》、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等媒体组织的年终盘点中,《昆虫记》也无一例外地入选“十大”之列,足可看出该书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地位。
我们都知道,早在20世纪初叶,《昆虫记》就得到了包括鲁迅、周作人等一大批领导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的赞誉和推荐,它在中国的传播史完全可以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
王富仁先生在此文中考证梳理了鲁迅先生与《昆虫记》的关系,今天我们品味鲁迅先生的有关论述,体会其中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和批判意识,依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法布尔《昆虫记》的全译本,这堪称中国文化的“世纪工程”。
我之称它为“世纪工程”,主要不是就其工程的规模而言,而是就其完成这一工程所经历的时间而言。
1923年1月,周作人在《晨报副镌》发表了他的《法布耳的〈昆虫记〉》,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这部世界名著,此后便陆续有各种选译本出版,直到2001年1月花城出版社这个全译本的出版,已经整整78年的时间了,还不足以称为“世纪工程”吗?我之知道法布尔的《昆虫记》,是通过鲁迅的作品。
从中学时代起,在我的印象中,法布尔就是和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爱迪生同样伟大的名字。
这种印象肯定是通过鲁迅作品形成的,因为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个渠道使我产生这样的印象了。
1925年4月,鲁迅写了他的杂文名篇《春末闲谈》,其中就讲到了细腰蜂的故事。
“细腰蜂”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称作“果蠃”。
据中国的博物家说,果蠃“纯雌无雄,必须捉螟蛉去做继子的。
她将小青虫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着,祝道…像我像我‟。
经过若干日,——我记不清了,大约是七七四十九日罢,——那青虫也就成了细腰蜂了,所以《诗经》里说:…螟蛉有子,果蠃负之。
‟”在中国,也有认为果蠃自能产卵,其捉青虫放在窠里是给孵化出来的幼蜂做食物的,但中国的老先生却宁肯相信果蠃捉螟蛉做继子的“趣谈”,没有人去做细致的观察,弄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昆虫记》读书笔记(15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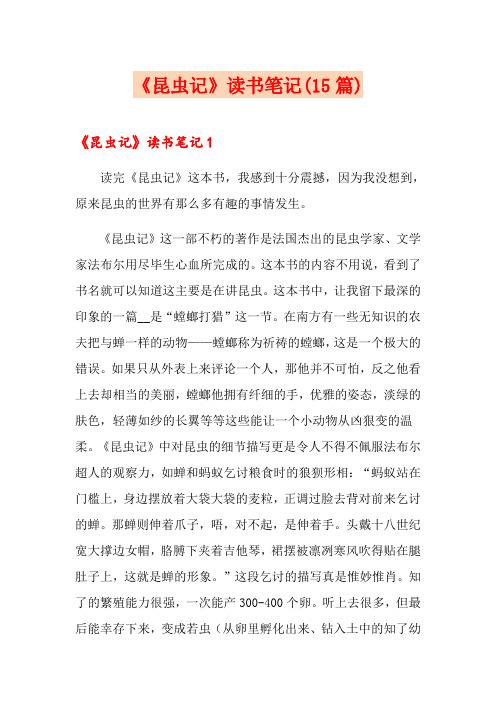
《昆虫记》读书笔记(15篇)《昆虫记》读书笔记1读完《昆虫记》这本书,我感到十分震撼,因为我没想到,原来昆虫的世界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
《昆虫记》这一部不朽的著作是法国杰出的昆虫学家、文学家法布尔用尽毕生心血所完成的。
这本书的内容不用说,看到了书名就可以知道这主要是在讲昆虫。
这本书中,让我留下最深的印象的一篇__是“螳螂打猎”这一节。
在南方有一些无知识的农夫把与蝉一样的动物——螳螂称为祈祷的螳螂,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如果只从外表上来评论一个人,那他并不可怕,反之他看上去却相当的美丽,螳螂他拥有纤细的手,优雅的姿态,淡绿的肤色,轻薄如纱的长翼等等这些能让一个小动物从凶狠变的温柔。
《昆虫记》中对昆虫的细节描写更是令人不得不佩服法布尔超人的观察力,如蝉和蚂蚁乞讨粮食时的狼狈形相:“蚂蚁站在门槛上,身边摆放着大袋大袋的麦粒,正调过脸去背对前来乞讨的蝉。
那蝉则伸着爪子,唔,对不起,是伸着手。
头戴十八世纪宽大撑边女帽,胳膊下夹着吉他琴,裙摆被凛冽寒风吹得贴在腿肚子上,这就是蝉的形象。
”这段乞讨的描写真是惟妙惟肖。
知了的繁殖能力很强,一次能产300-400个卵。
听上去很多,但最后能幸存下来,变成若虫(从卵里孵化出来、钻入土中的知了幼虫称为若虫)的为数不多,在这为数不多的若虫里,经过4年的途中生活,再变成真正的知了的那就是凤毛麟角了。
导致这一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有一种小苍蝇在知了产完卵后便把自己的卵也产在知了产卵的地方。
苍蝇的卵虽然比知了的卵小,但是蝇卵孵化地早,蝇蛆一出生就把知了的卵吃掉一大半。
可怜的知了到最后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还知道了:凌晨,蝉是怎样脱壳;屎壳螂是如何滚粪球的;蚂蚁是怎样去吃蚜虫的分泌物。
还弄清了:“螟蛉之子”是错误的,蜂抓青虫不是当成自己的儿子养,而是为自己的后代安排食物。
看!多么可爱的小生灵!难怪鲁迅把《昆虫记》奉为"讲昆虫故事,讲昆虫生活。
"的楷模。
法布尔坚持不懈地进行观察研究昆虫及植物,不断获得新成果。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鲁迅与《昆虫记》
王富仁
《昆虫记》全集的出版,无疑是2001年中国书界的一大收获。在本报和《Newton-科学世界》杂志社主办的年度“十大科普好书”评选中,该书榜上有名。此外在《南方周末》、《中国图书商报》、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等媒体组织的年终盘点中,《昆虫记》也无一例外地入选“十大”之列,足可看出该书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我们都知道,早在20世纪初叶,《昆虫记》就得到了包括鲁迅、周作人等一大批领导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的赞誉和推荐,它在中国的传播史完全可以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王富仁先生在此文中考证梳理了鲁迅先生与《昆虫记》的关系,今天我们品味鲁迅先生的有关论述,体会其中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和批判意识,依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法布尔《昆虫记》的全译本,这堪称中国文化的“世纪工程”。我之称它为“世纪工程”,主要不是就其工程的规模而言,而是就其完成这一工程所经历的时间而言。1923年1月,周作人在《晨报副镌》发表了他的《法布耳的〈昆虫记〉》,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这部世界名著,此后便陆续有各种选译本出版,直到2001年1月花城出版社这个全译本的出版,已经整整78年的时间了,还不足以称为“世纪工程”吗?我之知道法布尔的《昆虫记》,是通过鲁迅的作品。从中学时代起,在我的印象中,法布尔就是和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爱迪生同样伟大的名字。这种印象肯定是通过鲁迅作品形成的,因为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个渠道使我产生这样的印象了。1925年4月,鲁迅写了他的杂文名篇《春末闲谈》,其中就讲到了细腰蜂的故事。“细腰蜂”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称作“果蠃”。据中国的博物家说,果蠃“纯雌无雄,必须捉螟蛉去做继子的。她将小青虫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着,祝道‘像我像我’。经过若干日,——我记不清了,大约是七七四十九日罢,——那青虫也就成了细腰蜂了,所以《诗经》里说:‘螟蛉有子,果蠃负之。’”在中国,也有认为果蠃自能产卵,其捉青虫放在窠里是给孵化出来的幼蜂做食物的,但中国的老先生却宁肯相信果蠃捉螟蛉做继子的“趣谈”,没有人去做细致的观察,弄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长夏无事,遣暑林阴,瞥见二虫一拉一拒的时候,便如睹慈母教女,满怀好意,而青虫的宛转抗拒,则活像一个不识好歹的毛鸦头。”鲁迅这里说的,就是中国一般文人对自然事物的态度。他们不愿也不想了解事物的真相,宁愿相信各种虚幻不实但却趣味有加的想象性、杜撰性的解释,并在这种解释中闭上眼睛,求得自我心灵的刹那的满足。这就是中国文人常常说的“情趣”。在这时,鲁迅举出了法布尔。他说:“但究竟是夷人可恶,偏要讲什么科学。科学虽然给我们许多惊奇,但也搅坏了我们许多好梦。自从法国的昆虫学大家法勃耳(Fabre)仔细观察之后,给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证实了。而且,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一个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蜇,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烂,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的新鲜。”鲁迅这里说的,就是法布尔《昆虫记》花城出版社的全译本第1卷中关于节腹泥蜂几章特别是《高明的杀手》一章中所叙述的内容。花城出版社为法布尔《昆虫记》的出版所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法布尔的《昆虫记》“一方面用人性关照虫性,在昆虫身上倾注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又用虫性反观人类生活,思考人类的生存状态、生活态度、价值观念等等,睿智的哲思跃然纸上。”鲁迅是一个人性和国民性的解剖者,他在法布尔《昆虫记》中所获得的启发,主要用于对人性和国民性的解剖。虫性的生存动力几乎全部来源于本能,人类虽然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并常常用自己创造的文化标榜自己,掩盖自己的本能欲望,但人类的文化仍然是在本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许许多多的场合都还没有脱离纯粹动物本能的层次。人类的可笑与可悲不在于人类有本能,而在于人类常常用一种高雅的文化外衣掩盖起自己纯粹的动物本能欲望。人们无法发现各种文化外衣背后的本能欲望,也就无法识破这种文化的本质。鲁迅在《春末闲谈》中就指出,中国古代的圣君、贤臣、圣贤和圣贤之徒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其实也就像细腰蜂一样,是完全自私的,是损人利己的。什么“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石”了,什么“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了,什么“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了,无非只是一些细腰蜂的毒针,让广大社会群众承认他们的特权地位,承认他们作威作福的权利,而甘愿为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做牺牲,老老实实地听他们摆布,死心塌地地为他们服务。他们是人类的最高明的杀手,也希望把自己杀戮的本领锻炼到像细腰蜂那样完美无缺的地步。但是,他们面对的到底是同样有感受、有思想能力的人,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细腰蜂的水平。“要服从作威就需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需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棘手。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与果蠃并驱争先。即以皇帝一伦而言,便难免时常改姓易代,终没有‘万年有道之常’;‘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铁证。”正是利用细腰蜂的生活习性,鲁迅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古今中外所有那些为维护现实政治统治权力而编造出来的文化理论和文化学说。“遗老的圣经贤传法,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论”,都是这样一些既要人不活,又要人能为上等人服务的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集中于两点,一是“不准集合”,二是“不许开口”。鲁迅指出,这些统治术,虽然不能说没有任何的效果,但最终是免不了破产的命运的,因为它们根本无法达到细腰蜂毒针那种的效果。1925年,在与徐炳昶的通信中,鲁迅当谈到中国的思想启蒙的问题时说,民众“不是区区文字所能改革”的,当时的改革只好先从知识阶级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知识分子的启蒙,首先要有好的读物,而在适于青年的读物之中,鲁迅就特别提到了法布尔的《昆虫记》。他说:“单为在校的青年计,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我觉得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的。可惜中国现在的科学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过于高深,于是就很枯燥。现在要Brehm的讲动物生活,Fabre的讲昆虫故事似的有趣,并且插许多图画的;但这非有一个大书店担任即不能印。至于作文者,我以为只要科学家肯放低手眼,再看看文艺书,就够了。”在这里,鲁迅是把法布尔及其《昆虫记》同那些“踱进研究室”的学者和“搬入艺术宫”的文人相对举而言的。显而易见,鲁迅是不会绝对否认学者的研究和文人的艺术创作的,关键在于,一个学者的研究和一个文人的创作是建立在个人的所谓“成就”感之上,还是建立在中国社会的进步之上。中国社会正是利用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个人的“成就”感,把新旧两派的知识分子都从整个中国社会中孤立出来,使之成为有利于独裁政治而不是不利于自己独裁政治、有利于愚弄社会群众而不是有利于思想启蒙的现代文化摆设。鲁迅说:“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中了‘老法子’的计。我新近才看出这圈套,就是从‘青年必读书’事件以来,很收些赞同和嘲骂的信,凡赞同者,都很坦白,并无什么恭维。如果开首称我为什么‘学者’‘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是谩骂。我才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的。不料有许多人,却自囚在什么室什么宫里,岂不可惜。只要掷去了这种尊号,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舆论是以为学者只应该拱手讲讲义的),则世风就会日上,而月刊也办成了。”1933年,鲁迅写了《“人话”》一文,以法布尔《昆虫记》为例,说明读书观文要能够读出作者的立场来,虽是谈天说地,讲动物植物,也仍然离不开作者个人的立场。鲁迅说:“虽是意在给人科学知识的书籍或文章,为要讲得有趣,也往往太说些‘人话’。这毛病,是连法布耳(J.H.Fabre)做的大名鼎鼎的《昆虫记》(Souvenirs Entomologiques),也是在所不免的。”接着,鲁迅讲了一个中国作者讲动物生活的例子。这个作者在讲到鸟粪蜘蛛的时候说,鸟粪蜘蛛形体像鸟粪,又能伏着不动,“假做”鸟粪的样子;还说动物界中,“残食”自己“亲丈夫”的很多。鲁迅说:“这也未免太说了‘人话’。鸟粪蜘蛛只是形体原像鸟粪,性又不大走动罢了,并非它故意装作鸟粪模样,意在欺骗小虫豸。螳螂界中也尚无五伦之说,它在交尾中吃掉雄的,只是肚子饿了,在吃东西,何尝知道这东西就是自己的家主公。但经用‘人话’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