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舒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香港言情小说家-倪亦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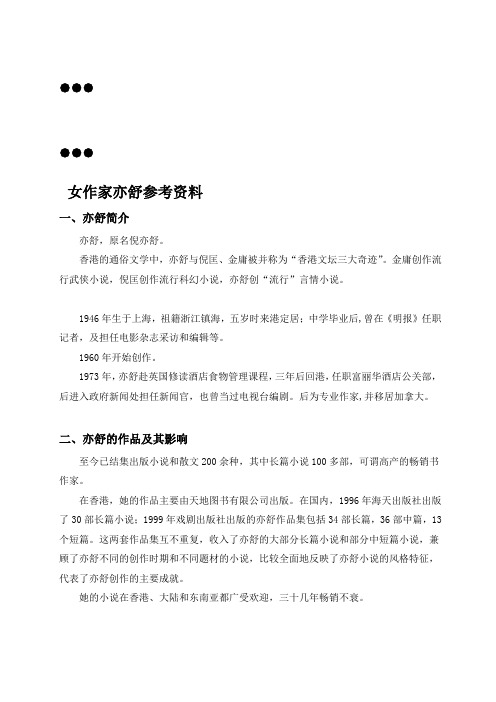
●●●●●●女作家亦舒参考资料一、亦舒简介亦舒,原名倪亦舒。
香港的通俗文学中,亦舒与倪匡、金庸被并称为“香港文坛三大奇迹”。
金庸创作流行武侠小说,倪匡创作流行科幻小说,亦舒创“流行”言情小说。
1946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镇海,五岁时来港定居;中学毕业后,曾在《明报》任职记者,及担任电影杂志采访和编辑等。
1960年开始创作。
1973年,亦舒赴英国修读酒店食物管理课程,三年后回港,任职富丽华酒店公关部,后进入政府新闻处担任新闻官,也曾当过电视台编剧。
后为专业作家,并移居加拿大。
二、亦舒的作品及其影响至今已结集出版小说和散文200余种,其中长篇小说100多部,可谓高产的畅销书作家。
在香港,她的作品主要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在国内,1996年海天出版社出版了30部长篇小说;1999年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亦舒作品集包括34部长篇,36部中篇,13个短篇。
这两套作品集互不重复,收入了亦舒的大部分长篇小说和部分中短篇小说,兼顾了亦舒不同的创作时期和不同题材的小说,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亦舒小说的风格特征,代表了亦舒创作的主要成就。
她的小说在香港、大陆和东南亚都广受欢迎,三十几年畅销不衰。
亦舒的小说属于通俗文学。
她的小说对通俗文化、香港流行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不单纯代表都市男女对爱情的幻想,而是负载了香港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家庭和爱情观念的变化、女性观念的转变等意义。
通过研究亦舒小说,可以了解香港通俗文化生产的方法、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等,进而了解香港社会文化发展的特征。
亦舒小说主要的读者群是女性。
由于亦舒小说非常流行,女性读者在传阅和讨论时形成了一种类似集体阅读的经验,这些经验影响了女性读者的精神世界,为她们理解都市人生、婚姻爱情以及时尚提供了参照,从而与她们的人生息息相关。
三、亦舒作品特色她的小说自成一格,开创了言情小说的新模式。
其特色有:1.亦舒的小说拥有地道的香港气息与浓郁的都市味道。
亦舒的作品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而且主要是以香港和欧美的现代大都市作为背景。
我看亦舒小说中的小资女性文学

我看亦舒小说中的小资女性文学摘要在香港的通俗文学中,亦舒以言情小说获得文学声誉,她的小说自成一格,散着浓郁的都市气息,语言简练流畅,篇章一气呵成,开创了言情小说的新模式。
她的小说,以独特的女性的角度,为女性的命运做出探索,从而塑造了其独特的女性形象,本文以探讨中国20世纪小资女性形象为主线,从爱情、寂寞、独立、衣食和旅行四个方面来论述了小资女性形象的特点,并阐述了亦舒塑造出的女性形象给我们现代女性所带来的启示。
关键词亦舒;小说;小资;女性形象“小资”是1990年代开始在中国大陆流行的名词,它是“小资产阶级”的简称,但是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者并不必然的是“小资”。
当下流行的“小资”一词的理解与看法众说纷纭,而我认为,“小资”一词实际上指的是一种生活情调,生活品位,在这种情调和品味中,渗透着对生活和生命的一種感悟和理解,作为这种感悟和理解,它是高于现实法则的一种浪漫情趣。
不管各人看法如何,随着社会的发展,小资文学也开始发展并形成了一种气候。
在这里我就以亦舒的小说为例,分析其中的小资女性。
一、关于爱情我认为有着小资情调的人都是怀旧的,比如一杯1878年的波尔多,或者一杯蓝山的咖啡,放着《卡萨布兰卡》或者《刺激1995》的D9碟片,或是和着一首《moon fiver》的舒缓音乐,但是他们的怀旧并非是这样单纯的怀旧,而是他们的脸面向着过去,倒退着走向新的时间和空间,生性有着浪漫的小资们就总是梦想着爱情或者是温暖。
亦舒小说中的一位女主人喜宝这样说过:“在生活中,你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爱。
”“第二希望得到什么?”“钱。
”“多少?”“足够。
”“多少是足够?”“不多。
”“还有其他的吗?”“健康。
”可以这么说,亦舒小说中的女主人都是渴望邂逅爱情的,爱情是重要的,奋不顾身的,但是爱与她们的现实生活是有别的,她们大多都是都会里的白领女性,聪明干练,但是在感情生活中却往往饱经沧桑,或情感受到挫折,或感到都市优秀男性的匮乏,苦于难觅知音,因而她们总是对男女间的感情有着清醒的认识,而非一般人的盲目。
女性主体意识的书写——浅析亦舒《她的二三事》

慧: “ 了十年舞,也 已经累透,纱裙被扯破,腰 间无数黑手 印,舞 人 却 不 贬 低 自 己。 从 这 方 面 看 , 李 亮 佳 不把 自己 立 于 客体 地 位 , 保 持 跳
池里全是十五六七岁 的小妹妹满场飞 ,也该是我这名前辈退下来的时 了可贵的主体性。亦舒 以女性为焦点创作出一系列别具意味的,不仅
人家就 不会说我贪钱 。” [ ] 4 她清 楚的知道 ,要 想达到 目标 的捷径
是主动出卖 自己,然后凭借 自身的实力一步步走 向成功。难能可贵的 是,在这一过程 中她没有像喜 宝一样迷失在金钱 的贪欲 中, 三伏 ,正 当人们 以为这次她肯定玩完 了,谁知她又再拔高大放异彩 ,
一
李亮佳与伏贞贞相反,她选择另一种表 现 自我主体性的方式,伏 贞贞是热烈的,她是沉 静的。她看似 最具中国传统儒 家哲 学意味 的形
、
叶结 好 一
风 信 子
《 的二三事》 中,叶结好并不是亦舒通常意义上钟情的女性形 象,是善解人意的化身。 “ 的静止 性能够产 生一种可贵的感受性, 她 她 象,她 一开始就 以家庭环境优越,不谙世事 的少女形 象出场 :5 O年代 因而她可 以做到忠 实、周到、通情达理 和充满深情 。” [ )这种特 7 打扮,红色跑车 ,不事生产,整 日玩乐 。 可在 如此表 象之 下,叶结好有着 令姐 姐芳好刮 目相看 的成熟 智 质使他深受 叶太太的喜爱,并获得叶芳好的赏识 。 从小是个孤女 ,所 以她接受现实。她给予但不失去 自我,取 悦他
的独到见解: “ 讲得难听点 ,之后万一有什 么不妥 ,也不致失救 ,家 像是一件不受欢迎 的杂务 , 干掉 它,好腾 出工夫来做正经事。” [ ] 8 里总欢迎 我, 我仍是母亲的宝贝女 , 以婚礼低调些好, 所 以免大袍大 甲, 女性主义者波伏娃说 “ 当她成为生产性的、主动的人时,她会重新获 有头威无尾阵,千万成本,只演出一年半载。” [ 3] 得超越性,她会通过设计具体地去肯定她的主体地位。”这是职业带 经济富足造就 了叶结好性格的 明媚 ,也许正是这种对生活的清醒 给 现 代 女 性 的 宝 贵 选 择 权 , 她 们 不 再 是 一 味 被 动 地 接 受 事 物 还 可 以 主 认知,使得叶结好不仅依靠 自身的乐观活泼收获一份好姻缘,也使之 动去选择 。 ( )亦舒笔 下的这些都会 职业女性 已经 走出 了女人 要为 9 成为 《 的二三事》中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她
女性主体意识的成熟:《我的前半生》中女性成长主题解读

女性主体意识的成熟:《我的前半生》中女性成长主题解读女性主体意识的成熟:《我的前半生》中女性成长主题解读摘要:亦舒关注女性命运,其大部分作品以女性为叙事主体,强调女性价值本位立场,她在《我的前半生》中以女性视角表达了对当代女性命运的关注。
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通过对书中女性角色独立意识的剖析、女性人物关系链条的梳理、男性角色对女性意识构建的反刺激作用以及女性主体意识的现实意义四个维度,对罗子君的自我成长道路进行探索和解读。
关键词:《我的前半生》;女性主体意识;女性成长;现实意义一、引言《我的前半生》是亦舒的代表作,在书中亦舒将女性在现实重压下坚持自我、寻求自我发展之路的强烈自我独立意识展现得淋漓尽致,并力图呈现罗子君成长中的困惑与蜕变,笔者希望在剖析书中女主人公成长道路的同时,也能挖掘其对现代女性的现实意义,引发女性读者对独立意识的思考和衡量。
二、女性的自我成长:女性独立意识的构建(一)挣脱感情的链条在离婚前,罗子君是困在婚姻围城里的人:她认为一个女人人生中所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嫁人,对丈夫表现出极大的依附性。
在罗子君的潜意识中她是承认女性应该依附于男性的,女人生而为丈夫的存在而存在,她自身的这种家庭父权意识成为了她离婚的阻碍。
除了自身对女性独立意识的怀疑,来自外部的父权主义拥护者亦组成罗子君成长道路上的一片荆棘。
一方面是史涓生对子君父权意识的灌输。
在子君刚毕业时,涓生就默许子君放弃她的工作过阔太太的生活,从那时起,子君就在经济上和精神上无限地依赖涓生。
在进行离婚谈判时,史涓生句句以自我为中心,反驳子君的辩驳和请求。
“我是你的丈夫,亦是你的老板,你总得以我为重。
”涓生将丈夫与老板等同起来,让子君跌入父权主义的深渊。
另一方面是来自子君母亲和大嫂的怂恿。
在离婚时,大嫂用她那套“婚姻哲学”劝说子君打死也不要离婚,应该继续扮演丈夫要求他们扮演的角色,做温顺贤惠的好妻子。
但是令人庆幸的是,子君挣脱了重重束缚,放下了对涓生的依恋,走出了家庭的牢笼。
亦舒笔下女性的主体意识

亦舒的自 我生存之路是一条女性自立、 强的道路。她 自 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心理体验, 思想状态, 往往就是她内心的 真实流露。亦舒前半生颇为坎坷, 用其侄倪震 的2 个字可 O 概括为“ 少家贫, 自 少年反叛, 早婚产子, 怀才未遇” 。她的情 感道路颇为曲折, 但生命中过去的几个男人, 都未能使她成 为人生道路上的输家。她中学毕业便到《 明报》 当记者, 期间 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2 岁时远赴英国伦敦, 7 学习酒店 管理, 年后返港, 3 先供职于酒店, 后成为政府新闻官, 期间 笔耕不辍, 终于成为享誉港台和大陆的女性作家, 香港“ 女强 人” 之一。她立言: “ 连我这样年纪的人, 都认为女性其实只 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先搞身心经济独立, 然后才决定是否 要成家立室, 希望工作可与家庭并重。Ⅲ ∞ ” 她以自己的经 1
作 者 简 介 : 丽 娟 (9 0一)女 , 北 沽 源人 , 家 口教 育 学 院 中文 系讲 师 。 常 18 , 河 张
・ 2 1 ・
21 0 0年 4月
常 丽 娟 亦 舒 笔 下 女 性 的 主 体 意 识
第 2期
男人一样成就事业、 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亦舒笔下的子君 对爱情和家庭, 也就是对男性的依附心态, 束缚了自己, 进而 失去了经济独立, 失去了自我意识。子君原为知识女性, 婚 后为家庭放弃了事业, 成为~名“ 专职主妇” 。在丈夫和孩子
Vo - 6 No 2 I2 .
A p . 01 r2 0
亦 舒 笔 下 女 性 的 主 体 意 识
常 丽 娟
( 家 口教 育学 院 中文 系, 北 张 家 口 0 5 0 ) 张 河 70 0
摘要 : 亦舒 把 女 性 的 主 体 意 识作 为新 的 精 神 注入 到其 作 品 中 , 时代 女 性 的 独特 经 验 、 体 感 受 、 存 困境 , 将 群 生 矛 盾 心理 一 一 展 现 给 读 者 , 女性 主体 意识 主要 表 现 为 : 导 经 济 独 立 、 异 性 交往 中 的 自主 意 识 、 同 性 之 谊 的珍 其 倡 与 对
论亦舒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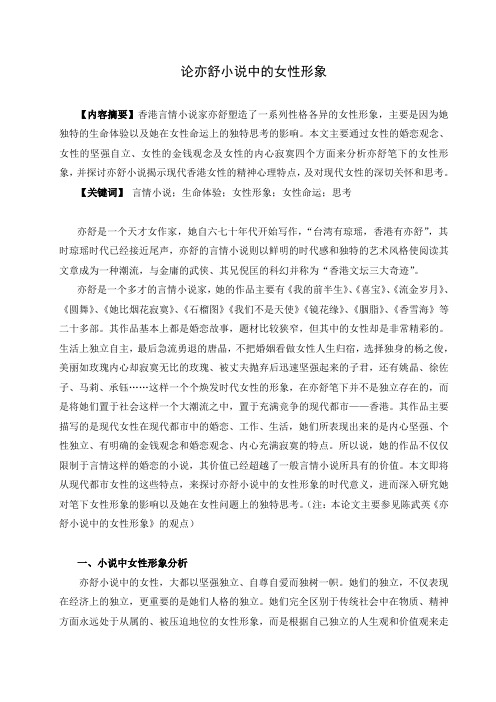
论亦舒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内容摘要】香港言情小说家亦舒塑造了一系列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主要是因为她独特的生命体验以及她在女性命运上的独特思考的影响。
本文主要通过女性的婚恋观念、女性的坚强自立、女性的金钱观念及女性的内心寂寞四个方面来分析亦舒笔下的女性形象,并探讨亦舒小说揭示现代香港女性的精神心理特点,及对现代女性的深切关怀和思考。
【关键词】言情小说;生命体验;女性形象;女性命运;思考亦舒是一个天才女作家,她自六七十年代开始写作,“台湾有琼瑶,香港有亦舒”,其时琼瑶时代已经接近尾声,亦舒的言情小说则以鲜明的时代感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使阅读其文章成为一种潮流,与金庸的武侠、其兄倪匡的科幻并称为“香港文坛三大奇迹”。
亦舒是一个多才的言情小说家,她的作品主要有《我的前半生》、《喜宝》、《流金岁月》、《圆舞》、《她比烟花寂寞》、《石榴图》《我们不是天使》《镜花缘》、《胭脂》、《香雪海》等二十多部。
其作品基本上都是婚恋故事,题材比较狭窄,但其中的女性却是非常精彩的。
生活上独立自主,最后急流勇退的唐晶,不把婚姻看做女性人生归宿,选择独身的杨之俊,美丽如玫瑰内心却寂寞无比的玫瑰、被丈夫抛弃后迅速坚强起来的子君,还有姚晶、徐佐子、马莉、承钰……这样一个个焕发时代女性的形象,在亦舒笔下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将她们置于社会这样一个大潮流之中,置于充满竞争的现代都市——香港。
其作品主要描写的是现代女性在现代都市中的婚恋、工作、生活,她们所表现出来的是内心坚强、个性独立、有明确的金钱观念和婚恋观念、内心充满寂寞的特点。
所以说,她的作品不仅仅限制于言情这样的婚恋的小说,其价值已经超越了一般言情小说所具有的价值。
本文即将从现代都市女性的这些特点,来探讨亦舒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时代意义,进而深入研究她对笔下女性形象的影响以及她在女性问题上的独特思考。
(注:本论文主要参见陈武英《亦舒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观点)一、小说中女性形象分析亦舒小说中的女性,大都以坚强独立、自尊自爱而独树一帜。
论亦舒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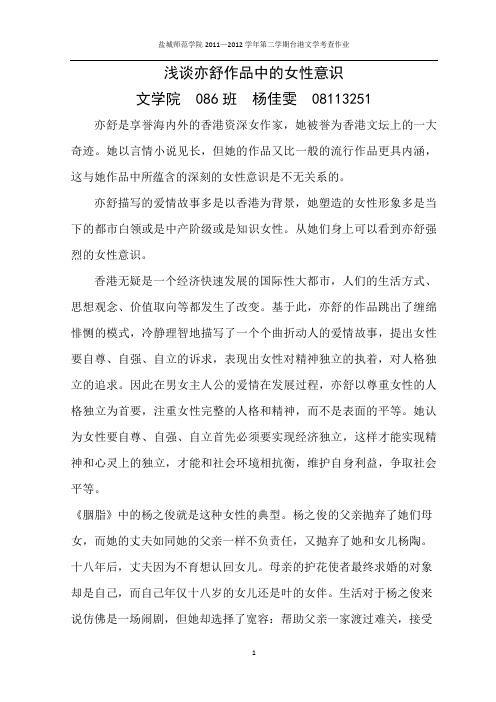
浅谈亦舒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文学院 086班杨佳雯 08113251 亦舒是享誉海内外的香港资深女作家,她被誉为香港文坛上的一大奇迹。
她以言情小说见长,但她的作品又比一般的流行作品更具内涵,这与她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刻的女性意识是不无关系的。
亦舒描写的爱情故事多是以香港为背景,她塑造的女性形象多是当下的都市白领或是中产阶级或是知识女性。
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到亦舒强烈的女性意识。
香港无疑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际性大都市,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都发生了改变。
基于此,亦舒的作品跳出了缠绵悱恻的模式,冷静理智地描写了一个个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提出女性要自尊、自强、自立的诉求,表现出女性对精神独立的执着,对人格独立的追求。
因此在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在发展过程,亦舒以尊重女性的人格独立为首要,注重女性完整的人格和精神,而不是表面的平等。
她认为女性要自尊、自强、自立首先必须要实现经济独立,这样才能实现精神和心灵上的独立,才能和社会环境相抗衡,维护自身利益,争取社会平等。
《胭脂》中的杨之俊就是这种女性的典型。
杨之俊的父亲抛弃了她们母女,而她的丈夫如同她的父亲一样不负责任,又抛弃了她和女儿杨陶。
十八年后,丈夫因为不育想认回女儿。
母亲的护花使者最终求婚的对象却是自己,而自己年仅十八岁的女儿还是叶的女伴。
生活对于杨之俊来说仿佛是一场闹剧,但她却选择了宽容:帮助父亲一家渡过难关,接受女儿的选择,和前夫冰释前嫌。
在她看来,她的归宿,便是健康与才干。
“一个人,终究可以信赖的,不过是她自己;能够为他扬眉吐气的,也是他自己,我要什么归宿?我已找回我自己,我就是我的归宿。
”像杨之俊这样,经济独立,精神独立的女性才能潇洒地走向社会。
这也是亦舒所倡导的女性独立精神。
亦舒对女性意识尚未觉醒,仍然依附于男性,不自尊、自强、自立的女性进行了批判,以此来提醒那些想要依附男性的女性。
《喜宝》中的姜喜宝就是这种女性形象的代表。
喜宝想“要很多很多的爱。
论亦舒小说女性人物的独立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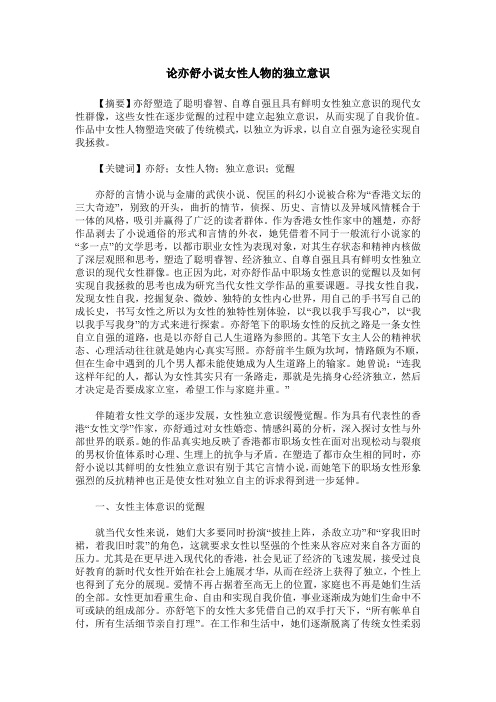
论亦舒小说女性人物的独立意识【摘要】亦舒塑造了聪明睿智、自尊自强且具有鲜明女性独立意识的现代女性群像,这些女性在逐步觉醒的过程中建立起独立意识,从而实现了自我价值。
作品中女性人物塑造突破了传统模式,以独立为诉求,以自立自强为途径实现自我拯救。
【关键词】亦舒;女性人物;独立意识;觉醒亦舒的言情小说与金庸的武侠小说、倪匡的科幻小说被合称为“香港文坛的三大奇迹”,别致的开头,曲折的情节,侦探、历史、言情以及异域风情糅合于一体的风格,吸引并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体。
作为香港女性作家中的翘楚,亦舒作品剥去了小说通俗的形式和言情的外衣,她凭借着不同于一般流行小说家的“多一点”的文学思考,以都市职业女性为表现对象,对其生存状态和精神内核做了深层观照和思考,塑造了聪明睿智、经济独立、自尊自强且具有鲜明女性独立意识的现代女性群像。
也正因为此,对亦舒作品中职场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如何实现自我拯救的思考也成为研究当代女性文学作品的重要课题。
寻找女性自我,发现女性自我,挖掘复杂、微妙、独特的女性内心世界,用自己的手书写自己的成长史,书写女性之所以为女性的独特性别体验,以“我以我手写我心”,以“我以我手写我身”的方式来进行探索。
亦舒笔下的职场女性的反抗之路是一条女性自立自强的道路,也是以亦舒自己人生道路为参照的。
其笔下女主人公的精神状态、心理活动往往就是她内心真实写照。
亦舒前半生颇为坎坷,情路颇为不顺,但在生命中遇到的几个男人都未能使她成为人生道路上的输家。
她曾说:“连我这样年纪的人,都认为女性其实只有一条路走,那就是先搞身心经济独立,然后才决定是否要成家立室,希望工作与家庭并重。
”伴随着女性文学的逐步发展,女性独立意识缓慢觉醒。
作为具有代表性的香港“女性文学”作家,亦舒通过对女性婚恋、情感纠葛的分析,深入探讨女性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她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香港都市职场女性在面对出现松动与裂痕的男权价值体系时心理、生理上的抗争与矛盾。
论亦舒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论亦舒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作者:马玙歆来源:《西部论丛》2019年第17期摘要:亦舒是香港文坛中难得的才女,几十年来笔耕不辍,其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以香港都市为核心圈子的女性心理抗争及矛盾。
本文针对亦舒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研究,首先分析了亦舒小说及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类型,其次分三个方面深入探讨了亦舒笔触下的女性形象,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对亦舒小说女性形象的解读提供帮助。
关键词:亦舒小说女性形象分析引言亦舒以简洁凝练、泼辣直率的语言风格描绘了现代都会中女性的生命体验与情感状态,以特立独行的女性意识抒写当代女性内在感受。
面对青春的渐行渐远、现实生活的迷茫与徘徊,亦舒有着独到的人生见解。
亦舒小说中丰富的女性形象,饱含了独特的婚恋观、人生观及价值观,值得我们去品味。
一、亦舒小说与女性形象迄今为止,亦舒已有三百多部小说作品。
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多半拥有姣好的面容,她们精明、世故,却懂得自矜自持,在香港中产阶级甚至名流圈里懂得进退,遂心淡定,这群早已放弃古典浪漫主义深情的女人,或轰轰烈烈,或宠辱不惊,在各自的故事里自爱自立。
亦舒笔下的女性形象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张扬的青春型女性。
这类女性美丽、颠倒众生,仅仅是出众的外貌便有无数男人为之癫狂。
这类女性主要以姜喜宝、黄玫瑰、花解语最为典型。
她们因美貌而追求者不断,却有超然洒脱的性格魅力,对生活见解独到,对人对事知世故而不世故,将一切事态发展掌握在手中。
年轻漂亮的姜喜宝13岁便学会了享受美丽带来的便利,让男孩子为其买单,诚然,将青春美貌折现喜宝是习惯的,懂得独善其身,以其风华正茂绽放光彩,极尽嫣妍;玫瑰拥有最无邪的美丽,被亦舒赋予最纯粹理想的女性形象,在男人眼里她是娇艳欲滴的玫瑰,在女人眼里她是所有美的化身,褪去外表,她是真正的性情中人,懂得打扮,头脑聪明,面对倾慕不屑一顾,却用极端的自由开放态度不顾一切追求美好。
二是成熟的职业型女性。
高学历,有稳定的职业,经济独立,特立独行是亦舒小说中成熟职业型女性的标志。
从亦舒笔下的女性说起

从亦舒笔下的女性说起看过席梦娟,为琼瑶流泪,替三毛悲痛,为张爱玲鼓掌,和张小娴一起感动,与龙应台一起犀利,唯独差了一味,清洌智慧而不失韵味。
不经世事之时,梦幻得最多的事情无非是爱情。
历经千山万水,读了许多许多的作品之后,我遇到了亦舒。
就是这种味道。
不管文字是犀利冰凉,是洒脱自然,还是清冽熨帖,却总带有些女性的言情味道,文字里流淌出来的各色味道,最重最深的无外乎于一个“情”字。
亦舒不愧是女性文学的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代表,从事写作以来创作的系列作品,无不旗帜鲜明地提出女性意识的觉醒和独立。
这是个长久不衰的话题。
所谓女性意识,是指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是认识到女人和男人也是一样,是人类的另一半的意识,正如斯帕克斯所言“女性意识就是女性对于自身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主题存在的地位和价值的自觉意识。
”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成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赋予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亦舒笔下的女性都是现代社会无数女性的楷模。
从亦舒的笔下走来的女子都带有一种清冽的气质。
她们多是直发,身材挺拔修长,大部分时间穿着灰白黑三色的简单质感的衣服和平跟鞋子,英姿飒爽。
干净的外貌下隐藏着独立而坚韧的性格,更为难得的是她们都有着看似与年龄并不太相称的睿智,参透世事沧桑却并不沉沦,自然而淡定的活出自我。
有时我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女性能写出如此吸引我的主人公。
原来亦舒也只不过是有着看似普通的外表而已,而其散发出的那种气质却会穿透你的心。
我想在亦舒的心里,多少都有个理想中的自己,幸运的是她可以驾驭自己,让“她”从笔端走出来终究是件让她满足的事。
亦舒多写婚恋爱情故事,题材不广,却写得入木三分。
成功塑造了一个个独特的现代香港女性形象,并通过这些都市女性的婚姻爱情经历关注女性命运,透视现代香港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至透视整个香港社会。
亦舒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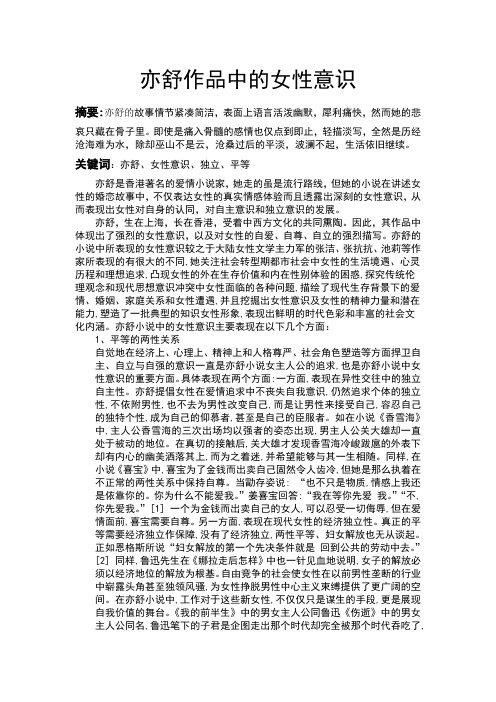
亦舒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摘要:亦舒的故事情节紧凑简洁,表面上语言活泼幽默,犀利痛快,然而她的悲哀只藏在骨子里。
即使是痛入骨髓的感情也仅点到即止,轻描淡写,全然是历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沧桑过后的平淡,波澜不起,生活依旧继续。
关键词:亦舒、女性意识、独立、平等亦舒是香港著名的爱情小说家,她走的虽是流行路线,但她的小说在讲述女性的婚恋故事中,不仅表达女性的真实情感体验而且透露出深刻的女性意识,从而表现出女性对自身的认同,对自主意识和独立意识的发展。
亦舒,生在上海,长在香港,受着中西方文化的共同熏陶。
因此,其作品中体现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以及对女性的自爱、自尊、自立的强烈描写。
亦舒的小说中所表现的女性意识较之于大陆女性文学主力军的张洁、张抗抗、池莉等作家所表现的有很大的不同,她关注社会转型期都市社会中女性的生活境遇、心灵历程和理想追求,凸现女性的外在生存价值和内在性别体验的困惑,探究传统伦理观念和现代思想意识冲突中女性面临的各种问题,描绘了现代生存背景下的爱情、婚姻、家庭关系和女性遭遇,并且挖掘出女性意识及女性的精神力量和潜在能力,塑造了一批典型的知识女性形象,表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和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亦舒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平等的两性关系自觉地在经济上、心理上、精神上和人格尊严、社会角色塑造等方面捍卫自主、自立与自强的意识一直是亦舒小说女主人公的追求,也是亦舒小说中女性意识的重要方面。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异性交往中的独立自主性。
亦舒提倡女性在爱情追求中不丧失自我意识,仍然追求个体的独立性,不依附男性,也不去为男性改变自己,而是让男性来接受自己,容忍自己的独特个性,成为自己的仰慕者,甚至是自己的臣服者。
如在小说《香雪海》中,主人公香雪海的三次出场均以强者的姿态出现,男主人公关大雄却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
在真切的接触后,关大雄才发现香雪海冷峻跋扈的外表下却有内心的幽美洒落其上,而为之着迷,并希望能够与其一生相随。
论亦舒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女性独立意识

才 譬
论亦舒才子佳人小说 中的女性独立意识
李 白梅 大理学院文学院
亦 舒 , 当代 香港 著 名 言 情 小说 家 ,著 有 小 说近 百 余 部 。亦 舒 主 要 以都 市 女性 的婚 恋为 创 作 内容 , 以一 双 极 具 洞 察 力 的眼 睛来 剖 析 女性 的 生 存现 状 。她 用 真实 的生
读亦舒浅谈女性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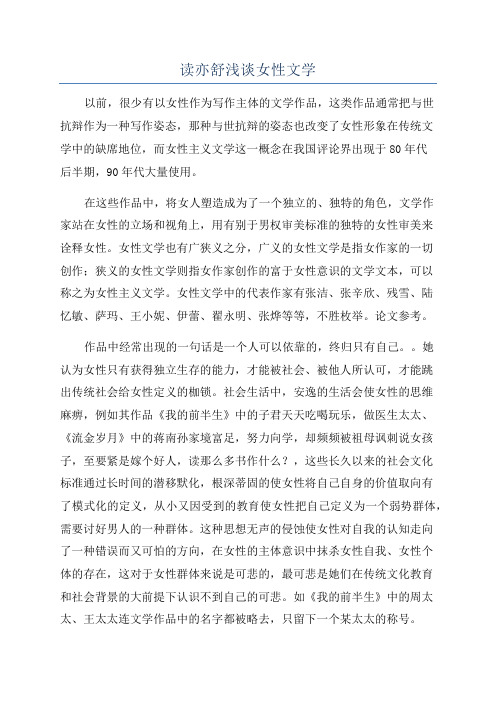
读亦舒浅谈女性文学以前,很少有以女性作为写作主体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通常把与世抗辩作为一种写作姿态,那种与世抗辩的姿态也改变了女性形象在传统文学中的缺席地位,而女性主义文学这一概念在我国评论界出现于80年代后半期,90年代大量使用。
在这些作品中,将女人塑造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独特的角色,文学作家站在女性的立场和视角上,用有别于男权审美标准的独特的女性审美来诠释女性。
女性文学也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女性文学是指女作家的一切创作;狭义的女性文学则指女作家创作的富于女性意识的文学文本,可以称之为女性主义文学。
女性文学中的代表作家有张洁、张辛欣、残雪、陆忆敏、萨玛、王小妮、伊蕾、翟永明、张烨等等,不胜枚举。
论文参考。
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是一个人可以依靠的,终归只有自己。
她认为女性只有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才能被社会、被他人所认可,才能跳出传统社会给女性定义的枷锁。
社会生活中,安逸的生活会使女性的思维麻痹,例如其作品《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天天吃喝玩乐,做医生太太、《流金岁月》中的蒋南孙家境富足,努力向学,却频频被祖母讽刺说女孩子,至要紧是嫁个好人,读那么多书作什么?,这些长久以来的社会文化标准通过长时间的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使女性将自己自身的价值取向有了模式化的定义,从小又因受到的教育使女性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弱势群体,需要讨好男人的一种群体。
这种思想无声的侵蚀使女性对自我的认知走向了一种错误而又可怕的方向,在女性的主体意识中抹杀女性自我、女性个体的存在,这对于女性群体来说是可悲的,最可悲是她们在传统文化教育和社会背景的大前提下认识不到自己的可悲。
如《我的前半生》中的周太太、王太太连文学作品中的名字都被略去,只留下一个某太太的称号。
在男权意识的强势压迫下,只有当女性摆脱传统定位的第二性依附心理,走入社会,独立面对承担自己的生活,才能找回自我。
女性作为被男性视为另一族群,在社会上打拼只会更加艰难:现代女性非得装成最坚强最大方不可,否则,会被讥笑为不懂自爱自重。
亦舒作品中女性形象分析

摘要:亦舒笔下多是那些徘徊在爱情与婚姻十字路口的现代女性形象,在亦舒的小说中塑造了现代独立女性群像,小说中的女性大多是经济独立、聪明睿智、自尊自强且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职业女性。
这些女性正代表了亦舒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人格。
叛逆是女性的个性魅力,她们都脱离了传统女性温婉柔弱的气质,多多少少都带有一些叛逆和刚强。
她们不仅在经济上独立,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独立。
关键词:女性形象理想人格独立叛逆一、充满着现代精神,独立与孤寂同在亦舒作品中充满了现代精神,城市味道。
香港无疑缺少自然风光,在那钢筋水泥的丛林中间,时间与空间仿佛被重新分割,人和大地疏离并与自身的家园相隔膜,于是,传统逐渐远去,人沉浮于现代大都市的喧哗中,受到空间挤压和时间的转换,人的内在情思被抽空,本真心被压抑,人在虚幻时空中,仅仅感受到虚幻的存在和虚幻的生命价值。
在骚动不安的文化地基上,人们难以建立自己真实的人生标准和价值尺度,只好成为流行文化的观赏者,成为别人痛苦幸福的旁观者或中西方文化的边缘者和多余人。
艰难的社会环境和混乱的价值取向,使香港人陷入生存和文化精神的困惑和迷醉之中。
于是,他们极度张扬人的本能欲望,香港逐渐变成了金钱与欲望拼贴的花花世界。
在香港这座都市舞台上演的男男女女,亦舒用心关注着女性。
亦舒可以说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的小说主角多为女性,特别是都市中中产阶级的女性。
她们的生活和爱情,快乐和痛苦,成功和挫折,挣扎与苦闷,她们的种种心态都是亦舒的抒写内容。
她笔下的女性各具特色,丰富多采:独立的子君,浪漫的玫瑰,神秘的宁馨儿;外冷内热的宋榭珊,善解人意的花谢语,少不更事的慕容琅;寂寞的姚晶,矛盾的杨之俊;明朗的邵子贵,沉静的邓永超,佻达的香雪海;还有喜宝是寄生的,贝秀月则漠视一切,海媚带点邪气,等等形象各异,却真实可信。
这些人都是都市的新新人类,重物质,表面上熙熙攮攮,骨子里则孤寂冷漠的。
纵观小说的女性形象最突出的特点有二,一是孤寂,二是独立。
浅议亦舒作品中的女性独立意识

香港通俗小说作家亦舒 ,借笔下 的现代女性角色探索都 市女性应 当如何改善 自身生活环境 的方法 ,并试 图寻求女性
的抗争 跟希望 。 “ 独立” 是其 中最为耀 眼的字 眼 , 也是亦舒小说 中极力宣扬 的女性观 。 亦舒 笔下形形 色色 风格迥异 的爱情故事 中的女性 ,对 于 她们 的生 活 , 生活方式 , 自身社会 地位 , 投入 了 自己 的思考 与 关注 , 试 图紧紧地把握住 自己的人生。 亦舒通过小说 中的女性 形象告诉 世间女性 , 生存在这个世 间 , 生活在这个社 会 , 女性 定要掌握保护 自己的方 法。 那么如何保护 自己呢 , 最要紧 的是
文 学 品 析
文艺 生活 L I T ER A TURE L I F E
2 0 1 3 — 0 4
浅议亦舒作 品中的女性独 立意识
郑 清
(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 , 福建 福州 3 5 0 2 0 0 )
摘 要: 亦舒的 小说 中描 写的大部分都是 自尊 自爱的现代 独立女性 , 她们不依 靠男性 , 而是凭借 自己的能力 闯荡社
首先 , 亦舒百分百肯定 了经济独立对于女性的重要性 。 对 于一个拥有事业 的女性来说 ,经 济上 的独立 可以给她带来 生
活上的 自信与坚强 。 金钱 不是万能 的, 但是没有金钱确是万万 人生负责 , 无需为他人负责 , 也无需 把 自己的存在建立他人的 不能 。 金钱是女性的重要物质保证 , 进而实现人 的 自我价值与
会。本文从女性在现代社会 中的经济独立跟精神独立两个角度 , 浅谈 亦舒 小说 中的女性独立意识 。 关键词 : 亦舒 ; 现代女性 ; 经济独立 ; 精神独立 中图分类号 : 1 2 4 7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1 0 0 5 — 5 3 1 2 ( 2 0 1 3 ) 1 2 - 0 0 1 2 - 0 1 其次 , 亦舒除了在小说中强调经济对女性的重要性 , 同时
亦舒小说中女性形象分析

亦舒通过人物之口,说出了人的三个基本愿望:在生 活中,最希望得到的是爱,被爱与爱人。第二希望得到 钱。第三是健康。很现实,也很真实。外表再坚强的人也 渴望爱,渴望被爱。无爱的人生是乏味的、孤寂的。《没有 月亮的晚上》的海媚,一直生活在黑夜之中,因为生母对 父亲的背叛,所有的罪孽便落在她身上,十六岁的她无法 忍受父亲的仇恨,继母的刻毒,疯狂的她用剪刀刺伤继 母,于是她从父亲的手上转到陈国维手上。陈国维帮她打 官司,并收容她。他喜欢幼稚无知又青春亮丽的海媚,他 自私的不肯让海媚长大,十年过去了,他却一直不肯了解
5 作者简介 6 田玮莉 1 7"!8— 4 ,女,浙江诸暨市人。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基础部助教。
!"
海媚的内心世界,任由她一直在黑暗中生活。海媚不甘 心,挣扎着想摆脱黑夜。她遇见了朱二,燃起了一丝希望, 她以为从此可以走进白天,但朱二是另一个陈国维,他们 只不过是旧戏重演,她清晰地说 “不”,于是,所有人都终 于露出了丑陋的一面。海媚无非就是在祈求一点爱,但无 论是父亲,或是她所谓的丈夫,还有情人,却都没能好好 的倾听她心底的声音。小说结尾是这样:“太阳落山以后, 遍地银光,夜温柔如水,抚平任何创伤忧虑,属于白天的 留给白天,没有人再会记得日间发生过什么。黑夜中的世 界完全不一样,只要等到夜里,一切不用烦恼。”#$ %哀莫大 于心死,海媚已没有心了,她今后的生活,无异于行尸走 肉。
论亦舒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亦舒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摘要:亦舒,原名倪亦舒,自幼酷爱文学,1962年在文坛一露头角就迅速成名。
亦舒言情小说与金庸额武侠小说、倪匡的科幻小说一起并称为“香港文坛三大奇迹”。
亦舒的小说虽然题材较为狭窄,几乎都是在讲婚恋故事。
但是,由于她成功塑造了一个个独特的现代香港女性的形象,并通过这些现代都市女性的爱情、婚姻的种种经历来关注女性的命运,透视现代香港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至透视整个香港社会。
因此,她的作品已不单单局限于言情,已经超越了一般言情小说所具有的价值。
本文将从女性的爱情观、金钱观、独立意识的探索、内心孤独寂寞等四个方面,来浅论亦舒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社会文化意义。
关键词:亦舒;爱情;金钱;孤寂;独立The female images in Yi Shu's NovelsAbstract:Yi Shu, formerly Ni Yi Shu, his childhood love of literature in the literary world,1962, be it quickly became famous. Yi Shu's romances and Jin Yong's martial arts novels, Ni Kuang's science fiction and together referred to as the" three wonders of Hongkong literature". The novels of Yi Shu although the subject matter is relatively narrow, almost all is telling the story of love and marriage. However, due to her success in shaping a unique modern Hongkong women's image, and through which the modern metropolis feminine love, marriage experienc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fate of women in modern Hongkong,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and people, and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ntire society of Hongkong. Therefore, her works have not only confined to the sentimental, has gone beyond the general love story has value. This article from the female 's view of love, money concept, the independent consciousness exploration, lonely heart four aspects, on the female images in Yi Shu's novels and social cultural meaning.Key words:Yi Shu; love; money; lonely; alone一、亦舒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一)女性形象蕴含的苦涩爱情观爱情在亦舒眼中是苦涩的。
浅析亦舒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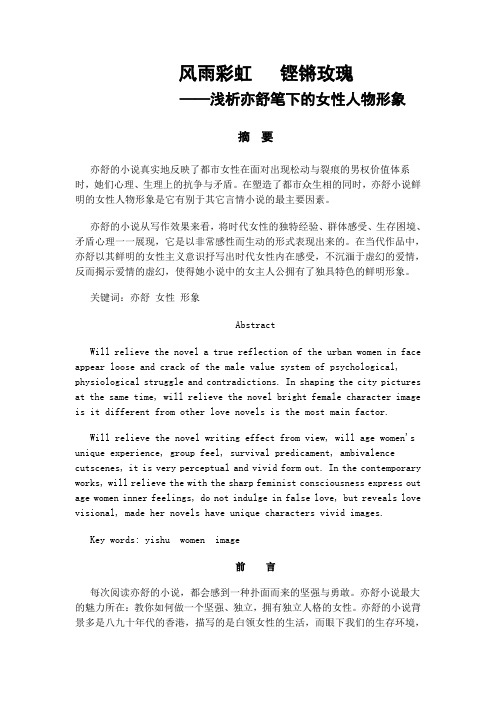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浅析亦舒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摘要亦舒的小说真实地反映了都市女性在面对出现松动与裂痕的男权价值体系时,她们心理、生理上的抗争与矛盾。
在塑造了都市众生相的同时,亦舒小说鲜明的女性人物形象是它有别于其它言情小说的最主要因素。
亦舒的小说从写作效果来看,将时代女性的独特经验、群体感受、生存困境、矛盾心理一一展现,它是以非常感性而生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在当代作品中,亦舒以其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抒写出时代女性内在感受,不沉湎于虚幻的爱情,反而揭示爱情的虚幻,使得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拥有了独具特色的鲜明形象。
关键词:亦舒女性形象AbstractWill relieve the novel a true reflection of the urban women in face appear loose and crack of the male value system of psychological, physiological struggle and contradictions. In shaping the city pictures at the same time, will relieve the novel bright female character image is it different from other love novels is the most main factor.Will relieve the novel writing effect from view, will age women's unique experience, group feel, survival predicament, ambivalence cutscenes, it is very perceptual and vivid form out. In the contemporary works, will relieve the with the sharp feminist consciousness express out age women inner feelings, do not indulge in false love, but reveals love visional, made her novels have unique characters vivid images.Key words: yishu women image前言每次阅读亦舒的小说,都会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坚强与勇敢。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亦舒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摘要:亦舒的故事情节紧凑简洁,表面上语言活泼幽默,犀利痛快,然而她的悲哀只藏在骨子里。
即使是痛入骨髓的感情也仅点到即止,轻描淡写,全然是历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沧桑过后的平淡,波澜不起,生活依旧继续。
关键词:亦舒、女性意识、独立、平等亦舒是香港著名的爱情小说家,她走的虽是流行路线,但她的小说在讲述女性的婚恋故事中,不仅表达女性的真实情感体验而且透露出深刻的女性意识,从而表现出女性对自身的认同,对自主意识和独立意识的发展。
亦舒,生在上海,长在香港,受着中西方文化的共同熏陶。
因此,其作品中体现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以及对女性的自爱、自尊、自立的强烈描写。
亦舒的小说中所表现的女性意识较之于大陆女性文学主力军的张洁、张抗抗、池莉等作家所表现的有很大的不同,她关注社会转型期都市社会中女性的生活境遇、心灵历程和理想追求,凸现女性的外在生存价值和内在性别体验的困惑,探究传统伦理观念和现代思想意识冲突中女性面临的各种问题,描绘了现代生存背景下的爱情、婚姻、家庭关系和女性遭遇,并且挖掘出女性意识及女性的精神力量和潜在能力,塑造了一批典型的知识女性形象,表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和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亦舒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平等的两性关系自觉地在经济上、心理上、精神上和人格尊严、社会角色塑造等方面捍卫自主、自立与自强的意识一直是亦舒小说女主人公的追求,也是亦舒小说中女性意识的重要方面。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异性交往中的独立自主性。
亦舒提倡女性在爱情追求中不丧失自我意识,仍然追求个体的独立性,不依附男性,也不去为男性改变自己,而是让男性来接受自己,容忍自己的独特个性,成为自己的仰慕者,甚至是自己的臣服者。
如在小说《香雪海》中,主人公香雪海的三次出场均以强者的姿态出现,男主人公关大雄却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
在真切的接触后,关大雄才发现香雪海冷峻跋扈的外表下却有内心的幽美洒落其上,而为之着迷,并希望能够与其一生相随。
同样,在小说《喜宝》中,喜宝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固然令人齿冷,但她是那么执着在不正常的两性关系中保持自尊。
当勖存姿说: “也不只是物质,情感上我还是依靠你的。
你为什么不能爱我。
”姜喜宝回答:“我在等你先爱我。
”“不,你先爱我。
”[1] 一个为金钱而出卖自己的女人,可以忍受一切侮辱,但在爱情面前,喜宝需要自尊。
另一方面,表现在现代女性的经济独立性。
真正的平等需要经济独立作保障,没有了经济独立,两性平等、妇女解放也无从谈起。
正如恩格斯所说“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
”[2] 同样,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中也一针见血地说明,女子的解放必须以经济地位的解放为根基。
自由竞争的社会使女性在以前男性垄断的行业中崭露头角甚至独领风骚,为女性挣脱男性中心主义束缚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在亦舒小说中,工作对于这些新女性,不仅仅只是谋生的手段,更是展现自我价值的舞台。
《我的前半生》中的男女主人公同鲁迅《伤逝》中的男女主人公同名,鲁迅笔下的子君是企图走出那个时代却完全被那个时代吞吃了,那不全是她的责任;亦舒笔下的子君,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重新振作起来。
她自寻职业,自食其力,不怕困难,终于获得了新生,成为一个在人格上、经济上独立的女性。
还有像《独身女人》等作品,亦舒都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去昭示:爱情不再是女人生命的最高目的,婚姻也不再是女性人生的第一要义。
她们有能力凭着自强不息,而不须仰赖男人的庇护或施舍改变自身命运,争得独立自主的社会地位。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亦舒的妇女观,也可以看出她对现代女性的出路与命运的关注。
2、反父权的思想传统的女性通常只能做生命的陪衬,只能默默奉献、任劳任怨;而男人希求的也是妻子的安抚与理解,希求妻子以她母性的温柔帮助他们鼓起勇气去面对外部世界的挑战。
但女性主义者却表示质疑和抗争,导致男权价值体系出现松动与裂痕。
亦舒小说中常见孤女、单亲家庭形式,形成了“无父文本”, “男性家长被排除或放逐于文本之外,构成了女性家长当家作主的模式”[3] ,表明了对父权的遗弃。
小说《胭脂》可视为对单亲家庭、对母性的一种审视。
对于杨之俊来说,如大多数的女人一样,盼望着正常的家庭,但她却清醒地将家庭制度和她自己的家庭清楚地区分开来。
前者是她追求的目标,而后者在她的经验中却常常无法达到她对家庭生活的渴望。
之俊的母亲还曾经有过婚礼,只不过婚纱尚未在箱子里压皱发黄,她的父亲便与母亲分开而另娶。
之俊却是连婚礼也欠奉,便生下了女儿杨陶。
《胭脂》讲述了三个女人的流年:老的落在了荒凉的土地上,一辈子弱不禁风,怨天尤人;中年的堪堪地将要掉下去,却又凭着自己的毅力硬是打出了一个局面;年轻的碰上了好时候,前程灿烂如锦。
女人的归宿也不再是丈夫和家庭,在杨之俊看来:“我的归宿,便是健康与才干。
你还不明白?妈妈,一个人终究可以信赖的不过是他自己;能够为他扬眉吐气的,也是他自己。
我要什么归宿?我已找回我自己,我就是我的归宿。
”[4] 在亦舒小说中很难找到“需要通过对女性的保护来反射两倍大的男性形象”[5] ,她在作品中撕碎了男性“强大”的伪装,甚至经常把他们描写得非常不堪。
仅《我的前半生》中就有如下数类:多年来老实正经、勤奋向上的丈夫,忽然发现了真我,发现了激情,死心塌地地要随着女演员去过全新的生活,而全不顾及妻儿的感受;在公司踌躇满志却窝窝囊囊混了半辈子的男同事,打着“我老婆一点儿也不理解我”的旗号向单身女人讨便宜;20多岁的男孩子,大学刚毕业,却想在成熟女人身上寻找经验及安慰;文雅体贴、热爱艺术、知情识趣的合伙人,却是个同性恋者;试探几招一看不行就立即出言不逊,转舵而走的洋鬼子……亦舒几乎是极力挖掘男性的猥琐来实现对女性的礼赞,读来令人深有感触。
3、姐妹情谊的书写在男权制度下,男性肝胆相照,寻求不背叛的生命情谊是男性历史中一以贯之的神话;而女性的情谊,在男性话语系统中,是长期被省略的,女性之间被更多书写的是彼此算计、互相提防。
而80年代高涨的女性主义写作却勇敢地突破了这一禁锢,这些女作家们在文学创作中大量书写了女性之间的同性情谊,大胆地开拓了文学表现生活的领域,从而也进一步地拓宽了女性写作的更为广阔的书写空间。
西方女权主义者萨拉・埃利期也极力倡导“姐妹情谊”。
她认为女人们必须诚心诚意,信心百倍地站在一起,并且指出女人在无法从男人那里获得救赎的时候,在无外援的自闭中,应该向自己的姐妹伸出救援之手。
亦舒本人也认为“每个女人都应该有好几个要好的女朋友,没有几个,最低限度也要有一个,有心事可以倾告,有想不开的事情可以互相劝慰,有女人觉得快乐的,可以一起快乐。
女人待男人不妨坏点,但是对女朋友必须要够坦诚,够真心,女人不对女人好,还有谁对女人好呢?”[2]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亦舒在作品中对女性情谊进行了大量的书写。
她的女主角大都有至少一个女性挚友(《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和唐晶),或是姐妹(如《西岸阳光充沛》中的汤宜室和汤宜家),或是母女(如《胭脂》里祖孙三代),或是同学、同事(如《小人儿》中的邓志高和甄子壮),甚至是陌生人、情敌(如《银女》中的林无迈和王银女),和她站在同一战线,欣赏她、鼓励她、帮助她,如《我的前半生》中,为了使婚姻出了问题的子君振作,唐晶激励子君说:“在大学时代你是我们之间最倔强的,为了试卷分数错误吵到系主任那里去,记得吗?一切要理智沉着的应付,我也懂得说时容易做时难,但你是大学生,你的本事只不过搁下生疏了, 你与一般无知妇孺不同……”[7] 正是唐晶的这一番话,才使子君打起精神,重新振作起来。
而在《花解语》里,花不语是个演员,就是因为长得太好,被宠坏了,不肯下苦功学习演技,老是做花瓶角色,人气一过,戏份接着下降。
宽厚、懂事的花解语出面找人帮忙,处事也很得体,还甘于牺牲自己。
在这里,女性友谊是女性对自身性别的认同、尊重与热爱,是感情的需要,甚至是对另一性别不公正对待的联合反抗。
二、亦舒小说中女性意识张扬的原因1、亦舒的个人经历亦舒生在上海,长在香港,其生活阅历极为丰富。
她在香港读完中学后即担任《明报》记者, 接触的社会面极广;在爱情生活上遭受极大挫折和困厄并经历了失败的婚姻后,离开香港,赴英留学,开始对人生采取客观而冷峻的态度。
亦舒在英国留学的几年恰逢一场席卷欧美的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女权运动。
女权主义所倡导的“妇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应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力的原则[8]。
”对亦舒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留英后的作品显得更有层次,技巧更趋简洁,取材上更能掌握今日职业女性的精神面貌,文字上也益见辛辣,女性意识日益凸显出来。
回到香港后,在新闻界以及公关机构中屡任高级职务的亦舒,在作品中以她个人闯荡社会的切身体验和实际经历,以她紧贴社会现实的女儿之身真切地道出了女性在追求人格独立、追求理想生活时的心理历程,刻画出了女性在生活中的失落、凄惶,表现出了女性在人生旅程中遭受的多重压力和羁绊,展示出了女性对生活的多方面的渴求和希冀。
也正是基于这种女性意识,才为其作品内容和艺术的超越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2、香港的社会环境70年代以来,伴随着香港经济的高速发展和香港女性就业机会的空前增多,香港女性的经济地位日益提高,女性独立意识亦有了前所未有的增强。
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传统家庭关系受到威胁,女人们内心也承受了更多的压力,于是她们借小说的样式实现自我与权利的幻想;在华洋混杂的香港上流社会,西方文化的熏陶是一个比较容易让女性———特别是受过较高文化教育和经济独立的女性获得自主意识的空间。
发端于西方的女权主义批评,也强化了香港女性作家的创作自觉。
女性意识的复苏和觉醒、女性价值定位的思考和寻求,便构成了这一时期香港文学的基本场景。
80年代是香港女性作家创作的盛期,女作家的崛起,不仅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时髦,更是人权平等包括受教育平等和生产力发展改变了女人的从属地位的产物。
亦舒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了发生在社会生活中的这一巨变,深切地意识到,中国自有社会制度以来,男性长期作为社会的中心,旧传统与礼教严重压抑着女性争取自由与独立的呼声;妇女地位虽然较从前有所改变,但无论在政治、法律或女性意识上,这些改变都显得十分迟缓,尤其对妇女角色的认同,仍沿袭着传统社会以家庭角色为主的刻板印象。
于是,亦舒在小说中便从女性视角出发,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的心理情感,表达女性的生命体验,在男权社会中进行久已失落的自我寻觅,企图从传统的男权话语空间中脱离出来,进而重构了女性话语空间。
亦舒在小说中所建立的这种女性主义视野,且不说是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得来的理念,还是从香港经验生活中获得的“不谋而合”,都有它在香港出现的现实依据。
3、香港的文化氛围文化是文学发生和发展的温床与动力,不仅影响着文学的存在形态、运动方式,还赋予了文学一定的文化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