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全知视角下的本相
王安忆小说的叙事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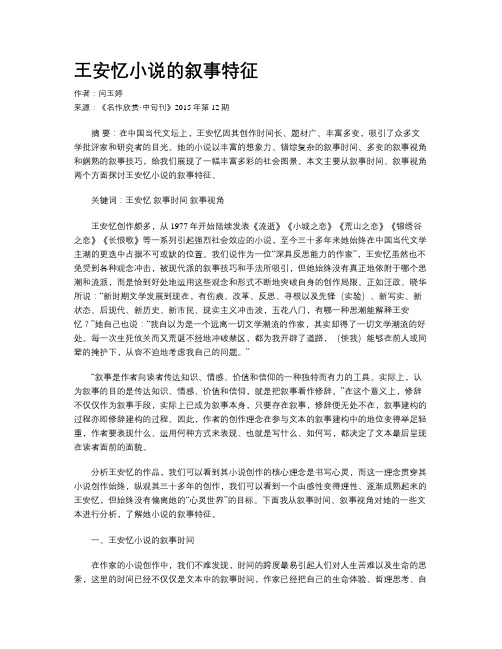
王安忆小说的叙事特征作者:闫玉婷来源:《名作欣赏·中旬刊》2015年第12期摘要: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王安忆因其创作时间长、题材广、丰富多变,吸引了众多文学批评家和研究者的目光。
她的小说以丰富的想象力、错综复杂的叙事时间、多变的叙事视角和娴熟的叙事技巧,给我们展现了一幅丰富多彩的社会图景。
本文主要从叙事时间、叙事视角两个方面探讨王安忆小说的叙事特征。
关键词:王安忆叙事时间叙事视角王安忆创作颇多,从1977年开始陆续发表《流逝》《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长恨歌》等一系列引起强烈社会效应的小说,至今三十多年来她始终在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的更迭中占据不可或缺的位置。
我们说作为一位“深具反思能力的作家”,王安忆虽然也不免受到各种观念冲击,被现代派的叙事技巧和手法所吸引,但她始终没有真正地依附于哪个思潮和流派,而是恰到好处地运用这些观念和形式不断地突破自身的创作局限。
正如汪政、晓华所说:“新时期文学发展到现在,有伤痕、改革、反思、寻根以及先锋(实验)、新写实、新状态、后现代、新历史、新市民、现实主义冲击波,五花八门,有哪一种思潮能解释王安忆?”她自己也说:“我自以为是一个远离一切文学潮流的作家,其实却得了一切文学潮流的好处。
每一次生死攸关而又荒诞不经地冲破禁区,都为我开辟了道路,(使我)能够在前人或同辈的掩护下,从容不迫地考虑我自己的问题。
”“叙事是作者向读者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的一种独特而有力的工具。
实际上,认为叙事的目的是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就是把叙事看作修辞。
”在这个意义上,修辞不仅仅作为叙事手段,实际上已成为叙事本身,只要存在叙事,修辞便无处不在,叙事建构的过程亦即修辞建构的过程。
因此,作者的创作理念在参与文本的叙事建构中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作者要表现什么、运用何种方式来表现、也就是写什么、如何写,都决定了文本最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面貌。
分析王安忆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其小说创作的核心理念是书写心灵,而这一理念贯穿其小说创作始终,纵观其三十多年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感性变得理性、逐渐成熟起来的王安忆,但始终没有偏离她的“心灵世界”的目标。
谁是谁的过客——王安忆小说《月色撩人》探微

界 主 义是一 种 真 正 跨 越 国界 的 ( 方 的 ) 英 文 西 精 化 的 果 实 。 尽 管 , 们 对 后 现 代 主 义 这 个 定 义 ” 我
仍 时有 争论 , 它 对社 会 潮 流 及 大 众 生 活所 引发 可 的辐射 与带 动 , 是 惊 人 的 。我们 不 管 愿 不 愿 意 却
第2 5卷 第 2期
V0. 5 N . I2 o 2
钦
州
学
院
学
报
21 0 0年 4月
Apr .,201 0
J RN L OF QI Z OU A N HOU U I ER I Y N V ST
谁 是 谁 的 过 客
王 安 忆 小说 《 月色 撩 人》 探微
颜 莺
到 了 这 一 点 即 在 常 态 的 生 活 中 , 匿 着 生 活 的 密 隐
码 , 这 种 生 活 的 密 码 在 每 个 人 却 是 不 同 的 , 不 而 在
联 系 的 。《月 色 撩 人 》恰 如 其 分 地 表 现 了 这 一 点 。
小 说 中不管 是人 物 的言行 , 是 画外 音 的评论 , 或 无
不 显 露 出 在 人 们 传 统 中挣 扎 的 痕 迹 。 王 安 忆 是 在
同时期需 求也 是不一 样 的 。
传 统 观 念 中 熏 陶 出 来 的 作 家 , 她 的 笔 触 伸 向 后 当 现代 的时候 , 就 必须用 后 现代 的手 法开 始解 构 , 她
解 构生 活 , 构社 会 , 构 人 。 解 解 生 活 在 这 个 消 费 主 义 充 斥 的 现 代 , 们 怎 样 我 生 活 ? 靠 什 么 生 活 ? 追 求 什 么 ?放 弃 什 么 ? 又 能
2024年高考语文备考之王安忆《弄堂里的白马》(附习题+答案)

01阅读导入车马喧嚣的都市、静谧幽长的弄堂、矜持的一人一马徐徐穿行其间,犹如天外来物,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年代。
有人时他们矜持得近乎木讷,无人时偶尔又会像飞天之鸢,活泼的样子惊艳了孩子的眼。
他们来自何处?又为何出现于此处?王安忆以儿童视角观察着这一人一马,揣测他们的来历,暗喻人与马相似的命运——裹挟于历史浪潮而无法掌控自我,他们又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面对这不幸,并借此以小见大的反映了上海的变化发展。
人、马、城成为一体,故在阅读时需要注意这一点。
02批文入情弄堂里的白马王安忆>>>标题:交代了写作对象及故事发生的地点;同时,白马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弄堂里,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白马,是全文的线索。
①弄堂里时常光顾一匹白马。
(开门见山,呼应题目。
)要知道,这是在弄堂,都是街道和房屋,还有熙来攘往的人和车,一匹白马,终究有些神奇。
(白马出现在现代都市的弄堂里,格格不入的事物,引起所有人的好奇。
)②不定什么时候,先是传来叮叮的铃声——那是它的主人,一个脸色严峻的北路人,拴在它脖子上的铃铛响,然后,就听见嘚嘚的马蹄铁敲在水门汀地面上,很清脆地过来了。
(以声切入,写出马的到来。
)白马徐徐走来,每到一扇门前,就停下来。
它的主人并不吆喝,只站着。
白马呢,也站着。
它的鬃发在前额上剪齐成刘海,加上脖子上的铃铛,使它显得很稚气,像一个小姑娘。
这一主一仆静静站立着,等待门里的人家决定要不要买一碗马奶尝尝。
他们等一时,并没有什么动静,就再向前走。
(一人一马,静默地站在某户门前,体现了主人较强的自尊心和马的温顺。
同时,作者用“仆”“稚气”“小姑娘”这些词将马拟人化,写出了人和马出奇的矜持,矜持到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喧腾、壅塞的地方。
)倘若有人从门里出来,买一碗马奶——这样的情形,概率大约是二十分之一,于是,北路人就从肩上卸下一个马扎,开始挤奶。
淡黄色的奶汁,极细弱地,吱吱洒在买主的白瓷碗里,渐渐积起一层,又渐渐平了碗沿。
女性的觉醒与成长—论王安忆作品中女性形象

女性的觉醒与成长—论王安忆作品中女性形象一、女性的生存环境1.1.女性社会意识的缺失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女性的地位一直处于缺失状态,甚至可以说,女性在我国传统社会是没有地位的,所有的生存价值都是以男性作为标准来制定的,而女性的价值没有得到该有的体现,出现了男尊女卑的负面状态,这种现状的根源是当时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耕社会及其较低的生产力水平所致。
在这种社会情况下,男性就成为了主要的劳动力,他们要负责在外劳作,支撑整个家庭的开支,要赡养父母和抚养子女,在古代社会中通过对子女教育不同而区分男女的社会地位,比如不支持和鼓励女性读书,以女性操持家务为价值导向等,进而维持以男性为尊的社会体系。
这种情况在先秦时期就已经确立,许多经文予以记载,例如《诗经・小雅・斯干》中就描述了不同的待遇状况:如果生了男孩,就可以赐给玉佩和衣裳,并且睡于床榻,百般喜爱,期待其成为君王。
而生了女儿就感到颜面全无,将其放在地上,“载衣之锡,载弄之瓦”,不教授礼仪,仅仅提供饮食,父母不加以管教。
男子的教育是忠孝仁义,为的是培养他们的阳刚气概,为国家做贡献;对女子的教育是希望她们温柔贤淑,能相夫教子做一个好媳妇。
在秦汉时期儒家将阴阳的观点与政治统治的理念相结合,提出的“三纲五常”的理论框架。
他们认为夫妻必须以夫为尊、君臣必须以君王为尊,父子必须以父亲为尊,并将这种意志以上天意志的意志,结合政治统治的加以推广和实施。
所以,根据这个理论推行和实施,妇女逐步成为男性附属,缺乏独立的生活和政治地位,由于政治的强硬性和思想上的禁锢,女性女权意识逐步被淡化和绝对化了,社会地位荡然无存。
这一点在前秦的诏书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诏书中规定,妇女未经批准不得在都城五百里范围内乘坐马车,不得穿戴金银和锦绣,不得经商、奴隶买卖等活动,如果触犯,将被丢弃于集市,甚至处死。
由此可见,妇女的社会地位极地,与奴隶相近、受人鄙视的商人列为一类,违反者处以死刑,国家对妇女的歧视程度可见一斑。
独特的历史观观照下的城市书写

独特的历史观观照下的城市书写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坛上,王安忆是一位引来很多评论家目光的作家。
就王安忆个人的生活经历而言,她有短暂的“知青”生活,而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生活。
这样,她的小说就有了城市和乡村两种视阈,而在其城市小说中,她始终是围绕着上海这座现代化的城市来进行书写的。
有评论家认为,她是海派作家的传人。
确实,王安忆继海派作家之后,又一次把目光聚集在上海这座城市对上海的饮食男女和他们的生活进行描绘,同时通过一些上海特有的的意象如弄堂、亭子间等,对上海的文化、历史进行深入、细致的表现。
在王安忆的城市书写中,时时体现出王安忆对历史的独特理解。
王安忆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
譬如上海街头妇女着装从各色旗袍变成一式列宁装,我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历史。
……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
”①本文以王安忆的历史观为切入点,分析她的城市小说,剖析在这种历史观观照下,其城市小说的空间意象所折射出的内涵,通过对具体文本中城市人物的分析来综观王安忆的城市小说。
在独特的历史观观照下,王安忆城市小说中的上海女性和上海男人各具特色,在这些上海饮食男女的身上,我们可以领略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以及文化。
本论文由引言、主体和结语三大部分组成。
引言部分简单回顾三十年来批评研究界对王安忆小说研究的几种视角,介绍本文的写作意义、写作目的和主要内容。
主体包括四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介绍王安忆独特的历史观,并且分析其历史观形成的原因。
王安忆的历史观最核心的观点是:小说应该表现“日常生活”。
王安忆“日常生活”的历史观是对80年代中后期文坛反驳宏大叙事和90年代文化怀旧热潮的强烈回应,也与她的个人经历和审美观有一定关系,同时是王安忆悲悯、宽容的人文情怀的体现。
第二部分,分析在独特历史观观照下的王安忆小说的城市空间描写,主要对上海特有的弄堂这一意象进行深入的开掘,揭示弄堂的文化意蕴。
第三部分,分析在“日常生活”的历史观观照下,王安忆上海小说中上海市民的性格。
论王安忆散文的心灵维度

论王安忆散文的心灵维度作者:罗华庚来源:《大观》2016年第08期摘要:王安忆的散文成就不容忽视,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解剖自我的心灵情节,展现生命的本相,并在行文中坚守着一种理性精神,有着深厚的现代意识。
关键词:心灵情节;生命本相;理性精神王安忆以写小说而闻名,她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善于以女性细腻的笔调书写历史与人生的关系,注重表达人性的复杂一面。
与她的小说做法一脉相承,她的散文也同样具有类似的特点,以缜密的心思记录着历史,观照着历史与社会、理想与现实,追寻着一种张扬理性的现代意识。
王安忆的散文大致可分为写人、记事、记游、讲演、创作谈这五类,她的叙述笔调是散漫中见其缜密的心思,情感抑制而又见其舒缓。
她的散文中有一种心灵维度,情感不偏不倚,适当地抒发,追求理性的表达,力求还原作者心灵中对事物的本来面貌,显示出其真率、通达、雅致、坚韧的散文精神。
一、重大的心灵情节心灵犹如散文的眼睛,作者以它来给读者展现散文内在的世界,窥见社会、历史与人生。
王安忆交涉广泛、博览群书,出游的地方甚多,她的散文独具慧眼,以其知性见长,把许多人物轶事、历史典故、小说故事、名胜古迹等娓娓道来,以她的心灵之眼发见内心深处的情节。
“情节”一般出现在小说中,包括人物与事件两大因素。
散文中的情节往往是配合作者用来表达情感、抒发心志的,而在王安忆的散文中她写的情节却大多是为刻画形象、表现个性服务,告诉读者一些人,一些事,一些地方,一些读书感悟等。
在王安忆谈散文的随笔中,她强调散文“是成熟的完美的作品”,应“承载起一些比较重大的心灵情节”。
王安忆的散文也正是如此,表现着重大的心灵情节。
她以驾驭小说的笔法写散文,善于刻画人物形象,表现许多不为人所知的一面。
《黄土的儿子》写了对黄土有着深厚感情而未老先衰的路遥,他抗拒名与利,还在一次吵架中因生气而说出“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这些“似乎有些词不达意的辩白”,刻画了一个人生艰辛又平凡脆弱的路遥。
王安忆_全知视角下的生命本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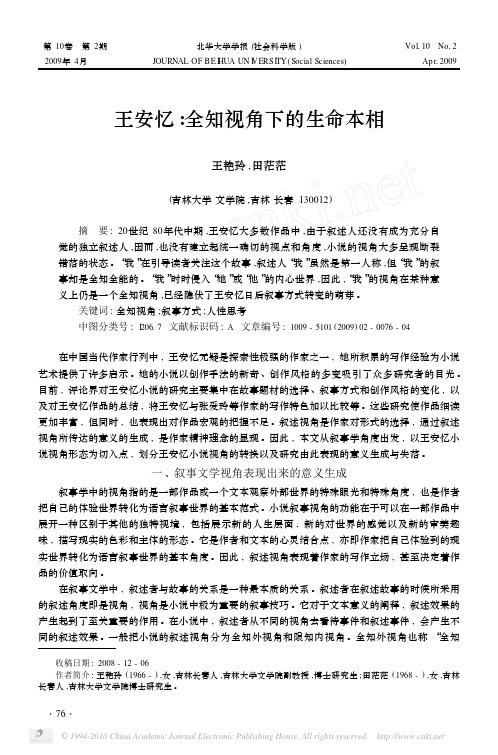
第10卷 第2期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 110 No 122009年4月JOURNAL OF BE I HUA UN I V ERSI TY (Social Sciences )Ap r 12009 收稿日期:2008-12-06作者简介:王艳玲(1966-),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田茫茫(1968-),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安忆:全知视角下的生命本相王艳玲,田茫茫(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摘 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安忆大多数作品中,由于叙述人还没有成为充分自觉的独立叙述人,因而,也没有建立起统一确切的视点和角度,小说的视角大多呈现断裂错落的状态。
“我”在引导读者关注这个故事,叙述人“我”虽然是第一人称,但“我”的叙事却是全知全能的。
“我”时时侵入“她”或“他”的内心世界,因此,“我”的视角在某种意义上仍是一个全知视角,已经隐伏了王安忆日后叙事方式转变的萌芽。
关键词:全知视角;叙事方式;人性思考中图分类号:I 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01(2009)02-0076-04在中国当代作家行列中,王安忆无疑是探索性极强的作家之一,她所积累的写作经验为小说艺术提供了许多启示。
她的小说以创作手法的新奇、创作风格的多变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
目前,评论界对王安忆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故事题材的选择、叙事方式和创作风格的变化,以及对王安忆作品的总结,将王安忆与张爱玲等作家的写作特色加以比较等。
这些研究使作品细读更加丰富,但同时,也表现出对作品宏观的把握不足。
叙述视角是作家对形式的选择,通过叙述视角所传达的意义的生成,是作家精神理念的显现。
因此,本文从叙事学角度出发,以王安忆小说视角形态为切入点,划分王安忆小说视角的转换以及研究由此表现的意义生成与失落。
一、叙事文学视角表现出来的意义生成叙事学中的视角指的是一部作品或一个文本观察外部世界的特殊眼光和特殊角度,也是作者把自己的体验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范式。
从王安忆看女性作家

如《 山之恋》 荒 中女 文 工 团 员 和 “ 谷 巷 女 金
世iWJ M l l
遗憾, 老年的不 中 动产。 ——李青
 ̄ 1年第 7 ・・・・・・・・・・写 作 0o 期 子” 。由于母 性 的苏 醒 , 在爱情 和 婚姻 的 l子 e t 里 ,她们 便 一 改少 女 时期 的矜 持 和 胆怯 , 而 变 得 主动 、 坚决 、 熟 、 成 勇敢 起 来 。她 们 脚 踏 找 到共 鸣 的东 西 , 在心 底 暗暗赞 叹 。因此说 , 女人 也 更 懂得 爱 情 。写 文章 从 不 张扬 , 细 细 地 、 轻地 , 能 够飘 进 你 心 里 , 抵 最 柔软 轻 却 直 的部 分 , 因为 再 细致 的男 人 也不 会 有 女人 只 对 感 情 的那 份 敏感 。
蠹
》
| l t t
嚣. ≯
一
2 1 年 第 7期男孩 , 我清 楚地 记 住 了他 的溜 圆的脑袋 , 以及 掏钱 的动作 。
是 的 ,这 个 男 孩 对 于我 不 过 是 个 陌 生
出 生 的作 家 群 ” 等种 种 的漫 长 沿 革 、 大发 巨
才 情 的 悲剧 性 所 在 , 个 女 人 太 聪 明 . 有 一 太 才情 , 对 文学 艺术 执 着往 往会 带 来悲 剧 性 再
体会 它, 这样 才是美 的最 大价值 。■
的命 运 。这 一点 跟男 人 有很 大 不 同 。 人 有 男 才 情再 加 上 自己 的执 着 则 会 将 男 人 的 艺 术 生涯 推 向巅 峰 。因此 , 人 在某 种 程度 上 说 女 虽 然有 优 势 但 仍 处 于 弱 势 地 位 。从 文字 人 手 ,把文 字 当做 ~种 生命 的出 口和 解脱 。 或 者 在文 字 中通 过 安 排 人 物 的 性 格命 运来 圆 自己的梦 , 是女 人 一种 独特 的 体验 生命 的 也
选择的焦虑--从《富萍》看王安忆的城乡观

缘由,而 《 富萍》中大半篇幅写的还是钢筋混泥土 的 “ 淮海路 ”中富萍与奶奶、吕凤仙等的生活。或 许作者花大量篇幅对 “ 淮海路”生活的描写 ,是为
了给之后 富萍选 择 “ 梅家 桥 ”做铺垫 。
但却不大真实 ,好像电影和戏里的人物。 ”[ 2 ] 2 7 还有 多次出现对劳动 、对 自食其力的肯定 ,如 “ 水 晶宫
她一方面希望故事能够按照她的预想走下去富萍能理所当然地选择留在?梅家桥?这个代表着作者本人最本真朴素的理想的象征之地但她本人对城市与乡村复杂纠结的感情却使得她在选择的过程中产生了焦虑的情绪无法以足够的理性说服自己因此在安排富萍的选择时现实与故事逻辑的冲突是必然的
2 0 1 4年 8月
安康学 院学报
摘
要 :王安忆以其小说作品 《 富萍》,深化 了对老上海生活方式的追忆和对城 乡关 系的探讨。作品中全知 全能
的叙述视 角决定 了 “ 富萍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着作者 的选择 ,然 而在作品看似平 实流畅的叙述表 面 ,却 游走 着故事与现 实的逻辑冲 突,造成 了文本 自身无法 弥合的裂 隙。这一裂 隙既是作者在创作构思与布局上 的缺 憾 ,但 同
J o u na r l o f An k a n g Un i v e r s i t y
A u g . 2 0 1 4 Vo l | 2 6 No . 4
第2 6卷 第 4期
选择 的焦虑
— —
从 《 富萍》 看王安 忆的城 乡观
李 讳
( 武汉大学 文学 院,湖北 武汉 4 3 0 0 7 2)
拉上 钱包 。心 里就 有一种 富 足和安 定 的感觉 。这 是 ”[ 2 1 3 《 富莽 ① 讲的是来 自 “ 扬州乡下”的女孩富萍 真正劳动吃饭 的生活 ,没有一点 隗对内心 的地方。 梅家桥”做铺垫。 到上 海谋 生 的故事 。 “ 走 人婆 娑扬 州 ,那过 往 的人 以上描述都是为富萍最后 留在 “ 事 忽就 显现 出它 的色泽 与情 调 ,我甚 至于 觉着 ,钢
王安忆小说中的物象分析

王 安 忆 小 说 中的物 象 分 析
圃 刮 妹
内容 摘 要 : 王 安 忆是 一位 多产 且 风 格 多 变 的作 家 , 三 十年 的创 作 生 涯 中 , 不 断 寻 求 创 新 与 突破 , 为读 者 构 建 了一个 丰 富 多彩 的“ 心 灵世 界” 。 她 在 小 说 中所 选 取 的诸 如 弄 堂 、 闺阁、 爱 丽 丝公 寓 、 邬桥 、 淮海路等独具特 色的
“ 意象 ” 一词 在诗 学 范畴 中意 义 内涵 极 其丰 富 ,它可 以被拆 分 为 两 个 方 滴— — “ 意” 和“ 象” , 意 指 作 家 主 观 的情 感 与思 想 , 而“ 象” 则 是 指 具体 客 观 的物 象 ,两者 结 合 使原 本 无感 的具体 客 观事 物 变成 传 达情 感 的充满 隐 喻 和明 喻 的介质 。刘勰 的
的基础 。
生 与繁 殖含 义 ” 。 1 . 弄堂 空间 狭小 、挤塞 是 上 海弄 堂 的 标 签 ,海 派 文学 的作 品中 写 到弄 堂 时总 是 弥漫 着一 种 局促 、拥挤 的气
《 文心 雕 龙 ・ 神思 》篇 中第 一 次提 出 了“ 意象” 的概 念 “ 然 后使 玄解 之 宰 ,
循 声 律而 定 墨 ; 烛 照 之将 , 窥 意象 而 运 斤 ;此 盖驭 文 之首 术 ,谋 篇 之 大 端 。” “ 认 为 作家 的创作 其 实就 像是 位 有独 到 见解 的工 匠 ,根 据 想象 来使 用工 具 一样 ,人 与 工具 合 而 为 这里 提 到 的“ 意象” 是指 作 者 把 在生 活 中获 得 的丰 富 的生 活经 验 和 独特 的感 悟 赋 予 到 特 定 事 物 之 中 , 达 到寄 情 于物 的效 果 ,是 主观 与 客 观结 合 的产 物 。 因而, 它 不是 单纯 的 客 观存 在 的结 果 ,而 是作 者 的 主观 感召 , 参 杂着 作者 的思 想 情感 , 意识 态 度 的特 定 “ 物象 ” 。美 国批评 家韦 勒 克认 为 : “ 意象 可 以作 为一 种 ‘ 描 述’ 存在 , 或 者 也 可 以作 为 一 种 ‘ 隐
从《叔叔的故事》浅窥王安忆的小说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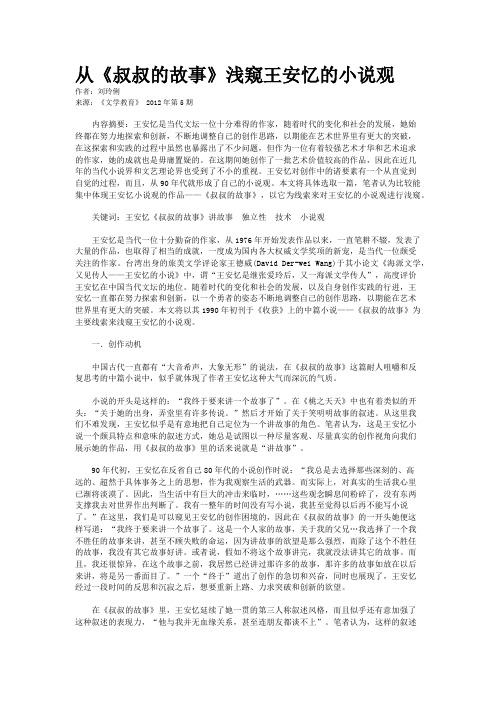
从《叔叔的故事》浅窥王安忆的小说观作者:刘玲俐来源:《文学教育》 2012年第5期内容摘要:王安忆是当代文坛一位十分难得的作家,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她始终都在努力地探索和创新,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创作思路,以期能在艺术世界里有更大的突破,在这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虽然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但作为一位有着较强艺术才华和艺术追求的作家,她的成就也是毋庸置疑的。
在这期间她创作了一批艺术价值较高的作品,因此在近几年的当代小说界和文艺理论界也受到了不小的重视。
王安忆对创作中的诸要素有一个从直觉到自觉的过程,而且,从90年代就形成了自己的小说观。
本文将具体选取一篇,笔者认为比较能集中体现王安忆小说观的作品——《叔叔的故事》,以它为线索来对王安忆的小说观进行浅窥。
关键词:王安忆《叔叔的故事》讲故事独立性技术小说观王安忆是当代一位十分勤奋的作家,从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以来,一直笔耕不辍,发表了大量的作品,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一度成为国内各大权威文学奖项的新宠,是当代一位颇受关注的作家。
台湾出身的旅美文学评论家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于其小论文《海派文学,又见传人——王安忆的小说》中,谓“王安忆是继张爱玲后,又一海派文学传人”,高度评价王安忆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以及自身创作实践的行进,王安忆一直都在努力探索和创新,以一个勇者的姿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创作思路,以期能在艺术世界里有更大的突破。
本文将以其1990年初刊于《收获》上的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为主要线索来浅窥王安忆的小说观。
一.创作动机中国古代一直都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说法,在《叔叔的故事》这篇耐人咀嚼和反复思考的中篇小说中,似乎就体现了作者王安忆这种大气而深沉的气质。
小说的开头是这样的:“我终于要来讲一个故事了”。
在《桃之天天》中也有着类似的开头:“关于她的出身,弄堂里有许多传说。
”然后才开始了关于笑明明故事的叙述。
从文学到银幕《长恨歌》的跨媒介叙事探赜

70CRITICISM ON FILMS电影批评《长恨歌》是中国当代作家王安忆于1996年首次出版的散文体长篇小说,2000年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18年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
2005年小说《长恨歌》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关锦鹏执导,郑秀文、梁家辉主演,并于同年获得第62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提名。
自电影摆脱“活动照相”起,电影改编也随之出现,大量电影以小说为蓝本向观众讲述故事。
但由于传播媒介不同,小说叙事和电影叙事在讲述故事的方式上有着很大区别,小说借助语言构成文字形象,而电影通过镜头构成银幕形象。
本文将以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和关锦鹏执导的同名电影为例,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从小说到电影的过程中在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主题等三方面的文本转换问题。
一、叙事视角:从全知视角到旁观视角叙事视角指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它是传递故事主题意义的一个重要工具。
无论是对于文字叙事、电影叙事亦或其他媒介的叙事,如果叙事时的观察角度不同,即使面对同一个故事,也会产生大相径庭的效果。
在小说《长恨歌》中,王安忆选取了传统上最常用的全知视角。
全知叙事者处于故事之外,叙事者可以从任何角度观察事件,可以透视任何人物的内心活动,也可以偶尔借用人物的内视角或佯装旁观者[1]。
王安忆将全知视角的功能赋予了飞翔在上海这座城市上空的鸽子:“鸽子是这城市的精灵……它们是唯一的俯瞰这城市的活物,有谁看这城市有它们看得清晰和真切呢……这城市的真谛,其实是为它们所领略的”[2]。
当鸽子站在一个制高点俯瞰上海,它不仅看到这座城市阡陌纵横的独特弄堂,也听到裹挟在这东方巴黎之下的鄙陋流言;它瞥见的不单是上海弄堂房子里流光溢彩的女儿闺阁,也见证着时光变迁中隐藏在这座城市犄犄角角的罪与罚、祸与福。
鸽子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见证者,也是主人公王琦瑶这一生的历史见证者。
它看着王琦瑶在弄堂穿梭来回渐渐长大,在狭小的闺阁想着少女心事;看着这个普通的弄堂女孩竞选“上海小姐”一举成名,做李主任的外室享尽人世的浮华与孤独;看着王琦瑶经历人生低谷不得不重回弄堂自力更生,遇到富家少爷康明逊后重燃爱火;看着王琦瑶独自抚养女儿薇薇并为她准备嫁衣,已至中年却与年轻人老克腊陷入畸形恋……在人生最后的可怖夜晚,也只有这群鸽子可以见证,因为“它们一代一代地永不中断,繁衍至今,什么都尽收眼底……等到天亮,鸽群高飞,你看那腾起的一刹那,其实是含有惊乍的表情。
时代下诗意的真实——王安忆小说中对人精神世界的体察

072文学·艺术《名家名作》·评论时代下诗意的真实—王安忆小说中对人精神世界的体察代修凡一、王安忆作品中的“上海情结”“上穷碧落下黄泉,续上海繁华旧梦。
”上海是王安忆的故乡,她经常将上海作为背景讲述她对故乡的眷恋和痴情,割舍不掉对故乡的深情。
上海代表的是好、先进、优越,是名副其实的“东方巴黎”。
这座城市带着与生俱来的奢靡感、华丽感甚至是优越感走在中国文化生活新潮流的制高点。
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日日熏染并沉浸在其中,不免沾染矫揉造作、傲视众生的贵族气质。
如王琦瑶少女时期生活的场所“闺阁”就是小说《长恨歌》中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意象,“闺阁八面来风”,崇尚奢侈、摩登等时尚要素的观念不自觉地进入人的意识中,成了王琦瑶“拜金主义”、渴望受到瞩目的最初启蒙。
在那个寸土寸金的地方,上海人宁愿家中好几口人挤一间幽黑的小屋,生活拮据、勉强度日,却依然享受这里的一切,怀揣着暴富的梦想努力地在这个“魔都”生存。
潜移默化的环境熏陶在女孩的心中早已播下根深蒂固的种子,最终她还是没能抵挡住整个城市对人内心汹涌的侵袭。
浪漫早已在她心中铺就罗网,她情愿被俘虏,一步一步跌入追寻与失落的迷雾之中。
上海诱惑着生存在这里的人们不断突破自身阶层。
对于王琦瑶来说便是选择在读书的年纪一步步当选“上海小姐”“沪上淑媛”,成功跻身上流社会,即便人尽皆知这类评选比赛是由政商界、军政界“大人物”主使的,最后的当选者也不过是达官贵人的玩物。
果不其然,她被“李主任”以情妇的身份包养,她甘当“金丝雀”,过上了一段看似安稳实则空虚,每天等待李主任回来的日子。
这是一场注定不能长久的美丽幻影。
王琦瑶和这段关系构成了宿命般的死结。
但是王安忆在叙述中对此并没有深度谴责,而是饱含对人性的理解和体察:“人心是最经不起撩拨的,一拨就动,这一动便不敢说了,没一个见好就收的。
”“她们都是人里的尖子,这样的人怎么能甘于平凡?谁该为谁垫底呢?” 很多人都无法从自己固有的认知出发判定很多事,作者将道德评价、世俗价值判断标准默默收起,单纯从上海这座城市的客观现实、“上海情结”和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的角度议论抒情。
自我本体意识的自觉与理牲自我的观照——王安忆文学创作管窥

作者: 王苹
出版物刊名: 当代文坛
页码: 20-21页
主题词: 王安忆;自觉;当代作家;本体意识;文学创作;观照;女作家;优秀作品;成绩;自我
摘要:在当代作家的行列中,王安忆是一位个性突出、成就卓然的女作家。
在80年代,她就创作出一批优秀作品,在90年代她依然风采依旧并充分显示出大家风范。
她始终是一位弄潮女,其作品有着很强的张力和连贯性。
王安忆取得今天斐然可观的创作成绩,与她既有自觉的自我本体意识又能对本体自我进行理性的观照分不开的。
她表现了一个完整、统一的世界——读王安忆小说随想

摘要: <正> 一在王安忆的作品里,美与丑,新与旧,光明与黑暗,积极与消极等交错、交融,浑 然一体,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完整、统一的世界,即一个全景的小社会。陈信的家(《本次列 车终点》)、歌舞团的小院(《小院琐记》)、运动学校(《新来的教练》)、中年级编辑室(《迷宫 之径》)、地区文工团(《舞台小世界》)等等,都是一个“小社会”。“正如吃了半个苹果以后就 再也不能有整个苹果一样,没有矛盾的另一面,就不可能有矛盾的这一面。”(《马恩选集》第4 卷 63页)王安忆写的不是“半个苹果”,而是整个苹果。她的作品象生活
繁华落尽见真淳--王安忆的日常化写作王安忆把目光投注于日常生活实

(附录二)繁华落尽见真淳--王安忆的日常化写作王安忆把目光投注于日常生活实与整个大环境的变化有关。
上海文学素有描写市民社会的传统。
此传统曾因抗战而一度中断。
1949年中共执政后,上海的建设每况愈下,都市的面貌保留三十年代的样子,而都市特色也在时间里褪色。
1990年四月,中共决意开发上海浦东新区,按照国际一流标准进行现代化城市基础建设,上海得以重新出发,面向世界。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鼓吹改革开放,上海的投资与建设也随着增加。
上海开始在新的兴建中改头换面,黄埔江新建的建筑再度显示出上海恢复了活力。
市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发展遥相呼应而抬头。
文学由单一化、政治化转向世俗化和多样化,由符合政治的要求转向表达个人的追求。
市民社会浮出台面,人们怎么生活变成一件重要的事,而文学开始关注最实际的生活面,即普通人的生存状况。
中国知识分子在过去常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
五四之后,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是政治的、启蒙的,在主流意识形态之下,日常生活的题材被忽视与遗忘。
1949年后,左翼文学大行其道,个体消融在党与民族的集体意识之中,日常生活书写在历史叙事的主题面前变得琐碎、平庸。
但是这种情形到80年代之后有了改变,启蒙使命和人文主义关怀被商业大潮281所取代,官方的意识形态逐渐退出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
在后工业社会里,知识分子开始以新的姿态面对新的现实。
在商业经济社会里,都市地位提升了,个人从集体中挣脱出来,市民阶层受到重视,他们所崇尚的俗世生活进入了创作的视野。
平民群体的生活价值获得关注,创作与历史叙述开始分离,文学多元化的格局遂形成。
因此,有论者认为王安忆的都市题材频繁的出现,不仅是她个人兴趣的转移,也是呼应90年代文坛对于宏大叙事的反驳。
1在这背景之下,人们被压抑的欲望和思想得到空前的释放和表达,理想主义被击溃,物质欲望的伦理崛起。
在创作上,宏大的观念语式被俗世的审美文化所取代,日常生活重回作家的创作视野中。
(一)王安忆与日常生活面对外在思潮的变化,王安忆的态度是谨慎的,在多元缤纷的都市意识中,王安忆推崇俗世生活的价值。
沉醉虚华浮云梦,只怨生却百姓家r——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虚与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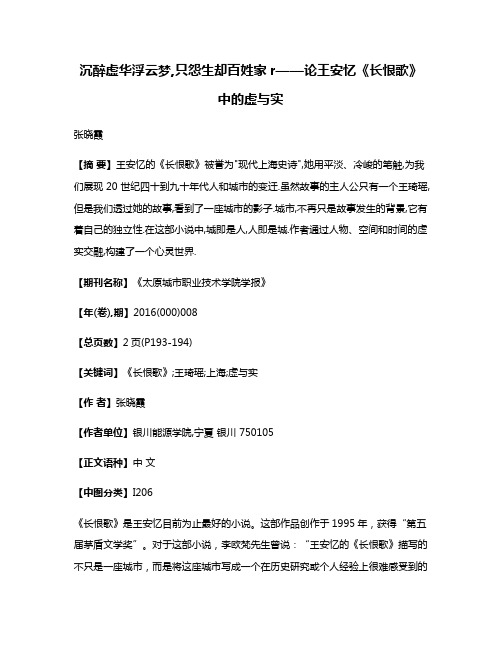
沉醉虚华浮云梦,只怨生却百姓家r——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虚与实张晓霞【摘要】王安忆的《长恨歌》被誉为"现代上海史诗",她用平淡、冷峻的笔触,为我们展现20世纪四十到九十年代人和城市的变迁.虽然故事的主人公只有一个王琦瑶,但是我们透过她的故事,看到了一座城市的影子.城市,不再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它有着自己的独立性.在这部小说中,城即是人,人即是城.作者通过人物、空间和时间的虚实交融,构建了一个心灵世界.【期刊名称】《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00)008【总页数】2页(P193-194)【关键词】《长恨歌》;王琦瑶;上海;虚与实【作者】张晓霞【作者单位】银川能源学院,宁夏银川 75010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长恨歌》是王安忆目前为止最好的小说。
这部作品创作于1995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对于这部小说,李欧梵先生曾说:“王安忆的《长恨歌》描写的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将这座城市写成一个在历史研究或个人经验上很难感受到的一种视野。
这样的大手笔,在目前小说界是非常罕见的,它可说是一部史诗。
”人即是城,城即是人。
王安忆用细腻冷峻的笔触,通过人物、空间和时间的虚实交融,在生活细节中为我们展现了20世纪四十到九十年代人和城市的变迁。
本是小户人家女儿的王琦瑶,在上海小姐的选拔中被评为“三小姐”。
她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为人内敛,如果按照真实的发展轨迹,她是不会虚化为三小姐的。
王琦瑶的梦起因于她的美,早在初中时候,她就懂得自己的美,穿着得体的衣服,这足以让她在同龄中表现出谦逊却有优势的美。
每天早上,提着花书包上学,哼唱“四季调”,结伴看费雯丽电影,这些是王琦瑶们做的事。
在小说开篇,王琦瑶就已不是个例,她被作者符号化。
这些女孩们身上有着极为相通的特点与气质,此时的王琦瑶便被赋予了很大的象征意义。
她代表着一个群体,也反映着一种共通性的心理。
直面现实可能性的虚构——王安忆《遍地枭雄》叙事情境的另一种解读

直面现实可能性的虚构——王安忆《遍地枭雄》叙事情境的另一种解读直面现实可能性的虚构——王安忆《遍地枭雄》叙事情境的另一种解读[论文关键词]王安忆《遍地枭雄》叙事情境 [论文摘要]王安忆《遍地枭雄》在直面现实可能性的虚构情境中建立起一个叙事意义上的“侠义”世界,但作者的叙事存在着观照生活与戏说英雄的矛盾,在一种看似充满温情与同情的叙事情境中隐藏着的是冷漠的眼神,并因此影响了文本意义的发挥。
众所公认,王安忆是高产并且敢于尝试不同风格写作的女作家,她的《遍地枭雄》再度让读者眼前一亮。
《遍地枭雄》讲述的是上海城乡结合部征地后的闲散劳动力韩燕来“游走天下”的故事,主人公在经历了几次工作变换后,选择了开出租车,意外的在圣诞夜连车带人一起被一个叫大王领导的小团体打劫,之后便跟着大王开始了一番情义的纠葛。
作者为主人公韩燕来安排了双重身份——韩燕来和毛豆。
这不仅仅是称谓上的不同,而是分别联系着两个完全对立的世界。
韩燕来所对应的是平常人普通的生活世态,虽庸庸碌碌也不乏温情自由纯洁正义;而毛豆所联系的则是充满冒险刺激的带有黑道色彩的另类世界。
作者的真正意图在于消解故事的真实性,便于在直面现实可能性的虚构中建立起一个叙事意义上的江湖。
正像作者自己所说的…大王’不过是叫叫罢了,只能自领了那三个小枭雄,也不能像古时的侠客云游天下,而是在地的隙缝里流窜,最终还是落入窠臼。
”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一改往日的女性叙述姿态,全力构建了一个完全男性的文本世界,一个通俗游走的母体下,王安忆用她娴熟细腻的独特感受让我们体验了一次细腻温情又稍具惊险紧张的冒险之旅。
对此,王安忆称这种变化没有风格上的改变,只是缘于文本情节的需要。
在这个冒险之旅中,作者在一种侠与非侠交错构织的叙事结构和一种温情脉脉的叙事情景中,构建了一个侠义的世界,这种叙事方式直面现实生活的可能性,让读者感受到了藏于文本背后那双思索着底层边缘人生活的智者的目光。
或许是因为那种叙事的智慧,或许是因为那种娴熟细腻的语言,读者为这种智者的目光所感动,但就在感动之余,笔者感受到的却是“戏说”英雄的调侃,甚至冷漠,在这种情形之下,所谓的“侠义”成了一种矛盾的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