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脂球
莫泊桑作品《羊脂球》讲析

(二)、作者采用同一件事中横向多层次的对照手法刻画人物。在
小说中出现三次。
1、接受羊脂球施舍之时九个人的不同表现对照
2、敌人对羊脂球提出无理要求时九个人的不同表现对照
3、获得“解放后”的表现及其对羊脂球的态度对照。
乌先生:是个极其庸俗、贪婪、粗鲁的酒店老板 布雷维尔伯爵:道貌岸然,阴险狠毒 卡雷·拉马东:利欲熏心,冷酷无情。 布雷维尔伯爵夫人 :骨子里是个毫无同情心的伪君子 乌夫人 :卑鄙无耻,毫无心肝 卡雷·拉马东太太 :通过这个形象使人民看到体面的贵妇人寡廉鲜 耻的一面 修女:她们假上帝之名,行罪恶之实,毫无圣洁可言
谢谢!
二、普法战争:小说背景
1870年发生了普鲁士和法国争夺欧洲 霸权的普法战争,莫泊桑参加过普法战争, 对于普鲁军的军队深入国土,烧杀掳掠,感 到十分的愤慨;对于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 苟且偷生,感到十分的痛心;对于人民大众 的同仇敌忾,英勇反抗,则充满由衷的敬佩。 而《羊脂球》就是表现作者上述感情的许多 小说中的优秀篇章。
多特镇事件
资产者、贵族、修女、“民族党”,这些法国社 会的重要成员,在国家民族经受考验的危难时
刻,在敌人面前卑躬屈膝,在涉及自己利益 的时候,卑鄙地出卖同胞,出卖民族气节。
第二段行程
资产阶级人物的虚伪自私和卑鄙无耻, 暴露无遗
三、人物形象分析
羊脂球的形象
《羊脂球》的中心人物,本名伊丽莎白·鲁塞。由于身体过早发胖,
4、肖像描写生动、逼真。
5、人物语言极具有个性化。
“羊脂球”的外貌: “她的脸庞儿好象一个红苹果,又象一朵含苞将 放的芍药 在这副脸蛋儿的上端睁着两只非常美丽的大眼睛,四周遮着 长而浓的睫毛 ,睫毛的阴影一直映在眼睛里,下端是一张窄窄的妩媚 的嘴 ,… …嘴里是两排细小光亮的牙齿。 ”
羊脂球

《羊脂球》是法国作家莫泊桑创作的中篇小说。
《羊脂球》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羊脂球》以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为背景。
通过代表当时法国社会各阶层的10个人同乘一辆马车逃往一个港口的故事,形象地反映出资产阶级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卑鄙自私和出卖人民的丑恶嘴脸。
在小说中,作者把下等人和上等人作了对比,检验了他们的道德水准。
羊脂球是一个有爱国心的妓女,10人当中只有羊脂球配得上称为高尚的人和有爱国心的人。
她心地善良,在马车上,尽管那些贵族资产阶级老爷太太对她表示了轻视和侮辱,可是当他们饥饿难耐的时候,羊脂球慷慨地请他们分享自己的食物。
她还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而那些所谓上等人都是些灵魂丑恶、损人利己的败类。
《羊脂球》写于1879年。
这年夏天的一个夜晚,莫泊桑、阿莱克斯、瑟阿尔、厄尼克、于斯曼五位青年作家,在法国自然主义大作家左拉的梅塘别墅聚会,商定以普法战争为背景,每人各写一篇中短篇小说,结成《梅塘之夜》作品集出版。
《羊脂球》所描写的普法战争是莫泊桑熟悉的,因为他在1870年7月应征入伍,亲身参加了普法战争,十年前法军战败溃退时的狼狈情形历历在目,而战后法国被普鲁士占领时的惨痛经验还使他心有余痛。
小说所描写的发生地鲁昂,正是莫泊桑儿时熟悉的地方,生于斯,长于斯,对于这里的一切都格外的亲切和熟稔。
作者的创作主旨在于,揭露普鲁士侵略者的残暴与野蛮,法国军队的腐败与无能,尤其是强烈地谴责那些逼迫别人做不道德的事,然后又用道德去指责人的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的自私与伪善,张扬下层人士极具爱国精神、极富正义感和同情心的美好心灵,表达对被凌辱的底层人们的同情与尊敬。
羊脂球

《羊脂球》是法国作家莫泊桑创作的中篇小说。
《羊脂球》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羊脂球》以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为背景。
通过代表当时法国社会各阶层的10个人同乘一辆马车逃往一个港口的故事,形象地反映出资产阶级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卑鄙自私和出卖人民的丑恶嘴脸。
小说《羊脂球》描绘了一八七零年普法战争期间,有一辆法国马车在离开普军占区时,被一名普鲁士军官扣留。
军官一定要车上一个绰号叫的羊脂球陪他过夜,否则马车就不能通过。
出于爱国心断然拒绝,可是和她同车的有身份的乘客为了各自私利,逼她为了大家而牺牲自己,出于无奈而作了让步。
可当第二天早上马车出发时,那些昨天还苦苦哀求的乘客们却突然换了一副嘴脸,个个疏远她,不屑再与她讲话。
她觉得自己被这些顾爱名誉的混帐东西轻视淹没了,当初,他们牺牲她,之后又把她当作一件肮脏的废物扔掉。
羊脂球

《羊脂球》是法国作家莫泊桑创作的中篇小说。
《羊脂球》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羊脂球》以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为背景。
通过代表当时法国社会各阶层的10个人同乘一辆马车逃往一个港口的故事,形象地反映出资产阶级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卑鄙自私和出卖人民的丑恶嘴脸。
在小说中,作者把下等人和上等人作了对比,检验了他们的道德水准。
羊脂球是一个有爱国心的妓女,10人当中只有羊脂球配得上称为高尚的人和有爱国心的人。
她心地善良,在马车上,尽管那些贵族资产阶级老爷太太对她表示了轻视和侮辱,可是当他们饥饿难耐的时候,羊脂球慷慨地请他们分享自己的食物。
她还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而那些所谓上等人都是些灵魂丑恶、损人利己的败类。
内容简介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普鲁士军队攻占了鲁昂城,有十个人同坐一辆马车出逃。
这十个人的身份很是特殊,分别是臭名昭著的奸商鸟先生和他的太太;大资产阶级、省议会议员卡雷·拉马东夫妇;省议会议员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夫妇;两个修女;民主党人科尔尼代和一个绰号叫“羊脂球”的妓女。
前面三对夫妇离开鲁昂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计划和目的却是一致的—这三对夫妇都不会回鲁昂了。
十个人中最没有地位的是“羊脂球”。
在马车上,几位有身份的阔太太得知了羊脂球身份后,对羊脂球的态度很是恶劣,她们悄声辱骂羊脂球是卖淫妇、是婊子、是社会的耻辱。
而这些阔太太的丈夫们则用一种看不起穷人的口吻大谈特谈金钱、吃喝。
马车在路上颠簸了大半天的光景,车上所有的人都饿了,只有羊脂球带了可供自己三天的食物。
羊脂球很大方地邀请车上所有的人都来分享她的食物,完全不计较先前这些有钱人对自己的不敬。
很快篮子里的食物都被瓜分光了,人们都摆脱了饥饿的困扰,于是人们对羊脂球的态度像肚子一样发生了变化。
先前的蔑视变成了亲昵,辱骂也变成了夸奖。
马车继续前行来到了托特镇,这里也被普鲁士军队侵占了,普鲁士军官扣下了马车,提出要羊脂球陪自己过夜。
《羊脂球》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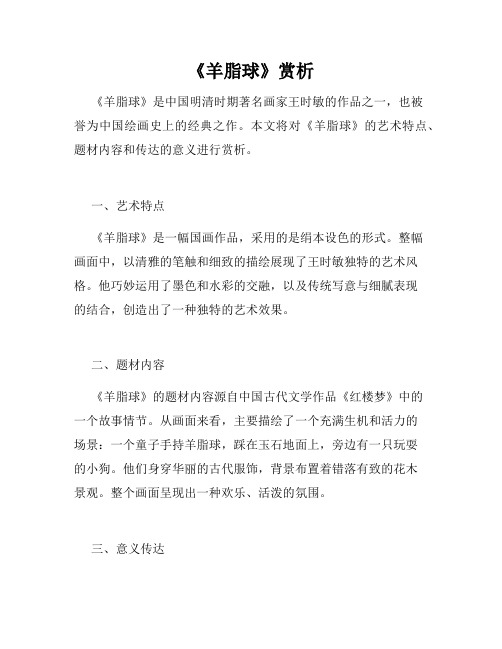
《羊脂球》赏析《羊脂球》是中国明清时期著名画家王时敏的作品之一,也被誉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经典之作。
本文将对《羊脂球》的艺术特点、题材内容和传达的意义进行赏析。
一、艺术特点《羊脂球》是一幅国画作品,采用的是绢本设色的形式。
整幅画面中,以清雅的笔触和细致的描绘展现了王时敏独特的艺术风格。
他巧妙运用了墨色和水彩的交融,以及传统写意与细腻表现的结合,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效果。
二、题材内容《羊脂球》的题材内容源自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红楼梦》中的一个故事情节。
从画面来看,主要描绘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场景:一个童子手持羊脂球,踩在玉石地面上,旁边有一只玩耍的小狗。
他们身穿华丽的古代服饰,背景布置着错落有致的花木景观。
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种欢乐、活泼的氛围。
三、意义传达《羊脂球》所传递的意义在于表达了一种快乐、天真、活力的精神状态。
画中的童子和小狗都象征着生命的活力和纯真的情感,以及对美好事物的热爱。
羊脂球作为整个画面的中心,象征着诗意和福康,暗示了幸福快乐的主题。
同时,王时敏通过细致的描绘和精湛的表现技巧,将这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画面中的花木景观和童子身上的华丽服饰,细节之处都表现出王时敏对生活美好的追求和对艺术的热爱。
通过这幅作品,他试图向观者传递一种向往、享受生活的心境,唤起观者内心最美好的情感。
总结起来,《羊脂球》这幅画通过独特的艺术特点和精心构思的题材内容,展现了王时敏作品中独有的风格与魅力。
它所传达的快乐、活力和对美好事物追求的意义,以及王时敏对艺术的热情和追求,都让这幅画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经典之作。
通过对《羊脂球》的赏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这幅杰作,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深刻内涵和美学意义。
希望这幅画作能够一直流传下去,为世人带来快乐和美好的享受。
羊脂球

羊脂球《羊脂球》是法国作家莫泊桑创作的中篇小说。
《羊脂球》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羊脂球》以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为背景。
通过代表当时法国社会各阶层的10个人同乘一辆马车逃往一个港口的故事,形象地反映出资产阶级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卑鄙自私和出卖人民的丑恶嘴脸。
在小说中,作者把下等人和上等人作了对比,检验了他们的道德水准。
羊脂球是一个有爱国心的妓女,10人当中只有羊脂球配得上称为高尚的人和有爱国心的人。
她心地善良,在马车上,尽管那些贵族资产阶级老爷太太对她表示了轻视和侮辱,可是当他们饥饿难耐的时候,羊脂球慷慨地请他们分享自己的食物。
她还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而那些所谓上等人都是些灵魂丑恶、损人利己的败类。
一连数日,溃军的一股股队伍,纷纷穿过这座城市。
那根本不算队伍,完全是散兵游勇。
那些人胡子拉碴,又长又脏,军装也破烂不堪,既没有军旗,又不成为团队,只是拖着脚步朝前走。
他们都显得神情沮丧、筋疲力尽,再也不能想什么,再也不能拿什么主意了,仅仅凭习惯机械地移动脚步,一站住就会累趴下了。
他们大多是应征入伍的性情平和的人、安分度日的年金领取者,一个个都被枪支压弯了腰,还有年轻而敏捷的国民别动队员,他们容易惊慌失措,又能立刻斗志昂扬,他们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也随时准备溃退逃跑。
此外,他们中间还零星夹杂着穿红色军裤的士兵,那是一次大型战役中被击垮的师团的残部。
身穿深色军装的炮兵,同各种步兵排列在一起。
有时也能看见一名龙骑兵的闪亮的头盔,他拖着沉重的步子,跟随脚步比较轻快的步兵,显得十分吃力。
随后,游击队也一批批穿城而过,每队都起了英勇的称号,诸如“败军复仇队”“坟墓公民团”“敢死队”等等,不过,他们的样子倒像土匪。
他们的官长,也都是从前的布商或粮商、油脂商或肥皂商,临时充当军人,因为钱多或者胡子长,就被任命为军官,全身披挂着武器、法兰绒绶带和军衔。
他们讲话声如洪钟,经常讨论作战方案,大言不惭,自以为肩负着危难的法国的命运。
初中名著导读《羊脂球》课件

母亲——莫泊桑的母亲热爱文学,努力指导儿子阅读和 写作,是他创作上的第一个老师。 中学老师——他中学的老师路易布耶观察到他的作文中 闪烁着天才的火花,于是孜孜不倦地教导这位年轻人。 福楼拜——19世纪70年代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准备阶段, 他的舅父和母亲的好友、著名作家福楼拜是他的文学导 师。中学毕业以后,著名作家福楼拜正式收他为徒,成 为他文学上的导师。这位严厉而苛刻的老师严格地要求 莫泊桑,对他的创作起到了极大影响。 屠格涅夫——以后莫泊桑又把旅居法国的屠格涅夫尊为 老师,虚心向他学习。
长篇小说
他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一生》(1883)、 《俊友》(1885)、《温泉》(1886)、《皮 埃尔和若望》(1887)、《像死一般坚强》 (1889)、《我们的心》(1890)。这些作品 揭露了第三共和国的黑暗内幕:内阁要员从金 融巨头的利益出发,欺骗议会和民众,发动掠 夺非洲殖民地摩洛哥的帝国主义战争;抨击了 统治集团的腐朽、贪婪、尔虞我诈的荒淫无耻。
评价
“他是19世级末法国文坛史上最卓越的天 才。” ——屠格涅夫 “他的作品无限地丰富多彩,无不精彩 绝伦,令人叹为观止。” ——左拉
小说题材
普法战争
小职员
乡村生活
普法战争
《羊脂球》、《菲菲小姐》、《女疯子》、 《俘虏》 、《瓦尔特· 施那夫斯奇遇记》、 《米隆老爹》、《一场决斗》、 《索瓦热老婆婆》、《两个朋友》等。
普法战争
《瓦尔特· 施那夫斯的奇遇》反映了敌军士兵 为了活着宁可当俘虏的厌战情绪; 《俘虏》描写的是法国妇女机智擒敌的故事。 其中内容最丰富、意义最深刻的作品,则是莫 泊桑的成名作《羊脂球》。
小职员
《羊脂球》讲解

《羊脂球》讲解《羊脂球》是中国古代文学名著《红楼梦》中的一个独立篇章,由曹雪芹所创作。
本文将对《羊脂球》进行详细讲解,包括篇章主题、情节发展、人物形象以及反映的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篇章主题及情节简介《羊脂球》是《红楼梦》第十一回的篇章,主要以贾府中宴会闲闲文娱的过程为主线,展现了贾府中众多人物的性格特点以及社交场景的细节描写。
此篇章亦可视作整个小说的微缩世界,具有一定的独立完整性。
故事发生在贾府中的春园,贾府的嫡系子弟及一些贵族子弟聚集在此举行宴会。
贾环通过唱羊脂球引起他人的注意,并借此机会向他人展示自己的才艺。
贾环的表演引发了其他人的热情参与,最终形成了一场宴会上的盛大娱乐活动。
二、人物形象塑造1. 贾环:贾环是贾府中的嫡系子弟,年幼聪慧,才艺出众。
他以唱羊脂球为媒介,展示了自己的音乐才华和灵动的性格,赢得了他人的赞赏。
2. 参与者:其他参加宴会的人物包括贾宝玉、贾政等贵族子弟及贾府的仆人等。
他们或是陪衬贾环表演,或是通过欣赏别人的表演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通过他们的参与,展示出各自的性格特点和家庭背景。
三、文化内涵《羊脂球》反映了中国古代贵族社会的文化特点和生活方式。
在宴会过程中,人们以音乐、歌舞等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和生活态度。
此外,文中还描绘了贵族子弟在家族内部的地位和社交交往的方式。
此外,《羊脂球》中的“羊脂”二字所象征的是一种高雅、浪漫的情感。
表演者以此为主题,表达了各自内心的梦幻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通过这一小节的讲述,曹雪芹将人物心理及社交场景展现得淋漓尽致。
四、文字描写及语言运用曹雪芹在《羊脂球》中运用了大量细腻的描写,通过对人物表情、动作、语言以及音乐声的描绘,展现了各种情感和情绪的流露。
例如,曹雪芹描写贾环的表演手法:“娇声振霄汉,细乐飞云里。
银瓶清早天气凉……”。
通过这些精彩的描写,读者能够感受到整个宴会过程的热烈气氛和各人的激情投入。
另外,曹雪芹在文中运用了大量的意象和象征手法,形象地描绘了贾环的才艺和个性特点。
羊脂球简介_莫泊桑名著《羊脂球》内容简介

羊脂球简介_莫泊桑名著《羊脂球》内容简介世界名著羊脂球简介:《羊脂球》是法国作家莫泊桑创作的短篇小说。
《羊脂球》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羊脂球》以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为背景。
通过代表当时法国社会各阶层的10个人同乘一辆马车逃往一个港口的故事,形象地反映出资产阶级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卑鄙自私和出卖人民的丑恶嘴脸。
在小说中,作者把下等人和上等人作了对比,检验了他们的道德水准。
羊脂球是一个有爱国心的妓女,10人当中只有羊脂球配得上称为高尚的人和有爱国心的人。
她心地善良,在马车上,尽管那些贵族资产阶级老爷太太对她表示了轻视和侮辱,可是当他们饥饿难耐的时候,羊脂球慷慨地请他们分享自己的食物。
她还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而那些所谓上等人都是些灵魂丑恶、损人利己的败类。
羊脂球内容简介: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普鲁士军队攻占了鲁昂城,有十个人同坐一辆马车出逃。
这十个人的身份很是特殊,分别是臭名昭著的奸商鸟先生和他的太太;大资产阶级、省议会议员卡雷·拉马东夫妇;省议会议员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夫妇;两个修女;民主党人科尔尼代和一个绰号叫“羊脂球”的妓女。
前面三对夫妇离开鲁昂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计划和目的却是一致的—这三对夫妇都不会回鲁昂了。
十个人中最没有地位的是“羊脂球”。
在马车上,几位有身份的阔太太得知了羊脂球身份后,对羊脂球的态度很是恶劣,她们悄声辱骂羊脂球是卖淫妇、是婊子、是社会的耻辱。
而这些阔太太的丈夫们则用一种看不起穷人的口吻大谈特谈金钱、吃喝。
马车在路上颠簸了大半天的光景,车上所有的人都饿了,只有羊脂球带了可供自己三天的食物。
羊脂球很大方地邀请车上所有的人都来分享她的食物,完全不计较先前这些有钱人对自己的不敬。
很快篮子里的食物都被瓜分光了,人们都摆脱了饥饿的困扰,于是人们对羊脂球的态度像肚子一样发生了变化。
先前的蔑视变成了亲昵,辱骂也变成了夸奖。
马车继续前行来到了托特镇,这里也被普鲁士军队侵占了,普鲁士军官扣下了马车,提出要羊脂球陪自己过夜。
羊脂球简介

羊脂球的常见食用方法
01
羊脂球的直接食用
• 将熟透的羊脂球从模具中取出,直接食用
• 外酥里嫩的口感,令人回味无穷
02
羊脂球作为主菜搭配其他食材
• 将羊脂球搭配蔬菜、土豆等食材烹制,形成丰富的口感
和层次
• 羊脂球还可与其他肉类、海鲜等食材搭配,制作成各种
美味佳肴
03
羊脂球作为点心或小吃食用
• 将羊脂球切成小块,搭配面包、葡萄酒等食材,作为点
• 羊脂球的制作工艺和原料可用于生产各种方便食品和冷冻食品
• 羊脂球还可以作为糕点、饼干等食品的原料,增加食品的口感和风味
羊脂球在现代食品加工中的拓展
• 一些食品企业通过研发新的羊脂球产品,拓展了市场
• 羊脂球逐渐成为现代食品加工中的一种热销原料
THANK 看
CREATE TOGETHER
DOCS
心或小吃食用
• 羊脂球的味道和口感,为休闲时光增添了一份美味和惬
意
羊脂球在不同地区的食用习俗
法国的羊脂球食用习俗
• 法国人通常将羊脂球作为家庭聚餐或朋友聚会时的美食
• 还可将羊脂球作为圣诞、新年等节日的特色菜肴
其他地区的羊脂球食用习俗
• 在德国、荷兰等国家,羊脂球也被视为一种美味佳肴
• 一些地区还将羊脂球与当地的特色食材结合,形成独特的食用习俗
羊脂球在餐饮业中的地位
• 羊脂球作为法国餐饮文化的一部分,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餐厅和餐馆
• 羊脂球成为法国餐厅的招牌菜和特色菜
羊脂球与餐饮业的发展
• 羊脂球的成功为餐饮业带来了商机和竞争力
• 一些餐厅和厨师通过创新羊脂球的制作工艺和原料,吸引了更多顾客
羊脂球在现代食品加工中的应用与拓展
羊脂球指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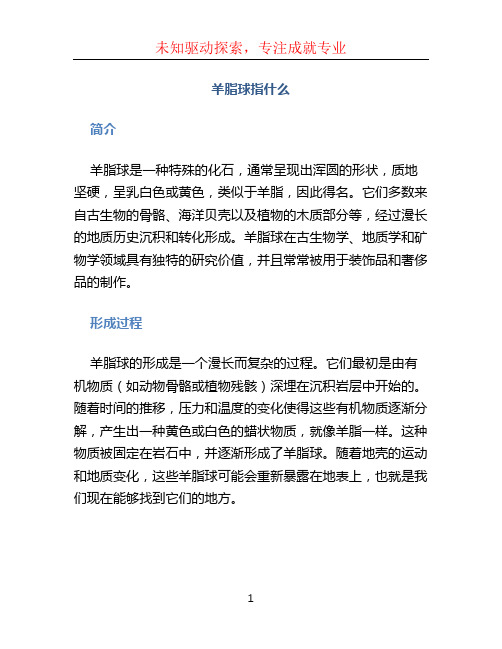
羊脂球指什么简介羊脂球是一种特殊的化石,通常呈现出浑圆的形状,质地坚硬,呈乳白色或黄色,类似于羊脂,因此得名。
它们多数来自古生物的骨骼、海洋贝壳以及植物的木质部分等,经过漫长的地质历史沉积和转化形成。
羊脂球在古生物学、地质学和矿物学领域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并且常常被用于装饰品和奢侈品的制作。
形成过程羊脂球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它们最初是由有机物质(如动物骨骼或植物残骸)深埋在沉积岩层中开始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压力和温度的变化使得这些有机物质逐渐分解,产生出一种黄色或白色的蜡状物质,就像羊脂一样。
这种物质被固定在岩石中,并逐渐形成了羊脂球。
随着地壳的运动和地质变化,这些羊脂球可能会重新暴露在地表上,也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找到它们的地方。
种类和特征羊脂球的种类和特征多种多样,取决于其原始来源和形成环境。
根据化石学家的研究,我们可以区分出以下几种常见的羊脂球:1.动物羊脂球:这种羊脂球主要由古代动物骨骼中的蜡状物质组成,如恐龙骨骼、海洋生物贝壳等。
它们通常呈浑圆形状,表面光滑,质地较硬。
2.植物羊脂球:这种羊脂球主要由古代植物的木质部分形成,例如树木的树脂和树脂等。
植物羊脂球的形状和质地与动物羊脂球相似,但在组织结构上可能有所不同。
3.矿物羊脂球:与动植物羊脂球不同,这种羊脂球主要由矿物质形成,如硫化物、石膏等。
矿物羊脂球的质地可能较硬,呈现出更多种类的颜色。
不同类型的羊脂球都有其独特的形态和物理特性,这使得它们成为科学研究和收藏中的重要对象。
科学研究的意义羊脂球在古生物学、地质学和矿物学领域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
首先,利用羊脂球可以推断出地质历史和古生态环境。
通过对羊脂球中的有机物分析,科学家们可以了解古代动物和植物的生态系统,进而揭示地球生物演化的过程和模式。
其次,羊脂球可以提供有关地质过程和岩石变化的信息。
羊脂球的出现和分布可以指示出地质构造活动和沉积环境变化。
此外,羊脂球的形成也与地下水活动、岩石风化和热液活动等地质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羊脂球指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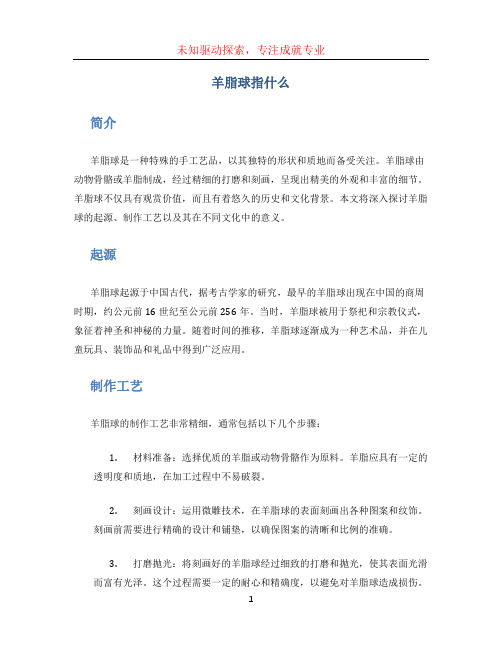
羊脂球指什么简介羊脂球是一种特殊的手工艺品,以其独特的形状和质地而备受关注。
羊脂球由动物骨骼或羊脂制成,经过精细的打磨和刻画,呈现出精美的外观和丰富的细节。
羊脂球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而且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本文将深入探讨羊脂球的起源、制作工艺以及其在不同文化中的意义。
起源羊脂球起源于中国古代,据考古学家的研究,最早的羊脂球出现在中国的商周时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256年。
当时,羊脂球被用于祭祀和宗教仪式,象征着神圣和神秘的力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羊脂球逐渐成为一种艺术品,并在儿童玩具、装饰品和礼品中得到广泛应用。
制作工艺羊脂球的制作工艺非常精细,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步骤:1.材料准备:选择优质的羊脂或动物骨骼作为原料。
羊脂应具有一定的透明度和质地,在加工过程中不易破裂。
2.刻画设计:运用微雕技术,在羊脂球的表面刻画出各种图案和纹饰。
刻画前需要进行精确的设计和铺垫,以确保图案的清晰和比例的准确。
3.打磨抛光:将刻画好的羊脂球经过细致的打磨和抛光,使其表面光滑而富有光泽。
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耐心和精确度,以避免对羊脂球造成损伤。
4.雕刻装饰:根据需要,可以在羊脂球上进行进一步的雕刻和装饰。
这些装饰品可以是珍贵的宝石、金属或其他材料制成。
文化意义羊脂球在不同文化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和象征。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文化意义:1.祈福和保平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羊脂球被视为吉祥物和祈福的象征。
人们相信通过佩戴或收藏羊脂球,可以获得平安和幸福。
2.祭祀和宗教仪式:古代的羊脂球经常被用于祭祀和宗教仪式中,象征着神圣的力量和神秘的宇宙。
3.艺术和收藏:羊脂球作为一种精细的手工艺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许多艺术家和收藏家都对羊脂球情有独钟,将其视为一种珍贵的艺术品。
4.民俗文化传承:羊脂球在一些地方被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下来并流传至今。
通过羊脂球的制作和传承,人们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独特性。
结论羊脂球作为一种精美的手工艺品,展示了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
羊脂球指的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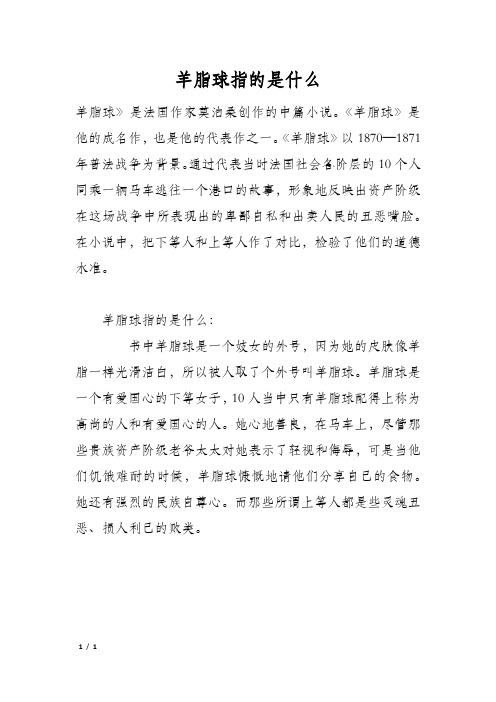
羊脂球指的是什么
羊脂球》是法国作家莫泊桑创作的中篇小说。
《羊脂球》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羊脂球》以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为背景。
通过代表当时法国社会各阶层的10个人同乘一辆马车逃往一个港口的故事,形象地反映出资产阶级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卑鄙自私和出卖人民的丑恶嘴脸。
在小说中,把下等人和上等人作了对比,检验了他们的道德水准。
羊脂球指的是什么:
书中羊脂球是一个妓女的外号,因为她的皮肤像羊脂一样光滑洁白,所以被人取了个外号叫羊脂球。
羊脂球是一个有爱国心的下等女子,10人当中只有羊脂球配得上称为高尚的人和有爱国心的人。
她心地善良,在马车上,尽管那些贵族资产阶级老爷太太对她表示了轻视和侮辱,可是当他们饥饿难耐的时候,羊脂球慷慨地请他们分享自己的食物。
她还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而那些所谓上等人都是些灵魂丑恶、损人利己的败类。
1/ 1。
羊脂球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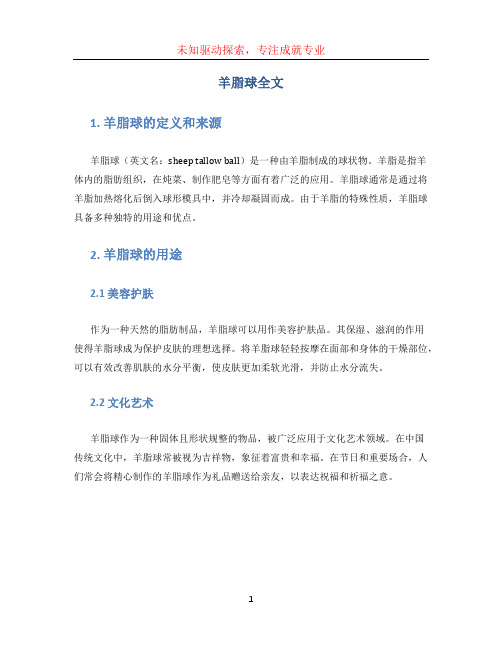
羊脂球全文1. 羊脂球的定义和来源羊脂球(英文名:sheep tallow ball)是一种由羊脂制成的球状物。
羊脂是指羊体内的脂肪组织,在炖菜、制作肥皂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
羊脂球通常是通过将羊脂加热熔化后倒入球形模具中,并冷却凝固而成。
由于羊脂的特殊性质,羊脂球具备多种独特的用途和优点。
2. 羊脂球的用途2.1 美容护肤作为一种天然的脂肪制品,羊脂球可以用作美容护肤品。
其保湿、滋润的作用使得羊脂球成为保护皮肤的理想选择。
将羊脂球轻轻按摩在面部和身体的干燥部位,可以有效改善肌肤的水分平衡,使皮肤更加柔软光滑,并防止水分流失。
2.2 文化艺术羊脂球作为一种固体且形状规整的物品,被广泛应用于文化艺术领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羊脂球常被视为吉祥物,象征着富贵和幸福。
在节日和重要场合,人们常会将精心制作的羊脂球作为礼品赠送给亲友,以表达祝福和祈福之意。
2.3 环境保护羊脂球可以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的替代品,用于代替传统的化石能源。
羊脂中含有丰富的油脂成分,可以通过加工提取燃料。
与化石能源相比,羊脂球的燃烧更为环保,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较低,并且不会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3. 羊脂球的制作过程3.1 原材料准备制作羊脂球的原材料主要是羊脂,可以通过宰杀羊只获得。
需要注意的是,羊脂应选择新鲜且无污染的部位。
3.2 脂肪提取将羊脂放入容器中,加热至完全熔化。
可以使用炉具或微波炉等加热设备。
待羊脂完全熔化后,使用滤网或纱布等过滤器将脂肪中的杂质过滤掉。
3.3 倒入模具将熔化的羊脂慢慢倒入球形模具中,确保填满模具。
注意不要倒入过热的羊脂,以免烫伤。
倒入后,等待羊脂自然冷却凝固。
3.4 完善球体如果羊脂球表面有凹凸不平的地方,可以使用热水浸泡之后用手轻轻抹平。
这样可以使得羊脂球的外观更加光滑。
3.5 保养制作好的羊脂球可以用于美容护肤或展示。
在存放和使用过程中,应避免直接阳光照射和高温存放,以免影响球体的形状和质量。
羊脂球

羊脂球《羊脂球》是法国作家莫泊桑创作的中篇小说。
《羊脂球》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羊脂球》以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为背景。
通过代表当时法国社会各阶层的10个人同乘一辆马车逃往一个港口的故事,形象地反映出资产阶级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卑鄙自私和出卖人民的丑恶嘴脸。
在小说中,作者把下等人和上等人作了对比,检验了他们的道德水准。
羊脂球是一个有爱国心的妓女,10人当中只有羊脂球配得上称为高尚的人和有爱国心的人。
她心地善良,在马车上,尽管那些贵族资产阶级老爷太太对她表示了轻视和侮辱,可是当他们饥饿难耐的时候,羊脂球慷慨地请他们分享自己的食物。
她还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而那些所谓上等人都是些灵魂丑恶、损人利己的败类。
作者的创作主旨在于,揭露普鲁士侵略者的残暴与野蛮,法国军队的腐败与无能,尤其是强烈地谴责那些逼迫别人做不道德的事,然后又用道德去指责人的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的自私与伪善,张扬下层人士极具爱国精神、极富正义感和同情心的美好心灵,表达对被凌辱的底层人们的同情与尊敬。
《羊脂球》的篇幅短小,不到三万字。
但在这短短的篇幅里,莫泊桑却把普鲁士侵略者的残暴无耻、法国军队的腐败无能以及法国各阶层的精神面貌和爱国思想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故事发生在一辆马车里,在这个狭窄有限的空间里,法国社会的政界、商界、教会以及社会底层的代表都集中在了一起。
莫泊桑把这些人物放在特定的环境中,通过这些人在逃亡路上的不同表现,对法国人在普法战争中的态度以及民族精神进行了生动的展示,其好恶之情溢于言表。
《羊脂球》发表后,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让人同情。
在读者眼中,羊脂球成为了一只集体性暴力残害下的无辜羔羊。
虽然,用暴力迫害羊脂球的集体有很多“合情合法”的理由,但在具有全知全能视角的读者看来,这些理由都是对羊脂球的欺骗。
作品打动读者的关键点就在于无辜的人受到伤害,而真正的凶手却逃脱了惩罚,成为胜利者。
羊脂球

年首次出版,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
作品以普法战争为背景,描写了主人公羊脂球和诸位高贵者在面对普鲁士军官无礼要求时的不同举动和态度,反衬鲜明,悬念迭生,引人入胜;写出了法国各阶层在占领者面前的不同姿态,揭露了贵族资产阶级的自私、虚伪和无耻,赞扬了羊脂球的牺牲精神。
内容简介:坐一辆马车出逃。
这十个人的身份很是特殊,分别是臭名昭著的奸代和一个绰号叫“羊脂球”的妓女。
前面三对夫妇离开鲁昂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计划和目的却是一致的—这三对夫妇都不会回鲁昂了。
十个人中最没有地位的是“羊脂球”。
在马车上,几位有身份的阔太太得知了羊脂球身份后,对羊脂球的态度很是恶劣,她们悄声辱骂羊脂球是卖淫妇、是婊子、是社会的耻辱。
而这些阔太太的丈夫们则用一种看不起穷人的口吻大谈特谈金钱、吃喝。
马车在路上颠簸了大半天的光景,车上所有的人都饿了,只有羊脂球带了可供自己三天的食物。
羊脂球很大方地邀请车上所有的人都来分享她的食物,完全不计较先前这些有钱人对自己的不敬。
很快篮子里的食物都被瓜分光了,人们都摆脱了饥饿的困扰,于是人们对羊脂球的态度像肚子一样发生了变化。
先前的蔑视变成了亲昵,辱骂也变成了夸奖。
马车继续前行来到了托特镇,这里也被普鲁士军队侵占了,普鲁士军官扣下了马车,提出要羊脂球陪自己过夜。
羊脂球面对侵略者的无耻要求断然拒绝了,于是同行的一车人都扣留了下来。
除了羊脂球外其余的人都急坏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九个人想尽了办法、施展了种种阴谋想迫使羊脂球就范。
最后还是老修女的“只要用意是好的,做任何事情都不会触怒天主”的宗教说教产生了相当好的效果,羊脂球为了大家的利益牺牲了自己。
普鲁士军官的淫欲得到了满足,第二天就放行了。
但大家非但不感激这位可怜的姑娘,反而还避而远之,之前的赞美和亲近又变成了最初的鄙视和唾弃。
这一次,大家各自准备了丰富的食物.唯独羊脂球没有来得及准备。
马车继续前行,车上的人拿出了自己的食物大口地嚼着,只有羊脂球缩在车的角落里受冻挨饿,在科尔尼代的“马赛曲”中呜咽。
羊脂球_精品文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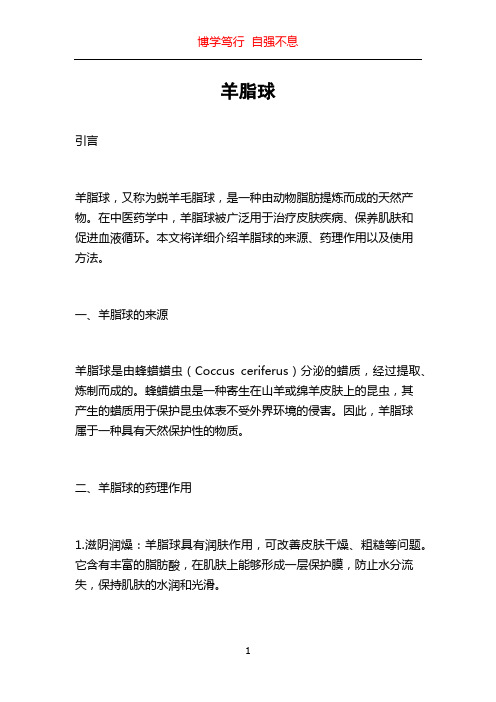
羊脂球引言羊脂球,又称为蜕羊毛脂球,是一种由动物脂肪提炼而成的天然产物。
在中医药学中,羊脂球被广泛用于治疗皮肤疾病、保养肌肤和促进血液循环。
本文将详细介绍羊脂球的来源、药理作用以及使用方法。
一、羊脂球的来源羊脂球是由蜂蜡蜡虫(Coccus ceriferus)分泌的蜡质,经过提取、炼制而成的。
蜂蜡蜡虫是一种寄生在山羊或绵羊皮肤上的昆虫,其产生的蜡质用于保护昆虫体表不受外界环境的侵害。
因此,羊脂球属于一种具有天然保护性的物质。
二、羊脂球的药理作用1.滋阴润燥:羊脂球具有润肤作用,可改善皮肤干燥、粗糙等问题。
它含有丰富的脂肪酸,在肌肤上能够形成一层保护膜,防止水分流失,保持肌肤的水润和光滑。
2.皮肤护理:羊脂球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可以滋养皮肤,改善皮肤质量。
它具有温和的镇静作用,可缓解皮肤敏感、红肿等症状。
3.促进血液循环:羊脂球可通过温热作用促进皮肤的微循环,增加皮肤的供氧和养分供应。
这对于改善肤色暗沉、毛细血管扩张等问题非常有效。
三、羊脂球的使用方法1.面部补水:将适量的羊脂球溶化后,涂抹在洁净的脸部肌肤上,轻轻按摩至吸收。
可在早晚各使用一次,能够为肌肤提供持久保湿。
2.手部护理:在清洁完双手后,取适量的羊脂球擦拭在手背和手指间,轻轻按摩至吸收。
它可滋养干燥的手部皮肤,防止龟裂和粗糙。
3.身体滋润:将羊脂球溶化后,均匀涂抹在身体干燥的部位,如手肘、膝盖等。
它能够改善皮肤干燥,保持皮肤的弹性和光滑。
四、注意事项1.避免过量使用:尽管羊脂球是天然的,但过量使用可能导致油腻感和毛孔阻塞。
建议根据个人的皮肤状况和需要适量使用。
2.避免敏感肌肤:对于敏感肌肤或容易过敏的人士,使用前应进行皮肤测试,确保不引发过敏反应。
3.存储注意:羊脂球应存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和高温。
同时,要尽量避免羊脂球受到空气的污染,以确保其功效。
结论羊脂球作为一种天然的皮肤保养品,具有多种药理作用,包括滋阴润燥、皮肤护理和促进血液循环。
羊脂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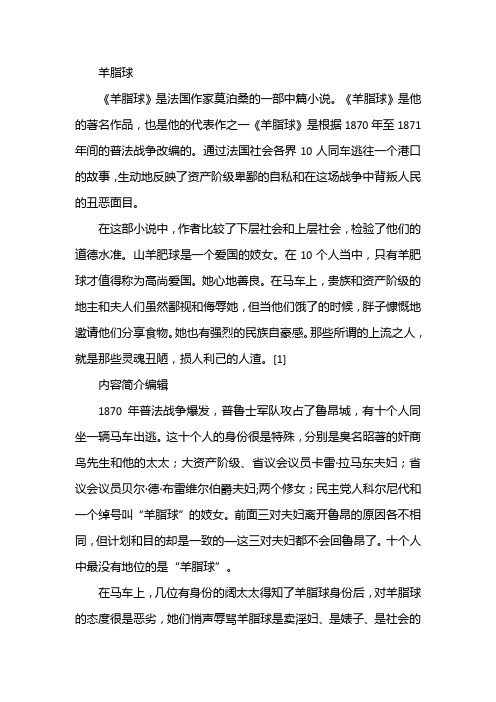
羊脂球《羊脂球》是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一部中篇小说。
《羊脂球》是他的著名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羊脂球》是根据1870年至1871年间的普法战争改编的。
通过法国社会各界10人同车逃往一个港口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卑鄙的自私和在这场战争中背叛人民的丑恶面目。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比较了下层社会和上层社会,检验了他们的道德水准。
山羊肥球是一个爱国的妓女。
在10个人当中,只有羊肥球才值得称为高尚爱国。
她心地善良。
在马车上,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地主和夫人们虽然鄙视和侮辱她,但当他们饿了的时候,胖子慷慨地邀请他们分享食物。
她也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那些所谓的上流之人,就是那些灵魂丑陋,损人利己的人渣。
[1]内容简介编辑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普鲁士军队攻占了鲁昂城,有十个人同坐一辆马车出逃。
这十个人的身份很是特殊,分别是臭名昭著的奸商鸟先生和他的太太;大资产阶级、省议会议员卡雷·拉马东夫妇;省议会议员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夫妇;两个修女;民主党人科尔尼代和一个绰号叫“羊脂球”的妓女。
前面三对夫妇离开鲁昂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计划和目的却是一致的—这三对夫妇都不会回鲁昂了。
十个人中最没有地位的是“羊脂球”。
在马车上,几位有身份的阔太太得知了羊脂球身份后,对羊脂球的态度很是恶劣,她们悄声辱骂羊脂球是卖淫妇、是婊子、是社会的耻辱。
而这些阔太太的丈夫们则用一种看不起穷人的口吻大谈特谈金钱、吃喝。
马车在路上颠簸了大半天的光景,车上所有的人都饿了,只有羊脂球带了可供自己三天的食物。
羊脂球很大方地邀请车上所有的人都来分享她的食物,完全不计较先前这些有钱人对自己的不敬。
很快篮子里的食物都被瓜分光了,人们都摆脱了饥饿的困扰,于是人们对羊脂球的态度像肚子一样发生了变化。
先前的蔑视变成了亲昵,辱骂也变成了夸奖。
马车继续前行来到了托特镇,这里也被普鲁士军队侵占了,普鲁士军官扣下了马车,提出要羊脂球陪自己过夜。
羊脂球

羊脂球“《羊脂球》”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莫帕桑(Maupassant)的经典小说之一。
莫帕桑(Maupassant)与俄罗斯的契kh夫(Chekhov)和美国的奥亨利(O'Henry)一样著名。
喜欢写作的人都知道,短篇小说比小说更难控制,因为篇幅有限,写得好也不容易。
莫帕桑(Maupassant)熟悉这种类型,他的其他书籍也很出名,例如项链和美丽的朋友。
“《羊脂球》”已被多次转载,这使人们感到难过。
在普鲁士战争中,法国成为失败者。
傲慢的法国人终于放下了高尚的头,屈服于普鲁士士兵。
他们不得不在家里招待普鲁士士兵,但是当他们离开家时,他们装作高贵而和平。
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法国人似乎很听话,但他们仍然私下起誓。
他们认为普鲁士士兵很庸俗,从内心看不起普鲁士人。
但是,他们的行动严重不一致,这总是使人们感到法国人远不如战斗国,而俄罗斯人却是血腥的。
看着斯大林格勒战役,他们宁愿死也不愿投降,勇者必胜。
在《羊脂球》一书中,十个人赶到了总参谋部,匆匆离开失败地区。
那里有贵族,商人,政客,修女,女士,还有我们的女主人公,这是一位著名的社交情妇,也是情妇。
起初,其他人觉得他们比社交花贵得多,并且特别不喜欢舞会。
但最后,由于途中有暴风雪,因此很难长时间旅行。
这些所谓的贵族急忙出去,还没准备好吃饭。
他们都饿了。
当社交之花“《羊脂球》”拿出丰盛的食物与大家分享时,他们奋斗了好几次,终于全心全意地接受了食物。
可以看出,食物对人们来说是最重要的,而面孔远没有食物重要。
最后,高于别人的人也放下了自己的胸膛,与社会花坛对话,并及时表达了对她爱国主义的赞赏。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的梁宏宇。
她有着相似的背景并且是如此的血腥。
因此,每一个坚持正义的宰狗一代都是社会底层的人们。
也许他们对这个国家崩溃的痛苦感到更深刻。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突然,厂长的妻子面如土色,双眼紧闭,晕了过去。她丈夫大叫帮忙,其他乘客都惊慌失措。年长的修女端起羊脂球的杯子,放到那女人的嘴边,喂了她几滴葡萄酒。
贵妇人睁开了眼睛,表达了感激之情,说自己没事了。
“不打紧,”修女说,“全是给饿的。”
羊脂球好几次弯下腰,好像要从她的衬裙下面取什么东西似的,但每次她都迟疑了一下,又坐直了身子。约莫3点钟,马车行至荒无人烟的平原上,她又躬身,这次从座位下拖出一只大篮子,上面盖着餐巾。
她先从里面取出一只陶制的小盘子;然后拿出一个精致的银杯;最后才端出一只大碟子,里面装着两只切好的裹着果冻的子鸡。在篮子里还可看到其他的好东西——馅饼、水果、美味的食物,甚至还有酒,看上去足够三天的旅行所需。
碰巧所有的女人都坐在同一边。伯爵夫人旁坐着两个修女:老的满脸都是大麻子,她的同伴则身材矮小,一脸病容,看上去甚至像得了痨病似的。不过看样子她们都对宗教很虔诚。
两个修女的对面坐着一男一女。男的叫高尼岱,他以放荡成性且政治理想狂妄而广为人知。本来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相当可观的财产,但却把钱浪费在喝酒和毫无用处的理想上。现在他异想天开,认为自己在阿弗尔会被重用,那里需要他的帮助。
《羊脂球》是有“短篇小说大师”之称的法国作家莫泊桑先生创作的小说,。《羊脂球》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故事以羊脂球的悲惨遭遇反衬了资本主义下的丑恶肮脏的灵魂。他们虚伪的面具下藏的都是腐朽的内脏和污秽的思想。
清晨4点半钟,天还黑蒙蒙的。旅客们早已聚在诺曼底旅馆的院子里,一个个冷得直哆嗦。
他们惊魂失魄地坐在车里时,马车夫提着的灯照着他们的脸。他身旁站有一个德国军官,此人头发金黄、身材高挑、极为瘦削,还戴着一顶平顶军帽,看上去就像英国旅馆里的侍者。他操着阿尔萨斯的法语腔说道:
“女士们,先生们,请下车吧。”
对他们来说别无选择,只好听从。军官带着他们来到旅馆的大厨房,要他们拿出准许他们离开的证件,并对他们进行了仔细地检查。末了,他说了句“好的”,便进了另一间屋子。
他们想找家路边的小客栈,但连最简陋的酒馆的影子也见不着。他们渐感饥饿,心情亦变得沮丧起来,因为身边没带一点吃的。偶尔在路旁碰到一些农夫,这些男人便想方设法向他们索取食物,但他们连光是面包都没得到。
将近1点钟,他们觉得越来越饿,闲话也不说了,人人都饿得发慌。
“我觉得真难受,”伯爵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得带点食物?”
伯爵夫人紧紧握住她的手。
“我们十二万分地感谢你,”她说。
羊脂球走了之后,他们都想猜出为何要叫她去;他们都在想如果轮到自己被叫去该怎么说。
10分钟后,羊脂球回来了,脸色因激忿而涨得通红。她怒气冲天,几乎窒息过去。她喘着直喊,“猪!下流坯!”没有人知道她为何如此气愤。
第二天早晨,这群人聚在厨房,但原定8点钟出发的马车仍旧停在院子里,毫无动身的迹象。
这些贵妇人一认出她,便开始窃窃私语。不一会儿,“娼妇”和“不要脸”之类的字眼便清晰可闻,并引起了这位可怜妇人的注意。
她抬起头,用挑衅的目光盯着她们,使得她们埋下头,没有作声。一贯对女色敏感的罗瓦索先生,好奇地偷偷瞟了她几眼。
然而,这三个贵妇人很快就被有夫之妇对共同对手的同声相应所鼓舞,重新开始交谈。另一方面,那三个做丈夫的,则踌躇满志地谈论着钱财,并以轻蔑的口吻议论比他们穷的人。
所有的乘客都祝贺她的成功。他们高度称赞她的勇气。然而,篮子很快就变空了,这十个饥肠辘辘的人把所有的食物一扫而光。他们又说了一会儿话,但东西已吃完,话说起来就没那么流畅了。
黑夜逐渐降临,马车内的光线越发暗淡。羊脂球冷得直发抖,德布雷维尔夫人把自己的暖足器给了她。卡雷?拉马东夫人和罗瓦索夫人也把她们的暖足器给了两个修女。
她看上去很庄重,非常好客,并且传闻她曾是路易?菲利普的一个儿子最喜爱的人,这使得她在当地的贵族圈子里更加受欢迎。她的客厅被认为是当地最好的,被邀去她家是很不容易的。而今只有她的客厅还保持着昔日的高雅情趣。布雷维尔夫妇靠他们所得的不动产,据说能有50万法郎的收入。
这6人是这一行人中最显赫的。他们都很富有,受人尊敬,是社会上很体面的人。
于贝尔伯爵谈到牲畜和庄稼因普鲁士人所遭受的损失,但说话时带着一种对损失毫无所谓的表情。
卡雷?拉马东说自己相当精明,已汇了60万法郎到英国存着;罗瓦索先生则声称在阿弗尔,政府将付给他一大笔钱,这钱是他卖给法军军需部的酒款。
这三个男人会意地相互望了望。虽然社会地位不同,但他们都崇拜金钱。
马车似蜗牛般地缓慢前行,到了10点钟还没有走上10英里。他们本来打算在多特吃午饭,但现在看来傍晚前都不可能到达那里。
罗瓦索先生悄不作声地催促他的老婆也学他们那样。最初她拒绝了,但饥饿感实在太强,难以长久抗拒。她丈夫问羊脂球他能否取一小份给他妻子。
“可以的,当然行,先生,”她答道,满脸欢笑,并递给他那只碟子。
随后有人打开了那瓶波尔多葡萄酒,虽然只有一只杯子,他们还是传着喝,每个轮到的人都把杯子揩一下,惟独高尼岱偏偏把嘴唇放到他美丽旅伴在酒杯上喝过尚未干的地方,以示殷勤。
“我带了我的妻子。”
“我也带了。”
“我也一样。”
马蹄声传了过来,小铃发出的丁当声告诉他们马具正将准备就绪。雪在下着,也夹杂有模糊不清的耳语。
一个提着灯的人出现了,还牵着一匹马。因为另一只手提着灯,只靠一只手调整马具,所以花了他很长的时间。当他准备去牵第二匹马时,才注意到那些旅客正冒着雪无助地站在那里。
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战争,大家谈到普鲁士人所犯的暴行和法国人所表现的英勇。不久他们就谈到了自己。羊脂球像她姊妹中的女人那样,一兴奋起来就口若悬河,她告诉了他们她离开鲁昂的原因。
“起初我想还可呆在那里,但那些普鲁士人实在让我受不了。啊,我要是个男人该多好!我从窗子上看着他们,那些戴着头盔的猪。要不是我的女仆拦住我,我早把桌椅板凳扔到他们身上了。我接到命令供他们一些人的食宿,但我看见第一个人就冲上去掐他的喉咙!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拖倒,打那以后我就只好东躲西藏,并一直寻找机会逃走。现在我就来了。”
他们这才松了一口气。在两个女招待准备晚餐的时候,他们去看了看房间,所有的房间都在一条长廊里。正当他们坐下来准备开饭,旅店老板出现了。
“伊丽莎白?鲁塞小姐在吗?”
羊脂球好像吃了一惊,转身答道:
“找我?”
“小姐,普鲁士军官要立刻与你谈谈。”
“跟我?”
“是的。”
“他或许想找我谈,但我不想跟他谈。”
诱人的食物香味四散,吸引了饥饿的旅客们的注意力。
贵妇们现在对这个风尘女子的蔑视,已上升变成了愤怒。当她们饿得要死时,她还一样样地摆弄食物!她们真想把她给杀了。
罗瓦索先生首先起来得体地应付这种情况。
“天啦!”他说,“夫人,你一直都考虑得很周全。”
羊脂球转身向着他。
“先生,要用一点吗?”她说。“一整天没吃东西是很难受的。”
羊脂球胆怯地望着那四个还空着肚子的高贵的夫人和先生,吞吞吐吐地说:
“唉呀,能让我给……”
她突然停住,怕被断然回绝。罗瓦索先生抓住了这个暗示。
“俗话说得好,我们现在是同舟共济。”他说。“我们得互相帮助。赶快,赶快!女士们,先生们,快接受吧。”
他们都迟疑不决,怕自己成为第一个向空腹低头的人。还是伯爵作了决走。他不失身份地说,“我们以感激之情接受你的提议,夫人。”
“车还没套好吗?”他们中有人问。
“是啊,还没呢。”他的同伴答道。
“好在我们从普鲁士军队那里弄到了离开鲁昂的许可证,”另一个人说。
“我在德国军官中有个熟人。”
“我明白了。”
“你认为我们能在阿弗尔做生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吗?”
“或许可以。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到英国去。不冒点险就会一无所得。”
“你说得对。在鲁昂这个被占领的地方我们只会一事无成。”
挨着他坐的,是一个被称为某一类型的女人,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她那极度肥胖的身段。因长得矮墩墩的,像面团般滚圆丰满,人们便给她取了个诨名:羊脂球,换句话说就是用肥膘做的团子。
不过,她的脸蛋光泽红润,好似那含苞欲放的牡丹;长长的睫毛掩蔽着一对乌黑而深沉的眸子;一张迷人的嘴噘着,不时露出两排小而洁白的玉齿。
这话使得这一行人惊骇不已。每个人都想知道他的用意。伯爵上前对羊脂球说:
“你要考虑好,夫人。你如拒绝可能会招致很大的麻烦,不仅对你不利,也对我们所有的人不利。他找你去,也许是漏了什么并不重要的手续。”
其他人都赞同他的说法,又央求她再考虑大家的处境。最后她说:
“好吧,为了诸位,我按你们的要求办。”
卡雷?拉马东夫人比她丈夫年轻多了。这个娇小玲珑的漂亮妇人,一直是驻扎在鲁昂的出身名门的军官们所注意的对象。裹着皮衣的她,绷着脸望着马车内的一切。
他们的邻座是于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夫妇,他们属于诺曼底最古老最高贵的世家。伯爵天生就酷似亨利四世的相貌,并且还精心打扮极力使这种相似更为明显。
很久以来,这个家族还自以为荣地私下传说,国王曾经与一位德?布雷维尔夫人有一手。国王为报答她的殷勤,还册封她的丈夫为公爵并任命他为省长。天知道,他为什么会娶南特地方一个不起眼的船主的女儿作老婆。
他们在旅馆里到处都找不到车夫,于是就到街上寻找。走到集市,他们看到了很多的普鲁士士兵。其中一个在削洋芋皮;一个在打扫理发店;另一个正对着抱在他手臂里的小孩,低声哼着歌;还有一个在帮老太婆洗衣服;有些士兵正在给乡村妇女劈柴。
这些普鲁士士兵表现出来的如此善行,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有个教堂职员从教堂里出来时,伯爵向他打听普鲁士人的所作所为。
在令人目眩的强光的照耀下,马喘着粗气,浑身是汗,在仿佛是无尽头的雪地上疾驰。马车里一片漆黑,但罗瓦索先生觉得他似曾看见高尼岱从羊脂球身旁跳开,好像是被拒绝了。
终于,在前面的黑暗处出现了些许闪烁着的灯光。那就是多特市。坐了13个小时车的旅程终于快要结束了。他们进城把车停在商业饭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