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吉原野散文在线:发出我们听不到的惊天
鲍尔吉·原野:雨水去过一切地方

鲍尔吉·原野:雨水去过一切地方我觉得树木开始走动。
好多树在雨中穿行。
它们低着头,打着树冠的伞。
雨水去过一切地方□鲍尔吉·原野泥土想起去年的事情雨点瞄着每株青草落下来,因为风吹的原因,它落在别的草上。
别的雨点又落在别的草上。
春雨落在什么东西都没生长的、傻傻的土地上,土地开始复苏,想起了去年的事情。
雨水排着燕子的队形,以燕子的轻盈钻入大地。
这时候,还听不到沙沙的声响,树叶太小,演奏不出沙沙的音乐。
春雨是今年第一次下,边下边回忆。
有些地方下过了,有些地方还干着。
春雨扯动风的透明的帆,把雨水洒到它应该去的一切地方。
春雨继续下起来,无需雷声滚滚,也照样下,春雨不搞这些排场。
它下雨便下雨,不来浓云密布那一套,那都是夏天搞的事情。
春雨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打雷谁不会?打雷干吗?春雨静静地、细密地、清凉地、疏落地、晶亮地、飘洒地下着,下着。
不大也不小,它们趴在玻璃上往屋里看,看屋里需不需要雨水,看到人或坐或卧,过着他们称之为生活的日子。
春雨的水珠看到屋子里没有水,也没有花朵和青草。
春雨飘落的时候伴随歌声,合唱,小调式乐曲,6/8拍子,类似塔吉克音乐。
可惜人耳听不到。
春雨的歌声低于20赫兹。
旋律有如《霍夫曼的故事》里的“船歌”,连贯的旋律拆开重新缝在一起,走两步就有一个起始句。
开始,发展下去,终结又可以开始。
船歌是拿波里船夫唱的情歌小调,荡漾,节奏一直在荡漾。
这些船夫上岸后不会走路了,因为大地不荡漾。
春雨早就明白这些,这不算啥。
春雨时疾时徐、或快或慢地在空气里荡漾。
它并不着急落地。
那么早落地干吗?不如按6/8的节奏荡漾。
塔吉克人没见过海,但也懂得在歌声里荡漾。
6/8不是给腿的节奏,节奏在腰上。
欲进又退,忽而转身,说的不是腿,而是腰。
腰的动作表现在肩上。
如果舞者头戴黑羔皮帽子,上唇留着浓黑带尖的胡子就更好了。
春雨忽然下起来,青草和花都不意外,但人意外。
他们慌张奔跑,在屋檐和树下避雨。
雨持续下着,直到人们从屋檐和树底下走出。
鲍尔吉·原野《朴素原来最有力量》阅读练习及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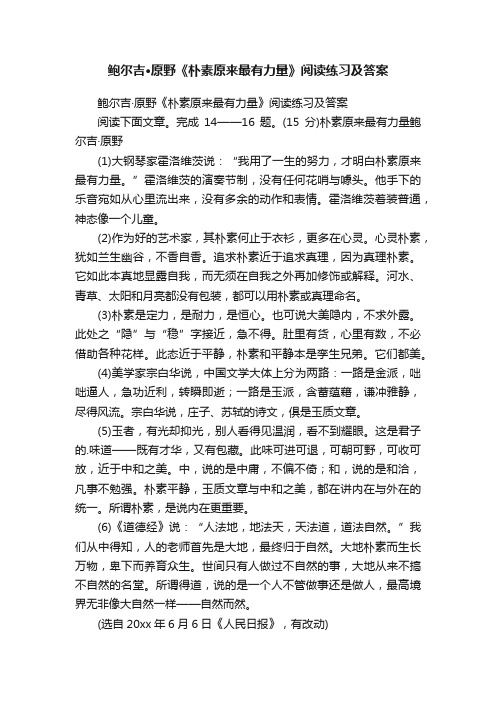
鲍尔吉·原野《朴素原来最有力量》阅读练习及答案鲍尔吉·原野《朴素原来最有力量》阅读练习及答案阅读下面文章。
完成14——16题。
(15分)朴素原来最有力量鲍尔吉·原野(1)大钢琴家霍洛维茨说:“我用了一生的努力,才明白朴素原来最有力量。
”霍洛维茨的演奏节制,没有任何花哨与噱头。
他手下的乐音宛如从心里流出来,没有多余的动作和表情。
霍洛维茨着装普通,神态像一个儿童。
(2)作为好的艺术家,其朴素何止于衣衫,更多在心灵。
心灵朴素,犹如兰生幽谷,不香自香。
追求朴素近于追求真理,因为真理朴素。
它如此本真地显露自我,而无须在自我之外再加修饰或解释。
河水、青草、太阳和月亮都没有包装,都可以用朴素或真理命名。
(3)朴素是定力,是耐力,是恒心。
也可说大美隐内,不求外露。
此处之“隐”与“稳”字接近,急不得。
肚里有货,心里有数,不必借助各种花样。
此态近于平静,朴素和平静本是孪生兄弟。
它们都美。
(4)美学家宗白华说,中国文学大体上分为两路:一路是金派,咄咄逼人,急功近利,转瞬即逝;一路是玉派,含蓄蕴藉,谦冲雅静,尽得风流。
宗白华说,庄子、苏轼的诗文,俱是玉质文章。
(5)玉者,有光却抑光,别人看得见温润,看不到耀眼。
这是君子的.味道——既有才华,又有包藏。
此味可进可退,可朝可野,可收可放,近于中和之美。
中,说的是中庸,不偏不倚;和,说的是和洽,凡事不勉强。
朴素平静,玉质文章与中和之美,都在讲内在与外在的统一。
所谓朴素,是说内在更重要。
(6)《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我们从中得知,人的老师首先是大地,最终归于自然。
大地朴素而生长万物,卑下而养育众生。
世间只有人做过不自然的事,大地从来不搞不自然的名堂。
所谓得道,说的是一个人不管做事还是做人,最高境界无非像大自然一样——自然而然。
(选自20xx年6月6日《人民日报》,有改动)14.下面文段是从原文中抽取出来的,你认为放回哪两段之间最合理,请简述两条理由。
鲍尔吉·原野的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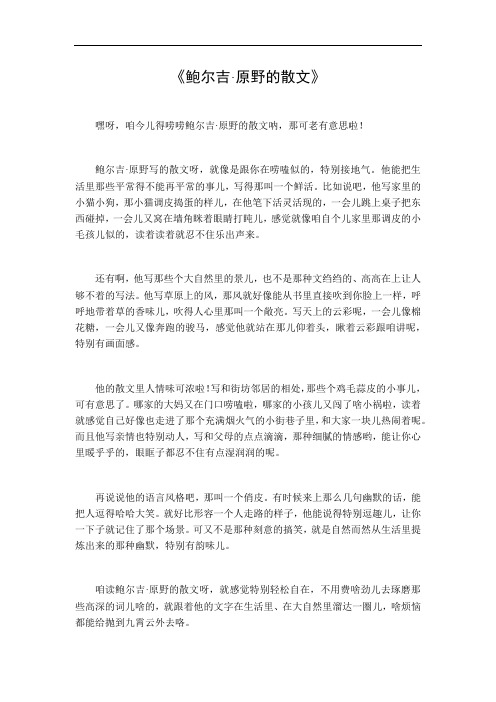
《鲍尔吉·原野的散文》嘿呀,咱今儿得唠唠鲍尔吉·原野的散文呐,那可老有意思啦!鲍尔吉·原野写的散文呀,就像是跟你在唠嗑似的,特别接地气。
他能把生活里那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事儿,写得那叫一个鲜活。
比如说吧,他写家里的小猫小狗,那小猫调皮捣蛋的样儿,在他笔下活灵活现的,一会儿跳上桌子把东西碰掉,一会儿又窝在墙角眯着眼睛打盹儿,感觉就像咱自个儿家里那调皮的小毛孩儿似的,读着读着就忍不住乐出声来。
还有啊,他写那些个大自然里的景儿,也不是那种文绉绉的、高高在上让人够不着的写法。
他写草原上的风,那风就好像能从书里直接吹到你脸上一样,呼呼地带着草的香味儿,吹得人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写天上的云彩呢,一会儿像棉花糖,一会儿又像奔跑的骏马,感觉他就站在那儿仰着头,瞅着云彩跟咱讲呢,特别有画面感。
他的散文里人情味可浓啦!写和街坊邻居的相处,那些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可有意思了。
哪家的大妈又在门口唠嗑啦,哪家的小孩儿又闯了啥小祸啦,读着就感觉自己好像也走进了那个充满烟火气的小街巷子里,和大家一块儿热闹着呢。
而且他写亲情也特别动人,写和父母的点点滴滴,那种细腻的情感哟,能让你心里暖乎乎的,眼眶子都忍不住有点湿润润的呢。
再说说他的语言风格吧,那叫一个俏皮。
有时候来上那么几句幽默的话,能把人逗得哈哈大笑。
就好比形容一个人走路的样子,他能说得特别逗趣儿,让你一下子就记住了那个场景。
可又不是那种刻意的搞笑,就是自然而然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那种幽默,特别有韵味儿。
咱读鲍尔吉·原野的散文呀,就感觉特别轻松自在,不用费啥劲儿去琢磨那些高深的词儿啥的,就跟着他的文字在生活里、在大自然里溜达一圈儿,啥烦恼都能给抛到九霄云外去咯。
我就觉着吧,鲍尔吉·原野的散文那就是生活里的一股清流呀,让咱能在这忙忙碌碌的日子里,停下脚步好好感受感受那些被咱忽略的小美好,那些实实在在的人情味儿。
读他的散文就像是和一个特懂生活的老朋友聊天,可带劲儿啦,反正我是打心眼里喜欢他的这些散文呢!。
美文天下:月光手帕(鲍尔.吉原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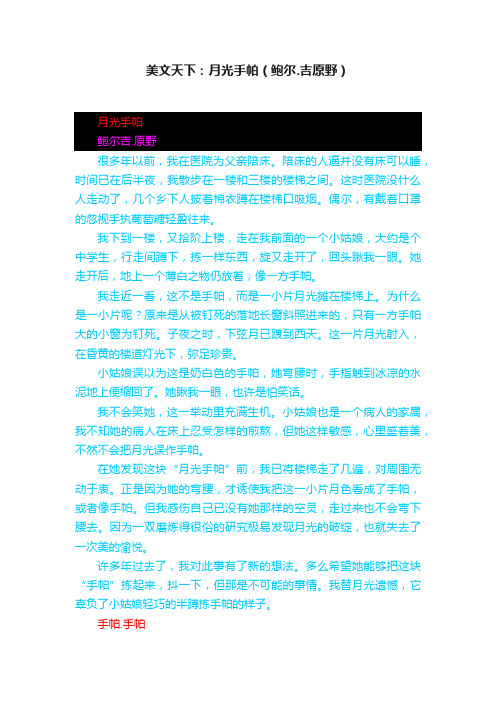
美文天下:月光手帕(鲍尔.吉原野)月光手帕鲍尔吉.原野很多年以前,我在医院为父亲陪床。
陪床的人逼并没有床可以睡,时间已在后半夜,我散步在一楼和三楼的楼梯之间。
这时医院没什么人走动了,几个乡下人披着棉衣蹲在楼梯口吸烟。
偶尔,有戴着口罩的忽视手执葡萄糖轻盈往来。
我下到一楼,又拾阶上楼,走在我前面的一个小姑娘,大约是个中学生,行走间蹲下,拣一样东西,旋又走开了,回头瞅我一眼。
她走开后,地上一个薄白之物仍放着,像一方手帕。
我走近一看,这不是手帕,而是一小片月光摊在楼梯上。
为什么是一小片呢?原来是从被钉死的落地长窗斜照进来的,只有一方手帕大的小窗为钉死。
子夜之时,下弦月已踱到西天。
这一片月光射入,在昏黄的楼道灯光下,弥足珍贵。
小姑娘误以为这是奶白色的手帕,她弯腰时,手指触到冰凉的水泥地上便缩回了。
她瞅我一眼,也许是怕笑话。
我不会笑她,这一举动里充满生机。
小姑娘也是一个病人的家属,我不知她的病人在床上忍受怎样的煎熬,但她这样敏感,心里盛着美,不然不会把月光误作手帕。
在她发现这块“月光手帕”前,我已将楼梯走了几遍,对周围无动于衷。
正是因为她的弯腰,才诱使我把这一小片月色看成了手帕,或者像手帕。
但我感伤自己已没有她那样的空灵,走过来也不会弯下腰去。
因为一双磨炼得很俗的研究极易发现月光的破绽,也就失去了一次美的愉悦。
许多年过去了,我对此事有了新的想法。
多么希望她能够把这块“手帕”拣起来,抖一下,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替月光遗憾,它辜负了小姑娘轻巧的半蹲拣手帕的样子。
手帕.手帕张丽钧一直对鲍尔吉.原野的《月光手帕》怀有一种莫可名状的喜爱。
一个小姑娘,在夜晚的走廊里突然蹲下,去捡拾一样东西——一方奶白色的手帕,但旋即又站了起来,回过头,对不经意瞥见这一幕的人羞赧地笑了。
其实,那不是一方手帕,那是从一个小窗口斜照进来的一片月光。
只有一个小姑娘才会犯这样的错误,而眼光修炼得老辣的是人断不被那一小片“伪装”成手帕的月光所迷惑的。
12鲍尔吉.原野

小鱼我被父母允许使用铅笔的时候,刚刚五岁。
为此大为兴奋,这种半截木棍并露出黑尖的东西,是另一种语言。
胡乱画出的一些线条,使自己佩服自己,而且挥之不去。
开始不知画什么,就弄心电图似的乱线,享受到怀素那种乐趣。
但很快觉得单调。
这时看我姐写字,十分嫉妒。
我想所有未及上学的孩子看哥哥姐姐写字,都有过这种嫉妒——集愤懑、无奈于一身。
她把字写进作业本的格子里,很有力。
每个格只有一个字,而不是像我那种连缓如湍流的线条。
我也曾宣示这些线条是字,让父母猜,但这种宣示除了被哄笑之外,不会有其他结局。
我所奇怪的事情是姐姐写的“字”,是一些复杂的图案。
笔触短也变化多端,兼有转折与交叉。
而有些“字”,她只写几笔便弃之不顾,去写其他的“字”。
有一次,我伏案观察她写字良久,指出有几个字她未写完,好像是“一”与“乙”,竟又遭到她的嘲笑。
我知道这些图案并不是她所创造的,但她居然能掌握,并在写完后用手指着,嘴里尖锐地发出音来,如“北——京——”,就令人稀奇了。
那时我也囫囵着写一些字,尽量写复杂一点,同样指着它赋予一个音,如“赤——峰——”,但我很快就忘记了它的读音,记不住。
这些一团乱麻似的字原本就是我生造的,念什么音都行。
后来我姐教我画小鱼,纾解了我的不安。
小鱼是一笔画出的。
从尾巴开始,沿弧线向前,在鱼嘴的地方转折向后,然后一竖,就是尾巴。
记住,鱼头一律是向左面,这就是向前,我姐就是这么教的。
如皋比较灵慧的话,可在鱼身画上瓦片似的鱼鳞,鱼尾由横线罗列而成。
我站在炕上,把小鱼一条接一条地从炕沿边的白墙上画到窗户边上,他们像箭头,一个跟着一个前进,永不掉头。
接着画它们腹下的第二排,然后是第三排。
鱼群在离我们家炕边三尺高的墙上庄严进军,比黄海或加勒比海汛期的鱼儿都要多。
当你相信渔的真实性之后,就无法怀疑墙乃是大海。
多么宽广的大海啊。
我常常坐在被垛上注视鱼群前进,为它们的气势而打动。
然后,再使被垛这面墙也布满鱼群,当然它们是向另一个方向行进的。
鲍尔吉·原野《马鬃燃烧》阅读练习及答案

鲍尔吉·原野《马鬃燃烧》阅读练习及答案编者序该文档是本知识店铺精心收集编制而成,希望同学下载后,能够帮助同学解决实际问题。
文档下载后可定制修改,请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和使用,谢谢!前言下载提示:为您提供阅读答案!阅读理解的意思是说先阅读一段文字,然后理解它的含义,并且总结出来。
本文档主要对《马鬃燃烧》进行阅读训练及参考答案解析。
Download tips: To provide you with reading answers! Reading comprehension means to read a paragraph first, then understand its meaning, and summarize it. This document mainly analyzes reading training and reference answers.(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4小题,16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马鬃燃烧鲍尔吉·原野马群冲过来,好像在你面前砌来一座奔流的城墙。
这座夹杂枣红色、灰色、白色和黑色的城墙顶端飘扬着群马的颈部鬃发,这是马的五色战旗,在风中猎猎招展。
马群踏过,你看不清每匹马是什么样的马,但马的鬃发和拉成直线的尾巴给你留下强烈印象。
阳光下,马的皮毛闪亮,马蹄如千足之虫的脚爪翻飞。
马鬃是马从天际拉过来的绳索,牵着云团迁移。
从山顶看马群跑过大地,看它们鬃发飞扬,仿佛大地燃烧着黑色亚麻色的火焰,一丛丛火焰下面有马蹄踏出的沉闷鼓点儿。
在河边看低头饮水的马群,马们伸着修长的脖子探向清澈并缓缓流动的河水。
河水映照马的鼻梁,而风用马的鬃发盖住了它们的眼睛。
这些没有修剪过的鬃发代表马的野性。
它们不是驾驭马车的牲畜,是大自然的子孙,崇尚自由,与人平等。
最健壮的马鬃发最长,这是马群中的公马,人称儿马。
牧民说,不要碰公马的鬃发。
不能修剪,甚至不能摸。
马馆告诉我,公马的鬃发不能碰到剪子,不能遇到一切铁。
鲍尔吉.原野散文集精选在线阅读

鲍尔吉.原野散文集精选在线阅读鲍尔吉·原野,蒙古族,他从大漠走来,与歌手腾格尔,画家朝戈被称为当今中国文艺界的“草原三剑客”,他的散文很美。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精选的鲍尔吉.原野散文集,供大家欣赏。
鲍尔吉.原野散文集精选一:《美与挂碍》美国的行为心理学家做过一个试验,让两组男女穿着泳衣回答智力问题,男人的成绩大致正常,女人却大失水准,也就是普遍低于她们穿着常服时的测验水准。
心理学家的结论是越美越愚蠢。
美与愚蠢的关系,中外有许多人在研究,虽然说法不一,但很少得出越美越聪明的结论。
而我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即情境与自信力的关系。
我以为泳装女郎变愚的原因在于自尊感,也可称为焦虑,当一个自己设定的缺陷,譬如腿粗,在长期隐蔽之下突然暴露出来之后。
所谓智力只好下降,可见并非越美越愚蠢,而是越焦虑越愚蠢。
人的智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集中注意力的能力,联想、判断均赖于此。
一个女人穿着泳装在大庭广众之下集中注意力,能吗?“忘我”从心理学说,是儿童游戏那种状态,物我两忘,浑然一体。
人在那种时刻最聪明。
儿童的忘我让人钦佩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在屙尿的时候,会投入对一只昆虫的观察,以至忘记自己在做什么。
老子将这种状态称为“赤子之心”。
有了此心,没有什么事情办不好。
与忘我相对的是“挂碍”,人的一生总被各种事情挂碍着。
腿粗只是其中的一种。
杰克逊为肤色挂碍,漂白或植皮。
有人被子性别挂碍,用手术造出另一套生殖系统。
这是一种并不重要的,但使当事人忘不掉的焦虑。
医治“挂碍”的药方,即古贤说的“平常心”。
平常心如今被滥用了。
倘如一个贪官被撤职了,也以“平常心”为自己解嘲。
他以为无法吃喝嫖赌,像老百姓一样过平实的日子就是平常心了。
平常心远非一两句话能够说清,但至少在于忘记自己的背景、缺陷、荣耀等等附加物,与人无异,双手空空。
这是摆脱焦虑的法门与境界。
这样的人气象平和,不让人讨厌。
还有一个好处是穿泳装考试的时候能够得第一。
鲍尔吉.原野散文集精选二:《厚道》契诃夫说:“有教养不是吃饭不洒汤,是别人洒汤的时候别去看他。
【散文海外版】鲍尔吉·原野:沃森花草原记事(节选)

【散文海外版】鲍尔吉·原野:沃森花草原记事(节选)我们坐在马倌班波若的房子里喝酒。
这座房子的客厅大,朝南的玻璃窗有六扇,主人可以有广角的视野看到窗外的草原。
草原南方尽头悄无声息的山峦,像一堆马鞍子堆在天的尽头。
主人班波若说他就这么看过去,看到自己老死那天,这里面包含着多大的福气啊。
是的,是的,来访者纷纷附和,语气诚恳,班波若用感谢的眼神环视大家,比摄像机“揺”的速度慢得多,仿佛这个事就这么定下来了,以后也改变不了。
今年七十岁的班波若到以后咽气那天,最后一眼看的是他家窗前的沃森花草原。
那也许是在六月,大朵的、雪白的芍药花开在如同堆了一堆马鞍子的山的山坡上。
过了小满,黄翅的鸟飞回来了,带回来绿翅的鸟。
草地上的白雾在早晨四点多钟覆盖膝盖那么厚,然后一层层变薄,野兔在雾里奔跑,谁也不知它去了哪里。
当然,班波若告别人世的时候也许是冬天,大雪把马鞍子似的山峦压没了,大地因为堆满积雪而显出笨拙,而有炊烟透露牧人的生机。
我们不能提前为班波若离世制订季节与时辰,他的白头发还不到全部头发的三分之一,今年春季他还参加过村里那达慕大会的摔跤比赛,被会场的广播喇叭授予“像山峰一样纹丝不动的摔跤手”。
当时会场上的男女老少全都听出了这个称号里的讥讽含义——“没有动作的、不主动进攻的摔跤手”,众人哈哈大笑。
班波若坐在沙发上。
他背后挂着牛车车厢那么大的镜子,陪我采访的乡干部贺西格、楚鲁、谢日哈达等人都反射在镜子里,他们手端吃饭的花瓷碗喝奶茶。
奶茶烫,人喝进嘴里前发出很响的声音“咻——”,用吸气为茶降温。
这个人端起碗,“咻——”,放下。
那个人端起碗,“咻——”。
班波若撩起裤子,用两只紫红大手的手心在膝盖上旋转,仿佛他的双腿可以在地下钻探出石油。
他愉快地看着窗外的草原。
没经历过游牧生活的人理解不了牧人何以长时间地注视空寂无物的草原,那里只有草和看不清的风,一如古代时分。
蒙古人看到的是寂静。
人在寂静里面看到了什么?这真是难以回答的问题。
鲍尔吉·原野《跟大自然说句话》阅读训练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7~9题。
跟大自然说句话鲍尔吉·原野我们说过许多话,我们记不起来都跟谁说过哪些话。
可是,我们跟大自然几乎没说过话,而它们就在我们身边。
大自然对我们说的话从来没有停歇过,它们有耐心。
早上,我们走出家门——如果你有这份细心体察的话——清风抚过面颊,风用它透明的小手轻轻摸你的脸,还有眉毛、眼窝和耳朵,好像它知道你会在这一刻走出门,在这里等你。
事实上,它的小手还抚过你的肩膀、后背和鞋子,只是你没察觉而已。
风是大自然千万种语言中的一种,可以叫风语,还可以叫其它语,随便你,风并不在意这个。
就在我们在做所谓“上班”或“上学”的活动时,在我们前往目的地而迈开第一步的时候,小鸟可能已经飞翔了三个多小时,已经看过了壮丽的日出。
它从天空看到人像蚂蚁一样陆陆续续从房子里走到大街上,它在树枝上看到草地上一朵小黄花正徐徐打开叶片,准备迎接阳光。
而人们对这一切浑然无知,径直走着,或径直开车走着。
他们不知道天边的白云跟昨天不一样,跟一小时之前也不一样。
人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外貌,而云可以。
云尽其一生变幻无穷却不停歇。
即使在城里,大自然也在人的身边,土地、天空、空气与光,俱有大自然的核心要素。
可是人并不关心大自然在做什么,人的皮肤和心灵已经感受不到季节的变化。
他们要通过资讯——比如说智能手机了解气温变化。
是不是可以说,人正一点点远离大自然。
人的心灵里装填了越来越多的东西,因为世上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在他们内心的容积中有关大自然的关注越来越少。
如果是这样,人会失去好多欣赏美的机会。
如实说,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审美,即使如美术师也不需要时时审美。
可是,美是真与善不可分割的并存物,是奠定人之人格的基础。
历史告诉人们:不懂美的人也是离愚昧与残暴很近的人。
而美的根源在哪里呢?大自然,只能是大自然。
我们看到的许多样式的艺术品,比如绘画、音乐、舞蹈、建筑等等,都是人类对大自然的模仿。
它们是“假的”,是抒发、是表白、是再现、是提炼、是集中;而大自然是真的,它并不抒发再现,它浑然一团而已。
《井》鲍尔吉原野阅读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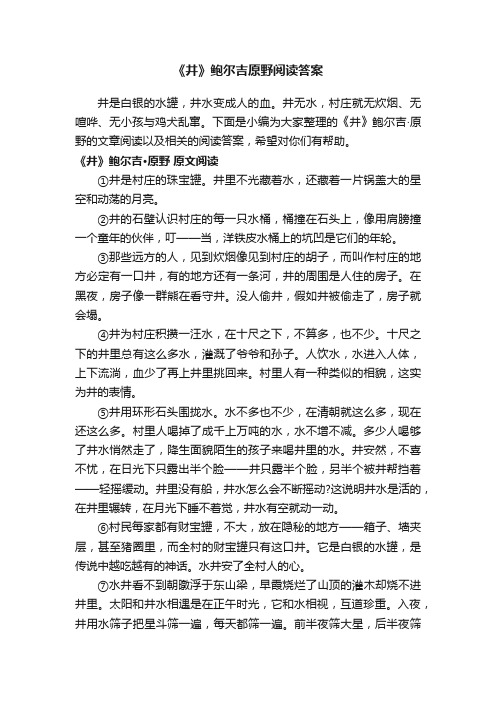
《井》鲍尔吉原野阅读答案井是白银的水罐,井水变成人的血。
井无水,村庄就无炊烟、无喧哗、无小孩与鸡犬乱窜。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井》鲍尔吉·原野的文章阅读以及相关的阅读答案,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井》鲍尔吉·原野原文阅读①井是村庄的珠宝罐。
井里不光藏着水,还藏着一片锅盖大的星空和动荡的月亮。
②井的石壁认识村庄的每一只水桶,桶撞在石头上,像用肩膀撞一个童年的伙伴,叮——当,洋铁皮水桶上的坑凹是它们的年轮。
③那些远方的人,见到炊烟像见到村庄的胡子,而叫作村庄的地方必定有一口井,有的地方还有一条河,井的周围是人住的房子。
在黑夜,房子像一群熊在看守井。
没人偷井,假如井被偷走了,房子就会塌。
④井为村庄积攒一汪水,在十尺之下,不算多,也不少。
十尺之下的井里总有这么多水,灌溉了爷爷和孙子。
人饮水,水进入人体,上下流淌,血少了再上井里挑回来。
村里人有一种类似的相貌,这实为井的表情。
⑤井用环形石头围拢水。
水不多也不少,在清朝就这么多,现在还这么多。
村里人喝掉了成千上万吨的水,水不增不减。
多少人喝够了井水悄然走了,降生面貌陌生的孩子来喝井里的水。
井安然,不喜不忧,在日光下只露出半个脸——井只露半个脸,另半个被井帮挡着——轻摇缓动。
井里没有船,井水怎么会不断摇动?这说明井水是活的,在井里辗转,在月光下睡不着觉,井水有空就动一动。
⑥村民每家都有财宝罐,不大,放在隐秘的地方——箱子、墙夹层,甚至猪圈里,而全村的财宝罐只有这口井。
它是白银的水罐,是传说中越吃越有的神话。
水井安了全村人的心。
⑦水井看不到朝暾浮于东山梁,早霞烧烂了山顶的灌木却烧不进井里。
太阳和井水相遇是在正午时光,它和水相视,互道珍重。
入夜,井用水筛子把星斗筛一遍,每天都筛一遍。
前半夜筛大星,后半夜筛小星。
天亮前筛那些模模糊糊的碎星。
井水在锅盖大的地方看全了星座,人马座、白羊座,都没超过一口井的尺寸。
⑧井暗喜,月亮每月之圆,是为井口而圆。
最圆的月亮只是想盖在井上,金黄的圆饼刚好当井盖,但月亮一直盖不准,天太高了。
《马灯》阅读练习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各题。
马灯鲍尔吉•原野那年我到坝后,干什么去已经忘了,但脑子里挂记着那盏马灯。
我们住在大车店的一铺大炕上,睡20 多人,都是马车夫。
白天,我和主车夫老杜套上我们的马车,拉东西。
把东西从这个地方拉到那个地方,好像拉过羊圈里的粪。
那羊圈真是世上最好的羊圈,起出20 多公分厚的羊粪,下面还有粪,黑羊粪蛋子一层一层地偷偷发酵,甚至发烫,像一片一片的毡子,我简直爱不释手。
并沉醉于羊粪发酵发出的奇特气味中。
晚上,我们住大车店。
大车店没拉电、客房挂一盏马灯,马厩挂一盏马灯。
晚上,车夫们掰脚丫子,亮肚子,讲猥亵笑话。
马灯的光芒没等照到车夫脸上就缩在半空中,他们的脸埋在黑暗中,但露着白牙。
不刷牙的车夫,这时也被马灯照出洁白的牙齿。
苇子编的炕席已经黄了,炕席的窟窿里露出炕的黑土。
肮脏的看不出颜色的被褥全在马灯的光晕之外。
房梁上,悬挂着一尺左右,像暖瓶一样的马灯。
灯的玻璃罩里面的灯蕊燃烧煤油。
花生米大小的火苗发出刺目的白光,马灯周围融洽一团桔黄的光芒,仿佛它是个放射黄光的灯,马灯的玻璃罩像电吹风的风筒,罩子四周是交叉的铁丝护具。
装煤油的铁盒是灯的底座,可装二两油。
蛾子在屋顶缭绕,它们靠近灯,但灯罩喷出的热气流把它们拒之灯外。
不久,车夫们响起鼾声,这声音好像是故意发出的极为奇怪的声音。
你让一位清醒的人打鼾,他发不出梦境里的声音,他忘记了梦中的发声方法。
有人像唱呼麦一样同时发出二、三个声音,有低音、泛音和琶音,有许多休止符使之断断续续。
有人在豪放地呼出嚕之后,吸气却有纤细的弱音,好像他嗓子里勒着一根欲断的琴弦,而且是琵琶的弦,仿佛弹出最后一响就断了,但始终没断。
打呼噜的人大都张着嘴,但闭着眼。
他们张嘴的样子如同渴望被解救出来。
我半夜解手回屋,背手踱步,在马灯的光亮下视察过这些打鼾的车夫,洞开的嘴还可以寓意失望,吃惊和无知。
他们是够无知的,把这个村的羊粪拉到另一个村的地里。
其实,我看到那个村也有羊圈。
那时候,农村里的一切都归公社所有,拉哪个羊圈的粪都一样。
《人民文学》2022年第6期|鲍尔吉·原野:母鸡麦拉苏(节选)

《人民文学》2022年第6期|鲍尔吉·原野:母鸡麦拉苏(节选)鲍尔吉·原野,蒙古族,内蒙古赤峰人。
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2021年度中国好书、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散文奖、内蒙古文艺特殊贡献奖及金质奖章、赤峰百柳文学特别奖等文学奖项,与歌手腾格尔、画家朝戈并称中国文艺界的“草原三剑客”。
多篇散文作品被选入大中小学语文课本以及语文试卷。
为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辽宁省作协副主席。
母鸡麦拉苏(节选)鲍尔吉·原野1、塔娜和麦拉苏。
打开这本书你认识的第一个人名字叫塔娜。
她是一个女孩子,今年七八岁,梳两根辫子。
辫子并不能把她所有的头发都编进去,金黄色的碎头发从她前额和后脖梗垂下来,远看她的脸像一个向日葵花的花盘。
塔娜喜欢大地,她手上经常带着泥土和伤口。
她喜欢和石头玩,和蒙古栎树以及爬上栎树的狗枣子藤玩。
野兔和花栗鼠也是她的玩伴。
看到这里你会问,她父母允许她这么顽皮吗?她父母不管的,他们在天津的餐馆打工。
塔娜和爷爷一起生活。
爷爷认为,人嘛,和动物是一样的,都要蹦蹦跳跳。
在大自然里磕伤了、碰伤了没有什么坏处,这是大自然送给人类的礼物。
正像你知道的,爷爷平常不怎么管塔娜。
她有时候会去邻近村落的姨娘家住几天,或者到舅舅家住几天。
爷爷都不在意,他知道塔娜在姨娘和舅舅家住够了就回来了。
牧民家养的小狗有时候也会出远门,到山上旅行。
在大自然里风餐露宿五六天,顶多半个多月也会回来的,不用担心。
塔娜的牙掉了好几颗。
笑起来,缺少门牙的缝隙里露出粉红的舌头。
刚才说塔娜头发金黄色。
她瞳仁也是金黄色的,这是说在屋里。
如果在阳光下,塔娜的瞳孔比金黄色浅,带一些淡绿色。
看上去很好玩。
以后你遇见有金黄色或者淡绿色瞳孔的人,会感觉他的思绪在远方,在高山和森林里。
塔娜就是这样。
你在这本书里认识的第二个主角不是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接受她。
不管你高兴不高兴,她都是一只母鸡,名字叫麦拉苏。
小狗睡觉文鲍尔吉·原野

小狗睡觉文鲍尔吉·原野我每天跑步经过市场,亲切接见红塑料大盆里的黄褐色的螃蟹、待宰的公鸡、胡萝卜和大蒜,有一窝小狗吸引了我。
小狗挤在柳条编的大扁筐里,它们把下巴放在兄弟姐妹们的脊背上,像鲜黄带黑斑的粘豆包黏在了一起,黑斑是豆馅挤到了皮外面。
我不知道还有哪些生灵比这些小狗睡得更香,它们的黑鼻子和花鼻子以及没有皱纹的脸上写着温暖、香甜。
小狗在市场上睡觉,自己不知道来这里要被卖掉。
它们压根听不懂“卖”这个词。
卖,是人类的发明,动物们从来没卖过东西。
狗没有卖过猫,猫没卖过麻雀,麻雀没卖过驼背的甲壳虫。
动物和昆虫也没卖过感情、眼泪和金融衍生品。
小狗太困了,不知是什么让它们这么困。
边上铁笼里的公鸡在刀下发出啼鸣,仿佛申诉打鸣的公鸡不应该被宰。
而宰鸡的男人背剪公鸡双翅,横刀抹鸡脖子,放血,那一圈土地颜色深黑。
笼子里的鸡慌慌张张地啄米,不知看没看到同类赴刑的一幕。
小狗睡着,仿佛鼻子上有一个天堂。
科学家说,哺乳类动物都要睡眠,那么感谢上帝让它们睡眠。
睡吧,在睡眠中编织你们的梦境,哪管梦见自己变成拿刀抹那个男人脖子的公鸡。
家里养了小猫后,我差不多一下子理解了所有小狗的表情。
原来怕狗,如耗子那么大的狗都让我恐惧。
后来知道,小狗在街上怔怔地看人,它们几乎认为所有人都是好人,这是从狗的眼神里发出的信号。
狗的眼神纯真、信任,热切地盼望你与它打滚、追逐或互相咬鼻子。
狗不知道主人因为它有病而把它抛到街头;狗不知道主人搂着它叫它儿子的时候连自己亲爹都不管;狗不知道世上有狗医院、狗香波、狗照相馆。
人发明了“狗”这个词之后自己当人去了。
人在教科书上说人是高级动物,为了佐证这一点,说人有思想、有情感、有爱心。
人间的历史书包括法国史、丝绸史、医药史以及一切史,却见不到人编出一部人类残暴史和欺骗史。
人管自己叫人已够恭维,管自己叫动物也没什么不可以,然而管自己叫高级动物有点说冒了,没有得到所有动物们的同意。
如果仅仅以屠杀动物或吃动物就管自己叫高级动物,那么狼早就高级了。
在这样的风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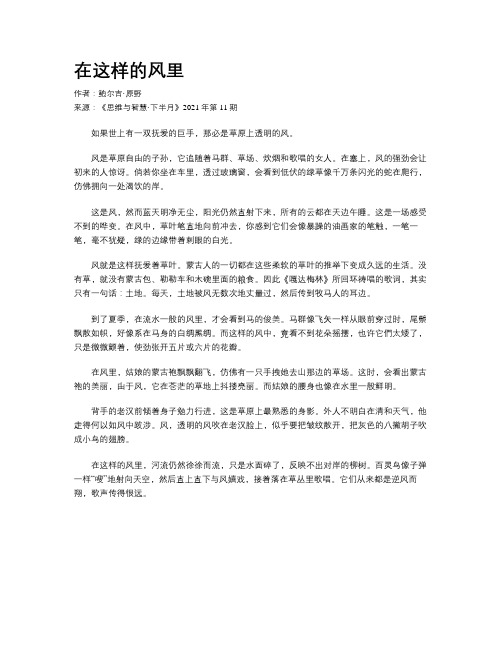
在这样的风里作者:鲍尔吉·原野来源:《思维与智慧·下半月》2021年第11期如果世上有一双抚爱的巨手,那必是草原上透明的风。
风是草原自由的子孙,它追随着马群、草场、炊烟和歌唱的女人。
在塞上,风的强劲会让初来的人惊讶。
倘若你坐在车里,透过玻璃窗,会看到低伏的绿草像千万条闪光的蛇在爬行,仿佛拥向一处渴饮的岸。
这是风,然而蓝天明净无尘,阳光仍然直射下来,所有的云都在天边午睡。
这是一场感受不到的哗变。
在风中,草叶笔直地向前冲去,你感到它们会像暴躁的油画家的笔触,一笔一笔,毫不犹疑,绿的边缘带着刺眼的白光。
风就是这样抚爱着草叶。
蒙古人的一切都在这些柔软的草叶的推举下变成久远的生活。
没有草,就没有蒙古包、勒勒车和木碗里面的粮食。
因此《嘎达梅林》所回环祷唱的歌词,其实只有一句话:土地。
每天,土地被风无数次地丈量过,然后传到牧马人的耳边。
到了夏季,在流水一般的风里,才会看到马的俊美。
马群像飞矢一样从眼前穿过时,尾鬃飘散如帜,好像系在马身的白绸黑绸。
而这样的风中,竟看不到花朵摇摆,也许它們太矮了,只是微微颤着,使劲张开五片或六片的花瓣。
在风里,姑娘的蒙古袍飘飘翻飞,仿佛有一只手拽她去山那边的草场。
这时,会看出蒙古袍的美丽,由于风,它在苍茫的草地上抖搂亮丽。
而姑娘的腰身也像在水里一般鲜明。
背手的老汉前倾着身子勉力行进,这是草原上最熟悉的身影。
外人不明白在清和天气,他走得何以如风中跋涉。
风,透明的风吹在老汉脸上,似乎要把皱纹散开,把灰色的八撇胡子吹成小鸟的翅膀。
在这样的风里,河流仍然徐徐而流,只是水面碎了,反映不出对岸的柳树。
百灵鸟像子弹一样“嗖”地射向天空,然后直上直下与风嬉戏,接着落在草丛里歌唱。
它们从来都是逆风而翔,歌声传得很远。
胡杨之地阅读题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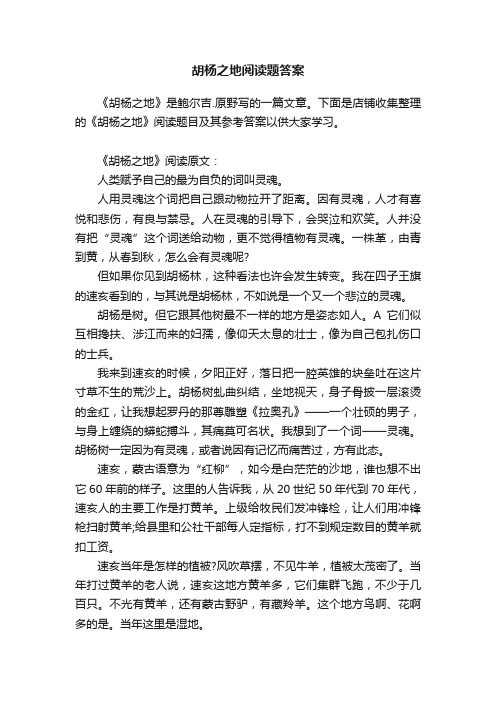
胡杨之地阅读题答案《胡杨之地》是鲍尔吉.原野写的一篇文章。
下面是店铺收集整理的《胡杨之地》阅读题目及其参考答案以供大家学习。
《胡杨之地》阅读原文:人类赋予自己的最为自负的词叫灵魂。
人用灵魂这个词把自己跟动物拉开了距离。
因有灵魂,人才有喜悦和悲伤,有良与禁忌。
人在灵魂的引导下,会哭泣和欢笑。
人并没有把“灵魂”这个词送给动物,更不觉得植物有灵魂。
一株革,由青到黄,从春到秋,怎么会有灵魂呢?但如果你见到胡杨林,这种看法也许会发生转变。
我在四子王旗的速亥看到的,与其说是胡杨林,不如说是一个又一个悲泣的灵魂。
胡杨是树。
但它跟其他树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姿态如人。
A它们似互相搀扶、涉江而来的妇孺,像仰天太息的壮士,像为自己包扎伤口的士兵。
我来到速亥的时候,夕阳正好,落日把一腔英雄的块垒吐在这片寸草不生的荒沙上。
胡杨树虬曲纠结,坐地视天,身子骨披一层滚烫的金红,让我想起罗丹的那尊雕塑《拉奥孔》——一个壮硕的男子,与身上缠绕的蟒蛇搏斗,其痛莫可名状。
我想到了一个词——灵魂。
胡杨树一定因为有灵魂,或者说因有记忆而痛苦过,方有此态。
速亥,蒙古语意为“红柳”,如今是白茫茫的沙地,谁也想不出它60年前的样子。
这里的人告诉我,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速亥人的主要工作是打黄羊。
上级给牧民们发冲锋检,让人们用冲锋枪扫射黄羊;给县里和公社干部每人定指标,打不到规定数目的黄羊就扣工资。
速亥当年是怎样的植被?风吹草摆,不见牛羊,植被太茂密了。
当年打过黄羊的老人说,速亥这地方黄羊多,它们集群飞跑,不少于几百只。
不光有黄羊,还有蒙古野驴,有藏羚羊。
这个地方鸟啊、花啊多的是。
当年这里是湿地。
这个老牧人指着白茫茫的沙砾说“当年这里是湿地”时,真的像是在痴人说梦。
如今除了天上的云朵和地上的胡杨属于有形状的东西,其他皆为空荡荡的虚无。
“打死的黄羊呢?”我问老师。
“都让上级拉走了,”老人说,“我们自己养牛养羊,从来不打黄羊。
打黄羊变成了政治任务,肉和皮子都出口换汇了。
鲍尔吉_原野《青草寂静》阅读练习及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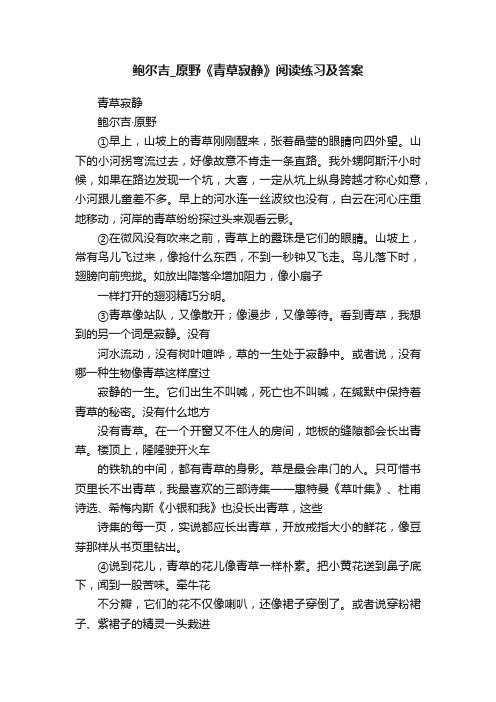
鲍尔吉_原野《青草寂静》阅读练习及答案青草寂静鲍尔吉·原野①早上,山坡上的青草刚刚醒来,张着晶莹的眼睛向四外望。
山下的小河拐弯流过去,好像故意不肯走一条直路。
我外甥阿斯汗小时候,如果在路边发现一个坑,大喜,一定从坑上纵身跨越才称心如意,小河跟儿童差不多。
早上的河水连一丝波纹也没有,白云在河心庄重地移动,河岸的青草纷纷探过头来观看云影。
②在微风没有吹来之前,青草上的露珠是它们的眼睛。
山坡上,常有鸟儿飞过来,像抢什么东西,不到一秒钟又飞走。
鸟儿落下时,翅膀向前兜拢。
如放出降落伞增加阻力,像小扇子一样打开的翅羽精巧分明。
③青草像站队,又像散开;像漫步,又像等待。
看到青草,我想到的另一个词是寂静。
没有河水流动,没有树叶喧哗,草的一生处于寂静中。
或者说,没有哪一种生物像青草这样度过寂静的一生。
它们出生不叫喊,死亡也不叫喊,在缄默中保持着青草的秘密。
没有什么地方没有青草。
在一个开窗又不住人的房间,地板的缝隙都会长出青草。
楼顶上,隆隆驶开火车的铁轨的中间,都有青草的身影。
草是最会串门的人。
只可惜书页里长不出青草,我最喜欢的三部诗集——惠特曼《草叶集》、杜甫诗选、希梅内斯《小银和我》也没长出青草,这些诗集的每一页,实说都应长出青草,开放戒指大小的鲜花,像豆芽那样从书页里钻出。
④说到花儿,青草的花儿像青草一样朴素。
把小黄花送到鼻子底下,闻到一股苦味。
牵牛花不分瓣,它们的花不仅像喇叭,还像裙子穿倒了。
或者说穿粉裙子、紫裙子的精灵一头栽进花里。
⑤青草让山坡的线条柔和,山的所有的坡度都被青草包裹的如在眼前,从山顶背后露出的云团像是从青草里冒出来的,而野花如奔跑。
在我记忆中,穿裙子的小女孩儿都喜欢奔跑,裙子上的花太漂亮,不跑腿不得劲。
野花的花瓣在风中俯仰摇摆,像笑得直不起腰。
而青草静穆地看野花笑。
⑥葡萄牙诗人Ramos Rosa,我译之为罗萨。
他有诗云“我所认识的天使伫立在青草和寂静之中”。
这个诗好,更有趣在他说“我所认识的天使”,可见每个人认识的天使都不一样。
散文百练:黄昏无下落(鲍尔吉·原野)

散文百练:黄昏无下落(鲍尔吉·原野)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15分)黄昏无下落鲍尔吉·原野是谁在人脸上镀了一层黄金?人在慷慨的金色里变为红铜般的勇士,破旧的衣裳连皱褶都像雕塑的手笔;人的脸棱角分明,不求肃穆,肃穆自来,这是在黄昏。
小时候,我无意中目睹了黄昏。
看到那离奇的光从红里生出诡异的蓝。
红里怎么会生出蓝呢?它们是两个色系。
玫瑰红诞生其间,橘红诞生其间,旋生旋灭。
这是怎么啦?西方的天空发生了什么?我结结巴巴地问大人,那里发生了什么?大人瞟了我一眼,只说了两个字:黄昏。
自那时起,我得知世上还有这两个字——黄昏,并知道这两个字里有忧伤。
我盼着观黄昏,黄昏却不常有,至少天空不老黄。
如果是多云天气或阴天,黄昏就没了下落。
我站在我家屋顶看黄昏。
西方的天空在柳树之上烂成一锅粥,云彩被夕阳绞碎,红云犹如在烈火中逃窜的野兽,却总逃不出西天的大火。
太阳以如此大的排场谢幕,它以炽热的情感告诉人们它要落山了。
人们习以为常,不过瞟一眼,名之“黄昏”。
而我心里隐隐有戚焉。
假如太阳不再升起,全世界的人都会在痛哭流涕中凝视黄昏,每日变成每夜,电不够用,煤更不够用,满街小偷。
黄昏里,屋顶的一株青草在夕照里显得格外妖娆,想不到生于屋顶的草会这么漂亮,红瓦衬出草的青翠,晚霞又给下垂的叶子抹上一层柔情的红。
草在风中摇曳,像在瓦上跳舞。
原来当一株草也挺好,如果能生在屋顶的话,就是一位在夕阳里跳舞的新娘。
地上的草叶金红,鹅卵金红,土里土气的酸菜缸金红,黄昏了。
我在牧区看到的黄昏惊心动魄。
广阔的地平线仿佛被泼上油烧起了火,烈火战车在天空穿行,在落日的光芒里,山峰渐渐变秃、变矮。
天空盛不下的金光全都倾泻在草地上,一直流淌到脚下,黄牛红了,黑白花牛也红了,它们扭颈观看夕阳。
天和地如此辽阔,我久久说不出话来,坐在草地上看黄昏,直到星星像纽扣一样别在白茫茫泛蓝的天空。
那时,我很想跟别人吹嘘我是一个看过牧区黄昏的人,但这事好像不值得吹嘘。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鲍尔吉原野散文在线:发出我们听不到的惊
天
鲍尔吉原野散文在线:发出我们听不到的惊天动地的呼喊“巴彦淖尔”,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富裕的湖泊”。
我问:“这里有叫巴彦淖尔的湖吗?”当地朋友说,“我们这里有河套。
黄河百害,惟富一套,说的就是巴彦淖尔。
我们有最好的面粉和葵花籽……”
他像没人管的录音机一样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的家乡。
我早知巴彦淖尔的盛名,比面粉、爬山调、甜瓜更有名的是这里的黄河改造工程。
黄河水利博物馆收藏了当地出土的自仰韶文化至今的各类文物,尤以水利文物为珍贵。
我在博物馆的一幅照片前注视良久。
照片上约有百人用粗麻绳合拉一个梢棒。
几十米宽的草编帘子里面裹上土,一层一层卷起来就叫梢棒,用于大坝合龙。
过去没有吊车,没有混凝土固件,梢棒是中流砥柱。
画面上的梢棒即将被拉上大坝,有人站在梢棒上喊号子,有人焦急等待,大多数人憋着劲儿拉滚动的梢棒。
照片拍摄于1952年,我惊叹解放初期的农民竟然有这么精壮。
他们头系羊肚白手巾,身穿土布露膊白短褂,正发出我们听不到的惊天动地的呼喊。
他们双腿如同扎进了土里,后背宽阔结实。
他们仿佛正把黄河拉进了自己的怀里,让它灌溉良田,产出“……最好的面粉和葵花籽。
”
流经总干渠和分干渠的黄河水,不仅哺育了庄稼,也美化了
村庄。
干渠里清澈的黄河水从临河区万丰村边流过,水面宽阔,垂柳依依,城里人每年来这个村举办龙舟赛。
秋风至,公路两旁高大的白杨树黄绿相间。
逆光的黄叶越发稀疏,遮不住从树林里飞过的喜鹊的身影。
白杨树下,玉米如一片等待渡河的人群。
它们叶片披纷繁复,像手里拿着数不清的东西。
白金色泽的玉米站满大地,干透的叶子夺走了所有的秋声。
鲍尔吉原野散文在线:村庄像被街灯包裹的桔子童年读过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这首诗一直留在我脑海里,我尤喜爱街灯在暮色里明亮的一瞬,仿佛暮色睡去,街灯猛地醒来。
夜晚进入一座城市,见到了延伸到远方的街灯才觉得进了城。
我这回去过的村庄,广而言之内蒙古现今完成“十个全覆盖”的八千多个行政村,都架设了太阳能街灯。
村庄里亮起街灯,是说它挣脱了夜色的捆绑,跟着光明一起奔跑。
我们来到扎鲁特旗北部的图布信嘎查(村)时,雨停了,躲在草叶里的水珠在夕阳里大胆地发光,这个村是蒙古四胡说书大师琶杰的故乡。
村里的街巷按交叉小径规划,白杨树掩映着牧民们的屋舍,低矮的院墙外边砌着花池,花朵成了保护院墙的彩衣卫兵。
说话间街灯亮了,这些灯低头观看路边的大丽花,还有牧户各家“羊”字变形的镂空黄门。
站在公路上回望,村子像被街灯包裹的玲珑的桔子,卧在起伏的山地草原上,牧民们正在桔子里喝酒看电视呢。
雨后的扎鲁特之夜,草地黑了。
从这边们在村庄里弯腰砌砖、抹灰、栽树、打井,秋风把奖章般的黄叶吹到他们的身旁。
鲍尔吉原野散文在线:吹麦子的风吹过我的胸膛在呼伦贝尔,我见到了像草原一样辽阔的麦地。
麦子铺展到天边时,你觉得它们正越过地平线,翻滚到地球的另一面。
如楼房般高大的联合收割机停在麦地尽头,竟只有甲虫大小,一共两台。
这是在额尔古纳市的上库力。
如果我是这里的乡镇书记,我会天天到麦地视察,敞开衣襟,拤腰,让吹过麦子的风吹在我的胸膛上,吹上一个月,身上比面包还香。
我们走过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
莫力达瓦是达斡尔语,意谓“只有骑马才能越过的山岗”。
而我们开车也越过了兴安岭,到达鄂伦春自治旗。
兴安,满语里的意思是小山丘,蒙古语的意思是大石头,汉语引伸为兴盛安康。
兴安这个地名跟神木、福鼎、仙游一样,都是中国好地名。
林区行车,视野里满是松树和白桦树。
采蘑菇的人们九月份已经穿上了羽绒服,挎着小筐嗖嗖走。
他们脚踩着金黄的落叶松的松针找蘑菇,松鼠爬上树顶为他们放哨。
看车窗外的獐子松看久了,觉得它们是密密叠叠的城墙,而巍峨的深绿城堡还在更远的远方。
车开了几个小时,松树从两旁跑过却永远跑不完。
你感觉自己出了幻觉,觉得这像是电脑游戏。
然而它们全是松树,斑驳笔直,这里是莽莽苍苍的大兴安岭。
在拉布大林镇的宾馆大堂,我见到两个人在聊天。
年轻人:“哎呀!大哥,昨晚喝多少?”中年人伸出一根手指。
年轻人:“一杯?”中年人摇头。
年轻人:“一壶?”中年人接着摇头。
年轻人:“一瓶?”中年人还摇头,手指屹立不动。
年轻人惊讶:“大哥,你到底喝多少啊?”中年人开口,镇定地说:“一直喝。
”
我想起了我堂兄朝克巴特尔。
这次去科左后旗的胡四台嘎查
(村),我们一起在村里餐馆吃饭。
朝克巴特尔和堂嫂灯笼,堂姐阿拉它和堂姐夫满特嘎四人并排坐一起,全用右手握着白酒杯,宁静的地看我们。
我们——我和我同行的朋友提酒时,他们四人一律把右手的白酒一饮而尽,手接着放桌子上,手里的玻璃杯再次倒满白酒。
他们不言语,对酒也没反应。
我后来明白,他们在用看牛羊的眼神看我们,无须说话。
朝克巴特尔每天步行五十里放三十只羊,满特嘎每天骑马八十里放二十头牛。
在草原上,他们自个儿跟自个儿喝酒,没咋跟别人喝过酒,也不会在酒桌上跟人说话。
然而酒就是话,酒钻进他们的肚子里跟他们窃窃私语。
喝到后面,他们四人全都喜笑颜开,酒把他们逗乐了。
晚上,我和朝克巴特尔睡一铺炕。
他光着上身坐着,瞪着兔子般的红眼睛问我:“政府咋啦?”没等我回答,他接着说,“政府给我们村铺路打井、翻建危房,全旗和全通辽市都这么弄了。
政府咋啦?他们以后会不会向我们收钱呢?”我说“不会。
全内蒙都这么弄呢,咋收钱?”朝克巴特尔警惕地想了半天,慢慢地咧嘴乐了,倒头睡去。
呼伦贝尔人的酒量好像比较大,他们更喜欢讲酒的笑话。
这里冬季漫长,有的地方一年只有三个月的无霜期。
修路人遇到沼泽地,要掏干一米多的淤泥。
如果在永冻层修路,先拿电锤把永冻土凿碎,从远方拉来砾石河沙填充到沼泽地和永冻层里面当路基。
这里的每一寸路都弥足珍贵。
在呼伦贝尔修路的工人们,冷了,累了就喝点酒热身,再讲一讲酒的笑话逗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