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树楷医生
依达拉奉右莰醇治疗急性进展性大动脉粥样硬化型脑梗死的临床效果

- 26 -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影响[J].淮海医药,2021,39(1):54-56.[15]张永博.腔镜辅助颈部小切口甲状腺手术治疗甲状腺良性肿瘤的效果分析[J].河南外科学杂志,2020,26(6):109-110.[16]林仁志,郑晨辉,钟吉俊,等.经口腔前庭入路腔镜甲状腺全切除术治疗cN0甲状腺乳头状癌临床研究[J].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20,40(10):1194-1196,1201.[17] CAMENZULI C,WISMAYER P S,AGIUS J C. Transoralendoscopic thyroidectomy: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practice so far[J]. JSLS,2018,22(3):26.(收稿日期:2023-06-22) (本文编辑:马娇)①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安徽 蚌埠 233000依达拉奉右莰醇治疗急性进展性大动脉粥样硬化型脑梗死的临床效果万雅迪①【摘要】 目的:探讨依达拉奉右莰醇治疗急性进展性大动脉粥样硬化(LAA)型脑梗死的临床效果。
方法:回顾性选取2021年11月—2023年4月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收治的100例急性进展性LAA 型脑梗死患者的临床资料。
根据治疗方案的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n =50)和观察组(n =50)。
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依达拉奉右莰醇治疗。
比较两组治疗前后氧化应激指标、炎症因子、神经功能和预后情况及不良反应。
结果:治疗后,观察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水平高于对照组,活性氧簇(ROS)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治疗后,观察组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治疗后3个月,两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改良Rankin 量表(mRS)评分均降低,观察组NIHSS 评分、mRS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如何扭转肝硬化,有效阻住肝癌的脚步

如何扭转肝硬化,有效阻住肝癌的脚步作者:来源:《祝您健康·养生堂》2019年第07期王福生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2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解放军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专业技术三级专家。
201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擅长慢性肝炎、肝癌和艾滋病的细胞免疫及抗病毒治疗。
门诊时间:周二、周四上午孟繁平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2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生物治疗科主任。
擅长肝炎、肝硬化、肝硬化并发症、原发性肝癌的诊治。
门诊时间:周四下午肝脏出现炎症损害之后,细胞的血供就会受到影响,肝脏的颜色会随之变浅变白;当发展到肝硬化,肝脏体积会缩小为正常体积的2/3左右,表面有硬化结节;如果肝硬化的硬化结节不受控制地长大,就会形成肝癌结节。
知识链接:正常肝脏的硬度类似嘴唇的硬度,肝硬化后肝的硬度类似额头的硬度。
王福生院士告诉我们,肝硬化患者在饮食上需要格外小心。
一些坚硬的食物可能会夺去患者的生命。
坚硬的食物包括黄瓜、各类水果、核桃、花生等。
这是因为,硬化后的肝脏会变小变硬,使流经食管和胃的血液在流经肝脏时受阻,出现血液回流,导致食管和胃部的血管变粗变薄。
患者会出现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此时,坚硬的食物就很容易划破消化道血管,导致出血。
孟繁平主任表示,水饺也可能對患者造成危害,因为水饺馅里可能含有没有切碎的软骨、菜根菜尖;此外,饺子馅打得太过劲道,或者饺子皮太硬,在进入食管后,食管的平滑肌也要用力才能把它推进胃里,这同样容易损伤血管。
辛辣的食物如辣椒也会对食管黏膜造成损伤,增加出血风险。
硬的食物不能吃,是不是软的食物就可以了呢,比如煮得软软的鸡蛋?一个曾经因肝硬化而昏迷的患者用事实告诉大家:软的食物,同样有危险!不仅仅是鸡蛋,类似于进补用的甲鱼汤等,同样有可能导致肝昏迷。
因为当肝硬化患者大量摄入高蛋白食物后,肠道里会产生血氨,大量的血氨进入人体以后会损伤中枢神经系统,导致肝性脑病,患者会出现意识障碍、行为异常甚至昏睡、昏迷。
试从病因、病理、证治上区别麻黄加术汤证和麻杏薏甘汤证。

试从病因、病理、证治上区别麻黄加术汤证和麻杏薏甘汤证。
佚名
【期刊名称】《河北中医》
【年(卷),期】1981(000)B12
【摘要】答:麻黄加术汤证和麻杏薏甘汤证均治湿邪在表的表实身疼证,均由风寒湿邪袭表,卫阳被遏,气机不利所致。
治法亦皆宜微发其汗。
但由于二方组成有异,其病因病理证治显然有别,试分析如下:麻黄加术汤证,系由平素湿盛复感风寒,寒湿
之邪伤表,卫阳被遏。
麻杏薏甘汤证则由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风湿之邪袭表,气机不利,风湿相合,而湿邪渐已化燥化热。
麻黄加术汤证身烦痛疼,其疼痛剧烈,不得安宁。
【总页数】1页(P4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692
【相关文献】
1.试从病因病理、证状、治法、组方特点上区别干姜附子汤证和茯苓四逆汤证 [J],
2.试从病理、证状、治法上比较桂麻各半汤证、桂二麻一汤证、桂二越婢一汤证。
[J],
3.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小青龙汤和麻杏甘石汤证均有喘,三者在病因病理、证状及治法上有何不同? [J],
4.三子养亲汤合麻杏甘石汤加减辨治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痰热壅肺证 [J], 王富;曾庆宁;符之月
5.麻杏苡甘汤化裁辨治湿热郁肺证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临床研究 [J], 苏利生;蔡建群;陈泽滨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碘甘油治疗口腔黏膜溃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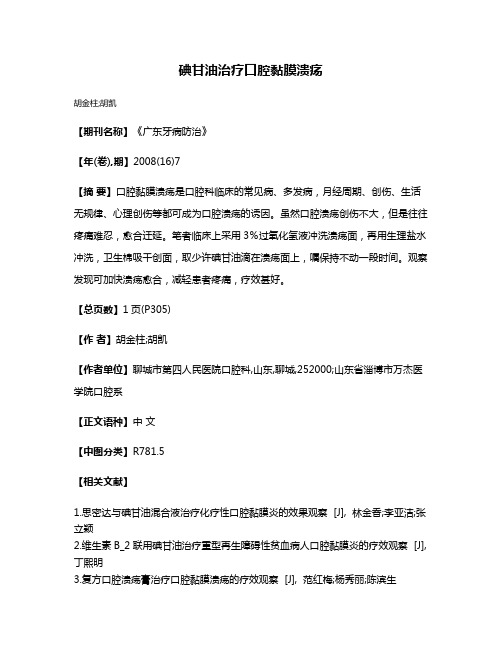
碘甘油治疗口腔黏膜溃疡
胡金柱;胡凯
【期刊名称】《广东牙病防治》
【年(卷),期】2008(16)7
【摘要】口腔黏膜溃疡是口腔科临床的常见病、多发病,月经周期、创伤、生活无规律、心理创伤等都可成为口腔溃疡的诱因。
虽然口腔溃疡创伤不大,但是往往疼痛难忍,愈合迁延。
笔者临床上采用3%过氧化氢液冲洗溃疡面,再用生理盐水冲洗,卫生棉吸干创面,取少许碘甘油滴在溃疡面上,嘱保持不动一段时间。
观察发现可加快溃疡愈合,减轻患者疼痛,疗效甚好。
【总页数】1页(P305)
【作者】胡金柱;胡凯
【作者单位】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山东,聊城,252000;山东省淄博市万杰医学院口腔系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781.5
【相关文献】
1.思密达与碘甘油混合液治疗化疗性口腔黏膜炎的效果观察 [J], 林金香;李亚洁;张立颖
2.维生素B_2联用碘甘油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病人口腔黏膜炎的疗效观察 [J], 丁熙明
3.复方口腔溃疡膏治疗口腔黏膜溃疡的疗效观察 [J], 范红梅;杨秀丽;陈滨生
4.口腔溃疡散治疗3种口腔黏膜溃疡351例临床疗效观察 [J], 仉建华
5.碘甘油与曲安奈德口腔软膏治疗口腔溃疡的效果分析 [J], 王海瑞;陈学升;姜海敏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糖皮质激素在结核病治疗中的合理应用专家共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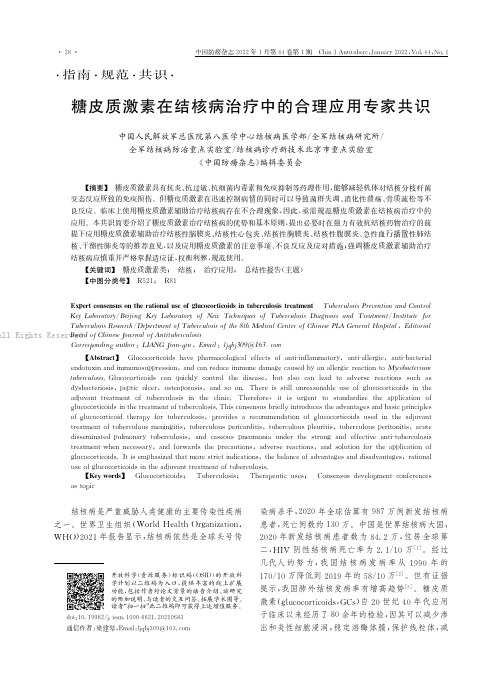
支持使用某项干预措施的强推荐干预措施明显利大于弊 支持使用某项干预措施的弱推荐干预措施可能利大于弊 反对使用某项干预措施的弱推荐干预措施可能弊大于利或利弊关系不明确 反对使用某项干预措施的强推荐明确显示干预措施弊大于利
&5)&
中国防痨杂志-)--年(月第EE卷第(期!F?'1GD1H'HIJKL>%G91I9LM-)--%C&:*EE%N&/(
管结核和 结 核 性 胸 膜 炎!占 各 器 官 结 核 病 总 数 的 ,)A"+)A!是最常见的结核病类型#肺以外器官 或部位的结核称为肺外结核!常见发病部位有淋巴 结"腹部"脑膜与脑"骨与关节"皮肤"肠道及泌尿生 殖系统等.,2+/#近年来!肺外结核在结核病中所占的 比重有所上升!我国-)(+年发表在C5':-%"-!")'3I $%(&#;%#'+#'# 的回 顾 性 研 究 提 示!某 胸 科 医 院 结 核 病患者 55*EA 为 肺 外 结 核!33*3A 为 肺 结 核.()/# `F0在肺内 外 结 核 病 尤 其 在 肺 外 结 核 病 辅 助 治 疗 中的广泛应用在国内外文献均有报道#
白芥膏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及哮喘

成人 的 12 / ,贴敷时间 8 2 ~1 小时。于夏季每伏第 1 天贴敷 1 次,连
维普资讯
连旅 教 育
DL a c d ∞t no Ch} qneE H { r fa o l 第 6卷第 O 7期 2 0 0 8年 O 月 7
单纯病毒性脑炎应用阿昔洛韦治疗 2 的体会 例
迟 帅 张 瑶 董 自艳 山东省 日照市岚 山区医院 (78 7 260)
2 脑出血术后 。予病毒唑、氟美松、头孢 唑啉 、胞磷胆碱 、甘露醇等 . 治疗,病情仍渐加重 ,体温有时高达 4 ℃,于第 7日加用干扰 素、纳 O
性脑炎最常见的病 因,常累及大脑颞叶、额 叶及边缘系统。早期抗病
毒治疗是降低病脑 死亡率 的关键 。 AV C 是广谱高效抗病毒药 ,是 目前最有效的抗 1 型和 2 H V 型 S 药 物之一 。对正常细胞几乎无影响 。而在被感染的细胞 内转化为三磷酸 无环 鸟苷 ,对病毒 D A多聚酶呈强大抑制作用, H V N 是 S 感染的首选药 。
白芥膏治疗慢性支气 管炎及哮喘
岳秀英 袁 兵 山东省聊城市中医院 (5 0 0 220)
关键 词:哮 喘 ;支气 管炎 : 白芥 膏 ;穴位 埋线法
白芥膏穴位贴敷 是对慢性支气管 炎及哮喘病症的内病外 治的中医
学 行 之 有 效 的 独 特 的 治 疗方 法 。 院 自 18  ̄2 0 我 9 0 0 6年 采 用 本 法 治 疗慢
滴 qh O 8 ,1h后体温降至 3  ̄ 4 8C,2 h后至 3. ℃,4 h 75 8 后体温正常、脑脊
液漏停止、精神及… 情况明显好转。第 8日自动出院。在家完成阿昔 散
贴剂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探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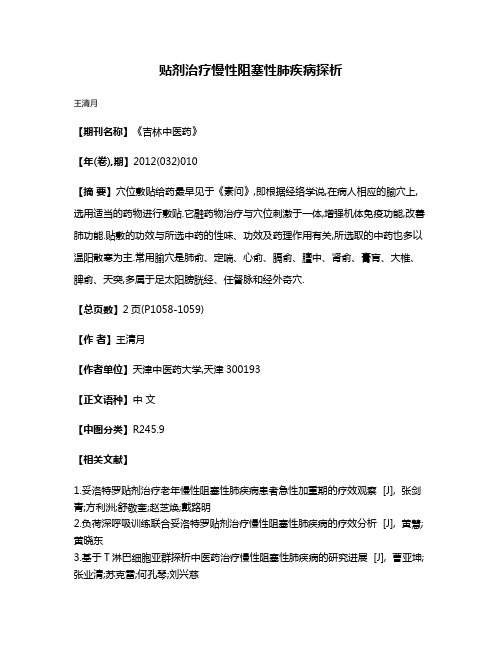
贴剂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探析
王清月
【期刊名称】《吉林中医药》
【年(卷),期】2012(032)010
【摘要】穴位敷贴给药最早见于《素问》,即根据经络学说,在病人相应的腧穴上,选用适当的药物进行敷贴.它融药物治疗与穴位刺激于一体,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改善肺功能.贴敷的功效与所选中药的性味、功效及药理作用有关,所选取的中药也多以温阳散寒为主.常用腧穴是肺俞、定喘、心俞、膈俞、膻中、肾俞、膏肓、大椎、脾俞、天突,多属于足太阳膀胱经、任督脉和经外奇穴.
【总页数】2页(P1058-1059)
【作者】王清月
【作者单位】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30019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245.9
【相关文献】
1.妥洛特罗贴剂治疗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急性加重期的疗效观察 [J], 张剑青;方利洲;舒敬奎;赵芝焕;戴路明
2.负荷深呼吸训练联合妥洛特罗贴剂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疗效分析 [J], 黄慧;黄晓东
3.基于T淋巴细胞亚群探析中医药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研究进展 [J], 曹亚坤;张业清;苏克雷;何孔琴;刘兴慈
4.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使用布地奈德联合沙丁胺醇进行治疗的效果探析 [J], 蓝文坪;王挺;卓怀书
5.妥洛特罗贴剂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的临床观察 [J], 严梅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支气管哮喘临证心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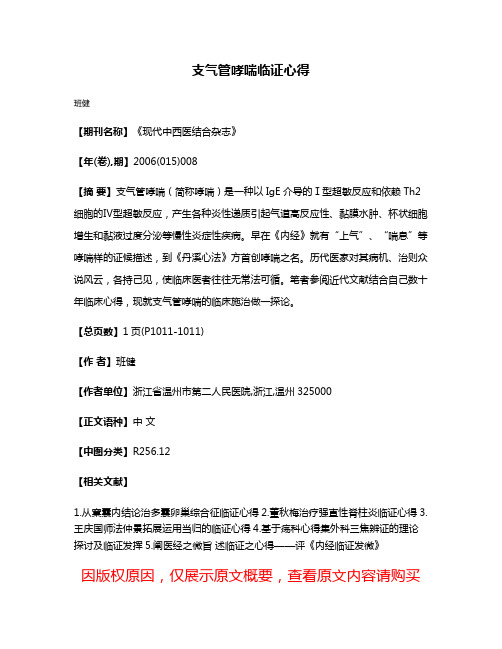
支气管哮喘临证心得
班健
【期刊名称】《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年(卷),期】2006(015)008
【摘要】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是一种以IgE介导的Ⅰ型超敏反应和依赖Th2细胞的Ⅳ型超敏反应,产生各种炎性递质引起气道高反应性、黏膜水肿、杯状细胞增生和黏液过度分泌等慢性炎症性疾病。
早在《内经》就有“上气”、“喘息”等哮喘样的证候描述,到《丹溪心法》方首创哮喘之名。
历代医家对其病机、治则众说风云,各持己见,使临床医者往往无常法可循。
笔者参阅近代文献结合自己数十年临床心得,现就支气管哮喘的临床施治做一探论。
【总页数】1页(P1011-1011)
【作者】班健
【作者单位】浙江省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浙江,温州325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256.12
【相关文献】
1.从窠囊内结论治多囊卵巢综合征临证心得
2.董秋梅治疗强直性脊柱炎临证心得
3.王庆国师法仲景拓展运用当归的临证心得
4.基于疡科心得集外科三焦辨证的理论探讨及临证发挥
5.阐医经之微旨述临证之心得——评《内经临证发微》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攻补兼施治疗小儿哮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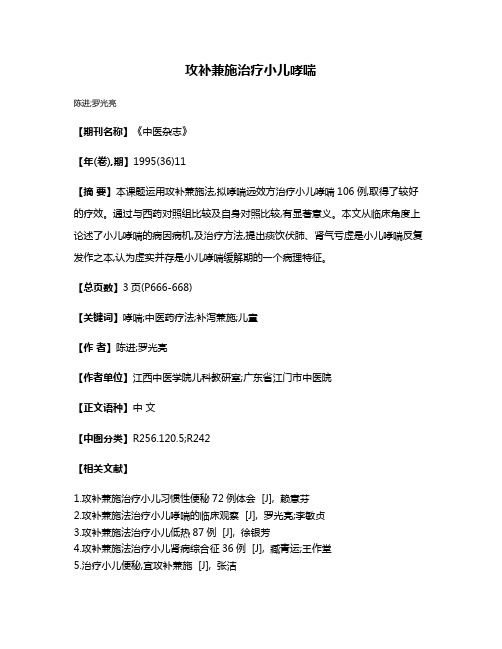
攻补兼施治疗小儿哮喘
陈进;罗光亮
【期刊名称】《中医杂志》
【年(卷),期】1995(36)11
【摘要】本课题运用攻补兼施法,拟哮喘远效方治疗小儿哮喘106例,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通过与西药对照组比较及自身对照比较,有显著意义。
本文从临床角度上论述了小儿哮喘的病因病机,及治疗方法,提出痰饮伏肺、肾气亏虚是小儿哮喘反复发作之本,认为虚实并存是小儿哮喘缓解期的一个病理特征。
【总页数】3页(P666-668)
【关键词】哮喘;中医药疗法;补泻兼施;儿童
【作者】陈进;罗光亮
【作者单位】江西中医学院儿科教研室;广东省江门市中医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256.120.5;R242
【相关文献】
1.攻补兼施治疗小儿习惯性便秘72例体会 [J], 赖意芬
2.攻补兼施法治疗小儿哮喘的临床观察 [J], 罗光亮;李敏贞
3.攻补兼施法治疗小儿低热87例 [J], 徐银芳
4.攻补兼施法治疗小儿肾病综合征36例 [J], 臧青运;王作堂
5.治疗小儿便秘,宜攻补兼施 [J], 张洁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鱼鳞病能治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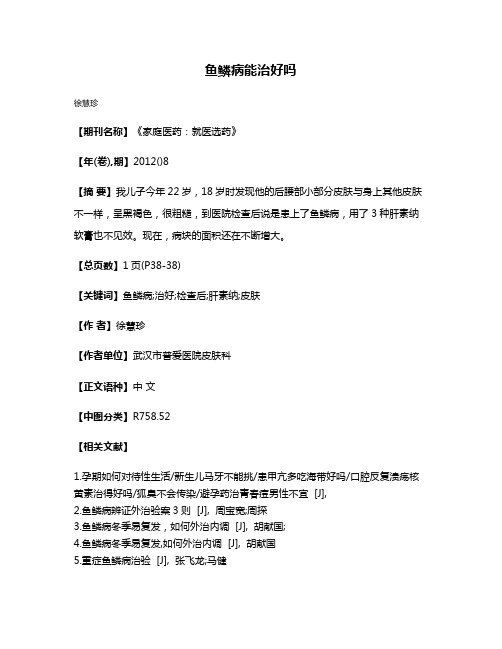
鱼鳞病能治好吗
徐慧珍
【期刊名称】《家庭医药:就医选药》
【年(卷),期】2012()8
【摘要】我儿子今年22岁,18岁时发现他的后腰部小部分皮肤与身上其他皮肤不一样,呈黑褐色,很粗糙,到医院检查后说是患上了鱼鳞病,用了3种肝素纳软膏也不见效。
现在,病块的面积还在不断增大。
【总页数】1页(P38-38)
【关键词】鱼鳞病;治好;检查后;肝素纳;皮肤
【作者】徐慧珍
【作者单位】武汉市普爱医院皮肤科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758.52
【相关文献】
1.孕期如何对待性生活/新生儿马牙不能挑/患甲亢多吃海带好吗/口腔反复溃疡核黄素治得好吗/狐臭不会传染/避孕药治青春痘男性不宜 [J],
2.鱼鳞病辨证外治验案3则 [J], 周宝宽;周探
3.鱼鳞病冬季易复发,如何外治内调 [J], 胡献国;
4.鱼鳞病冬季易复发,如何外治内调 [J], 胡献国
5.重症鱼鳞病治验 [J], 张飞龙;马健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中药超声雾化鼻吸入法治疗慢性鼻窦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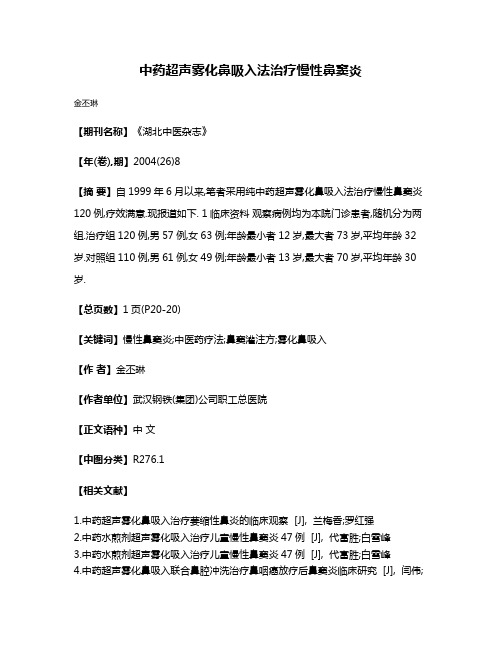
中药超声雾化鼻吸入法治疗慢性鼻窦炎
金丕琳
【期刊名称】《湖北中医杂志》
【年(卷),期】2004(26)8
【摘要】自1999年6月以来,笔者采用纯中药超声雾化鼻吸入法治疗慢性鼻窦炎120例,疗效满意.现报道如下. 1临床资料观察病例均为本院门诊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120例,男57例,女63例;年龄最小者12岁,最大者73岁,平均年龄32岁.对照组110例,男61例,女49例;年龄最小者13岁,最大者70岁,平均年龄30岁.
【总页数】1页(P20-20)
【关键词】慢性鼻窦炎;中医药疗法;鼻窦灌注方;雾化鼻吸入
【作者】金丕琳
【作者单位】武汉钢铁(集团)公司职工总医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276.1
【相关文献】
1.中药超声雾化鼻吸入治疗萎缩性鼻炎的临床观察 [J], 兰梅香;罗红强
2.中药水煎剂超声雾化吸入治疗儿童慢性鼻窦炎47例 [J], 代富胜;白雪峰
3.中药水煎剂超声雾化吸入治疗儿童慢性鼻窦炎47例 [J], 代富胜;白雪峰
4.中药超声雾化鼻吸入联合鼻腔冲洗治疗鼻咽癌放疗后鼻窦炎临床研究 [J], 闫伟;
李君辉;陈明;李玲玲;霍焱
5.中药超声雾化鼻吸入治疗萎缩性鼻炎的临床观察附:125例病例报告 [J], 卿丽华;朱力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对膝关节康复治疗的几点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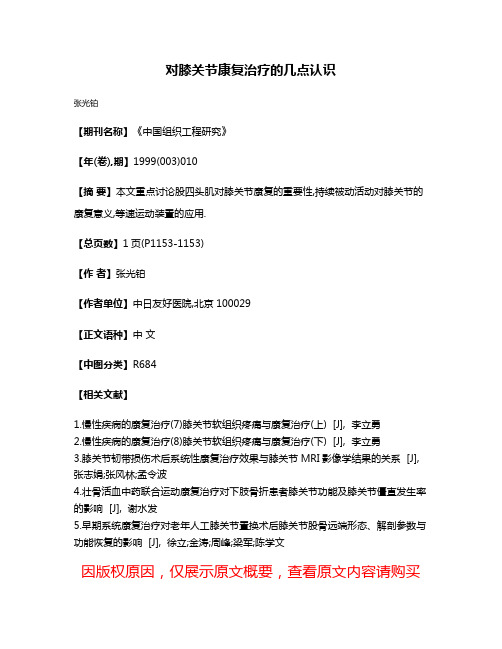
对膝关节康复治疗的几点认识
张光铂
【期刊名称】《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年(卷),期】1999(003)010
【摘要】本文重点讨论股四头肌对膝关节康复的重要性,持续被动活动对膝关节的康复意义,等速运动装置的应用.
【总页数】1页(P1153-1153)
【作者】张光铂
【作者单位】中日友好医院,北京10002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684
【相关文献】
1.慢性疾病的康复治疗(7)膝关节软组织疼痛与康复治疗(上) [J], 李立勇
2.慢性疾病的康复治疗(8)膝关节软组织疼痛与康复治疗(下) [J], 李立勇
3.膝关节韧带损伤术后系统性康复治疗效果与膝关节MRI影像学结果的关系 [J], 张志娟;张风林;孟令波
4.壮骨活血中药联合运动康复治疗对下肢骨折患者膝关节功能及膝关节僵直发生率的影响 [J], 谢水发
5.早期系统康复治疗对老年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膝关节股骨远端形态、解剖参数与功能恢复的影响 [J], 徐立;金涛;周峰;梁军;陈学文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反应性结节性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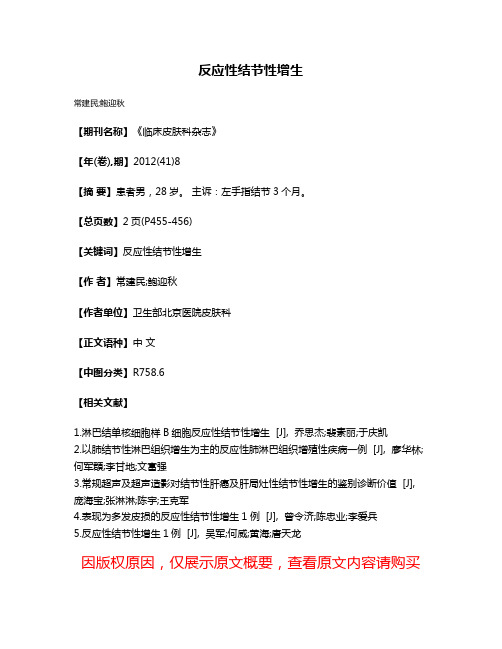
反应性结节性增生
常建民;鲍迎秋
【期刊名称】《临床皮肤科杂志》
【年(卷),期】2012(41)8
【摘要】患者男,28岁。
主诉:左手指结节3个月。
【总页数】2页(P455-456)
【关键词】反应性结节性增生
【作者】常建民;鲍迎秋
【作者单位】卫生部北京医院皮肤科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758.6
【相关文献】
1.淋巴结单核细胞样B细胞反应性结节性增生 [J], 乔思杰;裴素丽;于庆凯
2.以肺结节性淋巴组织增生为主的反应性肺淋巴组织增殖性疾病一例 [J], 廖华林;何军頵;李甘地;文富强
3.常规超声及超声造影对结节性肝癌及肝局灶性结节性增生的鉴别诊断价值 [J], 庞海宝;张淋淋;陈宇;王克军
4.表现为多发皮损的反应性结节性增生1例 [J], 曾令济;陈忠业;李爱兵
5.反应性结节性增生1例 [J], 吴军;何威;黄海;唐天龙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有关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诊治的若干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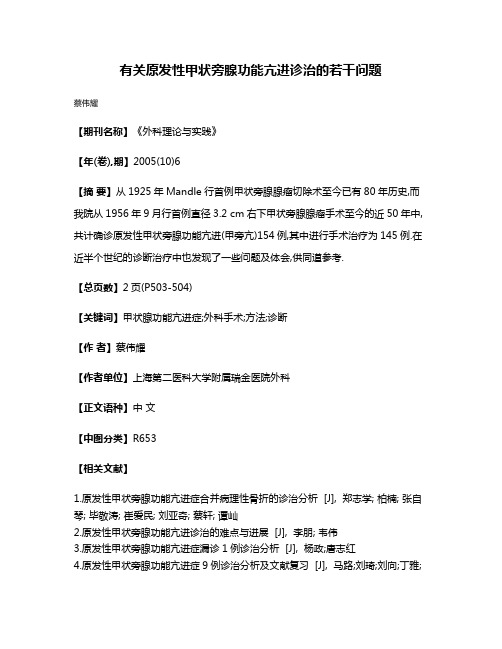
有关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诊治的若干问题
蔡伟耀
【期刊名称】《外科理论与实践》
【年(卷),期】2005(10)6
【摘要】从1925年Mandle行首例甲状旁腺腺瘤切除术至今已有80年历史,而我院从1956年9月行首例直径3.2 cm右下甲状旁腺腺瘤手术至今的近50年中,共计确诊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甲旁亢)154例,其中进行手术治疗为145例.在近半个世纪的诊断治疗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及体会,供同道参考.
【总页数】2页(P503-504)
【关键词】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外科手术;方法;诊断
【作者】蔡伟耀
【作者单位】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外科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653
【相关文献】
1.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合并病理性骨折的诊治分析 [J], 郑志学; 柏楠; 张自琴; 毕敬涛; 崔爱民; 刘亚奇; 蔡轩; 谭屾
2.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诊治的难点与进展 [J], 李朋; 韦伟
3.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漏诊1例诊治分析 [J], 杨政;唐志红
4.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9例诊治分析及文献复习 [J], 马路;刘琦;刘向;丁雅;
折占飞
5.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诊治中的焦点问题 [J], 杨帆;李平;朱大龙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中药口服及雾化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临床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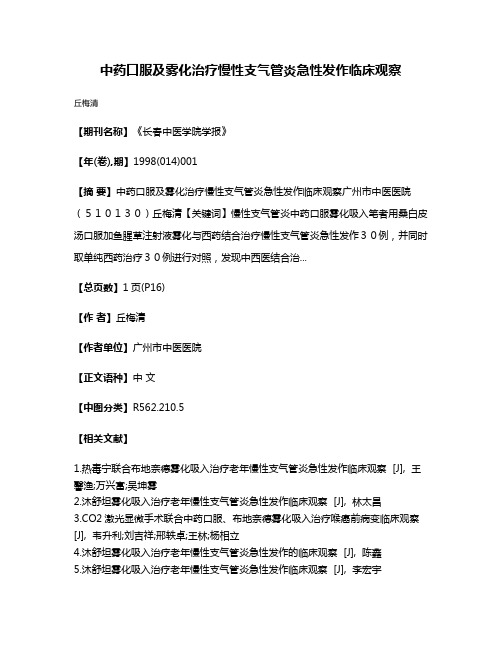
中药口服及雾化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临床观察
丘梅清
【期刊名称】《长春中医学院学报》
【年(卷),期】1998(014)001
【摘要】中药口服及雾化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临床观察广州市中医医院(510130)丘梅清【关键词】慢性支气管炎中药口服雾化吸入笔者用桑白皮汤口服加鱼腥草注射液雾化与西药结合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30例,并同时取单纯西药治疗30例进行对照,发现中西医结合治...
【总页数】1页(P16)
【作者】丘梅清
【作者单位】广州市中医医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562.210.5
【相关文献】
1.热毒宁联合布地奈德雾化吸入治疗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临床观察 [J], 王馨渔;万兴富;吴坤雾
2.沐舒坦雾化吸入治疗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临床观察 [J], 林太昌
3.CO2激光显微手术联合中药口服、布地奈德雾化吸入治疗喉癌前病变临床观察[J], 韦升利;刘吉祥;邢轶卓;王林;杨相立
4.沐舒坦雾化吸入治疗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的临床观察 [J], 陈鑫
5.沐舒坦雾化吸入治疗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临床观察 [J], 李宏宇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穴位敷贴佐治小儿喘息性支气管炎132例疗效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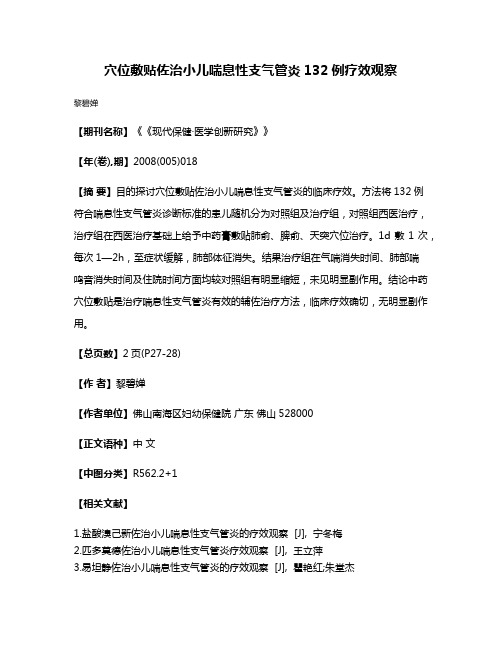
穴位敷贴佐治小儿喘息性支气管炎132例疗效观察
黎碧婵
【期刊名称】《《现代保健·医学创新研究》》
【年(卷),期】2008(005)018
【摘要】目的探讨穴位敷贴佐治小儿喘息性支气管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将132例符合喘息性支气管炎诊断标准的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及治疗组,对照组西医治疗,治疗组在西医治疗基础上给予中药膏敷贴肺俞、脾俞、天突穴位治疗。
1d敷1次,每次1—2h,至症状缓解,肺部体征消失。
结果治疗组在气喘消失时间、肺部喘
鸣音消失时间及住院时间方面均较对照组有明显缩短,未见明显副作用。
结论中药穴位敷贴是治疗喘息性支气管炎有效的辅佐治疗方法,临床疗效确切,无明显副作用。
【总页数】2页(P27-28)
【作者】黎碧婵
【作者单位】佛山南海区妇幼保健院广东佛山528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562.2+1
【相关文献】
1.盐酸溴己新佐治小儿喘息性支气管炎的疗效观察 [J], 宁冬梅
2.匹多莫德佐治小儿喘息性支气管炎疗效观察 [J], 王立萍
3.易坦静佐治小儿喘息性支气管炎的疗效观察 [J], 瞿艳红;朱堂杰
4.雾化吸入高张盐水佐治小儿喘息性支气管炎疗效观察 [J], 钟兴蓉;张玉清;廖莹
5.穴位敷贴佐治小儿喘息性支气管炎132例疗效观察 [J], 黎碧婵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请您诊断 病例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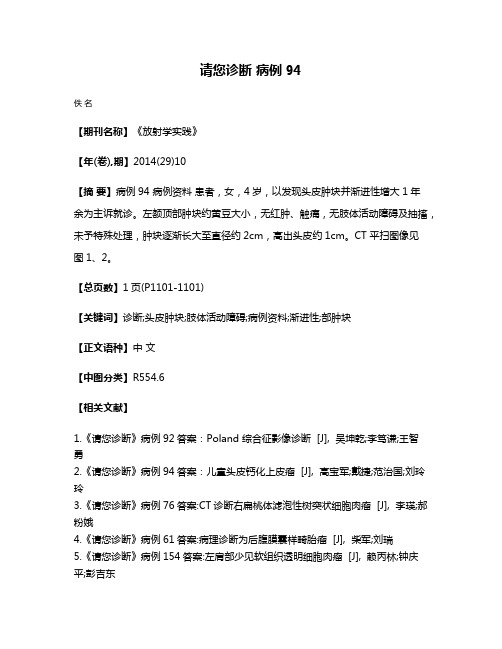
请您诊断病例94
佚名
【期刊名称】《放射学实践》
【年(卷),期】2014(29)10
【摘要】病例94 病例资料患者,女,4岁,以发现头皮肿块并渐进性增大1年
余为主诉就诊。
左额顶部肿块约黄豆大小,无红肿、触痛,无肢体活动障碍及抽搐,未予特殊处理,肿块逐渐长大至直径约2cm,高出头皮约1cm。
CT 平扫图像见
图1、2。
【总页数】1页(P1101-1101)
【关键词】诊断;头皮肿块;肢体活动障碍;病例资料;渐进性;部肿块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554.6
【相关文献】
1.《请您诊断》病例92答案:Poland 综合征影像诊断 [J], 吴坤乾;李笃谦;王智
勇
2.《请您诊断》病例94答案:儿童头皮钙化上皮瘤 [J], 高宝军;戴捷;范治国;刘玲玲
3.《请您诊断》病例76答案:CT诊断右扁桃体滤泡性树突状细胞肉瘤 [J], 李瑛;郝粉娥
4.《请您诊断》病例61答案:病理诊断为后腹膜囊样畸胎瘤 [J], 柴军;刘瑞
5.《请您诊断》病例154答案:左肩部少见软组织透明细胞肉瘤 [J], 赖丙林;钟庆平;彭吉东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环甲膜注射地塞米松、利多卡因治疗慢性咳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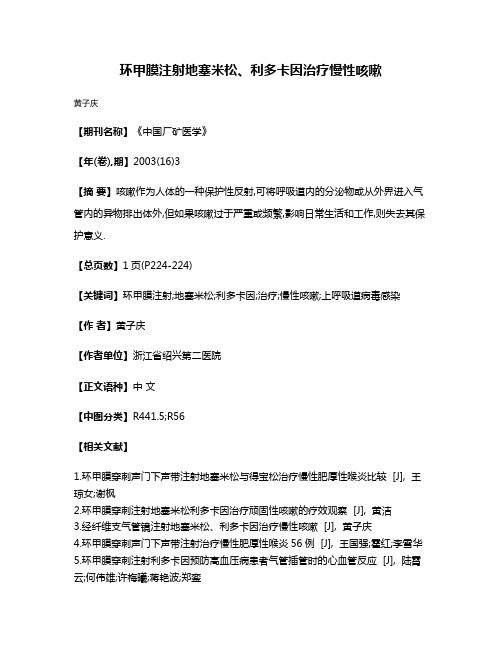
环甲膜注射地塞米松、利多卡因治疗慢性咳嗽
黄子庆
【期刊名称】《中国厂矿医学》
【年(卷),期】2003(16)3
【摘要】咳嗽作为人体的一种保护性反射,可将呼吸道内的分泌物或从外界进入气管内的异物排出体外,但如果咳嗽过于严重或频繁,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则失去其保护意义.
【总页数】1页(P224-224)
【关键词】环甲膜注射;地塞米松;利多卡因;治疗;慢性咳嗽;上呼吸道病毒感染【作者】黄子庆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第二医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441.5;R56
【相关文献】
1.环甲膜穿刺声门下声带注射地塞米松与得宝松治疗慢性肥厚性喉炎比较 [J], 王琼女;谢枫
2.环甲膜穿刺注射地塞米松利多卡因治疗顽固性咳嗽的疗效观察 [J], 黄洁
3.经纤维支气管镜注射地塞米松、利多卡因治疗慢性咳嗽 [J], 黄子庆
4.环甲膜穿刺声门下声带注射治疗慢性肥厚性喉炎56例 [J], 王国强;霍红;李雪华
5.环甲膜穿刺注射利多卡因预防高血压病患者气管插管时的心血管反应 [J], 陆霄云;何伟雄;许梅曦;蒋艳波;郑銮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探讨丙种球蛋白结合阿司匹林治疗小儿川崎病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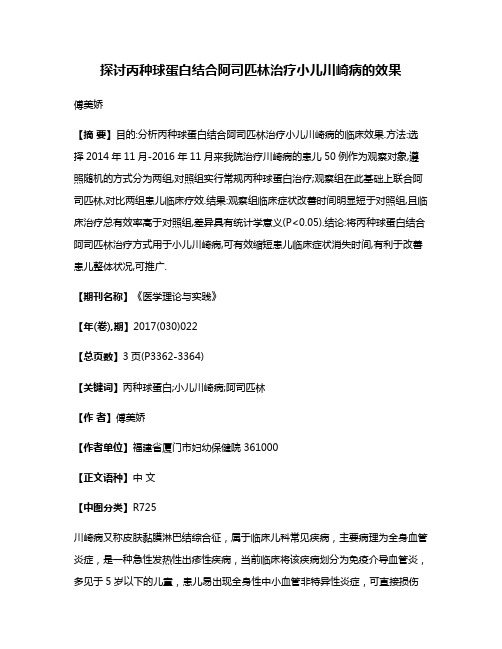
探讨丙种球蛋白结合阿司匹林治疗小儿川崎病的效果傅美娇【摘要】目的:分析丙种球蛋白结合阿司匹林治疗小儿川崎病的临床效果.方法:选择2014年11月-2016年11月来我院治疗川崎病的患儿50例作为观察对象,遵照随机的方式分为两组,对照组实行常规丙种球蛋白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联合阿司匹林,对比两组患儿临床疗效.结果:观察组临床症状改善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且临床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将丙种球蛋白结合阿司匹林治疗方式用于小儿川崎病,可有效缩短患儿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有利于改善患儿整体状况,可推广.【期刊名称】《医学理论与实践》【年(卷),期】2017(030)022【总页数】3页(P3362-3364)【关键词】丙种球蛋白;小儿川崎病;阿司匹林【作者】傅美娇【作者单位】福建省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361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R725川崎病又称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征,属于临床儿科常见疾病,主要病理为全身血管炎症,是一种急性发热性出疹性疾病,当前临床将该疾病划分为免疫介导血管炎,多见于5岁以下的儿童,患儿易出现全身性中小血管非特异性炎症,可直接损伤患儿的冠状动脉,导致冠状动脉瘤、冠状动脉扩张等问题,严重的情况下还会威胁到患儿生命安全。
但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川崎病的早期诊断率较低,治疗方案也存在较大的争议,基于此,本文重点探究丙种球蛋白结合阿司匹林治疗小儿川崎病的临床效果,数据分析整理如下。
川崎病属于儿科临床多发出疹性、发热性疾病[4],属于全身性中小血管炎症,目前尚未明确其发病机制,患儿表现为黏膜充血、皮疹、发热、手足肿胀、肛周脱皮等,且伴有不同程度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异常增加,血小板、C反应蛋白提升,或者血沉速度加快等,同时会出现冠状动脉病变[5]。
因患儿年龄较小,免疫力、抵抗力较低,易引发严重的冠状动脉瘤、冠状动脉扩张等问题,从而威胁到患儿正常的生长发育。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傅树楷医生(第二部分)2011.10.3 7.31pm 星期一-Teo Soh lung 六七十年代内安法下的政扣者没有得到适当的医疗服务。
生病了的政扣者被当做像生病了的畜牲一样关在笼子里。
曾福华先生患了晚期癌症是由同是政扣者的傅树楷医生诊断出来的,不是狱医。
监狱当局和医生不但没有给于适当的治疗,甚至冷漠无情,置之不理。
曾福华先生是一名散工。
他于1971年2月17日被捕。
1978年3月13日,政治部知道他已濒临死亡,才将他释放。
七年的时间,狱医没有发现曾先生的病情。
即使在已诊断出他已患上晚期癌症,他们还是拒绝送他去医院治疗。
只是在政扣者们的压力之下,他才被送去医院。
为什么政治部要释放已经病危的曾先生呢?大概是因为他们不要有人死在牢中,还得面对法医调查,会使他在狱中受到的虐待曝光。
曾先生于1978年3月26日病逝,即在他被释放的13天后。
政治部对患病政扣者态度之恶劣是难以置信的。
傅医生自己生病时就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
狱医没能诊断出他的病症,差点让他丢失性命。
幸运的是傅医生来自一个医生世家,他才有幸活到今天。
内政部现在拒绝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知道很多前政扣者受到政治部人员极大的伤害,这样一个委员会会让他们面对赔偿的法律程序。
以下是傅医生2011年9月13日在新加坡发表讲话的第二部分。
明月湾中心(MCC)在这个8间牢房的建筑物里,我被单独监禁了一年。
这是明月湾中心里最大的一座。
后来,我又被转去一座较小的,有5间牢房,位于中心最西部的尽头,被行政楼与其他的隔开。
我们私下都知道这是最“坚固”的一座。
我发现我和朋友在一起了。
曾福华、何标、谢太宝等人预先知道我要来,都站在栅栏后欢迎我。
经过多个月的单独监禁之后,又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感觉真好。
我有一个原则就是不去看生病了的政扣者,因为我无法给他们治疗。
我经常坚持他们必须看狱医。
一天,曾福华说他肚子痛。
N.Singh 医生来了,就在院子里的走廊上给他作检查,很随便的检查。
医生开了一些抗酸剂,下午送来。
晚上十点左右,当我们又都被锁进我们各自的牢房后,福华叫我,说他的肚痛吃了药没改善,更痛了。
福华是一个顽强的人。
在牢房被打得厉害时,他甚至抄起椅子,准备同政治部那些残暴的打手决一死战。
一个对死已无所畏惧的人,你还能拿他怎么样呢?于是政治部的头头只好出面,识相地吩咐那些打手停止使用酷刑。
福华是华中学运的领导人之一。
当警察追捕这些人时,他不得不逃亡。
他虽然出身富裕家庭,却对逃亡期间的贫困日子毫无怨言。
当他从他的牢房喊我时,我知道他一定是痛得很厉害了。
但我能做什么呢?只好告诉他明早看守一来开牢房,我第一件事一定是去看他。
在拂晓的朦胧中,牢房里显得更昏暗,我还是看出他虽然没有出现黄疸,但可以摸到肚子里有一个巨大的肿块。
他一定是意识到我在犹豫,所以接着说:“树楷,不用担心,告诉我真相。
我能接受的。
”我说,他已患上晚期癌症了。
我写了一封信给监狱负责人。
我不可以联络狱医。
福华被送去中央医院,发现已不宜动手术,又再被送回我们的牢房。
回到我们那座牢房时,监狱负责人要将他送去樟宜监狱的医院,那地方对患病的政扣者来说是个大笼子,不是医院。
在我们牢房这儿,我们还能给他更好的照顾。
我们都反对将福华送去监狱医院,并准备为此进行斗争。
狱吏推着轮椅来了,福华不肯去。
狱吏只好返回去告诉负责人。
又过了几天,监狱方面发慈悲,同意将福华送回中央医院里的监狱部门。
在那儿一个星期左右,已病危的他才被释放回家。
我又被送回去惠德里扣留中心关了几个月。
这次是被单独关在一个较大的附有一个小院子(供运动用)的牢房。
你可同你的邻居喊话,可你看不见他们。
1961年我在竹脚产科医院供职时,一个部门副主任Dr.Toh Siang Wah 来看我。
我们聊了一会儿,他决定要送我一部圣经,还要安排人来和我一起阅读。
而这个人就是惠德里的一名高级官员。
我没反对,只是坚持一定要从第一页读起,而他对创世纪一点儿都不懂。
他们一定是发现我的解释更合理,这个课程很快就结束了。
又过了一些时间,我被带去更衣室,让我换上被捕时穿进来的衣服。
换上后像样多了,我则纳闷他们要带我上哪儿呢?很快,我就被带到监狱职员的休息室。
桌上摆着茶点,两名曾和我在医院共事的医生——Dr.Teo 和Dr. Nagulendran 热情地问候我,让我大感意外。
这两人都是板桥医院的精神病专家。
他们解释说,他们被要求来指导一项关于政扣者精神状况的测试。
显然是要建立一份政扣者精神状况的病历,就如我们大家都有的心脏病历,关节病历等等。
这样一来,在筛选几百名实习生去进一步深造时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和金钱。
也许惠德里中心以后将作为一间精神病医院而著名,因为其扣留犯都成了精神病人。
他们给了一些问卷让我回答,题目的范围从智力测验到问我是不是家里最受爱戴的人。
我不准备填写这些问卷。
Dr.Nagulendran 说这项研究是绝对秘密的,与政治完全没有关系。
再说,我可以自由选择参加或拒绝参加。
我品尝着糕点,谢谢他们让我很高兴见到老朋友,并且告诉他们我谢绝参加。
我在想,其他的政扣者会怎样做,他们很大可能是参加,但会尽可能给予不真实的答案。
后来,我发现我的猜测是正确的。
然而,大约十天后,我被叫去审讯室。
一个警长单独来审问。
他板着脸,一开始就告诉我说,我因不参加那项测试将受惩罚。
我微笑着问他是怎么知道我没有参加,因为那些医生已向我保证,整个过程是保密的,秘密的。
他无法回答。
接着我又突然被送回明月湾,回到和谢太宝、何标一起的那座牢房。
与死神擦身而过最后于1980年,我又一次被送回惠德里。
这次也是把我一人关在一个大牢房里。
大概一个星期一次,把我传去审讯室谈谈话,关于健康课题或读报。
1981年,一个清晨,我从头顶一直到颈项剧烈地疼痛起来。
我肯定是昏倒在地了,然后又醒过来,听到看守发现我倒在地上。
大约凌晨四时半,他叫来值班的警长。
他们进了牢房,查问我的病情。
我说我必须住院检查,问题应该是头颅内压力上升。
他们打电话给主管,然后告诉我,他们提议送我去樟宜监狱。
那边的医生会护理我。
那天一大早,我就被载去樟宜医院,一路经受剧烈的头痛和不停地呕吐。
值班的男护士,人很好。
他和我说,已通知了Dr N.Singh ,他早上一上班会首先第一个看我。
这时大约早上六时半。
我被批准进入监狱医院。
这是一间大屋子,入口处两边各有一个笼子。
我被关进其中一个。
他给了我两粒班那杜,我躺在床上,感觉好一点了。
这么碰巧的是,那天早上刚好是我的家庭探访日。
我的家人到了惠德里扑空又赶来樟宜监狱。
沿着狭窄的走廊到探访室,这一路我都在不停地呕吐,情况糟透了。
这里没有对讲机,我直接同家人讲了我的情况以及我为什么被送来樟宜监狱医院。
Dr. Singh 有来看我吗?没有。
我父亲很担心。
回到家他就打电话给我的兄弟,让他联络一个在卫生部工作的朋友。
这才安排了樟宜中央医院的一个医生来看我。
大约下午三点半,那个内科医生来了。
他建议我转去樟宜中央医院。
在监牢里这么多年,现在有这么舒服的床和这么好的被单是让人高兴的。
可我已精疲力竭,没能真正享受这一新的环境。
神经科医生认为我需要做一个颅内透视,所以又将我送到陈笃生医院。
他们做了各种的透视,可没得出任何诊断结论。
在我的鼻腔和前额之间发现一个肿瘤。
最后的决定是让神经外科医生来作手术,时间定在星期一。
我被关在一个冷气病房里近一星期。
在进行预定的手术前,是得先在冷气室里呆上一天左右。
我咳出一大团黏糊糊的东西。
结论现在已很明显,我的前额一直到面颊有一个肿瘤,而且在手术之前爆裂了!现在我需要的不是打开头颅而是耳鼻喉科医生被叫来给我动鼻窦手术。
我长期的鼻窦炎已恶化了。
手术还算顺利。
第三天,耳鼻喉医生将塞在鼻腔里止血的纱布拿出来时,那持续受到肿瘤挤压的鼻腔壁变得很薄以至完全暴露,导致一条附在上面的动脉血管也随着那块纱布被拉掉了。
结果大脑失去血的供应,我昏迷过去。
这时一个医生赶紧给我做颈动脉结扎。
然后,我的心脏停止跳动。
我那可怜的朋友,那个耳鼻喉科医生发狂地按压我的胸部,做人工急救。
过后我被告知,这救了我一命。
可我在复原时感到肋骨断裂般的剧痛。
留给我的严重后遗症是视网膜缺氧和眼窝变形。
但感谢我的朋友们,我还活着。
释放1981年,在医院住了三个月后,我又继续被扣留了两年。
送回惠德里中心进行康复治疗。
1982年8月,他们说要释放我,但警告说我不可以批评任何人,不允许召开记者会来谈论我的案件和对我的指控,政治部将会以我的名义发布一项声明,他们甚至还打电话威胁我的父母说,如果我召开记者会,就立刻会被重新逮捕。
而且不管我签不签自白书,我都得遵守例常的限制令。
我的回答是,“我是一个公民,如果记者们来敲我的门,我会请他们进屋。
你们最好叫人守在我的门外,赶那些记者走。
”我绝对拒绝任何没有我的签名却乱说是我的声明。
我于1982年8月26日被释放,未经审判在李的监牢里被关了17年。
开始一段日子里没有记者来看我。
后来有一人自称是来自Associated Press 的Mr.DSilva来我的家。
我告诉他对我的限制令以及谈论我的案情将遭引关押的威胁,他可据此得出他自己的结论。
后来我又遇见他。
他告诉我说。
那次采访后,那晚他去AlbertStreet吃东西。
有人拍他的肩膀叫他跟那政治部的官员去惠德里中心。
他告诉他们采访时我说的一切都已录在他的卡带里,他离开后他们可以自己去看。
他们表示没有兴趣。
他被带去一个职员的会议室,让他坐在那儿整整一个夜晚。
第二天早早,他被要求签一项声明,说他在那儿没有受到虐待后,才让他离开。
我想这是为恐吓那些外国记者,因为他们比他们在本地的同行勇敢。
我还是不断地受到骚扰。
例如,当我受雇于机场里的一个诊所时,他们不允许我经过停机坪。
那些公务员们无法想象,我只是同他们说打电话给我诊所的老板——一个英国护士,跟她说我被拒绝进入停机坪,如果出现什么紧急情况,我不负任何责任。
几个电话后,我的准证就办妥了。
在那机场诊所服务了很短的时间。
1989年移民加拿大之前,我在实龙岗路上段开了一阵子私人诊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