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母
在童年中,外祖母令我印象深刻,写300字触动和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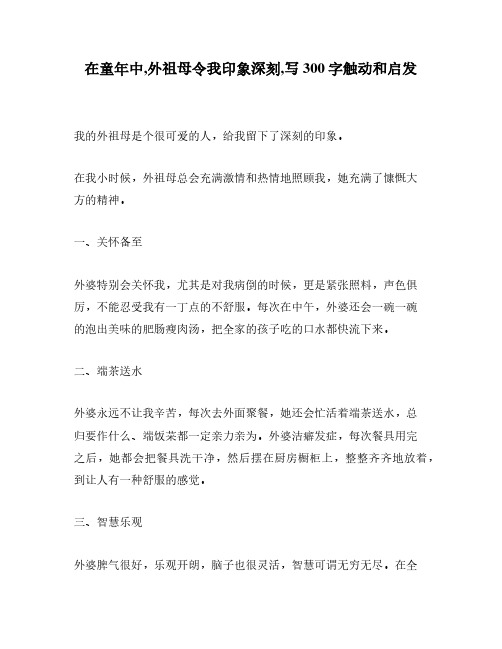
在童年中,外祖母令我印象深刻,写300字触动和启发
我的外祖母是个很可爱的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我小时候,外祖母总会充满激情和热情地照顾我,她充满了慷慨大
方的精神。
一、关怀备至
外婆特别会关怀我,尤其是对我病倒的时候,更是紧张照料,声色俱厉,不能忍受我有一丁点的不舒服。
每次在中午,外婆还会一碗一碗
的泡出美味的肥肠瘦肉汤,把全家的孩子吃的口水都快流下来。
二、端茶送水
外婆永远不让我辛苦,每次去外面聚餐,她还会忙活着端茶送水,总
归要作什么、端饭菜都一定亲力亲为。
外婆洁癖发症,每次餐具用完
之后,她都会把餐具洗干净,然后摆在厨房橱柜上,整整齐齐地放着,到让人有一种舒服的感觉。
三、智慧乐观
外婆脾气很好,乐观开朗,脑子也很灵活,智慧可谓无穷无尽。
在全
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外婆总会传给我们很多睿智的话语,也会天南海北远游的带着我们去探索世界,在探索中洞悉人生。
四、爱心无边
外婆爱心无边,有趣又有智慧,她给了我很多激励与力量,让我在大山里能够奔跑,在我踉跄拖拉的日子里看到阳光,在人生荆棘路上能够坚定的脚步。
更重要的是,外婆给了我和家人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幸福和亲情。
功德无量,总之,外婆给我的最大感触是传承了一股深厚的爱心,总能让我触碰到最原始的温暖,给我最真实的感受。
无论生活如何,给我弥足珍贵的时光,我们都会记得,外祖母的爱永远护佑着我们。
我的外祖母作文9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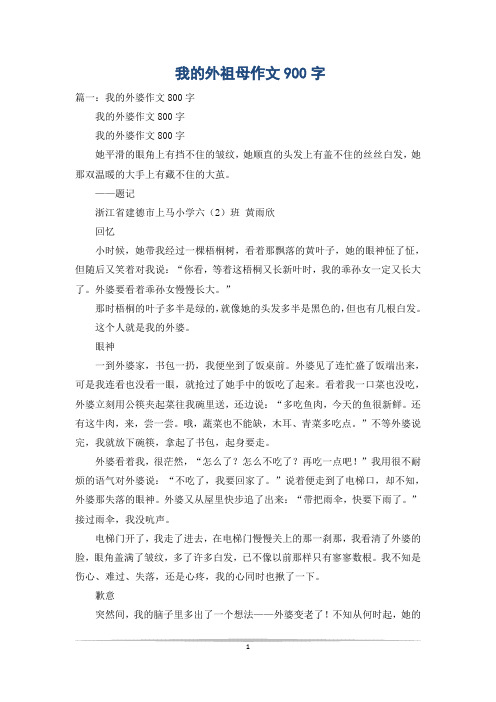
我的外祖母作文900字篇一:我的外婆作文800字我的外婆作文800字我的外婆作文800字她平滑的眼角上有挡不住的皱纹,她顺直的头发上有盖不住的丝丝白发,她那双温暖的大手上有藏不住的大茧。
——题记浙江省建德市上马小学六(2)班黄雨欣回忆小时候,她带我经过一棵梧桐树,看着那飘落的黄叶子,她的眼神怔了怔,但随后又笑着对我说:“你看,等着这梧桐又长新叶时,我的乖孙女一定又长大了。
外婆要看着乖孙女慢慢长大。
”那时梧桐的叶子多半是绿的,就像她的头发多半是黑色的,但也有几根白发。
这个人就是我的外婆。
眼神一到外婆家,书包一扔,我便坐到了饭桌前。
外婆见了连忙盛了饭端出来,可是我连看也没看一眼,就抢过了她手中的饭吃了起来。
看着我一口菜也没吃,外婆立刻用公筷夹起菜往我碗里送,还边说:“多吃鱼肉,今天的鱼很新鲜。
还有这牛肉,来,尝一尝。
哦,蔬菜也不能缺,木耳、青菜多吃点。
”不等外婆说完,我就放下碗筷,拿起了书包,起身要走。
外婆看着我,很茫然,“怎么了?怎么不吃了?再吃一点吧!”我用很不耐烦的语气对外婆说:“不吃了,我要回家了。
”说着便走到了电梯口,却不知,外婆那失落的眼神。
外婆又从屋里快步追了出来:“带把雨伞,快要下雨了。
”接过雨伞,我没吭声。
电梯门开了,我走了进去,在电梯门慢慢关上的那一刹那,我看清了外婆的脸,眼角盖满了皱纹,多了许多白发,已不像以前那样只有寥寥数根。
我不知是伤心、难过、失落,还是心疼,我的心同时也揪了一下。
歉意突然间,我的脑子里多出了一个想法——外婆变老了!不知从何时起,她的1眼角盖满了皱纹,不知从何时起,她的白发增多了许多,也不知是何时起,我对她的话越来越反感。
一个说着要看着我长大的人越来越老了,心中真不是滋味。
过去与外婆相处的情景一遍一遍地从我的脑海中浮现,对外婆的歉意一阵一阵地袭来,心中的酸楚湿了我的眼眶。
我立刻按下开门键,冲了出去,外婆转身看见冲出来的我,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说道:“怎么了?”看着外婆,原本想说的话仿佛卡在了喉咙里,但最后终于憋出了一句:“外婆,我要吃饭。
童年外祖母的外貌描写

童年外祖母的外貌描写
我的外祖母是一个非常美丽和优雅的女性。
她虽然已经年过六旬,但她保持着年轻的容貌和精神状态。
她身材苗条,高挑而匀称,稍显苍老的皮肤仍然光滑细腻。
她那浓密的银白色头发经过精心梳理,时而盘起来,时而披散在肩上,给人一种优雅而庄重的感觉。
外祖母有一双明亮而炯炯有神的眼睛,它们是深邃的褐色,透露出智慧和温暖。
每当她注视着我,我的内心都感到一种安慰和宽慰,仿佛她的目光能够洞悉我的内心世界。
她的面容线条柔和而和谐,没有岁月带来的皱纹和斑点。
她的嘴唇红润饱满,总是挂着温和而慈祥的微笑。
这个微笑是那么温暖和包容,让人感受到她对家人的深深关爱和无尽的宽容。
她的穿着总是考究而得体,无论是正式的场合还是休闲的时候,她总能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气质和风格。
她喜欢穿上华丽的礼服和珠宝,完美地展现了她的高贵和品味。
我的外祖母是一个像画中仙女般的存在。
她那高贵的气质、温和的笑容以及对家人无尽的关爱让她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我对她的景仰和尊敬将永远不变。
我的外祖母作文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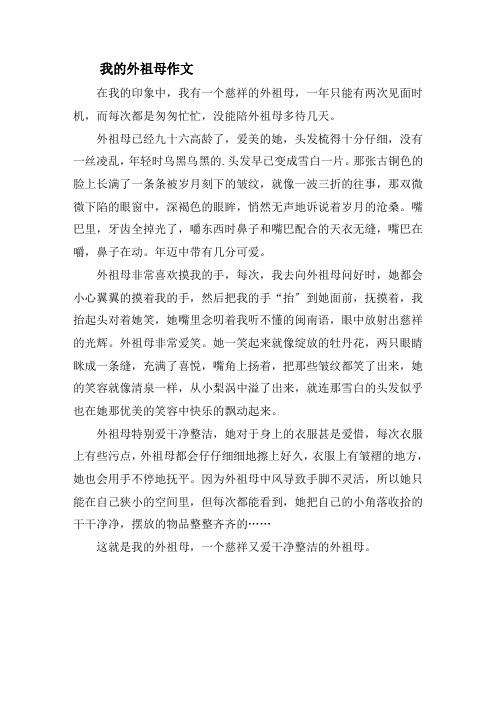
我的外祖母作文
在我的印象中,我有一个慈祥的外祖母,一年只能有两次见面时机,而每次都是匆匆忙忙,没能陪外祖母多待几天。
外祖母已经九十六高龄了,爱美的她,头发梳得十分仔细,没有一丝凌乱,年轻时乌黑乌黑的.头发早已变成雪白一片。
那张古铜色的脸上长满了一条条被岁月刻下的皱纹,就像一波三折的往事,那双微微下陷的眼窗中,深褐色的眼眸,悄然无声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嘴巴里,牙齿全掉光了,嚼东西时鼻子和嘴巴配合的天衣无缝,嘴巴在嚼,鼻子在动。
年迈中带有几分可爱。
外祖母非常喜欢摸我的手,每次,我去向外祖母问好时,她都会小心翼翼的摸着我的手,然后把我的手“抬〞到她面前,抚摸着,我抬起头对着她笑,她嘴里念叨着我听不懂的闽南语,眼中放射出慈祥的光辉。
外祖母非常爱笑。
她一笑起来就像绽放的牡丹花,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缝,充满了喜悦,嘴角上扬着,把那些皱纹都笑了出来,她的笑容就像清泉一样,从小梨涡中溢了出来,就连那雪白的头发似乎也在她那优美的笑容中快乐的飘动起来。
外祖母特别爱干净整洁,她对于身上的衣服甚是爱惜,每次衣服上有些污点,外祖母都会仔仔细细地擦上好久,衣服上有皱褶的地方,她也会用手不停地抚平。
因为外祖母中风导致手脚不灵活,所以她只能在自己狭小的空间里,但每次都能看到,她把自己的小角落收拾的干干净净,摆放的物品整整齐齐的……
这就是我的外祖母,一个慈祥又爱干净整洁的外祖母。
我的外祖母英语作文小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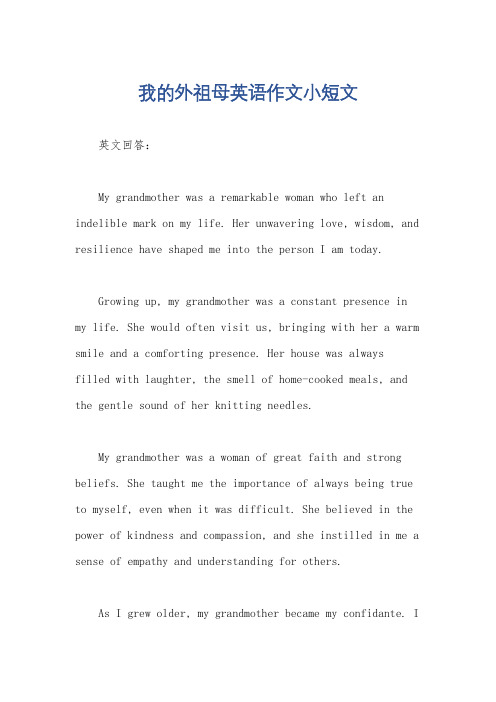
我的外祖母英语作文小短文英文回答:My grandmother was a remarkable woman who left an indelible mark on my life. Her unwavering love, wisdom, and resilience have shaped me into the person I am today.Growing up, my grandmother was a constant presence in my life. She would often visit us, bringing with her a warm smile and a comforting presence. Her house was alwaysfilled with laughter, the smell of home-cooked meals, and the gentle sound of her knitting needles.My grandmother was a woman of great faith and strong beliefs. She taught me the importance of always being true to myself, even when it was difficult. She believed in the power of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and she instilled in me a sense of empathy and understanding for others.As I grew older, my grandmother became my confidante. Iwould often turn to her for advice or just to talk about my day. She always had a listening ear and wise words to share. Her unwavering support and belief in me gave me the confidence to pursue my dreams.My grandmother was also an avid reader and had apassion for learning. She encouraged me to read widely andto explore the world around me. She taught me theimportance of curiosity and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In her later years, my grandmother faced numerous physical challenges. However, her spirit never wavered. She remained positive, resilient, and always thankful for thelife she had lived.My grandmother passed away peacefully a few years ago. Her loss left a deep void in my heart, but her memory continues to guide and inspire me. I am forever gratefulfor the love, wisdom, and strength she shared with me.中文回答:我的外祖母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她为我的生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描写外祖母的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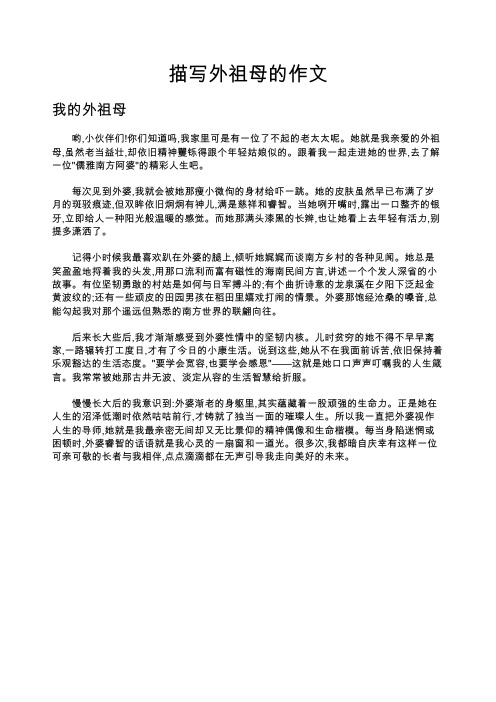
描写外祖母的作文我的外祖母哟,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我家里可是有一位了不起的老太太呢。
她就是我亲爱的外祖母,虽然老当益壮,却依旧精神矍铄得跟个年轻姑娘似的。
跟着我一起走进她的世界,去了解一位"儒雅南方阿婆"的精彩人生吧。
每次见到外婆,我就会被她那瘦小微佝的身材给吓一跳。
她的皮肤虽然早已布满了岁月的斑驳痕迹,但双眸依旧炯炯有神儿,满是慈祥和睿智。
当她咧开嘴时,露出一口整齐的银牙,立即给人一种阳光般温暖的感觉。
而她那满头漆黑的长辫,也让她看上去年轻有活力,别提多潇洒了。
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趴在外婆的腿上,倾听她娓娓而谈南方乡村的各种见闻。
她总是笑盈盈地捋着我的头发,用那口流利而富有磁性的海南民间方言,讲述一个个发人深省的小故事。
有位坚韧勇敢的村姑是如何与日军搏斗的;有个曲折诗意的龙泉溪在夕阳下泛起金黄波纹的;还有一些顽皮的田园男孩在稻田里嬉戏打闹的情景。
外婆那饱经沧桑的嗓音,总能勾起我对那个遥远但熟悉的南方世界的联翩向往。
后来长大些后,我才渐渐感受到外婆性情中的坚韧内核。
儿时贫穷的她不得不早早离家,一路辗转打工度日,才有了今日的小康生活。
说到这些,她从不在我面前诉苦,依旧保持着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
"要学会宽容,也要学会感恩"——这就是她口口声声叮嘱我的人生箴言。
我常常被她那古井无波、淡定从容的生活智慧给折服。
慢慢长大后的我意识到:外婆渐老的身躯里,其实蕴藏着一股顽强的生命力。
正是她在人生的沼泽低潮时依然咕咕前行,才铸就了独当一面的璀璨人生。
所以我一直把外婆视作人生的导师,她就是我最亲密无间却又无比景仰的精神偶像和生命楷模。
每当身陷迷惘或困顿时,外婆睿智的话语就是我心灵的一扇窗和一道光。
很多次,我都暗自庆幸有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与我相伴,点点滴滴都在无声引导我走向美好的未来。
童年中表现外祖母以直报怨的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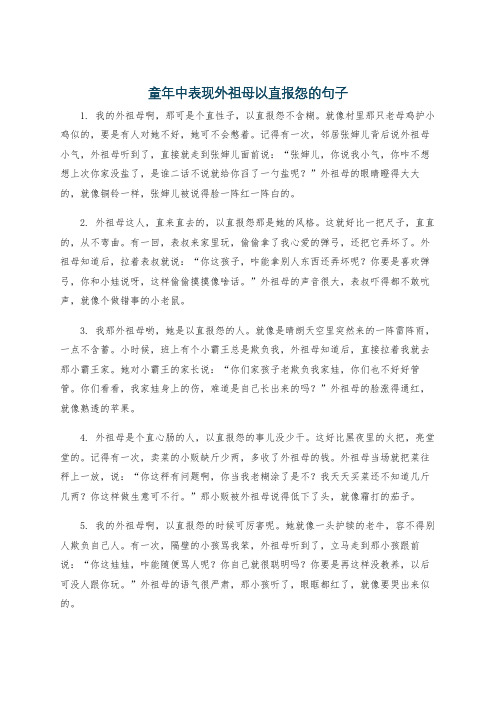
童年中表现外祖母以直报怨的句子1. 我的外祖母啊,那可是个直性子,以直报怨不含糊。
就像村里那只老母鸡护小鸡似的,要是有人对她不好,她可不会憋着。
记得有一次,邻居张婶儿背后说外祖母小气,外祖母听到了,直接就走到张婶儿面前说:“张婶儿,你说我小气,你咋不想想上次你家没盐了,是谁二话不说就给你舀了一勺盐呢?”外祖母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就像铜铃一样,张婶儿被说得脸一阵红一阵白的。
2. 外祖母这人,直来直去的,以直报怨那是她的风格。
这就好比一把尺子,直直的,从不弯曲。
有一回,表叔来家里玩,偷偷拿了我心爱的弹弓,还把它弄坏了。
外祖母知道后,拉着表叔就说:“你这孩子,咋能拿别人东西还弄坏呢?你要是喜欢弹弓,你和小娃说呀,这样偷偷摸摸像啥话。
”外祖母的声音很大,表叔吓得都不敢吭声,就像个做错事的小老鼠。
3. 我那外祖母哟,她是以直报怨的人。
就像是晴朗天空里突然来的一阵雷阵雨,一点不含蓄。
小时候,班上有个小霸王总是欺负我,外祖母知道后,直接拉着我就去那小霸王家。
她对小霸王的家长说:“你们家孩子老欺负我家娃,你们也不好好管管。
你们看看,我家娃身上的伤,难道是自己长出来的吗?”外祖母的脸涨得通红,就像熟透的苹果。
4. 外祖母是个直心肠的人,以直报怨的事儿没少干。
这好比黑夜里的火把,亮堂堂的。
记得有一次,卖菜的小贩缺斤少两,多收了外祖母的钱。
外祖母当场就把菜往秤上一放,说:“你这秤有问题啊,你当我老糊涂了是不?我天天买菜还不知道几斤几两?你这样做生意可不行。
”那小贩被外祖母说得低下了头,就像霜打的茄子。
5. 我的外祖母啊,以直报怨的时候可厉害呢。
她就像一头护犊的老牛,容不得别人欺负自己人。
有一次,隔壁的小孩骂我笨,外祖母听到了,立马走到那小孩跟前说:“你这娃娃,咋能随便骂人呢?你自己就很聪明吗?你要是再这样没教养,以后可没人跟你玩。
”外祖母的语气很严肃,那小孩听了,眼眶都红了,就像要哭出来似的。
6. 外祖母这个人,她的以直报怨就像镜子一样,清清楚楚地反映着是非。
我的外祖母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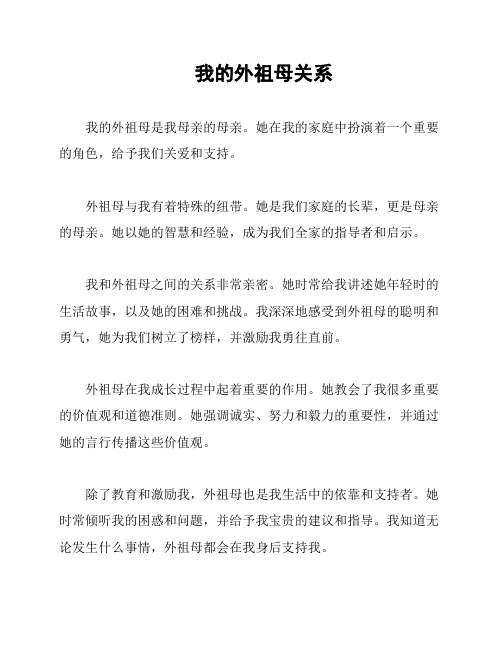
我的外祖母关系
我的外祖母是我母亲的母亲。
她在我的家庭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给予我们关爱和支持。
外祖母与我有着特殊的纽带。
她是我们家庭的长辈,更是母亲的母亲。
她以她的智慧和经验,成为我们全家的指导者和启示。
我和外祖母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
她时常给我讲述她年轻时的生活故事,以及她的困难和挑战。
我深深地感受到外祖母的聪明和勇气,她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并激励我勇往直前。
外祖母在我成长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她教会了我很多重要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
她强调诚实、努力和毅力的重要性,并通过她的言行传播这些价值观。
除了教育和激励我,外祖母也是我生活中的依靠和支持者。
她时常倾听我的困惑和问题,并给予我宝贵的建议和指导。
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外祖母都会在我身后支持我。
总的来说,我的外祖母在我的生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她是我尊敬和敬爱的长辈,是我的智者和引导者。
我感激她给予我的关爱和支持,我会努力成为她自豪的后代。
我的外祖母英语作文小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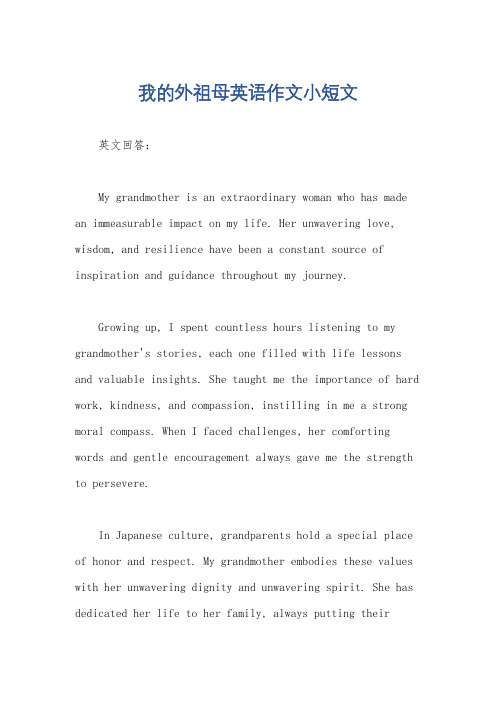
我的外祖母英语作文小短文英文回答:My grandmother is an extraordinary woman who has made an immeasurable impact on my life. Her unwavering love, wisdom, and resilience have been a constant source of inspiration and guidance throughout my journey.Growing up, I spent countless hours listening to my grandmother's stories, each one filled with life lessons and valuable insights. She taught me the importance of hard work,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instilling in me a strong moral compass. When I faced challenges, her comforting words and gentle encouragement always gave me the strength to persevere.In Japanese culture, grandparents hold a special place of honor and respect. My grandmother embodies these values with her unwavering dignity and unwavering spirit. She has dedicated her life to her family, always putting theirneeds before her own. Her selflessness and unconditional love have created an unbreakable bond between us.One of my most cherished memories with my grandmother is sitting together in her garden, surrounded by vibrant flowers and the gentle sound of birdsong. She would share her knowledge of nature and its wonders, teaching me to appreciate the beauty and wonder of the world around us.As I grew older, my grandmother continued to be a source of wisdom and support. She encouraged me to pursue my dreams with passion and determination, reminding me that anything is possible if I believed in myself. Her unwavering belief in my abilities gave me the confidence to face new challenges and break new ground.Today, my grandmother is in her twilight years, but her spirit and influence continue to inspire me. Her legacy of love, kindness, and wisdom will live on in my heart and guide me throughout my life.中文回答:我的外祖母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在我的生命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童年外祖母的典型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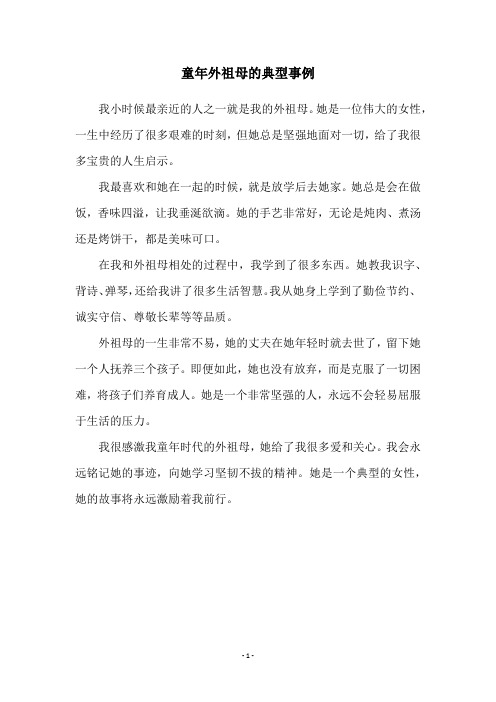
童年外祖母的典型事例
我小时候最亲近的人之一就是我的外祖母。
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一生中经历了很多艰难的时刻,但她总是坚强地面对一切,给了我很多宝贵的人生启示。
我最喜欢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放学后去她家。
她总是会在做饭,香味四溢,让我垂涎欲滴。
她的手艺非常好,无论是炖肉、煮汤还是烤饼干,都是美味可口。
在我和外祖母相处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她教我识字、背诗、弹琴,还给我讲了很多生活智慧。
我从她身上学到了勤俭节约、诚实守信、尊敬长辈等等品质。
外祖母的一生非常不易,她的丈夫在她年轻时就去世了,留下她一个人抚养三个孩子。
即便如此,她也没有放弃,而是克服了一切困难,将孩子们养育成人。
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永远不会轻易屈服于生活的压力。
我很感激我童年时代的外祖母,她给了我很多爱和关心。
我会永远铭记她的事迹,向她学习坚韧不拔的精神。
她是一个典型的女性,她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我前行。
- 1 -。
对外祖母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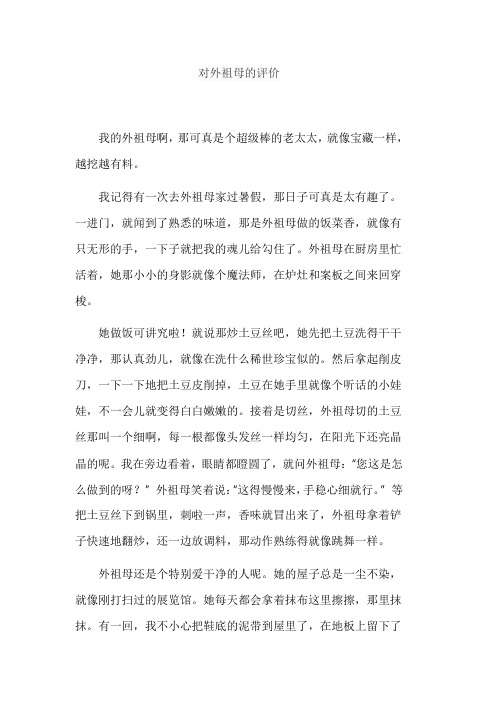
对外祖母的评价我的外祖母啊,那可真是个超级棒的老太太,就像宝藏一样,越挖越有料。
我记得有一次去外祖母家过暑假,那日子可真是太有趣了。
一进门,就闻到了熟悉的味道,那是外祖母做的饭菜香,就像有只无形的手,一下子就把我的魂儿给勾住了。
外祖母在厨房里忙活着,她那小小的身影就像个魔法师,在炉灶和案板之间来回穿梭。
她做饭可讲究啦!就说那炒土豆丝吧,她先把土豆洗得干干净净,那认真劲儿,就像在洗什么稀世珍宝似的。
然后拿起削皮刀,一下一下地把土豆皮削掉,土豆在她手里就像个听话的小娃娃,不一会儿就变得白白嫩嫩的。
接着是切丝,外祖母切的土豆丝那叫一个细啊,每一根都像头发丝一样均匀,在阳光下还亮晶晶的呢。
我在旁边看着,眼睛都瞪圆了,就问外祖母:“您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外祖母笑着说:“这得慢慢来,手稳心细就行。
” 等把土豆丝下到锅里,刺啦一声,香味就冒出来了,外祖母拿着铲子快速地翻炒,还一边放调料,那动作熟练得就像跳舞一样。
外祖母还是个特别爱干净的人呢。
她的屋子总是一尘不染,就像刚打扫过的展览馆。
她每天都会拿着抹布这里擦擦,那里抹抹。
有一回,我不小心把鞋底的泥带到屋里了,在地板上留下了几个黑乎乎的脚印。
外祖母看到了,也没说我,只是笑着摇摇头,然后拿着拖把就过来了。
她弯着腰,一下一下地拖着,那脚印就像调皮的小怪兽,被外祖母一点点地消灭了。
拖完后,她还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痕迹了才罢休。
外祖母还特别会讲故事。
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她就开始讲那些古老又神奇的故事。
有妖怪,有神仙,还有勇敢的战士。
她讲得绘声绘色的,眼睛里闪着光,就像她亲身经历过一样。
我听得入迷,感觉那些故事里的人物都在我眼前晃悠呢。
有时候讲到吓人的地方,我吓得往她怀里钻,她就笑着拍拍我的头,说:“别怕,有外祖母在呢。
”在我眼里,外祖母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人。
她能干、爱干净,还会讲好多好多有趣的故事。
她就像我生活里的太阳,温暖又明亮,只要有她在,我的日子就充满了快乐和温馨。
我的外祖母节选阅读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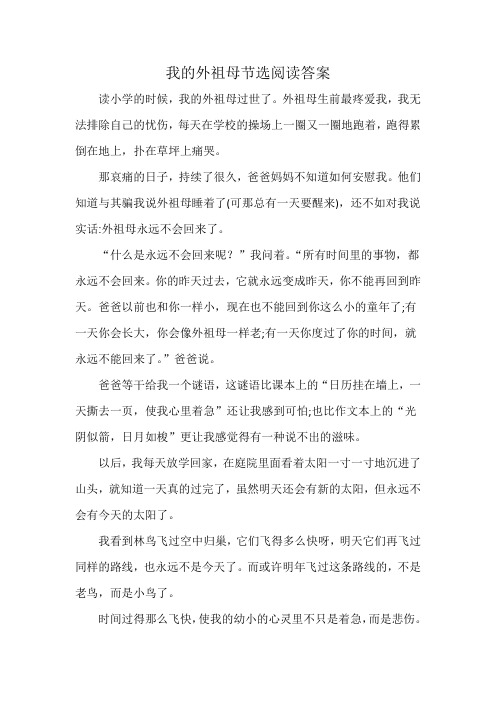
我的外祖母节选阅读答案读小学的时候,我的外祖母过世了。
外祖母生前最疼爱我,我无法排除自己的忧伤,每天在学校的操场上一圈又一圈地跑着,跑得累倒在地上,扑在草坪上痛哭。
那哀痛的日子,持续了很久,爸爸妈妈不知道如何安慰我。
他们知道与其骗我说外祖母睡着了(可那总有一天要醒来),还不如对我说实话:外祖母永远不会回来了。
“什么是永远不会回来呢?”我问着。
“所有时间里的事物,都永远不会回来。
你的昨天过去,它就永远变成昨天,你不能再回到昨天。
爸爸以前也和你一样小,现在也不能回到你这么小的童年了;有一天你会长大,你会像外祖母一样老;有一天你度过了你的时间,就永远不能回来了。
”爸爸说。
爸爸等干给我一个谜语,这谜语比课本上的“日历挂在墙上,一天撕去一页,使我心里着急”还让我感到可怕;也比作文本上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更让我感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以后,我每天放学回家,在庭院里面看着太阳一寸一寸地沉进了山头,就知道一天真的过完了,虽然明天还会有新的太阳,但永远不会有今天的太阳了。
我看到林鸟飞过空中归巢,它们飞得多么快呀,明天它们再飞过同样的路线,也永远不是今天了。
而或许明年飞过这条路线的,不是老鸟,而是小鸟了。
时间过得那么飞快,使我的幼小的心灵里不只是着急,而是悲伤。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太阳快落山了,就下决心说:“我要比太阳更快地回家。
”我狂奔回去,站在庭院前喘气的时候,看到太阳还露半边脸,我高兴地跳跃起来,那一天我跑赢了太阳。
以后我就时常做这样的游戏,有时和太阳赛跑,有时和西北风比快,有时一个暑假才能完成的作业,我十天就做完了。
那时我三年级,常常把哥哥五年级的作业拿来做。
每一次比赛胜过的时间,我都快乐得不知道怎么形容。
后来的二十年里,我因此受益无穷。
虽然我知道人永远跑不过时间,但是人可以比自己原来的时间跑快一步,如果跑得快,有时可以快好几步。
那几步很小很小,用途却很大很大。
如果将来有什么要教给我的孩子,我会告诉他,假若你一直和时间比赛,你就可以成功。
我的外祖母

我的外祖母文/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第一中心小学 四年级6班 班梓桐家庭教育一家一故事我的外祖母个子不高,有着一头雪白的头发,她总说这就是岁月的痕迹。
她有一对弯弯的眉毛,特别像弯弯的月牙儿。
外祖母的脸上长满了皱纹,由于经常操持家务,手也变得很粗糙,但这依旧遮挡不住外祖母由内到外散发的温柔。
外祖母最喜欢什么?外祖母最喜欢的当然是她经常穿的那件红蓝格围裙。
外祖母的围裙从早穿到晚,做饭的时候穿着围裙,收拾家务的时候穿着围裙,给小鸡小鸭喂食的时候穿着围裙……家里到处是外祖母穿着红蓝格围裙的身影,所以我认为外祖母最爱的是她的围裙。
有一年冬天,我特别想吃粽子。
当时已经过了吃粽子的节令,外祖母家住在农村,想要买到食材更是难上加难。
当时不懂事的我就一直闹,哭着喊着就要吃粽子。
外祖母一边收拾着家务,一边哄着哭闹的我,告诉我:“别着急,你乖乖听话,外祖母一会儿就能给你变出好吃的粽子来。
”外祖母收拾好后,便马不停蹄地赶往镇上买包粽子的食材。
我正在坐在院门口守着,远远地看到红蓝格围裙和那直不起来的背,酸涩的感觉涌上心头。
回到家后,外祖母一刻都没有休息,马上进入厨房,洗粽叶、洗红枣、煮豆沙、包粽子、烧热水。
看着穿着红蓝格围裙的外祖母在厨房里不停地忙碌,我的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一直忙到了天黑,额头上带着汗珠的外祖母端着香喷喷的粽子温柔地对我说:“快来,尝尝外祖母给你变出来的粽子好不好吃,小心烫……”这一刻,我再也忍不住,愧疚得哭起来:“外祖母,对不起,我再也不要吃粽子了,我不要您这么辛苦。
”外祖母温柔地说:“我家小宝真懂事,外祖母不累,只要你开心,外祖母就开心。
”外祖母一边安慰着我,一边帮我把粽子打开晾到盘子里。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外祖母尽管满脸皱纹、手变得粗糙了却依旧很温柔,为什么外祖母会穿着围裙从早忙到晚,这都是外祖母为家默默付出的痕迹。
其实,外祖母最喜欢的也许不是她的那件红蓝格围裙,她最喜欢的应该是穿上围裙后忙忙碌碌地照顾我们。
童年对外祖母的外貌描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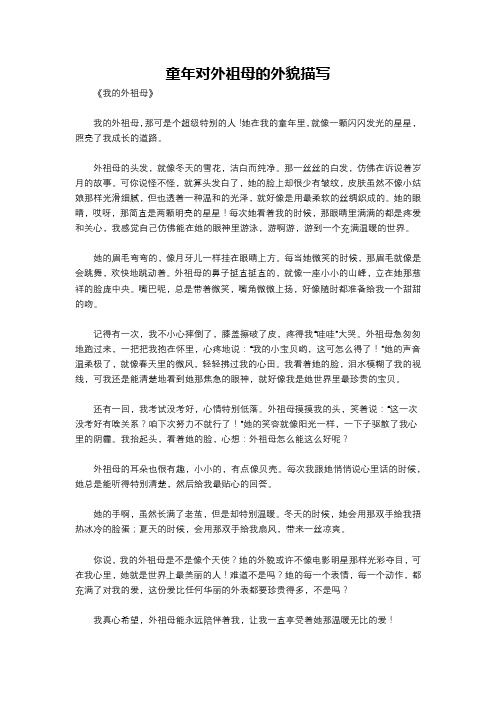
童年对外祖母的外貌描写《我的外祖母》我的外祖母,那可是个超级特别的人!她在我的童年里,就像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照亮了我成长的道路。
外祖母的头发,就像冬天的雪花,洁白而纯净。
那一丝丝的白发,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可你说怪不怪,就算头发白了,她的脸上却很少有皱纹,皮肤虽然不像小姑娘那样光滑细腻,但也透着一种温和的光泽,就好像是用最柔软的丝绸织成的。
她的眼睛,哎呀,那简直是两颗明亮的星星!每次她看着我的时候,那眼睛里满满的都是疼爱和关心,我感觉自己仿佛能在她的眼神里游泳,游啊游,游到一个充满温暖的世界。
她的眉毛弯弯的,像月牙儿一样挂在眼睛上方。
每当她微笑的时候,那眉毛就像是会跳舞,欢快地跳动着。
外祖母的鼻子挺直挺直的,就像一座小小的山峰,立在她那慈祥的脸庞中央。
嘴巴呢,总是带着微笑,嘴角微微上扬,好像随时都准备给我一个甜甜的吻。
记得有一次,我不小心摔倒了,膝盖擦破了皮,疼得我“哇哇”大哭。
外祖母急匆匆地跑过来,一把把我抱在怀里,心疼地说:“我的小宝贝哟,这可怎么得了!”她的声音温柔极了,就像春天里的微风,轻轻拂过我的心田。
我看着她的脸,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可我还是能清楚地看到她那焦急的眼神,就好像我是她世界里最珍贵的宝贝。
还有一回,我考试没考好,心情特别低落。
外祖母摸摸我的头,笑着说:“这一次没考好有啥关系?咱下次努力不就行了!”她的笑容就像阳光一样,一下子驱散了我心里的阴霾。
我抬起头,看着她的脸,心想:外祖母怎么能这么好呢?外祖母的耳朵也很有趣,小小的,有点像贝壳。
每次我跟她悄悄说心里话的时候,她总是能听得特别清楚,然后给我最贴心的回答。
她的手啊,虽然长满了老茧,但是却特别温暖。
冬天的时候,她会用那双手给我捂热冰冷的脸蛋;夏天的时候,会用那双手给我扇风,带来一丝凉爽。
你说,我的外祖母是不是像个天使?她的外貌或许不像电影明星那样光彩夺目,可在我心里,她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难道不是吗?她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对我的爱,这份爱比任何华丽的外表都要珍贵得多,不是吗?我真心希望,外祖母能永远陪伴着我,让我一直享受着她那温暖无比的爱!。
我的外祖母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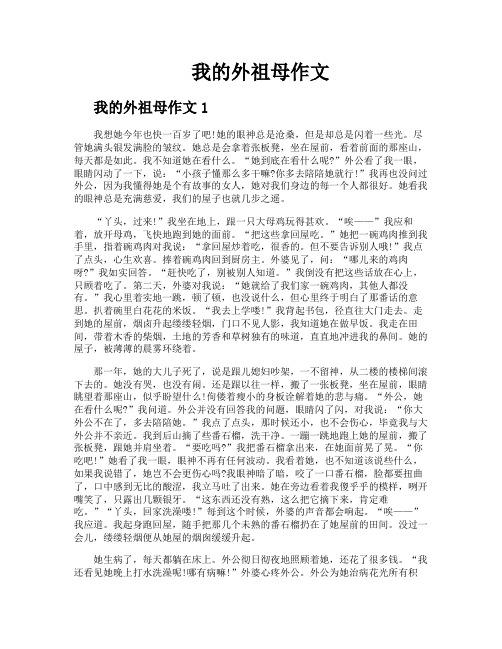
我的外祖母作文我的外祖母作文1我想她今年也快一百岁了吧!她的眼神总是沧桑,但是却总是闪着一些光。
尽管她满头银发满脸的皱纹。
她总是会拿着张板凳,坐在屋前,看着前面的那座山,每天都是如此。
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
“她到底在看什么呢?”外公看了我一眼,眼睛闪动了一下,说:“小孩子懂那么多干嘛?你多去陪陪她就行!”我再也没问过外公,因为我懂得她是个有故事的女人,她对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很好。
她看我的眼神总是充满慈爱,我们的屋子也就几步之遥。
“丫头,过来!”我坐在地上,跟一只大母鸡玩得甚欢。
“唉——”我应和着,放开母鸡,飞快地跑到她的面前。
“把这些拿回屋吃。
”她把一碗鸡肉推到我手里,指着碗鸡肉对我说:“拿回屋炒着吃,很香的。
但不要告诉别人哦!”我点了点头,心生欢喜。
捧着碗鸡肉回到厨房主。
外婆见了,问:“哪儿来的鸡肉呀?”我如实回答。
“赶快吃了,别被别人知道。
”我倒没有把这些话放在心上,只顾着吃了。
第二天,外婆对我说:“她就给了我们家一碗鸡肉,其他人都没有。
”我心里着实地一跳,顿了顿,也没说什么,但心里终于明白了那番话的意思。
扒着碗里白花花的米饭。
“我去上学喽!”我背起书包,径直往大门走去。
走到她的屋前,烟卤升起缕缕轻烟,门口不见人影,我知道她在做早饭。
我走在田间,带着木香的柴烟,土地的芳香和草树独有的味道,直直地冲进我的鼻间。
她的屋子,被薄薄的晨雾环绕着。
那一年,她的大儿子死了,说是跟儿媳妇吵架,一不留神,从二楼的楼梯间滚下去的。
她没有哭,也没有闹。
还是跟以往一样,搬了一张板凳,坐在屋前,眼睛眺望着那座山,似乎盼望什么!佝偻着瘦小的身板诠解着她的悲与痛。
“外公,她在看什么呢?”我问道。
外公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眼睛闪了闪,对我说:“你大外公不在了,多去陪陪她。
”我点了点头,那时候还小,也不会伤心,毕竟我与大外公并不亲近。
我到后山摘了些番石榴,洗干净。
一蹦一跳地跑上她的屋前,搬了张板凳,跟她并肩坐着。
“要吃吗?”我把番石榴拿出来,在她面前晃了晃。
写《童年》中的外祖母和我作文

写《童年》中的外祖母和我作文我的外祖母呀,那可是我童年里最特别的存在!她就像是一颗温暖的太阳,照亮了我的整个童年。
记得有一次,我在外祖母家玩,看到桌子上有一块看起来超级美味的蛋糕。
那蛋糕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我眨巴着眼睛对外祖母说:“外祖母,我想吃那块蛋糕。
”外祖母笑着说:“小馋猫,这是留给你舅舅的,等他回来再吃。
”我心里那个失落呀,就一直盯着蛋糕看,心想舅舅怎么还不回来呀。
过了一会儿,外祖母去厨房忙别的事情了,我那小眼珠一转,嘿嘿,机会来啦!我悄悄地走到桌子前,伸出小手,轻轻地摸了一下蛋糕,哇,好软呀!我实在忍不住了,偷偷地掰下了一小块放进嘴里,那香甜的味道瞬间在嘴里散开,真是太好吃啦!我正吃得开心呢,突然听到外祖母的脚步声,哎呀,不好,我赶紧把剩下的蛋糕藏在背后。
外祖母走过来,看着我一脸慌张的样子,笑着说:“小鬼头,你是不是偷吃蛋糕啦?”我红着脸,低着头,支支吾吾地说:“我……我就吃了一点点。
”外祖母哈哈大笑起来,说:“好啦好啦,吃就吃了吧,看你那小馋样儿。
”我一听,开心极了,又跑过去抱住外祖母。
外祖母对我可好了,她总是给我讲好多好多有趣的故事。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躺在外祖母的怀里,听着她那温柔的声音,慢慢进入梦乡。
有时候我会做噩梦,惊醒后大哭,外祖母就会轻轻地拍着我的背,安慰我说:“别怕别怕,外祖母在这儿呢。
”然后给我讲一个更有趣的故事,让我重新入睡。
我的外祖母就是这样一个温暖又可爱的人呀,她陪伴着我度过了无数个快乐的日子。
现在我长大了,依然会常常想起和外祖母在一起的那些时光,那些回忆就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永远照亮着我的内心。
我真希望时光能够倒流,让我再回到那个在外祖母身边无忧无虑的童年呀!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会永远珍惜和外祖母的这份深厚感情,因为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
童年中外祖母坚持忍耐的事例

童年中外祖母坚持忍耐的事例《我的外祖母:坚持与忍耐的榜样》我有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外祖母。
她就像一棵深深扎根在土地里的大树,无论狂风怎么吹,暴雨怎么打,都稳稳地站在那里,从不轻易倒下。
她的故事就像星星一样,在我的童年里闪闪发光,尤其是那些关于她坚持和忍耐的事例,真的让我特别敬佩。
记得有一次,我们家要盖新房子。
那时候,家里的钱并不是很充裕,很多事情都得自己动手。
外祖母虽然年纪已经不小了,可是她一点都没有退缩。
每天天还没亮呢,她就起来了,到工地上帮忙搬砖头。
那些砖头又重又粗糙,我看着都觉得手疼。
我就问外祖母:“外祖母,您不累吗?这砖头多重呀,您干嘛不歇着呀?”外祖母笑着对我说:“乖孩子,要是大家都歇着,这房子啥时候能盖好呢?这就像爬山一样,你不能爬到一半就不爬了呀,咬咬牙坚持下去,就能看到山顶的风景啦。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在盖房子的过程中,还遇到了很多麻烦事儿。
有一天,请来的工匠和家里人因为一些工钱的事儿闹了别扭。
工匠们都放下工具,说不干了。
这可把大家急坏了,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可是外祖母呢,她不慌不忙地走到工匠们面前,和声细语地说:“师傅们呀,咱们都是为了把这房子盖好。
大家都不容易,这工钱呢,咱们再商量商量,肯定能有个大家都满意的法子。
就像咱们做一道菜,盐放多了,加点水就好啦,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外祖母的话就像一阵春风,把工匠们心里的怒气吹散了不少。
经过一番商量,工匠们又开始干活了。
我当时就想,外祖母怎么这么厉害呢?她就像一个神奇的魔法师,能把坏事儿变成好事儿。
还有一次,家里的收成不太好。
粮食剩得不多了,每天只能吃很简单的饭菜。
我总是嘟囔着:“怎么又是这些呀,一点都不好吃。
”外祖母听了,并没有责怪我。
她把我拉到身边,给我讲她小时候的故事。
她说:“孩子呀,外祖母小时候,连这些饭菜都吃不上呢。
有时候饿了,只能去挖野菜吃。
那野菜又苦又涩,可是为了活下去,就得忍着呀。
现在咱们虽然吃得简单了点,但是比外祖母小时候可强多啦。
童年外祖母人物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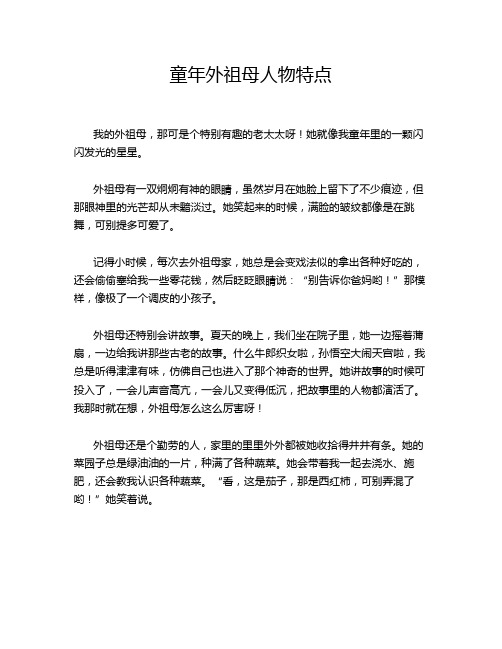
童年外祖母人物特点我的外祖母,那可是个特别有趣的老太太呀!她就像我童年里的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
外祖母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虽然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不少痕迹,但那眼神里的光芒却从未黯淡过。
她笑起来的时候,满脸的皱纹都像是在跳舞,可别提多可爱了。
记得小时候,每次去外祖母家,她总是会变戏法似的拿出各种好吃的,还会偷偷塞给我一些零花钱,然后眨眨眼睛说:“别告诉你爸妈哟!”那模样,像极了一个调皮的小孩子。
外祖母还特别会讲故事。
夏天的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她一边摇着蒲扇,一边给我讲那些古老的故事。
什么牛郎织女啦,孙悟空大闹天宫啦,我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仿佛自己也进入了那个神奇的世界。
她讲故事的时候可投入了,一会儿声音高亢,一会儿又变得低沉,把故事里的人物都演活了。
我那时就在想,外祖母怎么这么厉害呀!外祖母还是个勤劳的人,家里的里里外外都被她收拾得井井有条。
她的菜园子总是绿油油的一片,种满了各种蔬菜。
她会带着我一起去浇水、施肥,还会教我认识各种蔬菜。
“看,这是茄子,那是西红柿,可别弄混了哟!”她笑着说。
有一次,我不小心摔了一跤,膝盖擦破了皮,疼得我大哭起来。
外祖母赶紧跑过来,心疼地看着我,然后一边轻轻地吹着我的伤口,一边说:“哎哟,我的小宝贝,不哭不哭,外祖母给你呼呼就不疼啦。
”嘿,你还别说,被她这么一吹,我还真觉得没那么疼了。
外祖母的手也很巧,她会做很多漂亮的针线活。
我的小棉袄、小棉裤,都是她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穿上外祖母做的衣服,我觉得特别温暖,就好像她一直抱着我一样。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童年因为有了外祖母而变得格外美好。
她就像冬日里的暖阳,温暖着我;又像夏日里的微风,吹拂着我。
我多希望时光能够倒流,让我再回到那些和外祖母在一起的日子呀。
她虽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说过什么豪言壮语,但她用自己的爱和关怀,给了我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
她不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吗?她的那些点点滴滴,不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吗?她的善良、勤劳、风趣,不都一直影响着我吗?我亲爱的外祖母呀,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我的外祖母
最初的记忆
不知别人最早的记忆可以追溯到几岁,我最早的记忆是四岁,那一年经历的一些事情已过了这么多年,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我却至今念念不忘,历历在目。
那时我和外祖母住在济南市槐荫区十一马路路东一个大院里,院里住着十几户人家,院子的大门是两扇漆黑的木门,门柱插在两侧的方形石墩里,一尺多高的门槛插在门墩的竖槽里,我那时个头矮,每次跨过门槛都像是在艰难的翻越一道矮墙。
这个大院的房屋是我母亲的爷爷解放前花钱建造的,解放后被军管会收去分配给了大家。
我外祖母住的是一幢坐北朝南一厅两室的平房,进门是一个厅,门厅左右各有一间,但这一厅两室并不归我外祖母一户所有,我外祖母住西屋,另一户叫范兆海的人家住东屋,门厅两家共用。
我外祖母姓贺,名绳梅,祖籍德州市平原县张华乡贺沟村,1911年10月10日出生。
我四岁那年她50岁,身高一米六多,椭圆脸,齐耳短发,经常穿一件自己缝制的蓝布大襟上衣。
她学过裁缝,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平日的工作是给十一马路路口一家服装店加工服装。
服装店揽来了活就通知我外祖母去拿布料,在家里做好了再送回服装店,返回家时手里便多了块儿八毛的人民币。
我记的那时外祖母经常领着我去服装店要活做,而店老板则是经常回答:“没有,有了活一定会通知你。
”光靠做针线活不能养活我们祖孙二人,为了生存外祖母还给人家带看孩子。
她看的女孩叫莹莹,莹莹比我大3岁,听外祖母说,莹莹姐的爸爸是个穿军装的军官,在济南市委交际处工作,交际处是负责会议接待活动的,在社会上很有地位,莹莹姐的母亲在省立医院当护士,我出生时就在省立医院,她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照。
我刚记事莹莹姐的爸爸、妈妈就把她接走了,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像,是因为我外祖母珍藏着一张她扶着我拍摄的合影照片。
我四岁的时候是1962年,正赶上百年不遇的三年自然灾害,全
国都在搞“生产救灾”,我外祖母裹过脚,因放开的早,虽不是“三
寸金莲”,但行走仍有些不便,干一些劳动强度大的活力不从心,她
就帮着左邻右舍干些裁衣服、织毛衣、看孩子等力所能及的活,人家给钱也不要。
一个院的人就像一家人一样,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外祖母都是让我喊爷爷、奶奶、叔叔、婶子,爷爷、奶奶、叔叔、婶子多了,为了区别开来,就按年龄让我喊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大爷爷、二爷爷、三爷爷。
我记得三爷爷是个拉地盘车的,有时给罐头厂送货回来常带一些苹果皮、梨皮之类的食物送给我外祖母,外祖母舍不得吃都省给了我。
我外祖母吸烟,但她吸得都是用自己裁好的长方形纸条卷制的一头大一头小,类似小喇叭筒似地卷烟。
因为单吸烟叶吸不起,就到院内的白杨树下捡一些飘落在地上的叶子晒干搓碎了掺着吸。
我见外祖母这样做,就也学着捡干树叶搓碎了徃那盛烟沫的圆形铁罐头盒里装,外祖母见了先是高兴,后来见我放多了就阻止我说:“放多了不好吸,太呛。
”听了这话我就悄悄溜出去给外祖母捡别人丢弃在地上的烟头,
捡了烟头剥去烟纸把烟丝放到罐头盒里,再按比例加树叶,外祖母每每看到我做这些事时,都是默不作声地盯着我,眼里流露出的是一种既爱怜又欣慰的目光。
我和外祖母的日子过的虽然艰苦,但很温馨。
祖孙二人相依为命,我是她倾心培育的青禾,孤寂时的寄托,黑暗里的光亮,艰难面前的希望。
而外祖母则是我遮风避雨的大树,她的怀抱是我歇息沉眠的港湾,她的关爱是我成长沐浴的阳光,她的教诲是我滋润心田的雨露。
外祖母那时在我幼小心灵里就种下了一个至今不可颠覆的印像,这就是头脑清楚,心胸开阔,豁达坚强。
这一点也许是她从父亲,冯玉祥将军手下的旅长,人送绰号“贺大刀”的贺云良那儿遗传来的。
记得有一次,外祖母领着我去城郊赶集,集市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外祖母买了几十斤玉米,装进袋子里,一手拎着粮袋一手拽着我挤出人群,把粮袋放在路边的空地上让我看着,而后又转身去买烟叶,这时一个三四十岁的汉子趁机跑过来,抓起我身边的粮袋就跑,我用小手抓着粮袋子不松手,他就拖着我跑,我挣不过他只好松开手无奈的
放声大哭,外祖母闻听哭声返回来时,那汉子早已扛着粮袋躲进人群无影无踪。
外祖母抱起我来安慰说:“不怪你,也许那人家确实揭不开锅了。
”那时买几十斤粮食不容易,外祖母没白没黑地在灯下给人做衣服、打毛衣,要赚很长时间的钱才能买这么多粮食,而且有了粮食也要掺着菜叶树叶之类的动西等节省着吃。
可外祖母转身就像真的忘了这事似的,从此再没念叨这事。
粮食没了外祖母就每天出去捡一些能吃的东西回来煮着吃,省下好的东西喂我。
不久外祖母患了水肿病,我按过她那虚肿的腿,按下去就是一个坑,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而我却被她喂得胖乎乎的,每当有人看着我那圆润的脸庞,夸我是个大胖小子时,外祖母便笑的合不拢嘴,脸上洋溢着一种掩饰不住的成就感。
外祖母虽然出生在乡下一个贫穷的抗日军人家庭,但因父母包办婚姻,嫁到城里资本家家里当了儿媳,背上了“剥削阶级”的包袱,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自然不去想那些当官当先进的事,又因年幼时家里贫穷,只上过几天初小,识不了多少字,所以也没有当科
学家、作家的理想。
那时她的事业和理想就是把我抚养教育成人。
在我四岁那一年的夏天,我和外祖母离开济南去了淄博,去了我父母工作的地方淄博市博山区。
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走的那天是一个阴雨天,外祖母天不亮就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收拾起早已整理捆绑好的行李乘一辆三轮车去火车站,屋外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四周一片漆黑,为了不惊动左邻右舍,外祖母说话声音压的很低,搬动行李轻手轻脚。
可谁知左邻右舍的灯还是敏感地点亮了,家家户户的门都相继打开,涌出来很多人来为我们送行。
外祖母很感动,看不出她眼里是不是含着泪,但告别的声音里夹带着抑捺不住的哭腔。
同院住着的一个靠“蹬三轮”为生的叔叔用三轮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外祖母掏出钱给他,他说什么也不收,说:“你平时帮我们大家做了那么多事,我咋能要你的钱?”外祖母硬往他兜里塞,他就气急地说:“你这是在打我的脸。
”我害怕地拽拽外祖母的衣襟,外祖母才把钱收回来。
那人的脸也由怒转暖,动情地对外祖母说:“到了女儿那边别忘了给咱院子里的人回信报个平安。
”
我外祖母没再说什么,只是使劲地点了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