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鹿鼎记》试论金庸对“侠”的解构
解构中的建构:《鹿鼎记》中韦小宝形象的塑造

解构中的建构:《鹿鼎记》中韦小宝形象的塑造摘要:评论界对金庸的《鹿鼎记》及其主人公韦小宝的评价存在不少分歧,这从侧面说明了此部作品所具有的值得重视的价值。
本文认为,金庸在《鹿鼎记》中通过对韦小宝这一形象的塑造,首先解构了血缘师门对于武侠小说主人公的神圣性,但更加有力地建构了侠义精神的影响;其次解构了武侠小说主人公固有的行动驱动力的崇高感,但建构了真情至高无上的位置。
作为具有人文理想的武侠小说家,金庸在解构中建构,韦小宝这一形象是他努力拓展武侠小说传达思想认识空间、实践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韦小宝;解构;建构;侠义;真情一《鹿鼎记》不仅在金庸的武侠作品中,即使放在整个武侠小说史中看都是相当另类的作品。
作为这部作品的主人公,骨碌碌转着一双贼眼珠的韦小宝,跻身在顶天立地豪气干云重义轻生至情至性的萧峰杨过令狐冲郭靖等一干“侠之大者”中,一种意味深长的反讽也就油然而生。
于是,有人说《鹿鼎记》是反武侠之作,也有人说它更接近历史小说,但也有人说《鹿鼎记》:“站在俯视历史和世俗的思想高度上,探询着扩拓着侠义的真内涵和真精神。
”这些说法的产生,都有着立足于小说文本的依据。
虽然结论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鹿鼎记》的小说文本在结构过程中,显然创造出了产生诸多阐释可能的空间。
作者金庸是这样说的:“《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
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和形式,要尽可能地尝试一些新的创造。
”金庸以他强大的远远超出一般武侠小说作者的认识能力和对人性的关怀,成功地将武侠小说这一通俗小说形式提升到了新的境界。
他在对武侠小说固有的程式化表达形式充分继承的基础上,以丰沛的想像力、诗化和象征性的表达形式、以及巨大的情感蕴藉,革命性地改变了武侠小说的格调与内涵。
“射雕三部曲”可视为标志,其后在《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等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些造就了“射雕三部曲”成功的元素得到了更加纯熟更加充分的利用。
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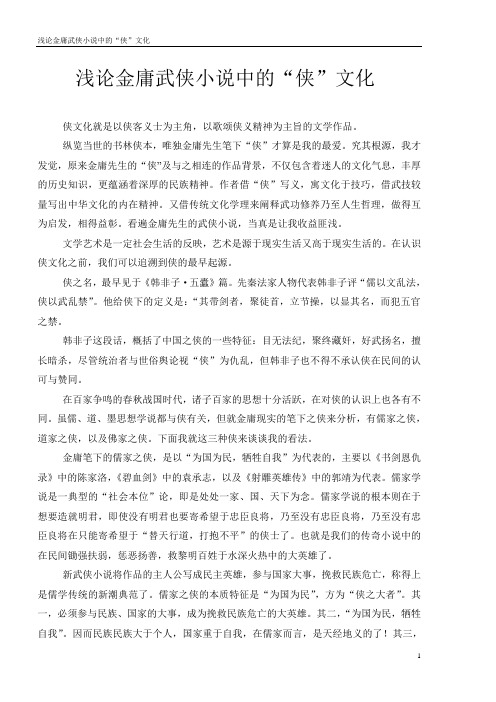
浅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文化侠文化就是以侠客义士为主角,以歌颂侠义精神为主旨的文学作品。
纵览当世的书林侠本,唯独金庸先生笔下“侠”才算是我的最爱。
究其根源,我才发觉,原来金庸先生的“侠”及与之相连的作品背景,不仅包含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更蕴涵着深厚的民族精神。
作者借“侠”写义,寓文化于技巧,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
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得互为启发,相得益彰。
看遍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当真是让我收益匪浅。
文学艺术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艺术是源于现实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的。
在认识侠文化之前,我们可以追溯到侠的最早起源。
侠之名,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篇。
先秦法家人物代表韩非子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乱禁”。
他给侠下的定义是:“其带剑者,聚徒首,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韩非子这段话,概括了中国之侠的一些特征:目无法纪,聚终藏奸,好武扬名,擅长暗杀,尽管统治者与世俗舆论视“侠”为仇乱,但韩非子也不得不承认侠在民间的认可与赞同。
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十分活跃,在对侠的认识上也各有不同。
虽儒、道、墨思想学说都与侠有关,但就金庸现实的笔下之侠来分析,有儒家之侠,道家之侠,以及佛家之侠。
下面我就这三种侠来谈谈我的看法。
金庸笔下的儒家之侠,是以“为国为民,牺牲自我”为代表的,主要以《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碧血剑》中的袁承志,以及《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为代表。
儒家学说是一典型的“社会本位”论,即是处处一家、国、天下为念。
儒家学说的根本则在于想要造就明君,即使没有明君也要寄希望于忠臣良将,乃至没有忠臣良将,乃至没有忠臣良将在只能寄希望于“替天行道,打抱不平”的侠士了。
也就是我们的传奇小说中的在民间锄强扶弱,惩恶扬善,救黎明百姓于水深火热中的大英雄了。
新武侠小说将作品的主人公写成民主英雄,参与国家大事,挽救民族危亡,称得上是儒学传统的新潮典范了。
论金庸武侠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

论金庸武侠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以其精彩纷呈的江湖世界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成为了华语文学的经典之作。
在他的笔下,众多人物各具特色,令人难以忘怀。
金庸先生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展现出了极高的艺术造诣,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金庸善于通过人物的出身和成长环境来塑造其性格特点。
例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他出生于蒙古大漠,成长在淳朴善良的牧民家庭。
这样的成长环境造就了他忠厚老实、正直勇敢的性格。
他心怀正义,始终坚守着自己的道德底线,面对困难和诱惑从不退缩。
与之相反,《神雕侠侣》中的杨过,自幼父母双亡,流落江湖,饱经沧桑。
他的性格敏感、孤傲,却又深情重义。
这种复杂的性格特点与他坎坷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
人物的性格发展也是金庸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
在《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一开始是个性格单纯、优柔寡断的少年。
但随着经历的增多,他在江湖的风雨中逐渐成长,变得更加成熟、果断。
他在面对感情问题时的纠结,以及在处理江湖纷争时的智慧和勇气,都展现了其性格的转变和发展。
同样,《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从一个自由洒脱、不拘小节的华山派弟子,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和考验后,最终看透江湖的险恶,选择了归隐江湖。
他的性格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被磨砺和完善。
金庸还善于通过人物的爱情观来丰富其形象。
《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与黄蓉的爱情,是一种相互扶持、相互成就的典范。
黄蓉的机智聪慧与郭靖的忠厚老实相得益彰,他们共同面对江湖中的风风雨雨,感情坚贞不渝。
而《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则是冲破世俗礼教的束缚,历经千辛万苦,依然不离不弃。
这种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使杨过和小龙女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在《天龙八部》中,段誉对王语嫣的痴情,乔峰对阿朱的深情,都为人物形象增添了一抹柔情。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金庸赋予了每个人物独特的武功和招式,这不仅是一种武力的象征,更是人物性格和气质的体现。
比如乔峰的降龙十八掌,刚猛无比,正符合他豪迈大气、义薄云天的性格特点。
金庸笔下的侠与情

金庸笔下的侠与情1200060608吴东方金庸先生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从50后60后到80后90后,都有着大量热爱金庸先生小说的读者。
金庸小说的迷人之处在于他的作品蕴含并表现着人类尤其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生活信仰,那就是侠义精神与美好爱情。
金庸小说本身属于武侠小说的范畴,故而侠义精神必然为所有作品不可或缺的部分,虽然在某些作品中并没有那么明显的大篇幅渲染,但是读过金庸作品的读者都知道,他善于将侠义精神融于作品的细节中,从不突兀的彰显,正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而金庸先生作品的另一主旋律则是美好爱情,孔老师曾说:“在一定意义上,金庸小说可以说是爱情的‘百科全书’”。
金庸先生往往在一部作品中就写出多组不同的爱情,而他的十五部作品中的爱情又各有风格,彼此不同。
因此,要系统全面的阐述金庸先生所有作品的所有爱情,必须是一位通读所有作品,且对其中人物、故事及其间爱情认真揣摩研究的学者,而金庸中的爱情这一命题所能写出的往往就非几千字的论文可止,或要十几万字甚至更多的一本书了。
学生虽读过金庸先生的多数作品,但真正捧卷细品,有所领悟的还当属倚天、碧血、连城、侠客行、越女剑、鸳鸯刀这几部。
笑傲和天龙两书虽也如狼似虎般吞咽着读了,但毕竟觉得没有摸清楚、嚼明白,至于射雕三部曲中的前两部和倪匡先生称为“古今中外第一好小说”的鹿鼎,学生还没有读完,因此不敢妄论。
在这里,学生只想就这自己感触最深、流泪最多的倚天着笔来写一写这本书中的侠与情。
倚天屠龙记,为射雕三部曲中最后一本,金庸先生在书的最后明白的承认,主人公张无忌是有些软弱的,不适合做好领袖,适合做好朋友。
我读这部书时,心却是与无忌一道的,仿佛便化进了书中,经历着无忌的经历,抉择着无忌的抉择。
还好我终于还是走出来了,要感谢金庸先生,让我真正认识了无忌,也重新认识了自己,认识了人生。
金庸先生善写武林斗争,在笑傲江湖中,就以宏大的笔触描写了一场武林正邪之争,一方是被当做魔教的日月神教,一方是以正派自居的五岳剑派。
《鹿鼎记》读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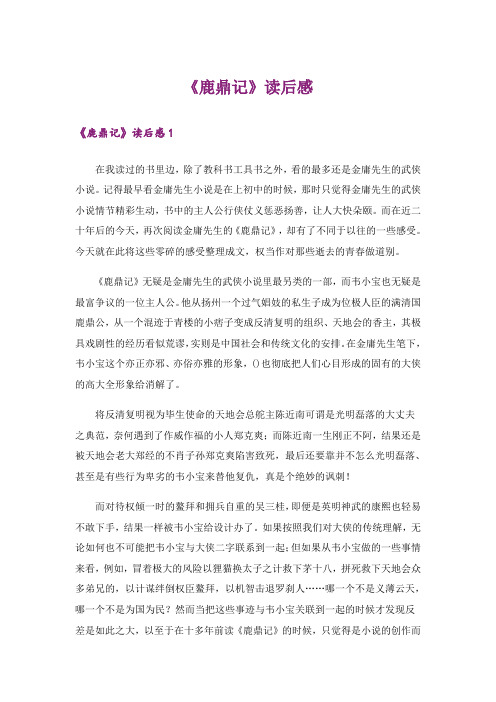
《鹿鼎记》读后感《鹿鼎记》读后感1在我读过的书里边,除了教科书工具书之外,看的最多还是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
记得最早看金庸先生小说是在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只觉得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情节精彩生动,书中的主人公行侠仗义惩恶扬善,让人大快朵颐。
而在近二十年后的今天,再次阅读金庸先生的《鹿鼎记》,却有了不同于以往的一些感受。
今天就在此将这些零碎的感受整理成文,权当作对那些逝去的青春做道别。
《鹿鼎记》无疑是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里最另类的一部,而韦小宝也无疑是最富争议的一位主人公。
他从扬州一个过气娼妓的私生子成为位极人臣的满清国鹿鼎公,从一个混迹于青楼的小痞子变成反清复明的组织、天地会的香主,其极具戏剧性的经历看似荒谬,实则是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安排。
在金庸先生笔下,韦小宝这个亦正亦邪、亦俗亦雅的形象,()也彻底把人们心目形成的固有的大侠的高大全形象给消解了。
将反清复明视为毕生使命的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可谓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之典范,奈何遇到了作威作福的小人郑克爽;而陈近南一生刚正不阿,结果还是被天地会老大郑经的不肖子孙郑克爽陷害致死,最后还要靠并不怎么光明磊落、甚至是有些行为卑劣的韦小宝来替他复仇,真是个绝妙的讽刺!而对待权倾一时的鳌拜和拥兵自重的吴三桂,即便是英明神武的康熙也轻易不敢下手,结果一样被韦小宝给设计办了。
如果按照我们对大侠的传统理解,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韦小宝与大侠二字联系到一起;但如果从韦小宝做的一些事情来看,例如,冒着极大的风险以狸猫换太子之计救下茅十八,拼死救下天地会众多弟兄的,以计谋绊倒权臣鳌拜,以机智击退罗刹人……哪一个不是义薄云天,哪一个不是为国为民?然而当把这些事迹与韦小宝关联到一起的时候才发现反差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十多年前读《鹿鼎记》的时候,只觉得是小说的创作而已作不得真,而在走入社会,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之后,尤其是在我从事了四年多的管理咨询工作之后,再读《鹿鼎记》之时也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论金庸小说的侠义形象

论⾦庸⼩说的侠义形象2019-07-19摘要:⾦庸先⽣是中国新派武侠⼩说的杰出代表⼈物,其⼩说描写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关于“侠义”精神的阐释。
“侠”的精神在故事的离奇与巧合中完成性格的升华,在不可思议的机缘中描绘出⼈世⼈情的多彩⾯貌。
“侠义形象”成为⾦庸⼩说反映的精神核⼼,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化精神。
关键词:⾦庸⼩说 “侠义”精神形象塑造武侠⼩说源于古代公案⼩说,在中国传统⽂化的精神浸润和影响下产⽣,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汲取着先秦诸⼦各家思想的精神内涵。
“侠,虽然正式出现于战国晚期,但它早就以⽂化基因的⽅式潜藏于先秦诸⼦之中,以儒、道、墨为载体,参与到中国本⼟⽂化主体格局的建构之中。
”①在⾦庸先⽣的⼩说中,“侠”与“义”是不容分割的,“侠义精神”是⼀种民族⼼理中根深蒂固的思想,是⼀种民族的集体⽆意识,并且与儒、道、佛诸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作⽤于中国民众的集体思想中,成为⼀种民族⽂化的核⼼内容。
⾦庸先⽣的新派武侠⼩说融通俗性与思想性于⼀炉,从民族精神的传统出发,在⼑光剑影爱恨情仇中寻找⼈性的⽅向,探索⼀种哲理性的⼈⽣道路。
⼀、“侠”的⼈格分析(⼀)侠与儒家⾦庸笔下的侠其实都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侠,因为他笔下的形象中有更多的传统思想的参与,使侠脱离了武⼠的形象特点,成为⼀种⼈格化的精神。
在⾦庸⼩说中,说到儒家之侠,⼈们⾸先想到的必定会是郭靖,其次还有萧峰、陈家洛、袁承志等⼈。
郭靖形象是⾦庸⼩说中塑造得最为成功、最为典型的⼀个形象,他寄托了作者对于传统社会理想侠⼠⼈格的⾼度概括,是正义与道德的化⾝,是侠中的“侠之⼤者”。
他的形象始终贯穿于《射雕》三部曲中,最后在《倚天屠龙记》中慷慨赴死,完成其精神的最后升华。
他何以成为⼀个儒家的侠之⼤者,原因有三:第⼀,这与家环境有关。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最根深蒂固的思想,它已经深深地印在国⼈脑海中⽽成为了⼀种民族的集体⽆意识,融⼊了民族的⾎液,永远不可能被抛弃或忘却。
鹿鼎记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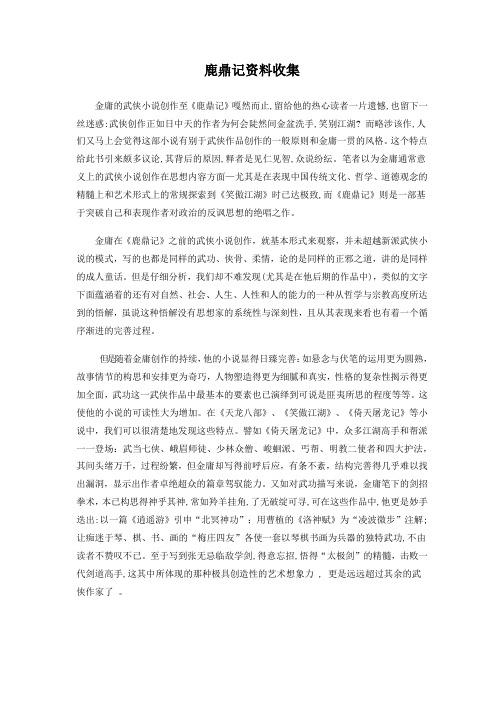
鹿鼎记资料收集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至《鹿鼎记》嘎然而止,留给他的热心读者一片遗憾,也留下一丝迷惑:武侠创作正如日中天的作者为何会陡然间金盆洗手,笑别江湖? 而略涉该作,人们又马上会觉得这部小说有别于武侠作品创作的一般原则和金庸一贯的风格。
这个特点给此书引来颇多议论,其背后的原因,释者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笔者以为金庸通常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创作在思想内容方面—尤其是在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哲学、道德观念的精髓上和艺术形式上的常规探索到《笑傲江湖》时已达极致,而《鹿鼎记》则是一部基于突破自己和表现作者对政治的反讽思想的绝唱之作。
金庸在《鹿鼎记》之前的武侠小说创作,就基本形式来观察,并未超越新派武侠小说的模式,写的也都是同样的武功、侠骨、柔情,论的是同样的正邪之道,讲的是同样的成人童话。
但是仔细分析,我们却不难发现(尤其是在他后期的作品中),类似的文字下面蕴涵着的还有对自然、社会、人生、人性和人的能力的一种从哲学与宗教高度所达到的悟解,虽说这种悟解没有思想家的系统性与深刻性,且从其表现来看也有着一个循序渐进的完善过程。
但是随着金庸创作的持续,他的小说显得日臻完善:如悬念与伏笔的运用更为圆熟,故事情节的构思和安排更为奇巧,人物塑造得更为细腻和真实,性格的复杂性揭示得更加全面,武功这一武侠作品中最基本的要素也已演绎到可说是匪夷所思的程度等等。
这使他的小说的可读性大为增加。
在《天龙八部》、《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等小说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这些特点。
譬如《倚天屠龙记》中,众多江湖高手和帮派一一登场:武当七侠、峨眉师徒、少林众僧、峻蛔派、丐帮、明教二使者和四大护法,其间头绪万千,过程纷繁,但金庸却写得前呼后应,有条不紊,结构完善得几乎难以找出漏洞,显示出作者卓绝超众的篇章驾驭能力。
又如对武功描写来说,金庸笔下的剑招拳术,本已构思得神乎其神,常如羚羊挂角,了无破绽可寻,可在这些作品中,他更是妙手迭出:以一篇《逍遥游》引申“北冥神功”;用曹植的《洛神赋》为“凌波微步”注解;让痴迷于琴、棋、书、画的“梅庄四友”各使一套以琴棋书画为兵器的独特武功,不由读者不赞叹不已。
[笔记] (六十九)《由“鹿鼎记”小议人物刻画(二)》
![[笔记] (六十九)《由“鹿鼎记”小议人物刻画(二)》](https://img.taocdn.com/s3/m/8252272ef46527d3250ce01f.png)
[笔记] 101谈写作(六十九)《由“鹿鼎记”小议人物刻画(二)》刚刚在群里跟人争得很不愉快,那人说金庸的书也没见得有多深,天天钻研对网文帮助不大,我就截取了一段给他看,他说没感觉。
而我的观点是,金庸的书是很可怕的,他创作的时候,思想可以通灵,去了另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鹿鼎记》.《射雕英雄传》都在另一个世界真实发生的,而金庸只是用笔记录下来了而已。
听起来很瘆人是吧?这就是写书的一种至高境界,通灵境界,这时候写的人物和故事都是活生生的,读者看书眼睛里看不到文字,而是看得人物和他们之间的情感,矛盾冲突。
而不能达到这状态的,写出来的书会让人无法100%投入,会被遣词造句,还有人物刻画所抽离出来,心里老想着:这故事怎么有点儿假啊?这人物怎么N……啊?这句子咋不通顺啊?所以,一方面作者自己要入戏,争取进入自己的故事世界,去那一片平行空间;另一方面,也得下点儿功夫去揣摩行文细节,深入研究一下平平常常的文字背后的大学问。
下面,放出那段被那人评价为没什么的段落来:--------------- 到得这年二月间,康熙差了赵良栋前来颁旨,皇帝立次子允(礻乃)为皇太子,大赦天下,韦小宝晋爵一级,封为二等通吃伯。
韦小宝设宴请赵良栋吃酒,席上赵良栋说起讨伐吴三桂的战事,说道吴三桂兵将厉害,王师诸处失利。
韦小宝道:“赵二哥,请你回去奏知皇上,说我在这里实在闷得无聊,还是请皇上派我去打吴三桂这老小子去罢。
“赵良栋道:“皇上早料到爵爷忠君爱国,得知吴逆猖獗,定要请缨上阵。
皇上说道,韦小宝想去打吴三桂,那也可以,不过他得给我先灭了天地会。
否则的话,还是在通吃岛上钓鱼捉乌龟罢。
” 韦小宝眼圈红了,险些哭了出来。
赵良栋道:“皇上说,从前汉朝汉光武年轻的时候,有个好朋友叫做严子陵。
汉光武做了皇上之后,这严子陵不肯做大官,却在富春江上钓鱼。
皇上又说,从前周武王的大臣姜太公,也在渭水之滨钓鱼。
周武王.汉光武都是古时候的好皇帝,可见凡是好皇帝,总得有个大官钓鱼。
《鹿鼎记》:历史虚构与幽默的结合

《鹿鼎记》:历史虚构与幽默的结合
简介
《鹿鼎记》是中国作家金庸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被广大读者誉为中国武侠小说中的经典之作。
这部小说以明朝嘉靖年间为背景,描绘了一个荒诞而离奇的故事,融合了历史与幽默元素。
本文将探讨《鹿鼎记》如何将历史虚构和幽默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历史虚构的背景设置
在《鹿鼎记》中,金庸通过对明朝时期各类人物、事件和社会现象进行刻画,虚构了一个独特的历史背景。
他重新演绎了明朝宫廷、江湖等环境,并且创造了许多重要人物角色。
通过这种历史虚构的手法,金庸能够自由地展示他想要呈现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
幽默元素的运用
与其他金庸小说相比,《鹿鼎记》有着更多的幽默元素贯穿全书。
通过对人物对话、行为的幽默描写,金庸成功地给小说增添了轻松活泼的氛围。
这种幽默元素常常出现在角色之间的互动中,例如韦小宝与其他人物间的对话扯皮,以及小说中各个角色身上发生的滑稽事情。
《鹿鼎记》的文学价值
《鹿鼎记》之所以成为经典之作,不仅在于其历史虚构和幽默元素的巧妙应用,更重要的是它所探讨的社会问题和人性追求。
小说中涉及了权谋、爱情、友情
等主题,并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反映了这些问题。
同时,《鹿鼎记》也提
供了对社会秩序、贵族与平民关系等方面深入探讨和思考的机会。
结论
综上所述,金庸先生创作的《鹿鼎记》通过将历史虚构和幽默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呈现了一个独特而有趣的故事世界。
这部小说以其文学价值和娱乐性赢得
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并不断影响着后来的文学作品。
无论是对于喜爱武侠小说
的读者还是对于文学研究者,阅读和探讨《鹿鼎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析金庸武侠小说中“侠”的文化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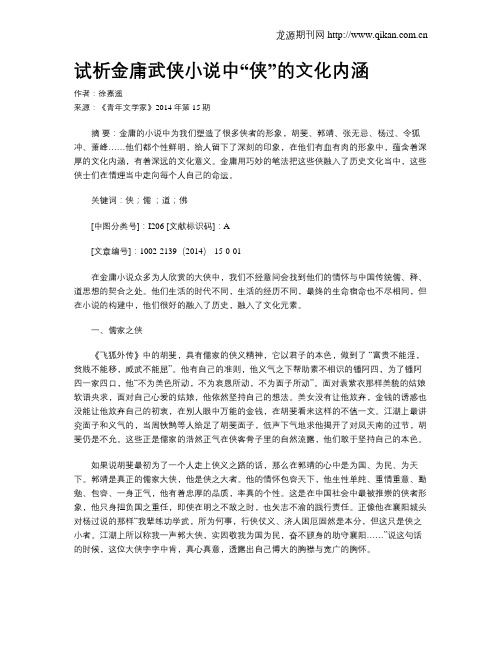
试析金庸武侠小说中“侠”的文化内涵作者:徐嘉遥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15期摘要:金庸的小说中为我们塑造了很多侠者的形象,胡斐、郭靖、张无忌、杨过、令狐冲、萧峰……他们都个性鲜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们有血有肉的形象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有着深远的文化意义。
金庸用巧妙的笔法把这些侠融入了历史文化当中,这些侠士们在情理当中走向每个人自己的命运。
关键词:侠;儒;道;佛[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5-0-01在金庸小说众多为人欣赏的大侠中,我们不经意间会找到他们的情怀与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的契合之处。
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同,生活的经历不同,最终的生命宿命也不尽相同,但在小说的构建中,他们很好的融入了历史,融入了文化元素。
一、儒家之侠《飞狐外传》中的胡斐,具有儒家的侠义精神,它以君子的本色,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他有自己的准则,他义气之下帮助素不相识的锺阿四,为了锺阿四一家四口,他“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
面对袁紫衣那样美貌的姑娘软语央求,面对自己心爱的姑娘,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
美女没有让他放弃,金钱的诱惑也没能让他放弃自己的初衷,在别人眼中万能的金钱,在胡斐看来这样的不值一文。
江湖上最讲究面子和义气的,当周铁鹪等人给足了胡斐面子,低声下气地求他揭开了对凤天南的过节,胡斐仍是不允。
这些正是儒家的浩然正气在侠客骨子里的自然流露,他们敢于坚持自己的本色。
如果说胡斐最初为了一个人走上侠义之路的话,那么在郭靖的心中是为国、为民、为天下。
郭靖是真正的儒家大侠,他是侠之大者。
他的情怀包容天下,他生性单纯、重情重意、勤勉、包容、一身正气,他有着忠厚的品质,率真的个性。
这是在中国社会中最被推崇的侠者形象,他只身担负国之重任,即使在明之不敌之时,也矢志不渝的践行责任。
正像他在襄阳城头对杨过说的那样“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
鹿鼎记江湖的荣辱与英雄的嬉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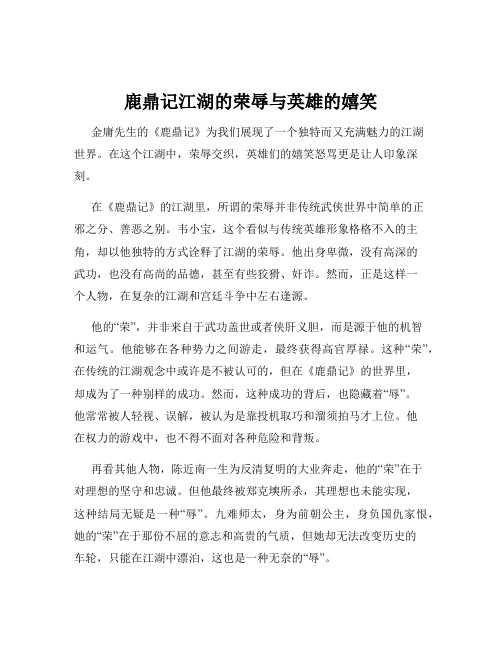
鹿鼎记江湖的荣辱与英雄的嬉笑金庸先生的《鹿鼎记》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独特而又充满魅力的江湖世界。
在这个江湖中,荣辱交织,英雄们的嬉笑怒骂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在《鹿鼎记》的江湖里,所谓的荣辱并非传统武侠世界中简单的正邪之分、善恶之别。
韦小宝,这个看似与传统英雄形象格格不入的主角,却以他独特的方式诠释了江湖的荣辱。
他出身卑微,没有高深的武功,也没有高尚的品德,甚至有些狡猾、奸诈。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物,在复杂的江湖和宫廷斗争中左右逢源。
他的“荣”,并非来自于武功盖世或者侠肝义胆,而是源于他的机智和运气。
他能够在各种势力之间游走,最终获得高官厚禄。
这种“荣”,在传统的江湖观念中或许是不被认可的,但在《鹿鼎记》的世界里,却成为了一种别样的成功。
然而,这种成功的背后,也隐藏着“辱”。
他常常被人轻视、误解,被认为是靠投机取巧和溜须拍马才上位。
他在权力的游戏中,也不得不面对各种危险和背叛。
再看其他人物,陈近南一生为反清复明的大业奔走,他的“荣”在于对理想的坚守和忠诚。
但他最终被郑克塽所杀,其理想也未能实现,这种结局无疑是一种“辱”。
九难师太,身为前朝公主,身负国仇家恨,她的“荣”在于那份不屈的意志和高贵的气质,但她却无法改变历史的车轮,只能在江湖中漂泊,这也是一种无奈的“辱”。
而英雄们的嬉笑,更是《鹿鼎记》的一大特色。
韦小宝的嬉笑,是他应对生活的一种方式。
他用看似不正经的态度,化解了无数的危机。
他的玩笑话背后,往往隐藏着他对世事的洞察和对人性的理解。
比如他与康熙之间的相处,常常以嬉笑打闹的方式进行,但在这背后,却是两人深厚的情谊和复杂的权力博弈。
又如多隆,这个看似头脑简单、只知道吃喝玩乐的角色,他的嬉笑让人觉得他是个糊涂虫。
但实际上,他的这种表现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和生存之道。
在充满阴谋和危险的宫廷中,他以这种看似愚笨的方式得以保全自己。
《鹿鼎记》中的江湖,没有了那种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形象,而是充满了世俗的气息。
论金庸武侠世界的异类

论金庸武侠世界的异类作者:高海鸥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14期摘要:说到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相信每个人想到的又会是小说中身怀绝技义薄云天的大侠们。
忠诚、仁义、善良、豪爽是这些大侠们的共同特点。
唯独《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却剑走偏锋,推翻了金庸先生原先对待笔下主人公的一贯写法。
关键词:韦小宝;精神;人性;民族观;武侠[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4-0-01如果问哪部作品是金先生武侠小说的总结之作,我想拿一定是《鹿鼎记》。
主人公“韦小宝是一个特殊的人物。
金庸把在香港观察到的丰富的社会经验化用到韦小宝身上,形成一个可以大大分析的人物。
”[1]一、从韦小宝谈“国民性格批判”金先生说,自己写《鹿鼎记》时想起《阿Q正传》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因而其在《阿Q正传》影响下,试图以韦小宝来描写“国民性格”:“精神胜利的意念在中国的确相当悠久而普遍,但是却不是中国所独有的。
有时走访国外,我也常发现:几乎每个地方的人民都有他们精神胜利的方式。
所以我试图从另一角度去探索中国人所特有的一面性格。
”[2](一)精神胜利法《阿Q正传》中的阿Q是民国时期的无名小卒,金先生笔下的韦小宝则是因为机缘巧合从市井小民摇身变成皇帝身边的王公大臣,两个人物虽然相隔250年,精神胜利法却都是他们共同的自乐心理。
“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阿Q在挨了赵太爷的打,回到土谷祠,忿忿地想到。
可是当他想到赵太爷的威风时,便自己爬起身,唱起《小孤孀上坟》来显示自己的得意。
市井的韦小宝完全如出一辙?偷偷摸摸坐了次皇帝的龙椅,不屑的放言“做皇帝也没什么了不起”,但终究没有胆量敢久坐,听到有人进来,就已经吓得一身冷汗,缩到书架后面去了。
当看到鳌拜向康熙叩头时,又把身子稍稍斜出,斜对鳌拜,心道:“你又向皇帝叩头,又向老子叩头,什么满洲第一勇士,第二勇士,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向我韦小宝叩头?”韦小宝的这种心态不就正是第二个“阿Q”?他用“精神胜利”法使自己始终保持着一种心理优势,而这种心理优势实际上只是处于社会最底层市井小民的自尊、麻木和自慰。
鹿鼎记读后感作文

鹿鼎记读后感作文鹿鼎记读后感1作为一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封笔之作,本书是本很特殊的作品,与金庸之前的作品截然不同!书名:《鹿鼎记》更是能引起读者的深思,取自逐鹿中原,问鼎中原。
本书的特殊之处便在于其主人公,他完全颠覆了金庸先前笔下所创造过的大侠!不是《射雕英雄传》中憨厚、老实的郭靖,不是《神雕侠侣》中用情专一的杨过……韦小宝武功平平,且为人贪财、好色、好赌、怕死,妓院出生的他,几乎包罗了清朝社会中最底层流氓的所有陋习!更是与“侠”字南辕北辙。
而金庸却和他一起结束了武侠写作生涯,给了他更多的古怪运气,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被茅十八带入皇宫的他,被收入海公公门下,却逃过惨酷的宫刑。
又在无意间结识了千古一帝——康熙。
二人心心相吸,更是结为兄弟!此后,韦小宝除熬拜、除吴三桂、平台湾……一路建立功勋,也一路搜刮钱财,从一个小太监竟升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鹿鼎公。
以大量的笔墨讽刺了清朝腐败、昏庸的官风。
不仅如此,他总能以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加上上帝赐予的运气逢凶化吉。
成为了陈近南的弟子,天地会香主,神龙岛的白龙使,取得人们梦寐以求的八本《四十二章经》……然而,人们谈论最多的是韦小宝和他的第七任妻子。
几乎一无是处的韦小宝用正直和高超的武艺赢得了比以往所有英雄更多的荣誉和快乐。
这难道真的只是因为犹如超自然现象的运气吗?更因为他有一个道德底线,对于外人他可以如地痞流氓般可恶,可一但关乎兄弟、亲人之时,他总会放弃自前所有的陋习。
因为仗义,他总是在天地会与清朝朝廷间两难!最后,不得不归隐山林。
然而,书中其余之人尽是些伪君子型的人物,一但涉及利害关系便会凶象必露。
书中,郑克塽如是,吴应熊亦是如是。
比起小宝的“真”而言,更要遭人厌恶百倍不只。
金庸便以如此另类的方式,以笔下最后一位英雄,深入人心地诠释了“武侠”二字。
在生活中,我们也应该保持一个人最真实的样子。
我们应该有明确的道德底线。
我们做不到如郭靖、杨过那般,可是高于韦小宝却是很容易的!鹿鼎记读后感2一口气看完了《鹿鼎记》,只觉畅快淋漓之极。
无极的寂寞——从《鹿鼎记》看金庸对侠义精神文化的独特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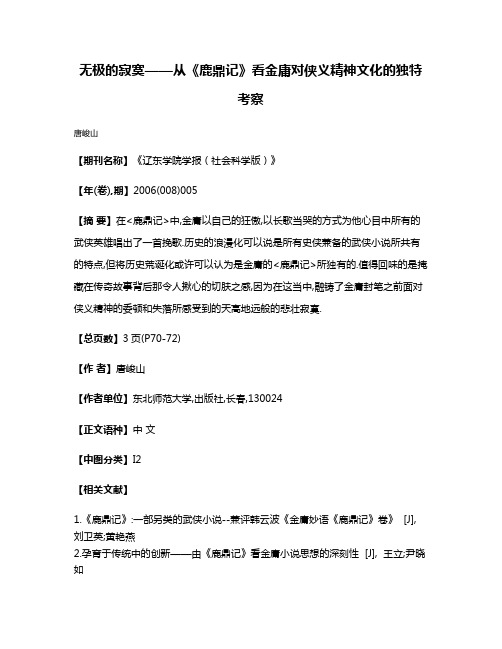
无极的寂寞——从《鹿鼎记》看金庸对侠义精神文化的独特
考察
唐峻山
【期刊名称】《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6(008)005
【摘要】在<鹿鼎记>中,金庸以自己的狂傲,以长歌当哭的方式为他心目中所有的武侠英雄唱出了一首挽歌.历史的浪漫化可以说是所有史侠兼备的武侠小说所共有的特点,但将历史荒诞化或许可以认为是金庸的<鹿鼎记>所独有的.值得回味的是掩藏在传奇故事背后那令人揪心的切肤之感,因为在这当中,融铸了金庸封笔之前面对侠义精神的委顿和失落所感受到的天高地远般的悲壮寂寞.
【总页数】3页(P70-72)
【作者】唐峻山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长春,13002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
【相关文献】
1.《鹿鼎记》:一部另类的武侠小说--兼评韩云波《金庸妙语《鹿鼎记》卷》 [J], 刘卫英;黄艳燕
2.孕育于传统中的创新——由《鹿鼎记》看金庸小说思想的深刻性 [J], 王立;尹晓如
3.《鹿鼎记》:一部另类的武侠小说 --兼评《金庸妙语〈鹿鼎记〉卷》 [J], 黄艳燕
4.从文体学视角看武侠小说英译——以金庸先生小说《鹿鼎记》为例 [J], 刘君雅;
5.随英雄侠客浪迹江湖——从武侠小说进语文课本看金庸小说的独特魅力 [J], 崔正升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侠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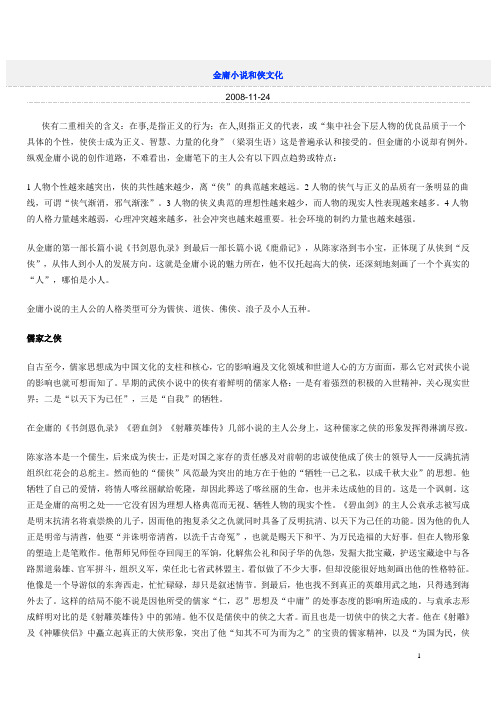
金庸小说和侠文化2008-11-24侠有二重相关的含义:在事,是指正义的行为;在人,则指正义的代表,或“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于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梁羽生语)这是普遍承认和接受的。
但金庸的小说却有例外。
纵观金庸小说的创作道路,不难看出,金庸笔下的主人公有以下四点趋势或特点:1人物个性越来越突出,侠的共性越来越少,离“侠”的典范越来越远。
2人物的侠气与正义的品质有一条明显的曲线,可谓“侠气渐消,邪气渐涨”。
3人物的侠义典范的理想性越来越少,而人物的现实人性表现越来越多。
4人物的人格力量越来越弱,心理冲突越来越多,社会冲突也越来越重要。
社会环境的制约力量也越来越强。
从金庸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剑恩仇录》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鹿鼎记》,从陈家洛到韦小宝,正体现了从侠到“反侠”,从伟人到小人的发展方向。
这就是金庸小说的魅力所在,他不仅托起高大的侠,还深刻地刻画了一个个真实的“人”,哪怕是小人。
金庸小说的主人公的人格类型可分为儒侠、道侠、佛侠、浪子及小人五种。
儒家之侠自古至今,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支柱和核心,它的影响遍及文化领域和世道人心的方方面面,那么它对武侠小说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
早期的武侠小说中的侠有着鲜明的儒家人格:一是有着强烈的积极的入世精神,关心现实世界;二是“以天下为已任”,三是“自我”的牺牲。
在金庸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几部小说的主人公身上,这种儒家之侠的形象发挥得淋漓尽致。
陈家洛本是一个儒生,后来成为侠士,正是对国之家存的责任感及对前朝的忠诚使他成了侠士的领导人——反满抗清组织红花会的总舵主。
然而他的“儒侠”风范最为突出的地方在于他的“牺牲一已之私,以成千秋大业”的思想。
他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将情人喀丝丽献给乾隆,却因此葬送了喀丝丽的生命,也并未达成他的目的。
这是一个讽刺。
这正是金庸的高明之处——它没有因为理想人格典范而无视、牺牲人物的现实个性。
论《鹿鼎记》的“反武侠”特征

论《鹿鼎记》的“反武侠”特征作者:罗麒来源:《江汉论坛》2009年第07期摘要:《鹿鼎记》以对传统武侠小说之道的选出与偏离,在形象塑造、情节架构和思想意蕴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反武侠”特征,但其内在灵魂仍是对侠义精神的呼唤,它开辟了新武侠小说的“另一种写法”。
关键词:《鹿鼎记》;反武侠;“英雄”;“传奇”;另一种写法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7-0122-04有人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这话也许略有夸大,但金庸小说的水准之高与传播之广却是不争的事实。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的十几部作品几乎将武侠小说创作推向了最为辉煌的状态。
而在这些作品中,《鹿鼎记》无疑是一个特例,它“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主角韦小宝的品德,与一般的价值观念太过违反”受作者这种判断的导引,很多人认为《鹿鼎记》称不上传统意义上的武侠小说,主人公韦小宝非但不是武林高手,连为人行事也与人们心目中的“侠”字相去万里。
那么何为武侠?武侠乃武者之侠,它最基本的组成要素一为武,一为侠。
武者,止戈为武,即以正义的非和平方式去制止非正义的争斗;侠者,用金庸的话说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虽分多种,本质上却都不脱侠、义二字。
若按此标准考察,《鹿鼎记》在形象塑造、情节架构和思想意蕴等方面,的确对传统的武侠小说之道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离。
但是我认为,说《鹿鼎记》是武侠小说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它在许多地方已经逸出武侠小说的常规和品性,带着一种“反武侠”的艺术倾向。
或者说。
它开启了武侠小说的另一种写法,是武侠小说中的“异类”,是具有“反武侠”特质的武侠小说。
一、非武非侠的“英雄”金庸笔下的主人公往往是武功盖世、行侠仗义的英雄,如陈家洛、袁承志、郭靖、杨过、张无忌、令狐冲等,可是《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却“非武非侠”,让人大跌眼镜。
金庸笔下的韦小宝,于武功实在是“不学无术”到了一定份上。
解读《鹿鼎记》中韦小宝的“侠”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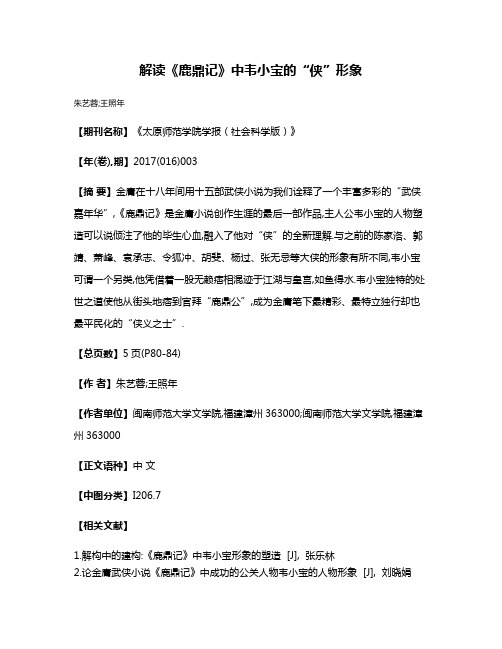
解读《鹿鼎记》中韦小宝的“侠”形象
朱艺蓉;王照年
【期刊名称】《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7(016)003
【摘要】金庸在十八年间用十五部武侠小说为我们诠释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武侠嘉年华”,《鹿鼎记》是金庸小说创作生涯的最后一部作品,主人公韦小宝的人物塑造可以说倾注了他的毕生心血,融入了他对“侠”的全新理解.与之前的陈家洛、郭靖、萧峰、袁承志、令狐冲、胡斐、杨过、张无忌等大侠的形象有所不同,韦小宝可谓一个另类,他凭借着一股无赖痞相混迹于江湖与皇宫,如鱼得水.韦小宝独特的处世之道使他从街头地痞到官拜“鹿鼎公”,成为金庸笔下最精彩、最特立独行却也最平民化的“侠义之士”.
【总页数】5页(P80-84)
【作者】朱艺蓉;王照年
【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漳州363000;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漳州363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7
【相关文献】
1.解构中的建构:《鹿鼎记》中韦小宝形象的塑造 [J], 张乐林
2.论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中成功的公关人物韦小宝的人物形象 [J], 刘晓娟
3.论金庸电影《鹿鼎记》中韦小宝形象的审美趣味 [J], 张鹏飞
4.反侠之侠--解读韦小宝身上的市井与传统 [J], 王建华
5.世俗中重构的英雄魂——试论《鹿鼎记》中韦小宝的形象塑造 [J], 陈启霞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既然金庸塑造的韦小宝是一个反侠形象,下面分析一下,金庸是如何在韦小宝身上实现对传统之“侠”的解构的。
1、韦小宝的工夫
韦小宝年幼力弱又偷懒,不肯花精力学武功,但却时时在强敌面前逞能,面临大敌时通常是动口不动手。他拜了天地会武林高手陈近南为师,这本来是个难得的机会,而韦小宝对那些高深的武功一点兴趣也没有。可是韦小宝是个现实的人,他自知所做的理亏事也不少,怕有危险时跑不快,故很卖力地练他的女师父九难师太教他的“神行百变轻功”。这脚底抹油的功夫是他最像样的功夫了,但也只练到三、四成功,因为他觉得能够让他逃离敌人就够了。
3、韦小宝的流氓处世学
韦小宝这个人物性格的复杂,绝对不能轻易以亦正亦邪就把他复杂多面的性格轻松地概括过去。曾有不少人赞扬过《鹿鼎记》里韦小宝有侠义精神,但那是真正的侠义吗?《鹿鼎记》中韦小宝在江湖和朝廷的双重历险记中最大的支撑点,是抽象化了的“江湖义气”。他正是倚靠“义气为重”的原则,才能游离于“正”与“邪”、“朝”与“野”等各种不同的社会,而且被价值观念如此迥然有别的多种社会所重视。韦小宝的深层文化精神却与他的“忠义”精神相矛盾。也即是说,在“忠义”和个人的生存权面前,韦小宝把个人的存在,个人的荣辱,个人的安危,个人的享乐置于“忠义”之上。韦小宝这位“反英雄”,是金庸的“自反”的实验描写。
三、韦小宝对“侠”的彻底解构
从传统意义上的儒之侠郭靖,道之侠令狐冲,佛之侠石破天,渐渐走向了非侠甚至反侠韦小宝。《鹿鼎记》中,金庸理想中的“阳刚”世界受到了颠覆。韦小宝这一“非英雄”形象,是金庸对自己定义的理想男性的嘲讽。通过滑稽摹仿的修辞手段和文学演绎,金庸对他以前理想的男性定义做了一番解构。
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化提炼和反映,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均可在文学作品中寻找到自己的对应物。流氓的角色和活动当然也包含在内,而反映社会小人物的通俗文学更是如此。韦小宝不是等闲之辈,控制朝野各派政治势力,甚至策动邻国政变,成就了一番惊天动地的政绩伟业,君主倚重,多少鸿儒英杰相形而见绌。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故事,是金庸对中国几千年的流氓政治生动的文学演绎。这部作品至少反映金庸对中国政治和历史的一个基本看法:“最后的胜利常常是属于流氓的。如果说严酷的政治斗争有时也会演出喜剧的话,那笑到最后也笑得最好的主角一定是个流氓。”[2]《鹿鼎记》通过流氓的胜利,政治的力量展示,反衬了武林人物的失败。
金庸笔下的英雄人物大都深明大义,自觉地在为百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生命的人物形象。大侠是一种价值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文化英雄。他们都体验到生存内在的困境,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存在的意义,肩负起民族精神。
二、金庸小说中侠者形象的早期解构
可是金庸并没有沿着这条高昂的侠义之路写下去,后期的小说创作中,却渐渐地走上了 对侠文化的解构这条道路,就是对侠观念的怀疑。《倚天屠龙记》中,金庸写过这样的对话“行侠仗义有什么好?为什么要行侠仗义?”“胡说八道,你说武林之中,当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么?”在这里,金庸借谢逊之口道出了江湖文化的本质,侠文化在消解江湖文化,维护秩序时的局限性。既然江湖是一个唯力世界(极权社会),波谲云诡,那么侠义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游戏规则,所以小说中,侠义往往敌不过武功和阴谋。
在《连城诀》中,我们就看到了当侠被逼上了生存绝境时,是如何的不堪一击。花铁杆设若不是被困在大雪山中谁也不会怀疑他是一代大侠,然而正由于他面对生存绝境时兽性战胜了侠性,卑躬屈膝,以致于吃掉义兄尸首,信口造谣,人性卑污大暴发,我们才不得不像谢逊那样,对侠的价值观到底有多大作用产生怀疑,对侠本身的道德标准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创作之初,金庸笔下的侠士就暴露了许多人的弱点:陈家洛优柔寡断,郭靖木讷愚笨,杨过偏狭,张无忌缺乏主见。
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作家向来相信“宁可无武,不可无侠”的观念进行创作, 武侠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侠士,这已经是一种共识。而没有侠义精神的小说还算得上武侠小说吗?因此有评论家说《鹿鼎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侠小说,而是一部描写世情的反武侠小说。该小说的风格、故事情节与金庸其他作品相去甚远,彻底地打破了我们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心态中的“侠之梦”。
《鹿鼎记》对侠的反讽,导致侠的非英雄化,江湖世界的非理想化,同时瓦解了武侠小说固有的崇高风格和乐观精神,甚至也消解了武侠小说中“武”与“侠”的崇拜。也许金庸以后还会有新的武侠小说出现,但可以断言,不会有超出金庸的武侠小说,因为一部《鹿鼎记》已经成功地完成了武侠小说的现代化实验,其结果是“侠之梦”的解体。
2、韦小宝的“国民劣根性”
在《鹿鼎记》中可看出金庸小说的创作主题离国家民族之本位愈来愈远,而离人性、人生的意旨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深。韦小宝这个人物形象就具有相当深刻的象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中华文化中某些共性的东西,即中国“国民的悲剧”与“文化悲剧”。孔庆东先生在《空山疯语》中提到:“这里蕴涵了对中国社会体制和国民性的深刻批判,其深度或不及《阿Q正传》,而广度则有过之。从文化价值上看,韦小宝是20世纪中国文学里仅次于阿Q的典型形象。” 金庸自己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说自己写韦小宝是受了阿Q的启发,实际上韦小宝是一个因意外奇遇而获得成功的“阿Q”。欲望被释放了的韦小宝一方面是中国各民族的“杂种”,一方面又是一个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纯种”中国人。“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国民劣根性的代名词,它的基本症状在小说主人公韦小宝身上都能找到最集中的体现。如:自轻自贱,自大自夸,化丑为美,麻木健忘,欺软怕硬,忌讳缺点,把失败幻想成胜利,在精神胜利中逃避失败的痛苦,却不思改变失败的现实。敌强我弱时,韦小宝用精神胜利法,一旦形势转化有利时,他又善于抓住时机,积极进攻,所以他总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
《鹿鼎记》是金庸小说的封笔之作,也是武侠小说中的“四不象”作品。《鹿鼎记》表面上看似一幕诙谐荒唐的喜剧,骨子里却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悲剧史诗和文化寓言,俗极而雅,奇而致真。在笔者看来它代表金庸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它超出了江湖恩怨、武林夺宝的旧模式,通过壮阔的画面与多彩的人物个性,运用调侃的语言,对他一直着力书写的“侠”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反讽与解构。主人公韦小宝是以一个反侠的形象走进读者的视野的,由于此形象的创新与反传统,他所带来的争议在“金迷”读者与“金学”研究者中一直未曾休止。
什么是侠的精神?金庸先生在为著名金评家吴霭仪的《金庸小说的男子》写的小序中说:“在武侠世界中,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当先’。仁是对大众的疾苦冤屈充分关怀,义是竭尽全力作份所当为之事。引申出去便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与墨家,两者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1]
那么金庸先生是如何在《鹿鼎记》中对“侠”进行解构的呢?笔者认为,主要是从小说的主角韦小宝身上来实现的。在论述这一论点前,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金庸先生其他著作中的传统侠者。
一、金庸其他著作中的传统之“侠”
什么是侠的行为?追溯起来,“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中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一句。这句话写出了侠必有武,必会武,必能武之意。
从这番解构中,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他的“游离性”立场。韦小宝能游离于江湖与朝廷之间,正与邪之间,情与欲之间,满人与汉人之间,在多种不同的价值体系中游刃有馀。没有甚么高尚的理想,不区分情与欲。他之所以能左右逢源,与他的“中间”(in-between)角色分不开。这种角色,不存在身份认同的危机,恰恰可以超越简单的“压迫/反抗”的殖民主义/反殖民主义话语。
“侠”在某种层面上来讲是儒家文化中的一部分,可用四个字来概括:忠孝节义。对父母亲要孝,对兄弟姐妹要亲如手足,对国家要忠,而对自己则要严格要求,做到讲信用、讲礼貌、讲义气、知廉耻。武德上者,侠士也。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侠”与“义”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义是中国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飞狐外传》中的胡斐才称得上古典之侠,为了素不相识的钟阿四一家,追杀恶霸凤天南而不遗余力;还有反清复明的陈家洛、反明抗清袁承志、抗金卫国的郭靖、邱处机、反元保家的张无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郭靖,以一介平民之身,“铁肩担道义”,死守襄阳十数载,最后以身殉国。至于萧峰比起郭靖来是更上了一个层次的大侠,他处在宋辽对峙的夹缝中,面对契丹、大宋百姓的灾难,义字当先、以死弭兵。除此之外,令狐冲信守承诺接掌恒山派300多个尼姑让人感叹;就算是狂放不羁的杨过,在攸关民族大义的大事上也还是有分寸的。
传统武侠小说在弘扬侠义精神的同时,表现出一种试图依靠武力来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倾向。武艺非凡是一个“侠者”必备的条件。《射雕英雄传》中生性迟钝的郭靖靠降龙十八掌独步天下,黄蓉的打狗棒法青出于蓝胜于蓝。《笑傲江湖》中令狐冲的独狐九剑更加是使得出神入化。《侠客行》中的石破天在故事的最末也学会了侠客行剑法。《神雕侠侣》中的杨过算是武功学得最多的:打狗棒法、弹指神功、蛤蟆功、九阴真经、默然销魂掌。众观金庸除《鹿鼎记》外的小说,不仅所有的小说主角都身怀绝技,就连许多配角也都是武功了得。金庸笔下的大侠们,有哪一个不是练成绝世武功而在武林中扬名立万的?
4、韦小宝现象的社会批判意义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曾经痛切地批判过中国社会的“酱醋缸文化”,这种文化与韦小宝种种行径不谋而合。鲁迅在谈到小说的社会影响时说:“中国人的江湖思想,妖巫湖鬼思想、堪舆、相命、卜筮、迎神赛会等等陋习劣行都来自小说,”因而他才主张要进行小说革命。[3]
韦小宝的马屁艺术、为官之道、流氓处世学与流氓政治手段,在现实社会中为了生存和利益而争相效仿的人不在少数。除此外他对女人的态度也给现实男权社会提供了一个现成的例子与导向。“韦小宝现象”给读者和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警醒,也带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它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以引导人们逃避现实的方式来肯定和维护现实,起着“社会水泥”的作用,对一般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