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耀华先生与新中国的民族研究
人类学家

人类学家人类学家介绍林耀华先生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介绍林耀华(1910年3月27日-2000年11月27日)中国福建省古田县人,于1910年3月27日生在福建省古田县岭尾村。
中国社会学界、人类学界、民族学界一代宗师。
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获学士学位;1935年获该校硕士学位;1940年获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哲学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并于1941年-1942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42年一1952年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并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52年起任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
他致力于原始社会史和民族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培养了一批教学和科研人员,为中国的人类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对中国汉族的宗族组织及凉山彝家的社会组织的研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一代宗师,学界泰斗。
林耀华先生主要著作:1.The Golden Wi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Family,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47. 中文版《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庄孔韶、林宗成译,三联书店,北京,1989。
2000年再版。
2.《凉山彝家》,商务印书馆,1947。
英文The Lolo of Liangshan (Liang-shan I-chia) 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Inc. New Haven, 1960.3.《从猿到人的研究》,北京耕耘出版社,1951。
4.《原始社会史教学大纲》(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审定,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
5.《原始社会史》(主编),中华书局,北京, 1984。
6.《父系家族公社形态研究》(合著)(青海人民出版社,青海,1984年)7.《民族学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5。
从《义序》,看中国传统社会的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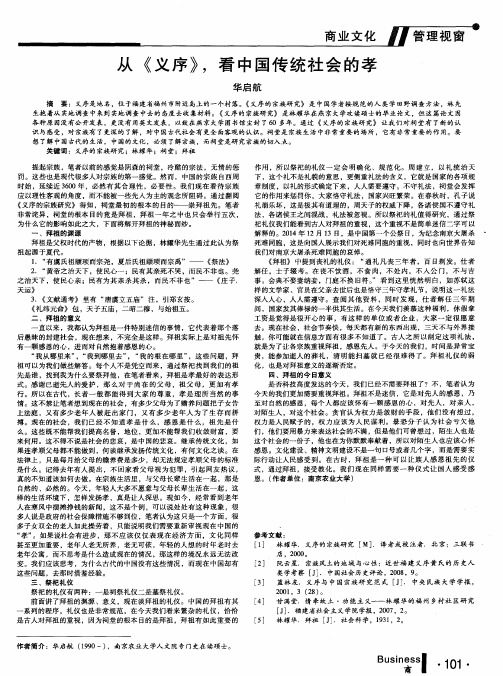
提起宗族 ,笔者 以前 的感觉是 阴森 的祠堂 ,冷酷 的宗法 ,无情 的惩 罚 。这些也是现代很多人对宗族 的第一感觉 。然而 ,中国的宗族 自西 周 时始 ,延续近 3 6 0 0年,必 然有其 合理性 ,必要性 。我们 现在看 待宗族 应以理性客观的角度 ,而不能被一些先人为 主的观念所 阻碍。通过 翻阅 《 义序 的宗族研究 》 得知 ,祠堂最初 的根本 的 目的——崇拜祖 先 。笔者 非常诧异 ,祠堂的根本 目的竟是拜祖 ,拜 祖一 年之 中也 只会举行 五次 , 为什么它的影响如此之大 ,下面将解开拜祖 的神秘面纱 。 拜 祖 的 渊 源 拜祖 是父权时代的产物 ,根据以下论据 ,林耀华先生通过 此认为祭 祖起 源于夏代。 1 .“ 有虞 氏祖颛顼 而宗尧 ,夏后 氏祖颛 项而宗禹”—— 《 祭法》 2 .“ 黄帝之治天下 ,使 民心一 ;民有其亲死不哭 ,而民不 非也 。尧 之 治天下 ,使民心亲 ;民有为其亲 杀其杀 ,而 民不非 也 ”—— 《 庄子. 天运 》 3 .《 文献通考》 里有 “ 唐虞立五庙” 注 ,引郑玄按。 《 礼纬元命》 包 ,天子 五庙 , 二 昭二穆 ,与始祖 五。
一
一
作用 ,所以祭祀的礼 仪一 定会 明确 化 、规 范化 。周建 立 ,以礼统 治天 下 ,这 个礼不是礼貌 的意思 ,更侧重礼法 的含义 ,它就是 国家 的各项规 章制 度 ,以礼 的形式确定下来 ,人人需要遵守 。不守礼法 ,祠 堂会 发挥 它的作 用来惩罚你 ,大家恪守礼法 ,国家兴旺繁荣 。在春秋 时 ,孔子说 礼崩乐坏 ,这是极其有道理 的,周天子的权威下降 ,各诸侯 国不遵 守礼 法 ,各诸侯王之间混战 ,礼法被忽视。所 以祭祀的礼值得研 究 ,通 过祭 祀礼仪 我们能看到古人对拜祖的重视 ,这个重视不是简单迷信 二字可 以 解释 的。2 0 1 4年 1 2月 1 3日,是 中国第一个公祭 日,为纪念南京大屠杀 死难 同胞 ,这是 向国人展示我们对死难同胞的重视 ,同时也 向世界 告知 我们对南京大屠杀死难 同胞 的哀悼 。 《 拜祖》 中提到丧礼的礼仪 : “ 通礼凡 丧三 年者 ,百 日剃发 。仕 者 解任 ,士子 辍考 。在 丧不 饮酒 ,不食 肉,不处 内 ,不入 公 门,不与 吉 事 。会典不娶妻纳妾 ,门庭不换 旧符 。 ” 看 到这 里恍然 明 白,如苏轼 这 样 的文学家 、官员在父亲去世后也是恪守三年守孝礼节 ,说 明这一 礼法 深人人心 ,人人需遵守。查 阅其 他 资料 ,同时发 现 ,仕 者解 任 三年 期 间,国家发其俸禄的一半供其生活 。在今天我们羡慕这种福利 ,休 假拿 工资是觉得是很开 心 的事 ,有这样 的单 位或 者企 业 ,大家 一定 很愿 意 去。现在社会 ,社会节奏快 ,每天都有新 的东西出现,三天不与外界 接 触 ,你可能就在信息方面有很 多不 知道 了。古人之 所 以制 定这项礼 法 , 就是为 了让各宗族重视拜祖 ,感恩先人。于今天的我们 ,时间是异 常宝 贵 ,能参加逝人的葬 礼 ,清 明能扫 墓就 已经 很难得 了。拜祖 礼 仪 的弱 化 ,也是对拜祖意义的逐渐否定。 四 、拜 祖 的 今 日意 义 是否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 ,我们已经 不需要拜 祖了?不 ,笔者认 为 今天的我们更加需要重视拜祖。拜祖不是迷信 ,它是对先人 的感 恩 ,乃 至对 自然的感恩 ,每个人都 应该怀有 一颗感恩 的心 ,对先 人 ,对亲人 , 对陌生人 。对这个社会。贪官认 为权力是 敛财 的手 段 ,他们 没有想过 , 权力是人民赋予 的,权 力应 该为人 民谋 利。暴恐 分 子认 为社会 亏欠 他 们 ,他们要用暴力来表达社会的不满 ,但 是他们 可曾想 过 ,陌生人也 是 这个社会的一份子 ,他也在为你默默奉献着 ,所 以对 陌生人也应该心 怀 感恩 。文化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不是一句 口号或者几个 字 ,而是需要 实 际行动让人民感受 到。在古 时,拜祖 是一种 可 以让族 人感 恩祖 先 的仪 式 ,通过拜祖 ,接受教化 。我们 现在 同样需 要一 种仪 式让 国人 感受感 恩。 ( 作 者 单 位 :南 京 农 业大 学 )
费孝通先生与民族研究入“阁”乃至毕生

□文 /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李玥霖费孝通先生与民族研究:入“阁”乃至毕生15年前的4月24日,费孝通先生逝世。
费孝通先生28岁那年(1938年),抵达抗战大后方的昆明,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
此后除短暂离开外,他一直生活在云南,直至1946年。
云南不仅仅是费孝通先生的“第二故乡”,也是他作为学者和民族工作者,积累学术思想的地方。
这期我们对话云大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李伟华老师,请他介绍费先生与云南和云大那些铭刻在学术史上的往事,以此作为对费先生的纪念。
费孝通在魁阁费孝通先生与云大的魁阁时代今日民族:费孝通先生在云南的学术活动,经常跟“魁阁”联系起来。
“魁阁”是什么?李伟华:“魁阁”原指云南呈贡的魁星阁,建于1818年,1922年重修,当地也叫它“古城魁阁”。
这个地方进入学术史,是因为1940年后,有一群社会学人类学学者把这里当做工作场所。
在抗战时期,艰苦的生活条件下,这些学者以此为基地,共同探讨学术,创造出了杰出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和让后世仰慕的学术氛围。
费孝通先生当时是云大社会学系教授,主持云大社会学研究室。
而在魁阁办公的学者们,大部分都是这个研究室的成员。
其中有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谷苞、张宗颖、胡庆钧等青年,以及云大教授许烺光、云大社会学系讲师李有义等学者。
费孝通把他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习得的学风带到研究室,注重理论和实际结合,要求每一个研究人员都有自己的专题,并到选定的社区去进行实地调查。
调查完后,在“席明纳”里进行集体讨论,讨论完再由个人负责编写论文。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云南三村》(费孝通、张之毅)、《汉夷杂区经济》(李有义)、《芒市边民的摆》(田汝康)、《汉村与苗乡》(胡庆钧)、《祖荫下》(许)、《昆厂劳工》(史国衡)等著作,都是费孝通先生率领的云大社会学研究室,或者说“魁阁”的成果。
INTERVIEW 对话企业的主张,为80年代的小城镇研究开辟了道路。
光时刻。
今天很多人不知道的是,1947年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云大被列为中国15所著名大学之一。
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民族学——论林耀华先生的学科建设思想

广西 民族研究 2 1 年第 4 ( 01 期 总第 16 ) 0期
a t rsiso t n l g ,t e d v l p ntd r cin o t o o n Ch n ce it fe h oo e y h e eo me ie to fehn lg i i a,d s i ln r ae t r i i g,a a y icp i a y tln stan n c— d mi ai n t l fsu y,fed r n O o .T sr l tst re tn y tm fChie eEtn lg e c qu lt a d sye o t d i l wo k a d S n hi ea e opef ci g s se o n s h o o y y a h c o a p cs n o g i ig ma y deal tt e mir s e t ft e d v lp n ft e d s i l . tt e ma r s e t ,a d t u dn n t i a h c o a p cso h e e o me to icp i s h ne Th st o g tb n ftd fo Wu W e z o’ a i o e ta o o sr c in o o ilS in e n Chna i u h e e e r m n a S b sc c nc p b utc n t t fs c a C e e s i i . h i u o Ke r s:e n l g y wo d h t oo y;Ch n i a;Li o ua;d s i ln o t cin n Ya h icp i e c nsr t u o
从《银翅》中看中国农村研究的一个视角

从《银翅》中看中国农村研究的一个视角1.金银联翅“1984年,林耀华教授把他的英文著作《金翼》借给我阅读……林师以中国福建省闽江边乡村的两个农人家族兴衰为线索,描写和分析了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30年代地方农业、商业、船运、政治、法律、教育、宗教、宗教家族以及民俗等多方面的社会生活。
然而,《金翼》写作距今已逾半个世纪,其间社会沧桑与人事迁移,黄村及其所在的县镇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人类学如何提供新的乡土民族志并发现进一步的解释性理论和方法呢?这是笔者后来重访‘金翼’黄村时经常思考的问题。
”(庄孔韶《银翅》,北京三联,2000,第1页)庄孔韶教授由于接受了得天独厚的人类学专业训练,更兼有《金翼》作者的直接指导,不仅完成了《金翼》中人物、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转换,而且在《银翅》中,使得中国地方文化的过程也得到了充的展现。
《银翅》接续了《金翼》之家的家族变迁史,展示了20世纪20~90年代以“黄村”为代表的社区的历程,铺叙出了中国地方社会与文化的变迁过程。
《银翅》是庄孔韶先生关于中国家族制度与乡村社区研究大作《金翅》的续篇。
在《银翅》中,庄教授重访金翼黄村,“以金翼之家后辈生活经历与地方县镇众多人物事件相互穿插的社区过程研究,尤其强调田野工作鱼中国哲学、历史文献、人物思想、政治过程与文化行为的关联分析……”使该作成了“一部由浅入深的随笔、民族志、分析与论证等方法合一的学术作品”。
《银翅》的研究涉及到了土地制度、基层社会结构、土地改革、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生计方式、亲属制度、民间信仰、地方权力组织、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等多个领域。
2.宗族、房、家族的关系及其影响2.1概念的界定家族和宗族,都是人类学研究中经常出现的关键词。
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领域的大量同类研究中,宗族和家族的概念总是模糊不清。
许多学者言及当今中国农村的家族研究,讨论的是祠堂、聚落等宗族制度;对家族和宗族两个概念随意交替使用的文章比比皆是,更多的情况是,众多的研究者对概念的理解各有己见,在各自的研究旨趣中发展了大量关于家族和宗族内涵及外延的分析,却并未在同一个层面上就两个概念的区分有所争议,似乎这是一个为学界所淡化的问题。
三足鼎立_民族志的田野_理论和方法

民间文化论坛没有明确的田野调查点,甚至有些硕士、博士的学位论文你都很难找到它有一个具体的社区为依托。
另一个是平面化、扁平化。
有一些研究成果也是经过了田野调查,但更多的是过程的叙述或材料的堆积,基本上讨论的是一种表面的现象,没有深入的思考。
比如说,在文化变迁过程中,往往是说某一个族群,或者是说某一个村寨,几十年前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
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这种著作,整本的东西,实际上他在向读者展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或者说民族改革以前,这个少数民族的状况,然后用更多的篇幅来说明50多年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
当然,我们要分析这些东西,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影响这些变迁的因素是什么,力量有哪些,有哪些原因。
往往是这方面的分析很简短,而且非常概括,有些甚至这些都没有。
那你谈文化变迁,最后能谈点什么事情?这实际上是缺乏学科理论分析和阐释的表现。
这些年一直在思索民族志问题,思索人类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问题,最近我们有一个即将结题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也是讨论这个问题的。
作为人类学从业者来说,应该得到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训练,思考关于研究方法的问题,才能成为专业的研究人才。
这个专业人才培养和成长的模式有三种:一是学院训练型,二是田野实践型,三是学科史熏陶。
培养人才有一个过程,你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有很多讲究。
学院训练可能更多地需要课程学习和阅读,需要开设相关课程和专门的研讨。
对此可能看法不一样。
有些人认为,我们不需要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课程,让学生去读民族志就好了。
可能在反思人类学之前,应该是这样。
在反思人类学以后,怎么去做人类学研究,怎么去撰写民族志已经有了更多思考以后,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讨论这样的问题,知道从研究方法上来说,我们应该避免什么东西,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我们大多数时间可能会通过课程学习和专门的研讨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研究中,我们首先要熟悉规程,从各个环节,比如说选题、课题的准备、调查提纲的拟定、文献资料的收集、进入田野、参与观察、引出访谈问题、话语和文本分析、意义和表征分析、田野笔记的记录和编码、资料整理和民族志撰写。
科学为本的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林耀华学术研究评述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based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作者: 马威[1]
作者机构: [1]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出版物刊名: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页码: 9-15页
年卷期: 2020年 第12期
主题词: 林耀华;学科发展;科学为本;进化论
摘要:从《严复研究》开始,林耀华始终将"科学"贯穿于学术工作与人才培养。
在林耀华的学术生涯中,他以科学树立规范,以科学服务社会并以科学开拓新领域,履行了一位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先驱者的使命。
林耀华的学术生命折射了整个中国百年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反映出社会科学学术生产的动力与价值。
20世纪9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我国学科建设的科学坚持造成冲击,实验式、感悟式、自省式的民族志写作和研究影响了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规范性,影响了学科公信度,也使学科的学术地位逐渐边缘化。
回归科学的学科发展,坚持学术研究的规范性,践行联系实践的人才培养,才能让民族学人类学融入学术服务现实的主流道路。
浅谈对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的认知

浅谈对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的认知作者:刘宇来源:《环球人文地理·评论版》2014年第12期摘要:田野调查作为民族学家获取资料最根本的途径,是民族志架构的源泉。
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民族学工作者,熟悉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田野调查,笔者认为:它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必须结合实际行动,才能更好的理解渗透在其中的真谛。
关键词:民族学;田野调查;参与观察作为一名民族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田野调查方法是我们最基本也是最常使用的研究方法之一。
所谓田野调查,指的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的过程。
但是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来获取研究资料的,不仅仅只有民族学,还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各类学科。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田野调查方法在各个学科中的重要性。
英国功能学派代表人物——马凌诺夫斯基开创的“参与观察”式田野调查方法,标志了现代民族学的开端。
他将以前古典民族学所用的宏观研究方式转变为微观的研究方式。
让那个时代的民族学家告别了“安乐椅上的民族学家”的称号。
作为马凌诺夫斯基学生的费孝通先生,在他的著作《江村经济》中运用参与观察的方法详尽地描述了江村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以及与该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
除费孝通先生以外,著名民族学家林耀华先生也运用参与调查的田野调查方法写过许多著作,如著名的《金翼》、《凉山夷家》、《义序的宗族研究》等。
虽读过很多关于田野调查的书籍,但要将其很好的运用到实地调查中,还得需不断的累积田野经验。
如何进行田野调查?没有人能简单、明了而又准确地回答,只有亲身进入到田野中才能真正的体会。
书中常言田野调查一般可分成五个阶段:准备阶段、开始阶段、调查阶段、撰写调查研究报告阶段、补充调查阶段。
但根据自己暑假亲身体验却认为第一、二阶段可以合二为一。
实际上的田野调查可为四个阶段。
《金翼 》书评

---------------------------------------------------------------最新资料推荐------------------------------------------------------《金翼》书评[键入公司名称]《金翼》书评[键入文档副标题]Acer [选取日期]姓名:张琴班级:社会学 1302 学号:2013311201017[在此处键入文档摘要。
摘要通常为文档内容的简短概括。
在此处键入文档摘要。
摘要通常为文档内容的简短概括。
]1/ 12学号:2013311201017姓名:张琴班级:社会学 1302《金翼》书评一、作者简介林耀华(1910 年 3 月 27 日—2000 年 11 月 27 日),福建古田人,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民族教育家。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
学术经历:林耀华在闽东乡镇汉人家庭长大,念过私塾,,长期在民俗生活中耳濡目染,直到赴省城和出国深造为止。
20 世纪 20 年代,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吴文藻先生,接受社会学、人类学训练。
1936 年,他利用从闽东田野调查得来的资料完成硕士论文《义序宗族研究》,驾轻就熟地将私塾国学知识、乡村民俗事象与社会学理论视角融为一炉,分析了中国宗族社会的结构功能,引起学界的重视。
1937 年,先生到哈佛大学转攻人类学,接受系统的跨文化研究训练。
1940 年获博士学位后,利用余暇,根据他在闽东家乡的生活经历,以及 1936~1937 年之间做的两次田野工作,写成小说体著作《金翼》并在国外发表。
《金翼》、《义序宗族研究》两本书成为汉人社会研究的学术经典。
学术贡献30 多年来,他应用人类学知识为新中国服务,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人类起源论研究,其著作《从猿到人的研究》使---------------------------------------------------------------最新资料推荐------------------------------------------------------ 国内的人类学研究转到新的方向。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云南民族识别的研究综述

科技信息
专题 论 述
2 0世 纪 5 0年代 以 来 云南 民族 识别 的 研 究综 述
一项理论性 、 科学性 、 政策性很强的基础性工作, 直接 关系到 中国共产 党民族平等政 策的落 实。云南共有 2 6个 民族, 中国民族成分最多的省份 , 是 因此云南民族识别工作异常艰 巨和 复杂。 本文 以综述的形式, 2 世 纪 5 对 O 0年代 以来有 关云南民 族识别的研 究作 了分类和 综述 , 并对现有的研 究状况进行 了评述 , 有一 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 [ 关键 词 ] 代 云 南 民族 识 别 研 究 综述 近 “ 民族识别是指对一个族体 的成份和名称 的辨别与确定。”嘶 中国 I 建立初期 , 各民族 的名称相当复杂 , 15 据 93年第一次全 国人 口普查 , 汇 总登记上报的民族有 4 0多个。从 5 0 O年代初开始 , 党和 国家组织大批 民族研究者和民族工作者深人少数 民族地 区进行 民族识别 。云南 民族 识别工作是中国民族识别工作 的重 要组成部分 : 在云南这块土地上 , 除 了汉族 以外 , 有 2 个 少数民族 , 中 1 个少数 民族为云南省独 有 , 共 5 其 5 这些 民族是由解放初云南所报的 20多种族称 , 6 经过长期 、 大量的科学 调查和甄别 , 才最终认定下来的。O世纪 5 2 0年代 以来 , 许多学者致力于 云南 民族识别 的研究工作 , 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 。 云 南 民族 识 别 的 综 合 性研 究 ( ) 一 云南 民族识别的依据及进程研究 云南民族识别和全 国其他地区的民族识 别一样 ,都是 以斯大林关 于民族的四个特征为理论依据 , 民族是人 们在历史上形成 的一个有 即“ 共同语言 、 共同地域 、 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 同文化上 的共 同心理 素质 的稳定的共同体 。 ” 民族识别 的实际标 准是 : 尊重民族意愿 , 名 即“ 从 主人” 的原则 ; 参考历史文献资料 。 云 南 民 族 识别 的进 程 : 15 9 0年 8月到 15 9 1年 5月 , 中央 访 问 团赴 云 南 进 行 了 为期 8个 月 的访 问, 虽然这次访 问主要是为了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 由于在访 问中 但 对云南的社会 、 文化 、 民族种类及人 口等有 了初 步的了解 , 也就初步接 触了云南民族识别 的问题 , 为以后的民族工作 打下了基础 。后来 , 访问 团的近百万字调查资料统编为《 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 ( 、 ,9 6年 由云南 民族出版社出版 , 上 下) 18 是后来 民族识别 的重要参考 资料 。 15 9 4年 5月至 1 , O月 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派 出的云南民族识别 调查组到云南 的文山 、 自、 蒙 玉溪 、 大理 、 丽江 、 普洱等 六个专 区 , 对彝 族、 、 壮族 傣族 、 哈尼族等 民族的不同族群进行民族归并 和识别调查 , 调 查经过两个 阶段 , 第一 阶段识别 了 2 个 民族单位 , 9 第二阶段识别 了 3 9 个民族单位。 16 95年到 17 9 8年, 云南的 民族识别 因文化大革命 而被迫 停止 。 17 9 9年确认 西双版纳基诺人为单一 民族。 18 9 2年确认布依族 、 水 族。1 8 9 7年恢苦聪人族称为拉枯族 , 并对 西双版纳州南部克木人再次 举行 学术会议讨论 , 建议确认为单一民族 。18 9 9年对马关县拉基人进 行识别研究 , 尚待确认 。至此 , 经过识别 , 云南共有 2 5个少数民族 。 ( ) 二 有关云南 民族识别的调查 报告 林耀华 主持编写的《 云南省 民族识别研究第一 、 阶段 初步总结》 二 ( 云南省 民族事务委员 印发 ,9 4 , 15 年)分两个阶段对云南 民族识别调查 进行 了报告 。《 云南 民族识别参考资料) 9 5年版 , 15 是云南省 民族事务 委员会研究室印发的内部资料 , 内容包括了《 云南民族识别研究组第二 阶段工作报告》 云南 民族识别研究初步总结》 《 ,还附有 l 4个民族 的识 别工作 总结 。虽然以上这两本调查报告都是繁体字 , 读起来 费力, 但今 天看 来 , 然 是 不 可 多得 的宝 贵 资 料 。 仍 云南 民族识别综合调查组编《 云南 民族识别综合调查报告》 云南民 ( 族 学 院 民族 研 究 所 ,9 9年 l 版 )是 16 17 O月 , 9 0年 1 根 据 在 云 南 的社 2月 会历史调查所写的报告 。 本书共分三部分 :. 1 各个族称单位 的基本情况; 2 . 民族识别初步意见 , 云南 的民族 分为 l 个 族系 , 个单一 民族 , 将 6 4 其 他民族支系 5 个 , 5 个 ;. 2 共 6 3 关于几个族称单位族 系识别 的具体问题 。 本书对研究和 了解云南民族识别问题有较高参考价值。 国家民委民族 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组编《 云南少数 民族社会历 史调查资料汇编》 云南人 民出版社 ,9 7 ,内容包括 了 2 ( 18 ) O世纪 5 O年 代中央访 问团在云南收集 的资料 , 国人大 民委 、 全 中央民委等组织民族 社会历史调查 以及民族识 别等工作所搜集到的资料 ,是民族研究和民 族工作中的重要参考资料 。 ( ) 他 相 关 研 究 三 其 15 , 9 6年 林耀华与费孝通教授联名发表 了新 中国第一篇有关 民族 识别理论研究 的文章《 关于少数民族识别问题的研究》 文章对斯 大林 , 民族四个特征理论加以研究 , 出许多具有创见性的见解 , 提 它对云南的 民族识别研究起着启迪 和指导作用 , 影响极为深广。 黄光学主编《 中国的民族识别》 民族 出版社 , 9 年 1 ( 1 5 9 月版 ) 在第 四章第一节简单介绍了云南在 15 年 民族识别工作的进程及成果 ; 94 在 第五章第二节 “ 民族 支系的认 定和归并” 详细介绍 了云南 民族 支系 中, 的 认 定 和 归并 , 外 , 第 22到 27页 还 专 门论 述 了 克 木 人 的识 别 问 此 在 8 8
《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

目录
• 著者序;英文版前言;英文版导第一章 东林的青少年时代 • 第二章 摆脱贫困 • 第三章 打官司 • 第四章 张家新居 • 第五章 早期教育 • 第六章 村里的节日 • 第七章 农业系统 • 第八章 大米交易 • 第九章 商店的生意 • 第十章 芬洲的命运 • 第十一章 求学雄心 • 第十二章 分裂 • 第十三章 店铺分家 • 第十四章 土匪 • 第十五章 兄弟争吵 • 第十六章 店铺的扩展 • 第十七章 趋向两极的张黄两家 • 第十八章 地方政治 • 第十九章 水路通 • 第二十章 僵局 • 第二十一章 把种子埋入土里 • 附录 《金翼》中张、黄两家系谱表
金翼_
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
金翼_
一、作者简介
• 林耀华(1910-2000),福建省古田县人,著名的民 族学家、人类学家,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 和民族教育家,中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2000年11月 27日逝世,享年91岁。
金翼_
• 第三个阶段,张家已经从生活的画面中消失 ,只有黄家仍然奋斗下去,为了获得更大的 成功,黄家继续扩大生意,并且与地方政治 发生了关系。社会和政治发展之快使换将不 可能跟上潮流,最后,巨大的民族危机使黄 家又回到他们最初的状态中去。
金翼_
三、本书特色
• 在传统中国社会,家庭(其扩大化就是家族)是 其他所有社会组织的同构体,是人们进行社会 活动的中心场所。本书紧紧抓住传统中国社 会这一特征,其副标题就是“中国家族制度社 会学研究”。像同类作品一样,本书提到了童 养媳、同姓不婚、包办婚等当时中国社会普 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但本书更详尽地描述了具 有浓郁地方性色彩的其他与家庭有关的社会 制度和风俗习惯。
民族识别的相关问题

民族识别我国民族识别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0年到1954年,经过识别,确认了38个少数民族。
其间,除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朝鲜、满、瑶、黎、高山等民族早已被确认外,其他被确认的少数民族有壮、布依、侗、白、哈萨克、哈尼、傣、僳僳、侗、东乡、纳西、拉古、水、景颇、柯尔克孜、土、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鄂温克、保安、羌、撒拉、俄罗斯、锡伯、裕固、鄂伦春等27个民族。
民族学家黄现璠对壮族的确认,方国瑜对纳西族的确认,都曾做出过重要贡献;第二阶段是从1954年到1978年年底,确认了土家、畲、达斡尔、么佬、布朗、讫佬、阿昌、普米、怒、崩龙(后改为德昂)、京、独龙、赫哲、门巴、毛难(后改为毛南)、哈巴等16个少数民族;第三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7年。
1979年确认了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至此,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基本完成。
民族识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民族工作。
它坚持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标准,成功地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构成,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和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在民族识别三个阶段的工作里,费孝通、黄现璠、夏康农、秋浦、翁独健、李有义、李安宅、吴泽霖、方国瑜、杨成志、杨堃、吴文藻、江应梁、刘咸、林耀华等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的名家,及大批学者、民族工作者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关于民族的界定民族识别在世界上是一个创举,没有借鉴可言。
因此,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首先要解决的是关于“民族”的概念或定义的理论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如何科学地界定一个族类共同体。
有关民族的界定问题,我国学术界历来有争议,但也有一个普遍共识,那就是,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仍是对民族概念最简明的科学概括。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共同体。
一场学术的薪火传承《金翼》《银翅》

一场学术的薪火传承《金翼》《银翅》这是一场学术之火的传承,这是一次老师学生的互动,这是一份中国家族发展的民族志记录。
《金翼》,作者林耀华,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
《银翅》,作者庄孔韶,浙江大学讲座教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教授,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
《金翼》是林耀华先生留美陪伴患病妻子期间,根据他在家乡福建省闽江流域黄村及所在县、乡、镇的生活经历,以及他本人离开中国前所做的最后两次田野工作写成的。
这本书叙述了两个农村家族兴衰起伏的历史过程。
林先生通过小说笔法给我们描绘了许多生动的家族生活场景,刻画了家族成员之间的合作与冲突,也进行了许多关于定亲、成婚、葬礼等仪式场面的再现,让人身临其境。
本书最后是在抗日战争中拉下了帷幕,书中这样写道:在抗日战争中,1941年春天,福州被敌军全面占领。
内陆乡村和外部世界的通讯完全中断。
东林,现在已经年逾古稀,依然扛起了锄头,再次像年轻时一样劳作。
围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孙儿,现在正看着他,学习农耕的技术,这是他们首要的、也是最持久的生计之源。
一架飞机从他们头顶飞过,孙辈们抬头仰望这充满敌意的天空,但老人却平静的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忘记把种子埋进土里了!”《银翅》可以说是《金翼》的续篇。
庄孔韶老师在本书中借探寻黄、张两家族后裔在近年的转变与发展,来归纳、分析近百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历程中所面临的变与不变。
在本书的封皮,写着林耀华的一段话:起初他(庄孔韶)透过我的《金翼》首次认识了福建乡镇社会的过去,如今我则从他的学术性续本《银翅》很快发现了我家长变迁中一脉相承的历史关联性。
关于《金翼》的金句。
为了在这个世界生存,一个人需要同各种圈子的人建立不同的关系。
现在东林很乐意听村民和镇上的居民谈论他的四个儿子,他们分别在商界、政界、学界和军界四个不同的领域取得了进步,真是各得其所呀。
自黄氏先祖定居黄村以来,还从未有过像东林的新居这样的华屋大宅。
当代学术范式下的彝族研究经典——纪念林耀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汉 学 专 家 、 台 湾 社 会 与 文 化 研 究 专 家 和 国 际 知 名 的 彝 学 专 家 。 他 的 多 数 论 著 皆 以 扎 实 的 田 野 实
地 调 查 为 基 础 , 其 内 容 涉 及 宗 族 社 会 组 织 、 谱 系 制 度 、 家 庭 结 构 、 民 间 信 仰 、 经 济 变 迁 、 族 群 关 系 和 民族 认 同等 方 面 的 研 究 。 上 世 纪 8 年 代 末 ,他 到 中 国 西 南 数 个 彝 族 社 区 进 行 定 点 观 察 , 0
象 作 为 跨 文 化 之 间 的学 术 旅 行 来 进 行 论 证 , 突 显 了 彝 汉 之 间 作 为 旅 行 者 关 系 的 差 异 及 其 学 者 研
究 纵 深 的学 术 特 征 。在 民 族 国家 的 建 构 及 其 政 治 背 景 下 ,林 耀 华 关 于 “ 者 ” 的 文 化 写 作 不 是 他
当代 学 术 范 式 下 的彝 族 研 究 经 典
— —
纪念 林 耀 华先 生诞辰 一 百周 比二 十世 纪 四 十 年 代 和 八 九 十 年 代 不 同 身份 的 人 类 学 家对 中 国彝 族 的
研 究 ,来探 讨人 类 学观 念 和 方 法 的 变 化 ,从 而 凸 显 了林 耀 华 先 生 对 彝 族 研 究 的 扎 实和 超 前 性 。 同时介 绍 了业 内人 士 关 于 “ 族 史” 界 定及 族群 认 同 的 一 些 不 同见 解 。 民
《 山 彝 家 》 是 林 耀 华 先 生 于 1 4 年 获 美 国 哈 佛 大 学 人 类 学 博 士 学 位 后 , 于 1 4 年 在 中 国 凉 0 9 3 9
民族学概论.d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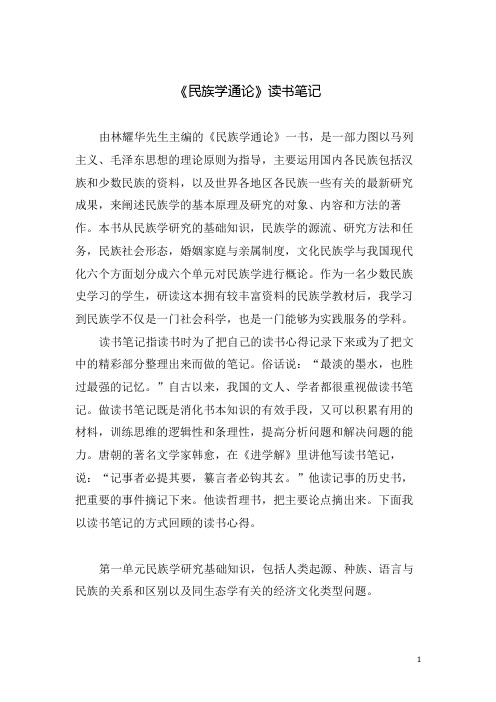
《民族学通论》读书笔记由林耀华先生主编的《民族学通论》一书,是一部力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原则为指导,主要运用国内各民族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资料,以及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一些有关的最新研究成果,来阐述民族学的基本原理及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的著作。
本书从民族学研究的基础知识,民族学的源流、研究方法和任务,民族社会形态,婚姻家庭与亲属制度,文化民族学与我国现代化六个方面划分成六个单元对民族学进行概论。
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史学习的学生,研读这本拥有较丰富资料的民族学教材后,我学习到民族学不仅是一门社会科学,也是一门能够为实践服务的学科。
读书笔记指读书时为了把自己的读书心得记录下来或为了把文中的精彩部分整理出来而做的笔记。
俗话说:“最淡的墨水,也胜过最强的记忆。
”自古以来,我国的文人、学者都很重视做读书笔记。
做读书笔记既是消化书本知识的有效手段,又可以积累有用的材料,训练思维的逻辑性和条理性,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唐朝的著名文学家韩愈,在《进学解》里讲他写读书笔记,说:“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
”他读记事的历史书,把重要的事件摘记下来。
他读哲理书,把主要论点摘出来。
下面我以读书笔记的方式回顾的读书心得。
第一单元民族学研究基础知识,包括人类起源、种族、语言与民族的关系和区别以及同生态学有关的经济文化类型问题。
人类起源问题的理论一直在随着人类科学的发展而更迭。
它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从唯心主义的我国女娲氏抟土造人传说、古埃及相信第一个人是由神在陶器场里塑成、泥土造人说的“上帝造人说”,到人类初步产生了自发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古希腊思想家阿那可西曼德及我国庄周分别提出的“从鱼到人”和“马生人”的论点,到“人猿同祖”的提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海克尔《自然创造史》,再到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确定劳动是人类、人类社会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及近年学术界的诸如劳动创造说、劳动“推动力”说、突变选择说对劳动在从猿转变到人过程中证明和确立。
回忆与反思_义序的宗族研究_及其价值_林耀华的学术贡献及其启示

I作者简介 刘 涛 , 郑州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助理研究员, 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与中国乡 村治理研究
92 ! 会 学 坛 社 科 论 团口.
陈巧云, 郑州市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 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宗教社会学与民 俗刻 七 研究
林 先生早 年从 中国传统 的私 塾教 育 启 蒙, 中学就读 于福 州英华 中学, 从 乡村到 福 州辗 转接 受传 统 学术 熏 陶, 莫定 了良好 的 国学基 础 正如 其所 言 , 五 六 岁送 往私 塾发 蒙 , 对 儒 家经典 , 中 国古典 文论诗 歌 倒 背如流 ,
考 为证据 ,知 古者 贤者皆从拜祖思想而创礼仪 , 由礼仪 而影响其 态度 行为 所有政 治 经济莫不受制 于礼仪 , 由此 而表述其与鬼神和拜祖意义所在 , 并 用 民族学的知识 来理 解不 同象征 崇拜的含义 , 展现 拜祖 的象征性意 义 林先 生
从 古籍 中对拜祖礼仪的考 究展示 出其 国学的深厚底 蕴, 又以 周礼 等 史料 书
世纪 4 年代初期 ,他 用小说笔 法, 撰写 了 金翼 0 中国家族 制度 的社会 学研
究 (以下简称 金翼 ) 一书, 以自己的家族为背景, 深刻全面地描述 了闺中山
区一个 大家族所历经的兴 衰荣辱 金翼 至今 仍是 国外学者研 究中国社会 文
化 的重要参 考读 物
义序 与 金 翼 堪称我 国 2 世 纪三四十年代人 类 学宗 0
多宝贵财 富
义序 是林先生于1 3 年利用从闽东田野调查得来的资料完成的硕士 96
论文 他驾轻就熟地将国学知识 乡 村经验与社会学理论融为一炉, 在此书中
尽 显林先 生的学术关照 , 通过对 中国古文献的解读和 民族精神 的诊释 , 把 义
序区域之宗族的生命脉络以地方性的知识厘清, 引起了学界的重视 相比 金 翼 , 早期的 义序 一书或许未能引起大家的关注, 其文本亦较难寻觅, 但它 的研究取向已 在很多方面先于 金翼 , 在有意无意之中为人类学的研究进行 了一个奠基 此书在 内 容上是 拜祖 的延伸, 并且资料来源和理论范式都有 转换:资料从文献转为田野调查, 理论则从古典进化论转为结构功能论 义
林耀华学术贡献

林耀华先生对当代中国人类学所作贡献的再认识□ 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林耀华先生尽管已经离开我们近10年,但他留给我们的宝贵学术遗产仍是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笔者认为,林耀华先生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有必要在他百年诞辰之际加以再认识。
这里所说的“再认识”,是指我们对林耀华先生所作的贡献,认识得还不充分、不到位、不深刻,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
林耀华先生是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的重要开拓者。
他的《金翼》和《凉山彝家》是两本最有代表性的力作。
其中,《金翼》已成为国际人类学研究的重大主题——中国汉族宗族社会研究的奠基作品之一,影响力延续至今;《金翼》同时也成为现代中国社会学家族与社会网络研究的基本国情依据之一。
同样,《凉山彝家》也早已被公认为现代彝族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他对彝族文化与社会的双重观察,提示了现代中国在多民族发展的背景下,急需对民族地区加以区域关照和整体性协调的重要意义。
这两大著作,分别代表着林耀华先生的两大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汉族社会研究和西南少数民族研究。
汉族社会是林耀华先生早期学术生涯的主要研究领域。
林耀华先生在闽东乡镇汉族家庭长大,念过私塾,目睹过农夫在田间插秧耕作,围观过闽江的龙舟赛,参加过拜祖仪式,长期在民俗生活中耳濡目染,直到赴省城和出国深造为止。
上世纪20年代,林耀华先生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吴文藻先生,接受社会学、人类学训练。
1936年,他利用从闽东田野调查得来的资料完成硕士论文《义序的宗族研究》,驾轻就熟地将私塾国学知识、乡村民俗事象与社会学理论视角融为一炉,分析了中国宗族社会的结构功能,引起学界的重视。
1937年,林耀华先生到哈佛大学转攻人类学,接受系统的跨文化研究训练。
1940年获博士学位后,他利用余暇时间,根据在闽东家乡的生活经历,以及1936年至1937年之间做的两次田野工作,写成小说体著作《金翼》并在国外发表。
《金翼》、《义序的宗族研究》两本书成为汉族社会研究的学术经典,在国际人类学界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今仍是国内外人类学课堂教学的必读书目、中国乡村人类学的延续性主题,产生了持久的学术影响。
《义序的宗族研究》简评

论文题目:课程名称:任课教师:专业:班级:学号:姓名:年月日《义序的宗族研究》简评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历史学类班王星城222011313210001摘要:《义序的宗族研究》(以下简称《义序》)是林耀华先生的硕士毕业论文,但由于此文没有及时发表,而是在燕京大学的图书馆里尘封了60多年。
所以《义序》一书并未广泛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不像林先生另一本著作《金翼》那样出名。
直到2000年,《义序》一书才由三联书店出版,发掘出了这一民族学的宝藏。
关键词:义序;宗族;林耀华一、《义序》其价值1935年,吴文藻先生邀请英国功能学派代表人物拉德克里夫·布朗到燕京大学讲学,林耀华在吴文藻的安排下,成为了布朗的助教兼学生。
在此背景下,林耀华选择了其家乡福建的一个村庄“义序”展开了田野调查。
经过3个月的调查,他收集了大量资料,并以功能主义的理论对祠堂在宗族社会中的作用做了详细的分析。
《义序》一书作为林耀华先生的硕士论文,显示了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国学功底。
他以中国宗族社会为题材,以田野调查的方法收集资料,以功能主义理论为分析,再以历史研究的文献法加以论证,最终写出了这一本著作。
其调查之精细,论证之详尽,足以作为我辈学习的典范。
《义序》开辟了中国宗族研究的道路,“在世界性的“中国研究”中取得了重要学术地位,其作品至今仍被世界学术界广泛参考和征引,显示出永久的汉人社会研究学术魅力”。
1《义序》为中国宗族研究塑造了一个参考模式,以宗族研究为切入点来研究中国文化,尤其是汉族文化,为后来者开辟了一条民族学研究道路。
浙江大学的阮云星教授对义序做了跟踪调查,算是对林先生的研究的继承与发展,写下不少文章。
《义序》的影响不仅限于国内,更是对国际人类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国外学者弗德里曼以林耀华、胡先缙、费孝通、杨懋春、许烺光等人的作品为资料,对中国宗族社会进行主观臆测式的研究,“将中国宗族研究推向汉学人类学,引起大家的讨论、争议、修正、批评,最终形成了库恩意义上的‘科学范式’,即中国宗族范式”。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林耀华先生与新中国的民族研究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社会学系,北京100872)摘要:林耀华是解放前就享有国际声望的中国人类学家,在新中国的民族研究实践和民族学学科建设活动中,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共产党员经受了历次运动的考验,在社会科学研究和应用以及民族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进行学术反思、总结经验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对于新中国人类学学术史的研究依然需要克服一定的困难。
关键词:学术史;民族研究;人类学;林耀华;新中国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我国的历史,浩淼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
——江泽民[1]林耀华先生(1910~2000)是享有国际声望的中国学者,解放前就已经以《金翼》、《凉山夷家》、《义序宗族的研究》等著作而在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界占有重要的地位[2]。
英伦学究莫里斯·弗里德曼的弟子们就认为,林耀华和费孝通、田汝康开启了一条“中国本土社会学中受英式训练的人类学路线”,它对于“在英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开启了一条中国路线”的弗里德曼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3]不过,本文要集中评论的是林耀华对新中国的民族研究以及人类学等相关领域的学术贡献。
解放初期,中国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民族社会历史和民族语言的实地调查[4]。
林耀华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费孝通和林耀华在1956年主持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
是年5月在列宁格勒召开“全苏民族学会议”,林耀华代表中国民族学工作者出席并在大会上宣读了此文。
1957年3月,民族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名为《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
事过不久,民族学与作为民族学家的费孝通便遭受不测风云,历史转入沉重的一页。
《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著作[5],其中的一些见解至今对于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比如他们认为,一门学科应该依靠密切结合实际生活所提出具体的问题来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而不是先从定义人手;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应包括一切民族在内,而不是单单关注落后人群或少数民族:把少数民族和汉族分开来作为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没有根据的。
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由于民族主义的偏见,歧视殖民地的各民族,曾经把所谓‘文明人’的研究划在民族学或‘社会人类学’的范围之外。
这是错误的。
我们将以苏联民族学为榜样,批判这种资产阶级错误思想,而肯定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一切民族在内的,在中国的范围里,不但要研究少数民族,也要研究汉族。
民族学在中国还可以说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因此还有许多人对于这门学科的名称、内容和方法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在这里不想从定义、学科分类上进行讨论。
为了避免各种讨论成为学究式的辩论,我们认为最好从这门学科所进行的研究工作的本身来说明它的内容,而且只有在研究工作的发展中,一门学科的性质和范围才能逐步明确起来。
一门学科的发展,我们认为,并不依靠开始时把范围划好,界碑树好,而是依靠密切结合实际生活所提出具体的问题来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
实际生活是丰富的、变化的,一门学科能从这个丰富和变化的泉源出发,它的工作也会是活泼的、常新的。
我们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来为中国民族学提出它的任务的(第33-34页)。
当前我们不是也在强调“民族学不仅要研究少数民族、也要研究汉族”吗?是否在经历了一番艰难曲折后又重新回到50年代的思路上了呢?林耀华还是所谓“苏联模式”时期中国民族学的一面旗帜,后人描写这段历史时,就以林先生为代表展开评论。
如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在他研究中国人类学的专著中就曾提到[6]有些人甚至一提到中国的“苏联模式”就气愤不已。
例如,林耀华说,中国民族学家从来就没有把苏联的民族学当成榜样,更多地只是拿它们作“参考”。
林的反应或许折射出人们事后对某一时期明确存在于中苏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吹毛求疵,这种说法与实情是有些出入的;然而,在此问题上的敏感和自傲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只要提到人类学科学,就离不开苏联对中国的重大而持久的影响(第168页)。
当我问林耀华,考虑到中国民族学家先是采用西方模式,然后是苏联模式,90年代他们会效仿哪种外国模式时,他笑着回答:“我们取这两者最好的部分,然后发展自己的模式。
”他接着解释说,中国人再也不会单纯地照搬外国模式了(第326页)。
新中国的民族学(或者“民族问题研究”)与政治运动密切相关是不争的事实[7]。
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几乎都可以作为民族学史小阶段的分期界标,“反右”自然也不例外。
敏锐的学科史研究者已然注意到,中国民族学界的新老交替竟是由这场政治运动来完成的,尽管这种变化完全不符合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8]。
于是,不论今天的评论家感情倾向如何,模范党员林耀华在1957-1966的十年间被历史地留在了民族研究学科大舞台的中央,较之他那些被剥夺权利、“缺席”“靠边站”的昔日师友,客观上对学科的发展(尽管是曲折的却并非停滞不前)产生了更多的影响[9]。
而且这种并非“常态”赢得的“先机”一直保持了大约十年之久[10]。
若从生命史的角度看,“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一批老学者即使“熬过”“文革”,也多半失去了为发展中国民族学做贡献的大好时光,像费孝通那样焕发“第二次学术青春”者实属凤毛麟角。
因此,今天我们说林耀华对中国民族学的贡献超过了他的老师吴文藻、“青胜于蓝”,其实并不奇怪,至少他的学术生命比他的老师长。
至于当事人事后如何看待亲身经历的历史,这里恰巧有两个现成的样本供我们讨论。
费孝通在分别接受美国人类学家巴博德和顾定国的采访时有如下应答:巴[巴博德]:但你是功能主义者。
你从未讲过奴隶制阶段、封建主义阶段、或摩尔根。
费[费孝通]:对,对了,甚至那时我也未真正全部接受那些。
关于那些问题我保持沉默。
巴:但那种理论看来是那时候发表的论少数民族的全部文献的特征。
费:到处都是,除了在我的著作中。
(11)我[即顾定国——引者注]问费孝通,你认为1957年和1958年对你所作的指控是否有属实的地方,费孝通略一沉吟,说,“1957年的批判只是反映当时的情况。
历史不能被批判。
人们必须找出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
”[12]1957年以后,中国民族学继续前进,在田野工作方面,社会历史调查仍然轰轰烈烈;在理论研究方面,重要的建树则有“经济文化类型”学说和关于“民族”译名和定义的探讨。
在政治风暴使得一些杰出的民族学家过早葬送学术生命后,林耀华一度学术地位分外醒目。
除实地调查和课题教学外,他发表的论著有《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1961)和《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问题》(1963)[13]。
其实,在此有必要指出,考察解放以后民族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应该注意到两种传统的交汇。
杨堃就认为民族学有资产阶级民族学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两大分支,而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所谓民族学就是资产阶级的学科[14]。
这种思想后来在施正一的广义民族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5]。
郑杭生在他对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中也提出了中国社会学领域的两种传统并做了仔细的分析[16]。
所以,我们不仅要思考“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术队伍中后来出现的红白分化,更应该考虑到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与“革命干部”和“工农群众”的地位差异。
施正一,1932年出生、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民族学家,是一个勤于思考、紧跟形势的人。
50年代他赞成在民族学领域清除资产阶级影响,90年代他牵头组织编写出《广义民族学》。
顾定国在写中国人类学史时注意到并引用了施的观点[17]。
1990年施正一曾经与人谈起:“从1955-1963年的八年中,我写了大约150万字的手稿,而当时公开发表的还不到8万字,只有二十分之一。
为了发表一点文章,我不知受了多少气,还挨了好几次批判,甚至还被扣上‘反党’、‘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和‘修正主义’的帽子。
”[18]关于“民族”一词的讨论,当时看到的更多的是“苗正身红”的学者发表的文章。
比如,牙含章(1916~1989)就是一个典型。
牙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题为《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翻译情况》的论文[19],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问题专家对相关问题的看法。
作为共产党员、红色专家的林耀华自然没有能够像“右派分子”那样“清闲”。
他经受的是另外一种压力。
在为后学留下功力深厚的专题论文的同一时期[20],林先生也在从事“另类”写作。
1958年夏,在“拔白旗、插红旗”的斗争中,“林耀华……作了检查,对自己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资产阶级民族学的路线和方法作了批判”。
依他晚年自述,“我那个时候相信路线始终正确,所以尽量从自己身上找错误根源,……在痛苦的思想反省和认真的检查中,我们这些搞民族学的人纷纷表示要‘大破大立’,拔掉资产阶级民族学的‘白旗’,插社会主义的红旗。
为了争做红色专家,拟定和提交了个人红专计划。
”1960年,在接受上级任务、批判资产阶级民族学时林耀华被指定为小组召集人,还“写了《美国资产阶级民族学心理学派的反动本质》的初稿”。
就在当年,林耀华被推选为北京市群英会的个人代表,参加全国教育、文化、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21]。
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带着镣铐跳舞的林耀华的图像,然而,他还是在民族学大舞台的中央活动,并没有靠边站。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人类学首先在南方复兴,1981年梁钊韬在中山大学重建了人类学系。
先师生前不止一次向我提起在重建过程中得到了林先生的声援(个人交流)[22]。
此后不久的1983年,林先生也在同事们的协助下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今民族大学)建立了“民族学系”并出任系主任。
林先生还培养了包括新中国第一个民族学博士在内的一大批民族学博士和硕士。
就此一点而言,时势和命运让他有幸超过了他的师辈吴文藻、潘光旦等人。
不过我同时注意到,林先生至少在1980年代早期是执著于民族学、而并不倾向在民族学院建立“人类学系”的,这又与费孝通、梁钊韬、陈国强等的思路略有不同[23]。
回头再看关于“民族”概念的结合实践的理论研究,林先生文革之后培养的几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对此问题有薪火相传性质的深入研究,并且目前都在该领域占据国内领先地位。
这些成果包括张海洋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1996)和潘蛟的博士论文《“民族”一词的舶来以及相关的论争》(2000),以及纳日碧力戈的专著《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2000)[24]。
除此之外,林先生的晚期研究有较大一部分集中在对新中国民族研究的回顾和前瞻,包括总结经验方面[25]。
本来在1956年的“12年科学研究规划”中,林先生与费先生等都认为民族研究并不仅仅局限在少数民族研究,只不过事后的局势让他们失去了对汉民族展开人类学参与式研究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