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顾城诗歌中的基本特色
以弧线为例简析顾城诗歌意象的特点

诗人在写作时想象的流动、跳跃就促进了文本意象的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和跳跃性,扩大了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的内涵和外延,如朦胧诗人顾城的《弧线》。
顾城习惯于运用奇特的想象、跳跃的短句、迷离的色彩和独特的意象组合来凸显他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
诗人在《弧线》中,通过跳跃的想象由“鸟儿”联想到“少年”;由“少年”想到“葡萄藤”;由“葡萄藤”再想到“海浪” ,把互不联贯的4个意象巧妙组合,共同置于“弧线”之下,从特殊感觉出发进行深度意味的探索,使“弧线”成为一种可供欣赏的诗化意象。
正是由于作者丰富的想象能力,才使文本的写作思路更加开阔,从而创造出成功的文学作品。
想象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存在,这就要求文学写作者要深入生活,以现实为基础,以激情为动力,去接触事实,接触越多,储存的表象材料就越丰富,并利用联想式等方法训练自己,那么其想象能力就越强,其写作的幅度就越宽。
顾城诗歌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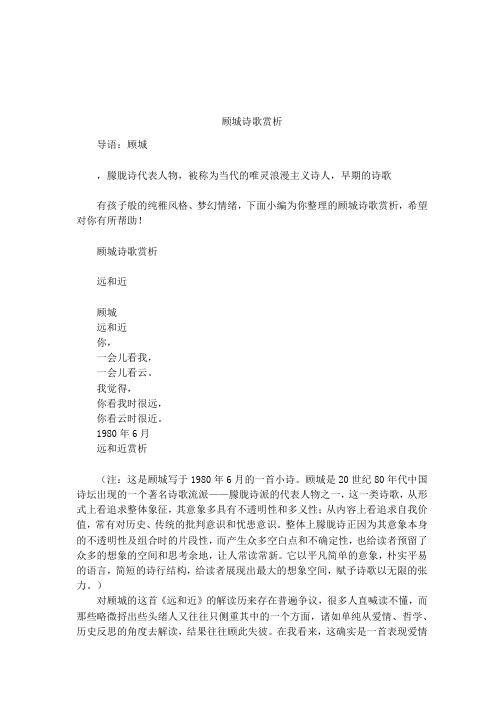
顾城诗歌赏析 导语:顾城 ,朦胧诗代表人物,被称为当代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早期的诗歌 有孩子般的纯稚风格、梦幻情绪,下面小编为你整理的顾城诗歌赏析,希望 对你有所帮助! 顾城诗歌赏析 远和近 顾城 远和近 你, 一会儿看我, 一会儿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1980 年 6 月 远和近赏析 (注:这是顾城写于 1980 年 6 月的一首小诗。
顾城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 诗坛出现的一个著名诗歌流派——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这一类诗歌, 从形 式上看追求整体象征, 其意象多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 从内容上看追求自我价 值,常有对历史、传统的批判意识和忧患意识。
整体上朦胧诗正因为其意象本身 的不透明性及组合时的片段性, 而产生众多空白点和不确定性, 也给读者预留了 众多的想象的空间和思考余地,让人常读常新。
它以平凡简单的意象,朴实平易 的语言,简短的诗行结构,给读者展现出最大的想象空间,赋予诗歌以无限的张 力。
) 对顾城的这首《远和近》的解读历来存在普遍争议,很多人直喊读不懂,而 那些略微捋出些头绪人又往往只侧重其中的一个方面,诸如单纯从爱情、哲学、 历史反思的角度去解读,结果往往顾此失彼。
在我看来,这确实是一首表现爱情的诗,却又不单单是写爱情的,更蕴含了诗人强烈的精神寄托和追求。
下面就具 体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读此诗: 一、单纯而复杂的特殊感情: 从诗行建构来看,顾城这首《远和近》,仅两节 6 行 24个字,如此短小的 篇幅中,“你”字却独占一行,这不得不引起人的注意,从而起到了突出强调的 作用。
“我觉得”也独占一行,在形式上与第一行“你”呈现一种呼应,同时暗 示了“我”的一切内心活动和感觉都是以“你”为中心的, “我”从你的动作和 飘忽的眼神中读出了“你”的内心。
上节主要客观描述“你”的举动, 展示的是“你”的世界, 是自由自在的世 界;下节主要描述“我”对“你”的举动的内心感受,是完全自主的、“我”的 世界,也可以说是“我”对“你”的世界的一种主观介入。
顾城的诗歌有什么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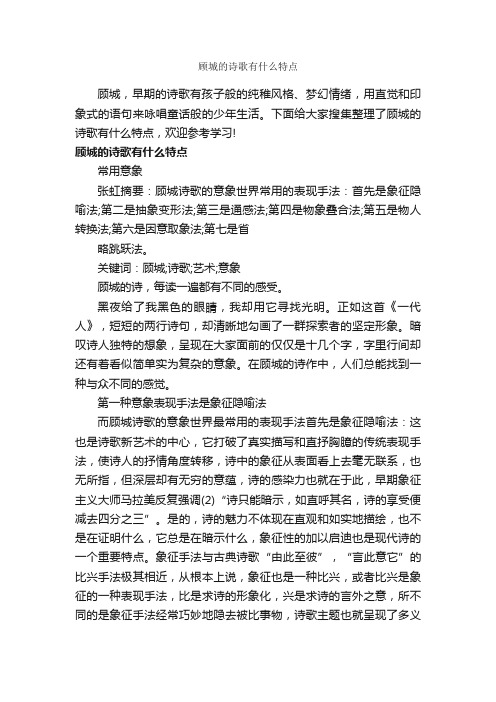
顾城的诗歌有什么特点顾城,早期的诗歌有孩子般的纯稚风格、梦幻情绪,用直觉和印象式的语句来咏唱童话般的少年生活。
下面给大家搜集整理了顾城的诗歌有什么特点,欢迎参考学习!顾城的诗歌有什么特点常用意象张虹摘要:顾城诗歌的意象世界常用的表现手法:首先是象征隐喻法;第二是抽象变形法;第三是通感法;第四是物象叠合法;第五是物人转换法;第六是因意取象法;第七是省略跳跃法。
关键词:顾城;诗歌;艺术;意象顾城的诗,每读一遍都有不同的感受。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正如这首《一代人》,短短的两行诗句,却清晰地勾画了一群探索者的坚定形象。
暗叹诗人独特的想象,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仅仅是十几个字,字里行间却还有着看似简单实为复杂的意象。
在顾城的诗作中,人们总能找到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
第一种意象表现手法是象征隐喻法而顾城诗歌的意象世界最常用的表现手法首先是象征隐喻法:这也是诗歌新艺术的中心,它打破了真实描写和直抒胸臆的传统表现手法,使诗人的抒情角度转移,诗中的象征从表面看上去毫无联系,也无所指,但深层却有无穷的意蕴,诗的感染力也就在于此,早期象征主义大师马拉美反复强调(2)“诗只能暗示,如直呼其名,诗的享受便减去四分之三”。
是的,诗的魅力不体现在直观和如实地描绘,也不是在证明什么,它总是在暗示什么,象征性的加以启迪也是现代诗的一个重要特点。
象征手法与古典诗歌“由此至彼”,“言此意它”的比兴手法极其相近,从根本上说,象征也是一种比兴,或者比兴是象征的一种表现手法,比是求诗的形象化,兴是求诗的言外之意,所不同的是象征手法经常巧妙地隐去被比事物,诗歌主题也就呈现了多义性。
例如开头出现的小诗《一代人》,它是由“黑夜”,“我”“黑色的眼睛”等感性形象构成的意象组合,它们既有其本身的客观意义,所代表的内在含义又都超越了这些词汇固有的客观意义,加上题目的指示,因而具有了强烈的象征性,即“黑夜”象征置于那一代人心灵上的阴影,“眼睛”象征一代人探索的眼睛,是一双渴望光明的眼睛,而诗中的“我”则象征着一代人。
顾城诗歌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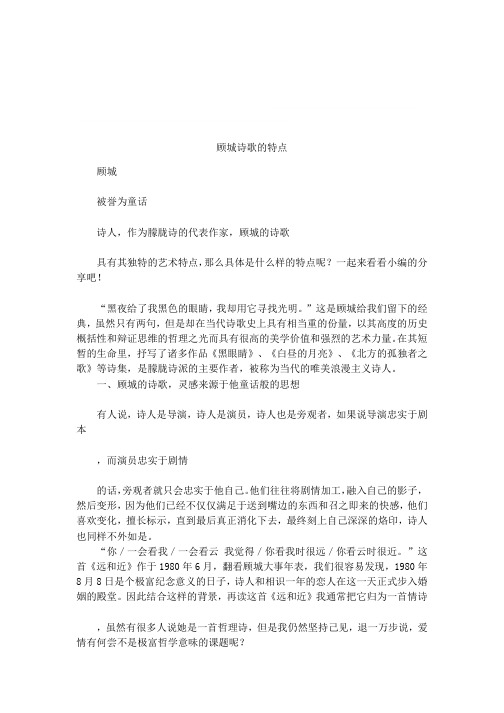
他的童年生活是幸福的。在他十二岁写成的《星月的由来》中充满了童年的天真和幻想,甚至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纯净。他刚读完初一上学期时,席卷全国的文革就波及他的家,他随父亲下放到了农村,一去就是十多年。农村明丽恬淡的山水风光,善良纯朴的人性深深感动了顾城。当他返城后,由于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差距而产生的种种格格不入的陌生感和不适感就油然而生。于是他就不由自主地回想幸福的童年时光,回想在农村耳闻目睹的一切,加深对它们的热爱,从而自觉地将自己的灵魂放逐于充满纯真美的童年和充满自然美与人性美的乡村。更为重要的是,年少时代在城市所看到的血腥、暴力图景难以忘怀,更使他对城市产生了极大厌恶感,使他更加偏向于对农村自然的描绘。正如他自己所说:“新的‘自我’,正是在这一片瓦砾上诞生的,他打碎了迫使他异化的模壳,在并没有多少花香的风中伸展着自己的躯体……他相信自己应作自己的主人走来走去。”我们分析这段话可以发现:这里“新的自我”应就是“无目的的我”,是作为一个自由自在的个体而存在的。在顾城的艺术追寻中,他将“新的‘自我’”的重建锁定于“天国”——由“童心”和“自然”构筑的具有精神家园意义的“天国”。他决心“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那天国的门”,去表现“纯净的美”。因而他幸福的童年,童年生活的农村便是“天国”的世间原形,如他的《生命幻想曲》中的沙漠和森林。少年的顾城,在离开农村回到他厌恶的城市之后,并没有激烈地抗争现实,他借鉴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避世传统,独自在寻找他梦中纯净的天国,借此来宣泄对人性沦丧的痛苦和失望,让自我获得一种心灵上的平静和慰藉。这些都让他的诗歌不含有人世间的一切丑恶,而只是一种对人性复归的美好憧憬。这一切都源于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继承,也是他的诗歌能打动那么多读者的根本原因。他说:“我喜欢古诗
现代诗歌鉴赏顾城的一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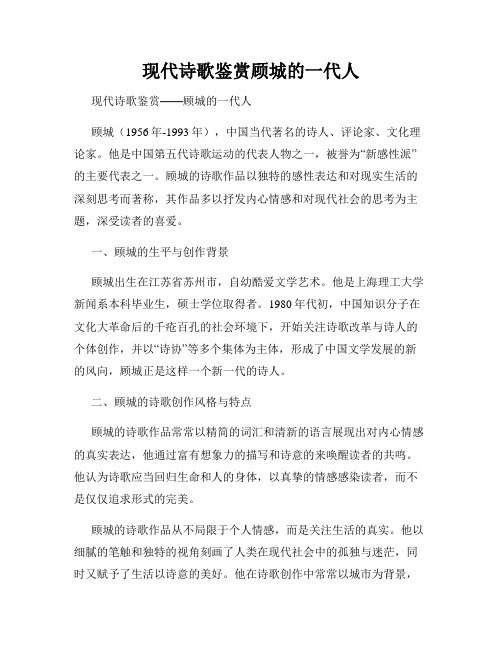
现代诗歌鉴赏顾城的一代人现代诗歌鉴赏——顾城的一代人顾城(1956年-1993年),中国当代著名的诗人、评论家、文化理论家。
他是中国第五代诗歌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新感性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顾城的诗歌作品以独特的感性表达和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思考而著称,其作品多以抒发内心情感和对现代社会的思考为主题,深受读者的喜爱。
一、顾城的生平与创作背景顾城出生在江苏省苏州市,自幼酷爱文学艺术。
他是上海理工大学新闻系本科毕业生,硕士学位取得者。
198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后的千疮百孔的社会环境下,开始关注诗歌改革与诗人的个体创作,并以“诗协”等多个集体为主体,形成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新的风向,顾城正是这样一个新一代的诗人。
二、顾城的诗歌创作风格与特点顾城的诗歌作品常常以精简的词汇和清新的语言展现出对内心情感的真实表达,他通过富有想象力的描写和诗意的来唤醒读者的共鸣。
他认为诗歌应当回归生命和人的身体,以真挚的情感感染读者,而不是仅仅追求形式的完美。
顾城的诗歌作品从不局限于个人情感,而是关注生活的真实。
他以细腻的笔触和独特的视角刻画了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的孤独与迷茫,同时又赋予了生活以诗意的美好。
他在诗歌创作中常常以城市为背景,通过对城市景物的描绘和对城市中个体命运的关注,表达了对现代生活的思考与怀疑。
三、顾城的代表作品欣赏1.《一代人》一代人在一个经过痛苦和毁坏的时代诞生探索死去这首诗以简约而深刻的语言展示了一代人在艰难时代中的成长和遭遇,以及对生与死的思考。
作者通过极简的词语传达了一代人的历史责任和命运,引发读者对现实生活的深度反思。
2.《十四行·绿》绿无边地绿没有公鸟独自飞过这首短诗以简洁的形式凝练出大自然中的清新与生机,以绿色为线索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自由的向往。
通过简单的描写,带给读者内心的宁静与欢愉。
四、顾城对当代诗歌的影响顾城的诗歌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刻的思考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他的作品被广泛翻译成多国文字,并对当代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顾城诗歌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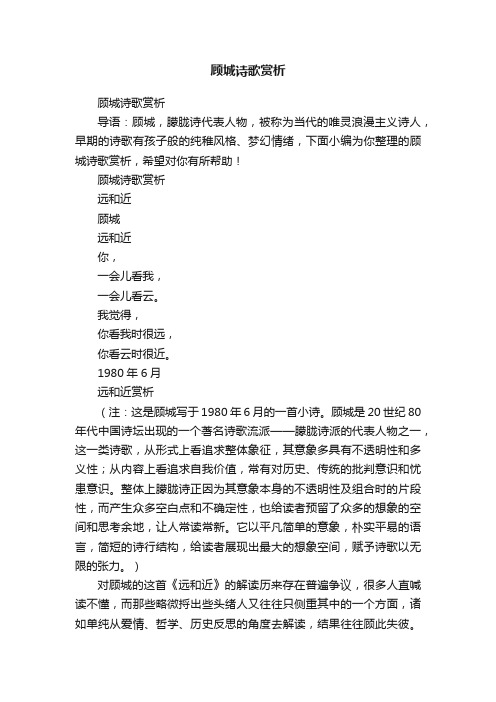
顾城诗歌赏析顾城诗歌赏析导语:顾城,朦胧诗代表人物,被称为当代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早期的诗歌有孩子般的纯稚风格、梦幻情绪,下面小编为你整理的顾城诗歌赏析,希望对你有所帮助!顾城诗歌赏析远和近顾城远和近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
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1980年6月远和近赏析(注:这是顾城写于1980年6月的一首小诗。
顾城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诗坛出现的一个著名诗歌流派——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一类诗歌,从形式上看追求整体象征,其意象多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从内容上看追求自我价值,常有对历史、传统的批判意识和忧患意识。
整体上朦胧诗正因为其意象本身的不透明性及组合时的片段性,而产生众多空白点和不确定性,也给读者预留了众多的想象的空间和思考余地,让人常读常新。
它以平凡简单的意象,朴实平易的语言,简短的诗行结构,给读者展现出最大的想象空间,赋予诗歌以无限的张力。
)对顾城的这首《远和近》的解读历来存在普遍争议,很多人直喊读不懂,而那些略微捋出些头绪人又往往只侧重其中的一个方面,诸如单纯从爱情、哲学、历史反思的角度去解读,结果往往顾此失彼。
在我看来,这确实是一首表现爱情的诗,却又不单单是写爱情的,更蕴含了诗人强烈的精神寄托和追求。
下面就具体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读此诗:一、单纯而复杂的特殊感情:从诗行建构来看,顾城这首《远和近》,仅两节6行24个字,如此短小的篇幅中,“你”字却独占一行,这不得不引起人的注意,从而起到了突出强调的作用。
“我觉得”也独占一行,在形式上与第一行“你”呈现一种呼应,同时暗示了“我”的一切内心活动和感觉都是以“你”为中心的,“我”从你的动作和飘忽的眼神中读出了“你”的内心。
上节主要客观描述“你”的举动,展示的是“你”的世界,是自由自在的世界;下节主要描述“我”对“你”的举动的内心感受,是完全自主的、“我”的世界,也可以说是“我”对“你”的世界的一种主观介入。
而诗的基本功能是“主情”、“言志”,因而很明显,下节才是诗歌的重点。
浅谈顾城诗歌创作的艺术风格

浅谈顾城诗歌创作的艺术风格摘要:顾城是著名的朦胧诗人,他的的诗歌闪动着灵性的光辉,他以一颗金子般的童心向我们娓娓叙说着关于人间自然的美好,关于纯净童真的种种向往。
顾城对大自然,对世外桃源的钟情缺乏广泛性的眼光,也许无法将它上升到宇宙意识和生命形式的更高层次,但是,他用率真的个性和执著的童心,为读者铸造了一个独特的诗歌王国,彰显了他在诗歌领域的超凡才气,和不可替代的独特魅力。
一、诗人简介顾城1956年出生于北京。
他十几岁时,随父顾工下放山东昌北火道村,在那里,他写下了许多小诗,由此拉开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之路,那些诗歌的一部分被他抄在一个小本子上,并统一命名为《无名的小花》。
1974年,顾城回北京,并于当年在《北京文艺》、《山东文艺》、《少年文艺》等报刊上。
零星发表自己的诗歌作品。
1977年,重新进入写作,在《蒲公英》小报发表诗作后,在诗歌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巨大争论,一跃而成为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1980年初他所在的单位解体,从此顾城就过起了漂游的生活。
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7年应邀出访欧美进行文化交流、讲学活动。
1988年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后来辞职,隐居在激流岛。
1992年,顾城获得了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创作年金。
1993年,他又获德国伯尔创作基金,在德国写作。
1993年10月8日于新西兰所居岛,因为离婚事件,顾城与他的妻谢烨发生冲突,结果他杀死自己妻子后自杀。
二、顾城诗歌的创作阶段在1992年底,顾城在德国波恩接受《袖珍汉学》杂志的编辑采访时,曾把自己的诗歌创作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1969—1974年间的自然创作阶段,1977—1982年间的文化阶段,1982—1986年间的反文化阶段,以及1986年以后的无我创作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诗人顾城童年时期的创作,主要是跟随他的父亲在山东昌北火道村下放时写下的许多诗歌。
这一阶段的诗歌创作倾向于童心写作,即是站在孩童的立场去书写自然和身边的事。
浅析顾城诗歌的特点

浅析顾城诗歌的特点浅析顾城诗歌的特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顾城,中国当代著名诗人,他的诗歌曾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他的作品充满着节奏感、细腻的语言、富有张力的句式以及深刻的思想内容。
下面,我们将从几个方面浅析顾城的诗歌特点。
一、独特的语言顾城的诗歌充满了浓郁的语言特色,他使用了大量的精致的比喻、隐喻、典故等,让读者不断发现其中的新意。
在《时间,你可曾听见》一诗中,他用“时间,你是穿行在天上的风”来描述时间的轻盈穿梭;在《夜》中,他用“夜是一只黑色的鸟,它的翅膀覆盖了整片天空”来描述夜的宁静而又神秘。
二、丰富的情绪顾城的诗歌中透露出丰富而复杂的情绪,他用一种内心深处的敏感来表达对生活的眷恋,也用坚定的信念去面对生活的挑战。
在《沉思》中,他用“我不要去期望明天,但也不要忘记昨天”来表达自己对未来的忧虑;在《初春》中,他用“初春,你好!你带着活力,带着梦想”来表达对新生命的向往。
三、优美的节奏顾城的诗歌带有流畅而优美的节奏感,他用五言、七言、九言等不同格律来表达不同的思想内容。
在《别离》中,他使用五言律诗来表达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在《沉思》中,他使用七言律诗来表达对人生道理的思考之情。
四、寓意深刻顾城诗歌中隐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寓意,他以独特的眼光去审视生活,以敏锐的心去感受人生。
在《思念》中,他用“思念是一只鸽子,它在夜里唱歌”来表达对亲人遥远之情;在《关于时间》中,他用“时间是一只无声的钟,它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游走”来表达对时间的无奈而又无力。
总之,顾城诗歌所体现出来的特点有很多:独特的语言、丰富的情绪、优美的节奏以及寓意深刻。
他用精妙而诗意化的文字和一种内心深处敏感而真切的感受去表达对生活的思考与感受,这也是顾城诗歌留存下来并不断发扬光大的原因所在。
顾城的作品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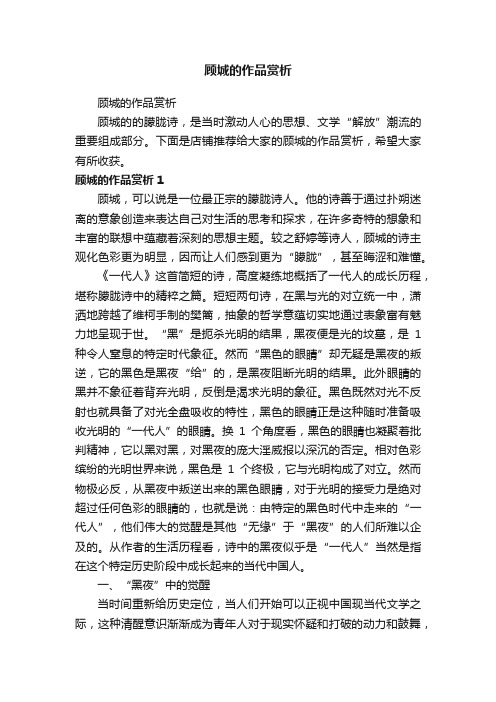
顾城的作品赏析顾城的作品赏析顾城的的朦胧诗,是当时激动人心的思想、文学“解放”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下面是店铺推荐给大家的顾城的作品赏析,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顾城的作品赏析1顾城,可以说是一位最正宗的朦胧诗人。
他的诗善于通过扑朔迷离的意象创造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思考和探求,在许多奇特的想象和丰富的联想中蕴藏着深刻的思想主题。
较之舒婷等诗人,顾城的诗主观化色彩更为明显,因而让人们感到更为“朦胧”,甚至晦涩和难懂。
《一代人》这首简短的诗,高度凝练地概括了一代人的成长历程,堪称朦胧诗中的精粹之篇。
短短两句诗,在黑与光的对立统一中,潇洒地跨越了维柯手制的樊篱,抽象的哲学意蕴切实地通过表象富有魅力地呈现于世。
“黑”是扼杀光明的结果,黑夜便是光的坟墓,是1种令人窒息的特定时代象征。
然而“黑色的眼睛”却无疑是黑夜的叛逆,它的黑色是黑夜“给”的,是黑夜阻断光明的结果。
此外眼睛的黑并不象征着背弃光明,反倒是渴求光明的象征。
黑色既然对光不反射也就具备了对光全盘吸收的特性,黑色的眼睛正是这种随时准备吸收光明的“一代人”的眼睛。
换1个角度看,黑色的眼睛也凝聚着批判精神,它以黑对黑,对黑夜的庞大淫威报以深沉的否定。
相对色彩缤纷的光明世界来说,黑色是1个终极,它与光明构成了对立。
然而物极必反,从黑夜中叛逆出来的黑色眼睛,对于光明的接受力是绝对超过任何色彩的眼睛的,也就是说:由特定的黑色时代中走来的“一代人”,他们伟大的觉醒是其他“无缘”于“黑夜”的人们所难以企及的。
从作者的生活历程看,诗中的黑夜似乎是“一代人”当然是指在这个特定历史阶段中成长起来的当代中国人。
一、“黑夜”中的觉醒当时间重新给历史定位,当人们开始可以正视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际,这种清醒意识渐渐成为青年人对于现实怀疑和打破的动力和鼓舞,年轻的“一代人”开始对现实的“黑暗”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顾城的这首诗,一方面对那些痛心刻骨的现实给予了强烈的批判和质疑,另一方面又对未来有某种改变的要求和期待。
顾城的诗的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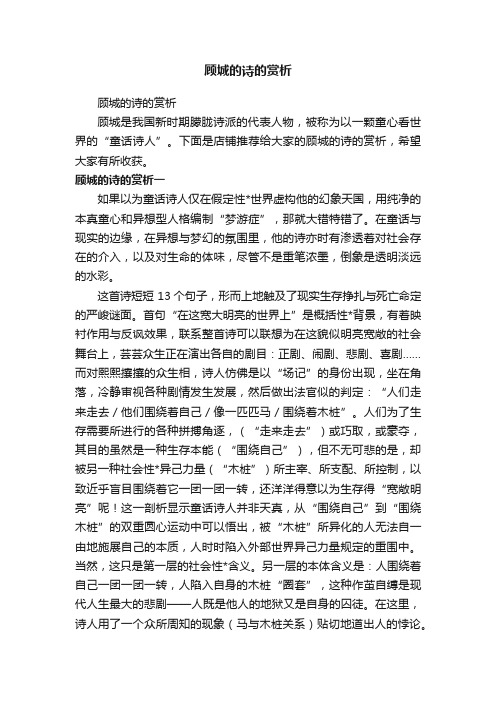
顾城的诗的赏析顾城的诗的赏析顾城是我国新时期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以一颗童心看世界的“童话诗人”。
下面是店铺推荐给大家的顾城的诗的赏析,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顾城的诗的赏析一如果以为童话诗人仅在假定性*世界虚构他的幻象天国,用纯净的本真童心和异想型人格编制“梦游症”,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童话与现实的边缘,在异想与梦幻的氛围里,他的诗亦时有渗透着对社会存在的介入,以及对生命的体味,尽管不是重笔浓墨,倒象是透明淡远的水彩。
这首诗短短 13个句子,形而上地触及了现实生存挣扎与死亡命定的严峻谜面。
首句“在这宽大明亮的世界上”是概括性*背景,有着映衬作用与反讽效果,联系整首诗可以联想为在这貌似明亮宽敞的社会舞台上,芸芸众生正在演出各自的剧目:正剧、闹剧、悲剧、喜剧…… 而对熙熙攘攘的众生相,诗人仿佛是以“场记”的身份出现,坐在角落,冷静审视各种剧情发生发展,然后做出法官似的判定:“人们走来走去/他们围绕着自己/像一匹匹马/围绕着木桩”。
人们为了生存需要所进行的各种拼搏角逐,(“走来走去”)或巧取,或豪夺,其目的虽然是一种生存本能(“围绕自己”),但不无可悲的是,却被另一种社会性*异己力量(“木桩”)所主宰、所支配、所控制,以致近乎盲目围绕着它一团一团一转,还洋洋得意以为生存得“宽敞明亮”呢!这一剖析显示童话诗人并非天真,从“围绕自己”到“围绕木桩”的双重圆心运动中可以悟出,被“木桩”所异化的人无法自一由地施展自己的本质,人时时陷入外部世界异己力量规定的重围中。
当然,这只是第一层的社会性*含义。
另一层的本体含义是:人围绕着自己一团一团一转,人陷入自身的木桩“圈套”,这种作茧自缚是现代人生最大的悲剧——人既是他人的地狱又是自身的囚徒。
在这里,诗人用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马与木桩关系)贴切地道出人的悖论。
为了不至于过于分散,第二节首句再现一次“背景”以便收拢,接着道出“偶尔”也有极少数英勇的“蒲公英”,能够做超脱性*飞行。
“童话诗人顾城诗歌中的童话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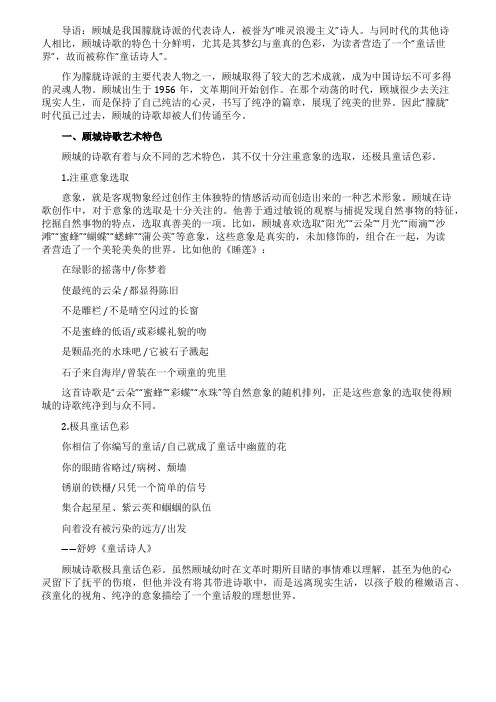
导语:顾城是我国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被誉为“唯灵浪漫主义”诗人。
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相比,顾城诗歌的特色十分鲜明,尤其是其梦幻与童真的色彩,为读者营造了一个“童话世界”,故而被称作“童话诗人”。
作为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顾城取得了较大的艺术成就,成为中国诗坛不可多得的灵魂人物。
顾城出生于1956年,文革期间开始创作。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顾城很少去关注现实人生,而是保持了自己纯洁的心灵,书写了纯净的篇章,展现了纯美的世界。
因此“朦胧”时代虽已过去,顾城的诗歌却被人们传诵至今。
一、顾城诗歌艺术特色顾城的诗歌有着与众不同的艺术特色,其不仅十分注重意象的选取,还极具童话色彩。
1.注重意象选取意象,就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顾城在诗歌创作中,对于意象的选取是十分关注的。
他善于通过敏锐的观察与捕捉发现自然事物的特征,挖掘自然事物的特点,选取真善美的一项。
比如,顾城喜欢选取“阳光”“云朵”“月光”“雨滴”“沙滩”“蜜蜂”“蝴蝶”“蟋蟀”“蒲公英”等意象,这些意象是真实的,未加修饰的,组合在一起,为读者营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
比如他的《睡莲》:在绿影的摇荡中/你梦着使最纯的云朵 /都显得陈旧不是雕栏 /不是晴空闪过的长窗不是蜜蜂的低语/或彩蝶礼貌的吻是颗晶亮的水珠吧 /它被石子溅起石子来自海岸/曾装在一个顽童的兜里这首诗歌是“云朵”“蜜蜂”“彩蝶”“水珠”等自然意象的随机排列,正是这些意象的选取使得顾城的诗歌纯净到与众不同。
2.极具童话色彩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你的眼睛省略过/病树、颓墙锈崩的铁栅/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着没有被污染的远方/出发――舒婷《童话诗人》顾城诗歌极具童话色彩。
虽然顾城幼时在文革时期所目睹的事情难以理解,甚至为他的心灵留下了抚平的伤痕,但他并没有将其带进诗歌中,而是远离现实生活,以孩子般的稚嫩语言、孩童化的视角、纯净的意象描绘了一个童话般的理想世界。
顾城我们去寻找一盏灯 诗歌鉴赏

《我们去寻找一盏灯》是现代著名诗人顾城的一首诗作。
这首诗歌以寻找一盏灯为线索,通过描述不同的场景和情感,表达了诗人对理想和生活的向往。
首先,从诗歌的第一节可以看到,顾城描绘了一个温暖而美丽的家庭环境,其中有一盏灯照耀着这个家庭。
这盏灯可以理解为家的象征,代表了温暖、安宁和爱。
诗人想象在这个环境中度过每一个夜晚,享受平静而幸福的生活,表达了他对家庭的向往和珍视。
在第二节中,诗人描述了一个荒草蔓延的荒凉景象。
这里的灯可以理解为旅行的灯塔,它照亮了旅人的路,让列车得以安静地驶过。
诗人通过这个画面表达了对未知的好奇和对自由的渴望。
这盏灯象征着对冒险和刺激的追求,以及对新生活的期待。
第三节中,诗人将画面转向了大海旁边。
这里的灯是灿烂的朝阳,它象征着童年的快乐和纯真。
朝阳初升,带来新的希望和美好的一天。
诗人想象在这个充满奇迹的环境中回忆每一个童年,保持一颗年轻而热情的心。
这表达了他对童年的怀念和对美好时光的珍视。
在最后一节中,顾城并没有具体描述要寻找的灯是什么样子,只是重复了“我们去寻找一盏灯”的句子。
这一句话在诗歌中反复咏唱,增强了诗歌的韵律美,也表现了诗人对理想和生活的坚定追求。
这盏灯象征着对未来的梦想和希望,诗人鼓励我们要有勇气去寻找它,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幸福。
顾城的这首诗歌充满了意象和隐喻,通过描绘不同的场景和情感,表达了他对理想和生活的向往。
这盏灯是家的象征,也是对未知的好奇和对自由的渴望的象征。
同时,它也是童年的快乐和纯真的象征,以及未来的梦想和希望的象征。
这首诗歌鼓励我们要有勇气去寻找这盏灯,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幸福。
浅析顾城诗歌中的基本特色

浅析顾城诗歌中的基本特色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大陆新诗坛上崛起的朦胧诗派,以思想上的叛逆和艺术上的反动向中国传统诗歌提出了双向挑战,以新的审美态势冲击了民族文化积淀的超稳定惰性。
这无疑是中国新时期诗坛上最深刻的事件。
而作为点燃朦胧诗之争导火线的顾城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一深刻事件中人们所关注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
不论是被称为“童话诗人”.(舒婷语)还是“城堡诗人”(黄凡语)的顾城在他的诗歌和诗学中,都一直在不懈地追求着自然和纯粹,这使他的诗歌“获得了一种更高层次的概括性与抽象性,一种面向未来的特质,·····一种堪成禅悟的明慧”,他的简洁而充满神秘的诗风是他对新诗潮无可替代的贡献,他的诗在新时期文化中所占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1987年他出国以后,曾在德国、美国、新西兰、法国、英国、西班牙、荷兰、罗马尼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接受过多次采访,并受聘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国外有的汉学家称他为“东方的明珠”。
如此骄人的成就与荣誉,足以让世人钦佩不已。
然而,荣耀的背后是些许无奈。
米歇尔·福柯曾说,“纯洁的行为包含着病态的痕迹。
”顾城诗歌的童话特色及其他艺术特色。
在这方面多以纯真的童话与顾城最后不纯真的暴力事件相对照来探讨事件成因或对其做出批评。
如张捷鸿的《童话的天真—论顾城诗歌的创作》,张颐武的《一个童话的终结—顾城之死与当代文化》等纯净他喜欢纯净的东西,他固执地认为成长是一个失去纯净的过程,是一种堕落,因此,当他真正长大之后,一直用拒绝的态度与外在世界对抗,固执地坚守着“孩子”的阵地,坚守着自己的童话理想,将自身以外的整个世界都视为异己的成人世界,而后又上升为将人异化的物质世界。
他始终不渝地抵抗着这个世界对自己的影响,直到1981年他还借一个孩子的口吻表达了他对成人世界的不友好不信任的态度:“在梦里/我的头发白过/我到达过五十岁/读过整个世界/我知道你们的一切/.··…出生入死/你们无事一样”(((十二岁的广场)))此时他己经25岁,可他仍用“你们”来称呼成年人。
顾城的诗歌内容赏析

顾城的诗歌内容赏析在现实生活或工作学习中,大家都接触过诗歌吧,诗歌能使人们自然而然地受到语言的触动。
什么样的诗歌才经典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顾城的诗歌内容赏析,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顾城的诗歌内容赏析1别顾城在春天,你把手帕轻挥,是让我远去,还是马上返回?不,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因为,就像水中的落花,就像花上的露水……只有影子懂得,只有风能体会,只有叹息惊起的彩蝶,还在心花中纷飞……一九七九年六月赏析:这首诗发表在1980年的《星星》诗刊第三期上,是一首抒情色彩较浓重的爱情诗。
诗中主要抒写了“我”在与恋人分别时,在“她”挥手的瞬间,难以言传的失落感。
诗歌开头两句描写的是“别”的情景,构筑了“别”的形象。
随即诗人便捕捉住这一瞬间的感觉。
抒写由此而生发的联想和幻觉,展现了分别时,“我”以目中的彷徨和迷惘。
同时,也从侧面暗示了“我”与“她”之间的深沉的恋情。
分手是无因的,离别是无由的,然而这无因无由的分别终归还是有因由。
这便是命运。
就象自然界的水中飘荡的落花,花朵沾染的露珠一样,是自然而自然的。
诗境至此,便脱出纷繁复杂的尘世,进入了一个静谧、透明、单纯、和美的天国中去了,达到了生命与自然、灵魂和本体高度和谐的境界,迷惘变得明朗,感伤变得平静,失落变得无谓。
“别”是命运的安排,是自然的注定。
但是这心平气和的自语给人留下的还是有些个无可奈何的隐痛和哀怨,更进一步增加了“我”的迷惘、彷徨与伤感。
心有大感而无言,也无须言。
压抑便会有幻觉,感伤总想有超脱,这便是“只有叹息惊起的彩蝶在心花中纷飞”。
而彩蝶只不过是往日的恋情与未来憧憬在潜意识中的象征而已,对失去的旧情的深切依恋和对未来飘渺无望的希冀便是这“彩蝶纷飞”的真切内涵。
诗文至此,嘎然而止,而心中的离愁别绪却萦绕往返,撞荡回流。
本诗作者以其独特而敏锐的心理感受,借助蒙太奇手法组合,抒写了“别”时瞬间捕捉到的丰沛感觉,造成意象的撞击和迅速转换,激发人们用丰富想象来填补大幅度跳跃而留下的空白,从而扩大了诗的容量。
浅谈顾城(共5篇)

浅谈顾城(共5篇)第一篇:浅谈顾城浅谈顾城摘要:顾城的诗篇闪动着诗篇和灵性的光辉,坦诚相对的心灵世界,以一颗金子般的童心向我们娓娓叙说着关于美好,关于纯净的种种传说。
也许他这种对自然,对世外桃源的钟情缺乏世界性的眼光,也无法将它上升到宇宙意识和生命形式层次,但正是他率真的个性和执著的童心铸造了他独特的诗歌世界,显示了他的超凡才气,并具有不可替代的魅力。
一、浪漫主义的“童话诗人”顾城是我国新时期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因为他的诗歌总是充满了纯净明丽的意象、轻快自然的节奏和浪漫的童话色彩,因而被称为以一颗童心看世界的“童话诗人”,同时也被认为是当代唯一唯灵浪漫主义诗人。
与朦胧诗派的其它代表人物相比,顾城的诗显得纯真无瑕、纤弱纯净,尤其是他早期的诗歌有孩子般的纯稚风格和梦幻情绪,用直觉和印象式的语句来咏唱童话般的少年生活。
顾城自一九七九年在《蒲公英》小报发表诗作后在诗歌界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争论。
作为当代新诗史上一位不可忽略的“重量级”诗人,毫无疑问,顾城是以他的朦胧诗奠定了自己在诗歌上的地位。
然而,他的寓言诗以及旧体诗同样也因含义隽永而倍受世人注目。
本文试着从其诗歌内容与艺术形式两方面来分析顾城诗歌前后期的转变。
二、顾城简介如果解读顾城诗歌的内容转变,那么了解顾城的生活经历就不是应该的,而是必须的了。
顾城1956年出生于北京,十几岁时随父顾工下放山东昌北火道村,在那里他写下了许多小诗,这些诗歌的一部分被他抄在一个小本子上,并取名为《无名的小花》。
1974年顾城回北京并于当年在《北京文艺》、《山东文艺》、《少年文艺》等报刊零星发表作品。
1977年起重新进入写作,在《蒲公英》小报发表诗作,一跃而成为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1980年初他所在的单位解体,自此顾城便失去工作,从此过漂游生活。
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7年应邀出访欧美进行文化交流、讲学活动。
1988年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
alevel 中文 顾城诗选

《探寻顾城诗选的艺术魅力》一、引言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顾城是一位备受瞩目的诗人,他的诗歌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内涵,深受读者的喜爱与赞赏。
而作为alevel 中文的学习内容之一,《顾城诗选》更是成为学生深入了解和研究这位诗人的重要窗口和资料。
今天,我将带领大家探寻顾城诗选的艺术魅力,深入品味其中的文学价值和思想内涵。
二、顾城诗选的艺术特色1. 动人的诗意表达顾城的诗作以其动人的诗意表达而著称,他借助于丰富多彩的形象语言和情感表达,将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在《顾城诗选》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对自然、对生活、对人情世故的细腻体验,以及对情感、思想的深刻反思和表达。
例如《再别康桥》一诗中,“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通过对临别离别的感怀和对生活变迁的见证,展现了作者对人生和命运的感慨和追问。
2. 深邃的思想内涵顾城的诗作在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背后,融入了深邃的思想内涵,体现出作者对人生、对命运、对人文情感的深刻思考。
《望蓟门》一诗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表现了作者对历史长河和人生奇迹的感慨和思索,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与拷问。
这种深邃的思想内涵,使得顾城的诗作具有超越时空的普世意义和历史深度。
三、对于alevel 中文学习的意义1. 拓展文学视野《顾城诗选》作为alevel 中文的重要学习内容,不仅仅是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一位诗人的生平和诗作,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诗歌艺术的鉴赏,拓展学生的文学视野和审美情趣。
在顾城的诗作中,学生不仅可以感受到诗人的创作激情和感情充沛,还能从中汲取文学启迪和人生感悟,使得学生的文学修养和情感体验得以深化与升华。
2. 培养文学素养通过学习《顾城诗选》,学生可以在课堂和课外阅读中,培养自己的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
学生可以透过诗歌的语言与音韵、意象与意境、节奏与节制,感受到诗歌的魅力和艺术之美;从诗歌中获取有关生活、世界的感悟和思考,积淀自己的情感和心灵,从而提升个人的文学修养和人文素养。
顾城诗歌《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全文赏析

顾城诗歌《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全文赏析顾城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内涵而广受赞誉。
他的诗歌《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是一首充满自我表达与情感宣泄的作品。
本文将从诗歌的主题、形式和语言等方面进行细致的赏析,探究诗歌背后的情感世界和艺术创作。
诗歌的主题是表达诗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矛盾与反叛,并展示了自己作为一个“任性的孩子”的态度。
诗歌通过孩子的视角,将反抗现实剥削与束缚的情绪表达了出来,并将这种反抗的精神和态度视为一种宝贵的资本。
诗歌的形式上采用了自由诗的形式,没有固定的节奏与韵律,更加贴近自然的流动感。
这种形式的选择使诗歌更加接近现实生活和个体情感体验,打破了传统诗歌语言的束缚,更加自由地表达了诗人内心的情感。
诗歌的语言表达简洁而凝练,以简单的词语和直接的意象呈现诗人的情感状态。
例如,“带着一颗叛逆的心”、“我是喧嚣的笑声”等,这些直接的词语和意象创造了一种鲜明的对比,将诗人内心的真实情感展现了出来。
同时,诗歌中还运用了排比句法和倒装等修辞手法,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表现力。
诗歌的整体氛围是一种反抗与追求自由的情绪。
诗人通过描绘自己作为一个任性孩子的形象,表达了对现实束缚和压迫的不满与反抗。
他渴望追寻自己内心的自由与真实,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生活的意义。
诗歌中的意象丰富而独特,展现了诗人独特的艺术创作风格。
例如,“世界是一颗日常的苹果”、“把墙颠倒过来不是一回事”等都是诗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独特意象,表达了诗人对于现实的扭曲与改造的愿望。
这种独特的意象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表达方式,使诗歌更具想象力和审美价值。
总的来说,顾城的诗歌《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通过自由的形式语言,直接而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内心的情感和态度。
诗歌中的主题、形式和语言等方面的运用都体现出了诗人的个人特色和艺术追求。
这首诗歌不仅在情感表达上引发读者共鸣,同时也在艺术创作上具备了独立的价值。
浅谈顾城诗歌的写作特点

浅谈顾城诗歌的写作特点作者:冉建平盛家林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2012年第02期顾城被誉为童话诗人,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作家,顾城的诗歌具有其独特的艺术特点,这使得他的诗歌显得特别,形成了顾城自己特有的诗歌艺术风格。
一.关怀的主题顾城诗歌关怀的主题,和其他众多作家一样,在他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具有反映现实的特点。
他们既反思历史又探索未来,在现实中彷徨,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小巷又弯又长没有门没有窗我拿把旧钥匙敲着厚厚的墙——《小巷》自《顾城的诗》49面重复的“又”“又”“没有”“没有”的字眼和“旧”“厚厚”的陈旧厚重感,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探索的艰辛和无路可寻,对未来的迷茫、不知该怎么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无奈都包含在其中。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着春天它梦见——自己舒展着颤动的腰身长睫旁闪耀着露滴的银钻它梦见——蝴蝶轻轻地吻它春蚕张开了新房的金幔它梦见——无数花朵睁开了稚气的眼睛就像月亮身边的万千星点……种子呵在冻土里梦想春天……——《梦想》自《顾城的诗》18面在这首诗里诗人还是对未来进行着憧憬和希望。
“春天”是在梦想中,而现实是“种子”被困在“冻土”里,现实的残酷和诗人坚持理想的信念形成鲜明对比。
面对时代的变迁,巨大的伤痛历历在目,诗人不能摆脱,他通过对未来希望来让自己坚持下去。
在他的《我们去寻找一盏灯》里顾城写道:走了那么远/我们去寻找一盏灯。
这句话在每一段描写前被重复着,全诗七节,而这段每次作为独立的一节一共出现了四次,对真理对未来的不懈追求如此执着。
这些都表现了顾城“时代式的彷徨”,这在他们那个时代的许多诗人的诗作中都有表现,他们处在一个新旧时代交叠的路口,免不了对方向的踟蹰和犹豫,并具有一种内心的忧郁。
不过顾城在后来还是有充满希望的诗。
尘土可以埋葬乡村可以埋葬水埋葬树林埋葬在水边开出大片花朵的愿望可以在远离水鸟的内陆让风吹出细细的波浪我始终相信人类不会这样灭亡雨在谷物和新鲜的平原上飘撒他们在密集地走动紫云英在软软的墓地上生长他们走动的姿态在渐渐改变天空开始晴朗淡蓝色的天光,青春闪在一个又一个少女脸上——《在尘土之上》自《顾城的诗》162面“我始终相信/人类不会这样灭亡”“天空开始晴朗”,这时的顾城以一种满怀希望的心情去看待事物,所以他看到“淡蓝色的天光,青春/闪在一个又一个少女脸上”。
试论顾城诗歌的艺术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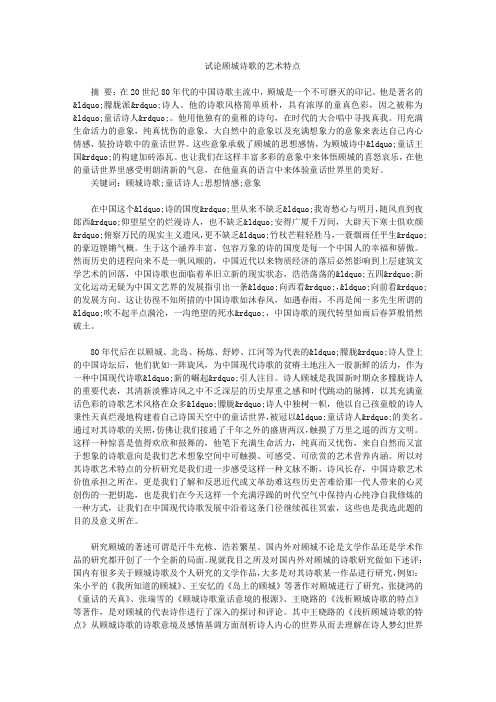
试论顾城诗歌的艺术特点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诗歌主流中,顾城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
他是著名的“朦胧派”诗人。
他的诗歌风格简单质朴,具有浓厚的童真色彩,因之被称为“童话诗人”。
他用他独有的童稚的诗句,在时代的大合唱中寻找真我。
用充满生命活力的意象,纯真忧伤的意象,大自然中的意象以及充满想象力的意象来表达自己内心情感,装扮诗歌中的童话世界。
这些意象承载了顾城的思想感情,为顾城诗中“童话王国”的构建加砖添瓦。
也让我们在这样丰富多彩的意象中来体悟顾城的喜怒哀乐,在他的童话世界里感受明朗清新的气息,在他童真的语言中来体验童话世界里的美好。
关键词:顾城诗歌;童话诗人;思想情感;意象在中国这个“诗的国度”里从来不缺乏“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仰望星空的烂漫诗人,也不缺乏“安得广厦千万间,大辟天下寒士俱欢颜”俯察万民的现实主义遗风,更不缺乏“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豪迈铿锵气概。
生于这个涵养丰富、包容万象的诗的国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幸福和骄傲。
然而历史的进程向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近代以来物质经济的落后必然影响到上层建筑文学艺术的回落,中国诗歌也面临着革旧立新的现实状态,浩浩荡荡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疑为中国文艺界的发展指引出一条“向西看”,“向前看”的发展方向。
这让彷徨不知所措的中国诗歌如沐春风,如遇春雨,不再是闻一多先生所谓的“吹不起半点漪沦,一沟绝望的死水”,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如雨后春笋般悄然破土。
简论顾城诗歌的情感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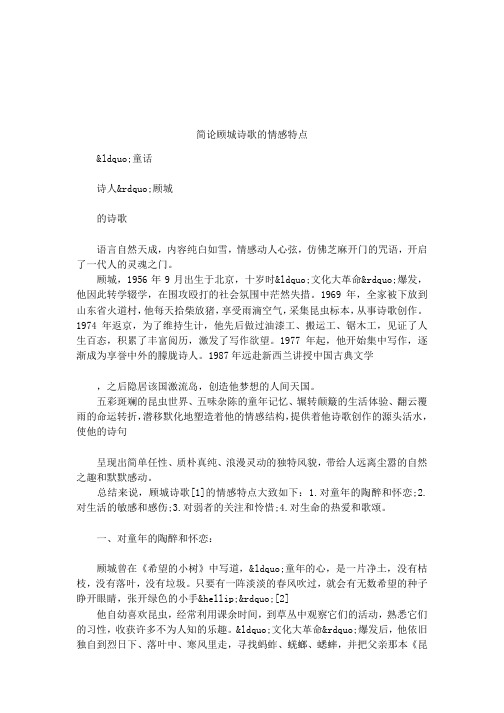
对生活的敏感和感伤在他的创作中比比皆是,使他的诗歌显得曲折动人、细腻温情,充满对自身和宇宙局限性的深刻洞察。
三、对弱者的关注和怜惜:
顾城曾在《学诗笔记(一)》[3]中写道,“当我在走我想象的路时,天地间只有我,和一种淡紫色的小草。小草是在苦咸的土地上长出来的,那么细小又那么密集,站在天空下面,站在乌云和烈日下面,迎接着不可避免的一切……正是它们告诉我春天,告诉我诗的责任。”
他感受着大自然的神奇,培养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生活和梦境似乎已浑然一体。“树枝想去撕裂天空,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它透出天外的光亮,人们把它叫做月亮和星星”(《星月的来由》)。这些诗句童趣盎然、惹人爱怜。
成年后,他仍然拥有一颗纯洁透明的童心,不满足科学世界的单一与死寂。例如“在白天 我变得很黑在黑夜我变得很白我想变成蓝色的 应该到哪里去呢?”(《变》),“和点心一样精美的小镇”《永别了,墓地》,“青青的野葡萄 淡黄的小月亮 妈妈发愁了 怎么做果酱 我说:别加糖 在早晨的篱笆上 有一枚甜甜的 红太阳”(《安慰》),“我们躲开它,一转身 就碰上了喝醉的太阳”(《我们喜欢葡萄》),“雾,缓缓化开像糯米纸一样”(《我相信歌声》)。这些诗句童心弥漫、令人惊叹。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浅析顾城诗歌中的基本特色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大陆新诗坛上崛起的朦胧诗派,以思想上的叛逆和艺术上的反动向中国传统诗歌提出了双向挑战,以新的审美态势冲击了民族文化积淀的超稳定惰性。
这无疑是中国新时期诗坛上最深刻的事件。
而作为点燃朦胧诗之争导火线的顾城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一深刻事件中人们所关注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
不论是被称为“童话诗人”.(舒婷语)还是“城堡诗人”(黄凡语)的顾城在他的诗歌和诗学中,都一直在不懈地追求着自然和纯粹,这使他的诗歌“获得了一种更高层次的概括性与抽象性,一种面向未来的特质,·····一种堪成禅悟的明慧”,他的简洁而充满神秘的诗风是他对新诗潮无可替代的贡献,他的诗在新时期文化中所占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1987年他出国以后,曾在德国、美国、新西兰、法国、英国、西班牙、荷兰、罗马尼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接受过多次采访,并受聘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国外有的汉学家称他为“东方的明珠”。
如此骄人的成就与荣誉,足以让世人钦佩不已。
然而,荣耀的背后是些许无奈。
米歇尔·福柯曾说,“纯洁的行为包含着病态的痕迹。
”顾城诗歌的童话特色及其他艺术特色。
在这方面多以纯真的童话与顾城最后不纯真的暴力事件相对照来探讨事件成因或对其做出批评。
如张捷鸿的《童话的天真—论顾城诗歌的创作》,张颐武的《一个童话的终结—顾城之死与当代文化》等
纯净
他喜欢纯净的东西,他固执地认为成长是一个失去纯净的过程,是一种堕落,因此,当他真正长大之后,一直用拒绝的态度与外在世界对抗,固执地坚守着“孩子”的阵地,坚守着自己的童话理想,将自身以外的整个世界都视为异己的成人世界,而后又上升为将人异化的物质世界。
他始终不渝地抵抗着这个世界对自己的影响,直到1981年他还借一个孩子的口吻表达了他对成人世界的不友好不信任的态度:“在梦里/我的头发白过/我到达过五十岁/读过整个世界/我知道你们的一切/.··…出生入死/你们无事一样”(((十二岁的广场)))此时他己经25岁,可他仍用“你们”来称呼成年人。
这种拒绝长大的心理定势左右了顾城一生的生活和创作。
在这之中,我们也能够清楚地看到他拒绝被污染、固守童真的纯洁,不向世俗社会妥协的一贯姿态。
顾城一生一直象教徒一样地崇拜童话作家安徒生,在《给我的尊师安徒生一》中他赞美到:“你运载着一个天国/运载着花和梦的气球/所有纯美的童心/都是你的港口”。
与其说这是写给安徒生最诚挚的礼赞,毋宁说这是诗人对自己理想、信仰、人格的写照与追求。
在倾轧践踏、屈辱暗算的岁月里,他就悄悄描画自己小小的纯洁的愿望,我希望每一个时刻都象彩色蜡笔那样美丽,希望“画下一只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一片天空/一片属于天空的羽毛和树叶/一个淡绿的夜晚和苹果”,在远离污染,充满田园韵味的净土上,精心构筑自己的天堂;木锯的节拍,稽的歌,拱桥和兰叶弧形的旋律奏起明快的乐章,既流露出对阴郁现实生活的脾院,同时也是对都市“文明病”蔓延的阻击。
他把所有的爱都撒向世界,无论高山大海,抑或小草小花。
他要让小河和丘陵挨得很近,“让他们相爱/让每一个默许/每一阵静静的/春天的激动/都成为一朵小花的生日”,他是那样不知疲倦地精心设计自己的“童心”家园,以致认为“灰烬变得纯洁,/火焰变得柔软/孩子象一群铝制的鸽子,/各种形状的叶子和日子,/都懂我们的语言”他的理想,他的“童心”家园都是基于一颗活泼好奇、生动不己的童心之上的。
郭沫若在致宗白华的信札里有一段话仿佛是专为顾城诗作而下的评语:“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
总之,诗人的本真童心使诗人永远处于率真而纯情的童年期,这是诗人“童心家园”得以构建的关键,也是诗人永葆创造力的一个不二法门。
诚如顾城所说:最好是用单线画一条大船/从童年的河滨驶向永恒心中有座梦之城
他在十四岁时写了一首《幻想与梦》:
我在时间上排徊
既不能前进,也不想后退
挖一个池沼
蓄起幻想的流水
在童年的落叶里
寻我金色的蝉蜕
我热爱我的梦
它象春流般
温暖我的心
在这首诗里,年少的诗人想“蓄起幻想的流水”在“童年”这个诗化了的家园模式中寻找他的梦,当时
文革严酷的现实,加上正处于做梦的年纪,他只好在梦境中找寻美与光明,所以,诗人说:“我热爱我的梦/它象春流般/温暖我的心”。
博尔赫斯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伤害和侮辱人的时代,要想逃避它,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做梦”。
从此开始,诗人开始了他的梦之旅,“把我的幻影和梦/放在狭长的贝壳里/柳枝编成的船篷/还旋绕着夏蝉的长鸣/拉紧桅绳/风吹起晨雾的帆/我开航了”。
(((生命幻想曲)))在他的诗歌中,自然万物被赋予“梦”的翅膀,和着诗人的心灵一起飞翔。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着春天”(((梦想》),星辰、月亮、蝴蝶、春天、黎明、灯火·····一切美丽的事物都装饰在他的梦境里,成为他的向往,也成为他的精神动力和生命源泉。
顾城的“梦”不仅有着动人的感性力量,也有着鲜明的理性色彩。
那种认为顾城的诗缺乏理性内涵的说法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他表达了“一代人”挣脱黑夜对黎明的向往,历经严寒对春天的期盼,身处社会转型期对新生活、新时代的渴望。
他写冬天,“风的梦”就是打通一条通向南方的道路;他写夏夜,听到“筑路的声音”,“我们相信/所有愉快的梦都能通过/走向黎明”(((我们相信—给姐姐和同代人》)。
“寻梦”主题,在顾城的笔下,就是寻找生命的安身之所,寻找灵魂的温暖巢穴,寻找精神的美丽家园。
“我的梦/是一座城”顾城只有沉浸于他的“梦之城”里,才能找到温暖纯净的抚慰,解放自己倍受现实世界生存原则压抑的心灵,使梦想的非理性激情得以尽情释放。
死亡崇拜:
在顾城的诗歌中,“死亡”是一个贯穿的主题。
有人把顾城的诗学命名为“死亡诗学”,指出他的作品中多次提到死亡,是他对死亡的一种诗意的想象、倾听和试验。
其实,顾城最终的归宿就是回归以“死亡”为旨归的“天国花园”。
“我的家在天上”,“我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那天国的门”是这个终极家园的标语口号。
返观他所建立的“天国花园”,我们可以从他的诗作及诗学中找到大量对死亡崇拜的依据。
十岁的顾城就己经想到了死亡
他在《剪接的自传》中写到:“我开始想到无限和有限、自然和社会、生的意义,开始想到死亡—那扇神秘的门……”,这仅仅是写他十岁时的思想经历,幼小的顾城心里,就有了死亡情结。
他的诗中很早就出现了死亡的字眼。
十七岁时作的《雨》中,就有“让死/来麻醉/我翻滚的心灵”的句子,同年所作的《银河》中,他希望“但愿我们能循着神秘的两岸,一直走向永恒的安息’,,再往后,他的诗中不断出现死亡的意象,任何事物都能引起他对死亡的联想。
嘉陵江上的渡轮,被他描摹为“戴孝的帆船”,船行之后涌起的浪花则是“暗黄的尸布”;“钟摆,它是死神催来丈量生命的”,金字塔,“你是一座坟墓”。
他由惧怕死亡转而品味死亡,而后发展到神化死亡直至颂扬死亡,最终,死亡成为他摆脱不了的宿命,成为他抵御外部与内心矛盾的唯一法宝。
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越来越喜欢这个话题,坚信死亡可以拯救生命,可以解决一切生之悖论,肉体的消失可以换来生命的永恒,死亡是肉体的消失与超越,生即是死,死即是生,大有一种无所谓的达观。
他多次说过:“死亡是没有的”,“死亡是我们的想象,所以它是没有的”。
这种独特的死亡观,使得他看来,生命是抽象
的,不是具体的,是永恒的,不是瞬间的,生活本身是暂时的,而生命是永远的。
顾城用同样的逻辑来理解死亡,对死亡作形而上的想象与赞美。
总之,无论是现实的家乡(土地家园)、山水田园,还是精神上的乌托邦、伊甸园·····一旦渗入艺术家的审美经验,就都具有精神归宿的指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