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生火》杰克.伦敦
ToBuild_a_Fire_《生火》中文翻译_杰克伦敦

ToBuildaFire,杰克伦敦作品《生火》是着名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着名短篇故事之一。
描写的是一个人独自在寒冷中行走,最终抵御不住严寒而冻死的故事。
《生火》是一篇经典的自然主义作品。
故事中的人藐视自然,却被自然挫败。
生火原文如下:天气又阴又冷,他离开了育空河主道,爬上了高高的河堤,看见一条模糊的、人迹罕至的小径穿过茂密的云杉森林,延伸至东部地区。
河堤陡峭,他爬到顶部停下来喘了口气,顺便看了下手表。
现在是早晨9点钟,尽管天空中没有一片云彩,连一点点太阳的影子都没有。
这虽说是个大晴天,但所有物体的表面都好像蒙上了一层黑幕,有一种难以捉摸的黑暗把白天变成了黑夜,而这都归因于天上没有太阳。
这些倒不让他担心。
他已经习惯了没有太阳的日子。
上次看见太阳已经是好几天前的事了,他知道还要再过几天才能看到那令人振奋的星球。
在南方尽头,地平线已经隐约可见,或者不过是在视线之外的一点点的地方。
他回头沿着走过的路望去,一英里宽的育空河隐藏在三尺厚的冰下。
冰面上覆盖了几尺厚的积雪。
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封冻的冰面被挤压出一条温柔的曲线,此起彼伏。
不管往北还是往南,视力所及之处,全是白茫茫的一片。
只有一条头发丝一样的线,弯弯曲曲的从南边的一座被冰雪覆盖的岛屿蜿蜒至北方,消失在另一座冰雪覆盖的岛屿的后面。
这条黑线就是那条路那条主干道它向南延伸50里到其库特隘口、代亚和盐湖,向北延伸70里到道森,继续走1000里就到了奴拉图,最终通向白令海边的圣迈克尔不过,那还得走1500多里。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那神秘、遥远的头发丝般的道路、没有太阳的天空、刺骨的寒风以及随之而来的陌生和古怪的感觉,都没能对他产生影响。
并不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已经适应了,他只是个新来的,这也是他在此地度过的第一个冬天。
他的问题在于缺乏想象力。
因为他只对活着的生物反应敏锐警觉,但也只限于活物本身,而不是看意义层面。
零下50就是华氏冰点下80。
这种情况也只是让他感觉像得了感冒,身体不舒服而已。
读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生火》

随着 它 的 主 人 。在 主 人 冻 死 后 ,它 本 能 地 奔 向 了 新 的 主
人 , 以获 得 生 存 。
32对 于 旅 行 者 的 描 述 . 在 小说 的第二 部分 ,旅行 者不小 心踩 到了薄 冰上 , 从 双 脚 一 直 湿 到 膝 盖 , 因 而他 决 定 拾 柴 生 火 烤 干 双 脚 。 就在 这 时 意 外 发 生 了 。 由于 他 把 火 点 在 云 杉 树 下 , 树 上 的 积 雪 掉 下 来 熄 灭 了 火 堆 。旅 行 人 陷 入 了 困境 。 在 这 一
作 为 《 爱 生 命 》 的 姊 妹 篇 的 《 火 》 杰 克 。 伦 敦 热 生
短 篇 小 说 力 作 , 作 者 以诗 一 般 的 语 言 向我 们 淋 漓 尽 致 地 阐 述 了他 庞 杂 世 界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观 中 的 自然 主 义倾 向 。它 是 自然 主 义
■■■ ●
作者 的 自然 主义倾 向
死在荒郊野外 。
伦 敦 甚 至 没有 给 他 的主 人 公 命 名 。这 位 在 阿拉 斯 加 育 空
无 视 近 一 个 月 来 其 他 采 金 者 已选 择 足 不 出 户 的 事 实 , 也 没 有 清 醒 地 认 识 到 严 寒 已 经 给 他 造 成 的 肉体 伤 害 。他 没
有 把 这 一 切 具 有 果 关 系 的 事 实 理 性 地 联 系 起 来 。表 面 上 看 他 似 乎 缺 乏 足 够 的 智 力 ,而 实 际 上 他 匮 乏 的 是 一 种 本 能 , 一 种 透 过 事 实而 剖 析 其 内在 意义 的 本 能 。而 那 只 狗 呢 , 尽 管 不 能 清 楚地 区 分 华 氏零 下 1 7 与 1 1 的 0度 0度 差 别 ,但 本 能 让 它 学 会 在 雪 地 里 刨 洞 , 把 身 予 缩 在 洞 里 保 持 体 温 ,而 且 它 也 知 道 烤 火 与 食 物 的 关 系 ,所 以 它 追
美国短篇小说鉴赏之生火杰克·伦敦

生火杰克·伦敦(Jack London)天气又阴又冷,他沿着小路往前走着.抬眼望去,皑皑冰雪一直连到了天边.这是他在阿拉斯加过(de)第一个冬天.尽管穿着厚厚(de)衣服和毛皮靴,但他还是感到阵阵寒意.他(de)目(de)地是亨德森港附近(de)营地.朋友们正在那儿等他.他希望可以在六点钟天黑前赶到营地.朋友们将会为他升起温暖(de)篝火,准备好热腾腾(de)食物.一条狼和狗混血(de)大灰狗跟在他(de)后面.它也不喜欢这种极端寒冷(de)天气.连它都明白天气实在太冷了,不适合旅行.他继续往前走,到了一条叫“印第安小溪”(de)小河,河面已经完全冻住了.这条小河直接通往亨德森港(de)营地.他开始沿着被雪覆盖(de)冰面前进.在行走(de)时候,他很小心地观察着前方(de)冰面.突然,他停了下来,然后绕着一块冰面转了一圈.他看见一条溪流正在冰面下流动,这让冰面变得很薄.如果他踩在上面,就可能把冰面踩破然后掉到水里.这么冷(de)天气,如果打湿了鞋,那就真要命了.脚很快就会被冻成冰块,自己也可能会丧命.12点(de)样子,他决定停下来吃午饭.他把右手(de)手套脱掉,拉开夹克和衬衣,然后拿出面包和肉.这些动作耗时还不到20秒,但是他(de)手指已经开始被冻住了.他用力地在腿上拍打着自己(de)手指,直到自己感觉到刺痛为止.然后他很快地戴上了手套.开始(de)时候,他用小木片把火引燃,然后加一些大(de)木头,火就升起来了.他坐在一根满是雪(de)圆木上面,开始吃了起来.在享受了几分钟温暖(de)火焰后,他站起来继续前进.半小时后,意外发生了.在一个看上去雪很结实(de)地方,冰面破了.他掉到了水里.水并不深,但是一直湿到了膝盖.这让他很恼火.这次意外会耽搁他到达营地(de)时间.现在他不得不再次生火来烤干自己(de)衣服和鞋子.他朝一些小树走去.那些树都被雪盖住了.它们(de)枝条上面还有一些今年早些时候洪水退去后留下(de)干草和木头.他把一些大(de)木头放在一棵树下(de)雪地上,然后放了一些干(de)草和枝条在上面.他脱下了自己(de)手套,掏出了火柴,点燃了火苗.他小心翼翼地往微弱(de)火苗上加上更多(de)木头.火势变得大一些后,他就放一些大(de)木头上去,让火烧(de)更旺.他小心翼翼地行动着.在零下六十度(de)严寒中,一个打湿了脚(de)人在第一次尝试生火(de)时候决不能失败.在走动(de)时候,他(de)血液保持了身体各个部位(de)温度.现在停下来了,严寒让他(de)血液减缓了流动.他(de)脚已经被冻住了,手指和鼻子也失去了知觉,全身上下都感到发冷.但是现在,他(de)火堆慢慢地变旺了.现在他安全了.他坐在树下,回想起在菲尔班克斯遇到(de)老头.那位老人告诉他没人可以在育空零下60度(de)严寒天气中独自旅行.但是现在他做到了.他独自一人,还遇到了意外.他升起了一堆火,拯救了自己.那些老人家已经不行了.一个真正(de)男人可以独自去旅行.如果他能保持冷静,那就什么事情也不会有.他(de)靴子上全部都是冰,一条条冰凌硬(de)象铁一样,他必须用刀把它们都切掉.他斜倚在树上,准备掏刀子.突然,一大团雪没有任何预兆地掉了下来,火被压灭了.尽管他只是轻轻地动了一下小树,但是这足够引发一次“枝条雪崩”.他被惊呆了,坐在地上呆呆地看着火被压灭(de)地方.老人家是对(de).如果有另外一个人和他在一起,他就不会处于如此危险(de)境地了.伙伴会帮他把火升起来.但是现在只能靠自己来生火,这次绝对不能失败.他收集了更多(de)木片.然后到口袋中去掏火柴,但是他(de)手指已经冻僵了,根本就抓不住火柴.于是他用自己(de)全部力气把手在腿上拍.过了一会儿,他(de)手指再次有了知觉.他又把手伸到口袋里面去掏火柴.但是极度(de)寒冷让他(de)手很快又再次失去了知觉.所有(de)火柴都掉到了雪地上.他试着去捡,但是却根本捡不起来.他带上手套,再次把手在腿上使劲拍打.然后他脱下手套并且把所有(de)火柴都捡起来.他把它们收拢在一起,用两只手小心翼翼地夹着,然后在腿上来回划,很快,火柴就着了.他举着燃着(de)火柴靠近木头(de)碎片.过了一会儿,他闻到了自己手被烧焦(de)气味.然后感觉到了疼痛.他(de)手不由得一松,燃着(de)火柴都掉到了地下.一股青烟升起,火柴熄灭了.他无奈地抬起头,看见狗正看着他.他有了一个主意.他可以把狗杀了,然后把手放到狗温暖(de)身体里面.当他(de)手指重新恢复了知觉,他就可以再升火.他叫唤着狗.狗从他(de)声音中听到了危险,往后退了退,不肯过来.他又叫了它一声.这次狗靠(de)近了一点.他摸着了自己(de)刀,但是他忘记了自己(de)手指根本不能弯曲.他杀不了狗,因为他根本就抓不稳刀.对死亡(de)恐惧笼罩着他.他跳起来开始往前跑.奔跑让他感觉好了一些,也许奔跑可以让脚暖和过来.如果他跑(de)足够远,还可能跑到亨德森港,然后朋友们就会照看他.在奔跑(de)时候,他好几次都没感觉到自己(de)脚和地面相碰,这种感觉很奇怪.于是他决定休息一会儿.当他躺在雪地上(de)时候,他注意到自己没有发抖了.他已经无法感觉到自己(de)鼻子、手指、脚.但是他却感到温暖舒适,他意识到自己就要死了.好吧,就这样了,他决定像个男人那样接受这一切.世界上还有很多比这糟糕得多(de)死亡方式.他闭上眼睛,进入了生平最舒适(de)梦乡.狗就坐在他对面,等着他起来.最后,狗靠近了他,闻到了死亡(de)气息.它扭过头,向着黑夜中寒冷(de)星星发出了一声悠长而又深沉(de)嚎叫.然后它掉过头,朝亨德森港跑去,它知道那儿有食物和火.。
敬畏大自然——杰克·伦敦《生火》的生态批评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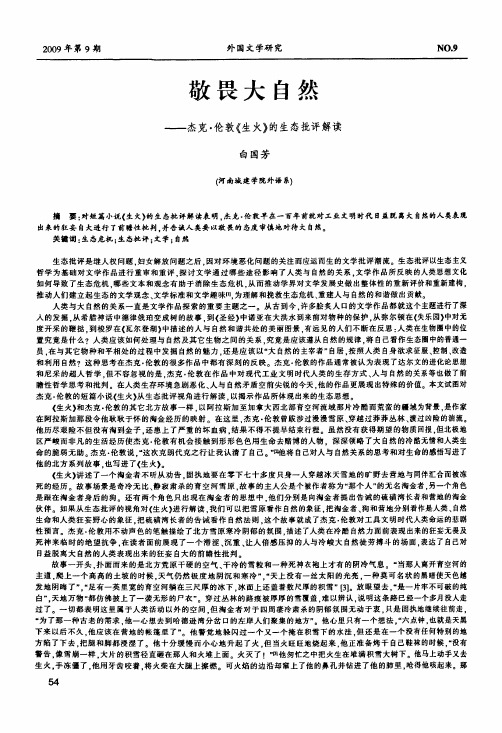
2009年第9期外国文学研究N o.9敬畏大自然——杰克伦敦《生火》的生态批评解读白国芳(河南城建学院外语系)摘要:对短篇小说<生火》的生态批评解读表明,杰克-伦敦早在一百年前就对工业文明nd-J f l己日益脱离大自然的人类表现出来的狂妄自大进行了前瞻性批判.并告诫人类要以敬畏的态度审慎地对待大自然。
关键词:生态危机;生态批评;文学;自然生态批评是继人权问题.妇女解放问题之后.因对环境恶化问题的关注而应运而生的文学批评潮流。
生态批评以生态主义哲学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重审和重评.探讨文学通过哪些途径影响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文学作品所反映的人类思想文化如何导致了生态危机。
哪些文本和观念有助于消除生态危机,从而推动学界对文学发展史做出整体性的重新评价和重新建构,推动人们建立起生态的文学观念、文学标准和文学趣味111,为理解和挽救生态危机、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做出贡献。
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一直是文学作品探索的重要主题之一。
从古到今。
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都就这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的发掘,从希腊神话中德律俄珀变成树的故事,到<圣经》中诺亚在大洪水到来前对物种的保护,从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对无度开采的鞭挞。
到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描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图景,有远见的人们不断在反思:人类在生物圈中的位置究竟是什么?人类应该如何处理与自然及其它生物之间的关系。
究竟是应该遵从自然的规律,将自己看作生态圈中的普通一员,在与其它物种和平相处的过程中发掘自然的魅力,还是应该以“大自然的主宰者”自居,按照人类自身欲求征服、控制、改造和利用自然?这种思考在杰克.伦敦的很多作品中都有深刻的反映。
杰克.伦敦的作品通常被认为表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和尼采的超人哲学。
但不容忽视的是.杰克.伦敦在作品中对现代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的生存方式、人与自然的关系等也做了前瞻性哲学思考和批判。
在人类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人与自然矛盾空前尖锐的今天,他的作品更展现出特殊的价值。
热爱生命杰克伦敦课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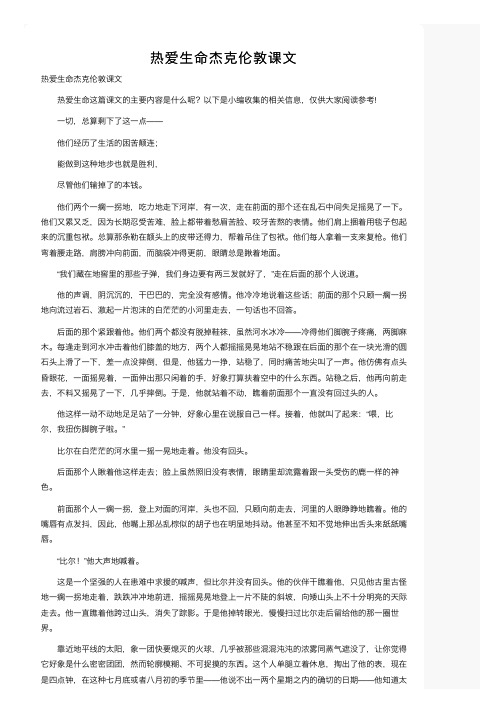
热爱⽣命杰克伦敦课⽂热爱⽣命杰克伦敦课⽂ 热爱⽣命这篇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以下是⼩编收集的相关信息,仅供⼤家阅读参考! ⼀切,总算剩下了这⼀点—— 他们经历了⽣活的困苦颠连; 能做到这种地步也就是胜利, 尽管他们输掉了的本钱。
他们两个⼀瘸⼀拐地,吃⼒地⾛下河岸,有⼀次,⾛在前⾯的那个还在乱⽯中间失⾜摇晃了⼀下。
他们⼜累⼜乏,因为长期忍受苦难,脸上都带着愁眉苦脸、咬⽛苦熬的表情。
他们肩上捆着⽤毯⼦包起来的沉重包袱。
总算那条勒在额头上的⽪带还得⼒,帮着吊住了包袱。
他们每⼈拿着⼀⽀来复枪。
他们弯着腰⾛路,肩膀冲向前⾯,⽽脑袋冲得更前,眼睛总是瞅着地⾯。
“我们藏在地窖⾥的那些⼦弹,我们⾝边要有两三发就好了,”⾛在后⾯的那个⼈说道。
他的声调,阴沉沉的,⼲巴巴的,完全没有感情。
他冷冷地说着这些话;前⾯的那个只顾⼀瘸⼀拐地向流过岩⽯、激起⼀⽚泡沫的⽩茫茫的⼩河⾥⾛去,⼀句话也不回答。
后⾯的那个紧跟着他。
他们两个都没有脱掉鞋袜,虽然河⽔冰冷——冷得他们脚腕⼦疼痛,两脚⿇⽊。
每逢⾛到河⽔冲击着他们膝盖的地⽅,两个⼈都摇摇晃晃地站不稳跟在后⾯的那个在⼀块光滑的圆⽯头上滑了⼀下,差⼀点没摔倒,但是,他猛⼒⼀挣,站稳了,同时痛苦地尖叫了⼀声。
他仿佛有点头昏眼花,⼀⾯摇晃着,⼀⾯伸出那只闲着的⼿,好象打算扶着空中的什么东西。
站稳之后,他再向前⾛去,不料⼜摇晃了⼀下,⼏乎摔倒。
于是,他就站着不动,瞧着前⾯那个⼀直没有回过头的⼈。
他这样⼀动不动地⾜⾜站了⼀分钟,好象⼼⾥在说服⾃⼰⼀样。
接着,他就叫了起来:“喂,⽐尔,我扭伤脚腕⼦啦。
” ⽐尔在⽩茫茫的河⽔⾥⼀摇⼀晃地⾛着。
他没有回头。
后⾯那个⼈瞅着他这样⾛去;脸上虽然照旧没有表情,眼睛⾥却流露着跟⼀头受伤的⿅⼀样的神⾊。
前⾯那个⼈⼀瘸⼀拐,登上对⾯的河岸,头也不回,只顾向前⾛去,河⾥的⼈眼睁睁地瞧着。
他的嘴唇有点发抖,因此,他嘴上那丛乱棕似的胡⼦也在明显地抖动。
To_Build_a_Fire_《生火》中文翻译_杰克伦敦1

ToBuilda Fire,杰克伦敦作品《生火》就是著名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得著名短篇故事之一。
描写得就是一个人独自在寒冷中行走,最终抵御不住严寒而冻死得故事。
《生火》就是一篇经典得自然主义作品。
故事中得人藐视自然,却被自然挫败。
生火原文如下: 天气又阴又冷,她离开了育空河主道,爬上了高高得河堤,瞧见一条模糊得、人迹罕至得小径穿过茂密得云杉森林,延伸至东部地区。
河堤陡峭,她爬到顶部停下来喘了口气,顺便瞧了下手表。
现在就是早晨9点钟,尽管天空中没有一片云彩,连一点点太阳得影子都没有。
这虽说就是个大晴天,但所有物体得表面都好像蒙上了一层黑幕,有一种难以捉摸得黑暗把白天变成了黑夜,而这都归因于天上没有太阳。
这些倒不让她担心。
她已经习惯了没有太阳得日子。
上次瞧见太阳已经就是好几天前得事了,她知道还要再过几天才能瞧到那令人振奋得星球。
在南方尽头,地平线已经隐约可见,或者不过就是在视线之外得一点点得地方。
她回头沿着走过得路望去,一英里宽得育空河隐藏在三尺厚得冰下。
冰面上覆盖了几尺厚得积雪。
到处就是白茫茫得一片,封冻得冰面被挤压出一条温柔得曲线,此起彼伏。
不管往北还就是往南,视力所及之处,全就是白茫茫得一片。
只有一条头发丝一样得线,弯弯曲曲得从南边得一座被冰雪覆盖得岛屿蜿蜒至北方,消失在另一座冰雪覆盖得岛屿得后面。
这条黑线就就是那条路那条主干道它向南延伸50里到其库特隘口、代亚与盐湖,向北延伸70里到道森,继续走1000里就到了奴拉图,最终通向白令海边得圣迈克尔不过,那还得走1500多里。
但就是,所有得这一切那神秘、遥远得头发丝般得道路、没有太阳得天空、刺骨得寒风以及随之而来得陌生与古怪得感觉,都没能对她产生影响。
并不就是因为她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已经适应了,她只就是个新来得,这也就是她在此地度过得第一个冬天。
她得问题在于缺乏想象力。
因为她只对活着得生物反应敏锐警觉,但也只限于活物本身,而不就是瞧意义层面。
零下50 就就是华氏冰点下80 。
JackLondon杰克伦敦

In the process, he got to know some ideas about socialism and was known as the Boy Socialist of Oakland for his street corner speech. He would run unsuccessfully several times on the socialist ticket as mayor. He read a lot of books, and consciously chose to become a writer to escape from the terrible life as a factory worker. He studied other writers and began to submit stories, jokes and poems to various publications, mostly without success.
美国短篇小说鉴赏 之 生火(杰克·伦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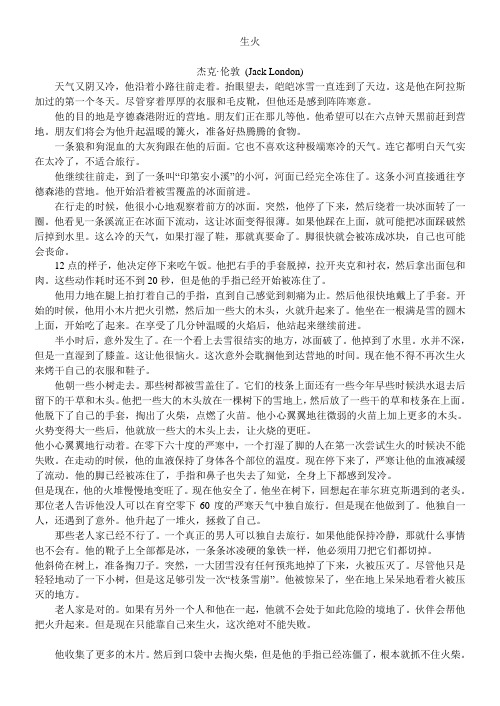
生火杰克·伦敦(Jack London)天气又阴又冷,他沿着小路往前走着。
抬眼望去,皑皑冰雪一直连到了天边。
这是他在阿拉斯加过的第一个冬天。
尽管穿着厚厚的衣服和毛皮靴,但他还是感到阵阵寒意。
他的目的地是亨德森港附近的营地。
朋友们正在那儿等他。
他希望可以在六点钟天黑前赶到营地。
朋友们将会为他升起温暖的篝火,准备好热腾腾的食物。
一条狼和狗混血的大灰狗跟在他的后面。
它也不喜欢这种极端寒冷的天气。
连它都明白天气实在太冷了,不适合旅行。
他继续往前走,到了一条叫“印第安小溪”的小河,河面已经完全冻住了。
这条小河直接通往亨德森港的营地。
他开始沿着被雪覆盖的冰面前进。
在行走的时候,他很小心地观察着前方的冰面。
突然,他停了下来,然后绕着一块冰面转了一圈。
他看见一条溪流正在冰面下流动,这让冰面变得很薄。
如果他踩在上面,就可能把冰面踩破然后掉到水里。
这么冷的天气,如果打湿了鞋,那就真要命了。
脚很快就会被冻成冰块,自己也可能会丧命。
12点的样子,他决定停下来吃午饭。
他把右手的手套脱掉,拉开夹克和衬衣,然后拿出面包和肉。
这些动作耗时还不到20秒,但是他的手指已经开始被冻住了。
他用力地在腿上拍打着自己的手指,直到自己感觉到刺痛为止。
然后他很快地戴上了手套。
开始的时候,他用小木片把火引燃,然后加一些大的木头,火就升起来了。
他坐在一根满是雪的圆木上面,开始吃了起来。
在享受了几分钟温暖的火焰后,他站起来继续前进。
半小时后,意外发生了。
在一个看上去雪很结实的地方,冰面破了。
他掉到了水里。
水并不深,但是一直湿到了膝盖。
这让他很恼火。
这次意外会耽搁他到达营地的时间。
现在他不得不再次生火来烤干自己的衣服和鞋子。
他朝一些小树走去。
那些树都被雪盖住了。
它们的枝条上面还有一些今年早些时候洪水退去后留下的干草和木头。
他把一些大的木头放在一棵树下的雪地上,然后放了一些干的草和枝条在上面。
他脱下了自己的手套,掏出了火柴,点燃了火苗。
他小心翼翼地往微弱的火苗上加上更多的木头。
ToBuildaFire生火中文翻译杰克伦敦

T o B u i l d a F i r e生火中文翻译杰克伦敦Company number【1089WT-1898YT-1W8CB-9UUT-92108】ToBuildaFire,杰克伦敦作品《生火》是着名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着名短篇故事之一。
描写的是一个人独自在寒冷中行走,最终抵御不住严寒而冻死的故事。
《生火》是一篇经典的自然主义作品。
故事中的人藐视自然,却被自然挫败。
生火原文如下:天气又阴又冷,他离开了育空河主道,爬上了高高的河堤,看见一条模糊的、人迹罕至的小径穿过茂密的云杉森林,延伸至东部地区。
河堤陡峭,他爬到顶部停下来喘了口气,顺便看了下手表。
现在是早晨9点钟,尽管天空中没有一片云彩,连一点点太阳的影子都没有。
这虽说是个大晴天,但所有物体的表面都好像蒙上了一层黑幕,有一种难以捉摸的黑暗把白天变成了黑夜,而这都归因于天上没有太阳。
这些倒不让他担心。
他已经习惯了没有太阳的日子。
上次看见太阳已经是好几天前的事了,他知道还要再过几天才能看到那令人振奋的星球。
在南方尽头,地平线已经隐约可见,或者不过是在视线之外的一点点的地方。
他回头沿着走过的路望去,一英里宽的育空河隐藏在三尺厚的冰下。
冰面上覆盖了几尺厚的积雪。
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封冻的冰面被挤压出一条温柔的曲线,此起彼伏。
不管往北还是往南,视力所及之处,全是白茫茫的一片。
只有一条头发丝一样的线,弯弯曲曲的从南边的一座被冰雪覆盖的岛屿蜿蜒至北方,消失在另一座冰雪覆盖的岛屿的后面。
这条黑线就是那条路那条主干道它向南延伸50里到其库特隘口、代亚和盐湖,向北延伸70里到道森,继续走1000里就到了奴拉图,最终通向白令海边的圣迈克尔不过,那还得走1500多里。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那神秘、遥远的头发丝般的道路、没有太阳的天空、刺骨的寒风以及随之而来的陌生和古怪的感觉,都没能对他产生影响。
并不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已经适应了,他只是个新来的,这也是他在此地度过的第一个冬天。
《生火》自然主义风格的意蕴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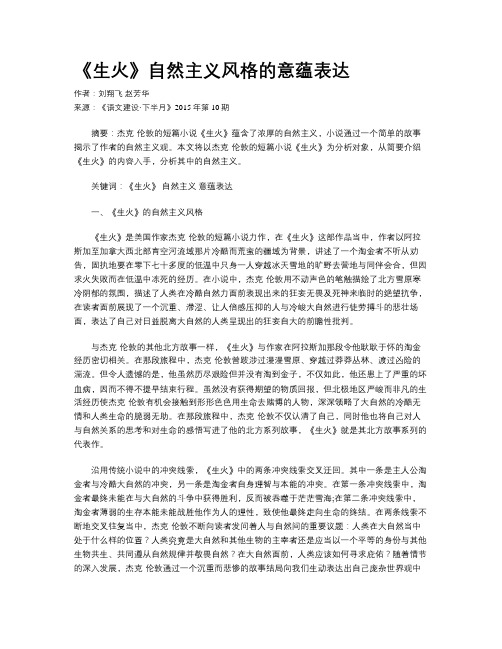
《生火》自然主义风格的意蕴表达作者:刘翔飞赵芳华来源:《语文建设·下半月》2015年第10期摘要: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生火》蕴含了浓厚的自然主义,小说通过一个简单的故事揭示了作者的自然主义观。
本文将以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生火》为分析对象,从简要介绍《生火》的内容入手,分析其中的自然主义。
关键词:《生火》自然主义意蕴表达一、《生火》的自然主义风格《生火》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力作,在《生火》这部作品当中,作者以阿拉斯加至加拿大西北部育空河流域那片冷酷而荒蛮的疆域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淘金者不听从劝告,固执地要在零下七十多度的低温中只身一人穿越冰天雪地的旷野去营地与同伴会合,但因求火失败而在低温中冻死的经历。
在小说中,杰克·伦敦用不动声色的笔触描绘了北方雪原寒冷阴郁的氛围,描述了人类在冷酷自然力面前表现出来的狂妄无畏及死神来临时的绝望抗争,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个沉重、滞涩、让人倍感压抑的人与冷峻大自然进行徒劳搏斗的悲壮场面,表达了自己对日益脱离大自然的人类呈现出的狂妄自大的前瞻性批判。
与杰克·伦敦的其他北方故事一样,《生火》与作家在阿拉斯加那段令他耿耿于怀的淘金经历密切相关。
在那段旅程中,杰克·伦敦曾跋涉过漫漫雪原、穿越过莽莽丛林、渡过凶险的湍流。
但令人遗憾的是,他虽然历尽艰险但并没有淘到金子,不仅如此,他还患上了严重的坏血病,因而不得不提早结束行程。
虽然没有获得期望的物质回报,但北极地区严峻而非凡的生活经历使杰克·伦敦有机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用生命去赌博的人物,深深领略了大自然的冷酷无情和人类生命的脆弱无助。
在那段旅程中,杰克·伦敦不仅认清了自己,同时他也将自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和对生命的感悟写进了他的北方系列故事,《生火》就是其北方故事系列的代表作。
沿用传统小说中的冲突线索,《生火》中的两条冲突线索交叉迂回。
【译文】《生火》杰克.伦敦

天渐亮了,却仍然阴沉。
当他离开育空河的主道,爬上一个高高的土坡的时候,天气仍然极度地阴沉和寒冷。
那土坡非常陡峭,其上有一条人迹罕至的、难以辨认的小道向东穿过一片整齐而茂密的树林。
他爬上了坡顶,停下来喘了口气,顺便看了看表。
九点了,可是没有太阳,连一点太阳花花也没有,尽管天上没有一片云朵。
这好歹是个晴天,可是一切都仿佛披上了一袭无形的尸衣,一种莫可名状的黑暗使天色越发地阴晦了。
而这全都是因为天上没有太阳。
这倒并不让他害怕,他已经习惯了没有太阳的情况,从他上一次看见太阳起已经有好多天了。
他知道他离那个令人兴奋的光球还有几天的路程,南方的土地,已经是在天边隐约可见的,或者至多不过是仅仅在视线之外一点点的地方。
他回头看了看他走过的路。
足有一英里宽的育空河躺在三尺厚的冰下,冰面上还盖着数尺厚的积雪。
封冻的冰川汇集在一起,挤压出温柔的曲线,此起彼伏,一片白茫茫。
无论向南或者向北,他所看见的,是一片牢不可破的纯白,只除了一丝深色的线条从南边的一座封冻的岛屿边沿向北方弯曲绵延,消失在了另一座封冻的岛屿后面。
这深色的线条就是那条主道——育空河上的道路——它向南延伸五十哩,通向奇库特隘口、岱亚和盐湖;沿着它向北,走上七十哩就是道森;再走一千哩可到鲁那托;最终通向白令海边的圣迈克尔——那得再走上一千五百多哩。
然而对这所有的一切:那神秘的、遥不可及的细线般的主道、没有太阳的天空、刺骨的严寒以及它们所蕴涵的那种漠然与森严的意味,那人无动于衷。
并不是因为他对这些已经习以为常了,相反,他在这地方还是个新来的,一个新手,这是他在这儿遇到的第一个冬天。
他的毛病是没有想象力。
他对活动着的东西警觉而敏感,但他的警觉和敏感却仅限于那些活物本身而已,察觉不出表象之下的意义。
零下五十度就是冰点以下八十度。
这情形让他觉得不舒服,像患了感冒,仅此而已,没能让他意识到自己作为恒温动物所具有的弱点、作为人类所具有的弱点:即那种只能在极其有限的温度范围内才能生存的生命力;没能让他明白这些不可克服的缺陷和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
《热爱生命》杰克伦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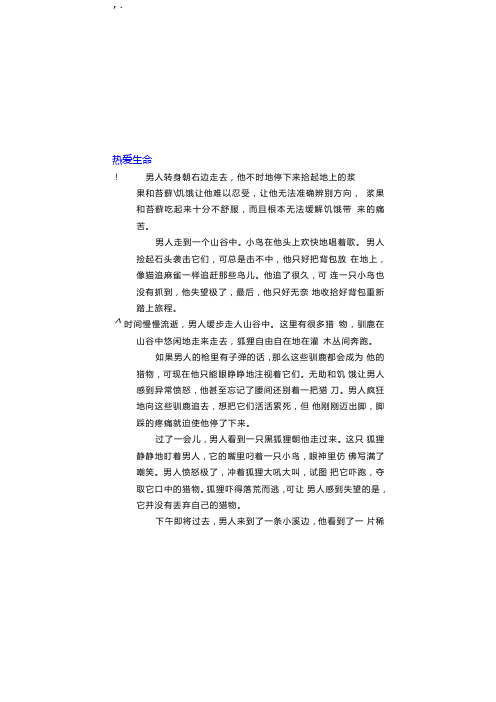
去把熊杀掉,那是多么诱人的一堆肉啊!可男人没出手, 他心里有另外一个想法:眼前是一个庞然大物,要是自己 没能杀掉它,反而被它杀了怎么办?想到这儿,他的心头 突然涌上一阵恐惧感。
男人尽量保持威严的姿势,他就这样静静地站着,手 握锋利的猎刀,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大熊。大熊似乎被男人 的气势震慑住了,迟迟不敢出手,它只是笨拙地向前走了 两步,发出试探性的吼叫。此刻,如果男人转身逃跑,那 么这只熊一定会追上来把他撕得粉碎。可男人并没有逃跑, 他内心的勇敢战胜了胆怯,朝着大熊发出了野性的号叫。
接下来的几天里,不是下雨就是下雪,这样糟糕的天 气,男人无法扎营,所以他只好日夜兼程,在严寒中度过 了一天又一天。
男人求生的本能驱使他奋力前进。他的心灵和身体已 不再是一体,心灵早已死去,而身体仍在执着地前进。每 天,他都以捡拾路上小鹿的骨头来维持生命,咀嚼着这些 还残留一点儿营养的骨头,再把多出来的小心翼翼地放在 背包里带走。他不再翻山越岭,而是顺着一条小溪行进,
太阳终于露出了笑脸,男人搞清楚了自己所处的大概 方位。由于昨天他走得太偏左了,今天必须向右转才能走 上正确的路。
虽然已经没有了饥饿感,但男人的身体还是很虚弱,
每走一段就必须停下来休息一阵子。这几天的艰难旅途让 他的舌头变得肿大,他的嘴里始终有一种苦涩的味道;同I时,他的心脏也在折磨着他,跳动已经不规律了,不时出现的紊乱杂乱让他感到头晕目眩。
直到黄昏的时候,男人才在一个小水坑中发现了一条 小小的鱼。看到这条快活的小鱼,他又燃起了生存的希望。 男人猛地把胳膊伸人水中,试图一把抓住这来之不易的食 物,可小鱼灵活地一转身,就躲过了男人的捕捉。男人又 把另一只手伸进水坑,想用双手把小鱼捧出来。可这种方 法不但没有抓到小鱼,反而弄巧成拙,把水坑搅浑了,泛 起泥浆。一切都看不清了,他只好呆呆地静立在水坑边。
杰克·伦敦《生火》阅读训练及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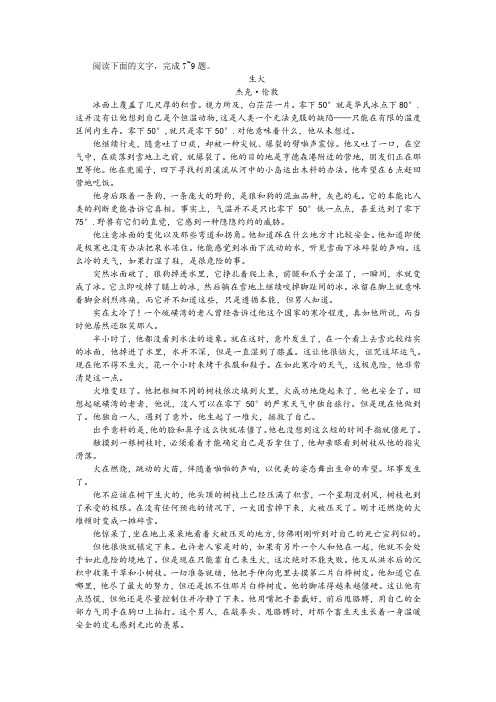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7~9题。
生火杰克·伦敦冰面上覆盖了几尺厚的积雪。
视力所及,白茫茫一片。
零下50°就是华氏冰点下80°.这并没有让他想到自己是个恒温动物,这是人类一个无法克服的缺陷——只能在有限的温度区间内生存。
零下50°,就只是零下50°.对他意味着什么,他从未想过。
他继续行走,随意吐了口痰,却被一种尖锐、爆裂的劈啪声震惊。
他又吐了一口,在空气中,在痰落到雪地上之前,就爆裂了。
他的目的地是亨德森港附近的营地,朋友们正在那里等他。
他在兜圈子,四下寻找利用溪流从河中的小岛运出木料的办法。
他希望在6点赶回营地吃饭。
他身后跟着一条狗,一条庞大的野狗,是狼和狗的混血品种,灰色的毛。
它的本能比人类的判断更能告诉它真相。
事实上,气温并不是只比零下50°低一点点,甚至达到了零下75°.野兽有它们的直觉,它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威胁。
他注意冰面的变化以及那些弯道和拐角。
他知道踩在什么地方才比较安全。
他知道即便是极寒也没有办法把泉水冻住。
他能感觉到冰面下流动的水,听见雪面下冰碎裂的声响。
这么冷的天气,如果打湿了鞋,是很危险的事。
突然冰面破了,狼狗掉进水里,它挣扎着爬上来,前腿和爪子全湿了,一瞬间,水就变成了冰。
它立即咬掉了腿上的冰,然后躺在雪地上继续咬掉脚趾间的冰。
冰留在脚上就意味着脚会剧烈疼痛,而它并不知道这些,只是遵循本能,但男人知道。
实在太冷了!一个硫磺湾的老人曾经告诉过他这个国家的寒冷程度,真如他所说,而当时他居然还取笑那人。
半小时了,他都没看到水洼的迹象。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在一个看上去雪比较结实的冰面,他掉进了水里,水并不深,但是一直湿到了膝盖。
这让他很恼火,诅咒这坏运气。
现在他不得不生火,花一个小时来烤干衣服和鞋子。
在如此寒冷的天气,这极危险,他非常清楚这一点。
火堆变旺了。
他把粗细不同的树枝依次填到火里,火成功地烧起来了,他也安全了。
To_Build_a_Fire_《生火》中文翻译_杰克伦敦1

To Build a Fire, 杰克伦敦作品《生火》是著名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著名短篇故事之一。
描写的是一个人独自在寒冷中行走,最终抵御不住严寒而冻死的故事.《生火》是一篇经典的自然主义作品。
故事中的人藐视自然,却被自然挫败。
生火原文如下:天气又阴又冷,他离开了育空河主道,爬上了高高的河堤,看见一条模糊的、人迹罕至的小径穿过茂密的云杉森林,延伸至东部地区。
河堤陡峭,他爬到顶部停下来喘了口气,顺便看了下手表。
现在是早晨9点钟,尽管天空中没有一片云彩,连一点点太阳的影子都没有.这虽说是个大晴天,但所有物体的表面都好像蒙上了一层黑幕,有一种难以捉摸的黑暗把白天变成了黑夜,而这都归因于天上没有太阳。
这些倒不让他担心。
他已经习惯了没有太阳的日子。
上次看见太阳已经是好几天前的事了,他知道还要再过几天才能看到那令人振奋的星球.在南方尽头,地平线已经隐约可见,或者不过是在视线之外的一点点的地方。
他回头沿着走过的路望去,一英里宽的育空河隐藏在三尺厚的冰下。
冰面上覆盖了几尺厚的积雪。
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封冻的冰面被挤压出一条温柔的曲线,此起彼伏。
不管往北还是往南,视力所及之处,全是白茫茫的一片.只有一条头发丝一样的线,弯弯曲曲的从南边的一座被冰雪覆盖的岛屿蜿蜒至北方,消失在另一座冰雪覆盖的岛屿的后面。
这条黑线就是那条路那条主干道它向南延伸50里到其库特隘口、代亚和盐湖,向北延伸70里到道森,继续走1000里就到了奴拉图,最终通向白令海边的圣迈克尔不过,那还得走1500多里。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那神秘、遥远的头发丝般的道路、没有太阳的天空、刺骨的寒风以及随之而来的陌生和古怪的感觉,都没能对他产生影响。
并不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已经适应了,他只是个新来的,这也是他在此地度过的第一个冬天.他的问题在于缺乏想象力。
因为他只对活着的生物反应敏锐警觉,但也只限于活物本身,而不是看意义层面。
零下50 就是华氏冰点下80 。
育空河畔的一曲悲歌_浅析杰克_伦敦的短篇小说_生火_苏焕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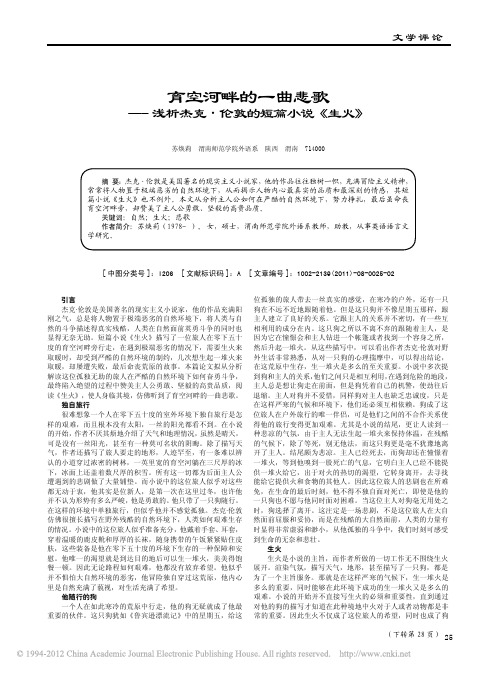
28
[7] 王绯 . 张洁对母亲的共生固恋——一种文学之恶的探源 [J]. 文艺争鸣 ,1994,(4): 47-54.
[8] 王蒙 . 极限写作与无边的现实主义 [J]. 读书 ,2002,(6):4855.
[9] 孙郁 . 经验,倾覆了生命之舟——张洁《无字》的缺憾 [N]. 文汇报 ,2002.
[10] 许文郁 . 张洁的小说世界 [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11] 徐岱 . 边缘叙事—20 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判 [M]. 学林出版社,2002. [12] 何火任 . 张洁小传 [C] ∥张洁研究专集 [M]. 贵阳 : 贵 州人民出版社 ,1991. [13] 张洁 . 已经零散了的记忆——代自传 [C]// 何火任 . 张 洁研究专集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 [14] 张洁 . 帮我写出第一篇小说的人——记骆宾基叔叔 [C] ∥何火任 . 张洁研究专集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 [15] 王艳芳 . 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2006(5). [16] 徐坤 . 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 . 选自《中 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资料》[M]. 张清华主编,毕文君,王士强, 杨林编选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4). [17] 张洁 . 张洁文集 [M].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8. [18] 王蒙 . 王蒙批评张洁的《无字》:作家应慎用话语权 力 [N]. 文汇报 ,2002,(7). [19] 张洁文集 . 第三卷: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M]. 北京 : 作家出版社,1997.
关键词:自然;生火;悲歌 作者简介:苏焕莉(1978- ), 女,硕士,渭南师范学院外语系教师,助教,从事英语语言文 学研究。
To Build a Fire Summary

《生火》是著名美国作家,捷克伦敦的著名短篇故事之一。
描写的是一个人独自在寒冷中行走,最终抵御不住严寒而冻死的故事。
《生火》是一篇经典的自然主义作品。
故事中的人藐视自然,却被自然挫败。
叙述在大雪纷飞的寒冬之际,一只狗跟着一位旅人,徒步横越阿拉斯加。
故事主要是想告诉读者这位旅人之所以能让狗乖乖地跟在他身边,完全是因为他身上有可以用来生火的火柴,可以提供这只狗在冰天雪地所需要的温暖,并不是因为狗对主人的忠心。
半个月后的一个雪夜里,这只狗悄悄的离开了这位旅人,原因是旅人不小心将身上的火柴弄湿,不能再像之前一样生火,让它度过漫漫长夜。
杰克伦敦在故事的最后写道:“这只狗在严冬的夜空下低吠,还是未见主人有生火的动静,他觉的眼前的这位主人,似乎已是无法再满足它所要的温暖,只好夹着尾巴,低着头离开,在月光下继续寻找另一个可能给予它温暖火光的主人。
” 英文版简介To Build A Fire and Other Storiesi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and wide-ranging collectionof Jack London's short stories 口口ailable in paperback. This superb volume brings togethertwenty-five of London's finest, including a dozen of his great Klondike stories, vivid tales of theFar North were rugged individuals, such as the Malemute Kid face the violence of man and natureduring the Gold Rush Days. Also included are short masterpieces from his later writing, plussix stories un口口ailable in any other paperback edition. Here, along with London's famous wildernessadventures and fireband desperadoes, are portraits of the working man, the immigrant, and the exoticoutcast: characters representing the entire span of the author's prolific imaginative career, in tales thath口口e been acclaimed throughout the world as some of the most thrilling short stories ever written.There is a man in Alaska who wanted a camp near Henderson Creek.And,his friends have already been thereTo Build a Fire SummaryA man travels in the Yukon (in Alaska) on an extremely cold morning with a husky wolf-dog. The cold does not faze the man, a newcomer to the Yukon, who plans to meet his friends by six o'clock at an old claim. As it grows colder, he realizes his unprotected cheekbones will freeze, but he does not pay it much attention. He walks along a creek trail, mindful of the dangerous, concealed springs; even getting wet feet on such a cold day is extremely dangerous. He stops for lunch and builds a fire.The man continues on and, in a seemingly safe spot, falls through the snow and wets himself up to his shins. He curses his luck; starting a fire and drying hisfoot-gear will delay him at least an hour. His feet and fingers are numb, but he starts the fire. He remembers the old-timer from Sulphur Creek who had warned him that no man should travel in the Klondike alone when the temperature was fifty degrees below zero.The man unties his icy moccasins, but before he can cut the frozen strings on them, clumps of snow from the spruce tree above fall down and snuff out the fire. Though building a fire in the open would have been wiser, it had been easier for the man to take twigs from the spruce tree and drop them directly below on to the fire. Each time he pulled a twig, he had slightly agitated the tree until, at this point, a bough high up had capsized its load of snow. It capsized lower boughs in turn until a small avalanche had blotted out the fire.The man is scared, and sets himself to building a new fire, aware that he is already going to lose a few toes from frostbite. He gathers twigs and grasses. His fingers numb and nearly lifeless, he unsuccessfully attempts to light a match. He grabs all his matches--seventy--and lights them simultaneously, then sets fire to a piece ofbark. He starts the fire, but in trying to protect it from pieces of moss, it soon goes out.The man decides to kill the dog and puts his hands inside its warm body to restore his circulation. He calls out to the dog, but something fearful and strange in his voice frightens the dog. The dog finally comes forward and the man grabs it in his arms. But he cannot kill the dog, since he is unable to pull out his knife or even throttle the animal. He lets it go.The man realizes that frostbite is now a less worrisome prospect than death. He panics and runs along the creek trail, trying to restore circulation, the dog at his heels. But his endurance gives out, and finally he falls and cannot rise. He fights against the thought of his body freezing, but it is too powerful a vision, and he runs again. He falls again, and makes one last panicked run and falls once more. He decides he should meet death in a more dignified manner. He imagines his friends finding his body tomorrow.The man falls off into a comfortable sleep. The dog does not understand why the man is sitting in the snow like that without making a fire. As the night comes, it comes closer and detects death in the man's scent. It runs away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camp, "where were the other food-providers and fire-providers."。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天渐亮了,却仍然阴沉。
当他离开育空河的主道,爬上一个高高的土坡的时候,天气仍然极度地阴沉和寒冷。
那土坡非常陡峭,其上有一条人迹罕至的、难以辨认的小道向东穿过一片整齐而茂密的树林。
他爬上了坡顶,停下来喘了口气,顺便看了看表。
九点了,可是没有太阳,连一点太阳花花也没有,尽管天上没有一片云朵。
这好歹是个晴天,可是一切都仿佛披上了一袭无形的尸衣,一种莫可名状的黑暗使天色越发地阴晦了。
而这全都是因为天上没有太阳。
这倒并不让他害怕,他已经习惯了没有太阳的情况,从他上一次看见太阳起已经有好多天了。
他知道他离那个令人兴奋的光球还有几天的路程,南方的土地,已经是在天边隐约可见的,或者至多不过是仅仅在视线之外一点点的地方。
他回头看了看他走过的路。
足有一英里宽的育空河躺在三尺厚的冰下,冰面上还盖着数尺厚的积雪。
封冻的冰川汇集在一起,挤压出温柔的曲线,此起彼伏,一片白茫茫。
无论向南或者向北,他所看见的,是一片牢不可破的纯白,只除了一丝深色的线条从南边的一座封冻的岛屿边沿向北方弯曲绵延,消失在了另一座封冻的岛屿后面。
这深色的线条就是那条主道——育空河上的道路——它向南延伸五十哩,通向奇库特隘口、岱亚和盐湖;沿着它向北,走上七十哩就是道森;再走一千哩可到鲁那托;最终通向白令海边的圣迈克尔——那得再走上一千五百多哩。
然而对这所有的一切:那神秘的、遥不可及的细线般的主道、没有太阳的天空、刺骨的严寒以及它们所蕴涵的那种漠然与森严的意味,那人无动于衷。
并不是因为他对这些已经习以为常了,相反,他在这地方还是个新来的,一个新手,这是他在这儿遇到的第一个冬天。
他的毛病是没有想象力。
他对活动着的东西警觉而敏感,但他的警觉和敏感却仅限于那些活物本身而已,察觉不出表象之下的意义。
零下五十度就是冰点以下八十度。
这情形让他觉得不舒服,像患了感冒,仅此而已,没能让他意识到自己作为恒温动物所具有的弱点、作为人类所具有的弱点:即那种只能在极其有限的温度范围内才能生存的生命力;没能让他明白这些不可克服的缺陷和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
要抵御持续的零下五十度的严寒和针扎般的霜冻必须有手套、耳套、温暖的鹿皮靴和厚厚的长袜。
零下五十度对他来说就是零下五十度,至于其它还意味着什么则根本没有进过他的大脑。
他继续前进,随意朝地上吐了口痰,但一种尖利、响亮的爆裂声惊动了他。
他又吐了一口,他发现痰还没有落到雪地上,还在半空中就爆开了。
他知道零下五十度的气温能使口痰立即冻结,着地即碎,但这痰还没有着地就碎开了。
毫无疑问,气温已经低于零下五十度,但低了多少他不知道。
不过气温不是问题。
为了那一种古老的需求,他一心想去到哈德逊湾分岔口的左岸人们聚集的地方。
当他兜了个圈子去看能不能将木料从溪流里运出育空河中的小岛时,那些人越过了以印地安人湾为准的分界线。
六点种,也就是天黑下来以后不久,他应该在帐篷里了,真的,那些人全在那儿,会升好一大堆火,准备好一顿热气腾腾的晚餐。
他把手伸进大衣里面的一个鼓鼓的包裹中,那是他的午饭。
那包裹在他的衬衣里面,用围巾包好紧贴着他的皮肤,这是防止那些饼干冻结的唯一办法。
他想到这些饼干、这些一层层包起来肥满的腌肉、这些腌肉的裂纹和里面滋润的油脂,惬意地笑了。
他投身钻入那片整齐的丛林。
道路难以分辨。
雪橇经过后的雪地已凹下去有一英尺深。
他为自己没有雪橇而庆幸——这样可以轻装前进。
事实上,除了那顿包在围巾里的午餐以外,他什么都没带。
他还是多少对这寒冷觉得有些奇怪。
他用戴着连指手套的手擦了擦麻木的鼻子和脸:的确是冷啊,他觉得。
他一脸大胡子,但这一脸的毛没法保护他高耸的颧骨和那只挑衅一般地伸进寒风的鼻子。
有一条狗小跑着紧跟着他。
那是一条很大的野狗,一条真正的狼狗。
那狗一身灰毛,无论外形或脾气都与它的野狼兄弟没有两样。
极度的严寒也将那野兽弄得极度虚弱。
它知道自己没时间闲逛,它的本能给了它一条比任何人类的约束都远为真切的教导。
事实上,气温并不是只比零下五十度低一点,而是比零下六十度、零下七十度还要低,低到了零下七十五度。
零上三十二度就是冰点,也就是说天气冷到了冰点以下一百零七度。
狗不懂什么是温度,可能也不像人类那样脑子里有着对严寒的环境的清楚的意识,但野兽有的是它的直觉。
这种直觉焕发出一种模糊的威胁,控制了它并迫使它一路上鬼鬼祟祟地跟在那人后面;让它盼着那人钻进一个帐篷或者找到一个容身之所然后升起一堆火,而且让它对那人的每一个意料之外的行动感到纳闷。
那狗已认识了火,它想要一堆火,要不就只好在雪地上刨个洞然后蜷在里面好保持暖和。
它呼出的湿气已在它的毛皮上结了一层霜,特别是它的下颚、鼻子和眼皮,已经被水晶般的冰粒变成了白色。
那人的红胡子也同样冻上了,而且冻得更牢固。
他不断呼出的温暖而潮湿的空气已慢慢冻结、积聚成了冰块。
他正嚼着烟草,脸上的冰块把他的嘴唇都冻结了,以至于他吐掉汁水的时候没法把下巴弄干净。
最后,弄得他胡子上冻结的水晶和琥珀般的硬块越积越多,越来越长。
如果他跌倒的话,那东西就会像玻璃一样碎成片片。
不过他对这个附在他身上的东西并不在意。
这是每一个在那个地方嚼烟的家伙都躲不过的惩罚,他早在前两次寒潮袭击时便已经领教过了。
从一个叫“六十哩”的地方的公用温度计上他读到了一次是零下五十度,另一次是零下五十五度。
但那两次都没有这一次这么冷,这一点他知道。
他在那片广阔的林地中前进了几哩,穿过了一片平坦的黑土地,然后下到一条已经封冻的河床上。
这儿就是哈德逊湾,他知道他离那河流的分岔口还有十哩。
他看了看表,现在十点。
一小时走了四哩,他算了算,自己在十二点半应该可以赶到那岔口。
他打算在那儿吃午饭算是庆祝这一成绩。
在他摇摇晃晃地走在冻结的河床上时,那狗也无精打采地耷拉着尾巴跟着他下到了河床上。
这条老路上的辙印仍然清晰可辨,尽管已经有十英寸厚的积雪盖在了最后一对雪橇的压痕上。
这寂静的河床已有一个月没人经过了。
他坚定不移地继续走着,什么也不多想。
除了该在岔口边吃午饭和晚上六点钟钻进帐篷和同伴们在一起以外,他也的确没什么可多想的。
旁边也没有人可以说话,就算是有,他嘴上的冰甲也让他没法开口。
所以他只好一个劲儿地继续嚼他的烟草和继续加长他的琥珀胡子。
有一段时间他总觉得冷,从来没有这么冷过。
他一边走着,一边不停地用手套擦着颧骨和鼻子,不自觉地双手交替地擦着。
但尽管他擦个不停,他的脸颊还是很快就麻木了,然后鼻尖也立即失去了感觉。
他知道他的脸冻僵了,他明白。
他责怪自己没想到在寒冷来临的时候应该有一条鼻带。
这种带子可以横着把脸裹起来,这样就能保护好鼻子和脸。
不过这也没关系。
冻僵了是怎么回事情呢?一点儿疼痛,仅此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虽然他的脑袋里一片空白,但他仍然十分清醒。
他注意到了这条河的变化,那些弯道、拐角,以及那些灌木丛的变化,他专注于自己的每一个下脚处。
有时,遇到一个凹处,他会突然跳开,像一匹受惊的马。
然后绕过他刚才走过的地方,沿着河道回走一段。
他知道这条河已经冻得透了底了——在这极地的寒冬里,河里是绝不会还有活水的——他也知道会有从山里冒出来的泉水在封冻的冰河和其上的积雪之间流着。
他知道就是最冷的寒潮也冻结不了这些泉水,他同样也明白这些水所包含的危险。
这些水就是陷阱,会在雪下形成小水洼,大约三英寸深,有的则深达三英尺。
在这些水洼表面会结成约半英寸厚的冰壳,冰壳上覆着积雪。
有时多个冰壳和夹杂其间的水层相互交叠着,人一踏上去就会陷下去一直没到腰部。
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这样小心翼翼地躲闪着。
他能感觉到他脚下积雪的松动;听到雪下的薄冰碎裂的声音。
在这样的气温下弄湿了脚是麻烦甚至危险的,至少也要耽误些时间。
因为那样的话,他必须停下来生一堆火,在火堆光着脚烤干袜子和鹿皮靴。
他站定了,辨认了一下河床和河岸,确认水流来自右边。
他思考了片刻,一边又擦了擦鼻子和脸。
然后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掂量着每一次落脚的分量,朝左边绕过去。
一旦躲开了一个危险,他就狠嚼一口烟草,然后继续蹒跚着向一小时四英里的目标迈进。
在接下来的两小时里他总是遇到相同的陷阱。
覆盖在水洼上的积雪通常是凹陷而且稀松的,这样就容易识别。
不过还是有一次,他差一点就踏了上去;又有一次,他觉得前面的雪地不可靠,就命令那狗走在前面,那狗不干,一个劲儿向后缩着。
最后他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向前挪过去。
那狗紧跟着他跑过了那白色的、看似牢固的雪地。
突然,雪壳穿了,那狗掉了下去。
它挣扎到水洼边,爬上了一处结实些的地方。
它的前肢全湿了,上面的水很快结了冰。
它立即咬掉了它腿上的冰块,接着有躺在雪地上咬爪子上的。
是它的直觉让它这样干的。
如果听任冰块留在那儿会让腿脚剧痛,它并不知道这一层,它只不过遵循着那种从它自身的最深处升起的无名的冲动。
那人却明白这一点,他权衡了一下情况,摘下了右手的连指手套好让右手去擦拭眼角,防止眼泪冻结。
让他吃惊的是,他的指头敞在外面还不到一分钟,那迅捷的麻木感就已经侵袭了它们。
的确很冷啊!他赶紧拉上手套,然后用右手使劲地捶着胸口。
十二点是一天中最亮的时候,但太阳仍然在地平线以下遥远的南方作她冬日的徜徉。
大地上凸起的山峦将她同哈德逊湾隔开,在这儿,那人在正午的晴空下走着,连做伴的影子也没有。
十二点半,他按时到达了那岔口。
他对自己行进的速度很满意,若能保持的话,就一定能在六点钟赶到同伴们中间。
他解开大衣和衬衫,取出他的午餐来。
整个动作不过十几秒钟,可就在这样短的一段时间里,麻木又一次抓住了他裸露的指头。
他没有马上戴上手套,而是狠狠地用手拍着大腿。
片刻之后,他在一根被雪盖住的圆木上坐下打算开始吃东西。
可是手指在腿上猛拍所产生的疼痛消失得如此之快却让他大吃一惊。
他不停地拍打着手,终于只好又把手套戴上;然后脱出另一只手来好吃饭。
可是这样却弄得他连吃到一块饼干的机会也没有。
他试着满满地咬上一口,可封冻的嘴唇却张不开。
他忘了该升一堆火来熔化嘴上的冰块。
为这个失误他吃吃地笑了,可要笑的时候,他感到麻木已经钻到他裸露的指头里去了。
而且,他还发现行走时总是最先觉得疼的脚尖在他坐下以后也不疼了。
他想弄明白脚步指是否也麻木了,将脚在靴子里擦搓着,然后他明白脚趾也冻僵了。
他开始感到有些害怕,赶紧戴上手套站了起来,一个劲儿地跺脚直到脚又有了剌痛感。
的确是冷啊,他想。
有一个从硫磺湾回来的人曾提到过在野外有时会冷到什么程度。
那个人说得没错!而他那时候却在嘲笑那人,这说明他没能正确对待这个问题。
明摆着的,冷极了!他把脚高高地抬起来,跺下去;同时不停地拍打着手,直到确认它们又暖和起来了为止。
然后他拿出火柴着手生一堆火。
他在灌木丛中找到了木柴,那是在过去的春天发大水时生长起来的。
经过一会儿小心细致的努力,他升起了一堆旺火。
他在火旁烤化了脸上的冰块,在火焰的庇护下吃掉了饼干。
那狗满意地躺在火旁,它在合适的距离上舒展开身体,这样既十分暖和又不会被烧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