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身体与空间 辨别胎儿性别小窍门
小方法知道自己怀的男孩女孩

小方法知道自己怀的男孩女孩怀孕是每个女性都会经历的一段特殊时期,而怀孕的过程中,很多人都会对宝宝的性别产生好奇。
虽然现在有很多科学方法可以帮助准确预测宝宝的性别,但是也有一些小方法可以帮助你知道自己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小方法吧。
首先,根据宝宝的胎动来判断。
一般来说,怀男孩的妈妈会感觉到胎动比较有力,而怀女孩的妈妈则会感觉到胎动比较柔和。
这是因为男孩的胎动会比较有力,而女孩的胎动则会比较轻柔。
其次,可以通过妊娠反应来判断。
据说,怀男孩的妈妈会有比较严重的孕吐和恶心的症状,而怀女孩的妈妈则相对会比较轻微。
这是因为怀男孩的妈妈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会比较高,而怀女孩的妈妈则相对较低。
另外,还可以通过孕肚的形状来判断。
据说,怀男孩的妈妈的孕肚会比较尖,而怀女孩的妈妈则会比较圆润。
这是因为男孩的胎位一般会比较低,而女孩的胎位则相对会比较高。
此外,还有一些人们口中的“民间传统方法”可以尝试。
比如,用针挑手背的方法,如果用针挑手背的时候,是直来直去的,那么是男孩;如果是绕圈圈的,那么是女孩。
当然,这些方法并没有科学依据,只是一些人们的传统经验总结,仅供参考。
最后,可以通过B超来确定宝宝的性别。
这是目前最准确的方法,通过B超可以清晰地看到宝宝的性别特征,从而准确判断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
总的来说,怀孕期间了解宝宝的性别,不仅可以增加准妈妈的期待和兴奋,也可以帮助准备宝宝的一些用品。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这些方法仅供参考,并没有科学依据,最终确定宝宝的性别还是需要通过医学检查来进行确认。
希望每一位准妈妈都能顺利度过怀孕期,迎接健康可爱的宝宝的到来。
小方法知道自己怀的男孩女孩

小方法知道自己怀的男孩女孩
有很多小方法可以判断自己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方法:
1. 生理特征:男胎发育较慢,女胎发育较快。
如果你的怀孕期间,发现胎儿的心率低于140次/分钟,可能是男孩;如果心率超过140次/分钟,可能是女孩。
2. 乳房变化:根据乳房变化也可以猜测胎儿的性别。
如果乳头颜色变深,乳晕增大,乳房肿胀,可能是男孩;如果乳头和乳晕颜色没有明显变化,可能是女孩。
3. 孕吐程度:据说,孕吐程度较重的妇女,怀的多是女孩;孕吐程度较轻的妇女,怀的多是男孩。
4. 孕肚形状:如果你怀孕时,孕肚显得较尖,就可能是男孩;如果孕肚比较圆润,可能是女孩。
5. 嗜好变化:孕妇的食欲和嗜好也可能与胎儿的性别有关。
如果你突然对甜食感兴趣,可能是女孩;如果你偏好咸食,可能是男孩。
这些方法只是参考,准确性并没有科学依据,最终性别仍需要通过B超或基因测试确认。
记住,性别无论男女,都是宝贵的生命,最重要的是健康。
如何从b超单上辨别胎儿性别-辨别胎儿性别小窍门

如何从b超单上辨别胎儿性别|辨别胎儿性别小窍门【科学科技公文】辨别胎儿性别小窍门准妈妈在孕期被问概率最高的恐怕就是宝宝的性别了.可是隔着肚皮,小东西的性别比爸妈当然猜不到,为了安慰诸位的好奇,小编把从网上看到的关于宝宝性别的各种根据发在这里,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辨别胎儿性别小窍门,供大家参考!1.清宫表推测是男就男,是女就女(清宫生男生女秘方表按照阴历推算,月经周期超过28天者怀孕月份推延一个月,月经无规律者不用此法)2.尖肚子男,圆肚子女;3.肚子小男,肚子大女;4.除了肚子身体其他部位没发胖的男,反之女;5.脚不肿,后期稍肿男,脚肿,后期更肿女;6.反应不重男,反应重女;7.准MM喜酸和咸食男,喜辣或甜食和果汁女;8.准MM变丑,皮肤变黑男,皮肤不变或变漂亮女;9.胎动早为男(16W),晚为女;10.胎动感觉拳打脚踢和整个身体翻动为男,只整个身体翻动女;11.比预产期早生男,晚生女;12.肚脐突出男,不突出女;辨别胎儿性别小窍门13.B超显示宝宝脸朝外的男,面对MM的女;14.妊娠线肚脐以上偏左,直、细、直达两乳间,且整个妊娠线浅淡是男,反之女;15.怀孕后准MM性欲变强是男,性欲没变化或变弱是女;16.胎动偏左男,偏右女;17.胎心140左右男,150左右女;胎儿窍门性别1、心率快是怎么回事(2016-03-28)2、心跳过快的原因(2016-04-12)4、半夜心跳过快是什么原因(2016-04-21)3、心跳偏快是怎么回事(2016-04-17)4、半夜心跳过快是什么原因(2016-04-21)5、孕妇食物中毒对胎儿有影响吗(2016-04-22)6、有时心跳过快是什么原因(2016-04-22)7、怀孕应该多吃什么对胎儿好(2016-04-24)8、胎儿生长推迟怎么办(2016-04-24)9、心跳过快有力可能是什么原因(2016-04-30)10、皮肤过敏会心率不齐(2016-04-30)13、双胞胎儿子(2016-08-03)11、为什么心率有时不齐(2016-06-20)12、医疗损害责任判决(2016-08-02)14、孕后期轻度贫血(2016-08-21)15、心率补齐(2016-09-23)16、怀孕二个月(2016-09-23)17、心跳经常过快是什么原因(2016-09-24)18、心跳一直过快是什么原因(2016-09-24)19、30周胎儿在肚子里图片(2016-12-14)20、13周胎儿图(2016-12-28)21、如何缓解狐臭(2016-04-12)22、怎样缓解狐臭(2016-04-16)23、菜汤洒在衣服上怎么办(2016-04-18)24、衣服菜汤(2016-04-18)25、我的发现:生活中小窍门(2016-04-20) 28、塑料吸盘钩,小窍门(2016-04-27) 26、怎样去除衣服上果汁印(2016-04-21)27、怎么去除衣服上的果汁(2016-04-24)29、衣服上隔夜果汁渍怎么去除(2016-05-06)30、养蚕小作(2016-07-25)31、去除手上老年斑(2016-08-04)32、夏日生活小常识(2016-08-15)33、如何去除衣服上的锈渍(2016-08-21)34、如何去衣服上的果汁(2016-08-25)35、宿舍防蚊虫叮咬小窍门(2016-08-30)36、小窍门如何快速洗毛巾(2016-09-01)37、小窍门,去除新脸盆上的标签(2016-09-03)38、怎样去除霉渍(2016-09-23)39、怎么挑好的榴莲(2016-09-24)41、感冒鼻塞喉咙痛怎么办小窍门(2016-09-26)49、iphone7使用技巧(2016-12-29)40、怎么去衣服上的果汁(2016-09-25)43、炒肉不粘锅的小窍门(2016-11-14)44、烫伤后怎样不留疤痕(2016-11-15)45、洗毛巾变柔软小窍门(2016-11-17)46、洗毛巾小窍门(2016-11-19)47、洗内裤窍门(2016-11-21)50、化学反应方程式配平方法(2017-01-11)。
判断男宝还是女宝的靠谱方法,要二胎的朋友可以看看哦

判断男宝还是女宝的靠谱方法,要二胎的朋友可以看看哦2017-03-27方法一、看孕妇的腹部情况在中华传统方法中,判断婴儿性别有一句比较经典的话,“男抱母,女背母。
同时也是一种判断婴儿男女的一种小技巧。
就是说如果腹部出现“抱”的状态(腹部向前凸出,有在腹前抱东西的样子)往往生男孩比较多。
相反,如果腹部出现“背”的形态(腹部凸出不明显,腹后和两侧比较宽有腹部背东西的样子)往往生女孩比较多。
方法二、根据胎儿胎心强弱一般认为胎心较强较慢的话,可能是男孩子。
胎心较弱较快的话是女孩子。
方法三、胎儿胎心的位置孕后期听胎心的时候,如果是在左侧可能就是男孩。
右侧可能是女孩。
是一个产科老医生分析得出的结论,据说她这个超准哦!方法四、看胎儿孕囊形状孕8周左右做的B超单,如果发现孕囊椭圆或者是茄子样的,多数是男孩。
圆形的可能是女孩。
方法五、看孕囊数据如果长跟宽差1倍以上,可能是男孩。
相差不大,可能是女孩。
方法六、看孕妇的胸部增长怀女宝宝的孕妈胸围增长8CM左右,甚至更多。
而怀男宝宝的孕妈增长在6.2-6.5之间。
胸围增加越多,说明怀女孩的几率越大。
因为怀男孩的妈妈体内会有更多的睾丸激素,会阻碍胸部长大!方法七、根据孕早期的孕吐反应一般怀女宝的妈妈孕早期孕吐反应比较大,而怀男宝宝的妈妈孕吐反应要轻很多。
方法八、根据怀孕的年龄跟月份民间流传一种算法也比较准,就是孕妇的怀孕年龄和怀孕月份,一般怀孕年龄+怀孕开始的月份=偶数的是男宝宝,怀孕年龄+怀孕开始的月份=奇数的是女宝宝。
方法九、看孕妈妈的孕期状态比较容易情绪化,喜怒无常。
孕期状态没有以前好的,多数是女孩。
如果孕期状态比以前好的可能是男孩。
方法十、看身材变化怀男孩的孕妈妈不怎么胖,怀女孩的可能就会感觉明显发胖。
男孩的肚脐眼凸出,女孩基本不会。
孕妈们,知道你们肚子里是男宝宝还是女宝宝了吗?。
怀孕自测男女简单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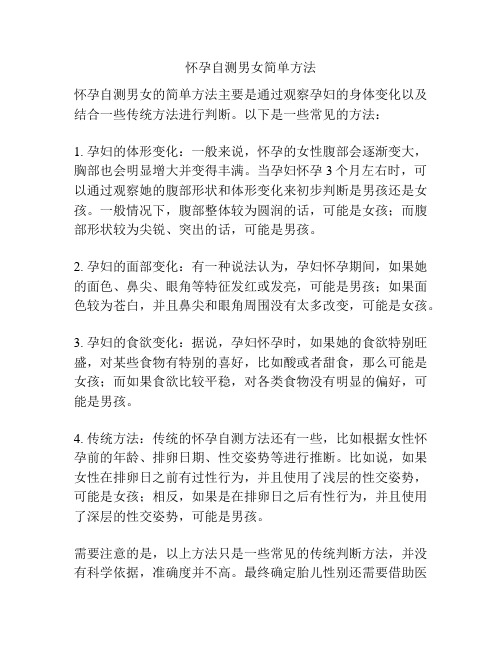
怀孕自测男女简单方法
怀孕自测男女的简单方法主要是通过观察孕妇的身体变化以及结合一些传统方法进行判断。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方法:
1. 孕妇的体形变化:一般来说,怀孕的女性腹部会逐渐变大,胸部也会明显增大并变得丰满。
当孕妇怀孕3个月左右时,可以通过观察她的腹部形状和体形变化来初步判断是男孩还是女孩。
一般情况下,腹部整体较为圆润的话,可能是女孩;而腹部形状较为尖锐、突出的话,可能是男孩。
2. 孕妇的面部变化:有一种说法认为,孕妇怀孕期间,如果她的面色、鼻尖、眼角等特征发红或发亮,可能是男孩;如果面色较为苍白,并且鼻尖和眼角周围没有太多改变,可能是女孩。
3. 孕妇的食欲变化:据说,孕妇怀孕时,如果她的食欲特别旺盛,对某些食物有特别的喜好,比如酸或者甜食,那么可能是女孩;而如果食欲比较平稳,对各类食物没有明显的偏好,可能是男孩。
4. 传统方法:传统的怀孕自测方法还有一些,比如根据女性怀孕前的年龄、排卵日期、性交姿势等进行推断。
比如说,如果女性在排卵日之前有过性行为,并且使用了浅层的性交姿势,可能是女孩;相反,如果是在排卵日之后有性行为,并且使用了深层的性交姿势,可能是男孩。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方法只是一些常见的传统判断方法,并没有科学依据,准确度并不高。
最终确定胎儿性别还需要借助医
学检查,比如B超、DNA性别鉴定等专业方法。
如果孕妇想要了解胎儿的性别,最好咨询医生进行相应的检查。
你轻松辨别胎儿性别

第一个办法就是看孕妇的气色
在中医里面,看一个人的气色可以知道身体的状况,看一个孕妇的气色就可以知道肚子里面是男是女,如果说肚子里的宝宝是男孩的话,孕妇的精神状态会很好,平时很少出现急躁或者精神分散的情况,这样一般是会生下男胎。
如果孕妇在怀孕的时候经常精神慌乱或者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心情起伏也比较大,这种情况下可能是阴气比较重,很可能是怀了女胎,这个情况下孕妇一定要多多注意休息而且要注意合理的膳食来补充营养。
第二个办法就是看胎儿在母体当中的运动情况
如果感觉到肚子里的宝宝运动节奏比较均匀的话可能是个小男孩,而且胎动的均匀还象征着这个胎儿十分的健康,以后比较容易养,如果是不均匀的话一般是女孩子。
由此可见,胎动不但能够辨别胎儿性别,还能够知道孩子的发育情况。
第三个办法是看孕妇的腹部
按照传统的说法,如果孕妇腹部向前突起,像抱东西一样的话往往就是怀了一个男宝宝,但是如果腹部突起比较明显,而且两侧比较宽的话就有可能是怀了女宝宝。
第四个办法是看孕妇的面部。
老中医教你如何预知宝宝性别

老中医教你如何预知宝宝性别现代人类虽然没有那么重的重男轻女观念,不过当妈妈们怀孕的时候总是有那么些期许肚子里的是千金还是公子,家里人坐在一起也会经常谈起这胎是男孩还是女孩,那这里呢老中医先教大家如何由孕妇的体征看男女。
1. 肚子看上去比较尖的则为男,肚子比较圆润的则为女2. 怀孕期间肚子比较小的为男,肚子很大的为女3. 除了肚子身体其他部位没发胖的则是男,反之为女4. 脚不肿男,脚肿女5. 反应不重男,反应重的相对来说女孩的概率高点6. 酸男,辣女(这个基本是老祖宗传下的了,也是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7. 有些妈妈在怀孕期间容貌变的有些变丑男,变漂亮女8. 皮肤变黑男,皮肤不变女9. 胎动感拳打脚踢男,整体翻动女10. 比预产期早生男,晚生女。
每个妈妈都会有做B超的经历,医生知道生男生女,可她又不告诉你,那怎么办?别着急,她总得给咱B超单吧! 老中医教你如何看B 超单:一:看B超数据,如果长和宽的相差在一倍以上男宝宝可能性大,长和宽相等女宝宝可能性大。
1:7W+1D的BC数据:孕囊2.91.9mm生的是男孩2:9W+4D的BC数据:宫内见46.630.2mm孕囊双胞胎都是女孩3:60天的BC数据:孕囊大小是3.61.6mm生的是男孩4:5W+6D的BC数据:孕囊25mm11mm是男孩5:数据,囊胚:23*17*16生的是小美女6:46天的BC数据:孕囊201717生的是女孩7:7W+1D的BC结果:3220妊娠囊生的是女孩8:8周时是4128mm生的是女孩9:8周时是1.6*1.7生的是女宝宝10:8周多的BC数据:胎囊是19mm10mm生的男孩11:胎囊35mm*34mm*28mm生的女孩12:孕囊大小:长18mm*宽16mm*厚18mm生的女宝宝13:62天孕囊2.61.8生的男孩14:50天孕囊35mm27mm生的女孩15:孕囊3318mm生的男宝宝16:孕囊4420mm生的男孩17:9周+6天BC数据5.62.4 23周+5天BC结果是男孩18:7周多的BC数据:宫内见3.82.3cm妊娠囊生的是男孩子19:孕囊3.32.0mm生的是男孩二:看形状,像茄子或长条状的生男孩可能性大,圆圆的生女孩的可能较大。
鉴定男孩女孩的方法

鉴定男孩女孩的方法
鉴定男孩女孩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虽然现在科技进步,可以通过B超等技术鉴定胎儿的性别,但是有一些老祖宗的方法其实也很准确,接下来介绍几种常见的鉴定男孩女孩的方法:
1、腹形鉴定法:女胎腹部较圆、男胎腹部较尖,因为男胎由于皮下脂肪少,腹部外突。
2、面部鉴定法:女胎面部比较光滑,男胎面部有点突出,这主要是因为体内荷尔蒙分泌的不同。
3、尿液鉴定法:在一片白布上收集孕妇的尿液,数小时后,如果有明显的颜色变化(大约是深绿色),则是男孩;如果没有颜色变化,则是女孩。
这个方法需要注意集尿过程中尽可能避免将洗涤剂或其他杂质加入尿液中。
4、心跳鉴定法:使用听诊器或超声波听设备在孕妇腹部检测胎儿心跳次数,如果胎儿心跳次数较快(通常在140次/分钟以上),则是女孩;如果胎儿心跳次数较慢(通常在130次/分钟以下),则是男孩。
以上方法虽然都有一定的准确度,但是结果并不百分百准确,不能代替专业的医学鉴定。
另外,鉴定胎儿性别并不重要,希望父母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孩子的健康成长和教育上,让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生活中12招辨别生男生女

生活中12招辨别生男生女在人们的生活中,有许多普遍的方法和传说来辨别孩子的性别。
尽管这些方法不能保证100%的准确性,但它们对于家长们来说仍然非常有趣和有用。
以下是生活中12招辨别生男生女的方法。
1. 早孕反应:有人认为怀的是男孩时,早孕反应比怀女孩时更严重,因为人的性别决定于受精卵中的精子是否带着Y染色体(男孩)或X染色体(女孩)。
但是,这种方法并不是完全可靠的科学依据。
2. 用脸形和尺寸预测性别:有人通过女性面部特征的变化,如乳晕的大小、颜色或皮肤质地的变化来预测胎儿的性别。
其他人则根据孕妇肚子的形状和位置来预测。
3. 选取正确的月份:一些父母会根据母亲的月份来预测胎儿的性别。
例如,如果怀孕时间落在“春分”到“秋分”期间,就有可能是男孩,反之则可能是女孩。
4. 水果实验法:将针头插入某种水果中,然后观察针是在旋转还是来回直行,即可判断胎儿的性别。
5. 遗传学预测性别:如果妈妈的父亲和母亲都有很多兄弟,那么她生男孩的几率就更大,因为男性精子带有Y染色体。
6. 大麦子实验:将大麦子放在盐水中,如果麦子向下向下沉,预示着你的孩子将会是男孩,如果麦子上浮则说明你孕育的是女孩。
7. 妊妇午睡体位法:在孕育小孩期间午睡时,若是以左侧卧位为主,则说明将要生女孩,若是右侧卧位为主,那么预示生男孩的几率相对较大。
8. 激素分泌体质法:结合更科学的观察方式,注重妈妈交感神经和内分泌系统的反應,如体温、胎心、尿酸、血压或卵巢合成的金字塔酮浓度等,来预测胎儿性别。
9. 预测胎儿心率:据称,女孩的心率比男孩的心率更快,比如120到160次/分钟是女孩,而110次/分钟则是男孩。
10. 穿衣打扮辨别法:也有些人相信穿蓝色衣服的妈妈将会生男孩,穿粉色衣服的妈妈将会生女孩。
11. 体物格局法:根据父母的体格来预测胎儿的性别。
比如,如果父亲很瘦,母亲很胖,女孩的可能性会更大。
12. 藏婴猜性:这种方法在中国已经流行了数百年。
判断胎儿性别的8种方法

判断胎儿性别的8种方法判断胎儿性别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很多准父母都希望能够在怀孕期间就了解到宝宝的性别。
虽然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使得通过超声波、遗传学等方法可以准确地判断胎儿的性别,但是还有一些传统的方法被很多人所信任和采用。
下面将介绍八种常见的判断胎儿性别的方法。
1.腹型判断法:据说男胎在母体腹部高位置,形状犹如一个篮球;女胎则低且横平竖直。
然而这种判断方式并没有科学依据,只是一种迷信的说法。
2.心率判断法:有人认为男胎的胎心率较快,女胎的胎心率较慢。
然而,胎儿的胎心率受孕周数、孕妇自身身体状态及环境等因素影响,因此不能作为可靠的性别判断依据。
3.脸部色斑判断法:据说孕妇如果脸上出现色斑,就是生男孩;如果没有色斑,就是生女孩。
然而这完全是无科学依据的迷信说法。
4.体重增长判断法:传统观念认为,妈妈怀男胎时胃口会变大,体重增长较快;怀女胎时则相对较小。
然而这种说法也完全无科学依据。
5.怀孕反应判断法:传统说法认为,怀男胎时孕吐严重,脸色变差;怀女胎则相对轻微。
虽然有些孕妇的确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但也有很多孕妇并没有孕吐或者孕吐轻微,因此不能作为可靠的判断依据。
6.妇科体格检查:通过妇科体格检查可以初步判断胎儿性别,如宫底位置、子宫内口大小等。
然而这种方法只是一种指导性的办法,仍然可能存在误差。
7.超声波检查:这是目前最准确的判断胎儿性别的方法。
通过超声波技术,医生能够看到胎儿的生殖器官,从而准确判断胎儿的性别。
一般来说,孕妇怀孕18~20周时进行超声波检查效果最好。
8.遗传学检测:通过遗传学检测,可以从孕妇的血液样本中提取胎儿的DNA,从而判断胎儿的性别。
这种方法准确率高,但成本较高,仅少数医疗机构提供。
需要注意的是,传统的判断胎儿性别的方法很容易产生误导,而且很多方法都没有科学依据。
如果准父母对胎儿的性别有较高的关注度,可以选择通过超声波或遗传学检测等科学方法来明确胎儿性别。
同时,要持有科学的态度,不要盲目迷信,给自己和宝宝带来负面影响。
生男生女最准确的方法

生男生女最准确的方法
生男生女的方法并没有科学可靠的依据。
以下是一些流传的方法,但并不一定有效:
1. 月经周期法:父母可以根据母亲的月经周期预测受孕时机和宝宝性别。
据说在受孕前几天进行,如果是排卵期且父亲提前排泄,有更大概率生男孩。
如果在排卵期的第二天或者后几天进行,会更有可能生女孩。
2. 饮食法:根据饮食来调节胚胎性别。
据说食物中富含钠的会促进生男孩,而富含钾的则更容易生女孩。
3. 温度法:男性睾丸需要相对较低的温度才能正常工作。
因此,如果宝爸长时间泡热水浴,睾丸所受温度增高,可能减少生男孩的概率。
所以建议减少泡热水浴的时间和频率。
4. 怀孕时间法:孕妇的怀孕时间也会影响宝宝的性别。
如果是在春天和夏天怀孕,很有可能生男孩,如果是在秋天怀孕,就更容易生女孩。
5. 姿势法:据说姿势也可能影响宝宝性别。
有些人认为女上位、侧入、后入等姿势会增加生男孩的几率,而男上位和悬崖勒马等姿势则有可能生女孩。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方法没有科学依据,只是一些传统偏信的观念。
宝宝的性别
是由父母的染色体决定的,我们无法通过特定的方法来控制。
怀孕怎么看是男是女准确

怀孕怎么看是男是女准确
怀孕之后很多的夫妻家庭都希望能够在没有生下宝宝之前就了解孩子的性别,而想要看是男是女,可以通过观察孕妇的肚型,变化以及饮食习惯的改变进行判断。
★1、检测胎心的快慢。
当检查出胎心较强较慢,则孕妈妈怀男孩的机率非常大。
胎心较弱较快,则很可能会是怀女儿。
★2、观察呕吐现象。
怀男孩时孕妈妈在早孕期间几乎没有呕吐的现象。
怀女孩时孕妈妈在孕早期就会经常孕吐的症状。
★ 3、观察孕妇的肚型变化。
如果孕妇的肚型尖凸,那么怀男孩的几率非常大。
一旦孕妇的肚型浑圆,则怀女孩的几率会更大一些。
★4、饮食习惯改变。
孕妇在怀孕期间的饮食习惯会出现变
化。
怀男孩的妈妈的口味转变为喜欢吃酸或吃甜,怀女孩的妈妈非常喜欢吃辣的食物。
★ 5、观察乳房变化。
乳晕颜色较深时,怀男孩的机率较大。
当乳房增大得比较明显,尤其是左边的乳房比右边的乳房大时,就很有可能是怀上了女孩了。
★ 6、孕妈妈的增胖程度。
当孕妈妈的腰部、髋部和臀部有明显的增胖现象时,生女孩的可能性比较大。
孕妈妈的肚子、胸部有明显的增胖,那么,很有可能是怀男孩。
★ 7、观察孕妇的容貌和皮肤变化。
孕妈妈怀女孩时皮肤会显得更加光滑,容貌更加漂亮。
当妈妈的容貌变丑,皮肤变粗糙时,甚至长青春痘时,那么怀男孩的几率非常大。
4招预测生男生女早知道

4招预测生男生女早知道
一:妊娠中线发黑是男孩如果怀孕以后的妈妈肚皮中央通常会出现一条黑色的线,称之为“妊娠中线”,江湖术士称其线条越黑,是男孩的几率越高。
二:胎心率看男女听胎心来判断男女,如果是女孩的话,心跳频率会比较快一点,男孩胎心会慢一些。
还有测试是胎心率每分钟超过140次的话就是男孩,如果每分钟小于140次的话就是女孩。
三:胎盘的位置要是胎盘的位置在子宫的后壁,猜测怀的大多数是男孩,相反如果胎盘的位置在子宫的前壁,怀的大多是女孩。
四:皮肤好坏判断男女怀孕的时候皮肤好坏也可以看出胎儿是男士女,如果怀孕期间皮肤变得细腻多半是女孩,如果是男孩则相反,脸上会长很多斑点,脸色也不会像原来那样好看。
识别胎儿性别的方法

识别胎儿性别的方法有哪些?说法1:孕妇腹部突出过大是女孩,腹部不太突出或下腹部突出为男孩解析:如果孕妇上身短,胎儿发育的空间只能向外延伸,所以腹部会显得很大。
反之,孕妇上身长,可为胎儿发育提供足够的空间,腹部就无须向外突出。
说法2:胎儿心率低于140次/分,则所怀胎儿是男孩解析:女孩心率比男孩高,这只是在刚出生时是对的,胎儿的心率就男孩和女孩之间没有任何差别。
心率的快慢只是随胎龄的不同而变化。
在约孕5周时,胎儿的心率与妈妈的心率接近,即80~85次/分。
然后到孕9周这段时间内心率逐渐加快至170~200次/分。
尔后到孕中期这段时间内又逐渐放慢至120~160次/分。
要想准确掌握孕期各阶段胎心率的数据和变化,可以使用家用胎语仪,还能将数据和胎心率曲线保存下来。
说法3:孕妇下怀下腹部大是男孩,上怀上腹部大是女孩解析:如果孕妇是上怀,那可能是第一次怀孕或孕妇的体形好。
当孕妇怀过一次孕以后,腹部肌肉松弛,再次怀胎时自然也就“下垂“了。
说法4:乳头发黑是男孩解析:乳头颜色受到体内激素的影响,孕期体内黄体酮和刺激黑色素细胞的激素水平的增加,导致体表面某些原本发黑的部位更黑,当生完孩子后就会很快恢复,这种现象与胎儿性别毫无关系。
说法5:吃酸吃碱与生男生女的关系解析:有人仅凭味道来确定食物是酸性还是碱性,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认识。
需要强调的是,人体出现酸碱不平衡的状态,通常是患病所致。
说法6:早孕反应便爱食酸辣“酸儿辣女”解析:“酸儿辣女”的说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从医学上说,生男生女主要是由染色体决定的,母体中的卵子都是带X染色体的,而精子中是含有X或Y的染色体,如果进入卵子的精子是带X染色体的,就是女孩;如果进入卵子的精子是带Y染色体的,就是男孩。
所以说生男还是生女其实是由父亲决定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生男生女跟受精卵的受孕环境有关系,也就说跟输卵管周围的环境有关系。
说法7:早上害喜生女孩?解析:针对5900位因为怀孕初期严重害喜而入院的孕妇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些孕妇生下女宝宝的比例是56%、男宝宝是44%。
判断胎儿性别的31个有趣方法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
生活常识分享判断胎儿性别的31个有趣方法
导语:怀孕期,准妈妈准爸爸最爱做的事情之一,莫过于猜测腹中宝宝的性别。
对于腹中宝宝性别的期待,是一个漫长而又幸福的过程,虽然生男生女都一
怀孕期,准妈妈准爸爸最爱做的事情之一,莫过于猜测腹中宝宝的性别。
对于腹中宝宝性别的期待,是一个漫长而又幸福的过程,虽然生男生女都一样,但这个猜测的过程却是充满无限神秘乐趣的快乐体验。
下面这31种有趣方法,仅作为准爸爸准妈妈猜测胎儿性别的参考,偶尔娱乐一下,宝宝和您都能更轻松、更健康!
Ta可能是个帅哥,如果准妈妈
1. 早孕期间(也就是怀孕最初的3个月),没有过孕吐的状况。
2. 胎宝宝的心率小于140次/分钟。
3. 身体的整体感觉,如精神状态、要比以前好一些。
4. 乳晕的颜色相对要变得更深。
5. 肚子、胸部等身体的前部,增胖会比较明显。
6. 日渐隆起的大肚子,看起来像个充足了气的、绷绷硬的、圆圆的篮球。
7. 体重增长相对比较慢。
8. 想吃酸味或者咸味更重的食物,这些食物会让你口感觉得更舒服些。
9. 对蛋白质的食物特别有食欲,比如肉类、奶酪等。
10. 双脚的温度要比怀孕之前感觉更凉一些。
11. 腿上的汗毛会比孕前长得快。
12. 手的皮肤发干。
13. 睡觉的时候,你喜欢把枕头朝北面的方向放。
测试生男生女的妙招

测试生男生女的妙招测试胎儿是男孩是女孩的方法是很多新妈妈感到好奇的,能够测试孩子性别对某些人来说很值得兴奋的。
其实如今传统上又很多测试方法,小编带新妈妈来了解一下测试生男生女的妙招。
1、看孕妇的神态。
影响孕妇胎内婴儿身体发育情况的主要因素就是神态的清浊。
具体方法是如果胎内有男婴,则孕妇的气色很好,并且气力很足,从神态上表现出神态常常精神有光,言谈举止中多了一些平静优雅,少了一些急躁、慌张、散乱的神态,有这种神态的孕妇往往在相学中寓意着有男婴降生,并且婴儿在出生之后身体茁壮,健康幸福。
如果孕妇的神态常常出现慌乱、浑浊或分散的情况,并且夹带心情上出现不稳定情况,往往是因为孕妇胎内的气力略有不足,因此降生女婴的可能性比较大,作为孕妇的亲人,应对孕妇多补充一些营养,注意孕妇的休息情况可以填补孕妇胎内的气力,降生一个聪明可爱的宝宝。
2、看孕妇的面部气色情况。
孕育男婴的气色是非常不错的,主要表现在孕妇的双眼下方的肤色比较白皙晶莹,有润泽感,此外孕妇的两眉之间的肤色光亮发明,没有发乌的情况,鼻头也比较亮泽洁净,有这种气色面相的孕妇往往男婴降生的概率会比较高,并且婴儿的发育情况和健康情况都比较理想。
3、看孕妇胎动情况。
如果孕妇的双眼上方如果出现肤色发青暗不光亮的情况,是因为气力不足而导致,因此生育女婴的几率会大一些。
相反,如果孕妇的胎动情况比较均匀有节奏感,则往往生育男婴的几率很大,并且如果胎动如果匀称有利,还象征着婴儿的发育情况很好,因此在出生之后不容易受到疾病的困扰,抚养起来比较良好,相反,如果孕妇的胎动时常出现不匀称、不稳定的情况往生育女婴的几率会大一些。
以上介绍的几种测试生男生女的妙招是大家比较容易掌握和接受的,而且效果也是不错。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性别、身体与空间一直是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
“女权主义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对空间与人的社会性做了很多的研究。
她们主要致力于对不同社会类别,如性别、种族、阶级等与物质的空间的关系的研究。
比如,人们是如何体验空间的?空间是否有性别属性?父权社会机制和话语是如何在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等领域对妇女的空间进行规范和限制的?”在男权主义为中心的社会控制下,女性始终处于被压迫的境遇,这种压迫正是通过空间对身体的圈限而得以具体的操作实施并最终完成。
因此,考察性别、身体与空间之间所充斥的权力统治的紧张关系,成为女性主义理解身体空间政治学的独特视角。
一、女性身体空间的圈限与解放
身体作为一种空间性存在,总是在空间中展现的,因此对身体的控制压迫也总是开始于空间。
从身体空间中的性别政治学角度看,性别、身体与空间始终是权力统制运作的场域,“对妇女来说,现存的空间是造成她们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男性对妇女的社会空间的安排是男性控制妇女的一个重要工具”。
因此,“女性在历史上向来被排斥于一些空间之外,或局限于一些空间。
与种族隔离一样,男女生存的空间从来就是“隔离的和不平等的”,对女性的“规范的空间”的建构往往能说明空间的性别”。
从此意义上说,身体控制的历史必然是空间控制压迫的历史。
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女性解放的倡导,打破了女性生存空间的圈限,女性终于走出身体残缺的闺房,女性被肢解的身体空间较之传统封建帝国
时期,呈现出敞开性、去蔽性的特点,特别是一部分进入学堂、接受教育的知识女性开始涉足一向由男性掌控的书写系统,以写作为职业,开始了现代女性文学的写作历程,改写了女性生存空间边缘化的地位。
在“五四”这个狂飙突进的时代,我们惊喜地看到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等一批女作家登上文坛,成为新女性文学的拓荒者。
她们将反对身体奴役,要求个性解放的目光对准爱情、婚姻问题,《海滨故人》、《隔绝》、《旅行》、《秋风秋雨愁煞人》、《再见》等文本均从女性身体经验出发,以委婉柔韧的笔致袒露了破除生存空间圈限的女性,因无法自由恋爱,而隐匿于心的伤痛,其中冯沅君笔下那个在母爱和情爱之间备受折磨,只能以自杀求得解脱的隽华成为时代女性的代表,“开了为要求恋爱自由而死的血路”。
其后的60年间,尽管战事频繁、政权更迭,中国社会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但以丁玲、萧红、谢冰莹、罗淑、冯铿、茹志娟、杨沫、宗璞、草明、刘真、柳溪、张洁、张抗抗、铁凝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女性作家与男性共执文化之牛耳,改写了文学史上女作家边缘化的地位。
但是,纵观这70年来的女性文学创作,我们发现其文本内部不是言说着对爱情无尽的痴迷与企盼,就是宣泄着事业家庭两难中的苦闷与哀愁;不是建构着国难乡愁中“忘记自己是女人”的民族想象,就是女英雄呼喊着“信仰就是我的太阳”的政治宣言,女作家并没有从身体出发思考女性的社会问题、家庭问题,建构自觉的女性意识,其文本仍然属于菲勒斯男性中心话语系统中的启蒙话语或革命话语,女性的身体解放归化于更大的民族、国家、阶级而获得意义。
如谢冰莹在《从军日记》中坦言,“恋爱是个人的私事,大家愿把生命献给国家民族的坚决信仰中,恋爱不过是有闲阶级的小姐少爷们的玩意而已”。
冯铿在《红的日记》
中塑造的马英完全将个人的身体生命融于民族的生存中,她“眼睛里只有一件东西溅着鲜红的热血,和一切榨取阶级、统治阶级拼个你死我活”。
丁玲在《苇护》、《我在霞村的时候》等文本中,将社会革命伦理高悬于个体生命伦理之上,显示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女作家自觉地将源于身体的性别意识融入阶级意识、革命意识、工农意识中的时代特质。
女性生存空间向男性空间的敞开,不但没有带来社会性别秩序的整体性改变,相反却进一步导致女性生存空间被男性所同质化、同一化。
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的性别身份丧失。
在张扬“男女都一样”的“十七年”,女作家将创作视角从家庭的狭小场域拓展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书写着伟大时代缔造者一“女英雄”的赞歌。
女性打着“人”的旗号,成为没有任何意义的空洞能指,女英雄不过是主流社会男性话语霸权的产物和修辞的策略,是为了召唤更多女性走出家庭,加入建设者行列而缔造出的一个文化符号。
女性这个在“五四”文化革命之后艰难地浮出历史地表的性别,在她们终于和男人共同拥有了辽阔的天空和伸延的地平线之后,却失落了其确认、表达或质疑自己性别的权利与可能。
西蒙·波伏瓦曾说,“男性不存在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割裂问题,(因为)在行动和工作上他对世界把握得越紧,他就越有男子汉气……而女人自主的胜利却与她女人气质相抵触”。
女作家韦君宜在《女人》中借助描写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在女性身上的矛盾冲突及互相抑制,传达出职业女性屈从家庭角色时的无奈。
即便在以社会氛围民主开放著称的新时期,以茹志鹃、谌容为代表的老作家和以张洁、张辛欣、陆星儿为代表的年轻女作家,也都关注着女性的心灵创伤和精神苦刑,慨叹着“我在哪儿错过了你”,言说着渴望与男性“站在同一地平线”的启蒙话语。
中国现代文学对身体的关注从理论的层面上看,直接受益于以西苏和伊瑞格瑞为代表的法国女性主义者,她们倡导女性通过“身体写作”这一自由的写作样态,改写其被凝视、被书写的命运。
西苏提出,在父权制文化压迫下女性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她们只有自己的身体可以凭借,因而,女性只能“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身体表达自己的思想”,女性必须写自己,“让身体被听见”(1etting the body be heard)。
此外,以纪丽安·罗斯为代表的后现代空间女权主义批判理论,也都用各种不同方法探究都市空间体验,“这些探究的核心处,是种对身体重新燃起的浓厚兴趣,把它看作个人和政治空间的最隐秘点,一切其他空间的一个情感小宇宙”。
上述诸多理论开启了从身体层面思考中国女性生存的先河,身体在文学的缝隙处生长起来,成为女性自我拯救的诺亚方舟。
正如列斐伏尔指出的那样“整个空间都是从身体开始的,不管它如何将身体变形以至于彻底忘记了身体,也不管它如何与身体彻底决裂以至于要消灭身体,只有立足于最接近我们的秩序,即身体秩序,才能对遥远的秩序(国家的、全球的)的起源问题做出解释。
”身体构成了我们思考女性解放,建构平等社会秩序的基础。
只要女性的身体依然被男性政治权力所征用,不能真正从身体出发思考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的话语都将陷入形而上学的谵妄之中。
身体作为在“思想与感情之后,立着的一个强大的主宰”,存在着反抗权力的能量,因此在民族国家和阶级革命文学的宏大叙事中,我们看到权力机制总是企图策略性地控制身体,征服身体中四处乱窜的力量,并将其改造为政治和道德教育的基地,而身体自身的价值却被消解,放逐于公众的视野之外。
即便是在彰显个性自我、追逐形式革新、热衷语言
试验的先锋派作家笔下,身体也始终处于缺席的地位,文学关于身体的书写一片空白。
“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没有身体的解放就没有真正的人的解放,社会平等与解放更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