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的桃源情结
《聊斋志异》中的爱情故事有哪些深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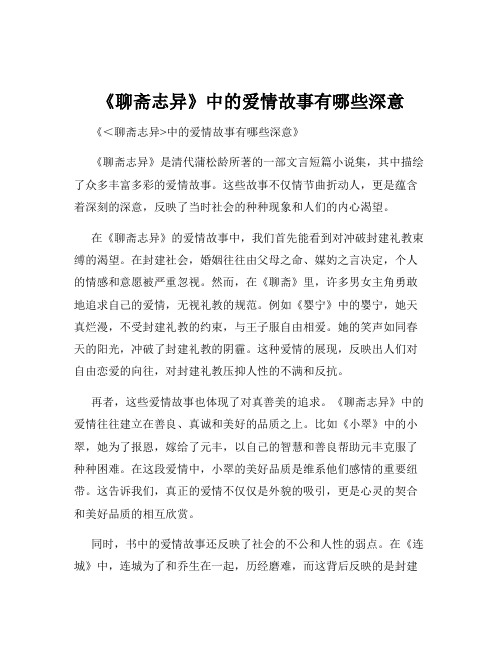
《聊斋志异》中的爱情故事有哪些深意《<聊斋志异>中的爱情故事有哪些深意》《聊斋志异》是清代蒲松龄所著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其中描绘了众多丰富多彩的爱情故事。
这些故事不仅情节曲折动人,更是蕴含着深刻的深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现象和人们的内心渴望。
在《聊斋志异》的爱情故事中,我们首先能看到对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渴望。
在封建社会,婚姻往往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个人的情感和意愿被严重忽视。
然而,在《聊斋》里,许多男女主角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无视礼教的规范。
例如《婴宁》中的婴宁,她天真烂漫,不受封建礼教的约束,与王子服自由相爱。
她的笑声如同春天的阳光,冲破了封建礼教的阴霾。
这种爱情的展现,反映出人们对自由恋爱的向往,对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的不满和反抗。
再者,这些爱情故事也体现了对真善美的追求。
《聊斋志异》中的爱情往往建立在善良、真诚和美好的品质之上。
比如《小翠》中的小翠,她为了报恩,嫁给了元丰,以自己的智慧和善良帮助元丰克服了种种困难。
在这段爱情中,小翠的美好品质是维系他们感情的重要纽带。
这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不仅仅是外貌的吸引,更是心灵的契合和美好品质的相互欣赏。
同时,书中的爱情故事还反映了社会的不公和人性的弱点。
在《连城》中,连城为了和乔生在一起,历经磨难,而这背后反映的是封建社会门第观念对爱情的阻碍。
有权有势的人家可以凭借自己的地位和财富,随意破坏他人的爱情。
这种情节揭示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公,让人们对封建社会的腐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此外,《聊斋志异》中的爱情也展现了对理想伴侣的憧憬。
在许多故事中,男主角往往是贫困书生,而女主角多为美丽善良的狐仙、女鬼等。
这些女性不仅容貌出众,而且聪慧过人、善解人意。
她们对书生不离不弃,帮助他们克服生活中的困难,实现人生的价值。
这反映了当时书生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对理想伴侣的渴望。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爱情故事还蕴含着对生死观的思考。
在《聊斋》中,人与鬼、人与狐的爱情屡见不鲜。
品析《聊斋志异》之爱情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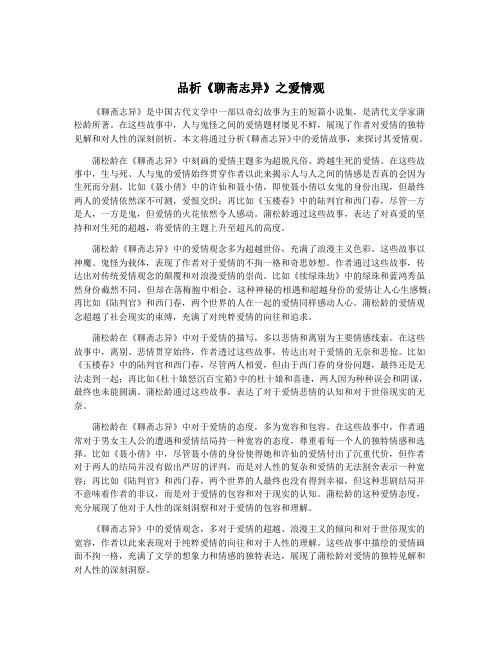
品析《聊斋志异》之爱情观《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部以奇幻故事为主的短篇小说集,是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所著。
在这些故事中,人与鬼怪之间的爱情题材屡见不鲜,展现了作者对爱情的独特见解和对人性的深刻剖析。
本文将通过分析《聊斋志异》中的爱情故事,来探讨其爱情观。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刻画的爱情主题多为超脱凡俗、跨越生死的爱情。
在这些故事中,生与死、人与鬼的爱情始终贯穿作者以此来揭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否真的会因为生死而分割。
比如《聂小倩》中的许仙和聂小倩,即使聂小倩以女鬼的身份出现,但最终两人的爱情依然深不可测,爱恨交织;再比如《玉楼春》中的陆判官和西门春,尽管一方是人,一方是鬼,但爱情的火花依然令人感动。
蒲松龄通过这些故事,表达了对真爱的坚持和对生死的超越,将爱情的主题上升至超凡的高度。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爱情观念多为超越世俗,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这些故事以神魔、鬼怪为载体,表现了作者对于爱情的不拘一格和奇思妙想。
作者通过这些故事,传达出对传统爱情观念的颠覆和对浪漫爱情的崇尚。
比如《续绿珠劫》中的绿珠和蓝鸿秀虽然身份截然不同,但却在落梅胞中相会,这种神秘的相遇和超越身份的爱情让人心生感慨;再比如《陆判官》和西门春,两个世界的人在一起的爱情同样感动人心。
蒲松龄的爱情观念超越了社会现实的束缚,充满了对纯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对于爱情的描写,多以悲情和离别为主要情感线索。
在这些故事中,离别、悲情贯穿始终,作者透过这些故事,传达出对于爱情的无奈和悲怆。
比如《玉楼春》中的陆判官和西门春,尽管两人相爱,但由于西门春的身份问题,最终还是无法走到一起;再比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和喜逢,两人因为种种误会和阴谋,最终也未能圆满。
蒲松龄通过这些故事,表达了对于爱情悲情的认知和对于世俗现实的无奈。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对于爱情的态度,多为宽容和包容。
在这些故事中,作者通常对于男女主人公的遭遇和爱情结局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尊重着每一个人的独特情感和选择。
《聊斋志异》涉仙题材与蒲松龄的“寒士”文化心理

古代文学研究NG NG 5聊斋志异6涉仙题材与蒲松龄的/寒士0文化心理侯学智一、道教仙境:失意文人的桃源追寻蒲松龄笔下神仙世界是令人神往的,这些仙人们所居住的天宫洞府与人间的黑暗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是理想的精神家园:这里环境优美,四季如春,/时十月中,山花满路,不类初冬。
0/异彩之禽,驯人不惊,声如笙簧,时来鸣于坐上。
0(5成仙6)即使是隆冬季节,湖上照样/弥望青葱,间以菡萏。
转瞬间,万枝千朵,一齐都开,朔风吹来,荷香沁脑。
0(5寒月芙蕖6)/时方严冬,,觉气候顿暖,似三月初旬。
又至亭中,益暖,异鸟成群,乱弄清味,仿佛暮春时。
亭中几案,皆镶以瑙玉。
有一水晶屏,莹澈可鉴,中有花树摇曳,开落不一;又有白禽似雪,往来句耪于其上。
以手抚之,殊无一物。
0(5丐仙6)天上的广寒宫:/内以水晶为阶,行人如在镜中。
0/檐外清水白沙,涓涓流溢,玉砌雕栏,殆似桂阙。
0镜里画外,亦真亦幻,妙不可言。
月宫口朱车舟中树茂花香,/桂树两章,参空合抱,花气随风,香无断际,亭宇皆红0。
宫中的丽人/冶容秀骨,旷世并无其俦。
0(5白于玉6)如此令人神往、美妙缥缈的仙境,当然不可能在现实中找到,这正是蒲松龄所向往的一种理想的桃源境界。
在5聊斋志异6中,神仙世界还是幸福美好、自由自在的理想王国。
在凡间,人们一生只为稻粱谋,可在这里,人们无忧无虑,衣食无愁:/取大叶类芭蕉,剪缀作衣0, /取而审视,则绿锦滑绝0。
/取山叶呼作饼,食之,果饼;又剪作鸡、鱼烹之,皆如真者。
0(5翩翩6)制草具数枝,布置如法,则/转眼化为巨第0;抛素练一匹,则转眼/化为长堤,其阔盈丈0。
(5仙人岛6)在这里,黑夜也并不可怕:/剪纸如镜,粘壁间。
俄顷,月明辉室,光鉴毫芒。
0还可以邀嫦娥翩翩起舞:/以箸掷月中。
见一美人自光中出。
初不盈尺;至地,遂与人等。
纤腰秀项,翩翩作-霓裳舞.。
已而歌曰:-仙仙乎,而还乎,而幽我于广寒乎!.其声清越,烈如箫管。
歌毕,盘旋而起,跃登几上。
聊斋志异偷桃故事概括

聊斋志异偷桃故事概括
《聊斋志异》中《偷桃》故事概述:
有一对卖艺的父子,在立春前一天来到布政司衙门门口表演“偷仙桃”戏法。
因为这对父子扬言自己能“颠倒生物”,所以命其在无桃季节中变出桃子。
父亲表示人间无桃,只有天上才有,随后拿出一根绳索扔到天上,绳索越升越高,直至没入云端。
父亲让儿子顺着绳索往上爬,不久儿子就从天上掉下一只碗大的桃子。
术人拿着桃子献给官员,官员们传看良久,辨别不出桃子的真假。
过了一会,绳索掉到地上,术人大惊,认为儿子被神仙发现了。
紧接着,儿子的头和四肢都从天上掉下来。
术人把肢体捡起来放到笥里盖好,大哭道:“我只有一个儿子,而今惨死,求各位老爷赏点钱安葬。
”满座之人又惊又骇,纷纷拿出赏钱,术人把钱装在身上,对着笥里喊道:“儿子,还不出来谢赏?” 忽然一个蓬头童子从笥里钻了出来朝堂上磕头致谢。
品析《聊斋志异》之爱情观

品析《聊斋志异》之爱情观《聊斋志异》是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故事中展现了许多关于爱情的故事。
这些故事从各个角度探讨了爱情的本质、形式和变化,展现了作者对于爱情的独特理解和深刻品析。
在本文中,我们将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聊斋志异》中的爱情观。
我们可以从作者的角度入手,品析《聊斋志异》中的爱情观。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是一位浪漫主义作家,他对于爱情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敏锐的洞察力。
在他的笔下,爱情并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更是一种超越时空的精神交流。
在他的故事里,爱情常常承载着对于人性的触摸、对于道德伦理的考量,以及对于世俗尘世的超越。
蒲松龄用他敏锐的笔触和深刻的情感揭示了爱情的本质和形态,使得故事中的爱情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表达,更是一种道德操守和人性解构。
我们可以从故事情节中品析《聊斋志异》中的爱情观。
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通过一系列离奇、奇幻的故事情节展示了爱情的多样性和变化。
有些故事中的爱情是单纯美好的,如《玉楼春》中的张生和玉楼,两人只因相爱而被天地万物阻挡,他们的纯洁的爱情感动了神仙,最终得以圆满。
有些故事中的爱情则是扭曲痴迷的,如《脂砚斋》中的陆判,他为了爱情可以不择手段,最终落得个魂飞魄散的下场。
这些故事情节既展示了爱情的美好,又揭露了爱情的阴暗面,使得《聊斋志异》中的爱情观变得丰富多彩。
我们可以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入手,品析《聊斋志异》中的爱情观。
《聊斋志异》中的爱情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表达,更是一种文学艺术的展现。
蒲松龄巧妙地运用了鬼神、妖怪、幻境等元素,使得他的故事不仅仅有了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空间,更增添了一丝超现实主义的魅力。
在这些奇幻的故事情节中,爱情变得更加奇特,更加超越,以至于读者通过这些故事深刻地品析了爱情的神秘和魔力。
这种文学艺术的表现方式使得《聊斋志异》成为了一部关于爱情的文学经典,永远不会过时。
通过不同的角度从作者、故事情节和文学艺术进行品析,《聊斋志异》中的爱情观展现出了丰富多彩的一面。
人异之恋的桃花源模式——兼论《聊斋志异》情爱故事思想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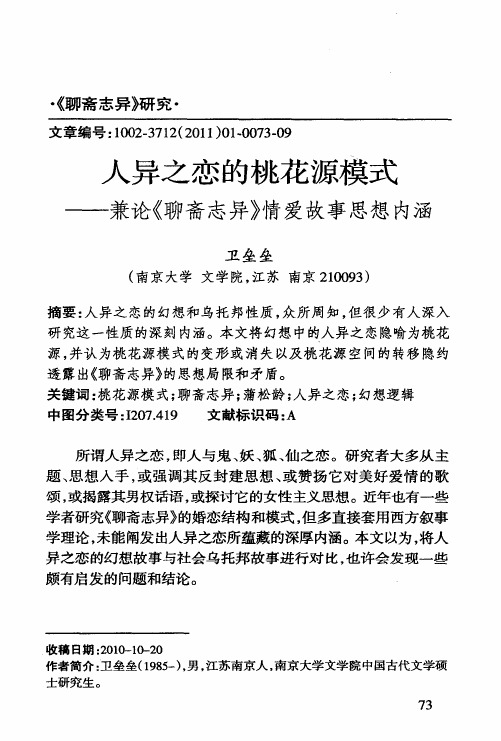
①马瑞 芳 :从 ( 斋志异 > ( 《 聊 到 红楼 梦> , 》 山东教 育出版 社 2 0 版 , 3 04年 第 5
页。
74
个 过 程也 暗含 了人 与异 类 的恋爱 经 过 : 遇— 婚恋— 结 局 ①。 相 这里 存在 两个 时空 , 域 和现 实 人 间 。鲁迅 在 评 《 斋 志异 》 异 聊 时 , 两 句话 “ 有 出于幻 域 , 人 人 间 ” 恰 可很 好 地 概括 这 种 爱情 顿 ②,
异 之恋 的幻想 故 事与 社会 乌 托邦 故 事 进行 对 比 , 也许 会发 现 一些 颇 有启 发 的问题 和结 论 。
收 稿 日期 :00 1- 0 2 1— 0 2 作 者 简 介 : 垒 垒 (9 5 )男 , 苏 南 京 人 , 京 大 学 文 学 院 中国 古代 文 学 硕 卫 1 8一 , 江 南 士研究生 。
从 现实 开始 , 入 异域 , 最终返 回现实 的三 部 曲。 进 并
由于现 实本 身 的缺 陷和人 们对 现 实 的不 满 , 在任 何社 会 都存 在着对于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设想 , 文学作品中关于乌托邦 的构思 也层出不穷。在 中国古代 , 诗经 ・ 鼠》 逝将去女 , 从《 硕 中“ 适彼乐 土” 的乐 土 , 老子》 邻国相望 , 到《 “ 鸡犬之声相 闻, 民至老死 , 不相 往来 ” 的小 国寡 民 , 到 陶渊 明 笔下 诗 情 画意 而 虚无 缥 缈 的桃 花 再 源 , 国人 的乌 托 邦之 梦越 来越 具体 , 中 不惟 可 见 , 能够 进入 。可 且 是 与其 说 它存 在 于现实 中一个 不为人 知 的角 落 , 不如 说 它 只存在 于人 民的幻想 中 , 以渔人 遇而 复失 。人们 向往 桃花 源 , 所 同时也清 醒地意识 到它 的幻 想性 。中国式 的乌托邦 因为 中 国人 的实用 性逻 辑 在建 立 的同 时就 被拆解 了。这 是 中 国式 乌 托邦 的命 运 , 总要 人
品析《聊斋志异》之爱情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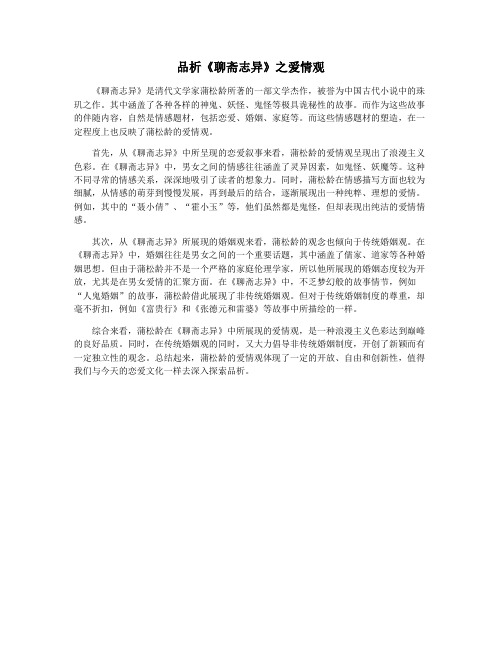
品析《聊斋志异》之爱情观《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所著的一部文学杰作,被誉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珠玑之作。
其中涵盖了各种各样的神鬼、妖怪、鬼怪等极具诡秘性的故事。
而作为这些故事的伴随内容,自然是情感题材,包括恋爱、婚姻、家庭等。
而这些情感题材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蒲松龄的爱情观。
首先,从《聊斋志异》中所呈现的恋爱叙事来看,蒲松龄的爱情观呈现出了浪漫主义色彩。
在《聊斋志异》中,男女之间的情感往往涵盖了灵异因素,如鬼怪、妖魔等。
这种不同寻常的情感关系,深深地吸引了读者的想象力。
同时,蒲松龄在情感描写方面也较为细腻,从情感的萌芽到慢慢发展,再到最后的结合,逐渐展现出一种纯粹、理想的爱情。
例如,其中的“聂小倩”、“霍小玉”等,他们虽然都是鬼怪,但却表现出纯洁的爱情情感。
其次,从《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婚姻观来看,蒲松龄的观念也倾向于传统婚姻观。
在《聊斋志异》中,婚姻往往是男女之间的一个重要话题,其中涵盖了儒家、道家等各种婚姻思想。
但由于蒲松龄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家庭伦理学家,所以他所展现的婚姻态度较为开放,尤其是在男女爱情的汇聚方面。
在《聊斋志异》中,不乏梦幻般的故事情节,例如“人鬼婚姻”的故事,蒲松龄借此展现了非传统婚姻观。
但对于传统婚姻制度的尊重,却毫不折扣,例如《富贵行》和《张德元和雷婆》等故事中所描绘的一样。
综合来看,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所展现的爱情观,是一种浪漫主义色彩达到巅峰的良好品质。
同时,在传统婚姻观的同时,又大力倡导非传统婚姻制度,开创了新颖而有一定独立性的观念。
总结起来,蒲松龄的爱情观体现了一定的开放、自由和创新性,值得我们与今天的恋爱文化一样去深入探索品析。
聊斋志异中的爱情主题

聊斋志异中的爱情主题在偌大的文学世界里,每一个有生命力的文本都埋藏着其所属的时代特征与文化底蕴。
明代文学大师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不仅记载了许多千奇百怪的传说故事,更融入了作者的思想观念、文学审美与情感体验。
其中,爱情作为一种至死不渝、跨越生死的感情主题,在《聊斋志异》中得到了精彩的诠释。
一、超脱世俗束缚的爱情在《聊斋志异》中,不少故事中的爱情都是超越了人世间的种种界限和桎梏的。
其中尤以《牛郎织女》和《草木仙》最为代表性。
《牛郎织女》追寻爱情的过程就是最大程度的诠释了人类内心深处爱情的力量,它无时无刻不在生活中潜移默化,它是让人向往、动容的,即使在物离人不离的痛苦中也不曾改变,时间,空间和桎梏的束缚都无法削弱它的力量。
而《草木仙》则通过仙人与人间姑娘对爱情的坚守,来探讨爱情关系的超越性,表达了作者穿越凡尘追求爱情的高远与卓尔不凡。
这些故事展示了自由、坚定不移的爱情,颠覆了传统家庭和社会的结构,呼唤了爱情自由的声音。
二、执念坚定的鬼怪恋情在《聊斋志异》的故事中,鬼怪恋情是作者所钟爱的一个主题,因为它向我们演示了一种超越时间,生死,种族,甚至是人与妖之间的界限的执念和坚定。
在《莺莺传》中,美丽的女鬼洁身自好,深情依恋一个人,为了守住爱情不顾一切,即使无法亲自赴约,也要化成绚烂的配戏,为忠诚的后续者保驾护航。
而在《聂小倩》中,聂小倩为爱一心一意,牺牲自己的肉身和精神,成为草木的精魂,终于于倪秀才食尽松花江,永别人世。
这些故事中的鬼怪恋情表达了作者对一种不被俗世所理解的、超越时间和生死的爱情的赞美。
三、跨越界限的文化融合明朝时期有着丰富的文化多样性,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在文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表达。
在《聊斋志异》的许多故事中,跨越种族、民族、文化的爱情更是引人入胜。
巨鹿女与卓文君的故事中,穿插其中的金陵、洛阳双城的对比和战略性的视角,使得故事具备了更深入的历史,社会风貌,气象万千,扣人心弦。
而混血女鬼何小妹和上官婉儿的故事,则通过妙语连珠的交锋和卓越的机智才智,激起了人们对文化融合、和谐发展的向往和神往。
品析《聊斋志异》之爱情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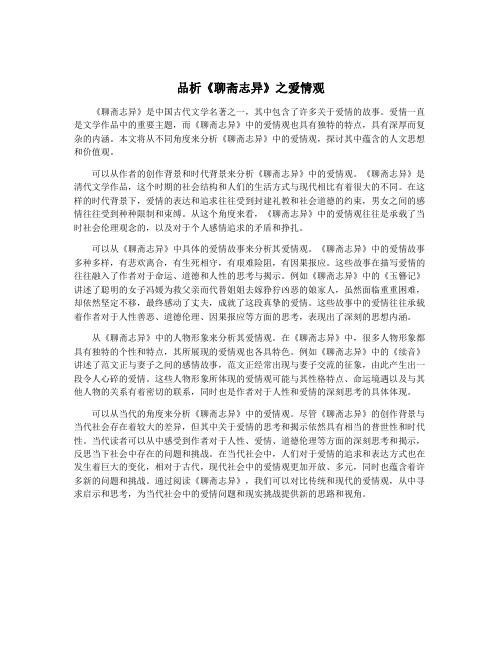
品析《聊斋志异》之爱情观《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学名著之一,其中包含了许多关于爱情的故事。
爱情一直是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主题,而《聊斋志异》中的爱情观也具有独特的特点,具有深厚而复杂的内涵。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来分析《聊斋志异》中的爱情观,探讨其中蕴含的人文思想和价值观。
可以从作者的创作背景和时代背景来分析《聊斋志异》中的爱情观。
《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作品,这个时期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现代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爱情的表达和追求往往受到封建礼教和社会道德的约束,男女之间的感情往往受到种种限制和束缚。
从这个角度来看,《聊斋志异》中的爱情观往往是承载了当时社会伦理观念的,以及对于个人感情追求的矛盾和挣扎。
可以从《聊斋志异》中具体的爱情故事来分析其爱情观。
《聊斋志异》中的爱情故事多种多样,有悲欢离合,有生死相守,有艰难险阻,有因果报应。
这些故事在描写爱情的往往融入了作者对于命运、道德和人性的思考与揭示。
例如《聊斋志异》中的《玉簪记》讲述了聪明的女子冯媛为救父亲而代替姐姐去嫁狰狞凶恶的娘家人,虽然面临重重困难,却依然坚定不移,最终感动了丈夫,成就了这段真挚的爱情。
这些故事中的爱情往往承载着作者对于人性善恶、道德伦理、因果报应等方面的思考,表现出了深刻的思想内涵。
从《聊斋志异》中的人物形象来分析其爱情观。
在《聊斋志异》中,很多人物形象都具有独特的个性和特点,其所展现的爱情观也各具特色。
例如《聊斋志异》中的《续音》讲述了范文正与妻子之间的感情故事,范文正经常出现与妻子交流的征象,由此产生出一段令人心碎的爱情。
这些人物形象所体现的爱情观可能与其性格特点、命运境遇以及与其他人物的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是作者对于人性和爱情的深刻思考的具体体现。
可以从当代的角度来分析《聊斋志异》中的爱情观。
尽管《聊斋志异》的创作背景与当代社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其中关于爱情的思考和揭示依然具有相当的普世性和时代性。
浅谈《聊斋志异》中的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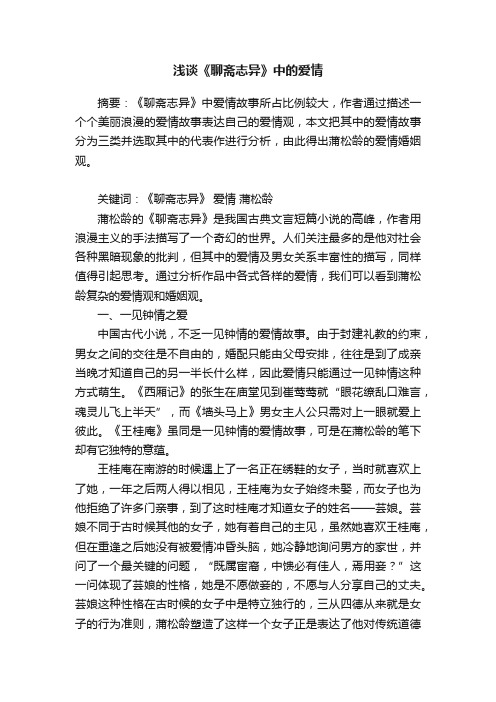
浅谈《聊斋志异》中的爱情摘要:《聊斋志异》中爱情故事所占比例较大,作者通过描述一个个美丽浪漫的爱情故事表达自己的爱情观,本文把其中的爱情故事分为三类并选取其中的代表作进行分析,由此得出蒲松龄的爱情婚姻观。
关键词:《聊斋志异》爱情蒲松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我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的高峰,作者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描写了一个奇幻的世界。
人们关注最多的是他对社会各种黑暗现象的批判,但其中的爱情及男女关系丰富性的描写,同样值得引起思考。
通过分析作品中各式各样的爱情,我们可以看到蒲松龄复杂的爱情观和婚姻观。
一、一见钟情之爱中国古代小说,不乏一见钟情的爱情故事。
由于封建礼教的约束,男女之间的交往是不自由的,婚配只能由父母安排,往往是到了成亲当晚才知道自己的另一半长什么样,因此爱情只能通过一见钟情这种方式萌生。
《西厢记》的张生在庙堂见到崔莺莺就“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上半天”,而《墙头马上》男女主人公只需对上一眼就爱上彼此。
《王桂庵》虽同是一见钟情的爱情故事,可是在蒲松龄的笔下却有它独特的意蕴。
王桂庵在南游的时候遇上了一名正在绣鞋的女子,当时就喜欢上了她,一年之后两人得以相见,王桂庵为女子始终未娶,而女子也为他拒绝了许多门亲事,到了这时桂庵才知道女子的姓名——芸娘。
芸娘不同于古时候其他的女子,她有着自己的主见,虽然她喜欢王桂庵,但在重逢之后她没有被爱情冲昏头脑,她冷静地询问男方的家世,并问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既属宦裔,中馈必有佳人,焉用妾?”这一问体现了芸娘的性格,她是不愿做妾的,不愿与人分享自己的丈夫。
芸娘这种性格在古时候的女子中是特立独行的,三从四德从来就是女子的行为准则,蒲松龄塑造了这样一个女子正是表达了他对传统道德对女子束缚的不满,也为下文芸娘投江作了性格上的铺垫。
在经过自己的试探之后,终于芸娘明确地告诉王桂庵要明媒正娶将自己娶过门,他们在爱情里是平等的,在婚姻中也必须是平等的。
历经波折,王桂庵终于如愿抱得美人归,但却由于自己的一句玩笑话,芸娘投江了。
品析《聊斋志异》之爱情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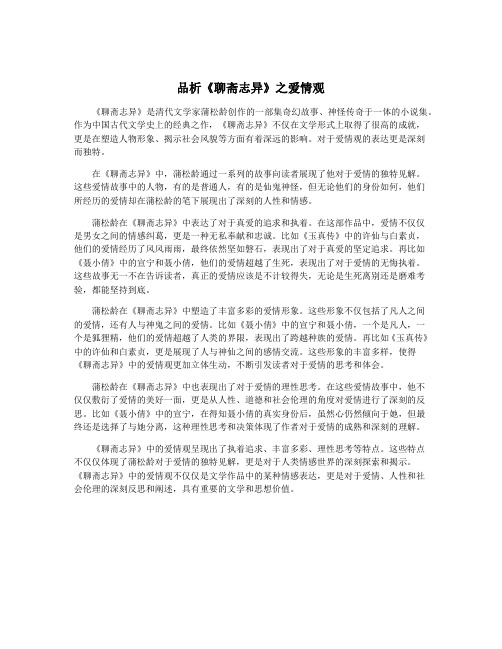
品析《聊斋志异》之爱情观《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创作的一部集奇幻故事、神怪传奇于一体的小说集。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聊斋志异》不仅在文学形式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更是在塑造人物形象、揭示社会风貌等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
对于爱情观的表达更是深刻而独特。
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通过一系列的故事向读者展现了他对于爱情的独特见解。
这些爱情故事中的人物,有的是普通人,有的是仙鬼神怪,但无论他们的身份如何,他们所经历的爱情却在蒲松龄的笔下展现出了深刻的人性和情感。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表达了对于真爱的追求和执着。
在这部作品中,爱情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更是一种无私奉献和忠诚。
比如《玉真传》中的许仙与白素贞,他们的爱情经历了风风雨雨,最终依然坚如磐石,表现出了对于真爱的坚定追求。
再比如《聂小倩》中的宣宁和聂小倩,他们的爱情超越了生死,表现出了对于爱情的无悔执着。
这些故事无一不在告诉读者,真正的爱情应该是不计较得失,无论是生死离别还是磨难考验,都能坚持到底。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丰富多彩的爱情形象。
这些形象不仅包括了凡人之间的爱情,还有人与神鬼之间的爱情。
比如《聂小倩》中的宣宁和聂小倩,一个是凡人,一个是狐狸精,他们的爱情超越了人类的界限,表现出了跨越种族的爱情。
再比如《玉真传》中的许仙和白素贞,更是展现了人与神仙之间的感情交流。
这些形象的丰富多样,使得《聊斋志异》中的爱情观更加立体生动,不断引发读者对于爱情的思考和体会。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也表现出了对于爱情的理性思考。
在这些爱情故事中,他不仅仅敷衍了爱情的美好一面,更是从人性、道德和社会伦理的角度对爱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比如《聂小倩》中的宣宁,在得知聂小倩的真实身份后,虽然心仍然倾向于她,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与她分离,这种理性思考和决策体现了作者对于爱情的成熟和深刻的理解。
《聊斋志异》中的爱情观呈现出了执着追求、丰富多彩、理性思考等特点。
异代知己:蒲松龄的“陶渊明情结”及其文学表现

异代知己:蒲松龄的“陶渊明情结”及其文学表现作者:徐文翔来源:《蒲松龄研究》2018年第04期摘要:蒲松龄可以说是陶渊明的异代知己。
蒲松龄具有“陶渊明情结”,性情上的相通是根本缘由,此外,爱好和个人际遇的相似也促进了情结的形成。
作为杰出的文学家,蒲松龄对这份“陶渊明情结”进行了富有内涵的文学表现,如对陶渊明诗文及典故的化用、对“桃源”意象的书写和借《聊斋志异·黄英》对自己心目中陶渊明进行解构等。
关键词:蒲松龄;陶渊明情结;酒与菊;桃源;黄英中图分类号:I207.419; ; 文献标识码:A陶渊明在文学上的经典地位确立之后,历代皆不乏崇拜者。
他们或仰慕陶渊明的人格,或追步陶渊明的文字,甚或二者皆有,可以形成一部“陶渊明接受史”。
在这部“接受史”中,有一位堪称陶渊明的异代知己,这就是清初著名文学家蒲松龄。
蒲松龄生活的年代,去陶渊明约1300年,虽相隔久远,世殊事异,但蒲松龄却从精神层面对陶渊明有着深刻的体认,不仅自己秉持一份“陶渊明情结”,还将此种情结倾注于创作中,形成了富有内涵的文学表现。
一、蒲松龄的“陶渊明情结”之形成心理学认为,“情结”是由有关观念、情感、意象的综合体。
对一位人物的情感深化至“情结”层面,除了对此人行为、品质的认同外,还要有心灵上的相通与共鸣。
蒲松龄能够形成“陶渊明情结”,并不是偶然的,可从三个层面来阐释。
1、性情层面蒲松龄对陶渊明的倾慕,性情上的相通是最根本的缘起。
陶渊明是东晋时期魏晋风度的典型人物,而蒲松龄亦深得“魏晋三味”。
在《聊斋自志》中,蒲松龄这样形容自己:“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
” [1]1 这句话中的三个关键字“狂”“旷”“痴”,便是蒲松龄对于魏晋风度中“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解读。
在具体的人生实践中,蒲松龄处处以陶渊明作为典范。
如“鸥眠春风暖日,会知陶处士醉里之风流” [2]10 ,此处“会知”一词,形容极为贴切。
在《荒园小构落成,有丛柏当门,颜曰绿屏斋》(其五)中,蒲松龄抒发新居建成之欣喜,写道:“须知膏火寒窗下,也有羲皇好梦来。
品析《聊斋志异》之爱情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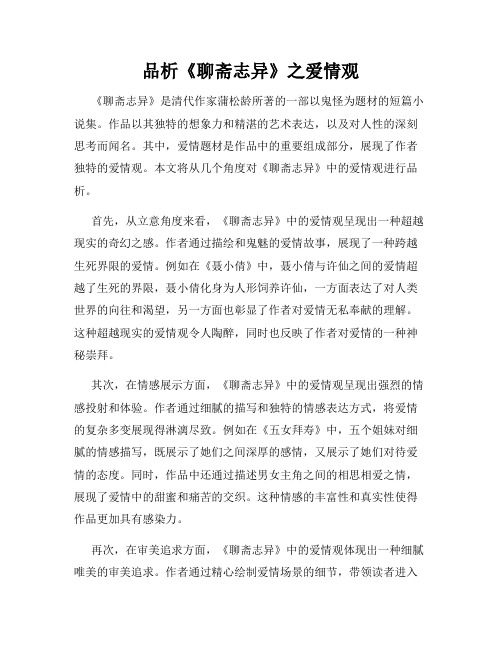
品析《聊斋志异》之爱情观《聊斋志异》是清代作家蒲松龄所著的一部以鬼怪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集。
作品以其独特的想象力和精湛的艺术表达,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思考而闻名。
其中,爱情题材是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了作者独特的爱情观。
本文将从几个角度对《聊斋志异》中的爱情观进行品析。
首先,从立意角度来看,《聊斋志异》中的爱情观呈现出一种超越现实的奇幻之感。
作者通过描绘和鬼魅的爱情故事,展现了一种跨越生死界限的爱情。
例如在《聂小倩》中,聂小倩与许仙之间的爱情超越了生死的界限,聂小倩化身为人形饲养许仙,一方面表达了对人类世界的向往和渴望,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作者对爱情无私奉献的理解。
这种超越现实的爱情观令人陶醉,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对爱情的一种神秘崇拜。
其次,在情感展示方面,《聊斋志异》中的爱情观呈现出强烈的情感投射和体验。
作者通过细腻的描写和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将爱情的复杂多变展现得淋漓尽致。
例如在《五女拜寿》中,五个姐妹对细腻的情感描写,既展示了她们之间深厚的感情,又展示了她们对待爱情的态度。
同时,作品中还通过描述男女主角之间的相思相爱之情,展现了爱情中的甜蜜和痛苦的交织。
这种情感的丰富性和真实性使得作品更加具有感染力。
再次,在审美追求方面,《聊斋志异》中的爱情观体现出一种细腻唯美的审美追求。
作者通过精心绘制爱情场景的细节,带领读者进入到一种诗境般的唯美世界。
例如在《艳娘》中,作者对女主角风姿绰约的描写,使得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纯洁。
这种唯美的审美追求不仅仅是对爱情的赞美,更是表达了作者对于美的敏感和执着。
最后,可以从道德反思的角度对《聊斋志异》中的爱情观进行品析。
作品中的爱情故事多有不合常理之处,甚至涉及到不道德的行为。
例如在《钟馗捉妖》中,钟馗与妖怪春宵一夜,违背了社会道德和伦理规范。
这种对于道德的反思使得作品更加丰富和深刻,也带给读者对于爱情的一种思考。
综上所述,《聊斋志异》中的爱情观呈现出超越现实的奇幻之感,表达了作者对爱情无私奉献的理解;展示了强烈的情感投射和体验,通过细腻的描写和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展现了爱情的复杂多变;体现了细腻唯美的审美追求,通过精心构建爱情场景的细节,带领读者进入到一种诗境般的唯美世界;同时,从道德反思的角度对爱情进行审视,使得作品更加丰富和深刻。
《聊斋志异》读后感3000字 美妙音律世外桃源

《聊斋志异》读后感3000字美妙音律世外桃源聊斋志异是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龄所创作的一部神怪小说集,内容涉及鬼魅、妖精、仙人、僵尸等超自然现象。
读完这部小说,我被其中美妙的音律所吸引,仿佛置身于一个世外桃源之中。
以下是我的读后感。
聊斋志异中的音乐元素渗透在每个故事之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论是妖精的歌声,还是仙女的音乐,都令人心旷神怡。
其中一篇故事《画壁》中,壁画中的女子与男子之间的呼应和对话,仿佛是一场动听的音乐会。
音符在心头起舞,让我仿佛听到了优美的旋律。
作者通过音乐元素的渗透,增强了故事的吸引力,使我沉浸其中。
在聊斋志异中,音律的作用不仅仅是为了增加故事的趣味性,更是对人性和情感的一种表达。
在《牡丹亭》中,音乐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杜丽娘的哀怨歌声,使得柳梧桐感受到了她心中的无尽思念。
音符传达了深深的情感,使得读者能够感同身受,被故事中的人物所打动。
音律的美妙与情感的共鸣相互辉映,使故事更加生动。
此外,聊斋志异中的音律也传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在《偷桃》这个故事中,桃树精凭借其出色的音律技巧,打动了人们的心灵。
音符的流淌让人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力量与魅力。
音乐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桥梁,让人们与自然和谐共生。
读完《聊斋志异》,我不仅对其中的故事情节和写作手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被其中美妙的音律所折服。
音乐元素的运用使得故事更加生动,情感更加真切,让人能够更好地投入其中。
通过音乐,作者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世外桃源的大门,让人们沉醉在美妙的音律之中。
总而言之,聊斋志异读后让我深深感受到了音律的魅力,仿佛置身于一个世外桃源之中。
音乐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达,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和沟通工具。
通过对音律的包装,作者赋予了故事更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读完聊斋志异,我更加意识到了音乐的奇妙之处,能够将人们带入一个与世界相隔离的美妙境地。
在音律的指引下,读者可以尽情享受文学作品带来的美妙体验,仿佛置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聊斋志异》中的桃源情结

作者: 侯学智
作者机构: 山东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潍坊261061
出版物刊名: 电影文学
页码: 89-90页
主题词: 《聊斋志异》;桃源情结;道教;功名情结
摘要: 在《聊斋志异》许多作品中,蒲松龄演绎了一个下层文人理想中的生活境界,反映出作者作为文人士子所具有的深重的桃源情结,这种超凡性表达了世人企图超越世俗局限的幻想。
而这种太虚幻境以及理想境界的超凡性,更加注重了世俗内容和欲望的实现。
蒲松龄的桃源情结与他的功名情结以及仕途遭遇是密切相关的。
同枝异花各擅其妙——论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双美情节

收稿日期:2012⁃11⁃16作者简介:曾丽容(1977-),女,广东茂名人,文学硕士,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文法学院讲师。
·《聊斋志异》研究·文章编号:1002⁃3712(2013)02⁃0075⁃11同枝异花各擅其妙———论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双美情结曾丽容(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文法学院,广东茂名525000)摘要:本文通过《聊斋志异》中双女类型属性的配列及男性在这种坐拥双美中优越心理的阐析,可以透视积淀了数千年之久的男性中心文化观及女性边缘化的客体地位的历史现实。
男性精神与物质的两极价值追求在两位女性身上得到确证和实现,“双美”情结使这些仕途科第无望的书生获得了遗落的人生梦想实现的另类途径。
同时双美并秀中愈益衬托与彰显这些花妖狐鬼各自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聊斋志异;双美;情爱模式;精神补偿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识码:A《聊斋志异》中有不少情爱故事表现二位女性围绕着一位男性,形成双美并秀、双凤戏龙的“一男双女”情节,这在《聊斋志异》的众多婚恋故事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同枝上花开两朵,双美并秀,美者更美。
本文试图通过对二女类型属性的配列及出场先后的深层寓意,以及男性在这种坐拥双美中优越心理的显现,透视积淀了数千年之久的男性中心文化观及女性边缘化的客体地位的历史现实。
男性关乎精神和物质的价值追求在两位女性身上得75hts Reserved.到确证和实现,“双美”情结使这些仕途科第无望的书生获得了遗落的人生梦想实现的另类途径,精神得到了极大的慰藉与补偿。
一、双美的类型属性《聊斋志异》是一个由花妖狐鬼组成的美丽女儿世界,叙述书生与这些萍水相逢的女性的因缘际遇是聊斋情爱故事的突出特征。
不少情爱故事中,两位女性双双出现,如并蒂之莲,左右摇曳,别有风情。
蒲松龄在《小谢》中不由得感叹:“绝世佳人,求一而难之,何遽得两哉?[1](P779)”可能因为深感美人难得,尤其双美更甚, hts Reserved.故而作者在小说中展开丰富的想象力虚构了系列“一男双女”的双美故事。
《聊斋志异》中人异之恋的桃花源模式

《聊斋志异》中人异之恋的桃花源模式杨淑慧(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摘要】人异之恋的幻想和乌托邦性质众所周知,但很少有人深入研究这一性质的深刻内涵。
本文将幻想中的人异之恋隐喻为桃花源,并认为桃花源模式的变形或消失以及桃花源空间的转移隐约透露出《聊斋志异》的思想局限和矛盾。
【关键词】桃花源模式 聊斋志异 蒲松龄 人异之恋【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497(2011)01—0014-02第1期2011年1月现代阅读MODERN READINGNO.1January.2011序所谓人异之恋即人与鬼、妖、狐、仙之恋。
研究者大多从主题、思想入手,或强调反封建思想,或赞扬对美好爱情的歌颂,或突出男权话语,或探讨女权主义思想。
近年也有一些学者研究《聊斋志异》的婚恋结构和模式,但多直接套用西方叙事学理论,未能阐发出人异之恋所蕴藏的深厚内涵。
或许将人异之恋的幻想故事与社会乌托邦故事进行对比,会发现一些颇有启发的问题和结论。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记载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后来渐渐成为一个象征——一种中国式乌托邦的代称,在此后的一千多年广泛流传,深入人心。
故事可以简化为一个“进入桃花源—离开桃花源—返回桃花源—迷失桃花源”的过程,这是一个从现实开始,进入异域,并最终返回现实的三部曲。
这里存在两个时空,异域或者幻域和现实人间。
鲁迅在评《聊斋志异》时,有两句话“出于幻域,顿入人间”,恰可很好地概括这种爱情模式的特征。
或人入幻域,或幻入人世,在这种时空的自由穿梭中,实现部分爱情自由。
但这个异域(自由爱情的空间)无论在现实之外,还是在现实之内,都无法与现实抗衡,一旦与现实相碰,则瞬间变形或粉碎。
在婚姻制度和伦理纲常无所不在的时代,彻底的爱情自由平等是不能设想的,幻想的翅膀总是被现实击落。
然而它毕竟展示了一个由纯粹爱情组成的空间。
我们将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考察这一恋爱模式的表现、特征和意义。
一、由发生过程看《聊斋志异》的桃花源模式在发生过程中,根据桃花源的最终消失与否(因遭遇现实而发生),可分为两类:一类,情爱桃花源在遭遇到现实之后,无声消失,随之消失的是异类女性。
聊斋故事:桃花妻

聊斋故事:桃花妻宋朝时期,有个书生叫陆判,这陆判平常十分的寒酸,家徒四壁,要啥没啥,因为这样的败落家世,陆判迟迟找不上媳妇。
其他人很为陆判发愁,你没有媳妇,怎么传宗接代呢,可陆判却不以为然。
陆判摸着自己俊俏的脸,笑嘻嘻怒骂道,我啊,生的如此俊俏,迟早是能找到媳妇的,不急不急,就算我家徒四壁,娶媳妇有什么难呢,我还是继续读书才是当务之急。
人们看陆判如此不着四六,摇了摇头,陆判也不以为然,就这样继续沉浸在读书的快乐中,愉快的做了个贫穷简单的穷书生,酸书生,日子倒也过的悠哉。
某天陆判回家的路上,忽然发现,家附近的一颗桃花树居然开了,陆判有些惊喜的走到这桃花树边,仔细的观察。
陆判仔细的观察,观察着观察着,就十分惊奇。
陆判发现,这桃花树其实已经开在他家门口十年了,只是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开花过,一直都是个不开花的树。
今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春风更加温暖,还是这桃花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这十年不开花的桃花,如今居然一夕之间开花了,真乃奇观啊。
陆判越想越觉得侃侃撑奇,于是陆判提笔写下了一首桃花吟,写好后,陆判陶醉的不得了,忍不住摇头晃脑的在桃花树下仿佛朗诵,十分自娱自乐。
陆判陶醉了,于是心满意足的回到了房间里,一摸到床榻就呼呼大睡倒头睡下,等陆判醒来的时候,却发现,天啊,在自己的面前,居然多了个面如桃李的姑娘!面如桃李的姑娘?陆判大吃一惊,连忙结结巴巴的询问姑娘:“怎么回事?姑娘,你,你是何许人也……?你怎么会出现在我一个穷书生的房间里……”眼前这姑娘发现陆判醒来了,双眼中顿时十分惊喜,惊喜之后,姑娘捂住嘴唇,轻轻的一笑。
姑娘笑着道:“我啊,就是你家门口那颗桃花树啊,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已经成精了,太好了,从此就可以和你长相厮守了。
”陆判十分害怕,当下就拒绝:“不了,虽然姑娘你十分好看,如如同桃花一样明艳,但是啊,姑娘你和我长相厮守,是不是想要害我呢,那就算了,我可不敢和不是人类的姑娘长相厮守啊……”姑娘愣了一下,先是有些黯淡,随即又释然了。
聊斋故事:桃树精

聊斋故事:桃树精苏州的秀才吴子瑜家境富裕,他长得仪表堂堂,有着潘安宋玉般的容貌,在此地有名,前来提亲的媒婆都快踏破门槛了。
尤其是薛县令的女儿自从在庙会看到他后,竟然甚是仰慕他,回去后,很是思念他,嚷着要嫁给他。
薛县令只有这一个女儿,遂托人前去提亲。
可吴子瑜性子冷傲,竟然拒绝了。
他的父母很是忧愁,前来提亲的都是非富即贵,女子容貌俊美,真不知道他到底想找啥样的。
母亲吴氏总是携带丫鬟去庙里拜菩萨,祈祷他赶紧早日成亲,他们好早日抱孙子。
有一天,吴子瑜因为母亲的唠叨,心里烦闷,偷着跑出来和文友出去游玩。
两个人出了门,犹如出了笼子的小鸟,心情大好。
看到外面美景如画,两个人一边欣赏景色,一边兴高采烈的吟诗作赋,甚是惬意。
不知不觉的走出很远,他的文友看夕阳西下,想回去了。
可吴子瑜好不容易才偷着跑出来,怎会轻易回去。
文友只好自己回去,嘱咐他注意安全,便回去了。
吴子瑜继续往前走,过了会,前面忽然现一桃树林,一望无际,桃花开得正旺,整个一花海,微风徐徐吹来,花香四溢,让人陶醉。
吴子瑜兴奋地快步走过去,如痴如醉地欣赏着。
他虽是个男子,却犹如女子一样甚是喜爱花。
他的母亲总是调侃他真是托生错了,一个男子身,却长得犹如女子一样俊美,见人还有点羞涩,竟然还喜欢花。
他流连忘返的看着,竟然忘了回家,不知不觉地天快黑了,可他仍然痴痴在桃树林里欣赏着。
不大会,黑天了,他也累了,靠在一棵桃树下休息。
想着反正出来一次不容易,就不回家了,在此将就一夜,明天玩够了再回去,全然不知外面很危险。
过了会,他的身子疲乏无力,竟然睡过去了。
过了会,迷迷糊糊地听到有女子嬉笑的声音……睁开眼睛一看,此时,月亮出来了,月光下,约有七八个身着粉衣,长着仙姿玉貌的女子在树下翩翩起舞……舞姿优美,犹如仙女下凡。
吴子瑜呆呆傻傻地看着,觉得他们是仙女下凡来,大气不敢喘,生怕把她们吓跑。
他出生在富裕的家里,吃喝不愁,还有人伺候着,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母亲因为他性子单纯,容貌俊美,性子冷傲,从不让他出去抛头露面,犹如女儿家一样待在家里,只管读书。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聊斋志异》中的桃源情结
一
古代文人心目中的桃源有两种故事模式。
《幽明录》载,东汉时,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迷不得返,旬余粮绝。
绝望时,遥见远山有一桃树,果实累累,攀援而上,各吃数枚。
后翻山涉水,在一大滨旁遇二女子,资质绝妙,二女子一见如故,邀请二位还家,设宴款待。
当夜,温柔相待,刘、阮遂忘忧,作了新郎。
居十年,求归。
出山之后,家乡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
问讯,得七世孙。
后来,刘、阮不能适应现实,再度失踪,不知去向。
从内容上看,这是人仙相爱的故事,表达的却是“幸入”的模式。
另一种就是进入的虽不是神仙所居之所,却是与仙境无异的人间乐园,是理想中的“洞天福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两个桃源故事的精神其实是相通的,都体现了人们对一种理想境界的追求。
(更多最新电影新剧尽在 ) 蒲松龄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在《聊斋志异》的许多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下层文人理想中的生活境界。
在《翩翩》中,罗子浮被邪人引诱堕落,沾染恶疾,满身臭疮,污秽难闻,令人不齿,流浪山中,遇到仙女翩翩,被带至深山洞府。
“入则门横溪水,石梁架之。
又数武,有石室二,光明彻照,无须灯烛。
”翩翩以溪水为罗子浮疗疮,以蕉叶剪作美馔,以蕉叶裁作“绿锦滑绝”的衣裳,而掇拾洞口白云为絮,制作“温暖如襦,且轻松如新绵”的冬衣。
罗子浮在洞中,不仅病被治好了,而且结婚生子,生活安定,精神也得到净化。
一次,另一位仙女花城来访,罗子浮羡其美貌,暗中加以挑逗,“生方恍然神夺,顿觉袍裤无温;子顾所服,悉成秋叶。
几骇绝。
危坐移时,渐变如故”。
不久又加挑逗,“突突怔忡间,衣已化叶,移时始复变。
由是惭颜息虑,不敢妄想”。
15年后,罗子浮思念家人,携子返乡。
“后生思翩翩,携儿往探之,则黄叶满径,洞口路迷,零涕而返。
”这种遇仙故事陈述,从创作意识上说,与刘、阮故事是一致的。
蒲松龄笔下单纯的桃花源型故事并不多,而是多与天台山型故事交织在一起,并充满浓厚的道教色彩。
如《巩仙》一篇,写尚秀才的情人惠哥被王府抢去,痛苦不堪而又无可奈何。
幸得巩道士神通广大,让尚秀才在袖中与惠哥幽会、生子,成全了好事。
这既是一个爱情的故事,又是一个避世的故事。
袖里乾坤的描写,是受道教天人合一、人身是一个小宇宙的理论的影响,也是最早的道教神仙小说中的“壶中天地”这一叙述模式的继承与延续。
所以,异史氏曰:“袖里乾坤,古人之寓言耳,岂真有之耶?亦何其奇也!中有天地、有日月,可以娶妻生子,而又无催科之苦,人事之烦,则袖中虮虱,何殊桃源鸡犬哉!设容人常住,老于是乡可耳。
”一袖之间,包容了人间仙境。
道教的人间仙境在《聊斋志异》中有多姿多彩的展现。
蒲松龄笔下的许多遇仙故事,虽不都是典型的桃源故事,但作品所描述的洞天福地和其它道教胜境,令人心驰神往。
洞穴遇仙故事是与“桃花源”型故事联系在一起的,自从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描绘了一个人间世外桃源之后,洞穴仙窟便成为人们理想中的乌托邦。
《翩翩》中所描写的仙境——洞府,“入则门横溪水,石梁架之。
又数武,有石室二,光明彻照,无须灯烛”,是一处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安期岛》写刘洪训在安期岛上所见,“时方严寒,既至,则气候温煦,山花遍岩谷。
导入洞府,见三叟趺坐。
东西者见客入,漠若罔知;惟中坐者起迎客,相为礼。
既坐,呼茶。
有僮将盘去。
洞外石壁上有铁锥,锐没石中;僮拔锥,水即溢射,以盏承之;满,复塞之。
既而托至,其色淡碧。
试之,其凉震齿”,完全是世间凡人的理想生活之所;《丐仙》中高玉成救了一个身上长疮的乞丐,后听乞丐劝告避难山中,这里的景象是:严冬季节,温暖如春,异鸟成群。
亭中几案,皆镶以瑙玉。
一水晶屏,莹彻可鉴:中有花树摇曳,开落不一;又有各种珍奇异鸟,上茶献酒,珍错杂陈,肴香酒洌,都非常品。
蝶化丽人,仙仙而舞……见有高门,口圆如井,如则光明如昼;街路皆苍石砌成,滑洁无纤翳。
有大树一株,高数丈;
上开赤花,大如莲,纷纭满树。
这无疑是桃源仙境。
可见,蒲松龄的桃源表现与以往许多文人笔下的桃源梦一样突出了理想境界的超凡性,这种超凡性表达了世人企图超越世俗局限的幻想。
仙境无寒暑荣枯的变化,无时间流逝之感;既无赋税科考之重压,又无疾病、死亡的威胁,是世人的理想乐园。
仙境中悠闲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与世人沧海桑田、地覆天翻的变化,仙境一日,世上千年的强烈对比,令人震惊。
所以遇仙者重返人世后,目睹几经沧桑的现实社会,往往顿悟人生的苦恼,遂决然抛开世间的一切,或再返深山,或寻之不果,或不知所踪。
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笔下的太虚幻境以及理想境界的超凡性,更加注重了世俗内容和欲望的实现。
由上文可以看出,蒲松龄更加注重描写与凡人比较贴近的“洞天福地”,仙境的描绘更加世俗化,仙境中的生活也更加世俗化。
蒲松龄心中的桃源,有的只是对艳遇、富贵、长生、享乐的大肆渲染,遇仙就意味着一切欲望的实现。
在这些桃源仙境里,吃穿不愁,逍遥自在;人间追求而不得的所有一切,在这里都会凭借道教神仙的异术轻而易举的得到:富贵长生,良偶佳丽,衣食住行皆无虑,声色美味皆享用。
例如翩翩能取洞口树叶剪裁为衣,绿锦绝滑,穿在身上舒适温暖,又能将山泉和树叶纸张变为酒、菜。
《仙人岛》中的芳云送王勉返里时白练一掷,无际的康庄立现眼前,连别墅居所也可以行时为篮,随身携带,居时一放,即楼阁耸立,从容安居。
《西湖主》中的陈生甚至分身有术地逍遥在人间与仙境两个世界之中,“一身两享其奉”,长生不死,享乐无穷,而人间的苦荣顿挫、遗憾烦恼却一概没有。
这种理想境界,实际上是更为幸福和快乐的人生境界。
二
蒲松龄的桃源情结与他的功名情结以及仕途遭遇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知道,典型的中国士人二重人格结构是所谓的儒道互补,即仕进与隐退,有为和无为的有机结合。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成了主流的人格理想,它带有强烈的现世性与实用性。
但是当人生失意时,古代的知识分子总能在文化土壤中找到心灵的安慰,总能寻找一处灵魂的家园和寄生处所。
蒲松龄一生热衷于功名仕途,并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虽然屡困科场,而功名之心未曾泯灭,直至51岁在其夫人的劝说下犹豫再三而放弃。
而到71岁“援例出贡”后,还写诗:“忆昔狂歌共夕晨,相期矫首跃龙津。
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
”对自己功名无就深表遗恨和痛心,并激励儿孙们继续努力:“无以乃祖空白头,一经终老良足羞”、“实望继世业,骧首登云路”。
也就是说,蒲松龄经历了人生理想的反复跌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戏剧性命运看似近在咫尺,实际上却是遥不可及。
他体会到了人生的幻灭和悲怆,也产生了强烈的孤愤与不平。
这种孤愤与不平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缓解和释放,他便自然而然的有了另一种寻求作为寄托,而可能的方式就是寻求一个心灵上的世外桃源。
从作品来看,早期的《叶生》篇抒发了作者科举失意的悲愤,篇中叶生解释他的行为是“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可见作者对当时科考失利心情既沉痛又不甘认输;至中期的作品,转而对考场舞弊现象进行揭露以及对试官目中无文加以讽刺嘲讽,也寄希望有人执凭文运,但这一希望最终也归于破灭;所以在晚期的《贾奉雉》中写主人公因劣等文章而中举,“真无颜出见同人”,便遁迹山林,逃离名场。
后因俗念未消,回到故乡,“但见方圆零落,旧景全非,村中老幼,竟无一相识者,心始骇异。
忽念刘、阮返自天台,情景真似”。
之后又赴科考,中进士,升高官,春风得意,声名赫奕,歌舞楼台,一时称盛,然而终不免发配充军的下场。
于是如梦初醒,“十余年之富贵,曾不如一梦之久。
今始知荣华之场,皆地狱境界,悔比刘晨、阮肇,多造一重孽案耳。
”又随郎生漂海而去。
《贾奉雉》一篇是最能体现蒲松龄功名情结与桃源情结交织纽合的作品。
蒲松龄于篇末评道:“世传陈大士在闱中,书艺既成,吟诵数四,叹曰:‘亦复谁人识得!’遂弃而更作,以故闱墨不及诸稿。
贾生羞而遁去,盖亦有仙骨焉。
乃再返人世,遂以口腹自贬,贫贱之中人甚矣哉!”“陈大士”即明末陈际泰,他少时家贫,父使治田事。
年10岁,于外家药笼中见《诗经》,携至田所读之,毕身不怠,后
以时文名天下。
68岁才考取进士,旋授行人卒。
无论陈际泰还是贾奉雉,都是因为不甘贫贱而对功名孜孜以求,求之不得固然是抱恨终身,求之已得又何尝不是自堕苦海!人生如梦,富贵无常,何必孜孜求之?由此看到了蒲松龄心路历程的转折,由仕进到寻隐,由现世到出世,这反映出蒲松龄内心的极度无奈:对功名的无奈,对现世人生的无奈。
所以,蒲松龄的桃源乐土是他倍尝人生挫折和失意后的理想境界,其中包含着他对现世人生的思考和感悟。
但是蒲松龄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厌世、出世思想,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忘怀这个并不令人满意的现实人生,追寻桃源只不过是他无奈的消解与补偿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