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1)
说寂寞——读读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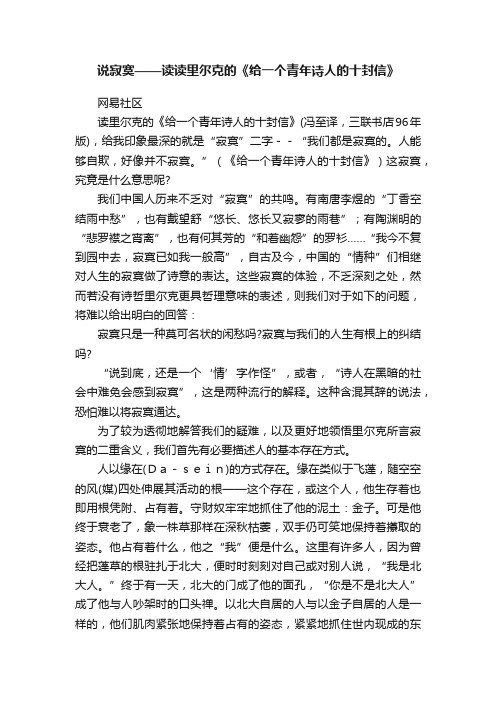
说寂寞——读读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网易社区读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冯至译,三联书店96年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寂寞”二字--“我们都是寂寞的。
人能够自欺,好像并不寂寞。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这寂寞,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国人历来不乏对“寂寞”的共鸣。
有南唐李煜的“丁香空结雨中愁”,也有戴望舒“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有陶渊明的“悲罗襟之宵离”,也有何其芳的“和着幽怨”的罗衫……“我今不复到园中去,寂寞已如我一般高”,自古及今,中国的“情种”们相继对人生的寂寞做了诗意的表达。
这些寂寞的体验,不乏深刻之处,然而若没有诗哲里尔克更具哲理意味的表述,则我们对于如下的问题,将难以给出明白的回答:寂寞只是一种莫可名状的闲愁吗?寂寞与我们的人生有根上的纠结吗?“说到底,还是一个‘情’字作怪”,或者,“诗人在黑暗的社会中难免会感到寂寞”,这是两种流行的解释。
这种含混其辞的说法,恐怕难以将寂寞通达。
为了较为透彻地解答我们的疑难,以及更好地领悟里尔克所言寂寞的二重含义,我们首先有必要描述人的基本存在方式。
人以缘在(Da-sein)的方式存在。
缘在类似于飞蓬,随空空的风(媒)四处伸展其活动的根——这个存在,或这个人,他生存着也即用根凭附、占有着。
守财奴牢牢地抓住了他的泥土:金子。
可是他终于衰老了,象一株草那样在深秋枯萎,双手仍可笑地保持着攥取的姿态。
他占有着什么,他之“我”便是什么。
这里有许多人,因为曾经把蓬草的根驻扎于北大,便时时刻刻对自己或对别人说,“我是北大人。
”终于有一天,北大的门成了他的面孔,“你是不是北大人”成了他与人吵架时的口头禅。
以北大自居的人与以金子自居的人是一样的,他们肌肉紧张地保持着占有的姿态,紧紧地抓住世内现成的东西,不管这现成的东西是肉眼可见的钱币、还是无形的北大身份,他们都当成是石头一般坚硬的对象去把捉。
奈何生命本身是流动的,水与石头无法融合,因此他们不得不花费大的气力才能抓住“对象”,不得不编造种种的谎来搪塞、安慰自己。
给爱国诗人的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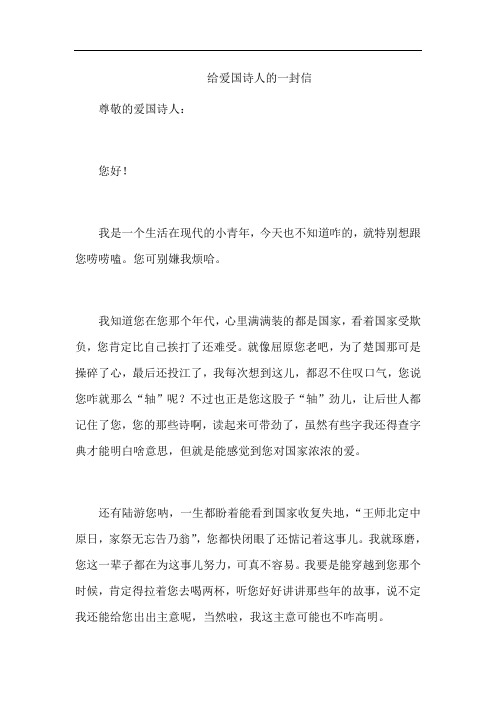
给爱国诗人的一封信
尊敬的爱国诗人:
您好!
我是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小青年,今天也不知道咋的,就特别想跟您唠唠嗑。
您可别嫌我烦哈。
我知道您在您那个年代,心里满满装的都是国家,看着国家受欺负,您肯定比自己挨打了还难受。
就像屈原您老吧,为了楚国那可是操碎了心,最后还投江了,我每次想到这儿,都忍不住叹口气,您说您咋就那么“轴”呢?不过也正是您这股子“轴”劲儿,让后世人都记住了您,您的那些诗啊,读起来可带劲了,虽然有些字我还得查字典才能明白啥意思,但就是能感觉到您对国家浓浓的爱。
还有陆游您呐,一生都盼着能看到国家收复失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您都快闭眼了还惦记着这事儿。
我就琢磨,您这一辈子都在为这事儿努力,可真不容易。
我要是能穿越到您那个时候,肯定得拉着您去喝两杯,听您好好讲讲那些年的故事,说不定我还能给您出出主意呢,当然啦,我这主意可能也不咋高明。
我在现代的生活可好了,吃的喝的玩的,要啥有啥。
可有时候我也会想,要是没有您这些爱国诗人在以前那么拼命,我们能有现在的好日子吗?我觉得可能够呛。
所以我特感激您。
我也想跟您说,我虽然没您那么有才华,写不出那么牛的诗,但我也会在我自己的小天地里,好好爱国。
我会努力学习,将来要是能为国家做点啥,肯定不含糊。
不管咋样,您在我心里那就是大英雄。
希望您在您那个世界里,也能看到现在国家的繁荣昌盛,能欣慰地笑一笑。
祝您一切都好!
一个敬仰您的现代人
XXXX 年XX 月XX 日。
给杜甫的一封信(通用10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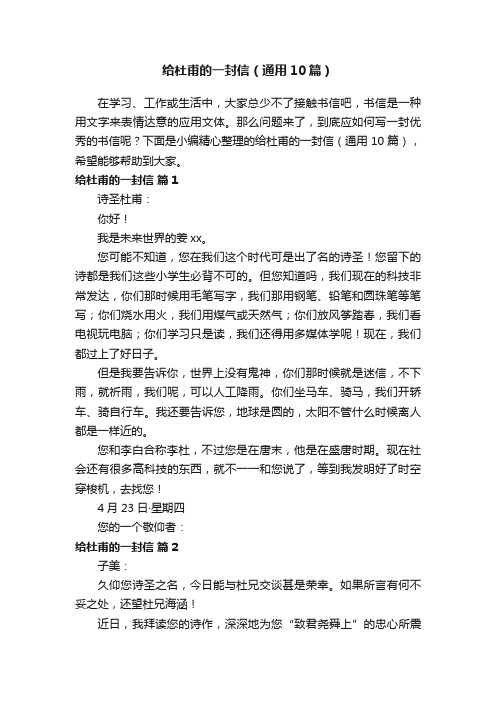
给杜甫的一封信(通用10篇)在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书信吧,书信是一种用文字来表情达意的应用文体。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应如何写一封优秀的书信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给杜甫的一封信(通用10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给杜甫的一封信篇1诗圣杜甫:你好!我是未来世界的姜xx。
您可能不知道,您在我们这个时代可是出了名的诗圣!您留下的诗都是我们这些小学生必背不可的。
但您知道吗,我们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你们那时候用毛笔写字,我们那用钢笔、铅笔和圆珠笔等笔写;你们烧水用火,我们用煤气或天然气;你们放风筝踏春,我们看电视玩电脑;你们学习只是读,我们还得用多媒体学呢!现在,我们都过上了好日子。
但是我要告诉你,世界上没有鬼神,你们那时候就是迷信,不下雨,就祈雨,我们呢,可以人工降雨。
你们坐马车、骑马,我们开轿车、骑自行车。
我还要告诉您,地球是圆的,太阳不管什么时候离人都是一样近的。
您和李白合称李杜,不过您是在唐末,他是在盛唐时期。
现在社会还有很多高科技的东西,就不一一和您说了,等到我发明好了时空穿梭机,去找您!4月23日·星期四您的一个敬仰者:给杜甫的一封信篇2子美:久仰您诗圣之名,今日能与杜兄交谈甚是荣幸。
如果所言有何不妥之处,还望杜兄海涵!近日,我拜读您的诗作,深深地为您“致君尧舜上”的忠心所震撼;也深深地为您“驻马望千门”的无奈而惋惜;深深地为您“两个黄鹂鸣翠柳”地闲适所称羡;也深深地为您“安得广厦千万间”的胸怀而感慨。
在颠沛流离之中,您即使自己食不果腹,但心中仍怀着风雨飘摇的人民,仍激荡着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您一生中从未放弃过自己远大的抱负,想要辅佐帝王成为千古贤君,想要让王朝和人民繁荣富强。
可是,残酷的现实给你一次又一次打击。
最终,生活捏碎了您美好的梦想,您永远与辅佐帝王的丰功伟绩,告别了。
背负了太多岁月的阴影,真的让您好累。
于是您选择了离开,选择了在一方草堂中过清贫而悠闲的日子。
[致诗人的一封信]给诗人的一封信
![[致诗人的一封信]给诗人的一封信](https://img.taocdn.com/s3/m/eee00425ae45b307e87101f69e3143323968f5dc.png)
[致诗人的一封信]给诗人的一封信致诗人杜甫的一封信范文一杜甫先生:最近忙否请原谅我这来自千年之后的冒昧打搅吧。
我是来自21世纪的一个青年,之所以给您写这封信,是想告诉您最近发生在您身上的一些事,还想跟您谈谈我现在所身处的这个世界。
我相信,作为一名诗人,您心里一定会希望自己的诗作能流传千古,为后人传诵,我想告诉您,您成功了,您的伟大诗作不仅时至今日还被万人传诵,而且它们已经走进了语文课本,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相信即使再过几千年,您和您的诗作依然传世不朽。
真的恭喜您,也感谢您,您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令万世景仰。
或许,这些您已经预料到,但我敢肯定,最近发生在您身上的这件事,您一定没有想到——千年之后,您成了微博红人。
您的照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具体请看来信所附的照片。
不知道看到这些恶搞自己的图片,您会不会生气。
不过,我猜,以您老人家“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大胸怀,肯定不会像那个博物馆负责人那么小家子气。
请允许我说明,这绝对不是在亵渎您,请您一定明白,网友们对您照片的涂鸦,其实完全是出于内心对您深沉的喜爱,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当今的应试教育实在是太无聊和枯燥了,人们通过这种涂鸦,以表达对应试教育制度的不满。
说到这里,不得不向您说一下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
现在我们所有人要想上大学,就必须得参加一个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简称高考,而高考的内容是指定的,您的诗作也是考试内容之一,高考指定的内容非常多,而我们必须将所有的内容都记住,然后参加考试,换取分数,在这里,分数就是一切。
您不知道,准备高考的日子是非常痛苦的,也是非常难熬的,所有人都像待宰的猪一样被人注水,压力非常大,这时,人们会通过涂鸦来发泄情绪,以此缓解压力,舒脑心安.说实话,之所以恶搞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可都是被逼出来的啊!恶搞归恶搞,不得不说,现在的中国,像您这样忧国忧民的人已经很少了,现在的中国都在为金钱和权力而痴狂,道德和良知都被丢弃了,很少人为中国的前途以及百姓的疾苦大声疾呼,而且现在权力和资源被垄断,人们的幸福感和平安感很低,人与人之间都很冷漠,普通民众生不起、住不起、吃不起甚至死不起,人们都很迷茫,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过上民主、自由、幸福而有平安感的生活。
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1)Letters to a Young Poet(1)(英语美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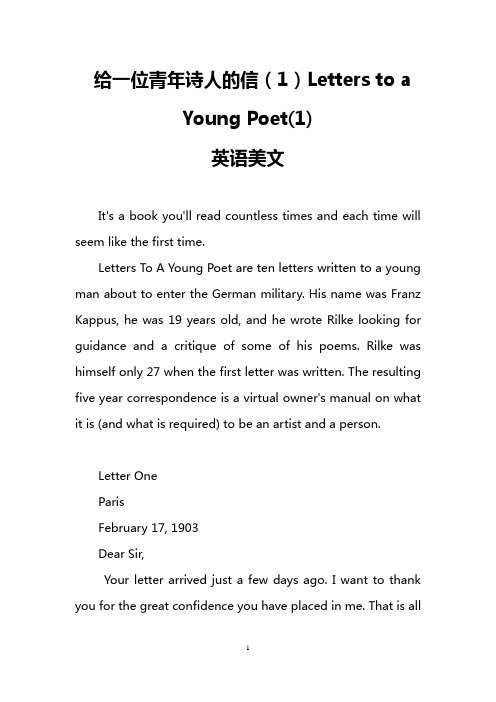
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1)Letters to aYoung Poet(1)英语美文It's a book you'll read countless times and each time will seem like the first time.Letters To A Young Poet are ten letters written to a young man about to enter the German military. His name was Franz Kappus, he was 19 years old, and he wrote Rilke looking for guidance and a critique of some of his poems. Rilke was himself only 27 when the first letter was written. The resulting five year correspondence is a virtual owner's manual on what it is (and what is required) to be an artist and a person.Letter OneParisFebruary 17, 1903Dear Sir,Your letter arrived just a few days ago.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the great confidence you have placed in me. That is allI can do. I cannot discuss your verses; for any attempt at criticism would be foreign to me. Nothing touches a work of art so little as words of criticism: they always result in more or less fortunate misunderstandings. Things aren't all so tangible and sayable as people would usually have us believe; most experiences are unsayable, they happen in a space that no word has ever entered, and more unsay able than all other things are works of art, those mysterious existences, whose life endures beside our own small, transitory life.With this note as a preface, may I just tell you that your verses have no style of their own, although they do have silent and hidden beginnings of something personal. I feel this most clearly in the last poem, "My Soul." There, some thing of your own is trying to become word and melody. And in the lovely poem "To Leopardi" a kind of kinship with that great, solitary figure does perhaps appear. Nevertheless, the poems are not yet anything in themselves, not yet any thing independent, even the last one and the one to Leopardi. Your kind letter, which accompanied them managed to make clear to me various faults that I felt in reading your verses, though I am not able to name them specifically.You ask whether your verses are any good. You ask me. You have asked others before this. You send them to magazines. You compare them with other poems, and you are upset when certain editors reject your work. Now (since you have said you want my advice) I beg you to stop doing that sort of thing. You are looking outside, and that is what you should most avoid right now. No one can advise or help you - no one. There is only one thing you should do. Go into yourself. Find out the reason that commands you to write; see whether it has spread its roots into the very depths of your heart; confess to yourself whether you would have to die if you were forbidden to write. This most of all: ask yourself in the most silent hour of your night: must I write? Dig into yourself for a deep answer. And if this answer rings out in assent, if you meet this solemn question with a strong, simple "I must", then build your life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necessity; your whole life,even into its humblest and most indifferent hour, must become a sign and witness to this impulse. Then come close to Nature. Then, as if no one had ever tried before, try to say what you see and feel and love and lose. Don't write love poems; avoid those forms that are too facile and ordinary: they are the hardest to work with, and it takes a great, fully ripened powerto create something individual where good, even glorious, traditions exist in abundance. So rescue yourself from these general themes and write about what your everyday life offers you; describe your sorrows and desires, the thoughts that pass through your mind and your belief in some kind of beauty Describe all these with heartfelt, silent, humble sincerity and, when you express yourself, use the Things around you, the images from your dreams, and the objects that you remember. If your everyday life seems poor, don't blame it; blame yourself; admit to yourself that you are not enough of a poet to call forth its riches; because for the creator there is no poverty and no poor, indifferent place. And even if you found yourself in some prison, whose walls let in none of the world's sound - wouldn't you still have your childhood, that jewel beyond all price, that treasure house of memories? Turn your attention to it. Try to raise up the sunken feelings of this enormous past; your personality will grow stronger, your solitude will expand and become a place where you can live in the twilight, where the noise of other people passes by, far in the distance. And if out of , this turning within, out of this immersion in your own world, poems come, then you will not think of asking anyone whether they are good or not. Nor will you try to interestmagazines in these works: for you will see them as your dear natural possession, a piece of your life, a voice from it. A work of art is good if it has arisen out of necessity. That is the only way one can judge it. So, dear Sir, I can't give you any advice but this: to go into yourself and see how deep the place is from which your life flows; at its source you will find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you must create. Accept that answer, just as it is given to you, without trying to interpret it. Perhaps you will discover that you are called to be an artist. Then take that destiny upon yourself, and bear it, its burden and its greatness, without ever asking what reward might come from outside. For the creator must be a world for himself and must find everything in himself and in Nature, to whom his whole life is devoted.But after this descent into yourself and into your solitude, perhaps you will have to renounce becoming a poet (if, as I have said, one feels one could live without writing, then one shouldn't write at all). Nevertheless, even then, this self searching that I ask of you will not have been for nothing. Your life will still find its own paths from there, and that they may be good, rich, and wide is what I wish for you, more than I can say.What else can I tell you? It seems to me that everythinghas its proper emphasis; and finally I want to add just one more bit of advice: to keep growing, silently and earnestly, through your whole development; you couldn't disturb it any more violently than by looking outside and waiting for outside answers to questions that only your innermost feeling, in your quietest hour, can perhaps answer.It was a pleasure for me to find in your letter the name of Professor Horacek; I have great reverence for that kind, learned man, and a gratitude that has lasted through the years. Will you please tell him how I feel; it is very good of him to still think of me, and I appreciate it.The poem that you entrusted me with, I am sending back to you. And I thank you once more for your questions and sincere trust, of which, by answering as honestly as I can, I have tried to make myself a little worthier than I, as a stranger, really am.Yours very truly,Rainer Maria Rilke亲爱的先生:您的信在几天前就到了这里。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一个个的人在世上好似园里的那些并排着的树。枝枝叶叶也许有些呼应吧,但是它们的根,它们盘结在地下 摄取营养的根却各不相干,又沉静,又孤单。人每每为了无谓的喧嚣,忘却生命的根蒂,不能在寂寞中、在对于 草木鸟兽(它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生物)的观察中体验一些生的意义,只在人生的表面永远往下滑过去。
目录分析
收信人引言
重印前言
第一封信
01
第二封信
02
第三封信
03
第四封信
04
第五封信
06
第七封信
05
第六封信
01
第八封信
02
第九封信
03
第十封信
04
附录一冯至 译里尔克作 品
06
附录三冯至 论里尔克
05
附录二相关 信件
作者介绍
这是《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的读书笔记模板,暂无该书作者的介绍。
谢谢观看
是朋友给懋懋的胎教书十封信看看很快里尔克很真诚完全没有架子看的时候一直有写信给朋友的冲动印象最 深的是那句“诗不是情感,是经验”。
好好忍耐,不要沮丧,如果春天要来,大地就使它一点一点完成,我们所做的少量的工作,不会比大地之于 春天更为艰难。
关于观看万物,艺术家“模制一件物,就是要:各处都看到了,无所隐瞒,无所忽略,毫无欺骗;认识一切 众多的侧面、一切从上看和从下看的观点、每个互相的交叉。
此书是认识里尔克以至于冯至的文学作品的存在主义特质的比较好的读物,同时也适合青年从存在主义和诗 意的角度认识自己。
精彩摘录
你向外看,是你现在最不应该做的事。没有人能给你出主意,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只有一个唯一的方法。请 你走向内心。探索那叫你写的缘由,考察它的根是不是盘在你心的深处;你要坦白承认,万一你写不出来,是不 是必得因此而死去。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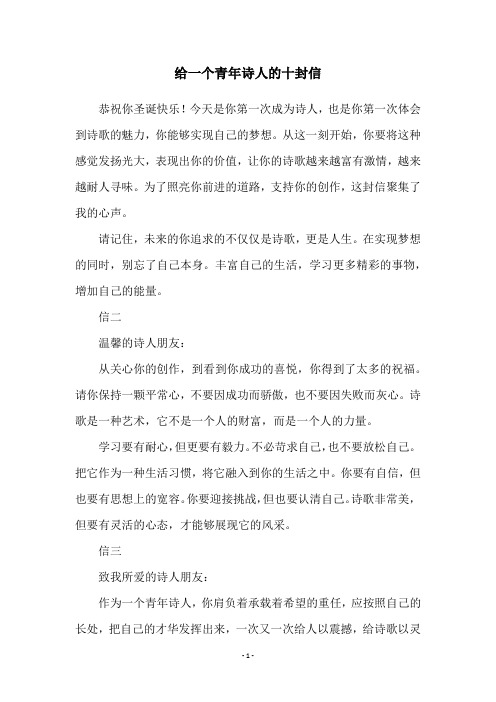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恭祝你圣诞快乐!今天是你第一次成为诗人,也是你第一次体会到诗歌的魅力,你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从这一刻开始,你要将这种感觉发扬光大,表现出你的价值,让你的诗歌越来越富有激情,越来越耐人寻味。
为了照亮你前进的道路,支持你的创作,这封信聚集了我的心声。
请记住,未来的你追求的不仅仅是诗歌,更是人生。
在实现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自己本身。
丰富自己的生活,学习更多精彩的事物,增加自己的能量。
信二温馨的诗人朋友:从关心你的创作,到看到你成功的喜悦,你得到了太多的祝福。
请你保持一颗平常心,不要因成功而骄傲,也不要因失败而灰心。
诗歌是一种艺术,它不是一个人的财富,而是一个人的力量。
学习要有耐心,但更要有毅力。
不必苛求自己,也不要放松自己。
把它作为一种生活习惯,将它融入到你的生活之中。
你要有自信,但也要有思想上的宽容。
你要迎接挑战,但也要认清自己。
诗歌非常美,但要有灵活的心态,才能够展现它的风采。
信三致我所爱的诗人朋友:作为一个青年诗人,你肩负着承载着希望的重任,应按照自己的长处,把自己的才华发挥出来,一次又一次给人以震撼,给诗歌以灵魂,以激情。
要坚定自己的信念,追求自己,不要迎合流行,更不要把自己给局限在一个角落里。
要有勇气主动去改变状况,把不能改变的情况接受,把能够改变的事情去改变,用自信和勇气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信四尊敬的朋友:用一首诗歌来写诗,写出自己的心情。
让它宣传自己的理念,借助它来建立自我的形象,让自己不只是一个单调的声音,而更成为一种思想的代言人。
让自己思想成长,孜孜不倦;让自己心境更加宽容,让自己的诗歌能够聋哑人也能听懂。
做一个真正的诗人,不只是一个艺术家,更是一个践行者,只有站在时代的前沿,才能够把诗歌的精神发扬光大。
信五我的朋友:诗歌就像一颗明珠,在漫漫长路中为你照亮前行,让你永远有路可走。
未来的你要有心,坚持正道。
让自己的诗歌让更多的人认识你,也让自己认识更多的人。
不要忘记你的原则,而要继续努力,让自己的成果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委内瑞拉伟大诗人西拉斯里尔克自1924年出生,至1969年过世之前,一生笔耕不辍,书写众多杰出的诗作,被誉为“拉丁美洲诗歌之父”。
他为期望发展的青年诗人写下了十封信,罗列其自身的经验和学习的教训,鼓舞后人继续他的遗志。
此篇文章将阐明西拉斯里尔克身为诗人的使命,以及他在十封信中赋予下一代的诗歌使命,以及如何把他的想法付诸行动,让他的遗志活着,让他的诗歌继续活跃于当今世界。
里尔克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使命,他把诗歌作为希望、觉醒和灵感,一步步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在他看来,诗歌是一种声音,一种表达,一种象征,能够帮助人们应对困境,并寻求解脱,特别是在20世纪拉丁美洲社会变革和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里尔克认为诗歌是改变时代的一种力量。
他的诗作总是充满激情,充满活力,他的诗歌涉及的民族主义、反资本主义、百姓痛苦、自由、民主等话题,在他的作品中,有着对于生活的各种期待、思考和忧虑,他也说“当我开始用诗歌承载我的信仰,我便成了一名诗人”。
里尔克将自己的使命传递给下一代,他写下的十封信,字迹端端正正,每封信都有其独特的内容,但是大体上都在强调一些共同的观点,例如,里尔克认为诗人应当有正义感,坚持正义,把自己的文学作品视作一种武器,用诗歌的美丽、力量与众不同,立志于改变现实社会的丑陋现象,使人们觉醒;同时,里尔克也倡导青年诗人坚持自己的梦想,获取更多的知识,从实际出发,坚持打破常规,也就是他的名言:“要不断持续着,渴望不断着,爱的烈焰不断着,要把它告诉世界”。
他还建议青年诗人多多了解世界,不断努力,不被现实的苦涩所支配,与世界斗争抗争,与梦想相遇;最后,他还鼓励年轻人创造属于自己的诗歌形式,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血液和灵魂注入作品中,完成自己对世界的贡献。
里尔克对青年诗人的期望一直活跃于当今,他在十封信中所赋予的灵感与激励都成就了一批有才华的青年诗人,使他们的作品不断的出现在世界的文坛上。
[给诗人的一封信]给诗人的一封信800
![[给诗人的一封信]给诗人的一封信800](https://img.taocdn.com/s3/m/4ad0a023ae45b307e87101f69e3143323968f5ea.png)
[给诗人的一封信]给诗人的一封信800给诗人的一封信范文一敬爱的“诗仙”李白:1200多年前的你还好吗?你是否还在为自己壮志难酬而满腔愤激?你是否还在为自己年老无功而惆怅满怀?呵呵,即使有再大的伤痛,再乱的愁思,你都能让它们溶解在一杯烈焰里,像黄河之水一样“不复回”吧。
岁月荏苒,1200年后,我坐在教室里给你写这封信:因为我仰慕你,我被你的气魄折服了。
我仰慕你的才华横溢。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巍巍香炉峰藏在云烟雾霭之中,浩浩庐山瀑如从云端飞流而下,临空而落。
纸上静止的文字似乎都具有了强烈的视觉冲击感。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有形有神,奔放空灵,可谓是无人能及。
洞庭烟波,赤壁风云,蜀道猿啼,浩荡江河,全都一下子飞扬起来。
诗里的你,洒脱自在,狂放不羁,豪气纵横像天上席卷的云气;诗里的你,神游八极,自由驰骋,酣畅洒脱如草原奔腾的骏马。
明代大家杨慎在《升庵诗话》中给予你盛赞“李白神于诗”,后世评论家冠于你“仙”,遂使你“诗仙”的雅号广为流传。
我仰慕你的自信乐观。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如此高度自信的惊人之句,能驱使金钱而不为金钱所使,真令凡夫俗子们咋舌。
正是你教会了我在面对挑战时要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胜利非我莫属!要认识到自己的人生价值,竭力去做人生舞台上的主角;“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崎岖坎坷,你仍然坚信总有一天,会长风破万里浪,挂云帆,济沧海,到达理想彼岸。
这也极大地激励了我在处于人生的低谷时战胜困难,走向辉煌的信心。
我仰慕你藐视权贵的铮铮傲骨与追求自由的无限豪情。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是啊,以你傲岸不屈的性格,在那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官场里,怎能得“开心颜”呢?你不愿阿谀奉承,也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你踌躇满志,渴望用世,但现实的黑暗幻灭了你的理想;你渴望自由,渴望解放,但封建礼教总是让你窒息。
给青年诗人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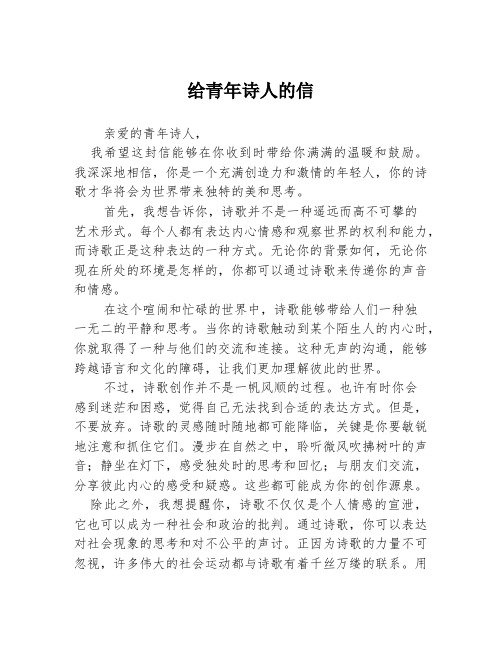
给青年诗人的信亲爱的青年诗人,我希望这封信能够在你收到时带给你满满的温暖和鼓励。
我深深地相信,你是一个充满创造力和激情的年轻人,你的诗歌才华将会为世界带来独特的美和思考。
首先,我想告诉你,诗歌并不是一种遥远而高不可攀的艺术形式。
每个人都有表达内心情感和观察世界的权利和能力,而诗歌正是这种表达的一种方式。
无论你的背景如何,无论你现在所处的环境是怎样的,你都可以通过诗歌来传递你的声音和情感。
在这个喧闹和忙碌的世界中,诗歌能够带给人们一种独一无二的平静和思考。
当你的诗歌触动到某个陌生人的内心时,你就取得了一种与他们的交流和连接。
这种无声的沟通,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让我们更加理解彼此的世界。
不过,诗歌创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
也许有时你会感到迷茫和困惑,觉得自己无法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
但是,不要放弃。
诗歌的灵感随时随地都可能降临,关键是你要敏锐地注意和抓住它们。
漫步在自然之中,聆听微风吹拂树叶的声音;静坐在灯下,感受独处时的思考和回忆;与朋友们交流,分享彼此内心的感受和疑惑。
这些都可能成为你的创作源泉。
除此之外,我想提醒你,诗歌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宣泄,它也可以成为一种社会和政治的批判。
通过诗歌,你可以表达对社会现象的思考和对不公平的声讨。
正因为诗歌的力量不可忽视,许多伟大的社会运动都与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用你的诗歌去挑战社会的不公和不合理,为正义和平等发声。
最后,我想告诉你,作为一名诗人,你将面临许多机会和挑战。
参加诗歌朗读会、写作工作坊、诗歌比赛等活动,你将能够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了解更多关于诗歌创作的技巧和经验。
同时,也要不断学习和发展自己的写作风格,保持对新事物的好奇心。
读书、旅行、观影,这些都能给你带来灵感和触动。
亲爱的青年诗人,你的诗歌是独一无二的,无论它们如何被世界接受,它们都是真实而有力的。
不要停止创作,不要气馁,相信自己的内心声音,让诗歌的力量融入你的生活和创作中。
无论是快乐还是悲伤,都可以借助诗歌来表达,让心灵得到释放。
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你要爱你的寂寞

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你要爱你的寂寞里尔克写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发之肺腑,深入心灵,对于喜好文学的人来说,这十封信,可说是文学创作之精髓了。
爱好文学的人自古至今为数众多,而今更是铺天盖地,文学接近民众原本是好事,然而如今的人所书所写却未必是真正的文学,浮躁忙碌喧嚣的时代,我们更应当如里尔克书中所言,要回归自己的内心。
在打开本书时,首先看到的是里尔克的孤独阴郁的脸。
对于里尔克,我坦诚不是很熟悉,只知道那几首非常著名的诗,对于文学,我只是一个缓慢的跟从者。
热爱文学的人,一般不会为这个看脸的社会所迷惑,然而每次读到作品,若看见作家长得帅气,总也不免流俗。
这是里尔克,我承认他的相貌过于阴郁忧愁,没有打动我,那是一张愁苦的脸,一张童年经历痛苦悲愁的脸。
于是先去了解他的生平。
果然如我所猜测,出生在平民家庭的他,父亲仕途不如意,脾气暴躁,母亲张扬虚荣整日幻想加入上流社会,在这样家庭中生活长大的里尔克自然谨小慎微,而姐姐一出生不久便夭折,母亲又把他当女孩来养,这样也使他的成长有了一些阴柔之气。
从他的脸上感到了深深的孤独。
可是孤独真的那么不讨人喜欢吗?“你要爱自己的寂寞,”在第四封信中,里尔克写给军官诗人,“你要负担起他,那以悠扬的怨诉给你引来的痛苦,当身边的人都同你疏远了,其实这就是你周围扩大的开始,因为你的矿源已经在星空下开展得很广大,你要以你的成长欢喜,可是向那里你不能带进来一个人”里尔克对于孤独是接受的,由此可见,我们知道诗人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变化。
如果排斥孤独,不接受生活送给自己的礼物,那么只会与生活格格不入,既然没办法选择生活,那么就去接受它,并好好的利用它,这就是里尔克的人生哲学,于是他把孤独变成了诗。
“要接受一切可能的生活,即使他令你不安,但那正是生活痛苦寂寞都是在生活接受它,把它变成实,即使没有朋友。
”这样的思想,也就是艺术文学创作者之所以能够在贫瘠的生活之上开出灿烂的文学之画的缘由。
里尔克对于创作的观点是要从日常生活中发事物去发现,让万物与心灵更贴近,要深幽寂静,谦虚真诚,假如你认为自己生活太贫乏,可是你还有回忆的宝库第一封信逝去的消沉了的动人的往事都可以为你提供丰富的写作素材,写诗要向内看,你的内心就是写作的源泉,这也是为什么写作的人要甘于寂寞的缘由。
写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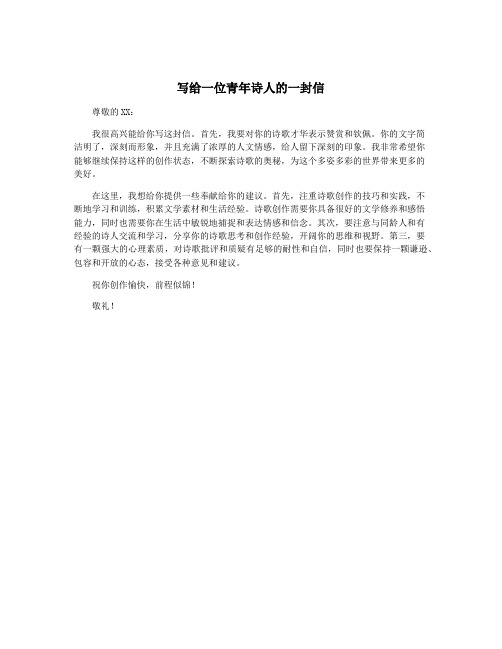
写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一封信
尊敬的XX:
我很高兴能给你写这封信。
首先,我要对你的诗歌才华表示赞赏和钦佩。
你的文字简
洁明了,深刻而形象,并且充满了浓厚的人文情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非常希望你
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创作状态,不断探索诗歌的奥秘,为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带来更多的
美好。
在这里,我想给你提供一些奉献给你的建议。
首先,注重诗歌创作的技巧和实践,不
断地学习和训练,积累文学素材和生活经验。
诗歌创作需要你具备很好的文学修养和感悟
能力,同时也需要你在生活中敏锐地捕捉和表达情感和信念。
其次,要注意与同龄人和有
经验的诗人交流和学习,分享你的诗歌思考和创作经验,开阔你的思维和视野。
第三,要
有一颗强大的心理素质,对诗歌批评和质疑有足够的耐性和自信,同时也要保持一颗谦逊、包容和开放的心态,接受各种意见和建议。
祝你创作愉快,前程似锦!
敬礼!。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读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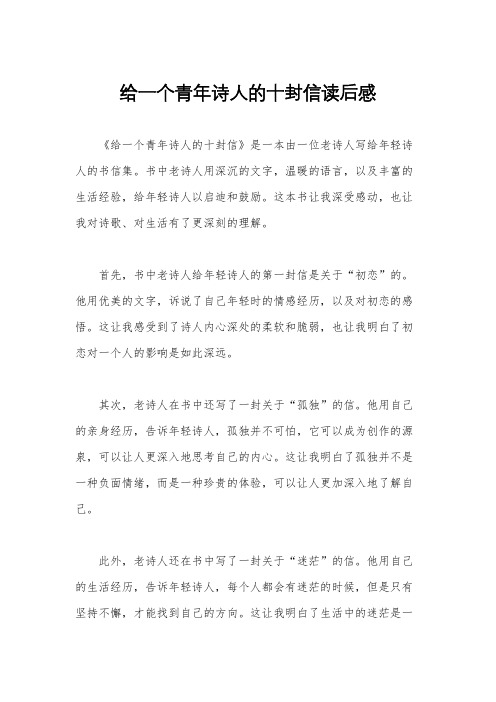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读后感《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是一本由一位老诗人写给年轻诗人的书信集。
书中老诗人用深沉的文字,温暖的语言,以及丰富的生活经验,给年轻诗人以启迪和鼓励。
这本书让我深受感动,也让我对诗歌、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首先,书中老诗人给年轻诗人的第一封信是关于“初恋”的。
他用优美的文字,诉说了自己年轻时的情感经历,以及对初恋的感悟。
这让我感受到了诗人内心深处的柔软和脆弱,也让我明白了初恋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如此深远。
其次,老诗人在书中还写了一封关于“孤独”的信。
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年轻诗人,孤独并不可怕,它可以成为创作的源泉,可以让人更深入地思考自己的内心。
这让我明白了孤独并不是一种负面情绪,而是一种珍贵的体验,可以让人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
此外,老诗人还在书中写了一封关于“迷茫”的信。
他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告诉年轻诗人,每个人都会有迷茫的时候,但是只有坚持不懈,才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这让我明白了生活中的迷茫是一种必然的状态,只有不断地前行,才能找到自己的出路。
另外,老诗人还在书中写了一封关于“梦想”的信。
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年轻诗人,梦想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只有有了梦想,才能有动力去追求。
这让我明白了梦想是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富,只有不断地追求,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最后,老诗人在书中写了一封关于“人生”的信。
他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告诉年轻诗人,人生是一场旅程,只有不断地前行,才能找到自己的归宿。
这让我明白了人生是一场充满挑战的旅程,只有不断地奋斗,才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总的来说,《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
通过老诗人的文字,我深刻地感受到了诗人内心的柔软和脆弱,也让我对诗歌、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这本书不仅让我感受到了诗歌的美好,也让我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相信,这本书对于每一个热爱诗歌的人来说,都是一本值得细细品味的佳作。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第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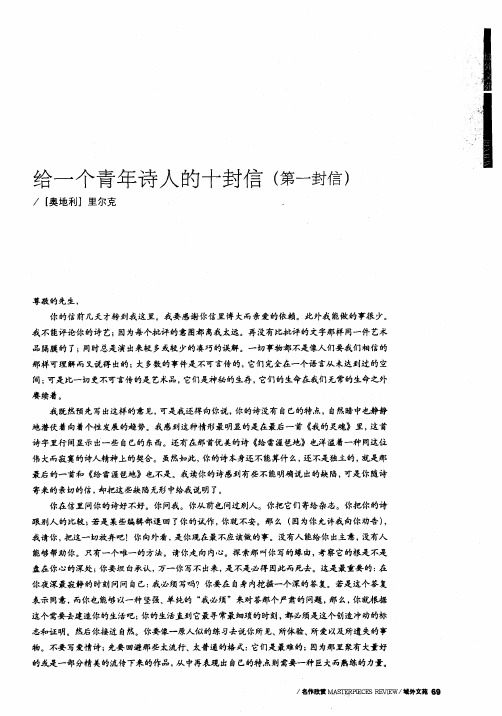
/名作歇簧 MAS E PE E E IW/域外文苑 的 T R IC SR VE
所 以你要躲 开那些普遍 的题 材 , 而归依于你 自己 日
重 地 伤 害 你 的 发展 了 , 你
道 , 的 问题 也 许 只是 你
常生活呈现给你的事物 ; 你描 写你的悲哀 与愿望, 流
逝的思想 与对于某一种 美的信念一 用深幽、 寂静、
伟 大而寂 寞的诗人精神上的契合。 虽然如此 , 你的诗 本身还不能算什 么, 还不是 独立 的, 就是那
最后的一首和 《 给雷渥琶地》 也不是 。我读 你的诗 感到有 些不 能明确说 出的缺 陷, 可是你 随诗
寄来的亲切的信 , 却把这些缺陷无形 中给我说 明 了。
你在信里问你的诗好不好 。你问我。你从前也 问过别人 。你把 它们寄给杂志。你把 你的诗
以一切的忠诚 与关怀 :
莱内 ・马利亚 ・ 里尔克
10 , , 52 1 9 8;巴黎 圈
所朦胧 的住 室, 别人 的喧扰 只远 远地从 旁走 过——
如 果 从 这 收 视 反 听 , 这 向 自己世 界 的深 处产 生 出 从
“ 诗” 来, 你一 定不会 再想 问别人 , 是不是 好诗。 这
你最深的情感在你最微妙的时刻所 能回答的。
我很 高兴, 在你 的信里 见到 了荷拉捷 克教 授 的 名 字; 我对 于这位 亲切 的学者 怀有很 大 的敬 意和 多
谦虚 的真诚描 写这一 切 , 用你周 围的事物 、梦中的
图影 、 回忆 中的对 象表现 自己。如 果你 觉得你 的 日 常生活很 贫乏 , 你不要抱 怨它 ; 还是 怨你 自己吧, 怨
你也 不会再 尝试让杂志去 注意这 些作品 : 因为你将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亲爱的青年诗人,这是一封特殊的信,它不仅代表了我的思念和问候,更是我给你的建议和启示。
作为一个诗人,你的灵感源泉从何而来?对于你来说,写作的过程是令人愉悦还是难以启齿?在接下来的十封信里,我将会向你分享我的观点和建议,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第一封信,我想说的是关于诗歌的创作技巧。
在写作之前,需要先了解多种不同的形式和结构。
例如,情诗和抒情诗的写作方式和要求是不同的。
除了形式,还要注意语汇、韵律和节奏。
将你的作品读给别人听,看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试着不断地调整和改进你的作品,才能逐渐成为一个更好的诗人。
第二封信,我想说的是关于诗歌的主题。
诗歌的主题非常广泛,可以是自然、人物、社会问题、历史事件等。
选择一个好的主题,是诗歌成功的关键。
写作的过程中,鼓励你去挖掘那些隐藏在背后的感受和想法,让读者感受到你写作的深度和内涵。
第三封信,我想说的是关于培养灵感的方式。
灵感的源泉来自于生活中的点滴,你可以通过练习创造力来培养自己的灵感,例如读书、旅行、观察人和事。
显然,别人的一句话、一幅画、一件事、一种表情、一首诗等都可以成为你的创作灵感之源。
第四封信,我想说的是关于自由写作的重要性。
在写作时,不要受制于任何限制或规则。
相反,去追求自由自在的创作过程,从中找到灵感和乐趣。
无论在创作中出现了哪些问题,都不要被想象的桎梏束缚住了,放开手脚大胆地创作。
第五封信,我想说的是关于语言的力量。
诗歌不仅是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更是一种表达思想的方式。
通过诗歌,你可以传达自己的观点和对世界的看法。
在创作时,建议你使用简练的语言、生动的词汇和有力的形象,用你的语言将主题表现的淋漓尽致。
第六封信,我想说的是关于阅读和学习。
写作需要读书,别好吸收、领悟,才能表达出你的思想和想象。
阅读不同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古诗和现代诗歌,可以为你的创作提供灵感和启示。
在阅读中,你可以学习他人的写作技巧,并且不断拓宽自己的写作思路。
第七封信,我想说的是关于创作的频率和时间。
给青年诗人的信(1)

晚上好,各位读书会的朋友们,也许您已守候多时,今天由我替班领读冯至翻译的里尔克的《给青年诗人的信》,原领读者是党玲芬老师,她由于时间关系无法亲自领读本书,因此暂由我代表,党老师很喜欢这本书,我资质有限,恐难以达到党老师对本书的理解高度,本次领读请大家积极发言,争取圆满完成本次领读任务。
奥地利作家20世纪德语世界最伟大的诗人欧洲现代最伟大的三位诗人之一德语文学史上唯一堪与荷尔德林比肩的诗哲里尔克曾说我的诗集就是我的坦白我一生的故事我的一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康复……孤独一如我历来的生活,甚至更甚。
诗人不断地旅行不断地道别漂泊成为他的宿命冯至(1905--1993)河北涿县人。
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曾任西南联大、北大教授,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协副主席等。
有诗集《昨日之歌》、《十四行诗》等,论著《杜甫传》等。
冯至先生是“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
他既有国学的扎实功底,又有西学的深厚造诣。
他不但能用母语写出优美的诗歌、散文,而且具有古文的过硬基础,故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也相当谙熟,尤对杜甫的研究卓有成就,以至拥有权威性的发言权。
在德国留学的五年里,他不仅攻读了德国文学,而且也攻读了德国哲学。
所以他关注的德国作家多是哲学味道较浓的诗人,除歌德、席勒、海涅外,他也关注带有“现代”特征的诗人:诺瓦利斯(这是他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荷尔德林、里尔克等。
他翻译的上述古典名家的诗歌、散文和美学论著在我国拥有众多的读者;他翻译的里尔克《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九封信》最早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这位世界级的现代诗人,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由于冯至先生在两个领域里的显著成就,他获得“双肩挑”的雅称。
毫不意外,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宣部在组织大学文科教材编写的时候,冯至以《中国文学史》与《欧洲文学史》总负责人的资格参与并领导这两部著作的编写工作。
一、里尔克的文字寂寞又忍耐,有一种沉默的力量,聊一聊书中触动你的句子。
年青人,珍爱你的寂寞吧!——读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读 里 尔克 的《 给一 个青 年诗 人 的十封 信 》
一 河南 大 学 附属 中学 杨 金 孝
一
个 比他 更 年 轻 的 诗 人 收 到 他 那 著 名 的 十 所 能拥 有 、 能 理解 的 。 所 在 里 尔 克 看 来 , 些 离 开 的人 都 是 一 些 “ 那 落 在 后 面 的人 ” 怎样 对 待 他们 ? 说 :要 好 好对待 。 他 “
绪委 婉 地传 达 出来 了 诗人 选 取 的景 物 和 自己的 则 景哀 , 情乐 则 景乐 ” 吴 乔《 ( 同炉诗 话 》 。诗 人将 )
说 : 正是 你 的周 围扩 大 的开 始 。“ 们 的亲 近离 成 . 从 这 呢 喃之 中透 露 出来 。 这几 乎是 一 个奇 这 我 并
远了. 可是 我 们 的 旷远 已 经在 星 空 下 开 展得 很 广 迹 。这不 能不 让 我 们 想 到 生命 质地 的不 同 , 天才
大 . 值得 欢喜 的一种 成 长 ” 是 。这是 何 等 自信 的理 与庸 人 的不 同 。 特立 独 行者 与 世 俗凡 人 的不 同 。
遥远 的 世界 的时 候 . 一个 人才 能 够 证 明 自己是 活
一
个 对 人 类 多 么 体 贴 入 微 的 人 才 能 有 这 样
对 对 对 着 的— — 这 个 特 异 的生 命 . 个 多 病 的 自小 孱 弱 的理 解 ; 人 , 世 界 , 生 活— — 这 个 时世 还会 这
解 。这 种 真正 的 、 容 动摇 的 自尊 。 不 这种 由于 长久
曾经 在哪 里 看过 里 尔 克 的一 个 头部 雕像 。 美
( 转第 3 下 0页 )
地守 护善 良而 引 发 的感 慨 和 自豪 . 不 是很 多人 丽 的五 官 棱 角 分 明 ,完 全 像 并
写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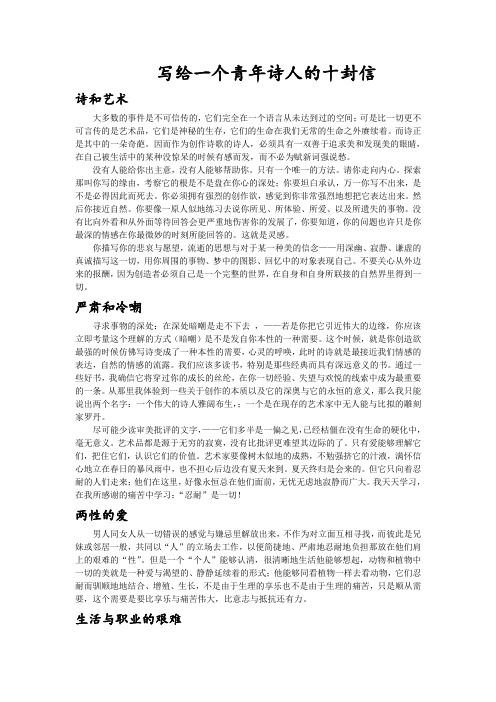
写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诗和艺术大多数的事件是不可信传的,它们完全在一个语言从未达到过的空间;可是比一切更不可言传的是艺术品,它们是神秘的生存,它们的生命在我们无常的生命之外赓续着。
而诗正是其中的一朵奇葩。
因而作为创作诗歌的诗人,必须具有一双善于追求美和发现美的眼睛,在自己被生活中的某种没惊呆的时候有感而发,而不必为赋新词强说愁。
没有人能给你出主意,没有人能够帮助你。
只有一个唯一的方法。
请你走向内心。
探索那叫你写的缘由,考察它的根是不是盘在你心的深处;你要坦白承认,万一你写不出来,是不是必得因此而死去。
你必须拥有强烈的创作欲,感觉到你非常强烈地想把它表达出来。
然后你接近自然。
你要像一原人似地练习去说你所见、所体验、所爱、以及所遗失的事物。
没有比向外看和从外面等待回答会更严重地伤害你的发展了,你要知道,你的问题也许只是你最深的情感在你最微妙的时刻所能回答的。
这就是灵感。
你描写你的悲哀与愿望,流逝的思想与对于某一种美的信念——用深幽、寂静、谦虚的真诚描写这一切,用你周围的事物、梦中的图影、回忆中的对象表现自己。
不要关心从外边来的报酬,因为创造者必须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在自身和自身所联接的自然界里得到一切。
严肃和冷嘲寻求事物的深处:在深处暗嘲是走不下去,——若是你把它引近伟大的边缘,你应该立即考量这个理解的方式(暗嘲)是不是发自你本性的一种需要。
这个时候,就是你创造欲最强的时候仿佛写诗变成了一种本性的需要,心灵的呼唤,此时的诗就是最接近我们情感的表达,自然的情感的流露。
我们应该多读书,特别是那些经典而具有深远意义的书。
通过一些好书,我确信它将穿过你的成长的丝纶,在你一切经验、失望与欢悦的线索中成为最重要的一条。
从那里我体验到一些关于创作的本质以及它的深奥与它的永恒的意义,那么我只能说出两个名字:一个伟大的诗人雅阔布生,;一个是在现存的艺术家中无人能与比拟的雕刻家罗丹。
尽可能少读审美批评的文字,——它们多半是一偏之见,已经枯僵在没有生命的硬化中,毫无意义。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1)

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译者序这十封信是莱内·马利亚·里尔克( 1875—— 1926)在他三十岁左右时写给一个青年诗人的。
里尔克除却他诗人的天职外,仍是一个永不疲备的书柬家;他一世写过无数比这十封信更和蔼、更美的信。
但是这十封信却浑然天成,无形中自有首尾;向着青年说得最多。
里边他论到诗和艺术,论到两性的爱,严肃和冷嘲,悲痛和思疑,论到生活和职业的困难——这都是青年人内心常常起伏的问题。
人们爱把青年比作春,这比喻是正确的。
但是相互的相像点与其说是青年人的明朗犹如春阳的明媚,倒不如从此外一个方面看,青年人的愁苦、青年人的生长,更像那在阴云黯淡的风里、雨里、寒里演变着的春。
因为后者比前者更漫长、深重而更存心义。
我常常在任何一个青年的眼前,便联想起荷兰画家梵高的一幅题作《春》的画:那幅画背景是几所矮小、狭小的房子,中央立着一个桃树或杏树,杈丫的枝干上孤独地开着几朵粉红色的花。
我想,这棵树是经过了长远的风雨,此刻还在忍耐着春寒,四围是一个贫乏的世界,在枝干内却流动着生命的汁奖。
这是一个真切地、没有炫耀的春季 !青年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生命无时不需要生长,而外边却不永久是日光和暖和的风。
他们要担当很多的严寒和无情、冷淡和误会。
他们全部都充满了新鲜的生气,而社会的风俗倒是腐旧的,腐旧的像习染了很多遍的衣衫。
他们感觉内心和外界没法协调,到处受着限制,同时又不可以像植物似的那样缄默,他们要向人告诉,——他们找寻能够听取他们话的人,他们找寻能从他们表现力不很充分的话里领会出他们的本义而给予解答的过来人。
在这样的找寻中几乎是一百个青年有一百个绝望了。
但是有一个人,原来是一时的兴会,写出一封抒发自己内心状况的信,既给一个不认识的诗人,那诗人读完了信有所会意,想起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忧如在抚摸他过去身上的伤痕,随即来一封,回答一封,对于每个问题都给一个精粹的回答和剖析。
——同时他却再三申明,人人都要自己料理,旁人是很难给予一些帮助的。
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此时,风静静吹着,一勾月亮缓缓探出,隐约能见着那周遭的云轮廓了。
晚风有些凉,似是将声音也冻缓了,带来片刻寂静,让人不免有些清冷,思绪自然地向内心深处钻去。
内心世界里,除去孤寂,便是这清冷月光。
于是我想要用这清冷月光来问候你,希望您也能从焦躁或麻木中走出,获得这片刻的宁静,亲爱的先生。
我想用这从莱内·马力亚·里尔克信中所学到的问候方式问候正在阅读这份文字的你,希望你能带着这名为“有趣”的第一印象去接触我文字中那执着于感受孤寂、让时间自己走来、自身向内心走去的里尔克去,了解他笔下的可爱及伟大。
浅读《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首先能感受到的便是里尔克对一个向其寻求写诗意见的陌生青年的亲切、包容与关爱。
“每个批评的意图都离我太远”、“报答你的信赖于万一”他在发表自己意见前后如此说道,使人在思考其意见时忍不住便接受了其温柔的教导。
就在这短短十封给那陌生青年的回信间,我看到了里尔克对诗与艺术、两性的爱、生活与职业的独特见解,也见证了一个陌生青年诗人由僵硬刻画到感受生活的成长。
他在诗的方面对青年的教导即使在我草草读来也觉得收获良多。
“没有人能给你出主意,没有人能够帮助你。
只有唯一的一个方法。
请走向内心”了解自己的内心是他做任何事都不可缺少的一环,写诗亦是如此,里克尔教导青年用深幽、寂静、谦虚的真诚描写悲哀与愿望,流逝的思想与对美的信念,其中的真诚尤为重要。
在真诚之下,暗嘲反讽的手法也能自然地描述伟大而严肃的事物,“纯洁地用,它就是纯洁的”。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无意的装腔作势,是自然的混元境地。
就像现今网络上常有的“阴阳”语气,如果是本性的需要,它便会成为严正的工具,是属于自己的创作艺术,如鲁迅一般。
里尔克的这个观点同样用到了两性之爱上,“身体的快感是一种官感体验,与洁净的观赏或是一个甜美的果实放在舌上无二”。
抛去社会对性爱的重重掩饰,将它从一个阴暗信封中拿出,彼时性爱将不再是被“神秘”“羞耻”所包裹的禁忌,从自身出发而不被世俗影响,它便是温存,是生命的延续。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译者序这十封信是莱内·马利亚·里尔克(1875——1926)在他三十岁左右时写给一个青年诗人的。
里尔克除却他诗人的天职外,还是一个永不疲倦的书简家;他一生写过无数比这十封信更亲切、更美的信。
但是这十封信却浑然天成,无形中自有首尾;向着青年说得最多。
里边他论到诗和艺术,论到两性的爱,严肃和冷嘲,悲哀和怀疑,论到生活和职业的艰难——这都是青年人心里时常起伏的问题。
人们爱把青年比作春,这比喻是正确的。
可是彼此的相似点与其说是青年人的晴朗有如春阳的明丽,倒不如从另外一个方面看,青年人的愁苦、青年人的生长,更像那在阴云暗淡的风里、雨里、寒里演变着的春。
因为后者比前者更漫长、沉重而更有意义。
我时常在任何一个青年的面前,便联想起荷兰画家梵高的一幅题作《春》的画:那幅画背景是几所矮小、狭窄的房屋,中央立着一个桃树或杏树,杈丫的枝干上寂寞地开着几朵粉红色的花。
我想,这棵树是经过了长期的风雨,如今还在忍受着春寒,四围是一个穷乏的世界,在枝干内却流动着生命的汁奖。
这是一个真实地、没有夸耀的春天!青年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生命无时不需要生长,而外边却不永远是日光和温暖的风。
他们要担当许多的寒冷和无情、淡漠和误解。
他们一切都充满了新鲜的生气,而社会的习俗却是腐旧的,腐旧的像习染了许多遍的衣衫。
他们觉得内心和外界无法协调,处处受着限制,同时又不能像植物似的那样沉默,他们要向人告诉,——他们寻找能够听取他们话的人,他们寻找能从他们表现力不很充足的话里体会出他们的本意而给以解答的过来人。
在这样的寻找中几乎是一百个青年有一百个失望了。
但是有一个人,本来是一时的兴会,写出一封抒发自己内心状况的信,既给一个不相识的诗人,那诗人读完了信有所会心,想起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仿佛在抚摸他过去身上的伤痕,随即来一封,回答一封,对于每个问题都给一个精辟的回答和分析。
——同时他却一再声明,人人都要自己料理,旁人是很难给以一些帮助的。
可是他告诉我们,人在世上来,是艰难而孤单。
一个个的人在世上好似院里的那些并排的树。
枝枝叶叶也许有些呼应吧,但是它们的根,它们盘结在地下摄取营养的根却更不相干,又沉静,又孤单。
人每每为了无谓的喧嚣,忘却生命的根蒂,不能在寂寞中、在对于草木鸟兽(它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生物)的观察中体验一些生的意义,只在人生的表面上永远往下滑过去。
这样,自然无所谓艰难,也无所谓孤单,只是隐瞒和欺骗。
欺骗和隐瞒的工具,里尔克告诉我们说,是社会的习俗。
人在遇见了艰难,遇见了恐怖,遇见了严重的事物而无法应付时,便会多在习俗的下边去求它的庇护。
它成了人们的避难所,却不是安身立命的地方。
——谁若是要真实地生活,就必须脱离开现成的习俗,自己独立成为一个生存着,但当生活上种种的问题,和我们的始祖所担当过的一样,不能容有一些儿代替。
在这几封信里,处处留搂着这种意义,使读者最受感动。
当我于1931年的春天,第一次读到这一封书信时,觉得字字都好似从自己心里流出来,又流回到自己的心里,感到一种满足,一种兴奋,禁不住读完一封,便翻译一封,为的是寄给不能德文的远方的朋友。
如今已经过了六年,原书不知又重版多少次,而我的译稿则在行箧内睡了几年觉,始终没有印成书。
现在我把它取出来,稍加修改付印,仍然是献给不能读德文原文的朋友。
后边附录一篇里尔科的散文《论“山水”》。
这篇短文内容丰富,在我看来,是抵得住一部艺术学者的专著的。
我尤其喜欢那文里最末的一段话,因为读者自然会读到,恕我不在这里抄引了。
关于里尔科的一生和他的著作,不能在这短短的序中有所叙述。
去年他逝世十周年纪念时,上海的《新诗》月刊第一卷第三期,曾为他出一特辑,读者可以参看。
他的作品有一部分已由卞之琳、梁宗岱、冯至译成中文,散见《沉钟》半月刊、《华胥社论文集》、《新诗》月刊、大公报的《文艺》和《艺术周刊》中。
至于收信人的身世,我知道得很少,大半正如他的《引言》上所说的一样,后来生活把他“赶入了正是这位诗人温暖、和蔼而多情的关怀”所为他“防护的境地”了。
1937年5月1日论“山水”关于古希腊的绘画,我们知道得很少;但这并不会是过于大胆的揣度,它看人正如后来的画家所看到的山水一样。
在一种伟大的绘画艺术不朽的纪念品陶器画上,周围的景物只不过注出名称(房屋或街道),几乎是缩写,只用字头表明;但裸体的人却是一切,他们像是担有满枝果实的树木,像是盛开的花丛,像是群鸟鸣啭的春天。
那诗人对待身体,像是耕种一片田地,为它劳作像是为了收获,有它正如具有一片良好的地基,它是直观的、美的,是一幅画图,其中一切的意义,神与兽、生命的感官都按着韵律的顺序运行着。
那时,人虽已赓续了千万年,但自己还觉得太新鲜,过于自美,不能超越自身而置自身于不顾。
山水不过是:他们走过的那条路,他们跑过的那条道,希腊人的岁月曾在那里消磨过的所有的剧场和舞场;军旅聚集的山谷,冒险里区、年老充满惊奇的回忆而归来的海港;佳节继之以灯烛辉煌、管弦齐奏的良宵,朝神的队伍和神坛畔的游行——这都是“山水”,人在里边生活。
但是,那座山若没有人体形的群神居住,那座山岬,若没有矗立起远远入望的石像,以及那山坡牧童从来没有到过。
这都是生疏的,——他们不值一谈。
一切都是舞台,在人没有登台用他身体上快乐或悲哀的动作充实这场面的时候,它是空虚的。
一切在等待人,人来到什么地方,一切就都退后,把空地让给他。
基督教的艺术失去了这种同身体的关系,并没有因而真实地接近山水;人和物在基督教的艺术中像是字母一半,它们组成有一个句首花体字母的漫长而描绘公演的文句。
人是衣裳,只在地狱里有身体;“山水”也不应该属于尘世。
几乎总是这样,它在什么地方可爱,就必须意味着天堂;它什么地方使人恐怖,荒凉冷酷,就算作永远被遗忘的人们放逐的地方。
人已经看见它;因为人变得狭窄而透明了,但是以他们的方式仍然这样感受“山水”,把它当作一段短短的暂驻,当作一带蒙着绿草的坟墓,下边联系着地狱,上边展开宏伟的天堂作为万物所愿望的、深邃的、奔来的真实。
现在因为忽然有了三个地方、三个住所要经常谈到:天堂、尘世、地狱,——于是地狱的判定就成为迫切必要的了,并且人们必须观看它们,描绘它们:在意大利的早期的画师中间产生了这种描画,超越他们本来的目的,达到完美的境界;我们只要想一想皮萨城圣陵中的壁画。
就会感觉到那时对于“山水”的理解,已经含有一些独立性了。
诚然,人还是想指明一个地方,没有更多的用意,但他用这样的诚意与忠心去做,用这样引人入胜的谈锋,甚至像爱者似地叙说那些与尘世、与这本来被人所怀疑而拒绝的尘世相关联的万物——我们现在看来,那种绘画宛如一首对于万物的赞美诗,圣者们也都齐合唱。
并且人所看到的万物都很新鲜,甚至在观看之际,就联系着一种不断的惊奇和收获丰富的欢悦。
那时自然而然的,人用地赞美天,当他全心渴望要认识天的时候,他就熟识了地。
因为最深的虔心像是一种雨:它从地上升发,又总是落在地上,而是田地的福祉。
人这样无意地感到了温暖、幸福和那从牧野、溪涧、花坡、以及从果实满枝、并排着的树木中放射出来的光彩,他如果画那些圣母像,他就用这些薄雾像是给她们披上一件氅衣,像是给她们戴上一顶冠冕,把“山水”像旗帜似地展开来赞美她们;因为他对于她们还不会备办更为陶醉的庆祝,还不认识能与此相比的忠心:把一切刚刚得到的煤都贡献给她们,并且使之与她们溶化。
这时再也不想是什么地方,也不想是天堂,起始歌咏山水犹如圣母的赞诗,它在明亮而清晰的色彩里鸣响。
但同时有一个大的发展:人画山水时,并不意味着是“山水”,却是他自己;山水成为人的情感的寄托、人的欢悦、素朴与虔诚的比喻。
它成为艺术了。
达芬奇就这样接受它。
他画中的山水都是他最深的体验和智慧的表现,是神秘的自然律含思自鉴的蓝色的明境,是有如“未来”那样伟大而不可思议的远方。
达芬奇最初画人物就像是画他的体验、画他的寂寞地参透了的命运,所以这并非偶然,他觉得山水对于那几乎不能言传的经验、深幽与悲哀,也是一种表现方法。
无限广泛地去运用一切艺术,这种特权就付与这位许多后来者的先驱了;像是用多种的语言,他在各样的艺术中述说他的生命和他生命中的进步与辽远。
还没有人画一幅“山水”像是《蒙娜丽莎》深远的背景那样完全是山水,而又如此是个人的声音与自白。
仿佛一切的人性都蕴蓄在她永远宁静的像中,可是其他一切呈现在人的面前或是超越人的范围以外的事物,都融合在山、树、桥、天、水的神秘的联系里。
这样的“山水”不是一种印象的画,不是一个人对于那些静物的看法,它是完成中的自然,变化中的世界,对于人是这样生疏,有如没有足迹的树林在以作未发现的岛上。
并且把山水看作是一种远方的和生疏的,一种隔离的何无情的,看它完全在自身内演化,这是必要的,如果它应该是任何一种独立艺术的材料与动因;因为若要使它对于我们的命运能成为一种迎刃而解的比喻,它必须是疏远的,跟我们完全是另一回事。
在它崇高的默然中他必须几乎有敌对的意味,才能用山水中的事物给我们的生存以一种新的解释。
达芬奇早已预感着从事山水艺术的制作,就在这种意义里进行着。
它慢慢地从寂寞者的手中制造出来,经过几个世纪。
它慢慢地从寂寞者的手中制作出来,经过几个世纪。
那不得不走的路很长远,因为这并不容易,远远地疏离这个世界,以便不再用本地人偏执的眼光去看它,本地人总爱把他所看到一切运用到他自己或是他的需要上边。
我们知道,人对于周围的事物看的是多么的不清楚,常常必得从远方来一个人告诉我们周围的真面目。
所以人也必须把万物从自己的身边推开,以便后来善于取用较为正确而平静的方式,以稀少的亲切和敬畏的隔离来同它们接近。
因为人对于自然,在不理解的时候,才开始理解它;当人觉得,它是另外的,漠不相关的、也无意容纳我们的时候,人才从自然中走出,寂寞底,从一个寂寞的世界。
若要成为山水艺术家,就必须这样,人不应再物质地去感觉它为我们而含有的意义,却是要对象地看它是一个伟大的现存的真实。
在那我们把人画得伟大的年代,我们曾经这样感受他;但是人却变得飘摇不定,它的像也在变化中不可捉摸了。
自然是较为恒久而伟大,其中的一切运动更为宽广,一切静息也更为单纯而寂寞。
那是人心中的一个渴望,用它崇高的材料来说自己,像是说一些同样的实体,于是毫无事迹发生的山水画就成立了。
人们画出空旷的海、雨日的白屋、无人行走的道路、非常寂寞的流水。
激情越来越消失;人们越懂得这种语言,就以更简洁的方法来运用它。
人沉潜在万物的伟大的静息中,他感到,它们的存在怎样在规律中消隐,没有期待,没有急躁。
并且在他们中间有动物静默地行走,同它们一样担负着日夜的轮替,都合乎规律。
后来有人走入这个环境,作为牧童、作为农夫,或单纯作为一个形体从画的深处显现:那时一切矜夸都离开了他,而我们观看他,他要成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