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在阳光与闪电间
鲁迅向左 胡适向右

回到邵建的《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书中,读到那场近一百年前发生在胡适与鲁迅之间的分歧,看起来只是倡导白话文的同时,给不给文言留恋者以申辩权利的意见之争,看起来只是改造国民性还是建立宪政的何种自由主义路径之争,其实,显露的还是“宽容”与“不宽容”的问题。我期待一种和平的景象,批判胡适的人能够理解胡适,他和他的思想遗产在建设和谐社会的21世纪,他从事的呐喊事业永远是中国知识分子担当的楷模。就像邵建那样,通过客观求证和对真相的还原来重整思想者的遗产。这让我想起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无知》:两个逃离祖国的捷克人,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结果,时间扭曲的记忆,再也找不到一丝的归属感。于是,所有的叙述都聚集到这样一个起点:全球化的现实、大同世界的历史和普世主义价值,能不能让所有新的精神历程,从“宽容”出发。
而邵建是客观地、审慎地、心平气和地走进这块“是非之地”。他更多的是还原了胡适与鲁迅“两种不同的价值遗产”。尽管批评了鲁迅的价值一元论,但邵建强调,启蒙的意义不可低估,但进而又指出,“不能以思想启蒙之一元排斥比如制度建构的他元。”
胡、鲁的相同与相异
邵建的“还原”从东西方两种不同的知识论开始,东方式的“知识意志上的绝对自信”和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知识不确定性的两种知识观取向,导致了二人对“宽容伦理”、“怨恨伦理”截然不同的伦理态度。这两种伦理态度可能也和他们各自赴美国留学和日本留学经历中受到的东西方知识观的强化有关,也必然来自于童年。
胡适还是鲁迅?对于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可能不是简单的学术思想和文化选择问题。鲁迅是自由左翼,相形之下,胡适属自由靠右。五四后的胡适,在未放弃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启蒙的同时,把注意力转移到政治改良和制度建构的努力上。而鲁迅穷其一生行走的是他改造国民性的呕心沥血的启蒙之路。
胡适与鲁迅

胡适与鲁迅你问我,为什么这两年来屡屡推荐你读胡适:胡适的书,或者关于他的书?模仿胡适的老师、历史学家布尔(George Lincoln Burr)的口吻:“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我年纪越大,越觉出胡适的重要性;而且不必和谁对比,他就是我们思想的维生素C。
许多人都喜欢拿胡适与鲁迅对比,通过抬高一者,贬斥另一者,譬如布尔那句话,换做他们,可能会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胡适比鲁迅更重要。
”我说过,鲁迅与胡适并不构成鱼与熊掌的二元关系,对我而言,他们都无比重要,如果说胡适是维生素C,鲁迅则是钙片,你愿意缺哪一个呢。
据我的阅读经验,鲁迅如高山,胡适如平原。
我从16岁开始读鲁迅,此后每重读一次,感悟便深一层,诚可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不过这座高山,只能仰止,无从超越:一来,他难以被超越,鲁迅之后,再无鲁迅(窃以为鲁迅之为鲁迅,个体的因素要超越时代的因素);二来,他不是我的路标,无须超越。
今年我重读鲁迅杂文集,以其写作时间为序,愈读到晚年,愈发心痛。
我以为在《三闲集》《二心集》之后,他的大多杂文,除了教人如何疑心、如何刻薄、如何骂战之外,意思实在不大,原本可以不写。
早在1925年底,他编《华盖集》,便意识到“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尽管他“并不惧惮这些”,然而我们却深深为他惋惜。
以鲁迅之雄才,“写这些无聊的东西”所耗费的精力与时光,若用来写作《故事新编》或《中国小说史略》之类,那该多好。
所以我从不建议你多读鲁迅,他生命晚期的作品,粗览即可,他既百无聊赖,你何必陪他空虚;更不建议你学鲁迅写作,他的杂文,陈义再高,都难改病态的本色。
相比之下,胡适就健康多了(当然另有一个原因,鲁迅不可学而胡适可学,正如李白不可学而杜甫可学、苏轼不可学而辛弃疾可学)。
病态与健康之别,不仅取决于思想,更取决于思想的逻辑与风度。
我们读胡适,他说出了什么道理,只是第二义,第一义在于他怎么说理。
胡适与鲁迅

我以为,鲁迅与胡适实质上是不可比的。
读过孙郁先生?鲁迅与胡适?,我自忖,他尽管花了那样多的笔墨比拟鲁迅与胡适,但内心里也是觉得,二人实际上不可比。
看?鲁迅与胡适?,孙郁先生把“性情〞列在首位,这也大有深意在了。
性情在他看来,二人是不同的;性情不同,还有什么可比性?“鲁迅与胡适由同一营垒到后来的分手、对立,不仅隐含着中国新文化的主线,而且也是东亚在全球化过程中确立自身的文化冲突。
鲁迅与胡适在现代化之旅中的两种思考,两种选择,代表了新型知识分子的精神路向。
〞“鲁迅与胡适的精神,都会给文化的开展带来长长的投影。
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类有过什么奉献的话,鲁迅与胡适的遗产,便会说明着什么。
〞这两段话出自书的?后记?。
据此,我们要说的是,这本书与其说是比拟二人,不如说是梳理二人间的关系,注意的那么是其中的交叉点。
再准确点说,是希望通过二人间的交叉点来思考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思想文化开展的不同路向及其成因。
我曾经读到过一位值得尊敬的文学评论家为此书撰写的评论,文字简洁、精当,结论却令人失望。
他得出的鲁迅比胡适“深刻〞的结论,未能走出传统的思维定势不说,可能也误读了孙著。
可是细想想,这种误读可能还是由于孙郁先生诱导的结果,读?鲁迅与胡适?,一个较深的印象,就是当写到鲁迅时,作者往往使用近乎诗化的文字,竭力挖掘,把优长处推向极致,于缺陷处那么不免优容;而写到胡适,那么大多文字舒缓,肯定处肯定得恰到好处,但态度上总逃不出“尽量理解〞的圈围,往直白里说,有些地方让人有怀揣难言之隐而扭扭捏捏的感觉。
说实在的,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看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胡适与鲁迅地位的变化,不能不成认这样一个事实:鲁迅正在走下神坛,而胡适那么渐渐上升到平地。
我的阅读面很有限,但在我所读到的,关于鲁迅与胡适地位变化的评论以及争论的意见中,有不少就是因为不适应、不习惯于这种变化而产生的。
无论是破口大骂,还是忠心保卫,也无论是全面提升,还是尽情挑刺,实际上在潜意识里都是不希望自己对历史的固有“想象〞落空。
鲁迅和胡适的角色定位

鲁迅、胡适及其角色定位1时间是检验一种思想是否深刻,一种精神是否伟大的试金石。
任何认为的力量,对思想家的诬蔑、诽谤或者美化、扭曲,都无法掩住思想与精神的光华。
时间的流水,必荡涤思想与精神之上的尘埃、光环,被湮没的必重新浮出水面,被蒙蔽的必再次绽放出来,在新的时代,催生新的力量,再次影响历史的进程。
鲁迅、胡适都曾经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的舞台上占据中心地位。
早在生前,鲁迅就被或褒或贬地称为知识界之“权威”,后来则成为名义上的左坛精神盟主。
先生逝后,躯体上那面“民族魂”的旗帜更说明他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地位。
而胡适自留学回来,便首倡白话文震动文坛,后又以半部哲学史,半部文学史奠定其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他发起人权运动,涉足教育,创办报刊,更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知识界的领袖人物。
鲁迅逝去,胡适出走之后,“鲁迅”与“胡适”在中国成为一种文化符号,遭到天渊之别的待遇。
“鲁迅”这一名词头上闪耀着权威论定的三个“家”七个“最”的光环。
早在这位战士的躯体被一面绣着“民族魂”的旗帜覆盖,各种各样的苍蝇、细菌便开始瓜分他的遗产。
而三个家七个最之中不乏对鲁迅的独到的评价,但是一旦成为鲁迅的惟一评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旦成为鲁迅的惟一形象,“鲁迅”这一名词便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与牺牲品,与鲁迅本人毫不相干了。
“文革”时期对鲁迅最大的伤害,在于权威的论断成为惟一论断,阻止了人们自由地接近鲁迅,感受鲁迅。
同一时期,与“胡适”这一名词联系在一起的却是八大册《胡适思想批判》,以及大人物小人物写的大大小小的批判文章。
不但胡适的书不能出版,甚至凡是语及胡适的,都必须划清界限。
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文革”时期的鲁迅神圣化,胡适妖魔化,都曾极大的阻碍了我们对中国现代思想传统的承续。
尽管鲁迅向来被抬高极高的地位,“文革”中与红宝书并列的就是鲁迅的著作。
但是这对鲁迅思想、精神的伤害丝毫不比对胡适的伤害更轻。
今天我们要理解胡适,只要绕开“胡适”这一符号在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的遭遇,直接阅读胡适原著与这一时期之外的相关回忆文章,便可自由地认识、理解胡适。
读书笔记:胡适与鲁迅

阳光总在风雨后——读《胡适与鲁迅》有感胡适与鲁迅是20世纪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鲁迅以其犀利尖锐的笔锋直指黑暗,如同闪电般照亮混沌的社会。
恰恰相反,温和的胡适却更像是阳光,在外面将黑暗照亮。
这是《胡适与鲁迅》的作者邵建先生在该书封面就急于告知读者的观点,而全书更是贯彻了这一思想。
通读全书,胡适与鲁迅仿佛不是我们经常接触的形象,至少我读完后,对他们有了重新的认识,也萌生了对他们思想观念的一些思考,再结合现实的生活,实在受益匪浅。
一本书的作者必然会将自己的爱好喜恶渗透入自己的作品中,不论他如何再三强调自己论断的客观性,他的价值倾向多多少少会影响读者的态度。
邵建先生虽然重在还原两位知识分子的真实性,也多引用原文原话,但在书中还是能捕捉到作者对胡适“tolerance”、“自由主义”的赞赏向往以及对鲁迅某些行为态度的不认同。
不可避免的,我深受作者思想的影响,鲁迅的闪电虽然刺穿了黑暗,让黑暗现出原形,但未免太过激进,憎恶分明,睚眦必报,我不喜欢他这样独断的个人主义。
阳光在黑暗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所以胡适的思想在当时可能被传为笑谈,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错的。
相反,胡适的思想是正确的,只是不能为当时的人所用,或者可以说是当时人们无法实现,如此一来,他的思想便沦为笑柄。
但黑暗不会永远占据着世界,总有一天会雨过天晴,到了那时,胡适的思想就会像阳光那样,将世界一寸一寸地照亮,为大地提供温暖。
依稀记得从小到大我们的语文课本里永远充斥着鲁迅的文学作品,他塑造的阿Q,祥林嫂,闰土等等一类的文学形象深入人心,他们不仅仅是简单的名字,甚至可以用作形容词,它们可以生动地勾勒出一些具有此类典型特征的群体。
他描绘的百草园,他课桌上的“早”,他故乡的山水田地,伙伴邻居似乎离我们如此之近,仿佛我们亲临过现场。
对于鲁迅的面容我没什么印象,但他的形象会一直烙印在我心里,他的勇敢无畏,他的仇恨叹息,他的呼喊沉默都十分清晰。
很奇怪,我对鲁迅的印象都是从课本里得来的,而书里的鲁迅永远是一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先锋模样。
鲁迅与胡适的文化思潮对决

鲁迅与胡适的文化思潮对决20世纪初,中国的文化界迎来了一场激烈的思潮对决,鲁迅与胡适成为两股代表性力量。
鲁迅是一位以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而闻名的作家,而胡适则是推崇西方文化的现代派作家和学者。
这两位文化巨匠的思想碰撞,反映出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抉择与挑战。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鲁迅与胡适的文化思潮对决,并探讨其影响及意义。
一、背景介绍鲁迅和胡适生活在中国近代最为动荡的时期,社会经历了战乱、政治改革、思想解放等巨大变革。
这种背景使得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思想都有着鲜明的态度和看法。
二、鲁迅:批判传统、倡导自由鲁迅以他反对封建迂腐的创作而受到广泛赞誉。
他通过小说、杂文等作品,直接批判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和落后。
他提倡科学、民主、自由,积极主张变革。
他抨击传统文化的陈腐和封建制度的束缚,提倡个人独立和自由思想。
他的代表作《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以及他的杂文,道出了那个时代的民众心声,激起了人们对于现实的思考和对于自由的渴望。
三、胡适:推崇西方、倡导变革胡适是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也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
他在留学日本、美国后,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影响甚深。
他提出了“致力于中西合璧”的思想,主张借鉴和吸纳西方的先进文化,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他强调个人的独立思考和自由创作,反对形式化的文学创作方式。
胡适的代表作有《我的母亲》和《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等。
他通过文学和学术研究,积极倡导变革与进步,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思潮对决的意义和影响鲁迅与胡适的文化思潮对决凸显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种不同观念与价值取向。
双方的辩论使得社会舆论更加广泛地参与到文化思想的传播中来。
鲁迅和胡适都对中国社会的变革和中国文化的前进做出了深远影响。
从中可见,思潮对决的结果并非单纯的胜负,而是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思想碰撞。
这不仅促进了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思考和评价,也进一步激发了中国社会的创新和进步力量。
无论是鲁迅批判封建迷信和落后现象,还是胡适强调融合中西文化的回归,都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和文化进步而努力。
鲁迅与胡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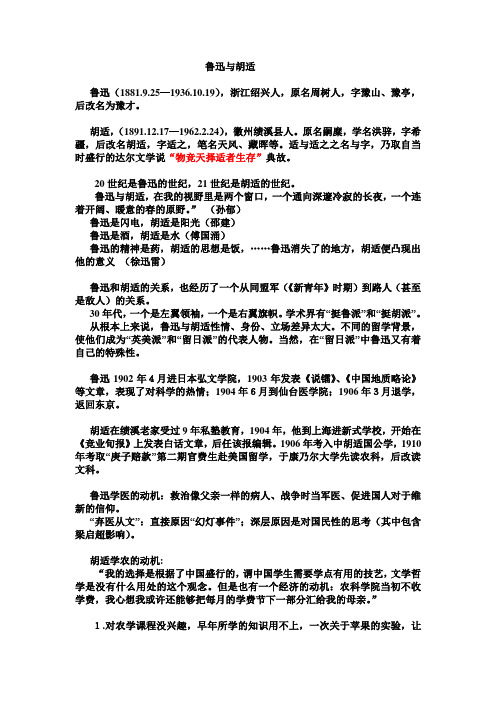
鲁迅与胡适鲁迅(1881.9.25—1936.10.19),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
胡适,(1891.12.17—1962.2.24),徽州绩溪县人。
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
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
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鲁迅与胡适,在我的视野里是两个窗口,一个通向深邃冷寂的长夜,一个连着开阔、暖意的春的原野。
”(孙郁)鲁迅是闪电,胡适是阳光(邵建)鲁迅是酒,胡适是水(傅国涌)鲁迅的精神是药,胡适的思想是饭,……鲁迅消失了的地方,胡适便凸现出他的意义(徐迅雷)鲁迅和胡适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从同盟军(《新青年》时期)到路人(甚至是敌人)的关系。
30年代,一个是左翼领袖,一个是右翼旗帜。
学术界有“挺鲁派”和“挺胡派”。
从根本上来说,鲁迅与胡适性情、身份、立场差异太大。
不同的留学背景,使他们成为“英美派”和“留日派”的代表人物。
当然,在“留日派”中鲁迅又有着自己的特殊性。
鲁迅1902年4月进日本弘文学院,1903年发表《说镭》、《中国地质略论》等文章,表现了对科学的热情;1904年6月到仙台医学院;1906年3月退学,返回东京。
胡适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1904年,他到上海进新式学校,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后任该报编辑。
1906年考入中胡适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
鲁迅学医的动机:救治像父亲一样的病人、战争时当军医、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弃医从文”:直接原因“幻灯事件”;深层原因是对国民性的思考(其中包含梁启超影响)。
胡适学农的动机:“我的选择是根据了中国盛行的,谓中国学生需要学点有用的技艺,文学哲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个观念。
但是也有一个经济的动机:农科学院当初不收学费,我心想我或许还能够把每月的学费节下一部分汇给我的母亲。
20世纪是鲁迅的,21世纪是胡适的

慎之先生显然意识到此,他晚年的工作是胡适未竟事业的赓续。历史就是这么让人感慨,从“李慎之看不起胡适之”到“李慎之赓续胡适之”,这样一个历史流转不是“华丽转身”,而是“风雨苍黄”。今天,二位不再,风雨依旧,当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关注我们时,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未竟就是我们的赓续……
蚌病成珠。晚年李慎之对胡适之的推崇是慎之老人一生的反省,其中更包括血与泪的经验:“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可以说我们这一代是被误导了。‘误导’这两个字,可以说是很沉痛的,也可以说是分量很重的。”是的,历史绕了一个巨大的弧圈,回头看去,却是歧途;但一代人却无可挽回地垫进去了自己的青春、热情、热血乃至生命,这样的反省如何不沉重、又如何不沉痛。慎之先生终于憬悟:“胡适的道路虽然迂远,却是无可替代的”。于是,历史进入21世纪,沉寂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胡适开始重返历史前台。
在慎之先生的表述中,胡适和鲁迅都不是他们个人,而是两种不同的价值。鲁迅的价值取向是苏俄,比如托洛茨基声称:俄国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这是铁与血的纪元。相应地,鲁迅的表述则是“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20世纪铁、血、火、剑的交错辉映,使得这个世纪成为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世纪(这是慎之老人的话:“整个二十世纪,对于形成主流的中国青年人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战争与革命的世纪”),这个世纪属于鲁迅,被边缘化甚至妖魔化的胡适则是这个世纪的“他者”。革命自有其道理,至少革命都是被剧烈的社会不公逼出来的,当然还有煽动。但,如果革命是社会不公的产儿,它一转身却是专制之父:这一点会不会让人始料未及,包括鲁迅。
但,有多少人能接受这个预言,包括能接受这个预言中的胡适呢?在构想这篇文章时,一位读者读我写胡适的《瞧,这人》后给我写来的电子邮件打动了我。这是原话:“我和您素昧平生,给您写这封信显得很唐突,请您原谅。我主要是想向您表明:认同自由价值观念、对胡适先生怀有理解之同情的人虽然很少,但是在慢慢增加。我们‘不怕二三人是少数’。”这最后一句,让我无语良久,在感动中。此人是1970年代人,这个年代出生的他们将是21世纪上半叶的中坚,如果他们能够普遍地接受由胡适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价值,那么,慎之先生的期待便是可以预期的。为此,我们要努力工作。
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读后感

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读后感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读后感提要:但纵观全书,我感觉颇为支离破碎,似乎不同章节的内容没有很好地整合,某些篇章的内容似乎应该大量取自于其他某本书自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读后感张宏杰的书一贯好看,这本《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第一版)也不例外。
题目相当宏大,但是本书的水平和他以前的相比,相差很多。
作者用了半本书,详细描写了中国人是怎么从勇武开放走到怯懦犬儒的过程,后半本论述专制的起源和发展,对我来说,大部分内容都知道,简单翻翻就行了。
唯一有新意的,我觉得是后面对胡适和鲁迅的论述。
作者认为,鲁迅过于理想化,而且过于追求精神上的东西,一生的思想也经过几次重大转向,而胡适则始终坚持改良,立足中国的实际,为当时的执政党提建设性意见。
如果蒋介石做得太过分,胡适也会激烈地批评。
但是鲁迅一贯以批评嘲讽为主,却提不出建设性意见。
作者对胡适和鲁迅的论述给了我很大教益。
最近几十年,尤其是在大陆上,鲁迅的地位被拔得很高,而胡适的地位则低多了,貌似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了解不深、只会写政论的半吊子文人。
因此在绝大部人心里,胡适的地位不仅远不如鲁迅,甚至可能不如林语堂、梁实秋、郭沫若、巴金等人。
但作者的详细论述,至少彻底改变了我的观点。
但纵观全书,我感觉颇为支离破碎,似乎不同章节的内容没有很好地整合,某些篇章的内容似乎应该大量取自于其他某本书。
这是我长期看书后的感受,作者旁征博引揉化观点,和主要取自于一本书,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书的不同部分的风格肯定不一致。
看了后记才知道,我的感觉完全得到了证实。
首先,作者说这本书“不是一本学术着作,……里面也许有太多的感性,太多的个人化感受,……关于国民性的演说显然更粗糙一些”。
显然,作者也认识到这不是一本高水平学术着作。
我甚至觉得这是一本愤青水平的书。
因为我觉得,对于一国国民性的探讨,除了历史文化、制度等因素,还应该有地理、经济因素,可惜这方面探讨的都不多。
胡适和鲁迅的通信

胡适和鲁迅的通信(节选)鲁迅先生你好:。
我们之间的焦点问题在于:你认为我是一个革命者,对于维权这样的活动不应该采用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我想对我们的行为都做一个理性的分析。
关于我的理念:在政治上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信仰上我是一个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我比较清楚自我权利和他人权利的边界,和他人保持适当的距离。
我这种理念比较西化,的确放在中国这种充满着江湖哥们义气的氛围中显得有些不太协调。
我还要再次声明,我不是什么革命者,我是一个追求世俗生活的普通人,我认为反抗暴政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也会注意分寸,避免暴政过分伤害我,也避免过分挑战暴政,自由主义讲究自发演进的秩序,也就是改良,反对暴力革命,也反对在政治纷争和利益纷争中不讲求操守,我希望所有的纷争都应该有君子风度。
尽管国民党很强大,拥有摧毁一切的暴力手段,但是我们仍然保持对它们必要的尊重,因为他们也是人,他们不是魔鬼,是这个制度让他们变得扭曲。
所以我追求的是有分寸的反抗和博弈,你把我想象成革命者是大错而特错的政治想象。
恰恰相反,无论是什么主义,只要搞集权和暴政,这个制度就是我的敌人,同样地,无论这个人信奉的是多么高尚的主义,只要从事暴力活动、恐怖活动,或者在纷争中使用欺骗、背信弃义等手段,都是我的敌人。
我们要避免这种历史的怪圈,我们只有从基督教那里寻找资源,那就是:理性、宽容与和解。
你有很强的革命主义情结,你认为反抗暴政就应该无所不用其极,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
我注意到你的观念中有很浓厚的佛家色彩和江湖义气,我不喜欢讲因果报应,我相信我们都是罪人,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只有通过宽容与和解才能找到共同的出路,而不是以恶制恶。
中国古人曾讲"以暴易暴,未知其可",你看看中国五千年的暴力轮回了多少次,数都数不清,结果如何呢?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仍然走不出那种以暴易暴、以恶制恶的思维怪圈,我们就不会进步,这个时代就不会进步,就是新桃换旧符,无非是统治者变了,统治模式丝毫不会改变。
从历史文化视角看20世纪的胡适与鲁迅的个性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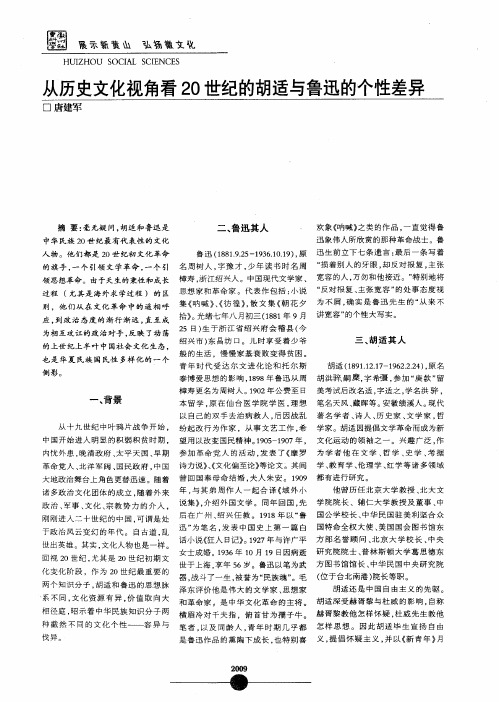
中 国开 始 进 入 明显 的 积 弱 积 贫 时 期 . 望 用 以改 变 国民 精 神 。 9 5 10 1 0 — 97年 , 文 化 运 动 的领 袖 之 一 。 兴趣 广 泛 , 作 发 摩 哲 史 考 内忧 外 患 , 清 政 府 、 平 天 国 、 期 参 加 革 命 党 人 的 活 动 , 表 了 《 罗 为 学 者 他 在 文 学 、 学 、 学 、 据 晚 太 早 、文 等论 文 。其 间 学 、 育 学 、 理 学 、 学 等 诸 多领 域 教 伦 红 革 命 党 人 、 洋 军 阀 、 民 政 府 , 国 诗 力说 》 《 化 偏 至论 》 北 国 中 夫 99 大 地政 治 舞台 上 角 色 更 替迅 速 。随 着 曾 回 国 奉 母 命 结 婚 , 人 朱 安 。 10 都 有 进 行 研 究 。 他 曾 历 任 北 京 大 学 教 授 、 大 文 北 年 , 其 弟 周 作 人 一 起 合 译 《 外 小 与 域 诸 多 政 治 文 化 团体 的 成 立 . 着 外 来 随 , 先 政 治 、 事 、 化 、 教 势 力 的 介 入 , 说 集 》 介 绍 外 国 文 学 。 同年 回 国 , 军 文 宗 后在广 州 、 兴任 教 。11 绍 9 8年 以 “ 鲁 刚 刚 进 入 二 十 世 纪 的 中 国 , 谓 是 处 可 迅 ” 笔 名 , 表 中 国 史 上 第 一 篇 白 为 发 于 政 治 风 云 变 幻 的年 代 。 自古 道 , 乱 话 小说 《 人 日记 》 1 2 狂 。 9 7年 与许 广平 世 出 英雄 。其 实 , 文化 人 物 也 是 一 样 。 女 士成 婚 。 9 6年 1 13 O月 1 9日因病 逝 回视 2 0世 纪 , 尤其 是 2 0世纪 初 期 文 世 于 上海 , 享年 5 6岁 。鲁 迅 以 笔 为武 化 变 化 阶 段 ,作 为 2 O世 纪 最 重 要 的 器 , 斗了一生 , 誉为“ 族魂” 战 被 民 。毛 两 个 知 识 分 子 , 适 和 鲁 迅 的 思 想 脉 胡 泽 东 评 价 他 是 伟 大 的 文 学 家 、 想 家 思 系 不 同 , 化 资 源 有 异 , 值 取 向 大 文 价 和 革 命 家 。是 中华 文 化 革 命 的 主 将 。 相 径 庭 , 示 着 中 华 民 族 知 识 分 子 两 昭 横 眉 冷 对 干 夫 指 ,俯 首 甘 为 孺 子 牛 。 种 截 然 不 同 的 文 化 个 性 —— 容 异 与 笔 者 。 及 同 龄 人 , 年 时 期 几 乎 都 以 青
[精品](精品)希望者与绝望者——胡适与鲁迅
希望者与绝望者——胡适与鲁迅](https://img.taocdn.com/s3/m/c3ec6e32bcd126fff7050b76.png)
()希望者与绝望者——胡适与鲁迅()希望者与绝望者——胡适与鲁迅碰壁书生()希望者与绝望者——胡适与鲁迅班布尔汗胡适与鲁迅,两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在文化层面上,若说激进,可以说是针尖对麦芒,不分轩轾。
但在随后的日子里,两人从隔膜到生疏到分道扬镳,直至近乎敌人。
如果以官方的说法,那是因为胡适逐渐被国民党反动派收买,成为过河卒子,是与有权势者相勾结,扼杀中国的新生力量,而鲁迅,则一直是站在劳苦大众一方,决绝的与有权势者作着毫不妥协的斗争。
两者一个是在后退另一个是在不断前进。
成为敌对,那就毫不奇怪了。
可如果历史人物或是历史事件都是如此概念化的,如教科书般的解释,容易倒是容易,浅陋却也是一定的了。
到现在为止,《鲁迅全集》可以买到,但其中被抽掉的文章或章节却不在少数,《胡适全集》虽在市面上也有销售,但被阉割的更不成样子,在继承文化遗产的婊子牌坊之后,有着极为卑鄙的取其糟粕,去其精华的的用心。
但既然已经把东西摆在那里,虽然没有鲁迅来特意标出党老爷的蹄印,不想欲盖弥彰,也是困难的。
两人在文化层面上有着相同的追求。
都曾经希望用文化改变国民性,然后在国民性改造的基础上,改变中国的政治。
一个从诗入手,一个以小说作先锋,都从默默无闻而名声大噪,成为文化上的旗手。
文化是他们的当务之急,而政治则仿佛还很遥远。
而最初的志同道合,由于他们年轻时所不同的经历,很快就出现了变奏,终于在不断深的介入到政治而凸现出来,分道扬镳的命运已经是注定的了。
鲁迅早年留学于日本学医,起因是父亲被中医所误,要去学习先进的西医科学,但在一次看电影时,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明白了治疗精神比治疗躯体更为重要,于是决定弃医从文改造国民性,但因为父亲的死,他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已完全的不信任,并进而对于一切都有着深刻的怀疑,他这时已经准备好要对一切丑恶开战了。
从始至终,他都没有走出文化的层面,文化是追求完美的,于是他设想了一个乌托邦,然后以此为基础用医生的眼睛来审视自己的国家,洞察力之惊人连他自己都感到不堪负重,他发现了太多的丑恶,揭露得越多自己便越陷入绝望。
胡适读书会十六期读书报告:胡适与鲁迅

那么胡适是怎么认识自由主义以及自由与容忍的呢?在20年代,胡适就有这样的认识:“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在1948的《自由主义》一文中,胡适称赞自由主义,说:“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反过来,胡适也主张少数人也要容忍多数人,如果少数人时常怀有“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教方罢休”的心理,多数人也不能不行“斩草除根”的算计了。在那样的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胡适提出这样的一个主张,无疑是空谷足音无人听了,可是并不能确定胡适的这话不对。而针对那些不要和平演进,要暴力革命的年轻人,胡适说:“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承认反对的人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的说,自由主义为了尊敬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而鲁迅呢?“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胡鲁的截然相反,从中也不难看出谁的表达是自由主义了。
鲁迅与胡适的恩怨情仇(随笔)

鲁迅与胡适的恩怨情仇(随笔)鲁迅与胡适的恩怨情仇(随笔)西山守望近段时间,系统地读了些鲁迅与胡适的文集,以及介绍两位先生的传记文章。
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更深刻地感受到发生在“五四”时代两位大知识分子之间,由合到分,由近而远的两种选择,以及他们之间无比纠结的爱恨情仇。
(一)从鲁迅的日记中看,两人交往于1918年,而真正来往于1923和1924年。
这期间,两人有着比较一致的思想观点与共同主张。
那就是: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特别是在反对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方面,两人亦有共识:或是胡适倡导观念,鲁迅相继发表文章,予以呼应;或是两人同时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对某一问题作深入的阐发。
鲁迅倡导文学革命,注重新文学的创作实践。
他在《〈自选集〉自序》一文中表述说:“我做小说,是开手于1918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
”鲁迅认为,文学革命实际上是对死的封建文学的革命,首先要有思想的革命,它需要胆识和勇气。
而胡适倡导文学革命,则注重从理论上突破,先后写出了《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在否定旧文学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革命文学论述。
从《鲁迅日记》中,也可以见证两人在学术研究方面曾经的过从甚密。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前后,曾多次征求过胡适的意见。
胡适在写作《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一书时,也曾多次向鲁迅请教。
在胡适的作品中也有明确描述两人友谊的片断:两人在讨论学术问题时,从不拐弯抹角,多是正确的欣然表示认同,错误的直言相告,有疑问的也不苟同,互相商榷。
(二)鲁迅与胡适的矛盾,始于1925年。
那时的鲁迅,正由官场走向民间,而胡适,则由书斋走向议政之路。
在鲁迅的文章里,也有明确记载:先是清朝末代黄帝溥仪召见胡适,而后,则是胡适与段祺瑞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互递秋波。
一个成了现政权的拥护者,一个成了现政权的批评者,两种选择,使两人分道扬镳,站在了对立面上。
他们以各自为中心,分别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使寂静的知识界一时热闹起来。
鲁迅胡适并行不悖

《 鲁迅全集》 1 卷 4 3 ) 第 4 0 页 约会去不成 ,
“ 抱歉 …‘ 拜托 …‘ 首” 顿 ,一个若 非 “ 俯首
生生死线上的黄金分割点吗?
在纪念先生逝世 7 0周年 的 日子里 ,
文集》( 民文学 出版社 1 9 年 1 月版 ) 郑重地表示 了歉意 ,而 自己正在重病 中 。 人 98 2 版《 鲁迅全 集》( 民文学 出版社 18 年 甘为孺子牛 ” 人 91 的人 , 么可能在生命的最 怎
个有展示 的意味 ,一 个有珍藏的意 味? 前者 为公众开放 ,后者为 自我提 升?前 。 者从 “ ” 后者 从 ” 是的 , 沉重是肯定的 。 大先生要 “ 肩住黑 者尊 敬?不完全 是 ,但还真有一 点细微 暗的闸 门” 要知道 , NH所处的时代 , , 他 i ,
大抵和个人 斗争 ,但实 为公仇 ,决 非私 点不对劲 。胡适的 自由思 想与鲁迅的 社
个人的少; 用一个人的有 , 贬损另一个
物 馆发起了 “ 鲁迅与胡适研讨会 ” ;学者 人的无; 用一个人的长板 , 贬损另一个人 的短板 , 都是非逻辑非理性思维 。 鲁迅 胡 有学者说 ,鲁迅精神是 “ ” 药 ,胡适 是对立而是并列; 这是左手与右手 , 不是 喻之 : 鲁迅如拿着橡皮擦的左手 , 擦去误 ( 中国工人 出版社 2 0 年 8 0 6 月第2 次印刷 ) 适 ,并行不悖 。 出版了 , 作家韩石山的学术著作 《 少不读
学者谢泳主编的学术著作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8月第2次印刷出版了作家韩石山的学术著作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10月第1版也面世了鲁胡之争的话题于是旧貌展新颜
维普资讯
UANCHA YUSI AO K
鲁迅与胡适的异中之同

鲁迅与胡适的异中之同游宇明一些人习惯于将鲁迅与胡适看作死敌,在他们看来,鲁迅是属于左翼的,而胡适则顽固地坚持依附某某集团,彼此“道不同,不相与谋”。
其实,这样的看法是非常狭隘的。
无须讳言,鲁迅与胡适不怎么和谐。
鲁迅的杂文经常有讽刺胡适的字句,连“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别人说的话也曾被鲁迅拿来说事。
他们一个读的是矿路学堂之类的改良型学校,即使留学也进的是仙台医学专科学校这样的偏于技术的学校;一个入的是新式学堂,留学时研究的是人文学科之祖——哲学。
一个基本上与官方“老死不相往来”,甚至上过特务们的暗杀名单;一个虽然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见解,经常给带头大哥提意见,但始终跟官方保持良好的关系。
一个不时宣称要青年人不读中国书,但其思想意识却渗透着传统文化;一个思想高度西化,有中国自由主义始祖之称。
有个段子颇能说明两人的后期关系。
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赴北平省亲,应邀到一些大学演讲。
某次,两人相遇了。
胡适开玩笑说:“你又卷土重来了。
”鲁迅回答:“我马上就卷土重去,绝不抢你的饭碗。
”胡适尴尬地说:“还是老脾气呵!”鲁迅回答:“这叫至死不变!”然而,有一点我们没有想到,鲁迅与胡适曾经关系非常密切,他们一起曾参与《新青年》的编辑会议,胡适想出版《尝试集》,也曾让鲁迅替他删减诗作。
就算是后期两人暂行暂远,他们在做人处事上依然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鲁迅与胡适都是富有亲和力的人。
鲁迅有“青年导师”之称,在文学上尽力托举一些有潜力的年轻作家,他不止一次地或者在书信中鼓励这些人,甚至替他们荐稿、作序。
肖军、肖红、柔石、殷夫、白薇、叶紫、巴金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得到过他的帮助。
要知道,当时的鲁迅在文坛的地位如日中天,约稿很多,他能抽出时间替青年作家做这些事,足见其为人的热心。
胡适呢,交往的人自然更多了,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官员,有学者,也有年轻学生,当时民国学界有点声望的人物,比如梅贻琦、蒋梦麟、傅斯年、陈寅恪、翁文灏、丁文江等等,几乎都是他的朋友。
胡适与鲁迅:能找到一个共同的起点吗?

我曾读过许多鲁迅的论战对手当年的文字,他们的文字在鲁迅的凌厉攻势面前,常常不堪一击。我也读过后来去了台湾的女作家苏雪林写的那本书《我论鲁迅》,通篇都是对鲁迅的不敬,但是从头到尾读下来,也找不出多少有分量的足以击倒鲁迅的事实依据。鲁迅生前论敌似乎遍于国中,却仿佛常胜将军,这是我们这些吃着鲁迅偏饭成长起来的人,从教科书中得出的一个模糊印象。历史的事实是,包括胡适在内许多知识分子不愿意与鲁迅对阵,不愿意选择与鲁迅交锋的姿态。在一个天下未定于一尊的时代,他们能包容鲁迅,包容一个住在上海租界坚持社会批判的鲁迅。这个更重要的因素,可能常常被忽略了,就是像胡适这样的人,是不愿挺身回应鲁迅,在这方面浪费笔墨的,这有周策纵的回忆可证,到晚年,鲁迅去世多年,胡适说过鲁迅是自己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鲁迅正面批评他也好,侧面讽刺他、挖苦他也罢,他都一概不回应,不仅如此,当他的学生苏雪林在鲁迅身后写信抨击鲁迅时,他还给了她很重的批评。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胡适: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出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与俄国终不的当然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个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两面鲜明的旗帜,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影响着一代代后来人。他们的敌人是共同的,那就是黑暗。阳光温暖和煦,在黑暗之外将黑暗照亮;闪电迅猛锐利,在黑暗内部将黑暗刺穿。他们就是胡适和鲁迅。
成稿于08-03-06
摘抄:
如果说“威权型独裁”基本上是一种传统型独裁的话,极权型独裁则是它的现代形态。极权型独裁表现为“政治全能主义”,它从两个方向上把政治权力发挥到极致:一是权力的范围,一是权力的程度。前者,权力走向“无限”,即政治权力渗透于社会的每一空间,它使经济、文化和一般社会生活都高度政治化。整个社会已然没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没有民间社会可言。社会的边界在哪里,权力的半径就指向哪里。后者,权力走向“无形”,作为一种深度渗透,政治权力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进入看不见的思想、观念、意识和人心。
关于鲁迅,说得太多了,前文《假如鲁迅还活着》已经表达了我的景仰之情。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对胡适的了解也许并不真实,更不客观。加上胡适温和宽忍的性格,以及与蒋家王朝特殊的渊源,使其始终游离于“官方的”道德体系和是非标准之外,以至成为“软弱、妥协、不彻底”、“帮闲、帮凶”的代名词而大受挞伐,甚至蒙尘于史。
鲁迅的自由主义体现在个人自由和捍卫个人自由的实践上,这种以己为中枢的的自由初读之下给人痛快淋漓的个性豪放解放快感,然细细回味,我却读出了卢梭的民粹主义气息。个人自由须止于他人自由之前,是法治下的自由,这点在密尔和霍布豪斯的思想体系里表明无疑。而且洛克的《政府论》指出,在一个政治社会里,遵照社会契约,每一成员放弃自然法权力并把所有不排斥他可以向社会所建立的法律请求保护的事项都交由社会处理。所以严复翻译密尔的《论自由》时,由于中文词库里尚无自由一词,故神使鬼差命名为《群己权界论》,默契中得真谛,绝妙!故由此分析鲁迅身上的自由主义,是不完整的,同时他浓厚的无政府主义、唯意志主义和尼采的超人哲学让我有点心悸不安,一边呼吁立人,一边大斥庸众,“置众人”“排众数”,很是矛盾。这在自由主义那里是解释不痛的,倒是鲁迅曾自谓为“个人的无治主义”,此等同“无治的自由主义“,与胡适“法治的自由主义”泾渭分明。从自由到自由主义,是人类天性向理性的演绎。再者,从两人的思想启蒙典籍上即能一瞥,鲁迅熟习达尔文的《天演论》甚至能背诵一些篇章可是对密尔的《论自由》是轻斥的;胡适则相反,从他的多次演讲中皆能看到密尔的萍踪,虽然作为“古典自由主义最后一人”的密尔较之洛克纯正的古典自由主义学说缺乏对于私有财产的肯定态度,是为白璧微瑕。按此相对应到各自的民主观,鲁迅归于古希腊广场意义上的“直接民主”,胡适则是以立宪代议制出现的现代民主。
从两人最直接的行为效应上看差异,体现在一个如何解决中国出路的“路径依赖”之上,胡适是“政治制度的依赖”,他素抱的自由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制度诉求,力图将英美自由主义在制度上的内容即代议制政府与宪政民主移植到中国社会中来,例如胡适的好政府主义建立在三项基本要求上,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鲁迅是“思想启蒙的依赖”,强调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坚持“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两种路径以及向着各自方向行进所作的努力,合起来绘出了了中国现代思想界的波澜壮阔画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要了解胡适必须先了解他是身世。胡适祖籍安徽绩溪,世代乡居,靠小本经营茶叶为生,主要是将家乡的茶叶贩运到上海一带自设的茶叶店销售。父亲胡铁花于同治四年进学为秀才,但参加了几次省试都不能如愿,便进了龙门书院读书,在此期间对中国地理,尤其是边疆的地理发生了研究的兴趣。光绪七年,胡铁花远游北京,被一位经商的族伯推荐给时在宁古塔(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境内)的钦差吴大徵,吴对他的地理知识非常赏识,带着他巡行阅边,1882年中俄堪定疆界时,他们曾一同会晤俄方堪界人员,也在这年,吴大徵聘请胡铁花作为其幕僚,参与机要,并专折向朝廷保荐了胡铁花。
胡适与鲁迅,阳光与闪电,公民与国民,见仁见智。
作为鲁迅的乡人,作为红旗下的臭蛋,鲁迅对我的影响可谓刻骨铭心,自然包括权威化和商业化后的形象,这些已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人间鲁迅”;而饮汲胡适的“清汤寡水”则是近两年内的事。按理说,一个开放社会、宽容时代,蕴涵了各种分化群体,容许接纳各自的不同理想、不同使命,彼此无法互换。不过,我内心里是倾向胡适,从上推行制度改良,从下唤醒人们的权利意识,吃喝拉撒中培养政治生活的习惯,在妥协与调和中上下层面良性互动。一个博弈的时代里,宪政就这般开张了。而鲁迅的呐喊似乎难以适合一个“蝇营狗苟”的世俗社会,他的思想走向不是趋于无政府主义即是道德至上的政治全能主义,也就是像1793年腥风血雨里的雅各宾派。
到美国后,迫于生计,胡适先是就读于康乃尔大学的农学院,一年后转入该校的文学院,读政治、经济、哲学等,1915年,胡适对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转到常春藤盟校的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哲学。唐德刚先生著的《胡适口述自传》中说:“杜威对我其后一生的文化生命有决定性的影响。”他的实证主义思想体系帮助胡适找到了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的治学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
当然早期的胡适身上也有着激进因子作怪,这点在邵建《瞧,这人》一书里有详述,炸弹诗也罢,“推翻这个鸟政府”也罢,或者是将“惑世诬民”的否定冠于《西游记》《封神演义》之类的神魔小说,但胡适一生的轨迹是始终趋于保守的,及至晚年的胡适被余英时喻为“落日余晖”,而殷海光则略带着腹诽,称为“余晖犹存”。值得玩味的是,“落日余晖”之意象不仅仅独属于胡适一人,也属于殷海光、雷震和他们的《自由中国》,属于20世纪在凄风苦雨中死守阵地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
关于Tolerance(宽容)之议上,是本书一大吃重点,作者总揽观点如下:“胡文化”便是一种以宽容理念为价值取向的自由主义文化,“鲁文化”则相反,它是公开拒绝宽容并带有其独断性的刀笔文化。从“我一个都不宽恕”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从“明确的是非”“热烈的好恶”到反对“正义的火气”,一边本能一边知性,一边“怨恨伦理学”一边“责任伦理学”,前者由“恨”生出复仇心理,绝望中对谁都开枪。孰对孰过,不言自喻。
胡铁花笃信宋儒,尤其崇奉程朱,即所谓的理学,对当时清朝政府信仰的政治宗教提出诸多怀疑,这些对胡适后来的治学理念和政治信仰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1910年,胡适作为第二批“庚款留学生”赴美,据说胡适是提前一个月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清华的留美考试,结果全榜70名,胡适以勉强及格的分数(五十九点几)考中第55名,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很接近榜尾了”。
鲁迅揭示的是一种道德症候和精神痼疾,他的医治之道是从精神自身入手,如此一来过分相信精神的内在超越,就好比当下面对道德败落、世风日下用喊唱道德高调是于事无济的;更何况,人性这东西我认为是无法改造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毋论古今中西,个性乃人类的福祉,个性自然包括各种毛病缺陷,要想给每人本性任何公平的发展机会,最主要的事是容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若真有改造成功之日,岂不成了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所有人可以按各自生产编号来称呼了。
与出生于没落的封建地主家庭,亲身体会到家道中落的世态炎凉,并希望从根本上“砸碎”旧体制的鲁迅不同,深受英美文化熏陶,一生服膺英美自由主义的胡适,希望用西方传统的改良方式实现他心目中的民主政治。
胡适首先从改良文学入手,“五四”前夕,他最有名的一篇文学革命宣言式的文章题目就叫《文学改良刍议》,对文学改良提出了八条建议,俗称“胡八条”。这一运动对推动白话文的革命厥功至伟。从文学到政治,胡适自然而然地运用了他的改良主张,提倡从体制内部实行温和的政策改变现状,反对使用激烈的革命手段,从而使他的后半生始终与需要改良的体制纠缠不清,甚至进入了体制内部,被人们误认为是旧体制的维护者,这也是他“帮闲、帮凶”恶名的起因。然而遗憾的是,20世纪的中国显然选择了鲁迅而不是胡适,即使在当时,鲁迅的声音也比胡适更响亮,更具号召力。
1892年,胡铁花被遴选赴台湾襄赞省政(相当与巡抚助理),在此期间他巡视全岛防务,重新训练海军,改革台湾盐政。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遭到台湾军民的一致反对,他们群起呼吁当时的巡抚唐景崧制止割让,并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推选唐景崧为“总统”。胡铁花则奉命回国,并与同年病逝于厦门。
《20世纪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在阳光与闪电间
闲话几句,此书的责任编辑是徐晓,那个参与《今天》的徐晓,那个写作《半生为人》的徐晓,傅老师极力举荐此书,作者贯注的心血与思想是一方面,出版的艰难更是值得书写。
尚在封皮上,邵建开门见山将温和的胡适与犀利的鲁迅比作阳光与闪电,同为面对黑暗的两种方式。我猜测此譬喻采颉自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一书,朱学勤是这么说的:“所谓阳光,是指北美革命的性格,温和而耐久;而闪电则指法国革命之特色,爆发于黑暗,电闪雷鸣,暴雨如注,照亮并荡涤旧世界的角角落落,但也迅速回归黑暗。”无独有偶,如此具有对立性的相似现象不仅浮现在胡鲁之争,美法革命上,还有法兰西民族自己的知识分子群体,激进而张扬着感情力量的一方可以从左拉、卢梭历数到当代的萨特、福科、德里达;而代表理性、自由主义的则有托克维尔、雷蒙?阿隆,相对孤单势薄,所以法国总是左翼知识分子的温床,至始笼罩着一种为各式乌托邦信念而奋斗的浪漫主义情怀,一种轻浮的文学家情结,或者按照朱学勤的说法“几何与美学的差别”。而中国呢?
但20世纪里,鲁迅的价值更多被官方扭曲包装了,所以一俟有机会重新解读,我承认我也无可避免带上了不公正的心理,犹如将对官方意识形态对我造成的伤害无辜旁及到夫子身上。作为独立知识分子,至始远离权力,这种体制外的批判精神难能可贵,与胡适的体制内建设性批判形成互补。在这点上,鲁迅是决绝孤傲、令人起敬的,胡适的矛盾言行多被世人诟病,邵建的辩护理由很准确到位“胡适不断更换主子,就是不断承认现政权的合法性。承认现政权的合法性,就是反对推翻现政权的一切暴力行为。”就是说维护现政权出自反对火与剑的革命,反对现政权出于实行宪政之梦,出于知识分子的批判定位。同时体制内批评进入权力本身之故不追求社会效应,尤需要一种不刺激对方的温和方式。导致悲剧的是,胡适身上的欧美民主底色在中国的畸形土壤上遭遇了困境,力求程序正义的他往往身不由己被推到实质正义的反面,成为愤怒民意和道德理由下的替罪羊,哎,谁让这个过程中行为主体的方式手段总是充满阴谋与鲜血呢,然,揆诸长远意义上看,胡适功莫大焉。具体举一例,面对辛亥革命后不久发生的贿选丑闻,胡适的分析与众不同:“民治的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教育。给他一票,他今天也许拿去做买卖,但将来总有不肯卖票的一日;但是你若不给他一票,他现在虽然没有卖票的机会,将来也没有不卖票的本领。”时光倏忽而去,今日的我感受巨深,选票能标价买卖,从反面肯定了选票的价值,现今是杜绝了贿选陋习,可连着选举的形式一并废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