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医疗事故处理
国外医患纠纷处理机制及借鉴

国外医患纠纷处理机制及借鉴在国外,医患纠纷处理机制已经较为成熟。
本文将介绍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国家的医患纠纷处理机制,并对其进行借鉴总结。
一、美国美国对医疗事故的处理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协商达成和解;二是通过司法程序解决。
1.协商解决美国的协商解决主要是指患者和医生之间的谈判,通过洽谈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和解协议。
此种方式通常是由专业的调解员或律师指导并协助处理。
2.司法程序解决美国的司法程序主要是通过患者将医生或医院起诉的方式来解决。
按照美国各州不同的法律规定,患者可以选择哪种司法程序途径来解决医疗事故问题。
其中,最常见的诉讼途径为民事诉讼,具体程序如下:(1)起诉程序患者通过律师起诉医生或医院。
(2)诉讼程序患者和医生或医院在某一法院受审。
在这一过程中,律师将出庭辩护。
(3)判决程序法院将根据案情和法律规定作出最终判决。
二、加拿大加拿大的医患纠纷处理主要通过以下途径:1.协商解决加拿大的协商解决方式与美国类似,但加拿大也有其自己独特的解决方式。
例如,一些省份设立了“纠纷调解中心”,专门协调患者和医生之间的纠纷,协商达成和解。
2.仲裁解决加拿大多个省份也设立了纠纷仲裁委员会来解决医患纠纷。
仲裁委员会通常是由专业的仲裁员组成,仲裁员会根据法律规定作为客观的第三方进行仲裁,裁决一些小额争议。
三、英国英国采取的医患纠纷处理机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1.投诉阶段患者首先向医院或临床中心投诉,投诉通常由医院或中心的管理人员进行处理。
2.独立机构阶段如果患者不满意医院或中心的投诉处理结果,可以向独立机构提出申诉。
独立机构尽可能在短时间内详细了解事情的经过,最终对申诉做出判断。
3.司法程序阶段如果患者对独立机构作出的裁决不满意,可以选择通过司法程序来解决医患纠纷。
对于涉及到大额赔偿的争议,通常将委托专业律师处理。
综上所述,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国家的医患纠纷处理机制,大多都是以协商为主,辅以司法程序或独立机构的方式来解决。
国外医疗纠纷处理的方式方法【热门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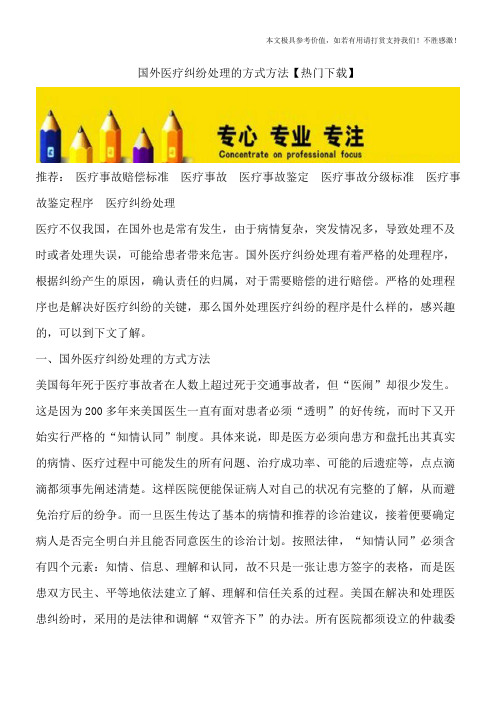
国外医疗纠纷处理的方式方法【热门下载】推荐:医疗事故赔偿标准医疗事故医疗事故鉴定医疗事故分级标准医疗事故鉴定程序医疗纠纷处理医疗不仅我国,在国外也是常有发生,由于病情复杂,突发情况多,导致处理不及时或者处理失误,可能给患者带来危害。
国外医疗纠纷处理有着严格的处理程序,根据纠纷产生的原因,确认责任的归属,对于需要赔偿的进行赔偿。
严格的处理程序也是解决好医疗纠纷的关键,那么国外处理医疗纠纷的程序是什么样的,感兴趣的,可以到下文了解。
一、国外医疗纠纷处理的方式方法美国每年死于医疗事故者在人数上超过死于交通事故者,但“医闹”却很少发生。
这是因为200多年来美国医生一直有面对患者必须“透明”的好传统,而时下又开始实行严格的“知情认同”制度。
具体来说,即是医方必须向患方和盘托出其真实的病情、医疗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所有问题、治疗成功率、可能的后遗症等,点点滴滴都须事先阐述清楚。
这样医院便能保证病人对自己的状况有完整的了解,从而避免治疗后的纷争。
而一旦医生传达了基本的病情和推荐的诊治建议,接着便要确定病人是否完全明白并且能否同意医生的诊治计划。
按照法律,“知情认同”必须含有四个元素:知情、信息、理解和认同,故不只是一张让患方签字的表格,而是医患双方民主、平等地依法建立了解、理解和信任关系的过程。
美国在解决和处理医患纠纷时,采用的是法律和调解“双管齐下”的办法。
所有医院都须设立的仲裁委员会,其实就是“变相”的调解委员会,成员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
仲裁委员会的任务一是专门负责调查医疗事故,调查的重点在于认证主管医生是否尽责尽力以及是否有过失,并向患方如实通报。
一旦证实主管医生有过失,便向司法部门报告,由法院作出裁决和处罚。
二是担负着类似我国居委会里“调解委员会”的角色。
由于医、患双方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医患发生冲突实际上在所难免,此时委员会就得出面,负责“缓冲”双方的紧张关系,说白了即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直至双方达到理解或谅解。
国外医疗事故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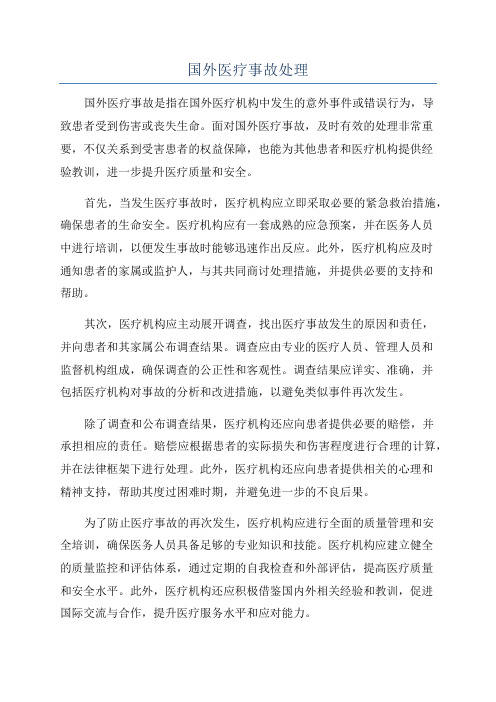
国外医疗事故处理国外医疗事故是指在国外医疗机构中发生的意外事件或错误行为,导致患者受到伤害或丧失生命。
面对国外医疗事故,及时有效的处理非常重要,不仅关系到受害患者的权益保障,也能为其他患者和医疗机构提供经验教训,进一步提升医疗质量和安全。
首先,当发生医疗事故时,医疗机构应立即采取必要的紧急救治措施,确保患者的生命安全。
医疗机构应有一套成熟的应急预案,并在医务人员中进行培训,以便发生事故时能够迅速作出反应。
此外,医疗机构应及时通知患者的家属或监护人,与其共同商讨处理措施,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其次,医疗机构应主动展开调查,找出医疗事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并向患者和其家属公布调查结果。
调查应由专业的医疗人员、管理人员和监督机构组成,确保调查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调查结果应详实、准确,并包括医疗机构对事故的分析和改进措施,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除了调查和公布调查结果,医疗机构还应向患者提供必要的赔偿,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赔偿应根据患者的实际损失和伤害程度进行合理的计算,并在法律框架下进行处理。
此外,医疗机构还应向患者提供相关的心理和精神支持,帮助其度过困难时期,并避免进一步的不良后果。
为了防止医疗事故的再次发生,医疗机构应进行全面的质量管理和安全培训,确保医务人员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医疗机构应建立健全的质量监控和评估体系,通过定期的自我检查和外部评估,提高医疗质量和安全水平。
此外,医疗机构还应积极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和教训,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和应对能力。
最后,国外医疗事故的处理应注重法律和国际规范的遵守。
针对医疗事故的法律责任和惩罚机制应明确和有效,以起到震慑和警示作用。
医疗机构应了解国际规范和标准,并根据其要求制定相关政策和流程,确保国外患者的权益得到充分保护。
总之,国外医疗事故的处理需要医疗机构和相关部门共同努力,以确保患者的权益和安全。
医疗机构应及时采取紧急救治措施,展开调查并公布结果,提供必要的赔偿和支持,推进质量管理和安全培训,遵守法律和国际规范。
国外处理医患纠纷的方式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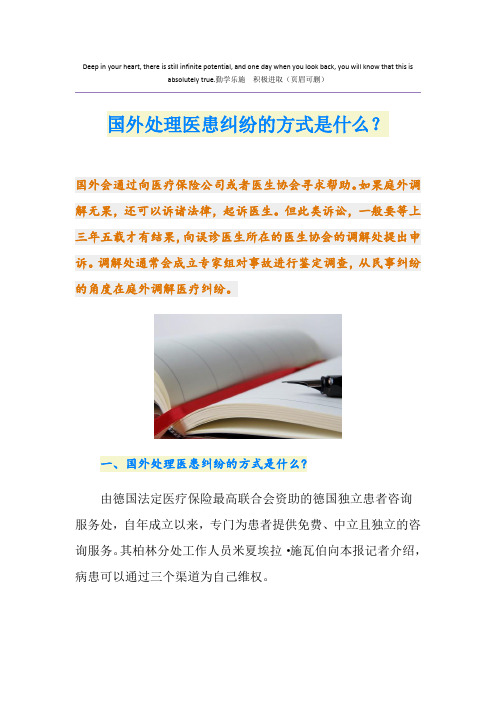
Deep in your heart, there is still infinite potential, and one day when you look back, you will know that this isabsolutely true.勤学乐施积极进取(页眉可删)国外处理医患纠纷的方式是什么?国外会通过向医疗保险公司或者医生协会寻求帮助。
如果庭外调解无果,还可以诉诸法律,起诉医生。
但此类诉讼,一般要等上三年五载才有结果,向误诊医生所在的医生协会的调解处提出申诉。
调解处通常会成立专家组对事故进行鉴定调查,从民事纠纷的角度在庭外调解医疗纠纷。
一、国外处理医患纠纷的方式是什么?由德国法定医疗保险最高联合会资助的德国独立患者咨询服务处,自年成立以来,专门为患者提供免费、中立且独立的咨询服务。
其柏林分处工作人员米夏埃拉·施瓦伯向本报记者介绍,病患可以通过三个渠道为自己维权。
第一是向自己的医疗保险公司寻求帮助。
“所有的医疗保险公司,都有针对医疗事故提供咨询的服务处。
病患怀疑自己被误诊后,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医保公司寻求帮助。
”第二是向误诊医生所在的医生协会的调解处提出申诉。
调解处通常会成立专家组对事故进行鉴定调查,从民事纠纷的角度在庭外调解医疗纠纷。
“通常一个申诉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有结果。
”第三,如果庭外调解无果,还可以诉诸法律,起诉医生。
但此类诉讼,一般要等上三年五载才有结果,比如今年8月18日在波恩结束的一起诉讼中,女病人去世已经4年,才最终裁定其死亡是医生误诊导致。
二、医疗纠纷处理程序A,基本程序1、医疗纠纷发生,患者及家属向医疗单位或其主管部门投诉,提出查处要求。
2、医疗单位或其主管部门接到投诉后应立即指派专人妥善保管原始资料,封存有关医疗物品,严禁涂改、伪造、隐匿、销毁。
如病人死亡应主动提出尸体解剖。
3、组织医疗行政管理部门展开调查,并形成调查报告,必要时报告上级卫生行政部门。
新西兰的医疗事故和意外伤害的赔偿

南半球上看东西新西兰的医疗事故和意外伤害的赔偿其实这个问题我过去就写过。
今天早上一个国内的朋友问我,说是她先生看到一则消息,说是新西兰的医疗事故,造成一个婴儿的脑瘫。
然后她问,如果是医疗事故,那么谁来赔偿,是个人吗?现在来说一说新西兰的医疗事故赔偿问题。
早在1974年,新西兰就推出了意外事故补偿法,该法实行无过失责任原则,即只要有伤害,有因果关系,受害人就可以得到赔偿。
新西兰的医疗意外事故的赔偿涵盖了所有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人身伤害,当然也包括医疗事故。
也就是说,新西兰全民都加入到了这个医疗系统的保障体系。
这个补偿法经过1992年的修订,补充了医疗事故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将医疗意外事故专门放在一个审理单位,二是将医疗事故分成医疗不幸和医疗失当,采用不同的赔偿方式。
另外一个保障体系是意外伤害保障体系,简称ACC,这部分的赔偿不是从医疗保障体系支出,而是政府支出。
不过新西兰所有的公司都必须缴纳ACC的费用,每年一次,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在新西兰,不会发生因为医疗事故造成医院或者个人倾家荡产的事情。
而意外伤害无论是否有责任,都会得到国家的赔偿,甚至不限于新西兰人,连海外的旅游者到新西兰来旅游发生了意外,都会得到赔偿。
我们家两个同学都深得到过这样的好处,一个是拐哥哥,9岁的时候出车祸,费用也是ACC承担,另外一个是黄老爸,做花园的时候腰扭到了,也是ACC付款,得到免费治疗。
下面,让我们一起看看新西兰意外伤害赔偿局的详细情况吧。
这是从他们的网站上看来的。
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新西兰的意外伤害赔偿是多么到位,甚至连因为意外伤害导致不能工作了,没有工资收入了,都可以得到赔偿。
ACC (意外伤害赔偿局)的职能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预防意外伤害的发生,同时帮助那些已经意外受伤的人士尽快恢复工作和日常生活。
在纽西兰的任何人都可以申请ACC的帮助——无论伤者年龄大小、在职或退休、是学生还是领取福利的人士。
多数情况下,也与受伤的原因和场所无关——在家里、在工作场所、在路途或运动中发生的大多数意外伤害,我们都能提供赔偿。
世界各国医疗事故处理法律制度概述

医疗事故
追究医方法律责任
英国(England) 医
疗
被告负有某职责
过
失
被告违反此职责
构
成 要Leabharlann 使原告受到损害件损害后果
因果关系
美国 (USA)
医
含 义
一个理智、谦和、谨慎的医生在 相同情况下不会做的事或者应该 做的但没有做到的事。
疗
过
失
分 类
治疗和处理的不良后果 诊断不当或治疗不当产生的后果
预防和护理不完善的后果
引言
医疗事故纠纷呈逐年递增趋势,已成 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是世界 各国政府、法学界和医学界都需要面 对的问题,也是一大难题。
世界各国医疗事 故纠纷数量惊人
世界各国医疗过失 的赔偿额惊人增长
就诊病 人总数
医疗 事故 伤害 人数
医疗 事故 死亡 人数
车祸 死亡 人数
4000 万
130万 10万
不同点: 中国大陆有行政调解无仲裁 国外有仲裁无行政调解
医疗事故法律责任的性质
美国 医疗事故性质认定经历了三个阶段 对患者个人的默示合同责任 医疗者承担对公众的责任 对受害者承担侵权责任
美国
医疗损害案件证明要素
存在侵权人对受害人一方的义务 侵权行为人违反了此种义务 对原告的伤害非常可能是由于侵 权人违反义务而引起的
医疗过失责任保险制度是欧美各国 破解医疗风险的主要途径
日本:医师会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对 已经参保的会员的医疗过失负赔偿责任
美国:医疗过失保险公司和医生相互 保险基金
各国医疗事故处理法律制度共同点
The medical treatment trouble in all countries processing law system orders together
外国处理医患纠纷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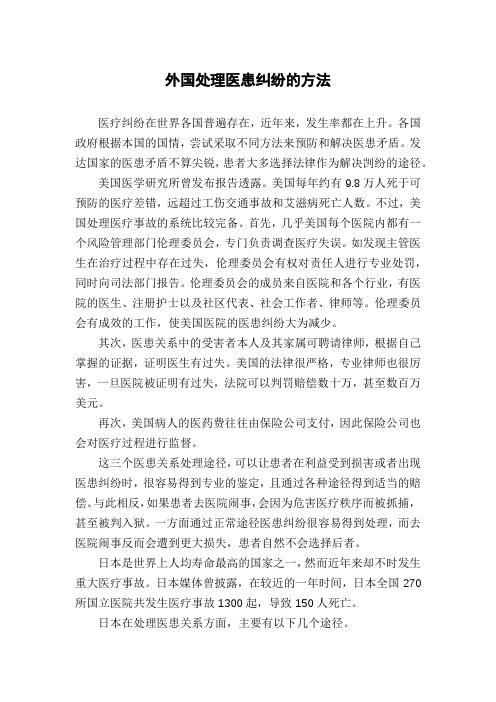
外国处理医患纠纷的方法医疗纠纷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近年来,发生率都在上升。
各国政府根据本国的国情,尝试采取不同方法来预防和解决医患矛盾。
发达国家的医患矛盾不算尖锐,患者大多选择法律作为解决剀纷的途径。
美国医学研究所曾发布报告透露。
美国每年约有9.8万人死于可预防的医疗差错,远超过工伤交通事故和艾滋病死亡人数。
不过,美国处理医疗事故的系统比较完备。
首先,几乎美国每个医院内都有一个风险管理部门伦理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医疗失误。
如发现主管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存在过失,伦理委员会有权对责任人进行专业处罚,同时向司法部门报告。
伦理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医院和各个行业,有医院的医生、注册护士以及社区代表、社会工作者、律师等。
伦理委员会有成效的工作,使美国医院的医患纠纷大为减少。
其次,医患关系中的受害者本人及其家属可聘请律师,根据自己掌握的证据,证明医生有过失。
美国的法律很严格,专业律师也很厉害,一旦医院被证明有过失,法院可以判罚赔偿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美元。
再次,美国病人的医药费往往由保险公司支付,因此保险公司也会对医疗过程进行监督。
这三个医患关系处理途径,可以让患者在利益受到损害或者出现医患纠纷时,很容易得到专业的鉴定,且通过各种途径得到适当的赔偿。
与此相反,如果患者去医院闹事,会因为危害医疗秩序而被抓捕,甚至被判入狱。
一方面通过正常途径医患纠纷很容易得到处理,而去医院闹事反而会遭到更大损失,患者自然不会选择后者。
日本是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近年来却不时发生重大医疗事故。
日本媒体曾披露,在较近的一年时间,日本全国270所国立医院共发生医疗事故1300起,导致150人死亡。
日本在处理医患关系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
第一是建立医患信任关系。
为了增加病人对医生的信任,日本1995年成立了医疗评估机构,对医院进行监督和评估,合格者发给合格证书,并在网上公布结果。
第二是从失败中汲取教训。
建立医疗事故数据库,成立由医生、律师、民间组织代表参加的医疗事故信息研究会,研究如何预防事故、查明事故原因以及应对策略。
跨国医疗法律问题案例(3篇)

第1篇一、案例背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医疗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
然而,在跨国医疗过程中,由于法律制度、文化差异等因素,常常会出现各种法律问题。
本文将以一起美国患者在中国的医院治疗纠纷为例,探讨跨国医疗法律问题。
二、案例简介2019年,美国公民约翰(化名)因工作原因来到中国。
不久后,约翰突然感到身体不适,经检查被诊断为急性阑尾炎。
为了尽快治疗,约翰选择了一家知名的中国医院进行手术。
在手术过程中,由于医院操作失误,约翰的阑尾被切除不全,导致病情恶化。
术后,约翰要求医院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然而,由于约翰和中国医院在法律制度、医疗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双方就赔偿问题产生了严重的纠纷。
三、法律问题分析1. 医疗标准差异美国和中国在医疗标准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在美国,医院和医生在手术过程中必须遵循严格的医疗操作规范,而在中国,医疗操作规范相对宽松。
因此,约翰在中国医院接受手术时,由于医疗标准的不同,导致手术失误。
2. 法律适用问题约翰和中国医院在法律适用上存在争议。
约翰认为,根据美国法律,医院和医生应承担过错责任,而中国法律则规定了医疗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
由于法律适用不同,双方对赔偿责任的认定存在分歧。
3. 证据收集问题在跨国医疗纠纷中,证据收集是一个重要问题。
约翰在治疗过程中产生的病历、医疗费用等相关证据,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难以在中国法院得到有效认定。
4. 管辖权问题约翰和中国医院在管辖权问题上存在争议。
约翰认为,根据美国法律,美国法院有权管辖此案;而中国医院则认为,根据中国法律,中国法院有权管辖此案。
四、案例分析1. 医疗标准差异导致的纠纷由于约翰在中国医院接受手术时,由于医疗标准的不同,导致手术失误。
因此,约翰有权要求医院承担赔偿责任。
然而,在具体赔偿金额上,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同,双方存在争议。
2. 法律适用问题根据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跨国医疗纠纷的法律适用应遵循“最密切联系原则”。
在本案中,由于约翰与中国医院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且约翰在中国医院接受治疗,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国法律。
外国处理医患纠纷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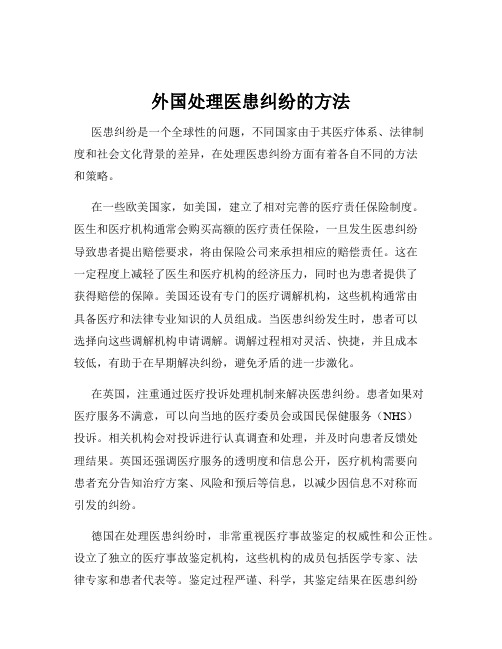
外国处理医患纠纷的方法医患纠纷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不同国家由于其医疗体系、法律制度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在处理医患纠纷方面有着各自不同的方法和策略。
在一些欧美国家,如美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医生和医疗机构通常会购买高额的医疗责任保险,一旦发生医患纠纷导致患者提出赔偿要求,将由保险公司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医生和医疗机构的经济压力,同时也为患者提供了获得赔偿的保障。
美国还设有专门的医疗调解机构,这些机构通常由具备医疗和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
当医患纠纷发生时,患者可以选择向这些调解机构申请调解。
调解过程相对灵活、快捷,并且成本较低,有助于在早期解决纠纷,避免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在英国,注重通过医疗投诉处理机制来解决医患纠纷。
患者如果对医疗服务不满意,可以向当地的医疗委员会或国民保健服务(NHS)投诉。
相关机构会对投诉进行认真调查和处理,并及时向患者反馈处理结果。
英国还强调医疗服务的透明度和信息公开,医疗机构需要向患者充分告知治疗方案、风险和预后等信息,以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纠纷。
德国在处理医患纠纷时,非常重视医疗事故鉴定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设立了独立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这些机构的成员包括医学专家、法律专家和患者代表等。
鉴定过程严谨、科学,其鉴定结果在医患纠纷的处理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德国也鼓励通过协商和调解来解决医患纠纷,并且在必要时可以通过法律诉讼来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
日本在应对医患纠纷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综合性的措施。
一方面,加强医疗机构的内部管理,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减少医疗差错的发生。
另一方面,建立了患者权益保护组织,为患者提供咨询和支持。
在法律层面,日本对于医疗事故的赔偿标准有明确的规定,这有助于在处理医患纠纷时做到有法可依。
澳大利亚则注重医患之间的沟通和教育。
通过开展医患沟通培训,提高医生与患者的沟通能力,增进相互理解。
同时,加强对公众的医疗知识普及,让患者对医疗服务有更合理的预期,从而降低因期望过高而产生的纠纷。
国外医闹的法律规定(3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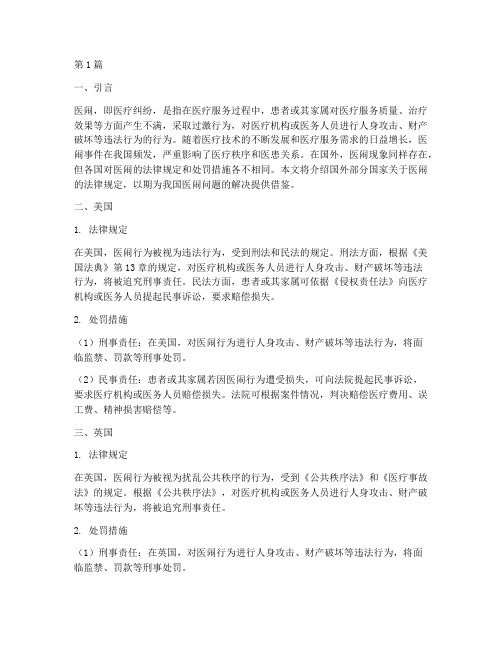
第1篇一、引言医闹,即医疗纠纷,是指在医疗服务过程中,患者或其家属对医疗服务质量、治疗效果等方面产生不满,采取过激行为,对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进行人身攻击、财产破坏等违法行为的行为。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医疗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医闹事件在我国频发,严重影响了医疗秩序和医患关系。
在国外,医闹现象同样存在,但各国对医闹的法律规定和处罚措施各不相同。
本文将介绍国外部分国家关于医闹的法律规定,以期为我国医闹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
二、美国1. 法律规定在美国,医闹行为被视为违法行为,受到刑法和民法的规定。
刑法方面,根据《美国法典》第13章的规定,对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进行人身攻击、财产破坏等违法行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民法方面,患者或其家属可依据《侵权责任法》向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损失。
2. 处罚措施(1)刑事责任:在美国,对医闹行为进行人身攻击、财产破坏等违法行为,将面临监禁、罚款等刑事处罚。
(2)民事责任:患者或其家属若因医闹行为遭受损失,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赔偿损失。
法院可根据案件情况,判决赔偿医疗费用、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等。
三、英国1. 法律规定在英国,医闹行为被视为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受到《公共秩序法》和《医疗事故法》的规定。
根据《公共秩序法》,对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进行人身攻击、财产破坏等违法行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2. 处罚措施(1)刑事责任:在英国,对医闹行为进行人身攻击、财产破坏等违法行为,将面临监禁、罚款等刑事处罚。
(2)民事责任:患者或其家属若因医闹行为遭受损失,可依据《医疗事故法》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赔偿损失。
法院可根据案件情况,判决赔偿医疗费用、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等。
四、加拿大1. 法律规定在加拿大,医闹行为被视为违法行为,受到刑法和民法的规定。
刑法方面,根据《加拿大刑法典》第266条的规定,对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进行人身攻击、财产破坏等违法行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国外医疗事故争议处置法律制度专家讲座

国外医疗事故争议处置法律制度专家讲座
第26页
六、护理事故和投诉防范
1.加强安全意识教育和安全防范办法 2.严格执行查对、统计、交接班制度 3.合理安排护士班组 4.加强责任心教育,提升服务质量
国外医疗事故争议处置法律制度专家讲座
第27页
第四节 日本医疗纠纷处理制度
一、当前医疗纠纷特点
据1971年日本医师会关于处理医疗事故调查 汇报记载,当初全国46个都道府县医师会中 已设置处理医疗纠纷机构有43个,现在己全 部建立。
科护士长要针对事故严重性拿出初步处理意见,病 区护士长需提出处理意见,并马上汇报护理部。
护理部依据事故轻重程度与类型按章妥善处理,处
理结果需及时通知病员家眷,后果严重者还需通知
警方立案。
国外医疗事故争议处置法律制度专家讲座
第25页
2.病员投诉处理
医院管理部门只要收到病员投诉,马上由护理 部负责各病区护理助理向病区护士长和科护士 长了解情况。
国外医疗事故争议处置法律制度专家讲座
第33页
提出控告举证责任则在病员一方,他或她责 任是用证据证实医生确实是粗心大意,伤害、 损失,或事故可能是由医生造成或归因于医 生。
过失不但必须给予证实,而且其与医生粗心 联络须加以证实。
国外医疗事故争议处置法律制度专家讲座
第34页
国外医疗事故争议处置法律制度专家讲座
第16页
二、危险控制系统 三、意外事故汇报 四、事故汇报方式 六、病历调查
国外医疗事故争议处置法律制度专家讲座
第17页
第三节 新加坡医院护理事故处理与 防范制度
一、护理事故及病员投诉定义 护理事故,是指护理失误并对病员或医护人
员造成伤害或潜在伤害意外事件。 病员投诉,是指病员因不满意医护人员服务
各国如何处理医疗纠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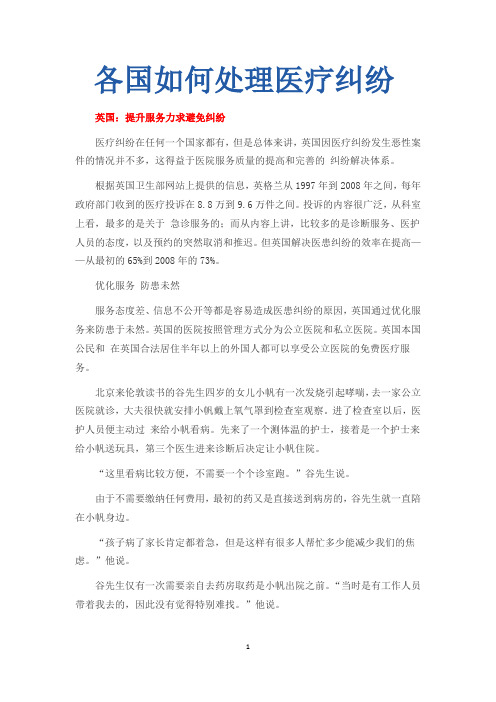
各国如何处理医疗纠纷英国:提升服务力求避免纠纷医疗纠纷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但是总体来讲,英国因医疗纠纷发生恶性案件的情况并不多,这得益于医院服务质量的提高和完善的纠纷解决体系。
根据英国卫生部网站上提供的信息,英格兰从1997年到2008年之间,每年政府部门收到的医疗投诉在8.8万到9.6万件之间。
投诉的内容很广泛,从科室上看,最多的是关于急诊服务的;而从内容上讲,比较多的是诊断服务、医护人员的态度,以及预约的突然取消和推迟。
但英国解决医患纠纷的效率在提高——从最初的65%到2008年的73%。
优化服务防患未然服务态度差、信息不公开等都是容易造成医患纠纷的原因,英国通过优化服务来防患于未然。
英国的医院按照管理方式分为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
英国本国公民和在英国合法居住半年以上的外国人都可以享受公立医院的免费医疗服务。
北京来伦敦读书的谷先生四岁的女儿小帆有一次发烧引起哮喘,去一家公立医院就诊,大夫很快就安排小帆戴上氧气罩到检查室观察。
进了检查室以后,医护人员便主动过来给小帆看病。
先来了一个测体温的护士,接着是一个护士来给小帆送玩具,第三个医生进来诊断后决定让小帆住院。
“这里看病比较方便,不需要一个个诊室跑。
”谷先生说。
由于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最初的药又是直接送到病房的,谷先生就一直陪在小帆身边。
“孩子病了家长肯定都着急,但是这样有很多人帮忙多少能减少我们的焦虑。
”他说。
谷先生仅有一次需要亲自去药房取药是小帆出院之前。
“当时是有工作人员带着我去的,因此没有觉得特别难找。
”他说。
英国很多公立医院设施都比较旧,但是服务还是不错的。
由于医生比较忙,医院里面专门有社工和病人沟通。
但是由于去公立医院看病的人多,患者需要预约,而预约过的病人需要等待短则一周长则数月的一段时间才能看上病,很多人选择去私立医院看病。
在英国,私立医院的很多服务(美容相关的除外)也是被医疗保险所覆盖的,因此虽然需要花钱,也不至于太贵。
为了招揽生意,私立医院的服务比公立医院更好。
国际医疗事故应急预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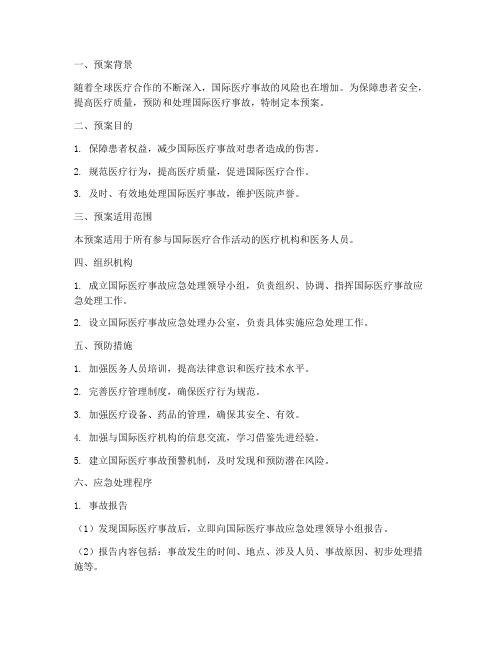
一、预案背景随着全球医疗合作的不断深入,国际医疗事故的风险也在增加。
为保障患者安全,提高医疗质量,预防和处理国际医疗事故,特制定本预案。
二、预案目的1. 保障患者权益,减少国际医疗事故对患者造成的伤害。
2. 规范医疗行为,提高医疗质量,促进国际医疗合作。
3. 及时、有效地处理国际医疗事故,维护医院声誉。
三、预案适用范围本预案适用于所有参与国际医疗合作活动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
四、组织机构1. 成立国际医疗事故应急处理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指挥国际医疗事故应急处理工作。
2. 设立国际医疗事故应急处理办公室,负责具体实施应急处理工作。
五、预防措施1. 加强医务人员培训,提高法律意识和医疗技术水平。
2. 完善医疗管理制度,确保医疗行为规范。
3. 加强医疗设备、药品的管理,确保其安全、有效。
4. 加强与国际医疗机构的信息交流,学习借鉴先进经验。
5. 建立国际医疗事故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和预防潜在风险。
六、应急处理程序1. 事故报告(1)发现国际医疗事故后,立即向国际医疗事故应急处理领导小组报告。
(2)报告内容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涉及人员、事故原因、初步处理措施等。
2. 事故调查(1)国际医疗事故应急处理领导小组组织调查组,对事故进行全面调查。
(2)调查内容包括:事故原因、涉及人员、医疗行为是否符合规范等。
3. 事故处理(1)根据调查结果,对事故责任人和医疗机构进行处理。
(2)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包括医疗费用、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等。
(3)对医疗机构进行整改,提高医疗质量。
4. 事故总结(1)对事故进行总结,分析事故原因,制定整改措施。
(2)对事故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对医疗机构进行考核。
七、应急保障措施1. 人力资源保障:加强应急处理队伍的建设,提高应急处理能力。
2. 财务保障:设立专项基金,用于事故赔偿和整改。
3. 物资保障:储备必要的医疗设备和药品,确保应急处理工作顺利进行。
八、预案实施与监督1.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国际医疗事故应急预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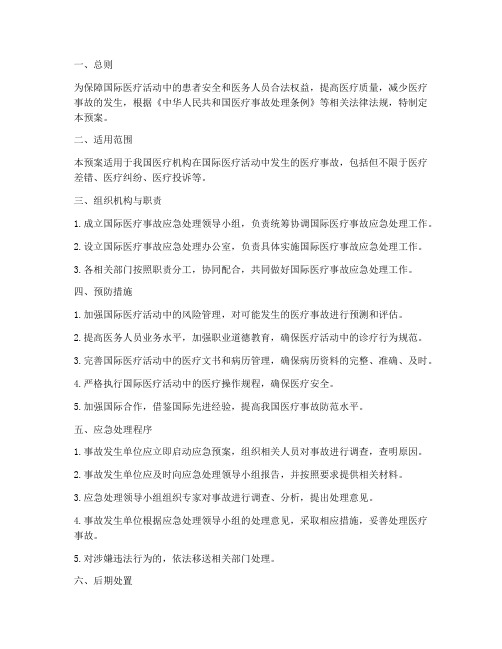
一、总则为保障国际医疗活动中的患者安全和医务人员合法权益,提高医疗质量,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特制定本预案。
二、适用范围本预案适用于我国医疗机构在国际医疗活动中发生的医疗事故,包括但不限于医疗差错、医疗纠纷、医疗投诉等。
三、组织机构与职责1.成立国际医疗事故应急处理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国际医疗事故应急处理工作。
2.设立国际医疗事故应急处理办公室,负责具体实施国际医疗事故应急处理工作。
3.各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协同配合,共同做好国际医疗事故应急处理工作。
四、预防措施1.加强国际医疗活动中的风险管理,对可能发生的医疗事故进行预测和评估。
2.提高医务人员业务水平,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确保医疗活动中的诊疗行为规范。
3.完善国际医疗活动中的医疗文书和病历管理,确保病历资料的完整、准确、及时。
4.严格执行国际医疗活动中的医疗操作规程,确保医疗安全。
5.加强国际合作,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提高我国医疗事故防范水平。
五、应急处理程序1.事故发生单位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相关人员对事故进行调查,查明原因。
2.事故发生单位应及时向应急处理领导小组报告,并按照要求提供相关材料。
3.应急处理领导小组组织专家对事故进行调查、分析,提出处理意见。
4.事故发生单位根据应急处理领导小组的处理意见,采取相应措施,妥善处理医疗事故。
5.对涉嫌违法行为的,依法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六、后期处置1.事故发生单位应总结经验教训,完善相关制度,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2.对涉及医疗事故的医务人员,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理。
3.对事故发生单位进行责任追究,确保医疗安全。
七、保障措施1.加强应急处理队伍建设,提高应急处理能力。
2.完善应急物资储备,确保应急处理工作顺利进行。
3.加强应急处理培训,提高医务人员应对医疗事故的能力。
4.加强与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及医疗机构的信息交流与合作,共同提高医疗事故防范水平。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四、美国医疗纠纷立法和第三方调解机制对我们的启示
一我国医疗纠纷处理法律架构急待健全:一般认为,中美两国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服务保障体系差异很大,加之一些概念定义不清,即使是学者和专业人员也常常陷于"盲人摸象"的争论。实际上中美两国在医疗纠纷防范与处理上的共同点很多,美国医学界和社会各界从19世纪中期就遭遇、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应对两次医疗纠纷高峰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从实际情况看,近年来我国卫生系统相继遇到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签字事件"、医疗过失归责原则等突出卫生信访问题和争论,都与医疗纠纷相关法律不完善有关。目前,正在广泛征求意见的我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就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英美法系侵权法的立法模式,并将成为今后我国处理医疗纠纷的支架性法律,应当引起卫生系统的高度重视,力争使医疗纠纷防范与处理在立法层面有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此外,美国对于医疗损害赔偿封顶的认识过程、不同州采取不同方法导致的不同结果,为我们出台医疗损害赔偿封顶政策提供了实例。目前我国某些地区出现的"医闹"现象,几乎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一些地区在医疗纠纷中"中彩"心态的翻版。
一、美国医疗纠纷与医患关系现状及特点
根据美国仲裁协会副主席P.Jean Baker女士和美国医学会的三位专家介绍,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由于美国的医疗卫生行业逐渐商业化,投资与回收的需要使医生演变为"商人",医患关系也渐渐成为一种商业关系,患者对医疗过失的容忍度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律师行业也已商业化,需要通过代理诉讼而赚钱,因而鼓励诉讼。同时,虽然美国人可以通过四种不同途径获得医疗保险,但仍有近15%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他们只有在病重时才会到医院急诊室就诊,这易直接或间接引发医疗纠纷。媒体报道患者因医疗诉讼获得天价赔偿,使人感到医疗纠纷投诉如同买彩票,都有可能"中彩"。上述因素,导致了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医疗纠纷及诉讼数量激增。美国的医生和医疗机构都购买了医疗责任保险,开业医生和私立医院的医疗过失责任与赔偿主要由当事医生承担,而在公立医院,医生作为雇员,其医疗过失责任与赔偿主要由医院承担。法院判决的医疗过失赔偿均由保险公司支付。据统计,1991年到2003年平均每件医疗责任案件的赔偿额增加了1倍。目前,美国每年医疗责任赔偿数额达到了45亿美元。由于医疗纠纷诉讼及赔偿额激增,导致医疗责任险保费大幅上升。据AMA提供的数据,全国50个州中有17个州医疗责任险保费大幅上升,25个州增幅明显,只有个州基本稳定。例如,在2000年至2008年期间,新泽西州保费增加了151%,康涅狄格州增加了170%,费城则增加了286%。由于医疗责任诉讼及医疗责任险保费大幅上升,医生不得不采取更多的防御性医疗措施。据统计,防御性医疗措施使整个美国医疗卫生系统增加了700亿~1260亿美元的支出。而美国妇产科医生组织200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职业风险或畏惧医疗责任投诉,12个产科医生中就有一个医生不再接生,超过2/3的产科或妇科医生由于难以负担医疗责任险费用而变更执业内容。美国专科医师协会调查数据显示,由于全国医疗责任险保费大幅上升,75%的神经外科医生不再给儿童做手术,55%的整形外科医生避免做高风险手术,其中39%的医生不再做脊柱外科手术。医疗纠纷大量增加及其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影响已经成为美国医疗卫生服务系统面临的重大挑战。
由此推论,原告原始的身体状态,如癌症,即便是没有任何医疗过失存在的情况下,其生存的机会也小于50%的话,那么,多数此类情况的患者不能状告一个存在过失行为的医护为其丧失生命负全责。这些案例提供了一个法律上的规则:如果原告本身疾病根本不能康复,他们就不能把未康复的可能归咎于被告的损害上。相反,必须假定唯一的医疗损害是导致了患者生命丧失的原因。如果医疗损害被定义为独特的全部的话,原告有义务提供被告的玩忽职守是近似完全损害的原因--导致了患者的死亡。换句话说,原告有义务证明死者原始存在的身体状态,假定医护得当的话,其有非常良好的生存机会。在这一理论下,一个原患有癌症的患者,如果其不拥有大于50%而仅有49%的不充分的生存可能,他本身不能康复任何损害,即便他是医疗失误误诊的牺牲者,那医疗过失也只是加速其死亡而剥夺了他生存的机会。只有癌症患者存在远大于50%康复的机会者可以诉讼,同时只要有51%的生存可能的就可以诉讼,此时患者通过治疗可以康复痊愈。第一例受害诉讼者因本身未有任何的康复而未获赔偿;第二例受害诉讼者因其后完全康复而获满意的赔偿。
二"第三方援助"有可能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纠纷处理的有效途径:在与美方交流中,美国法律工作者和组织对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美国律师协会曾立项考察我国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Carole Houk国际冲突管理咨询公司将我国文化中的"和气"作为该公司调解工作的核心理念。虽然美国同行"改变文化"的提法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我们在加强法制建设和改善我国社会法制环境的过程中,也应当吸取美国因过度诉讼而导致社会管理成本剧增、一些律师成为纠纷的始作俑者的教训,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挖掘有助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因素。近年来,我国很多省区市、地市和县市相继成立了一些医疗纠纷专业调解机构,人民调解、仲裁机构和社会组织也积极加入到医疗纠纷调解实践中来,人民法院十分重视诉前调解在解决医疗纠纷诉讼案中的重要作用,一个多元化的医疗纠纷大调解格局正在形成。然而,尽管我国现有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方式与美国的ADR方式"形似",但在"神似"方面仍有很大距离。美国各种ADR方式原则明确、程序完备,虽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但不能脱离基本的归责原则,也必须履行严格的程序。目前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援助机制需要解决的问题:在鼓励多元调解机制建设的同时,适时加以统筹,提出指导性意见,在宏观层面上搞好制度设计,在操作层面上规定各类调解组织的工作规则和程序。
二、美国医疗纠纷立法和诉讼特点
据AMA介绍,美国医疗纠纷相关法律主要来自于三方面:一是联邦的法律、法规和以往判例;二是各州的法律、法规和以往判例;三是联邦和各州法院的规定。医疗机构、医生、健康管理组织和保险公司大都由各州管辖,因此医疗纠纷诉讼都在各州法院进行。虽然英美法系以判例为主要审判依据,成文法较少且不够具体,但美国联邦层面涉及医疗纠纷的主要法规仍比较完备。其主要有五个:一是联邦侵权索赔法(Federal Tort C1aims Act);二是志愿者保护法(Volunteer Protection Act);三是紧急医疗处置与分娩法(Emergency Medical Treatment andActive Labor Act);四是儿童预防接种伤害法(Na-tional Childhood Vaccine Injury Act);五是国家执业人员资料库(National Practitioner Databank)。上述立法架构从不同的角度明确了医疗过失责任和常见医疗纠纷判定原则,国家执业人员资料库则完整记录从业医师被诉讼和医疗责任险赔付情况。目前,美国完善医疗纠纷立法的焦点问题之一是对医疗损害赔偿是否应予封顶,包括是只对非经济性损害主要是精神损失赔偿封顶,还是对全部损偿额和整个医疗费用支出情况好于没有封顶条款的州。美国是一个具有浓厚"诉讼文化"背景的国家。然而,尽管我们接触的不同机构和人员因各自立场不同而对医疗纠纷解决方案所持观点存在差别,但对目前美国以诉讼作为医疗纠纷法定解决途径的现状均持批评态度,甚至提出应"改变文化"。其主要原因:一是诉讼费用昂贵,赔偿标的低于10万美元的医疗纠纷案没有律师愿意代理;二是诉讼旷日持久,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等候时间达5年,审判过程达2年;三是胜诉的关键因素之一专家证人(expert witnesses)只为当事人服务,而非客观公正地依据科学事实说话,美国没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程序,是由当事双方聘请的医学专家就专业问题质证,无力聘请高级医学专家的一方往往败诉;四是胜诉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律师抗辩能力、表演才能及其对陪审团成员态度的影响,而陪审团成员大都没有医学专业背景,容易被同情心左右。据统计,只有13%的不当治疗被提起诉讼,而其中只有1/3能够胜诉,大部分不当治疗的患者并未得到补偿,医疗纠纷也并未得到解决。
导致患者丧失被救治机会的医疗过失行为[英]/Med Malpractice Rep, 1999,12(11):566-569
依照民事侵权法律的有关规定,被告因近似玩忽职守而造成原告的损害,应对损害的结果承担责任。为此,原告须提供证实被告因玩忽职守足以造成其损害、或为其损害的一个原因的证据,同时原告并因此损害寻求了相应的康复治疗。在医疗过失的案例中,这方面的证据要求一个专家证言:证明被告的行为从合理的医学确证上,是造成原告损害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