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老师的名家散文
歌颂教师的名篇散文作品

歌颂教师的名篇散文作品有很多,以下列举一些:
1. 朱自清的《背影》:这篇散文通过描写作者的父亲在家境困顿的情况下,仍亲自送他到浦口火车站的情形,表现了父亲对儿子的深情。
作者在文中表达了对父亲的理解和思念,以及对自己当时未能尽孝的愧疚和悔恨。
2. 冰心的《寄小读者》:这篇散文是冰心写给小朋友的信,其中表达了她对孩子们的关爱和教导,同时也表达了她对教师这个职业的敬爱和感慨。
3. 丰子恺的《给我的孩子们》:这篇散文是丰子恺写给孩子们的信,其中表达了他对孩子们的期望和希望,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追求。
4. 贾平凹的《我的老师》:这篇散文是贾平凹写给他的老师的一封信,其中表达了他对老师的感激和敬意,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教育和成长的感慨和思考。
这些名篇散文作品都表达了对教师职业的敬爱和赞美,同时也展现了作者的文学造诣和思想境界。
老师的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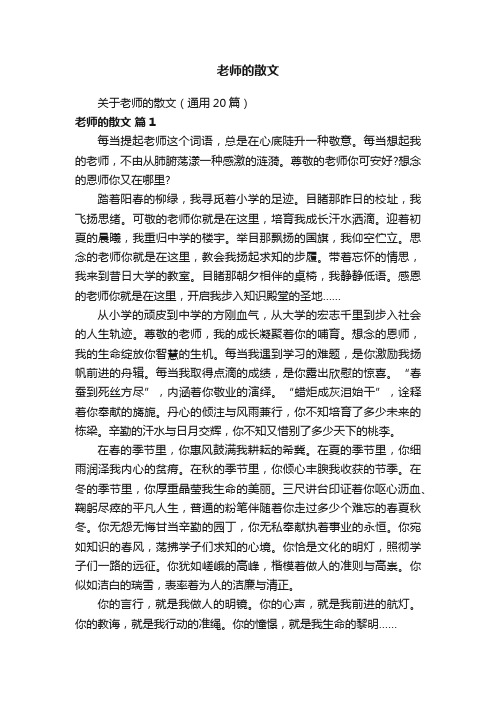
老师的散文关于老师的散文(通用20篇)老师的散文篇1每当提起老师这个词语,总是在心底陡升一种敬意。
每当想起我的老师,不由从肺腑荡漾一种感激的涟漪。
尊敬的老师你可安好?想念的恩师你又在哪里?踏着阳春的柳绿,我寻觅着小学的足迹。
目睹那昨日的校址,我飞扬思绪。
可敬的老师你就是在这里,培育我成长汗水洒滴。
迎着初夏的晨曦,我重归中学的楼宇。
举目那飘扬的国旗,我仰空伫立。
思念的老师你就是在这里,教会我扬起求知的步履。
带着忘怀的情思,我来到昔日大学的教室。
目睹那朝夕相伴的桌椅,我静静低语。
感恩的老师你就是在这里,开启我步入知识殿堂的圣地……从小学的顽皮到中学的方刚血气,从大学的宏志千里到步入社会的人生轨迹。
尊敬的老师,我的成长凝聚着你的哺育。
想念的恩师,我的生命绽放你智慧的生机。
每当我遇到学习的难题,是你激励我扬帆前进的舟辑。
每当我取得点滴的成绩,是你露出欣慰的惊喜。
“春蚕到死丝方尽”,内涵着你敬业的演绎。
“蜡炬成灰泪始干”,诠释着你奉献的旖旎。
丹心的倾注与风雨兼行,你不知培育了多少未来的栋梁。
辛勤的汗水与日月交辉,你不知又惜别了多少天下的桃李。
在春的季节里,你惠风鼓满我耕耘的希冀。
在夏的季节里,你细雨润泽我内心的贫瘠。
在秋的季节里,你倾心丰腴我收获的节季。
在冬的季节里,你厚重晶莹我生命的美丽。
三尺讲台印证着你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平凡人生,普通的粉笔伴随着你走过多少个难忘的春夏秋冬。
你无怨无悔甘当辛勤的园丁,你无私奉献执着事业的永恒。
你宛如知识的春风,荡拂学子们求知的心境。
你恰是文化的明灯,照彻学子们一路的远征。
你犹如嵯峨的高峰,楷模着做人的准则与高崇。
你似如洁白的瑞雪,表率着为人的洁廉与清正。
你的言行,就是我做人的明镜。
你的心声,就是我前进的航灯。
你的教诲,就是我行动的准绳。
你的憧憬,就是我生命的黎明……从春秋孔子的论语中,我读懂教育兴国你的地位尤为神圣。
从毛泽东给徐特立的书信中,我凝思着教书育人你的职业倍受尊敬。
关于师生的课文

关于师生的课文以下是关于师生的课文:1. 《师恩难忘》:这是一篇深情而又朴实的记叙文,作者是著名作家刘绍棠。
文章讲述了作者对小学一年级时一位田野老师的回忆,表达了对老师的感激和怀念之情。
2. 《陶校长的演讲》:这是一篇演讲稿,作者是教育家陶行知。
他在演讲中谈到了如何建筑“人格长城”,以及如何成为“真人”,表达了他对教育的独特见解和对学生的期望。
3. 《古诗两首》(《寻隐者不遇》和《所见》):这两首诗都是描述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
《寻隐者不遇》是贾岛的诗,描述了他与隐者的问答,体现了隐者高洁的性格以及诗人对他的仰慕。
《所见》是袁枚的诗,描述了一个牧童骑黄牛、高声唱歌的场景,展现了儿童的纯真和老师的欣赏。
4. 《题秋江独钓图》:这是清代诗人王士禛的一首题画诗,描述了一个渔翁在秋江边独钓的画面,体现了诗人对渔翁的同情和理解,也可以引申为师生之间的情感共鸣。
5. 《师说(节选)》:这是韩愈的一篇著名文章,阐述了教师的职责、作用以及师生之间的关系。
文章强调了教师的重要性,提出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
6. 《藤野先生》:这是鲁迅的一篇散文,回忆了他在日本留学期间遇到的藤野先生。
文章表达了作者对藤野先生的感激和怀念之情,展现了师生之间的深厚情谊。
7. 《我的老师》:这是魏巍的一篇散文,通过描述他小学时的一位老师蔡芸芝先生,表达了对老师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8. 《再塑生命的人》:这是海伦·凯勒的一篇自传体散文,讲述了她的老师安妮·莎莉文如何帮助她重获生命的故事。
9.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这是梁实秋的一篇散文,回忆了他的一位国文老师徐锦澄先生。
文章表达了作者对老师的感激和怀念之情,同时也展现了老师的独特教学方法和人格魅力。
10. 《我的老师孙涵泊》:这是贾平凹的一篇散文,通过描述他的老师孙涵泊的言行举止,表达了对老师的敬仰和感激之情。
11. 《我的第一个老师》:这是胡适的一篇散文,回忆了他的第一个老师韦先生。
关于老师的名家散文

关于老师的名家散文老师和我们相处就像朋友一样,但他对我们的学习可是一点也不马虎。
别人都说严师出高徒,我认为他,不应该用“严”来概述,而应该用“真”。
下面是有关于老师的名家散文,欢迎参阅。
关于老师的名家散文:那些年的老师那一天我漫步在夕阳下,偶遇到了我曾经的老师,她的头发有了白雪的痕迹,她冲着我笑笑,眼角多了皱纹,那一刻我突然往事涌上心头……每当上她的课,我都会特别认真,因为我们认真,她就告诉我们家长,让家长表扬我们,那时候我最爱听到父母的表扬了。
那一天她依然认真讲课,唯一不同的就是总盯着我看,她看一次我,我就把头稍稍低下,装模作样的看书,再偷偷瞄一眼看看老师还有没有看我,我想她可能要叫我回答问题了,心里七上八下的,再仔细想想上课回答问题不是她的风范,只有在小组比赛时才让同学回答问题的,想到这里,心便踏实一点,我便抬起头了。
老师怎么又看我,我不是很认真吗,我有做笔记啊,心里又忐忑不安了,低着头心里默想,应该是我太认真过头吧,对,一定就是这样,我再次抬起头来。
咦,老师怎么老爱看我呢,我脸上有东西吗,俩手不知不觉在脸上来回搜索,难道是我的圆珠笔画到脸上吗,问了同桌,同桌很坚定的语气对我说没有,这心里真的有崩溃的感觉,我明明什么都没有,老师就爱盯着我看,表面听课,心里在狠狠的骂老师神经病……终于,下课铃响了,她下课之后指着我说,你过来办公室一下,这下我心里的积怨差一点脱口而出了。
在走去办公室的路上,我心里没有停止对老师的唾骂,看了我一节课,让我别扭了一节课不说,还让我去办公室,什么人嘛,真是有够气人的。
我很不情愿的说一声报告,刚刚进办公室,她就对我说,你一节课的脸色都不太好,难受了那么久也不说说,说完手摸着我的额头,便皱了眉,便说;"发烧了,你回家一定要人爸妈带你去看医生的,我这里有一些退烧药,你先服下"。
听到这里心里的积怨瞬间消失了,服药的时候虽然很苦,但心里却充满了甜。
这就是那年我读初中的时候教我语文的林老师。
教师节经典散文(精选20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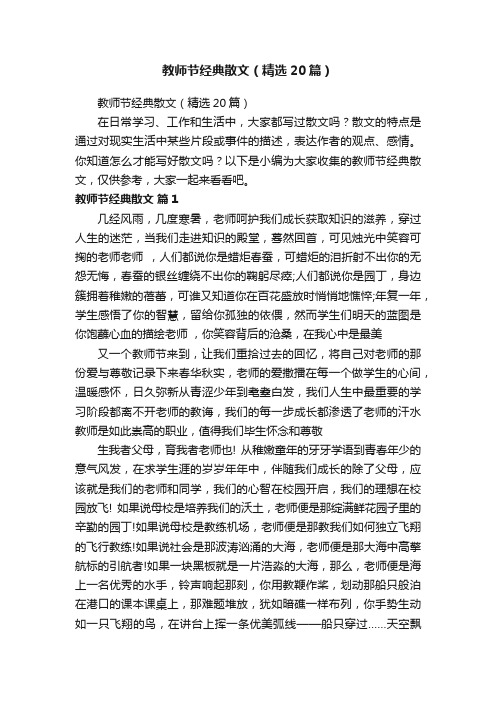
教师节经典散文(精选20篇)教师节经典散文(精选20篇)在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大家都写过散文吗?散文的特点是通过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片段或事件的描述,表达作者的观点、感情。
你知道怎么才能写好散文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师节经典散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教师节经典散文篇1几经风雨,几度寒暑,老师呵护我们成长获取知识的滋养,穿过人生的迷茫,当我们走进知识的殿堂,蓦然回首,可见烛光中笑容可掬的老师老师,人们都说你是蜡炬春蚕,可蜡炬的泪折射不出你的无怨无悔,春蚕的银丝缠绕不出你的鞠躬尽瘁;人们都说你是园丁,身边簇拥着稚嫩的蓓蕾,可谁又知道你在百花盛放时悄悄地憔悴;年复一年,学生感悟了你的智慧,留给你孤独的依偎,然而学生们明天的蓝图是你饱蘸心血的描绘老师,你笑容背后的沧桑,在我心中是最美又一个教师节来到,让我们重拾过去的回忆,将自己对老师的那份爱与尊敬记录下来春华秋实,老师的爱撒播在每一个做学生的心间,温暖感怀,日久弥新从青涩少年到耄耋白发,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学习阶段都离不开老师的教诲,我们的每一步成长都渗透了老师的汗水教师是如此崇高的职业,值得我们毕生怀念和尊敬生我者父母,育我者老师也! 从稚嫩童年的牙牙学语到青春年少的意气风发,在求学生涯的岁岁年年中,伴随我们成长的除了父母,应该就是我们的老师和同学,我们的心智在校园开启,我们的理想在校园放飞! 如果说母校是培养我们的沃土,老师便是那绽满鲜花园子里的辛勤的园丁!如果说母校是教练机场,老师便是那教我们如何独立飞翔的飞行教练!如果说社会是那波涛汹涌的大海,老师便是那大海中高擎航标的引航者!如果一块黑板就是一片浩淼的大海,那么,老师便是海上一名优秀的水手,铃声响起那刻,你用教鞭作桨,划动那船只般泊在港口的课本课桌上,那难题堆放,犹如暗礁一样布列,你手势生动如一只飞翔的鸟,在讲台上挥一条优美弧线——船只穿过……天空飘不来一片云,犹如你亮堂堂的心,一派高远我们是老师的一个动态的作品,漫漫人生路,我们感受着老师语重心长的叮咛,我们看见了年迈老师那脸上挂着的会心的微笑!我们知道,老师的得意在于他的满园桃李已经芳芬! 我们对人生成长路上的每一位老师,深怀敬意地在这里道一声:老师辛苦了!岁月苍老了年轻的容颜,奉献铸就了民族的希望,无数教育工作者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了一个又一个春秋但是,当人们在享受着时代发展带来的日新月异的美好生活的时候,当第24个属于教师的节日即将来临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学教师,我和许许多多的教师一样,感受到了这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节日的冷清,没有欢欣,没有赞歌,我们依然在晨曦微露到华灯初上的忙碌中履行着人民教师的神圣职责即便外面的世界如何喧嚣着它的繁华,我想,我和身处校园的千千万万个教师一样,并不会在意这一份节日的冷清9月10日,虽是金秋,是收获的时节,但如果一名教师用自己毕生的心血与汗水换来了教坛的累累硕果,回首往事时感慨万千,热泪盈眶,甚至痛哭流涕,那么他定会将这一辈子的每一天都视为自己的节日,因为他没有虚度光阴,他的每一天都充盈着崇高的奉献当然,如果一名教师碌碌无为地虚度了自己的教学生涯,我想,他也必将远离这个节日,因为他会在内心产生一种深深的愧疚我不会苛求学生在这个节日送上鲜花与祝福,为人师非一时,授其知识,教其立人,对于学生而言,老师的教育就是一辈子的事在学生走出校门步入社会的时候,运用聪明才智取得了事业的成功,或者用老师曾经授予他的文化知识与为人之道战胜了生活的困难,他自然会在内心铭记与怀念自己的老师,甚至用心用文颂扬着浩浩师恩,这一份深情远远胜过作为学生的他们在节日里给老师送上的程式化的祝福即使张张贺卡里饱含着浓浓情谊,那也仅仅说明一名学生的知情知义,并不代表教育成就的内涵与外延学生在离开老师之后走上正道取得成功,那才是对老师最宝贵的回报反之,班上的学生毕业后内心苍白头脑无物,走上自我沉沦的歧路,至少,作为他的老师,我们会有莫名的失败感,那么,他曾经送上的那一张精美的贺卡那一束娇艳的鲜花又有多大的意义呢?至于社会将教师如何冷落,我想这并不重要因为,选择了教师,就选择了清贫;选择了教师,就选择了寂寞今日社会呈现出的种种世态,实质上与学校的教育不无关系因此,让人与人之间更懂尊重与关爱,让社会日渐趋于和谐,这是时代赋予我们教师更加神圣的使命既为教师,何需在意节日的冷清!在寂寞中奉献,这本身就是对被教育者一种良好的引导与感化!为人师才知道老师的辛苦和辛酸,也才明白老师对学生的深情关怀与殷切期望无论遇到什么老师都默默承受,一如既往的站在三尺讲台上,真是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物悲!老师在讲台上、生活中都为我们的成长付出了一年的辛劳教师节经典散文篇2自从汶川大地震之后,全国人民都在为一位平凡而普通的老师流泪。
余秋雨散文《老师》

余秋雨散文《老师》我是一九五七年刚刚十一岁时到上海读初中的。
那所中学的校园典雅富丽,甚至还有欧洲式的大理石喷水池,这在我这么一个农村来的孩子眼中,就像是海市蜃楼。
但当时学校里的第一景观是飘飘拂拂的大字报,我们看不懂,只在纸帘间窜来窜去,捉迷藏。
记得第一节课是音乐课,老师是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他从画满五线谱的黑板前走到钢琴旁,弹了几个乐句便张口领唱,他的声音,那么漂亮又那么沉闷,我们已知道,他刚刚划为右派,正在检讨。
他上课时,我们教室的窗口,经常有人头晃动,音乐老师一看,便只唱不讲,唱的声音则更加奇怪。
三个星期之后,我们接到通知,音乐老师不来了,音乐课的时间,到操场的角落里练大合唱。
大合唱的歌词曰:“一九五七年呀,真是个胜利年……”没过多久,其它课程也很难正常进行了。
大理石喷水池已停止喷水,旁边搭起了一个养猪棚,养猪棚边上又砌了炼钢炉。
高年级学生养猪、炼钢,我们的任务则是到街上拾捡破铜烂铁,作为炼钢的原料。
当时全民都在炼钢。
国家领导发出号召,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但对英国和的情况却不了解,只相信了一种说法,即赶上赶不上的标志是看钢产量,于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中国大地无处不在炼钢。
里弄铁门和各家各户阳台上的铁架,已全部砸下来充作原料,我们这些孩子再到哪里去找铁呢?谁拾到一枚锈迹斑斑的铁钉就如获至宝了。
捡拾了几个月所得寥寥,而喷水池旁炼出来的钢更是一团丑陋不堪的黑疙瘩。
于是学校根据上级指示转移方向,让学生进附近的工厂劳动,说是要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不能老坐在课堂里读书。
老师们出发了,到一家家工厂去商量,希望他们能接纳我们劳动。
这么多十岁刚出头的孩子涌到车间去,既无劳动能力又极不安全,工厂理所当然是不欢迎的。
老师们只能红着脸一次次恳求,一直恳求得那些厂长突然想起了自己早年的老师而感动起来,才迟迟疑疑地同意我们去劳动几个月。
毕竟不行,工厂很快下了逐客令,老师只能再去找另一家。
就这么一家家工厂轮着转,初中三年,几乎把学校周围所有的工厂都劳动遍了。
冰心散文推荐:我的老师

冰心散文推荐:我的老师冰心散文推荐:我的老师冰心,中国诗人,现代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散文家。
小编整理了冰心散文,欢迎欣赏与借鉴。
我从小住在偏僻的乡村里,没有机会进小学,所以只在家塾里读书,国文读得很多,历史地理也还将就得过去,吟诗作文都学会了,且还能写一两千字的文章。
只是算术很落后,翻来覆去,只做到加减乘除,因为塾师自己的算学程度,也只到此为止。
十二岁到了北平,我居然考上了一个中学,因为考试的时候,校长只出一个“学而后知不足”的论说题目。
这题目是我在家里做过的,当时下笔千言,一挥而就。
校长先生大为惊奇赞赏,一下子便让我和中学一年级学生同班上课。
上课两星期以后,别的功课我都能应付自如,作文还升了一班,只是算术把我难坏了。
中学的算术是从代数做起的,我的算学底子太坏,脚跟站不牢,昏头眩脑,踏着云雾似的上课,T女士便在这云雾之中,飘进了我的生命中来。
她是我们的代数和历史教员,那时也不过二十多岁罢。
“螓首蛾眉,齿如编贝”这八个字,就恰恰的可以形容她。
她是北方人,皮肤很白嫩,身体很窈窕,又很容易红脸,难为情或是生气,就立刻连耳带颈都红了起来。
我最怕是她红脸的时候。
同学中敬爱她的,当然不止我一人,因为她是我们的女教师中间最美丽、最和平、最善诱导的一位。
她的态度,严肃而又和蔼,讲述时简单而又清晰。
她善用譬喻,我们每每因着譬喻的有趣,而连带的牢记了原理。
第一个月考,我的历史得九十九分,而代数却只得了五十二分,不及格!当我下课自己躲在屋角流泪的时候,觉得有只温暖的手,抚着我的肩膀,抬头却见T女士挟着课本,站在我的身旁。
我赶紧擦了眼泪,站了起来。
她温和地问我道:“你为什么哭?难道是我的分打错了?”我说:“不是的,我是气我自己的数学底子太差。
你出的十道题目,我只明白一半。
”她就款款温柔地坐下,仔细问我的过去。
知道了我的家塾教育以后,她就恳切地对我说:“这不能怪你。
你中间跳过了一大段!我看你还聪明,补习一定不难;以后你每天晚一点回家,我替你补习算术罢。
赞美教师的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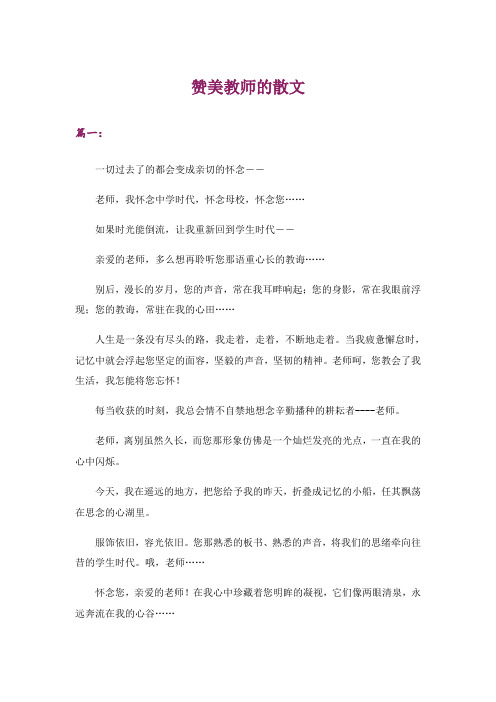
赞美教师的散文篇一:一切过去了的都会变成亲切的怀念――老师,我怀念中学时代,怀念母校,怀念您……如果时光能倒流,让我重新回到学生时代――亲爱的老师,多么想再聆听您那语重心长的教诲……别后,漫长的岁月,您的声音,常在我耳畔响起;您的身影,常在我眼前浮现;您的教诲,常驻在我的心田……人生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我走着,走着,不断地走着。
当我疲惫懈怠时,记忆中就会浮起您坚定的面容,坚毅的声音,坚韧的精神。
老师呵,您教会了我生活,我怎能将您忘怀!每当收获的时刻,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念辛勤播种的耕耘者----老师。
老师,离别虽然久长,而您那形象仿佛是一个灿烂发亮的光点,一直在我的心中闪烁。
今天,我在遥远的地方,把您给予我的昨天,折叠成记忆的小船,任其飘荡在思念的心湖里。
服饰依旧,容光依旧。
您那熟悉的板书、熟悉的声音,将我们的思绪牵向往昔的学生时代。
哦,老师……怀念您,亲爱的老师!在我心中珍藏着您明眸的凝视,它们像两眼清泉,永远奔流在我的心谷……饮其流者怀其源,学其成时念吾师。
篇二:您用火一般的情感温暖着每一个同学的心房,无数颗心被您牵引激荡,连您的背影也凝聚着滚烫的目光……您不是演员,却吸引着我们饥渴的目光;您不是歌唱家,却让知识的清泉叮咚作响,唱出迷人的歌曲;您不是雕塑家,却塑造着一批批青年人的灵魂……老师啊,我怎能把您遗忘!刻在木板上的名字未必不朽,刻在石头上的名字也未必流芳百世;老师,您的名字刻在我们心灵上,这才真正永存。
您的思想,您的话语,充溢着诗意,蕴含着哲理,又显得那么神奇――呵,在我的脑海里,它们曾激起过多少美妙的涟漪!您推崇真诚和廉洁,以此视作为人处世的准则。
您是我们莘莘学子心目中的楷模。
我崇拜伟人、名人,可是我更急切地把我的敬意和赞美献给一位普通的人――我的老师您。
您对我们严格要求,并以自己的行动为榜样。
您的规劝、要求,甚至命令,一经提出,便要我们一定做到,然而又总使我们心悦诚服,自觉行动。
这就是您留在我心中的高大形象。
赞美老师的散文(11篇)

赞美老师的散文(优秀11篇)赞美老师的散文篇一老师——这个美丽而有神圣的称呼,伴随着我们学习、成长。
每一位老师都会为我们含辛茹苦的付出,但却不知为什么,英语老师却是令我最与众不同的。
也许是因为永久不变的性格。
在每次的课堂,郑老师总与往常一样孜孜不倦地为我们讲课,那清爽的声音,倾吐着流利而又风趣的英语。
这不仅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位认真听讲的同学,还在我的内心深处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痕迹。
在那一次的课堂上,我更加感受到了她那持久温驯的性情。
这堂英语课并没有与往日那么严肃,已失去了那课堂纪律的严谨,许多男同学在这节课上任意妄为地捣乱,砸蛋放肆地不听老师的劝导,反而还与她对抗,此时,教室里充满了他们的吵闹声,这样不但对他们的学习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而且还间接影响到了其他同学的学习。
郑老师见到这一情况,她并没有火冒三丈,也没有若无其事,知识耐心地劝阻他们,并进行教育。
但是,这些嚣张的同学还是没有得到领悟,继续他们那“打乱活动”。
正在这时的老师只好那他们没办法。
“叮咚叮咚……”下课铃声已响彻校园,尽管他们再胡闹,但郑老师也并没有放弃。
于是,她决定利用空余的时间为这些同学补课,将落下的知识重新传授于他们。
啊!多么负责的老师,多么特别的老师,她拥有美丽的容貌,但更美的而是她那颗特别的心灵。
赞美老师的散文篇二袖卷清风,翘首处、一泓秋水。
敛帘底、千秋华夏,满园桃李。
玉露生辉繁景瑞,金风送爽丹枫魅。
纵怀时、秋韵润衷扉,陶心醉。
为师者,期心慰;闻学子,关情寄。
叹含辛茹苦,育人无悔。
三尺讲台攒岁月,一枝粉笔耕天地。
甘丝竭、织锦绣人间,芳流世。
——《满江红·秋望》九月金秋,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就要到了,中国有着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每年这个季节,人们总是将最感激的语言、最秀丽的文字献给教师。
教师,用人类最崇高的感情——爱,播种春天,播种理想,播种力量……用语言播种,用彩笔耕耘,用汗水浇灌,用心血滋润,这就是我们敬爱的教师们崇高的劳动。
大作家写给老师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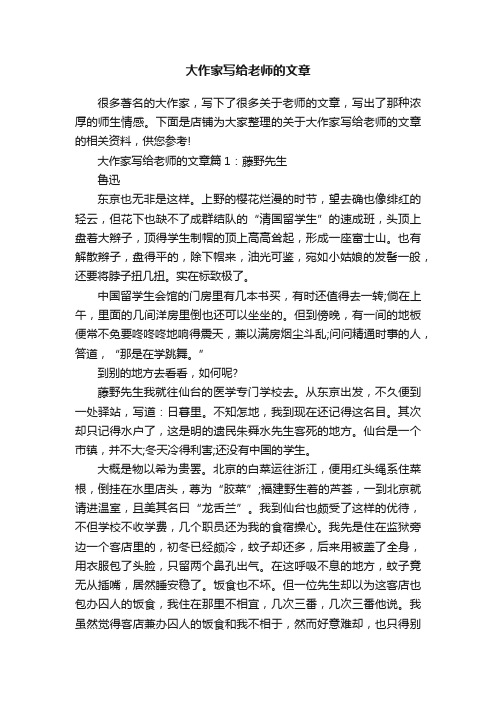
大作家写给老师的文章很多著名的大作家,写下了很多关于老师的文章,写出了那种浓厚的师生情感。
下面是店铺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大作家写给老师的文章的相关资料,供您参考!大作家写给老师的文章篇1:藤野先生鲁迅东京也无非是这样。
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
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
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
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藤野先生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
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
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
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
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
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里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
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
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
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
饭食也不坏。
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他说。
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于,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
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
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
最初是骨学。
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
名人写给老师的信范文名人写老师的文章有些

名人写给老师的信范文名人写老师的文章有些名人写老师的文章有,贾平凹《我的老师》、鲁迅《藤野先生》、冰心《我的老师》、魏巍《我的老师》、肖复兴《那片绿绿的爬墙虎》、《再塑生命》海伦凯勒。
贾平凹《我的老师》原文部分我的老师孙涵泊,是朋友的孩子,今年三岁半。
他不漂亮,也少言语,平时不准父母杀鸡剖鱼,很有些良善,但对家里的所有来客却不瞅不睬,表情木然,显得傲慢。
开始我见他,只逗着他取乐,到后来便不敢放肆,并认了他作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赏析:是贾先生经典的写人散文,字数不多,更无华丽句式,这种写法,是我一直崇尚的,对老师表示谦虚和尊敬。
鲁迅《藤野先生》原文部分“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
《藤野先生》赏析:这鲁迅的一篇回忆散文,记叙了作者从东京到仙台学医的几个生活片断。
其中有东京“清国留学生”的生活情况,由东京到仙台的旅途回忆,有在仙台的食住情况,也有受到日本具有狭隘民族观念的学生的排斥,还有一次看电影受到的刺激,而重点却是记叙藤野先生的可贵品质。
藤野先生本名藤野严九郎,是作者的老师。
本文内容丰实,笔意纵横,形散神凝,错落有致,发人深省,一条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线索贯穿了全文,使每个看来似乎是平淡无奇的生活片断闪耀着夺目的光华,从而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
冰心《我的老师》原文部分我永远忘不掉的,是T女士,我的老师。
我从小住在偏僻的乡村里,没有机会进小学,所以只在家塾里读书,国文读得很多,历史地理也还将就得过,吟诗作文都学会了,且还能写一两千字的文章。
只是算术很落后,翻来覆去,只做到加减乘除,因为塾师自己的算学程度,也只到此为止。
冰心《我的老师》赏析:冰心写的我的老师,通过老师对我的补习,父母的感恩和我对老师的感恩,来表达老师无私,慈爱的性格特征,通过几个小事来写出来,每个小事写出老师的一种特征,很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感谢老师的名家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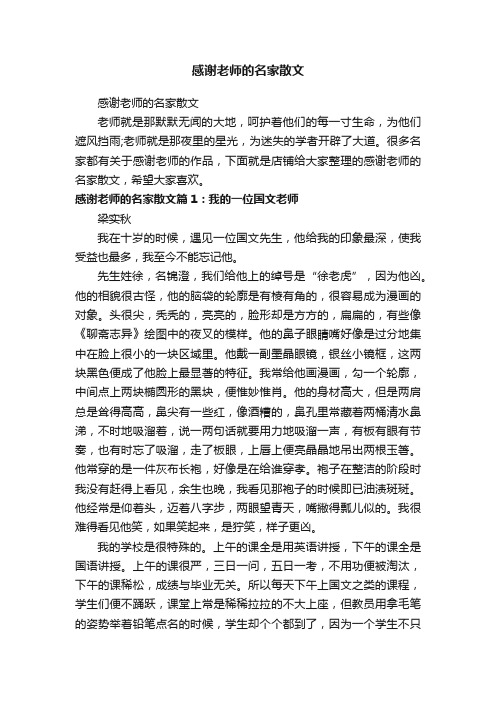
感谢老师的名家散文感谢老师的名家散文老师就是那默默无闻的大地,呵护着他们的每一寸生命,为他们遮风挡雨;老师就是那夜里的星光,为迷失的学者开辟了大道。
很多名家都有关于感谢老师的作品,下面就是店铺给大家整理的感谢老师的名家散文,希望大家喜欢。
感谢老师的名家散文篇1:我的一位国文老师梁实秋我在十岁的时候,遇见一位国文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最深,使我受益也最多,我至今不能忘记他。
先生姓徐,名锦澄,我们给他上的绰号是“徐老虎”,因为他凶。
他的相貌很古怪,他的脑袋的轮廓是有棱有角的,很容易成为漫画的对象。
头很尖,秃秃的,亮亮的,脸形却是方方的,扁扁的,有些像《聊斋志异》绘图中的夜叉的模样。
他的鼻子眼睛嘴好像是过分地集中在脸上很小的一块区域里。
他戴一副墨晶眼镜,银丝小镜框,这两块黑色便成了他脸上最显著的特征。
我常给他画漫画,勾一个轮廓,中间点上两块椭圆形的黑块,便惟妙惟肖。
他的身材高大,但是两肩总是耸得高高,鼻尖有一些红,像酒糟的,鼻孔里常藏着两桶清水鼻涕,不时地吸溜着,说一两句话就要用力地吸溜一声,有板有眼有节奏,也有时忘了吸溜,走了板眼,上唇上便亮晶晶地吊出两根玉箸。
他常穿的是一件灰布长袍,好像是在给谁穿孝。
袍子在整洁的阶段时我没有赶得上看见,余生也晚,我看见那袍子的时候即已油渍斑斑。
他经常是仰着头,迈着八字步,两眼望青天,嘴撇得瓢儿似的。
我很难得看见他笑,如果笑起来,是狞笑,样子更凶。
我的学校是很特殊的。
上午的课全是用英语讲授,下午的课全是国语讲授。
上午的课很严,三日一问,五日一考,不用功便被淘汰,下午的课稀松,成绩与毕业无关。
所以每天下午上国文之类的课程,学生们便不踊跃,课堂上常是稀稀拉拉的不大上座,但教员用拿毛笔的姿势举着铅笔点名的时候,学生却个个都到了,因为一个学生不只答一声到。
真到了的学生,一部分是从事午睡,微发鼾声,一部分看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玉梨魂》之类,一部分写“父母亲大人膝下”式的家书,一部分干脆瞪着大眼发呆,神游八表。
教师节感恩老师的名家散文精选三篇

导语:有人说,老师是辛苦的园丁,有人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有人说,老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在我看来,老师是一支蜡烛,点亮自己,照耀别人。
篇一:教师节感恩老师的名家散文人生旅程上,您丰富我的心灵,开发我的智力,为我点燃了希望的光芒。
谢谢您,老师!春雨,染绿了世界,而自己却无声地消失在泥土之中。
老师,您就是滋润我们心田的春雨,我们将永远感谢您。
老师,您是海洋,我是贝壳,是您给了我斑斓的色彩……我当怎样地感谢您!踏遍心田的每一角,踩透心灵的每一寸,满是对您的敬意。
有如从朔风凛冽的户外来到冬日雪夜的炉边;老师,您的关怀,如这炉炭的殷红,给我无限温暖。
我怎能不感谢您?对于您教诲的苦心,我无比感激,并将铭记于心!天涯海角有尽处,只有师恩无穷期。
感谢您,老师!您用心中全部的爱,染成了我青春的色彩;您用执著的信念,铸成了我性格的不屈……老师,我生命的火花里闪耀着一个您!鸟儿遇到风雨,躲进它的巢里;我心上有风雨袭来,总是躲在您的怀里--我的师长,您是我遮雨的伞,挡风的墙,我怎能不感谢您!没有您的慷慨奉献,哪有我收获的今天。
十二万分地感谢您,敬爱的老师。
您送我进入一个彩色的天地,您将我带入一个无限的世界……老师,我的心在喊着您,在向您敬礼。
把精魂给了我,把柔情给了我,把母亲般的一腔爱给了我……老师,您只知道给予而从不想收取,我怎能不向您表示由衷的敬意?您的眼神是无声的语言,对我充满期待;是燃烧的火焰,给我巨大的热力:它将久久地、久久地印在我的心里……假如我能搏击蓝天,那是您给了我腾飞的翅膀;假如我是击浪的勇士,那是您给了我弄潮的力量;假如我是不灭的火炬,那是您给了我青春的光亮!老师,在今天我们身上散发的智慧光芒里,依然闪烁着您当年点燃的火花!往日,您在我的心田播下了知识的种子,今天,才有我在科研中结出的硕果――老师,这是您的丰收!您谆谆的教诲,化作我脑中的智慧,胸中的热血,行为的规范……我感谢您,感谢您对我的精心培育。
「名家美文欣赏」苏叔阳:我的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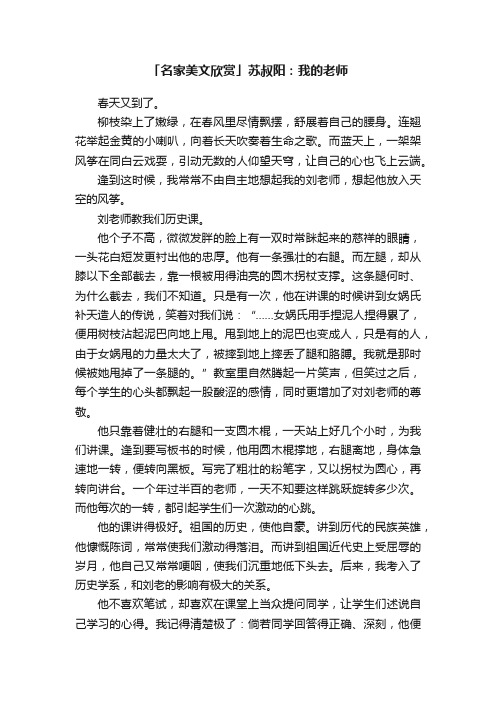
「名家美文欣赏」苏叔阳:我的老师春天又到了。
柳枝染上了嫩绿,在春风里尽情飘摆,舒展着自己的腰身。
连翘花举起金黄的小喇叭,向着长天吹奏着生命之歌。
而蓝天上,一架架风筝在同白云戏耍,引动无数的人仰望天穹,让自己的心也飞上云端。
逢到这时候,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刘老师,想起他放入天空的风筝。
刘老师教我们历史课。
他个子不高,微微发胖的脸上有一双时常眯起来的慈祥的眼睛,一头花白短发更衬出他的忠厚。
他有一条强壮的右腿。
而左腿,却从膝以下全部截去,靠一根被用得油亮的圆木拐杖支撑。
这条腿何时、为什么截去,我们不知道。
只是有一次,他在讲课的时候讲到女娲氏补天造人的传说,笑着对我们说:“……女娲氏用手捏泥人捏得累了,便用树枝沾起泥巴向地上甩。
甩到地上的泥巴也变成人,只是有的人,由于女娲甩的力量太大了,被摔到地上摔丢了腿和胳膊。
我就是那时候被她甩掉了一条腿的。
”教室里自然腾起一片笑声,但笑过之后,每个学生的心头都飘起一股酸涩的感情,同时更增加了对刘老师的尊敬。
他只靠着健壮的右腿和一支圆木棍,一天站上好几个小时,为我们讲课。
逢到要写板书的时候,他用圆木棍撑地,右腿离地,身体急速地一转,便转向黑板。
写完了粗壮的粉笔字,又以拐杖为圆心,再转向讲台。
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师,一天不知要这样跳跃旋转多少次。
而他每次的一转,都引起学生们一次激动的心跳。
他的课讲得极好。
祖国的历史,使他自豪。
讲到历代的民族英雄,他慷慨陈词,常常使我们激动得落泪。
而讲到祖国近代史上受屈辱的岁月,他自己又常常哽咽,使我们沉重地低下头去。
后来,我考入了历史学系,和刘老的影响有极大的关系。
他不喜欢笔试,却喜欢在课堂上当众提问同学,让学生们述说自己学习的心得。
我记得清楚极了:倘若同学回答得正确、深刻,他便静静地伫立在教案一侧,微仰着头,眯起眼睛,细细地听,仿佛在品味一首美妙的乐曲,然后,又好像从沉醉中醒来,长舒一口气,满意地在记分册上写下分数,亲切、大声地说:“好!五分!”倘若有的同学回答得不好,他就吃惊地瞪大眼睛,关切地瞧着同学,一边细声说:“别紧张,想想,想想,再好好想想。
散文窗张继东我的老师燕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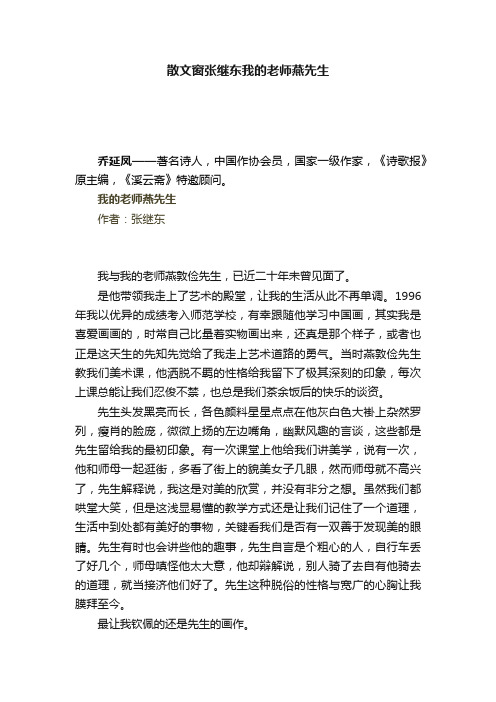
散文窗张继东我的老师燕先生乔延凤——著名诗人,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诗歌报》原主编,《溪云斋》特邀顾问。
我的老师燕先生作者:张继东我与我的老师燕敦俭先生,已近二十年未曾见面了。
是他带领我走上了艺术的殿堂,让我的生活从此不再单调。
1996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师范学校,有幸跟随他学习中国画,其实我是喜爱画画的,时常自己比量着实物画出来,还真是那个样子,或者也正是这天生的先知先觉给了我走上艺术道路的勇气。
当时燕敦俭先生教我们美术课,他洒脱不羁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每次上课总能让我们忍俊不禁,也总是我们茶余饭后的快乐的谈资。
先生头发黑亮而长,各色颜料星星点点在他灰白色大褂上杂然罗列,瘦肖的脸庞,微微上扬的左边嘴角,幽默风趣的言谈,这些都是先生留给我的最初印象。
有一次课堂上他给我们讲美学,说有一次,他和师母一起逛街,多看了街上的貌美女子几眼,然而师母就不高兴了,先生解释说,我这是对美的欣赏,并没有非分之想。
虽然我们都哄堂大笑,但是这浅显易懂的教学方式还是让我们记住了一个道理,生活中到处都有美好的事物,关键看我们是否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先生有时也会讲些他的趣事,先生自言是个粗心的人,自行车丢了好几个,师母嗔怪他太大意,他却辩解说,别人骑了去自有他骑去的道理,就当接济他们好了。
先生这种脱俗的性格与宽广的心胸让我膜拜至今。
最让我钦佩的还是先生的画作。
先生最擅长工笔,当时有幸见到他很多意境深邃的力作,花鸟鱼虫,情态各异,画面背景深邃静谧,给人一种精神的沉静和心灵的净化。
我时常去到先生的家里或者画廊里虔心学习,有时就我一个人,看先生忙着创作,单是墙上六尺的线描底稿就能让我看上半天,先生会给我讲些基本技法,他说写意画的“似与不似”、“巯可跑马密不透风”、这些现在看来最基本的东西其实是值得用一生参悟的,也是给我留下的毕生最为宝贵的财富。
先生看我好学,推荐我去购买《芥子园画谱》,说古人的技法都在这一本书里,也会给我们印些讲义,教导我们绘画和书法要兼修。
冰心赞美老师的散文诗【赞美老师的散文精选700字】

冰心赞美老师的散文诗【赞美老师的散文精选700字】老师的爱,是一艘游轮,他带你领悟这世间的美好。
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赞美老师的散文精选700字的内容,希望对你有用。
赞美老师的散文精选700字篇一:老师,你辛苦了心灵是谁一直在默默无闻地批改着堆积如山的作业啊?是谁一直在深夜准备着明天要上的课啊?是谁一直在给予我们知识,并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啊?是谁把雨露撒遍大地啊?是谁把幼苗辛勤哺育啊?这都是老师。
老师如醇酒,味浓而易醉;老师如花香,芬芳而淡雅;老师如秋天的雨,细腻又满怀诗意;老师如寒冬的梅花,高洁又傲然挺立。
老师,您就是美的耕耘者,美的播种者。
是您用美的阳光普照,用美的雨露滋润,我们的心田才绿草如茵,繁花似锦!老师,您对我们的付出与我们对您的回报是那样地截然不同!如果说老师像那堆砌万里长城的劳动者们,他们用汗水洗刷过的一块块砖建起了蜿蜒长城。
那老师正是如此,就像那建长城的人们一样,不辞辛苦,用您所拥有的知识一点点地给予我们……您为花的盛开,果的成熟忙碌着,默默地垂着叶的绿荫!您就象一根蜡烛,光虽然微弱,却照亮了每一个人;您也象一级级石梯,帮助我们一步步登上学习的顶峰。
啊,老师,您的精神,我永远也不会忘怀!您的爱,太阳一般温暖,春风一般和煦,清泉一般甘甜。
您的爱,比父爱更严峻,比母爱更细腻,比友爱更纯洁。
您的爱,天下最伟大,最高洁。
在那百花盛开的春天,我愿化作绚烂的阳光,为您增添几分光彩。
在那烈日炎炎的夏季,我愿化作一把遮阳伞,为您遮住那酷热的阳光。
老师的爱是无止境的,是无微不至的。
老师的爱是五颜六色的粉笔,为黑色的土地添上色彩;是甜润的雨水,滋养着大地;是温暖的太阳,使幼苗茁壮成长;是清爽的春风,吹拂着我们稚幼的心灵。
伟大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啊!赞美老师的散文精选700字篇二:我最喜爱的老师蜜蜂辛勤地把花粉传播给花朵,老师辛勤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在众多辛勤的老师中我最喜欢我现在的语文老师封老师。
你看那边身穿黄色衣服正在讲课的就是封老师,她像妈妈一样美丽,有一头又黑又亮的长头发像小瀑布似的披到肩上,浓浓的眉毛挂在眼睛上;不大不小的眼睛好像会说话,时刻在提醒我们,要好好学习,她的嘴巴笑起来很温暖。
写人的散文名家名篇

写人的散文名家名篇1. 《我的老师》“哎呀,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听讲啊!”这是我们的语文老师经常说的话。
记得有一天,上课铃响了,教室里还是闹哄哄的,老师走进来,看着我们,无奈地摇摇头说:“你们呀,怎么就不能安静会儿呢?”老师在讲台上认真地讲课,我们在下面听得津津有味,那一堂课真的让我学到了好多知识呢!我觉得我的老师就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2. 《我的妈妈》“宝贝,快来吃饭啦!”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来。
有一次,我生病了,妈妈焦急地守在我身边,一会儿给我量体温,一会儿给我喂水,还温柔地对我说:“宝贝,别怕,妈妈在这里呢。
”妈妈就是这样,时刻关心着我,她的爱就像温暖的阳光,让我感到无比幸福。
3. 《我的好朋友》“嘿,我们去玩吧!”这是我的好朋友经常对我说的话。
那次我们一起去公园,他兴奋地跑在前面,还不停地回头喊我:“快点呀,你怎么这么慢!”我们在公园里尽情地玩耍,笑声回荡在整个公园。
他就是我的开心果呀,有他在身边,每天都很快乐。
4. 《爷爷的故事》“孩子啊,爷爷给你讲个故事。
”爷爷总是这样开头。
记得一个晚上,我坐在爷爷身边,爷爷就给我讲起了他年轻时候的故事,他说:“那时候啊,可艰苦了,但我们都很努力地生活。
”我听得入了迷,爷爷的经历真的好丰富啊!爷爷的故事就像一本厚厚的书,让我百读不厌。
5. 《那个善良的陌生人》“小姑娘,你怎么了?”一个陌生的声音传来。
有一次我迷路了,急得快哭了,这时一个陌生人走过来,关切地问我情况,还耐心地给我指路,说:“别着急,慢慢走就能找到啦。
”这个陌生人的善良真的让我好感动,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
6. 《我的同桌》“这道题应该这样做。
”同桌认真地对我说。
有一回考试我有道题不会做,正发愁呢,同桌小声地给我讲解,他说:“你看呀,这里要这样算。
”同桌可真是我的学习好帮手啊,和他坐在一起真好。
7. 《我的邻居》“哟,孩子,又见面啦!”邻居阿姨总是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有次我忘带钥匙进不了家门,在门口着急,邻居阿姨看到了,就邀请我去她家等,还说:“别着急,在阿姨家玩会儿。
名家描写老师的散文 赞美老师的散文 赞美老师的名家散文(共2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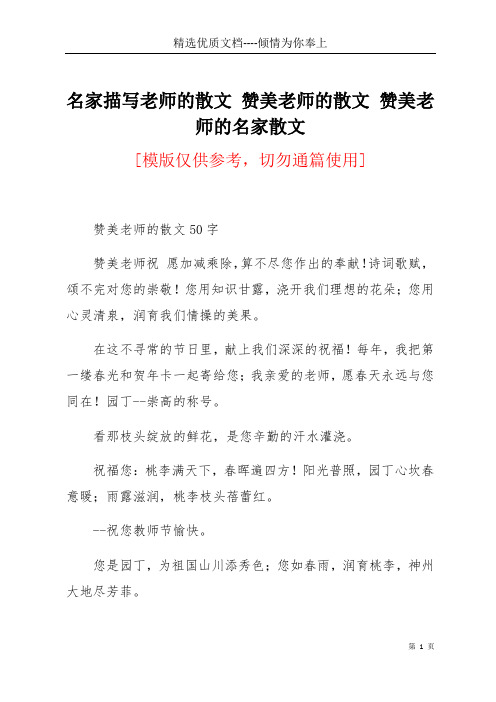
名家描写老师的散文赞美老师的散文赞美老师的名家散文[模版仅供参考,切勿通篇使用]赞美老师的散文50字赞美老师祝愿加减乘除,算不尽您作出的奉献!诗词歌赋,颂不完对您的崇敬!您用知识甘露,浇开我们理想的花朵;您用心灵清泉,润育我们情操的美果。
在这不寻常的节日里,献上我们深深的祝福!每年,我把第一缕春光和贺年卡一起寄给您;我亲爱的老师,愿春天永远与您同在!园丁--崇高的称号。
看那枝头绽放的鲜花,是您辛勤的汗水灌浇。
祝福您: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阳光普照,园丁心坎春意暖;雨露滋润,桃李枝头蓓蕾红。
--祝您教师节愉快。
您是园丁,为祖国山川添秀色;您如春雨,润育桃李,神州大地尽芳菲。
在这喜庆的节日里,让我献上一支心灵的鲜花,向您表达衷心的祝愿。
用满天彩霞谱写颂歌,用遍地鲜花编织诗篇,也表不尽我们对老师节日的祝贺!“桃李满天下”,是教师的荣耀。
--值此日丽风清、秋实累累的园丁佳节,敬祝老师康乐如意,青春永葆!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而您却是我最尊敬的老师。
在您的节日里,我要把一份崇高的敬意献给您。
敬爱的老师,您的谆谆教诲如春风,似瑞雨,永铭我心。
我虔诚地祝福您:康乐、如意!我们从幼苗长成大树,却永远是您的学生。
在您花甲之年,祝您生命之树常青。
您因材施教,善启心灵。
我们捧着优异的成绩,来祝贺您的胜利!老师,祝您教育的学生,人才济济,精英辈出。
老师,您是真诚的、善良的、美好的。
愿所有同学的心扉都向您敞开。
愿我这小溪的乐音,永远在您深邃的山谷中回响。
海水退潮的时候,把五彩的贝壳留在沙滩上。
我们毕业的时候,把诚挚的祝愿献给老师。
赞美教师的散文·老师,您好一日,在闹市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大学的系主任小心翼翼地推着破旧的自行车经过我的面前。
退休了的他身上穿的还是原来的老样子,是不合时宜的朴素,他也显得苍老多了。
我赶紧走上前问候了一声:“老师,您好!”老教授显然已经记不清我不是谁,但他与我握手道别时却非常诚恳地道了一声:“谢谢!”仿佛好久都没有人问候过他了。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老钱的灯孔庆东当着导师的面,自然是叫钱老师。
但背后,还是觉得叫“老钱”过瘾。
老钱在世上混了五十个年头了,还没有混到一块法定的私人居住空间。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
”可他还是一天到晚弥勒佛似的教导我们如何做学问。
我有时便不免暗发一点鲁智深式的腹诽:今日也要做学问,明日也要做学问,冷了弟兄们的心。
当我们十来个弟兄“保甲连坐”般拥挤在他那间斗大的宿舍里时,一片黑乎乎的身影在墙上漫涌着。
常常是这边正谈着天底下最高雅清玄的问题,那边突然杯翻壶仰,刹那间造就了几位诗(湿)人。
于是老钱笑得更加开心,青黄的灯光在他秃得未免过早的头顶上波动着。
我常常首先倡议解散,因为我知道人走茶凉之后,那支灯说不定要亮到寅时卯刻。
我常常从那支灯下经过。
二十一楼的西半边,冲南,二层中间的那个窗口。
我披星戴月从三教(指北京大学第三教学楼——引者注)回来,耳朵里落进一串老钱粗犷的笑——大概又接见什么文学青年吧。
我深更半夜晚上出门,来回总要绕到那窗下。
看一眼那灯,似乎心里就多了一份舒坦。
每当我冲着书缝打呵欠时,不禁就想到:老钱大概还在干着吧?我再忍会儿。
有一次送女朋友,我说:“从那边儿绕一下,看看老钱的灯。
”她勃然小怒:“又是老钱,老钱!老钱的灯有什么好看的?简直是变态!”我勃然大怒,顺手给了她一记红焖肉,酿成了一场大祸。
所以我有时觉得,老钱的灯恐怕不是什么好东西。
老钱的满头黑发,不就是被它弄没的么?只要它亮着,老钱就像着了魔似的翻呀,写呀。
写鲁迅,写周作人。
可是人家那哥俩儿有他这样的“贵府”,有他这样的青灯么?“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也许他很欣赏陆游的这联名句吧?一件事念叨三遍以上,就再也说不清了——我的经验。
所以还是盲目崇拜一点什么为好,一种主义,一个人,一盏灯……当我面对书本“读欲”不振时,当我独望窗外无所事事时,当我觉得白天之重和黑夜之轻都压得自己难以承受时,我就想:去看看老钱的灯吧,顺便吃个煎饼果子。
站在那窗下,仿佛能听见那灯嗡嗡地喘息着,好像一盘时间的磁带在转动。
有时真想喊一声:“嘿,老钱,悠着点儿!”灯嗡嗡地喘息着。
老钱是个普通人。
但他的灯,亮在我心上。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傅斯年凡认识蔡先生的,总知道蔡先生宽以容众;受教久的,更知道蔡先生的脾气,不严责人,并且不滥奖人,不像有一种人的脾气,称扬则上天,贬责则入地。
但少人知道,蔡先生有时也很严词责人。
我以受师训备僚属有25年之长久,颇见到蔡先生生气责人的事。
他人的事我不敢说,说和我有关的。
蔡先生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个同学,长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满人意的事,于是同学某某在西斋(寄宿舍之一)壁上贴了一张“讨伐”的告示;两天之内,满墙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件,把这个同学骂了个“不亦乐乎”。
其中也有我的一件,因为我也极讨厌此人,而我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深的语意,却是挖苦他。
为同学们赏识,在其上浓圈密点,批评狼藉。
这是一时学校中的大笑话。
过了几天,蔡先生在一大会中演说,最后说到此事,大意是说:诸位在墙壁上攻击××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
诸君对×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
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
这才是正当的办法。
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
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端。
这一篇话,在我心中生了一个大摆动。
我小时,有一位先生教我“正心”“诚意”①〔“正心”“诚意”〕出自《大学》。
“正心”,指端正心思;“诚意”,指意念真诚。
“不欺暗室〔不欺暗室〕指不在暗处伤人。
”,虽然《大学》念得滚熟,却与和尚念经一样,毫无知觉;受了此番教训,方才大彻大悟,从此做事,决不匿名,决不推自己责任。
大家听蔡先生这一段话之后印象如何我不得知,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从此减少,几至绝了迹。
蔡先生第二次游德国时,大约是在民国十三年吧,那时候我也是在柏林。
蔡先生到后,我们几个同学自告奋勇照料先生,凡在我的一份中,无事不办了一个稀糟。
我自己自然觉得非常惭愧,但蔡先生从无一毫责备。
有一次,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说是要从莱比锡来看蔡先生。
这个同学出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一面要钱,我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得了,所以与三四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他,以此意陈告先生。
先生沉吟一下说:“《论语》上有几句话,‘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①〔与其进也,……不保其往也。
〕语出《论语?述而第七》。
意思是,赞成他的进步,不赞成他的退步,何必做得太过分呢?人家洁身而来,就应该赞成他的自洁,不要老追究他过去的事。
与,肯定、赞成。
’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于是我又知道读《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北伐胜利之后,我们的兴致很高。
有一天在先生家中吃饭,有几个同学都喝醉了酒,蔡先生喝得更多,不记得如何说起,说到后来我便肆口乱说了。
我说:“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彝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
”蔡先生听到这里,不耐烦了,说:“这除非你做大将。
”此外如此类者尚多,或牵连他人,或言之太长,姑不提。
即此三事,已足证先生责人之态度是如何诚恳而严肃的,如何词近而旨远的。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梁实秋我在十岁的时候,遇见一位国文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最深,使我受益也最多,我至今不能忘记他。
先生姓徐,名锦澄,我们给他上的绰号是“徐老虎”,因为他凶。
他的相貌很古怪,他的脑袋的轮廓是有棱有角的,很容易成为漫画的对象。
头很尖,秃秃的,亮亮的,脸形却是方方的,扁扁的,有些像《聊斋志异》绘图中的夜叉的模样。
他的鼻子眼睛嘴好像是过分地集中在脸上很小的一块区域里。
他戴一副墨晶眼镜,银丝小镜框,这两块黑色便成了他脸上最显著的特征。
我常给他画漫画,勾一个轮廓,中间点上两块椭圆形的黑块,便惟妙惟肖。
他的身材高大,但是两肩总是耸得高高,鼻尖有一些红,像酒糟的,鼻孔里常藏着两桶清水鼻涕,不时地吸溜着,说一两句话就要用力地吸溜一声,有板有眼有节奏,也有时忘了吸溜,走了板眼,上唇上便亮晶晶地吊出两根玉箸。
他常穿的是一件灰布长袍,好像是在给谁穿孝。
袍子在整洁的阶段时我没有赶得上看见,余生也晚,我看见那袍子的时候即已油渍斑斑。
他经常是仰着头,迈着八字步,两眼望青天,嘴撇得瓢儿似的。
我很难得看见他笑,如果笑起来,是狞笑,样子更凶。
我的学校是很特殊的。
上午的课全是用英语讲授,下午的课全是国语讲授。
上午的课很严,三日一问,五日一考,不用功便被淘汰,下午的课稀松,成绩与毕业无关。
所以每天下午上国文之类的课程,学生们便不踊跃,课堂上常是稀稀拉拉的不大上座,但教员用拿毛笔的姿势举着铅笔点名的时候,学生却个个都到了,因为一个学生不只答一声到。
真到了的学生,一部分是从事午睡,微发鼾声,一部分看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玉梨魂》之类,一部分写“父母亲大人膝下”式的家书,一部分干脆瞪着大眼发呆,神游八表。
有时候逗先生开玩笑。
国文先生呢,大部分都是年高有德的,不是榜眼,就是探花,再不就是举人。
他们授课不过是奉行公事,乐得敷敷衍衍。
在这种糟糕的情形之下,徐老先生之所以凶,老是绷着脸,老是开口就骂人,我想大概是由于正当防卫吧。
有一天,先生大概是多喝了两盅,摇摇摆摆地进了课堂。
这一堂是作文,他老先生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题目尚未写完,当然照例要吸溜一下鼻涕,就在这吸溜之际,一位性急的同学发问了:“这题目怎样讲呀?”老先生转过身来,冷笑两声,勃然大怒:“题目还没有写完,写完了当然还要讲,没写完你为什么就要问?……”滔滔不绝地吼叫起来,大家都为之愕然。
这时候我可按捺不住了。
我一向是个上午捣乱下午安分的学生,我觉得现在受了无理的侮辱,我便挺身分辩了几句。
这一下我可惹了祸,老先生把他的怒火都泼在我的头上了。
他在讲台上来回地踱着,吸溜一下鼻涕,骂我一句,足足骂了我一个钟头,其中警句甚多,我至今还记得这样的一句:×××?你是什么东西?我一眼把你望到底?这一句颇为同学们所传诵。
谁和我有点争论遇到纠缠不清的时候,都会引用这一句“你是什么东西?我把你一眼望到底?”当时我看形势不妙,也就没有再多说,让下课铃结束了先生的怒骂。
但是从这一次起,徐先生算是认识我了。
酒醒之后,他给我批改作文特别详尽。
批改之不足,还特别地当面加以解释,我这一个“一眼望到底”的学生,居然成了一个受益最多的学生了。
徐先生自己选辑教材,有古文,有白话,油印分发给大家。
《林琴南致蔡了民书》是他讲得最为眉飞色舞的一篇。
此外如吴敬恒的《上下古今谈》,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以及张东荪的时事新报社论,他也选了不少。
这样新旧兼收的教材,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开通的榜样。
我对于国文的兴趣因此而提高了不少。
徐先生讲国文之前,先要介绍作者,而且介绍得很亲切,例如他讲张东荪的文字时,便说:“张东荪这个人,我倒和他一桌上吃过饭……”这样的话是相当地可以使学生们吃惊的,吃惊的是,我们的国文先生也许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吧,否则怎能和张东荪一桌上吃过饭?徐先生介绍完作者之后,朗诵全文一遍。
这一遍朗诵很有意思。
他打着江北的官腔,咬牙切齿地大声读一遍,不论是古文或白话,一字不苟地吟咏一番,好像是演员在背台词,他把文字里蕴藏着的意义好像都宣泄出来了。
他念得有腔有调,有板有眼,有情感,有气势,有抑扬顿挫,我们听了之后,好像已经理会到原文意义的一半了。
好文章掷地作金石声,那也许是过分夸张,但必须可以琅琅上口,那却是真的。
徐先生最独到的地方是改作文。
普通的批语“清通”、“尚可”、“气盛言宜”,他是不用的。
他最擅长的是用大墨杠子大勾大抹,一行一行地抹,整页整页地勾;洋洋千余言的文章,经他勾抹之后,所余无几了。
我初次经此打击,很灰心,很觉得气短,我掏心挖肝地好容易诌出来的句子,轻轻地被他几杠子就给抹了。
但是他郑重地给我解释,他说:“你拿了去细细地体味,你的原文是软巴巴的,冗长,懈啦光唧的,我给你勾掉了一大半,你再读读看,原来的意思并没有失,但是笔笔都立起来了,虎虎有生气了。
”我仔细一揣摩,果然。
他的大墨杠子打得是地方,把虚泡囊肿的地方全削去了,剩下的全是筋骨。
我离开先生已将近50年了,未曾与先生一通音讯,不知他云游何处,听说他已早归道山了。
同学们偶尔还谈起“徐老虎”,我于回忆他的音容之余,不禁地还怀着怅惘敬慕之意。
金岳霖先生汪曾祺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
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
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