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历史
中国纪录片发展历程

中国纪录片发展历程
中国纪录片发展历程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
纪录片被视为一种宣传和教育手段,被广泛用于展示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成就,以及推广党和政府的政策和理念。
在这个时期,纪录片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宣传中国人民的劳动精神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这些纪录片通常以长篇纪录片的形式展现,其内容结构比较传统且严谨,符合社会主义的审美要求。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
纪录片的风格开始发生变化。
国内外的纪录片思潮影响了中国的纪录片创作,引入了更加自由和个性化的表现手法。
一些纪录片导演开始拍摄关于社会问题和个人生活的作品,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突破和创新。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变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国纪录片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方面,纪录片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作品的题材和风格更加多样化。
许多纪录片涉及到社会矛盾、历史反思、民间故事等话题,展现了一个更加真实和多元的中国社会。
另一方面,中国纪录片也开始涉足国际舞台,参与国际电影节和展览。
一些中国纪录片导演因其出色的作品而获得了国际认可和奖项,为中国纪录片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做出了巨大贡献。
总的来说,中国纪录片发展历程经历了从宣传教育到个性化创
作的转变,从传统审美到多元化表达的演变。
它不仅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也反映了中国导演在表达个人观点和情感方面的成长和突破。
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变化,纪录片创作必将继续追求更高的艺术和社会意义。
3.6 中国纪录片发展简史

第三章流派纷呈:纵观纪录片思潮第六节中国纪录片的发展简史大家好,我是李蓉。
这一讲,我们将给大家来简要介绍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程。
如果追溯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史,还要从西方国家的摄影师来中国拍新闻片开始。
费利斯•比特(felice beato 1833年 - 1907年),这位兼具英国与意大利双重国籍的摄影师,是最早拍摄东亚地区的摄影师之一,也是最早的战地摄影师之一。
他通过照片来描述有价值的新闻事件,这也是后来被称之为的图片新闻报道。
他所拍摄的风俗镜头、人物肖像以及亚洲与地中海地区的美丽风景与建筑的全景极负盛名。
这些在纪录片《费利斯•比特 1860》中均有详细介绍。
在19世纪末,外国摄影师拍摄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进京,同时又拍摄了纪录当时中国社会生活风貌的影片。
20世纪初拍摄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大出丧等新闻片。
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日本摄影师拍摄了《辛亥鳞爪录》,中国摄影师朱连奎等拍摄了反映武昌起义的《武汉战争》等。
1918年前后,商务印书馆拍摄了一些以时事和风景为内容的纪录短片,如《欧战祝胜游行》《第五次远东运动会》《南京名胜》《西湖风景》等。
1924年前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十分重视纪录片。
他支持摄影师黎民伟拍摄了《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等新闻片和纪录片。
黎民伟后来去了香港拍摄商业片并取得成功,成为香港电影之父。
同一时期,苏联摄影师布留姆等在中国拍摄了《伟大的飞行与中国国内战争》《1927年的上海》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电影工作者拍摄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新闻纪录片,并培养起专业的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
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摄影场以及西北影业公司等先后摄制了《抗战特辑》《抗战实录》《芦沟桥事变》等。
建国后,1953年7月在北京建立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这是中国第一个摄制新闻片和纪录片的专业机构。
我综合了一些学者的观点将建国以来的纪录片进行了分阶段的划分,第一阶段是1958年~1977年,这一时期是政治化纪录片时期;第二阶段是1978年~1992年,这一时期是人文化纪录片时期;第三阶段,1993年~1998年,这一时期是平民化纪录片时期;第四阶段是1999年至今多元化纪录片时期。
中国纪录片发展历史(202006301138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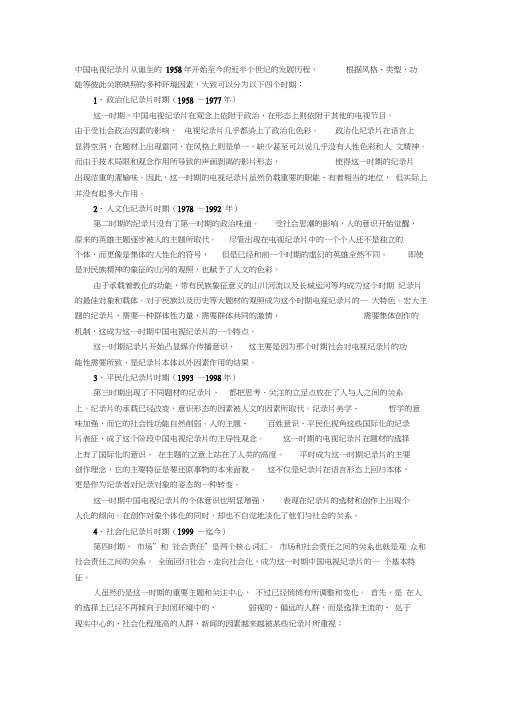
中国电视纪录片从诞生的1958年开始至今的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根据风格、类型、功能等彼此关联映照的多种环境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1、政治化纪录片时期(1958 —1977年)这一时期,中国电视纪录片在观念上依附于政治,在形态上则依附于其他的电视节目。
由于受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电视纪录片几乎都染上了政治化色彩。
政治化纪录片在语言上显得空洞,在题材上出现雷同,在风格上则是单一,缺少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人性色彩和人文精神。
而由于技术局限和观念作用所导致的声画剥离的影片形态,使得这一时期的纪录片出现浓重的灌输味。
因此,这一时期的电视纪录片虽然负载重要的职能、有着相当的地位,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多大作用。
2、人文化纪录片时期(1978 —1992 年)第二时期的纪录片没有了第一时期的政治味道。
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人的意识开始觉醒,原来的英雄主题逐步被人的主题所取代。
尽管出现在电视纪录片中的一个个人还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更像是集体的人性化的符号,但是已经和前一个时期的虚幻的英雄全然不同。
即使是对民族精神的象征的山河的观照,也赋予了人文的色彩。
由于承载着教化的功能,带有民族象征意义的山川河流以及长城运河等均成为这个时期纪录片的最佳对象和载体。
对于民族以及历史等大题材的观照成为这个时期电视纪录片的一大特色。
宏大主题的纪录片,需要一种群体性力量,需要群体共同的激情,需要集体创作的机制,这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电视纪录片的一个特点。
这一时期纪录片开始凸显媒介传播意识,这主要是因为那个时期社会对电视纪录片的功能性需要所致,是纪录片本体以外因素作用的结果。
3、平民化纪录片时期(1993 —1998年)第三时期出现了不同题材的纪录片,都把思考、关注的立足点放在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
纪录片的承载已经改变,意识形态的因素被人文的因素所取代。
纪录片美学、哲学的意味加强,而它的社会性功能自然削弱。
人的主题、百姓意识、平民化视角这些国际化的纪录片表征,成了这个阶段中国电视纪录片的主导性观念。
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程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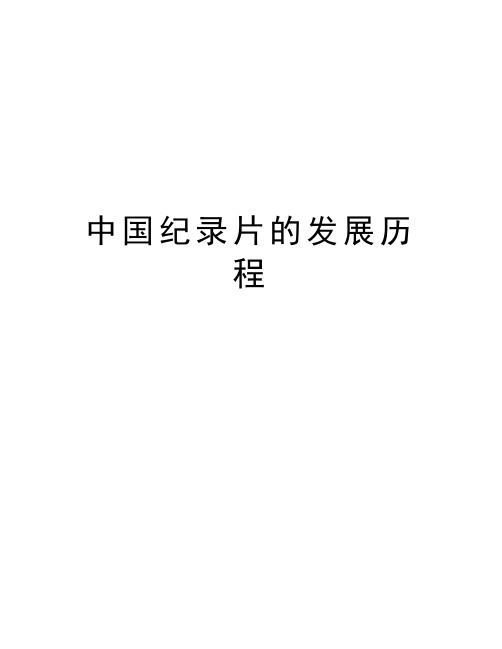
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程一 .中国纪录片的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请结合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品展开论述。
1.战争时期的新闻纪录片电影。
重要作品1938年《延安和八路军》(袁牧之导)反映了全国各地抗日爱国青年从四面八方来到延安的情景;重点纪录了毛泽东、朱德和八路军其他高级指挥员的风采,以及延安的自然风貌与社会风貌、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
那时的人力物力严重匮乏,纪录片发展速度缓慢。
2.建国初期的起步阶段(1958~1966文革前)这阶段是对新闻纪录电影的延续,传播渠道主要是电视。
主要创作人员有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
主要任务:报道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事物和新成就。
主要形式:电视纪录片和新闻片。
作品有《收租院》(北京电视台拍摄)重大意义1.突破了“报道型”新闻纪录片的僵化模式2.开创了以文学性见长的散文体纪录片3 既有“宣传教育”的思想性,又有艺术的生动性3.十年动乱时期的纪录片(1966~1978)被极左路线和帮派压制和束缚的时代,公式化,概念化,题材严重狭窄手法严重僵化。
状态:在夹缝中顽强生存。
优秀作品《深山养路工》吉林省铁岭地区一支活跃在深山峡谷中的铁路养路队,十几年如一日坚守岗位,爱护国家财产,保证铁路运输安全。
本片运用老工人的同期声讲话,以多种蒙太奇手法,制造了戏剧性效果,具有生动感人的表现力。
《放鹿》《下课以后》《太行山下新愚公》等。
4.纪录片的初步繁荣(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末)1,纪录片开始栏目化1978年9月30日央视《祖国各地》1989年《地方台50分钟》2.作品数量多,内容广,形式多样。
内容:人物,城市风光民俗宗教历史文化等。
形式:散文式,抒情诗式音画式调查报告式等。
3.出现了系列化,长篇化的创作倾向《话说长江》(25集1983年播出)《丝绸之路》(15集1979年中日联合摄制)《话说运河》(35集央视摄制)4.主要模式解说词+画面格里尔逊模式《西藏的诱惑》(刘郎 1988年) (男)“西藏的诱惑,不仅因为它的历史,它的地理,更因为:西藏,是—种境界。
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程资料

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程资料在1950年代,中国纪录片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政府开始重视纪录片的宣传功能。
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末,中国纪录片主要以宣传政治理念和社会进步为主题,强调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实践。
这一时期的中国纪录片以《沂蒙山》和《船山血泪史》等作品为代表,通过各种镜头手法和叙事方式,强调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宣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开放的到来,中国纪录片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1980年代初,中国纪录片逐渐从“光宗耀祖”向“拿得出手”转变,开始注重片子的艺术性和探索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一时期,徐克的《火种》、黄建新的《壮乡》等作品尝试挖掘中国历史的文化和社会问题,以及展现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1990年代开始,中国纪录片进入了一个多样和开放的发展阶段。
纪录片制作的主题和风格变得更加多元化,反映了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例如,赵晓亮的《芙蓉镇》和傅晨光的《金宝岛》等作品试图通过个人叙事和情感引导观众思考人与自然、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21世纪初,随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中国纪录片进入了一个新的创新时期。
新一代纪录片导演开始采用新的影像和叙事手法,通过多媒体和网络平台进行创作和传播。
例如,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和贾樟柯的《咱们还未成年》等作品,在风格上有着明显的个人表达和艺术特色。
总之,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从简单记录到宣传宣传,再到独立思考和多样化的阶段。
中国纪录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反映了社会和政治变革的特点,并通过不同的形式和风格表现出中国社会和人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未来,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年轻一代导演的崛起,中国纪录片将有更多的创新和突破。
影像中的20世纪中国——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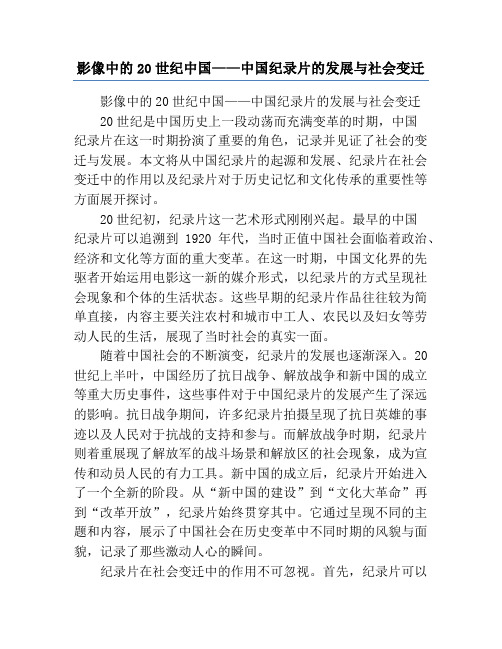
影像中的20世纪中国——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变迁影像中的20世纪中国——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变迁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动荡而充满变革的时期,中国纪录片在这一时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记录并见证了社会的变迁与发展。
本文将从中国纪录片的起源和发展、纪录片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以及纪录片对于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等方面展开探讨。
20世纪初,纪录片这一艺术形式刚刚兴起。
最早的中国纪录片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当时正值中国社会面临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变革。
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界的先驱者开始运用电影这一新的媒介形式,以纪录片的方式呈现社会现象和个体的生活状态。
这些早期的纪录片作品往往较为简单直接,内容主要关注农村和城市中工人、农民以及妇女等劳动人民的生活,展现了当时社会的真实一面。
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演变,纪录片的发展也逐渐深入。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对于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抗日战争期间,许多纪录片拍摄呈现了抗日英雄的事迹以及人民对于抗战的支持和参与。
而解放战争时期,纪录片则着重展现了解放军的战斗场景和解放区的社会现象,成为宣传和动员人民的有力工具。
新中国的成立后,纪录片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从“新中国的建设”到“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开放”,纪录片始终贯穿其中。
它通过呈现不同的主题和内容,展示了中国社会在历史变革中不同时期的风貌与面貌,记录了那些激动人心的瞬间。
纪录片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首先,纪录片可以促进社会的认知与理解。
通过真实生动的影像和事件,社会公众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到当时的生活状况和社会现象,对历史事件有更深入的理解。
其次,纪录片可以为人们提供回顾历史的窗口。
通过观看纪录片,人们可以回顾过去的岁月,对历史事件进行回顾和反思,这对于塑造个体的身份认同和国家的历史记忆非常重要。
此外,纪录片还可以培养社会的观察力和思考能力,激发人们对社会发展的关注和思考。
中国纪录片发展现状研究报告

中国纪录片发展现状研究报告引言:纪录片作为一种独特的电影艺术形式,具有真实、客观、独立的特点,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文旨在研究中国纪录片的发展现状,探讨其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中国纪录片的历史回顾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纪录片就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从最初的政治宣传工具到逐渐追求艺术表达和思想探索的作品,中国纪录片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
其中,上世纪80年代的新浪潮时期,出现了一批代表作品,如《黄土地》、《天浴》等,这些作品在国内外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也为中国纪录片的独立性和艺术性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纪录片的现状中国纪录片产量逐年增长,质量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中国纪录片在国内外各类电影节上屡获殊荣,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关注。
同时,中国纪录片的题材也日益多元化,涵盖了社会问题、人物传记、自然环境等各个方面,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多种面貌和人民的生活状态。
三、中国纪录片面临的挑战尽管中国纪录片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但仍面临着一些挑战。
首先,审查制度对纪录片的创作自由性有一定限制,一些敏感话题难以得到真实呈现。
其次,市场化程度不高,导致纪录片的宣传和推广渠道相对有限。
此外,纪录片创作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也相对不足,制约了作品的质量和水平。
四、中国纪录片的未来发展趋势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观众需求的不断变化,中国纪录片在未来有望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首先,政策的放宽将有助于纪录片创作的多样化和多元化。
其次,网络平台的兴起为纪录片的传播提供了更广泛的渠道,增加了观众的选择和接触机会。
此外,与其他艺术形式的交叉融合也将为纪录片的创新和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
结论:中国纪录片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在数量上有了显著增长,质量也越来越受到认可。
然而,中国纪录片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如审查制度限制和市场推广渠道不足等。
在未来,随着政策环境和观众需求的变化,中国纪录片有望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纪录片中国第一集主要内容

纪录片中国第一集主要内容12月7日,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中国》,在湖南卫视、芒果TV正式播出。
作为《中国》的首篇,第一集《春秋》通过讲述孔子的一生,展现老子与孔子“双星闪耀”的春秋时期。
影片中,崇尚礼制的孔丘(孔子)来到东周都城洛邑,向当时掌管国家档案典籍的史官李耳(老子)请教,共同探讨“礼”。
孔子期待用伦理规范、鲜明礼制拯救社会秩序,而老子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
两人的观点虽然相去甚远,但是道家与儒家两大思想体系,以老子与孔子的会面,形成了交流与融合,流淌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血脉中,影响后世千年。
孔子在杏坛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私学,广收门徒,有教无类。
无论出身贵贱、禀赋高下,都可以受到孔子的悉心教导。
他教“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以此作为维系社会运转的纽带;他说“仁”:核心是“爱人”,以此为做人秉持的基本道理。
孔子的“有教无类”,倡导每个人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打破了那个时代贵族对知识的垄断,知识的火种遍洒民间,当时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被不断扩大,“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教育。
“丧家之犬”这个词在历史上第一次被使用,就是形容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一路颠沛流离的状态。
影片中,因为被人在国君面前说了坏话,孔子和弟子在卫国只待了十个月便匆匆离去;到了宋国,宋国司马通过砍树来加害在大树下研习礼仪的孔子和弟子;到了郑国,和弟子走散的孔子被人形容为“丧家之犬”。
孔子遇到最糟糕的情况是在公元前489年,他们一行人由于一场战争,被陈、蔡两国的主事大夫围堵在荒野之中。
整整七天,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荫蔽,直到被围困的第七天,求救的子贡才终于带着兵马回来解围。
但即使这一路凄风苦雨,困苦、挣扎、隐忍、愤懑常常盘踞,理想主义者孔子也从未放弃过。
郑国人说孔子像“丧家之犬”时,孔子却哈哈大笑:然哉!然哉!说我像丧家之狗,那个人说得很对啊!这样积极乐观、永不言弃的精神,支撑着孔子一路风雨兼程,不畏艰难险阻地追求信仰。
中国20部大神级历史纪录片,见证真正历史的厚重

中国20部大神级历史纪录片,见证真正历史的厚重中国20部大神级历史纪录片,见证真正历史的厚重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翰墨音缘整理01《长征》伟大的转折https:///video/BV1JD4y1d7JD/?spm_id_fro m=333.788.recommend_more_video.002【央视720P高清纪录片】《大国崛起》全12集(The Rise Of Great Nations)https:///video/BV1fE411u7KZ?from=search &seid=13451723127924320455&spm_id_from=333.337.0.0 03【大秦帝国】复活的军团【D9珍藏版】【纪录片】https:///video/BV15x411c7ga?from=search &seid=4793511817100375427&spm_id_from=333.337.0.0 04大型历史纪录片《大明宫2020精华版》全6集 1080P超清https:///video/BV1jZ4y1L7iD?from=search &seid=11970990514799276720&spm_id_from=333.337.0.0 https:///bangumi/play/ss26415/?from=sear ch&seid=6916618636755899001&spm_id_from=333.337.0.0 05【HD1080】iCNTV「楚國八百年」(全八集)〔中語發音、簡體中文字幕〕周志强配音解说https:///video/BV1sx411H7WH?from=searc h&seid=11374416563498753524&spm_id_from=333.337.0.0 06探秘时刻—前清秘史细说(十集全)https:///video/BV1Up4y167kb?from=search &seid=13218086657391950929&spm_id_from=333.337.0.0 07《敦煌》孙悦斌配音https:///bangumi/play/ss25948/?from=sear ch&seid=10452625348378120633&spm_id_from=333.337.0.0 08【央视】《河西走廊》全10集(2015)https:///video/BV19f4y157oq?from=search &seid=9654021091935454173&spm_id_from=333.337.0.0 09【CCTV纪录片】圆明园https:///video/BV1vt411m7ct?from=search &seid=4070244146868731042&spm_id_from=333.337.0.0 10【纪录片】《走近毛泽东》【2003】旁白解说:齐克建。
中国历史纪录片前十名

中国历史纪录片前十名排行榜中国历史纪录片有哪些优秀的吗?中国历史纪录片虽然繁且杂,但是也有不错的中国历史纪录片前十名,常识坊供广大网友消磨时光。
10《大明宫》《大明宫》由导演金铁木耗时三年倾力打造的历史剧情纪录片。
由李翠翠、刘长纯等人主演。
影片时间跨度近300年,以大唐帝国的权力中枢大明宫为主线,通过这一空前绝后的庞大宫殿群自建造、辉煌到毁弃的全过程,讲述初唐雄健、盛唐豪奢、晚唐衰落的历史风云。
本片于2009年9月10日上映。
9《大国崛起》《大国崛起》(英文:The Rise of the Great Powers),是2006年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CCTV-2)首播的一部12集历史题材电视纪录片,记录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九个世界级大国相继崛起的过程,并总结大国崛起的历史规律。
8《复活的军团》《复活的军团》是2004年金铁木指导的历史纪录片。
2000多年前,秦始皇的军队第一次统一了中国大地,也创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
大型纪录片《复活的军团》以考古证据和历史研究为依托,借鉴故事片的表现形式,层层揭示秦军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的历史真相。
7《前清秘史》《前清秘史》是一部采用情境再现形式拍摄的24集历史电视纪录片,不同于以往的所有历史纪录片,是独创的一种叙事样式的新品种,开辟了我国历史专题纪录片的崭新形式。
它使用“尤小刚秘史剧系列”的所有素材和新拍摄的真人演绎再现历史情境,并加入大量历史遗迹、历史文档,讲述了明清两代自明朝万历至清朝雍正共9位皇帝、579位历史人物、236个历史故事。
是继《故宫》和《圆明园》后我国历史题材或者专题片的又一重要收获。
6《圆明园》《圆明园》是由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出品,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发行的大型纪录片,由薛继军担任总导演,金铁木执导,刘俊清、哈日巴拉等人主演。
影片从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切入,描述了清朝皇家园林圆明园从初建到大规模扩建成旷世园林,再到英法联军对这座人间仙境的破坏、焚烧的发展历史。
中国纪录片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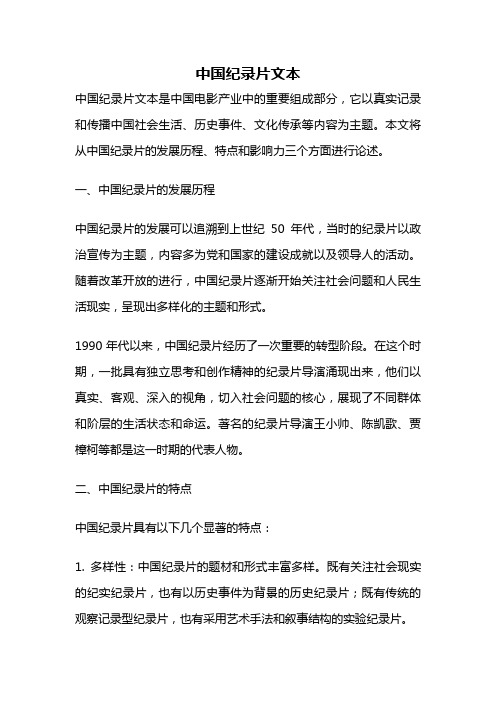
中国纪录片文本中国纪录片文本是中国电影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真实记录和传播中国社会生活、历史事件、文化传承等内容为主题。
本文将从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程、特点和影响力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程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当时的纪录片以政治宣传为主题,内容多为党和国家的建设成就以及领导人的活动。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纪录片逐渐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和人民生活现实,呈现出多样化的主题和形式。
1990年代以来,中国纪录片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型阶段。
在这个时期,一批具有独立思考和创作精神的纪录片导演涌现出来,他们以真实、客观、深入的视角,切入社会问题的核心,展现了不同群体和阶层的生活状态和命运。
著名的纪录片导演王小帅、陈凯歌、贾樟柯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二、中国纪录片的特点中国纪录片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1. 多样性:中国纪录片的题材和形式丰富多样。
既有关注社会现实的纪实纪录片,也有以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历史纪录片;既有传统的观察记录型纪录片,也有采用艺术手法和叙事结构的实验纪录片。
2. 深入挖掘:中国纪录片常常以深入挖掘社会问题为特点。
它们通过对人物的生活和命运的描摹,展现出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引发观众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反思。
3. 独立精神:中国纪录片在创作上具有独立精神。
纪录片导演们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敢于挑战权威和制度的约束,以客观真实的态度面对社会现实,展示出了清晰的个人风格和独特的创作思路。
三、中国纪录片的影响力中国纪录片在国内外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在国内,纪录片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产品,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了解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的窗口,也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提供了珍贵的记载。
同时,纪录片的独立精神和批判思维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和变革。
在国际上,中国纪录片也逐渐受到认可和关注。
一些中国纪录片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奖项,赢得了国际观众的喜爱。
这些纪录片通过展示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传统,使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并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与对话。
中国十大必看纪录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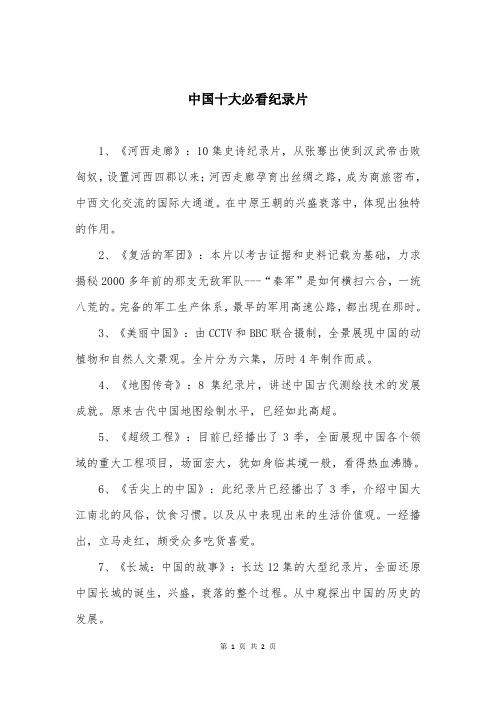
中国十大必看纪录片1、《河西走廊》:10集史诗纪录片,从张骞出使到汉武帝击败匈奴,设置河西四郡以来;河西走廊孕育出丝绸之路,成为商旅密布,中西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通道。
在中原王朝的兴盛衰落中,体现出独特的作用。
2、《复活的军团》:本片以考古证据和史料记载为基础,力求揭秘2000多年前的那支无敌军队---“秦军”是如何横扫六合,一统八荒的。
完备的军工生产体系,最早的军用高速公路,都出现在那时。
3、《美丽中国》:由CCTV和BBC联合摄制,全景展现中国的动植物和自然人文景观。
全片分为六集,历时4年制作而成。
4、《地图传奇》:8集纪录片,讲述中国古代测绘技术的发展成就。
原来古代中国地图绘制水平,已经如此高超。
5、《超级工程》:目前已经播出了3季,全面展现中国各个领域的重大工程项目,场面宏大,犹如身临其境一般,看得热血沸腾。
6、《舌尖上的中国》:此纪录片已经播出了3季,介绍中国大江南北的风俗,饮食习惯。
以及从中表现出来的生活价值观。
一经播出,立马走红,颇受众多吃货喜爱。
7、《长城:中国的故事》:长达12集的大型纪录片,全面还原中国长城的诞生,兴盛,衰落的整个过程。
从中窥探出中国的历史的发展。
8、《楚国八百年》:共8集,非常全面,系统的讲述楚国从立国,兴盛到灭亡的八百年历史。
通过一件件精美的文物,来见证其灿烂的的文明。
9、《瓷路》:中国陶瓷沿着丝绸之路,海路等到达世界各国。
中华文化也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相互碰撞,交流。
一路伴随着冒险,财富,沉船。
10、《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全长6300多公里,滋养了众多的中国人。
一路东流入海,纵横半个中国。
适合初中生学历史的纪录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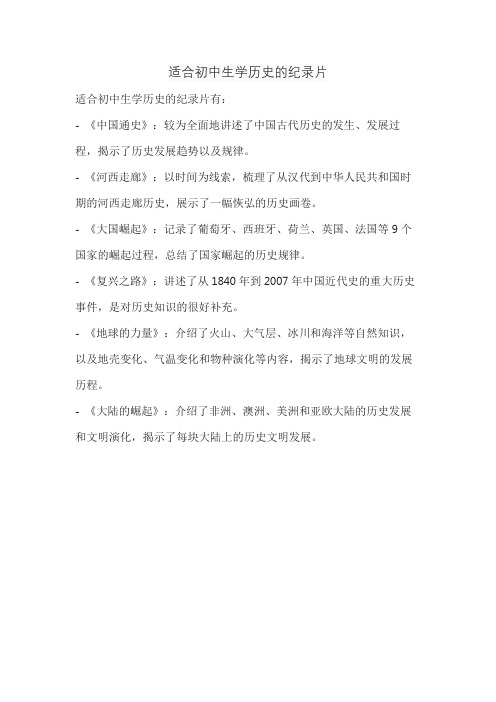
适合初中生学历史的纪录片
适合初中生学历史的纪录片有:
- 《中国通史》:较为全面地讲述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发生、发展过程,揭示了历史发展趋势以及规律。
- 《河西走廊》: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从汉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河西走廊历史,展示了一幅恢弘的历史画卷。
- 《大国崛起》:记录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9个国家的崛起过程,总结了国家崛起的历史规律。
- 《复兴之路》:讲述了从1840年到2007年中国近代史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对历史知识的很好补充。
- 《地球的力量》:介绍了火山、大气层、冰川和海洋等自然知识,以及地壳变化、气温变化和物种演化等内容,揭示了地球文明的发展历程。
- 《大陆的崛起》:介绍了非洲、澳洲、美洲和亚欧大陆的历史发展和文明演化,揭示了每块大陆上的历史文明发展。
中国人文纪录片发展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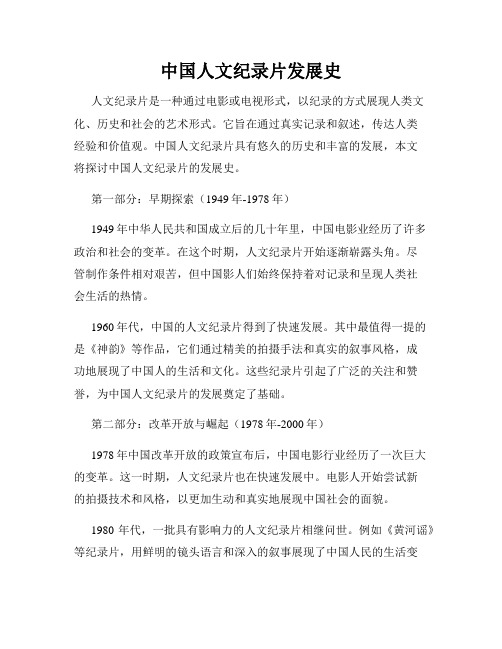
中国人文纪录片发展史人文纪录片是一种通过电影或电视形式,以纪录的方式展现人类文化、历史和社会的艺术形式。
它旨在通过真实记录和叙述,传达人类经验和价值观。
中国人文纪录片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发展,本文将探讨中国人文纪录片的发展史。
第一部分:早期探索(1949年-1978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电影业经历了许多政治和社会的变革。
在这个时期,人文纪录片开始逐渐崭露头角。
尽管制作条件相对艰苦,但中国影人们始终保持着对记录和呈现人类社会生活的热情。
1960年代,中国的人文纪录片得到了快速发展。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神韵》等作品,它们通过精美的拍摄手法和真实的叙事风格,成功地展现了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
这些纪录片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为中国人文纪录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部分:改革开放与崛起(1978年-2000年)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宣布后,中国电影行业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革。
这一时期,人文纪录片也在快速发展中。
电影人开始尝试新的拍摄技术和风格,以更加生动和真实地展现中国社会的面貌。
1980年代,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人文纪录片相继问世。
例如《黄河谣》等纪录片,用鲜明的镜头语言和深入的叙事展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变迁。
同时,一些探索性的作品也出现了,探讨了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为中国人文纪录片开辟了新的道路。
到了1990年代,中国人文纪录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
许多优秀的纪录片相继问世,如《天堂》、《江山》等作品,它们通过深入的人物描写和独特的叙事角度,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也使中国人文纪录片在国际上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第三部分:创新与多元化(2000年至今)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文纪录片持续创新,呈现出更多的多样性和多元性。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人文纪录片的制作和传播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制作团队开始使用新的技术手段,如无人机拍摄、虚拟现实等,为观众带来更为震撼和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
中国纪录片发展现状研究报告

中国纪录片发展现状研究报告中国纪录片发展现状研究报告摘要:中国纪录片在过去几十年中得到了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纪录片生产国之一。
本文对中国纪录片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以几部具有代表性的纪录片为例进行了解读。
关键词:中国纪录片、发展现状、历史、现状、未来发展趋势正文:一、中国纪录片的历史中国纪录片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主要是为了宣传政策和形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纪录片逐渐走向了自主研发和制作的道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纪录片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90 年代,中国纪录片开始进入国际市场,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二、中国纪录片的现状目前,中国纪录片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繁荣的时期。
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纪录片,如《我在故宫修文物》、《舌尖上的中国》、《大国崛起》等。
这些作品不仅在国内市场得到了高度认可,还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
同时,中国纪录片也在不断地创新和进步。
比如,《我在故宫修文物》采用了全新的纪录片制作模式,将纪录片的制作与文物修复相结合,展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又如,《舌尖上的中国》采用了网络直播的方式,让观众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美食的诱惑。
三、中国纪录片的未来发展趋势在未来,中国纪录片将继续朝着更加多元化、精品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网络空间的不断扩大,纪录片也将更多地出现在网络平台上,并与数字化营销相结合,形成更加广泛的传播渠道。
同时,中国纪录片还将不断地加强与国际同行的合作,通过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的制作技术和理念,提升自身水平。
四、总结综上所述,中国纪录片在过去几十年中得到了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纪录片生产国之一。
当前,中国纪录片已经进入了全面繁荣的时期,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纪录片。
未来,中国纪录片将继续朝着更加多元化、精品化的方向发展,并加强与国际同行的合作,提升自身水平。
中国纪录片历史

90年代之前中国纪录片的历史是从西方国家的摄影师来中国拍新闻片开始的..19世纪末;外国摄影师拍摄了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同时又拍摄了纪录当时中国社会生活风貌的影片..以后在20世纪初拍摄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大出丧等新闻片..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除日本摄影师拍摄了《辛亥鳞爪录》外;中国摄影师朱连奎等也拍摄了反映武昌起义的《武汉战争》;稍后一些;又拍摄了反映二次革命的《上海战争》..1918年前后;商务印书馆拍摄了一些以时事和风景为内容的纪录短片:《欧战祝胜游行》、《第五次远东运动会》以及《南京名胜》、《西湖风景》等..1924年前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十分重视纪录片的拍摄..他以大元帅的名义下令有关方面给予电影摄影师黎民伟工作上的方便..黎民伟这个时期拍摄了《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等新闻片和纪录片;并在孙中山逝世后;利用已拍的材料汇编为《勋业千秋》..在这个时期;苏联摄影师布留姆等人也在中国拍摄了《伟大的飞行与中国国内战争》、《1927年的上海》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电影工作者走出摄影棚;用手提摄影机拍摄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新闻纪录片;并从实际工作中培养起一批专业的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所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以及西北影业公司等先后摄制了《抗战特辑》、《抗战实录》等新闻杂志片;纪录片则有《芦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松沪前线》、《湘北大捷》、《民族万岁》和《华北是我们的》等;也给中国新闻纪录电影事业带来了新的发展..1953年7月;在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摄制新闻片和纪录片的专业机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其它电影厂也拍摄一定数量的纪录像片..新闻纪录电影从业人员的数量和素质都有很大提高;并在少数民族中培养了创作人员;摄制了大量新闻片和长短纪录片..如《百万雄师下江南》、《新中国的诞生》、《红旗漫卷西风》、《抗美援朝》、《中国民族大团结》、《伟大的土地改革》、《早春》、《百万农奴站起来》、《黄河巨变》、《非洲之角》、《在激流中》、《征服世界最高峰》、《先驱者之歌》、《莫让年华付水流》、《我们看到的日本》等;其中有些曾在国内外获奖..中国第一部彩色舞台纪录片是1953年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70年代以后;电视在全国迅速发展和普及;为新闻纪录电影的播映提供了更及时的手段;开拓了更广阔的领域;新闻纪录电影除继续在影院放映外;也大量进入了电视屏幕..在此期间;台湾国民党系统的“中制”、“台制”和民营的公司等也拍摄了一些新闻纪录像片..较有影响的有《传统小镇──美浓》、《国剧艺术》和《龙的传人》等..香港的某些电影企业也拍摄过一些反映中国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纪录片如《惨痛的战争》等..90年代以后新纪录电影是1990年代存在于体制之外的“边缘纪录片”不包括通过国家电视台体制内运作;以栏目的形式存在;代表着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和视角的电视纪录片;是建立在对传统政论风格纪录片的一种反动而产生的新运动..新纪录电影运动开始是以“地下”、民间的形式和往国外电影节送展的方式推动;是通过VCD、DVD、酒吧放映等“自动、自由”的传播方式在民间广为开展的..新纪录电影运动产生于1980年代末期;以散兵游勇的状态兴起或者说它的萌发完全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曾在昆明电视台工作过的吴文光凭着朦胧的感觉拿起了摄影机;对准他周围的“盲流艺术家”;便有了《流浪北京》的诞生..尤其片子的拍摄横跨了80年代末的政治事件;而格外引人注意..同时吴文光的行为也暗示了这种独立制作人存在的可能..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康健宁的《阴阳》;杨天乙的《老头》;朱传明的《北京弹匠》;雎安奇的《北京的风很大》;杜海滨的《铁路沿线》;王芬的《不快乐的不止一个》;赵亮的《纸飞机》等等;这些纪录片在短短几年内不断涌现并在国内外名目繁多的纪录片奖项中得奖..其中有好多制作人都是第一次拍纪录片;而且不是专门的纪录片工作者..这些新纪录片人的出现;似乎标志着一个“业余影像时代”的到来..和1990年代早期的“新纪录片运动”不同的是;当时的纪录片工作者;无论是吴文光、段锦川还是蒋樾等人;大都有在电视台工作的背景;他们是苦于不能在传统体制内进行真实的表达;才选择了独立制片的道路..而当下年轻的纪录片创作者们则多半不在专业影视从业人员之列;他们或者是还在电影学院读书的学生如朱传明与杜海滨;拍片那时尚未毕业;或者是流浪北京的青年;甚至是像杨天乙那样原本对影视制作一窍不通的门外汉..他们用来创作的器材;除了雎安奇使用了16毫米摄影机和总共20分钟的过期黑白胶片;显得稍微“职业化”一点;其他人则是靠数码DV甚至超8家用摄像机完成了自己的作品..虽然从专业的角度而言;他们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视听方面的缺陷;但这些新纪录片人却以影片内容的真实性与原创力震动了国际影坛..这些奖项不仅仅是对这几位纪录片导演的褒奖;更重要的是;它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一个普通人可以通过他的才华、毅力、对生活的热爱以及简陋的摄影器材;成为一位“真正”的纪录片导演..而且他们关注的对象大多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像王芬把摄影机对准了自己的父母暂且不管这样做带来的某些伦理问题;“新纪录片运动”似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壮大;仿佛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全民健身运动似的“业余影像时代”的狂欢..。
《中国》纪录片观后感6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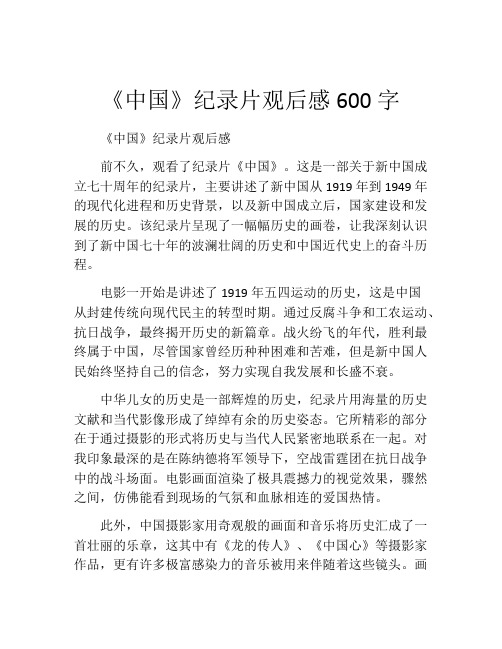
《中国》纪录片观后感600字《中国》纪录片观后感前不久,观看了纪录片《中国》。
这是一部关于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纪录片,主要讲述了新中国从1919年到1949年的现代化进程和历史背景,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历史。
该纪录片呈现了一幅幅历史的画卷,让我深刻认识到了新中国七十年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和中国近代史上的奋斗历程。
电影一开始是讲述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历史,这是中国从封建传统向现代民主的转型时期。
通过反腐斗争和工农运动、抗日战争,最终揭开历史的新篇章。
战火纷飞的年代,胜利最终属于中国,尽管国家曾经历种种困难和苦难,但是新中国人民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努力实现自我发展和长盛不衰。
中华儿女的历史是一部辉煌的历史,纪录片用海量的历史文献和当代影像形成了绰绰有余的历史姿态。
它所精彩的部分在于通过摄影的形式将历史与当代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陈纳德将军领导下,空战雷霆团在抗日战争中的战斗场面。
电影画面渲染了极具震撼力的视觉效果,骤然之间,仿佛能看到现场的气氛和血脉相连的爱国热情。
此外,中国摄影家用奇观般的画面和音乐将历史汇成了一首壮丽的乐章,这其中有《龙的传人》、《中国心》等摄影家作品,更有许多极富感染力的音乐被用来伴随着这些镜头。
画面与音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背景和着迫切将国家建设得更好更富强。
看完这部纪录片,我体会到了如何走出了一条不辞劳苦的新路程。
观看这部电影,我对新中国七十年的历史也有了更加深刻地理解,在历史的长河中,更加意识到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同时,我也更加懂得了如何发扬光大我们的先辈们留下来的优秀品质,为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不断努力。
总之,这部纪录片让我认识到在中国这个土地上,中国人民经历了沉重的历史和许多苦难。
最终,他们用自己的勇气、毅力和智慧,为世界树立了新的榜样。
我相信,通过观看这部纪录片,每个观众都会对新中国的历史有深入的理解和感受。
这是一部振奋人心的纪录片,我会一直把这份精神见证到日后的每个时刻中。
[整理]中国纪录片简史
![[整理]中国纪录片简史](https://img.taocdn.com/s3/m/aa9ac6280812a21614791711cc7931b764ce7b45.png)
中国纪录片简史中国纪录片简史(单万里)发端于1905年的中国纪录电影,至今已经走过百年历程。
中国纪录电影的开端也是中国电影的开端,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对一出京剧表演的记录。
几乎所有国家的电影都起源于纪录片,电影在发明之初首先是作为记录手段而存在的。
作为一种以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记录手段,电影擅长记录事物的运动:从简单的物理位移到复杂的化学反应,从微小的粒子变化到宏大的天体运行,从神奇的物种更迭到频繁的社会变迁,从自然的风风雨雨到人间的恩恩怨怨……。
地球上的许多事物都未逃脱摄影机的眼睛,甚至地球之外某些地方发生的事情也被记录在胶片上。
在一个世纪的漫长而短暂的岁月里,几代电影工作者(以及后来的电视工作者)拍摄了大量的纪录片。
这些影片记录了时代风云的变幻:从辛亥革命的战役到北伐战争的战场,从抗日战争的烽火到解放战争的硝烟,从建国之初的兴奋到文革时期的狂热,从改革开放的大潮到新旧世纪的交替;这些影片展示了多姿多彩的画卷:既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又有平凡的日常生活,既有迷人的领袖风采又有亲切的百姓容貌,既有壮美的山川河流又有繁多的飞禽走兽,既有庞杂的社会新闻又有丰富的科学知识。
环顾全景,琳琅满目的影片不禁令人头晕目眩,但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纪录片;回望历史,数以万计的作品难免令人眼花缭乱,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为之勾画一个简单的发展脉络。
中国纪录电影的开端(1905—1921)电影在发明不久就传到了中国。
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路易·卢米埃尔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的印度沙龙内放映了《工厂大门》、《火车到站》等影片,这一天是世人公认的电影的生日。
自1896年初开始,卢米埃尔陆续派遣了近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至1897年底这些摄影师涉足过南极洲之外的各个大陆,拍摄了750多部影片,包括在中国拍摄的影片,电影正是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的。
根据记载,1896年8月11日是中国最早放映电影的日子。
中国纪录片发展历史

中国电视纪录片从诞生的1958年开始至今的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根据风格、类型、功能等彼此关联映照的多种环境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1、政治化纪录片时期(1958—1977年)这一时期,中国电视纪录片在观念上依附于政治,在形态上则依附于其他的电视节目。
由于受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电视纪录片几乎都染上了政治化色彩。
政治化纪录片在语言上显得空洞,在题材上出现雷同,在风格上则是单一,缺少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人性色彩和人文精神。
而由于技术局限和观念作用所导致的声画剥离的影片形态,使得这一时期的纪录片出现浓重的灌输味。
因此,这一时期的电视纪录片虽然负载重要的职能、有着相当的地位,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多大作用。
2、人文化纪录片时期(1978—1992年)第二时期的纪录片没有了第一时期的政治味道。
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人的意识开始觉醒,原来的英雄主题逐步被人的主题所取代。
尽管出现在电视纪录片中的一个个人还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更像是集体的人性化的符号,但是已经和前一个时期的虚幻的英雄全然不同。
即使是对民族精神的象征的山河的观照,也赋予了人文的色彩。
由于承载着教化的功能,带有民族象征意义的山川河流以及长城运河等均成为这个时期纪录片的最佳对象和载体。
对于民族以及历史等大题材的观照成为这个时期电视纪录片的一大特色。
宏大主题的纪录片,需要一种群体性力量,需要群体共同的激情,需要集体创作的机制,这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电视纪录片的一个特点。
这一时期纪录片开始凸显媒介传播意识,这主要是因为那个时期社会对电视纪录片的功能性需要所致,是纪录片本体以外因素作用的结果。
3、平民化纪录片时期(1993—1998年)第三时期出现了不同题材的纪录片,都把思考、关注的立足点放在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
纪录片的承载已经改变,意识形态的因素被人文的因素所取代。
纪录片美学、哲学的意味加强,而它的社会性功能自然削弱。
人的主题、百姓意识、平民化视角这些国际化的纪录片表征,成了这个阶段中国电视纪录片的主导性观念。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90年代之前
中国纪录片的历史是从西方国家的摄影师来中国拍新闻片开始的。
19世纪末,外国摄
影师拍摄了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同时又拍摄了纪录当时中国社会生活风貌的影片。
以后在20世纪初拍摄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大出丧等新闻片。
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除日本摄影师拍摄了《辛亥鳞爪录》外,中国摄影师朱连奎等也拍摄了反映武昌起义的《武汉战争》,
稍后一些,又拍摄了反映二次革命的《上海战争》。
1918年前后,商务印书馆拍摄了一些以时事和风景为内容的纪录短片:《欧战祝胜游行》、《第五次远东运动会》以及《南京名胜》、《西湖风景》等。
1924年前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十分重视纪录片的拍摄。
他以大元帅的名义下令有关方面给予电影摄影师黎民伟工作上的方便。
黎民伟这个时期
拍摄了《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等新闻片和纪录片,并在孙中山逝世后,利用已拍的材
料汇编为《勋业千秋》。
在这个时期,苏联摄影师布留姆等人也在中国拍摄了《伟大的飞行与中国国内战争》、《1927年的上海》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电影工作者走出摄影棚,用手提摄影机拍摄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新闻纪录片,并从实际工作中培养起一批专业的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政治部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所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以及西北影业公司等先后摄制了《抗战特辑》、《抗战实录》等新闻杂志片,纪录片则有《芦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松沪前线》、《湘北大捷》、《民族万岁》和《华北是我们的》等,也给中国新闻纪录电影事业带来了新的发展。
1953年7月,在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摄制新闻片和纪录片的专业机构----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其它电影厂也拍摄一定数量的纪录像片。
新闻纪录电影从业人员的数量和素质都有很大提高,并在少数民族中培养了创作
人员,摄制了大量新闻片和长短纪录片。
如《百万雄师下江南》、《新中国的诞生》、《红旗漫卷西风》、《抗美援朝》、《中国民族大团结》、《伟大的土地改革》、《早春》、《百万农奴站起来》、《黄河巨变》、《非洲之角》、《在激流中》、《征服世界最高峰》、《先驱者之歌》、《莫让年华付水流》、《我们看到的日本》等,其中有些曾在国内外获奖。
中国第一部彩色舞台纪录片是1953年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70年代以后,电视在全国迅速发展和普及,为新闻纪录电影的播映提供了更及时的手段,开拓了更广阔的领域,新闻纪
录电影除继续在影院放映外,也大量进入了电视屏幕。
在此期间,台湾国民党系统的“中制”、“台制”和民营的公司等也拍摄了一些新闻纪录像片。
较有影响的有《传统小镇一一美浓》、《国剧艺术》和《龙的传人》等。
香港的某些电影企业也拍摄过一些反映中国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纪录片如《惨痛的战争》等。
90年代以后
新纪录电影是1990年代存在于体制之外的“边缘纪录片”(不包括通过国家电视台体制内运作,以栏目的形式存在,代表着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和视角的电视纪录片),是建立在对传统政论风格纪录片的一种反动而产生的新运动。
新纪录电影运动开始是以“地下”、民间的形式和往国外电影节送展的方式推动,是
通过VCD DVD酒吧放映等“自动、自由”的传播方式在民间广为开展的。
新纪录电影运动产生于1980年代末期,以散兵游勇的状态兴起或者说它的萌发完全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曾在昆明电视台工作过的吴文光凭着朦胧的感觉拿起了摄影机,对准
他周围的“盲流艺术家”,便有了《流浪北京》的诞生。
尤其片子的拍摄横跨了80年代末的政治事件,而格外引人注意。
同时吴文光的行为也暗示了这种独立制作人存在的可能。
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康健宁的《阴阳》,杨天乙的《老头》,朱传明的《北京弹匠》,雎安奇的《北京的风很大》,杜海滨的《铁路沿线》,王芬的《不快乐的不止
一个》,赵亮的《纸飞机》等等,这些纪录片在短短几年内不断涌现并在国内外名目繁多的纪录片奖项中得奖。
其中有好多制作人都是第一次拍纪录片,而且不是专门的纪录片工作者。
这些新纪录片人的出现,似乎标志着一个“业余影像时代”的到来。
和1990年代早期的“新纪录片运动”不同的是,当时的纪录片工作者,无论是吴文光、段锦川还是蒋樾等人,大都有在电视台工作的背景,他们是苦于不能在传统体制内进行真实的表达,才选择了独
立制片的道路。
而当下年轻的纪录片创作者们则多半不在专业影视从业人员之列,他们或者是还在电影学院读书的学生(如朱传明与杜海滨,拍片那时尚未毕业),或者是流浪北京
的青年,甚至是像杨天乙那样原本对影视制作一窍不通的门外汉。
他们用来创作的器材,除了雎安奇使用了16毫米摄影机和总共20分钟的过期黑白胶片,显得稍微“职业化” 一点,其他人则是靠数码DV甚至超8家用摄像机完成了自己的作品。
虽然从专业的角度而言,他们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视听方面的缺陷,但这些新纪录片人却以影片内容的真实性与原创力震动了国际影坛。
这些奖项不仅仅是对这几位纪录片导演的褒奖,更重要的是,它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一个普通人可以通过他的才华、毅力、对生活的热爱以及简陋的摄影
器材,成为一位“真正”的纪录片导演。
而且他们关注的对象大多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像王芬把摄影机对准了自己的父母(暂且不管这样做带来的某些伦理问题),“新纪录片运动”似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壮大,仿佛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全民健身运动似的“业余影像时
代”的狂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