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术期单肺与双肺通气的肺保护策略
围手术期肺部护理

对于痰液粘稠不易咳出的患者,可给予雾化吸入以稀释痰液,促 进排痰。
疼痛控制与呼吸运动锻炼
疼痛控制
术后疼痛会影响患者的呼吸和咳嗽,应给予有效的镇痛措施,如 使用镇痛泵、口服或肌注镇痛药物等。
呼吸运动锻炼
指导患者进行深呼吸、缩唇呼吸等呼吸运动锻炼,以增加肺活量和 改善肺功能。
早期活动
鼓励患者早期下床活动,以增加肺通气量和促进血液循环,有利于 肺部康复。
健康教育内容
向家属讲解手术过程、 术后注意事项、肺部护 理知识等,提高家属照 护能力。
家属心理支持
关注家属自身情绪状态 ,提供心理支持和情绪 疏导,共同应对手术带 来的压力。
2023-2026
END
THANKS
感谢观看
KEEP VIEW
REPORTING
并发症预防与处理
肺部感染
术后应密切观察患者的体温、呼吸、咳嗽等症状,及时发现并处 理肺部感染。
肺不张
对于术后出现肺不张的患者,应给予吸氧、拍背、鼓励咳嗽等处理 措施,必要时行纤维支气管镜吸痰或气管切开。
呼吸衰竭
对于严重肺部并发症如呼吸衰竭,应立即给予机械通气等抢救措施 ,并积极治疗原发病。
PART 05010203戒烟术前患者应严格戒烟,以 减少呼吸道分泌物和降低 术后肺部感染的风险。
呼吸训练
指导患者进行深呼吸、咳 嗽排痰等呼吸训练,有助 于改善肺功能和提高手术 耐受性。
雾化吸入
对于呼吸道分泌物较多的 患者,可给予雾化吸入以 稀释痰液,促进排痰。
术前宣教与教育
讲解手术过程及注意事项
01
向患者详细介绍手术过程、麻醉方式及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
饮食调整原则
以高热量、高蛋白、高维生素、易消化为主,保证患者摄入足够的营养素,同 时避免刺激性食物和饮料的摄入。
单肺通气与肺保护通气策略PPT课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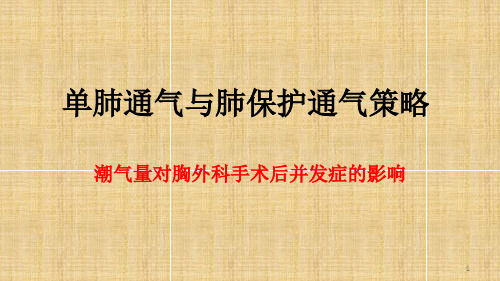
女性PBW = 45.5kg + 2.3kg×(身高[英寸] -60)
• 主要并发症定义为呼吸道并发症,包括气管切开术,需要治疗的肺脓肿,肺炎,重新 插管,大于48小时的呼吸机支持,ARDS,支气管胸膜瘘,肺栓塞,大于5天的肺部漏 气,需要支气管镜检查的肺不张和呼吸衰竭。
• 次要并发症定义为总体术后并发症,包括上文列出的所有呼吸道并发症以及非呼吸道 并发症,如计划外重返手术室,需要治疗的房性或室性心律不齐,心肌梗死,败血症, 肾衰竭,中枢神经系统事件,计划外转入ICU及吻合口漏等。
13
• ΔP可以可反映动态肺泡张力。NEJM有文献表明ΔP可作为ARDS预 后的监测指标,但未见在胸外科手术中的相关研究。
• 本研究中,ΔP与总体术后并发症发病率相关,但在去除VT因素的 回归模型中,ΔP并无统计学意义。
• OLV时,胸腔内膜压会发生变化,可能PL(跨肺压)也是合适的预 测指标。
14
• 驱动压力(ΔP)和肺顺应性(Cs): ΔP= Pplat-PEEP; Cs = VT /(Pplat-PEEP)。
5
6
7
8
9
10
r=0.467
r=0.126
11
讨论
• 胸外科手术患者中,OLV导致肺损伤和严重并发症的发生。很少有临 床研究探讨OLV时的肺保护性通气管理。
• 在肺切除术的回顾性研究中,过高VT、通气压力和OLV的持续时间已 被确定为肺损伤发展的危险因素。
单肺通气与肺保护通气策略
潮气量对胸外科手术后并发症的影响
1
• 机械通气对于危重患者和重大手术来说一种必要的支持治 疗。
• 既往的术中机械通气方法研究主要集中在预防术中肺不张, 从而支持使用较高的潮气量(VTs)。但常规正压通气下的肺 部过度扩张会诱发炎症反应等一系列有害刺激因素,最终 可能导致机械通气相关肺损伤(VILI)。
胸外科围手术期肺保护中国专家共识解读PPT课件

专家共识的制定和实施 ,有助于推动胸外科领 域的学科发展,提高医 疗水平。
未来研究方向与展望
深入研究肺保护机制
进一步探讨围手术期肺损伤的机制和 肺保护的有效措施。
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
通过多中心临床研究,验证专家共识 中提出的肺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和安全 性。
推动技术创新和转化
鼓励技术创新和转化,研发更加安全 有效的肺保护药物和器械,为临床实 践提供更多选择。
分类
根据保护措施的作用机制和时机,可 分为术前肺保护、术中肺保护和术后 肺保护。
肺保护的生理和病理基础
生理基础
肺是呼吸系统的重要器官,具有气体 交换、防御和代谢等功能。正常肺功 能依赖于气道通畅、肺泡完整和呼吸 肌有力等因素。
病理基础
胸外科手术可能导致肺功能受损,如 肺部炎症、感染、肺不张等并发症。 此外,手术创伤、麻醉药物和术后疼 痛等因素也可能影响肺功能。
呼吸衰竭处理
一旦发现患者出现呼吸衰竭症状,应立即采取相应措施,如吸氧、 机械通气等,以维持患者的生命体征稳定。
06 专家共识解读与展望
专家共识的核心内容
01
肺保护的重要性
强调在胸外科围手术期中,肺保 护是降低手术并发症和死亡率的 关键措施。
02
围手术期肺保护措 施
包括术前评估、术中管理和术后 康复等多个环节,提出了一系列 具体的肺保护措施。
通过脑电双频指数(BIS)等监测手段,确保麻醉深度适宜,避免 麻醉过深或过浅对肺功能的损害。
呼吸道管理
保持呼吸道通畅,及时清除呼吸道分泌物,减少肺部感染风险。
机械通气策略
1 2 3
通气模式选择
根据患者病情和手术需要,选择合适的通气模式 ,如压力控制通气(PCV)、容量控制通气( VCV)等。
单肺通气与肺保护通气策略护理课件

常见并发症及处理
诊断
患者血氧饱和度下降,可能出现呼吸 困难、发绀等症状。
处理
通过提高吸氧浓度、延长吸氧时间, 或使用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等措施纠 正低氧血症。
常见并发症及处理
诊断
患者可能出现胸闷、气短、咳嗽等症状,胸部X线检查可见肺 部萎陷。
处理
鼓励患者咳嗽、深呼吸,使用支气管扩张剂以改善肺通气, 严重时可考虑纤维支气管镜治疗。
THANKS
感谢您的观看
Part
06
总结与展望
单肺通气与肺保护通气策略的总结
肺保护通气策略
通过采用适当的机械通气 方式,减少呼吸机相关肺 损伤,保护肺组织。
单肺通气
在某些手术中,为了暴露 手术视野,采用单侧肺通 气,使手术侧肺萎陷。
护理措施
在实施单肺通气与肺保护 通气策略时,采取相应的 护理措施,确保患者的安 全和舒适。
Part
05
临床案例分享
成功案例分享
成功经验
分享单肺通气与肺保护通气策略在临床实践中的成功应用案例,包括患者基本信 息、手术过程、通气策略实施情况、护理措施及效果评价等。
失败案例分析
失败教训
分析单肺通气与肺保护通气策略在临床实践中失败的案例,探讨失败原因、通气策略的不足之处以及如何避免类似失败的发 生。
Part
03
单肺通气与肺保护通气策略的 护理
术前评估与准备
评估患者情况
了解患者病史、手术类型 、麻醉风险等,为制定护 理计划提供依据。
术前宣教
向患者及家属介绍手术及 麻醉相关知识,减轻焦虑 和恐惧情绪。
术前准备
确保患者术前禁食、禁饮 ,完成必要的实验室检查 和影像学检查。
术中护理要点
ERAS理念下肺保护通气策略在全麻手术中应用

3
全麻手术中的效果
减少术后肺部并发症
肺保护通气策略可以降低术 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率
肺保护通气策略可以减少术 后肺部感染的发生率
肺保护通气策略可以减少术 后肺部水肿的发生率
肺保护通气策略可以减少术 后肺部血栓的形成率
缩短术后恢复时间
01
04
肺保护通气策略可以降低 术后肺部功能障碍的风险, 从而缩短术后恢复时间。
ERAS理念下肺保护通气策略 在全麻手术中应用
演讲人
目录
01
ERAS理念与肺保护通气策略
02
全麻手术中肺保护通气策略的应用
03
肺保护通气策略在全麻手术中的效果
04
肺保护通气策略在全麻手术中的挑战与展望
ERAS理念与肺
1
保护通气策略
什么是ERAS理念
ERAS理念:即加速康复外科理念,是一种以 患者为中心的围手术期管理策略。
03
肺保护通气策略可以减少 术后肺部炎症反应,从而 缩短术后恢复时间。
02
肺保护通气策略可以降低 术后肺部感染的风险,从 而缩短术后恢复时间。
肺保护通气策略可以减少 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 从而缩短术后恢复时间。
提高患者满意度
01
减少术后并发症: 肺保护通气策略 可以降低术后肺 部并发症的发生 率,提高患者满 意度。
02 肺保护通气策略通过
控制呼吸频率、潮气
量、吸气压力等参数,
实现肺部的有效通气。
03 肺保护通气策略可以
减少肺泡塌陷,降低
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的
消耗,从而保护肺部。
04 肺保护通气策略还可
以减少术后肺部炎症 反应,降低肺部感染 的风险。
全麻手术中肺保护
单肺通气肺功能保护策略

04
预防感染,保持良好 的卫生习惯
加强护理措施
保持呼吸道通畅,
01
避免气道阻塞
保持呼吸道通畅,
04
避免气道阻塞
02
保持呼吸道湿润, 避免干燥
03
保持呼吸道清洁,
Hale Waihona Puke 避免感染谢谢肺泡通气量:反映肺 泡通气功能的指标
肺顺应性:反映肺组 织弹性和扩张能力的
指标
肺泡-动脉二氧化碳分 压差:反映肺二氧化
碳排出功能的指标
肺泡-动脉氧饱和度差: 反映肺氧合功能的指 标
临床症状
呼吸困难:评估患 者呼吸困难程度, 如呼吸频率、呼吸 深度等
01
咳嗽:评估患者咳 嗽程度,如咳嗽频 率、咳嗽持续时间 等
用,如呼吸抑 制、低血压等
气短等
定期检查肺功 能,了解病情 变化
监测患者心理 状态,如焦虑、 抑郁等
监测呼吸频率、 监测血氧饱和
心率、血压等 度,了解患者
生命体征
缺氧情况
预防并发症
保持呼吸道通畅,避 免气道阻塞
01
避免过度通气,防止 肺泡损伤
03
定期监测肺功能,及 05 时发现并处理并发症
02
保持肺部湿润,避免 干燥
单肺通气肺功能保护策略
演讲人
目录
01. 单肺通气的原理 02. 肺功能保护的方法 03. 肺功能保护的效果评估 04. 肺功能保护的注意事项
单肺通气的原理
单肺通气的定义
单肺通气是指在麻醉过程 中,通过机械通气或人工 通气,使一侧肺通气,另 一侧肺不参与通气的技术。
单肺通气常用于胸外科手 术、肺移植手术等需要单 侧肺通气的情况。
02
痰液:评估患者痰 液情况,如痰液颜 色、痰液量等
单肺通气与肺保护通气策略

选择单肺通气还是肺保护通气,需要根据患者 的病情、手术类型、麻醉方式等因素综合考虑。
单肺通气和肺保护通气可以结合使用,以提高 手术效果和患者安全。
单肺通气:通常采用双腔 气管插管,保证手术侧肺 的通气
肺保护通气:通常采用低 潮气量、高峰压等通气策 略,保护肺部免受损伤
单肺通气:适用于需要手 术侧肺通气的情况,如肺 癌手术等
肺保护通气:适用于需要 保护肺部的情况,如急性 呼吸窘迫综合征等
单肺通气与肺保护通气的优缺点
单肺通气:优点是操作简 单,适用于大多数手术; 缺点是容易导致肺不张和 通气不足。
肺复张:通过间歇 性正压通气,使肺 泡重新张开,减少 肺损伤
保护性通气策略: 根据患者的病情和 肺功能,选择合适 的通气模式和参数, 以减少肺损伤
单肺通气与肺保护通气的异同
单肺通气:主要用于手术 中的一侧肺通气,减少手 术对健康肺的干扰
肺保护通气:主要用于保 护肺部,减少肺部损伤, 适用于多种肺部疾病
肺保护通气策略可以提高患者的生存率,降低并 发症的发生率。
肺保护通气的目标
减少肺损伤 保护肺功能
降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发生率 提高患者舒适度和生存质量
肺保护通气的实施方法
低潮气量通气:将 潮气量控制在68ml/kg体重,以 减少肺损伤
呼气末正压通气: 在呼气末施加正压, 以保持肺泡开放, 减少肺损伤
B
麻醉医生在患侧支气管 插管,健侧支气管封堵
C
机械通气设备调整至单 肺通气模式
D
监测患者生命体征,确 保通气效果和患者安全
肺保护通气的定义
肺保护通气策略是一种旨在减少肺损伤的通气方 式。
围术期单肺与双肺通气的肺保护策略

围术期单肺与双肺通气的肺保护策略本页仅作为文档封面,使用时可以删除This document is for reference only-rar21year.March围术期单肺与双肺通气的肺保护策略围术期患者存在发生多种肺损伤的风险,包括肺不张、肺炎、气胸、支气管胸膜瘘、急性肺损伤、急性肺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LI/ARDS)等。
而麻醉管理既可能改善肺功能,也有可能导致或加重肺损伤。
应用“更接近生理状态的潮气量及适当呼气末正压(PEEP)”的肺保护性通气策略能够减轻肺损伤的程度。
本文将对肺功能正常患者与存在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COPD)患者进行单肺与双肺通气时,机械通气的效果以及机械通气在呼吸机相关肺损伤(VILI)中的作用进行探讨。
1、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COPD是手术患者中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包括三种病变形式:肺气肿、外周气道疾病和慢性支气管炎。
呼吸驱动力许多严重COPD患者存在静息下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升高的情况,通常的病史采集、体格检查以及肺功能检查难以将这类“CO2潴留”与其他非潴留情况相鉴别。
对于机械性肺功能低下的患者,这种CO2潴留的主要原因可能并非呼吸控制机能的改变,而更多是因为缺乏维持正常PaCO2所需要增加呼吸功的能力。
之前的理论认为,慢性高碳酸血症的患者有赖于低氧刺激以保证呼吸驱动,而对PaCO2敏感性降低。
这被用来解释临床上COPD患者濒临呼衰时,给予高浓度氧气反而诱发高碳酸血症性昏迷。
实际上,由于分钟通气量基本上没有改变,因此这类患者的PaCO2增高仅有很小一部分是由呼吸驱动减弱引起的。
PaCO2升高的主要原因是:较高的吸入氧浓度引起肺泡通气量的相对减少以及肺泡死腔和分流的增加,而这一现象又是由于局部缺氧性肺血管收缩(HPV)减弱使肺血流灌注从正常V/Q比区域向低V/Q比区域发生再分布造成的。
而Haldane效应(饱和氧合血红蛋白的携CO2能力不如非饱和氧合血红蛋白)也是造成PaCO2小幅升高的原因。
保护性肺通气策略在单肺通气中的应用

吸窘迫综 合征 (c t rsi t ydsessn rm ,A D ) aue epr o irs ydo e R S 和 ar t 其他原因导致的呼吸衰竭 的治疗 中提 出的机械通气 策略 , 其 目的是 在进 行机械通气支持 的同时 , 保护 肺组织 免受 呼吸机
气不 足 , 小气道过早关 闭 , 肺不 张和肺顺 应性 降低 , 气血 流 通 比例失调 , 产生严重的低氧血症 , 并加重肺部感染及 A Il。 Ll j J 健侧予适 当的 P E E P可 以增 加功能残气量 , 改善 通气/ 血 流 比例失调 , 防止术 中发 生肺泡萎 陷 , 加肺 的顺应性 , 明 增 可
阻力 , 降低微循环 阻力 , 对缺血性肺血管收缩也有加强作用 。
现多数观点 认 为 , L O V中采用 4~ lk 6m/ g潮气量并 结
、
小潮气量结合健侧合适 的 P E E P和 P H
合适 当的 P E E P和 P H是一种有效的保 护性肺 通气 策略 , 既能 较好地降低低 氧血症 、 不 张发生 , 可避 免气 道 内压 力 过 肺 又 高, 导致肺组织 的气压伤及血流动力学异常 , 改善 围术期患 者
临床症状 。
传统观点认 为 O V时应 采用接 近双肺 通气 时的潮气量 , L 因为大潮气量确 实能增加 动脉氧分压 , K z n等 报道 在 但 oi a
O V时大潮气量 可造 成肺 损伤 , A I L 使 L 发病 率显 著增 加 , 并
明显增加某些有 害炎性 细胞 因子 的产 生 。G j a c等_ 发现 潮 i 2 气量 大于 7 0m 和呼吸道峰压大 于 3 n H O是 A D 0 l 0cl R S的独
小潮气量通气时 , 有可能产生高碳酸血症 , 最近的研究 表 明在没有相关禁忌症 时适 当 的高碳 酸血症 是有益 的 , 可使 它
胸外科围手术期肺保护中国专家共识(2019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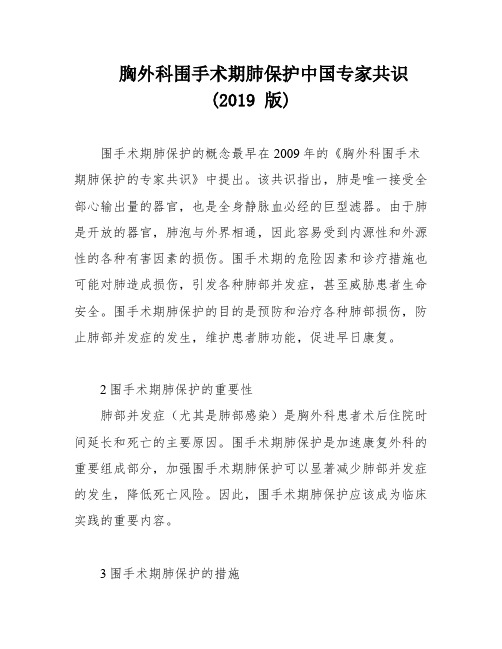
胸外科围手术期肺保护中国专家共识(2019 版)围手术期肺保护的概念最早在2009年的《胸外科围手术期肺保护的专家共识》中提出。
该共识指出,肺是唯一接受全部心输出量的器官,也是全身静脉血必经的巨型滤器。
由于肺是开放的器官,肺泡与外界相通,因此容易受到内源性和外源性的各种有害因素的损伤。
围手术期的危险因素和诊疗措施也可能对肺造成损伤,引发各种肺部并发症,甚至威胁患者生命安全。
围手术期肺保护的目的是预防和治疗各种肺部损伤,防止肺部并发症的发生,维护患者肺功能,促进早日康复。
2围手术期肺保护的重要性肺部并发症(尤其是肺部感染)是胸外科患者术后住院时间延长和死亡的主要原因。
围手术期肺保护是加速康复外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围手术期肺保护可以显著减少肺部并发症的发生,降低死亡风险。
因此,围手术期肺保护应该成为临床实践的重要内容。
3围手术期肺保护的措施围手术期肺保护的措施包括预防和治疗两个方面。
预防方面,应该避免各种危险因素的影响,如避免吸烟、控制呼吸道感染、预防误吸等。
治疗方面,应该及时发现和治疗各种肺部损伤和并发症,如肺不张、肺炎、肺栓塞等。
同时,还应该加强术后康复护理,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4围手术期肺保护的实践意义围手术期肺保护不仅是加速康复外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多学科模式下的重要内容。
通过加强围手术期肺保护,可以显著降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减少死亡风险,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因此,围手术期肺保护的实践意义非常重要,应该在临床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
XXX alveoli。
respiratory tract。
and lung interstitium。
Alveoli are the sites where gas exchange occurs een the body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XXX。
such as surgical trauma。
stress response。
围手术期的护理

围手术期的护理
围术期肺部保护措施和策略
1、术前宣教:可以减少肺部并发症。
2、戒烟:>2周,减少气道分泌物并改善通气,有效降低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成。
3、呼吸训练、运动训练:呼吸操及各组呼吸训练器械、腹式呼吸等。
4、营养支持,纠正贫血、应积极纠正低蛋白、贫血和水电解质失衡。
5、清洁呼吸道(物理疗法、雾化吸入)。
6、解除气道痉挛(支管扩张剂)。
7、抗感染
1、择期手术应推迟至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治愈之后;
2、痰液量大者应在经治疗痰液减少2周后再行手术;
3、合并慢性呼吸道疾病者,可在术前3天使用抗生素。
术前备皮准备新观点
1、一类二类手术术前24一72小时清洁消毒,肥皂水清洁,再葡泰消毒。
2、三类四类手术(会阴、腋下、头部)可以用电动剃毛刀、前毛剪刀、脱毛剂。
3、术前剃毛增加手术部位感染率。
围手术前糖尿病患者血糖监测标准
1、大中型手术中,患者血糖控制的目标为7.8-10.0mmol/L。
2、中、小型手术后患者血糖控制目标为空腹血糖<7.8mmol/L,随机血糖<10.0mmol/L。
3、危重症、心脏术后或机械通气的患者,血糖应保持为7.8-10.0mmol/L,避血糖<6.1mmol/L。
4、有明确糖尿病史的患者,糖化血红蛋白>8%应考虑推迟择期手术。
围术期肺保护通气策略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021版)

术后肺部并发症与肺保护
(2)机械通气模式优化 ▪ 临床常用PCV与VCV两种模式,PCV具有较低吸气峰压,能改善动
脉血气分析结果;而VCV能维持较高潮气量、较低平台压,通过 测量吸气平台压,从而准确测定肺驱动压。
术后肺部并发症与肺保护
▪ 两种通气模式各有利弊,无证据表明哪种方式对降低PPCs更具式的选择与优化 (1)补偿性通气策略 ▪ 潮气量补偿尤其适用于婴幼儿,其动态调节能改善肺顺应性。压
力控制-容量保证通气模式(pressure controlled ventilation-volume guaranteed,PCV-VG)可通过恒定压力提供减速气流,对于预设 潮气量采用最小正压,降低高气道压导致的潜在气道和肺泡损伤 的同时,又能保证肺泡有效通气和换气。
术后肺部并发症与肺保护
(一)高危因素和易感人群 ▪ 围术期肺功能保护主要包括呼吸机相关肺损伤(ventilation-
induced lung injury,VILI)和PPCs的防范。VILI主要因压力伤、容 积伤、剪切伤及生物伤等诱发; ▪ 而PPCs目前尚无标准定义和明确机制,多数专家认为,PPCs包括 术后肺不张、肺炎、支气管痉挛和呼吸衰竭等。其高危因素和易 感人群主要有:
术后肺部并发症与肺保护
▪ 2019欧美多中心指南高级别推荐(BJA)建议ARDS患者潮气量 ≤6ml/kg或尽量使吸气平台压不超过30~35cmH2O。
▪ 对于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危重型患者,行有创机械通气时,也建 议采用小潮气量4~8ml/kg(理想体重)和低吸气压力(平台压< 30cmH2O)的“LPVS策略”,以降低VILI。
术后肺部并发症与肺保护
5. 呼吸频率与吸气/呼气比值(I:E) ▪ 为保证氧合可在降低潮气量后逐渐增加呼吸频率至15~20次/分,
胸外科围手术期肺保护专家共识-11-(7-14-2)

外科围手术期肺保护的专家共识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医师分会、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分会“快速康复外科”专家组肺保护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
狭义肺保护是肺移植或心肺移植时对供体肺脏的保护,使之在移植于受体后仍能发挥正常肺功能。
广义肺保护则是主动地对各种原因引起的,即将发生的肺损伤的预防和治疗,以维护患者肺功能,促进早日康复。
外科围手术期肺保护,属于广义肺保护的范畴。
肺脏是体内唯一接受全部心输出量的器官,也是全身静脉血必经的巨型滤器;同时肺脏也是开放的器官,肺泡经各级支气管、气管与外界相通。
因此,肺脏很容易受到内源性和外源性有害因素的作用而受到损伤。
术前危险因素、手术、麻醉,输血、体外循环以及其他医疗措施等均可在围手术期对肺脏造成一定的损伤,发生围手术期各种肺部合并症,严重者发生呼吸功能不全,威胁患者生命安全。
因此,围手术期肺保护措施,预防和治疗围手术期肺部并发症非常重要,是外科手术患者快速康复的有力保证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医师分会,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分会,在近年来各种学术会议有关围手术期处理、快速康复外科学术交流的基础上,组织胸外科专家多次讨论对围手术肺保护问题达成以下共识,供同道们参考:一、围手术期常见肺部并发症及其相关危险因素(一) 围手术期常见肺部并发症术后肺部并发症是胸外科手术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围手术期患者常见的肺部并发症包括肺不张、肺水肿、肺炎、支气管炎、支气管痉挛、呼吸衰竭甚至ARDS、基础慢性肺疾患加重等。
多项研究显示,术后肺部并发症与心脏疾病一样或更常见。
研究显示,上腹部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病率高达35%,其中肺炎占16.6%、支气管炎占15%、肺不张和肺栓塞各占1.7%1。
术后肺炎通常为院内获得性肺炎,其死亡率高达10%~30%,术后肺部并发症导致住院时间平均延长1~2周2,3。
伴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等呼吸道疾病时,围手术期支气管痉挛的发生率增加。
有哮喘病史患者术中支气管痉挛发生率为10%左右。
围术期肺保护通气策略

▪ 结论:在相对较低的PEEP下,小潮气量通气与大潮气量通气在减少术后并发症方面,并 没有什么优势,甚至反而增加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
机械通气策略
z 围术期肺保护策略
z
前言
▪ 2009 年发表的《胸外科围手术期肺保护的专家共识》首次提出了“围手术期肺保护”的概念。 ▪ 围手术期的各种危险因素以及诊疗措施均可能对肺造成一定的损伤,从而引发各种肺部并
发症,严重者发生呼吸功能不全,甚至威胁患者生命安全。 ▪ 加强围手术期肺保护可以显著减少肺部并发症的发生、降低死亡风险。 ▪ 2019 版《胸外科围手术期肺保护中国专家共识》在 2009 版的基础上加入了围手术期肺保
•术后肺部并发症高风险患者围手术期肺保护策略,国际麻醉学与复苏杂志,2018,39(03):268-272
z
设置合适的FiO2
▪ 在确保满意的血氧饱和度条件下,术中应使用低-中度吸入氧浓度(FiO2,30%~50%)。
✓ 胸外科围手术期肺保护中国专家共识(2019 版).《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2019, 26(9): 835-842.
▪ 增加FiO2虽可改善PaO2,但长时间吸入高浓度氧气可发生氧中 毒。
▪ Olivant Fisher等 发现,用100%的氧气双肺通气1 h或单肺通气 3 h的动物比用低于50%氧气通气的动物有较大的肺部炎症损害。 在单肺通气中,较低的FiO2导致较少的炎症反应。
▪ 目前认为吸入高浓度氧气时(FiO2>60%),肺泡内大部分氮气 被氧气替代,肺泡内氧气迅速弥散入血,如因呼吸道不畅,相应 肺泡得不到补充可发生萎陷,最终发生肺不张。
▪ 研究显示,术后肺部并发症是胸部手术围手术期主要风险之一,发病率高达 15%~40%,导致住院时间延长 1~2 周。
围术期肺保护通气策略临床应用专家共识护理课件

04
围术期肺保护通气策略的临床案例分析
案例一:肺保护通气策略在心脏手术中的应用
总结词
有效降低肺部并发症
详细描述
在心脏手术中,采用肺保护通气策略可以显著降低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率, 如肺炎、肺不张等。通过调整潮气量、呼气末正压等参数,可以减少肺损伤, 促进术后肺功能的恢复。
案例二:肺保护通气策略在胸科手术中的应用
宣教与沟通
向患者及家属介绍手术及 通气策略的相关知识,减 轻其焦虑和恐惧情绪。
术前准备
指导患者进行呼吸功能锻 炼,如深呼吸、有效咳嗽 等,以增强其呼吸肌力量 。
术中护理措施
监测呼吸指标
密切观察患者的呼吸频率 、血氧饱和度、气道压力 等指标,及时发现并处理 异常情况。
保持呼吸道通畅
协助患者排痰、咳嗽,确 保呼吸道畅通,减少肺部 感染的风险。
监测气体交换
通过监测患者的氧饱和度、二氧化碳分压等指标,及时调整通气参 数,确保良好的气体交换。
肺复张操作
在特定情况下,如出现严重肺不张或肺部萎陷,需要进行肺复张操 作,以恢复肺部正常形态和功能。
肺保护性通气策略的临床应用
手术中应用
在手术过程中,采用肺保护性通 气策略可以降低术后肺部并发症
的风险。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对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肺保护通气策略应注重采用 适当的气道压力支持和适当的呼气末正压,以改善通气和 氧合。
肺保护通气策略与其他保护措施的联合应用
药物治疗
01
某些药物如糖皮质激素、抗炎药等,可以与肺保护通气策略联
合应用,以进一步减轻肺损伤。
液体管理
02
优化围术期液体管理,控制液体平衡,有助于减少肺水肿和肺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围术期单肺与双肺通气的肺保护策略围术期患者存在发生多种肺损伤的风险,包括肺不张、肺炎、气胸、支气管胸膜痿、急性肺损伤、急性肺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LI/ARDS)等。
而麻醉管理既可能改善肺功能,也有可能导致或加重肺损伤。
应用更接近生理状态的潮气量及适当呼气末正压(PEEP的肺保护性通气策略能够减轻肺损伤的程度。
本文将对肺功能正常患者与存在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COPD患者进行单肺与双肺通气时,机械通气的效果以及机械通气在呼吸机相关肺损伤(VILI)中的作用进行探讨。
1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COPD是手术患者中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包括三种病变形式:肺气肿、外周气道疾病和慢性支气管炎。
呼吸驱动力许多严重COPD患者存在静息下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升高的情况,通常的病史采集、体格检查以及肺功能检查难以将这类“ CO2潴留”与其他非潴留情况相鉴别。
对于机械性肺功能低下的患者,这种CO2潴留的主要原因可能并非呼吸控制机能的改变,而更多是因为缺乏维持正常PaCO2所需要增加呼吸功的能力。
之前的理论认为,慢性高碳酸血症的患者有赖于低氧刺激以保证呼吸驱动,而对PaCO2敏感性降低。
这被用来解释临床上COPD患者濒临呼衰时,给予高浓度氧气反而诱发高碳酸血症性昏迷。
实际上,由于分钟通气量基本上没有改变,因此这类患者的PaCO2增高仅有很小一部分是由呼吸驱动减弱引起的。
造成PaCO2小幅升高的原因然而此类患者术后必须补充给氧,以预防与术后不可避免的功能残气量减少有关的低氧血症发生,同时要预料到可能会伴随有PaCO2升高,密切监测PaCO2 变化。
为了在术前识别此类患者,所有3期(FEV1 30-49%预期值)及4期(FEVK30濒期值)COPD患者都需要进行动脉血气分析检查。
肺大泡许多中重度COPD患者的肺实质会出现囊状空腔,即形成肺大泡。
肺大泡通常占据胸腔>50%时才出现症状,患者在原有阻塞性肺病的基础上出现限制性肺病的表现。
肺组织周围的肺间质具有弹性回缩能力,而肺大泡是其中出现的结构性支撑组织丧失形成的局限性区域,肺大泡内的压力实际上等于周围肺泡在一个呼吸周期内的平均压力。
在正常自主呼吸下,肺大泡内压力与周围组织相比为轻度负压;当正压通气时,肺大泡相对周围组织形成正压而不断膨胀,存在出现破裂、张力性气胸和支气管胸膜痿的风险。
在维持低气道压力的情况下,肺大泡患者可以安全地应用正压通气;但应保证配备合适的专业人员和设备,以便必要时可以及时置入胸腔引流管和进行肺隔离。
气流受限合并严重COPD的患者即使在静息下也常表现出呼气“气流受限”。
正常患者仅在用力呼气时才会有此流量受限的现象。
“流量受限”的发生是呼气过程中胸内段气道内等压点(EPP, equal pressure poin t出现造成的。
正常患者在平静呼气中,肺泡弹性回缩形成的上行压力可使气道内压始终高于胸腔内压。
弹性回缩压力的这种效应随着气流在气道内下行而逐渐减弱。
用力呼气时,胸腔内压在某一点等于气道内压而达到EPP从而限制了呼出气流。
这时,肺容量一定的情况下,无论怎样增加呼气力也不会产生呼气气流的增加。
肺气肿患者由于肺弹性回缩力的丧失,气流受限尤其常见,表现为严重的呼气性呼吸困难。
气流受限因存在于呼吸肌、胸腔以及气道等压点远端的机械感受器受到刺激而引起患者出现呼吸困难。
任何因素引起的呼吸功增加都会进一步加重呼吸困难症状。
这种肺泡过度膨胀引起的变异性气道机械受压是导致肺气肿患者气流阻塞的主要原因。
由于肺的动力性高度膨胀,严重气流受限的患者接受正压通气时存在血流动力学崩溃的风险。
因为他们吸入阻力没有增加,但是存在明显的呼气阻塞,所以面罩手动通气时即使轻微的正压通气也可引起患者出现低血压。
这也是在某些情况下发生“Lazaru综合症”(抢救措施和正压通气停止后,心跳骤停的患者却复苏过来的现象)的原因。
自发性呼气末正压(Auto-PEEP)具有严重COPD的患者在其肺泡压降至大气压之前经常以中断呼气的方式进行呼吸,这种呼气不全的现象是由于气流受限、呼吸功增加、气道阻力增加等一系列因素共同造成的。
呼气提前中断可导致呼气末肺容量升高超过功能残气量。
这种静息下出现的肺泡内呼气末正压被称为自发性呼气末正压(auto-PEEP或内源性呼气末正压(in tri nsic PEER。
COPD患者在自主呼吸的吸气开始前,胸内压力需先降低至一定程度才可以抵消内源性呼气末正压的作用,这进一步加重了患者原有的呼吸负担。
Auto-PEEP在机械通气时更加显着。
其与潮气量呈正比,而与呼气时间成反比。
常规麻醉机的通气压力表无法探测出Auto-PEEP的存在,新一代ICU使用的呼吸机可以通过呼气末气流中断来测量Auto-PEEP绝大多数麻醉中进行单肺通气的COPD患者被发现存在Auto-PEEP但给予少量外源性PEEP(达到患者Auto-PEEP的50%压力水平,女口5cmH2O)反而可以减轻很多机械通气的COPD 患者肺部的过度膨胀,这可能是因为PEEP对远端气道可产生充气支撑作用,从而减少了气道塌陷。
单肺通气时,auto-PEEP与外源性PEEP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得更为复杂。
COPD 患者在单肺通气时会出现典型的auto-PEEP,而开胸手术可以使呼气末肺容量接近功能残气量,这反而可缓解auto-PEEP且改善氧和。
此时给与这类患者外源性PEEP会进一步增加呼气末肺容量,阻碍肺血流向通气侧肺的再分布。
然而,进行单肺通气的肺功能正常患者在呼气末时肺容量常常低于功能残气量,因此加用外源性PEEP通常是有益的。
2\机械通气麻醉医师曾经被灌输“围术期应给予通气患者相对大的潮气量”的理念,并被建议使用15ml/kg的潮气量用以预防手术期间的肺不张,这远远超出了大部分哺乳动物自主呼吸的正常潮气量(6ml/kg)。
近期研究表明:大潮气量的应用是无急性肺损伤(ALI)患者发生肺损伤的主要危险因素。
Gajic等报道,约25%肺部正常的患者在ICU经历2天或更久的机械通气后发生了ALI或ARDS ALI的主要危险因素包括:使用大潮气量、存在限制性肺部疾病以及输注血液制品。
同一研究小组的一项前瞻性研究发现:潮气量〉700ml以及气道峰压〉30cmH2O 是ARDS 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
一项对接受食道手术的患者进行的术中研究做了“单肺/双肺通气中使用9ml/kg潮气量不加用PEEP与单肺通气5ml/kg或双肺通气9ml/kg全程加用5cmH2O PEE P的比较。
研究显示,小潮气量合并PEEP组患者的血浆炎症因子(IL-1、IL-6、IL-8)水平明显更低;两组间术后转归方面没有显示出明显差异,但该研究还不足以能够确实地证明这一点;该研究还显示小潮气量通气组患者具有更好的单肺通气中和单肺通气后即刻的氧合水平(仅限于术后18小时)。
Olivera等在一项研究中对无ALI的ICU患者接受常规通气与肺保护性通气进行了对比,他们将患者随机分组并按预测体重分别以10-12ml/kg和6-8ml/kg进行通气。
两组患者都加用5cmH2O的PEEP并逐级调整吸入氧浓度以保持SpO2>90%经12小时通气后,大潮气量组患者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炎症因子(TNF a和IL-8)显着升高。
Choi等比较了12ml/kg无PEEF和6ml/kg加用10cmH2O PEE两种通气策略,5小时机械通气后大潮气量组灌洗液显示促凝性改变。
另一项纳入了150例无ALI危重患者的随机对照研究将按预测体重给予10ml/kg与6ml/kg两种潮气量的效果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常规通气量组患者的血浆炎性因子显着升高。
非伤害性或所谓保护性的通气设定仍可能使原本健康的肺形成肺损伤,这样的提示也很重要。
一项使用小鼠“单次打击”所致VILI模型进行的动物研究显示:即使是最小的伤害性肺通气设置仍可引起符合肺损伤的生化和组织病理学改变。
对啮齿动物模型进行机械通气的另一项研究显示:仅仅90分钟的保护性通气后就会出现显着的基因表达(包括参与免疫和炎症反应的基因)。
这些改变是否对临床转归有影响,目前还不能确定。
ALI是术后发生呼吸衰竭最常见的病因且与降低的术后生存率有关。
Fernandez-Perez等在4000名患者中进行了一项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观察术中呼吸机设定与择期手术后发生ALI的情况。
研究显示:高危择期手术后ALI的发生率为3%。
与对照组相比,发生ALI的患者术后生存率明显降低且住院时间延长。
有趣的是,ALI的发生与术中气道峰压有关,而与潮气量、PEEP或吸入氧浓度无关。
一项特别观察危重患者发生ARDS的术中危险因素的回顾性队列研究发现:术中接受液体复苏大于20ml/kg/h的患者比接受液体复苏小于10ml/kg/h的患者发生ARDS 的可能性高3倍(OR , 95% CI =- , P =)。
在此项研究中,潮气量和血制品输注量与ARDS的发生无相关性,且大多数患者按理想体重设置潮气量为8-10ml/kg的通气,术中PEEP为0。
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Ventilator-induced Lung Injury ,VILI)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VILI)这一现象,在需要大量输血的手术中或者伴有肺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体外循环手术中VILI的发生尤其明显。
机械通气的不良效应由局限性炎症反应和炎性因子的全身性释放介导(生物学创伤)。
肺泡的周期性开合形成的机械牵拉可引起肺泡及血管内皮的炎症反应。
过度膨胀可引起作为参与炎症反应的多种基因表达过程及其他前炎症细胞因子上调过程的主要调节者的NF-B因子的核转位,多形核白细胞的浸润和激活似乎是机械牵拉诱导的炎症反应的关键。
缺血再灌注损伤和机械牵拉还可引起凋亡-坏死之间平衡的不良改变。
生物学创伤不仅持续加重肺损伤,而且这些炎性介质流出到体循环还会引起远隔器官发生功能障碍而导致发生严重的全身后果。
一项探讨VILI引起远隔器官损伤新机制的研究显示:机械通气可引起肾脏及小肠的内皮细胞凋亡,并且同时伴有器官功能障碍的生化改变。
对小鼠进行的损伤性机械通气发现:肺泡牵拉诱发的粘性分子不只见于肺部,也可见于肝脏和肾脏。
此外,机械通气后肺、肝、肾中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表达伴随着粒细胞聚集的增加。
这些研究部分解释了在ALI/ARDS中见到的远隔器官发生功能障碍以及优化通气策略在改善这种情况中的意义。
术中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ARDS患者应用的肺保护性通气策略是否适用于肺部健康患者的术中阶段呢一篇针对该问题的论文指出:目前仍缺少关于术中最佳潮气量、PEEP和肺复张应用的随机对照研究。
尽管关于转归方面的研究不足,但基于我们对机械通气作用的认知,围术期目标性应用保护性肺通气策略似乎是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