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研究中的_转向 李林波
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美学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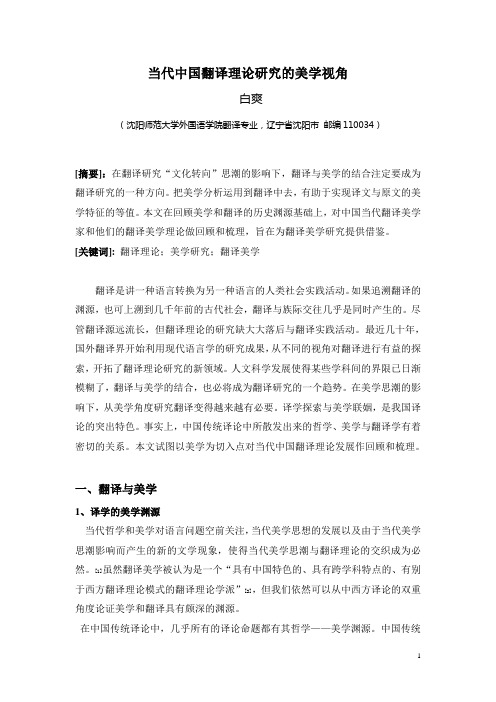
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美学视角白爽(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辽宁省沈阳市邮编110034)[摘要]: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思潮的影响下,翻译与美学的结合注定要成为翻译研究的一种方向。
把美学分析运用到翻译中去,有助于实现译文与原文的美学特征的等值。
本文在回顾美学和翻译的历史渊源基础上,对中国当代翻译美学家和他们的翻译美学理论做回顾和梳理,旨在为翻译美学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 翻译理论;美学研究;翻译美学翻译是讲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
如果追溯翻译的渊源,也可上溯到几千年前的古代社会,翻译与族际交往几乎是同时产生的。
尽管翻译源远流长,但翻译理论的研究缺大大落后与翻译实践活动。
最近几十年,国外翻译界开始利用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视角对翻译进行有益的探索,开拓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新领域。
人文科学发展使得某些学科间的界限已日渐模糊了,翻译与美学的结合,也必将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趋势。
在美学思潮的影响下,从美学角度研究翻译变得越来越有必要。
译学探索与美学联姻,是我国译论的突出特色。
事实上,中国传统译论中所散发出来的哲学、美学与翻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本文试图以美学为切入点对当代中国翻译理论发展作回顾和梳理。
一、翻译与美学1、译学的美学渊源当代哲学和美学对语言问题空前关注,当代美学思想的发展以及由于当代美学思潮影响而产生的新的文学现象,使得当代美学思潮与翻译理论的交织成为必然。
[1]虽然翻译美学被认为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跨学科特点的、有别于西方翻译理论模式的翻译理论学派”[2],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西方译论的双重角度论证美学和翻译具有颇深的渊源。
在中国传统译论中,几乎所有的译论命题都有其哲学——美学渊源。
中国传统译论大约始于1700年前的佛家论经书翻译,早在汉代佛经翻译,支谦就批评当时的翻译“其辞不雅”,道宣还提出过翻译须“风骨流便”,他们分别涉及翻译中的辞章美学与文艺美学,开创了我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源头。
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操控——以《浮生六记》两个英译本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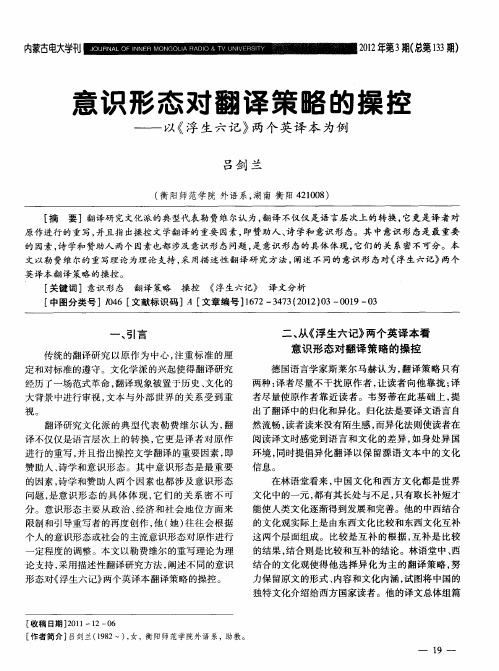
现了他妻子的纯洁、 美丽的形象, 也表达了对妻子深 深 的爱 。林语 堂对 之 进 行逐 字 翻译 , 留 了 中国独 保
特 的文 化 。在译 文 中 , 还 用 异 化 的 翻译 策 略保 留 林 了许多 其 他 的 中 国 特 有 的 文 化 词 汇 , “ 股 时 如 八
宗 教信仰 是每Leabharlann 国家文化 的重要 组成 部分 。原
文 中的“ 阳” 中 国佛 教 文 化 中重 要 的 术语 。 中 阴 是
文” “ 、 童媳 ” “ 明 1 、 马褂 ” “ 饨 ” , 、 清 3” “ 和 馄 等 向西
方 读者 介绍 了 中国特有 的文 化 。
国 的佛 教信徒 把世 人所 生存 的世 界 称 作 “ 阳间 ” 他 , 们相 信人死后 , 灵魂 会 在 另一 个 世界— — “ 间 ” 其 阴 继续 生存 。布 莱 克 将 之 翻 译 成 “h ehrw r f tente ol o d H ds ae”—— 一个 希腊神 话 中人死后 , 魂所 去 的地 灵 方 , 西方读 者认 为 中国古人 都相 信希腊 神话 , 让 曲解
绍 了“ 鸿案相庄 ” 这个 中文成语所涉及 的两个 主人公 ,
理解和接受 , 在对《 浮生六记》 的翻译过程中主要采 用 了归 化策 略 。他 以 自以为不 致 让 人含 混 的顺 序 ,
从句法翻译到语用翻译的转向——翻译研究语言学派的发展历程回顾

从句法翻译到语用翻译的转向——翻译研究语言学派的发展
历程回顾
马冬梅
【期刊名称】《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7(000)002
【摘要】许多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试图用语言学的观点来解释翻译研究中的一系列主要问题,并逐渐形成了翻译理论的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对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回顾了翻译学研究的语言学流派的发展历程,即由句法翻译发展为语义翻译并向语用翻译的转向,并探讨了这三个阶段的翻译研究方法的差异.
【总页数】2页(P53-54)
【作者】马冬梅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059
【相关文献】
1.翻译研究的“历史转向”还是历史研究的“翻译转向”?——《欧洲近代早期的文化翻译》述评 [J], 彭萍;
2.语言·文本·翻译--论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与独立的翻译学科的建立 [J], 唐姿
3.英汉谚语的语义、句法特征及语用翻译 [J], 许晖
4.当前语用翻译研究的问题与对策——语用学介入翻译研究的再思考 [J], 陈吉荣;
5.国内外语用翻译研究:回顾、述评与前瞻 [J], 李占喜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翻译理论与教学内容

翻译理论与教学内容(54学时)1.翻译理论部分(18学时)第一章翻译的方法(2学时)词的翻译,句子翻译,语篇翻译,文化问题,直译,意译,变译,转译,交际翻译。
阅读:《实用翻译教程(英汉互译增订本)》,冯庆华编著,外语教育,2008年《新英汉翻译教程》,王振国、李艳琳编著,,2008年《英汉翻译入门》,陈德彰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年《译艺——英汉汉英双向笔译》,陈文伯编著,世界知识,2004年《非文学翻译理论与》,李长栓编著,对外翻译出版,2004年《文学翻译原理》,张今、张宁著,,2005年《中外文学经典翻译教程》,王宏印编著,,2007年第二章翻译理论(4学时)传统翻译思想:古代佛经翻译思想。
传统翻译思想时期(近代西学翻译:马建忠,,严复,林纾)。
传统翻译思想转折时期(五四新文学时期:,瞿秋白,,成仿吾).传统翻译思想时期(四十年代:林语堂,朱光潜,艾思奇,贺麟,朱生豪,梁宗岱)。
传统翻译思想鼎盛时期(建国初期:矛盾,傅雷,钱钟书,焦菊隐)。
现代翻译思想:中西翻译思想的融合(王佐良,许渊冲,叶君健)。
翻译学科的建设。
阅读:《20世纪翻译思想史》,王秉钦编著,南开大学,2004年《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陈福康编著,外语教育,2003年《翻译的艺术》,许渊冲著,五洲传播,2006年《翻译通史》(五卷),马祖毅,教育,2006年《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上下卷),查明建著,教育,2007年《傅雷谈翻译》,怒安编,辽宁教育,2005年《新编当代翻译理论》,刘宓庆著,对外翻译出版,2005年《新时期翻译研究考察:1981—2003》,李林波著,西北大学,2007年《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研究》,严晓江著,译文,2008年《翻译家》,王友贵著,南开大学,2005年《翻译家周作人论》,刘全福著,外语教育,2007年《二十世纪翻译之争》,王向远、陈言著,百花洲文艺,2006年《重释“信、达、雅”——20世纪翻译研究》,王著,,2007年第三章西方当代翻译理论主要流派(6学时)翻译培训班学派,翻译科学派,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解构主义派,建构主义翻译学.阅读:《西方翻译理论精选》,申雨平编,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年《西方翻译理献阅读》,李养龙编著,世界图书出版,2007年《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谢天振,南开大学,2008年《当代翻译理论》(ContemraryTranslationTheories),Edwin Gentzler 编著,外语教育,2006年《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SusanBassnett编著,外语教育,2005年《语言、文化与翻译》(Language,Culture andTranslating),Eugene da著,外语教育,1993年《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吕俊、侯向群著,外语教育,2006年《西方翻译简史》,谭载喜编著,商务印书馆,2004年《西方翻译研究方:70年代以后》,李和庆、黄皓、薄振杰编著,,2005年《当代翻译理论》,郭建中编著,教育,2000年《当代翻译理论》,廖编著,教育,2001年《西方译论研究》,刘重德著,对外翻译出版,2003年《奈达翻译理论研究》,娟著,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年《新编奈达论翻译》,谭载喜编著,对外翻译出版,1999年第四章翻译研究(2学时)翻译研究的领域,翻译的理论模式,翻译研究的种类,问题、假设,各种变量的关系,选择分析变量,写研究报告,口头陈述报告,评估研究.阅读:《路线图——翻译研究方法入门》(The Map: A Beginner's GuidetoDoing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Jenny Williams &Andrew Chesterman著,外语教育,2006年《超越文化断裂》,Maeve Olohan著,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年《跨文化侵越》,Theo Hermans著,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年《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转向》,李菁著,译文,2009年《翻译研究:从教学到译论》,宋志平著,吉林大学,2008年《红译艺坛:翻译艺术研究》,冯庆华,外语教育,2006年《红楼译评:翻译研究集》,刘世聪,南开大学,2004年《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孙迎春编著,对外翻译出版,2004年第五章翻译过程(2学时)原作,译者,译品与读者,文体与翻译,翻译的单位,语言层次处理,篇章处理。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

后殖民主义翻译观
殖民文学与文化文本中隐含的政治霸权。
文本是一个缄默化的过程,通过翻译解释殖民过程中的话语暴力,再现殖民 化过程中弱势群体被缄默化的过程。
翻译是具有高度操控性的行文,原文和译文两个文本、源语与译语两个系统、 作者和译者等级少处于平等的地位。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后殖民主义翻译观
—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汇报人:哈尔滨 Troy 汇报时间:2020.10.23
“
”
contents
1.思想渊源
the Intellectual Context
2.代表性学说
Representative Theories
3.对译学的影响
Influence on Translatology
这些怀疑、适者生存的理念“颠覆”了上帝和一切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伦理结构, 而 后发展起来蕴涵“反叛”和“独立”的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等。胡塞尔 现象学为先导的经验主义对古希腊以来的“形而上学”的传统进行发掘的“后哲学” 思潮, 强调主体意识而非客观存在。这为我们理解文化转向“ 颠覆” 以前的译论提供 深层理据。
对译学的影响
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 因为它意味着 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 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 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 翻译即改写” 、“翻译即操纵”
对译学的影响
文化学与翻译学的兴起和繁荣促进了翻译的文化转向, 而文化转向在扩 展研究领域、开拓研究思路的同时, 也使翻译研究的边界日益模糊。
生理差异(gender,not sex) 社会差异(社会期望) 可以平等(推翻传统)
20世纪中国翻译界的一场论争与转型_兼论林纾与新文学家的译介观

上海翻译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2005No .3[收稿日期]2005-05-08[作者简介]王建开(1953-),男,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翻译系副系主任,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英汉对比、英美文学与文化.20世纪中国翻译界的一场论争与转型)))兼论林纾与新文学家的译介观王建开(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上海200433)[摘要]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文学界和翻译界发生了一场论争,关系到究竟应该/译什么0以及/为什么译0的问题。
这实际上是新、旧两种文学观念的交锋,致使翻译传统受到质疑,并由此确立了新的译介观和转型,强化了译介与国情相连的趋向,预示着从此之后的译介方向。
[关键词]中国翻译史;译介观论争;国情与翻译;林纾与新文学家[中图分类号]H 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358(2005)03-0061-05中国现代翻译史上,曾有一场关于/译什么0的持续讨论。
发生在20年代的这场重大讨论实质上涉及到/为什么译0的问题,它对之前的翻译传统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并提出了新的译介观)))申明译介对改变社会现实负有的责任,由此对之后的译介确立了方向。
归结起来,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向性的层面:一.倡导译介名著;二.译作的主题倾向与国情的关联。
这是新、旧两种文学旨趣的碰撞,预示着文学观的又一次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新译介观的形成。
结果是,在此之后中国翻译界在译介倾向上发生了转型,影响到随后整个20世纪中国译介史的走向。
一、倡导译介名著与林译批判五四以后,国内学界对晚清文学译介的趣味性倾向渐生反叛。
新文学的倡导者们积极投身于翻译,急欲以此改造社会并开辟创作的新传统。
受此目的的支配,他们在翻译实践中有一系列的举措。
最早的一项便是提倡译介名著,并且强调介绍(也说/绍介0,当时专指文学翻译)切合现实的作品。
在新文学家们对译介传统的批判中,作为20世纪初期中国译坛代表人物的林纾首当其冲,成了众矢之的。
奈达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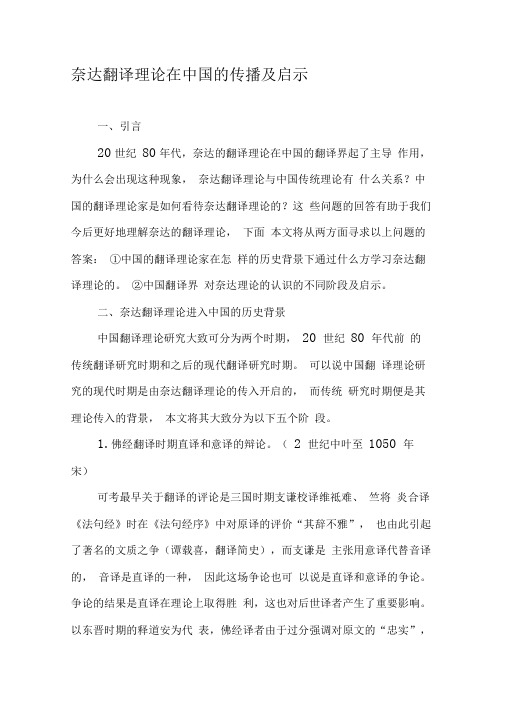
奈达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启示一、引言20世纪80年代,奈达的翻译理论在中国的翻译界起了主导作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奈达翻译理论与中国传统理论有什么关系?中国的翻译理论家是如何看待奈达翻译理论的?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今后更好地理解奈达的翻译理论,下面本文将从两方面寻求以上问题的答案:①中国的翻译理论家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通过什么方学习奈达翻译理论的。
②中国翻译界对奈达理论的认识的不同阶段及启示。
二、奈达翻译理论进入中国的历史背景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20 世纪80 年代前的传统翻译研究时期和之后的现代翻译研究时期。
可以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现代时期是由奈达翻译理论的传入开启的,而传统研究时期便是其理论传入的背景,本文将其大致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1.佛经翻译时期直译和意译的辩论。
(2 世纪中叶至1050 年宋)可考最早关于翻译的评论是三国时期支谦校译维祗难、竺将炎合译《法句经》时在《法句经序》中对原译的评价“其辞不雅”,也由此引起了著名的文质之争(谭载喜,翻译简史),而支谦是主张用意译代替音译的,音译是直译的一种,因此这场争论也可以说是直译和意译的争论。
争论的结果是直译在理论上取得胜利,这也对后世译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东晋时期的释道安为代表,佛经译者由于过分强调对原文的“忠实”,导致大量字对字的直译作品的出现,可读性很低,“直到公元401 年,鸠摩罗什到长安主持佛经翻译工作这一状况才得到改善”,鸠摩罗什反对直译,他指出如果佛经从梵语译入汉语后让读者觉得像在吃别人嚼过的东西,那么即便保留了原文意思,也是索然无味甚至让人厌恶的。
(马会娟,2003:27)鸠摩罗什的翻译可读性强但有时对原文的修饰过多,与之相比,唐朝的玄奘则成功地处理了直译和意译的关系,这得益于他优秀的双语能力。
玄奘之后佛经翻译开始走下坡路,没再出现什么值得讨论的论述。
总的来说,关于直译和意译的争论一直未有让人满意定论,到奈达理论传入中国后,争论的焦点从文本转向了读者。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征文名单(一)

点击量:295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十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征文通告在各主要外语媒介刊载以后,组委会收到了海内外许多学者及研究生的征文论文(含部分论文摘要)。详情请见附件名单(截止2012年5月10日)。
所收到论文将经过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在杭州举行的审稿会(2012年5月下旬)审阅后,拟在6月份发出正式会议邀请函。
张青青
在读硕士
重庆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概念隐喻在汉语经济语篇中的体验性研究
刘雪莲
讲师
中国地质大学外国语学院
格式塔视角下的语篇翻译
仉嘉粒
在读硕士
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公示语翻译的互文性视角
田希波
讲师
山西张掖河西学院外国语学院
汉、英、法、日语中副词修饰副词现象及成因探析
王立娟
徐以中
汉英顶真的理论基础和翻译策略
许峰
副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外语学院
殷甘霖
在读硕士
中国地质大学外语学院
汉英对比视界中的矛盾修辞法哲学底蕴疏议
孙毅
副教授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编辑部;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
王晋秀
在读硕士
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汉英多义词词义引申方式的认知对比——以“烛”与CANDLE的文化义项为例
王宇晨
讲师
南京解放军理工大学外训系
俞德海
讲师
福建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
解析中国文化外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引发的思考--如何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周锋
在读博士
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科学系
方锃华
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精神分析与译者心理研究
张洁
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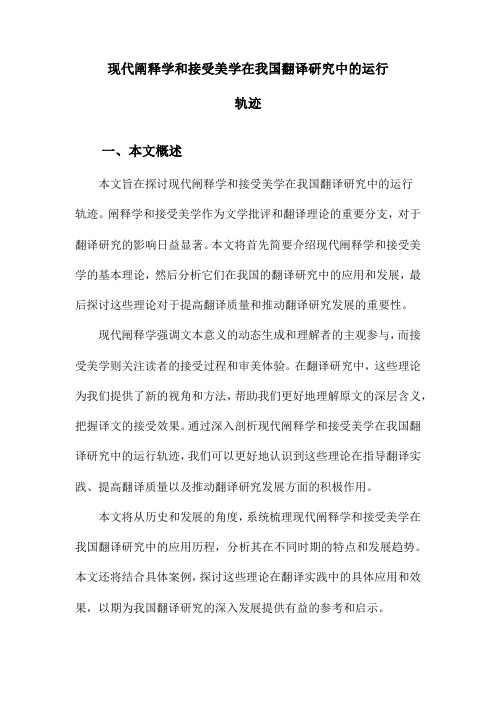
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
阐释学和接受美学作为文学批评和翻译理论的重要分支,对于翻译研究的影响日益显著。
本文将首先简要介绍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基本理论,然后分析它们在我国的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和发展,最后探讨这些理论对于提高翻译质量和推动翻译研究发展的重要性。
现代阐释学强调文本意义的动态生成和理解者的主观参与,而接受美学则关注读者的接受过程和审美体验。
在翻译研究中,这些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深层含义,把握译文的接受效果。
通过深入剖析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这些理论在指导翻译实践、提高翻译质量以及推动翻译研究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本文将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系统梳理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历程,分析其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本文还将结合具体案例,探讨这些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和效果,以期为我国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二、现代阐释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现代阐释学,源自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以来,对我国的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一理论主张文本的多元解读和读者主体性的发挥,为我国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在我国翻译研究的初期,现代阐释学主要被用于解决翻译中的理解和解释问题。
翻译被视为一种阐释活动,译者作为读者和解释者,通过自身的理解和诠释,将原文的意义转化为译文。
这一阶段,阐释学的主要关注点在于译者的主体性和文本的开放性,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现代阐释学开始关注翻译中的接受问题。
接受美学,作为阐释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强调读者的接受和反应在翻译中的重要性。
在这一阶段,翻译研究不再仅仅关注译者的主体性,而是将读者的接受和反应纳入考虑范围。
2022年全国新高考Ⅱ卷语文真题深度解析+答案解析(附后)

2022年全国新高考Ⅱ卷语文真题深度解析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试题。
材料一:中国学者进入典籍英译领域时间相对较晚,据现有汉学书目统计,中国典籍译本绝大多数是由西方汉学家或独立、或在中国合作者帮助下完成的。
传教士以降的西方译者为中国典籍的异域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以往的西方译者翻译中国文化典籍时,大多采取迎合译语读者的翻译策略,翻译过程中曲解、误译中国文化之处比比皆是。
此外,中国古代经典文本的语言具有语义的浑圆性、语法的意合性和修辞的空灵性这三大特点,使得绝大多数外国学习者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触及中华文化的内核。
然而,典籍英译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世界介绍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让西方了解真正的中国。
我们应当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典籍翻译实践和接受之间的窘况与差距,从典籍翻译大家身上汲取翻译的智慧,获取前行的指导和力量。
在这方面,对杨宪益、戴乃迭(英国籍)合译的与英国人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译本的比较,是一个值得我们静下心来认真思考的课题。
这两个译本于20世纪70年代出版,三位译者皆因此获得巨大声誉,也同时掀起了翻译界此后对两种译本经久不息的对比研究热潮。
在这过程中,我们应深入了解中国典籍的外译事实,客观分析两种译本的优长与不足,将中国的本土经验和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相结合,取其精华,让中国的翻译研究与实践在传承和发展的良性循环中获得升华,在实践中不断培养和提高我们讲述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时代能力。
(摘编自辛红娟《中国典籍“谁来译”》)材料二:翻译思想是决定译者翻译行为和翻译结果的主因,只有通过其翻译思想,读者才能理解其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策略,也才能对这些策略所产生的译文进行更客观的评价。
从霍克思的译本中可见,他对原文采取了大多时候“忠实不渝”、间或背信弃“意”的态度。
为证此言,举个背信弃“意”的例子。
《红楼梦》第一回中,曹雪芹用了一个较长的段落交代自己的写作目的,并说明选用“甄士隐”和“贾雨村”作为人物姓名的缘由,为读者理解整部小说进行铺垫。
理念转变,技术先行——记2012年暑期全国翻译专业师资翻译与本地化技术、项目管理培训

第10卷第3期2013年3月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Mar.2013Vol.10No.32012年7月26日至8月3日,中国翻译协会、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教学协作组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了第二次全国翻译专业师资翻译与本地化技术、项目管理培训。
笔者有幸参加了此次培训,深刻感受到翻译技术所带来的巨大产业力量,认为开展翻译的产业视域研究,树立动态的翻译质量观,意义重大。
一、翻译的产业视域新认识:翻译产业学传统翻译研究大多以翻译文本为基石,从语言学、文艺学、哲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等视角研究语言符号的转换、接受与认知机制(杨平,2012:9),而明确指出从产业的视域认识翻译本体,审视翻译客体,分析翻译现象,则所见不多。
本次培训从产业的视角审视翻译,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使文本维度、翻译过程、译者地位等诸多翻译概念都有了全新的诠释。
知识传播的数字化、网络化与影像化,使翻译的“文本”意义呈现出“多维多模式”,除了线性的语言符号外,“文本”还包括声音、图像、空间等因素(张莹,2012:16),以网站、软件、多媒体影音内容为代表的新型“文本”成为翻译的对象(穆雷,2012:13)。
翻译的产业化发展与升级,使预翻译、译后编辑与排版、翻译项目管理、翻译质量监控与评估、翻译软件与工具、翻译记忆与语言资产、语料库对齐与检索、术语库与术语管理、在线翻译、众包翻译、远程口译服务平台、云翻译或云计算的多语在线服务平台、语联网等纷纷进入翻译的不同环节,影响着翻译的每个过程(钱多秀,2011:目录;韦忠和,2012:71-74)。
在产业化进程中,翻译的主体(译者)也呈现出职业化、专业化与网民化,翻译正产生出诸多全新的课题,概念得到不断地延伸与扩展,研究领域也随之得以拓展与深化。
修改

翻译研究的几大主流研究范式一.语文学研究范式关于19世纪50年代之前的论文及专著数量较少,此处暂不做列举。
二.语言学范式这一类的文献可分为几类。
第一类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的宏观概述[1].冯奇万华,对立与统一排斥与互补__翻译的语言学视角【J】.上海翻译,2012(4).[2].莫娜.贝克尔,李尚杰(ed.),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模式与方法【J】. 外语研究,2005(3).[3].吕俊,建构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J】.外语学刊,2004(1).[4].王秀丽.梅涛,国外语言学在中国的译介及其影响(1911-1949)【J】.法国研究.2013(2).[5].李林波,中国语言学模式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回顾【J】.外语教学.2007(V ol.28,No.5).[6].赵践,语言学视角下的中国翻译理论透视【N】.辽宁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V ol.9,No.4).[7].张柏然,试析翻译的语言学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6).[8].董赛金,语言学及其与翻译的关系【J】.译苑.2011(1).[9].隋荣谊,语言学方法【J】.翻译理论.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Publishing House国外翻译界.2011(4).[10].吕俊,语言学的语言研究能替代翻译学中的语言研究吗?【J】. 山东外语教学.2011,(5).[11].欧爱萍,浅谈语言学对翻译学科的影响【J】.广角镜.2012(7).[12].张荣臻,浅谈语言学与翻译【J】. 甘肃科技.2009(V ol.25 No.10).[13].梁琦,许钧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方面【J】.科技信息.2010(28).[14].何妍,语言学派的传统与现代语言学阐释模式透视【N】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15].唐姿,语言.文本.翻译___论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与独立的翻译学科的建立.【J】.山东外语教学。
《翻译研究的转向——新范式还是视角转换》评介

,
。
,
,
,
。
r
e
p l in
d P 叩 c r s fr e : S e le e
。
o
m th
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e
te
d Pa p e
E S T C 皿g r e s s T r s r o m th e Ta f r
,
r
s a 即 l
t i
o n
n s
la t io
n
作
国 内 引 进 她 的 专 著 有 《翻 译研究
S t u d i e s : A n l城 e r d i s e i S t u d ie s C o n g r e s :
-
T r — 综 合法 》 ( a
等著 o l t i二 a
-
诞生 介绍 了从 德 国 很 涅 土 义 叼 朋 到 上世 纪 8 0 年 代 以 前 的 翻 译理论 作者 援引 勒菲 佛 尔 的分类方法 将 为 翻 译理 论 发展 做 出 的 贡 献 的主 要人 物分 为 四 个 类 别 先驱 先锋 大 师和 学徒 并逐 一 展 开 论述 揭 示 翻 译 文化转 向 发生肇 始 期 的前 兆 霍 恩 比 在第 一节 中列举 出 几位 e e e e 。。 l a e h 翻 译 理 论先 驱 包括 歌 德 ( o G , h ) 施 莱 尔 马 赫 厂S h l i e S ) 诺 瓦 利斯 ( N v o i l ) 等 浪 漫学 派 的翻 译 见 解 并 指 出 应 该 结 a 合时代 背 景来解读 这 一 时期 的浪 漫学 派 翻 译 理 论 尼 采 本雅 z e r n爪o s e 明 和 罗 森茨 威 格 ( F a n wi 动三 位德 国 近 代 学 者 也 作 为 伟大先 驱 在 本节 介绍 对 于 德 国 以 外 的先 驱 作 者还 简 单 提
换言之翻译第三章讲义西外李林波

换言之翻译第三章讲义西外李林波(总5页)--本页仅作为文档封面,使用时请直接删除即可----内页可以根据需求调整合适字体及大小--5 Textual equivalence: thematic and information structuresText: The verbal record of a communicative event; an instance of language in use rather than language as an abstract systemof meanings and relations. (p111)Cohesion: 衔接 A network of lexical, grammatical, and other relations which provide links between various parts of a text, andwhich organize and create a text; a surface relation whichconnects together the actual words and expressions that wecan see or hear.(p180)[The connection between successive sentences in texts,conversations, etc., in so far as it can be described interms of specific syntactic units.]Coherence: 连贯 A network of relations which organize and create a text; the network of conceptual relations which underliethe surface structure. (p218)[The way in which the content of connected speech or texthangs together, or is interpreted as hanging together, asdistinct from that of random assemblages of sentences.]Theme: What the clause is about. (p121)Rheme: What the speaker says about the theme. (p122)Communicative dynamism(交际动力):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element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cation. (p161) . Parts of a sentence representing given information are said to have the lowest degree of communicative dynamism (or CD), . the amount that, in context, they communicate to addressees is the least.A general overview based on the Hallidayan approach to information flowThematic structure: theme and rhemeTheme: what the clause is aboutFunction: 1) connecting back to previous stretchesof discourse— orientation2) connecting forward and contributing tothe development of later stretches—departureRheme: what the speaker says about the theme—the goal ofdiscourseThe most important; what the speaker wants to conveyThe structure of a message in every clause—It sayssomething (the rheme) about something (the theme)(a) Thematic analysis can be represented hierarchically.(b) Some elements are not part of the basic thematicstructure.(c)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me and rheme is more orless identical to the traditional distinction betweensubject and predicate.Thematic structure: grammaticality vs acceptabilitySubject-predicate——grammaticalityTheme-rheme——acceptabilityThematic structure: text org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thematic patterningThematic structure: marked vs unmarked sequences◆Relationship between meaning, choice, and markedness:1). Choice—Meaning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choice, sothat the more obligatory an element is, the less markedit will be and the weaker will be its meaning.2). Expectedness—The less expected a choice, the moremarked it is and the more meaning it carries; the moreexpected, the less marked it is and the lesssignificance it will have.◆ The degree of markedness is determined by:1) Frequency —The more frequent an element in themeposition, the less markedness it has.2) Extent of mobility—The more mobile an element in theclause, the more marked it is as the theme. (see‘Choice’)◆ The function of marked theme:A marked theme is selected specifically to foreground aparticular element as the topic of the clause or itspoint of departure.Local prominence (marked theme) vs overall discourseprominence (rheme)◆ Three main types of marked theme in English:(a) Fronted theme(b) Predicated theme—it clause (implying contrast)(c) Identifying theme—wh- clause (implyingcontrast)A brief assessment of the Hallidayan position on theme※Marked structure and translation1) Marked SV (VS)Beneath the emblem on a table stood a big box.Translated version:标志下面有张桌子,上面立着一个大盒子。
中国翻译研究中的_转向 李林波

[收稿日期]2011-03-17[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0XYY002;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7J005Z[作者简介]李林波(1978-),女,陕西米脂人,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研究。
20世纪末是各学科集中发生“转向”的时期。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已成常谈,其他学科的各种新转向也相继迭出,如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哲学的人文转向、心理学的文化转向等等。
在西方翻译研究中,继20世纪5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之后,80年代又出现了文化转向,近年来又有社会—心理学转向之说。
在中国翻译研究中,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分别成为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及20世纪末的两个主要动态。
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所发生的历史背景不同,各自的功用与特色也截然不同。
但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的翻译研究中,语言学转向都是翻译研究“科学化”诉求的结果,文化转向则是顺应翻译研究“跨学科”需求的必然趋向。
本文将采用实证性研究方法,针对中国翻译研究中部分标志性研究成果,回顾两次转向的背景、原因、动力及具体表现。
一、“转向”概述在本文中,“转向”指的是一种在研究模式上的显著变化,标志着一种新的、力量强大研究模式的形成。
中国翻译研究中的转向在方向上与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轨迹基本一致,即先有语言学转向,之后出现文化转向。
但在时间上却晚于西方,原因一方面在于西方译学是转向的先行者,而中国译学是后继者,另一方面在于中国学界在翻译研究领域基础较弱、创新性仍嫌不足。
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奈达、费道罗夫等人把现代语言学的‘科学’概念引入翻译研究”[1]287,这是西方翻译理论从古典和近代的语文学翻译研究向语言学转向之后的第一次研究飞跃。
以奈达、纽马克、维奈和达贝尔内、卡特福德等理论家为代表的研究者以“对应”或“对等”、“转换”等为核心概念进行翻译研究。
之后,哈蒂姆与梅森将语篇引入翻译研究,奈达也将语境在翻译中的地位予以更多的强调,格特用关联理论来解释翻译中的一系列问题,这些研究将语言学各领域的成果都加以应用,使得语言学成为翻译研究的理论来源与学科基础。
翻译研究的发展回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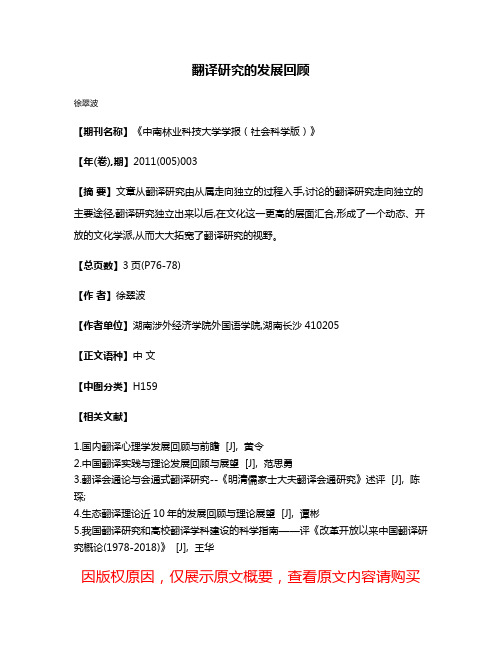
翻译研究的发展回顾
徐翠波
【期刊名称】《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05)003
【摘要】文章从翻译研究由从属走向独立的过程入手,讨论的翻译研究走向独立的主要途径,翻译研究独立出来以后,在文化这一更高的层面汇合,形成了一个动态、开放的文化学派,从而大大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总页数】3页(P76-78)
【作者】徐翠波
【作者单位】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20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159
【相关文献】
1.国内翻译心理学发展回顾与前瞻 [J], 黄令
2.中国翻译实践与理论发展回顾与展望 [J], 范思勇
3.翻译会通论与会通式翻译研究--《明清儒家士大夫翻译会通研究》述评 [J], 陈琛;
4.生态翻译理论近10年的发展回顾与理论展望 [J], 谭彬
5.我国翻译研究和高校翻译学科建设的科学指南——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1978-2018)》 [J], 王华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关注翻译研究三个“转向”推进翻译学科专业建设

作者: 庄智象[1];戚亚军[2]
作者机构: [1]上海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上海200083;[2]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浙江湖州313000
出版物刊名: 外语教学
页码: 90-94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6期
主题词: 翻译学科建设;实践转向;文化转向;过程转向;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
摘要:作为当前高校外语学科谱系中的“朝阳产业”,翻译学科的专业建设任重道远。
本文针对翻译学科所面临的现实挑战,指出翻译研究应积极关注三个转向,即翻译人才培养的实践转向、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与翻译教学实施的过程转向,以期在理论与实践上为翻译学科专业建设做好顶层设计与建基打底,从而更好达成高素质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的专业教育目标。
《文心雕龙·原道》三种英译文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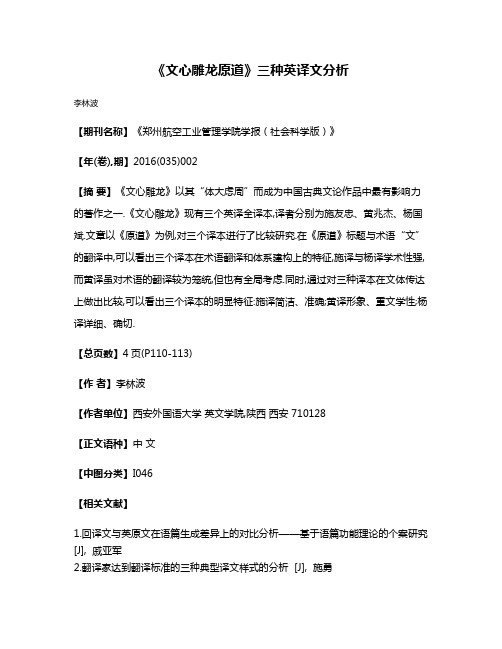
《文心雕龙原道》三种英译文分析
李林波
【期刊名称】《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6(035)002
【摘要】《文心雕龙》以其“体大虑周”而成为中国古典文论作品中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文心雕龙》现有三个英译全译本,译者分别为施友忠、黄兆杰、杨国斌.文章以《原道》为例,对三个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在《原道》标题与术语“文”的翻译中,可以看出三个译本在术语翻译和体系建构上的特征,施译与杨译学术性强,而黄译虽对术语的翻译较为笼统,但也有全局考虑.同时,通过对三种译本在文体传达上做出比较,可以看出三个译本的明显特征:施译简洁、准确;黄译形象、重文学性;杨译详细、确切.
【总页数】4页(P110-113)
【作者】李林波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2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046
【相关文献】
1.回译文与英原文在语篇生成差异上的对比分析——基于语篇功能理论的个案研究[J], 戚亚军
2.翻译家达到翻译标准的三种典型译文样式的分析 [J], 施勇
3.《文心雕龙·原道》文本分析与再标点 [J], 蔡鑫泉;
4.《文心雕龙·原道》文本分析与再标点 [J], 蔡鑫泉
5.运动事件框架下《画皮》三种译文的比较分析 [J], 庄娇娇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收稿日期]2011-03-17[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0XYY002;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7J005Z[作者简介]李林波(1978-),女,陕西米脂人,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研究。
20世纪末是各学科集中发生“转向”的时期。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已成常谈,其他学科的各种新转向也相继迭出,如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哲学的人文转向、心理学的文化转向等等。
在西方翻译研究中,继20世纪5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之后,80年代又出现了文化转向,近年来又有社会—心理学转向之说。
在中国翻译研究中,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分别成为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及20世纪末的两个主要动态。
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所发生的历史背景不同,各自的功用与特色也截然不同。
但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的翻译研究中,语言学转向都是翻译研究“科学化”诉求的结果,文化转向则是顺应翻译研究“跨学科”需求的必然趋向。
本文将采用实证性研究方法,针对中国翻译研究中部分标志性研究成果,回顾两次转向的背景、原因、动力及具体表现。
一、“转向”概述在本文中,“转向”指的是一种在研究模式上的显著变化,标志着一种新的、力量强大研究模式的形成。
中国翻译研究中的转向在方向上与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轨迹基本一致,即先有语言学转向,之后出现文化转向。
但在时间上却晚于西方,原因一方面在于西方译学是转向的先行者,而中国译学是后继者,另一方面在于中国学界在翻译研究领域基础较弱、创新性仍嫌不足。
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奈达、费道罗夫等人把现代语言学的‘科学’概念引入翻译研究”[1]287,这是西方翻译理论从古典和近代的语文学翻译研究向语言学转向之后的第一次研究飞跃。
以奈达、纽马克、维奈和达贝尔内、卡特福德等理论家为代表的研究者以“对应”或“对等”、“转换”等为核心概念进行翻译研究。
之后,哈蒂姆与梅森将语篇引入翻译研究,奈达也将语境在翻译中的地位予以更多的强调,格特用关联理论来解释翻译中的一系列问题,这些研究将语言学各领域的成果都加以应用,使得语言学成为翻译研究的理论来源与学科基础。
在中国情况类似,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指的是以语义学、语用学、篇章语言学等现代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翻译研究,其肇起缘于1979年之后奈达、纽马克等人翻译理论的译介,在中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在90年代,一方面随着英汉语比较研究的大规模、深层次展开,语言学各个层次的理论———语义学、句法学、语用学、篇章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中国翻译研究中的“转向”李林波(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1)[摘要]中国翻译研究中出现过两次显著的转向: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及始于20世纪末的文化转向。
语言学转向顺应了中国翻译研究“学科化”与“科学化”的需求,是对传统翻译研究经验性、零散性不足的克服;文化转向顺应了中国翻译研究“跨学科”与“拓展”的需求,是对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微观性、静态性局限的超越。
语言学转向的实质是学科化,文化转向的实质是学科融合,二者都是中国翻译研究在不同阶段所必需经历的过程。
[关键词]中国翻译研究;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2)02-0085-05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3月第39卷第2期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Mar .,2012Vol.39No.2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9卷86都成为进行英汉语比较以及解释英汉互译实践的理论工具。
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第一批及随后相继而出、接受过系统的语言学及翻译训练的研究者队伍的成长,语言学模式的翻译研究逐渐成为中国翻译界的主要研究模式。
关于文化转向的问题比较复杂。
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为其主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论文集撰序———“序言:普鲁斯特的祖母与一千零一夜:翻译学的‘文化转向’”(Introduction:Proust’s Grandmother and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The“Cultural Turn”in Translation Studies),“文化转向”一说正式确立。
但文化转向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已在西方开始,80年代发展至巅峰,90年代已入多元拓展期。
对于“文化转向”的说法存在一些争议,有人认为“文化”一词模糊了研究派别的特征与区别,也有人认为研究模式之间的差别被“转向”之说夸大。
蒙娜·贝克认为:“我认为这是那些企图建立‘学术王国’的人提倡和推销的一个比喻。
有些人是想表明他们在做一些全新的、创新的事情等等,所以他们将这些事情称作‘转向’,并将自己和相关朋友放到这些‘转向’当中。
”[2]12她并不认为翻译研究中存在任何足以被称作“转向”的变革。
显然,关于“转向”的讨论涉及到学术划界与命名的问题,但如将重心置于研究路线的性质上,“转向”的说法是有据可依的。
以“文化转向”而论,从研究内容和方法上来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描述译学、多元系统论等新趋势反映了一种学科融合的趋向,和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相比具有跨学科、超文本、综合的显著特点,因此,如给其命名以示与语言学派的区别,则“文化转向”虽失之模糊,但仍不能不说是当前一个较为恰当的名称。
在中国,翻译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西方文化模式翻译理论的译介为媒介开始发端,在世纪之交和本世纪前几年成为中国翻译研究界的一种热点模式。
二、语言学转向一切改变都缘于对现状的不满。
建立在中国古典文论与美学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译论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已经达到巅峰。
在其原有的理论基础、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之下,已难有突破。
经过古典佛经译论、近代社科译论、现代文学译论的发展,当代译论已很难在已有的“信达雅”、“神似”、“化境”基础之上创新,只是一遍又一遍的循环阐释。
“在过去八十年里,我国的翻译理论始终是朝着同一个方向,那就是‘重神似不重形似’,以便达到翻译上的‘化境’”[3]964。
此时,研究者们已经认识到了传统译论研究陷入举步维艰之境,却不得革新的方法、动力与契机。
董秋斯总结说:“我们有一千几百年历史的翻译工作走的并非直路,有时简直是兜圈子。
”[4]601传统译论中虽有其宏观或思辨的部分,但大多都不离“信”与“顺”或类似命题的讨论。
围绕这些讨论产生了诸多的翻译标准,但其弊病正如季羡林所谈文艺批评:“中国文论讲究韵,即神韵,讲求味。
……我们的这些名词,包括司空图的《诗品》,说不清楚。
一看就懂,一问就糊涂。
……有点玄乎,各有各的理解。
”[5]92中国传统译论的局限性注定翻译研究在原有的研究方法与模式之上无法突破。
对传统译论研究方法的批评并不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50年代就已有人指出。
如董秋斯指出传统翻译研究一千多年进步缓慢的原因在于:“因为它不是在自觉的努力下得到的,而是在别种改革的推动下(例如文体的改革)得到的。
也因为过去科学不发达,从事翻译工作的人,不能运用科学方法,总结前人的经验,发见进展的法则,而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4]602。
中国传统翻译研究之所以脱离不了经验性与随意性,根本原因在于翻译研究本身的边缘性。
20世纪80年代之后翻译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快速的发展,根本原因在于翻译学科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域,而不是游离于文学研究的边缘。
这种改变的契机,一在于学科本身的发展,二在于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促进。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学术界开始复苏。
中国翻译研究在资源、环境、人力等诸方面都获得前所未有的有益条件,此时译介西方翻译理论,能够被给予最及时、最迫切的关注,变革翻译研究不仅必须,而且可能。
1987年,谭载喜在与奈达合撰的论文中对翻译做出了如下定义:“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科学。
它通过对翻译的性质、过程、方法等方面进行客观的、科学的描写,提出系统的翻译理论,推动翻译的实践”[6]24。
这个定义中包含了几点非常重要的信息:(1)明确使用“翻译学”这个名称,而不是“翻第2期李林波:中国翻译研究中的“转向”87译科学”或“翻译研究”。
尽管“翻译学”在此并非中国译界首次提到,但其在学科建构意义上的使用,应该是较早的;(2)强调翻译研究要“客观”、“科学”。
这是对翻译研究的理性要求,“科学”就要“客观”,要反映出规律;(3)理论要“系统”。
系统的理论是学科建构的核心。
“翻译学”的这个定义是一种典型的“科学化”定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努力的方向,也正是语言学派翻译研究成为主流研究模式的主要原因。
1982年,包振南在介绍卡特福德的理论时,文章使用了“开拓翻译理论研究的新途径———介绍卡特福德著《翻译的语言学理论》”[7]68~73这一标题。
“开拓新途径”正是译介国外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意义所在。
以杨自俭所编《翻译新论(1983-1992)》(以下简称《新论》)为例,《新论》在时间上可以看作是罗新璋主编的《翻译论集》的延续,但其中所辑论文在研究方法、理论、研究对象上却与《翻译论集》有非常大的差别。
尤其是《新论》第二编“译学研究”所收集的27篇文章中,有过半或探讨翻译学的体系、构建,或将语言学理论作为探讨翻译问题的理论依据与基础。
其中,如谭载喜的“试论翻译学”、刘宓庆的“论中国翻译理论基本模式”、杨自俭的“关于建立翻译学的思考”等文章,都具有构建学科、建设理论体系的开拓性性质,可以被视作中国翻译学科建设的先锋性话语。
杨自俭先生在《新论》前言“论我国近期的翻译理论研究”一文中认为:“中国的翻译学理论体系已于1988—1989两年间初步构建问世。
笔者孤陋寡闻,只能举出两个证据。
一是黄龙的《翻译艺术教程》(1988),二是刘宓庆的《西方翻译理论概评》(1989)和《现代翻译理论》(1990)。
”[8]6《翻译艺术教程》是一部中国传统翻译美学、艺术论的集大成者,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总结和提升。
而刘宓庆的两项成果则意味和标志着中国翻译研究重点和方法的转向。
以系统性与全面性而论,刘宓庆的《现代翻译理论》当之无愧为中国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研究的开拓性、奠基性成果。
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的翻译理论研究尝试性转向在1990年以刘宓庆的《现代翻译理论》的问世走出了标志性的一步。
此后,随着专业研究队伍的成长与壮大、翻译学科的逐渐发展、以及语言学研究自身的成熟,语言学模式的翻译研究成果不断增加。
不仅语义学、句法学等语言学理论被应用于翻译研究,90年代中期之后,篇章语言学、语用学也与翻译研究进行了比较深层次的结合,关联理论也在90年代末在中国翻译研究中得到了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