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笔下的“人性”——以《萧萧》为例
《萧萧》读书笔记8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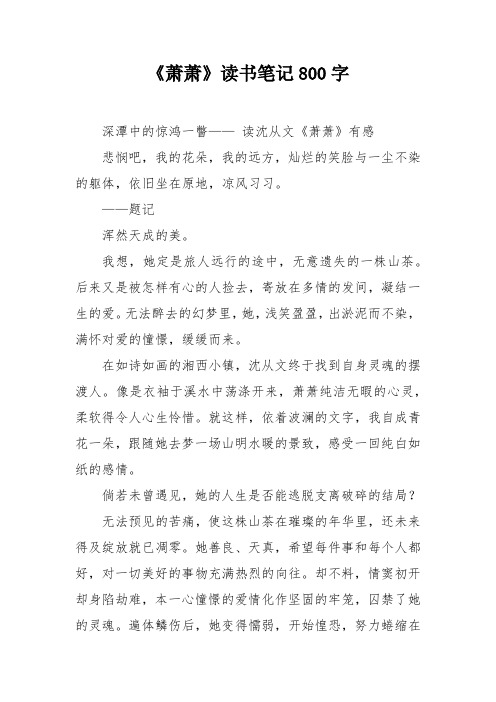
《萧萧》读书笔记800字深潭中的惊鸿一瞥——读沈从文《萧萧》有感悲悯吧,我的花朵,我的远方,灿烂的笑脸与一尘不染的躯体,依旧坐在原地,凉风习习。
——题记浑然天成的美。
我想,她定是旅人远行的途中,无意遗失的一株山茶。
后来又是被怎样有心的人捡去,寄放在多情的发间,凝结一生的爱。
无法醉去的幻梦里,她,浅笑盈盈,出淤泥而不染,满怀对爱的憧憬,缓缓而来。
在如诗如画的湘西小镇,沈从文终于找到自身灵魂的摆渡人。
像是衣袖于溪水中荡涤开来,萧萧纯洁无暇的心灵,柔软得令人心生怜惜。
就这样,依着波澜的文字,我自成青花一朵,跟随她去梦一场山明水暖的景致,感受一回纯白如纸的感情。
倘若未曾遇见,她的人生是否能逃脱支离破碎的结局?无法预见的苦痛,使这株山茶在璀璨的年华里,还未来得及绽放就已凋零。
她善良、天真,希望每件事和每个人都好,对一切美好的事物充满热烈的向往。
却不料,情窦初开却身陷劫难,本一心憧憬的爱情化作坚固的牢笼,囚禁了她的灵魂。
遍体鳞伤后,她变得懦弱,开始惶恐,努力蜷缩在自我世界的小小角落里,才找寻一丝的安慰。
她把青春献给正牙牙学语的小丈夫,献给蒙昧的世俗,更献给无声的岁月。
在那个年纪承受她本不应该承受的苦难,萧萧乏力的抗拒令人揪心。
她本和其他的女孩子无异,可天不遂人愿,生活逼迫她凭借内心的力量来撑起一整片生命的天空,沈从文称之为——“命运”。
或许一开始,会觉得萧萧的故事是个偶然。
可当她抱着新生的毛毛,迎接儿子的童养媳,我有种恍如隔世之感,那熟悉的场景与多年前夫家迎娶萧萧如出一辙。
我突然明白,所谓的偶然是谬论,生命的下一个轮回正在悄然上演。
仿佛一粒石子落入无底的深潭,萧萧一生的喜乐悲欢不过是深潭中的惊鸿一瞥。
在人性与制度的对抗中,沈从文传达人性的胜利。
这样的对抗,都是不自觉的,甚至带些自我抑制。
在这些古老的村庄里,沈从文不动声色地搭建他心中永恒的“人性希腊小庙”,渴求“一个人的村庄”,来安放他的灵魂。
而萧萧,如同暖风一般的女子,路过他的心,留下深浅不一的烙印。
封建女性的悲凉命运——再读沈从文《萧萧》中的女性

6 2
S
警 謦霸Hale Waihona Puke 命 聱蓐— —i
再读 沈从 文《 萧萧》 中的女性
● 王海 妹
沈从文是我 国近现代 一位著 名的文 学家 , 出生 于湘西凤凰县 。他 的家乡荒 僻但 风光如 画 、 富有传 奇 色彩 , 如今 已成为著 名 的旅 游圣 地。在 旧中国战 火蜂 起 的动 荡 局 势 下 , 从 文 坚 持 纯 文学 的立 场 , 沈 从 人性 的角度 , 以散文化 的笔 法写小 说。他用作 品建 造 了一 个 神 奇 的 “ 西 世 界 ”这 个 世 界 摒 弃 了 世 间 湘 , 的丑 与 恶 , 处 弥 漫 着 善 与 美 的 梦幻 色彩 , 满 了对 处 充 生命野性 的歌颂 , 一如 乱世 中的世外 桃源 。尤 其是 文 中的一个个美丽 、 纯真的女性 形象 , 更是寄托了作 者美 的理想 。但理想 的背后却有作者无法言说的悲 哀, 因为现实毕竟是龌 龊而残 酷的 。下 面结合他 的 短篇小说《 萧萧》 来分析其作 品中女性 的命运 。 《 萧萧》 讲述 了一个名 叫萧萧的乡下女孩子悲凉 的命运 。她 从小 是孤 儿 , 寄人 篱 下 , 后被 卖 作童 养 媳, 出嫁时丈夫不到三岁。情窦初开 时 , 家里的一个 雇 工 敲 开 了她 的心 , 幸 的 怀孕 使 萧 萧 陷入 困境 , 不 几 乎 被 沉 潭 、 卖 , 因她 生 下 儿 子 才 捡 回一 条 命 。 十 发 只 多 年 后 她 的私 生 子 又 娶 进 一 个 “ 萧萧 ” 。 童养媳买来有两大用处 : 一是劳力 , 二是传宗接 代 。萧萧是从来不被 当人看的 , 时被卖作童养媳 , 幼 到 后 来 的劳 力 和 工 具 , 只是 一 个 物 的存 在 , 一 件 她 是 可 以买卖 的物 品, 是一 件具 有价值 的工具 。 萧萧生活在黑 暗、 落后 的封建社会 家庭 中。封 建社会 的整个历史和文化都被打上 了浓重的男性色 彩, 他们 用伦 理道 德 、 法律习俗 等枷 锁 , 身体 和思 从 想 两 方 面 牢 牢 控 制 着 女 人 , 人 就 是 他 们 的 财 产 和 女 奴隶 。出嫁 时 , 的女孩都 哭 , 有萧 萧在笑 , 她 别 只 对 而 言 , 不 过 是 “ 一 家 到 另 一 家 ” 这 从 。 后来 , 萧萧怀 了花狗 的儿子 , 十年后 预备 给小 “ 丈夫生儿子继香火 的肚子 , 已被 被人抢 先下 了种 ” 。 已被使用 , 件物 品还有 什 么用 途?于是 等待萧 萧 这 的只有两种命运 : 沉潭 或发卖 。前 者是一 帮家庭 里 的主事者对 他 人生 命生 死予 夺 的权 利 , 谁赋 予 的? 父 权 文 化 , 论 多 么 惨 烈 也 无 人 质 疑 !愚 昧 的思 想 无 依 旧统治着这个荒僻 的小 山村 , 种野蛮 的行 为深 这 刻揭示 了封 建宗法 制 对人 的生 命价 值 的无 视和 毁 灭, 此种 观念 的深 入 骨 髓 , 妇 女 自然 成 了首 当 其 冲 而 的牺牲 品。后者又是卖 , 原来 封建 社会里 的男人 都 是有买卖女人 的权利 的!并且如果发卖 ,还可以在 “ 改嫁上收 回一笔钱 , 当作赔 偿夫 家人损 失的数 目” 。 整个人都 已被剥夺 , 如今连 这点蝇 头小利 尚要斤 斤 计较 。 萧萧终于没有被沉 潭或发卖 , 因为她 生 了个 儿 子 。儿子是家族的血脉 和未来 , 封建家庭 重视 的 是 人物 。儿子拯救 了母亲 !看起来萧萧的命运似乎 还 不错 , 但实 际上是 作者利用 “ 然” 个 因素更为 深 偶 这 入地揭示 了萧萧 的命 运—— 不管是 “ 偶然” 还是 “ 必 然” 都掌握在 他人 的手里 , 至取 决 于他 人 的“ , 甚 一 念” 间 , 之 从而进一步揭露和鞭挞了宗法 制及其有 关
《萧萧》读后感

《萧萧》读后感《萧萧》读后感1沈从文先生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师之一。
沈从文先生的文学创作旨在“表现1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以乡村为题材的小说是典型的乡村文化小说,正如沈从文先生所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因此在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中无不透露着人性美,人性是沈从文先生小说作品的表现中心,在小说《萧萧》中也深深的透露着1种淳朴、自由的人性美。
《萧萧》描述了1个农村少女萧萧作为童养媳的故事。
小说语言朴实、自然,寓技巧于平实之中,小说通篇洋溢着浓重的民间乡土气味的同时,也透露着1种浓厚的人性美,这主要体现在小说塑造的几个人物形象和描写的乡风民俗上。
《萧萧》的主人公萧萧是在自然里长着的1个农村少女,在她的成长中无不彰显着1种人性美。
萧萧是1个童养媳,在风气淳朴的乡村,“在这些小女人心中,做新娘子,从妈妈身边离开,且准备做他人的妈妈,从此将有许多新事情等待发生。
像做梦一样,将同1个陌生男子汉在1个床上睡觉,做着承宗接组的事情,当然十分害怕,所以照例觉得要哭,就哭了”,在萧萧做新娘子时,“出嫁只是从这家转到那家。
因此到那一天这女人还只是笑。
她不害羞,又不怕。
她是什么事也不知道,就做了人家的新媳妇了。
”,面对着比自己小9岁的丈夫,她整天带着他玩,干杂货,倒也不觉得怎么苦;面对爷爷喊她“女学生”时,她是既排斥又向往;15岁发育成熟的萧萧在与长工花狗懵懵懂懂发生了关系后,她并没有害怕,只是在怀孕后身体发生变化时才产生了恐慌,并萌生了逃跑的念头。
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萧萧有着优点的同时也是存在着缺点,这是1个有血有肉的灵魂。
沈从文先生从这些点点滴滴向人们展示了萧萧纯真、善良、懵懂的天然之美,这种天然之美成长在偏僻的山村,正是人性美的最好诠释!在《萧萧》中,除了萧萧展示了人性美之外,其爷爷、伯父、丈夫及婆家也展示了人性美。
浅论《萧萧》中的主人公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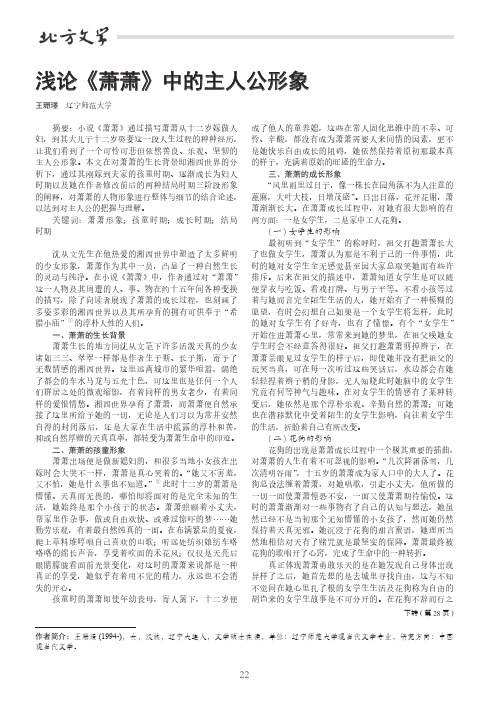
浅论《萧萧》中的主人公形象王珊璟辽宁师范大学摘要:小说《萧萧》通过描写萧萧从十二岁嫁做人妇,到其大儿子十二岁娶妻这一段人生过程的种种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可怜可悲但依然善良、乐观、坚韧的主人公形象。
本文在对萧萧的生长背景即湘西世界的分析下,通过其刚嫁到夫家的孩童时期、逐渐成长为妇人时期以及她在作者修改前后的两种结局时期三阶段形象的阐释,对萧萧的人物形象进行整体与细节的结合论述,以达到对主人公的把握与理解。
关键词:萧萧形象;孩童时期;成长时期;结局时期沈从文先生在他热爱的湘西世界中塑造了太多鲜明的少女形象,萧萧作为其中一员,凸显了一种自然生长的灵动与纯净。
在小说《萧萧》中,作者通过对“萧萧”这一人物及其周遭的人、事、物在约十五年间各种变换的描写,除了向读者展现了萧萧的成长过程,也刻画了多姿多彩的湘西世界以及其所孕育的拥有可供奉于“希腊小庙”①的淳朴人性的人们。
一、萧萧的生长背景萧萧生长的地方同沈从文笔下许多活泼天真的少女诸如三三、翠翠一样都是作者生于斯、长于斯,寄予了无数情感的湘西世界。
这里远离城市的繁华喧嚣,隔绝了都会的车水马龙与五光十色,可这里也是任何一个人们群居之处的微观缩影,有着同样的男女老少,有着同样的爱恨情愁。
湘西世界孕育了萧萧,而萧萧便自然承接了这里所给予她的一切,无论是人们习以为常并安然自得的封闭落后,还是大家在生活中流露的淳朴和善,抑或自然厚赠的天真直率,都转变为萧萧生命中的印迹。
二、萧萧的孩童形象萧萧出场便是做新媳妇的,和很多当地小女孩在出嫁时会大哭不一样,萧萧是真心笑着的。
“她又不害羞,又不怕,她是什么事也不知道。
”②此时十二岁的萧萧是懵懂、天真而无畏的,哪怕即将面对的是完全未知的生活,她始终是那个小孩子的状态。
萧萧照顾着小丈夫,帮家里作杂事,做或自由欢快、或难过惊吓的梦……她勤劳乐观,有着最自然纯真的一面。
在布满繁星的夏夜,爬上草料堆哼唱自己喜欢的山歌;听远处纺织娘纺车咯咯咯的绵长声音,享受着吹面的禾花风;仅仅是天亮后眼睛朦胧看面前光景变化,对这时的萧萧来说都是一种真正的享受,她似乎有着用不完的精力,永远也不会消失的开心。
凄美的生命之1

凄美的生命之歌——浅淡沈从文小说《萧萧》摘要:《萧萧》向人们讲述了一个童养媳曲折命运的故事。
她生活在一个弥漫着乡村原始文化的氛围中,纯朴、天真、勤劳,同时也是愚昧与无知的。
她是准乎自然的,充满了原始生命的活力,代表了自然人性的优点与弱点,从而导致了她悲哀的一生。
但沈从文仍在她身上寄托了对生命与自由的向往。
“女学生”与无意识的冲动给她的生活也带来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关键词:自然人性生命无意识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表现者与反思者。
在他所展现的湘西世界里:人们单纯而勇敢,均以诚相待,以善相亲,充满了温爱。
他们总是“很从容地在那里尽情性命之理”,尽情享受造化赋予“生命本来种种”,在生活与感情的撞击中闪现“生命”的火花,呈现“乡下人”的内在精神气质。
从而可以看出:一方面,人们的道德状态与人格气质与古老的湘西文化相连接,他们热情、诚实、勤劳以及人性准乎自然;但另一方面,又使他们无法适应现代生活环境,从而导致了他们的悲剧命运。
一、湘女之命1、自然人性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体现了强烈的人性美,充满着浓郁的牧歌气息,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生的人性形式’”。
①他把自然人心之美通过一个个少女形象的塑造呈现出来。
从翠翠、三三、萧萧到他笔下凤凰小城,苗家山寨,沅河流域的少女们的音容笑貌,使半个世纪后的人们一想起湘西,便联想到豆寇年华的少女形象。
这窈窕的形象如清风,如洒落在腥风血雨中荒凉土地上的阳光。
这美,也是沈从文作品魅力之所在。
主人公萧萧就是一个生活在安静、平和的自然环境里的“自然之子”。
“风里雨里过日子,象一株长在园角落在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枝大叶,日增茂盛。
”她的成长如此平淡无奇,悄无声息,是一种原生,自然的成长,真如那偏远的山野里,一朵灿烂盛开“山花”,自然、健康、优美的展现着自身。
萧萧在美好的自然环境陶冶中,显得多么单纯与质朴。
“萧萧十五岁时,已高如成人,心却还是糊糊涂涂一颗心。
把握萧萧中对人性和风情的描写

对都市的批判
属于使文明趋于健康的文学警示。
沈从文创作的思想源流:
chuangzuosixiang
这可以上溯到“五四”文化运动中关于“人的文
学”和“国民性改造”以致“美育代宗教”的传统,
两者的合流,即沈从文的文学人性立场。不进入革命
性改造中国的一途,而主张经由文化改造人、改造民
族。沈从文离开30年代主流文学的道理就是这样形成
正是对中国社会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民族 品德的消失”、“人性”的堕落、人类的“不可知
的命运”的忧患意识,及“重造”民族的不懈追寻,
构成了沈从文创作的内在动力与思想内核。
使他对城乡世界的美丽和丑陋特别敏 向善和向美的 感,企图用湘西世界保持的那种自然
文学理想
生命形式作为参照,来探求“民族品
德的消失于重造”,探求人的重造这 一过于沉重的题指旨。
小“弟弟”是萧萧一手带大的,要论姐弟情谊,两
人感情很好,就是失身,也是萧萧自自然然顺从情欲的
结果。萧萧的结局倒还是“大团圆”式的,她在等待主 顾的过程中生下了一个儿子,逗得全家人开心,对萧萧 网开一面,不将其嫁于别处了。
(2)梦想和幻想穿插于现实,反映出中国 传统文化执着于生命的安乐和长久而轻视对 生的超越这一重要特色。
课文例句:
这时经祖父一为说明,听过这话的萧萧,心中却忽 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以为倘若她也是女学生,
她是不是照祖父说的女学生一个样子去做那些事?不
管好歹,做女学生并不可怕,因此以来却已为这乡下 姑娘体念到了。
课文例句:
萧萧从此以后心中有个“女学生”。做梦也便常 常梦到女学生,且梦到同这些人并排走路。仿佛也坐
叹之处。
人物的幸运点 从生存层次来讲,萧萧的无知倒使她 回避了对痛苦的感受,使她能满足于 温饱生活,在当下生活的细节中获得 快乐。一如祖父他们,生活在闭塞的 乡下,恪守着传统的习俗,他们从不 追问为何终年的劳作并没有使他们过 上美好的生活,更不烦心于生存的意 义这样一些抽象的问题。
浅析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

浅析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作者:于晓楠向沁杨冬曾晓辉来源:《神州·中旬刊》2013年第06期摘要:沈从文是中国文学史上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
在他的湘西作品中为我们描绘了众多的女性形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对女性形象、女性命运有着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湘西沈从文女性形象人性沈从文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作家。
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却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声誉。
作家的写作离不开自己的生活圈,如钱钟书熟悉无锡,茅盾熟悉乌镇,汪曾祺熟悉江苏,沈从文熟悉凤凰。
可以说湖南凤凰这个地方没有沈从文和他的湘西作品,就不会名声鹊起。
女性形象是沈从文作品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我国,女性历来深受封建礼教的压迫,她们没有足够的人身自由,更得不到社会的关爱。
沈从文在描写湘西女性的时候,用优美的自然环境取代了复杂的社会社会环境,将讴歌的重点放在湘西女性的人性美上。
一、以翠翠为代表的湘西少女形象。
1、翠翠名字的由来作品《边城》中的女性翠翠,是摆渡老船夫的外孙女,祖孙二人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
老人的女儿爱上了戍城的士兵,珠胎暗结,想走又舍不得老父亲,士兵为此自杀了。
女儿生下翠翠后不久,殉情而死。
翠翠成了孤儿。
因为祖孙俩住的地方有很多竹子,老人便为外孙女取了一个清新的名字,叫“翠翠”。
2、翠翠的性格、命运作品中描写了祖孙俩“渡人”生涯的尽职尽责和闲来无事时晒太阳、吹曲子、训练黄狗的快乐。
预示着翠翠在和老人相依为命的过程中,秉承了老船夫心地善良,与人为乐的高尚情操,同时又具有乡村少女固有的天真活泼,柔顺多情。
翠翠原来是一个天真、活泼、善良的女孩,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对爱情产生了美好的向往。
终于有一天,翠翠遇到了自己的恋人傩送并对他产生了朦胧的暗恋之情。
遗憾的是傩送的哥哥天保也喜欢上了翠翠,天保直接向翠翠提亲,然而翠翠却心有独钟,她不能违背内心,他选择会唱歌的傩送。
天保离家出走,死于意外。
这样,翠翠虽然依照自己的内心做出了选择,傩送却对哥哥的死不能释怀。
沈从文《萧萧》的文本解读

萧萧一朴素质朴之美小说萧萧取材于湘西农村,这里虽偏远闭塞,沈从文对它始终怀有真挚的感情,文中,作者的情感与故乡独有的乡情风俗、地域文化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令人心驰神往的优美意境,阅读萧萧,乡土朴野之风铺面而来:夏日里“天上的星”“屋角的萤”“纺织娘娘咯咯咯的”长声。
构成了一幅宁静而朴素的乡村图景;“硕大如盘”的“灰粉大南瓜”、“大红大黄的木叶”“满地的”落枣、刺莓。
毛毛虫。
说明生活劳作于此的人们生活平淡自足且颇有野趣。
在沈从文的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是社会的一部分,更是山水、天地、自然的一部分,山川天地给人以滋养以熏陶。
沈从文正是以这一朴素的“湘西农村”为背景来抒写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生的人生形式”。
萧萧十二岁时嫁给了不到三岁的小丈夫,他们年纪尚小,不明白何为夫妻关系,彼此以姊弟相待,天天黏在一起打笑取闹。
弟弟饿了,萧萧喂他东西吃;哭了,就哄他。
小说一开始,就将人物安排在天真烂漫的儿童世界里,将成人世界的一切礼法规矩拒之于外。
儿童世界是纯真而诗意的,两小孩关系未带有任何杂念。
萧萧家里的公公婆婆、祖父祖母,对待萧萧完全就像对待孙女儿,爷爷常跟萧萧开玩笑,拿女学生来逗笑萧萧,萧萧也在爷爷跟前撒娇。
童养媳制度自然有违人性,但沈从文写作萧萧,其意不在批判不合理制度对人性的戕害,而是着重开掘人性的善良与宽厚。
当萧萧受花狗的引诱大了肚子后,在“正常”的情况下,萧萧面对的惩罚是“沉塘”或者“发卖”,但是沈从文先生纵容萧萧,不愿让她为所做的错事受苦,作者甚至把这种纵容态度扩大到整个湘西世界,村民们都带有一种孩子般的宽容与善良,他们不认面对“成人”律法的道德后果,用童心来奉行和化解成人的法规。
萧萧的命运终于因为善良的人性对礼法制度的胜利而有了美丽温情的结局。
二、蒙昧无知之悲哀深切的忧伤、沉重的悲哀也贯注在萧萧全篇。
萧萧从小失去双亲,寄养在伯父家。
湘西女孩出嫁时“照例”要哭哭,而萧萧十二岁出嫁,“小女子还只是笑”,懵懵懂懂地开始了童养媳的生活。
浅析沈从文“乡村人”的形象——以《萧萧》《边城》为例

现当代文学浅析沈从文“乡村人”的形象——以《萧萧》《边城》为例蒋乐璇湖南师范大学摘要: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表现者与反思者,其关于乡村题材的书写既唱出了他的理想生命之歌,同样寄予了他对乡村人生的反思。
本文将以《萧萧》《边城》为例来探讨沈从文笔下的“乡村人”形象。
关键词:《边城》《萧萧》;沈从文;乡村人一、乡村人生的反思——《萧萧》(一)身处悲剧地位而不自知《萧萧》叙述了古老湘西文化中的童养媳的传统。
萧萧做媳妇时年纪才十二岁,嫁给的小丈夫还不到3岁,丈夫比她年少九岁,断奶还不多久。
在萧萧试图逃跑被发现以后,按照本族的传统,要“沉塘”或是“发卖”。
这些湘西古老有些落后的传统自然是导致人物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们身处悲剧地位而不自知。
即便伯父不忍把萧萧沉塘,萧萧也是“当然应当嫁人作二路亲了。
”“这处罚好像也及其自然。
”丈夫不愿意萧萧被发卖,萧萧自己也不愿意去,“大家全莫名其妙,只是按照规矩像逼到要这样做,不得不做。
”萧萧一家在大儿子十二岁时也为他接了亲,而这一天萧萧“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文中有现代新思想的象征即女学生们,然而当地人的印象中,“一想起来就觉怪可笑的!”即便此处的人们身处不幸,却浑然不知。
他们好像都是“不得不做”,或者“好像就应该这样”,却从未思考过原因,或者有所反抗。
萧萧作为童养媳习俗下的牺牲者,最后却成为了这个习俗的遵从者。
(二)保留着的源于古老传统的善良,纯朴尽管在《柏子》《萧萧》》《贯生》等沈从文众多的小说中,乡村人虽然身处悲剧地位置而不自知,但是在他们身上,还一律保留善良,纯朴,诚实的品性。
在小说最初萧萧还是一个12岁的小女娃,天真,单纯,“她什么事也不知道,就做了人家的媳妇。
”尽管如此,她还是尽心尽力的像对待弟弟一般的照顾着自己的小丈夫。
她常常一个人爬到草料上面去,抱着已经熟睡的丈夫,轻轻的轻轻的随意唱着自编的山歌。
浅谈沈从文笔下的人性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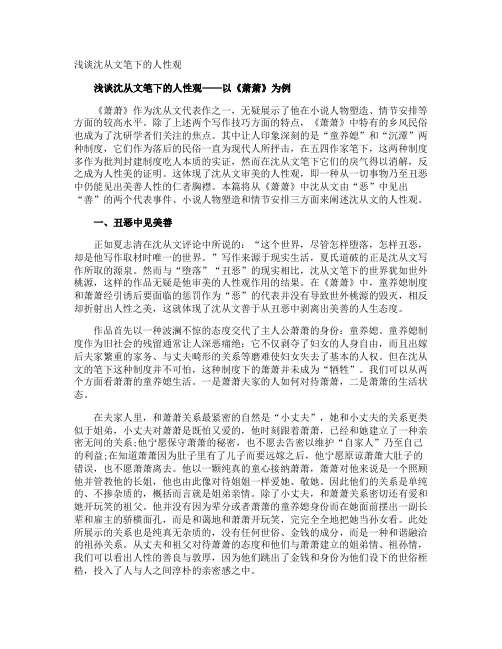
浅谈沈从文笔下的人性观浅谈沈从文笔下的人性观——以《萧萧》为例《萧萧》作为沈从文代表作之一,无疑展示了他在小说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等方面的较高水平。
除了上述两个写作技巧方面的特点,《萧萧》中特有的乡风民俗也成为了沈研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童养媳”和“沉潭”两种制度,它们作为落后的民俗一直为现代人所抨击,在五四作家笔下,这两种制度多作为批判封建制度吃人本质的实证,然而在沈从文笔下它们的戾气得以消解,反之成为人性美的证明。
这体现了沈从文审美的人性观,即一种从一切事物乃至丑恶中仍能见出美善人性的仁者胸襟。
本篇将从《萧萧》中沈从文由“恶”中见出“善”的两个代表事件、小说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三方面来阐述沈从文的人性观。
一、丑恶中见美善正如夏志清在沈从文评论中所说的:“这个世界,尽管怎样堕落,怎样丑恶,却是他写作取材时唯一的世界。
”写作来源于现实生活,夏氏道破的正是沈从文写作所取的源泉。
然而与“堕落”“丑恶”的现实相比,沈从文笔下的世界犹如世外桃源,这样的作品无疑是他审美的人性观作用的结果。
在《萧萧》中,童养媳制度和萧萧经引诱后要面临的惩罚作为“恶”的代表并没有导致世外桃源的毁灭,相反却折射出人性之美,这就体现了沈从文善于从丑恶中剥离出美善的人生态度。
作品首先以一种波澜不惊的态度交代了主人公萧萧的身份:童养媳。
童养媳制度作为旧社会的残留通常让人深恶痛绝:它不仅剥夺了妇女的人身自由,而且出嫁后夫家繁重的家务、与丈夫畸形的关系等磨难使妇女失去了基本的人权。
但在沈从文的笔下这种制度并不可怕,这种制度下的萧萧并未成为“牺牲”。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萧萧的童养媳生活。
一是萧萧夫家的人如何对待萧萧,二是萧萧的生活状态。
在夫家人里,和萧萧关系最紧密的自然是“小丈夫”,她和小丈夫的关系更类似于姐弟,小丈夫对萧萧是既怕又爱的,他时刻跟着萧萧,已经和她建立了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他宁愿保守萧萧的秘密,也不愿去告密以维护“自家人”乃至自己的利益;在知道萧萧因为肚子里有了儿子而要远嫁之后,他宁愿原谅萧萧大肚子的错误,也不愿萧萧离去。
沈从文和萧红笔下的童养媳形象对比-以《萧萧》和《呼兰河传》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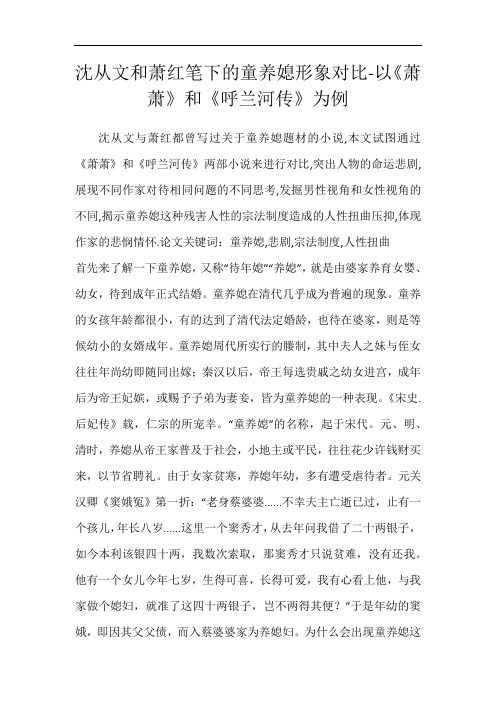
沈从文和萧红笔下的童养媳形象对比-以《萧萧》和《呼兰河传》为例沈从文与萧红都曾写过关于童养媳题材的小说,本文试图通过《萧萧》和《呼兰河传》两部小说来进行对比,突出人物的命运悲剧,展现不同作家对待相同问题的不同思考,发掘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的不同,揭示童养媳这种残害人性的宗法制度造成的人性扭曲压抑,体现作家的悲悯情怀.论文关键词:童养媳,悲剧,宗法制度,人性扭曲首先来了解一下童养媳,又称“待年媳”“养媳”,就是由婆家养育女婴、幼女,待到成年正式结婚。
童养媳在清代几乎成为普遍的现象。
童养的女孩年龄都很小,有的达到了清代法定婚龄,也待在婆家,则是等候幼小的女婿成年。
童养媳周代所实行的媵制,其中夫人之妹与侄女往往年尚幼即随同出嫁;秦汉以后,帝王每选贵戚之幼女进宫,成年后为帝王妃嫔,或赐予子弟为妻妾,皆为童养媳的一种表现。
《宋史.后妃传》载,仁宗的所宠幸。
“童养媳”的名称,起于宋代。
元、明、清时,养媳从帝王家普及于社会,小地主或平民,往往花少许钱财买来,以节省聘礼。
由于女家贫寒,养媳年幼,多有遭受虐待者。
元关汉卿《窦娥冤》第一折:“老身蔡婆婆......不幸夫主亡逝已过,止有一个孩儿,年长八岁......这里一个窦秀才,从去年问我借了二十两银子,如今本利该银四十两,我数次索取,那窦秀才只说贫难,没有还我。
他有一个女儿今年七岁,生得可喜,长得可爱,我有心看上他,与我家做个媳妇,就准了这四十两银子,岂不两得其便?”于是年幼的窦娥,即因其父父债,而入蔡婆婆家为养媳妇。
为什么会出现童养媳这种现象呢?原因之一是为了帮助夫家增加劳动力,也可以为娘家带来一笔收入.显示了婚姻和金钱的交易.童养媳早早失去了童年的快乐,过早承受繁重的家务,等到年龄合适了就圆房,开始了传统女性的相同命运.文学作品反映童养媳生活的有《萧萧》,写于1929年冬天,小说写童养媳生活, 12岁嫁到婆家就失去了人生自由,小说这样写到: 也有做媳妇不哭的人。
人性之美与生命之伤:读沈从文《萧萧》

人性之美与生命之伤:读沈从文《萧萧》作者:袁媛来源:《魅力中国》2018年第20期摘要:《萧萧》是沈从文湘西文学作品的代表作之一,作品在表现手法上交错运用多重对比,有力地表现了沈从文一贯追求的对“人性”、“人生形式”的探索。
反映了湘西大地的自然人性之美和湘西民众代代相传的生命形式,同时不乏作者对那蒙昧悲凉的深刻思考。
关键词:沈从文;萧萧;人性;悲哀;对比湘西二字,总会令人想起纯朴、美好、自然这些词语,多少没接触过这片土地的人也把它奉为魂牵梦绕的地方,只因我们在那位追随人性而走的“乡下人”――沈从文笔下领略过这片土地的太多美好,读者已经跟随他的笔端走进这片土地,恋上这片土地。
沈从文先生用一个个湘西故事不动声色地在搭建的是他心中爱与美的,永恒的“人性的希腊小庙”,而《萧萧》无疑是这座小庙里不可缺的片瓦。
《萧萧》作为沈从文的代表作之一,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的突出的作品。
通过写童养媳制度下的萧萧的生命悲喜剧,以听从自然人性召唤的萧萧,写出了湘西少女的天真、纯洁、活泼的特点,同时也反映出湘西人民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凉的人生,寄托了作者的隐痛。
一、闪耀的人性之光――湘西大地的爱与美萧萧是沈从文所塑造的一系列湘西少女中的一个典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萧萧是山水的女儿,她骨子里天生带着的柔情与水性,她的一生都在顺应着命运,顺应着人性。
她的成长像棵蓖麻一样,几次降霜落雪,几次清明谷雨,她就长大了,她的出嫁也没有像别的女孩一样哭哭啼啼,而是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
小说写道:“也有做媳妇不哭的人,萧萧做媳妇就不哭。
这小女子没有母亲,从小寄养在伯父种田的庄子上……到那一天,这女人还只是笑.她又不害羞,又不怕。
”[1]就连她的失身都是因为被花狗的歌声唱开了天性,所以才成了妇人。
即使意外怀孕,她的害怕也不是来自于所谓的世俗压力,而是身体的变化。
她把人性之光体现的淋漓尽致,她生来就是为着人性,顺着人性,从不乖违,从不附和,只是沿着那条路平静的走下去。
民俗及人情――论沈从文《萧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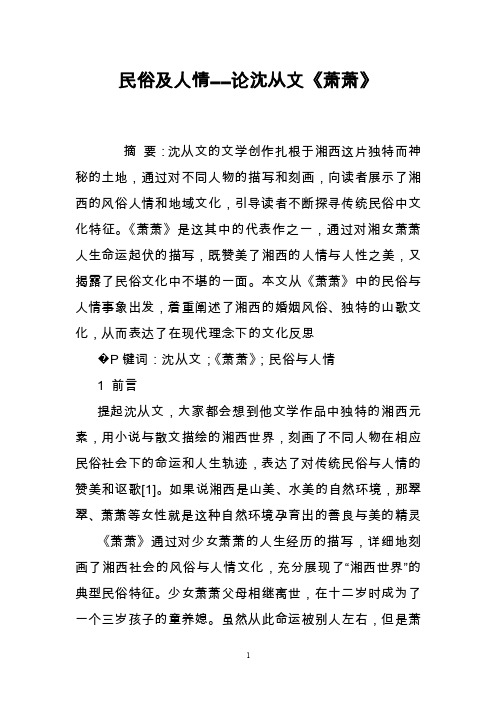
民俗及人情――论沈从文《萧萧》摘要: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扎根于湘西这片独特而神秘的土地,通过对不同人物的描写和刻画,向读者展示了湘西的风俗人情和地域文化,引导读者不断探寻传统民俗中文化特征。
《萧萧》是这其中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对湘女萧萧人生命运起伏的描写,既赞美了湘西的人情与人性之美,又揭露了民俗文化中不堪的一面。
本文从《萧萧》中的民俗与人情事象出发,着重阐述了湘西的婚姻风俗、独特的山歌文化,从而表达了在现代理念下的文化反思�P键词:沈从文;《萧萧》;民俗与人情1 前言提起沈从文,大家都会想到他文学作品中独特的湘西元素,用小说与散文描绘的湘西世界,刻画了不同人物在相应民俗社会下的命运和人生轨迹,表达了对传统民俗与人情的赞美和讴歌[1]。
如果说湘西是山美、水美的自然环境,那翠翠、萧萧等女性就是这种自然环境孕育出的善良与美的精灵《萧萧》通过对少女萧萧的人生经历的描写,详细地刻画了湘西社会的风俗与人情文化,充分展现了“湘西世界”的典型民俗特征。
少女萧萧父母相继离世,在十二岁时成为了一个三岁孩子的童养媳。
虽然从此命运被别人左右,但是萧萧把丈夫照顾的很周到,通过辛勤劳作获得了不错的农田收成,所以倒也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少女时期。
后来萧萧遇到了花狗,情窦初开的她和花狗发生了私情并怀孕了。
这在当时的湘西社会是应该被沉谭的,但是后来萧萧生了个儿子才免于这种命运。
后来儿子逐渐长到六岁,在当地的民俗文化下也娶了媳妇,萧萧最终成为了婆婆[2]2 《萧萧》中的民俗与人情事象2.1 婚姻风俗在《萧萧》中沈从文描绘了湘西当地的童养媳婚姻风俗。
主人公萧萧十二岁时,她的丈夫才是三岁稚子。
童养媳是指由在传统父母包办婚姻的情况下,把女孩从小嫁给婆家当做媳妇。
一般的童养媳大多家境贫困,父母无力抚养女孩,所以为了获得婆家的聘礼而变相把女儿卖给婆家,作为童养媳在婆家生活。
通常来说,童养媳的结局都十分悲惨,由于和丈夫年龄差距过大,无法得到圆满的婚姻生活。
试比较沈从文作品中翠翠-夭夭-萧萧的形象

试比较沈从文作品中翠翠\夭夭\萧萧的形象摘要:沈从文先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尤具魅力,她们纯真善良,在灵山秀水的湘西世界中演绎着不同的人生故事。
而本文只选择了沈从文先生作品中的三个人物为代表,分别从她们的生活环境,性格,爱情方面做粗浅的比较,只是希望能从中更了解湘西农家少女的形象,以及美丽而神秘的湘西世界。
关键词:翠翠夭夭萧萧湘西农家少女纯真顽强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先生创作了很多湘西少女的形象,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边城》中翠翠这一形象。
但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同样也存在着温柔、清丽、纯真的湘西农家少女形象,如萧萧、夭夭等等。
沈从文先生依顺着她们的各自成长及命运,创作出了不同的或喜或悲的故事,也造就了一个个的鲜活的个体。
我们将从不同的故事经历中,了解和认识她们。
她们都不认识字,都生活在一群最原始最善良的人群之中,所以也保持了最纯真天然的一面,所以说她们之间存在了太多的相似性,但同时她们也是作为独特的个体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一、生活的环境――都是生活在湘西的农家少女翠翠是茶峒白河边摆渡老人的外孙女,是老船夫女儿的遗孤。
因为住在两山多篁竹的山城边境,篁竹的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便为这可怜的孤雏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翠翠’。
在一种近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已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
在沅水流域上游有一条支流叫做辰河,辰河的中部小口岸是吕家坪,河下游约四里一个小土坡叫“枫树坳”,坳上有个滕姓祠堂,祠堂前后有十几株老枫树木,枫木坳对河萝卜溪有一大片桔子园。
那就是夭夭生活的地方。
萧萧是个孤儿,十二岁就被唢呐吹进了农家,出嫁作了童养媳。
她生活的地方也非常宁静。
如:夏夜光景说来如做梦,大家饭后坐到院中心歇凉,挥摇蒲扇,看天上的星同屋角的萤,听南瓜棚上纺织娘子咯咯咯拖长声音纺车,远近声音繁密如落雨,禾花风悠悠吹到脸上,正是让人在各种方便中说笑话的时候。
她们都是生活在青山绿水之中的女儿,他们和这片山水一样都透着纯净与灵气。
二、性格之比较──都有着秀丽的外表和纯真顽强的性格沈从文塑造的湘西少女形象总是如精灵般的灵动,散发着巨大的魅力。
沈从文小说《萧萧》《丈夫》浅析

沈从文小说《萧萧》《丈夫》浅析撰写者:谢兴华导师:熊岩【内容提要】小说《萧萧》《丈夫》中,沈从文以一个“乡下人”的眼光和平等的民间立场温和地去看待湘西的“人和事”,描绘了湘西世界奇异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批判了传统道德和城市文明对人性的摧残,表达了人性回归的主题。
平静中透出悲哀与忧愁。
【关键词】沈从文;湘西世界;人性;艺术魅力沈从文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范例,他那富有传奇性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独特的文学思想与政治观念既为解读其文带来多种阐释的可能,又为研究其人留下了诸多课题。
沈从文作为孤独者在文学上踽踽独行,逐步为他人理解。
由于创作时代的限制,他的才华和光芒被长期掩盖。
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外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经久不衰的“沈从文热”,而如今沈从文作品的艺术价值显得弥足珍贵,“时光改变了,沈从文的价值就像一只绩优股,每天都在上涨”目前,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贡献已得到学者们的充分肯定,其独具特色的“沈从文体”在中国现文学史上享有盛誉。
固然,这源于沈从文作品超越时间空间的生命力,具有永恒价值。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其小说《丈夫》《萧萧》作一番分析,试图解释其独具特色的写作风格和艺术魅力。
一、沈从文其人其文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岳焕,苗族,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他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
沈从文在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散文集《湘行散记》。
沈从文精心构建的“湘西”是一个风景优美、人民淳朴,与都市世界相对的,未被现代商业文明完全浸染的世界。
他以一个湘西人的视角看待乡村和城市的冲突,以及现代文明和自然的对峙,反映现代文明的发展带来不可调和的矛盾。
同时,以舒缓柔和的笔调,把故事放在湘西边陲。
这块风景如诗如画,人性单纯善良的土地展现出与都市截然不同的美与和谐,诠释人与自然和谐的道理。
沈从文《萧萧》的内在冲突分析

沈从文《萧萧》的内在冲突分析作者:罗清吴道毅来源:《文学教育》 2014年第17期罗清吴道毅内容摘要:《萧萧》是苗族作家沈从文的短篇小说名篇,表现湘西童养媳制度下生命悲喜剧,其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在看似不经意之处充满了一个又一个矛盾冲突,诸如童养媳制度衍生的婚外情、萧萧女学生梦的起与落、私生子风波与沉潭闹剧与童养媳悲剧的重演,让人感到荡气回肠。
这些矛盾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沈从文小说的普遍性艺术特点。
关键词:《萧萧》童养媳文化冲突悲剧轮回外在看来,沈从文小说所讲述的故事大多都平淡无奇乃至波澜不惊。
然而,当我们深入文本后便会发现沈从文小说的故事中往往包含着众多的内在冲突,一种推动故事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显示出作家非凡的艺术匠心。
《萧萧》便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
小说讲述了湘西一个童养媳的故事,但故事里却内含了至少四个方面的冲突,会使读者感到跌宕起伏,玩味无穷。
一.童养媳制度衍生的婚外情《萧萧》中的第一个内在冲突应该是童养媳制度下的人性压抑及其衍生的婚外情。
小说的开篇即十二岁的主人公萧萧以童养媳身份出场了,萧萧没有母亲,从小寄养到伯父种田的庄子上,对年幼孤苦无依的她而言,还不太懂什么是婚姻,什么是童养媳,只是知道要从这家转到另一家去住了。
所以到成为人家的媳妇那一天,她依旧是少女般的天真活泼,开心地笑着。
虽然萧萧是幸运的,没有遇上恶婆婆,过得苦不堪言,但她身为童养媳,女大男小的童养媳制度已无形中开始摧残她的人性,消磨她的童真。
丈夫比她年少九岁还未断奶,萧萧按照当地的风俗,要喊丈夫做弟弟,而她的新生活就是每天照顾“弟弟”的饮食起居,“饿了,喂东西吃;哭了,就哄他,摘南瓜花或狗尾草戴到小丈夫头上”,还像母亲那般在小丈夫脏兮兮的脸上亲了又亲,逗他开心。
她自己本还处于孩子的年龄,但在这畸形婚姻中却承担起一个像姐姐、像母亲又像妻子的责任。
不过这不影响萧萧开心的生活,除了每日陪丈夫玩,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日子不比在伯父家时苦,所以夜晚在梦里,萧萧依旧做着同龄少女会做的梦,如精灵般飞天下地到处游戏着。
民俗与人情——论沈从文《萧萧》

民俗与人情——论沈从文《萧萧》
《萧萧》是中国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小说,小说以广东农村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有关水浒传故事的周转和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半老徐娘的故事。
小说通过描述一个农村的生活,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古代民俗和人情。
在小说中,沈从文为读者呈现了广东农村的独特风俗和民俗。
首先,小说中描绘了农民的生活和劳作,如翻地、播种、耕田、捕鱼、打猎等,这些都是广东农村地区的传统生活方式。
同时,小说也描述了农民们在节日和婚礼等特殊场合下的习俗,比如吃端午节的粽子、过年时点灯放炮、结婚时搓糖等。
《萧萧》还描写了农民的人际关系和互动,这体现了中国人的人情世故。
小说中,半老徐娘和其他人的接触是基于关系的,她同乡亲是相互关怀、互相帮助的,而她与周转之间的接触则是一种互惠关系,同时也展现了人情的纠葛。
此外,小说也描述了不同年龄、地位和性别的人之间的不同相处方式,如老年人之间的敬重和尊重、年轻人之间的互相嬉戏和打闹、男女之间的羞涩和接近等。
通过描写这些民俗和人情,沈从文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其深刻的内涵。
这种文化的主要特点是注重关系、强调互惠和尊重,这种文化存在于中国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之中,从而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念之一。
通过深入探讨和理解这种文化,我们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底蕴和思想体系。
总之,《萧萧》是一部反映中国农村风俗和人情的小说,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文化内涵,使得读者无论是从文学还是文化的角度来看,都能够从中受益。
“萧萧”悲剧背后隐伏的民族悲剧——重读沈从文的《萧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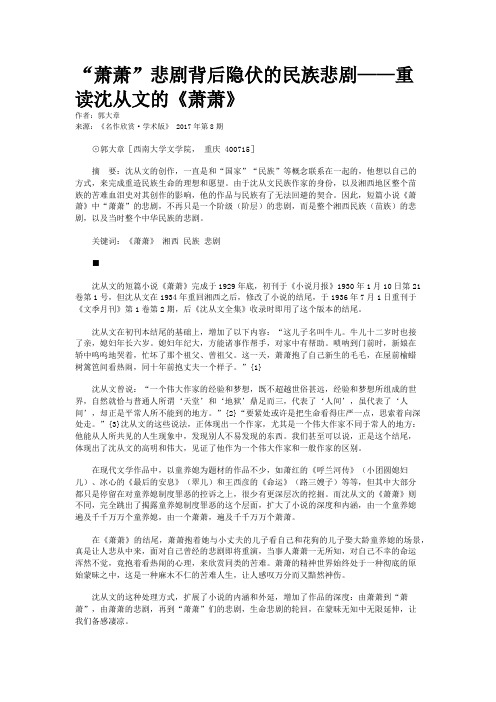
“萧萧”悲剧背后隐伏的民族悲剧——重读沈从文的《萧萧》作者:郭大章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7年第8期⊙郭大章[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摘要:沈从文的创作,一直是和“国家”“民族”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他想以自己的方式,来完成重造民族生命的理想和愿望。
由于沈从文民族作家的身份,以及湘西地区整个苗族的苦难血泪史对其创作的影响,他的作品与民族有了无法回避的契合。
因此,短篇小说《萧萧》中“萧萧”的悲剧,不再只是一个阶级(阶层)的悲剧,而是整个湘西民族(苗族)的悲剧,以及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
关键词:《萧萧》湘西民族悲剧■沈从文的短篇小说《萧萧》完成于1929年底,初刊于《小说月报》1930年1月10日第21卷第1号,但沈从文在1934年重回湘西之后,修改了小说的结尾,于1936年7月1日重刊于《文季月刊》第1卷第2期,后《沈从文全集》收录时即用了这个版本的结尾。
沈从文在初刊本结尾的基础上,增加了以下内容:“这儿子名叫牛儿。
牛儿十二岁时也接了亲,媳妇年长六岁。
媳妇年纪大,方能诸事作帮手,对家中有帮助。
唢呐到门前时,新娘在轿中呜呜地哭着,忙坏了那个祖父、曾祖父。
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1}沈从文曾说:“一个伟大作家的经验和梦想,既不超越世俗甚远,经验和梦想所组成的世界,自然就恰与普通人所谓‘天堂’和‘地狱’鼎足而三,代表了‘人间’,虽代表了‘人间’,却正是平常人所不能到的地方。
”{2}“要紧处或许是把生命看得庄严一点,思索着向深处走。
”{3}沈从文的这些说法,正体现出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伟大作家不同于常人的地方:他能从人所共见的人生现象中,发现别人不易发现的东西。
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个结尾,体现出了沈从文的高明和伟大,见证了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和一般作家的区别。
在现代文学作品中,以童养媳为题材的作品不少,如萧红的《呼兰河传》(小团圆媳妇儿)、冰心的《最后的安息》(翠儿)和王西彦的《命运》(路三嫂子)等等,但其中大部分都只是停留在对童养媳制度罪恶的控诉之上,很少有更深层次的挖掘。
沈从文关于“禁锢”的悲剧观——以沈从文笔下的《萧萧》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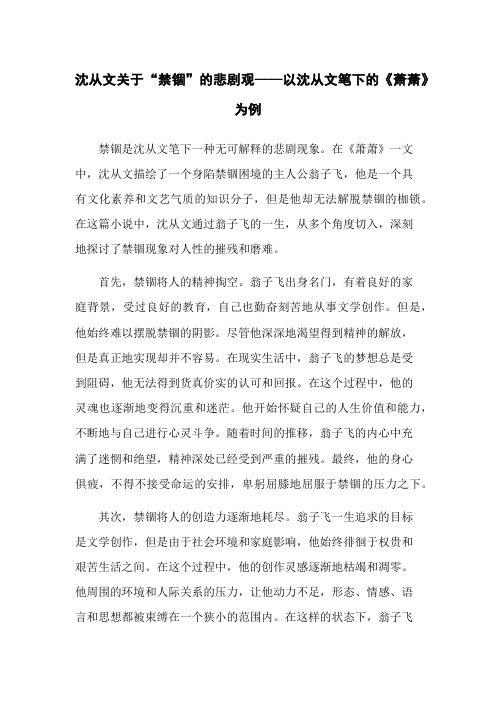
沈从文关于“禁锢”的悲剧观——以沈从文笔下的《萧萧》为例禁锢是沈从文笔下一种无可解释的悲剧现象。
在《萧萧》一文中,沈从文描绘了一个身陷禁锢困境的主人公翁子飞,他是一个具有文化素养和文艺气质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却无法解脱禁锢的枷锁。
在这篇小说中,沈从文通过翁子飞的一生,从多个角度切入,深刻地探讨了禁锢现象对人性的摧残和磨难。
首先,禁锢将人的精神掏空。
翁子飞出身名门,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受过良好的教育,自己也勤奋刻苦地从事文学创作。
但是,他始终难以摆脱禁锢的阴影。
尽管他深深地渴望得到精神的解放,但是真正地实现却并不容易。
在现实生活中,翁子飞的梦想总是受到阻碍,他无法得到货真价实的认可和回报。
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灵魂也逐渐地变得沉重和迷茫。
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价值和能力,不断地与自己进行心灵斗争。
随着时间的推移,翁子飞的内心中充满了迷惘和绝望,精神深处已经受到严重的摧残。
最终,他的身心俱疲,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卑躬屈膝地屈服于禁锢的压力之下。
其次,禁锢将人的创造力逐渐地耗尽。
翁子飞一生追求的目标是文学创作,但是由于社会环境和家庭影响,他始终徘徊于权贵和艰苦生活之间。
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创作灵感逐渐地枯竭和凋零。
他周围的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压力,让他动力不足,形态、情感、语言和思想都被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
在这样的状态下,翁子飞失去了对自己才华的信心,失去了对文学的热情,最终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总的来说,禁锢搅混了他的创作思路和创作动力,阻碍了他的文学之路。
此外,禁锢还让翁子飞的感情生活备受摧残。
在翁子飞的爱情世界里,他总是与他所爱的人相思相望,却因为社会和个人原因而无法相守。
克制和自我抑制成为了他生活的主旋律。
翁子飞既有恋爱的欲望又有理智的智慧,他深爱着自己所去爱的女子,却只能目送她远去。
这样的禁锢让翁子飞的情感生活充满了无尽的苦痛,内心矛盾折磨着他,他希望得到快乐,却总是陷入了绝境。
综上所述,沈从文笔下的《萧萧》揭示了禁锢的悲剧现象对人的灵魂、创造性和情感生活的摧残。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我所理解的沈从文笔下的“人性”
——以《萧萧》为例
华师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俞明海
沈从文的以描写湘西原始民风的作品,向来被赞誉为“歌颂人性的至美”、“表现人性美的力作”、“人性美的赞美诗”等等。
沈从文在其《从文习作选集代序》中的说过:“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
由此可见,在其湘西小说中,沈从文先生重在强调的是“人性”。
而小说《萧萧》作为沈从文的展示湘西原始的民风和朴素的人性的代表作品之一,自然而然的表现了其“神庙”所供奉的“人性”。
《萧萧》所写的便是一个童养媳的故事。
“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到了十二月是成天会有的事情。
”——小说《萧萧》,就从萧萧的出嫁开始。
萧萧作为童养媳出嫁时才十三岁,可她的“丈夫”断奶还不久。
她的丈夫还不到三岁,不过她也不懂得为这婚姻愁烦。
在为夫家做变相的免费劳工的日子,尽管婆婆象一把剪刀,把凡是给萧萧暴长的机会都剪去,却根本阻止不了萧萧一颗长大的心。
在大自然的荫护下,萧萧长大了。
在那如做梦般的夏日光景,萧萧偶尔听到了女学生,那神奇的另类。
惶恐后,竟模模糊糊地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女学生。
十五岁,萧萧被比她大十多岁的长工花狗用山歌长开了情窦,胡里糊涂地受引诱失身、怀孕,犯下了伤风败俗的“弥天大罪”,面临着被“沉潭”或“出卖”的严厉惩罚。
出事后,萧萧曾想收拾东西到,跟女学生走的那条路上城去“自由”,但终未成功。
就在绝望之中,她的命运出现了戏剧性转折——她并没有受到婆家人的“规矩”严惩,奇迹般地活下来。
最后到萧萧正式同丈夫拜堂圆房时,儿子已经年纪十岁,名叫牛儿。
牛儿十二时也接了亲,媳妇年长六岁唢呐吹到村前时,新娘在轿中鸣鸣的哭着。
小说是这样结尾的: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小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小毛毛哭了,唱歌一般地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
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也讨个女学生媳妇!”
初读此文,为萧萧的不抗争感到惋惜,会对这种蒙昧命运的轮回悲剧感到悲愤,并由此
而对沈从文所谓的“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感到不理解,甚至反感。
萧萧不懂得去反抗她的婚姻,也没有强烈的贞洁观。
对于命运,她只是顺从,只是蒙昧的接受,毫无怨言。
她的所谓的“上城去‘自由’”,也只是一种无意识的、无自主性的,只是按自己的性子的行事,根本就没有自我意识的争取自由,后文的“我们也讨个女学生媳妇!”就是力证。
而更令人悲愤的是,萧萧的这种蒙昧命运悲剧在轮回,将会被第二个,第三个“萧萧”重演。
然而,结合《边城》细读、细想之后,我觉得,造成难以理解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的原因是:沈从文先生所谓的“人性”,与我们是所理解的“人性”是有区别的。
沈从文先生强调的“人性”,基本不包含理性,是特指的自然状态的人性,是原始的野性的的生命力。
小说写的萧萧的成长,是一种原生的、自然的成长,她对于身处其中的婚姻制度、礼法制度从来没有过自觉的反抗。
她的一生却只能服从于外在力量的摆布,从来没有过对于自己的命运的自主的权力。
她的快乐里头,潜伏着无知与麻木。
萧萧的自然成长、蒙昧顺从命运,正是沈从文先生所谓的自然的“人性”。
在沈从文先生绝多数的湘西小说中,其所谓的“人性”,实际就是自在蒙昧的原始生命形态存在。
这种“人性”,其人往往是缺乏主体意志的自在存在。
《萧萧》中的萧萧为另一世界的“女学生”心动,幻想自己做女学生的情景。
“女学生”对于萧萧来说,显然是新奇事物。
但实际上,这一“新奇”事物在文章中的出现,只使两者的差距显得更加明显,只更突出萧萧的蒙昧无知的自然状态的存在。
将萧萧与《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对比,萧萧绝不会像现代娜拉那样出走。
因为在萧萧是世界里,人的主体意志是消失了的,人只是原始生命形态的存在。
人性的力量是天然的,却带着蒙昧的面目。
沈从文先生这样写的目的当然不实在突出萧萧的愚昧与无知,而是侧面强调萧萧的自然“人性”,强调自己神庙所供奉的“人性”。
为什么我们会难以理解、认同与接受沈从文先生的“人性”观念呢?
关于人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人的两大属性。
自然属性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生命力,侧重于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社会属性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创造力,侧重于强调人与社会的关系。
我们对于人的这两大属性存在较多的片面认识。
常常把人的自然属性直接等同于“动物性”,从而对于文学中人性描写中的人的一些自然属性的描写(比如“食”与“色”)当成是作人“动物性”的描写。
正因为存在这样的误区,以前的一些评论才对沈从文的人性描写作出了“活生生的春宫图”、与30年代的黄色歌曲是“姊妹篇”的结论。
在人的身上,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是有机统一,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共同构成人性的复杂内涵,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我们“文明人”所认同的“人性”,就是要伦理道德,要高扬个体精神,追求人的自由
发展,追求人的主体觉醒与主体意志的爆发,一如子君所言“我是我自己的”。
我们认同的“人性”,是“现代化”的“文明”的“人性”。
而沈从文小说中的“人性”,张扬的是人的强悍的生命力,肯定了人作为大自然的精灵所应该享受到的自然属性的欢乐,鞭挞的是人的虚伪、懦弱、自私。
沈从文先生强调的“人性”,基本不包含理性,是特指的自然状态的人性,是原始的野性的的生命力。
与浪漫主义者高扬的人性不同的是,沈从文先生的“人性”,崇尚的是自然的人性,不是心灵的自由激情。
沈从文先生在其《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
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
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
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对自己字典里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的叙写,一直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主旋律。
在他笔下,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童养媳、小店伙等等,都具有一种自然生命的美。
湘西的人们似乎“没有深沉的感慨,也不作高远的遐想,一切都听凭本能和习惯,自自然然地做去”。
读沈从文先生的湘西小说乃至其他小说,如果不能理解其理解的“人性”,如果不能明晰我们自己理解的人性与沈从文先生理解的人性的差异,就不可能读懂沈从文先生的小说,体会不出其中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倘若我们在读其湘西小说的时候,固执的带上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化”的“文明”的“人性”,就不仅不能读懂、不认同其价值,甚至会误读沈从文的小说,发出卫道士式的所谓的“我要说,不,沈从文的作品不是表现了人性的优美健全,恰恰相反,他的作品表现的是人性的贫困和简陋!”(刘永泰《人性的贫困和简陋——重读沈从文》)或者“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推进,为了真正优美健全人性的生成发展,拆毁沈从文的‘人性神庙’吧!”(刘永泰《<边城>人性美的质疑》)的“文明”的“疾呼”了。
在读小说,我们要出作家出发的那个角度,带着作家的情感,理解作家的作品。
而不是自以为是的以自我的标准去衡量作家的创作,去要求作家和作品规顺自己的阅读。
为什么沈从文先生字典里的“人性”会是一种“基本不包含理性,是特指的自然状态的人性,是原始的野性的的生命力”的人性呢?
沈从文读过两年私塾,正规教育仅是小学,他的知识和智慧更多是自然和人生这部大书给他的。
他曽经说过:自己始终与都市文明有一种难以消除的隔膜。
他将这种隔膜称为“乡下人”和“城市人”的隔膜。
根本上,他与城市人在生活、经验、知识乃至价值观上,具有无法沟通的天渊之别。
他的什么和情感,已经停留在那个给与他生命、知识和智慧的“想象中的湘西世界”。
在他看来,“城市”是民族文化的歧路,“现代文明”是对人性的一种阉割和扭曲。
在他看来,乡下原始、淳朴、自然的人性和人生,才是民族理想的精神和人生状态。
他还在《水云》一文中宣称:“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
”而这里的这个“生命”,就是自然状态的人性。
沈从文的这种“人性”、信仰与对文明的观点,究竟是对还是错?是进步还是倒退?这一点,本文没有能力回答。
这一点,自会有历史与时间去评价。
沈从文字典里的“人性”,是一种基本不包含理性,是特指的自然状态的人性,是原始的野性的的生命力的状态。
尝试抛开我们“文明人”理解的“人性”吧,用沈从文的“人性”观理解沈从文的“人性”,也许我们会更好地理解沈从文的作品。
参考文献:
1.沈从文《萧萧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沈从文《边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3.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上海书店1990年版
4.刘永泰《人性的贫困和简陋——重读沈从文》
5.刘永泰《<边城>人性美的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