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米修斯神话与民主政制的难题_柏拉图_普罗塔戈拉_中的神话解析_刘小枫
普罗米修斯形象的政治意味

文学评论・外国文学普罗米修斯形象的政治意味赖力嘉 四川大学摘 要:普罗米修斯作为希腊神话中一个广为人知的神祇,被众多学者文人加以创作。
在众多文本中,普罗米修斯总是作为一种“先驱”、“殉道者”的形象被人们反复歌颂。
但事实上,由于各个作者所处时代、创作意图的不尽相同,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变得复杂,对普罗米修斯形象的认识并非只有这种单一的解释。
本文将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讨论古希腊文学作品中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变迁背后的政治文化意义。
关键词:普罗米修斯;城邦;民主作者简介:赖力嘉(1992-),女,汉族,四川德阳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诗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2-147-01一、受罚者和立法人普罗米修斯形象最早见于赫西俄德(约公元前8世纪)的《神谱》和《工作与时日》。
《神谱》是对奥林波斯神族的形成和建立神权统治的历史的记叙;《工作与时日》则是描写人世劳作生活。
普罗米修斯先是和宙斯较量智慧,结果骗过了宙斯使之吃了暗亏;之后在火种问题上,宙斯不肯将这谋生之法传授给人类,普罗米修斯求而不得选择盗走火种;宙斯再三被骗,积怨已深,将灾难带给人类,并且将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的一块巨石上,不得自由。
赫西俄德诗作中反复出现诸如“伟大的宙斯意愿如此”,“欺骗宙斯和蒙混他的心志是不可能的”的话语,歌颂了宙斯的至高无上和他建立的诸神秩序。
而在《工作与时日》中大量的劝诫,警告人们要按照宙斯的安排从事农作。
至此天神和人类都生活在宙斯的秩序之下。
如果说《神谱》是在歌颂宙斯的权力和新生的奥林波斯秩序,那么《劳作与时日》则揭示了人类世界的两个根本秩序:正义和工作。
在主题如此鲜明的诗作中,普罗米修斯的存在显得格外具有深意。
既然“骗宙斯和蒙混他的心志是不可能的”,普罗米修斯又是如何做到一而再地骗过宙斯?既然身为“预知者”,他是否预知了自己将被绑在高加索山上的结局?赫西俄德的《神谱》有意识地重新建构了神话符号体系,使“神话服从于有意识的智力运作。
普罗米修斯盗火与宙斯立法——赫西俄德《神谱》和《劳作与时日》中的政治哲学意涵

普 罗米修斯 ( pwqa g 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 “ H o 06 ) 先见之明”正如他的弟弟厄庇米修斯 (  ̄ xOd ) , Er ' e q 的 qq 字 面 意思是 “ 后知 后觉 ” 一样 。但 阅读 赫 西 俄 德 的诗作 , 人 无法 不 面 对 这 样 的 追 问 : 个 具 有 “ 见 之 使 一 先 明” 的神 , 然应该 知 道 自己的命 运 , 以会 触 怒众 神 之 王 宙斯 , 显 何 最终 被 宙 斯 锁缚 在 柱 子 上惨 遭 巨鹰 啄 食 肝 脏之 苦? 又何 以 明知弟弟 厄庇 米修 斯 “ 后知后 觉 ” 却在 告诫 其不 要接 受来 自宙斯 的任何 礼 物 之后 撒 手 , 不管 , 以至人 世从 此 断绝 了其神 圣来 源 , 只能在 劳作 与艰 辛 中成就 其生 活 ?
Ap . r 201 2
第3 0卷 第 2期
V 13 o 2 o .O N .
普 罗 米 修 斯 盗 火 与 宙 斯 立 法
赫西俄 德《 神谱》 《 和 劳作 与 时 日》 的政 治哲 学 意 涵 中
张 杨
( 海南大学 社会科 学研 究中心 , 海南 海 口 5 02 ) 7 2 8
腊 哲学。
张杨 : 普罗米修斯 盗火 与宙斯立法 5 6) 5 。
这样 的叙 述 使人 更加 确 定 “ 人 ” 神一 已就 此 分 离 。就 像 让 一 埃 尔 ・ 尔 南 所 说 的 , 香 祭神 “ 皮 韦 焚 将人 和 神结 合 在 一 起 , 就 在 让 他 们 彼 此 接 近 的 那 一 刻 , 又 强 调 并 认 可 了把 两 者 彼 此 分 开 的 不 可逾 越 的距 但 它 离 。 …∞并且 , ” 。 当焚香 祭 神开 始成 为人 类 的传 统 时 , 与人 之 间 的尊卑 上下 之分 别也 已经 不言 而喻 。 神
古希腊悲剧普罗米修斯读后感

古希腊悲剧普罗米修斯读后感读《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有感于乐源11级建筑学20115570听完刘小枫老师讲课之后,才意识到《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这部看似简单易懂,线路单一的剧本竟然有深刻的含义。
经典之所以能历久弥新,不也因为其中最大限度的包含了作者的问题与想法而让人越读越有劲吗?这个故事并不复杂,以高加索山为背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被震怒的宙斯惩罚,火神赫菲斯托斯把他捆绑在蛮荒之地,让他时刻忍受煎熬和痛苦。
随后是普罗米修斯和奥克阿诺斯,少女们,伊奥,赫尔墨斯的交流,碰撞。
刘小枫老师首先抛出了一个解读的切入点,正义。
这是普罗米修斯和宙斯间的矛盾。
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火、传授技艺是正义的吗?在这里我首先想确定一下正义是什么。
正义的客观标准就是人们的行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
正义是人类社会普遍认为的崇高的价值,是指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观点、行为、活动、思想和制度等。
那么正义就是相对的了——不同人或集体对正义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正义观。
宙斯的统治是一种差距格局,文明技术和权威的结合——他所想要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为了自己,宙斯要用他的闪电劈碎诸神的言路和民主的思想,压迫无数向往自由的生灵给他进贡,要强迫少女奉献自己作为掌上玩物。
在这种环境中的绝大多数人——除了宙斯和宙斯的狗腿——都不会幸福。
难怪立志为人类奋斗终生的马克思称普罗米修斯为哲学日历上最高的圣者,把他当做自己永远的精神榜样。
相对于普罗米修斯,懦弱而善良的火神赫菲斯托斯——虽然他们都是仁慈的神,并且这仁慈是他们的感情基础——伏在父神宙斯的羽翼之下,执行自己不愿意做的任务——把自己的同伴钉在艰苦的高加索山脉,让他永远忍受着煎熬。
因为他不仅敢于像伊壁鸠鲁那样敢于冒险,挑战权威,藐视统治者,在如此专制的环境中不放弃民主世界的信念与思想;他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改变差序的格局,把思想的结晶宣布与世。
但是,我并不认为普罗米修斯给人类带来技术能够从根本上帮助人类。
古希腊神话故事普罗米修斯故事

古希腊神话故事普罗米修斯故事嘿,伙计们,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可是关于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大神——普罗米修斯哦!你们可要好好听我说,这个故事可是充满了惊险、感人和幽默的元素,保证让你们听得津津有味,哈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普罗米修斯吧。
他是个非常聪明的神,据说他还是人类的始祖赫菲斯托斯的老师呢!普罗米修斯最著名的事迹就是他为人类偷来了火种。
你们知道吗?在古代,人们还没有火种,生活可真是苦哇!每天都要靠生食和熟食之间反复加热来取暖,而且还容易生病。
普罗米修斯看到人类这么可怜,就决定帮他们一把。
于是,他偷偷地从天上拿了一颗火种,带给了人类。
从此,人类就有了火种,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但是,这个行为却惹恼了众神之王宙斯。
宙斯认为普罗米修斯是在挑战他的权威,于是他派来了一只鹰把普罗米修斯抓走了。
接下来的故事就更加精彩了!普罗米修斯被关在了高加索山上的一座神庙里,每天都有一只大鹰啄食他的肝脏。
但是,普罗米修斯并没有向宙斯屈服,他决定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逃出神庙。
他找来了一只老鹰,告诉它自己的计划。
老鹰答应了他的请求,帮他一起逃离神庙。
于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普罗米修斯带着老鹰来到了神庙。
他们成功地逃出了神庙,但是老鹰在飞回高加索山的路上被猎人抓住了。
普罗米修斯为了救老鹰,只好把自己绑在了一块巨石上。
这样一来,宙斯就无法把他带走了。
宙斯看到了这一切,也被普罗米修斯的勇敢和智慧所感动。
于是,他允许普罗米修斯回到了人间,并且每年都会给他带来一种特殊的礼物——橡树果实。
这些橡树果实可以用来造火柴,让人类永远不会失去火种。
好了,故事讲完了。
你们觉得普罗米修斯是个英雄吗?我觉得他绝对是个超级英雄!他为了人类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这种精神真的是太值得我们学习了。
而且,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有智慧和勇气,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所以,大家一定要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勇往直前,永不言败哦!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成语——“自投罗网”。
典故:这个问题就像是普罗米修斯的火种,点燃了无数人的思维。

典故:这个问题就像是普罗米修斯的火种,点燃了无数人的思维。
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英雄,他给人类带来了火种,
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
与之类似,这个问题也点燃了无数人的思维,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
正如普罗米修斯的火种给人类带来了文明和进步,这个问题也
给人们带来了思维的启迪和创新的动力。
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
探索,促使了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和认识的深化。
普罗米修斯的火种象征着知识和智慧,而这个问题也在点燃人
们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
通过探讨这个问题,人们可以不断研究和
成长,拓宽自己的视野,开拓新的思路。
另一方面,普罗米修斯的火种也带来了不确定性和挑战。
当人
类获得了火种后,他们必须学会如何运用它,才能避免被它所烧伤。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需要注意思维的深度和广度,避免盲目追求
和错误的方向。
总之,这个问题就像是普罗米修斯的火种,点燃了无数人的思维。
它引发了人们的思考、讨论和创新,使我们不断向前进步。
我们应该珍视这个问题,并用智慧和创造力去回答它,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贡献。
普罗米修斯

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巨神,他被认为是最早的文明者和人类的创造者之一。
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有着深刻的含义和启示,被广泛运用于文学、艺术和哲学领域。
普罗米修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希腊神话的创世纪,他是克里奥斯(时间)和厄勒涅耳(黑暗)的儿子,是泰坦神族的一员。
当他的兄弟宙斯成为了奥林匹斯众神的王者后,普罗米修斯成为了他的忠实臣子,并负责管理人类的事务。
据说在人类刚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宙斯将火种赐给了人类。
然而,由于宙斯对人类非常不满,他决定把火给收回去,让人类生活在黑暗和寒冷中。
普罗米修斯为了保护人类,偷走了火,带给人类光明和温暖。
宙斯对此非常愤怒,他惩罚普罗米修斯的方式非常残酷。
他让赫淮斯托斯锁住普罗米修斯,用一只鹰来啄他的肝脏,每天重复这个过程,直到他的肝脏生长完全恢复。
这个折磨一直持续了数年,直到赫拉克勒斯将普罗米修斯解救出来。
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体现了人类对光明和知识的追求,但也暴露出神与人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
他受到的惩罚也反映了宙斯的暴虐和独裁。
普罗米修斯在文学、艺术和哲学领域里也有着广泛的影响。
在古希腊文学中,他常被描述为创造者、教师和英雄。
而在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则象征着不服从和反抗,代表着个性和自由。
例如,雪莱的诗歌《普罗米修斯解放》就是以他的故事为蓝本的。
其他文艺作品,如悲剧《普罗米修斯受刑》或歌剧《普罗米修斯就义》,更是将他的故事解读为意义深刻的启示和带有强烈批判性的社会政治寓言。
总的来说,普罗米修斯是一个重要的神话形象,他的故事以及对文学、艺术和哲学的影响,使他成为西方文化中一个有着极高象征意义的人物。
他的故事反映了我们对光明和知识的渴望,以及我们所面对的权力、人性和罪恶。
普罗泰戈拉简介

普罗泰戈拉简介普罗泰戈拉是公元前五世纪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是当时著名的智者派的代表性人物,下面是店铺搜集整理的普罗泰戈拉简介,希望对你有帮助。
普罗泰戈拉简介普罗泰戈拉生于公元前490年或者是480年,卒于公元前420年或者是410年,大约活了七十岁,出生地是阿布德拉城,公元前五世纪是希腊城邦民主政治高度发展的时期,普罗泰戈拉是当时著名的智者,在哲学和伦理学方面都有非常高的成就,但是后来却因为“不敬神灵”被指控,其著作被烧毁,本人被赶出了雅典。
普罗泰戈拉曾经多次来到当时希腊的政治中心雅典,并且与当时的民主政治家伯利克里是至交好友,据说曾经为当时希腊的殖民地图里城制定过法典,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学习机会,并且宣扬自己的主张,普罗泰戈拉在各地旅行,并且广泛的收授徒弟,教给他们修辞以及论辩的知识。
普罗泰戈拉是当时非常著名的智者派成员,受到人们广泛的敬重。
普罗泰戈拉著有《论神》、《论真理》和《论相反论证》等,在这些著作中系统的介绍了普罗泰戈拉的哲学思想和伦理思想,但是不幸的是晚年的时候普罗泰戈拉却被指控“不敬神灵”,并且因此获罪,统治者将普罗泰戈拉的著作搜集起来在雅典的广场上予以焚毁,并且将普罗泰戈拉赶出了雅典城,之后普罗泰戈拉渡海前往西西里岛,但是不幸在路上就去世了。
今天的人们之所以能够了解到普罗泰戈拉的情况完全得益于柏拉图的对话《泰阿泰德篇》、《普罗泰戈拉篇》中记述了普罗泰戈拉的思想与言行。
普罗泰戈拉的故事一次普罗泰戈拉教了一个叫做欧提勒士的学生,并且预先收了这个学生一半的学费,另外的一半两个人约好等到欧提勒士在法庭上打赢第一场官司之后再付给普罗泰戈拉,师徒两个人还签订了一份合同,声明如果欧提勒士的第一场官司输了的话就不必付另一半学费了,如果赢了就要付清另一半学费。
欧提勒士毕业之后并不出庭打官司,所以就不会有输赢,那么另一半学费普罗泰戈拉就没有办法收回来了,经过思考普罗泰戈拉向法庭提出了起诉,要求欧提勒士付清另一半学费,普罗泰戈拉认为如果欧提勒士官司赢了就应该付给自己学费,如果欧提勒士官司输了根据判决也应该付给自己另一半学费。
普罗米修斯盗火神话及其文化意蕴

普罗米修斯盗火神话及其文化意蕴普罗米修斯是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中注释道:“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狄坦神,他从天上盗取火种,带给人们;宙斯把他锁缚在悬崖上,令鹰啄食他的肝脏,以示惩罚。
”在这个盗火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三点特质让马克思产生共鸣。
首先,普罗米修斯是反抗不合理的觉醒者。
在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火之前,由于宙斯禁止人类用火,人类的生活黑暗而困苦。
普罗米修斯看到人类的苦难,因而挺身出来反对。
面对宙斯等神的非理性行为,他抗议说:“总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认为,普罗米修斯的这句话“就是哲学自己的自白,是哲学自己的格言,表示它反对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
以此,马克思表明自己的无神论立场,期待一种高扬人的自我意识、促进人和世界变得合理的哲学。
马克思坚持认为哲学家应该秉持批判精神以对抗现实中的不合理因素。
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的任务,以此不断实现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其次,普罗米修斯是播撒光明的启蒙者。
普罗米修斯从太阳神阿波罗处偷走天火,将光明播撒至人间。
从表面看,人间从此有了光明,不再是黑暗一片。
古希腊作家埃斯库罗斯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写道,“他们可以用火学会许多技艺”“我为他们发明了数学,最高的科学;还创造了字母的组合来记载一切事情,那是工艺的主妇,文艺的母亲”“人类的一切技艺都是普罗米修斯传授的”。
可见,普罗米修斯予人以极大的信任,尽可能地从多个方面帮助人、赋予人技艺。
普罗米修斯对人的信任,与西方哲学史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认为哲人要避世的态度形成对比——柏拉图曾因为苏格拉底之死而提出哲人应该对自己的理论采取隐微态度,以此规避理论无法被接受而带来的风险。
类似于柏拉图的态度在西方哲学家中并不在少数,提出“大众”(mass)一词,并普遍地视大众为一个消极的、有待于改善的对象便是证明。
戏剧欣赏丨5分钟了解古希腊三大悲剧

戏剧欣赏丨5分钟了解古希腊三大悲剧希腊悲剧古希腊悲剧一般主要写主人公的个人意志和命运的冲突。
早在古希腊的神话里,命运就是支配神和人的无上力量。
按古希腊人的观念,命运是不可抗拒的,是不可知的, 它既支配人,也支配神。
这种命运观产生的社会背景是人类处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期。
01这里的翡翠件件精品,工厂直供,成本价!《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它描写普罗米修斯被钉在悬崖上遭天帝宙斯惩罚受苦刑的情景,渲染出浓重的悲剧气氛。
作品歌颂了普罗米修斯为人类不惜牺牲一切的崇高精神,肯定了雅典奴隶主民主派反对专制统治的正义性,同时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宙斯的暴虐和专横。
02《俄狄浦斯王》取材于古老的传说。
俄狄浦斯王杀父娶母,自己却毫无所知。
为了平息忒拜国内流行的瘟役,按照神的指示,俄狄浦斯寻找杀害前王拉伊俄斯的凶手,结果发现要找的凶手就是自己。
王后伊俄卡斯忒的在悲痛中自尽,俄狄浦斯自己在百感交集中刺瞎了双眼,一步步把戏剧冲突推向高潮。
剧本热烈歌颂了俄狄浦斯的坚强意志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并对当时流行的命运观提出了怀疑。
在艺术上,索福克勒斯的悲剧结构比较复杂,布局非常巧妙,被文学史家们誉为“戏剧艺术的荷马”。
展开剩余50%03《美狄亚》伊阿宋是传说中的一个令人敬爱的英雄,娶美狄亚为妻,回国后为了个人前途另寻新欢。
伊阿宋由一个勇敢的英雄变成了卑劣的小人,美狄亚由一个多情的少女发展成为敢于反抗的妇人,原本歌颂英雄的故事,变成了谴责社会罪恶、控诉不平等现象、赞美反抗行为的悲剧故事。
三大悲剧的命运观念都有不同,但都围绕着人的意志与命运的冲突的主题,其主题不断的由神向人转换,渐渐重视人的作用。
悲剧作品中的主人公面对落到头上的不公的命运,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也让人看到了古希腊悲剧中命运观念的发展:传统的、带有宗教宿命论色彩的古希腊悲剧早期的命运观念逐渐被具有进步性和现代性的人性命运观取代。
当今时代,个人的命运要努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为您牢牢守住和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是我们一贯的服务承诺!未来的路还很漫长,农行私行将与您一路同行,让我们携手相伴,共创美好明天!。
普罗米修斯深度解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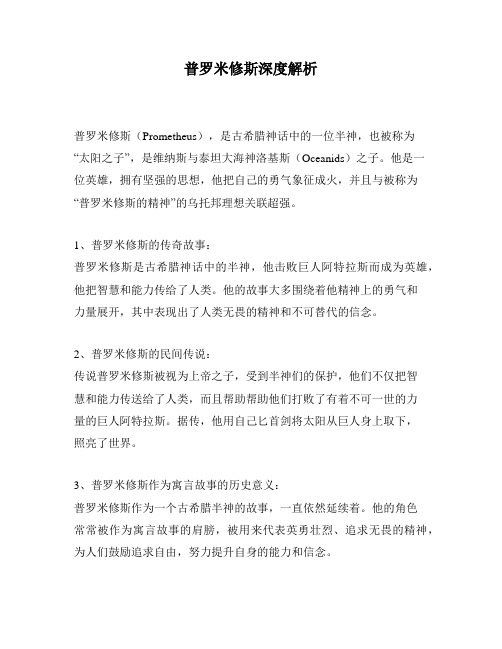
普罗米修斯深度解析
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半神,也被称为“太阳之子”,是维纳斯与泰坦大海神洛基斯(Oceanids)之子。
他是一
位英雄,拥有坚强的思想,他把自己的勇气象征成火,并且与被称为“普罗米修斯的精神”的乌托邦理想关联超强。
1、普罗米修斯的传奇故事:
普罗米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半神,他击败巨人阿特拉斯而成为英雄,他把智慧和能力传给了人类。
他的故事大多围绕着他精神上的勇气和
力量展开,其中表现出了人类无畏的精神和不可替代的信念。
2、普罗米修斯的民间传说:
传说普罗米修斯被视为上帝之子,受到半神们的保护,他们不仅把智
慧和能力传送给了人类,而且帮助帮助他们打败了有着不可一世的力
量的巨人阿特拉斯。
据传,他用自己匕首剑将太阳从巨人身上取下,
照亮了世界。
3、普罗米修斯作为寓言故事的历史意义:
普罗米修斯作为一个古希腊半神的故事,一直依然延续着。
他的角色
常常被作为寓言故事的肩膀,被用来代表英勇壮烈、追求无畏的精神,为人们鼓励追求自由,努力提升自身的能力和信念。
4、普罗米修斯的具体形象:
普罗米修斯的具体形象,是一个头戴青铜冠冕、衣衫褴褛,有着双足
俯膝、右手间一把长剑的正义英雄。
他身上散发着神圣气息,吸引着
所有看见过他的人,令人尊敬而畏惧。
5、普罗米修斯所代表的乌托邦理想:
普罗米修斯的乌托邦概念,就是个人的自由、勇敢的追求自由、和平
的生活,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不仅被认为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哲学,从而影响后面实践变成一种改造社会的行为,也是古希腊一贯追求的
理想情怀。
希腊神话故事普罗米修斯的主要内容

希腊神话故事普罗米修斯的主要内容嘿,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个在希腊神话里超级有名的家伙——普罗米修斯。
首先,大家都知道普罗米修斯这名字不怎么容易念对吧?别担心,我们就叫他“普罗”,省得绕口。
1. 普罗米修斯的前情提要好啦,普罗米修斯这位大神其实是泰坦神族的一员。
泰坦神族在神话里可是老一辈的神,能量满满,气场十足。
普罗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家伙,跟那些爱发脾气、爱争权的泰坦不一样。
他有点像那种过于热心肠的邻居,总是想着怎么帮忙。
他不仅是天生的心善,还很聪明,这让他在神话故事中与众不同。
1.1 神偷的角色普罗的传奇开始于他偷火这个事儿上。
说实话,这事儿听起来简直像是个恶作剧,但他真的干了!古希腊的神话里,人类那会儿过得可惨了,没火、没热水,过着石器时代的苦日子。
普罗看不下去了,心想,“哎呀,这帮小可怜的家伙可真不容易,我得给他们点热乎的。
”于是,他就偷了天神之火,从神界带到了地球。
要知道,这可是大忌啊!就像是你偷了邻居家最新款的电视机,还没顾上逃跑呢,已经被抓了。
1.2 代价与惩罚事情没那么简单,偷火的事儿一传开,天神宙斯可炸了锅了。
宙斯是个典型的高冷老板,啥事都喜欢搞个大新闻。
这一次,他决定给普罗一个特别“温馨”的欢迎。
普罗被抓住了,被绑在了高加索山上。
每天,一只大鹰都会来啄他的肝脏,而肝脏每天都会再生。
简直是永无止境的折磨,跟那种永远做不完的作业简直一个道理。
2. 普罗米修斯的英雄救赎在普罗受尽折磨的同时,别忘了他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英雄。
话说,有一天,赫拉克勒斯(就是那个十二劳作的大力士)路过这儿,看到普罗在山上受难,心里挺不忍的。
赫拉克勒斯这小子可是有些英雄情结的,他对普罗说:“别担心,我来救你!”于是,赫拉克勒斯一箭射死了那只害人的大鹰,解救了普罗。
普罗虽然从山上解放了,但他还是得继续忍受其他的折磨。
不过,赫拉克勒斯的这一行为,多少让普罗觉得人生有点希望了。
2.1 普罗的遗产虽然普罗过得不太如意,但他留给人类的却是无价的财富——火。
神话原型理论下《普罗米修斯的解放》的精神启示

142一、普罗米修斯神话内容和起源希腊的普罗米修斯神话与人类苦难和死亡以及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和神性的疏离有关,人类的思考和对火的使用分别代表着人类对神的一定的怀疑和人类对美好的物质生活的向往。
普罗米修斯是一位泰坦神,这意味着他属于神的时代先于奥林匹亚诸神宙斯、阿波罗、雅典娜等。
宙斯的父亲是克罗诺斯,而他的父亲是伊阿佩托斯是泰坦之神,他是泰坦的后裔,他的母亲是克吕墨涅。
他从父亲那里获得了力量、聪明才智和雄心,而他母亲那里获得了宽阔的胸怀和长远的眼光。
宙斯在宇宙战争中击败父亲之后,,召普罗米修斯帮助建立等级制度。
在神界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为了维护人类的权益,普罗米修斯杀了一头牛,把牛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一包厚厚的白色动物脂肪,里面藏着光秃秃的白骨和所有可食用的肉。
另一部分则是将所有的可食用的肉,包在牛的皮里,放在牛的肚子里。
宙斯选择包裹在脂肪里的诱人的骨头,于是人类就获得了含有可食用肉的胃。
宙斯对这个把戏很生气 (尽管他已经知道包裹的内容),并将火从人类使用中撤回,从而让他们无法制作美食。
而之后普罗米修斯取了一个巨大的茴香茎来将宙斯的火种盗走。
宙斯再次愤怒,并决定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以确保人再也不能挑战神。
潘多拉女神是一个美丽无比的女神,但她完美的外表下隐藏着恶毒的心,宙斯通过潘多拉对迪欧普罗米修斯的兄弟伊皮米修斯进行诱惑,而伊皮米修斯最终也无视弟弟普罗米修斯的劝告迎娶了潘多拉,使得最后潘多拉魔盒在人间打开,魔盒中蕴含着世界上一切的不幸和疾病,这些也被释放在人间。
自那以后,所有的男人都必须通过女人生育与繁殖。
普罗米修斯则被锁在荒野的一块岩石上数千年,在那里宙斯的鹰每天吃掉他的整个肝脏,再让其在夜晚恢复,依此往复来折磨普罗米修斯。
在埃斯库罗斯创造的版本中,普罗米修斯被锁链锁住了3万多年后,在宙斯的允许下,他的儿子赫拉克勒斯杀死了老鹰并释放了普罗米修斯。
二、《普罗米修斯的解放》的创作当雪莱还在学校读书时,其思想就形成了。
课文 普罗米修斯 课文内容提出问题

课文普罗米修斯课文内容提出问题《普罗米修斯》:一场关于人类命运和自由意志的思辨1. 引言在人类文明史上,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作为一篇寓言故事,它涉及了人类的命运、自由意志以及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引发了无数文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对这一主题的深入探讨。
在本文中,我们将以《普罗米修斯》为主题,以从简到繁的方式展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探讨。
2. 对《普罗米修斯》主题的浅显理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发生在古希腊神话时代,主要讲述了普罗米修斯偷取了火种给了人类,导致宙斯的愤怒并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这个故事引发了很多问题,比如普罗米修斯是如何看待人类的命运的?他的行为是否符合自由意志的原则?宙斯对普罗米修斯的惩罚是否过于严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思考。
3. 对《普罗米修斯》主题的深入思考3.1 人类的命运在故事中,普罗米修斯偷取了火种给了人类,这个行为给了人类文明以巨大的进步,但也引发了神祇的震怒。
这让我们思考,人类的命运究竟是被神明决定的,还是要靠自己的奋斗和努力来改变?普罗米修斯的行为是否是在帮助人类改变命运,还是触犯了神明的意愿?这些问题都触及了人类的自我认知和对未来的思考。
3.2 自由意志故事中的普罗米修斯用自己的行动改变了人类的命运,这是否是他所拥有的自由意志的表现?亦或者他只是在扮演着神明安排好的角色?这些问题涉及到人类的自由意志和命运的掌控,是我们思考人类存在意义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议题。
3.3 宙斯的惩罚在故事中,宙斯对普罗米修斯的惩罚让人深思。
他是否过于严厉?他的行为是否是出于对人类的担忧和对自身权力的维护?这个问题可以引发我们对于权力和公正的思考,对于神明与人类的关系的思考。
4. 总结和回顾通过对《普罗米修斯》这一主题的深入探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寓言,更是关于人类命运和自由意志的思辨。
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可以思考人类的命运、自由意志以及神与人之间的关系。
普罗米修斯ppt课件

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带来火种,体现 了他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这 启示我们要有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 神。
对人类未来的启示
面对挑战
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提醒我们,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和挑战,我们 都需要有勇气和坚定的信念去面对。
科技与道德
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中涉及到科技的运用和道德的判断,这启示我们 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思考科技与道德的关系。
智慧与创造性的思维
总结词
普罗米修斯的另一个重要价值观是智慧和创造性的思维。在面对问题时,我们需要运用智慧和创造力寻找解决方 案,不断开拓新的领域。
详细描述
普罗米修斯作为众神的创造者之一,他的智慧和创造性思维为人类带来了很多福祉。他不仅教会了人类如何生存 ,还为人类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应该学习普罗米修斯的智慧和创造性思维,积极探索新 的方法和思路,为解决问题和创新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要点二
详细描述
在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是人类的创造者之一,他不 仅赋予了人类生命,还教会了人类如何生存。然而,他的 行为触犯了宙斯的规定,遭到了残酷的惩罚。普罗米修斯 在面对困难和痛苦时,展现出了勇敢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他从未放弃自己的信仰和追求。这种精神对于我们在面对 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CHAPTER 05
普罗米修斯的启示
对个人成长的启示
勇气和坚持
普罗米修斯面对巨大的压力和困 难,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为人 类带来火种,这启示我们在面对 困境时,需要有勇气和坚持去追
求我们的目标。
独立思考
普罗米修斯不愿接受既定的命运 ,独立思考并采取行动改变自己 的命运,这启示我们要有独立思
考的能力,勇于挑战现状。
然而,这一行为激怒了宙斯, 宙斯决定对普罗米修斯进行惩 罚。
普罗米修斯反思

普罗米修斯反思
瑞塔铺小学高红春
《普罗米修斯》是一篇希腊神话,这个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感人,语言准确,结构清楚,在课文中,还非常注意人物的个性描写,特别是普罗米修斯,他的勇敢、极富同情心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篇课文的重点和难点是感悟普罗米修斯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从有关语段的描写中体会人物的心情。
在教学时,我一开始是让学生想象人类在没有火时的生活画面,再想象有了火人们过的幸福生活,让两个画面对比更明显。
这篇课文重点是感受普罗米修斯遭受惩罚部分,从“锁”和“啄”两个词中,体会普罗米修斯所承受的漫长的痛,让学生感受普罗米修斯的伟大精神,同时认识、了解神话的特点。
这节课也存在一些不足。
由于这一节课的内容设计较多,为怕时间不够,在让学生回答问题上,我没有充分的让学生发挥,学生思考的时间很少,读书的时间也不多。
在今后的教学中,要特别注意发挥学生的潜能,课堂上尽可能让学生多发表,只有这样,让学生各抒己见,才能更快的成长。
普罗米修斯哲学意义

普罗米修斯哲学意义普罗米修斯,那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啊!在古希腊神话中,他可是个敢和众神叫板的狠角色。
你想想,他从众神那里偷来了火种,送给了人类。
这就好比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突然有人点亮了一盏明灯,那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这火种可不单单是个火苗,它代表着希望、智慧和进步。
就像咱生活中,突然有了个超级厉害的发明,能让一切都变得不一样。
普罗米修斯这一举动,那是相当勇敢的。
他明知道会惹怒众神,可还是义无反顾地去做了。
这就像现实中那些敢于挑战权威,为了真理和正义不顾一切的人。
他们不怕困难,不怕被人嘲笑,就是要去追求自己心中的那个目标。
他的行为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无私的奉献精神。
他为了人类,不惜自己受苦受累,甚至遭受残酷的惩罚。
这多像那些默默为我们付出的人啊,比如我们的父母,他们总是把最好的给我们,自己却不辞辛劳。
还有那些在各个岗位上辛勤工作的人们,他们为了大家的生活更美好,一直在努力着。
普罗米修斯哲学意义重大啊!他让我们知道,人要有勇气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能因为困难就退缩。
就像咱平时遇到点小挫折,难道就放弃啦?那可不行!得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勇敢地向前冲。
而且他也告诉我们,要学会奉献,不能只想着自己。
如果每个人都自私自利,那这个世界还能好吗?大家都互相帮助,互相关爱,这世界不就变得更美好了嘛。
再想想,普罗米修斯被绑在高加索山上,每天被老鹰啄食肝脏,那得多痛苦啊!可他都没有屈服,这是多么强大的意志力啊!咱在生活中也会遇到各种困难和痛苦,难道就轻易被打倒啦?得学学普罗米修斯的坚韧不拔。
他就像是我们心中的一座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让我们知道,只要有勇气、有奉献精神、有坚韧的意志,就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咱不能辜负了普罗米修斯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宝贵财富啊!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流传了这么久,不就是因为他身上的这些品质值得我们一直学习吗?他的哲学意义就像是埋在我们心底的一颗种子,只要我们用心浇灌,它就能生根发芽,让我们变得更加优秀,更加勇敢,更加有爱心。
普罗米修斯深度解析

这是一部极好的片子,但是看了一连串的影评,多数是骂娘的,骂娘的都是没看懂,觉得导演糊弄观众了。
也有少数影评是在捧,在分析的,但又捧的地方又不对,分析也全不在点上。
索性自己写一篇,给自己理思路,也给大家理思路,并请诸位冷静等待斯科特的导演剪辑版。
1. 楔子一直很好奇中国古典小说的写法。
现代小说的写法是要注意结构的,如同砌墙造屋,严丝合缝,首尾相应,不多一条梁,不少一只角。
但古典小说却如同一片荒原,四野茫茫。
从最遥远处的一星墨点开始勾绘宏大的框架。
西游记的开头是“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
”封神榜从盘古开始说起,红楼梦的开头是女娲补天,多出了块石头,故名《石头记》。
镜花缘从王母过生日说起;三国和水浒算是写实派,一个从周朝说起,一个从本朝说起此类楔子几乎成了小说必备,一番长长的叙述,但与之后要开始的故事完全脱节,往往要到了结局时分,才知道楔子的作用。
就好似佛所说的因缘,楔子的存在就是为了证因果,讲道理。
旧时茶馆里的说书人,讲到结局时,惊堂木一拍,听众恍然大悟,原来中心思想在这里等着你呢!但最初故事的产生并非为了宣扬枯燥的伦理道德,而是为了纯娱乐。
在那个文字还没建立的远古,无书可读,没有电影,没有电视,没有非诚勿扰和原始好声音。
夜晚野兽出没,整个部落的人只能点起火堆,围坐在一起,讲天花乱坠的故事,这是消遣,也是一种安全感。
在人类文明发展之后,依然很流行讲故事,只是讲故事这件事开始变得低俗。
古人说“文以载道”,但在古人说这句话时,“文”并不包括小说。
文是八股文,修身治国平天下。
写小说是要被人看不起的(写黄色小说更是被人看不起,至今无人知晓写出《金瓶梅》的兰陵笑笑生的真实身份)所以,小说是不负责“载道”的,要写得跌宕起伏,吸人眼球才是正经事。
到了近一百年,五四运动,中国的小说越写越开始讲道理。
于是,鲁迅就开始指责起那些只讲故事而不启民智的鸳鸯蝴蝶派来------这是题外话。
回过来说“载道”。
想要“载道”又必须会讲故事,孔孟都是讲故事的好手,诸子百家在各地游说诸侯王,都是要先说段故事,然后才讲道理,于是王信服。
普罗米修斯 解析

普罗米修斯解析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一位英雄人物。
他是卓越的创造者和智者,也是人类的朋友和保护者。
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充满了悲壮和勇敢,他为人类带来了火种,挑战了众神的权威。
在这个故事中,普罗米修斯以人类的视角展示了对自由和进步的渴望。
普罗米修斯是泰坦神族之一,他与众神相互对立。
他创造了人类,并教会他们农业、医药和其他许多技艺。
然而,众神却嫉妒人类,将他们束缚在黑暗中,无法享受到火的温暖和光明。
普罗米修斯看到人类的苦难,决定帮助他们。
为了夺取火种,普罗米修斯冒着巨大的风险。
他爬上奥林匹斯山,偷走了火种,并把它带给了人类。
火的到来,为人类带来了光明和温暖,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然而,众神发现了普罗米修斯的行为,他们愤怒地惩罚了他。
众神将普罗米修斯绑在了一块岩石上,并派来了一只巨大的秃鹰,每天啄食他的肝脏。
普罗米修斯忍受了无尽的痛苦,但他从未后悔过他为人类做的一切。
他坚信,人类应该拥有自由和进步的权力,而他的牺牲将会为人类带来希望和机遇。
经过长时间的折磨,普罗米修斯最终被赦免了。
他的故事传诵于世,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传奇。
普罗米修斯的精神激励了无数人,他的勇气和智慧成为人类追求进步和自由的象征。
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信念而奋斗。
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和挑战,我们都应该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勇敢地追求自由和进步。
我们应该珍惜智慧和创造力,为人类的幸福和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永远不会被遗忘。
他的精神将激励我们不断前行,追求真理和进步。
让我们铭记普罗米修斯的勇气和智慧,为人类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让我们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点燃心中的火焰,为自由和进步而努力。
《普罗米修斯》优秀课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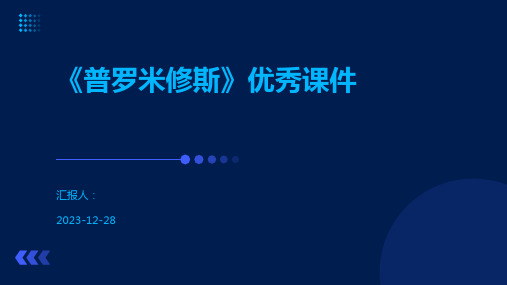
强调道德责任
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的福祉而不惜牺牲自己,提醒现代人在面对道德抉择时,应勇于承担责任,关注他人的福祉 。
对人类未来的思考
反思科技伦理
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引发人们对科技伦理 的深入思考,在科技发展过程中,如何 平衡人类的利益与道德责任是值得关注 的问题。
科学与宗教
《普罗米修斯》中科学与宗教的主题也值得 探讨。影片中科学家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与 宗教对神的信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引发了 对科学和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的
思考。
THANKS
谢谢您的观看
VS
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
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激发人们对未来人类命 运的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和谐、平等、公 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 题。
05
普罗米修斯的评价与反思
观众与批评家的评价
观众反馈
观众对《普罗米修斯》的评价褒贬不一。一 些观众认为影片的视觉效果和氛围营造非常 出色,而剧情和角色发展则较为薄弱;另一 些观众则认为影片的深度和内涵远超一般科 幻电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思考空间。
人类的起源
普罗米修斯作为人类的创造者, 为人类带来了智慧和技艺,使人 类得以在世界上生存和发展。
普罗米修斯的人物介绍
普罗米修斯
作为故事的主人公,他是一位智慧和 勇敢的神祇,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 自我牺牲精神。
宙斯
作为众神之王,他对普罗米修斯的惩 罚和压迫体现了权力和权威的冷酷和 自私。
普罗米修斯的主题思想
04
普罗米修斯的影响与启示
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激发了科幻文学的创作灵感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自然、自然状态与自然法普罗米修斯神话与民主政制的难题——柏拉图《普罗塔戈拉》中的神话解析刘小枫摘 要 民主政制的正当性论证,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论题,其中的一些理论难题迄今没有世所公认的答案。
自然状态论是现代民主政制理论的基石,然而,政治哲学中的自然状态论并非17世纪的西方理论家的发明,古希腊的政治理论中最为成形的自然状态论见于柏拉图的著名对话《普罗塔戈拉》中的普罗米修斯神话。
智术师普罗塔戈拉史称西方第一位政治学家,他通过编造普罗米修斯神话提出了一种政治的自然起源说。
但与17世纪的哲人通过自然状态论来论证民主政制不同,普罗塔戈拉的自然状态论却是要论证君主制的正当性。
可见,自然状态论也可以证明民主政制的正当性难以成立。
关键词 柏拉图 苏格拉底 普罗塔戈拉 普罗米修斯 民主政制作者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6)05-0005-08现代民主政制的理论基础是霍布斯设计的政治社会的自然起源论证,也就是随后经洛克和卢梭发展的著名自然状态说。
从自然状态出发探究政治社会的起源并非霍布斯的发明,毋宁说,以这种方式论证某种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是一种古希腊传统。
a无论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曾从自然状态出发探究政治社会的起源,但他们并没有得出民主政制是最佳政制的结论。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圣人政制论同样基于某种政治社会的自然起源论。
因此,如今的我们很难说自然状态论堪称民主政制法理的坚实基础——毕竟,依据某种自然状态说,人们也可以得出君主制-贵族制的混合才是最佳政制的结论。
柏拉图的《普罗塔戈拉》为此提供了一个饶有兴味的例证——在这篇对话中,著名智术师普罗塔戈拉讲了一个神话故事,以此演示他对人类政治生活的自然起源的理解。
就现存古希腊文献来看,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与普罗塔戈拉的这个神话故事中的自然状态论最为相似。
也许正因为如此,普罗塔戈拉被一些现代学者视为现代政治科学的古代先驱。
b然而,尽管普罗塔戈拉的“政治学”甚至带有现代意味,他的自然a 李猛:《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90—105页。
b 米勒:《作为修辞共同体的城邦》,刘小枫编:《古希腊修辞学与民主政制》,冯庆、朱琦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1—36页。
Academic Monthly第48卷05May 2016状态神话并没有引出与霍布斯一样的结论。
通过析读普罗塔戈拉的这个著名神话,本文将表明民主政制的根本困难在于道德秩序的建立。
a一、普罗米修斯神话故事的叙述背景《普罗塔戈拉》记叙的是苏格拉底讲述的一段亲身经历——普罗塔戈拉第二次来到雅典时,有个名叫希珀克拉底的年轻人请求苏格拉底引荐他做普罗塔戈拉的学生。
苏格拉底把希珀克拉底领到普罗塔戈拉面前,问普罗塔戈拉能在哪方面让这个有政治抱负的年轻人进步,普罗塔戈拉回答说:他将传授“持家方面的善谋,亦即自己如何最好地齐家,[319a]以及治邦者方面的善谋,亦即如何在治邦者方面最有能耐地行事和说话”。
b苏格拉底听了后进一步问:“你对我说的似乎是治邦术,而且许诺造就[319a5]好城邦民?”这里的“治邦术”(political technique)一词就是如今西方的“政治学”的词源,由于在现存古希腊文献中这个语词是第一次出现,柏拉图的这篇对话通常也被视为西方政治学的原典之一。
我们看到,首先用这个术语的是苏格拉底,但苏格拉底用的是疑问句。
苏格拉底问的是:治邦术的具体含义是否就是“造就好城邦民”——今天所谓的培育好公民。
如果是这个意思,就意味着普罗塔戈拉的政治学是为民主政制服务的,因为,民主政制需要所有公民参政,如果没有培育出“好”公民,就不会有“好”的民主政治,或者说民主政制就不可能好。
其实,普罗塔戈拉的原话是“如何最好地齐家,以及治邦者方面的善谋”——“治邦者”与“城邦民”是两个有差异的语词。
用今天的话说,“治邦者”就是“政治家”,凭常识我们也知道,即便在崇尚自由民主的今天,也没可能让个个公民都成为政治家。
政治家需要特别的政治德性,这往往来自天赋,不是大学的政治学专业能够教出来的。
换言之,苏格拉底的疑问句偷换了普罗塔戈拉的概念。
事实上,普罗塔戈拉明明说的是“如何最好地齐家”,这意味着他的政治术是“齐家”式的(即“家长制”或君主制式的),因此才需要培育“治邦者方面的善谋”。
翻开我国古代的治邦之书《新序》就会看到,刘向开章明义以孝为先,继而推论仁道,最后以“善谋”两卷收尾。
显然,普罗塔戈拉说的“治邦者”指少数人而非全体公民。
换言之,普罗塔戈拉的政治观念至多是贵族制式的。
他懂得这样的常识:好政治绝不是人人可以参政的民主制。
毕竟,即便在普及高等教育的国家,也不可能每个公民都是“好”公民——即便后来的民主理论家卢梭也清楚这一点,除非像孟德斯鸠那样,用“爱民主共和”和“爱平等”取代用智慧、正义、节制等德性来界定“好”。
如果普罗塔戈拉的表述并没有含糊其辞,苏格拉底偷换概念就显得不地道。
然而,苏格拉底为人太地道了:普罗塔戈拉是外国人,他来到民主政制的雅典竟然说自己要传授君主制或贵族制式的政治术,岂不是自找麻烦。
换言之,苏格拉底偷换概念是在替他打掩护。
聪明的普罗塔戈拉听出了这一点,他赶紧回答说:“我承诺的正是这个承诺。
”如果要看懂普罗塔戈拉接下来讲的神话故事,我们就得记住普罗塔戈拉的这个承诺:他承诺的是要传授符合民主政制的政治术——但他心底里认可的却是君主制式的政治术。
换言之,由于害怕在民主政制的雅典受到迫害,普罗塔戈拉不得不隐藏自己的真实政治观点。
苏格拉底接下来的说法就真有点儿不地道了——他揪住这个并不真实的“承诺”当众给普罗塔戈拉出了个难题。
苏格拉底说,自己作为雅典人知道,雅典民主政制预设个个雅典公民都有政治“智慧”,根本无需普罗塔戈拉来教他们。
不过,苏格拉底又说,“即便我们最智慧、最优秀的城邦民,也没法把自己具有的德性传授给其他人”(319e)。
苏格拉底的说法显然前后矛盾:既然如此,雅典人何以可能个个是好公民呢?这个自相矛盾不是苏格拉底的脑子不清楚,而是故意为难普罗塔戈拉。
为什么要如此为难?因为普罗塔戈拉在起初曾自鸣得意地宣称自己勇敢,不害怕民主的政治迫害。
苏格拉底装样子地向普罗塔戈拉表达a 关于这个神话故事的研究文献,参见莫尔甘:《〈普罗塔戈拉〉:智术师与神话》,张文涛编:《神话诗人柏拉图》,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190—220页;参见米勒:《〈普罗塔戈拉〉中的普罗米修斯故事》,刘小枫编:《谁来教育老师:〈普罗塔戈拉〉发微》,蒋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
笔者的解析依循的是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普罗塔戈拉》讲疏(未刊讲课稿)。
b 译文见刘小枫编:《柏拉图四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方括号中的编码代替页码。
普罗米修斯神话与民主政制的难题了自己的困惑:民主的雅典人自以为人人有政治智慧,或者优秀的政治家也没法把自己的儿子教成同样优秀的政治家,因此,普罗塔戈拉宣称可以传授的政治德性要么不需要教,要么不可教。
苏格拉底说,他希望普罗塔戈拉开导自己。
由于当时有很多人在场,好面子的普罗塔戈拉自信地说:“我不会吝啬。
不过,我是该像老人给年轻人讲故事那样来给你们揭示呢,还是一步步论述?”大家让普罗塔戈拉随意,于是,普罗塔戈拉选择了讲故事。
普罗塔戈拉需要解答苏格拉底的两个困惑:第一,雅典人何以个个是好公民即有政治德性;第二,何以伯利克勒斯这样的民主政治家也没法把自己有的政治德性教给儿子——我们说过,这两个困惑相互矛盾。
对于普罗塔戈拉来说,苏格拉底的第二个困惑其实不是问题,因为,他主张的是家长制式的君主制或贵族制。
这种政制需要对少数天素优异的人施行教育,因此需要普罗塔戈拉这样的教育家。
但是,普罗塔戈拉不敢这样直接回答,否则有违民主意识形态。
他只能被迫回答前一个问题:雅典人何以个个有政治德性——这样一来就成了为民主政制作论证。
普罗塔戈拉面临一个两难:讲真话可以很容易回答苏格拉底,但会得罪民主意识形态,不讲真话可以逃过这一劫,但在苏格拉底面前就会丢脸。
他毕竟懂得,在几个聪明人面前丢脸,远比在一大群没脑筋的人面前丢脸更伤自尊心,因为他认为自己属于聪明人。
二、普罗塔戈拉如何讲神话故事搞清了上述背景,我们来看普罗塔戈拉如何通过讲故事解答这两个问题——普罗塔戈拉这样开始:从前那个时候,诸神已经有了,会死的族类[320d]还没有。
后来,会死的族类诞生的命定时刻到了,神们就搀和土和火以及由火和土混合起来的一切,在大地的母怀里打造出他们。
“从前……”是神话故事的起头方式——普罗塔戈拉要解答的问题是何以雅典公民人人有政治德性,故事却从人类的诞生开始讲起,这表明普罗塔戈拉认为,政治秩序的起源应该追溯到人类生成的自然开端。
这是哲人一类人探究政治制度的起源的惯常做法,这类人不会相信什么凭靠神的启示人类就有了某种政治秩序的说法。
不过,在不同的哲人那里,对自然起点的设定相当不同。
比如,苏格拉底从人吃饭穿衣的自然需要出发(参见《王制》369b以下),亚里士多德则从男女两性的自然结合出发(参见《政治学》1252a25—30)。
普罗塔戈拉从“神们”造人开始探究政治制度的起源,看起来似乎很传统,其实不然。
由于“搀和土和火以及由火和土混合起来的一切”需要计算比例,普罗塔戈拉强调的其实是某种算术式的技术。
在17世纪,算术或数学的确成了政治学的基础——且不说霍布斯本人就是数学迷,一个名叫佩蒂(Sir William Petty)的学人甚至写了《论政治算术学》,更不用说18世纪的启蒙政治家好些是数学家出身(如达朗贝尔、杜尔哥、孔多塞)。
普罗塔戈拉还提到“土和火”一类自然元素,这表明他的自然状态观与自然哲学有渊源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说,普罗塔戈拉的政治起源说与现代的自然状态说更为相似,两者都以某种自然科学式的知识为前提。
无论苏格拉底说的自然需要还是亚里士多德说的两性结合,都不属于自然科学式的形而上学知识。
普罗塔戈拉用一句话铺设了故事的时间、地点甚至角色——然而,这仅仅是开始:人与其他会死的族类还没有分化,人与动物具有共同的浑然未分的自然性。
随后我们会看到,普罗塔戈拉的自然状态说具有一个发展进程,这一点对他来说相当重要。
到了神们想到该把会死的族类引向光亮的时候,神们便吩咐普罗米修斯和[d5]厄琵米修斯替每个[会死的族类]配备和分配相适的能力。
厄琵米修斯恳求普罗米修斯让他来分配:“我来分配,”他说,“你只管监督吧”。
这样说服普罗米修斯后,他就分配。
普罗塔戈拉的自然状态有一种莫名的紧迫感,打造动物本性有“命定的时刻”,不能无限期拖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