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和女人
女人和女人的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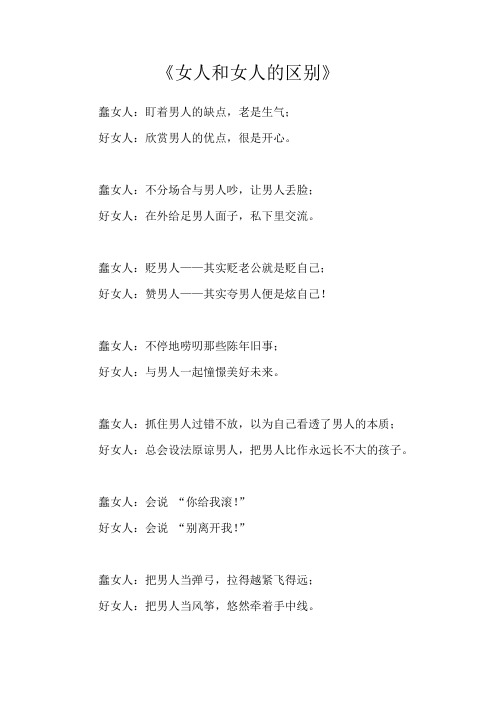
《女人和女人的区别》
蠢女人:盯着男人的缺点,老是生气;
好女人:欣赏男人的优点,很是开心。
蠢女人:不分场合与男人吵,让男人丢脸;
好女人:在外给足男人面子,私下里交流。
蠢女人:贬男人——其实贬老公就是贬自己;
好女人:赞男人——其实夸男人便是炫自己!
蠢女人:不停地唠叨那些陈年旧事;
好女人:与男人一起憧憬美好未来。
蠢女人:抓住男人过错不放,以为自己看透了男人的本质;好女人:总会设法原谅男人,把男人比作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蠢女人:会说“你给我滚!”
好女人:会说“别离开我!”
蠢女人:把男人当弹弓,拉得越紧飞得远;
好女人:把男人当风筝,悠然牵着手中线。
蠢女人:过于强调自我;
好女人:善于寄托依靠。
蠢女人:对男人寸步不离;
好女人:和男人若即若离。
傻女人:知道洗衣做饭,不愿梳妆打扮;好女人:不仅洗衣做饭,而且精心打扮。
傻女人:带给男人压抑和压力;
好女人:带给男人激情和动力。
傻女人:让男人在她泪水中失败;
好女人:让男人在她笑容中成功!。
女人梦见和女人亲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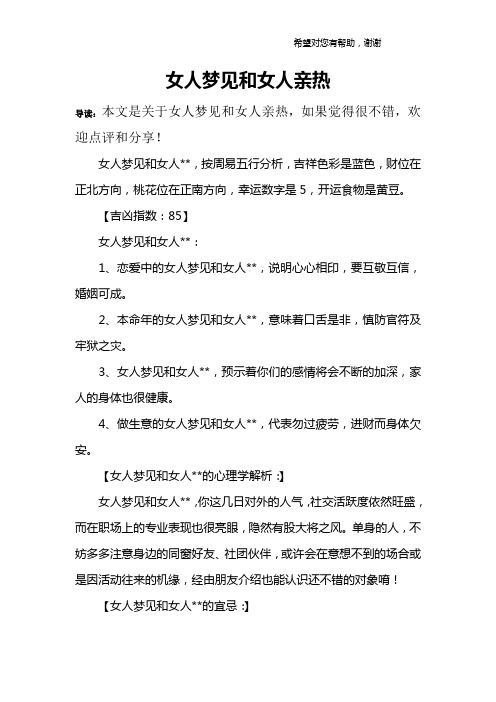
女人梦见和女人亲热
导读:本文是关于女人梦见和女人亲热,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女人梦见和女人**,按周易五行分析,吉祥色彩是蓝色,财位在正北方向,桃花位在正南方向,幸运数字是5,开运食物是黄豆。
【吉凶指数:85】
女人梦见和女人**:
1、恋爱中的女人梦见和女人**,说明心心相印,要互敬互信,婚姻可成。
2、本命年的女人梦见和女人**,意味着口舌是非,慎防官符及牢狱之灾。
3、女人梦见和女人**,预示着你们的感情将会不断的加深,家人的身体也很健康。
4、做生意的女人梦见和女人**,代表勿过疲劳,进财而身体欠安。
【女人梦见和女人**的心理学解析:】
女人梦见和女人**,你这几日对外的人气,社交活跃度依然旺盛,而在职场上的专业表现也很亮眼,隐然有股大将之风。
单身的人,不妨多多注意身边的同窗好友、社团伙伴,或许会在意想不到的场合或是因活动往来的机缘,经由朋友介绍也能认识还不错的对象唷!
【女人梦见和女人**的宜忌:】
宜:宜相亲,宜冲动消费,宜承认差距。
忌:忌收拾旧物,忌给植物浇水,忌听歌。
揭中国女人和日本女人在性方面的区别

揭中国女人和日本女人在性方面的区别中国女人一般不像西方世界的女子一样,会比较直接的说出自己的性需求,做为另一半,有必要去主动的观察伴侣的需求;其次,有性需求,也不是非要你大兴土木、宽衣解带做“整套”的爱,有时她只需要一个让她喘不过气来的拥抱,或者一次和衣而卧的聊天。
国产女性喜欢含蓄,甚至有时过分压抑,不敢表达自己的心声,特别是“性”声,结果,就把它扭曲变相成无明火、唠叨等负面情绪或状态,男人本身就粗心,往往不会去领会这些特别的不可爱的“性”号,结果更加深彼此感情的裂痕,影响婚姻的品质。
所以,你想不冷落太太的心,免得她多心、疑心,平常你就得多用心,甚至多往“歪”处去想想,说不定老问题就迎刃而解,新问题也化险为夷。
暗示一:无明火。
太太如果莫名其妙地发脾气,东西扔得叮当响,一屁股坐下来地球也会“抖三抖”的话,你就要检讨一下,多久没有“麻烦”过她了,什么叫“知足”,知足就是快乐,就是安心,而现在她不快乐,还躁动,说明你有些疏远了她的身体,她的身体在抗议,其实她自己也控制不了。
对策:今天晚上,你要好好安抚她。
古代宫里多斗争、阴谋,其实,就是女人太多而皇帝一个人又忙不过来的缘故,男人是女人最好的灭火器。
暗示二:唠叨吃零食。
女人爱吃零食,是因为寂寞,那些旧时代的姨太太喜欢嗑瓜子、东家长西家短地搬弄是非,就是因为缺乏老爷的滋养,是唇舌寂寞的表现。
对策:寂寞最好的解药当然就是心爱男人的哄或者拱了。
“拱”字也许不雅,好像是猪的动词,但是,它意味着五官的参与性,是最感性的亲昵。
女人是感性的,只要你与她来个额头相碰,她就会开心的,觉得你不单是为了狭隘的性,而是爱。
暗示三:刻意的贤惠。
这是一种隐忍,是火山爆发的前夜,所以,你要赶紧响应,否则你后果自负。
她的低姿态,她的勤劳,是做给你看的,其实就是要打动你的心,让你犒劳她。
对策:最简单的方式是在她手洗你的衣服时,从背后拦腰抱住她,贴着她的耳朵呢喃或者说肉麻的话,不要吝啬你的赞美或者有些“下流”的话,她“正”,而且是“太正了”,这时,你的“邪”就是她的甘露,就是阴阳互补。
女人梦见和女人讲话

女人梦见和女人讲话
女人梦见和女人讲话,五行主水,主事业有所烦恼,乃是因金钱之事与他人间争执,则相处更有不利之意,冬天梦之吉利,秋天梦之不吉利。
在外求财者梦之,往北走吉利,往南走不吉利,与属鼠之人,属龙之人共同求财,五行主水,事业可得他人相助之迹象,乃是贵人运多之征兆。
单身女人梦之,五行主水,求财者不可有任意妄为之事,与他人间争执,则相处更有不宁之意,郁结于心,发之于梦。
单身男人得此梦,人情世故处理不良,求财多有烦恼在心。
已婚女人梦之,生活有烦恼,求财不可有自作主张之想法,乃是听从他人之劝诫,彼此生活可得改善之征兆。
从事运输,物流等相关行业者,五行主水。
得此梦财运良好,求财多可得他人之相助,事业可得提升之意。
女人梦见和女人亲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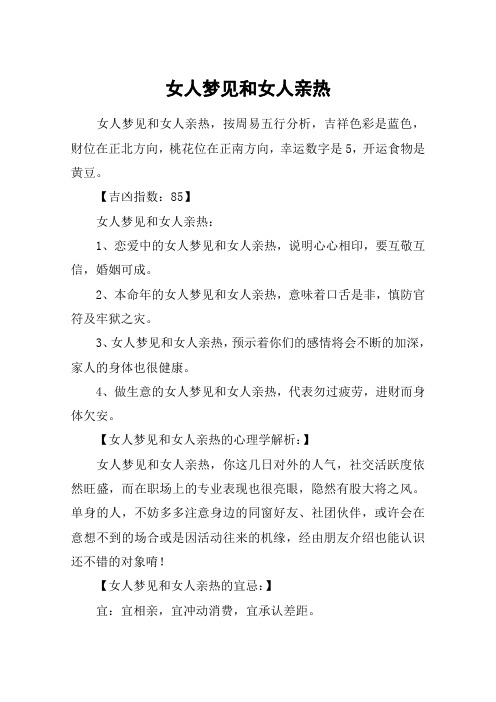
女人梦见和女人亲热
女人梦见和女人亲热,按周易五行分析,吉祥色彩是蓝色,财位在正北方向,桃花位在正南方向,幸运数字是5,开运食物是黄豆。
【吉凶指数:85】
女人梦见和女人亲热:
1、恋爱中的女人梦见和女人亲热,说明心心相印,要互敬互信,婚姻可成。
2、本命年的女人梦见和女人亲热,意味着口舌是非,慎防官符及牢狱之灾。
3、女人梦见和女人亲热,预示着你们的感情将会不断的加深,家人的身体也很健康。
4、做生意的女人梦见和女人亲热,代表勿过疲劳,进财而身体欠安。
【女人梦见和女人亲热的心理学解析:】
女人梦见和女人亲热,你这几日对外的人气,社交活跃度依然旺盛,而在职场上的专业表现也很亮眼,隐然有股大将之风。
单身的人,不妨多多注意身边的同窗好友、社团伙伴,或许会在意想不到的场合或是因活动往来的机缘,经由朋友介绍也能认识还不错的对象唷!
【女人梦见和女人亲热的宜忌:】
宜:宜相亲,宜冲动消费,宜承认差距。
忌:忌收拾旧物,忌给植物浇水,忌听歌。
“三不”女人和好女人的本质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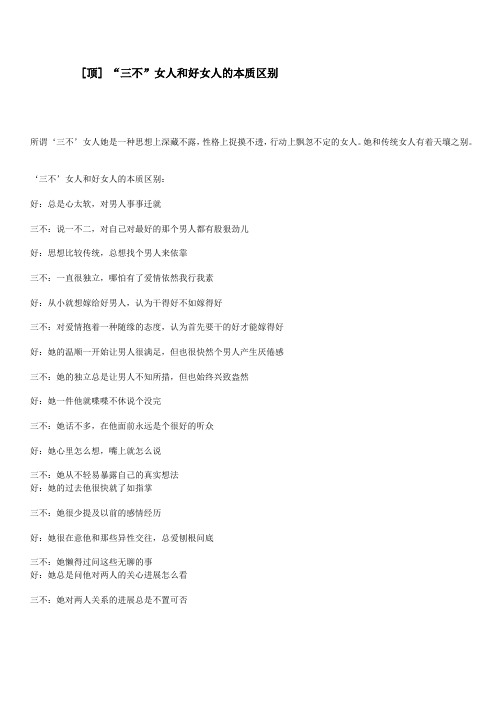
[顶] “三不”女人和好女人的本质区别所谓‘三不’女人她是一种思想上深藏不露,性格上捉摸不透,行动上飘忽不定的女人。
她和传统女人有着天壤之别。
‘三不’女人和好女人的本质区别:好:总是心太软,对男人事事迁就三不:说一不二,对自己对最好的那个男人都有股狠劲儿好:思想比较传统,总想找个男人来依靠三不:一直很独立,哪怕有了爱情依然我行我素好:从小就想嫁给好男人,认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三不:对爱情抱着一种随缘的态度,认为首先要干的好才能嫁得好好:她的温顺一开始让男人很满足,但也很快然个男人产生厌倦感三不:她的独立总是让男人不知所措,但也始终兴致盎然好:她一件他就喋喋不休说个没完三不:她话不多,在他面前永远是个很好的听众好:她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三不:她从不轻易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好:她的过去他很快就了如指掌三不:她很少提及以前的感情经历好:她很在意他和那些异性交往,总爱刨根问底三不:她懒得过问这些无聊的事好:她总是问他对两人的关心进展怎么看三不:她对两人关系的进展总是不置可否好:她无心睡眠,一天到晚想着他三不:她会首先安排好工作和生活,之后才会和他约会好:她每天向他报告行踪,随时等他的召唤三不:她行踪神秘,总是让他难以把控好:她只知道取悦男人三不:她让男人取悦自己好:她不敢对性有非分之想,在床上基本上屈从于他的要求三不:她在床上依然挥洒自如,让他如痴如醉好:一旦分手,她会哭得死去活来,还会大骂那个男人不负责任三不:分手时她会微笑着喝他说拜拜,然后调整好心态,继续上路三不女人妩媚的外表下有一颗从容镇静的心,就像变色龙一样,让男人无法琢磨,难以猜透,她是那种自强不息而不失温柔的女性,她既有实力,又不乏伶俐,她不会牺牲自己的生活,也不会主动追求男人,她不会让男人以为他百分之百吃定了她,即使一个男人在得到了她之后,她也依然自强自立,带着我行我素的风采。
女人梦见和女人打架

女人梦见和女人打架
女人梦见和女人打架,按周易五行分析,幸运数字是2,桃花位在西南方向,财位在正西方向,吉祥色彩是红色,开运食物是苹果。
【吉凶指数:76】
女人梦见和女人打架:
女人梦见和女人打架,远方的朋友会有联系,要保持友谊。
【女人梦见和女人打架的心理学解析:】
女人梦见和女人打架,学业和专业上的表现出色,象征着你对自己和整个团体的负责,这份紧密相连的使命感,改变了你看事情的角度,提高了你的学习意愿,办事效率好,心里面也充满了斗志,整个人散发着向前进的能量,带动周遭的人们跟着你一起勇往直前。
【女人梦见和女人打架的宜忌:】
宜:宜放空自己,宜冲动消费,宜批评不文明行为。
忌:忌看中医,忌发邮件,忌遛狗。
女人与女人之间

女人与女人之间我嫁过来的时候,公公婆婆是很开心的。
当时,他们从企业中层领导的位置上双双退休。
门前冷落不说,连小姑子的婚事,也意外告吹。
所以,他们认为我是个好媳妇,不势力。
与婆婆的交锋,是因我的怀孕引起的。
老公的哥嫂,早已去了南方,这一对企业白领,是铁了心的丁克族。
所以,婆婆的一双眼,便盯在我身上。
做检查的那个医生,和婆婆很熟,她笑呵呵地说,恭喜啊,是个男孩。
婆婆听后闷声说,恭喜什么,我生了两个儿子,有什么用!女孩儿要疼人得多。
我知道,婆婆又犯了小心眼儿了。
之前,她得知我的文凭比我老公高时,就喜忧参半。
喜的是有了体面,忧的是儿子会受气。
这一年来,看清楚我并不是那种骄横的人,才渐渐放下心来。
现在又怕我恃子生骄,所以开始拼命打压。
这样有心机,到底是当过领导的人。
我抱住婆婆的胳膊,笑嘻嘻地说:太好了,妈跟我想到一块儿了,这孩子,我决定做掉。
医生瞅着婆婆直笑。
婆婆大惊失色,话都不敢说了。
她的心脏不好,我怕把她吓出个三长两短,又柔声道,可我害怕人流受罪呢,她松了口气,轻轻扶着我的背,连叫了七八声好孩子,让我别多想,一定好好保养。
从怀孕到孩子出生,婆婆尽心尽力地照顾我,我也常常给她买件衣服,送套化妆品什么的。
一时间,我们俩成了小区里的模范婆媳。
可孩子十个月的时候,我们之间又出现了问题。
当时,老公调到外地的分公司,一周后报到。
婆婆爽快地说,都搬到我这儿来吧,我带孩子做饭,什么也不用你干。
就这样,我们住在了一起。
下班回家,餐桌上热气腾腾,荤素齐全。
宝宝干干净净,精神也很好,我好不容易才抢的了洗碗的差事。
同事们都羡慕我有福气,遇见了个好婆婆。
可老公一走一切待遇取消。
厨房里冰锅冷灶,宝宝爬在床上,婆婆歪在一边看电视。
她说胃痛犯了,让我随便做点什么凑合吃。
还告诉我,洗衣机坏了,宝宝的几套脏衣服,要赶快洗洗。
我心里有数,只是含笑点头。
婆婆亦不动声色,不停夸我炒的菜好吃,家务活干得利落,还嗔着宝宝道,怎么妈妈一抱你,你就笑呢,看来咱们还要妈妈多抱抱啊。
“妇女”和“女人”的区别在哪里

“妇女”和“女人”的区别在哪里在今年全国两会的提案中,有两个提案跟“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有关系。
一是全国政协张晓梅委员建议将三八“妇女”节更名为“女人”、“女性”或“女子”节;二是全国政协李汉秋委员提出要把三八“国际”妇女节,更名为“中国”妇女节。
InternationalWomen'sDay本来就是国际性的节日,李汉秋委员的提案,多少是因为思维惯性———他一直致力于在公众节日中注入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的元素,一不留神把国际性节日当中国节日过了也情有可原。
李汉秋委员还为中国妇女找了一些古人楷模:“她们身上有着现在提倡的传统美德,既爱国也爱家,既相夫也教子,完全可以作为妇女的榜样。
”可见李委员的“中国妇女节”论述,重点在“妇”———在三八节“革命女性”的文化之外,添加“既相夫也教子”的传统妇道。
而张晓梅委员的侧重点则在“女”。
“妇女”在中国的公共语境,无论是立法、公共政策或是主流传媒中,本来是最正式的指称“女人”、“女性”或“女子”的词语,可是在张委员那里,“妇女”二字“多有女性文化偏低,年龄偏大之意”。
张委员甚至认为,因为人们通常会在“家庭妇女”、“农村妇女”、“中年妇女”、“保护妇女儿童”等词组中用到“妇女”这个词,因此这个词含有弱者的联想、有贬低的倾向。
那些“不仅追求自由、平等、独立,也对自身的生活品质和生活细节十分重视,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女性在被称为“妇女”时,会感到不满或不快。
如果我没有弄错,张晓梅委员自己就是一位中年妇女,因此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她会在本来非常中性的“中年妇女”等词组中,感受到弱者、贬低之意。
如果这些词组确实让人有不快联想的话,那么这种不快,是来自“妇女”这个名称,还是另一些认为针对妇女的年龄、阶层和职业的歧视?张委员本人有没有内化这些观念?李汉秋委员认为妇女节是一个给妇女学习榜样的节日,张晓梅委员则认为给妇女节改名“还能拉动消费”。
考虑到张委员在美容业界的资深背景,或许可以理解她心目中那种充满城市精英气息和享乐主义气氛的“女人节”景象。
女人梦见和女人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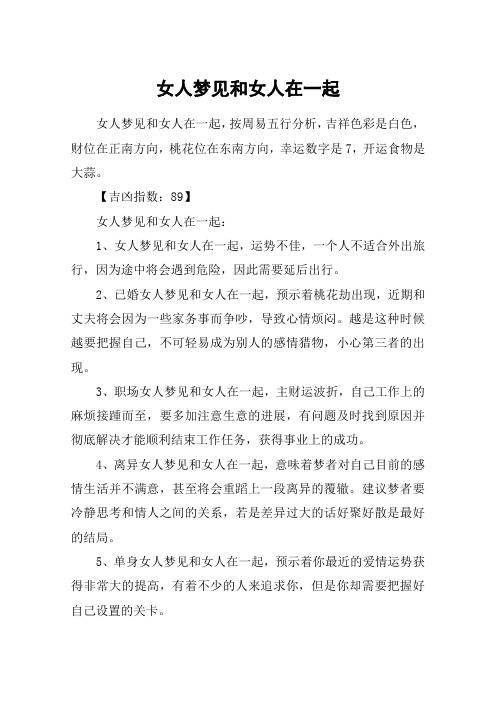
女人梦见和女人在一起
女人梦见和女人在一起,按周易五行分析,吉祥色彩是白色,财位在正南方向,桃花位在东南方向,幸运数字是7,开运食物是大蒜。
【吉凶指数:89】
女人梦见和女人在一起:
1、女人梦见和女人在一起,运势不佳,一个人不适合外出旅行,因为途中将会遇到危险,因此需要延后出行。
2、已婚女人梦见和女人在一起,预示着桃花劫出现,近期和丈夫将会因为一些家务事而争吵,导致心情烦闷。
越是这种时候越要把握自己,不可轻易成为别人的感情猎物,小心第三者的出现。
3、职场女人梦见和女人在一起,主财运波折,自己工作上的麻烦接踵而至,要多加注意生意的进展,有问题及时找到原因并彻底解决才能顺利结束工作任务,获得事业上的成功。
4、离异女人梦见和女人在一起,意味着梦者对自己目前的感情生活并不满意,甚至将会重蹈上一段离异的覆辙。
建议梦者要冷静思考和情人之间的关系,若是差异过大的话好聚好散是最好的结局。
5、单身女人梦见和女人在一起,预示着你最近的爱情运势获得非常大的提高,有着不少的人来追求你,但是你却需要把握好自己设置的关卡。
【女人梦见和女人在一起的心理学解析:】
女人梦见和女人在一起,休闲运良好的周末,找几个朋友一起热热闹闹的过一天。
尤其是与青梅竹马、学生时代的友人一起聊天的时间里,平日疲倦的心灵也治愈了不少。
而这两天越是身处在人多热闹的地方越有幸运事件发生,像是宴请宾客中自己也得到乐趣,交际费用就不要太计较了。
【女人梦见和女人在一起的宜忌:】
宜:宜跑步,宜对酒当歌,宜买基金。
忌:忌观星,忌吃醋,忌穿格子衬衫。
女人和女的人

女人和女的人坐在飞机上无聊地在商务通上画汉字,因为写起来不流畅,于是,习惯一笔写下来的女人这个词,在心里被拆成了女和人两个字。
“女人”、“女、人”?这么一拆,我突然发现,原来“女”和“人”字并不是有始以来就连在一起的。
女人,一定是有了男人这个词以后才被相对应产生的。
但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习惯忽略了女人首先是有“女”和“人”两个独立的意思组合而成的呢?在我看来,“女人”是在人的基础上更柔软、更阴性、更接近生命的一种特质。
作为一个女人,可以很温柔,很细腻,很柔媚,力气很小,胆子很小,甚至可以撒娇,使小性子,这些都是由“女”这个生理特性所派生出来的心理或是性格特征。
女人相比于男人,似乎体力差些、力气小些,在某些方面需要得到男性的帮助。
女人因此得到了社会的一些共识和特权,也很快乐的使用着这些属于“女”带来的特权,诸如,使性子、感性、依赖、没主见等等,男人们允许女人这样。
后来,女人们也就这样了,而且美滋滋地尝着这些小甜头。
尝着尝着,女人发现自己把“人”字给丢了,光剩下“女”字在那里,无依无靠,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于是女人开始害怕了,想寻求安全感和生存。
在黑漆漆的旷野上,除了萧萧的冷风,还有一点一点闪烁的灯头,那是男人在社会上挣得的领地。
每一块领地上都高挂着一块醒目的木牌子:欢迎女人入住。
这是男人生理上的需要。
同时他们还需要有后代来继承他的领地,这却只有在女人的协助下完成。
基于这两点原因,几乎每一个男人都是欢迎女人入住的。
招牌在黑夜里看不分明,或者有些女人在又冷又热又害怕的境况下,也顾不得看个仔细。
殊不知,每块牌子的“欢迎女人入住”几个大字下面,通常是隐藏了一行小字的。
打着灯笼凑过去一看,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入住的女人的条件,诸如年龄、容貌、贤良程度等等硬件,就像招聘启示似的。
其实招聘本身也是从男人求偶时下聘礼这儿衍生来的。
如果遇到领地大的而又很在乎继承人的男人,他可能还会加一条:家庭出身。
需要是个有血统干净的女人,才可以保证财产不落入异性野种之手。
女人梦见和女人接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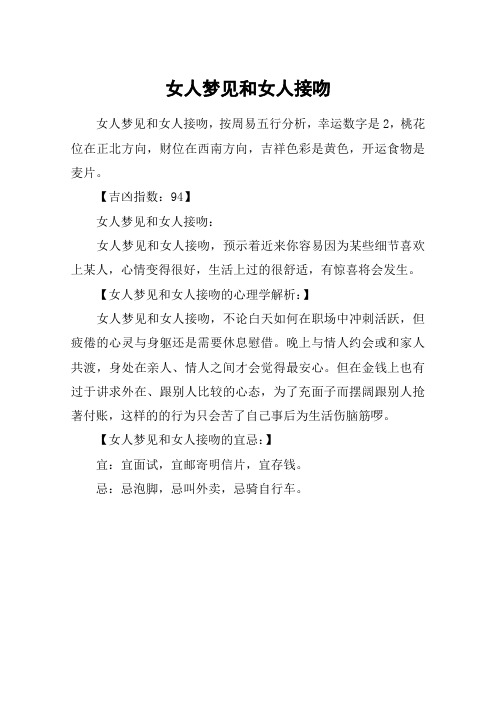
女人梦见和女人接吻
女人梦见和女人接吻,按周易五行分析,幸运数字是2,桃花位在正北方向,财位在西南方向,吉祥色彩是黄色,开运食物是麦片。
【吉凶指数:94】
女人梦见和女人接吻:
女人梦见和女人接吻,预示着近来你容易因为某些细节喜欢上某人,心情变得很好,生活上过的很舒适,有惊喜将会发生。
【女人梦见和女人接吻的心理学解析:】
女人梦见和女人接吻,不论白天如何在职场中冲刺活跃,但疲倦的心灵与身躯还是需要休息慰借。
晚上与情人约会或和家人共渡,身处在亲人、情人之间才会觉得最安心。
但在金钱上也有过于讲求外在、跟别人比较的心态,为了充面子而摆阔跟别人抢著付账,这样的的行为只会苦了自己事后为生活伤脑筋啰。
【女人梦见和女人接吻的宜忌:】
宜:宜面试,宜邮寄明信片,宜存钱。
忌:忌泡脚,忌叫外卖,忌骑自行车。
雪花秘扇和女人的那些事儿

尼娜(李冰冰饰)是索菲亚(全智贤饰)最好的朋友,她们一起玩耍、一起长大。
为了保持着年少时的亲密关系,她们在尼娜姑妈(邬君梅饰)的安排下,结为老同,并发誓要同心同意,至死不渝。
然而身在21世纪的上海,彼此因为爱情和职业的关系,渐行渐远,儿时的友情也饱受考验,当索菲娅交往的男友约瑟(休·杰克曼饰)再次被尼娜否定,两人的友情也终于破裂。
所幸,一次意外事故,唤起了索菲亚有关古代百合(李冰冰饰)和雪花(全智贤饰)老同情谊的记忆:同年同月同日生、相貌相近脾气投缘,结下盟誓,不离不弃。
终于,尼娜和索菲亚,两位现代女性,真切地触摸到了深埋在彼此心里,强烈而不可磨灭的老同情谊……无论是在青葱岁月时我们的互相取暖和照应,还是成为少淑名媛后的慰藉与疏离,女人之间的感情从来没有停止过滋生和延续。
和古代女子之间的质朴女书、“老同”情谊相比,现代社会里的女性情谊显得太随意,太不稳定。
可没有人能否定,那些只会发生在女人之间的心灵患难和成长,永远都不会因为任何变迁而发生改变。
御姐萝莉几乎所有人都认同,最好的时光,不属于一个现在时态的词组。
而女人和女人之间,更愿意用过去最好的时光,来替代想象中的幸福未来。
还记得儿时最好的玩伴,总是那个脸蛋红扑扑,跑步超级快的好动女孩。
约好了一起上厕所,还相互为对方暗恋的男孩子传纸条、要照片,就算是晚上前胸贴后背地睡在一张单人床里,也比回到自己冷冰冰的空旷房间里,更有满足感。
穿运动短裤的体育课上,知了在树上叫着,两个女生在树下偷懒,你在侧面看她,她也在心里幻想着你的未来。
影片中,尼娜和索菲亚穿着校服,在房间里摇头晃脑、假装跳舞的样子,让你想起有一个夏天,你给她戴上自己暗恋男生的纸面具,相拥而舞,还不停地逼问,“他会不会爱上我”这类傻傻的问题。
等到某天,你向她介绍新认识的男友时,她的眼神,你分不清是高兴,还是醋意,为了哄她开心,想尽了一切办法,她还是嘟着嘴巴,假装生气,只有等到回家路上的一碗热鱼丸,她便能在寒风里一路笑到底。
女人和女人比什么

女人年龄大了,就不要跟人家比新鲜度,比那个干什么?也不要比单纯,没必要。
确实有很多男人喜欢单纯的女孩子,让他们喜欢去好了,第一,单纯的女孩子也会长大,很快她们就不单纯了;第二,如果她们到了一把岁数还单纯,那她们一定平庸而乏味。
女人和女人之间,比的不仅仅是美貌和青春,有的时候,经验和智慧同样重要。
如果我没有记错,查尔斯王子的父亲曾对自己的儿媳戴安娜王妃说过这样的话:“我无法想象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离开你而选择卡米拉。
”是呀,卡米拉凭什么——她比查尔斯王子还要年长,她已经有了丈夫,她不美,她凭什么?我相信戴安娜至死都希望卡米拉漂亮一些,年轻一些,这样世人就会把查尔斯的移情别恋理解为“男人的风流”——男人犯这样的错,相对来说,总是令女人好受一些。
我甚至想,戴安娜之所以感到愤怒、疯狂,也许不是不能接受失去查尔斯,她早不爱他了,她不能接受的是,他居然真会为了一个美丽不及她一半而年龄大自己一倍的女人而离开自己,这是对她的侮辱,她败在一个不美且老的女人手下。
一直以为,女人的岁数和她获得幸福的能力成反比,女人越年轻,男人越喜欢。
而事实上,那不过是一些普通男人和普通女人的定律。
普通女人,因为普通,所以一旦失去青春,就失去了一切。
普通女人的青春并不比其他人的青春更短暂,但是她们的青春就像一卷胶卷,过期作废。
所以,如果不在有效期内多按几张,将来恐怕连个回忆都没有。
因此,女人都渴望能遇到摄影大师一级的男人,因为只有这样,她们的青春才会转变成珍贵的图片。
可惜,大多数女人的命运和大多数胶卷一样,她们根本没有成为珍贵图片的可能,她们不过是照片上一大堆庸俗的风景之一。
有阅历的女人与年轻女子比,除了失去青春,实际上没有失去任何其他的宝贵东西——相反,她多了阅历。
一个有阅历的女人,对于男人来说,就像一幅历经朝代更迭的名画,虽然有些残破,但她是唯一的,不可再生的。
我认为一个女人如果把自己修炼成了名画,就不必着急出手了。
急什么?又不是挂历,今年卖不掉,明年就卖不出去了。
不要拿自己的老婆和别人的老婆做比较,老婆还是自己的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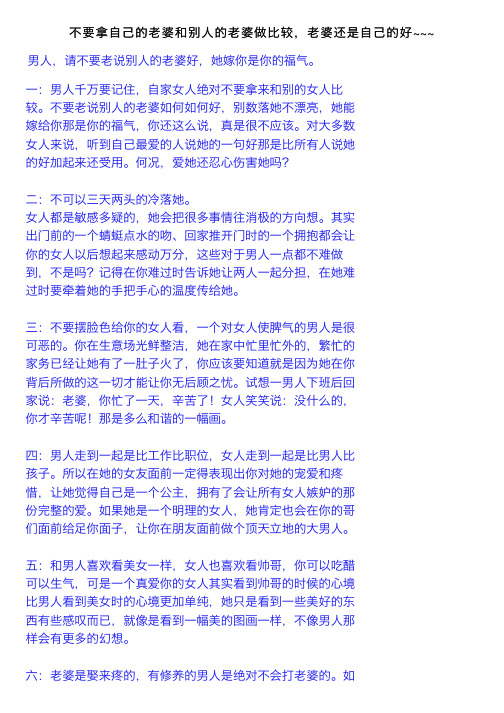
不要拿⾃⼰的⽼婆和别⼈的⽼婆做⽐较,⽼婆还是⾃⼰的好~~~男⼈,请不要⽼说别⼈的⽼婆好,她嫁你是你的福⽓。
⼀:男⼈千万要记住,⾃家⼥⼈绝对不要拿来和别的⼥⼈⽐较。
不要⽼说别⼈的⽼婆如何如何好,别数落她不漂亮,她能嫁给你那是你的福⽓,你还这么说,真是很不应该。
对⼤多数⼥⼈来说,听到⾃⼰最爱的⼈说她的⼀句好那是⽐所有⼈说她的好加起来还受⽤。
何况,爱她还忍⼼伤害她吗?⼆:不可以三天两头的冷落她。
⼥⼈都是敏感多疑的,她会把很多事情往消极的⽅向想。
其实出门前的⼀个蜻蜓点⽔的吻、回家推开门时的⼀个拥抱都会让你的⼥⼈以后想起来感动万分,这些对于男⼈⼀点都不难做到,不是吗?记得在你难过时告诉她让两⼈⼀起分担,在她难过时要牵着她的⼿把⼿⼼的温度传给她。
三:不要摆脸⾊给你的⼥⼈看,⼀个对⼥⼈使脾⽓的男⼈是很可恶的。
你在⽣意场光鲜整洁,她在家中忙⾥忙外的,繁忙的家务已经让她有了⼀肚⼦⽕了,你应该要知道就是因为她在你背后所做的这⼀切才能让你⽆后顾之忧。
试想⼀男⼈下班后回家说:⽼婆,你忙了⼀天,⾟苦了!⼥⼈笑笑说:没什么的,你才⾟苦呢!那是多么和谐的⼀幅画。
四:男⼈⾛到⼀起是⽐⼯作⽐职位,⼥⼈⾛到⼀起是⽐男⼈⽐孩⼦。
所以在她的⼥友⾯前⼀定得表现出你对她的宠爱和疼惜,让她觉得⾃⼰是⼀个公主,拥有了会让所有⼥⼈嫉妒的那份完整的爱。
如果她是⼀个明理的⼥⼈,她肯定也会在你的哥们⾯前给⾜你⾯⼦,让你在朋友⾯前做个顶天⽴地的⼤男⼈。
五:和男⼈喜欢看美⼥⼀样,⼥⼈也喜欢看帅哥,你可以吃醋可以⽣⽓,可是⼀个真爱你的⼥⼈其实看到帅哥的时候的⼼境⽐男⼈看到美⼥时的⼼境更加单纯,她只是看到⼀些美好的东西有些感叹⽽已,就像是看到⼀幅美的图画⼀样,不像男⼈那样会有更多的幻想。
六:⽼婆是娶来疼的,有修养的男⼈是绝对不会打⽼婆的。
如果真爱她那就⼀定要尊重她,不能随便动⼿。
如果你已经不爱她了,那么你就摸摸⾃⼰的良⼼:我还能让她幸福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放她⾛吧,让她找个真正能对她好的⼈。
女人“嗯”和“嗯嗯”有哪几种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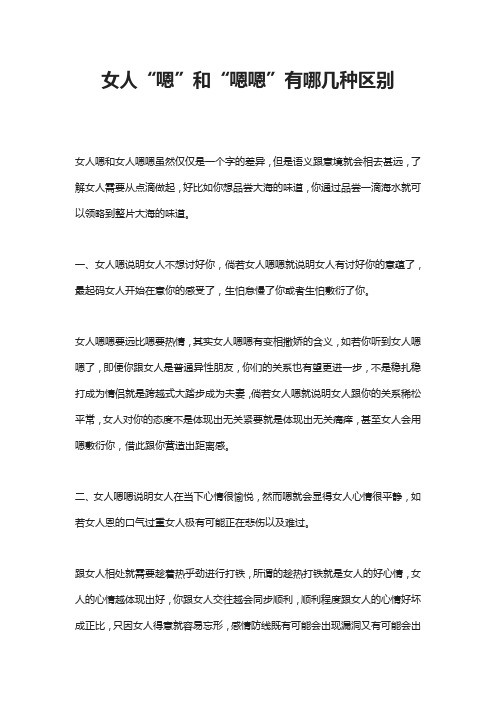
女人“嗯”和“嗯嗯”有哪几种区别女人嗯和女人嗯嗯虽然仅仅是一个字的差异,但是语义跟意境就会相去甚远,了解女人需要从点滴做起,好比如你想品尝大海的味道,你通过品尝一滴海水就可以领略到整片大海的味道。
一、女人嗯说明女人不想讨好你,倘若女人嗯嗯就说明女人有讨好你的意蕴了,最起码女人开始在意你的感受了,生怕怠慢了你或者生怕敷衍了你。
女人嗯嗯要远比嗯要热情,其实女人嗯嗯有变相撒娇的含义,如若你听到女人嗯嗯了,即便你跟女人是普通异性朋友,你们的关系也有望更进一步,不是稳扎稳打成为情侣就是跨越式大踏步成为夫妻,倘若女人嗯就说明女人跟你的关系稀松平常,女人对你的态度不是体现出无关紧要就是体现出无关痛痒,甚至女人会用嗯敷衍你,借此跟你营造出距离感。
二、女人嗯嗯说明女人在当下心情很愉悦,然而嗯就会显得女人心情很平静,如若女人恩的口气过重女人极有可能正在悲伤以及难过。
跟女人相处就需要趁着热乎劲进行打铁,所谓的趁热打铁就是女人的好心情,女人的心情越体现出好,你跟女人交往越会同步顺利,顺利程度跟女人的心情好坏成正比,只因女人得意就容易忘形,感情防线既有可能会出现漏洞又有可能会出现缺口,但凡你瞅准时机,跟女人开暧昧以及内涵的玩笑,或者跟女人间接进行表白,女人极有可能会半推半就选择迎合,至于女人嗯,你就需要安慰女人,或者识趣暂时远离女人。
三、女人嗯嗯说明女人是在表现出可爱的言谈,或者女人是在紧跟着时尚的潮流,女人嗯嗯会从侧面反映出时尚,然而女人嗯就说明女人既不会刻意彰显出可爱又不会人云亦云,不排除女人嗯有古板或者死板的可能性。
很多女人即便可爱也会用嗯嗯进行锦上添花,如若不可爱也会用嗯嗯进行雪中送炭,主要是现如今嗯嗯的势头已经有超过嗯的迹象,然而女人嗯照样会跟女人嗯嗯并存,形同并驾齐驱,其实通过女人嗯或者女人嗯嗯就可以推断出女人的内心世界,既然女人的外在起源于女人的内在也就可以运用逆向思维进行顺藤摸瓜。
结语:听女人说话需要听潜在的音,即便是只言片语也需要推敲出弦外之音,了解女人在于精细,越精细,你越知道女人的心路历程,为你日后攻心为上绘制出路线图。
解放的女人和幸福的女人_长沟流月去无声_与_爱_是不能忘记的_比较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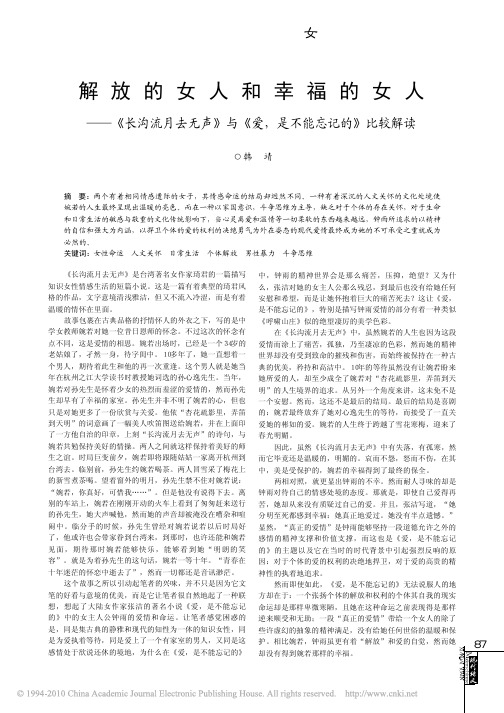
女性文学研究专题odern chinese2007.11《长沟流月去无声》是台湾著名女作家琦君的一篇描写知识女性情感生活的短篇小说。
这是一篇有着典型的琦君风格的作品,文字意境清浅雅洁,但又不流入冷涩,而是有着温暖的情怀在里面。
故事包裹在古典品格的抒情怀人的外衣之下,写的是中学女教师婉若对她一位昔日恩师的怀念。
不过这次的怀念有点不同,这是爱情的相思。
婉若出场时,已经是一个34岁的老姑娘了,孑然一身,待字闺中。
10多年了,她一直想着一个男人,期待着此生和他的再一次重逢。
这个男人就是她当年在杭州之江大学读书时教授她词选的孙心逸先生。
当年,婉若对孙先生是怀着少女的热烈而羞涩的爱情的,然而孙先生却早有了幸福的家室。
孙先生并非不明了婉若的心,但也只是对她更多了一份欣赏与关爱。
他依“杏花疏影里,弄笛到天明”的词意画了一幅美人吹笛图送给婉若,并在上面印了一方他自治的印章,上刻“长沟流月去无声”的诗句,与婉若共勉保持美好的情操。
两人之间就这样保持着美好的师生之谊。
时局巨变前夕,婉若即将跟随姑姑一家离开杭州到台湾去。
临别前,孙先生约婉若喝茶。
两人冒雪采了梅花上的新雪煮茶喝。
望着窗外的明月,孙先生禁不住对婉若说:“婉若,你真好,可惜我……”。
但是他没有说得下去。
离别的车站上,婉若在刚刚开动的火车上看到了匆匆赶来送行的孙先生,她大声喊他,然而她的声音却被淹没在嘈杂和喧闹中。
临分手的时候,孙先生曾经对婉若说若以后时局好了,他或许也会带家眷到台湾来,到那时,也许还能和婉若见面,期待那时婉若能够快乐,能够看到她“明朗的笑容”。
就是为着孙先生的这句话,婉若一等十年。
“青春在十年迷茫的怀恋中逝去了”,然而一切都还是音讯渺茫。
这个故事之所以引动起笔者的兴味,并不只是因为它文笔的好看与意境的优美,而是它让笔者很自然地起了一种联想,想起了大陆女作家张洁的著名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女主人公钟雨的爱情和命运。
让笔者感觉困惑的是,同是集古典的静雅和现代的知性为一体的知识女性,同是为爱执着等待,同是爱上了一个有家室的男人,又同是这感情处于欲说还休的境地,为什么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钟雨的精神世界会是那么痛苦,压抑,绝望?又为什么,张洁对她的女主人公那么残忍,到最后也没有给她任何安慰和希望,而是让她怀抱着巨大的痛苦死去?这让《爱,是不能忘记的》,特别是描写钟雨爱情的部分有着一种类似《呼啸山庄》似的绝望凄厉的美学色彩。
女孩和女人

老妈在做糖醋鱼和肉丸子,我趴在炕沿边上,看着她熟练的摆弄着一道道的工序,那样的娴熟,仿若已经习惯了几个世纪。
“妈咪呀,你在嫁给老爸之前就可以做这么多好吃的美味吗?”“不是啊,是嫁给他之后才一点一点学会的”“啊?那老爸不是很可怜吗?因为您不可能一次性就成功的掌握好量来做出现在这样好吃的东西啊”“应该不会吧,我哪有那么差劲,再说了,在你做的时候心里面就会想着要为他做出很好吃的食物啊,怎么可能会做的很差劲啊”“那我现在用不用学做菜啊,我觉得这些东东好像必读书还要难哎”“不用啦,和你说啊,一个女孩和女人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于他愿意为了一个男人放下自己的一切身段,从头开始研究一道道看似复杂的菜肴并且乐在其中,不是妈妈和你瞎说啊,任何的顶级餐馆、食堂都比不上家里妈妈做的一份哪怕是简单的糖醋鱼,因为家里面有妈妈,你老爸的老婆在啊。
只有你爱一个人才会愿意去经历琐碎和枯燥平淡,也只有因为爱一个人“好像是哦,重要的不是菜式的好吃与否,才不会介意最初的那份菜式到底是好吃还是难吃。
”而是做菜的那个人,和尝菜的那个他,所以,回家吃饭,其实是回家看那个人。
”“对啊,所以,你也好,你姐姐也好,每次回家我总不用你们做家务事,因为你们是我的孩子啊,无论长多么大,都还是孩子啊,而在这里,我才是女主人!”“所以呢,你现在呀,不用着急,会有那么一天的额,你会为了我未来的女婿,也就是你的丈夫掌勺,一整个厨房和家庭的琐碎都由你来掌握,那个时候,你就不只是一个女孩子了。
”老妈笑的很开心,她很自然的和我进行着谈话。
忽然想起高考后的那个夏天,好像那天餐桌上也是肉丸子,我问老妈,是什么原因让她愿意嫁给老爸的。
她刹那间红了脸,继而望向老爸“我们是因为相爱才在一起的啊”老爸呷了一口二锅头,夹一个肉丸子放进嘴里,继而慢慢悠悠的说:“那个时候啊,我还在建筑队工作,你妈妈呢给人家代班做过菜,有一天,对她说,以后你天天给我做菜吧,后来,她就天天给我做菜了。
想来,都好几十年的事情咯”老爸回忆的样子,像是探寻几个世纪之前的事情。
woman的复数形式和用法例句翻译及阅读

woman的复数形式和用法例句翻译及阅读woman有女人,妇女; 成年女子等意思,那么你知道woman的复数是什么吗?下面跟着店铺一起来学习woman的英语知识吧,希望对大家的学习有所帮助!woman的复数形式womenwoman的用法woman的用法1:woman用作可数名词时,意思是“成年女子”,泛指一切成熟的女性,而不管婚否。
woman的用法2:woman也可用作“女人,女性”的总称, woman还可指“女人的气质和属性”,是抽象名词,不可数。
woman的用法3:woman还可作“女仆,女佣人”解,作此解时,是可数名词。
woman的用法4:woman可用于其他名词前作定语,表示“女性的…”,如果被修饰的名词是单数,就用其单数形式,如果被修饰的名词是复数时,通常用其复数形式。
woman的复数例句1. It is nearly always women who are the primary care givers.从事初级保健护理工作的几乎都是女性。
2. I supported us by writing bilge for women's magazines.我胡乱给女性杂志写点东西,维持我们的生计。
3. In many respects Asian women see themselves as equal to their men.在很多方面,亚洲女性都认为自己和丈夫是平等的。
4. In 1986, 44 per cent of those admitted to articles were women.1986年,44%的实习生为女性。
5. Many women know how to carry out repairs on their cars.许多妇女懂得怎样修自己的车。
6. There's a reason why women don't read this stuff; it's not funny.女人不读这种东西是有原因的,它并不好笑。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女人和女人初绿姐住在鼓浪屿升旗山脚下一座红砖洋房里,孤门独户,清幽安静。
自儿子1982年去了美国,初绿姐就独自守着这幢空荡荡的双层楼房。
厝边(邻居)们都记得,从太平洋事变那年的夏天嫁给倪先生以后,她就一直住这里,寸步未移。
“你父亲沾了点满清的边,他是辛亥革命前三个月出生的,比我大12岁。
”儿子稍大点,初绿姐就常给他唠些南洋爸爸的事,尽量加强他对父亲的印象。
但其实,别说小孩,初绿姐对自己的丈夫也不见得有太深刻的印象。
扳着手指头算算,她这辈子与倪先生呆在一块儿的日子,七凑八凑,恐怕不足五年吧。
“文革”前夕,正读高中二年级的儿子为争取入团,要向组织老实说明家庭状况,追问父母的早年行踪,初绿姐也只能轻描淡写说个大概:“我们结婚没几个月,日本人挟着奇袭珍珠港的狂势,把鼓浪屿也给吞了。
你爸就逃内地去了,后来又从昆明转辗到仰光找到你爷爷。
我自己单独一身在鼓浪屿呆了五年。
”那五年是她的花季,又刚让一位成熟的男性教会她成了个女人。
她关在空荡荡的红砖墙内,极少出门。
望着新婚房间四面钉满了痛苦和心酸的白壁,她常嘤嘤低泣,更常在黑夜里哭醒过来,拼命地追忆梦中扑到她身上的东西,缓缓地滑进,令她在甜美的汹涌中感受到生命的充实与满足。
然而,每回都是那么匆促,瞬间的存在那么无情地消失在惊醒的意识里,她只能咬紧双唇,让泪水涔出紧叠的睫毛。
实在难忍,初绿姐就抓过丈夫睡过的枕头,夹在自己的髀间,让那柔软的绸面磨擦着刚长齐的茸毛,直到小腹和枕面都涂成滑润的一片。
初绿姐当然不能把这青春的阵痛向儿子转述,她只能含羞地把它深埋在心底。
或许她可以挑些含蓄的词句:“你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理解,一个不满20岁的女人守着这幢空楼的恐慌与心虚。
你父亲杳无音讯,我只能靠变卖首饰度日,那时候,幸亏有林姑娘常来陪我,林姑娘……”多少年了,初绿姐一提到林姑娘就涌上一股莫名的激情,她感到心律加速,脸部发热,赶紧瞅儿子一眼。
儿子正埋头忙于记录,一点没注意母亲表情的变化。
“我父亲是哪一年回来的呢?”“1946年吧。
”“哪一年又离开鼓浪屿?”儿子的口气接近于审讯了,他急于澄清“父亲”这个陌生的概念。
“抗美援朝那阵吧,不对不对,那是林姑娘被押下船的日子。
”初绿常把她生命中两位最亲密的人叠合一体,她理了理混乱的思绪,确定了答案:“你父亲走的时候,厦门还没解放,49年春节刚过……”“为什么解放后就没回来过呢?”面对儿子的责问,初绿姐一阵悲伤,觉得鼻子酸酸的,但还是强忍住了外涌的泪水。
几十年间的艾怨与苦楚都默默地吞下了,孩子高中还没毕业,能懂吗?她其实早听说了,丈夫在缅甸又有一个家,那边的儿女都比阿辉还大了。
男人也难呵,他们对异性的渴求比女人强烈得多。
那新婚后的挥别是五年而不是五个月,她都那么难熬,何论是他!初绿姐回答不了儿子的问题,她不忍心把真相端出。
这孩子长这大了,就靠那几张照片与父亲沟通,残缺的家已使他变得有点古怪。
她望了望儿子,快快地回到自己的卧房里。
1941年刷上的白灰已经泛黄脱剥了,但卧房里的一切摆设还保持着原貌,只是在床头的小桌上,多了一张林姑娘的照片。
这个穿着中国旗袍的美国女人微笑着,她的脸属方型,轮廓清楚,双眼和嘴唇洋溢着一种不寻常的,对男人和女人都同样有效的魅力。
她才长得像明娜呢! ①初绿姐至今仍这么认为。
二如今年近古稀的鼓浪屿人都记得林姑娘,她本名艾丽达·林娜,是美国人办的毓德女中的英文老师,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据说她出身纽约的豪门望族,1936年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毕业后就飘洋过海,到鼓浪屿执教鞭。
那年,初绿姐正读毓德初中三年级,第一次班里点名,林姑娘就对她兴趣盎然。
“叶初绿,这么美的名字!叶——初绿,妙极了,简直是首海登斯坦的诗。
” ②林姑娘赞叹不已,她才24岁,充满了对文学的浪漫憧憬。
“令尊是作家吗?”“不是。
”叶初绿红着脸,含羞答道:“家父是慈群女中的国语教员……”“他会成为诗人的。
”“不会了,他前年就病逝了。
”“哦,对不起。
”林姑娘表达了歉意与同情。
她对这个少年丧父的女生更倍加呵护,常鼓励她朝文学方向发展。
叶初绿的英语和语文都很受林姑娘的赞赏:“你的作文很有卡尔·杰洛拉普的韵味,读过《明娜》吗?乘着年轻记性好,不妨多读点北欧作家群的名著,他们的作品就像他们的国土一样美丽。
”在林姑娘的影响下,初绿真的一度迷上了文学。
她常在课余独自漫步到大德记,面对柔沙细浪,轻声诵读杰洛拉普或庞陀彼丹的小说, ③但更令她醉心的是拉格洛芙想象力丰饶的作品, ④她甚至幻想着远嫁到北欧那块童话的土地。
叶初绿高中毕业前夕,林姑娘写信给母校哥大,极力推荐这位文静的国语教员女儿:“鼓浪屿是中国的北欧,宁静而和谐。
叶小姐可能成为中国的拉格洛芙,东方式的尼尔斯奇遇毫无疑义应出自鼓浪屿人的手笔。
”但是,初绿姐错过了这个良机,高中刚毕业就被窘境下的母亲把她许配给仰光华侨弟子倪尔思先生,一位太古洋行的会计,前年才不幸丧妻,独居在那幢红砖洋房里。
叶初绿哭肿了眼皮,找林姑娘商议。
美国人激动得大叫起来:“不行,你不能这样轻易地断送自己,哥大已答应给你全额奖学金了。
”初绿只能低泣着:“我没办法,我看母亲实在太可怜了……”“你自己更可怜!你应该逃婚,你不应该成为另一个明娜。
”初绿姐没有选择逃,而顺从了母亲做主的婚姻。
那时,一水之隔的厦门早叫日本人占领了,大量厦门的富贵人家都拥进租界的鼓浪屿,那是这个小岛畸形繁荣的年代。
倪而思先生和叶初绿的婚礼是在紧邻博爱医院的海滨旅舍举行的,主人和来宾还在临海的草坪上照了张全家福式的照片,林姑娘也一身洁白长裙地紧挨着初绿站着,她终于答应了充当新娘伴的角色。
“贺喜你,初绿,你没写成东方的尼尔斯奇遇,却奇遇了倪而思先生,妙极了!命运之神就这么捉弄人类。
”林姑娘在倪家的喜宴上风趣地显耀着自己的文学才能和中文水平,略带醉意的碧眼里闪烁着狡洁而嫉妒的火花。
过后,当她收到叶初绿送来的全家福式的结婚照,竟醋意大发作地把它撕个粉碎,过会儿,又含着泪水仔细地把它拼凑粘合起来。
思忖许久,林姑娘提笔在照片的背面写下了一行英文的叶慈《塔》里的第一行诗句:这种荒谬,我该怎么办?心呵,烦恼的心呵——三初绿姐坐在那张硕大的长形会议桌前,粗糙的桌面上就搁着那帧破碎重粘的全家福式的结婚照。
她的心一阵紧缩,想搞清楚这帧30年前的老照片,一个普通人家的结婚照,怎么会落到派出所的手里并好像引起了公安们的极大兴趣。
今天午饭时接到派出所的开会通知时,初绿姐就满腹狐疑,虽正处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揪心日子,人人都有可能突然变成敌人的危险,但她自以为一辈子都当家庭主妇,连鼓浪屿都难得离开,像菜篮子里就摆着的青葱和豆腐,有啥好查呢?说是开会,大得有点夸张的会议桌旁只坐着三个人,她自己,对面那位挺脸熟的老安公,绷着一身皱巴巴的蓝色干部装和一脸严肃的神气,还有一位女孩子好像与她儿子同班的同学。
她儿子去年下乡去了,这女孩大概是留城的街道新“桌布”吧。
“初绿姐,”女孩子倒挺礼貌地先开腔:“这是市里三○办的洪同志,他想了解一下你结婚照片上那位美帝女间谍的事。
”她脑袋嗡嗡直响,似乎看见洪同志狞笑着掏出枪来,幸亏是错觉,他掏出的是香烟,边划火柴,边翻过那帧照片的背面:“知道这上面写的英文是什么意思吗?”初绿姐刹那间有一种触电的感觉,那是多么熟悉的字迹,流利而又漂亮!叶慈的诗,“这种荒谬”,好几回她们相拥在夜幕中,林姑娘低吟起这位爱尔兰诗人啜泣般的诗句。
她摇摇头,颤粟的双唇含混不清地喃语着。
“你不是毓德女中的高材生吗?英文都忘光啦?”洪同志嘲弄道,把照片又翻过来,“这只不过是帝国主义走狗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狂吠,无奈的狂呔。
”“是的,是的。
”初绿姐连忙附合道。
幸亏他们都是玩政治的高手,也幸亏那是泛政治的年代,无人可理解林姑娘“烦恼的心”,更无人窥视到她们之间的“荒谬”。
“市三○办已经决定重审1951年的美帝间谍小组案,深挖隐藏的阶级敌人。
这帧照片是我们从林娜的宗卷里调出来的,这个女间谍既然当了你的新娘伴,就说明了你很早就与她有紧密的关系。
”初绿姐一阵战战兢兢地表白:“她是我的老师,后来又比较要好。
真的一点不知道她是间谍,我一辈子都呆在家里,真的一点也不懂,真的只是好朋友,没看出她……”初绿姐有很深的文学根底和很高的语言天份,但她此时却语无伦次,不知所云。
她已深深地被恐惧掳住,她觉得自己就是小卡尔岛上山洞里的雌雁黛芬,狐狸已出现在山崖上,她已听到脚爪碰到石头,发出咯嗒的响声,她指望尼尔斯和公羊的出现,但她们都远在国外,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绝望地闪过了死亡的念头:这回准得死在这个山洞了,面对翻滚的海涛,映着月光,美景如画。
⑤她把头埋得很低,掏出手帕接捂住簌簌下流的泪水。
“你不要紧张,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
”洪同志把那帧破碎重粘的老照片收进文件夹子里,缓缓地说:“你是老鼓浪屿,我也是老鼓浪屿,对鼓浪屿的过去都很清楚……”初绿姐抬起头,透过泪眼望着捏住她的命运的男人:他也是鼓浪屿人?难怪这么脸熟,她猛然想起来了,这位三○办的同志就是40年代在龙头街卖烤地瓜的“番薯洪”!“这次清理阶级队伍跟以前的运动不一样,是要最广泛地发动群众,挖地三尺也要把隐藏的阶级敌人揪出来。
你先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回忆回忆,把有关林娜的材料写出来,家里还有什么林娜的照片统统缴出来……”洪同志语气严厉,但脸色并不太凶神恶煞。
结束谈话时,他甚至伸出手,摆出要握手告别的姿态。
初绿姐一时不知所措,但还是很快清醒过来,忙不迭地伸出细纤小手,让她和那只粗如砂纸的大手搓合着。
这是22年来初绿姐第一次与成年男人的肉体接触,她竟有点脸红耳热。
她48岁了,月事停停来来的,正烦人,况且她对异性早有一种抗拒的惊惶,但那卖烤地瓜的手还是让她产生一种尼尔斯靠在大公羊身上的幻觉。
四从派出所出来,初绿姐并没有回家的欲望。
她需要冷却自己,又好像急于找到林姑娘商议如何对付眼前的困境。
她漫无目的地朝博爱医院的海边走去,很快就置身于她30年前结婚摆宴的海滨旅舍。
这家三四十年代鼓浪屿最豪华的宾馆,如今住满了解放军和他们的家属,而旅舍前的那座石筑的码头已倒塌成一堆乱石。
初绿呆呆地凝视着那堆长满青苔和蠔苗的石条,似乎看见林姑娘从涂滩徐徐升起。
她出淤泥而不染,绣花的旗袍紧裹着白皙的躯体。
林姑娘回过头,含着一丝很甜的微笑,很从容大方,一点也不像正被驱逐出境的女间谍。
林姑娘和长期居住鼓浪屿的十来位美国人,就是从这座码头押上汽艇的,那令人心碎的一幕永远定格在初绿姐日渐老花的视网膜里。
她那天得到消息,抱着不满3岁的儿子匆匆赶到海边,码头正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站满持枪的军人。
她只能远远地站在电灯杆下,不顾一切地向那串在滑溜溜的石板上举步艰难的美国人挥手。
正要跨上小汽艇的林姑娘好像也感觉到相濡以待的密友的出现,回过头,做了一个飞吻的动作。
海风吹乱了她的金发,遮盖着她大半个脸,什么也看不清,初绿姐觉得她正含着眼泪,而她自己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