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俊文 散文[精品]
第二单元《一个消逝了的山村》教案+++2020—2021学年统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

第二单元 7.1 一个消逝了的山村教案教学目标1.了解作者,品味其散文的特色。
2.品读文章,涵咏主旨,领悟意象的内涵。
3.培养珍爱自然、珍爱生命的意识。
核心素养语言建构与运用:分析散文的结构特征,体会散文的语言特色。
思维发展与提升:领悟文中意象的丰富内涵。
审美鉴赏与创造:感受作者珍爱自然、珍爱生命、共创美好家园的思想感情。
文化传承与理解:培养珍爱自然、珍爱生命的意识。
教学重难点重点:分析散文的结构特征,体会散文的语言特色。
难点:品读文章,涵咏主旨,领悟意象的内涵。
课前准备1、指导学生完成预习2、制作课件教学过程一、导入新课现代散文家余秋雨先生曾在他的散文集《千年一叹》中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大自然的景物有百分之一能写进历史,千分之一能成为景观,万分之一能激发诗情。
这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的神奇瑰丽之处。
她繁富缤纷,延往续来,既孕育了万物生灵,又滋润了人类灵魂。
古往今来,无娄文人墨客面对那即使是只有万分之一才能激发诗情的景物,寄怀感慨,与自然同悲喜、共哀乐。
这一节课,就让我们一起走近作家马至,聆听他与自然的心灵碰撞。
二、写作背景《一个消逝了的山村》选自冯至的散文集《山水》。
《山水》的出版有一个过程,1942年秋,冯至将过去写的十篇散文集在一起,题名《山水》,1943年9月在重庆出版。
后来冯至又加上之后写的三篇散文,再加上一个《后记》。
《山水》出版后,学界对它的评价很高,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认为:虽然冯至在四十年代只有《十四行集》和《山水》两小本著作,但是在诗和散文两方面,他都站住“一览众山小”的高峰。
《山水》中的《一棵老树》和《一个消逝了的山村》最为精纯,并将前者称为“白话散文诞生以来的杰作”。
三、作者介绍冯至(1905-1993),现代著名诗人。
原名冯承植,河北涿州人。
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1923年后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始发表新诗。
1927年4月出版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1929年8月出版第二部诗集《北游及其他》,记录自己大学毕业后的哈尔滨教书生活。
《有些路,你并不清楚》阅读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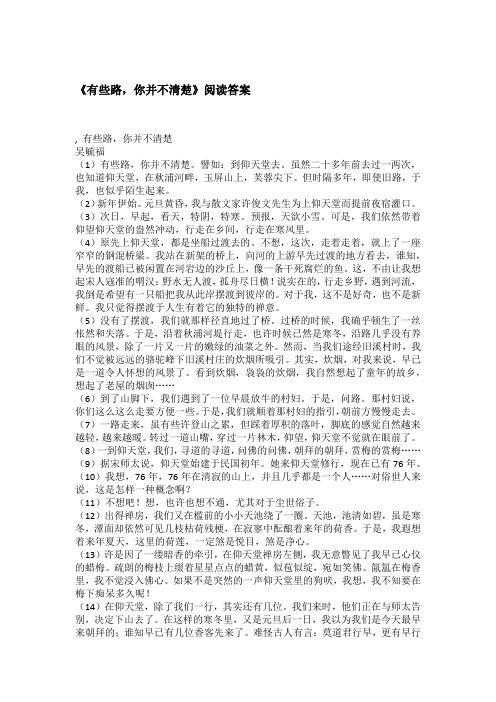
《有些路,你并不清楚》阅读答案, 有些路,你并不清楚吴毓福(1)有些路,你并不清楚。
譬如:到仰天堂去。
虽然二十多年前去过一两次,也知道仰天堂,在秋浦河畔,玉屏山上,芙蓉尖下。
但时隔多年,即使旧路,于我,也似乎陌生起来。
(2)新年伊始。
元旦黄昏,我与散文家许俊文先生为上仰天堂而提前夜宿灌口。
(3)次日,早起,看天,特阴,特寒。
预报,天欲小雪。
可是,我们依然带着仰望仰天堂的盎然冲动,行走在乡间,行走在寒风里。
(4)原先上仰天堂,都是坐船过渡去的。
不想,这次,走着走着,就上了一座窄窄的钢混桥梁。
我站在新架的桥上,向河的上游早先过渡的地方看去,谁知,早先的渡船已被闲置在河岩边的沙丘上,像一条干死腐烂的鱼。
这,不由让我想起宋人寇准的喟汉: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说实在的,行走乡野,遇到河流,我倒是希望有一只船把我从此岸摆渡到彼岸的。
对于我,这不是好奇,也不是新鲜。
我只觉得摆渡于人生有着它的独特的禅意。
(5)没有了摆渡,我们就那样径直地过了桥。
过桥的时候,我确乎顿生了一丝怅然和失落。
于是,沿着秋浦河堤行走,也许时候已然是寒冬,沿路几乎没有养眼的风景,除了一片又一片的嫩绿的油菜之外。
然而,当我们途经旧溪村时,我们不觉被远远的骆驼峰下旧溪村庄的炊烟所吸引。
其实,炊烟,对我来说,早已是一道令人怀想的风景了。
看到炊烟,袅袅的炊烟,我自然想起了童年的故乡,想起了老屋的烟囱……(6)到了山脚下,我们遇到了一位早晨放牛的村妇。
于是,问路。
那村妇说,你们这么这么走要方便一些。
于是,我们就顺着那村妇的指引,朝前方慢慢走去。
(7)一路走来,虽有些许登山之累,但踩着厚积的落叶,脚底的感觉自然越来越轻,越来越暖。
转过一道山嘴,穿过一片林木,仰望,仰天堂不觉就在眼前了。
(8)一到仰天堂,我们,寻道的寻道,问佛的问佛,朝拜的朝拜,赏梅的赏梅……(9)据宋师太说,仰天堂始建于民国初年。
她来仰天堂修行,现在已有76年。
(10)我想,76年,76年在清寂的山上,并且几乎都是一个人……对俗世人来说,这是怎样一种概念啊?(11)不想吧!想,也许也想不通,尤其对于尘世俗子。
许俊文散文 落在故土的雪 文学类文本阅读理解题

许俊文散文落在故土的雪文学类文本阅读理解题(最新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文档下载后可定制修改,请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和使用,谢谢!并且,本店铺为大家提供各种类型的经典范文,如语文试题、作文大全、写作练习、文学阅读、语文教学、阅读理解、诗词鉴赏、成语词典、时评借鉴、其他资料等等,想了解不同范文格式和写法,敬请关注!Download tips: This document is carefully compiled by this editor.I hope that after you download it, it can help you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The document can be customized and modified after downloading, please adjust and use it according to actual needs, thank you!In addition, this shop provides you with various types of classic sample essays, such as Chinese test questions, composition books, writing exercises, literary reading, Chinese teach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poetry appreciation, idiom dictionary, time evaluation reference, other materials, etc.,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difference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the format and writing of the sample essay!许俊文散文落在故土的雪文学类文本阅读理解题(二)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
许俊文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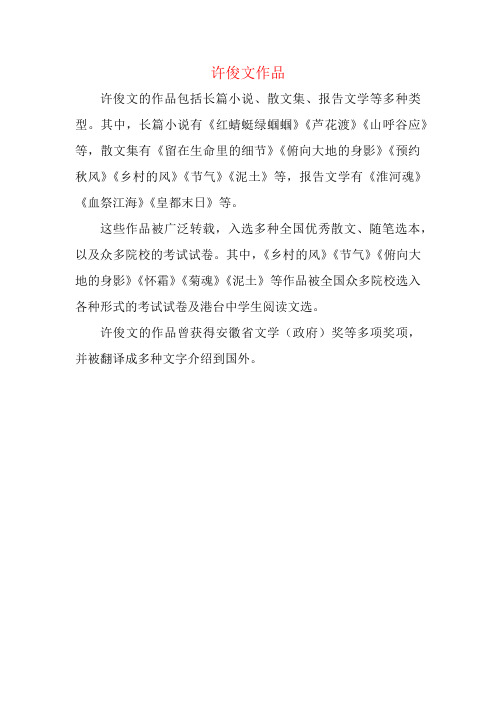
许俊文作品
许俊文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散文集、报告文学等多种类型。
其中,长篇小说有《红蜻蜓绿蝈蝈》《芦花渡》《山呼谷应》等,散文集有《留在生命里的细节》《俯向大地的身影》《预约秋风》《乡村的风》《节气》《泥土》等,报告文学有《淮河魂》《血祭江海》《皇都末日》等。
这些作品被广泛转载,入选多种全国优秀散文、随笔选本,以及众多院校的考试试卷。
其中,《乡村的风》《节气》《俯向大地的身影》《怀霜》《菊魂》《泥土》等作品被全国众多院校选入各种形式的考试试卷及港台中学生阅读文选。
许俊文的作品曾获得安徽省文学(政府)奖等多项奖项,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2020年高考语文二轮现代文专题复习--许俊文作品精选精练

许俊文作品精选精练苍凉许俊文①认识塔里木河,我收获的却是苍凉。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只给了“苍凉”两个字的释义:凄凉。
其实压根儿就不是那么回事。
不错,苍凉里是包含着凄凉的成分,但不能因此就把苍凉与凄凉一锅煮了。
以我的真实感受,凄凉不过是心灵里一块缓慢融化的残冰,而苍凉就如同置身于一片迷茫、空旷的雪原,你很难确切知道它的边际在那里。
②塔里木河给我的感觉正是如此。
本来,在我的西部之旅中,是没有塔里木河的。
不是我不想见识这条西部最长的河流,而恰恰是因为它实在太长,使我望尘莫及。
③那是五月初,一场沙尘暴刚刚谢幕,烈日便在大漠堂而皇之地登场。
那天,我兴冲冲地向罗布泊中的楼兰遗址贸然前行,不料,车出米兰镇不远即被路卡强行拦阻,多年积存的那么一点心愿陡然落空,不觉怅然弥怀。
于是,我只好抱着舍而求其次的想法,转道去了塔里木河。
④眼下正是高山冰雪消融的季节,按说,靠雪水滋养的塔里木河该是血脉贲张的。
然而,当我翻越一座沙梁又一座沙梁,直到抵达一处凹槽形的地带时,陪同的向导这才把真相端给我:这就是塔里木河。
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心里直犯嘀咕,塔里木河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呢?是不是向导蒙骗了自己?向导见我神情不爽,反问道,你说塔里木河该是什么样子?我哑然。
就在那一刻,我心中萦绕已久的梦突然间破灭了。
我怔怔地站在河岸的沙丘上,半天都没有醒过神来。
⑤于是,我不得不接受眼前与想象反差极大的现实,开始打量这条早已枯竭的河流。
尽管当时沙漠中的气温高达摄氏40多度,但是,我却感到一种彻骨的寒冷和旷世的苍凉扑面而来。
在下心里想,与其说我来领略塔里木河的雄姿,倒不如说是来凭吊它的亡灵。
⑥这里,我不妨用战栗的目光勾勒一幅苍白的素描:宽不过百米的塔里木河,如同一条干瘪而扭曲的血管,自西向东,从沙漠里来,再到沙漠中去。
没有水。
也没有飞鸟。
河底偶尔可以见到一小片潮湿的沙土,上面长满了瘦弱的芦苇和罗布麻。
河岸即是一座座不规则的沙丘,它们从南北两个方向楔入河床,窄一点的地方即将完成合龙。
许俊文乡村的泥土读后感

许俊文乡村的泥土读后感读许俊文写的关于乡村泥土的文章,就像在炎热的夏日里喝了一杯凉凉的井水,那股清爽劲儿直透心底,又像是在寒冬里钻进了暖和的被窝,满是熟悉又亲切的感觉。
文章一开篇,那泥土就像是一个许久未见的老友,一下子蹦到了眼前。
许俊文笔下的乡村泥土,可不是那种干巴巴、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活灵活现的。
他写泥土的气息,就仿佛我能闻到那股特有的、带着淡淡草香和腐朽树叶味道的泥土香。
每次读到描写泥土气味的句子,我就想起小时候在农村,下过雨之后,空气里弥漫的那种味道,恨不得马上跑回乡下再去闻一闻。
而且呀,这泥土还像是一个有故事的老人。
许俊文把泥土和乡村里的各种事情联系起来,那些在泥土上耕种的农民,就像是泥土的孩子一样。
他们依赖着泥土,泥土也孕育着他们。
读到这儿,我就想起我老家的那些叔叔伯伯,每天扛着锄头在地里忙活着,那片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根子。
每一粒粮食的收获,都是泥土和他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许俊文在写泥土的时候,还写了很多乡村里的小细节。
比如说小孩子在泥土里玩耍,弄得满身是泥,回家被大人骂,这场景简直太熟悉了。
感觉那时候的泥土就是我们最好的玩具,捏个小泥人,挖个小泥坑,能玩上一整天。
他把乡村泥土里蕴含的那种欢乐、质朴都给写出来了。
这篇文章让我重新认识了乡村的泥土。
以前觉得泥土嘛,就是脚下踩的东西,平平无奇。
但现在我知道了,那是乡村的灵魂所在。
它承载着乡村的历史、文化,还有人们的情感。
就像我们现在住在城市里,看着那些高楼大厦,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读完这篇文章才明白,少的就是那片能让我们心灵得到慰藉的泥土。
许俊文的文字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我记忆深处关于乡村泥土的大门,让我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能有那么一刻,沉浸在乡村泥土那简单又纯粹的世界里,感受那份宁静和美好。
许俊文 散文[精品]
![许俊文 散文[精品]](https://img.taocdn.com/s3/m/b4795dee65ce05087632135c.png)
许俊文散文[精品]蛙鸣城更幽许俊文沐浴过杜牧笔底的杏花雨,也饮过李白诗中的秋浦水,至于莲花峰上采兰,仙寓山中品茗,黄公酒垆里饮酒,只要兴致所至,便是举手投足的事了。
——池州这座袖珍的江南小城,就这么不动声色地羁留了我。
于是,或早或晚的,我便以散步来触摸与体味这座城市的细节。
我是一个在意细节的人,起码写作是如此。
一个人若是爱上一个地方,最好的方式就是散步;脚步所到之处,那些地方才是你的,你也才有资格属于那个地方。
不然,你顶多也只能算个客人而已。
池州是个适宜于散步的城市,到处小桥流水,游目芳草时花,即便是冬天,这座城市的底色也不会有多少改变——依然绿着,人徜徉其间,并不觉得萧杀。
譬如我,就是从这里的冬天开始散步的,散着散着,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春天。
这里的春天是一幅气韵横生的水墨画,那夹道红杏,那满城烟雨,那杏花烟雨中穿梭啁啾的紫燕,都是其他城市难得一见的好景致。
不过,我还是更喜欢这里的蛙声。
是的,蛙声。
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诗人移花接木的艺术想象。
青蛙这个大自然中的小灵物,说它们是这座小城的纯情歌手,是不会有谁质疑的,每当夜幕缓缓降临,它们就亮开了歌喉:咕、咕咕……咯、咯咯……咯咕、咯咕……咕咯、咕咯……这声声蛙鸣,犹如行歌的散板,空灵,清越,既包含着泥土的朴素,又有着神曲的飘渺,任你百遍千遍地聆听,也不会生厌。
常常,我就一个人坐在水边,关了手机,断了尘念,专注地听蛙,想听多久就听多久。
有时候干脆躺在草地上,似听非听,恍恍惚惚的,于蛙声中载沉载浮……记得初次听到蛙鸣,是在“惊蛰”后的某个夜晚。
当时大地与草木刚刚还阳,乍暖还寒的气温游魂似的难以捉摸。
然而,就在我经过城中的一个半地下停车场时,几声脆生生的蛙鸣,竟从车库的屋顶上和着雨水一起洒落下来,每一个音符都是湿漉漉的,当时就把我给怔住了。
要知道,这里可不是青草池塘,也非稻花香里,那一人多高的屋顶上,怎么就有了蛙呢,这是一个谜。
谜底似乎只有青蛙知道。
几场烟雾般的细雨过后,气温便在江南小城慢慢地扎下了根。
在错综的层次里反复咏叹——评许俊文的《那些去向不明的事物》

式( 生存环 境 ) 的转 变 , 当然也 必
然 涉及 人 类 精 神 的 形 成 , 导 致 精 神之 变。恐怖 , 禁 忌, 于 此 前 人 类
般 而言 ,这 类题材 的作 品
常常 比较 单调 , 内容和结 构 多平 直的铺 陈和正面 的渲染 。而这 篇
益彰、 水 乳 交 融 的 艺术 整 体 。而 我
最 看 重 的是 作 家 透 过 去 向 不 明 的
以前 记忆 中的村 庄里 曾经发 生的 失踪 事件 ,一是 满仓 的毛驴 失而 复得 ,一是 陈百步 的狗被 人打 死
剥皮 。 这 是引子 , 后 面 的 正 题 部 分
着 重写 了三种 失踪 的 乡下事 物 : 红稻 、 红 娘 子 和 炊 烟 。红 稻 写 得 最 简 略 , 但 前 面 也 有 两 段 铺 垫 和 转
学教育
在 错 综 的 层 次 里 反 复 咏 叹
— —
评许俊 文 的《 那些 去 向不 明的事物》
看 到 这 篇 散 文 的 题 目时 我 并 旧之 情 。但是 到 了后来 , 作 者 逐 渐 发力 , 步步 深 入 追 问 。在 写 因为 我 本 人 多 年
的 , 也 许 可 以说 它 们 对 人 类 精 神 的形 成 不 全 是 无 益 的 。 中 医是 一 种 文化 , “ 不 知道 中 医少 了红 娘 子 这 味 药 后 果 会 如 何 ,更 不 知 道 随 着 地 球 上 许 多 物 种 的加 速 灭 绝 ,
后 ,从 墓 地 到 舞 台 ,从 往 昔 到 当 下, 不 断跳跃 , 波 澜 横 生 。 写 炊 烟 的 文 字 则 同写 鸡 鸣 的 文 字 结 合 起 来 ,鸡 鸣 的消 失 也 就 是 炊 烟 的 消 失, 结 构 和 意 蕴 得 到 双 重 的拓 展 。 繁 复 的层 次 中贯 串着 一个 灵 魂, 即作 者 深 广 的 忧 思 , 丰 富 的 层 次 安 排 与深 广 的思 想 内涵 是 相 得
一首生命的赞歌—许俊文《乡村的风》赏析

一首生命的赞歌—许俊文《乡村的风》赏析许俊文的《乡村的风》,它给了我们太多的感动,也激励了我们去做好每一件事。
那么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美文欣赏——《乡村的风》吧!首先,我要说的是这篇文章的标题,因为只有当你的眼睛注视到“乡村”两个字的时候,才能明白作者为什么选择了如此一个小小的窗口,然后再慢慢地融入到文章里面,才能真正懂得作者写作时的心情。
一个女孩子,她想像妈妈一样画画,但是他却没有相应的技巧;她希望自己长得和别的女孩一样,可惜又不可能成为那样的“美丽姑娘”。
对于农村的贫穷,女孩从内心深处感到恐惧。
后来,她遇见了一个朋友,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有关画画的知识和技巧。
但是,女孩并不知道这位好友的名字,只知道他的头发是白色的,像秋天里飘零的树叶一样。
小小的窗口上,挂着一张白纸,几支粉笔。
纸上,勾勒出了几个醒目的字母,外加几条歪歪扭扭的线条。
或许是因为画得实在难看,所以字母的笔触都比较潦草,一点儿也不像。
女孩拿着这张纸,反复端详着,泪水模糊了双眼。
她无意间瞥见旁边的草垛,下意识地伸手去抓了一把,然后放在嘴里咬了一口,但是这种味道并不好吃,还带着泥土的清香。
这时候,女孩似乎想起了什么,赶忙冲到妈妈身边:“妈妈,您在干什么?为什么我总是闻到泥土的气息?”“傻孩子,我在修补墙壁呀!”“为什么呢?”女孩听了很惊讶,她赶紧把手中的粉笔扔掉,捡起那张纸,“妈妈,我想跟您学画画。
”“哈哈,你在开玩笑吗?”“我知道您在骗我,但是我真的想学画画。
”“小孩子家家的,整天就想着玩儿,我早就烦透了!”“不嘛,不嘛,就算您烦我,我也愿意!”女孩急了,两只手使劲扯着妈妈的衣服。
妈妈虽然心疼,却狠不下心来。
我一直是在体会着作者这种大爱和人间大爱的。
即使是这种小孩子们的纯真,也感动了作者。
我无法用言语来描述这种爱,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文化,哪个国家的人,爱的文化都是一样的。
生命,本就是一种存在。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心灵最隐秘的角落,编织着五彩缤纷的梦,即使只是为了活着,也会燃烧出熊熊的火焰。
许俊文乡村的泥土读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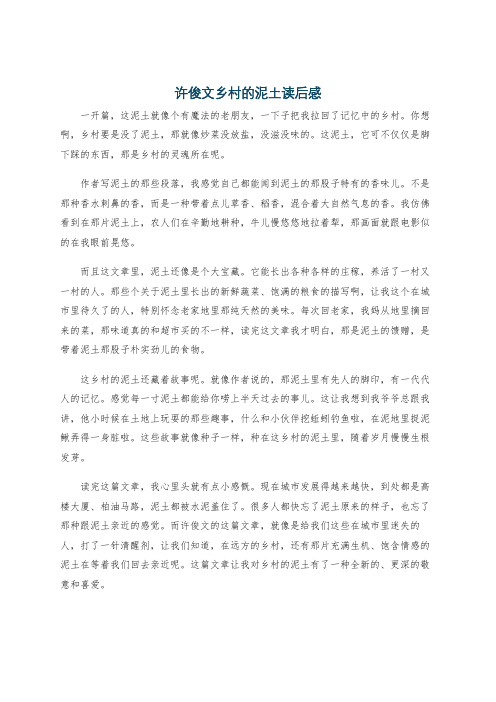
许俊文乡村的泥土读后感一开篇,这泥土就像个有魔法的老朋友,一下子把我拉回了记忆中的乡村。
你想啊,乡村要是没了泥土,那就像炒菜没放盐,没滋没味的。
这泥土,它可不仅仅是脚下踩的东西,那是乡村的灵魂所在呢。
作者写泥土的那些段落,我感觉自己都能闻到泥土的那股子特有的香味儿。
不是那种香水刺鼻的香,而是一种带着点儿草香、稻香,混合着大自然气息的香。
我仿佛看到在那片泥土上,农人们在辛勤地耕种,牛儿慢悠悠地拉着犁,那画面就跟电影似的在我眼前晃悠。
而且这文章里,泥土还像是个大宝藏。
它能长出各种各样的庄稼,养活了一村又一村的人。
那些个关于泥土里长出的新鲜蔬菜、饱满的粮食的描写啊,让我这个在城市里待久了的人,特别怀念老家地里那纯天然的美味。
每次回老家,我妈从地里摘回来的菜,那味道真的和超市买的不一样,读完这文章我才明白,那是泥土的馈赠,是带着泥土那股子朴实劲儿的食物。
这乡村的泥土还藏着故事呢。
就像作者说的,那泥土里有先人的脚印,有一代代人的记忆。
感觉每一寸泥土都能给你唠上半天过去的事儿。
这让我想到我爷爷总跟我讲,他小时候在土地上玩耍的那些趣事,什么和小伙伴挖蚯蚓钓鱼啦,在泥地里捉泥鳅弄得一身脏啦。
这些故事就像种子一样,种在这乡村的泥土里,随着岁月慢慢生根发芽。
读完这篇文章,我心里头就有点小感慨。
现在城市发展得越来越快,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柏油马路,泥土都被水泥盖住了。
很多人都快忘了泥土原来的样子,也忘了那种跟泥土亲近的感觉。
而许俊文的这篇文章,就像是给我们这些在城市里迷失的人,打了一针清醒剂,让我们知道,在远方的乡村,还有那片充满生机、饱含情感的泥土在等着我们回去亲近呢。
这篇文章让我对乡村的泥土有了一种全新的、更深的敬意和喜爱。
乡村的风 许俊文

16.作者借“乡村的风”表达了多种情感, 请分要点加以概括。(6分) ①对自然生态环境下的乡村的热爱。 ②对给予自己温情的故乡的感激。 ③对朴实而明晓事理的父亲的敬爱。 ④对故乡纯朴的风格人情的赞美。 ⑤对自然的永恒、生命的生生不息的敬畏。
17.无形的风在文中被描绘得可见可感。试从修 辞手法的角度,在第二、五两个自然段中分别举 出一例加以赏析。(6分) 第二自然段:“用顽皮的小手……”句,运用拟人 句,写出风的轻柔,让“我”感受到故乡的温馨、 亲切。(举出“摇头摆尾的小花狗……”或“好像 一个去镇上打酒的孩子……”等句,并指出拟人、 比喻等修辞手法,进行赏析,均可) 第五自然段:“庄稼在风中拔节……”句,运用排 比,描绘风中动人景象,使读者感受到风中勃勃 生机。(举出“春风归来遍地绿……”句,并指出 对偶的修辞手法,进行赏析,也可)
乡村里的许多事物,小至一片浮萍,一株草,大 到一棵树,一座山,都与风息息相关。春风归来 遍地绿,它们不得不绿;秋风君临千叶黄,它们 不得不黄。在这回黄转绿的变幻之中,永远不老 的似乎只有土地,只有风。一拔又一拔的风,吹 了几千年,几万年,它吹走了许多东西,又吹来 了许多东西。庄稼在风中拔节,驴马在风中友情, 鸟雀在风中飞翔,蟋蟀在风中浅唱低吟…… 倘若没有风,这个世界多么沉寂!
乡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的风 许俊文
风是乡村的魂。它不喜欢老是待在一个地方,到 处游荡着,时南时北,忽东忽西的。它走到哪里, 哪里就能感觉到乡村的呼吸。 每次从城里回到老家豆村,第一个迎接我的便是 风。我们虽然好多年没见面了,但它一点儿也不 生分,先是用顽皮的小手,把我服服帖帖的头发 拨弄乱,再在我干净的皮鞋和西服上,随意撒些 尘土与细碎的草屑。要是春天,风就像一只摇头 摆尾的小花狗,当我刚从汽车上走下来,视觉还 没来得及舒展开,它就从我的身上嗅出了豆村的 气味,亲亲热热地扑过来,伸出温软的小舌头, 一下一下舔我的手与脚踝,你赶也赶不走。如果 是秋天,风里便有了果实发酵的味道,那幽微的 醇意,好像一个去镇上打酒的孩子,不小心把酒 洒了一路,惹人隐隐地有些陶醉。
一首生命的赞歌—许俊文《乡村的风》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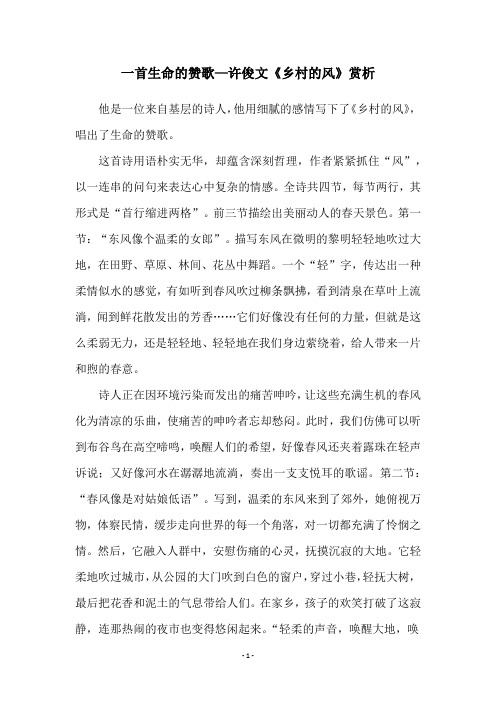
一首生命的赞歌—许俊文《乡村的风》赏析他是一位来自基层的诗人,他用细腻的感情写下了《乡村的风》,唱出了生命的赞歌。
这首诗用语朴实无华,却蕴含深刻哲理,作者紧紧抓住“风”,以一连串的问句来表达心中复杂的情感。
全诗共四节,每节两行,其形式是“首行缩进两格”。
前三节描绘出美丽动人的春天景色。
第一节:“东风像个温柔的女郎”。
描写东风在微明的黎明轻轻地吹过大地,在田野、草原、林间、花丛中舞蹈。
一个“轻”字,传达出一种柔情似水的感觉,有如听到春风吹过柳条飘拂,看到清泉在草叶上流淌,闻到鲜花散发出的芳香……它们好像没有任何的力量,但就是这么柔弱无力,还是轻轻地、轻轻地在我们身边萦绕着,给人带来一片和煦的春意。
诗人正在因环境污染而发出的痛苦呻吟,让这些充满生机的春风化为清凉的乐曲,使痛苦的呻吟者忘却愁闷。
此时,我们仿佛可以听到布谷鸟在高空啼鸣,唤醒人们的希望,好像春风还夹着露珠在轻声诉说;又好像河水在潺潺地流淌,奏出一支支悦耳的歌谣。
第二节:“春风像是对姑娘低语”。
写到,温柔的东风来到了郊外,她俯视万物,体察民情,缓步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对一切都充满了怜悯之情。
然后,它融入人群中,安慰伤痛的心灵,抚摸沉寂的大地。
它轻柔地吹过城市,从公园的大门吹到白色的窗户,穿过小巷,轻抚大树,最后把花香和泥土的气息带给人们。
在家乡,孩子的欢笑打破了这寂静,连那热闹的夜市也变得悠闲起来。
“轻柔的声音,唤醒大地,唤醒人们的希望。
”“我的眼睛”从初春二月的阳光到五月花开时的山野香气,饱览了春风带给我们的幸福和快乐。
是啊,在阳光照耀的早晨,看着成群的蝴蝶飞舞,闻着野花的芬芳,聆听百灵鸟清脆的歌声,谁能不被这快乐陶醉?此时,大地已经苏醒,万物萌生,遍地是青草、绿叶、红花。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时,大地像蒸笼一样被火烤着,而东风仍在大地的身旁“轻歌曼舞”。
“炎热的太阳滚烫着大地,仿佛热浪在翻滚。
”诗人用热烈的笔调,抒发出内心的焦灼和热切盼望春风早日归来的愿望。
有些路你并不清楚-许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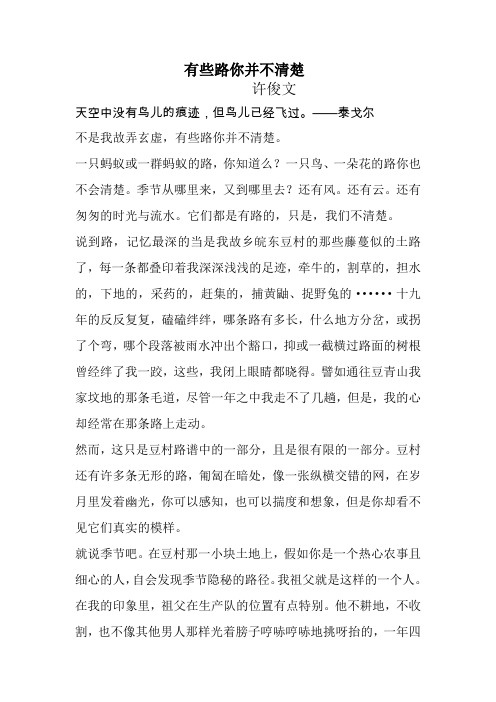
有些路你并不清楚许俊文天空中没有鸟儿的痕迹,但鸟儿已经飞过。
——泰戈尔不是我故弄玄虚,有些路你并不清楚。
一只蚂蚁或一群蚂蚁的路,你知道么?一只鸟、一朵花的路你也不会清楚。
季节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还有风。
还有云。
还有匆匆的时光与流水。
它们都是有路的,只是,我们不清楚。
说到路,记忆最深的当是我故乡皖东豆村的那些藤蔓似的土路了,每一条都叠印着我深深浅浅的足迹,牵牛的,割草的,担水的,下地的,采药的,赶集的,捕黄鼬、捉野兔的······十九年的反反复复,磕磕绊绊,哪条路有多长,什么地方分岔,或拐了个弯,哪个段落被雨水冲出个豁口,抑或一截横过路面的树根曾经绊了我一跤,这些,我闭上眼睛都晓得。
譬如通往豆青山我家坟地的那条毛道,尽管一年之中我走不了几趟,但是,我的心却经常在那条路上走动。
然而,这只是豆村路谱中的一部分,且是很有限的一部分。
豆村还有许多条无形的路,匍匐在暗处,像一张纵横交错的网,在岁月里发着幽光,你可以感知,也可以揣度和想象,但是你却看不见它们真实的模样。
就说季节吧。
在豆村那一小块土地上,假如你是一个热心农事且细心的人,自会发现季节隐秘的路径。
我祖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我的印象里,祖父在生产队的位置有点特别。
他不耕地,不收割,也不像其他男人那样光着膀子哼哧哼哧地挑呀抬的,一年四季肩上只扛着一把锃光瓦亮的铁锹,整天在田野上转悠,系在青布长衫外的腰带上永远别着一根老长的烟袋,转一处,坐下来吃一袋烟,再接着转。
他这里瞅一眼,那里挖几锹土,看上去倒像个神秘兮兮的风水师。
但是,祖父有一手“绝活”是其他人望尘莫及的,他知道季节的路,更清楚庄稼的路,说得玄乎点,他有第三只眼。
可不!当豆村的最后一场雪还没化净时,我祖父就把生产队长章一哲叫到跟前,说,该整玉米墒了。
只此一句。
章一哲是个上海下放知青,对政治形势倒很敏感,分析起来一套一套的,可种地却是狗拉套子——不对路。
感受时光之美 二十四节气之春来万物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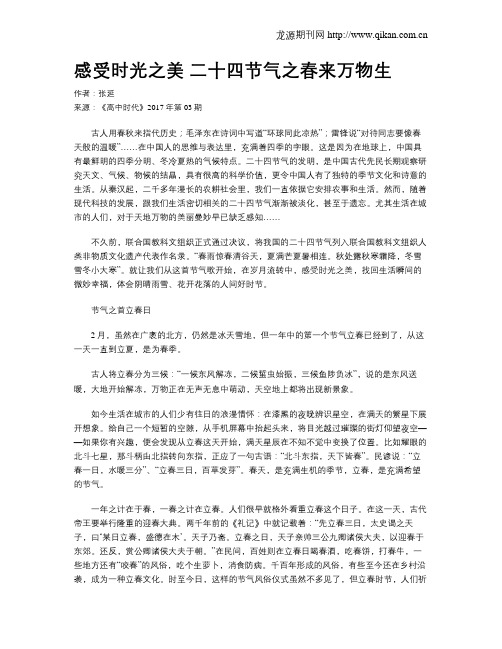
感受时光之美二十四节气之春来万物生作者:张延来源:《高中时代》2017年第03期古人用春秋来指代历史;毛泽东在诗词中写道“环球同此凉热”;雷锋说“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在中国人的思维与表达里,充满着四季的字眼。
这是因为在地球上,中国具有最鲜明的四季分明、冬冷夏热的气候特点。
二十四节气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先民长期观察研究天文、气候、物候的结晶,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更令中国人有了独特的季节文化和诗意的生活。
从秦汉起,二千多年漫长的农耕社会里,我们一直依据它安排农事和生活。
然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跟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二十四节气渐渐被淡化,甚至于遗忘。
尤其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对于天地万物的美丽曼妙早已缺乏感知……不久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决议,将我国的二十四节气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就让我们从这首节气歌开始,在岁月流转中,感受时光之美,找回生活瞬间的微妙幸福,体会阴晴雨雪、花开花落的人间好时节。
节气之首立春日2月,虽然在广袤的北方,仍然是冰天雪地,但一年中的第一个节气立春已经到了,从这一天一直到立夏,是为春季。
古人将立春分为三候:“一候东风解冻,二候蜇虫始振,三候鱼陟负冰”,说的是东风送暖,大地开始解冻,万物正在无声无息中萌动,天空地上都将出现新景象。
如今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少有往日的浪漫情怀:在漆黑的夜晚辨识星空,在满天的繁星下展开想象。
给自己一个短暂的空隙,从手机屏幕中抬起头来,将目光越过璀璨的街灯仰望夜空——如果你有兴趣,便会发现从立春这天开始,满天星辰在不知不觉中变换了位置。
比如耀眼的北斗七星,那斗柄由北指转向东指,正应了一句古语:“北斗东指,天下皆春”。
民谚说:“立春一日,水暖三分”、“立春三日,百草发芽”。
春天,是充满生机的季节,立春,是充满希望的节气。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春之计在立春。
人们很早就格外看重立春这个日子。
评许俊文的《暗物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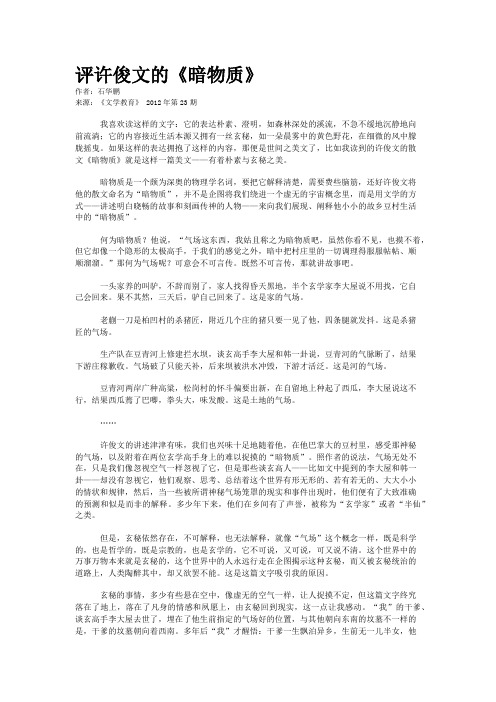
评许俊文的《暗物质》作者:石华鹏来源:《文学教育》 2012年第23期我喜欢读这样的文字:它的表达朴素、澄明,如森林深处的溪流,不急不缓地沉静地向前流淌;它的内容接近生活本源又拥有一丝玄秘,如一朵晨雾中的黄色野花,在细微的风中朦胧摇曳。
如果这样的表达拥抱了这样的内容,那便是世间之美文了,比如我读到的许俊文的散文《暗物质》就是这样一篇美文——有着朴素与玄秘之美。
暗物质是一个颇为深奥的物理学名词,要把它解释清楚,需要费些脑筋,还好许俊文将他的散文命名为“暗物质”,并不是企图将我们绕进一个虚无的宇宙概念里,而是用文学的方式——讲述明白晓畅的故事和刻画传神的人物——来向我们展现、阐释他小小的故乡豆村生活中的“暗物质”。
何为暗物质?他说,“气场这东西,我姑且称之为暗物质吧,虽然你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它却像一个隐形的太极高手,于我们的感觉之外,暗中把村庄里的一切调理得服服帖帖、顺顺溜溜。
”那何为气场呢?可意会不可言传。
既然不可言传,那就讲故事吧。
一头家养的叫驴,不辞而别了,家人找得昏天黑地,半个玄学家李大屋说不用找,它自己会回来。
果不其然,三天后,驴自己回来了。
这是家的气场。
老蒯一刀是柏凹村的杀猪匠,附近几个庄的猪只要一见了他,四条腿就发抖。
这是杀猪匠的气场。
生产队在豆青河上修建拦水坝,谈玄高手李大屋和韩一卦说,豆青河的气脉断了,结果下游庄稼歉收。
气场破了只能天补,后来坝被洪水冲毁,下游才活泛。
这是河的气场。
豆青河两岸广种高粱,松岗村的怀斗偏要出新,在自留地上种起了西瓜,李大屋说这不行,结果西瓜蔫了巴唧,拳头大,味发酸。
这是土地的气场。
……许俊文的讲述津津有味,我们也兴味十足地随着他,在他巴掌大的豆村里,感受那神秘的气场,以及附着在两位玄学高手身上的难以捉摸的“暗物质”。
照作者的说法,气场无处不在,只是我们像忽视空气一样忽视了它,但是那些谈玄高人——比如文中提到的李大屋和韩一卦——却没有忽视它,他们观察、思考、总结着这个世界有形无形的、若有若无的、大大小小的情状和规律,然后,当一些被所谓神秘气场笼罩的现实和事件出现时,他们便有了大致准确的预测和似是而非的解释。
说明文《趣谈扇子文化》+散文《太朴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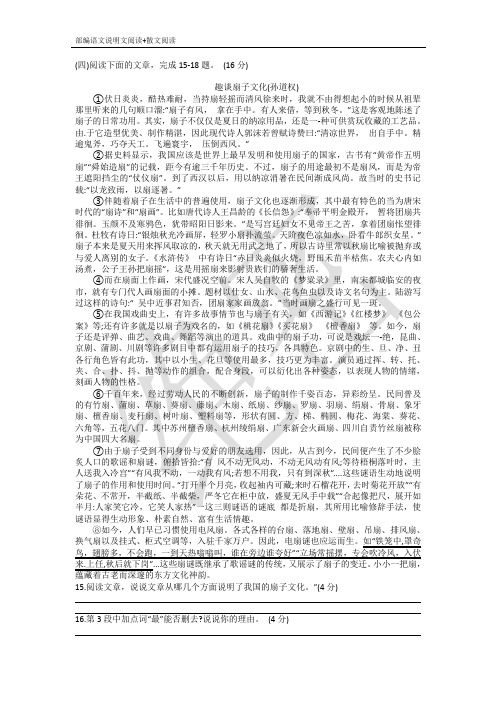
(四)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15-18题。
(16分)趣谈扇子文化(孙道权)①伏日炎炎,酷热难耐,当持扇轻摇而清风徐来时,我就不由得想起小的时候从祖辈那里听来的几句顺口溜:“扇子有风,拿在手中。
有人来借,等到秋冬。
”这是客观地陈述了扇子的日常功用。
其实,扇子不仅仅是夏日的纳凉用品,还是一-种可供赏玩收藏的工艺品。
由.于它造型优美、制作精湛,因此现代诗人郭沫若曾赋诗赞曰:“清凉世界,出自手中。
精逾鬼斧,巧夺天工。
飞遍寰宇,压倒西风。
”②据史料显示,我国应该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扇子的国家,古书有“黄帝作五明扇”“舜始造扇”的记载,距今有逾三千年历史。
不过,扇子的用途最初不是扇风,而是为帝王遮阳挡尘的“仗仪扇”。
到了西汉以后,用以纳凉消暑在民间渐成风尚。
故当时的史书记载:“以龙致雨,以扇逐暑。
”③伴随着扇子在生活中的普遍使用,扇子文化也逐渐形成,其中最有特色的当为唐宋时代的“扇诗”和“扇画”。
比如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长信怨》:“奉帚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是写宫廷妇女不见帝王之苦,拿着团扇怅望徘徊。
杜牧有诗日:“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牛郎织女星。
”扇子本来是夏天用来挥风取凉的,秋天就无用武之地了,所以古诗里常以秋扇比喻被抛弃或与爱人离别的女子。
《水浒传》中有诗日“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苗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是用摇扇来影射贵族们的骄奢生活。
④而在扇面上作画,宋代盛况空前。
宋人吴自牧的《梦粱录》里,南宋都城临安的夜市,就有专门代人画扇面的小摊。
题材以仕女、山水、花鸟鱼虫以及诗文名句为主。
陆游写过这样的诗句:“ 吴中近事君知否,团扇家家画放翁。
”当时画扇之盛行可见一斑。
⑤在我国戏曲史上,有许多故事情节也与扇子有关,如《西游记》《红楼梦》《包公案》等;还有许多就是以扇子为戏名的,如《桃花扇》《买花扇》《檀香扇》等。
如今,扇子还是评弹、曲艺、戏曲、舞蹈等演出的道具。
许俊文《俯向大地的身影》的阅读答案

许俊文《俯向大地的身影》的阅读答案许俊文《俯向大地的身影》的阅读答案这些年来,我的笔下总是很少提到自己的母亲。
我觉得至今还没有找到可与母亲般配的文字,就好比我们已探明脚下是一座丰富的矿藏,由于担心技术水平达不到,而一直犹豫不决,迟迟没有开采。
那是去年深秋的一个黄昏,我从定远县东部的小镇岱山下车去豆村,沿途的田野,该收割的已经收割了,眼前的每一块赤裸的土地,就像产后的孕妇似的,安安静静地躺在那儿,见不到一个来打扰它的人,只有田边地角盛开的野菊花静悄悄地陪伴着它。
一个老妇人的背影出现在我的视野里:青衣青裤,头上扎着时下很少见到的那种黑色的包巾,右手握着一把小锄。
举起,落下,举起,落下在锄头偶尔停顿的间隙,从翻起的泥土里捡起一点什么,随手丢进身旁的篮子里,再继续翻着泥土。
当我走近,才认出是母亲。
我小声地叫了一声妈,她愣怔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急忙丢下手里的锄头,想立即站起来,可是挣扎了几次,最后还是在我的协助下才完成了那个简单的动作。
母亲的两个膝盖处粘满了泥土,我不由自主地就跪了下去,替母亲轻轻地扑打,扑着扑着,眼泪就出来了。
母亲是一个惜粮如命的人。
她三岁就跟着外婆讨饭,至今她的`左腿还有当初被恶狗咬伤留下的疤痕;七岁下地给东家割麦子,饿极了就搓生麦粒吃;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她的两个女儿相继被饥饿夺去了生命。
粮食在母亲的眼里比什么都金贵。
记得小时候,我家的粮食总是不够吃,为了能够从工分以外多获得一点粮食,母亲请铁匠给我打了一把小锄头,每到秋天,当队里的花生、红薯、胡萝卜起获之后,她就叫我到地里翻找遗落的果实。
虽然如今的生活早已改变,父母的生活费用也由儿女们全包了,可母亲依然是一个拾穗的人,是如今村里唯一的一个,可能也是最后一个了。
母亲总感叹道,人哪,最容易忘本,只要三顿饱饭一吃,就记不得挨饿的滋味了。
前年秋天,父亲打电话说母亲病了,我匆匆忙忙赶回到豆村,只见瘦弱的母亲睡在床上蜷作一团,我上前握住她枯瘦的手,粗糙得犹如一截干枯的树干。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许俊文散文[精品]蛙鸣城更幽许俊文沐浴过杜牧笔底的杏花雨,也饮过李白诗中的秋浦水,至于莲花峰上采兰,仙寓山中品茗,黄公酒垆里饮酒,只要兴致所至,便是举手投足的事了。
——池州这座袖珍的江南小城,就这么不动声色地羁留了我。
于是,或早或晚的,我便以散步来触摸与体味这座城市的细节。
我是一个在意细节的人,起码写作是如此。
一个人若是爱上一个地方,最好的方式就是散步;脚步所到之处,那些地方才是你的,你也才有资格属于那个地方。
不然,你顶多也只能算个客人而已。
池州是个适宜于散步的城市,到处小桥流水,游目芳草时花,即便是冬天,这座城市的底色也不会有多少改变——依然绿着,人徜徉其间,并不觉得萧杀。
譬如我,就是从这里的冬天开始散步的,散着散着,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春天。
这里的春天是一幅气韵横生的水墨画,那夹道红杏,那满城烟雨,那杏花烟雨中穿梭啁啾的紫燕,都是其他城市难得一见的好景致。
不过,我还是更喜欢这里的蛙声。
是的,蛙声。
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诗人移花接木的艺术想象。
青蛙这个大自然中的小灵物,说它们是这座小城的纯情歌手,是不会有谁质疑的,每当夜幕缓缓降临,它们就亮开了歌喉:咕、咕咕……咯、咯咯……咯咕、咯咕……咕咯、咕咯……这声声蛙鸣,犹如行歌的散板,空灵,清越,既包含着泥土的朴素,又有着神曲的飘渺,任你百遍千遍地聆听,也不会生厌。
常常,我就一个人坐在水边,关了手机,断了尘念,专注地听蛙,想听多久就听多久。
有时候干脆躺在草地上,似听非听,恍恍惚惚的,于蛙声中载沉载浮……记得初次听到蛙鸣,是在“惊蛰”后的某个夜晚。
当时大地与草木刚刚还阳,乍暖还寒的气温游魂似的难以捉摸。
然而,就在我经过城中的一个半地下停车场时,几声脆生生的蛙鸣,竟从车库的屋顶上和着雨水一起洒落下来,每一个音符都是湿漉漉的,当时就把我给怔住了。
要知道,这里可不是青草池塘,也非稻花香里,那一人多高的屋顶上,怎么就有了蛙呢,这是一个谜。
谜底似乎只有青蛙知道。
几场烟雾般的细雨过后,气温便在江南小城慢慢地扎下了根。
那根,是一寸一寸往泥土里扎的,人眼自然无法看见,然而,想必草木和鸟雀们能看得见,青蛙当然也能看得见。
青蛙怎么能看不见气温的根呢,那些丝丝缕缕的“根”,恰似一只只温柔的小手,在泥土里挠呀挠的,一不小心就把它们冬眠的梦给挠醒了,于是“咕”地一声,就成了春天的宣言。
古人说什么“春江水暖鸭先知”,许多人还跟着叫好,那是扯淡,准确地说是“蛙先知”。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就在一声声纵情歌唱的蛙鸣里。
得了春风春雨的蛙,就无所顾忌了,只消几天,它们的歌声就把我居住的这座江南小城之夜给渗透了,无论我走到哪儿,蛙们欢快的叫声总是如影随形;就是呆在家中,蛙声也会穿越夜幕抵达我的耳鼓。
我住的地方窗户正对着一条清澈的河流,夜晚读书灯下,寂寞枯燥时,静听如雨的蛙声款款地敲打着窗棂,由不得眼前就会出现白石老人“蛙声十里出山泉”的画面来。
听几阕宋词般的蛙声,尘胸如洗,再接着读下去,则是另一番境界了。
是的,在红尘沸腾的城市,能有蛙声添趣夜读书,无疑是现代人一种古典的奢侈了。
城市听蛙,乍听让人匪夷所思。
这也难怪,时下许多城市简直太像城市了,过分膨胀的体量却容不下寸土,和寸土上细弱的野草,更不用说胆怯、脆弱的蛙类了。
然而池州却不。
这座江南的小城多水,秋浦河、清溪河、白洋河、平天湖、白沙湖、西盆湖……,犹如纵横交织的血脉,把小城滋润的美如莲花。
那些水呢,又都是清凌凌的活水,它们来自周围的一座座青山,一片片森林,一眼眼山泉,你说青蛙能不喜欢么,一喜欢,它们就跳呀,唱呀,结果把小城之夜鼓噪得越发地幽静了。
在幽静的小城之夜踏着蛙声散步,你不喜欢它是不可能的。
俯向大地的身影许俊文俯向大地的那个熟悉的身影,剪纸一样单薄,蹒跚的脚步每挪动一下,都显得非常吃力,似乎一阵不大的风就会把她吹倒,使她永远不再起来。
那就是我已经82岁的母亲。
那是去年深秋的一个黄昏,我从皖东部的小镇岱山下车去豆村,沿途的田野,该收割的已经收割了,眼前的每一块赤祼的土地,就像产后的孕妇似的,安安静静地躺在那儿,见不到一个来打扰它的人,只有田边地角盛开的野菊花静悄悄地陪伴着它。
当我拐过一个凸出的山嘴,一个人影儿便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远远看去便知是位老妇人,青衣青裤,头上扎着时下很少见到的那种黑色的包巾,背朝着我,右手握着一把小锄,举起,落下,举起,落下……在锄头偶尔停顿的间隙,那人便从翻起的泥土里捡起一点什么,随手丢进身旁的篮子里,再继续翻着泥土。
我是一个对土地和庄稼十分敏感的人,从丢弃在田埂上的那些花生秧子就能够判断出,这是一个拾秋的人。
至于那个拾秋的老人原来竟是自己年迈体弱的母亲,是我压根儿也没有想到的。
当我走到母亲身边,小声地叫了一声妈,她愣怔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急忙丢下手里的锄头,想立即站起来,可是挣扎了几次,最后还是在我的协助下才完成了那个简单的动作。
此时我发现,母亲的两个膝盖处沾满了泥土,我不由自主地就跪了下去,替母亲轻轻地扑打,扑着扑着,眼泪就出来了。
母亲是一个惜粮如命的人。
她三岁就跟着外婆讨饭,至今她的左腿还有当初被恶狗咬伤留下的疤痕;七岁下地给东家割麦子,饿极了就搓生麦粒吃;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她的两个女儿相继被饥饿夺去了生命。
因此,粮食在母亲的眼里比什么都金贵。
她常说,粮食来到世上,是上天的恩赐哩,谁要是糟蹋了,哪怕一粒,上天也会知道的。
记得小时候,我家的粮食总是不够吃,为了能够从工分以外多获得一点粮食,母亲请铁匠家斗给我打了一把小锄头,每到秋天,当阴里的花生、红薯、胡萝卜起获之后,她就叫我到地里翻找遗落的果实。
那年头村时缺粮的人家很多,家家户户的老人孩子都争着拾秋,因而每次我总是满怀希望而去,常常带着失望而归。
后来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地还是那些鸡血土的地,可庄稼已不是原来的庄稼了,谁还会再为饭碗发愁呢,渐渐地,拾秋这种延续了不知多少年的现象,便也悄然终止了。
有一次我回到老家豆村,刚从地里拾回一背稻子的母样唏嘘不已:这哪像是过日子做的事,遍地撒的都是粮食,连脚都踩不下去,阎王见了都心疼的。
也许就是打那时起,母亲便成了村里唯一一个拾穗的人。
可能也是最后一个了。
其实母亲是用不着这样做的,道理很简单:虽然她和我父亲服侍不动庄稼了,但我家送给柏凹村学灯耕种的那几亩地,每年都会得到几百斤粮食的回报,这足够他们一年的口粮了,至于油盐酱醋、穿衣看病等等,儿女们全包了。
对此,村里和他们年纪相仿的老人暗地里都羡慕得直咂嘴。
可是母亲不这么看。
她感叹道,人哪,最容易忘本,只要三顿饱饭一吃,就记不得挨饿的滋味了。
不是什么呢,我就见过秋收时的场景,收割机铆足了劲,呼啦啦就下了一块地,呼啦啦又下了一块地,这样省事倒省事,可是漏掉了稻穗,碰落的稻粒多得惊人,许多人看见就像没有看见一样。
你听松岗村的大改子说得多轻巧,现在谁也不缺那几碗饭吃,弯腰磕脑地捡,还不如打两圈麻将呢。
大改子说的不错,拾穗的确是一件弯腰磕脑的事儿,不说一声苦,它把种子抱在自己的怀里,哺育出一茬又一茬的好庄稼,容易吗,别看母亲没有文化,双手在泥土里扒挠了一辈子,但她似乎最懂得对土地的敬畏,尽管她平时不求仙、不拜佛,然而每年大年三十晚上总忘不了给土地爷烧一炷香,说上几句感恩的话,即使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也从未间断过。
她说给这个磕头,给那个磕头,不如给土地磕头,值。
我们今生今世能且口饱饭吃,给土地磕几个头是应该的。
是的,土地养活了母亲和她众多的儿女,母亲也给土地磕了辈子的头。
现在母亲老了,土地给她吃得很少,吃得也很慢,有时吃着吃着就会停顿下来,捧着饭碗接连不断地打呃,眼泪哗哗的,但母亲还在为自己的那一碗饭给土地磕头。
看来,母亲的这个长头可能一直会磕到土地里去了。
大概是前年秋天吧,父亲打电话说母亲病了,我匆匆忙忙赶回到豆村,只见瘦弱的母亲睡在床上蜷作一团,我上前握住她枯瘦的手,粗糙得犹如一截干枯的树干国。
这时父亲开始唠叨起来,他说牛喘气那块水稻田你是知道的,烂泥深得连牯牛都拔不动腿,我叫她不要去拾(稻穗),她非不听……母亲微微地睁开眼,下意识地剜了父亲一下,父亲便不再吱声了。
这时我发现母亲的床边码放着一堆稻子,我一下全明白了。
后来为此我写了一首诗:在我家的老屋里整整齐齐码着十一蛇皮口袋稻子父亲用拐杖戳戳说少说也有七百多斤它们都是我八十多岁的母亲弓着腰一穗一穗从地里拾的拾一穗她磕一个头拾一百穗她就磕一百个头七百多斤稻子她究竟磕了多少头母亲不知道秋风也未必知道可是土地知道但土地不会说话母亲拾稻子、麦子,也拾花生、棉花、豇黄绿豆,凡是地里生长的她都拾,自己吃不了,就托人拿到镇子上去卖。
其实她也不缺那几个钱。
得了钱,母亲会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一张一张叠得齐齐整整的,再去信用社缼成十无一张的整币,然后放在一个小木匣里,就等着过年了。
母亲喜欢过年,过年时儿孙们就像归巢的小鸟,一个个都从很远的地方飞回来了,这时母亲会打开那只木匣子给大家发压岁钱,发一个,说一句,这是从地里拾来的。
当我的儿子接过压岁钱时,扑通一声双膝跪地,深深地磕了三个头。
我想,儿子的头,既是给母亲磕的,也是给土地磕了,尽管他离土地已经很远了,但他的生命里却流淌着土地的血脉。
母亲另一个做法就是用拾来的粮食喂鸡。
母亲养了十几只柴鸡,清一色的芦花白,无论我什么时个回到豆村,总能听到母鸡下蛋的欢叫声。
母亲的鸡蛋从来没有卖过一只,她听说现在的城里的洋鸡蛋不好吃,平时就把鸡下的蛋一只一只地积攒起来,积攒得多了,就打电话叫儿女们回去取。
这些年来,我吃的鸡蛋全是母亲和豆村的那片土地提供的。
在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朦胧中,我仿佛看见母亲那佝偻的身影,离豆村的土地越来越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