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场所》与法国记忆史研究
教育记忆史: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

教育记忆史: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作者:刘大伟周洪宇来源:《现代大学教育》 2018年第1期一、记忆史的提出及发展20世纪70年代,西方历史学家提出了“新文化史”这一概念,在史料和史观两个层面极大的拓展了历史研究的内涵和外延。
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彼得·伯克(PeterBurke)将新文化史的研究主题分为五个层面:一、物质文化的研究,如食物、服装等;二、身体、性别研究;三、记忆、语言的社会历史;四、形象的历史;五、政治文化史。
[1]这其中,记忆史近年来开始成为研究的热点,在历史学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记忆”属于心理学范畴的概念,原本强调的是心理活动与过程,其最早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chs)。
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法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战争创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人民的心中都印刻有战争的痕迹,所以法国学界开始关注到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关系。
哈布瓦赫在1925年出版了《记忆的社会框架》一书,提出了“集体记忆”这一概念。
1950年,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一书在其逝世后出版,该书通过挖掘家庭、宗教等的集体记忆,阐述了他对集体记忆的观点,如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集体记忆与时间、空间的关系,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之间的差异等等。
随着哈布瓦赫惨死在纳粹集中营里,“集体记忆” 的概念也似乎从公众的记忆中被抹去了。
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文化史学的兴起再度让“记忆”一词回到了历史研究的视线当中。
受到“经济快速增长的终结,戴高乐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观念的消退,国外压力的强烈感受”[2]三大因素的刺激,法国急需国民意识的再度形塑,在此背景下“记忆史” 成为了法国历史学界关注的焦点。
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Nora)组织百余人的作者队伍,花费十年之久编写出版了三部七卷本的《记忆之场》,探讨挖掘了法国国民意识形成之中的记忆之场,可谓是“集体记忆史研究成果的大检阅”[3]。
城市建筑学

城市建筑学(论述——总括)1.类型学2.形态3.集体记忆4.场所5.纪念物■序言:记忆的场所:类比的论题 (5)《城市建筑学》从许多方面批判了现代建筑运动,但书中却表现出对现代建筑的一种矛盾心理。
罗西对现代建筑的普遍思想和现代建筑特定理想的失败一样地半信半疑。
因此,他在对现代建筑所深切关注问题的赞同中,也折射出对现代建筑的忧虑。
毕竟正是现代建筑运动才把城市作为建筑的中心问题之一来加以强调的。
在现代主义以前,城市被以为是通过仿照自然法则这种进程在时刻中演变进展的。
▲类比的论题P6纪念物:是城市中持续存在的单个建筑实体,是城市中的首要元素,是特有且经久的城市建筑体,与时刻有关。
作为城市中的经久和首要元素,纪念物与城市进展之间的关系是辨证的,这种经久和进展的辨证关系是罗西构架中城市的时刻特征。
“城市中那些既可阻碍也能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元素。
”-罗西城市中的经久建筑物吧“过去”带入“此刻”,从而令人们“此刻”仍然能够体验到“过去”。
像帕多瓦的拉吉翁府邸,长期存在的原因并非仅仅是其初始或先进的功能,也不是文脉,而恰正是它们自身的形式,这种形式能够容纳因时刻转变而产生的不同功能。
场所:是由单体建筑物组成的,就像经久的物体一样,不仅是由空间、时刻、地形和形式来决定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由其作为古代和此刻的事件联系出现的地址来决定的。
地址、事件和标记之间的这种三重关系组成了城市建筑体的特征。
场所能够以为是能够留下建筑或形式印记的地方。
建筑给予了场所独特的形式,二场所正是在那个特定的形式中历经许多转变而延续下来的。
独特的场所限定了客体的属性,而集合的市民则框定了在主体的形制。
-场所人们正是通过事件的集合记忆,场所的独特性和表此刻形式中的场所标记之间的彼此关系来了解历史的。
所谓类比,就是由两个对象的某些相同或相似的性质,推断它们在其他性质上也有可能相同或相似的一种推理形式。
类比是一种主观的不充分的似真推理,因此,要确认其猜想的正确性,还须通过严格的逻辑论证.-百度▲记忆的场所 (12)《城市建筑学》一书试图通过类型那个仪器,向人们展示如此一种城市:虽有历史,但记忆能够构思和重建富于空想的未来时刻。
“社会记忆”理论的发展概述

第10卷第9期 2019年05月Vol.10 No.9May 201973“社会记忆”理论的发展概述李 宁(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重庆 401120)摘 要:尽管“社会记忆”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当代社会学、历史学、新闻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中,但其术语仍缺乏统一性。
本文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社会记忆”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概括出包含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阿拜·瓦尔堡的“社会记忆”理论、皮埃尔·诺拉的“记忆场”理论、保罗·康纳顿的“习惯记忆”理论、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在内的五种代表性“社会记忆”理论,并叙述了这些理论的基本思想、理论来源以及主要贡献,以期对后续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集体记忆;“社会记忆”;“记忆场”;“习惯记忆”;“文化记忆”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9)09-0073-0220世纪20年代,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首次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并将“记忆”从心理学范畴扩展到人文社会学科领域。
20世纪80年代,文化学研究开始兴起,哈布瓦赫的理论不断被西方国家的学者采用和发展,同时也产生了诸多差异性的术语。
20世纪末,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该理论展开译介和研究,由于概念术语的缺乏统一性,国内对于“社会记忆”的理论运用也是各取所需。
[1]基于此,本文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五种代表性记忆理论进行了整理和概述,以期对后续研究有所助益。
这五种记忆理论分别为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集体记忆”理论、阿拜·瓦尔堡(Aby Warburg)的“社会记忆”理论、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记忆场”理论、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的“习惯记忆”理论以及扬·阿斯曼(Jan Assman)的“文化记忆”理论。
拯救记忆场所,构建文化认同—旧城改造规划中开敞空间设计初探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众多的城市也会面临着“拆迁”、“重建”、“旧城改造”等方面的问题;每一座城市都应当拥有属于自己的时代符号,但部分城市在对旧城进行改造的过程之中,却未对具有历史符号的旧城建筑加以利用,甚至使得部分古建筑文物等受到了破坏,所以,笔者以“拯救记忆场所,构建文化认同”为基础,从而浅析旧城改造规划中关于开场空间设计的初探,以此来为同行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3.2 “拯救记忆场所,构建文化认同”—旧城改造规划城市广场的设计
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广场,它不仅是城市中一种由物质要素以及非物质要素的复合物,也是市民交往的主要活动空间,同时也是一座城市的价值所在。除此之外,城市的广场也是重要的记忆场所之一,例如:大连市南部海滨风景区的滨海广场兴建于1997年6月30日,其修建的主要目的在于庆祝澳门回归祖国;所以,这一城市广场也成为了大连市的一个重要文化明信片。虽然,部分中小城市并没有较为重大的城市广场,但是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依然会有一些具有历史特色的时代广场;所以,在旧城改造的过程之中,应当对此类具有历史特色的城市广场进行改造,例如:为原有的面积进行扩大,同时对原有的独特建筑进行保留;当然,为了确保广场能够为居民提供更加宽敞、舒适的活动场所,还应当在其地下进行相应的给排水系统设计,同时做好供电、照明等方面的工作,从而确保改造过后的城市广场,能够满足现代居民的日常需求。由于广场的面积较大,为了能够拯救或打造记忆场所,可以对已经破坏或者消失的建筑进行重建与修复,从而打造具有文化符号的新时代场所,例如:成都的天府广场是成都重要的明信片之一,由于该城市分区主分成了武侯、金牛、青羊等多个区,而为了符合此种文化类型,天府广场也被设计成为太极八卦的图案并对原有建筑进行了修复,从而让其展示与成都市有关的文化特色;与此同时,广场旁边还设立有四川省博物馆,所以,设计人员在对旧城进行改造的过程之中,当重点关注城市广场并对其加以合理的利用。
图书馆与社会记忆研究的理论脉络

17·专题 社会记忆研究·图书馆与社会记忆研究的理论脉络郑秀花 王晓琳 姜 申(浙江图书馆 浙江杭州 310007)摘 要:西方社会记忆研究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20—1930年代的理论奠基时期、1980年代的“记忆潮”时期,以及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性记忆时期”。
纵观西方记忆研究的脉络,记忆的机制和作用一直都是研究者关注的中心问题。
记忆的形塑、记忆的传承以及记忆和认同的关系是其中最核心的三个问题。
西方图书馆学记忆研究的范畴基本是在社会记忆研究的框架之下进行的,中国图书馆学记忆研究的理论性文章较少,多数研究是在信息管理框架下进行的“记忆资源开发和整理”研究,阐释性研究有待深入。
关键词:社会记忆;图书馆学;研究范畴中图分类号:G250.1 文献标识码:AThe Theoretical Context of Library and Social Memory ResearchAbstract The history of western social memory research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theoreticalfoundation period from the 1920s to 1930s, the "memory boom" period in the 1980s, and the ongoing "cosmopolitan memory". Throughout the context of western memory research, the mechanism and role of memory have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researchers. The formation of memory, the inheritance of memor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mory and identity are the three core issues. The research of western library science memory is carried ou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social memory research. There are few theoretical articles on library science memory research in China. Most of the researches are carried ou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further studies on interpretative research need to be done.Key words social memory;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category*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图书馆与社会记忆研究”(项目编号:17CTQ002)的研究成果之一。
记忆与历史的博弈_法国记忆史的建构

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建构沈 坚摘 要:集体记忆长期与历史混为一体。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法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法国面临着记忆的危机。
人们越来越对历史学有意遗忘某些现象、某些群体表示不满,因而出现了集体记忆的觉醒和对传统历史学的反抗。
在此过程中,历史学本身也面临着重大的转向。
在这两种趋向的双重影响下,集体记忆成为历史学新的研究对象,相应地,记忆史研究成为历史学的新兴研究领域,历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法国 新史学 记忆 记忆场所作者沈坚,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杭州 310028)。
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 ff)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史学专家提出了!新史学∀的概念,他们陆续推出了 制作历史、 新史学等大型百科全书式的史论著作。
在新史学的推动下,!记忆∀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记忆史研究逐渐形成一股强劲的学术思潮。
到20世纪90年代甚至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法国表征史的逐渐升温,记忆史研究继续保持着不减的势头,!历史记忆∀问题常常成为学术研讨会的主题。
法国记忆史在选题和研究方法上均给人以许多启发,为此笔者不揣简陋,对法国记忆史研究作一学术史的考察,以引起中国史学界的关注。
一、!记忆∀的觉醒与记忆史的建构!记忆∀最早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它在法国之所以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既有历史原因,也是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
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记忆问题的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的战争给人们造成极大的心灵创伤,痛苦的经历长期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法国知识分子由此开始关注记忆问题。
首先是文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此有所涉猎,如普鲁斯特(Marcel Pro ust)和柏格森(H enri Bergson)等。
曾师从柏格森、后又受杜尔凯姆( mile Durkheim)影响的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尔布瓦克(M aurice H albw achs)于192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 记忆的社会框架,#该书引入本文曾提交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第三届!史学前沿论坛∀。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历史悠久的快速记忆法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历史悠久的快速记忆法“记忆宫殿”据说起源于一位希腊诗人西蒙尼德斯,一次,当这位诗人满怀地在大宴会厅里朗读一首赞美卡斯托尔和波拉克斯两位大神的抒情诗后,被叫了出去,正在此时,宴会厅坍塌了,厅内无一宾客存活,尸体模糊,亲属难辩,西蒙尼德斯却凭借记忆力根据人们在厅内的座位而把尸体一一辨认出来。
记忆宫殿法最早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年-1610年)传入中国,著有《西国记法》,又称《记忆宫殿》,详细绍利玛窦本人如何能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这种方法基本于这样的原理:我们非常善于记住我们所知的场所。
“记忆宫殿”是一个暗喻,象征任何我们熟悉的、能够轻易地想起来的地方。
它可以是你的家,也可以是你每天上班的路线。
这个熟悉的地方将成为你储存和调取任何信息的指南。
比如十个地点可以用身体的不同部分,10-20地点可以用地铁点、公交站点或火车站点,这些东西是你每天接触的,基本上不用特意去想。
当然你也可以用游戏的地点来代替,只要选条你印象最深最熟悉的路线就行了。
宫殿记忆主要是说当需要记忆的东西太多时,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个宫殿,有很多间房子,每个房间有很多格子,这样把需要记忆的东西都放在里面,同时通过生动的联想,越是血腥的恐怖的越记忆犹新。
使用记忆宫殿也造就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记忆绝活。
例如,8次世界记忆冠军Dominic O’ Brien,他能记住54张桌子上的所有牌(2808张)的顺序,每张牌只看一次。
通过运用记忆宫殿法,人们还取得了无数类似的成就,比如《汉尼拔》中连环杀手汉尼拔·莱克特就利用记忆宫殿长期储存了对复杂病历的极其鲜明的记忆。
你要知道这是快速记忆最基本的方法之一,但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你唯一需要做的就反复练习,当你掌握这种方法之后,会很容易从前向后,或从后向前进行复述。
运用记忆宫殿法的五个步骤:1、选择你的宫殿首先和首要的,你需要选择一个你非常熟悉的地方。
本技巧的有效性取决于你在脑海中轻易地再现这个地方并在其中漫步的能力。
“记忆之场”视域下的唐代长安--以李白、杜甫诗歌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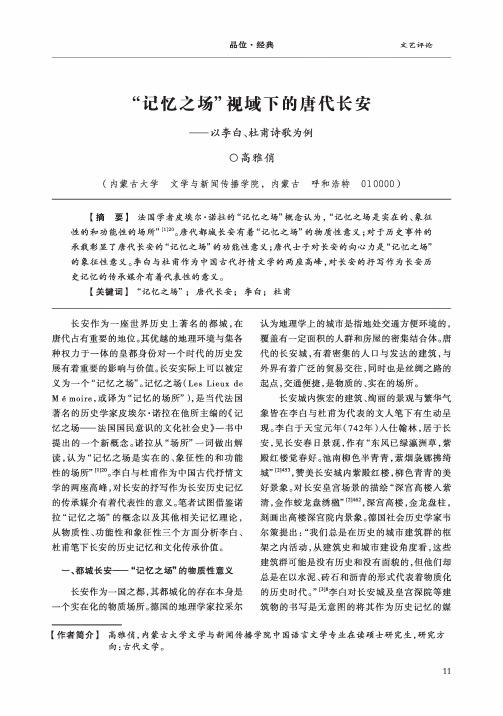
品位・经典丈艺评论“记忆之场”视域下的唐代长安——以李白、杜甫诗歌为例O高雅俏(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00)【摘要】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概念认为,“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E2。
唐代都城长安有着“记忆之场”的物质性意义;对于历史事件的承载彰显了唐代长安的“记忆之场”的功能性意义;唐代士子对长安的向心力是“记忆之场”的象征性意义。
李白与杜甫作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两座高峰,对长安的抒写作为长安历史记忆的传承媒介有着代表性的意义。
【关键词】“记忆之场”;唐代长安;李白;杜甫长安作为一座世界历史上著名的都城,在唐代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优越的地理环境与集各种权力于一体的皇都身份对一个时代的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与价值。
长安实际上可以被定义为一个"记忆之场"。
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 e moire,或译为“记忆的场所”),是当代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在他所主编的《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
诺拉从“场所”一词做出解读,认为“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呻。
李白与杜甫作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两座高峰,对长安的抒写作为长安历史记忆的传承媒介有着代表性的意义。
笔者试图借鉴诺拉“记忆之场”的概念以及其他相关记忆理论,从物质性、功能性和象征性三个方面分析李白、杜甫笔下长安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价值。
一、都城长安一“记忆之场”的物质性意义长安作为一国之都,其都城化的存在本身是一个实在化的物质场所。
德国的地理学家拉采尔认为地理学上的城市是指地处交通方便环境的,覆盖有一定面积的人群和房屋的密集结合体。
唐代的长安城,有着密集的人口与发达的建筑,与外界有着广泛的贸易交往,同时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交通便捷,是物质的、实在的场所。
长安城内恢宏的建筑、绚丽的景观与繁华气象皆在李白与杜甫为代表的文人笔下有生动呈现。
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

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皮埃尔诺拉,一位跨学科的先驱,与众不同的思想家和科学家,通过其独特的理论——“记忆之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理解文化传承和记忆研究。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将探讨皮埃尔诺拉的理论、其重要性、以及在当代科技环境下的应用。
皮埃尔诺拉的理论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记忆理念,他认为记忆不仅仅是一个个孤立的事件或经验,而是与我们的文化、历史、社会环境紧密相连。
他借鉴了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记忆之场”这一概念,以描述记忆如何在个体和社会之间流动和保存。
“记忆之场”的核心在于它强调了记忆的情境性和参与性。
记忆不是静态的,而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
它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感知、去参与、去互动,才能得以保存和传承。
皮埃尔诺拉认为,记忆之场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和共享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可以相互交流和分享记忆。
与当前的先进记忆技术相比,皮埃尔诺拉的理论具有其独特的优势。
他的理论强调了记忆的情境性和参与性,这使得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分享记忆。
他的理论鼓励人们积极参与到记忆的保存和传承中,而不是被动地接受。
然而,皮埃尔诺拉的理论也存在一些挑战,例如如何衡量和评估记忆的质量和价值,如何确保记忆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等。
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为我们理解文化传承和记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他的理论强调了记忆的情境性和参与性,鼓励人们积极参与到记忆的保存和传承中。
在当代科技环境下,“记忆之场”的理念可以应用于多个领域,如历史保护、文化传承、社会记录等。
然而,如何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实践,以及如何解决其面临的挑战,仍需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理论的价值,更在于其对我们理解记忆和文化传承的启示。
在快速发展的科技社会中,我们不能忽视记忆的价值。
记忆不仅塑造了我们的个体经验,也构建了我们的社会和文化。
通过深入研究和理解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复杂而重要的现象,进一步推动文化传承和记忆研究的发展。
心理学发展历程

基于记忆场所视角的胶东古村落微更新设计探究

基于记忆场所视角的胶东古村落微更新设计探究作者:孙杨静王莹莹来源:《美与时代·城市版》2023年第10期摘要:随着乡村记忆工程的推进,维系乡愁情感和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古村落记忆场所的营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当前,不少传统村落面临着空心化、地方传统文化消逝等问题,需要设计者基于记忆场所理论,以更长远的视角,结合现状进行探索及微更新设计。
以山东省烟台市西河阳村为例,系统梳理古村落中的记忆要素,提出记忆传承与再现的路径,并通过对村落文化主题面域、记忆轴线及公共空间节点的活化设计,验证了路径的有效性。
关键词:记忆场所;西河阳村;微更新设计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基于记忆场所的胶东传统村落公共空间营建策略研究”(2022-YYYS-05)研究成果。
乡愁是一种寄寓时代变迁的历史见证,其表面承载的是对家乡和人情的依恋,深层则是一种文化的皈依与寄托。
维系乡愁情感和传统文化的载体——古村落记忆场所,是集体、个人记忆的重要承载地。
当下,现代化的物质生产冲击着传统多样化的社会文化传承,导致一些处于遗产保护名录之外但蕴含着丰富邻里情感与地域文化信息的记忆场所遭到破坏,同时部分传统村落面临着空心化、地方传统文化消逝、环境恶化甚至濒临消失的困境,使得栖居于此的村民愈发找不到情感依赖,存在文化记忆消逝、地方文化认同感消解的危机。
留住乡愁,保护、活化记忆场所,现已成为人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基于记忆场所视角研究古村落的微更新设计,有利于塑造古村落的地域文化认同感,故本文基于记忆场所理论,以烟台市西河阳村为例,通过调查、访谈了解当地村民的记忆场所分布,分析现存问题,开展记忆场所微更新设计实践,努力传承和保护红色记忆、商帮、黄水河文化,提高古村落居民的空间认同、文化认同,推动乡村记忆工程的开展。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一)记忆场所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于1978年提出了“记忆场所”这一概念,他认为其在大众生活中承担着多样化的人文内涵。
“记忆之场”:皮埃尔·诺拉的档案记忆思想发凡

“记忆之场”:皮埃尔·诺拉的档案记忆思想发凡作者:丁华东黄琳来源:《档案与建设》2020年第04期摘要: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主编的三部七卷本的《記忆之场》汇集了众多法国史学家的研究结晶,是当代法国最具影响力的历史著作之一。
全书内容涉猎面广泛,颇具启发性,故文章聚焦“记忆之场”这一主旨概念,对皮埃尔·诺拉的档案记忆思想进行剖析和揭示,以期为档案学研究引入新的学术视角。
关键词:档案记忆;记忆之场;国家权力;档案强迫症;历史研究分类号:G270"Places of Memory ":Pierre Nora’s Ideas of Archival MemoryDing Huadong, Huang Lin(Department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200444)Abstract:Places of memory, edited by French historian Pierre Nola, brings together articles of many French historians, and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historical works in France. The whole book covers a wide range of contents and is quite enligtening. Focusing on the key concept of "places of memory",this paper analyzes and reveals Pierre Nora’s ideas of archival memory, in order to introduce a new academic perspective for archival research.Keywords:Archival Memory; Places of Memory; Power of State; Archives Obsession;History Research“历史在加速”,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其主编的《记忆之场》导言中这样说道。
记忆宫殿法提升记忆力的古老技术

记忆宫殿法提升记忆力的古老技术记忆是人类认知和学习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在众多提升记忆力的技巧中,记忆宫殿法因其独特性和有效性而被广泛应用。
作为一种古老且流传悠久的记忆提升技巧,记忆宫殿法利用了空间记忆、联想和可视化等心理特性,使得信息更容易被存储和提取。
本文将探讨记忆宫殿法的起源、基本原理、构建方法,以及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
一、记忆宫殿法的起源记忆宫殿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据传,罗马诗人西涅卡(Quintilian)曾提到一个技巧,即通过在心中构建一个熟悉的空间来帮助背诵信息。
这一方法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完善,成为了今日我们所称的“记忆宫殿”。
在这些古代智者的影响下,许多演说家、学者和学生都将此技巧应用于学习和演讲中,从而显著提升了他们的信息存储与检索能力。
在古代希腊有一位名叫西摩拉斯(Simonides)的诗人,他在一次宴会上经历了一场灾难。
当宴席倒塌,许多宾客不幸遇难,警方无法辨认死者身份。
西摩拉斯通过回忆宴席上的座位布局,将每个座位与具体的人物相联系,从而准确地识别了遇难者。
这一经历使他领悟到,将信息与空间进行联结,可以大幅增强对信息的记忆效果。
二、记忆宫殿法的基本原理记忆宫殿法运用了一些关键的心理机制来增强记忆:空间记忆:人脑对空间位置和环境的记忆通常远远强于对抽象信息的记忆。
因此,通过构建一个虚拟的宫殿或场景,可以利用这种空间优势来存储信息。
联想:人脑更容易记住有趣、生动且富有联想的信息。
通过将需要记住的信息与特定的位置或物品关联起来,可以提升回想时的信息检索效率。
可视化:将抽象概念或信息具象化为具体形象,使得理解和记忆更为清晰便捷。
因此,在构建自己的记忆宫殿时,可以利用色彩、形状以及动态等元素来增强可视性。
情感关联:与情感相关的信息更容易被牢记。
当我们在构建一个记忆宫殿时,可以通过加入一些感人的故事情节或幽默的情境,以增加情感共鸣,提高信息保留率。
三、如何构建自己的记忆宫殿构建一个个人化的记忆宫殿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但需要一定的方法和创意。
保罗·康纳顿社会记忆理论探析

保罗·康纳顿社会记忆理论探析作者:景磊白雪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1期摘要:社会记忆理论,已然成为一个跨学科、多向度的概念,当下在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应用并发展。
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和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作为研究社会记忆理论的两位著名学者,分别在“社会记忆”与“集体记忆”研究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二者将“记忆”的呈现均看作社会的建构,而这样的建构由当前的关注所形塑。
保罗·康纳顿用社会记忆理论代替集体记忆理论形成自己的理论理解与阐释,社会记忆理论成为继集体记忆理论之后又一具有深刻学术影响的理论范式。
关键词:社会记忆;权力关系;社会忘却;纪念仪式;身体实践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11-0064-05社会记忆什么,如何记忆,可以反映出社会的内在结构,体现出社会的功能。
社会记忆是人类认知自身社会历史发展的坐标,粘连着人类社会的过去与现在,也是文明传承、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的内驱因素。
保罗·康纳顿指出:“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件和事物有因果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从而,当我们体验现在的时候,会参照我们未曾体验的事件和事物。
”[1]社会承载的记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存在的形态,使得我们不断地回忆着社会的文化传统。
“只要个体从属于社会,他的思考和行动也就超越了自身。
”[2]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了记忆,那么这个社会也就无法进步和发展,作为存在于社会中每个独立的个体而言,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脱离记忆,拥有了社会记忆也就找到了个人存在的社会的、文化的档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记忆理论受到不同学科的关注,在社会学理论、人类学理论、民俗学理论研究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提及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的社会记忆理论必然离不开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二者具有明显接续和发展关系。
记忆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2014.06作者简介:邵卉芳(1984~),女,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教师㊂记忆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方法邵卉芳㊀㊀摘要:通过对社会记忆的深层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过去对于现在和未来的重要意义,因此,记忆研究的重要性逐渐凸显㊂民俗学的个人生活史㊁民俗志研究及战争与灾害记忆的研究都离不开记忆论,记忆论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方法㊂在研究中需要注意记忆的选择性㊁记忆建构身份的特性㊁记忆的对峙性以及个人记忆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㊂尽管记忆研究这一跨学科研究的发展不够完善,但民俗学需要直面记忆研究的难题,建立和完善属于本学科的记忆研究理论体系,不可忽视理论和实证任一层面㊂关键词:记忆;记忆论;身体记忆;民俗学中图分类号:K890㊀㊀文献标识码:A㊀㊀文章编号:1000 8691(2014)06 0083 06㊀㊀尼采早就指出: 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需要对过去有一定了解 只有为了服务于现在和将来,而不是削弱现在或是损坏一个有生气的将来,才有了解过去的欲望㊂[1]可见,社会学㊁历史学㊁民俗学㊁人类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对于记忆的研究非常迫切㊂但对社会记忆进行理论化和全球化的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成为热点,这些研究加深了人类对自己历史的了解与反思㊂较早对社会记忆进行研究的主要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学者,有爱弥儿㊃涂尔干(émileDurkheim)㊁西格蒙德㊃弗洛伊德(SigismundSchlomo Freud)㊁亨利㊃柏格森(Henri Bergson)㊁莫里斯㊃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㊁卡尔㊃曼海姆(Karl Mannheim)㊁阿比㊃沃伯格(Aby Warburg)㊁弗雷德里克㊃沃尔特雷特(Frederick C Bartlett)㊁沃阿诺尔德㊃茨威格(Arnold Zweig)㊁尔特㊃本杰明(Walter Benjamin)等,最为杰出的当推莫里斯㊃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他是社会记忆研究的鼻祖㊂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法国㊁德国和北美分别出现了一批较为出色的研究者,但他们都在两大范畴展开研究,即:民族国家的记忆 对个人以及个人所属的集团或国家记忆的研究;全球记忆 对他国㊁他民族的记忆㊂传统记忆研究者认为记忆是跟过去紧密相连的概念,人们通过记忆直接或间接地了解和认知个人和集体的过去㊂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新的研究者颠覆了以上看法,认为记忆包括现在的㊁未来的和动态的内容,记忆是一个带有可塑性的动态系统㊂因为 记忆中把过去和将来两个维度的联系表现为一个人㊁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对将来的期待㊂没有对自己的过去的把握,则很难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充满意义的期待㊂所谓的希望也就是产生在这样一个 期待的空间 (evwartungsraum),而这期待的空间的大小是由记忆的内容以及容量来决定的 [2](P2)㊂一㊁民俗学的记忆研究在明确地提出 记忆 和 社会记忆 概念之前,民俗学界就已有学者进行记忆的研究,只是没有把记忆明确提出来作为理论思考的对象,更没有把它上升到 记忆论 的高度来看待㊂当社会学㊁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加深了对社会记忆的研究力度后,民俗学者对记忆论的关注才逐渐自觉起来㊂在民俗学界,对记忆进行研究最多的要数日本民俗学者,主要研究有:阿部安成㊁小关隆的‘コメモレイションの文化史㊃記憶のかたち“是日本记忆论研究的先驱,作者在记忆的概念㊁战争记忆的形成㊁文化遗产等方38面的考察都做出了开拓性贡献㊂羽賀祥的‘史蹟論 19世紀日本の地域社会と歴史意識“调查分析了日本近世以来的纪念碑和纪念物的建造过程,揭示了建造过程背后的相关因素㊂名古屋大学出版会出版的‘記録と記憶の比較文化史“对欧美㊁日本以及中国的社会记忆做了比较研究㊂小关隆‘記念日の創造“对近代各国的纪念日的起源和意义作了分析㊂其中小关隆在1999年对人文学领域的记忆概念下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记忆是人们对过去的知识和情感的集合体,记忆的形成是一个表象化的行为㊂ 记忆不单纯是过去事件的储藏库,它是记忆主体针对自身所处状况唤起特定的过去事件并赋予意义的主体行为㊂因此,记忆和记忆的主体,即生活在当下现实的人们所属的社会集团的自我认同有着本质的联系㊂ 由于个人㊁集团的自我认同是不断变化的,与此对应,记忆也不断地被重新建构, 值得记忆的 在不断被选择㊁唤起的同时,相反的事件则被排除㊁隐瞒㊂从这个意义上说,忘却也是构成记忆的一部分㊂任何一个记忆的表象的背后,都有无数被忘却的事象[3]㊂根据该定义,记忆的特点为:(1)记忆形成于人们对过去事件的表象化过程中㊂记忆与记忆主体的当下状态直接相关㊂(2)记忆本身包含着忘却的机能,记忆不仅代表过去的静态的内容,而且是关联现在与未来的动态的概念㊂如今,记忆论在民俗学界的应用与研究逐渐增多,民俗学者对记忆论之于民俗学研究的看法也各具特色㊂岩本通弥指出: 记忆作为一个有效的分析性概念,在分析社会㊁政治现象时得到广泛运用㊂在民俗学领域,记忆论的研究也开始成为瞩目的焦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俗学的最本质性的存在就是记忆㊂ [4](P109~115)岩本通弥极为肯定记忆论研究的重要性,但笔者认为这一论点不太合适,说 记忆是民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 或者是 民俗学的最本质的存在是 研究记忆 或 用记忆方法研究民俗 似乎更为恰当㊂另外,针对传统民俗学的研究取向①,岩本提出记忆论在民俗学研究方面的几个相关事项㊂(1)民俗学不是以文献记录,而是以记忆为素材的学问㊂它主要以没有被文献记录下来的事项作为研究对象㊂(2)在研究中,它的基本方法是对直接性的口述㊁对话进行访谈记录㊂(3)通过以言语为媒介的记忆提取信息,原生态地把握当地人们的生活世界㊂(4)同时,把非言语的如身体行为㊁感觉㊁思维方式㊁价值观㊁感情㊁身体技能作为研究对象㊂(5)这些知识系统以身体作为媒介,在不同的个体㊁群体之间发生的保持㊁传承㊁传播㊂力图去把握这个传承的过程和特征㊂(6)将使这样的记忆可视化㊁有形化的行为,通过访谈记录㊁民俗语汇化㊁民俗志等方法加以记录,(主要是文字化)[4](P109~115)㊂岩本还认为,访谈记录法是民俗学区别于人类学参与观察法的重要指标,在方法论上,岩本总结了千叶德尔的访谈方法论,指出:访谈记录 既是民俗学发挥本领的领域,也是未来文化研究必须解决的重大难题 [5](P274)㊂为了强调记忆论与访谈方法研究,岩本使用了比较绝对的说法,实际上,除了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也同样在非常广泛地使用参与观察法,且参与观察与访谈记录两种方法相得益彰地运用才是民俗学研究的题中之义㊂关于记忆论对民俗学研究的意义,王晓葵认为,记忆论在民俗学研究中的一个尝试是用口述史的方法,分析民俗现象在现代社会多元化结构中潜在的多种变体㊂这些变体依据传统的研究方法往往会被简单地作为例外加以排除㊂但通过对口述史材料的分析,可了解具体的民俗传承人的生活经历和传承行为的关系,敏锐地把握现代社会的民俗变迁[5](P276~277)㊂另外,王晓葵还举川森博司的例子指出,新的民俗志的书写将基本上完全依靠记忆,因为有很多现实中不存在但是依然存活在人们记忆之中的 潜在民俗 ㊂王晓葵认为现代民俗学的研究离不开记忆论,但笔者认为若单纯依赖记忆则必然会使研究走入死胡同,因为现代民俗学有很多内容是当下发生的,不需要过多地凭借记忆,而现时的参与观察显得更为重要㊂笔者赞同日本民俗学者对记忆论之于民俗学研究重要性的论述,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下文有详述㊂二、记忆论之于民俗学研究记忆论应如何引入民俗学研究?民俗学可在记忆论研究方面发挥什么作用?这些都是民俗学者理应深入思考的问题㊂首先,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口述史研究以及战争与灾害记忆的研究,民俗志的书写也离不开记忆48①即追求民俗资料的 真实性 ,口述访谈资料被当作文献资料的补充,民俗学变成了历史学的辅助学科㊂2014.06论㊂对此,王晓葵认为: 民俗学的主要方法之一是民俗志的方法,而传统的民俗志的撰写工作,往往是直接对口头传承的访谈记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民俗事象随着生活方式的变迁,已经丧失了其存在的外在形态㊂比如很多地方已经不再使用耕牛,相关的农具等也不复存在㊂但是,这并不意味者相应的民俗已经消失㊂ 如有需要,他们(老农)是可以回复这个民俗事象的㊂这种现象,日本民俗学家樱田胜德称之为 潜在民俗 ㊂所谓潜在民俗,就是保存在人的记忆之中的㊁失去了外在形态,但是经过记忆的重构,是可以恢复原来的形态的㊂因此,民俗志的书写,开始越来越依据记忆的材料㊂ [5](P278)记忆的材料固然是民俗志研究与书写中的重要材料,但仅将记忆看作关于过去事情的回忆,确有片面性㊂因为如前所述,记忆研究的不仅是过去,更重要的是当下㊂小关认为:对过去事件的记忆和 记忆的主体,即生活在当下的人们所属集团的自我认同的本质,复杂地交织在一起㊂ [6](P5~22)因为 民俗 及与 民俗 关系密切的文化遗产 的承担者是当今的民众,他们本身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㊂民俗学现在不断地对那种变了形的现场进行调查并尽量地把它们记录下来,可问题是与 文化遗产 关系密切的亘古的 记忆 里没有包括当今的民众㊂在这种情况下,民俗学正试图刻画现在承担着 文化遗产 的民众的生活,作者也认为应当这样做㊂本文所论及的正是这样的 现在 的记忆㊂ [7](P302)过去的记忆与现在的记忆应有机地统合在民俗志的研究与书写中㊂其次, 非遗 项目中保护的其实就是 记忆 ,既有 物质上的记忆 也有 身体上的记忆 ㊂王晓葵指出: 人们往往认为,文化遗产是为了保存或者唤起过去的 记忆 ㊂ 其实 文化遗产 保存的 记忆 不是原本就有的,而是在人们回顾过去时产生的㊂ [7](P299~301)笔者赞同王晓葵的说法,记忆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在与人的回忆行为发生关系之后的特殊产物㊂民俗学的记忆研究不只是记录与整理㊂因为,仅仅将记忆存档并不等同于文化记忆,只堆积资料而不进行甄别筛选,便缺乏感情与历史的投入,也不能表明其与当下的联系㊂记忆研究指的不仅是记录访谈录音,记录的前提是访谈,访谈的视角㊁如何访谈等本来就极为重要,这些也值得探究;如何记录也很关键,按照学界多数学者的观点,民俗学的记录不但要记录谈话内容,而且要注意观察和记录访谈现场的气氛㊁环境以及被访谈者的表情㊁动作等细节,这些是连视频都无法 完整记录 的重要内容,更不用说录音和笔录了㊂更重要的还有 记录何为 的问题㊂退一万步讲,按照理想状态,我们把发生在访谈现场的 所有 内容一应俱全地完整记录了下来,但记录的目的是什么?记录的内容作何用途?难道仅仅把民俗学研究看作资料搜集的手段吗?因此,要解决上述问题,在进入田野之前就应弄清访谈目的㊁田野作业的旨归㊁民俗学研究的追求等问题㊂再次,民俗学目前还面临着一个与大众传媒紧密纠缠的问题 即媒体与记忆的关系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民众包括 非遗 传承人都深受媒体的影响㊂较早注意 文化记忆 与媒体之间关系的是阳㊃阿斯曼(Jan Assmann)和爱蕾达㊃阿斯曼(Aleida Assmann)夫妇,他们的贡献是突破了哈布瓦赫的视野,将媒体引入记忆研究领域㊂他们认为 文化记忆 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走过了三个历史阶段:口头叙述阶段㊁笔录阶段与印刷阶段㊂阿斯曼夫妇非常反感印刷技术发展以后文化记忆的发展状态,他们指出,正是由于 文化民主化 ,才使得 文化传统不是得到了保护,而是得到了(不必要的或是别有用心的)更新,回忆也就变成了编造, 文化民主化 必然使传统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8](P114~140)㊂客观而言,阿斯曼夫妇的这种观点显得片面,事实是,逐渐发展的大众媒体使得人们的回忆意识慢慢地变成了生产消费品与消费人为编造 历史 的状态[8](P114~140)㊂当消费欲望超过文化传统保护理念的时候,记忆文化便会为 眼球文化 所代替,从这个角度来看,阿斯曼夫妇大声疾呼 记忆的危机 也就理所当然了㊂笔者以为,阿斯曼夫妇的这种批判实际上是对那些利用媒体制造社会记忆的权威势力的批判,也就是说,他们的批判对象不是媒体本身,而是制定记忆政策的威权者,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这种批判在当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㊂现如今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人依靠媒体形成自己的社会记忆,在大众传媒的强烈冲击之下,口头叙述显得如此稀缺与无力㊂因此,媒体与社会记忆的关系问题依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深远话题㊂概括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值得思索:一是大众传媒如何帮助人们建立社会记忆?二是不同阶层的社会记忆如何反过来影响媒体的叙述,从而在媒体上表现出来?这一点在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人的身上表现得极为明显,一方面传承人的身体记忆为媒体的言说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另一方面媒体的言说又影响了传承人的言说与身体记忆,二者之间的58这种互动关系值得考察㊂另外,笔者认为民俗学的记忆研究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记忆的选择性记忆都是有选择的,记忆或忘却的标准分别是什么?为何记忆这个而忘却那个?记忆的标准与原则是什么?不论是个人记忆㊁集体记忆㊁社会记忆还是文化记忆,都是选择的结果,这里就存在选择的原则与标准的问题,而这也就是需要着力探讨的内容㊂选择的原则与标准并不是客观地存在于那里的,而是受到各种外界因素影响的㊂ 从技艺规定身份这个角度看,应该记住什么,忘却什么,就不仅仅是一个纯技术性的问题,也不仅仅是 记忆的策略 的问题,而更是反映了这个人或这个民族现实的需求,也反映了该人或该民族面对过去的道德责任和勇气㊂这种记忆的需求和面对过去的道德责任,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记忆,规定了这个人或这个民族怎么看自己以及希望他人怎么对待他/它㊂ [2](P2)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区分了 记忆 与 回忆 ,认为回忆是过程,记忆是结果,并且指出: 既然个人回忆的前提是社会需要,记忆是回忆的结果,那记忆也必然充满瑕疵㊂记忆是社会回忆过程中的重新建构,是一种社会行为㊂换言之,记忆本身和它所涵盖的事件本身之间有很大差异㊂也就是说,在记忆的构建过程中,事件有所丢失,也有所补充,但作为回忆的结果即记忆和曾经发生过的事件之间绝对不是等同的㊂回忆是有策略的,社会的忘却和记忆有一部分是迎合了当权者或者是社会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的某种需要㊂ [9](P66)如上文谈到的媒体与记忆的关系,其中隐藏的威权势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㊂2.记忆建构身份在现实社会,一个人的身份,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无不与这个人㊁这个民族对自己过去的记忆有关㊂ [2](P2)可见,不论是个人记忆㊁集体记忆还是社会记忆,均不同程度地具有建构身份的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建构身份是记忆存在的最本质特征之一㊂ 在塑造自己的身份时必然要求我们找出能说明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一连串事件㊂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从无数的经验中筛选一些我们认为可面对今天的事实,同时我们又根据事实的重要性来决定我们的筛选㊂记忆就是这个筛选作业的产物㊂没有忘却就没有记忆㊂ [10](P170)记忆建构身份的过程实际就是把过去与现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过程,是一个赋予过去事件以一定意义的主体行为,其中含有充分的主体性㊂回到田野个案,朱仙镇木版年画艺人郭太运的身体记忆有助于他现在的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身份的塑造,因此,探究身体记忆(包括郭太运本人的身体记忆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身体记忆,包括政府相关资料的记忆即记载或记录)是如何塑造的以及塑造的过程等,搞清楚身体记忆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话题㊂3.记忆的对峙性不同主体对同一件事情的记忆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便出现了不同记忆的对峙与共存㊂例如,在上述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人郭太运的身体记忆与朱仙镇木版年画的身体记忆中,存在着官方的记忆与民间的记忆㊁公共的记忆与私人的记忆㊁正式的记忆与非正式的记忆㊁ 正确的 记忆与 错误的 记忆的对峙与共存㊂上述现象在现代通信技术高度发展之后,在非政府组织大量出现之后,更加凸显出来㊂不同的群体对似乎是同样的 过去 ,明显有着不同的 故事 ,而这不同的故事,则限定着这些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甚至限定了他们对未来的设想㊂ [2](P6)面对不同的记忆与叙述,民俗学者究竟应持何种态度?笔者以为,最先明确的便是不同的记忆是如何进行叙述的?诸如此类的不同的叙述方式因何得以存在?在分析这些不同记忆与不同叙事时,关键不在于探讨其合情合理性,而在于探讨它们究竟是如何形成的㊂另外,还存在一种比较特殊的 对峙 ,即同一个人的 不同的记忆 ㊂在郭太运的 身体记忆 中也包含着这种 对峙 ,也就是说郭太运的对自己记忆的讲述以及对朱仙镇木版年画等民俗的讲述,都不完全是他关于记忆与民俗的最本源的 知识 ,而是通过与外边世界 比较 之后的 知识 ㊂简单地说,就是针对同样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时间段或在不同的场合,传承人也会有不同的记忆与言说㊂究竟哪一种记忆与言说是正确的?这不是笔者着重讨论的话题,不同记忆与言说的形成原因与过程才是最值得思考的问题所在㊂不可否认的是,传承人在受到媒体影响的过程中主观上认可威权势力的话语权,而对自己的本来记忆产生了疑惑甚至是背离㊂4.个人记忆与社会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是社会记忆研究的鼻祖㊂在他之前,学界对社会记忆的研究重点几乎都682014.06放在了生理遗传条件或心理条件方面㊂哈布瓦赫对社会记忆的研究具有名副其实的颠覆性㊂他认为,个人记忆由社会来决定,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不可分割,集体记忆可以共享并且可以传递给后代,并且指出集体记忆存在于现代社会和一些社会团体中㊂哈布瓦赫非常关心个体记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只有在社会里人们才能获取他们的记忆㊂也只有在社会里人们才能回忆,认同其回忆以及使记忆找到自己的位置㊂ [11](P38)按照其观点,个人记忆只有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才能形成,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相对,个人记忆具有社会性并受社会的制约㊂因此,民俗学对个人记忆的研究意义重大,例如对传承人等人口述史的研究便显得格外紧迫,因为这些看起来属于个人记忆的内容其实与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集体与社会的某些内容与动向㊂透过个人记忆,来审视集体和社会的某些变化与特征,才是研究的关键所在㊂三㊁身体记忆与民俗学研究在民俗学记忆研究中身体记忆占据重要位置,因此笔者把身体记忆作为独立的一个小节进行论述㊂首先来对 身体记忆 的概念进行界定,界定之前有必要对以往学术界的相关概念进行回顾㊂社会记忆研究的鼻祖莫里斯㊃哈布瓦赫使用的概念是 集体记忆 (collective memory),德国的古埃及学家阳㊃阿斯曼(Jan Assmann)则用 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的概念,其后的学者也有使用 公共记忆 (public memory)和 社会记忆 (social memory)这两个概念的㊂但以上概念均没有明确其 身体性 ㊂而之后的学者也没有对之作出明确的定义㊂只有刘铁梁才真正强调了身体记忆的重要性,他的观念深深影响了弟子们,张青仁在2009年发表的‘身体性:民俗学的基本特性“便是例证㊂笔者对刘教授 身体记忆 的理解是: 身体记忆 一方面包括 头脑中的记忆 ,另一方面包括 身体实践 或曰 身体技艺 ,因此笔者在做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田野调查时,比较注意收集记忆与技艺这两方面的资料信息,实际上,二者紧密杂糅在一起,艺人按照师傅传下来的方法制作木版年画这个身体实践过程本身,既有技艺的成分,又有记忆的成分,可以说记忆包含在技艺中 通过大脑的记忆来记住师傅传授的年画制作技艺;同时技艺也包含在记忆中 大脑中记住的不仅有木版年画其他方面的知识,而且还有其传统的制作工艺即技艺知识,这里的记忆将为年画制作技艺的实施助一臂之力[12](P111~133)㊂需要指出的是,笔者这里谈到的身体记忆不局限于某一个体的身体范围之内,也可以指两个个体或者是多个个体之间的身体记忆,即身体记忆具有主体间性,它存在于互动的主体间的范围内㊂因此可以说,身体记忆概念的提出与在民俗学研究中的运用将是一个不小的突破,同时也拓展了民俗学身体研究的路径㊂笔者认为,身体记忆概念在民俗学研究中的引入,与刘铁梁的 感受民俗学 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只要提到身体,就不可回避感受㊂这里的感受既包括研究者主体的感受㊂刘铁梁说: 民俗学直接面对的却是有主人在场的生活文化㊂ [13](P24)在这里,他强调不要忽视生活的整体性,并且指出 应该说,只有通过人的行动,才能呈现出生活的整体性,而不是靠民俗事象的排列组合 [13](P24)㊂根据刘教授的观点,笔者认为民俗学研究应该重视人㊁人的生活与感受,其中包括对人身体记忆的思考与研究㊂刘铁梁还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中指出: 地方社会保护民俗文化就是在保护其共同的历史记忆 , 对于一个地方社会来说,保护民俗文化就是在保护地方社会共同的历史记忆,即一个集体对于共同经历的生活变化的记忆㊂既要求改变生活,又要求记住自己的过去,这两方面的要求构成了当代人的文化心态 [14]㊂另外刘铁梁还强调: 民俗学的 根本性的价值是对于生活整体的关照㊂ [13](P2)而关照生活整体,最需要关注的则是生活中的人,因此对人的身体记忆的关照与研究就显得如此迫切㊂笔者认为,除了上述之主体间性,身体记忆还具有复合性㊂即身体记忆这一概念的使用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人记忆的范畴之内,它同时还适用于集体记忆㊁社会记忆与国家记忆等范畴㊂因为身体虽然首先是个人的身体(包括身与心),但同时也是集体㊁社会和国家的身体㊂尽管集体㊁社会和国家没有具像的身体存在,但这并不影响身体记忆的研究,因为笔者所谈论的身体记忆从根本上来讲,与其说是一种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倒不如说是一种研究方法㊂这种观点深受刘铁梁教授的影响,之所以强调身体记忆在民俗学学科范围内的重要性,实际上依然还是在回应与践行刘铁梁的 感受生活的民俗学 的理论观点㊂因此,不论是 通过民俗 还是 通过身体 ,方法论的凸显才是关键所在㊂四㊁结㊀语目前,记忆研究还未成为主流的考察方法,依78。
“二十四节气”的集体记忆与中华文化认同

广西民族研究2022年第6期(总第168期)“二十四节气”的集体记忆与中华文化认同*林继富何佩雯【摘要】二十四节气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中孕育而生,包含着中华各民族共创共享自然时序与人文时序的生活实践和生活智慧,包含了多民族共同的情感体验、共同的生活经历和共同的认知观念,成为体认中华文化一脉相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
二十四节气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是二十四节气焕发当代价值的重要转折点,二十四节气通过多种形式的记忆建构、传统复兴、生活交流,展现了其集体记忆、庆典文化和知识体系,实现了身份认同、价值认同、文化认同的回归,从而成为凝聚中华文化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团结。
【关键词】二十四节气;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体记忆;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者】林继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何佩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俗学专业2020级博士研究生。
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 (2022)06-0083-0010一、问题的提出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的重要见证,是中华民族在生存和发展中科学实践与智慧生活的重要体现,反映着中国人的科学观、宇宙观、生命观和文化观。
二十四节气作为传统时间制度是民众生产生活的重要参照坐标,涉及农业生产、饮食养生、仪式信仰、节日庆典、民间文艺等方方面面。
因此,二十四节气作用于国家管理、指导稼穑、精神需求、社会和谐的价值与功能也得到进一步彰显与强化。
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了持续传承和生产生活的实践动力。
中国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为二十四节气的保护和发展提供可持续路径,学者们通过对二十四节气起源、内涵、特征、功能等分析,对二十四节气的形成过程、生成结构、民俗生活有了整体性观照,为探讨二十四节气的传统社会生活、文化传承发展、当代价值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
场所的记忆和记忆的场所再现--电影《1942》重庆场景地建筑设计

柯林·罗和弗瑞德·科特在《拼贴城市》中提出 了一个问题,即“理想的城市可否同时表现得既是未来 的又是记忆的剧场”。1994年,克里斯蒂娜·博耶在 《集体记忆的城市》中再次探讨了“城市如何成为集体 记忆的场所”。虽然关于城市与记忆的研究在西方学术 界已经有比较充分和广泛的探讨,但总体上相关的设计 实践并不充分。而中国近年来建筑创作中以记忆再现为 主题的项目逐渐增加,对于场所记忆要素的运用已成为 设计的有效策略并在文化传承中发挥着作用。文化
活动之一,在文本出现以前,仪式是保证传统得到延续 和发展的重要手段。记忆与仪式的关系恰如意义与文本 的关系,仪式通过自身的程序规则使记忆再现,使意义 得到传递。古代仪式对于特定环境的选取使记忆和场所 建立起了基本的关联。运用场所意识来辅助记忆的方法 还包括西方古典记忆术。主要借助“场景”与“形象” 两大要素建立记忆的内部结构,场景建构的是记忆的框 架,作为存放形象的位置[1]。现实世界中一些类型的建 筑也被寓意为记忆设施。从中世纪的藏宝屋、晚期文艺 复兴盛行的奇珍屋到现代的博物馆和图书馆都从不同层 面作为历史知识和人类记忆的物质储藏空间,成为唤醒 记忆的殿堂。但是,由于记忆的可靠性一直受到历史学
摘 要 近年来,随着以记忆再现为主题的项目不断增多,以跨学科的视野,从保护历史遗产和地方性知识的角度 出发,探讨如何以场所记忆唤起城市共同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感,逐渐成为我国当代建筑设计的一个新内容。电影 《1942》重庆场景地的打造是电影场景设计学、文物建筑修复学与建筑学三者的一次跨界合作,是城市尺度下一次 记忆重建之旅。设计构思以城市记忆的寻找、唤起与呈现为核心,从城市形态记忆、城市空间记忆、建筑记忆、景 观记忆及符号事件记忆五要素入手,通过空间叙事和节点再现、复原与拼贴等组织手法,使记忆在真实物质空间得 以复苏与重生。 关键词 城市记忆 写意性 再现 叙事 文化景观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cultural-type buildings related to “local memory and homesickness”, how to arouse the city’s “common cultural memory and identity”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nd the perspective of protecting historical heritage and local knowledge, is gradually becoming a new issue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al design in China. Movie 1942 was a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between film scene design, cultural relics restoration and architecture. It was a “memory rebuilding” journey on the city scale. The design concept was centered on “seeking, awakening and presenting of urban memory”, starting with the five elements including urban form memory, urban spatial memory, architectural memory, landscape memory, and symbolic event memory. Using organizational methods such as “spatial narrative and node reproduction, restoration, and collage”, the project enabled “memory” to be revived and reborn in the real material space. KEY WORDS urban memory, freehand, reproduction, narrative, cultural landscape DOI 10.12069/j.na.201906054 中图分类号 TU-0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3959(2019)06-0054-0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1878083)
“记忆的阐释学”与当代文学的记忆书写问题——以毕飞宇为例

“记忆的阐释学”与当代文学的记忆书写问题以毕飞宇为例赵坤关于文学与记忆的关系,毕飞宇曾说:“记忆是不可靠的。
是动态的,充满了不确定性。
这种动态或不确定使记忆本身带上了戏剧性,也就是说,带有浓重的文学色彩。
”①这是哲学现代性层面的讨论,理性主义将记忆书写纳入文学的范畴,经验主义则证明记忆与文学之间必然的关系,问题就这样集中到文学的主体性。
当代文学中,围绕现代国家的合法化、后革命时代的革命书写、社会主义道路的想象与认同,以及创伤记忆的清理和反思等问题,关于个体与集体的记忆主题不断展开、深入,记忆书写也呈现出与历史叙述之间的复杂关系,以至于关于记忆的写作,越来越多地被视为文学重返、发现、重写历史,解释、认识现实,兼与观察当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情感结构以及社会思想变化的“记忆的阐释学”问题。
一、“记忆之场”:个体与集体记忆如何交互苏格拉底曾经对特埃特图斯说,记忆是“缪斯的母亲摩涅莫绪涅所赐的礼物”,如果没有记忆,那些音乐、诗歌、绘画,所有人类史上的艺术杰作都会被遗忘。
所以书写作为助记方法被发明,在各种文明形式中被赋予记忆历史的原始功能,但“人工记忆”会有选择和遗忘,并在漫长的历史、文化和文明史中“影响我们对记忆和遗忘的认识”。
②后现代理论发现了这一点,提示了人类在“反思”和“重构”中考察思想史的形成脉络。
在这条脉络的20世纪端口,法国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物质性、象征性和功能性的“记忆之场”,质疑了拉维斯主义那种“条分缕析又严丝合缝的‘统一体’”“时序上和归旨上的连续性”的历史逻辑,转以历史的遗迹(那些真实的场所、纪念碑、档案之类)为中心,对“建构之象征物”与“施加之象征物”展开意义生成路线的追溯。
有趣的是,历史学家们讨论的重点对象是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
也因此,记忆除了“国民意识的形成和自我观照的历史”的贡献之外,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启示是,文学如何作为文化“遗产”在社会历史的构建与反思性自我意识中发挥重要作用。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记忆的场所》与法国记忆史研究
作者:洪庆明《光明日报》(2016年03月17日13版)
法国记忆史研究始兴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历30年而方兴未艾。
在此期间,各种专题性或综合性的记忆研究文丛纷至沓来,如“刻录记忆”“历史、记忆与遗产”“历史与记忆之间”“记忆/历史”“历史与战士的记忆”“重要战役与各民族记忆”以及新近推出的“记忆史”等大量系列丛书,仅“刻录记忆”丛书到目前为止就已出版了563种图书,内容涵盖各个学科领域,历史学在其中占据着十分显赫的位置。
各种学术会议也层出不穷,主题涉及记忆史的各个重要研究领域:殖民和非殖民化历史、两次世界大战、拿破仑遗产、维希政府和犹太人的命运等,如2012年10月在巴黎举办的“作家论坛”,研讨1954-1962年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进程塑造的多样记忆;2013年11月巴黎军事博物馆主办的“从记忆到历史”国际研讨会,以老兵回忆为基础探讨20世纪的创伤性话题——老兵问题的研究状况和路径,诸如此类的会议不胜枚举。
法国这股史学新潮流兴起的动力,源自二战后法国社会政治和集体心态均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在战后工业化的有力推动下,到20世纪60年代,法国农业人口急剧下降,代之以深度的城市化,所谓“深邃的法兰西”的农耕社会观念渐行渐远;对民主共和体制的共识已然生成,大革命以来的政治分歧和冲突不再是扰动法兰西民族的力量,取而代之的是非殖民化和全球政治成为法国人界定自身政治价值信仰的标杆。
对于在历史时空中逐渐消逝的“我们失去的世界”,一种集体的历史乡愁弥漫开来,正如《记忆的场所》主编皮埃尔·诺拉所说:“人们之所以如此之多地谈论记忆,是因为它不再存在。
”在此种背景下,作为出版编辑兼历史学家的诺拉在20世纪70年代末便开始酝酿出版一套有关民族记忆场所丛书,意在“将维护和保持社会恒久长存所需要的想象力激发出来”,同时革新史学研究的方法和路径。
通过他的精心组织、协调和亲身参与,第一部分《共和国》1984年面世,旋即在欧美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两年后第二部分《民族》出版;1992年又推出第三部分《法兰西》,最终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民族记忆场所系列。
《记忆的场所》的面世,是法国记忆史研究当中里程碑式的事件。
它不仅以一种新颖的方式来表现法兰西的文化特性,帮助锻造民族身份认同,而且使民族历史得以体现的各种物事——包括纪念碑、博物馆、历史文本、人物、城市等实在的、象征性的或功能性的场所,都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对激发法国记忆史研究的热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书籍出版的第二年,词组“记忆的场所”即被收入《罗贝尔法语大词典》,成为与民族集体记忆对话交流的中心词语。
而且,它开辟的新视野和新路径,使其影响迅速扩散到欧美乃至亚洲各国,作为样板被应用于研究各种不同的记忆文化,2015年底中文节译本出版。
诺拉原本计划将构成民族的元素拆解开来,一个个单独加以研究,在重视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上,以象征性语汇重新诠释法国史。
他希图通过这样的视角,开辟一条通往新型史学之路。
这种史学对结果的兴趣甚于对原因的兴趣,对事件构建过程的兴趣甚于对事件本身的兴趣,对事件不断地被再利用或误用的兴趣甚于对实际发生的事件的兴趣,对传统构建和消失方式的兴趣甚于对传统的兴趣……其目的在于反抗线性的历史叙事,解构民族—国家的宏大话语,反映多样的声音。
然而,他最终未能摆脱民族—国家的“幽灵”。
众多评论者集中批评的一点是,《记忆的场所》原欲做民族—国家叙事框架的解构者,但最终却无意中重构了一部整体的法兰西史,展现的更多是中央集权的雅各宾主义法国图景,并成为一座纪念的丰碑。
之所以如此,在笔者看来,盖因两种智识因素的辐辏:一是抽象层面上,法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氛围中浸润着深深的民族—国家关怀,正如沈坚教授指出的,诺拉是在法国社会和文化心理已发生翻天覆地
变化的情境下,试图拯救民族记忆,重构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二是具体操作上,诺拉在记忆的界定上,深受法国历史学家哈布瓦赫的影响,即有多少个族群就有多少种记忆,但每个族群都有自己一以贯之的记忆语言。
这样的定义必然导致对法兰西民族内部异质性的排斥,更多地强调同质的一面以彰显它作为一个民族的统一性和整体性。
这种内蕴在方法论中的排斥机制,使《记忆的场所》将法兰西民族特性局限在晚近才形成的六边形领土之内,既未能完整地呈现形塑法国民族特性的历史图景,也未能准确地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实图景。
其一,漫长的殖民历史、残酷的非殖民化冲击以及后殖民时代移民缺席,但它们曾是法国历史的重要一页,其影响延续至今(尤其是移民问题);其二,忽略了法国内部多样且相互冲突的地区差异和阶级分层,民族—国家层面的集体记忆压倒了复杂多样的地方性记忆共同体;其三,那些与民主共和价值相悖的历史也未得到应有的关照,譬如拿破仑帝国和维希政权。
但无论如何,《记忆的场所》在法国乃至世界记忆史研究中的开创和引领之功是无可否认的。
而且,就法国来说,它的遗缺实际上也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开拓的空间。
近年来,法国记忆史论著源源不断地出版,蔚为大观,主要聚焦于殖民史和战争史领域,在研究对象上趋于注重地方和群体/个人的记忆,而非六边形之内的法国民族—国家记忆。
首先,在殖民史方面,阿尔及利亚、西非、圭亚那、加拿大和黎巴嫩等法国不同时期的殖民地均有专门的著作涉猎。
阿尔及利亚是殖民记忆史研究中最为醒目的热点,因为阿尔及利亚战争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至今尚未愈合的巨大创伤事件,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非殖民化进程中的残酷战争和后殖民时代双方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使之成为法阿两国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相互冲突的记忆之所。
2014年出版的《我父亲,一位老兵的人生旅程》是一部私人史,作者米歇尔·梅萨埃尔历时五年搜集证人证据,回顾其父和家庭颠沛流离的历程,揭示了战争给普通人命运造成的影响。
本杰明·斯托拉教授所著的《面向所有人解释阿尔及利亚战争》(2012),在缕述了战争的重大事件和主要人物之后,转而通过法裔阿尔及利亚人、战争老兵、侨民和移民等不同群体的战争记忆,勾勒这场战争给法阿双方留下的政治后果和记忆遗产。
他希图借记忆的复原实现身份构建,消弭偏见和双方持久的怨恨。
此外,2015年普罗旺斯大学出版社还推出了一本题为《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一部断裂史》,除回顾1830-1962年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的艰难处境和身份转变外,末尾也提到了这种经历给他们留下的种种记忆的场所。
其次,战争主题的论著是许多记忆史文丛重要的组成部分。
大至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小至知名或不知名的单个战役,均被纳为专门研究的对象,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仍然鲜活地存在于当代法国人的记忆中,且与现实的社会政治紧密地纠葛在一起,因此成为记忆史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
史学家们梳理了二战中“抵抗运动与通敌合作”这对相互冲突的记忆在当代法国的演变过程:战后初期为重构国民团结和民族共识而制造的“抵抗主义神话”;1947-1968年的记忆爆炸和戴高乐派记忆取得胜利;1969年之后抵抗主义神话终结,对维希政权时期的看法变得更加精细。
“集中营和大屠杀”的记忆也同样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1945-1961年被遗忘的大屠杀;1961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犹太人记忆得到彰显;20世纪80年代初犹太人记忆的胜利。
尽管不像美国那样,大屠杀在记忆史研究中占据着半壁江山的地位,但法国对该主题的重视也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与记忆之间”丛书中包含着大量相关著作,“记忆史”丛书2015年推出的两部著作中就有一本题为《大屠杀记忆史》。
总的说来,法国记忆史历经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间的种种发展变化,是学术自身创新发展需求的结果,也与思想氛围转变紧密相关。
身处一个不断变动的世界中,记录过往的记忆,既是我们对先辈的责任,也是我们自己安身立命的支柱,对于正急剧从千年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