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新闻学--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
晚清民国时期传媒公共性的生成与演变_1815_1949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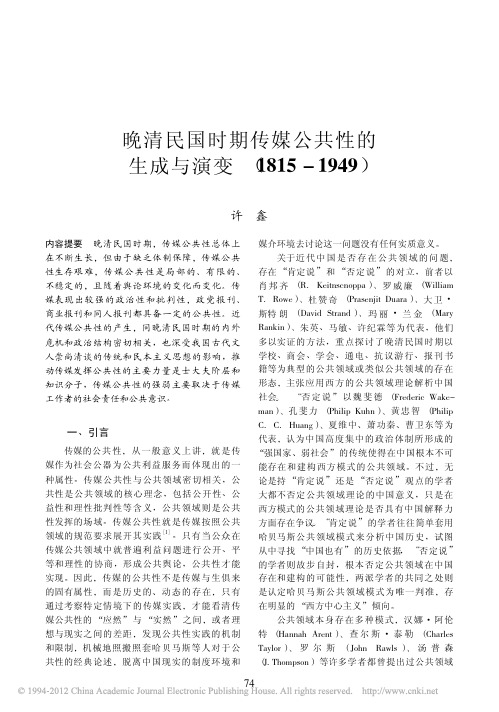
晚清民国时期传媒公共性的生成与演变(1815-1949)许鑫内容提要晚清民国时期,传媒公共性总体上在不断生长,但由于缺乏体制保障,传媒公共性生存艰难,传媒公共性是局部的、有限的、不稳定的,且随着舆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传媒表现出较强的政治性和批判性,政党报刊、商业报刊和同人报刊都具备一定的公共性。
近代传媒公共性的产生,同晚清民国时期的内外危机和政治结构密切相关,也深受我国古代文人崇尚清谈的传统和民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推动传媒发挥公共性的主要力量是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传媒公共性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传媒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公共意识。
一、引言传媒的公共性,从一般意义上讲,就是传媒作为社会公器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体现出的一种属性。
传媒公共性与公共领域密切相关,公共性是公共领域的核心理念,包括公开性、公益性和理性批判性等含义,公共领域则是公共性发挥的场域。
传媒公共性就是传媒按照公共领域的规范要求展开其实践[1]。
只有当公众在传媒公共领域中就普遍利益问题进行公开、平等和理性的协商,形成公共舆论,公共性才能实现。
因此,传媒的公共性不是传媒与生俱来的固有属性,而是历史的、动态的存在,只有通过考察特定情境下的传媒实践,才能看清传媒公共性的“应然”与“实然”之间,或者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发现公共性实践的机制和限制,机械地照搬照套哈贝马斯等人对于公共性的经典论述,脱离中国现实的制度环境和媒介环境去讨论这一问题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关于近代中国是否存在公共领域的问题,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的对立,前者以肖邦齐(R.Keitnscnoppa)、罗威廉(William T.Rowe)、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大卫·斯特朗(David Strand)、玛丽·兰金(Mary Rankin)、朱英、马敏、许纪霖等为代表,他们多以实证的方法,重点探讨了晚清民国时期以学校、商会、学会、通电、抗议游行、报刊书籍等为典型的公共领域或类似公共领域的存在形态,主张应用西方的公共领域理论解析中国社会。
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史

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史一、引言中国新闻传播学是中国近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学科之一,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媒体的兴起,中国新闻传播学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
本文将从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起源、发展阶段和主要成就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二、起源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初。
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动荡的时期,社会变革和媒体发展成为推动新闻传播学兴起的重要因素。
1919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系,这标志着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正式诞生。
此后,中国新闻传播学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
三、发展阶段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1. 初期阶段(1919年-1949年)在这一阶段,中国新闻传播学主要关注新闻传播的技术和实践问题。
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新闻报道的规范、新闻编辑的方法和新闻传播的技术手段等方面。
此时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还受到西方传媒理论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理论框架。
2. 建国初期阶段(1949年-1978年)在这一阶段,中国新闻传播学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强调新闻传播的社会责任和服务大众的功能。
研究重点主要放在新闻舆论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和新闻媒体的组织管理等方面。
同时,中国新闻传播学也开始研究国际传媒理论,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3. 改革开放阶段(1978年-2000年)改革开放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在这一阶段,中国新闻传播学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开始关注媒介技术的发展和传播效果的评估。
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媒体融合、传媒产业、新闻媒体经营等方面。
此外,中国新闻传播学也开始关注公共传播、网络传播和国际传播等新兴领域。
4. 当代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新闻传播学面临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挑战。
在这一阶段,中国新闻传播学开始关注全球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传播问题,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全球传媒治理、跨文化传播和媒介素养等方面。
同时,中国新闻传播学也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国际学界共同研究全球传媒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公共新闻学--国内公共新闻学研究的分析

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 试图拓展公共新闻的研究领域。
在传统意义上进行报道, 提供信息和书写供受众阅读的新
( 一) 公共新闻与公共领域的构建
闻文本, 而是将协商对话的过程通过公共新闻保留在公共
近年来, 大众传媒与公共领域的构建问题是新闻传播 视野中, 有助于人们认识自己的参与价值, 对认知持续的
学界关注较多的一个热点问题-./。公共新闻概念引入后, 学 鼓 励 , 使 得 公 民 有 更 广 泛 参 与 的 积 极 性 。 参 与 公 共 事 务 讨
行 动 , 也 就 是 说 公 民 不 再 被 动 、单 向 地 接 收 媒 体 的 报 道 , 转 诸多质疑, 但其立论精神, 即企图创造公民对公共议题的关
而主动地发掘切合个人需求的讯息。由于强调公民— ——而 注与积极参 与 这 一 点 , 与 西 方 政 治 学 中 的 审 议 民 主( delib-
对于公民新闻的发展, 罗森教授指出:“网络上的新闻
审 议 民 主 是20世 纪90年 代 以 来 在 西 方 政 治 学 界 兴 起
交易, 意味着一种新的公共领域, 在这个领域里每个读者都 的 一 种 民 主 理 论 , 在 国 内 又 译 为 协 商 民 主 、商 议 民 主 等 。审
能成为作者, 而且人们对新闻的这种‘消费’是在他们更主 议 民 主 理 论 强 调 公 民 是 民 主 体 制 的 参 与 主 体 , 应 该 积 极 促
纸上充斥着候选人的相互指控和民意调查的枯燥数字, 而
首先, 新闻工作者直接参与新闻事件并担任组织者的
对实质性的问题几乎没有涉及; 竞选过程中, 只有一半选民 角色是否恰当? 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就是客观、公正地报道新
参加投票。梅里特认为新闻媒体应该为此种现象负责②。这 闻 , 为 公 众 提 供 信 息 , 如 果 他 们 直 接 参 与 了 新 闻 事 件 , 受 众
建立公共性传媒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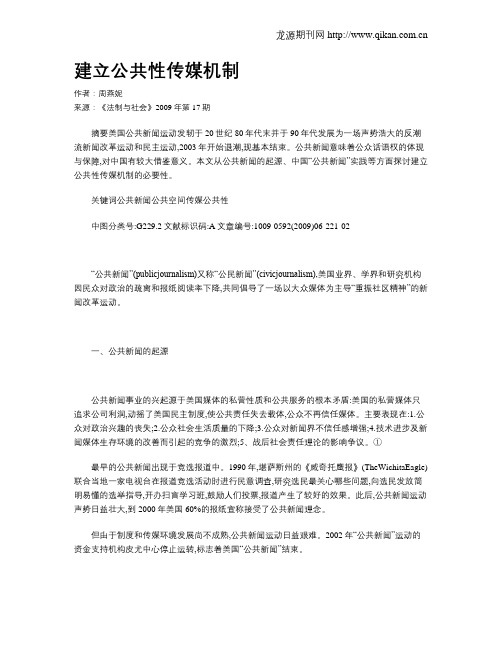
建立公共性传媒机制作者:周燕妮来源:《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17期摘要美国公共新闻运动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末并于90年代发展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潮流新闻改革运动和民主运动,2003年开始退潮,现基本结束。
公共新闻意味着公众话语权的体现与保障,对中国有较大借鉴意义。
本文从公共新闻的起源、中国“公共新闻”实践等方面探讨建立公共性传媒机制的必要性。
关键词公共新闻公共空间传媒公共性中图分类号:G22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6-221-02“公共新闻”(publicjournalism)又称“公民新闻”(civicjournalism),美国业界、学界和研究机构因民众对政治的疏离和报纸阅读率下降,共同倡导了一场以大众媒体为主导“重振社区精神”的新闻改革运动。
一、公共新闻的起源公共新闻事业的兴起源于美国媒体的私营性质和公共服务的根本矛盾:美国的私营媒体只追求公司利润,动摇了美国民主制度,使公共责任失去载体,公众不再信任媒体。
主要表现在:1.公众对政治兴趣的丧失;2.公众社会生活质量的下降;3.公众对新闻界不信任感增强;4.技术进步及新闻媒体生存环境的改善而引起的竞争的激烈;5、战后社会责任理论的影响争议。
①最早的公共新闻出现于竞选报道中。
1990年,堪萨斯州的《威奇托鹰报》(TheWichitaEagle)联合当地一家电视台在报道竞选活动时进行民意调查,研究选民最关心哪些问题,向选民发放简明易懂的选举指导,开办扫盲学习班,鼓励人们投票,报道产生了较好的效果。
此后,公共新闻运动声势日益壮大,到2000年美国60%的报纸宣称接受了公共新闻理念。
但由于制度和传媒环境发展尚不成熟,公共新闻运动日益艰难。
2002年“公共新闻”运动的资金支持机构皮尤中心停止运转,标志着美国“公共新闻”结束。
学界对公共新闻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公共新闻”运动的学术领袖、纽约大学新闻学系主任杰·罗森(JayRosen)教授第一个提出“公共新闻(Public/CivicJournalism)”概念,他呼吁新闻记者报道新闻时还应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取新闻信息基础上的行为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或观看这些问题。
中共三次新闻改革与传媒公共性的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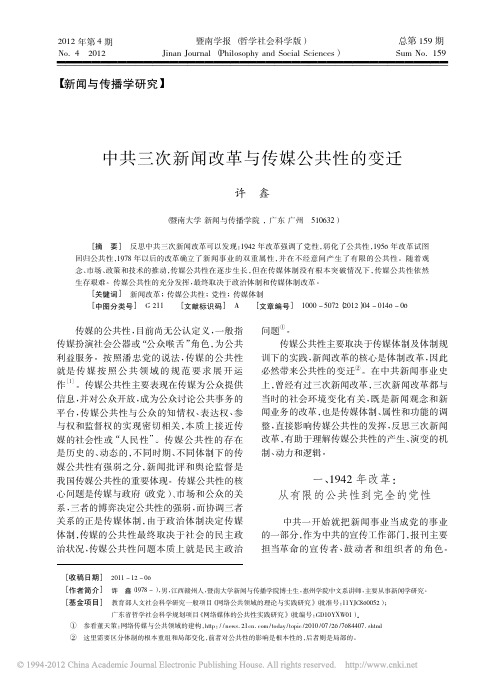
传媒的公共性, 目前尚无公认定义, 一般指 传媒扮演社会公器或“公众喉舌 ” 角色, 为公共 利益服务。按照潘忠党的说法, 传媒的公共性 就是 传 媒 按 照 公 共 领 域 的 规 范 要 求 展 开 运 [ 1] 作 。传媒公共性主要表现在传媒为公众提供 信息, 并对公众开放, 成为公众讨论公共事务的 平台, 传媒公共性与公众的知情权、 表达权、 参 与权和监督权的实现密切相关, 本质上接近传 。 传媒公共性的存在 媒的社会性或“人民性 ” 是历史的、 动态的, 不同时期、 不同体制下的传 媒公共性有强弱之分, 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是 我国传媒公共性的重要体现。传媒公共性的核 心问题是传媒与政府 ( 政党 ) 、 市场和公众的关 系, 三者的博弈决定公共性的强弱, 而协调三者 由于政治体制决定传媒 关系的正是传媒体制, 体制, 传媒的公共性最终取决于社会的民主政 治状况, 传媒公共性问题本质上就是民主政治
[ 收稿日期] 2011 - 12 - 06
问题 ① 。 传媒公共性主要取决于传媒体制及体制规 新闻改革的核心是体制改革, 因此 训下的实践, ② 必然带来公共性的变迁 。 在中共新闻事业史 上, 曾经有过三次新闻改革, 三次新闻改革都与 当时的社会环境变化有关, 既是新闻观念和新 闻业务的改革, 也是传媒体制、 属性和功能的调 整, 直接影响传媒公共性的发挥, 反思三次新闻 改革, 有助于理解传媒公共性的产生、 演变的机 制、 动力和逻辑。
[ 4] [ 3] 26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为了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 自 1942 年 8 月起, 中共中央决定《解放日报 》 兼为中共中 《关于 < 解放 央西北局机关报, 随后西北局发布 , 强调党报必须由全党 日报 > 工作问题的决定》 来办, 要求各级党委要把帮助与利用《解放日 当成自己经常的重要业务之一, 定期检查自 报》 《解放日报》 己对 所做的工作并向西北局汇报, 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长要担任《解放日报 》 的通 。《解放 讯员并负责组织所属地区的通讯工作 日报》 也加强了内部学习, 要求党报工作者必须 不允许与党唱对台 认识到自己是党的一分子, 戏, 坚持“人民公仆 ” 的思想, 反对“无冕之王 ” “政治第一, 的主张, 坚持 技术第二 ” 的原则, 反 “技术第一, 政治第二 ” 的观点。 改革以后, 对 新闻工作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明显弱化, 王实味 王实 等具有自由化倾向的文章较少见诸报端, 味本人还受到批判。 第一次新闻改革, 虽然也提出了党报要有 “群众性 ” 、 “战斗性 ” 的口号, 但这里的“群众 ” 、 “战斗性 ” 性 与“公共性 ” 的内涵有着本质差 。“群众性” 异 强调新闻报道的内容和形式要 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出发 符合群众特点和需要, , “战斗性 ” 点是为了提高党的宣传工作效果 即 “报刊要成为革命事业的一支方面军, 鼓舞人
传媒公共性与公共性传媒

传媒公共性与公共性传媒作者:曹国跃来源:《智富时代》2018年第03期【摘要】随着网络时代的跨越式发展,全人类已经越到了一个信息时代的形态中。
其中,传媒公共性和公共性传媒是信息传播形式的主要系统之一。
基于“十三五”计划的重要实施中,想要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与时俱进,就需要从传播的角度进行构建,实现传媒公共性和公共性传媒之间的有效区分,展现政府和传媒、公众指三者之间的博弈平衡状态,这样才能保证传媒结构的可持续发展和合理性构建。
【关键词】公共性;结构;传媒一、政府和传媒公众之间的稳定结构在信息传播社会角色和独立社会组织上,不仅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系统。
还在一定的子系统构建中,展现了时代的变迁和拓展中,传递着一种相互依赖性的关系,并在相互融合的构建中,展现一种,社会的变迁影响着传媒组织的生存发展。
从本质上看,社会是一种作为物质生活生产关联的生活共同体,并在主体的社会展现中,行使国家机构和权利执行能力,并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构建公众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传递一种强有力的思想理念。
在政府社会的委托中,国家的权利就是相应的执行机构,也是管理媒体的权利。
在作为社会公众的委托方同时,也受到了有关的监督。
在历史发展的选择下,始终保持的是一个生存的发展因素,并以社会为基础,进行展现自身的弥补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依托于公众,构建相应的组织形态,承担着强有力的压力,满足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需求[1]。
在独立的系系统的构建中,依托三角形具有稳定性的原理,不仅需要展现社会政治和社会公共事务的传递点,还需要为自身代言,行使政府监督,实现多样化的需求。
在社会公共性是意识中,需要根据场所的转变实,实现社会的互动,并在稳定性的结构中国,展现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对陆行和组织性。
其中,所谓公共领域(publicsphere)从哈贝马斯的思想中,可以提炼出,一个国家个社会之间的公共性空间的构建,并且具有自由言论的权利,不受到任何的干涉行为。
在这样一个整合的空间上,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构建,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典形态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展现具有现代化思想的适用性价值,传递一种本质的属性[2]。
公共关系学-公共关系传播模式与媒介_真题(含答案与解析)-交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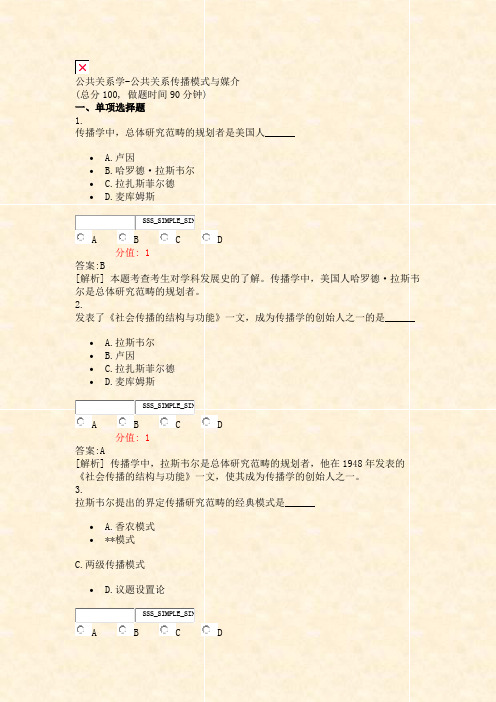
公共关系学-公共关系传播模式与媒介(总分100, 做题时间90分钟)一、单项选择题1.传播学中,总体研究范畴的规划者是美国人______• A.卢因• B.哈罗德·拉斯韦尔• C.拉扎斯菲尔德• D.麦库姆斯SSS_SIMPLE_SINA B C D分值: 1答案:B[解析] 本题考查考生对学科发展史的了解。
传播学中,美国人哈罗德·拉斯韦尔是总体研究范畴的规划者。
2.发表了《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成为传播学的创始人之一的是______ • A.拉斯韦尔• B.卢因• C.拉扎斯菲尔德• D.麦库姆斯SSS_SIMPLE_SINA B C D分值: 1答案:A[解析] 传播学中,拉斯韦尔是总体研究范畴的规划者,他在1948年发表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使其成为传播学的创始人之一。
3.拉斯韦尔提出的界定传播研究范畴的经典模式是______• A.香农模式•**模式C.两级传播模式• D.议题设置论SSS_SIMPLE_SINA B C D答案:B[解析] 本题属于识记内容,考生需认真掌握。
5W模式是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的界定传播研究范畴的经典模式。
4.“把关人”这一概念出自______• A.《原则宣言》• B.《修辞学》• C.《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 D.《群体生活的渠道》SSS_SIMPLE_SINA B C D分值: 1答案:D[解析] 本题属于识记内容,考生需牢记。
1947年,德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最早提出了“把关人”这一概念。
5.传播学学者十分重视把关人的作用,并认为这是一种信息传播的______• A.特殊现象• B.简单现象• C.普遍现象• D.复杂现象SSS_SIMPLE_SINA B C D分值: 1答案:C[解析] 本题考查考生对“把关人”这一知识点掌握的熟练程度,属于识记内容。
传播学学者十分重视把关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枢纽作用,认为把关人是一种信息传播的普遍现象。
当代中国传媒政治的内涵与演变——以改革开放为起始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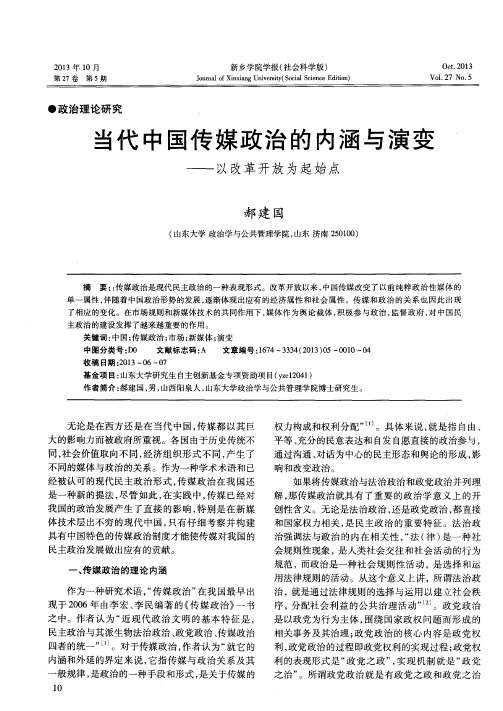
关键词 : 中国; 传媒政治 ; 市场 ; 新媒体 ; 演 变
中图分 类号 : D O 文献标 志码 : A 文章编号 : 1 6 7 4~ 3 3 3 4 ( 2 0 1 3 ) 0 5— 0 0 1 0— 0 4 收稿 日期 : 2 0 1 3—0 6— 0 7 基 金项 目: 山东大学研究生 自主创新基金专项资助项 目( y z c 1 2 0 4 1 )
是 以政党 为行为 主 体 , 围绕 国家 政 权 问 题而 形 成 的
作 为一 种研究 术语 , “ 传媒政治” 在 我 国最 早 出
现于 2 0 0 6 年 由李宏 、 李 民编著 的《 传媒政治》 一书 之 中。作 者 认 为 “ 近 现 代 政 治 文 明 的基 本 特 征 是 , 民主政治与其派生物法治政治 、 政党政治、 传媒政治 四者 的统一 ” _ 1 。对 于传 媒政 治 , 作 者认 为 “ 就 它 的 内涵和外 延 的界定 来 说 , 它 指 传 媒 与政 治 关 系 及 其
2 0 1 3年 1 0月
第2 7卷 第 5期
新 乡学 院学报 ( 社会科 学版)
J o u na r l o f X i n x i a n g U n i v e r s i t y ( 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E d i t i o n )
0c t . 2 01 3
V0 1 . 2 7 No . 5
●政 治 理 论 研 究
当代 中 国传 媒 政 治 的 内涵 与演 变
以 改革 开放 为起 始 点
郝建 国
( 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 山东 济南 2 5 0 1 0 0 )
摘
要: : 传媒政治是现代 民主政治 的一种表现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传媒改变 了以前纯 粹政治性媒体 的
试论新闻媒体的公共性及其实现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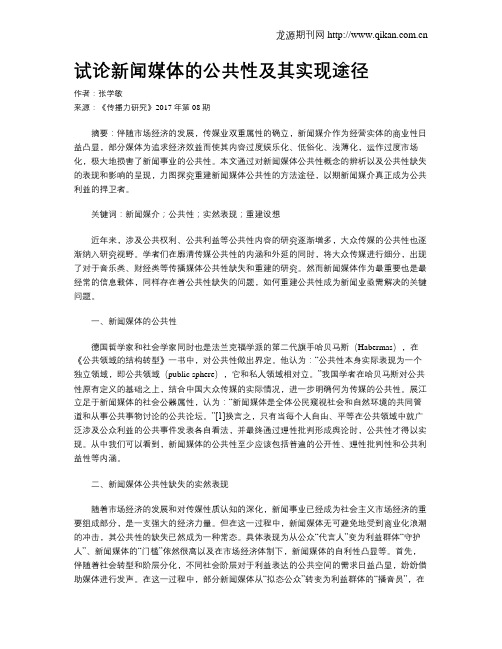
试论新闻媒体的公共性及其实现途径作者:张学敏来源:《传播力研究》2017年第08期摘要: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传媒业双重属性的确立,新闻媒介作为经营实体的商业性日益凸显,部分媒体为追求经济效益而使其内容过度娱乐化、低俗化、浅薄化,运作过度市场化,极大地损害了新闻事业的公共性。
本文通过对新闻媒体公共性概念的辨析以及公共性缺失的表现和影响的呈现,力图探究重建新闻媒体公共性的方法途径,以期新闻媒介真正成为公共利益的捍卫者。
关键词:新闻媒介;公共性;实然表现;重建设想近年来,涉及公共权利、公共利益等公共性内容的研究逐渐增多,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也逐渐纳入研究视野。
学者们在廓清传媒公共性的内涵和外延的同时,将大众传媒进行细分,出现了对于音乐类、财经类等传播媒体公共性缺失和重建的研究。
然而新闻媒体作为最重要也是最经常的信息载体,同样存在着公共性缺失的问题,如何重建公共性成为新闻业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新闻媒体的公共性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同时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哈贝马斯(Habermas),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对公共性做出界定。
他认为:“公共性本身实际表现为一个独立领域,即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它和私人领域相对立。
”我国学者在哈贝马斯对公共性原有定义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大众传媒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何为传媒的公共性。
展江立足于新闻媒体的社会公器属性,认为:“新闻媒体是全体公民窥视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共同管道和从事公共事物讨论的公共论坛。
”[1]换言之,只有当每个人自由、平等在公共领域中就广泛涉及公众利益的公共事件发表各自看法,并最终通过理性批判形成舆论时,公共性才得以实现。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新闻媒体的公共性至少应该包括普遍的公开性、理性批判性和公共利益性等内涵。
二、新闻媒体公共性缺失的实然表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传媒性质认知的深化,新闻事业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支强大的经济力量。
传媒公共性_概念的解析与应用_许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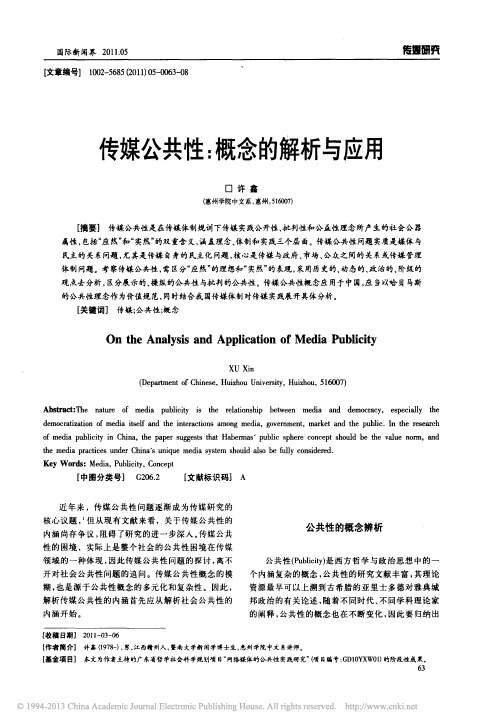
我国学者 常根
据 研 究需 要 简单 套 用 其 中一 种含 义 来 分析 中 国问
传媒公共性的界定
传媒公共性 的 内涵与公共性 内涵一 样 , 尚存争
议 作为第一位 系统论述 公共领域 的学者 , 哈 贝马斯 没有正面论述 传媒的公共性 问题 , 只是指 出 : 到 了
大众传媒领域 , 公共性的意 思无疑又有 所变化 , 它从
63
公共性的概念辨析
公共性 (Public it y )是西方 哲学 与政 治思想 中的一
个 内涵复杂 的概 念 , 公共性 的研究 文献 丰富 , 其理论 资源 最早可以上溯 到古希腊 的亚里士 多德对 雅典城 邦政 治的有关论述 , 随着不 同时代 不同学科 理论家 的 阐释 , 公共性 的概念也在 不断变化 , 因此要 归纳 出
国际新 闻界 加1 1. 5 0 了更加 宽泛 更加 多元的广义 公共领域 概念 , 公共领
域 被 作为一种 用来交 流信息 和 观 点的 网络 , 这种
网络能 够把 私 人 世界 的 经验 和 政 治 系统联 系在 一 起 , 各种公共利益集 团和 各类专 业人士是 公共领域 内的积极分子 , 他们 的介入能够使 批判性 的辩论联 合并 生成各 种 有 关特 定话题 的 公共意 见 , 对政治 系统 构成持续的压 力并 迫使其做 出谨 慎的 回应 4 显 然 , 哈 贝马斯 的 多元 公共 领域模式 比其资 产阶级 公 共领域 模式更加符合现 代社会特点 不过 , 由于 其广 义公共领 域概念过于宽泛 , 削弱 了公共领 域理论 所 具有 的价 值批判意义 尽管哈 贝马斯的 资产阶级 公共领域 思想 遭受各 种批评 , 但其 蕴涵的平等 开放 自由讨论 理性批 判 关注普遍利益 达成共识等 思想原则具 有普世价 值 , 并 可被置于任一具 体语境 中进行 探讨 现代意义
论传媒公共性及其实现途径

论传媒公共性及其实现途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传媒行业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媒机构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然而,传媒机构在传播信息的也需要考虑到公共性的问题。
本文将探讨传媒公共性的内涵和实现途径,以期为传媒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些思路。
传媒公共性是指传媒机构在传播信息时,不仅要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还要维护公共利益。
传媒公共性对于传媒行业来说至关重要,它是传媒机构赢得公众信任、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同时,传媒公共性也是社会公正、公平的重要保障,它可以让公众了解到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为了实现传媒公共性,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传媒机构的体制和机制是影响传媒公共性的重要因素。
因此,传媒机构需要从体制和机制上做出改革,以保障传媒公共性的实现。
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和完善传媒机构的内部管理机制,加强新闻职业素养教育,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社会责任感;同时,还要加强传媒机构的公众参与程度,让公众更加深入地参与到传媒决策中来。
新闻职业素养教育是实现传媒公共性的重要保障。
通过教育和培训,可以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同时,公众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新闻素养,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判断媒体信息。
这需要媒体机构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公众参与是实现传媒公共性的重要途径之一。
通过加强公众参与,可以让公众更加深入地参与到传媒决策中来,从而提高传媒机构的公共性和公信力。
例如,可以通过举办公开论坛、听证会等方式,让公众对媒体内容产生质疑或提出建议,使媒体决策更加科学、合理。
以英国的广播公司(BBC)为例,它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公共广播机构,一直以来非常注重传媒公共性的实现。
BBC的新闻报道具有很高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这与其严格的新闻职业素养教育是分不开的。
BBC要求和编辑在报道新闻时要保持中立、公正,不得带有任何个人情感色彩。
BBC还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公众参与,比如开通新闻热线、举办公开论坛等,以便听取公众的声音和意见。
浅谈中国大众传媒的公共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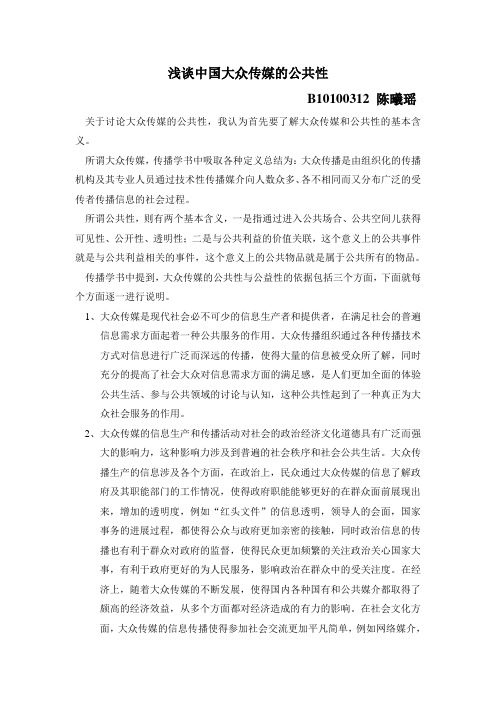
浅谈中国大众传媒的公共性B10100312 陈曦瑶关于讨论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我认为首先要了解大众传媒和公共性的基本含义。
所谓大众传媒,传播学书中吸取各种定义总结为:大众传播是由组织化的传播机构及其专业人员通过技术性传播媒介向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传者传播信息的社会过程。
所谓公共性,则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指通过进入公共场合、公共空间儿获得可见性、公开性、透明性;二是与公共利益的价值关联,这个意义上的公共事件就是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件,这个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就是属于公共所有的物品。
传播学书中提到,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与公益性的依据包括三个方面,下面就每个方面逐一进行说明。
1、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信息生产者和提供者,在满足社会的普遍信息需求方面起着一种公共服务的作用。
大众传播组织通过各种传播技术方式对信息进行广泛而深远的传播,使得大量的信息被受众所了解,同时充分的提高了社会大众对信息需求方面的满足感,是人们更加全面的体验公共生活、参与公共领域的讨论与认知,这种公共性起到了一种真正为大众社会服务的作用。
2、大众传媒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具有广泛而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涉及到普遍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共生活。
大众传播生产的信息涉及各个方面,在政治上,民众通过大众传媒的信息了解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工作情况,使得政府职能能够更好的在群众面前展现出来,增加的透明度,例如“红头文件”的信息透明,领导人的会面,国家事务的进展过程,都使得公众与政府更加亲密的接触,同时政治信息的传播也有利于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使得民众更加频繁的关注政治关心国家大事,有利于政府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影响政治在群众中的受关注度。
在经济上,随着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使得国内各种国有和公共媒介都取得了颇高的经济效益,从多个方面都对经济造成的有力的影响。
在社会文化方面,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使得参加社会交流更加平凡简单,例如网络媒介,促使了网民的诞生,网络文化的快速发展也改变的社会文化的结构。
论公共新闻理论在我国运作的社会基础

第27卷第5期V ol 127 N o 15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 al o f Chang chun N ormal University (Human 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8年9月Sep 12008论公共新闻理论在我国运作的社会基础刘 聪(长春师范学院人事处,吉林长春 130032)[摘 要]公共新闻在进入我国之后被认为是中国新闻报道的“新希望”,是继民生新闻之后中国电视新闻的第二次革命、中国新闻改革的出路。
公共新闻理论的引入与我国现代的舆论环境及传播环境、传播行为、传播心理有着直接的关系,我国社会及新闻本身的发展均为公共新闻理论在我国的运作提供了基础。
[关键词]新闻;公共新闻理论;媒体[中图分类号]D923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8X (2008)05-0021-04[收稿日期]5[作者简介]刘 聪(),女,辽宁沈阳人,长春师范学院人事处,硕士研究生,从事新闻学及人事管理研究。
“公共新闻”兴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由纽约大学新闻学系主任杰伊罗森(Jay R osen )教授最早提出。
公共新闻理论是对如何使新闻媒体担当起更积极的社会角色的思考结果。
它强调新闻报道者不仅要报道新闻事实,同时更需要以一种组织者的身份介入到公众事务中,组织各种活动,发起公民讨论,从而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使公共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正是由于公共新闻强调新闻媒介和公众之间的紧密联系,突出了新闻媒介在社会协调中的积极作用。
因此,公共新闻在进入我国之后被认为是中国新闻报道的“新希望”,是继民生新闻之后中国电视新闻的第二次革命、中国新闻改革的出路。
然而,公共新闻理论的适时引入并非偶然,我国社会及新闻本身的发展才为公共新闻理论在我国的运作提供了基础。
一、社会发展为公共新闻运作提供了现实条件伴随着我国正在加速进行的现代化建设进程,无论国家还是社会成员都在向新型现代化加速转型。
公共新闻学

公共新闻学公共新闻学(Public Journalism)又称为“公民新闻学”(Civic Journalism),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美国新闻界,尔后波及西方其他国家,但主要的理论和实践展开还是在美国。
在美国,公共新闻学被称为“美国新闻理论的第三次革命”或“第四种新闻理论”。
但公共新闻学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还处于探索阶段,争议颇多,前景难测。
一、公共新闻学的兴起和内涵什么是公共新闻学,这在公共新闻学的发源地美国的新闻学界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难题。
最早提出“公共新闻”理论的学者是纽约大学新闻学系的罗森(Joy Rosen)教授,他认为,“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是报道新闻,新闻记者的工作还应该包含这样的一些内容: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或观看这些问题。
”他还进一步提出,新闻业是健康的公共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被公共生活包围着的人——记者、学者、政治家、市民、左派、右派、中立者……都应该认识到如果市场取代了公共而成为现代社会中唯一的舞台,我们将全部沉沦。
”一直致力于倡导公共新闻学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菲利普·迈耶(Philip Meyer)提出了公共新闻学可以从六个方面进行界定:一是对重新树立公共意识的一种期望。
公共意识是一个社会存在的基础,公共意识的削弱与报纸读者的减少是有因果关系的,实际上报纸和读者都是社会体系中的一部分,对公共生活的不关心,使得读者不再需要报纸。
二是更长时间的注意力的保持。
新闻媒介不能总是从报道一个事件迅速地转向另一个事件,而应该对那些重要的公共问题保持更长时间的关注,直到这些问题的所有方面都为公众了解,并且使他们能够认真地思考和作出决策。
三是深刻地解析引导我们生活的社会系统的愿望。
仅仅关注事件本身的报道,不仅在时间爱你跨度上是受限制的,而且在内容挖掘上也是肤浅的,不能帮助读者看到事实背后所潜在的社会问题的根源。
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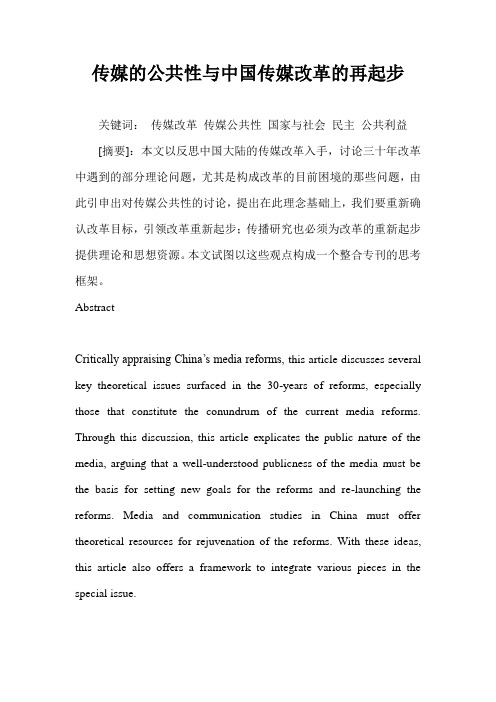
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关键词:传媒改革传媒公共性国家与社会民主公共利益[摘要]:本文以反思中国大陆的传媒改革入手,讨论三十年改革中遇到的部分理论问题,尤其是构成改革的目前困境的那些问题,由此引申出对传媒公共性的讨论,提出在此理念基础上,我们要重新确认改革目标,引领改革重新起步;传播研究也必须为改革的重新起步提供理论和思想资源。
本文试图以这些观点构成一个整合专刊的思考框架。
AbstractCritically appraising China’s media reform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several key theoretical issues surfaced in the 30-years of reforms, especially those that constitute the conundrum of the current media reforms. Through this discussion, this article explicates the public nature of the media, arguing that a well-understood publicness of the media must be the basis for setting new goals for the reforms and re-launching the reform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 must offer theoretical resources for rejuvenation of the reforms. With these ideas, this article also offers a framework to integrate various pieces in the special issue.Keywords: media reforms, the public nature of the media, state and society, democracy, public interests本期专刊的稿件、组织、撰写于汶川大地震之前。
当代中国传媒改革与媒介公共性的变迁

后者强 调大众传 媒在推 进信息公 开方 面 的超 越 时空 的技 术优 势 ,其理 论 渊源 是代 议 制 民主 ,关 注 当今
媒 介化社 会下西 方媒体 与 民主关 系 的 “ 实 然” 面貌 ,具有 明显 的乐 观技术决定 论色彩 。
尽 管不 同学者对传 媒公共 性 的具体 表 述不 同 ,但依 然 可 以归 纳 出一 些普 遍 的原 则 。从 一 般意 义 上 理解 ,传 媒 的公 共性就是 传媒 作 为社会 公 器 ,扮 演 “ 群众 喉舌 ” 的角色 。笔者 以为 ,传媒 公 共性 是 指
第2 O卷
第 3期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Vo 1 . 2 0 NO . 3
2 0 1 3年 6月
J o u r n a l o f Z h e j i a n g Un i v e r s i t y o f Me d i a a n d C o mmu n i c a t i o n s
基金项 目:2 0 1 1 年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研 究青年基金项 目 《 网络公共领域 的理论与实 践研究》 ( 1 1 Y J C 8 6 0 0 5 2 )和2 0 1 0年广东 省哲学 社会科 学 规划项 目 《 网络媒 体的公共性 实践研究》 ( G D 1 0 Y X W0 1 )的研究成 果。
济上的利益 ,倾 听他们 的呼声 ,反映他 们 的疾 苦 ,解 决 他 们 的 困难 ;体 现 人 民 的监督 ,主持 公道 ,伸
张正义 ,扶植 正气 ,打击歪风 ,充分发 扬 民主 ,保 护人 民的 民主 自由 ,使人 民有效 地行 使 当家 作 主 的
社会主人 的权利 等等 。从 以上表 述来 看 ,人 民性 的 内涵 至 少包 括 了公 益性 和批 判性 ,因此 与公 共性
历年中传传播学考研真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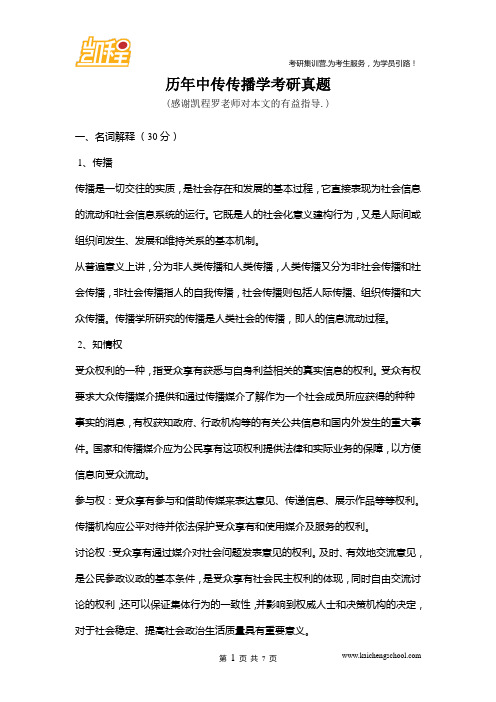
历年中传传播学考研真题(感谢凯程罗老师对本文的有益指导.)一、名词解释(30分)1、传播传播是一切交往的实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过程,它直接表现为社会信息的流动和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
它既是人的社会化意义建构行为,又是人际间或组织间发生、发展和维持关系的基本机制。
从普遍意义上讲,分为非人类传播和人类传播,人类传播又分为非社会传播和社会传播,非社会传播指人的自我传播,社会传播则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
传播学所研究的传播是人类社会的传播,即人的信息流动过程。
2、知情权受众权利的一种,指受众享有获悉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真实信息的权利。
受众有权要求大众传播媒介提供和通过传播媒介了解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应获得的种种事实的消息,有权获知政府、行政机构等的有关公共信息和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
国家和传播媒介应为公民享有这项权利提供法律和实际业务的保障,以方便信息向受众流动。
参与权:受众享有参与和借助传媒来表达意见、传递信息、展示作品等等权利。
传播机构应公平对待并依法保护受众享有和使用媒介及服务的权利。
讨论权:受众享有通过媒介对社会问题发表意见的权利。
及时、有效地交流意见,是公民参政议政的基本条件,是受众享有社会民主权利的体现,同时自由交流讨论的权利,还可以保证集体行为的一致性,并影响到权威人士和决策机构的决定,对于社会稳定、提高社会政治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隐私权:受众享有对个人和公众利益无关的私生活进行保密、不受新闻媒介打扰和干涉的权利。
由于传播媒介的失实报道、不公正报道或评论而使公民名誉、利益受到损害的事件时有发生。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对权利较为完整的成文法保护体系,受众已经有了保护自己免受新闻侵害的法律保障,有了要求损害自己权利的传播机构播发对等等更正、答辩或要求赔偿的权利。
监督权:受众享有对大众传播媒介的运作和传播者的传播行为进行监察和督促的权利。
通常,受众可以根据法律条文、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标准,以写信、打电话、停止订阅、舆论声张灯形式对新闻媒介和新闻传播者进行监督,促使其寻求适合国情、民情的途径,按照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行事。
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

此外,促进公众参与和加强媒体监督也是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途径。 公众的参与能够为媒体提供更广泛的信息来源和监督力量,推动媒体更加公共 议题和履行社会责任。同时,加强媒体监督可以促使媒体更加谨慎地处理信息 传播,确保报道的真实性和公正性。
最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也是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的必要保障。 政府应该逐步完善传媒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为媒体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同 时,政府还应该加强对媒体的监管力度,对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进行严厉 打击,维护媒体的形象和公信力。
三、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
5、促进了新闻行业的规范和发 展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兴起,促进了新闻行业的规范和发展。它为新闻媒体建立 了一套标准和规范,使得新闻报道更加客观、公正、准确和有价值。它也为受 众提供了更加可靠和有用的信息,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6、对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产 生了影响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不仅对新闻行业产生了影响,也对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产 生了影响。它使得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决策更加透明和公正,也使得其他领域 更加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
四、结语
公共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实践是新闻界需要深入探索的重要课题。它不仅要 求新闻工作者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还要求媒体加强独立性和自主 性建设,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公众的参与和监督以及政府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和政策措施也是促
进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发展的必要保障。只有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公共新闻专 业主义才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与实践。
总之,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追求事实真相、传播有价值的信息和促进社会 进步的理念。它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实践,并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和启示。然而,在实践中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和困难,如如何保持报道 的客观性和独立性
我国新闻媒体公共性之新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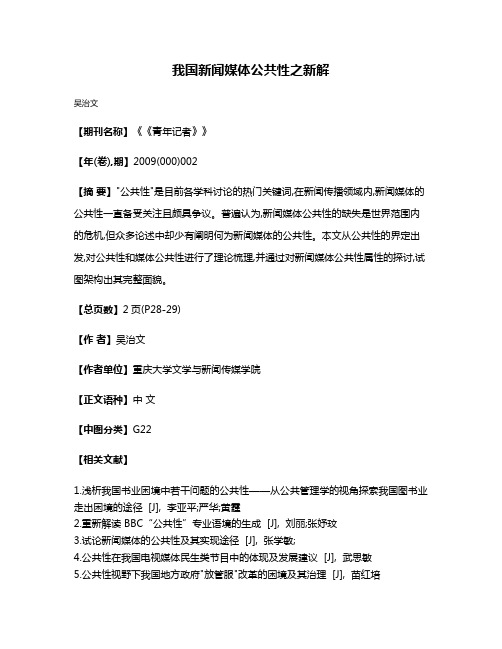
我国新闻媒体公共性之新解
吴治文
【期刊名称】《《青年记者》》
【年(卷),期】2009(000)002
【摘要】"公共性"是目前各学科讨论的热门关键词,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新闻媒体的公共性一直备受关注且颇具争议。
普遍认为,新闻媒体公共性的缺失是世界范围内的危机,但众多论述中却少有阐明何为新闻媒体的公共性。
本文从公共性的界定出发,对公共性和媒体公共性进行了理论梳理,并通过对新闻媒体公共性属性的探讨,试图架构出其完整面貌。
【总页数】2页(P28-29)
【作者】吴治文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2
【相关文献】
1.浅析我国书业困境中若干问题的公共性——从公共管理学的视角探索我国图书业走出困境的途径 [J], 李亚平;严华;黄霆
2.重新解读BBC“公共性”专业语境的生成 [J], 刘丽;张妤玟
3.试论新闻媒体的公共性及其实现途径 [J], 张学敏;
4.公共性在我国电视媒体民生类节目中的体现及发展建议 [J], 武思敏
5.公共性视野下我国地方政府"放管服"改革的困境及其治理 [J], 苗红培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作者:潘忠党单位: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来源:《传播与社会学刊》关键词:传媒改革传媒公共性国家与社会民主公共利益本期专刊的稿件、组织、撰写于汶川大地震之前。
作为学者,除以自己的方式,与全中国人民一道,共同赈灾、救灾外,我们也看到一个内涵丰厚的个案,即以中国传媒为演绎平台的全民抗灾,已成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一个政府、传媒、民众共同参与民族和国家建设(nation and state building)的热点时刻。
中国传媒在抗震救灾报导中的表现,可以说是传媒改革三十年成就和局限的一次大检阅。
以此为个案,系统考察中国新闻实践、新闻再现及其话语构成,以及新闻与公共议题的建构、公共政策的制订及实施等之间的关系,并进而考察中国传媒体制、市场机制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传媒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等,应当成为今后研究中国传媒改革的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这些研究议题,渗透在本期专刊的各个部分。
专刊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实践为考察对象,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学界专家应邀展开的笔谈,二是特邀专稿(三篇),三是经公开征稿、匿名评审所选择的研究论文(四篇)。
三部分的侧重有所不同。
专家的笔谈,力求言简意赅,意在比较广泛地反映学界对传媒改革三十年一些重要问题的反思;特邀专稿每篇针对传媒改革的某方面或现象,以经验考察为基础,勾勒历史的轨迹,并展开理论分析;公开征稿的研究论文各自就改革过程中的某一现象,以理论为指导,展开经验的研究。
综合起来,我们力图在有限的篇幅内,使专刊具有思想和学术的结合,历史和现实分析的结合,理论阐述和经验考察的结合。
这样的目标实现了多少,有待同行们来判断。
作为专刊的编辑,我在此对专刊整体的考察对象──传媒改革三十年──作一概述,并讨论这三十年的改革或触碰、或回避、或提出的部分理论问题,尤其是体制改革中的困境,传媒及其话语的公共性,以及传媒改革研究的思想性和学术性等问题。
这些都是大范畴的问题,其中实然和应然的维度相交叉,为求比较清晰的解答,需要长期、系统的研究积累和各种观点的相互交锋。
我在这里只能作一简单的概述,目的是在宏观的层面,一为串连专刊的各篇论文,二为今后的传媒研究勾勒一个提出研究问题的思路。
改革开放与传媒改革考察传媒改革,一个基本的现实和逻辑起点是,新闻和传播领域的改革,与经济体制、法制体制和行政治理等的改革,以及与之相伴的中国社会变迁相互交织、相互构成。
首先,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改革开放路线的确定,有此前在传媒上展开的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作铺垫。
这个路线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也都通过传媒得到大力宣扬和推广。
因此,传媒是中国改革的舆论及话语的平台和推行工具。
其次,与其他领域的改革开放几乎同步的是传媒管理经营和新闻实践领域的改革。
在经营管理领域,1978年中央政府开始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原则,赋予了传媒单位一定的经营自主权;1979年中宣部肯定了传媒恢复商业广告的做法,开始了中国广告业与传媒经济的发展;1996年经中宣部同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广州日报》组建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的试点,开始了经由报业集团化、广电媒体集团化,再到包括传媒在内的文化产业化这一演变历程。
在新闻实践领域,改变新闻语态(如反对假大空)、将新闻宣传的重心转向服务于经济建设、重启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新闻教育等,都起步于1978年前后。
自此之后,新闻的“语态”(孙玉胜,2003)和新闻实践的不断演变,与其他领域的改革交相呼应,导致了新闻传媒的实践话语和新闻传媒所呈现的话语逐渐向走出全能国家的场域演变。
因此,传媒的变迁又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内容和轨迹都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契合。
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传媒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产业,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镇。
有研究者预测,2008年,中国传媒产业──包括报刊、图书、广播、电视、影像、移动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技术平台及服务──总产值将达5,440亿元(崔保国等,2008)(编按: 此项参考数据于参考文献中缺漏, 请作者于该部分提供)。
业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出版报纸1,938种,广告经营额达312.6亿元;全国有广播电台267座,电视台296座,广播电视广告收入为527亿元(孙正一、柳婷婷,2007)。
截至2007年底,中国有网民2.1亿,域名总数1,193.1万个,网站150.4万个;全国有4亿手机用户,12.6%的用户通过手机上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8)。
2007年我国具备运营能力的行业网站达2,300家,总营业收入147亿元,从业人数超过19万人(徐晓巍,2008)。
2006中国互联网用户个人互联网消费市场总规模约为2,767.46亿元人民币,网络广告(不含搜索引擎在内)、网络游戏两个领域2006年度的市场营收规模分别达到了49.8和59.6 亿元(中国互联网协会,2007)。
这些数字描述了产业规模的轮廓。
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可说是日新月异,以至于搜集、描述、分析这类数据,并以此显示传媒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成为一个热门的“产业描述和对策分析”行业。
[1]这些围绕基础经济指数而展开的实践活动,一方面其本身日益成为发展中的传媒产业的一个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也在日益以一种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基本框架,[2]建构传媒研究的话语体系,并以此常识化这种意识形态。
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对发展规模和趋势的分析,预设了源自西方的全球经济的“统一”或“规范”指标之合理性,并将衡量传媒发展的政策和既定目标,锁定在是否快速和有效地发展产业规模这个基点上。
其次,反映产业规模的数据并不能显示媒介资源占有的人均水平、媒介资源在群体中的分布形态、内容制作和流通体制等方面牵涉到的公正、自由、开放等基本原则的问题。
缺乏对这些问题及其背后的民主原则的关注,使得以经济指标为核心标杆的研究缺乏批判性,无法揭示制度、伦理、改革目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缺乏通过分析改革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张力而对改革历程的理解,无力批判改革过程中政治权力与垄断资本相勾结的体制弊病、市场对媒体公共性的侵蚀、表达自由和舆论监督的苍白、数码沟(digital divide)对两极分化的深化和扩大,等等。
传媒体制改革中的困境经济指标之外,是亟需深入探讨的传媒体制改革目前面临的困境,即三十年的传媒改革如何得以展开,今后又何去何从?本期刊载的文字中,有不少涉及这个困境。
这个困境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构成:第一,中国的改革是在不变中求变,以变来实现不变。
具体而言,就是如陈力丹(本期,页20-23)所指出的,“党管媒体”的原则不可触动,它不仅身处改革范畴之外,而且是确定改革措施的基石;或如赵月枝(本期,页25)所指出的,中国的“传媒体制改革实际上是在无意或无法抛弃国家社会主义遗产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策略”。
在这样严格的前设条件下,改革的展开显示出体制变迁中高度政治化的、临场发挥式的“路径依赖”和“有限创新”特征,呈现出气候多变、步履蹒跚的表象(潘忠党,2007)。
改革的内核,因此即是守成。
那么,经过三十年,在这前设条件的框框内,还有进一步改革的空间吗?第二,中国的改革是执政党运用其组织力量和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discursive hegemony)以及它所掌握的国家机器所展开的历史变迁项目,改革的进程是党的利益、国家利益、市场内生发的集团或阶级利益等相互间博弈、协调的政治过程,其结构呈现出国家法团主义(state corporatism)的形态,即在以表述和实现公共利益为名的国家这个公共政策制订与执行的场域,各利益团体──包括执政党──相互博弈,达成互依和互益的交换格局(潘忠党,2007)。
更具体来说,国有传媒成为依赖党-国政治权威庇护而在市场运作的实体(Lee, He, Huang, 2007),并由此获得所谓双重属性,受制于不同的逻辑(黄升民等,本期,页49-70)。
那么,改革究竟是为形成、体现并最大限度地保护公共利益,还是为维护国内外垄断资本以及与之相依存的政权的利益?第三,与这些体制及其演变的结构场景相应的是,改革缺乏明确的目标,更准确地说是缺乏将公共利益、公平、公正等民主基本价值准则作为改革的起点,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改革目标的广泛、开放、容纳、自由和理性的讨论。
不同的改革推进者或实践者在不同场合或领域,会依据国家社会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赵月枝,本期,页25-27)开出不同的目标处方,结果是:在传媒改革中,首先,宪法的权威地位无法确立(陈力丹,本期,页20-23),言论自由面临困境(吴飞,本期,页29-31),宪法规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无法通过新闻或传播法得到实行(孙旭培,本期,页27-29;魏永征,本期,页31-33),而必须依赖执政党表述在其”权威档”中(李良荣,本期,页23-24);其次,传媒无法形成真正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专业主义模式运作(陆晔、潘忠党,2002)。
因此,改革要继续并深入,如赵月枝(本期,页25-27)所提出的,就必须以”国内和国际传播的民主化”作为未来方向。
综上,作为一个历史的项目(historical project),中国的改革开放旨在重建一党独政的国家,传媒改革是这个项目的构成部分,也是实现这个项目的核心举措之一。
经过三十年,若以改革前的集权党-国(totalitarian party-state)下的“命令型”传播体制(Lee, 1990)为参照,那么,确实,社会的场域得到了很大拓展,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功能有了很大发挥。
本期发表的论文中,孙玮(页71-92)对大众报纸的研究、雷蔚真和陆亨(页143-166)对“舆论监督”的探讨、郭中实和陆晔(页167-191)对报告文学演变中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论述,都为这样的总体概括提出了经验的支持。
但是,同样具有历史现实性的概括是,尽管有“公共利益”作为媒介话语的正当化资源之一,有公民主体性在媒介话语中的一定表述,采用国家-社会的视角所看到的社会之成长和公共领域之发端,都是市场逻辑所不经意催生的成果,并非是以社会和体制的民主化为基本出发点而设计的改革目标之实现;林芬和赵鼎新(页93-119)所显示的中国传媒对社会运动的亲和倾向,更只是偶有所现,虽然这呈现是理解中国改革中传媒与社会变迁的重要方面,但它并未改变传媒仍然是党的喉舌的体制定位(童兵,1994)。
也就是说,三十年的传媒改革,释放了巨大的发展能量,建设了规模庞大的传媒产业,并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社会这二元结构中社会这一极的成长,推动了对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的期待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部分话语实践。
这是历史的进步,是市场经济带来解放力量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