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在文莱的地位 [华人独特饮食的由来及对文化的影响]
文莱研究报告

文莱研究报告
文莱是位于东南亚的一个国家,位于亚洲的马来群岛上,北临南中国海。
以下是关于文莱的研究报告:
1.地理位置:文莱位于婆罗洲岛的北岸,与马来西亚的沙巴州相邻,东临菲律宾。
河流和淡水湖泊在文莱非常常见,其中最著名的是巴起尼河。
2.经济特点:文莱是东南亚富裕国家之一,主要依靠石油和天然气输出为主的经济。
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占文莱国内生产总值的大部分。
该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福利,使其民众享有高水平的生活。
3.政治形势:文莱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国家元首是苏丹,具有广泛的行政权力。
政府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致力于提高文莱的国际声誉。
4.文化特色:文莱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由于其悠久的历史,受到马来、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邻国的影响。
伊斯兰教是文莱的官方宗教,因此该国有许多华丽的清真寺。
文莱也以其独特的传统和文化庆祝活动而闻名。
5.教育系统:文莱的教育水平较高,教育资源相对充足。
政府非常重视教育,并为学生提供免费教育,包括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文莱大学是该国最主要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
6.旅游业:尽管文莱的旅游业不如其他东南亚国家发达,但该
国拥有一些独特的旅游资源。
这些资源包括美丽的海滩、丛林和国家公园等,吸引了一部分自然爱好者和生态旅游者。
总结:文莱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政府积极发展经济并提供社会福利。
伊斯兰教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使其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
尽管旅游业发展尚需努力,但文莱在自然景观方面的资源丰富,为旅游者提供了一些独特的体验。
文莱PPT

Brunei Darussalam
一、文莱概况(2) 文莱概况(
首都
斯里巴加湾市 ,位于文莱-穆阿拉 位于文莱- 区,面积16平方公里,人口约6万。 面积16平方公里 人口约6 平方公里, 原称文莱市, 原称文莱市,从十七世纪起即成为 文莱首都,1970年10月 日改为现名。 文莱首都,1970年10月4日改为现名。
Brunei Darussalam
三、饮食文化(3) 饮食文化(
小吃
文莱有很多特色小吃,但他们 文莱有很多特色小吃, 最喜欢的是一些油炸食品, 最喜欢的是一些油炸食品,喜欢黄 奶酪等高热量食品。 油、奶酪等高热量食品。所以如果 去到文莱的夜市, 去到文莱的夜市,你就可以看到好 多烧烤食品, 多烧烤食品,夜市周围到处弥漫着 烟气, 烟气,在中国会严令禁止的烧烤在 这里可是大大的盛行呢! 这里可是大大的盛行呢!
文莱人都爱逛夜市
Brunei Darussalam
四、旅游住宿(1) 旅游住宿(
文莱是个很小的国家,领土总面积约5765平方公里,在世界领土面积排行榜上位居172名, 平方公里, 文莱是个很小的国家,领土总面积约5765平方公里 在世界领土面积排行榜上位居172名 因此住宿的可选择性较弱。文莱的住宿酒店大多是价格昂贵的高级酒店, 因此住宿的可选择性较弱。文莱的住宿酒店大多是价格昂贵的高级酒店,当然也有一些适合旅 游的旅客们喜欢光顾的小型的旅馆。 游的旅客们喜欢光顾的小型的旅馆。
Brunei Darussalam
三、饮食文化(4) 饮食文化(
椰浆饭
椰浆饭本是印尼的宫廷菜。这道菜 椰浆饭本是印尼的宫廷菜。 以前只有在日惹王宫里才能享受到, 以前只有在日惹王宫里才能享受到,是 王室贵族们非常喜欢的菜肴。 王室贵族们非常喜欢的菜肴。 椰浆饭看起来和普通的米饭差不多, 椰浆饭看起来和普通的米饭差不多, 但实际上却是很不一样。 但实际上却是很不一样。它的做法是将 白米饭用椰浆调味后, 白米饭用椰浆调味后,再加入各种名贵 的香料, 的香料,这样煮出来的椰浆饭口感十分 鲜美。 鲜美。 此外,在吃椰浆饭的同时, 此外,在吃椰浆饭的同时,还需要 搭配几种配菜,比如红烧肉、 搭配几种配菜,比如红烧肉、调味炸鸡 和煮蛋等等。美味当前, 和煮蛋等等。美味当前,再来上一些用 印尼特有香料调制出的饮料, 印尼特有香料调制出的饮料,曾经王室 的生活也不过如此了。 的生活也不过如此了。而现在文莱的人 们把它当做是早餐, 们把它当做是早餐,就可以看出文莱的 人们是多么的富裕了。 人们是多么的富裕了。
《东南亚汶莱》课件

速发展,包括餐饮、零售、金融等。
投资环境
投资政策
汶莱政府制定了多项投资优惠政策,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前来投资 。
基础设施建设
汶莱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包括公路、铁路、航 空和水路等,为投资者提供便利的交通条件。
人力资源
汶莱拥有一定数量的高素质人力资源,为投资者提供必要的人才支 持。
05
社会问题与挑战
教育问题
1 2 3
教育资源不足
汶莱的教育资源相对有限,学校设施和师资力量 无法满足需求,导致许多孩子无法接受优质教育 。
教育公平问题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差异,一些孩子无法获得平 等的教育机会,贫困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受到忽视 。
教育观念落后
传统的教育观念强调应试教育,忽视了学生的创 造性和实践能力培养,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经济结构调整
为了降低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汶莱政府正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 ,鼓励发展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
主要产业
石油和天然气产业
01
汶莱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是主要出口商品和经济支
柱。
旅游业
02
汶莱政府大力推动旅游业发展,吸引游客前来参观历史遗迹和
自然风光。
服务业
03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汶莱服务业也得到了快
欧洲的殖民统治
16世纪起,东南亚地区相 继受到欧洲列强的殖民统 治。
反抗与独立
东南亚各国在二战后纷纷 独立,摆脱了殖民统治。
冷战的影响
在冷战期间,东南亚成为 了东西方阵营争夺的焦点 。
现代历史
经济改革和开放
金融危机
20世纪80年代起,东南亚各国开始实 行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
独特的东南亚饮食文化

独特的东南亚饮食文化东南亚,位于亚洲东南部,包括中南半岛以及马来群岛的大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才出现的一个新的地区名称。
该地区共有11个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东帝汶(2002年5月20日,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正式成立)。
东南亚因其独特的地理、气候、历史环境,造就了其丰富多彩的东南亚文化。
既吸取了东西方文化中的特色,又融合本地人文特色产生了独特的东南亚文化。
其中,东南亚在饮食方面的独特最为明显。
东南亚善于将外来饮食本土化,混杂各地口味和食材,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
因为地理的关系,以前中东,印度和中国来往经商的船只都必须经过马六甲海峡,东南亚各国成为了必经之路,也自然成了交汇站,各国商人都会在这里停留,甚至永居这里。
由于历史原因,这个区域也曾经是到西方各国的殖民地。
长期受法国、荷兰等国的文化影响。
另一方面。
由于华人的大量聚居,受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到了现代东南亚又是我国旅游人士旅游频率最高的地区,东南亚不但面积广阔,而且民族也比较复杂,风俗禁忌大多与当地宗教有关。
佛教、回教、印度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对亚洲各国的政治、文化或多或少都有影响。
因为如此,东南亚国家受了来自西方,中东,印度和中国的饮食文化的重大影响。
但也因为食材和本土文化的关系,与来自原产国家的饮食又有所不同,因此东南亚菜中,特别注意汇集了东西方做法,配制成适合当地饮食习惯的菜式,使其更具地方特色,形成了汇合东西方文化和当地习俗融为一体的独具魅力的东南亚饮食文化。
东南亚饮食文化:东南亚菜肴多取以天然可食植物为原料,烹调出色、香、味型具佳的菜系。
如越南菜则有美容保健菜肴之美称。
新马泰、印尼等国菜肴则多配以当地盛产的丰富的椰子、香茅、肉桂、豆蔻、丁香等香料植物为配料,使其菜肴色味浓郁,风味独特。
东南亚各国的饮食文化也因为区域的关系都略有不同,比较重口味,主要以酸,辣,烧烤和煎炸为主,口味较重。
美食文化了解世界各地的美食历史和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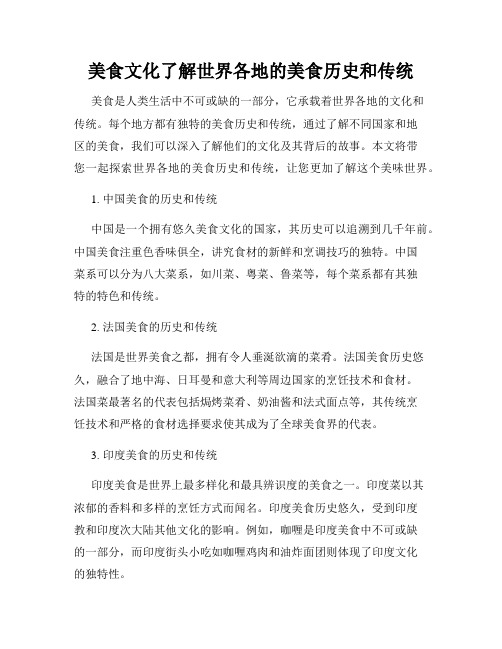
美食文化了解世界各地的美食历史和传统美食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承载着世界各地的文化和传统。
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美食历史和传统,通过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美食,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他们的文化及其背后的故事。
本文将带您一起探索世界各地的美食历史和传统,让您更加了解这个美味世界。
1. 中国美食的历史和传统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美食文化的国家,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中国美食注重色香味俱全,讲究食材的新鲜和烹调技巧的独特。
中国菜系可以分为八大菜系,如川菜、粤菜、鲁菜等,每个菜系都有其独特的特色和传统。
2. 法国美食的历史和传统法国是世界美食之都,拥有令人垂涎欲滴的菜肴。
法国美食历史悠久,融合了地中海、日耳曼和意大利等周边国家的烹饪技术和食材。
法国菜最著名的代表包括焗烤菜肴、奶油酱和法式面点等,其传统烹饪技术和严格的食材选择要求使其成为了全球美食界的代表。
3. 印度美食的历史和传统印度美食是世界上最多样化和最具辨识度的美食之一。
印度菜以其浓郁的香料和多样的烹饪方式而闻名。
印度美食历史悠久,受到印度教和印度次大陆其他文化的影响。
例如,咖喱是印度美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印度街头小吃如咖喱鸡肉和油炸面团则体现了印度文化的独特性。
4. 日本美食的历史和传统日本美食以其简约、精致和健康而闻名于世。
日本美食注重食材的新鲜和烹调的精细,以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
日本料理包括寿司、刺身、烧烤和炖菜等,其中寿司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之一。
日本美食历史悠久,其传统烹调技术和仪式感使其成为了全球美食爱好者的追捧对象。
5. 意大利美食的历史和传统意大利美食是深受全球喜爱的美食之一,它以其简单和地道的口味而著称。
意大利美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如披萨和面食等都是意大利美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意大利人对于食材的选择和烹调方式非常讲究,他们崇尚慢食文化,注重细细品味食物的美味。
通过了解世界各地的美食历史和传统,我们可以更好地欣赏和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
饮食偏好礼仪:不同地域的独特饮食偏好

饮食偏好礼仪:不同地域的独特饮食偏好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饮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每一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饮食文化和偏好。
我们所处的地域和文化背景会影响我们对食物的偏好和对饮食礼仪的看法。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不同地域的独特饮食偏好,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饮食礼仪。
1. 东亚地区:米饭与筷子的重要性东亚地区,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米饭是主食的核心。
这些地区的人们通常以米饭为主食,配以各种菜肴。
与之相伴的是筷子的使用。
在东亚文化中,筷子被视为一种符号,代表着食物的尊重和对饮食礼仪的重视。
1.1 中国的饮食偏好和礼仪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这也反映在其饮食文化中。
中国人经常将米饭作为主食,配以多样化的菜肴,如炒菜、炖汤等。
一顿传统的中国饭菜通常包括主菜、配菜和汤。
在中国饮食文化中,人们强调的是“色、香、味”,即食物外观的美感、香气的诱人和口味的丰富。
中国人认为食物的味道和外观是同样重要的。
在中国,饮食礼仪也非常重要。
例如,在家庭聚餐中,人们经常按照“长辈先用”的原则开始就餐。
另外,尊重食物也是中国饮食礼仪的一部分。
人们通常会慢慢地品尝食物,不会过快地吃完。
此外,礼貌地夹取食物也是中国饮食礼仪的一部分。
使用筷子时,人们应该夹取适合一口大小的食物,不要使筷子直接接触自己的嘴巴。
日本的饮食文化也非常独特。
日本人通常以米饭和鱼类为主食。
传统的日本餐通常包括饭、鱼、蔬菜和豆腐等。
日本人认为食物的新鲜和制作过程的精细是非常重要的。
在日本,人们在餐桌上使用的是筷子而不是刀叉。
与中国相似,日本人非常重视饮食礼仪。
在用完餐巾后,人们会将餐巾折叠成一个矩形并放在旁边。
在使用筷子时,人们应该持筷子的一端,而不是中间或末端。
此外,将筷子插在饭中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另外,人们在饮食时应尽量避免发出声音。
1.3 韩国的饮食偏好和礼仪韩国的饮食文化与中国和日本有些相似,但也有其独特之处。
韩国人通常以米饭和辣椒为主食。
他们的餐桌上通常摆满了各种小菜,以增加食物的多样性。
文莱是个怎样的国家?10个知识点,带你走进真实文莱人的生活

文莱是个怎样的国家?10个知识点,带你走进真实文莱人的生活文莱人口只有45万左右,登记的汽车却由差不多30万辆!国虽小,却是世界上汽车保有量最高的国家。
文莱王室更是夸张!不仅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皇宫,还在皇宫放了7000多辆顶级豪车,其中600多辆都是劳斯莱斯。
文莱王室就可以开个豪车展。
文莱女孩不仅温柔,漂亮,结婚还不要彩礼,真是让一群国内男人感动到哭,想立马飞过去抱得美人归。
文莱的空姐最让人意外的是:富得流油的文莱招待客人用的顶级美食,你以为可能是龙虾鲍鱼,但是不好意思,竟然会是鸡屁股!这是要多大的勇气才能接受,文莱这一种这么有味道的热情呢?文莱人这么有钱,生活又幸福,国民不仅有免费教育还有免费医疗,但是被粉丝叫做文莱王子的明星吴尊,却要举家定居到中国,这是为什么呢?今天用10个知识点,带大家来看一下富的流油的文莱到底是个怎样的国家?第一、文莱的地理概况文莱的全称叫文莱达鲁萨兰国,是亚洲东南部的国家。
文莱,位于加里曼丹岛西北部,北边是我们的南海,东南西三面和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州接壤,而且国土直接被马来西亚分成了两个不相连的片区。
文莱国土面积一共就只有5765平方公里,而被单独出去的那一小块国土叫淡布隆区,面积1305平方公里。
文莱主要国土的那一大半分成了三个片区,其实文莱的区,当地人也称之为县,文莱国内分区,乡,村三级。
纠正一下:国内一直写的名字是文莱,其实文莱应该是汶莱才对,文莱国内的广告牌都是这个汶…将错就错吧,就感觉是本身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这错的人多了,错的就成了正牌了!文莱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国土面积只有5765平方公里。
有多小?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这个面积其实比我们的上海市的土地面积都还要小。
上海的土地面积是6340.5平方千米,比文莱大了不少呢,差不多大了个新加坡!文莱的海岸线长约有162公里,周围有33个岛屿。
国内还有四条河流经过文莱,分别是文莱河,都东河,马来奕河,淡布隆河。
亚洲最富小国,面积相当于5个香港,视华人为开国始祖

亚洲最富⼩国,⾯积相当于5个⾹港,视华⼈为开国始祖⽂莱,亚洲东南部国家,位于海南岛东南部1500公⾥加⾥曼丹岛北部,北⾯临海,剩余三⾯被马来西亚⾯积最⼤的砂拉越州包围,其国家主体被分隔成不相连两部分,⾯积5765平⽅公⾥,相当于5个⾹港⼤⼩,⼈⼝约42万。
⽂莱最初是英国在东南亚额殖民地,⼆战期间曾短暂被⽇本占领。
⽇本战败之后,⽂莱再次成为英国保护国。
这⼀次英控制期间,⽂莱享有很⼤程度上的⾃治,除了外交、国防、治安,剩余事务均掌握在⽂莱⼿中。
英控制期间,曾试图将⽂莱并⼊马来西亚,遭到⽂莱的武装反抗。
最然⽂莱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在这次事件之后,⽂莱获得了更多的⾃治权,并且和英国之间达成独⽴约定。
⽂莱是个临海国家,⾃然资源丰富,虽然是个⼩国,却拥有数量不少的⽯油和天然⽓资源,储备量在东南亚排名第2位,仅次于印尼。
除此之外,这⾥环境优美,吸引了众多游客来这⾥旅游。
得天独厚的⾃然优势让⽂莱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2016年的时候,⼈均GDP⾼达26939美元,位居亚洲地区⾸位。
作为中国的海上邻国,⽂莱和中国之间有很深的历史渊源。
早在南北朝时期,⽂莱皇帝就派使⾂访问中国,郑和下西洋时期也曾经访问过⽂莱。
⽂莱受中国⽂化影响深远,⽂莱更是将中国⼈黄森屏视为开国始祖。
黄森屏,元末明初将领,因其抗倭有功,明太祖朱元璋特为其赐名并派他出使婆罗洲(加⾥曼丹岛)。
黄森屏从军出⾝,骁勇善战,很快就在婆罗洲建⽴起独⽴的华⼈政权,声名在外。
当时的⽂莱被称为渤泥国,是个国⼒微弱的⼩国。
为了让国家强⼤不受外辱,渤泥国苏丹特将⼥⼉嫁给黄森屏,以寻求华⼈⼒量的帮助。
在黄森屏的带领下新的⽂莱国建⽴,⽽他也因此成为⽂莱国家创始⼈之⼀,受到⽂莱皇室的爱戴。
海外华人的社会地位和历史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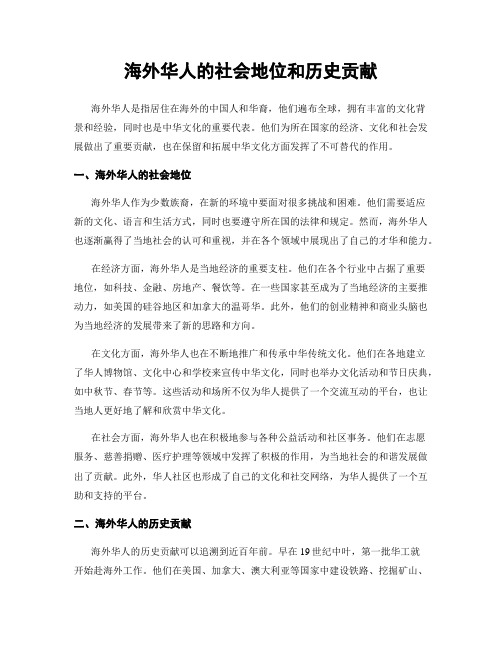
海外华人的社会地位和历史贡献海外华人是指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和华裔,他们遍布全球,拥有丰富的文化背景和经验,同时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代表。
他们为所在国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在保留和拓展中华文化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海外华人的社会地位海外华人作为少数族裔,在新的环境中要面对很多挑战和困难。
他们需要适应新的文化、语言和生活方式,同时也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和规定。
然而,海外华人也逐渐赢得了当地社会的认可和重视,并在各个领域中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在经济方面,海外华人是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
他们在各个行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如科技、金融、房地产、餐饮等。
在一些国家甚至成为了当地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如美国的硅谷地区和加拿大的温哥华。
此外,他们的创业精神和商业头脑也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在文化方面,海外华人也在不断地推广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他们在各地建立了华人博物馆、文化中心和学校来宣传中华文化,同时也举办文化活动和节日庆典,如中秋节、春节等。
这些活动和场所不仅为华人提供了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也让当地人更好地了解和欣赏中华文化。
在社会方面,海外华人也在积极地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和社区事务。
他们在志愿服务、慈善捐赠、医疗护理等领域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当地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了贡献。
此外,华人社区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社交网络,为华人提供了一个互助和支持的平台。
二、海外华人的历史贡献海外华人的历史贡献可以追溯到近百年前。
早在19世纪中叶,第一批华工就开始赴海外工作。
他们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中建设铁路、挖掘矿山、开垦土地等,为当地的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同时,他们也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外华人的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也开始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政治方面,海外华人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到当地政治生活中。
他们积极投票、参选和支持候选人,为华人争取政治代表权和福利待遇。
第十二讲 文莱的民族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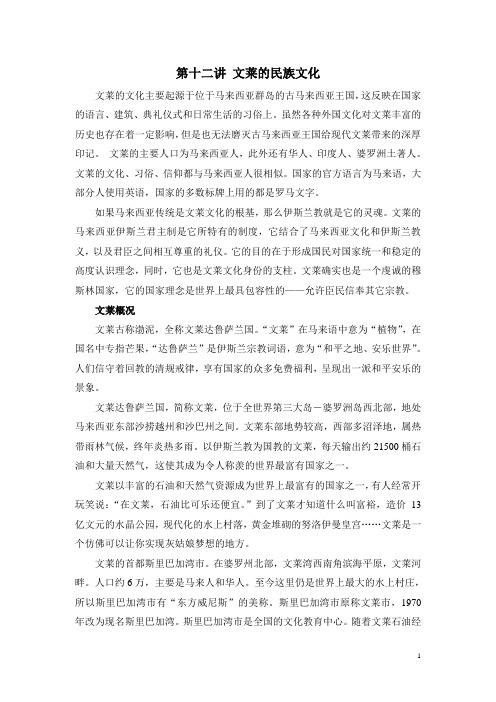
第十二讲文莱的民族文化文莱的文化主要起源于位于马来西亚群岛的古马来西亚王国,这反映在国家的语言、建筑、典礼仪式和日常生活的习俗上。
虽然各种外国文化对文莱丰富的历史也存在着一定影响,但是也无法磨灭古马来西亚王国给现代文莱带来的深厚印记。
文莱的主要人口为马来西亚人,此外还有华人、印度人、婆罗洲土著人。
文莱的文化、习俗、信仰都与马来西亚人很相似。
国家的官方语言为马来语,大部分人使用英语,国家的多数标牌上用的都是罗马文字。
如果马来西亚传统是文莱文化的根基,那么伊斯兰教就是它的灵魂。
文莱的马来西亚伊斯兰君主制是它所特有的制度,它结合了马来西亚文化和伊斯兰教义,以及君臣之间相互尊重的礼仪。
它的目的在于形成国民对国家统一和稳定的高度认识理念,同时,它也是文莱文化身份的支柱。
文莱确实也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国家,它的国家理念是世界上最具包容性的——允许臣民信奉其它宗教。
文莱概况文莱古称渤泥,全称文莱达鲁萨兰国。
“文莱”在马来语中意为“植物”,在国名中专指芒果,“达鲁萨兰”是伊斯兰宗教词语,意为“和平之地、安乐世界”。
人们信守着回教的清规戒律,享有国家的众多免费福利,呈现出一派和平安乐的景象。
文莱达鲁萨兰国,简称文莱,位于全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岛西北部,地处马来西亚东部沙捞越州和沙巴州之间。
文莱东部地势较高,西部多沼泽地,属热带雨林气候,终年炎热多雨。
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文莱,每天输出约21500桶石油和大量天然气,这使其成为令人称羡的世界最富有国家之一。
文莱以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有人经常开玩笑说:“在文莱,石油比可乐还便宜。
”到了文莱才知道什么叫富裕,造价13亿文元的水晶公园,现代化的水上村落,黄金堆砌的努洛伊曼皇宫……文莱是一个仿佛可以让你实现灰姑娘梦想的地方。
文莱的首都斯里巴加湾市。
在婆罗州北部,文莱湾西南角滨海平原,文莱河畔。
人口约6万,主要是马来人和华人。
至今这里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上村庄,所以斯里巴加湾市有“东方威尼斯”的美称。
由华人建国的文莱,和中国有啥关系?为何王室富可敌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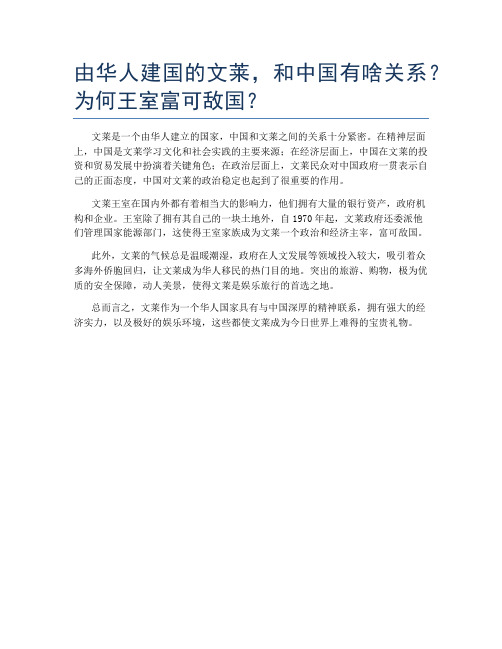
由华人建国的文莱,和中国有啥关系?为何王室富可敌国?
文莱是一个由华人建立的国家,中国和文莱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
在精神层面
上,中国是文莱学习文化和社会实践的主要来源;在经济层面上,中国在文莱的投
资和贸易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在政治层面上,文莱民众对中国政府一贯表示自
己的正面态度,中国对文莱的政治稳定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文莱王室在国内外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拥有大量的银行资产,政府机
构和企业。
王室除了拥有其自己的一块土地外,自1970年起,文莱政府还委派他
们管理国家能源部门,这使得王室家族成为文莱一个政治和经济主宰,富可敌国。
此外,文莱的气候总是温暖潮湿,政府在人文发展等领域投入较大,吸引着众
多海外侨胞回归,让文莱成为华人移民的热门目的地。
突出的旅游、购物,极为优
质的安全保障,动人美景,使得文莱是娱乐旅行的首选之地。
总而言之,文莱作为一个华人国家具有与中国深厚的精神联系,拥有强大的经
济实力,以及极好的娱乐环境,这些都使文莱成为今日世界上难得的宝贵礼物。
伊斯兰化和君主制度下文莱华人的社会地位

华人居住在首都的有22600人,居住在马来奕县的 有17700人。[4]
如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华人一样,迄今文莱华
网络的密切联系,积极参与新兴产业的开发。政府 对全球化下华族在文莱经济中的作用也予以高度评 价。文莱工业暨主要资源部长丕显阿都拉曼在 2001年出席第34届斯里巴加湾市中华商会理事会 上演讲时说,“在面对全球化及自由贸易趋势上, 商会扮演着领导的角色,作为一个已经拥有和外国 伙伴开展合资商业网的族群,华商在具备优越先机 下,有必要发展成为推动更有竞争能力及权威性的
坡。林德甫1927年从金门南渡文莱,战后独资经 营美成号。1962年,林德甫在新加坡创设友利行,
一个得到政府承认的原住民族(列14种),可以自 动取得公民身份;凡1949年1月28日以后出生于
成为杨协成食品罐头及外国名牌啤酒文莱区的总代 理;1970年,他在台湾创设高汶贸易股份有限公 司。同年,在香港设立美成船务有限公司,业务蒸 蒸日上。1958年,文莱前苏丹奥玛里赛弗丁殿下 册封他为华人甲必丹,授权他代表政府处理华人事
筑业和电子电器业领域有一定优势,规模在数万至 数百万美元的产业有170余家。其中,电子电器业 有41家,资本额占当地份额的40%。华商从事专 营贸易的公司有50家,业务遍及进出口、外商代 理、批发及零售等,平均资本为10万美元,约占 当地份额的10%。美成号甲必丹林德甫为此行业
权、穆斯林化、君主制度”,因此,华侨华人在法 律地位上就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但早在文莱尚未 获得自治权时期,华人就已占文莱总人口的20— 25%。华人在文莱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是不可或 缺的角色,尤其在商贸和石油技工领域,其主导地 位是其他族群难以取代的。因此,华人的社会地位
中餐在国际饮食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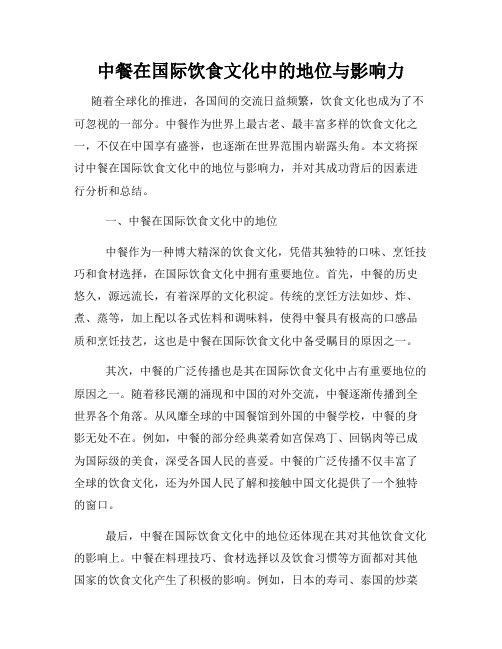
中餐在国际饮食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力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各国间的交流日益频繁,饮食文化也成为了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中餐作为世界上最古老、最丰富多样的饮食文化之一,不仅在中国享有盛誉,也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崭露头角。
本文将探讨中餐在国际饮食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并对其成功背后的因素进行分析和总结。
一、中餐在国际饮食文化中的地位中餐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凭借其独特的口味、烹饪技巧和食材选择,在国际饮食文化中拥有重要地位。
首先,中餐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
传统的烹饪方法如炒、炸、煮、蒸等,加上配以各式佐料和调味料,使得中餐具有极高的口感品质和烹饪技艺,这也是中餐在国际饮食文化中备受瞩目的原因之一。
其次,中餐的广泛传播也是其在国际饮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之一。
随着移民潮的涌现和中国的对外交流,中餐逐渐传播到全世界各个角落。
从风靡全球的中国餐馆到外国的中餐学校,中餐的身影无处不在。
例如,中餐的部分经典菜肴如宫保鸡丁、回锅肉等已成为国际级的美食,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
中餐的广泛传播不仅丰富了全球的饮食文化,还为外国人民了解和接触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
最后,中餐在国际饮食文化中的地位还体现在其对其他饮食文化的影响上。
中餐在料理技巧、食材选择以及饮食习惯等方面都对其他国家的饮食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例如,日本的寿司、泰国的炒菜和马来西亚的炒粿条等都融合了中餐的元素,并形成了独特的风味,在各自国家里享有盛誉。
中餐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口味上,还深刻地促进了各国饮食文化的多样性和创新性。
二、中餐在国际饮食文化中的影响力中餐作为世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力一直在不断扩大。
首先,中餐的烹饪技巧和用餐习俗对其他国家的饮食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例如,中国的烹饪方法和烹饪工具如炒锅、蒸锅等被国际上广泛采用,并对不同国家的菜肴烹饪方式产生了积极的借鉴作用。
此外,中餐的餐桌礼仪、饮食习惯等方面也逐渐融入了国际社会,促进了全球餐饮文化的多元发展。
中餐文化及其对海外华人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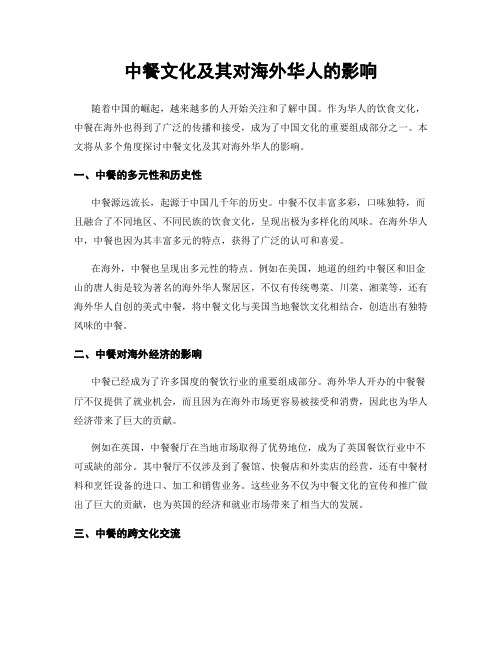
中餐文化及其对海外华人的影响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了解中国。
作为华人的饮食文化,中餐在海外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接受,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中餐文化及其对海外华人的影响。
一、中餐的多元性和历史性中餐源远流长,起源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中餐不仅丰富多彩,口味独特,而且融合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饮食文化,呈现出极为多样化的风味。
在海外华人中,中餐也因为其丰富多元的特点,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喜爱。
在海外,中餐也呈现出多元性的特点。
例如在美国,地道的纽约中餐区和旧金山的唐人街是较为著名的海外华人聚居区,不仅有传统粤菜、川菜、湘菜等,还有海外华人自创的美式中餐,将中餐文化与美国当地餐饮文化相结合,创造出有独特风味的中餐。
二、中餐对海外经济的影响中餐已经成为了许多国度的餐饮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外华人开办的中餐餐厅不仅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且因为在海外市场更容易被接受和消费,因此也为华人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贡献。
例如在英国,中餐餐厅在当地市场取得了优势地位,成为了英国餐饮行业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其中餐厅不仅涉及到了餐馆、快餐店和外卖店的经营,还有中餐材料和烹饪设备的进口、加工和销售业务。
这些业务不仅为中餐文化的宣传和推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英国的经济和就业市场带来了相当大的发展。
三、中餐的跨文化交流除了影响经济,中餐也推动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海外华人会将自己的传统文化与当地文化进行结合,创造出独特的中餐文化形式,进一步促进了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例如在加拿大,有“芝加哥炸鸡沙爹炒饭”这样的特色美食。
这种美食将中国传统菜式与加拿大当地餐饮文化相结合,呈现了一种全新的风味,这样的跨文化交流不仅对于华人,也对于当地人民拓宽了文化视野。
四、中餐走出国门的必然趋势世界多元化的开发,是中餐走出国门的必然趋势。
中餐的文化内涵、品牌价值、技术优势等方面,已经具备了向世界输出的条件。
中餐的发展受众已经不仅仅是全球的华人,更是来自世界各国的爱好者和当地人。
文莱概况

文莱是宗教色彩和马来民族传统较浓厚的国家,有一些独特的习惯和风俗:如, 当地马来人与人握手时,通常会把手收回到胸前轻触一下,以示真诚;从有身份的 人或长辈面前经过时,要把手下垂并贴着身体,侧身轻步走过等。 伊斯兰教是国教。文莱马来族多信仰伊斯兰教,属逊尼派。伊斯兰教徒占人口的 63%,佛教占12%,基督教占9%,其它信仰还有道教等。文莱是政教合一的国家, 在社会生活方面,伊斯兰教规几乎成了生活的准则。比如,按照“古兰教”的训诫, 马来人禁酒,不吃猪肉、死物和血液,这在文莱、在马来西亚都一样。对不要浪费、 不要偷懒,要遵守社会公德等,文莱的新闻媒介也多强调这是伊斯兰教的要求,每 天礼拜5次,即破晓时的“晨礼”,中午的“晌礼”,下午的“哺礼”,日落时的 “昏礼”,人夜后的“宵礼”。每星期五必须到教堂参加聚礼和祈祷。开斋节是文 莱马来人最隆重的宗教节日。斋月期间,成年穆判,在斋月的最后一天到月亮升起 时,家家户户连夜煎制糕点。翌日,他们互相拜贺,并向贫穷的穆斯林送礼,到麦 加朝圣是每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的最大的心愿,文莱虔城的伊斯兰教徒多,按信教 人口比例,到麦加朝圣的人数,比东南亚其他国家都多。 文莱的主要节日有:新年元旦(1月1日)、国庆节(2月23日)、文莱皇家 武装部队庆祝日(5月31日)、苏丹陛下华诞(7月15日)、斋戒月(每年回历9 月)、开斋节(每年回历10月初,根据观察新月定)、穆罕默德先知诞辰日(6月 15日)、回历新年(4月6日)、华人春节及圣诞节等。从节日可看出文莱是个多民 族和睦相处的国家,无论是哪个民族的传统节日,其它民族的人一起共享,互致祝 福。
【外交】文莱奉行不结盟和同各国友好的外交 政策。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应相互尊重。 1984年1月7日成为东盟第六个成员国,与 东盟各国关系密切,视东盟为外交基石。重视同 中国、美国、日本等大国关系。积极发展同伊斯 兰国家间的关系,是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此 外,文莱还是英联邦和不结盟运动等国际组织成 员国。
美食文化探寻世界各国独特的饮食习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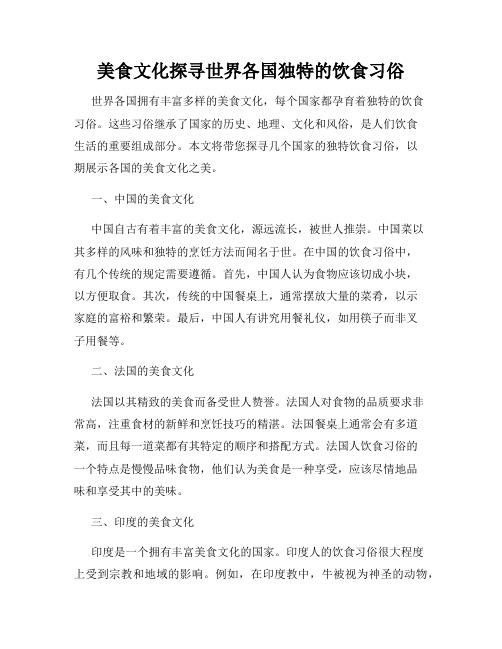
美食文化探寻世界各国独特的饮食习俗世界各国拥有丰富多样的美食文化,每个国家都孕育着独特的饮食习俗。
这些习俗继承了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和风俗,是人们饮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将带您探寻几个国家的独特饮食习俗,以期展示各国的美食文化之美。
一、中国的美食文化中国自古有着丰富的美食文化,源远流长,被世人推崇。
中国菜以其多样的风味和独特的烹饪方法而闻名于世。
在中国的饮食习俗中,有几个传统的规定需要遵循。
首先,中国人认为食物应该切成小块,以方便取食。
其次,传统的中国餐桌上,通常摆放大量的菜肴,以示家庭的富裕和繁荣。
最后,中国人有讲究用餐礼仪,如用筷子而非叉子用餐等。
二、法国的美食文化法国以其精致的美食而备受世人赞誉。
法国人对食物的品质要求非常高,注重食材的新鲜和烹饪技巧的精湛。
法国餐桌上通常会有多道菜,而且每一道菜都有其特定的顺序和搭配方式。
法国人饮食习俗的一个特点是慢慢品味食物,他们认为美食是一种享受,应该尽情地品味和享受其中的美味。
三、印度的美食文化印度是一个拥有丰富美食文化的国家。
印度人的饮食习俗很大程度上受到宗教和地域的影响。
例如,在印度教中,牛被视为神圣的动物,所以印度人不食用牛肉。
此外,印度菜有着独特的香料和调味品,如姜、大蒜、辣椒等,使得印度菜具有浓郁的口味和香气。
此外,印度人还有以手抓饭和平饼作为主要饮食方式的习俗。
四、日本的美食文化日本的美食文化充满品味和独特性。
日本人对食材的选择和烹饪技巧都十分注重,追求简洁、清淡的味道和精美的摆盘。
在日本的饮食习俗中,有一些重要的规则需要遵循,比如使用筷子进食、不用筷子插在饭菜中、用小碟子装饭等。
此外,日本人在享用日本料理时通常也会非常注重食物的新鲜度和季节性。
五、墨西哥的美食文化墨西哥的美食文化深受国家的民族传统和地理位置的影响。
墨西哥菜以其丰富多样的口味和独特的调味品而闻名。
墨西哥人的饮食习俗中,热辣的味道和玉米成为了重要的元素。
例如,墨西哥人喜欢用玉米面制作玉米饼,并以此作为主食。
中国男人在文莱有多吃香?当地美女道出真相:来了就不想再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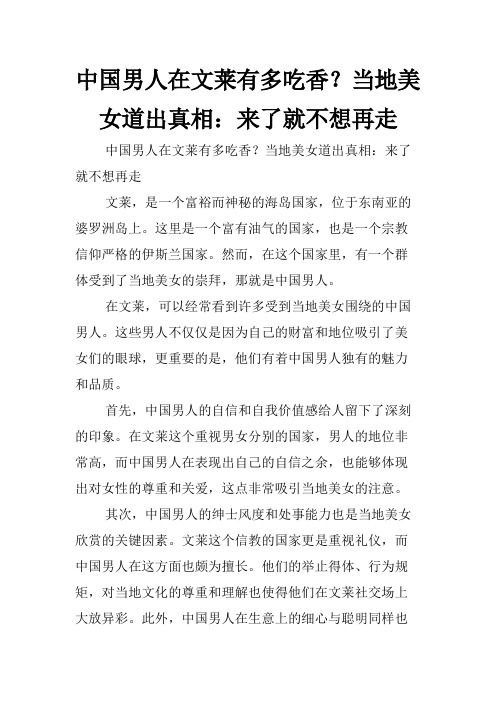
中国男人在文莱有多吃香?当地美女道出真相:来了就不想再走中国男人在文莱有多吃香?当地美女道出真相:来了就不想再走文莱,是一个富裕而神秘的海岛国家,位于东南亚的婆罗洲岛上。
这里是一个富有油气的国家,也是一个宗教信仰严格的伊斯兰国家。
然而,在这个国家里,有一个群体受到了当地美女的崇拜,那就是中国男人。
在文莱,可以经常看到许多受到当地美女围绕的中国男人。
这些男人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吸引了美女们的眼球,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中国男人独有的魅力和品质。
首先,中国男人的自信和自我价值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文莱这个重视男女分别的国家,男人的地位非常高,而中国男人在表现出自己的自信之余,也能够体现出对女性的尊重和关爱,这点非常吸引当地美女的注意。
其次,中国男人的绅士风度和处事能力也是当地美女欣赏的关键因素。
文莱这个信教的国家更是重视礼仪,而中国男人在这方面也颇为擅长。
他们的举止得体、行为规矩,对当地文化的尊重和理解也使得他们在文莱社交场上大放异彩。
此外,中国男人在生意上的细心与聪明同样也深受当地美女喜爱,因为他们会给女性带来安全感和获利机会。
当然,目前在文莱的中国男人也有不少,正面或者负面的言论存在。
有些人认为这只是富裕男性的一种表现,是赤裸裸的物质交换,对文莱品德形象的破坏。
然而,更多的文莱女性对来自中国的男性是持欢迎态度的。
她们表示中国男人普遍有起码的教养、内涵、才华,他们温柔体贴,有责任感,在社交场上的周到体贴会让人心动。
总之,在文莱这样一个富有、多元文化的地区,中国男人无疑是一道令人眼前一亮的风景。
他们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和文化,在这个世界不同的角落里,展现了中国男人的魅力和风采。
文莱有哪些风俗禁忌

文莱有哪些风俗禁忌文莱有哪些风俗禁忌文莱达鲁萨兰国古称渤泥,又称为文莱伊斯兰教君主国,寓意警惕,并求安定,简称文莱(Brunei),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
首都为斯里巴加湾市。
下面店铺推荐文莱风俗习惯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文莱的文化习俗社交礼仪由于独特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文莱宗教色彩和马来民族传统均较浓厚,形成了注重和谐、委婉、谦恭的马来文化。
其基本特征为:重视社会、族群、人际关系的和谐,不采用过激行动;关注弱势群体;重视礼节和传统,循规蹈矩,礼节繁多。
接待礼仪文莱人与客人相见时,一般都以握手为礼,然后把右手向自己胸前轻轻一扶。
文莱的年轻人见到老人后,要把双手朝胸前作抱状,身体朝前弯下如鞠躬。
文莱的马来人很注重待人接物的礼节,待人态度谦逊,说话极为和气。
家里来了人,不论认识与否,是朋友或是仇人,只要对方向自己请安问好,都要笑脸相迎并给予热情的款待。
在他们看来,给对方好脸色是对客人的施舍,向对方问候就是个祈祷。
客人来了不能问对方想吃点,有吃的尽管拿出来,对方不吃不要勉强,吃了不能问对方喜欢不喜欢。
客人告辞时,还要向客人表示感谢,并邀下次再来。
他们在待客必须使用左手时方能使用左手,但他们在这时,一定会很有礼貌地向你道一声:“对不起”。
餐饮礼仪文莱人在饮食上,对西餐和中餐都能适应,但对比起来,他们更偏中餐。
对辣味菜肴更感兴趣,尤其是干炸类的菜品,更属他们的餐中佳肴。
文莱的马来族人有食用佬叶的习惯,一般都常与蜂蜜和食用石灰一起嚼着吃,并用以招待宾朋好友。
文莱人在饮食嗜好上有如下特点:讲究菜肴香、酥、脆,注重量小质高;一般口味以不太咸为好,喜欢辣味;主食以米饭为主;副食喜欢牛肉、羊肉、鸡肉、鸡内脏、蛋类等;蔬菜爱吃黄瓜、西红柿、莱花、茄子、土豆等。
宗教文莱是宗教色彩和马来民族传统较浓厚的国家,有一些独特的习惯和风俗:如,当地马来人与人握手时,通常会把手收回到胸前轻触一下,以示真诚;从有身份的人或长辈面前经过时,要把手下垂并贴着身体,侧身轻步走过等。
文莱风俗文化礼仪

文莱风俗文化礼仪人文人情1.饮食文莱人以穆斯林最多,所以对牛、羊肉消费很多,也常吃鸡肉。
主食以大米、白面为最多。
他们常吃的蔬菜与我国相似,如西红柿、黄瓜、茄子、马铃薯之类。
他们做菜喜用调料,咖喱、虾酱、辣椒是必不可少的。
他们所做的食品菜肴以质取胜,讲究香、酥、脆。
饮料主要是咖啡、红茶、可可,也喝葡萄酒。
如果是有客人一起吃饭时,不能问“你想吃什么”,吃过饭后,也不能问你爱吃不爱吃,可口不可口之类的话。
2. 服饰文莱人传统服装多以热带人经常喜欢穿的长宽大的上衣和沙笼为主。
由于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喜欢出国、旅游等接触外界事物多,所以他们的服装多以西装为主,特别是在公共场合,女士多以裙装为主,当然她们的裤子是很宽长的;男士多穿西服,与其他国家的西服没有什么区别。
老年人,特别是不愿出门的老年人还以传统服装为主。
日常礼仪握手礼节文莱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穆斯林人相互间多为握手礼。
当地马来人在和人握手时,往往会把手收回到胸前轻轻碰触下,以示真诚。
不少马来人不愿与异性握手,所以,除非他(她)们先伸出手来,不要主动与他(她)们握手。
对啦,要注意别随便用手去摸他人的头部,他们认为这样将会带来灾祸。
尊敬长辈文莱人很尊敬老年人,晚辈见到长辈会恭恭敬敬地将双手抱于胸前,低头欠身。
这种礼仪形式就好像把合十礼与作揖礼合在一起。
作为后辈,当你从有身份地位的人或长辈的面前经过,要把手垂下贴着身体,侧身轻步走过。
对于长辈的召见,晚辈要立刻应召,保持仪容端庄、举止谨慎。
在长辈面前,晚辈坐时双腿并拢;如果是席地坐,那么男子要盘腿,女子则要跪坐。
长辈传递物品,晚辈要用双手来接。
手脚礼仪在文莱,不能用食指直接指人指物;和人打招呼或招出租车时也不能用食指,要挥动整个手掌。
文莱人认为左手是不洁的、不干净的,因此在接送物品时,我们要用右手。
另外,在正式场合下,要注意不要翘二郎腿或两脚交叉。
参观清真寺的注意事项来到文莱自然要去参观清真寺。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编者按】《礼记》明言,饮食是古代文化的本原。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饮食文化亦是国人引以为豪的,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近代中国“唯饮食之一道,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
中国人历来讲“民以食为天”,然而这一“天大的问题”至今无缘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饮食文化在西来的学科体系中毫无地位。
学理需靠华人论证,而学科体系又难以由华人突破。
本刊认为,为解决这一学术困境,值得开展多学科学者广泛参与的大讨论。
高成鸢先生多年来致力于该问题的研究,1994年即在《中国烹饪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论饮食文化在世界学科体系中的地位》的学术论文。
本期所刊登的高先生如下文章,则更为详尽地论证了中华独特饮食的源起和发展。
【内容摘要】著者在研究中华“尙齿”课题时突然对华人古怪的饮食经历发生兴趣,开始追寻中餐形成之若隐若现的轨迹,发现千回万转的演进、光怪陆离的现象都能归结为因果关系链条的环环相扣。
汤因比曾断言,生存逆境能激发民族的创造力。
不同于欧洲密林群兽的顺境,古华人遭遇干旱的黄土地带,粟食的致熟,逼出鬲甑等陶器及水火交攻原理的发明,导致中餐饭菜分野及华人“味”的启蒙,走出一条饮食“歧路”。
吃是人类最重要的实践,吃的殊途难免导致文化的异型。
日常饮食最易造成“习焉不察”。
《易·系辞》所说的“百姓日用而不知”,后贤常用之于水火。
“水火相灭相济”的中华哲理,历来没饮过开水的洋人是相当陌生的,遑论“‘道可道’,是‘味道’”的奥妙。
比较饮食史研究需要熟悉甲骨文、饱览人类学原著,资质很差的笔者之所以要犯难涉嫌,不过因为机缘所赐,偶逢中餐暗堡隐蔽的入口,惊喜中不禁“嘤其鸣矣”,以期“求其友声”。
【关键词】饮食史;饥饿;味道;比较文化;人类学。
【作者简介】高成鸢,天津市图书馆研究馆员,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主
要从事文化史研究。
王蒙先生说中华文化最突出的特色是汉字、中餐。
其实饮食又比文字更重要,就说常用虚词即、既二字,左边同像食具,右边都是人形“即”是凑前来吃,“既”是吃完背身而去。
很多人反感于近年“文化”名目的泛滥,笔者亦然,还曾举“厕所文化”为极端,不料在探索饮食文化中却自陷于窘境中华文化是以“家”为核心的,而家不离“豕(猪)”,猪圈就是粪坑;“五谷轮回”,还能“化臭腐为神奇”,有白捡的猪、鸡;不然何来美味的中餐肉肴?
以华人之吃为参照系,或许可以启示西人拓展出生趣及学术的广阔天地,是为中华文化对人类的新贡献。
一、中餐的历史
得天独薄的肉食时期。
人类都经过肉食阶段,恩格斯就肯定过[1]。
古华人毫无例外,《白虎通·号》总结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因为“禽兽不足”,连蚌蛤等类都成充饥之物(《韩非子·五蠹》等),终于被饥饿所迫走上独特的生路。
中餐始于粟食,其由来还得上溯到远古。
中原黄土地带自来干旱,缺少大森林,这终于被华裔史学权威何炳先生借助古花粉分析资料论定;干旱而肥沃的黄土适合粟类生长,因此古华人独能极早超越原始农业必需经历的“游耕”“半牧”阶段,过上纯农的定居生活[2]。
植被不茂密,则少大兽。
笔者发现,继吃鱼之后,史上还有过被忽视的以水鸟为主食的阶段。
高飞的“鹏”(朋字以双“月”表示肉多)可能是大群候鸟的幻象,反映了对肉类的渴望。
汉语自古总是鸟(禽)在兽先,骂人也说“禽兽”,动词擒、穫都跟鸟(隹即鸟)相关,一“隻”(简化为只)人手也成了鸟爪。
据《易·系辞》,堪称猎神的伏羲发明的猎具是网罟而非弓箭,用弓做猎具的“夷”(从大弓)族是华人的异类。
最可怪的是古书中常见的“弋”,即带丝绳的箭,如《诗·郑风·女曰鸡鸣》说,“弋凫与雁”;陆游诗“忽忆江湖泊船夜,飞鸣避弋闹群鸿”表明弋的对象是大群水鸟。
著名的汉代“弋射图”中,坐着的猎人射的鸟还带着丝线,但西来的考古学对“弋”至今没有正视。
人类学家说游猎会自然过渡到游牧(尾随兽群→豢养幼畜)[3],真是坐享其成。
马克思说最早种粮食是为给牲畜加料,印第安人因美洲没有马牛羊而直接进入“园艺时代”[4]。
华人主流文化也基本上没有经历畜牧阶段,不过另有缘由。
充分的根据表明,华人祖先迫于饥饿曾陷入“茹草”生活。
《淮南子·修务训》说“古者,民茹草饮水……”据《说文》,茹即喂马;同篇又说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
后人误以为他在找药,忘了“神农”不是神医。
药是找食的副产,所以中华文化医食同源。
草籽富含热量,便挑选粟(与黍合称稷)为主食。
“百谷”里早有麦,“麥”与“來”通,《说文》解释为不期而来的天赐瑞物。
麦粒大而好吃,先民为什么弃优取劣?麦类一穗才几十粒,饿极的先民舍得冒着绝收的危险撒进地里?唐诗名句“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透露的“投入产出比”该是决定因素。
粟食的“歧路”。
古华人自称“粒食者”,《大戴礼记·少闲》一篇就出现六次,《礼记·王制》还把四夷的人称为“不粒食者”。
粟、稻都是粒食,粟为正统。
最早的纯农业定居以周部落为代表,《周本纪》说其先祖“务农耕”“在戎狄之间”,收成必遭游牧者抢夺;《孟子·梁惠王》记载,文王的祖先一再向入侵者送礼哀求。
农人天然柔弱,战胜彪悍对手的唯一策略是“以柔克刚”,途径是人多势众,由此形成聚居-繁生的文化基因。
笔者认为,这一假说能解释何以唯独中华文化能成为唯一不被猎牧者冲散的文化[5]。
人多又不挪地,必然导致“生态破环→饥饿→夭亡→繁生”的恶性循环。
据《说文》,幸字古体为上屰(逆)下夭,似乎透露不被饿死就算幸事。
用繁生对抗夭亡,堪称民族生存的“鱼子战略”。
华人与大熊猫真像难兄难弟,“国宝”是唯一改变食性的兽类[6]。
至于熊猫趋少、华人反而趋多,那是智慧战略过度的结果。
素食者用“礼”提升了文明,便具有对落后部落的同化力,头一个被“滚雪球”的是黄河下游半猎的商族,《史记·汤本纪》说汤王惊呼鸟兽“尽之矣”而要求“网开一面”。
周人灭商后,“不食周粟”的义士伯夷兄弟躲进山中饿死,洋人会奇怪何不打猎采果?岂知山上已只有薇草可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