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诗的诗体重建
废名对新诗“诗质”的探索及其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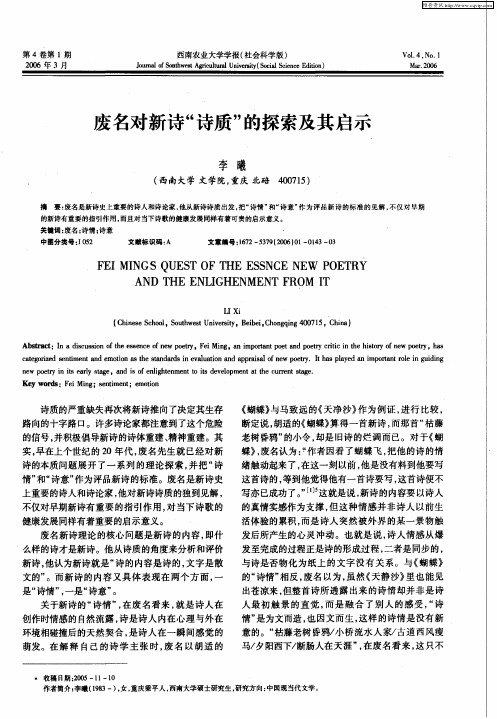
Vo . N . 14, o 1
M8" 0 6 12 0 .
废 名对新诗 “ 诗质 ” 的探索及其启示
李 曦
( 西南大学 文学院, 重庆 北碚 4 0 1 ) 075
摘 要: 废名是新诗 史上重要 的诗人和诗论家 , 他从新诗诗 质出发 , 诗情” “ 意” 把“ 和 诗 作为评 品新诗 的标准 的见解 , 不仅 对早期 ,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 号:62— 39 20 )l 04 0 17 57 (06 O 一 13— 3 ‘
关于新诗的“ 诗情” 在废名看来 , , 就是诗人在 创作时情感的 自然流露 , 诗是诗人 内在心理与外在 环境相碰撞后的天然契合 , 是诗人在一瞬间感觉 的
萌发。在解 释 自己的诗 学 主张 时, 废名 以胡 适 的
・ 收稿 日期 :0 5一l —1 20 1 0
作 者简介 : 李曦 (93 , , 18 一)女 重庆梁平人 , 大学硕 士研究生 , 西南 研究方向 : 中国现当代 文学 。
Ke r s:F i n ;s ni n ;e t n y wo d e Mi g 定其生存
路 向的十字路 I。许多诗论家都注意到了这个危险 = 1 的信号 , 并积极倡导新诗的诗体重建 、 精神重建。其 老树昏鸦” 的小令 , 却是 旧诗 的烂调而已。对于《 蝴
蝶》 废名认为 :作者因看 了蝴蝶飞 , , 把他的诗 的情 这首诗的 , 等到他觉得他有一首诗要写 , 这首诗便不 写亦已成功了。 … 这就是说 , ” 新诗 的内容要以诗人
不仅对早期新诗有重要 的指引作用 , 对当下诗歌 的 健康发展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废名新诗理论的核心 问题是新诗 的内容 , 即什 么样的诗才是新诗。他从诗质的角度来分析和评价 新诗 , 他认为新诗就是“ 诗的内容是诗的, 文字是散
不应忽视无韵诗的价值_与张中宇先生商榷

不应忽视无韵诗的价值———与张中宇先生商榷Ξ蒋登科(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400715)[摘要]韵律在中国传统诗歌中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但这种价值在现代诗歌中却出现了变化,韵律不再是诗之为诗的必要条件。
无韵诗、散文诗创作出现了如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等大批优秀作品,国外如惠特曼、艾略特、波德莱尔、纪伯伦等也是公认的巨匠。
本文针对张中宇关于韵律与中国诗歌繁荣的对应关系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新诗中的韵律与诗歌繁荣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韵律;新诗;无韵诗[中图分类号]I20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3)02-0031-04 在中国传统诗学中,韵律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是作为诗歌文体构成的必要条件来看待的,甚至有无韵不成诗的观念,并以此作为探讨诗与文或者韵文与散文的文体差别的重要方面。
诗歌创作亦是如此,重视韵律这一文本特征在大多数传统诗歌中都显得非常突出。
按照一般的理解,诗的韵律包括韵式、节奏、平仄等构成要素。
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这些韵律要素或其中的某些方面,都在诗歌创作中体现出了自己的特点,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中国诗歌独具的文体特征。
但是,承认韵律在中国传统诗歌发展中的重要性,我们在探讨中国诗歌的韵律及其美学效用时就可能面临这样一些问题:是不是在传统诗歌中几乎成为必要条件的韵律在现代诗歌中就一定也是诗之为诗的必要条件?如果是,它是否与传统诗歌中的韵律方式具有同样的特征?或者进一步问,不注重韵律是不是就一定不可能出现优秀的诗歌作品?作为从事现代诗歌研究的人,我曾经思考过这些问题,也在谈论中国诗歌传统时有所涉及。
[1]近读张中宇的《韵律与中国诗歌繁荣的相关度分析》[2]一文(以下简称《相关度》),又一次引起了我对中国诗歌韵律的兴趣和思考。
在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中,人们对于韵律之于诗歌文体的作用有多种不同的理解,而且越到后来,人们对它的关注似乎越来越少。
为诗消得人憔悴——新诗研究者东南大学王珂教授访谈录

法共生的文体。诗体研究实质上是对诗的本体研究, 访问100位诗人、100位诗歌理论家、100位诗歌编
新诗诗体学不仅具有诗学的意义,还具有政治学和伦 辑、100位诗歌教育工作者、100位诗歌读者。有诗友
理学的价值。很有必要广泛借鉴中外文体学及诗体学 说,这是王珂的“五个一工程”。
研究成果,建设包括新诗文类学、新诗语言学、新诗意 我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两大方面。一是本学科基
I03 中图分类号: A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1674-3210(2014)02-0005-08
王觅:王教授您好!您在年轻时很喜欢莱蒙托夫 者检索”中输入“王珂”,查看近 10 年(2002—2012)
的两句诗:“返顾过去,往事不堪回首;遥望将来,竟 您在国内发表的论文,结果显示:您在中国文学排名
研究学术问题来反思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快感。 诗体生成与流变的历史及原因;《诗体学散论— ——中
王觅:您的著作显示您的研究方向非常专一,主 外诗体生成流变研究》(2008年),39万字,较全面地
要是新诗研究, 特别是诗歌文体学的诗体研究。但 探讨了诗体的概念和影响诗体演变的各种因素;《新
是,从您发表的几百篇论文看,您的研究方向又十分 时期30年新诗得失论— ——当代新诗诗体、技法、功能
有人认为古代汉诗有定型诗体和准定型诗体,如格 同时,我还做新诗生态调查研究。开始的时候我
律诗体和散曲,现代汉诗根本就没有诗体,研究诗体 选择的是大陆地区,两年前扩展到两岸四地,现在延
也是可笑的。著名新诗学者叶橹先生甚至认为“重建 伸到全球。华人文化记忆、汉语诗歌和现代汉语保证
诗体是一个伪命题”。当然,也有新诗学者主张诗体 了文体的连续性,但受所处地区政治体制、文化观念
中文系任教。在专门的文学研究所、写作教研室、文艺 学视野中的刘勰诗体进化论》(2002年)、《古代汉诗
迎向诗意“空白”的世界——论现代汉语新诗咏物形态的创建

基金 项 目: 浙 江省 博 士后 科 研 项 目“ 汉 语 新 诗 的 象征 结 构 演 变研 究 ” ( b s h l 2 0 1 0 4 0 )
第 3 2卷 第 3期 2 0 1 3年 6月
江 汉 学 术
J i a n g h a n A c a d e m i c
Vo 1 . 3 2 No . 3
J u n , 2 0 1 3
迎 向诗意 “ 空 白” 的世 界
— —
论 现 代 汉语 新诗 咏 物形 态 的创 建
关键词 : 现 代 汉语 新 诗 ; 抒 情 主 体 ;诗 意 “ 空白” ; 咏 物; 意 象结 构 中 图分 类 号 : I 2 0 7 . 2 5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 0 0 6 - 6 1 5 2 ( 2 0 1 3 ) 0 2  ̄ 0 4 1 - 0 8
一
、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绪 论
依赖 的形 而上学 基 础 ( 比如 , 刘勰说的“ 原道” 、“ 征 圣 ”、 “ 宗经 ” ) 之后 的“ 空 白” 的 抒 写 。 在 古 典 诗 歌与世 界 的亲 密关 系 解 体 之 后 , 现 代汉 语 诗 人 如 何 迎 向诗 意 “ 空 白” 的世界, 重 建 汉 语 的诗 性 空 间 , 成 为汉语 新诗 切 实 的 困境 。因 此 , 现代 汉 语 新 诗 的发 生, 在 经历 了由语 言变革 引发 的文 化运 动 的同 时 , 开 启 了创 造 白话汉 语 诗 意 的运 动 。其 典 型 表 现 之一 , 就是现 代汉 语新 诗创 建 咏物形 态 的过程 。 以研究 想象 力诗 学 著 称 的法 国哲 学 家加 斯 东 ・ 巴什拉 曾按 亚里 士 多 德 的划 分 模 式 , 将 想 象 划 分 为
高一年级上册第一次月考语文试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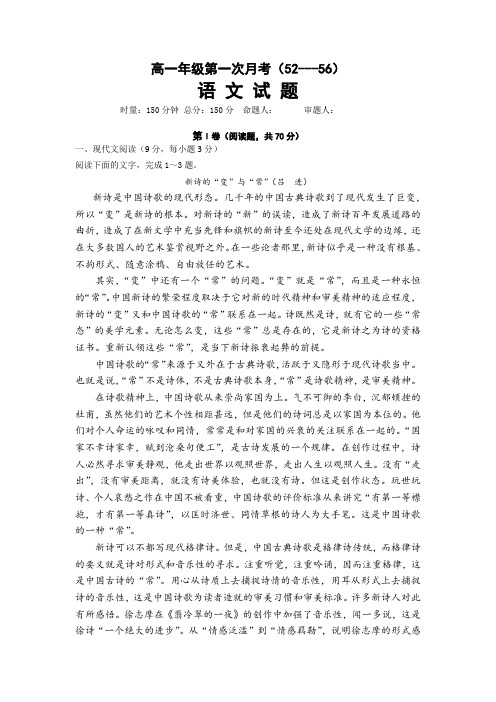
高一年级第一次月考(52---56)语文试题时量:150分钟总分:150分命题人:审题人:第Ⅰ卷(阅读题,共70分)一、现代文阅读(9分,每小题3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新诗的“变”与“常”(吕进)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
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
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造成了在新文学中充当先锋和旗帜的新诗至今还处在现代文学的边缘,还在大多数国人的艺术鉴赏视野之外。
在一些论者那里,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
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
“变”就是“常”,而且是一种永恒的“常”。
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它对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新诗的“变”又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
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
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
重新认领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振衰起弊的前提。
中国诗歌的“常”来源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
也就是说,“常”不是诗体,不是古典诗歌本身,“常”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为上。
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
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常常是和对家国的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古诗发展的一个规律。
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必然寻求审美静观,他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
没有“走出”,没有审美距离,就没有诗美体验,也就没有诗。
但这是创作状态。
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从来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
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
新诗可以不都写现代格律诗。
但是,中国古典诗歌是格律诗传统,而格律诗的要义就是诗对形式和音乐性的寻求。
建立新诗形式和韵律体系

建立新诗形式和韵律体系——中国汉诗创作规范略谈作者:周拥军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3468 更新时间:2005-10-29 17:17:44自“五四”新民主文化运动以来,新诗大行其道,得到充足的发展,毫无疑问,新诗已成为诗坛发展的主流。
这是先进文化的“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文化进步,新诗相对古诗(格律诗)而言,其主流的地位将永恒地传承下去。
但新诗的发展并不尽人意,中国新诗“鼻祖”胡适曾经梦想过要出几个白话的雨果和几个白话的东坡,一百年快要过去了,终归还是一个梦想。
更可悲的是,在新世纪里,新诗面临困惑的选择却越来越多。
譬如说,有诗人就曾明确主张:“我要让诗意死得难堪。
”“没有诗意是现代艺术的一个前提。
” 另外,网络盛行的“下半身诗歌”的口号更是干脆:“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
这种推动是唯一的、最后的、永远崭新的、不会重复和陈旧的。
因为它干脆回到了本质。
”这种充分获得了诗歌创作的个性之后,却有意地回避了诗歌应当承载的精神意义的现象,正是新诗健康发展的“困惑”。
诚然,诗是一种美学和哲学,是无法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的。
每个诗人的诗观,以及各类诗歌的风格和流派的存在,都是诗人理想追求和生产劳动的结果,都应该获得尊重。
但诗歌的底线——“文以载道”“歌以咏志”,作为诗人是无能无何也不能“摧残”的。
毋庸置疑,诗人的品格便是诗的品格。
任何一个伟大的诗人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品格就是真诚,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的真诚热爱。
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定豪迈,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高尚大义情怀,无不让人感动和追忆。
诗歌是人性本真的呼唤,是一种至纯境界。
确实,“诗人但求本真。
”当诗人有了这种赤诚的本真,他即使遭受一切不幸,遭受命运所有的打击,也会如食指“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的信心,也会有如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的心境。
由此可见,诗人关注诗歌的内在精神,是诗人的社会责任。
论坛闭幕式领导致辞5篇

论坛闭幕式领导致辞5篇(最新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文档下载后可定制修改,请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和使用,谢谢!并且,本店铺为大家提供各种类型的经典范文,如演讲稿、讲话稿、发言稿、致辞稿、主持稿、合同协议、条据书信、作文大全、教学资料、其他范文等等,想了解不同范文格式和写法,敬请关注!Download tips: This document is carefully compiled by this editor.I hope that after you download it, it can help you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The document can be customized and modified after downloading, please adjust and use it according to actual needs, thank you!In addition, this shop provides you with various types of classic sample essays, such as speech drafts, speech drafts, speech drafts, speech drafts, host drafts, contract agreements, letter letters, essays, teaching materials, other sample essays, etc. I want to know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t format and writing styles of sample essays!论坛闭幕式领导致辞5篇闭幕词,是会议的主要领导人代表会议举办单位,在会议闭幕时的讲话。
从两部《诗论》看朱光潜与艾青的新诗理论建构

目录摘要 (I)Abstract..................................................................................................................... I I 绪论 .. (1)第一章两种不同的诗质观念与诗美追求 (8)第一节关于新诗的界定:音律性纯文学与诗即真善美的统一 (9)第二节新诗的审美标准:诗美即形式美与诗情是诗美的本质 (11)第二章新诗创作的两种主张:主观感性释放与现实理性思考 (13)第一节意象的捕捉:形象的直觉与形象思维 (14)第二节意境的营造:情趣和意象结合与感觉是思想情感的契合16第三节语言的选择:音乐性语言与朴素、单纯、明快的语言 (19)第四节诗体的掌控:新格律诗与自由体诗 (21)第三章诗歌反作用于时代的两种观念:出世与入世的诗歌功用.. 23第一节朱光潜:诗歌具有超脱社会现实的功用 (23)第二节艾青:诗歌具有社会宣传的功用 (24)第四章两种诗论的思想、理论资源 (26)第一节西方文艺理论资源:“直觉说”与法国象征派 (26)第二节传统哲学思想资源:道家“消极避世”与儒家“求善”30第五章两部《诗论》对于现代新诗理论建构的意义 (32)第一节为现代新诗理论建构带来了新的审美标准 (32)第二节为现代新诗理论建构提供了多种创作方式 (33)结语 (36)参考文献 (37)后记 (40)绪论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发展史上,诗词文化可谓源远流长,拥有非常辉煌的成就。
到了“五四”时期,随着西方新思想、新文化的大量涌入,“五四”革命浪潮的席卷而来,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大力开展,以文言文为书写根本,模式僵化的旧诗不再适应文学发展的时代需求。
革新知识、抛弃死的诗学重建新的诗学迫在眉睫。
于是,激烈地批判传统诗词,从韵律、语言以及情感等方面,进行不断地变革和创新的创作实践与理论主张风起云涌般出现。
广西名校联盟2024-2025学年高二上学期开学考试 语文试题

2024年秋季学期高二入学检测卷语文考生注意:1.本试卷共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2.请将各题答案填写在答题卡上。
3.本试卷主要考试内容:部编版必修上册、下册和选择性必修上册第一、二单元。
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新诗是在打破旧诗形式中站立起来的,但即使是“五四”时期的开路先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们对传统持有的一种近乎“暧昧...:胡适是在“以文为诗”的“宋诗运动”中袭取传统的;俞平伯在..”的情绪《社会上对新诗的各种心理观》中更是直言不讳:“我们现在对于古诗,觉得不能满意的地方自然很多,但艺术的巧妙,我们也非常惊服的。
”百年新诗总是要竭尽全力地摆脱传统诗学的影响,走上自己的道路,但事实却总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又回到了传统的层面之上,从新月派、象征派到现代派,新诗尽管吸收了许多西方诗歌的技巧,但与此同时,新诗无疑也再现了古典时代诗歌的格调与韵致;而中国诗歌会在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50年代中后期两次大规模地采集民歌也确实再现了遥远的“采诗”景象,这些能够说明的问题或许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全离开传统而谈新诗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百年新诗在文体重建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要从传统诗学中寻找依据。
当然,那种要从形式与韵律的角度重新为新诗套上“枷锁”的做法无疑是不切实际的。
新诗的文体建设要从传统诗学中寻找依据,但绝不是将过去的一切照搬过来。
从文体形式的角度上说,今天的新诗已经形成了形式灵活、文体自由的特点,那么,我们从吸收的角度上说,关键是应当从类似形式较为灵活多变的屈原骚体诗、宋词中找寻与传统的融合点。
(摘编自张立群《反思与重建—论百年新诗文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重构的可能》)材料二:“传统”是古已有之的,也可以是正在创造的。
它一方面可以是作为中国新诗存在前提的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可以是中国新诗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传统。
现代诗学的两个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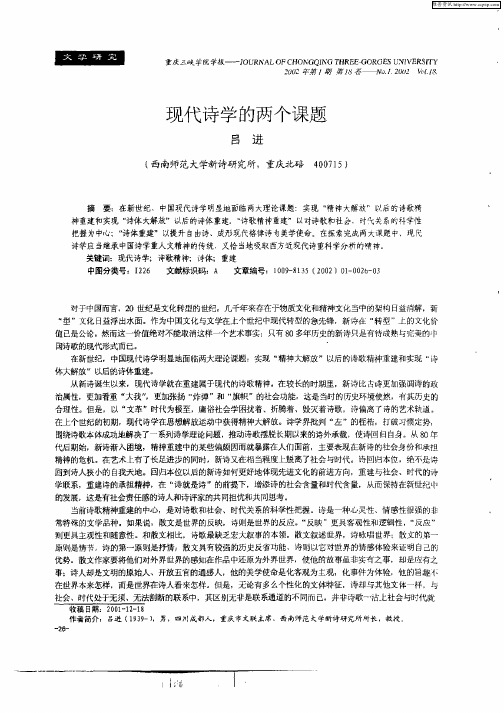
国诗歌 的现代 形式而 已 。
在新世纪,中国现代诗学明显地面临两大理论课题 :实现 “ 精神大解放 ”以后的诗歌精神重建和实现 “ 奇 体太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 。 从新诗诞生以来,现代诗学就在重建属于现代的诗歌精神。在较长的时期里,新诗比占许更加强调诗的政 治属性,更加看重 “ 大我” ,更加张扬 “ 炸弹 ”和 “ 旗帜”的社会功能 这是当时的历史环境使然,有其历史的 合理性。但是,以 “ 文革”时代为扳至,庸俗社会学困扰着 、折腾着、毁灭着诗歌,诗偏离了诗的艺术轨道。 在上个世纪的初期,现代诗学在思想解放运动中获得精神大解放 。诗学界批判 “ 左”的桎梏,打破习惯定势 , 围绕诗歌本体成功地解决了一系列诗学理论问题 ,推动诗歌摆脱长期以来的诗外承载 ,使诗回归自身。从 8 年 0
吕 进
40 1 ) 07 5 ( 西南师范大学新诗研 究所 ,重庆北碚
摘 要:在新世纪 ,中国现代诗学明显地面临两大理论课题:实现 “ 精神大解放” 后的诗歌精 神重建和实现 喵 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 嚼 歌精 神重建”以对诗歌和社会、时代关系的科学性 把握为中心;“ 重建”观提升 自由诗、成形现代格律诗为美学使命。在探索完成两大课题 中,现代 诗体 诗学应当继承中国诗学重人文精神的传 统,又恰 当地吸取西方近现代诗重科学分析的精神。 关键词:现代诗学;诗歌精神;诗体;重建
一
2一 6
垂
维普资讯
■蟹田
会贬值甚至毫无价值。因为,一方面,诗歌是一种社
会现象,诗人总是属于某一时代:另一方面,关心中 国改革 开放 的 中国读 者 要 求 诗歌 不 仅 要 具有 生 命关 怀,也要具有社会关 口 时代关怀:最后,中国新诗 发展史 J 的不少名篇佳作都是 以关注社会、拥抱时代 来获得读者的承认和喜爱 的 拒绝所有社会和时代维 度 的诗学 和当年 流行 的庸 俗社会 学 诗学一样 是片面 而
新诗格律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略论新诗对古诗应有的扬弃

一
精 神 品性 诸 多要 素 于 一身 ,是 深 刻 的情 感 与 情 志表 露 。需 要 通 过制 定 一 定 的规则 来 对 艺术 语 言 进 行规 范, 确 立 某 种大 家 都认 同的典 范 和标 准 , 艺 术 也 由此 得 以在人 与 人 之 间交 流无 碍 , 自由诗 就 因为 缺 乏规
关键词 : 新诗 ; 格律 ; 对称 ; 诗行 ; 音 组
中图 分 类 号 : I 2 0 7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 6 7 3 — 1 9 9 9 ( 2 0 1 3 ) 1 2 — 0 0 9 9 — 0 3
作者简介 : 林桢 ( 1 9 8 7 -) , 男, 江西上饶人 , 喀什 师范学院( 新 疆喀 什 8 4 4 0 0 8 ) 人 文 系硕 士 研 究 生。 收 稿 日期 : 2 0 1 3 — 0 7 - 0 6
新诗格律建设 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略论新诗 对古诗应有的扬 弃
林 桢
摘要 : 从体裁、 可评 判 性 、 艺 术 美 感 与历 史发 展 等 方 面 分析 新 诗 建立 格 律 的必 要 性 , 以及 格 律 体 新 诗 在 诗 行 、 字数 与 音 组
等 问题 上 对 古诗 的 继 承 和 新 变 的 可 能性 : 林庚 “ 半逗律 ” 所 揭 示 的 是 中 国 古典 艺 术 的 对称 原 则 , 格 律 体 新 诗 的诗 行 亦应 符合这 一原则 , 但 新 时期 当 有 新 的 特 点 , 诗行可二分或三分 , 形 式 上 形 成 首 尾 或 首 中尾 的 对称 结 构 : 诗 行 字数 不 宜作 精 确控制 , 但 大 致 可 限 定在 一到 十 字之 间 ; 音 组 兼 顾 文 意 与 诵 读 习惯 , 字数 在 一 字 到 五 字 为要 。
本质建构与历史实践:新诗“变常”略辩——兼谈新诗“诗体重建”与“精神重建”

着 这 一 历史 吊诡 。
属 。研 究 的 基 本 歌作 为 一种 以形 式 美 学 为 显 著 特 征 的 艺术 , 如 何 建 ’ , 它
问题 , 是 前 沿 问 题 。文 体 特 征 和 文 体 的 自觉 性 , 也 是 构 自身 的文 体 特 质 ? 这 不 仅 仅 是 “ 式 ” 技 巧 的 问 形 和
学 版 ,O O 3 :32. 2 L ( )2 —5
为 什 么不 再舒 服 一 些
嗯
再 舒 服 一 些 嘛
再 温 柔 一 点 再 泼 辣 一 点 再 知 识 分 子 一 点 再 参 考 文 献 :
民 间 一 点
为 什 么 不 再 舒 服 一 些
这种 “ 叫床 体 ” 歌 一 时 被 奉 为 杰 作 , 广 泛 评 诗 被
出“ 诗 将 死 ” 论 调 , 就 是 中 国 新 诗 面 临 的 那 个 中最 重 要 的一 种 “ 常 ” 系 : 体 与 文 体 意 识 。无 论 新 的 这 变 关 文
“ 恒 危 机 ” 何 为 新 诗 ? 新 诗 何 为 ?毫 无 疑 问 , 种 是 2 世 纪 中 国新 诗 史 上 自由 诗 和格 律 诗 等 外 在 体 格 永 : 这 O
法 ) 诗 意 精神 ( 想 、 验 与 情 感 ) 方 面 的 自我 焦 但 就 在 这 “ ” 中 , 蕴 含 着 一 种 “ ” 恒 量 , 就 和 思 经 等 变 之 又 常 的 那 虑 。但 历 史 的 吊 诡 之 处 恰 恰 在 于 : 到 现 在 , 国 新 是 新 诗 写 作 的 “ 体 意 识 ” 无 论 是 “ 韵 说 ” 刘 半 直 中 文 。 新 ( 诗 不 但 没 “ , 然 还 一 次 又 一 次 地 度 过 了“ 机 ” 农 ) “ 死” 竟 危 , 、 内节 奏 ” 郭 沫若 ) 还 是 “ 文 美 ” 艾 青 ) “ 格 ( 、 散 ( 、创
论新诗的语言意识与汉语诗性智慧

回汉语诗性。如果说 2 0世纪汉语诗歌在现代化 进程中语言意识的觉醒和强化 , 并不能标示汉语 意 识 的 自觉 , 么 2 世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纪 汉 诗 的发 展 之路 , 那 1 不得 不凭藉 自 身发育健全的生成机制。本文试图从对 新诗的现代性与汉语性 相统一 的基点上 , 从对诗 歌文本结构的整体形态及其艺术价值的全面理解 中, 重整诗歌精神 , 赋予新诗 以汉语言艺术的灵性
会历史语境 的回应。闻一多在 1 3年对郭沫若 9 2 《 女神》 所阐释的两层意思: 一是“ 与旧诗词相去最 远”二是“ , 最要紧的 ‘ 完全是时代的精神” , 基
收 稿 日期 :0 5—1 20 2—1 0
作者简介 : 玉(9 7 姜耕 14 一 12 1
)男 , , 江苏苏州人,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 向为艺术学 、 诗学。
错位现象 , 却成 了否认汉语韵律的 口实。1 2年 9 3 l 月《 1 现代》 刊登的《 望舒诗论》 最早表明戴望舒 , 放弃诗中“ 音乐的成分” 主张纯粹的“ , 情绪韵律” 。 这就是不满 于当时新月社 的新格律 形式而提 出的。
内在韵律与 外在韵 律 也成 了鉴 别 自由诗 与 格律 诗 的尺度 , 由此造成 诗体 的两极 分离 。西 洋格律 与汉 语格 律 , 差异 很大 。汉 诗模 仿西 洋 格律 , 免 削足 难 适履 或 貌合 神 离 。 台湾诗 家林 以华 曾作 过 批 评 : “ 整齐 的字数不一定 产生调和 的音节 。新月派诗 人 有 时硬性规定某一 个 中国字 等于英 文 的一个 音节 , 所 以英文 中的五拍 诗 到 了中文 就变成 了十个 字一 行 。 中西语 音有着 严 格 的区别 。不顾 汉诗 的格 ” 律与 汉字词汇组合 的诗意效应 , 能形成独 特 的汉 怎 语诗 意结 构 及 审美 空 间?新 诗 “ 律 ” 西化 , 格 的 只 能标示新 诗背离汉语诤 f 生传统而孱 弱无依 , 这大概
闻一多 诗歌中的三美

闻一多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集诗人、学者和斗士于一身的重要诗人。
他不但致力于新诗艺术美的探索,提出了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诗歌“三美”的新格律诗理论主张,还努力进行创作实践,写出了许多精美诗篇。
他的新格律诗理论被后人称为现代诗学的奠基石,影响深远。
“三美”诗论《诗的格律》是闻一多先生系列诗论中最重要的一篇。
在这篇论文中,他系统的提出“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
”这一关于新诗“三美”主张遂成为新格律诗派的理论纲领。
闻一多先生认为诗歌的音乐美是最首要的。
他大肆宣扬格律,声称“诗所以能激发情感,完全在它的节奏;节奏便是格律……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
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缚束。
这首诗在艺术上采用了象征的手法,对“恶”的歌咏,受到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来尔《恶之花》的影响。
这首诗在艺术上最主要的成就还在于对于新格律体诗体的创造。
在闻一多加入新月社之后,针对五四白话新诗的过分直白和散漫无羁,主张“诗应该带着镣铐跳舞”,并具体提出了“三美”的主张,也就是“音乐美”,即音节的和谐;“绘画美”,即辞藻的美;“建筑美”,即形式的整饬。
这首《死水》就是他的诗学主张的具体的实践。
《死水》是闻一多自认为“第一次在音节上最满意试验”的作品。
全诗每一行均由一个“三字尺”和三个“二字尺”组成,三字尺在诗行中处于一个颤动的过程,即由第一句的第三个音尺到第二、三、四行的第二个音尺;隔行压韵,最后都以双音节词收尾,读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节奏感和韵律感很强。
全诗共五节,每节四行,每一行都是九个字。
汉字被称为方块字,每个字都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建筑体。
这样每一行就形成了一个长方体;而四和长方体又构成了一个大的长方体;而全诗是五个大长方体,这就是构成了一个更大长方体。
从整体外形上看,结构工整、章法整饰,节与节之间匀称,行与行之间均齐。
论臧克家新诗创作的押韵及新诗押韵观

论臧克家新诗创作的押韵及新诗押韵观姚家育摘要:臧克家新诗的押韵,以叠韵和转韵居多,较少用随韵和交韵,很少用抱韵。
臧克家对新诗的新格律体诗、半格律体诗和自由体诗的押韵进行了探索,有些诗具有鲜明的格律美,节奏分明,声韵和谐。
臧克家对新诗押韵的看法,是他的新诗发展观和文体意识的体现。
关键词:臧克家;新诗;押韵;新诗诗体;格律臧克家的新诗创作自1929年到1999年整整七十年,说他是一部生动的二十世纪新诗史或许并不过分。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臧克家向读者捧出诗集《烙印》时,人们的目光就始终注视着他。
此后臧克家一本又一本诗集飞到读者面前,奠定了他在新诗史上的地位。
臧克家是有成就的诗人、诗歌批评家、编辑家、散文家,洋洋大观的《臧克家全集》十二卷即是明证。
既往讨论臧克家的新诗创作,从诗体层面上一般把他的新诗视为自由体诗,这个判断基本合乎事实。
但是,臧克家的自由体诗不同于其他诗人的自由体诗,在许多抒情诗中,他讲究格律,讲究音韵,讲究均齐对称,尤其在诗歌的押韵方面,似乎特别着力用心。
收入《臧克家全集》的第一首诗《默静在晚林中》写于1929年11月,是押韵的;同样收入《臧克家全集》的最后一首新诗《老舍先生永在——为老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作》写于1999年2月,也是押韵的。
这不是巧合。
臧克家不但重视新诗创作的押韵,而且他对新诗押韵的思考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没有中断过,这对诗人臧克家颇有意思。
本文拟在细读的基础上,对臧克家新诗押韵的韵式、体式和他对新诗押韵的看法作一些初步探讨,以期对臧克家新诗的文体研究有所推进。
一臧克家新诗押韵的韵式什么是韵?“韵,和也。
从音,员声”[1],也就是说,韵是声音的和谐。
沿用“韵”的一般意义,在诗中则指押韵脚,句尾成韵即押韵。
臧克家的新诗创作,他的抒情短诗有许多是押韵的。
关于新诗的押韵,臧克家认为“现在新诗押韵的很多,形式也各式各样。
有的一二两句、三四两句押韵的,也有一三、二四押韵的,在不分节的诗中有连押的,也有几句之后换韵的。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论新诗的诗体重建
我已多次说过,我认为,提升自由诗,成形格律体新诗,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项美学使命。
审美视点是创作主体审美地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
不同的审美视点形成不同的艺术门类,带来不同的文体可能。
诗人要进入诗的世界,首先要获得诗的审美观点。
不同的审美视点,使不同文学品种的创作者,哪怕在面对同一审美对象时,也显现出在审美选择和艺术思维上的区别。
散文的审美视点偏向绘画,诗的审美视点偏向音乐。
诗的视点是内视点,内视点决定了作品对于诗的隶属度。
诗的生成一般是三个阶段:诗人心上的诗——纸上的诗——读者心上的诗。
诗情体验转化为心上的诗,还只是诗生成的第一步。
心上的诗要成为纸上的诗,就要寻求外化、定型化和物态化。
审美视点是内形式,语言方式是外形式,即诗的存在方式。
从内形式到外形式,或日从寻思到寻言,这就是一首诗的生成过程。
诗体,是诗歌的外形式的主要元素。
换个角度,寻求外形式主要就是寻求诗体,中国新诗就是对于古诗诗体的大解放的产物。
散文,它的形式是内容化的形式;诗歌,它的内容是形式化的内容。
甚至可以极端地说,对于诗歌而言,形式就是内容。
在诗体解放以后,如果忽略重建,放弃对新时代的诗体的创造,将是极大的失误。
从新诗在近一个世纪里的摸索前行中,越来越多的人悟出了一个道理:无体则无诗。
没有成熟诗体,就没有成熟新诗。
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诗体重建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向度的努力:一是自由诗体,多少有些像古之杂言诗;一是现代格律诗体,多少有些像古之齐言诗。
在自由诗体的探索上,有以郭沫若为发端,而以艾青集大成的(通行)自由诗体,有以冰心、周作人领军的小诗。
前者对西方诗体有更多借鉴,后者对东方(印度与日本)和本国古代诗体更为注意。
由沈尹默《三弦》开端,经刘半农、鲁迅达到高峰的散文诗体,也有成就。
其实,经田汉最先从西方引入的“自由诗”的概念,只能在与格律诗相对的意义上去把握。
只要是诗,就不可能享有散文的“自由”,更没有无限的自由,它一定只有非常有限的“自由”。
从这个角度,“自由诗”这个名称是不够确切的。
所以,这一路的共通难题是自由诗的“自由”规范。
既然是诗的一个品种,自由诗的诗美规范何在?
在格律体新诗的探索上,陆志韦开创了先河。
“新月”诗人、冯至都是创作实践的先行者。
闻一多、何其芳在理论上的成绩较为显著。
这一路的诗体重建,共通难题是有待成功作品的支撑和“成形”的无限多样。
现代格律诗建设的中心问题
是音乐性。
如果说,自由诗以“成功”(最纯诗质的获取)为“成熟”的话,那么,对于现代格律诗,“成形”才是“成熟”。
现代格律诗的诗体,除了以“顿”或“字”为节奏单位的(通行)格律诗,还有由外国格律诗改造而来的中国现代格律诗。
李唯建肇始、冯至等领潮的十四行,林林等的汉俳,李季、阮章竞、贺敬之、张志民等的民歌体,都在此列。
此外,郭小川创建的“郭小川体”,也有诗学价值。
近一个世纪的诗体探索,无论自由诗还是现代格律诗,都进展缓慢,这和诗人队伍的状况、心态有关。
对于如何把握新诗之“新”,老实说,不少诗人的头脑里是一团雾水。
有个流行的说法,似乎“新”就是随心所欲,没有限制。
一些自由诗人习惯于“自由”,在诗体上不受任何约束,在创作时没有形式制约感,并不认为有诗体建设之必要,他们不一定会同意胡适的“作诗如作文”的说法,但也许信服郭沫若的“不定型正是诗歌的一种新型”的见解。
格律体新诗探索也几起几落,成效不显。
新诗长期处在革命、救亡、战争的生存环境中,忙于充当时代号角,无暇他顾,这是可以理解的外部原因。
这就影响到新诗对民族性与世界性、艺术性与时代性、自由性与规范性等一系列问题的处理与建设,尤其影响到诗体重建。
诗体,成了妨碍新诗在中国发展与繁荣的重要缘由之一。
由此,周而复始的生存“危机”近百年来一直困扰着新诗。
新诗的诗体重建,在无限多样的诗体(而不是为数很少甚至单一的诗体)创造中,有两个美学使命:给自由诗以诗美规范,如《文心雕龙·熔裁》所说,“规范本体谓之熔,剪裁浮词谓之裁”;倡导格律体新诗。
诗体的基本美学要素是音乐性,诗体重建的基本使命是重建诗歌的音乐性。
诗体是诗的音与形的排列组合,是诗的听觉之美和视觉之美的排列组合。
诗歌文体学就是研究这个排列组合的形式规律的科学。
从诗体特征讲,音乐性是诗与散文的主要分界。
从诗歌发生学看,诗与音乐从来就有血缘关系。
依照流行的说法,诗的音乐性的中心是节奏。
节奏有内外之分。
内在音乐性是内化的节奏,是诗情呈现出的音乐状态,即心灵的音乐。
外在音乐性是外化的节奏,表现为韵律(韵式,节奏的听觉化)和格式(段式,节奏的视觉化)。
内在音乐性就是音乐精神,它并非只属于诗歌,而是一切艺术的本质和最高追求。
只有外在音乐性才是诗的专属,它是诗的定位手段。
一种情感体验可以外化为小说、戏剧、散文,但只要有了外节奏,它就外化成了诗。
中国新诗不起于音乐,不来自民间,甚至不产生于中国。
它来自国外,诞生时的语境正是外国诗歌的非格律化大潮汹涌澎湃的时候,所以新诗给中国读者的
感觉是,它和此前的中国古诗大异其趣。
新诗与古代的歌诗不相通,多少相通的是诵诗。
音乐性是新诗的弱项,相反,音乐性却历来是中国古诗的强项。
《诗》三百,《风》、《雅》、《颂》即以音别。
《楚辞·九歌》凭借祭神的曲调。
汉魏《乐府》以“横吹”、“鼓吹”、“清商”等乐调为诗名。
唐人近体诗与唐代大曲有关,宋词就更不必言说了。
但任何一种语言写成的诗,其音乐美都受制于这一语言的语音体系。
世界上没有两种独立的语言具有完全相同的语音结构,因此,对于每一种语言的诗歌,它的音乐性虽然可能有某种相通,但都是不可能完全重复的。
换言之,较之诗的内蕴,诗的音乐性具有更强的民族性,因而具有更强的抗译性。
和原诗相比,译诗在音乐性上总是会有较大程度的变形。
艾青曾经几次提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不押韵的例子。
其实,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格律诗是在译成汉语后变成自由诗的,他的押韵的作品成了无韵的诗。
而裴多菲那首著名的自由诗《自由,爱情!》译成汉语后又成了格律诗。
从这个角度,诗歌无法翻译,更绝对地说,诗歌不可译,翻译作品的阅读总是一定程度的误读。
中国新诗虽然与西方诗歌关系密切,但是,和西方语言相比,汉语属于另一语系,在音乐性上有自己的特点。
西语有重音,西语诗的节奏是力的节奏和时的节奏,所以看重“声”(轻重、长短),弥尔顿的《失乐园》、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这样的名篇都是无韵诗;汉语没有重音,它的诗的节奏只有时的节奏,所以诗歌看重“音”(押韵及韵式)。
韵,不但使诗歌具有难言的音乐之美,而且使诗歌易于为读者记忆——韵脚是读者短暂休息的地方,也是提示读者回忆前文的地方。
不懂音韵的人在中国很难被称作诗人。
从发展走向看,中国诗歌的押韵有一个从严到宽、从细到粗的过程。
南宋刘渊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共106韵(即平水韵)。
后来,不计四声,只要求韵腹和韵尾相同,就只有18韵了。
18韵中韵腹相近的韵再合并,就成了新诗现在通用的13韵。
无论怎样宽松、怎样粗略,大体押韵是中国诗歌始终具有的美学品格。
这个品格,千百年来不但造就了一代代诗人,也造就了一代代读者。
无视这个审美积淀,新诗就会在中国遭遇站不住脚跟的命运。
总之,没有音韵,自由诗就“自由”成了散文。
还是鲁迅的言说能经得住时间的淘洗,鲁迅分析为什么“新诗直到现在,还是在交倒霉运”时说:“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站了它的地位。
”新诗至今“挤”的成绩有限,和音乐性的贫弱大有关系。
应该说,诗体重建主要并不是理论问题,关键在于艺术实践,由诗人们的多种实验逐渐推进。
现在许多诗人在进行丰富多彩的探索,在格律体新诗、微型诗、小诗上已多有建树。
理论家的任务是敏锐地关注和科学地抽象,为诗体重建鸣锣开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