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 理性 秩序
为什么说法律是理性的?

为什么说法律是理性的?这个话题好像有点⽏庸置疑?法律是理性的,因为⼈是理性的,那么,理性的⼈制定出来的法律是理性的,按照逻辑的推演,应该是这么⼀个情况。
但另外⼀个⽅⾯,⼈也是感性的,那么,感性的⼈制定出来的法律也应该是感性的,按照逻辑的推演,难道不应当是这样吗?那么,⼜为什么没有⼈说法律是感性的呢,或许,法律本⾝是感性的,只是没有发现。
我以为,法律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
其⼀,从理性⽅⾯来说,制定法律经过了⼈的深思熟虑。
从法律的起源来讲,是禁⽌性的规定居多,⽐如,不应该偷盗、不应该抢劫、杀⼈等。
那么,这样的法律是没有感性的成分的,因为这是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态度。
禁⽌性的规定,就是基本排除了恣意妄为,凭借感情⽤事,这应该是法律的题中之义。
其⼆,再从理性上看,法律的第⼀属性是秩序,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圆,秩序这个东西,强调⾏为的界限,⽽从感情⽅⾯看,感性意味着丰富,意味着千姿百态,这很难和理性相容。
其三,法律虽然是⼈制定,但⼈的⾏为应该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也就是说,法律不能违背⾃然法则。
所以,在很多法学家看来,⾃然法则就是万事万物固有的法则,只不过,⼈认识到这这⼀点,规定为法律,所以,法律是理性的。
我觉得,说法律是理性的,甚⾄还可以找出更多的理由,但法律有没有感性的成分?我以为,这⼏乎是肯定的了。
现代的法律的体系,是社会运⾏的⼀部分,并不是机械的,⽽是可以⼗分有弹性的⼀的种制度,也就是说,很有⼈性,⼈本主义。
也就是说,法律的⽬的,已经考虑到了个体的状况,个体的感受,个体的经济、社会地位等各个⽅⾯。
先说刑法。
刑法有没有感性的地⽅,⼜在哪⾥。
刑法的原则是罪⾏法定,从反⽅⾯理解,也就是法⽆明⽂规定不为罪,法⽆禁⽌皆⾃由。
这个原则,可是近代以来才有的,在古代社会,可没有这么⼀个规定。
所以,法学家贝卡利亚很了不起,就是看到了罪刑法定原则对⼈的⼀种保护。
旨在现在国家对⼈的⼀种⼲涉,很⼈⽂。
再说民法。
民法是⼀个普通⼈的法律。
社会秩序的维护主要靠法律还是靠道德辩论赛(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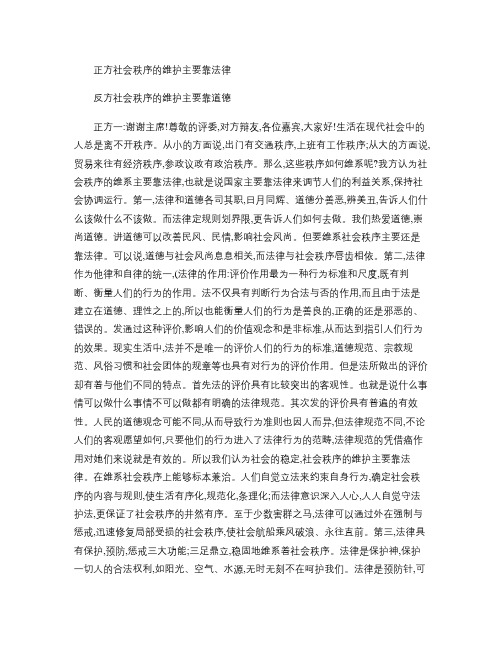
正方社会秩序的维护主要靠法律反方社会秩序的维护主要靠道德正方一:谢谢主席!尊敬的评委,对方辩友,各位嘉宾,大家好!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总是离不开秩序。
从小的方面说,出门有交通秩序,上班有工作秩序;从大的方面说,贸易来往有经济秩序,参政议政有政治秩序。
那么,这些秩序如何维系呢?我方认为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也就是说国家主要靠法律来调节人们的利益关系,保持社会协调运行。
第一,法律和道德各司其职,日月同辉、道德分善恶,辨美丑,告诉人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而法律定规则划界限,更告诉人们如何去做。
我们热爱道德,崇尚道德。
讲道德可以改善民风、民情,影响社会风尚。
但要维系社会秩序主要还是靠法律。
可以说,道德与社会风尚息息相关,而法律与社会秩序唇齿相依。
第二,法律作为他律和自律的统一,(法律的作用:评价作用最为一种行为标准和尺度,既有判断、衡量人们的行为的作用。
法不仅具有判断行为合法与否的作用,而且由于法是建立在道德、理性之上的,所以也能衡量人们的行为是善良的,正确的还是邪恶的、错误的。
发通过这种评价,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是非标准,从而达到指引人们行为的效果。
现实生活中,法并不是唯一的评价人们的行为的标准,道德规范、宗教规范、风俗习惯和社会团体的规章等也具有对行为的评价作用。
但是法所做出的评价却有着与他们不同的特点。
首先法的评价具有比较突出的客观性。
也就是说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都有明确的法律规范。
其次发的评价具有普遍的有效性。
人民的道德观念可能不同,从而导致行为准则也因人而异,但法律规范不同,不论人们的客观愿望如何,只要他们的行为进入了法律行为的范畴,法律规范的凭借癌作用对她们来说就是有效的。
所以我们认为社会的稳定,社会秩序的维护主要靠法律。
在维系社会秩序上能够标本兼治。
人们自觉立法来约束自身行为,确定社会秩序的内容与规则,使生活有序化,规范化,条理化;而法律意识深入人心,人人自觉守法护法,更保证了社会秩序的井然有序。
法律与理性

理性主义对我国的影响是在20世纪后期,在西方哲学理性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的学者 们开始了对理性问题的研究。在我们日常的话语中,人们对理性有着非常不同的读解, 并出现了对理性概念的不同描述:如有学者认为,在古希腊社会,最初的理性概念主要 是指事物的存在及其显示的方式,包含有在对话与交谈中去认识的意思,但总体上是一 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注:参见葛洪义:《法与实践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 002年版,第19页。)也有人认为,理性不是一个概念,而只是一个描述性的用词。但也 不否认理性所描述的是人的一种思维能力,或称思维工具。(注:参见刘世铨、和平: 《理性与非理性》,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还有学者认为,理性首先指的是一 种能力,其次是指一种态度、一种伦理。(注:参见王一乐:《逻辑、理性与信仰》,/。)还有人认为,理性一般在两种意义上被使用:第一,在 哲学的认识论中,理性是指人的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和思维活动的能力;第二 ,理性还常常被看作是人独有的用来调节和控制人的欲望和行为的一种精神力量。(注 :参见吴增基等:《理性精神的呼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也有学者 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所谓理性,不是别的,乃是追求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理性 追求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问题的实质在于,人们是否根据自身所认识到的约束条件和所 拥有的信息结构寻求该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注:参见谢作诗:《还谈“理性”》,/xiezshilixingz.htm。)2000年版《辞海》对理性的解释是: “‘理性’一般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活动或能力;理性还是划分认识能力或认识能 力发展阶段的用语。”(注:《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7页。)
人们最早是从哲学领域开始对理性进行形而上学探讨的,学科分类的发展使得人们从 各自的视角对理性概念进行开放与多元的理解,从而使人们对理性范围的理解更加广泛 。如:在哲学家看来,由于人是会思考的动物,所以理性就是用逻辑的思维方式进行思 维的活动;而非理性就是逻辑混乱、荒诞无稽。在伦理学家看来,由于人性本善,所以 理性就是遵循人伦常理的规则;而非理性就是违背人伦。在宗教学家看来,由于人是上 帝的孩子,所以理性就是对神qí@①信仰;而非理性就是背离神qí@①,就是异端。而在经济学家看来,由于人是精于盘算的动物,所以理性不是别的,乃是追求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理性追求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问题的实质在于,人们是否根据自身所认识到的约束条件和所拥有的信息结构寻求该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如“昨天我买了十张股票,今天股票大跌”,这并不否定我的理性。肯尼迪追求梦露,这是肯尼迪的理性,我不为麦当娜所迷,这是我的理性;城里人送孩子学这学那,这是城里人的理性,农民不送孩子读书也是农民的理性。只是约束条件不同是也。(注:参见谢作诗:《还谈 “理性”》,/xiezshilixingz.htm。)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加利?S?贝克教授在探讨犯罪行为是理性的理论假设以 及其经济含义时举例说,他本人在一次去参加一名学生的口试时迟到了,“因此我迅速 决定是否将车子放在一个停车场上,或冒险非法停在街上而得到一纸罚款收据。我计算 了得到一纸罚款收据的可能性,罚款的数额和把车子放进停车场的费用。我决定冒险停 在街上合算。(事实上我并未得到罚款收据)。”(注:[美]加利?S?贝克:《观察生活 的经济方式》,载《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87/1995)》,王宏昌编译,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6页。)加利?S?贝克教授甚至认为,由于犯罪与合 法工作比较有时存在财务报酬优势,考虑了被发现和定罪的可能性,以及处罚的严重性 ,理性意味着有些人会变成罪犯。(注:参见[美]加利?S?贝克:《观察生活的经济方 式》,载《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87/1995)》,王宏昌编译,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6页。)因此,经济人在权衡利益后作出的违法选择也应该被认 为是理性的。当然,这种理性是被法学家所反对的。法学家认为,法的理性就是遵守具 有正当性的法的规范;而非理性就是行为的越轨与犯法。
法律与秩序

MING RI FENG SHANG148人 文 科 学文|黄成敬欣法律与秩序摘要:在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进程中,经济、政治和文化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显现出了开放、自由的特征,从而也使人类文明的发展又迈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对于这些社会成果,则必须由社会秩序加以维护和保障。
关键词:法律;社会秩序;依法治国法律是以调整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以减少摩擦降低成本来维持社会关系的,它通过调整人们的行为来间接调整宏观的社会关系。
[1]对于那些不可能影响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是不会受到法律所约束的;而那些与社会关系有关,涉及到个体以及周围是否安稳的行为,就必然会受到法律的限制。
秩序是指有条理、不混乱的情况。
从法理学角度来看,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序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
[2]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不是仅通过法律来维持,也不是仅通过道德来约束,而是二者共同作用下的社会秩序。
一、社会秩序靠法律维持法律具有在指引和衡量人们行为上的明确性,它明确规定了法律主体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它是一种统一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
[3]法律具有公正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可以保障人们的合法权益;维护人间正义。
与此同时,法律的教育作用和惩戒作用使人们具备自身的法律意识,从而能更好地维系社会秩序。
社会主义要求3个至上,法律至上就是其中之一,可见,治理社会是离不开法律的,必须作为最高准则,建立社会主义法治,这是我国发展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法治是符合现阶段的社会管理模式,是社会秩序发展的前提保障,是治国惠民的前提要求。
第一,完善法律制度。
首先要制定良法,法律不仅要有实质合理性,还应当具备形式合理性;其次要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法律在国家生活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依法治国,把法律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最后,根据国情和时代发展,在保持法律稳定性的前提下,对法律进行及时的立、改、废,确保法律体系运行良好。
法律的实质理性.

法律的实质理性2008-01-20从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的分梳来看,法律理性是法律之所以为法律的内在逻辑品质,同时并为法律的外在技术品质。
“规则性”法律的最为根本的属性,是法律之所以蔚为人世生活的规则的根本原因所在,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其他各项职业伦理的基础。
任何法律总是现实的规则,立于生活现实并对生活现实作出自己的反映。
正是“现实性”使得法律区别于道德与宗教。
现实主义或者说现世主义,成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禀性。
法律天然具有“保守性”,守成的态度因而成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理性。
规则性、现实性、时代性、保守性和价值性,构成法律的实质理性的基本内涵,成为法律理性的内在逻辑品质。
法律是一种人世生活的规则。
作为法律公民,法律从业者是规则的寻索者和整合者,是法律“意义”的生产者和阐释者。
法律的实质理性作为法律的内在逻辑力量,经由一系列制度安排,赋予人世规则与人间秩序以明晰、稳定、确切、可靠以及可操作等技术秉性,从而使人世生活得有可恃的凭依。
人们在研习法律之初就应当明了并有所思想准备的是,法律从业者应将自己的个性色彩归纳入、体现在对于法律、法学的学科域界和学术纪律的规范之下,以对法学和法律的基本学术纪律的服膺为个性伸张的前提。
“规则性”应是法律从业者细予领会的法律理性的重要内涵,而“规则意识”则为法律从业者“起步伊始”所当养成的职业伦理。
法律从业者作为人世生活的一分子,由设身处地、推己及人、能近比譬的格局中,思考、对待法律之为一种人世规则和人间秩序。
法律从业者需要深深铭记并时时用来警策自己的事实是,为生活本身所固有,从而能够将生活组织起来的最为深厚而宏大的力量,不是法律,不是法学,也不是“行走着的法律理性”,而是叫做“生计”的这一燃眉之急。
实际上,所谓法律,从其为规则及其意义的合成体的最为原始的意义而言,正是对于人世生活中的常识、常理和常情的理性主义归纳为形式主义展现。
法律从业者应当从生活本身省视规则,在包括“法律实践”在内的起居之中,体会基本的人情世故,包括自己在内的普通居民的想法,对自己所要处理的论题,力争作设身处地的同情的了解和理解。
[秩序,理性,哲学]谈康德哲学中的理性秩序
![[秩序,理性,哲学]谈康德哲学中的理性秩序](https://img.taocdn.com/s3/m/b4c1c25402d276a201292ec2.png)
谈康德哲学中的理性秩序康德按照理性的不同功能将其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理论理性具有认知意义,但不具有实践意义;相对于此,实践理性主要在于指导人的行为。
人能给予两种秩序,自然因果必然性与自由因果必然性。
这也说明,人有两种生命状态,一是被经验性条件决定,要么形成科学判断,要么形成利弊判断;二是不被经验性条件决定,只被超验的东西决定。
被经验条件决定的生命状态及其领域被称为自然;被超验的东西决定的生命状态及其领域被称为自由。
自然的生命状态适合从事科学研究,自由的生命状态适合从事实践活动。
若用自然的生命状态从事实践,用自由的生命状态从事科学研究,二者就会导致二律背反。
在此意义上,本文就康德理性的界限以及功能进行了深入的阐释。
一、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理性(ratio),是指世界的客观秩序和原则。
从词源上来考察,理性最初源于赫拉克利特提出的逻各斯和阿那克萨戈拉提出的努斯(Nous)。
逻各斯是指万物的生成、运动所遵循的尺度和原则;努斯是指宇宙万物有序、合理的原因。
由此可知,理性从诞生之初就代表着宇宙、世界的秩序和规则。
需要注意的是,理性最初规定的秩序是在自然哲学领域的,是在苏格拉底那里才把理性与人联系起来,即从对自然哲学的关注转向伦理学。
苏格拉底继承了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他把理性代表的秩序称为善。
也正是由于对理性秩序的肯定,他认为,人作为理性存在物,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能够自制,他指出:一个不能自制的人和最愚蠢的牲畜没有什么分别。
在他看来,人如果不能够自我控制,也就几乎和动物无异,不能自制的人也就不能忍受饥饿、克制情欲;相反,能够自制的人不仅可以通过言语和行为对事物进行甄别与选择,而且还能够控制自己。
这样,人就超越了本身,实现了自由。
然而,苏格拉底并没有对理性的范围和界限进行划分,同时,他的理性主义是建立在知识论基础上的。
在此背景下,康德继承了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传统,并第一次将理性的理论应用和实践应用明确区分开来。
法律重在维持秩序还是主持正义?辩论赛 正方辩词一辩、二辩、三辩、四辩发言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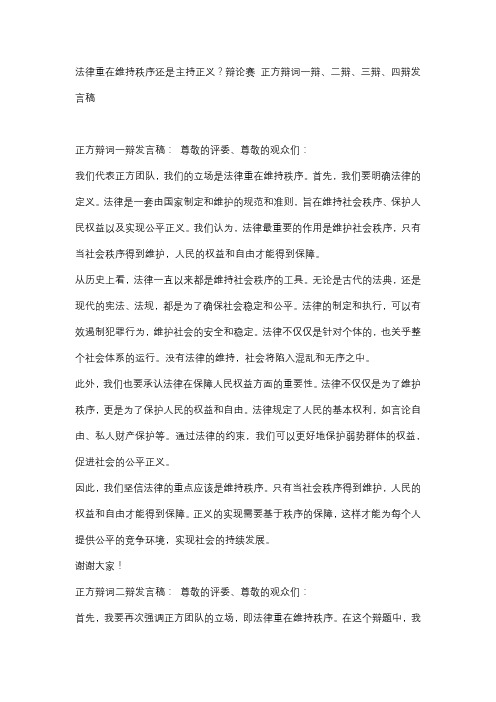
法律重在维持秩序还是主持正义?辩论赛正方辩词一辩、二辩、三辩、四辩发言稿正方辩词一辩发言稿:尊敬的评委、尊敬的观众们:我们代表正方团队,我们的立场是法律重在维持秩序。
首先,我们要明确法律的定义。
法律是一套由国家制定和维护的规范和准则,旨在维持社会秩序、保护人民权益以及实现公平正义。
我们认为,法律最重要的作用是维护社会秩序,只有当社会秩序得到维护,人民的权益和自由才能得到保障。
从历史上看,法律一直以来都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
无论是古代的法典,还是现代的宪法、法规,都是为了确保社会稳定和公平。
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可以有效遏制犯罪行为,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法律不仅仅是针对个体的,也关乎整个社会体系的运行。
没有法律的维持,社会将陷入混乱和无序之中。
此外,我们也要承认法律在保障人民权益方面的重要性。
法律不仅仅是为了维护秩序,更是为了保护人民的权益和自由。
法律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如言论自由、私人财产保护等。
通过法律的约束,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因此,我们坚信法律的重点应该是维持秩序。
只有当社会秩序得到维护,人民的权益和自由才能得到保障。
正义的实现需要基于秩序的保障,这样才能为每个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
谢谢大家!正方辩词二辩发言稿:尊敬的评委、尊敬的观众们:首先,我要再次强调正方团队的立场,即法律重在维持秩序。
在这个辩题中,我们坚持认为维持社会秩序是法律的首要目标。
秩序是任何社会的基础,它是人们生活和发展的基石。
正义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秩序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义,而秩序却是可以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来维护和保障的。
法律的职责就是通过规范行为、约束权力,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法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规范社会行为。
法律的制定是经过合法程序和各方参与共同达成的结果,它代表了社会普遍价值观和共识。
法律的权威性和适用性使得人们有依法行事的指导,并且在争议和冲突中能够找到解决的方式。
社会秩序的维持主要靠法律

法律的稳定性,有基准和相对完善。
法律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法律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法律的三大功能,这几个方面说法律的优点,再对比道德而言,说道德的缺失,这是我做为一辩的陈词观点下面由我来阐述我方观点。
我方认为维系社会秩序,主要靠法律。
首先,让我们来对辩题有个更好的理解:社会秩序指的是社会运行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有条不紊的客观状态。
下面来了解法律的概念:法律是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国家政权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由经济基础决定,为维系社会秩序服务的公正不偏的权衡标准,是理性的体现。
而道德是人们以善恶为标准并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俗来维持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道德通过影响社会风尚间接影响社会秩序,而法律则通过强制性手段来直接维系社会秩序。
既然要比较二者对于维系社会秩序的作用,当然要从二者的衡量标准是否统一、约束力大小、公正性。
1.法律具有在指引和衡量人们行为上的明确性。
它明确规定了法律主体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
它是一种统一的价值判断和行为规则。
而道德取决于人的认识、情感、意志,是对个人利益取向的判断。
可见,道德判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是仁者该听智者的还是智者该听仁者的呢?试问,这样的道德怎样能很好地维系社会秩序呢!2.法律具有通过制裁违法犯罪行为来规范人们行为的强制性。
只有通过国家机器保证实施的法律才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和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威慑作用。
而道德是不具备这种约束力的。
对于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道德能做的充其量是舆论的谴责和当事人内心的自责,如同隔靴搔痒,是不能起到实际的作用的。
3.法律具有公正性。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可以保障人们的合法权益;维护人间正义。
与此同时,法律的教育作用和惩戒作用使人们将之内化为自身的法律意识。
防患于未然,从而能更好的维系社会秩序。
4.社会秩序的某些领域是道德无法涉及的。
在这些领域只能通过法律来维系。
例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政府的组织规则等领域,法律的指导更便利同时更有效率,道德是做不到的。
维护社会秩序主要靠法律

正方一:谢谢主席!尊敬的评委,对方辩友,各位嘉宾,大家好!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总是离不开秩序。
从小的方面说,出门有交通秩序,上班有工作秩序;从大的方面说,贸易来往有经济秩序,参政议政有政治秩序。
那么,这些秩序如何维系呢?我方认为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也就是说国家主要靠法律来调节人们的利益关系,保持社会协调运行。
第一,法律和道德各司其职,日月同辉、道德分善恶,辨美丑,告诉人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而法律定规则划界限,更告诉人们如何去做。
我们热爱道德,崇尚道德。
讲道德可以改善民风、民情,影响社会风尚。
但要维系社会秩序主要还是靠法律。
可以说,道德与社会风尚息息相关,而法律与社会秩序唇齿相依。
第二,第二,法律作为他律和自律的统一,在维系社会秩序上能够标本兼治。
人们自觉立法来约束自身行为,确定社会秩序的内容与规则,使生活有序化,规范化,条理化;而法律意识深入人心,人人自觉守法护法,更保证了社会秩序的井然有序。
至于少数害群之马,法律可以通过外在强制与惩戒,迅速修复局部受损的社会秩序,使社会航船乘风破浪、永往直前。
第三,法律具有保护,预防,惩戒王大功能;三足鼎立,稳固地维系着社会秩序。
法律是保护神,保护一切人的合法权利,如阳光、空气、水源,无时无刻不在呵护我们。
法律是预防针,可以防患于未然,使一些居心不良的人悬崖勒马,雷池止步。
法律是无情剑,刀光剑影下邪恶何处立足?铁面无私中罪行怎能藏身?有道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一个癌细胞可能会威胁人的生命,一个社会的毒瘤可能会葬送国家的前程。
托尔斯泰说得好“行善需要努力,惩恶更需要努力。
”所以,惩恶扬善的法律才是社会秩序的根本保障。
综上所述,法律在维系社会秩序时,既可以未雨绸缎,也可以亡羊补牢,既可以惩治罪恶,又可以保护良善。
所以说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部!谢谢各位!(掌声主席:谢谢杨蔚同学!现在我们请反方一辩陈佩珊同学阐述反方立场,时间也是3分钟反方一辩:下面由我来阐述我方观点。
理性的法律秩序

理性的法律秩序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理性的法律秩序成为了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是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公共利益的重要保障,还能够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等基本权利。
在本文中,我们将会探讨什么是理性的法律秩序以及它的重要性。
一、什么是理性的法律秩序理性的法律秩序是指一套以理性为基础的、能够保障社会公正与稳定的公共秩序。
这种秩序建立在对社会的自主性、平等性、公正性和普遍性等社会公共原则的认识之上,采用科学的方法,有系统地构建起涵盖人民生命、财产、自由、尊严等多个方面的法律体系。
理性的法律秩序的实现,需要建立在社会的基层制度上,如民主制度、司法制度和管理制度等,从而依附于这些制度的共同作用下建立的规章、法律等多种法规的体系,才能够在实践中完整达到其目标。
二、理性的法律秩序的重要性1、保障社会公正理性的法律秩序制度能够打造一个公正、明朗的社会环境,公正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只有建立在公正的法律的基础上,社会才能健康稳定发展。
理性的法律秩序不仅为人民提供了平等和公正的生存场所,也为企业、机构等提供一个公正、非腐败、竞争公平的营商环境。
2、保障个人生存和财产管理理性的法律秩序不仅为人们保障了生命、财产安全等基本权利,还针对人格尊严、社会福祉、参政权利等方面制定了相应规章制度,可以保障个人的权利受到侵犯的程度尽量降低,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安全和稳健的生存空间。
3、提高社会诚信建立理性的法律秩序,不仅可以强化人们之间的约束关系,还可以大大提高社会诚信,可进一步帮助人们自觉遵守交往准则、重视谈判诚信、提高竞争诚信、奉行诚实守信和善良品德等。
三、总之理性的法律秩序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不可忽视。
它不仅能够保障社会稳定和繁荣,还能为人们提供平等公正和尊严的社会环境。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理性的法律秩序的重要性,不断加强对法律秩序的理解,同时不断提升尊重法律的意识,以期达到全民参与、共同建设与遵守正义的目标。
法律的合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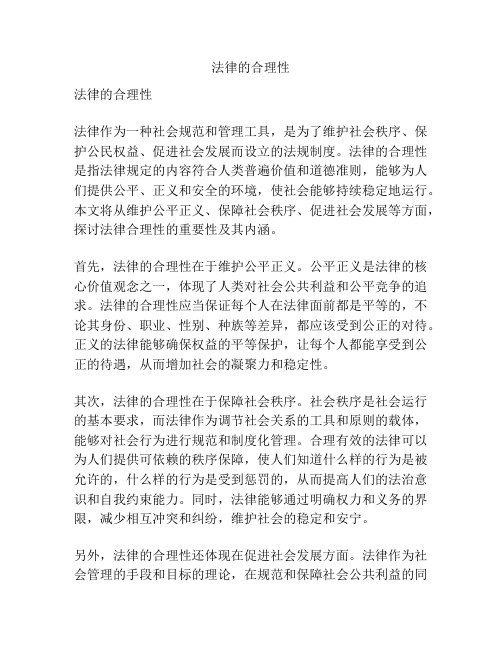
法律的合理性法律的合理性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和管理工具,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权益、促进社会发展而设立的法规制度。
法律的合理性是指法律规定的内容符合人类普遍价值和道德准则,能够为人们提供公平、正义和安全的环境,使社会能够持续稳定地运行。
本文将从维护公平正义、保障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探讨法律合理性的重要性及其内涵。
首先,法律的合理性在于维护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法律的核心价值观念之一,体现了人类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平竞争的追求。
法律的合理性应当保证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不论其身份、职业、性别、种族等差异,都应该受到公正的对待。
正义的法律能够确保权益的平等保护,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公正的待遇,从而增加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
其次,法律的合理性在于保障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是社会运行的基本要求,而法律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的工具和原则的载体,能够对社会行为进行规范和制度化管理。
合理有效的法律可以为人们提供可依赖的秩序保障,使人们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被允许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受到惩罚的,从而提高人们的法治意识和自我约束能力。
同时,法律能够通过明确权力和义务的界限,减少相互冲突和纠纷,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安宁。
另外,法律的合理性还体现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
法律作为社会管理的手段和目标的理论,在规范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也可以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保障和推动力。
如企业法律制度的完善能够促进公平竞争和市场规范,提高经济效率和资源配置的优化;知识产权法律的保护能够鼓励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劳动法律的健全可以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增加工作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等。
合理的法律能够为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秩序保证,对于社会的繁荣与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法律的合理性还表现在其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透明性和参与性。
合理的法律应当依据民主决策的原则,充分听取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形成广泛的共识。
法律制定过程中的透明性可以有效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发生,保证社会的公信力和法治的效力。
浅谈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

观 念 和 利 益 诉 求 的 人 群 ,如 果 公 安 工 作 仍 然 按 照 一 个规 则 、一把 尺 子 来 进 行 执 法 ,就 不 能 满 足 多
样 化 的利 益 主 体 。法 律 规 则 已 经
抽 象 出个 体 特 性 ,而 公 安 执 法 时
ZHlF A TAN SU o
公 安执法工作 指明了努 力的方 向。
一
、
什 么 是 理 性 、平 和 、文 明 、
法 律 性 ,是 指 程 序 和 处 理 符 合 法 律 规 定 。文 明 、规 范 是 执 法 的 应
有之 义 ,但 仅 有 文 明 、规 范 执 法
规 范执 法
( )理 性 、 平 和 、 文 明 、规 一
20 0 9年 4月 1日起 施 行 的 《道 路
音 调 会彰 显 平 和 与 不 平 和 。 因为
口头语 言 ,是被受 众感官 感知的 。
交通安 全违 法行 为处理 程 序规 定 》 第 2 条第 ( ) 1 三 项规 定 ,有 证 据
证 明 救 助 危难 或 者 紧 急避 险 造 成 的违 法 信 息 予 以 消 除 ,这 说 明 , 此种 情 形 就 不 能 处 罚 。修 订 后 的
他从一麻袋零钱发现了的现实性和实效性增强公安尽致如身着公安制式服装插队l现在有部分民警的能力不当前考核以破案论英雄导致买票
ZHIFA : TAN SUo
20 0 8年 1 2月 1 日 , 国 务 委 9
现 在 又 提 出 理 性 、平 和 执 法 ,这
有 一 个 基 本 的悖 论 ,正如 哈 贝 马 斯 在 《 事 实 与 规 范 之 间 》一 书 在 中所 言 ,“ 通过 合 法律 性 而确定 正
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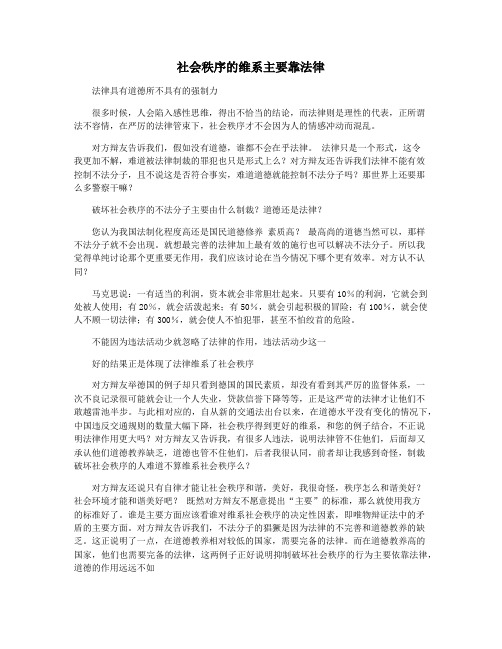
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法律具有道德所不具有的强制力很多时候,人会陷入感性思维,得出不恰当的结论,而法律则是理性的代表,正所谓法不容情,在严厉的法律管束下,社会秩序才不会因为人的情感冲动而混乱。
对方辩友告诉我们,假如没有道德,谁都不会在乎法律。
法律只是一个形式,这令我更加不解,难道被法律制裁的罪犯也只是形式上么?对方辩友还告诉我们法律不能有效控制不法分子,且不说这是否符合事实,难道道德就能控制不法分子吗?那世界上还要那么多警察干嘛?破坏社会秩序的不法分子主要由什么制裁?道德还是法律?您认为我国法制化程度高还是国民道德修养素质高?最高尚的道德当然可以,那样不法分子就不会出现。
就想最完善的法律加上最有效的施行也可以解决不法分子。
所以我觉得单纯讨论那个更重要无作用,我们应该讨论在当今情况下哪个更有效率。
对方认不认同?马克思说: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
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
不能因为违法活动少就忽略了法律的作用,违法活动少这一好的结果正是体现了法律维系了社会秩序对方辩友举德国的例子却只看到德国的国民素质,却没有看到其严厉的监督体系,一次不良记录很可能就会让一个人失业,贷款信誉下降等等,正是这严苛的法律才让他们不敢越雷池半步。
与此相对应的,自从新的交通法出台以来,在道德水平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中国违反交通规则的数量大幅下降,社会秩序得到更好的维系,和您的例子结合,不正说明法律作用更大吗?对方辩友又告诉我,有很多人违法,说明法律管不住他们,后面却又承认他们道德教养缺乏,道德也管不住他们,后者我很认同,前者却让我感到奇怪,制裁破坏社会秩序的人难道不算维系社会秩序么?对方辩友还说只有自律才能让社会秩序和谐,美好,我很奇怪,秩序怎么和谐美好?社会环境才能和谐美好吧?既然对方辩友不愿意提出“主要”的标准,那么就使用我方的标准好了。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一、问题的提出国家权力、特别是20世纪以来政府权力的大规模扩张,将传统的民间领域逐渐缩小、乃至侵蚀殆尽。
在法律领域,“我们所看到的情形是,制定法差不多已经把习惯法逐出了战场。
”(3)民间的规则几乎只能是“无声”的、“默默”的发挥作用。
对此,伯尔曼敏锐地提出,在每一个国家,各种各样的司法管辖权和法律体系全都淹没在一个中央的立法和行政规章中的现象,极大地威胁了法律至上的基础(4)。
这种现象和忧虑并不是政治法律领域独有的,而是一个普遍的现代性问题。
18世纪,人们要求在理性的法庭上对各种确信和信念进行审判,人们有理由相信,理性的千年王国即使没有实现,也不会太遥远。
20世纪,思想界的重大课题则是对理性的反思。
在哈贝玛斯看来,源于黑格尔的现代性对话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客观理性的普遍性要求与主体中心的理性的有限性的矛盾。
现代性就是理性。
理性源于对传统集权统治的挑战,具有个人自由的个性特征;同时,理性及其发展又蕴涵着建立新秩序的普遍性要求。
现代性自身的矛盾是结构的矛盾,即现代社会的结构既蕴藏着的巨大的发展潜力,也潜伏着不断危及自身的危机。
这个矛盾未能克服。
现代性问题甚多的根源就在于植根于前现代的信念正在消退,例如宗教与道德。
与后现代学者不同的是,他不是解构理性,而是认为必须对理性进行建设性的批判,重建理性(5)。
在这一现代的问题争辩的语境中,法学领域出现了一种反现代的思潮。
法治的传统理念面临挑战。
18世纪的人们坚信体现人类理性的法律能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正的社会。
而在20世纪,即使是我国这样一个尚未现代化的国家也有学者对法治建设的规则模式(6)提出质疑和否定。
如苏力提出,“这种对立法之重视,不仅是由于当年中国知识界的急于求成和天真,过分相信现有的科学知识及其解释力,因而常常以愿望的逻辑完全代替了对具体问题的细致分析,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中国,它具有相当程度的语境化的合理性。
”(7)在他看来,立法的危险“不仅在于近代以来立法一直是同国家的合法暴力相联系,更重要的是一种对于立法者或法学家的理性的过分迷信,将法律等同于立法,同时将那些社会自生的习惯、惯例、规则完全排除在外,视其为封建的、落后的、应当废除和消灭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不利于社会秩序的内部生成和自发调整,社会变成一个仅仅可以按照理性,按照所谓现代化的目标、原则而随意塑造的东西。
”(8)无论是对政府推进型法制,还是对国家立法的怀疑,实际上都涉及如何评价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更进一步说,则涉及如何看待法律的问题,即将法律视为理性的体现,还是把法律仅仅看成不涉及任何价值评价的“规则”和“秩序”。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本文仅试图说明:第一,对国家立法的依赖,根本上是对人的理性能力的依赖;第二,以“秩序”规定法治和法律在不同的语境中有没的含义和意义;第三,法律是国家与社会的媒介,所以法律是一种文化的命题,只包含有限的“真实”性;第四,法治不是一个价值无涉的论域,法学研究不可能保持“价值中立”。
二、立法与理性现代立法与理性、民主的概念联系密切。
但理性与民主却不是两个完全相同的概念。
法治国家的基本精神是理性精神,基于理性的法治是民主价值的保证,而理性的民主制度则是法律价值的体现。
现代社会,国家通过立法全面介入社会生活的合理性源于理性的正当性,换言之,正是由于人们对自身理性能力的确信导致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扩张。
即使有资料表明国家政权的历史悠久,人们也有充分理由认为:现代国家是现代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的产生。
在古代和中世纪,国家生活与民间生活即使不能概括为两个世界,他们之间的联系也远不如今天这么密切,民间生活中有许多国家权力无法也无力触及的领域。
这种状况使民间法在国家法之外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得以发展(9)。
工业革命真正的“革命”意义就在于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变迁。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式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
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10)按马克斯•韦伯的话说,社会生活呈现为合理性状态。
人们开始学会用最经济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
也就是说,人类不仅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使自然界服务于自己的目的,而且也能够领先自己的理性能力控制社会-自己的生活世界。
知识就是力量成为现代的基本“信条”。
人们在注意到资产阶级时期立法的大规模发展的同时,却往往忽略了:正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国家主权理论才开始盛行,主权的、独立的民族国家才开始大量出现(11)。
国家对内职能的强化与立法的发展之间显然存在密切联系,都源于理性的权威化。
人们支持国家权力扩张的一个重要的直接的理由是:现代国家是民主政权。
在民主的社会,尽管制定法律和政策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的活动支配着社会生活,但是,这些机构产生于民主过程,他们的活动,包括制定和实施法律,理论上必须经过人民的同意。
所以,人民所服从的自己的意志和法律。
卢梭的观点可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
在他看来,主权之所以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意志要么是公意,要么不是;要么是人民共同体的意志,要么就只是一部分人的。
在前一种情形下,这种意志一经宣示就成为一种主权行为,并且构成法律。
在第二种情形下,它便只是一种个别意志或者是一种行政行为,至多也不过是一首命令而已,”(12)然而,民主与其他国家形式一样,都是一种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13)。
况且,人民直接参与国家活动的卢梭式构想在大多数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
现代民主主要是代议制民主,即由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来管理国家。
如何使自己所选择的代表始终愿意并能够真正为自己服务,这是一个难题。
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也“对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民主作了最大的颂赞。
因为他们全都用最尖声叫喊的语调坚持他们所支配的制度,不管其外表如何,实际上是‘更高意义的’民主。
”(14)可见,民主本身也是一个有待法律保障的制度。
强调民主面临的挑战并不是否定民主,而是试图说明,国家权力全面介入社会生活的正当性最终源于社会生活的理性化,并由理性的制度设计来保障,而民主恰恰是在这一制度中得到实现的。
国家通过立法方式在从中央到最基层的地方,从如国家权力的组成等“大事”到公民婚姻家庭关系的结构等“小事”等各领域建立全面的制度调控机制。
其“合法性”在于社会生活理性化程度的提高。
因此,面对国家权力的扩张,强调扩大立法的公共参与,或许是必要的,但很难说就是根本的。
国家权力的行使总是少数人的事,国家立法权也总是由少数人实际掌握着,这与国家是民主政体或是专制政体无关,而是国家管理体制的分工(15)。
社会生活的理性化直接表现为广泛的社会分工、知识化和“科学”精神,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确定性程度的提高以及人们把握这种关系的理性能力的提高。
法治则是这种理性化趋势的要求:对国家立法的依赖,根本上是对人的理性能力的依赖。
三、法律与秩序(1)法律与理性的联结考察意味着法律是有明确价值取向的制度设计,法治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价值。
那么,法律与秩序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不能用秩序代替理性来规定法律和法治?法律的目的之一是建立秩序,而秩序本身却不是法律。
在秩序的构成中,法律、公共政策、习惯、惯例等社会规范都可能起作用。
所以,有依法形成的秩序和非依法形成的秩序之分。
依法形成的秩序意味着国家意志在秩序形成过程中具有重大作用,意味着人的理性能力是法治建设的重要保证。
近代以来的国家生活中,法治逐渐取代非依法形成的秩序,正在对人的理性能力的确信。
如果将任何秩序都视为法治,其结果必然是淡化国法与其他社会规范的界限,进而否定或削弱理性在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使“法治”变成与价值选择无关的活动和状态。
秩序客观上具有一定的自发性。
法治和秩序联系起来考察在西方和中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法治最初和在通常意义上都是指“法律的统治”,即领先国法规范社会行为,秩序则是指自然和社会中的某种程序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16)。
哈耶克把社会秩序分为不是生成的就是建构的,前者指“自生自发的秩序”,后者指“组织”或者“人造的秩序”(17),并认为“那种认为人已经拥有了一种构设文明的心智能力、从而应当按其调计创造文明的整个观念,基本上是一种谬误。
”(18)真正的秩序只能是适应性进化的结果,而不是人预先设计的。
卡尔•波普也认为,人不能对社会进行整体上的有意识的设计,现实的社会秩序经常是超乎人的理性的预期的(19)。
应该注意到,哈耶克并不是否定理性,如他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并不是要废弃理性,而是要对理性得到确当控制的领域进行理性的考察。
这个论点的一部分含义是指,如此明智地运用理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在尽可能多的场合中运用主观设计的理性。
”(20)哈耶克关于理性的观点与他关于法治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他看来,法“我们必须维护那个不受控制的、治的核心是个人自由,理性的发展也取决于个人自由,因此,理性不及的领域;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因为正是这个领域,才是理性据以发展和据以有效发挥作用的惟一环境。
”(21)在哈耶克那里,法治是西方社会秩序的文化进化的因素和组成部分。
而在我国,情况则完全不同。
我国的“本土资源”中没有西方意义的“法治”,甚至也没有作为法治和理性基础的个人自由。
法治是外来的,一定意义上是被动的,与自发秩序是对立的。
在这样的语境中,过分强调法治建设中的本土资源和秩序的自发性,必然是或者导致否定法治的结论,或者赋予法治和法律不同的解释-使其中国化的解释。
我国有的学者正是这样分析问题的。
“我不主张把法律视为一种抽象的、理想化的价值或体现了这样的价值的条文,而更倾向于从社会学角度来理解法律,把法律理解为与人们的具体现实的生活方式无法分离的一种规范性秩序。
”“中国有久远的、相对独立的发展史,并演化了自己的法律制度,尽管这些法律制度依据西方标准看来未必是‘法律的’……我认为,在中国的法治追求中,也许最重要的并不是复制西方法律制度,而是重视中国社会中的那些起作用的,也许并不起眼的习惯、惯例,注生经过人们反复博弈而证明有效有用的法律制度。
”(22)如此一来,法治问题的讨论就主要不是如何运用法律形成一个与我国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秩序,而是如何放任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秩序的自发性。
苏力先生从秋菊的困惑、山杠爷的悲剧到破产法的困境中,巧妙地指出了中国民间的自发的秩序的强大力量和普通公民对传统的心理认同,尽管分析存在漏洞,但仍然富有启发性,至少说明了法律的制定与法在社会中的实现是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