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作品中独特的生命意识第1期
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悲剧意识与生命意识解读

摘要:萧红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基于自身曲折的情感经历和漂泊的生命体验,在民族苦难的大背景下,终身不停地探索人的生命意识、叩问女性的悲剧命运,给后世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萧红,女性意识,悲剧意识,生命意识一、女性意识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把男性设定为“自我”,把女性设定为“他者”,她指出女性摆脱“他者”处境的途径在于取得经济独立、社会制度的变更,以及两性和谐关系的建立。
而萧红生活的大环境,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东北落后的农村,在这样一个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背景下,女性要背负阶级剥削、男权社会的性别压迫、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不可能有平等的政治人格、独立的经济能力,在婚姻里多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在萧红真实的生活里,她童年时期感受着父亲的冷漠;不喜欢未婚夫王恩甲的恶俗而逃婚,又不得不囿于现实与他同居至怀孕被丢弃于旅馆;和萧军相爱相杀,情感的纠缠、理想的背离、生下孩子被迫送人的苦楚——这些往事的印痕,在她的小说里都有不同形态的呈现,比如《生死场》中,金枝未婚先孕后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对自己一天天胀大起来的肚子产生了恐惧。
这何尝不是萧红怀孕后,被未婚夫抛弃在旅馆里的恐惧情绪的真实写照呢?这种来自作者女性身份的真实体验,使得文字饱满而生动,有生命的张力。
小说中,五姑姑的姐姐难产时,丈夫不但咒骂她、用长烟袋来砸她,还端来一大盆凉水泼向她。
生孩子对于女人变成了一种酷刑。
萧红还多处描写动物繁殖,这暗示女人生育和动物一般毫无尊严,更突出了女性受到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
回望萧红的两次生育经历,根本没有幸福喜悦可言,她体味的是一个女人最深切的折磨与痛楚, 所以,她对男权中心社会强加给女人的那些冷漠、摧残、迫害与不公,有着不自觉的抗争。
这种抗争,是在经历过一次次情感伤害之后的彻悟,那就是:在男权、夫权的重压下,女人们没有生命价值可言,也没有生育自主权,尽管萧红不知道明确的出路,但是对妇女问题的思考与叩问,已经难得可贵。
论萧红小说中的生命意识

论萧红小说中的生命意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之一,萧红的小说中不断探讨着人类的生命意识。
她描写的笔墨各异的人物,无不具备着对于生命的探求和认知。
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生命的眷恋、对于生存价值的思考、对于爱情的执着等等,都在小说中得到了恰当的体现。
先说,对于生命的眷恋。
萧红的小说中,有很多人物都深刻地表现了对于生命的热爱和眷恋,这种眷恋来自于对于自己的存在的感受和对于他人的关爱。
《生死场》中,那些妇女们在绝望中依然献身于爱情、母爱和互相生死相托,确实感人至深。
而《朝花夕拾》中的讲述父亲因为为了医治女儿而卖了活鸟的故事,也表达了对于生命的珍视,这种珍视在萧红小说中不断出现,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桂花树。
桂花树的枝头上,虽然没有花儿,但是因为树干上的虫子而继续发芽。
只有这样的生命才能存活下去,这其中蕴含着对于生命的热爱和珍视。
其次,对于生存价值的思考。
萧红小说中,很多人物都在探究着生存的意义和生存的价值,这种思考虽然常常被伤害和挫折所打击,但是小说中的人物们总是在坚持探究着,寻找一份希望。
《游泳》中,主人公游泳的过程不仅是对于自己生命价值的认知,同时也表明了对于生命的敬畏和探究。
在《落花梦》中,《萝卜》中,《乌审旗》中的人物们同样在寻找着生存的价值,探索着存在的意义。
在这种寻找和探索中,人物们虽然承受了很多的痛苦,但是却不放弃。
最后,对于爱情的执着。
萧红小说中,很多人物都执着于爱情。
这种爱情的执着常常是一种深深的感情的沉淀,在很多时候是值得我们赞赏的。
在《一个女剩客》中,女主人公王秀梅虽然多次遭受生活的打击,但是在母亲的殷切要求下,她还是选择了嫁给了大龄剩男,因为仅仅这份爱情,就足以让她感到幸福。
在《胡杨的夏天》中,撤退的女兵们同样抱着对于爱情的执着,她们在战火中寻找着爱情,用爱情温暖彼此的生命。
萧红小说中的生命意识,不同人物的探讨不尽相同,但是无一不是对于生命的探究和认知。
论萧红作品中的生命意识——以《呼兰河传》《生死场》为例 汉语言文学专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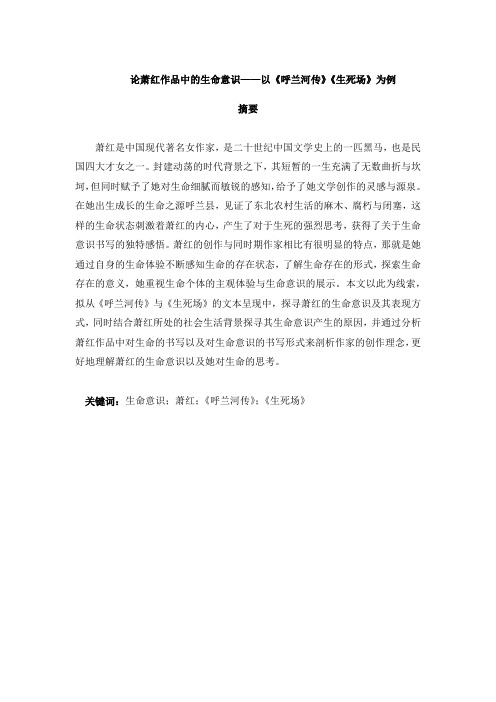
论萧红作品中的生命意识——以《呼兰河传》《生死场》为例摘要萧红是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匹黑马,也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
封建动荡的时代背景之下,其短暂的一生充满了无数曲折与坎坷,但同时赋予了她对生命细腻而敏锐的感知,给予了她文学创作的灵感与源泉。
在她出生成长的生命之源呼兰县,见证了东北农村生活的麻木、腐朽与闭塞,这样的生命状态刺激着萧红的内心,产生了对于生死的强烈思考,获得了关于生命意识书写的独特感悟。
萧红的创作与同时期作家相比有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她通过自身的生命体验不断感知生命的存在状态,了解生命存在的形式,探索生命存在的意义,她重视生命个体的主观体验与生命意识的展示。
本文以此为线索,拟从《呼兰河传》与《生死场》的文本呈现中,探寻萧红的生命意识及其表现方式,同时结合萧红所处的社会生活背景探寻其生命意识产生的原因,并通过分析萧红作品中对生命的书写以及对生命意识的书写形式来剖析作家的创作理念,更好地理解萧红的生命意识以及她对生命的思考。
关键词:生命意识;萧红;《呼兰河传》;《生死场》On the Life Consciousness in Xiao Hong's Works:Take Hulan River Biography and Life and Death Field as anexampleAbstract: Xiao Hong is a famous modern Chinese female writer, a dark hors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one of the four talented wome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the feudal turbulent times, her short life was full of countless twists and turn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gave her a delicate and keen perception of life, and gave her the inspiration and source of literary creation. In Hulan County, the source of life where she was born and grown, she witnessed the numbness, decay and obstruction of rural life in the Northeast. Such a state of life stimulated Xiao Hong's heart, produced a strong thinking about life and death, and gained a unique writing about life consciousness. Sentiment. Xiao Hong’s creation is unique from the writers of the same period, that is, she constantly perceives the existence of life through her own life experience, understands the form of life existence, and explores the meaning of life existence. She values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and life of individual life. A display of consciousness. Taking this as a clue,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Xiao Hong's life consciousness and its expression methods from the textual presentations of "Hulan River Biography" and "Life and Death Field", and at the same time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Xiao Hong's life consciousnes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Xiao Hong's social life , And analyze the author’s creative concept by analyzing the writing of life and the writing form of life consciousness in Xiao Hong’s works, so as to better understand Xiao Hong’s life consciousness and her thinking about life.Key words: Life Consciousness; Xiao Hong; "Hulan River Biography"; "Life and Death Field"目录引言一、生命意识与中国新文学小说创作的源流(一)西方现代生命哲学的起源(二)中国新文学小说发展过程中生命意识的觉醒二、萧红作品中对生命的书写(一)原始的生命动力(二)生命的悲剧意识(三)孱弱的女性地位三、生命意识的书写形式(一)情绪体验式的创作(二)意象化的叙事手法四、萧红生命意识形成的原因(一)充满抗争的时代背景(二)饱含激昂的地域文化(三)遭受曲折的生命体验五、结语参考文献致谢论萧红作品中的生命意识——以《呼兰河传》《生死场》为例引言被誉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萧红曾经在文艺界掀起过巨大的波澜,众多学者也曾多方面的去调查并且研究萧红创作的灵感源泉,通过回溯其经历过的历史背景以及时代环境等方面。
浅谈萧红作品中的孤独意识与生命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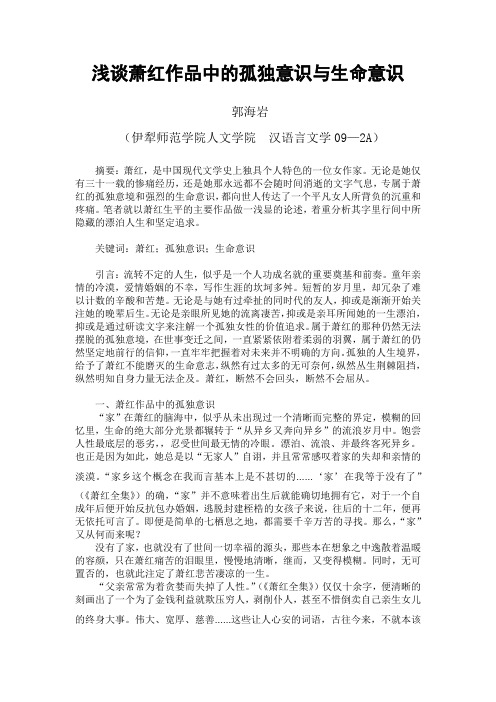
浅谈萧红作品中的孤独意识与生命意识郭海岩(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09—2A)摘要: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个人特色的一位女作家。
无论是她仅有三十一载的惨痛经历,还是她那永远都不会随时间消逝的文字气息,专属于萧红的孤独意境和强烈的生命意识,都向世人传达了一个平凡女人所背负的沉重和疼痛。
笔者就以萧红生平的主要作品做一浅显的论述,着重分析其字里行间中所隐藏的漂泊人生和坚定追求。
关键词:萧红;孤独意识;生命意识引言:流转不定的人生,似乎是一个人功成名就的重要奠基和前奏。
童年亲情的冷漠,爱情婚姻的不幸,写作生涯的坎坷多舛。
短暂的岁月里,却冗杂了难以计数的辛酸和苦楚。
无论是与她有过牵扯的同时代的友人,抑或是渐渐开始关注她的晚辈后生。
无论是亲眼所见她的流离凄苦,抑或是亲耳所闻她的一生漂泊,抑或是通过研读文字来注解一个孤独女性的价值追求。
属于萧红的那种仍然无法摆脱的孤独意境,在世事变迁之间,一直紧紧依附着柔弱的羽翼,属于萧红的仍然坚定地前行的信仰,一直牢牢把握着对未来并不明确的方向。
孤独的人生境界,给予了萧红不能磨灭的生命意志,纵然有过太多的无可奈何,纵然丛生荆棘阻挡,纵然明知自身力量无法企及。
萧红,断然不会回头,断然不会屈从。
一、萧红作品中的孤独意识“家”在萧红的脑海中,似乎从未出现过一个清晰而完整的界定,模糊的回忆里,生命的绝大部分光景都辗转于“从异乡又奔向异乡”的流浪岁月中。
饱尝人性最底层的恶劣,,忍受世间最无情的冷眼。
漂泊、流浪、并最终客死异乡。
也正是因为如此,她总是以“无家人”自诩,并且常常感叹着家的失却和亲情的淡漠。
“家乡这个概念在我而言基本上是不甚切的……‘家’在我等于没有了”(《萧红全集》)的确,“家”并不意味着出生后就能确切地拥有它,对于一个自成年后便开始反抗包办婚姻,逃脱封建桎梏的女孩子来说,往后的十二年,便再无依托可言了。
即便是简单的七栖息之地,都需要千辛万苦的寻找。
那么,“家”又从何而来呢?没有了家,也就没有了世间一切幸福的源头,那些本在想象之中逸散着温暖的容颜,只在萧红痛苦的泪眼里,慢慢地清晰,继而,又变得模糊。
论萧红作品中的死亡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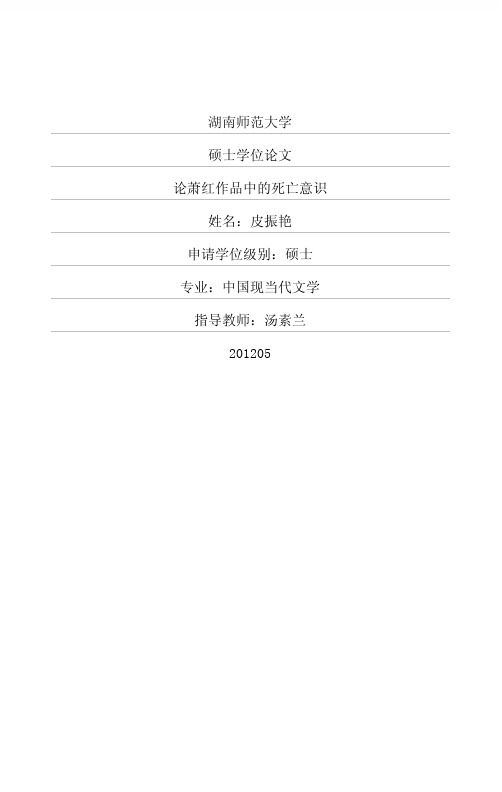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论萧红作品中的死亡意识姓名:***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指导教师:***201205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一位颇具鲜明个性的女作家。
她一生来去匆匆,不足十年的创作生涯,却奉献给世人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这显示了她非凡的创作生命力,鲁迅称萧红为“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之一”①。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多元化趋势,萧红作品也以其视角的丰富、多方位而被纳入更加广阔的研究范围,纵观前人的研究成果,对萧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萧红的身世和人生情感的考证;二、对萧红作品的解读和再评价,主要是从悲剧意识和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
本文拟从死亡意识这个研究者较少涉及的角度入手,以文本解读为主,死亡哲学为辅的研究方法,细致分析萧红作品中存在的两种类型的死亡形式,重点阐释萧红作品死亡意识的四种呈现方式,从而归纳这些呈现方式下所隐藏的死亡观,并进一步挖掘萧红作品中死亡书写的价值意义,以期对萧红的研究做一些有益的补充。
论文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介绍萧红的作品和萧红研究的总体情况,以及本课题的创新之处。
第二部分是本论文的研究基础,阐述死亡意识的定义及其形成,进而探讨死亡意识之于文学、作家的关系。
①王观泉.怀念萧红[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17.I第三部分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分析萧红作品中的死亡意识。
萧红对死亡意识的书写,主要是从蝼蚁般的死亡、飞蛾扑火般的死亡、掘墓与超生这三方面来叙写的。
根据死亡形式的类型,重点阐释死亡意识在作品中的四种呈现方式。
第四部分是萧红作品死亡书写的意义探寻。
萧红通过书写各种类型的死亡,一方面对男权社会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揭露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最后在浓郁的死亡背景下反思人性,对人的生存价值进行深入思考。
第五部分是结语。
再次提出把握萧红作品中的死亡意识对于完整解读萧红作品、正确认识萧红在现代文学史中地位的重要性。
浅析萧红作品中的生命意识

浅析萧红作品中的生命意识作者:李娜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12期摘要:萧红的小说为我们展示了东北这块黑土地上的生存景观和文化生态,蕴涵着深厚的感情,她抓住了“生”和“死”—人生中的起点与终点这两个重要环节,对人们的死亡意识和生命意识进行了深刻地剖析和突出地展现。
关键词:萧红;生命意识;[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2-0-01一、麻木混沌的生与死萧红抓住“生”和“死”这两个最重要的生命环节来描写乡村里不能逃遁的生命循环,在文明和愚昧的对立中,小人物们都像是从极古远的过去一直这样活过来的,“浪费”似的生存,随意地死亡,这生和死的麻木使她心痛并且心怀悲悯。
(一)无聊寂寞的生萧红的代表作《呼兰河传》和《生死场》把“呼兰河畔”和“生死场上”的生和死对比来写,表现了当时人们状态的异化,展现的是旧中国的儿女们在无意识的空间里“蚊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就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的前线。
蚊子似的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的为生而死了”的生存状态。
“生命为什么不挂着铃子?不然丢了你,怎能感到有所亡失。
”在一个人短暂的生命过程里,“生”是一种自然现象,“死”同样也是自然现象,它们都是大自然的结果。
生命的意义,在于知道自己这样活着是为了什么,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正如马克思所说:“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
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对象,他们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存在物。
”(二)浑浑噩噩的死除了描写那时候的北方人民没有任何意识的生存状况,萧红对“生”的另一个方面“死”还作了一些叙述,描述了他们对待死亡的态度,这揭示了那时候人们生和死的没有价值。
海德格尔曾说过:“日常生活就是生和死之间的存在。
”《生死场》的第十章《十年》中有这样写道,“十年前村中的山,山下的小河,而今依旧似十年前。
浅论萧红小说的生命意识与艺术缺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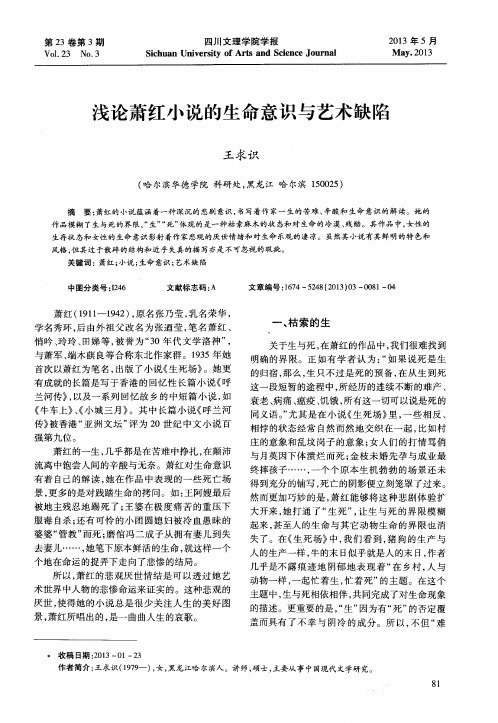
的归 宿 , 那 么, 生 只 不 过 是死 的预 备 , 在 从 生 到死 这一 段短 暂 的途程 中 , 所 经历 的连续不 断 的难 产 、 衰老 、 病痛 、 瘟疫 、 饥饿 , 所有 这一 切可 以说 是死 的 同义 语 。 ” 尤其是在小说《 生死 场 》 里, 一些相反 、
相悖 的状 态 经 常 自然 而 然 地 交 织在 一 起 , 比如 村
庄 的意象 和乱 坟 岗子 的意 象 ; 女 人 们 的 打情 骂 俏 与月 英 因下体 溃烂 而 死 ; 金 枝 未 婚 先 孕 与成 业 最 终摔 孩子 … … , 一 个 个原 本 生 机勃 勃 的场 景 还 未 得到 充分 的铺 写 , 死 亡 的 阴影 便立 刻笼 罩 了过 来 。 然而更 加 巧妙 的是 , 萧 红 能 够 将 这 种 悲剧 体 验 扩 大开来 , 她 打通 了 “ 生死 ” , 让 生 与 死 的界 限 模 糊 起来 , 甚至 人 的生 命 与 其 它 动 物 生命 的界 限也 消
作者简介 : 王求识( 1 9 7 9 一) , 女, 黑龙 江哈 尔滨人 。讲 师 , 硕 士, 主要从事 中国现代 文学研 究。
81
2 0 1 3年第 3期
王求识 : 浅论萧红小说 的生命 意识 与艺术缺 陷
产、 衰老、 病痛 、 瘟疫 、 饥饿 ” 是 死 的 同义 语 , “ 生”
服毒 自杀 ; 还 有 可怜 的小 团 圆媳 妇 被 冷 血 愚 昧 的
婆婆“ 管教” 而死 ; 磨倌冯二成子从拥有妻J L N失 去妻儿…… , 她笔下原本鲜活的生命 , 就这样一个 个 地 在命 运 的捉弄 下走 向了悲惨 的结局 。 所 以, 萧红 的悲 观厌 世 情 结 是 可 以 透 过 她 艺
生命意识与萧红小说创作研究

生命意识与萧红小说创作研究一、本文概述《生命意识与萧红小说创作研究》旨在深入探索萧红小说创作中的生命意识及其表达。
萧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女作家,以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感悟,赋予其作品深刻而丰富的内涵。
本文将从萧红的生平经历、创作背景、作品主题等方面入手,全面梳理和解析其小说创作中的生命意识,以期对萧红作品的艺术价值和人文内涵有更深入的理解。
本文将回顾萧红的生平经历,特别是她的成长环境和人生遭遇,这些经历无疑对她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后,我们将分析萧红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文学环境,探讨这些外部因素如何与她的生命意识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她独特的创作风格。
接着,本文将重点解读萧红小说中的生命意识。
我们将通过细读文本,分析她如何在作品中描绘生命的苦难与坚韧、挣扎与抗争,以及她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和追问。
我们还将关注萧红如何通过艺术手法和叙事策略,将生命意识融入作品的结构和语言中,从而使其作品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本文将对萧红小说创作中的生命意识进行总结和评价,指出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并探讨其对于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启示意义。
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希望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作品的人文内涵和艺术价值,同时也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二、萧红生命意识的形成萧红生命意识的形成,离不开她独特的生活经历与深刻的社会洞察。
她的生命意识,一方面源于她个人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另一方面则深受她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萧红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然而家庭的冷漠和封建礼教的束缚使她在成长过程中深感压抑。
这种家庭环境让她对个体的生命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反思,也使她在后来的创作中,常常以女性视角探讨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同时,萧红在成长过程中也经历了多次生活的变故,如家庭的破产、亲人的离世等,这些经历使她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和脆弱。
她在这些经历中开始思考生命的真谛,这也为她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深刻的素材和灵感。
论萧红的“生死文学”

论萧红的“生死文学”王晶晶辽宁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学院摘要:萧红的一生承载了太多的苦难,在她营造的艺术世界里饱含丰富的悲剧意蕴。
萧红把自己的不幸与苦难、不堪忍受与自己的希望写进作品,批判与揭露自己和别人的不幸,控诉着时代的悲哀,寄托自己的理想。
而她文章中体现的独特的且强烈的“生死观”从一个个鲜活的女性角色的生活悲剧中展现的淋漓,观之触目惊心,在那个麻木与黑暗交织的时代,萧红用“女人的血”似乎“轻而易举”的就描绘出了一场场生死,一场场轮回。
萧红用她的文章把“生死”就那样几乎残忍的端到读者眼前,让读者细品那个年代那个女性地狱的生死之味。
关键词:萧红;生死文学;女性意识一、萧红作品中独特的“生死文学”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6月1日(阴历五月初五)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母亲姜玉兰是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人,父亲张延举自私而残酷,张家大院对男性子嗣期待已久,可萧红偏偏是个女孩子,同家庭期望相悖的女儿身份,注定了她一生的不幸。
萧红跌宕起伏的生命体验让她对生死有了独特的体验与解读。
这种“生死文学”的创作方式主要体现在人们的生存方式、封建思想的揭示和对死亡的独特描写上。
萧红有对生命的独特的悲剧化理解,即“我们出生即决定了有一天会死亡,而这生与死之间的过程充斥着苦难与困境”。
而萧红小说的深刻内涵不仅表现在阶级压迫、封建礼教等方面,更体现在对生死问题的深切关注和独特体验上。
在她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关于生命本身的探索,而她笔下的人物也都如同她的命运一般在压迫下完成了从生到死的过程。
通过对生死问题的描绘来启示人们探索生命的意义和生与死的价值。
《生死场》中有这样一段描写:金枝因为错摘了青柿子,惹怒了母亲踢打起来,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
农家无论是菜棵或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
王婆将不幸摔倒在犁上的女儿小钟扔在草堆上,眼睁睁地看着女儿流血而死。
“小手颤颤着,血在冒着气从鼻子里流出,从嘴也流出”,“孩子死,不算一回事,你们以为我会暴跳着哭吧?我会嚎叫吧。
浅论萧红生命意识变化: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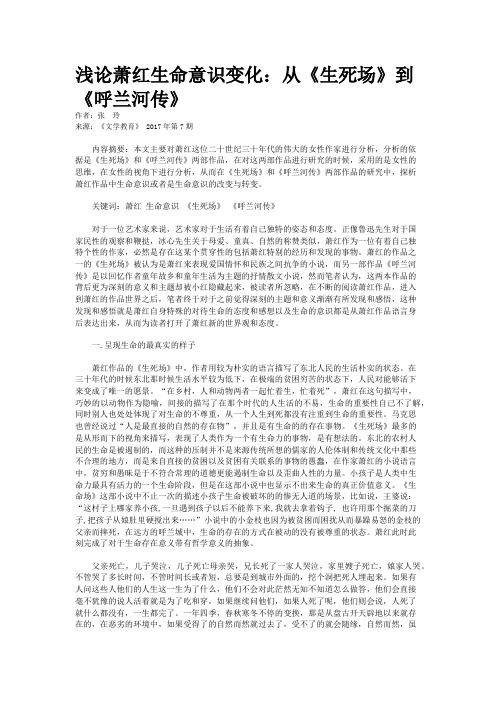
浅论萧红生命意识变化: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作者:张玲来源:《文学教育》 2017年第7期内容摘要:本文主要对萧红这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伟大的女性作家进行分析,分析的依据是《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两部作品,在对这两部作品进行研究的时候,采用的是女性的思维,在女性的视角下进行分析,从而在《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两部作品的研究中,探析萧红作品中生命意识或者是生命意识的改变与转变。
关键词:萧红生命意识《生死场》《呼兰河传》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艺术家对于生活有着自己独特的姿态和态度。
正像鲁迅先生对于国家民性的观察和鞭挞,冰心先生关于母爱、童真、自然的称赞类似,萧红作为一位有着自己独特个性的作家,必然是存在这某个贯穿性的包括萧红特别的经历和发现的事物。
萧红的作品之一的《生死场》被认为是萧红来表现爱国情怀和民族之间抗争的小说,而另一部作品《呼兰河传》是以回忆作者童年故乡和童年生活为主题的抒情散文小说,然而笔者认为,这两本作品的背后更为深刻的意义和主题却被小红隐藏起来,被读者所忽略,在不断的阅读萧红作品,进入到萧红的作品世界之后,笔者终于对于之前觉得深刻的主题和意义渐渐有所发现和感悟,这种发现和感悟就是萧红自身特殊的对待生命的态度和感想以及生命的意识都是从萧红作品语言身后表达出来,从而为读者打开了萧红新的世界观和态度。
一.呈现生命的最真实的样子萧红作品的《生死场》中,作者用较为朴实的语言描写了东北人民的生活朴实的状态。
在三十年代的时候东北那时候生活水平较为低下,在极端的贫困穷苦的状态下,人民对能够活下来变成了唯一的愿景。
“在乡村,人和动物两者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萧红在这句描写中,巧妙的以动物作为隐喻,间接的描写了在那个时代的人生活的不易,生命的重要性自己不了解,同时别人也处处体现了对生命的不尊重,从一个人生到死都没有注重到生命的重要性。
马克思也曾经说过“人是最直接的自然的存在物”,并且是有生命的的存在事物。
论萧红的“生死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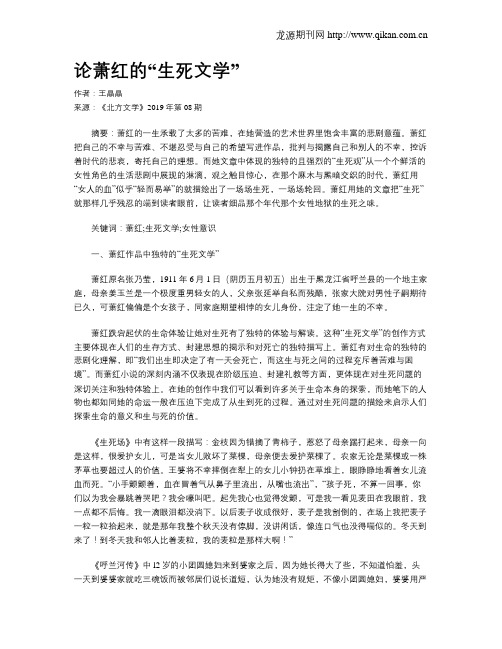
论萧红的“生死文学”作者:王晶晶来源:《北方文学》2019年第08期摘要:萧红的一生承载了太多的苦难,在她营造的艺术世界里饱含丰富的悲剧意蕴。
萧红把自己的不幸与苦难、不堪忍受与自己的希望写进作品,批判与揭露自己和别人的不幸,控诉着时代的悲哀,寄托自己的理想。
而她文章中体现的独特的且强烈的“生死观”从一个个鲜活的女性角色的生活悲剧中展现的淋漓,观之触目惊心,在那个麻木与黑暗交织的时代,萧红用“女人的血”似乎“轻而易举”的就描绘出了一场场生死,一场场轮回。
萧红用她的文章把“生死”就那样几乎残忍的端到读者眼前,让读者细品那个年代那个女性地狱的生死之味。
关键词:萧红;生死文学;女性意识一、萧红作品中独特的“生死文学”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6月1日(阴历五月初五)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母亲姜玉兰是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人,父亲张延举自私而残酷,张家大院对男性子嗣期待已久,可萧红偏偏是个女孩子,同家庭期望相悖的女儿身份,注定了她一生的不幸。
萧红跌宕起伏的生命体验让她对生死有了独特的体验与解读。
这种“生死文学”的创作方式主要体现在人们的生存方式、封建思想的揭示和对死亡的独特描写上。
萧红有对生命的独特的悲剧化理解,即“我们出生即决定了有一天会死亡,而这生与死之间的过程充斥着苦难与困境”。
而萧红小说的深刻内涵不仅表现在阶级压迫、封建礼教等方面,更体现在对生死问题的深切关注和独特体验上。
在她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关于生命本身的探索,而她笔下的人物也都如同她的命运一般在压迫下完成了从生到死的过程。
通过对生死问题的描绘来启示人们探索生命的意义和生与死的价值。
《生死场》中有这样一段描写:金枝因为错摘了青柿子,惹怒了母亲踢打起来,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
农家无论是菜棵或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
王婆将不幸摔倒在犁上的女儿小钟扔在草堆上,眼睁睁地看着女儿流血而死。
试论萧红创作的生命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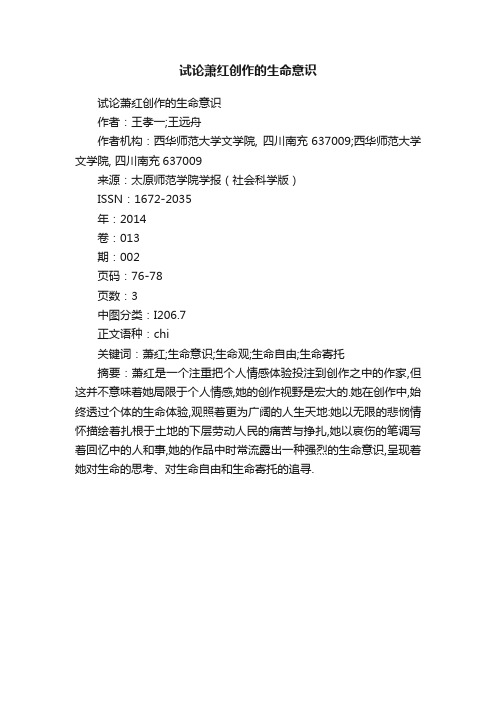
试论萧红创作的生命意识
试论萧红创作的生命意识
作者:王孝一;王远舟
作者机构: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南充637009;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南充637009
来源: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ISSN:1672-2035
年:2014
卷:013
期:002
页码:76-78
页数:3
中图分类:I206.7
正文语种:chi
关键词:萧红;生命意识;生命观;生命自由;生命寄托
摘要:萧红是一个注重把个人情感体验投注到创作之中的作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局限于个人情感,她的创作视野是宏大的.她在创作中,始终透过个体的生命体验,观照着更为广阔的人生天地:她以无限的悲悯情怀描绘着扎根于土地的下层劳动人民的痛苦与挣扎,她以哀伤的笔调写着回忆中的人和事,她的作品中时常流露出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呈现着她对生命的思考、对生命自由和生命寄托的追寻.。
论萧红作品中的生命书写与生存追问

论萧红作品中的生命书写与生存追问摘要萧红作品具有浓厚的生命意识,生命书写与生存追问是其创作的重要内容。
她常将人和物置于一个独特的时空坐标中,以封闭循环的时空描写人物命运,用开放发展的时空描写自然风貌,来表现自己对生命的思考与关注。
萧红尤其擅长写人,特别是儿童、女人和男人。
她描写了三种不同的儿童形象,即最纯粹的儿童、被伤害的儿童以及已异化的儿童。
她从自身的女性经验出发,思考女性的生命价值。
认为女性的生育和女性的身份得不到男权社会的公平对待,是女性悲剧的根源。
她抨击男权社会,笔下有各式各样的男性,唯独欠缺一个能够顶天立地的男性形象。
在不同人的描写中,体现出萧红对人的特别关怀。
萧红认为人的原始生命力和来源于人心底的爱,是人克服生存困境的最根本力量。
萧红关注民间生活,她知悉民间思想对大众具有操控性,希望消除民间思想中的糟粕,呼唤“五四”精神。
关键词:萧红;生命书写;生存追问On the Description of Life and the Inquiry aboutSurvival in Xiao Hong's WorksABSTRACTXiao Hong's works possess the intense life consciousness. The description of life and the inquiry about survival are important contents of her works. She always places people and things in a unique space-time coordinate, in order to use a closed cycle space-time coordinate to describe the fate of characters and use an open develop space-time coordinate to describe the natural landscape, which to express her thoughts and concerns about life.Xiao Hong is especially good at describing people which are children, women and men. She describes three kinds of different children images who are the purest children, the injured children and the alienated children. She thinks about the value of women's life from her own female experience. The origin of women's tragedy is that there is no fair treatment for female fertility and identity in male-dominated society. She criticized the male-dominated society. She describes every kind of men, but only lack image of a stand-up man. Xiao Hong's works possess the intense consciousness of life. It shows that Xiao Hong is particularly concerned about people. She believes that the primitive vitality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love from the bottom of heart are the most fundamental force to overcome the plight of human existence.Xiao Hong focuses on the folk life and she knows that the nongovernmental ideological control the public. She wants to eliminate the dross in the folk thought and calls for the May Fourth spirit.Keywords:Xiao Hong, Description of Life, Inquiry about Survival目录摘要 (3)ABSTRACT (4)第一章绪论 (6)1.1选题缘由 (6)1.2文献综述 (7)1.3研究方法 (8)第二章人生体验与萧红作品中的生命意识 (9)2.1童年经验与萧红自身生命意识的确立 (9)2.2“无家情结”与萧红作品中的生命意识 (12)第三章萧红作品对生命的书写 (15)3.1时空体形式下的生命书写 (15)3.1.1封闭循环的时空与人物命运 (16)3.1.2开放发展的时空与自然风貌 (17)3.2萧红作品对人的开掘 (18)3.2.1三种不同的儿童形象 (18)3.2.2女性悲剧的根源 (20)3.2.3懦弱的“掌权”之人 (22)第四章萧红作品对生存的追问 (25)4.1女性生存意义的追问 (25)4.2生存困境中生存意义的追问 (27)4.2.1 生存困境中人所迸发的原始生命力 (27)4.2.2生存困境中人源于心底的爱 (29)4.3中国民间思想对人生存影响的追问 (31)4.3.1民间思想对人生存的影响 (32)4.3.2回归人文关怀,探寻生存之路 (34)结语 (37)参考文献 (38)读研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40)后记 (41)第一章绪论萧红的作品以人和生存作为关注点,她写活了生命,写绝了生存。
独具魅力的萧红及其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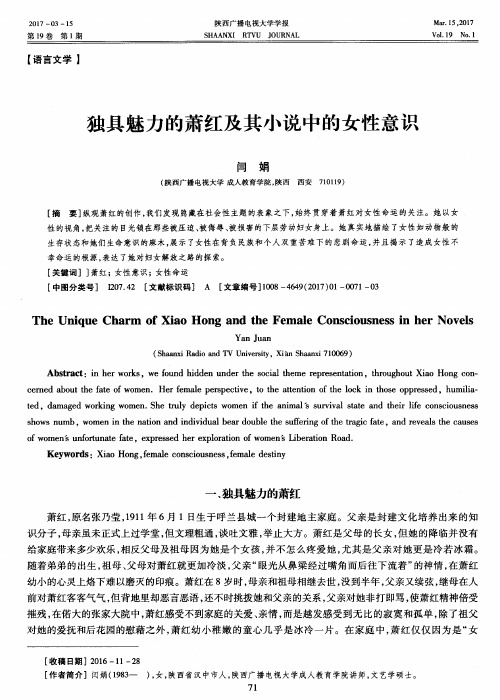
随着弟弟 的出生 , 祖母 、 父母对萧红就更加冷淡 , 父亲“ 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 ” 的神情 , 在萧红
幼 小 的心 灵上 烙下 难 以磨 灭 的印痕 。萧 红在 8岁 时 , 母亲 和祖 母相 继 去世 , 没 到半年 , 父 亲又 续 弦 , 继母 在 人
幸命运 的根 源 , 表达 了她 对妇女解放之路 的探 索。 [ 关键词 】] 萧红 ; 女性 意识;女性命运 [ 中图分 类号] I 2 0 7 . 4 2 [ 文献标识 码] A [ 文章编号 ] 1 0 0 8— 4 6 4 9 ( 2 0 1 7 ) 0 1— 0 0 7 1 — 0 3
o f wo me ng u n f o r t u na t e f a t e,e x pr e s s e d h e r e x p l o r a t i o n o f wo me ng L i b e r a t i o n Ro a d. Ke y wo r d s:Xi a o Ho n g, f e ma le c o n s c i o us n e s s, f e ma le d e s t i n y
s h o ws n u mb,w o me n i n t h e n a t i o n a n d i n d i v i d u a l b e a r d o u b l e t h e s u f f e r i n g o f t h e t r a g i c f a t e,a n d r e v e a l s t h e c a u s e s
探寻萧红书写中的生命意识与书写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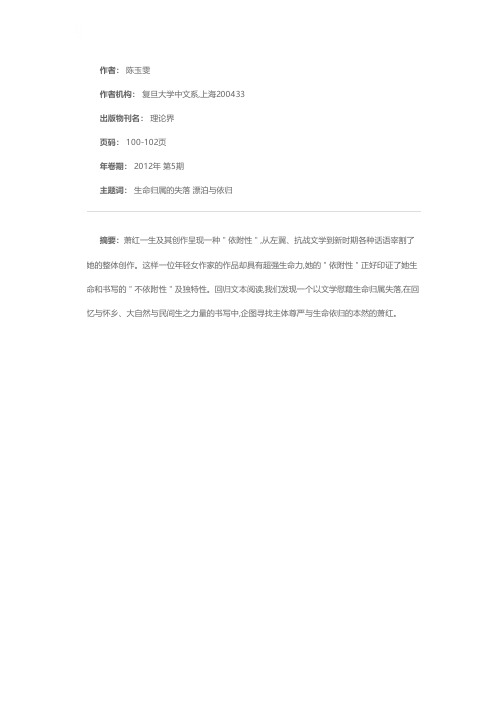
作者: 陈玉雯
作者机构: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出版物刊名: 理论界
页码: 100-102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5期
主题词: 生命归属的失落 漂泊与依归
摘要:萧红一生及其创作呈现一种"依附性",从左翼、抗战文学到新时期各种话语宰割了她的整体创作。
这样一位年轻女作家的作品却具有超强生命力,她的"依附性"正好印证了她生命和书写的"不依附性"及独特性。
回归文本阅读,我们发现一个以文学慰藉生命归属失落,在回忆与怀乡、大自然与民间生之力量的书写中,企图寻找主体尊严与生命依归的本然的萧红。
论萧红小说中的生命意识

作者: 韩雅
作者机构: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3
出版物刊名: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页码: 72-76页
年卷期: 2015年 第1期
主题词: 萧红小说 生命意识 生死观 女性命运 生命悲剧
摘要:生命意识是个体生命对于自身存在及其意义和价值的认知和感悟,体现在萧红的小说中,它表现为对自然景物的喜爱与赞美,对种种生命形态的细致描摹,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悲悯以及对荒凉人生命运的感叹。
进一步来说,则是对自由美好的生存状态的向往,对麻木自私人性的敏锐洞悉,对社会人生的深切反思。
正是通过对种种充满原生态意味的生命形态的描写,作品不仅实现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与反思,更通过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思索,达到了对整个人类生存意义的文化观照。
论萧红小说中的生命意识

作者: 肖海凤
作者机构: 白城师专
出版物刊名: 白城师范学院学报
页码: NULL-NULL页
主题词: NULL
摘要: 萧红在其小说中关注人们普遍的精神病态和中国人最根本的生与死的问题,她的生命意识充分体现了她的人生价值观,并通过小说的形式呈现给人们对生命的热爱。
一、萧红对生命冷静而悲观的思考正是自己对生命爱到极点的一种背向表示 在她的作品中经常看到她对于充满生命力的大自然的珍爱。
萧红笔下的花草树木都有声响,虫蝶蜂鸟都会说话,风云雷电都有颜色。
她感受着这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大自然。
并以丰富。
试论萧红小说《生死场》中的生命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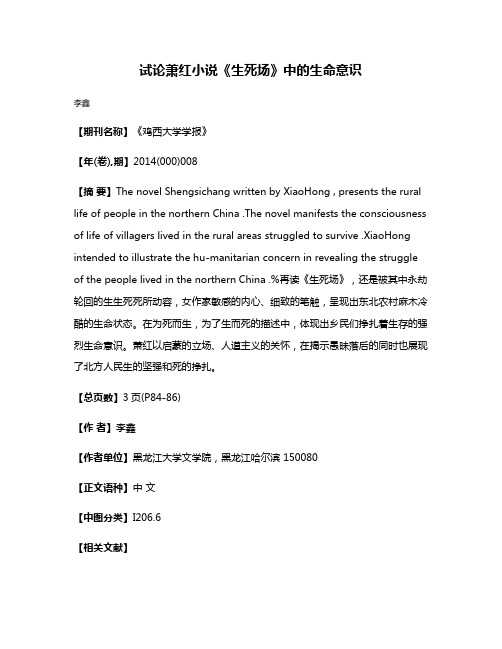
试论萧红小说《生死场》中的生命意识李鑫【期刊名称】《鸡西大学学报》【年(卷),期】2014(000)008【摘要】The novel Shengsichang written by XiaoHong , presents the rural life of people in the northern China .The novel manifests the consciousness of life of villagers lived in the rural areas struggled to survive .XiaoHong intended to illustrate the hu-manitarian concern in revealing the struggle of the people lived in the northern China .%再读《生死场》,还是被其中永劫轮回的生生死死所动容,女作家敏感的内心、细致的笔触,呈现出东北农村麻木冷酷的生命状态。
在为死而生,为了生而死的描述中,体现出乡民们挣扎着生存的强烈生命意识。
萧红以启蒙的立场、人道主义的关怀,在揭示愚昧落后的同时也展现了北方人民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
【总页数】3页(P84-86)【作者】李鑫【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6【相关文献】1.永劫轮回的生死场--论萧红小说中的生死观 [J], 罗良金2."生死场"中的"后花园":萧红小说中的"爱情" [J], 杨劲平3.萧红小说中的生命意识——以《生死场》为例 [J], 宋唯毓4.萧红小说中的生命意识——以《生死场》为例 [J], 宋唯毓;5.从生命意识角度解读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形象 [J], 吴芳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我们不难看出萧红作品中所营造的整体氛围和意境与她的“生”“死”意识紧密交织。她的文字底色是清冷的,氛围是荒凉的,读来有着微微的寒意。
在萧红的笔下, 一切的生死都是那么的无关紧要,都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人生的荒凉也许无过于此吧。然而萧红她对于这样的“荒凉”更有着深刻的体会。从始至终她都在人生荒凉的旷野上孤独前行,她感慨“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一生追求幸福而不得,三十一岁便香消玉殒,临死前也只能哀叹“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萧红的悲剧对于她个人固然显得残酷,我们却仍然不妨说,萧红的透骨的“寂寞”,在某种意义上也“成全”了她,使她浸透着个人身世的悲剧感,能与生活中弥漫着、浮荡着的悲剧气氛相通,那种个人的身世之感也经由更广阔的悲剧感受而达于深远。
萧红似乎略带残忍地在小说的结尾敲碎了读者对于“春天 ”的梦 ,春天曾是那样美 ,可是却逃脱不掉 “短命”的宿命,这是带血的文字,是萧红内心的悲歌。 景物的描写因翠姨的生死而渲染出不同的氛围,前者的生机勃勃与后者的凄清哀怨使得文字更富有张力。
《生死场》中王婆被生活所迫服毒自尽,在此之前有一处令人难忘的景物描写:“弯月相同弯刀刺上林端,王婆散开头发,她走向房后柴栏,在那儿她轻开篱门。 柴栏外是墨沉沉恬静的,微风不敢惊动这黑色的夜昼;黄瓜爬上架了! 玉米响着雄宽的叶子,没有蛙鸣,也少虫叫。 ”这段景物描写富有意境美,充斥一种凝重的悲剧氛围,像是一幅作者泼墨而成的“暗夜之画”。“弯月”不是以往诗歌中常见的象征寓意,而是一把“弯刀”,一上来就给读者一种尖锐的痛感。夜是“墨沉沉”的,“微风也不敢惊动这黑色的夜昼”,夜好像严肃得甚至令人感到恐怖的宇宙之神, 他笼罩了万物。
诞生、婚姻、丧葬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三大礼仪。在古代任何一项都有其特定的一系列程序、仪式,不同的仪式在人心理上产生的情绪是不同的,因而在整个礼仪中这种心理情绪会以某种色彩基调得到渲染。考查一下不同的礼仪中所积淀下来的色彩民俗语汇,会对此产生更为深入的认识。
一、色彩民俗语汇与诞生习俗
诞生是人一生的开端,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极为重视子嗣的国度里,更是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的一件大事。尽管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有自己的一套庆生礼仪,但有一些习俗却是相当普遍的,如“挂红布”,“送红蛋”,“食红蛋”,“系红腰带”等。“挂红布”是指婴儿降生后要在门口挂上红布,以向乡邻报喜。这一习俗产生很早,《礼记·内则》中就有“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的记载。“弧”,即弓;“帨”,即佩巾,后来由红布来代替,可见挂红布原来是特指“生女”的,后来成为一种普遍意义的报喜之象征。挂红布除了报喜的作用外,还有一层意义,即向外人表示不要随意进入打扰,以免带来邪气冲撞了新生儿,比如孕妇、着孝者不能靠近新生儿和产妇。而用选用红色本身也带有祛邪的意味。产妇在生产期间要“系红腰带”也是同样的道理。
春天充满了生机与希望,“春来了。人人像久久等待着一个大暴动,今天夜里就要举行,人人带着犯罪的心情,想参加到解放的尝试……春吹到每个人的心坎, 带着呼唤,带着蛊惑”。[2]
这样的一种生意盎然、想要冲破一切束缚的生命力,就像翠姨这个充满希望的姑娘,生命的乐观和喜悦与春天的精致浑然一体, 一切都有可能,一切都充满力量。 可是随着情节的一步步发展,翠姨还是无法逃脱悲剧的命运,成为了礼教束缚下的牺牲品。 翠姨去世之后的那个春天,和以往相比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为何又是那么的悲凉?“翠姨坟头的草籽已经发芽了,一掀一掀地和黏土成了一片,坟头显出淡淡的纯色,常常会有白色的山羊跑过。”仍然是春天的景色,文字中没有一个“悲”字,但是那种人生的怅惘与物是人非的无奈尽在其中。 “春天为什么它不早一点来,来到我们这城里多住一些日子,而后再慢慢地到另外的一个城里去,在另外一个城里也多住些日子。 但那是不可能的了,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 ”
她将“生命感”灌注于她笔下那些极其寻常的事物,使笔下随处有生命的勃发、涌动。一切都像是有生命的意识,活得蓬蓬勃勃,活得生气充溢。萧红在她的作品中从来都不会大声赞美生命,但是生命却被揉在她的字里行间,流淌在一字一句中。萧红这种“明丽”[4]的文笔最为鲁迅所赞赏。 在她笔下,强烈的生命意识与茫漠无际的寂寞悲凉之感,充满童真的意趣与充满人生厚度的智慧相互交融。也正因如此才有萧红富于智慧的稚气、有深度的单纯,与生命的欢欣同时并存的生命的悲凉感。生命的欢乐节制了她关于生命的悲哀, 而悲剧感的节制又使关于生命的乐观不流于盲目———两个方面都不至达于极端, 既不会悲痛欲绝,也不会喜不自胜。
第一章
萧红是凭借天赋和敏锐的艺术感觉进行创作的杰出作家。 她的文字如行云流水,注重环境因素的作用,把抒情散文的语言和“形散神不散”的散文结构特点揉进小说创作中,她的小说是反完整的,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例如《生死场》第十章只有三行;《呼兰河传》每章相当于一个独立的房间,而彼此间并没有廊庑相连。 故事无中心,无主角,甚至无情节。 没有一个人物是支配性的, 支配的力量唯在命运的逻辑本身。
例如,《小城三月》中的主人公翠姨原本是一个端庄、美丽、温柔的姑娘,她像春天的使者,给人间带来了爱的希望与欢欣。 作品中描写“我”和翠姨一起玩耍、倾谈时,是非常愉悦的,所以在写小城春景时,作者便带着一种喜悦的心情来描绘:“三月的原野已经绿了,像地衣那样绿,透出在这里、那里。 ”[1]
小说家昆德拉曾说:“只有散文,才是生活的真实面孔。”萧红将小说散文化,娓娓道来,无边伸展,忠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她摆脱了情节一类沉重的外壳,赢得了写作的自由。她让写作回归本原,让心灵和生活面对面呼吸、对话、吟唱。 在这散文化、抒情化的文字中流露出来的是她对于人生的思考,对“生”与“死”的理解。有时,她不直接描写“生”与“死”,而是将自己充沛的感情融入景物的描写, 做到情景交融;她还常常以蕴藉清新的诗的笔调来营造一种独特的意境与氛围,使景物有了灵气,有了深意,有了生命,平添了美感。
读萧红的小说有谁能够忘记这些在阴暗的画面中时时闪现的亮Hale Waihona Puke ? 这是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诗!
“充满着忧郁的灵性,但又不囿于忧郁和哀伤”。
萧红在这充满悲剧的人世间发现 “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 就向着‘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6]她“不甘”在不幸中沉没,挣扎着,用带血的声音呼唤阳光、鲜花、自由与美。
[6] 萧红.永久的憧憬和追求[A]//萧红全集[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166.
我们经常会发现在众多的民俗活动中总是会涉及到一些色彩问题,不同的民俗活动形成了不同的民俗色调,在有关民俗活动中若出“黑白颠倒”的现象可是要受到世人非议的一件大事。同时,人们往往只是知道在某种活动中应该是怎样的,不应该是怎样的,只是作为一种传统相沿习,并不真正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民俗内在的文化意蕴。
[3] 萧红.我家的大花园[J].语文世界(小学版),2004(6).
[4] 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A]//且介亭杂文二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5] 王秀珍.忧 郁中的憧憬 ———简论萧红作品的审美风格[A]//萧红研究·第三辑[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3.
第二章
在萧红的作品中我们恍惚感到了她作品潜藏最深的悲观,关于生命的悲观。但是我们读萧红的作品,却不觉得压抑与沉闷,她面对着人间的悲剧却能安静地表达着对生命的挚爱与向往,所以虽“忧伤成河”,但却不失明丽,是一种“明丽的忧伤”。萧红是寂寞的,却也正是她这颗寂寞的心,最能由人类生活、也由大自然中领略生命感。 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在萧红的作品中,还有表现得那样热烈,却也热烈得凄凉的关于生命的乐观。 在我看来,也只有这两面才使萧红更成其为萧红。 她在尝尽生命的荒凉与孤独之后,却能一片天真地表达对于生命、对于生存的喜悦———其中也寓有作者本人对于“生”的无限眷恋。两面的结合才更显其深刻。 《呼兰河传》中有这样一段:“花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 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 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 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 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一只白蝴蝶。 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