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忘不掉那个夜晚
那个夜晚作文

那个夜晚作文那个夜晚作文1在我的记忆里,难忘的往往是一些小小的细节:班会课时悄悄和同桌玩百年不变的“石头,剪子,布”;音乐课上的传纸条;上课时的走神;在体育课上跑步时畅谈电影。
还有那些傻傻的回忆,就像在沙坑上用手刨出一个大洞,把字条放进去,用沙子把坑填满,然后微笑着告诉对方永远都是朋友。
这些小事虽然看似是浪费时间,可是以后想起,没有书中人物的自责,快乐却会一荡一荡的。
就连小时候坐在秋千上的刹那,现在想起,都会因为那时纯粹的兴奋与幸福热泪盈眶,正如一年前夏天的那个夜晚。
那是一个夏令营的夜晚,当进入睡觉时间时,我们却一边享受零食一边盯着电视机,不记得在看什么,也不去注意情节,只记得零食嚼起时“咔吱,咔吱”的清脆声。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们明明已经困得要死却还坚守着电视,现在想起那沉重的眼皮和接二连三的哈欠声,还会会心一笑。
不知道是深夜几时,老师过来查夜,我们甚至拉着老师进来吃零食,看电视。
不知道那时到底哪儿来的胆子,只记得老师和我们一起看电视时相互的捂嘴笑。
接着,实在是困得不行时,终于把灯关了,只剩一人在那里看世界杯。
我是看不懂的,只能坐在那边的床上看一群外国人跑来跑去,到了最后,查夜的老师大喊睡觉了才肯乖乖躺下。
我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她们可能不知道,又或永远都不可能去知道,那时的我躲在被子里偷偷地笑。
那种有些做贼心虚的感觉,一想起便想笑,那种快乐,老老实实睡觉的乖孩子或许永远不能明白。
不知几时,我真的睡着了,不知又几时,我在她们熟睡时打开电视看《哆啦A梦》,看着看着我又睡着了,在椅子上睡着了。
后来,她们告诉了我,我睡着的时候口水都流了出来。
那是一种无法言语的快乐。
后来的后来,老师布置了这篇作文,我问别人想怎么写,她说随便编个有意义的事。
我迷茫了,难忘一定要有意义吗?为什么一定要编呢?那个夜晚作文2三四年前,我尚是一个二三年级的小学生,如今中学已向我招手了,回想起旧时过往,有一个曾令我恐惧的夜晚,那个晚上更像一位面色凶狠的指路人,难以接触却令我往前一步。
王菲的歌词

王菲——暧昧眉目里似哭不似哭还祈求甚么说不出陪著你轻呼著烟圈到唇边讲不出满足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la...... la......茶没有喝光早变酸从来未热恋已相恋陪著你天天在兜圈那缠绕怎么可算短你的衣裳今天我在穿未留住你却仍然温暖徘徊在似苦又甜之间望不穿这暖昧的眼爱或情借来填一晚终须都归还无谓多贪犹疑在似即若离之间望不穿这暖昧的眼似是浓却仍然很淡天早灰蓝想告别偏未晚music茶没有喝光早变酸从来未热恋已相恋陪著你天天在兜圈那缠绕怎么可算短你的衣裳今天我在穿未留住你却仍然温暖徘徊在似苦又甜之间望不穿这暖昧的眼爱或情借来填一晚终须都归还无谓多贪犹疑在似即若离之间望不穿这暖昧的眼似是浓却仍然很淡天早灰蓝想告别偏未晚徘徊在似苦又甜之间望不穿这暖昧的眼爱或情借来填一晚终须都归还无谓多贪犹疑在似即若离之间望不穿这暖昧的眼似是浓却仍然很淡天早灰蓝想告别偏未晚天上人间——王菲风雨过後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流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後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颂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天大地大世界比你想像中朦胧我不忍心再欺哄但愿你听得懂music风雨过後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流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後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颂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天大地大世界比你想像中朦胧我不忍心再欺哄但愿你听得懂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颂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天大地大世界比你想像中朦胧我不忍心再欺哄但愿你听得懂但愿你会懂该何去何从棋子--王菲想走出你控制的领域却走近你安排的战局我没有坚强的防备也没有后路可以退想逃离你布下的陷阱却陷入了另一个困境我没有决定输蠃的勇气也没有逃脱的幸运我像是一颗棋进退任由你决定我不是你眼中唯一将领却是不起眼的小兵我像是一颗棋子来去全不由自己举手无回你从不曾犹豫我却受控在你手里王菲红豆曲.柳重言词.林夕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颤抖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没跟你牵著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後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还没为你把红豆熬成缠绵的伤口然後一起分享会更明白相思的哀愁还没好好的感受醒著亲吻的温柔可能在我左右你才追求孤独的自由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王菲<< 催眠>>曲:郭亮词:林夕编:郭亮第一口蛋糕的滋味第一件玩具带来的安慰太阳下山太阳下山冰淇淋流泪第二口蛋糕的滋味第二件玩具带来的安慰大风吹大风吹爆米花好美从头到尾忘记了谁想起了谁从头到尾再数一回再数一回有没有荒废啦┅┅第一次吻别人的嘴第一次生病了要喝药水太阳下山太阳下山冰淇淋流泪第二次吻别人的嘴第二次生病了需要喝药水大风吹大风吹爆米花好美忽然天亮忽然天黑诸如此类远走高飞一二三岁四五六岁千秋万岁流年(国) 王菲作曲: 陈晓娟作词: 林夕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用一种魔鬼的语言上帝在云端只眨了一眨眼最后眉一皱头一点爱上一个认真的消遣用一朵花开的时间你在我旁边只打了个照面五月的晴天闪了电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懂事之前情动以后长不过一天留不住算不出流年哪一年让一生改变遇见一场烟火的表演用一场轮回的时间紫微星流过来不及说再见已经远离我一光年人间风雨过後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流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後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颂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天大地大世界比你想像中朦胧我不忍心再欺哄但愿你听得懂但愿你会懂该何去何从但愿人长久词/苏轼曲/梁弘志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月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王菲- 乘客作曲:Sophine Zelmani/Lars Halapi作词:林夕高架桥过去了路口还有好多个这旅途不曲折一转眼就到了坐你开的车听你听的歌我们好快乐第一盏路灯开了你在想什么歌声好快乐那歌手结婚了坐你开的车听你听的歌我不是不快乐白云苍白色蓝天灰蓝色我家快到了我是这部车第一个乘客我不是不快乐天空血红色星星灰银色你的爱人呢Yes I'm going homeI must hurry homeWhere your life goes onSo I'm going homeGoing home aloneAnd your life goes on旋木——王菲作词:杨明学作曲:袁惟仁拥有华丽的外表和绚烂的灯光我是匹旋转木马身在这天堂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爬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我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上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需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梁咏琪 << 短发 >>词:郑淑妃曲:陈国华哭到喉咙沙哑还得拼命装傻我故意视而不见你外套上有她的发她应该非常听你的话她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乖乖的呆在家静静的守着电话我已剪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岔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剪短我的发剪断了惩罚剪一地伤透我的尴尬反反覆覆清清楚楚一刀两断你的情话你的谎话李小璐 - 爱的无可救药从爱上你开始自己就变得不重要从前的我哪去了如今的我实在太糟糕爱情曾经是自己梦中的最需要如今却感觉像是在坐牢爱你爱的无可救药恨你恨得备受煎熬你的坏你的好都是我手心里的宝爱你爱的无可救药恨你恨得无处可逃想放弃又忘不掉痛并快乐着的心情如何是好从爱上你开始自己就变得不重要从前的我哪去了如今的我实在太糟糕爱情曾经是自己的梦中的最需要如今却感觉像是在坐牢爱你爱的无可救药恨你恨得备受煎熬你的坏你的好都是我手心里的宝爱你爱的无可救药恨你恨得无处可逃想放弃又忘不掉痛并快乐着的心情如何是好爱你爱的无可救药恨你恨得备受煎熬你的坏你的好都是我手心里的宝爱你爱的无可救药恨你恨得无处可逃想放弃又忘不掉痛并快乐着的心情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后来词:施人诚曲:玉城干春编曲:王继康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槴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似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著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永远不会再重来有一个男孩爱著那个女孩很爱很爱你——刘若英词:施人诚曲:玉城千春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成熟优雅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所以愿意不牵绊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飞向幸福的地方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看着她走向你那幅画面多美丽如果我会哭泣也是因为欢喜地球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作不成你的情人我仍感激当爱在靠近—刘若英词:潘协庆/李宗盛曲:潘协庆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只想有人在一起不管明天在哪里爱从不容许人三心两意遇见浑然天成的交集错过多可惜如果我是真的决定付出我的心能不能有人告诉他别让我伤心每一次当爱再靠近感觉他在紧紧地抱住你他骚动你的心遮住你的眼睛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每一次当爱在靠近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天地都安静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只想有人在一起不管明天在哪里爱从不容许人三心两意遇见浑然天成的交集错过多可惜如果我是真的决定付出我的心能不能有人告诉他别让我伤心每一次当爱再靠近感觉他在清楚地告诉你他骚动你的心遮住你的眼睛却不让你知道去哪里每一次当爱在靠近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天地都安静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每一次当爱再靠近感觉像他一定要说服你他骚动你的心遮住你的眼睛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每一次当爱在靠近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天地都安静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天地都安静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梁静茹- 满满的都是爱打个结绑起来就分不开靠着你不小心就飞起来去滑翔去冲浪让太阳晒热带鱼统统游过来只要跟着你就很放心放了一百二十颗心只要想到你就很开心哦满天都是小星星满满的都是爱想不到那么快遇见你什么都说出来谁叫我就是爱爱你的一点点呆很难不被你打败满满的都是爱像香槟满出来我的爱像气泡飘起来地球转得很快心脏快要跳出来想要逃也逃不开桃红色让心情都好起来粉水晶让爱情都亮起来敞蓬车跑得快昨天拜拜跟着你现在到未来只要跟着你就很放心二十四小时都不腻只要想到你就很开心哼我最爱的melody满满的都是爱想不到那么快遇见你什么都说出来谁叫我就是爱爱你的一点点呆很难不被你打败满满的都是爱像香槟满出来我的爱像气泡飘起来地球转得很快心脏快要跳出来想要逃也逃不开给我彩虹白日梦甜甜蜜蜜和闹哄哄打开天空对我说爱就像蜜蜂嗡嗡嗡满满的都是爱想不到那么快遇见你什么都说出来谁叫我就是爱爱你的一点点呆很难不被你打败满满的都是爱像香槟满出来我的爱像气泡飘起来地球转得很快心脏快要跳出来想要逃也逃不开地球转得很快心脏快要跳出来想要逃也逃不开梁静茹-亲亲曲:五月天怪兽词:陈没那一年顶楼加盖的阁楼什么人忘了锁是谁找不到未满十八岁的我你是一滴滴隐形的眼泪风一吹就乾了只能这样了是吗同时甜蜜与心碎是你的幽默还是温柔是瞬间烟火还是不甘寂寞第一次你抱紧我轻轻的亲亲紧紧闭著眼睛是你不是你说不定还不一定梦一样轻的亲亲不敢用力呼吸不敢太贪心太相信我的幸运百分之百是你思念被时光悄悄的摇落酸酸的咬了一口青春的苹果香香的催眠了我是你脸粉红了我的耳后烫伤了我额头现在想起来会痛同时甜蜜与心碎是你的幽默还是温柔是瞬间烟火还是不甘寂寞第一次你抱紧我轻轻的亲亲紧紧闭著眼睛是你不是你说不定还不一定梦一样轻的亲亲不敢用力呼吸不敢太贪心太相信我的幸运百分之百是你哦...轻轻的亲亲紧紧闭著眼睛是你不是你说不定还不一定梦一样轻的亲亲不敢用力呼吸不敢太贪心太相信我的幸运百分之百是你梁静茹-暖暖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的汤我们俩吃汤吃一个碗左心房暖暖的好保暖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他从心里暖暖的你对自己更重要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你手掌的厚实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很这个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我知道暖暖就在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他从心里暖暖的你对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从来都很低调自信心不高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他从心里暖暖的你对自己更重要我有希望变更好孤单北半球用你的早安陪我吃晚餐记得把想念存进扑满我望着满天星在闪听牛郎对织女说要勇敢不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看你的问候骑着魔毯飞用光速飞到我面前你让我看到北极星有十字星作伴少了你的手臂当枕头我还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等你有一天靠岸少了你的怀抱当暖炉我还不习惯E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不会偷懒我的梦通通给你保管爱你不是二三天退给你的信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迹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收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爱你不是二三天每天却想你很多遍还不习惯孤独街道拥挤人潮没你拥抱一眨^眼^ 心就能沉淀你是否想念我还是像我只和寂寞做朋友担心你没有好好的过又怕你已经忘了我刚刚分手像告别很久还想为你做些什么燕尾蝶兴高采烈的破蛹华丽新生的冲动寻找灿烂禁地美梦主宰爱情的是谁奋不顾身的扑火就算轮回只为衬托你笑你哭你的动作都是我的圣经珍惜的背颂我喜我悲我的生活为你放弃自由要为你左右你是火你是风你是织网的恶魔破碎的燕尾蝶太多最後的美梦你是火你是风你是天使的诱惑让我做燕尾蝶拥抱最後的美梦让我短暂快乐很感动兴高采烈的破蛹冲破心神的冲动寻找爱情世界美梦既然不是毛毛虫就要壮烈的扑火短短青春要像烟火自生自爱自个挥霍挥霍我的色采在你的天空你想你说而要我做其实我很快乐全都因为你是火你是风你是织网的恶魔破碎的燕尾蝶太多最後的美梦你是火你是风你是天使的诱惑让我做燕尾蝶拥抱最後的美梦让我短暂快乐很感动你是火你是风你是织网的恶魔破碎的燕尾蝶太多最後的美梦你是火你是风你是天使的诱惑让我做燕尾蝶拥抱最後的美梦让我快乐让我痛梁静茹-分手快乐(独唱版+合唱版)我无法帮你预言委曲求全有没有用可是我多么不舍朋友爱的那么苦痛爱可以不问对错至少有喜悦感动如果他总为别人撑伞你何苦非为他等在雨中泡咖啡让你暖手想挡挡你心口里的风你却想上街走走吹吹冷风会清醒的多你说你不怕分手只有一点遗憾难过情人节就要来了剩自己一个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分手快乐请你快乐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离开旧爱像坐慢车看透彻了心就会是晴朗的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你发誓你会活的有笑容你自信时候真的美多了瘦瘦的在童话很远的世界漂流完美是个多奢侈的念头终于搜集够多的伤口才懂八十分的幸福已足够你让我感动是多过心动踏实却比浪漫来得持久朋友还在怀疑我的选择而我不当仙女已经很久了我的心现在瘦瘦的很容易就饱了为了抢快乐搞得不快乐为什么人总那么傻呢我的梦现在瘦瘦的一下子就满了你的爱或许不是最美的你的手却很厚很念旧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分到一块叫做幸福的蛋糕宁愿一小口很小口品尝味道不想过瘾的一口吃掉丝路——梁静茹如果流浪是你的天赋那么你一定是我最美的追逐如果爱情是你的游牧拥有过是不是该满足谁带我踏上孤独的丝路追逐着你脚步谁带我离开孤独的丝路感受你的温度我将眼泪流成天山上面的湖让你疲倦时能够扎营停伫羌笛声胡旋舞为你笑为你哭爱上你的全部放弃我的全部爱上了你之后我开始领悟陪你走过一段最唯美的国度爱上了你之后我从来不哭谁是谁的幸福我从来不在乎谁是谁的旅途我只要你记住星星就是穷人的珍珠你的笑支撑着我虔诚的最初狂风沙是我单薄衣服穿越过亚细亚的迷雾云破日出你是那道光束带著平凡的我走过奇迹旅途梁静茹-小手拉大手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起回到凉凉深秋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交游今天别想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却正能帮我悠扬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一起回到凉凉深秋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交游今天别想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却正南方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LALALA...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交游今天别想太多LALALALALA...像北方的风却正南方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为我加油舍不得挥挥手梁静茹- 会呼吸的痛在东京铁塔第一次眺望看灯火模仿坠落的星光我终於到达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我们的梦想你总说时间还很多你可以等我以前我不懂得未必明天就有以后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哼你爱的歌会痛看你的信会痛连沉默也痛遗憾是会呼吸的痛它流在血液中来回滚动后悔不贴心会痛恨不懂你会痛想见不能见最痛没看你脸上张扬过哀伤那是种多么寂寞的倔强你拆了城墙让我去流浪在原地等我把自己捆绑你没说你也会软弱需要依赖我我就装不晓得自由移动自我地过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哼你爱的歌会痛看你的信会痛连沉默也痛遗憾是会呼吸的痛它流在血液中来回滚动后悔不贴心会痛恨不懂你会痛想见不能见最痛我发誓不再说谎了多爱你就会抱你多紧的我的微笑都假了灵魂像飘浮着你在就好了我发誓不让你等候陪你做想做的无论什么我越来越像贝壳怕心被人触碰你回来那就好了能重来那就好了梁静茹- 爱很简单I love you 一直在这里baby一直在爱你i love you oh yes i do永远都不放弃这爱的权利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突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wu oh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wu ohII love you 一直在这里baby一直在爱你wui love you oh yes i do永远都不放弃这爱的权利。
(初三作文)忘不了的身影初三语文作文

忘不了的身影初三语文作文它的身影,是忘不了的身影!忘不了的身影,被我们所恋恋不忘。
这一年冬天,它的身影,是一种关爱,是我们寒风中的坚决。
忘不了的身影,是我们繁华中的期望。
下面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忘不了的身影作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忘不了的身影初三语文作文1我无法忘记那个腊月寒冬,无法忘记那个寒风凛冽的早晨,那位清洁工阿姨的背影让我难以忘怀。
清晨,我背上书包准备上学。
刺骨的寒风吹光了路旁的树叶,吹得我直打哆嗦。
路途中,我遇见一位清洁工阿姨,只见她身穿黄色的工作服,手里拿着扫把“唰-唰-唰〞地把一大堆树叶扫进垃圾车里。
她一边扫地一边搓着冻红的双手,饱经风霜脸上胀得通红。
我凝望着这位清洁工阿姨。
这时一阵猛烈的寒风吹过,她依然挺立在风中,默默地把小路扫得一尘不染。
看到这个场景,我的思绪被带到那个温暖的回忆中……那天,天气寒冷,天上飘着点点小雨,昨夜那么下了一场倾盆大雨。
因此,很多人都会呆在家里。
小区里面的小路变得十分安静,少了几分喧闹。
这时一位小朋友手里拿着一个面包塑料袋,随手往草地里面扔去。
就在这时,清洁工阿姨出现在我的视线中。
她轻轻地说:“小朋友,你这样乱扔垃圾是不对的,要丢到垃圾箱里。
美丽的环境要靠大家来维护啊。
〞说完她走过去捡起垃圾袋放进垃圾桶里。
而那位小朋友涨红了脸低下了头说了一声:“谢谢阿姨!〞清洁工阿姨满脸笑容,点了点头推着垃圾车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看到清洁工阿姨,我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清洁工虽然没有惊人的壮举,却有着崇高圣洁的品质。
她那热爱工作,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
在阳光的照耀下,被她双手扫过的路面闪闪发光。
忘不了的身影初三语文作文2在那浩荡无边的夜空中,有许许多多的星星,在群星中有几颗出了奇的璀璨。
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故事,越闪烁越难忘,我怎能忘记你的温柔,你的美丽,你的身影……妈妈,您在您儿子的心中永远是最美的。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因为忘了盖被子而发了高烧。
烧到了40度,感觉头晕目眩,全身发热。
那声音很特别作文伤感

那声音很特别作文伤感
《那声音很特别》
唉,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夜晚听到的声音,那可真的太特别了,还带着满满的伤感。
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呢,有一天晚上我正躺在床上准备睡觉。
突然,我就听到隐隐约约传来一阵哭声,那哭声断断续续的,呜呜咽咽的,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我听错了。
可仔细一听,真的有哭声啊!而且这声音感觉就是从很近的地方传来的。
我就心里直发毛,这啥玩意儿啊。
于是我鼓起勇气,循着声音悄悄走到窗边,小心翼翼地往外瞅。
哎呀呀,你猜我看到啥了?原来是对面楼的一个小姐姐,她蹲在楼下花坛边哭得那叫一个伤心啊。
我就盯着她看,她一会儿拿手擦眼泪,一会儿又低着头抽泣,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看着她那样子,我都感觉心跟着揪起来了,也不知道她是遇到啥事儿了才会哭得这么惨。
也许是失恋了?也许是遭受了什么挫折?我就这么胡乱猜着。
我也不敢去打扰她,就在那默默地看着,听着她的哭声。
那哭声好像有一种魔力,就一直往我心里钻,让我也跟着难受起来。
我就想啊,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让人难过的声音呢,真的太特别了。
后来过了好久,那个小姐
姐终于不哭了,慢慢地站起来走了。
而我呢,躺在床上却好久都睡不着,满脑子都是那哭声和那个小姐姐的身影。
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那个夜晚听到的哭声,心里还是会涌起一股别样的感觉。
那声音真的很特别啊,让我永远都忘不掉,一直留在我记忆的深处,提醒着我生活中有着那么多的无奈和伤感。
哎呀呀,真是的!。
那个夜晚作文15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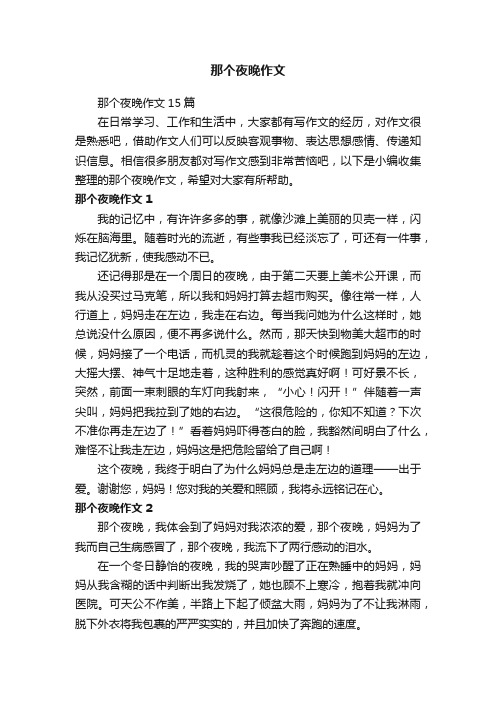
那个夜晚作文那个夜晚作文15篇在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大家都有写作文的经历,对作文很是熟悉吧,借助作文人们可以反映客观事物、表达思想感情、传递知识信息。
相信很多朋友都对写作文感到非常苦恼吧,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那个夜晚作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个夜晚作文1我的记忆中,有许许多多的事,就像沙滩上美丽的贝壳一样,闪烁在脑海里。
随着时光的流逝,有些事我已经淡忘了,可还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使我感动不已。
还记得那是在一个周日的夜晚,由于第二天要上美术公开课,而我从没买过马克笔,所以我和妈妈打算去超市购买。
像往常一样,人行道上,妈妈走在左边,我走在右边。
每当我问她为什么这样时,她总说没什么原因,便不再多说什么。
然而,那天快到物美大超市的时候,妈妈接了一个电话,而机灵的我就趁着这个时候跑到妈妈的左边,大摇大摆、神气十足地走着,这种胜利的感觉真好啊!可好景不长,突然,前面一束刺眼的车灯向我射来,“小心!闪开!”伴随着一声尖叫,妈妈把我拉到了她的右边。
“这很危险的,你知不知道?下次不准你再走左边了!”看着妈妈吓得苍白的脸,我豁然间明白了什么,难怪不让我走左边,妈妈这是把危险留给了自己啊!这个夜晚,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妈妈总是走左边的道理——出于爱。
谢谢您,妈妈!您对我的关爱和照顾,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那个夜晚作文2那个夜晚,我体会到了妈妈对我浓浓的爱,那个夜晚,妈妈为了我而自己生病感冒了,那个夜晚,我流下了两行感动的泪水。
在一个冬日静怡的夜晚,我的哭声吵醒了正在熟睡中的妈妈,妈妈从我含糊的话中判断出我发烧了,她也顾不上寒冷,抱着我就冲向医院。
可天公不作美,半路上下起了倾盆大雨,妈妈为了不让我淋雨,脱下外衣将我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并且加快了奔跑的速度。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到了医院,此时,妈妈全身上下都被雨水淋湿了,她也不顾自己的身体,赶紧找来医生为我看病,医生急匆匆地为我看病、开药,并将医嘱给了我妈妈,妈妈迅速地取了药,又把我抱回了家。
那一个忘不掉的夜晚作文初中

那一个忘不掉的夜晚作文初中
“轰隆隆”,雨哗哗的下个不停,粗大的雨点纷纷落下来,打得玻璃啪啪直响。
我望着窗外的倾盆大雨,开始纠结起来,我去还是不去书法班呢?
不知不觉,指针已经指上六点钟整。
爸爸还在犹豫着,他想等雨小一点送我去书法班。
时间慢慢流逝,又过去了十二分,经过爸爸的深思熟虑,决定让我步行去书法班。
我穿上了鞋套,拿了吧小雨伞,提起了书包,便匆匆忙忙的下了楼。
雨水顺着房檐流了下来,开始向断链的珠子,渐渐连成了一条线。
雨越下越大,地上的水也随之越来越多,汇成了一条条泛黄的小河。
我打着雨伞在雨中艰难地行走,一不留神被绊了一下,一脚踩到了小河里,尽管穿着鞋套,可调皮的雨点还是顺着裤缝流进我的鞋里。
好不容易出了小区门口,我却发现自己忘了带眼镜,没办法,我只好打电话让爸爸来送。
我抬手一看表一18:22,离上课只有八分钟了。
迟到了!要迟到了!一想到这,我的眼泪都差点流了出来。
爸爸在电话中听到我的声音,似乎感觉到我这副焦急的模样,安慰我说:“迟到了也没事,爸骑车去送你,你先慢慢走着。
”我点了点头,边赶路边张望,一步三回头,心里除了着急还是着急,盼望着爸爸早点来到我面前,终于一阵摩托车声响,爸爸来了。
但他身上什么遮雨的也没有,我赶忙用伞努力的帮她遮挡。
雨更大了,豆大的雨珠砸在了我们身上,他却说“别管我,你自己打好
伞就行。
到了书法班了,爸爸什么也没说,接过我的雨伞,骑上了车,又混入了来来往往的车流中。
我望着他那湿透了的背影,流下了眼泪。
那个下雨的夜晚,让我怎么也忘不了,。
难忘那个夜晚作文

难忘那个夜晚作文难忘那个夜晚作文(8篇)难忘那个夜晚作文1除夕年年过,今宵最难忘。
不错的,今天的除夕对我来说的确不同以往。
因为在今年的除夕,我陪一位孤老度过了她在旧居的最后一个除夕夜。
李老师曾是我母亲的小学语文老师;在我五年级时又辅导过我的学习。
因此,她是我家两代人的老师。
李老师知识渊博,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还不停地学习,订了不少报刊杂志。
她的精神生活十分丰富。
但她的日常生活却很孤独,因为在这世界上她已经没有一位亲戚了,于是我们这些她往昔的学生就成了她最亲的亲人。
今年,由于市政动迁,李老师将告别她已居住几十年旧居。
因此,我们这些受教于她的学生来到了她家。
准备和李老师一起过个热热闹闹的除夕夜。
我们首先将各自带来的礼物拿了出来。
哇!好丰富呀,有同学自己制作的李老师家这一带的房屋模型;有同学书写的“感谢您,李老师!”的字幅;有同学素描的李老师像还有不少“参丸”之类的滋补品。
夜幕降临,屋外"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和窜入高空的烟花所迸裂的流光异彩,给节日欢乐的气氛抹上了浓重的一笔。
我们几个人轮流下了厨房,各自做了几道拿手菜。
在餐桌上,我带头举起了杯子,发表了祝酒词:“祝李老师能在一年内拥有365个笑容满面的日子!同时,我代表大家感谢您以毕she生的精力培养和教育了我们这几代人。
你比我们的祖母还要亲”我的声音颤抖了。
“同学们,我更要感谢你们。
”李老师的眼圈红了,“你们是我的精神支柱。
因为我没有子女,所以我的学生都好比自己的子女,所以我的学生都好比自己的子女。
同学们,你们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你们是我乐观的源泉”夜空中的烟花五彩缤纷,绚丽夺目。
“难忘今宵”的歌声从电视机内传出,却是真的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夜早已深沉,可大家仍然依偎在李老师的怀里。
凝视着她满头的银丝,凝视着她慈祥的笑容,凝视着这间老屋仿佛要将这一切都铭刻在脑海中呵,多么难忘的那个夜晚,多么难忘的这份师生情谊前天,我和同学们来到了佘山少儿活动营地,开始了“毕业之旅”。
五月天歌词(闽南语也有)

軋車(ga qia)--五月天詞/曲阿信(五月天)是按怎阿花和阿嬌 xi an zua a huei ga a giao攏無佳意我 long mou ga yi wa我撇車技術一流 wa pei qia gi su yi liu 無人甲我軋 mou lang ga wa ga是按怎學校的老師 xi an zua ha hao e lao shi攏無疼痛我 long mou tia tang wa是不是ABCD看無 xi mu xi ABCD kua mou 卡憨就攏免教ka gong dou long mien ga老爸老媽 lao bei lao mu整天底罵 gui gang dei ma喋喋喋念 sei sei sei niang不知念啥 mu zai niang sa是按怎哪會按呢 xi an zua na e an nei 身邊的問題一攤 xin bin e wun tei ji tua 這時陣上好作陣來去軋車 zei xi zun xiong hao zuei ding lai ki ga qia作陣來軋車 zuei ding lai ga qia作陣來軋車 zuei ding lai ga qia不管伊員警底抓 mu guan yi ging ca dei lia不管伊父母底罵 mu guan yi bei mu dei ma 只要我引擎催落 ji yao wa ein jing cui luei無人可當甲我軋 mou lang e dang ga wa ga 在這我最快最趴最大 di jia wa xiong gin xiong pa xiong dua是按怎今日的觀眾 xi an zua gin a lei guan jiong攏底打拍仔 long dei pa po a大家看我一個 da gei kua wa ji lei那像Super Star na qiun Super Star lalala lalalalalala la~~ la~~la~~ lalalalalala la~~la~~愈騎愈緊愈爽 lu kia lu gin lu song我想欲唱歌 wa xiun me qiun gua 頭腦底飛 tao nao dei buei身軀底顫 xin ku dei cua風底吹我 hong dei cuei wa心底流汗 xin dei lao gua是按怎哪會這爽 xi an zua na e jiong song 要瞭解我的感覺 me liao gai wa e gan ga 這時陣上好作陣來去軋車 zei xi zun xiong hao zuei ding lai ki ga qia ~~~~~~~~~~~~~~~~~~~~~~~~按怎:怎樣攏無佳意:都不喜歡甲我:和我疼痛:疼愛卡憨:比較笨攏免教:都不用教底罵:在罵按呢:這樣時陣:時候上好:最好作陣:(作伴)一起催落:催下去可當:能夠那像:當作像緊:快哪會:為什麼會這爽:這麼爽趴:搶風頭打拍仔:鼓掌志明與春嬌(ji ming ga cun giao)--五月天詞/曲阿信(五月天)志明真正不知要安怎 ji ming jin jia mu zai me an zua為什麼 wi xia mi愛人不願閣再相偎 ai lin mu wuan go zai xiong wa春嬌已經早就無在聽 cun giao yi ging za diou mou dei tia講這多 gong jia zei其實攏總攏無卡抓 gi xi long zong long mou ka zua走到淡水的海岸 gia gao dan zui e hai (er)ua兩個人的愛情 neng e lang e ai jing已經無人看 yi ging mou lang kua已經無人聽啊啊 yi ging mou lang tia a~ a~我跟你 wa ga li最好就到這 xiong hao lo gao jia你對我 li dui wa已經沒感覺 yi ging mou gan ga到這凍止 gao jia dong dia你也免愛我 ni ya mien ai wa我跟你 wa ga li最好就到這 xiong hao lo gao jia你對我 ni dui wa已經沒感覺 yi ging mou gan ga麥閣傷心 mai go xiong xin麥閣我這愛你 mai go wa jia ai ni你沒愛我 ni mou ai wa志明心情真正有影寒 ji ming xin jing jin jia wu ya gua風這大 hong jia dua你也真正攏沒心肝 ni ya jin jia long mou xin gua春嬌你哪無要和我播 cun giao ni na mou me han wa bua這出電影 ji cu dien ya 咱就走到這位准底煞 lan dou gia gao ji wi zun du sua安怎:怎樣(在這一句比較適合解釋成 "怎樣才好")閣再:再(....雖然 "閣" 是 "又" 的意思) 無:沒有攏總:通通(全部) 攏無卡抓:都沒有用凍止:停住(結束) 麥閣:不要又有影:真的真正攏沒:真的都沒有哪無要:為什麼不要這位:這裏(這個位置) 准抵煞:正好剛剛結束(散)HoSee--五月天詞/曲阿信(五月天)槍子無聲鑽來鑽去 qing ji mou xing zeng lai zeng ki打破今眠的空氣 pa pua gin min e kong ki 半眠一點的巷仔內 bua min ji diang e hang a lai在播一出戲 dei bua ji cu hi哪會按呢我想來想去 na e a nei wa xiun lai xiun ki活得真不舒適 wa ga jin mei su si稍微一點風吹草動 xiou kua ji kua hong cuei cao dang把仔抓緊緊 an la tei gin ginHosee Hosee Hosee Hosee呼伊死 ho yi xi看誰人先倒下去 kua xia lang xin do lou kiHosee Hosee Hosee Hosee呼伊死 ho yi xi看誰人的卡大支 kua xia lang e ka dua giHosee Hosee 呼伊死 Hosee Hosee ho yi xi Hosee Hosee 呼伊死 Hosee Hosee ho yi xi Hosee Hosee 呼伊死 Hosee Hosee ho yi xi 不爽就 Hosee Hosee mei song dou Hosee Hosee(我手拿黑星走三關(wa qiu tei o qin zao san guan一天到晚驚乎抬ji li gao an gia ho tai兄弟啊你要是太搖擺hia di ya ni na xi siu hiao bai我就送你蘇州賣鴨蛋)wa diou sang ni su zhou mai ya dan)世界哪會顛三倒四 sei gai na e dien san do xi人生過甲親像戰爭 lin xing gue ga qin qiun zien jin委屈若是吞不下去 wi ku na xi tun muei lou ki一聲就翻臉 ji xia dou bin min江湖變甲這沒義氣 gang hou bien ga jia mou yi ki朋友變甲這歹逗陣 bin yu bien ga jia pai dao ding真正若是發生事情 jin jia na xi hua xing dai ji人攏溜緊緊 lang long suan gin gin昨眠閣再夢到伊 zang min go zai mang diou yi牽手散步的日子 kan qiu san bo e li ji 甘知當初的男兒 gang zai dong co e nan ni 變甲按呢生 bien ga a nei xing四面八方團團包圍 xi min ba hong tuan tuan bao wi左邊右邊撞不出去 jia bin dou bin long mei cu ki我嘛不知 wa ma mu zai過了今眠 gue liao gin min是生還是死 xi xing ya xi xi今眠:今夜半眠:半夜哪會按呢:怎麼會這樣把仔:槍把呼伊死:給(讓)他死卡:比較黑星:(槍)驚乎抬:怕被殺搖擺:囂張送你蘇州賣鴨蛋:送你上西天過甲親像:過得就像這歹逗陣:這麼難(相處)在一起攏:都緊緊:快快閣:又甘知:怎麼知道(哪里知道) 按呢生:這個樣子嘛:也黑白講(o bei gong)--五月天詞/曲阿信(五月天)轉過了一遍又一遍的街仔路 sei guei liao ji bai go ji bai e gei a lo整天是攏無意義的走沖 gui gang xi long mou yi yi e zao zong天光到天黑 ti gang gao ti o萬事攏照常 man su long jiao xiong無聊 mou liao叫人要起狂 giou lang me ki gong忍受到一遍又一遍的囉嗦 ning siu diou ji bai go ji bai e lo so你給我的世界只有一條路 ni ho wa e sei gai ji wu ji diao lo愛拼才會贏 ai bia jia e yia我不是聽無 wa mu xi tia mou前途 zian dou我攏看不著 wa long kua muei diou哪會世界攏無聲音 na e sei gai long mou xia yin青春是戰爭 qing cun xi zien jing我渴望流血 wa ko mang lao hui有什麼絕招作你變 wu xia mi zua jiao zuei li bing我的好兄弟 wa e hou hia di我打攏不死 wa pa long mei xi我想要走路有風 wa xiun me gia lo wu hong 我想要作真真正正的英雄 wa xiun me zuei jin jin jia jia e ying hiong你叫我 li giao wa麥憨麥憨麥憨 mai gong mai gong mai gong 我聽你在黑白講 wa tia li dei o bei gong 街仔路:大街小巷攏:都走沖:忙碌天光:天亮聽無:聽不懂看不著:看不到作你變:隨你變麥憨:別傻黑白講:胡說八道I Love You-無望(I love you mou mang)--五月天詞/曲阿信(五月天)是你的形影 xi li e hing ya叫我逐天作眠夢 giou wa da gang zuei min mang夢中可愛的人 mang diong ko ai e lang 伊不是別人 yi mu xi ba lang我的每一天 wa e mui ji gang一分鐘也不當輕鬆 ji hun jing ya mei dang king sang你是阮愛的人 li xi wun ai e lang將阮來戲弄 jiong wun lai hi lang九月的風在吹 gou wue e hong dei cuei 哪會寒到心肝底 na e gua gao xin gua dei 希望變無望 hi mang bien mou mang決定我的一世人 gua ding wa e ji xi langI love you無望 I love you mou mang你甘是這款人 li gang xi ji kuan lang 沒法度來作陣 mou hua do lai zuei ding 也沒法度將我放 ya mou hua do jiong wun bangI love you無望 I love you mou mang我就是這款人 wa diou xi ji kuan lang 我身邊沒半項 wa xin bin mou bua hang 只有對你的思念 ji wu dui li e su niang 陪伴我的每一天 bue bua wa e mui ji gang逐天:每天伊:她(他) 不當:不能阮:我一世人:一輩子甘是這款:難道是這種沒法度:沒辦法作陣:(作伴)在一起沒半項:沒半樣(甚麼都沒有)風若吹(hong na cuei)--五月天詞/曲阿信(五月天)生活在這個奇怪的社會 xing wua dei ji lei gi guai e xia huei你甘無一款奇怪的體會 li gang mou ji kuan gi guai e te huei甘講一定就愛讀冊 gan gong yi ding dou ai ta cei一世人找人拼高低 ji xi lang cuei lang bia guan ge我已經無力甲你去相爭 wa yi ging mou la ga li ki xioung zei這些道理我不是沒聽過 ji gua dou li wa mu xi mou tia guei我是真正在不瞭解 wa xi jin jia lei bu liao jie我的性命無法度照我的 wa e xing mia mou hua do jiao wa e命運你往哪轉 mia wun li dui dou sei 攏無法度去控制 long mou hua do ki kong zei風若吹我就飛 hong na cuei wa dou buei 不知我會飛到哪 mu zai wa e buei gao duei朋友親戚甲厝邊頭尾 bing yiu qin cei ga cu bin tao wue生雞蛋的無放雞屎多 sei gei neng e mou bang gei sai e zei一天到晚攏在冤家 ji gang gao ang long dei wuan gei甘著一定愛按呢 gan diou yi ding ai an nei 有一天我要放舍我一切 wu ji gang wa me bang sa wa yi cei免閣整天驚東又驚西 mien go gui gang gia dang go gia sei一定給你攏無底找 yi ding ho lin long mou dei cuei一定給你攏無底可找 yi ding ho lin long mou dei tang cuei甘無:難道沒有一款:一種甘講:難道說愛讀冊:要讀書一世人:一輩子甲你:和你無法度照:沒辦法按照攏:都甲厝邊頭尾:和街頭巷尾的鄰居冤家:吵架甘著:難道就愛按呢:要這樣放舍:放棄免閣:不必(不用)又驚:怕你(念成令):你們無底找:找不到攏無底可找:都沒辦法可以找到為什麼(今日的愛情)wui xia mi(gia li e ai jing)—五月天詞/曲阿信(五月天)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wui xia mi wui xia mi wui xia mi為什麼又擱是我傷心 wui xia mi yu go xi wa xiong xin手牽著手的熱天 qiu kan li qiu e rua ti 凍未到風吹的寒天 dang muei gao hong cuei e gua ti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wui xia mi wui xia mi wui xia mi為什麼惦在這個都市 wui xia mi diang zai ji lei do qi應該是歡喜的代志 ying gai xi hua hi e dai ji哪會每一次攏目屎滴 na e mui ji bai long ma sai di真正我不甘願 jin jia wa mu gang wuan 嘛不相信 ma mu xiong xing今日的愛情 gia li e ai jing為什麼 wui xia mi一聲來一聲去 ji xia lai ji xia ki一聲放未記 ji xia bang mei gi為什麼昨日的愛情 wui xia mi zo li e ai jing聽人講框金又包銀 tia lang gong kong gin go bao yin 為什麼今仔日這件代志 wui xia mi gin a li ji gia dai ji親像在吃泡面 qin qiun dei jia pao mi為什麼變甲這呢生 wui xia mi bien ga a nei xing最憨是春嬌甲志明 zuei gong xi cun giao ga ji ming真心藏在心內避 jin xin zang zai xin nai bi愛情我真正真正玩不起 ai jing wa jin jia jin jia sen muei ki真正我放未落 jin jia wa bang mei lo 嘛玩不起 ma sen me ki今日的愛情 gia li e ai jing無睬我這愛你 mou cai wa jia ai li這愛你 jia ai li這這這愛你 jia jia jia ai li擱:再凍未到:撐不到惦在:待在代志:事情攏目屎滴:都掉眼淚嘛:也未記:忘記(不記得)親像:就像變甲:變得這呢生:這個樣子放未落:放不下無睬:不值得(可惜)心中無別人(xin diong mou ba lang)詞/曲阿信(五月天)會記哩牽手 e gi li kan qiu散步的彼暗 sang bo e hi ang公車擱過站 gong qia go guei zan你我的心願 li wa e xin wuan講也講不完 gong ya gong mei sua開始期待 kai xi ki dai無聊的人生 mou liao e lin xing我已經覺悟 wa yi ging ga o攏可以結束 long e sai ge so你甘知一種 ni gang zai ji jiong神秘的力量 xin bi e lei liong改變阮前途 gai bien wun zian do全新的人生的路 zuan xin e lin xing e lo 不知是光明是錯誤 mu zai xi gong ming xi co o是你給阮一個夢 xi li ho wun ji lei mang 未記人生的苦澀 buei gi lin xing e ko xia 真正想要對你講 jin jia xiun me dui li gong甘擱有別項 gang go wu ba hang是你放阮一個人 xi li bang wun ji lei lang走過風雨的思念 gia guei hong ho e su niang真正想要對你講 jin jia xiu me dui li gong心中無別人 xin diong mou ba lang(我的心中無別人wa e xin diong mou ba lang)無味的命運 mou mi e mia wun平凡的世界 bin huan e sei gai混亂的心內 hun luan e xin nai微微的怨歎 bi bi e wuan tan一天又一天 ji gang go ji gang你甘不曾 ni gang mu ma開太多氣力 kai xiu zuei kui la在這個世界 zai ji lei sei gai有稍微無睬 wu xiou kua mou cai愛你是唯一 ai li xi wi yi真正有價值 jin jia wu gei da真正阮甘願 jin jia wun gan wuan甘願阮放棄一切 gan wuan wun bang sa yi cei又流出歡喜的目屎 go lao cu hua hi e ma sai代志要按怎繼續 dai ji me an zua gei xiou 我也不知影wa ma mu zai ya只想要和你逗陣 ji xiun me ga li dao ding 抱你身軀 po li xin ku聽你唱歌 tia li qiun gua記哩:記得彼暗:那晚擱:又攏:都甘知:是否知道阮:我未記:不記得(忘掉) 甘擱有:難道還有別項:別種(事情) 甘不曾:難道沒有過開:花無睬:不值得目屎:眼淚代志:事情按怎:怎樣不知影:不知道有你的將來(wu li e jiong lai)—五月天詞/曲阿信(五月天)甘真正像你講 gang jin jia qiu li gong 這簡單 jia gan dan為怎樣你要離開 wui zua yiu li me li kui 我不知 wa mu zai天頂的月娘笑 ti ding e wue niun qiou 我不識 wa mu ma認真就是浪費時間 ling jin do xi long hui xi gan你甘愛聽阮講阮的愛 ni gang ai tia wun gong wun e ai為怎樣一片一片 wui zua yiu ji pin ji pin 你不知 li mu zai逗陣的日子啊 dao ding e li ji ya這天才 jia tien cai無看到愛情有傷害 mou kua diou ai jing wu xiong hai我愛甲這出力 wa ai ga jia cu la你只是試看麥li ji xi qi kua mai 擾亂我原本平靜的世界 liao luan wa wuan bun bin jing e sei gai我愛甲這出力 wa ai ga jia cu la你甘未歹交待li gang muei pai gao dai你的心肝無人瞭解 li e xin gua mou lang liao gai(無人能夠瞭解) (mou lang e dang liao gai)找不到你的真情真愛 cuei muei diao ni e jin jing jin ai你的心像大海 li e xin qiun dua hai聽未到阮的真心真意的無奈 tia muei diao wun e jin xin jin yi e mou nai走未到你我當初約束的所在 gia muei gaoli wa dong co yo so e so zai想不到你的愛 xiun muei gao li e ai甘真正像你講這簡單 gan jin jia qiun li gong jia gan dan為怎樣你要離開我不知 wui zua yiu li meli kui wa mu zai逗陣的日子啊這天才 dao ding e li ji ya jia tien cai無看到愛情有傷害 mou kua diou ai jing wu xiong hai找不到你的真情真愛 cuei muei diou li e jin jing jin ai你的心像大海 li e xin qiun dua hai聽未到阮的真心真意的無奈 tia muei diou wun e jin xin jin yi e mou nai走未到你我當初約束的所在 gia muei gaoli wa dong co yo so e so zai想不到 xiun muei gao你的愛 li e ai愛的甲青睬 ai ga jia qing cai想不到 xiun muei gao阮的愛 wun e ai找不到有你的將來 cuei muei diao wu li e jiong lai甘:難道阮:我甘愛:是否要愛甲:愛得試看麥:試看看甘未歹交代:難道不會難交代約束:約定青睬:隨意(敷衍)憨人(gong lang)—五月天詞/曲阿信(五月天)我的心內感覺 wa e xin nai gan ga人生的沉重 lin xing e din dang不敢來振動 mu ga lai ding dang我不是好子 wa mu xi hou gia嘛不是歹人 ma mu xi pai lang我只是愛眠夢 wa ji xi ai min mang我不願隨浪隨風 wa mou wuan sui ying sui hong飄浪西東 piao long sei dang親像船無港 qin qiun zun mou gang我不願做人 wa mu wuan zuei lang奸巧鑽縫 gan kiao lang pang甘願來作憨人 gang wuan lai zuei gong lang我不是頭腦空空 wa mu xi tao nao kang kang我不是一隻米蟲 wa mu xi ji jia mi tang 人啊人一世人 lang a lang ji xi lang 要安怎歡喜 me an zua hua hi過春夏秋冬 guei cun ha ciu dang我有我的路 wa wu wa e lo有我的夢 wu wa e mang夢中的那個世界 mang diong e hi lei sei gai甘講伊是一場空 gang gong yi xi ji diun kang我走過的路 wa gia guei e lo只有希望 ji wu hi mang希望你我講過的話 hi mang ni wa gong guei e wei放在心肝內 bang zai xin gua nai總有一天 zong wu ji gang看到滿天全金條 kua diou mua ti zuan gin diao要煞無半項 me sa mou bua hang環境來戲弄 huan ging lai hi nang背景無夠強 bue ging mou gao giong天才無夠弄 tien cai mou gao lang我逐項是攏輸人 wa da hang xi long su lang只好看破這虛華 ji hou kua pua zei hi hua 不怕路歹行 mu gia lo pai gia不怕大雨淋 mu gia dua ho lang心上一字敢 xin xioung ji di ga面對我的夢 min dui wa e mang甘願來作憨人 gang wuan lai zuei gong lang嘛:也歹人:壞人眠夢:做夢親像:就像安怎:怎樣甘講伊:難道說它煞:抓無半項:甚麼都沒弄:賣弄叫我第一名(giou wa dei yi mia)—五月天詞/曲阿信(五月天)你說我這款人可以沖啥 li gong wa ji kuan lang e sai cong xia你說我最好丟進垃圾車 li gong wa xiong hou dang dui bun sou qia你說我這款人可以沖啥 li gong wa ji kuan lang e sai cong xia電影看了吃宵夜擱去唱歌 dien ya kua liao jia xiao ya go qi qiun gua吃飽困困飽吃 jia ba kun kun ba jia 你賣想這多 li mai xiun jia zei講到七桃我就走 gong diou qi tou wa diou gia 有什麼代志 wu xia mi dai ji一定要計較輸贏 yi ding ai gei gao su yia啦…… la……愛玩才會贏 ai sen jia e yia啦…… la……誰人倘跟我拚 xiang lang tang ga wa bia 啦…… la……你問我叫啥米名 li men wa giou xia mi mia 啦…… la……叫我第一名 giou wa dei yi mia你說晚時倒垃圾早時堵車 li gong wa xi do bun sou za xi ta qia你說寒天太寒熱天太熱 li gong gua ti xiu gua rua ti xiu rua你說甲意的人無甲意你啦 li gong ga yi e lang mou ga yi li la你說人生的路哪會這陡 li gong lin xing e lo na e jia gia這款:這種沖啥:做甚麼擱:再困:睡麥:別(不要)七桃:遊玩代志:事情倘:能夠啥米:甚麼甲意:喜歡雨眠(ho min)—五月天詞/曲阿信(五月天)親愛的你甘放未記 qin ai e ni gang bang me gi彼個有你的暗眠 hi lei wu ni e an min 雨聲撞不停 ho xia long mei ting你親像溫柔的海浪 ni qin qiun wun riu e hai ying棉被底下的代志 mi puei e ka e dai ji 已經不再可能 yi ging bu zai ko ning天頂是小雨落不停 ti ding xi xio ho lo mei ting海底是眼屎落未漧 hai dei xi ma sai lo mei di我是雲一朵 wa xi hun ji rui命運將你我逗作陣 mia wun jiong ni wa dao zuei din享受到愛人的甜蜜 hiang xiu diou ai lin e di mi再將你和我拆分開 zai jiong ni ga wa tia hun kui親愛的親愛的 qin ai e qin ai e你所說過的話 ni so gong gei e we哪會到今仔日 na e gao gin a li攏總無地找 long zong mou dei cuei人生太無知 lin xing tai mu di愛情是什麼 ai jing xi xia mi永遠太空虛 ying wuan tai kang hi無人擔當得起 mou lang dang dong e ki將你的將我的 jiong ni e jiong wa e昨日說過的話 zo li gong gei e we放水流 bang zui lao受風吹 xiu hong cuei藏進海底 zang jin hai dei將你放未記 jiong ni bang mei gi永遠麥想起 ying wuan mai xiun ki你是彼粒星 ni xi hi lia qi飛過我的天頂 buei gue wa e ti ding又擱是落雨的暗眠 yiu go xi lo ho e an min甘放未記:是否忘記彼:那暗眠:夜晚親像:就像代志:事情眼屎:眼淚逗作陣:湊合在一起甲:和今仔日:今天攏總:全部未記:忘記麥:不要擱:再好不好(hou mu hou)—五月天詞/曲阿信(五月天)不知是對或是不對 mu zai xi diou a xi mu diou不知是好或是不好 mu zai xi hou a xi mu hou不知你甘會笑阮憨 mu zai li gang e qiou wun gong夏天西北雨的下午 rua ti sai ba ho e e bo 想你不知影你在哪 xiun li mu zai ya li dei do真希望 jin hi mang看到你的笑容 kua diou li e qiou riong你的溫暖 li e wun nuan充滿著阮孤單的心臟 qiong muan diou wun go dua e xin zong我不能繼續在等待 wa mei dang gei xiou zai dan tai想要對你說 xiun me dui li gong乎你想 ho li xiun乎你猜 ho li yo是誰人整眠煩惱 xi xia lang gui mi huan lou煩惱著 huan lou diou無情的風 mou jing e hong無情的雨 mou jing e ho阻礙咱的路 zo ai lan e lo甲你疼 ga li tia甲你惜 ga li xiou甲你捧在我雙手中 ga li pang dia wa xiang qiu diong我一生唯一的希望 wa yi xing wi yi e hi mong要給你快樂 me ho li kuai lo好或不好 hou ya mu hou日子有甜也有艱苦 li ji wu di ma wu gang ko有你有我互相照顧 wu li wu wa hou xiong jiao go想要聽 xiun me tia你心內的感想 li xin nai e gan xiong親愛 qin ai你甘有聽阮講 li gang wu tia wun gong 親愛 qin ai到底是好不好 dao dei xi hou mu hou甘講你驚阮沒信用 gang gong li gia wun mou xin yiong還是你擱有苦衷 ya xi li go wu ko jiong甘會:是否會阮:我西北雨:雷陣雨不知影:不知道乎:給`讓整眠:整夜甲:把甘有:是否有甘講:難道說驚:怕(擔心)擱有:還有借問眾神明(jio men jiong xin min)—五月天詞/曲阿信(五月天)遇到歹歹時機 du diou bai bai xi gi 只有他顛倒無閑 ji wu yi dien do mou yin 性命吹到風浪 xing mia cuei diou hong ying我的頭頂開始變天 wa e tao ding kai xi bien ti不用百萬大富貴 mu mien ba man dua hu gui 議員立委吃百面 yi wan li wi jia ba min 只要是看到天邊雲一朵 ji yao xi kua diou ti bin hun ji lui逐天攏有好心情 da gang long wu hou xin jingLALALALALALA la~~la~~借問喂眾神明 jio men e jiong xin min 命運甘攏有決定 mia wun gang long wu gua dingLALALALALALA la~~la~~咱來借問眾神明 lan lai jio men jiong xin min人生甘有成功時 lin xing gang wu xing gong xi(甘有?丫知!) gang u? a zai!阿嬤嘛有煩惱 a ma ma wu huan lou燒金擲茭抽籤詩 xiou gin bua bue qiu qiang xi聞到香火香味 pi diou hiu hue pang mi 親像伊的溫柔心情 qin qiun yi e wun riu xin jing伊講做人麥貪心 yi gong zuei lang mai tan xin好人就有好保佑 hou lang diou wu hou bou bi好保佑 hou bou bi走的順順好搖喂 gia e sun sun hou you qi 順順勢勢小生意 sun sun xi xi xiou xin liLALALALALALA la~~la~~借問喂眾神明 jio men e jiong xin min 命運甘攏有決定 mia wun gang long wu gua dingLALALALALALA la~~la~~咱來借問眾神明 lan lai jio men jiong xinmin人生甘有成功時 lin xing gang wu xing gong xi海海人生舵位去 hai hai lin xing dou wi ki男女愛情青紅燈 nan nu ai jing cei ang ding緣起緣盡有註定 ein ki ein jing wu zu ding甘真正 gang jin jia命運就是無可選 mia wun diou xi mou tang ging真正沒睬這多年 jin jia mou cai jia zei ni離開的伊 li kui e yi 歹歹:不好的顛倒:反而吃百面:吃得開逐天:每天甘攏有:難道都有甘有:是否有丫知:哪知道呀嘛:也親像伊:就像她麥:不要舵位:哪里甘真正:是否真的沒睬:(可惜`浪費`不值得)永遠的永遠(ying wuan e ying wuan)—五月天詞/曲阿信(五月天)我昨眠的夢 wa zang min e mang細漢的我 sei han e wa熟悉的所在 xi sai e so zai夢猶原是夢 mang yiu wuan xi mang什麼時陣 xia mi xi zun我卻這大棕 wa sua ja dua zang為什麼 wui xia mi心內的感覺 xin nai e gan ga鼻頭在酸澀 pi tao dei sen sa我想說 wa xiun gong我已經是漂泊的人 wa yi ging xi piao pei e lang不管按怎過按怎變 mu guan an zua guei an zua bien按怎的人 an zua e lang永遠的永遠我是彼個人 ying wuan e ying wuan wa xi hi lei lang愛過的一切 ai guei e yi cei我攏不甘放 wa long mu gang bang不管天涯海角 mu guan ti ya hai ga不管按怎笑按怎哭 mu guan an zua qiou an zua kao按怎眠夢 an zua min mang永遠的永遠我是彼個人 ying wuan e ying wuan wa xi hi lei lang只要你一句話 ji yao li ji gu we我就敢搥胸膛 wa diou ga tun tang是不是你會等我 xi mu xi ni e dan wa 阮愛的人 wun ai e lang(故鄉的人) (go hiong e lang)昨花朵的紅 zang huei lui e ang一聲變作 ji xia bien zo反白的頭髮 huan bei e tao zang 啊爸媽疼痛 a bei mu tia tang攏無代念 long mo dai niang阮不是故意 wun mu xi tiao gang 只因為 ji yin wi厝內的門窗 cu nai e men tang關不住美夢 gui muei diao mi mang 我想說 wa xiun gong阮打拼 wun pa bia一定有那天 yi ding wu hi gang 昨眠:昨夜小漢:(小孩子) 猶原:仍然這大棕:(長這麼大)按怎:怎樣彼:那眠夢:做夢阮:我疼痛:(捨不得)攏無代念:(都沒有設想) 厝內:屋內啾啾啾(jiu jiu jiu) (Chu Chu Chu)—五月天詞/曲阿信(五月天)頭殼裏面攏裝書 tou ka lai di long di zu 攏無所在 long mou so zai裝著阮的靈魂 dei diou wun e lin hun心肝裏面是心事 xin gua lai di xi xin su 我不敢想 wa mu ga xiun眼淚會一直噴 ma sai e yi di pun想要沒煩惱 xiun me mou huan lou沒憂愁 mou yu qiu來晃頭 lai hain tao來跳舞 lai tiao mu喔喔喔喔喔喔啾啾啾 o~~ o~~ jiu~~~ 耶耶耶啾啾啾 ye~~ jiu~~喔喔喔啾啾啾 o~~ jiu~~耶耶耶啾啾啾 ye~~ jiu~~啾啾啾啾啾啾啾 jiu~~jiu~~ jiu應該是彩色人生 ying gai xi cai xie lin xing這個時陣 ji lei xi zun哪會感覺愛困 na e gan ga ai kun檢查著我的目珠 gan ca diou wa e ma jiu 你甘看有 li gang kua wu什麼色的鬱卒 xia mi xie e wu zu想要變快樂 xiun me bien kuai lo變單純 bien dan sun想要牽 xiun me kan伊的手 yi e qiu喔喔喔啾啾啾 o~~ jiu~~沒煩惱沒憂愁 mou huan lou mou yu qiu 耶耶耶啾啾啾 ye~~ jiu~~放輕鬆來跳舞 bang king sang lai tiao mu 啾啾啾啾啾啾 jiu~~jiu~~攏:都阮:我時陣:時候目珠:眼睛甘看有:是否看到鬱卒:鬱悶垃圾車sui ang li pi qi miai雖然你脾氣壞dui dai pieng you mai對待朋友又dup cui yao gan kan tu凸槌又更愛牽拖gia diou li do diou wa佳在你遇到我moo ai gie gai ye wa不愛計較的我sen li pai lang wu ho mia算你壞人有好命wa gia lo li jie qia我走路你坐車li jia ben wa xiai wa你吃飯我洗碗li ko ki hu wa bia mia你被欺負我拼命na wei lou song diou li若為了爽到你ko yi gan ko giou wa可以艱苦到我yin wei lang wun hun wu ko sua因為咱緣分不可散wu li wa zia mie go dua有你我才未孤單wu li ye pie bua wa zia wu ko sua有你的陪伴我才有靠山li na mie song wa xi li ye ben suo qia 你若不爽我是你的垃圾車da dan tia li ye xinm xia每天聽你的心聲wu li wa jia mie go dua有你我才未孤單wu li ye pie pua wa zia wu ko sua有你的陪伴我才有靠山li na hua hi wa xi li ye ben suo qia 你若歡喜我是你的垃圾車da dan tia li ciu gua每天聽你唱歌向前走(hiong zian gia)火車漸漸在起走huei qia jiang jiang dei ki gia再會我的故鄉和親戚 zai huei wa e go hiong ga qin gia親愛的父母再會吧 qin ai e bei mu zai huei ba逗陣的朋友告辭啦 dao ding e bin yu go xi la我欲來去臺北打拼 wa me lai ki dai ba pa bia聽人講啥物好空的攏在那tia lang gong xia mi hou kang e long di hia朋友笑我是愛做瞑夢的憨子bin yu qiou wa xi ai zuei ming mang e gong gia不管如何路是自已走 mu guan ru hou lo xi ga gi giaOH! 再會吧 o~~ zai huei baOH! 啥物攏不驚 o~~ xia mi long mu giaOH! 再會吧 o~~ zai huei baOH! 向前走 o~~ hiong zian gia車站一站一站一站過去啦qia zan ji zan ji zan ji zan guei ki la風景一幕一幕一幕親像電影hong ging ji mo ji mo ji mo qin qiun dien ya把自已當作是男主角來扮ba ga gi dong。
难忘那个夜晚作文(精选41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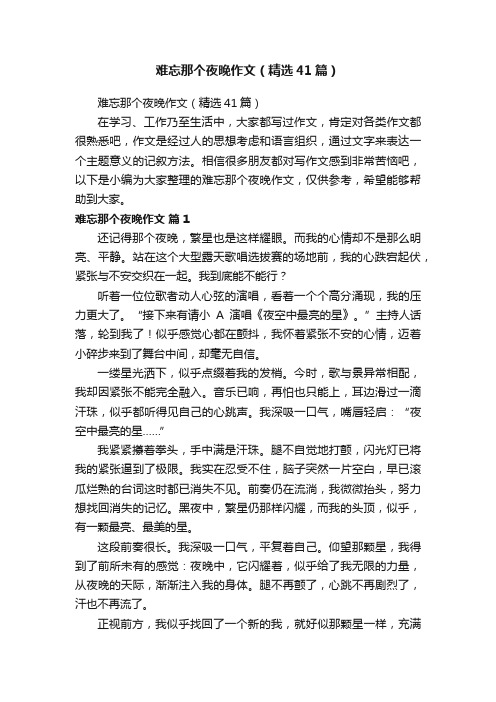
难忘那个夜晚作文(精选41篇)难忘那个夜晚作文(精选41篇)在学习、工作乃至生活中,大家都写过作文,肯定对各类作文都很熟悉吧,作文是经过人的思想考虑和语言组织,通过文字来表达一个主题意义的记叙方法。
相信很多朋友都对写作文感到非常苦恼吧,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难忘那个夜晚作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难忘那个夜晚作文篇1还记得那个夜晚,繁星也是这样耀眼。
而我的心情却不是那么明亮、平静。
站在这个大型露天歌唱选拔赛的场地前,我的心跌宕起伏,紧张与不安交织在一起。
我到底能不能行?听着一位位歌者动人心弦的演唱,看着一个个高分涌现,我的压力更大了。
“接下来有请小A演唱《夜空中最亮的星》。
”主持人话落,轮到我了!似乎感觉心都在颤抖,我怀着紧张不安的心情,迈着小碎步来到了舞台中间,却毫无自信。
一缕星光洒下,似乎点缀着我的发梢。
今时,歌与景异常相配,我却因紧张不能完全融入。
音乐已响,再怕也只能上,耳边滑过一滴汗珠,似乎都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声。
我深吸一口气,嘴唇轻启:“夜空中最亮的星……”我紧紧攥着拳头,手中满是汗珠。
腿不自觉地打颤,闪光灯已将我的紧张逼到了极限。
我实在忍受不住,脑子突然一片空白,早已滚瓜烂熟的台词这时都已消失不见。
前奏仍在流淌,我微微抬头,努力想找回消失的记忆。
黑夜中,繁星仍那样闪耀,而我的头顶,似乎,有一颗最亮、最美的星。
这段前奏很长。
我深吸一口气,平复着自己。
仰望那颗星,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感觉:夜晚中,它闪耀着,似乎给了我无限的力量,从夜晚的天际,渐渐注入我的身体。
腿不再颤了,心跳不再剧烈了,汗也不再流了。
正视前方,我似乎找回了一个新的我,就好似那颗星一样,充满力量。
乐律,再次回荡耳畔,而消失不见的记忆,这时又回到了我的脑海。
很准,很恰巧。
嘴角微扬,露出一抹醉人的微笑。
嗓音放开,已是一个新的我:“你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对观众唱,也是对自己唱。
这个夜晚,都是我的世界!旋律悠扬,我随着旋律,随着夜风,一起轻轻摇摆。
难忘的一夜作文(通用21篇)

难忘的一夜作文难忘的一夜作文(通用21篇)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吧,作文是人们把记忆中所存储的有关知识、经验和思想用书面形式表达出来的记叙方式。
怎么写作文才能避免踩雷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难忘的一夜作文,欢迎大家分享。
难忘的一夜作文篇1这次,我们去的是黄山,到黄山的第一天,住的是房车。
因为这是第一次住房车,所以我无比激动。
首先看到的是一大一小的两张床,小床是架子床,那里有:电视、沙发、冰箱……应有尽有。
让我们震惊不已,就在这时,我的好朋友在门外喊:“快出来!”我打开门一看,只见他们正骑着脚踏车过来,我立即跑过去,找到一个空位子坐下,我们蹬啊蹬,蹬啊蹬,玩的好开心……太阳落山的时候,爸爸开始烧烤了,爸爸把小朋友喜欢吃的鸡翅先放在上面烤,他在鸡翅上一会加点盐,一会洒点孜然,忙的浑身是汗。
过一会,香香的味道就飘了出来。
我们几个小馋猫馋的口水都流下来了,爸爸把鸡翅端上来,我们狼吞虎咽,把它们都消灭了。
晚餐之后,我们一起去看星星,天上的星星可真多啊!“一、二、三、四……”数也数不清,看得我眼花缭乱。
突然想起天上有牛郎星、织女星、牵牛星……我让爸爸给我讲它们的故事。
正当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妈妈喊:“睡觉了!”我躺在车子里的床上,看着与平时不一样的房子。
不一会儿,就进入了美美的梦乡。
难忘的一夜作文篇2我因手术的剧烈疼痛而昏迷在病床上,爸妈用那饱经风霜磨砺的大手握着我的手,头伏在床沿上睡着了。
初生的太阳用光芒照着大地,我还在昏迷中,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手术了吗?事情是这样的。
那是六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正值五岁,还不是很懂事,一天,我在路上看到了一个熟人,便过去搭话,当我跑到路蹭时,一辆车撞过来,觉得视线有些模糊,只看见山在移动,不知过了多久,我模糊地看见我躺在一辆面包车里,看见爸爸那焦急的神情,嘴里不知在说些什么,可见了非常担心,妈妈似乎不在车里,但其实她就在我身后担忧,车窗外的风景不怎么好,一下子就没了,车不知什么时候到了医院,爸爸和妈妈的脸上那焦急,担忧的神情显然没有了。
忘不了作文600字(8篇)

忘不了作文600字(8篇)忘不了作文篇一每当我含起一块冰糖,就会想起一个人。
她就是我二年级的同学王昕怡。
她一双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一张樱桃小嘴,长长的头发。
她待人温和,善解人意。
认识没多久,我们就成了一对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一天,不知什么原因,我的脸长出了许多小痘痘,妈妈带我去药店开了药,不仅没用,还让灰尘爱上了和我“亲密接触”。
上学时,我也不得不戴着口罩。
看到我这样子,她就关心地问:“你怎么啦,是生病了吗?”我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吃饭时,我才摘下口罩,她的朋友和我是一桌的,看见了便一直在笑我,我哭了。
回到教室,她的朋友也把这件事告诉了她。
她一听到,就朝我走了过来。
我心想,她应该也会像她的朋友那样嘲笑我吧!可出人意料的是,她不仅没有嘲笑我,反而是从书包里找出一片湿巾给我擦拭,她跟我说:“别哭了,我不会笑你的,还有你这脸上,不过是因为上火才长痘的,过几天就会自己消掉。
”说完还从口袋里拿出一块冰糖给我,我把这颗冰糖放到嘴里,心情不禁好了许多。
我对她笑了笑,她也露出像太阳般明媚的微笑,暖暖的。
转眼间,上三年级了。
开学时,她突然找到我,拉着我的手噙着泪水,告诉我——她转学了。
我清楚地看见:乌云遮住了原本明媚的阳光,外面下起了连绵的细雨。
如今我们都上六年级了,可我还是时不时想起我们一起的温暖时光。
忘不了作文篇二有一个寒冷的夜晚,大风与大树进行搏斗,雨滴“嗒嗒嗒”地在教学楼顶上跳舞,我在教室里望向窗外,心中不禁引起一阵惶恐。
“呀!这雨可真大”,“我今天可没带伞啊!”“天气预报上怎么没说啊,唉……”同学们在我身边议论纷纷,都很担心待会下课回不了家。
阿嚏,我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本以为今天阳光明媚的,可春天就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比翻书还快。
我今天早上只穿了一件短袖,我已经被冻得瑟瑟发抖了。
突然,在我的视线里,我看到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走了过来。
说他熟悉,是因为这个人高高的,瘦瘦的,像极了我的外公;说他陌生,是因为外公早上也感冒了,他一早还到医院输液过。
满分作文:记住那个夜晚

满分作文:记住那个夜晚那个夜晚,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镶嵌在我记忆的银河之中,永远闪耀着温暖而柔和的光芒。
我深知,无论岁月如何更迭,那份深藏于心的感动与幸福,都将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夜,深沉而静谧,仿佛整个世界都沉浸在一片宁静的海洋之中,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远处的犬吠,或是风穿过树叶的沙沙声,才打破了这份沉寂。
我躺在床上,双眼紧闭,试图通过深呼吸来平复内心莫名的波澜。
我努力构造出一个梦境的轮廓,企图说服自己,我已安然入睡。
然而,那不过是徒劳,我的心,如同被一根无形的线牵引着,无法真正沉入梦乡的深渊。
“吧嗒吧嗒”——那是拖鞋与地板轻柔接触的声音,在这寂静的夜晚里显得格外清晰。
我知道,那是妈妈。
她从未如此早地准备就寝,至少在我有记忆以来,她总是忙碌到深夜,为家庭,为我。
但今晚,她却已开始梳洗,准备休息。
我在心里默默计算着时间,离期末考试的钟声敲响,还剩九个小时。
我并非因紧张而难以入眠,相反,我对自己充满信心,那是一种对知识的掌握,对自我的肯定。
然而,妈妈的举动,却让我心中泛起了涟漪。
她轻轻躺在我身边,为我掖好被角,那动作轻柔而熟练,仿佛是我儿时无数次入睡前的重复。
我紧闭双眼,尽量让自己的呼吸变得均匀而深沉,试图营造出一种熟睡的假象。
然而,我的心,却如同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拨动,无法完全平静下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体验到失眠的滋味,那种既想沉睡又无法入眠的矛盾,让我有些许的辗转反侧。
但我相信,我已装得足够像,足以让妈妈以为我已进入梦乡。
然而,母亲的心,总是那么细腻,那么敏感,她或许早已察觉到我的异样。
“麦麦,睡不着吗?”她的声音轻柔而温暖,如同春日的微风,轻轻拂过我的心田。
我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轻声应和:“嗯……”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她能不为我担心,希望她能相信,我已足够坚强,足够独立,去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
然而,妈妈却将身子移近我,轻轻地将手放在我的肩上,开始轻轻地拍打,一下,又一下。
那个夜晚作文15篇

那个夜晚作文精选15篇那个夜晚作文精选15篇在日常学习、工作抑或是生活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作文吧,作文是一种言语活动,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和创造性。
怎么写作文才能避免踩雷呢?下面是为大家整理的那个夜晚作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那个夜晚作文1天渐渐的暗了下来,月亮悄悄的走上了天空,窗外刮起了一阵阵刺骨的寒风,让门来回的拍动着,屋外的大树上的树叶一个劲的往下落,小草不得不弯下了腰,乌鸦的叫声是那么的难听,那么的令人讨厌。
哎!都怪我,谁叫我迷上了电脑游戏呢,一天到晚总是玩个不停晚上凌晨一、二、点的时候,爸爸、妈妈都睡着了,但我还没有一丝睡意。
现在我考了个不及格,等会儿妈妈开家长会回来,一定不会饶过我的。
正在这个时候,妈妈回来了。
只听见一声巨响“砰”的一声妈妈把门使劲一关,不禁让我打了个哆嗦,又一声“啪”,妈妈气的把皮包一扔,吓得我蹲到了墙角,又一声“砰”吓得我直发抖,原来妈妈把皮鞋往墙上一板,鞋底在墙上印了一个印子。
她气呼呼得往沙发上一坐,捏着卷子往桌子上重重的一拍,然后走到我面前,用眼睛望着我,她的眼睛红了,有一些晶莹的泪珠在滚动。
从妈妈的眼睛里流露出几丝失望;几丝愤怒。
妈妈用手把头托着,叹了口气说:“你……你太让我失望了,你自己看看吧!”她的声音时而洪亮,时而如同蚊子叫。
那个夜晚作文2夜晚,我踏出家门,找到一片空地,抬头一看,天空中群星密布,闪闪发亮。
四周安静了,好像都在听星星说故事呢!这时我想起了那个夜晚……那一天,我们来到了一个饭店,饭店里面可大了,桌子快和房子一样大了。
我们立刻找了一个地方坐了下来,爸爸妈妈在点菜,我们几个在商量一些秘密。
终于上菜了,我们几个狼吞虎咽,好像贪吃的小猪。
直到我们肚子实在是装不下任何东西时,我们要开始完成一件事。
我急快地飞奔出来,决定拼个你死我活。
哈哈,第一局是弟弟抓人,我们只有五十秒逃跑时间,我躲在了桌子底下,至于她们,我就不知道了。
只听一声“我来抓了!”弟弟的脚步声渐行渐近,我心里就像闯进了一只小鹿砰砰乱跳。
那夜星光璀璨作文初中生

那夜星光璀璨作文初中生《那夜星光璀璨》嘿!你知道吗?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夜,那夜的星光璀璨得就像童话里的世界。
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白天的热气还没完全消散,我跟着爸爸妈妈来到了乡下的奶奶家。
奶奶家的院子可大啦,一进去就觉得特别宽敞。
“哎呀,我的宝贝孙子来啦!”奶奶满脸笑容地迎了出来,拉着我的手就往屋里走。
我在屋子里坐不住,没一会儿就跑了出来,在院子里晃悠。
这时候,邻居家的小伙伴明明也跑了过来。
“嘿,咱们一起去玩吧!”明明冲我喊道。
“好呀!”我兴奋地回答。
我们俩在村子里到处跑,一会儿跑到田边看看绿油油的庄稼,一会儿又跑到小池塘边听听青蛙的叫声。
玩累了,我们就躺在草地上,仰望着天空。
这一抬头,我简直呆住了!那满天的星星,密密麻麻的,就像无数颗闪闪发光的宝石镶嵌在黑色的幕布上。
“哇,这星星也太多了吧!”我忍不住感叹道。
“是呀,比咱们城里看到的多多啦!”明明也兴奋地说。
我看着那些星星,有的亮一些,有的暗一些,它们组成了各种各样的形状。
我指着天空说:“你看,那几颗星星连起来像不像一个勺子?”明明看了看,笑着说:“还真像!难道那就是传说中的北斗七星?”就在我们俩叽叽喳喳讨论的时候,爸爸和奶奶也走了过来。
“孩子们,看星星呢?”爸爸笑着问。
“爸爸,这星星太好看啦!”我兴奋地说。
奶奶在一旁坐下,轻轻地说:“奶奶小时候呀,一到夏天晚上就喜欢看星星,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星星就是最好的伙伴。
”我好奇地问奶奶:“奶奶,那您能认出很多星座吗?”奶奶笑着摇摇头:“奶奶可不懂那些,就是觉得好看。
”我们一家人就这么静静地坐在草地上,看着天上的星星。
微风轻轻吹过,带来一丝丝凉爽,周围的草丛里传来阵阵虫鸣声,仿佛在为这美好的夜晚演奏着乐曲。
我不禁想到,这些星星离我们那么远,它们是不是也有自己的故事呢?它们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有时候开心,有时候烦恼呢?那夜的星光,是那么璀璨,那么迷人。
它就像一个美丽的梦境,让我陶醉其中。
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那个夜晚,心里都会涌起一股温暖的感觉。
我最想念的人作文

我最想念的人作文我最想念的人作文在日常学习、工作抑或是生活中,大家都写过作文,肯定对各类作文都很熟悉吧,作文可分为小学作文、中学作文、大学作文(论文)。
如何写一篇有思想、有文采的作文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我最想念的人作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最想念的人作文1一天晚上,床上的老人没再说话也没再喃喃,有一个女孩呆呆的凝视着床上的老人,强忍着眼眸的泪水感到悲伤、无助,心里的一个词语始终回荡——“外公”。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夜晚,一夜之间给我关爱的人没了没了……天下着雨,敲打着房顶上的瓦砾,叮咚———叮咚,好像在位逝去的老人落泪。
我傻傻的望着床上的老人哭不出来,外婆、妈妈等人的哭声徘徊耳边。
屋里暗黄的灯光照耀着我的悲伤!“妈,我出去了!”我说,因为我是在不想再外公面前留下他所谓不争的眼泪!走出门。
无数的悲痛,无数的迷茫,无数的泪水,在这一刻悄然来临。
无声无息,正如外公无声无息的走了一样。
抬起头眼里的泪花突然映着两颗樱桃树,我至死都不会忘记,外公生前对我的关爱就是在那生根发芽!回忆只增添了美好……我记得小时候,自己最喜欢坐在樱桃树上的大枝干上吃果子呢!而外公就在下面叮嘱我小心点儿。
每当夏至,我就和外公、外婆一起坐在樱桃树下乘凉,然而现在回忆起来却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
由于外公家有很多果树,所以每年都是外公摘好了给我送来。
但外公离去的四年来,果子不甜了不红了,也没人再给我送了,唉!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姊妹几个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外公讲那古老的故事。
“薛仁贵”、“聊斋”、“三皇五帝”……我外公可精通不少哩!经常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也许是外公的关系我酷爱历史!如今想起来心里酸酸的,但同时暖暖的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回忆只增添了美好,美好中却还有悲伤!今天我随着风儿飘逝来到了外公的家。
小屋子里的两件床还是那么瞩目,老旧的柜子还是那么简朴,暗黄的灯光却同往常不一样,因为它曾照耀的我的悲伤!门上的红布帘飘啊飘荡啊荡,却怎么也荡不走,飘不走我的思念!“外公!我想你了!外公……”我最想念的人作文2我最思念的人,就是我的奶奶。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作文600字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作文600字《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
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夜晚特别难忘。
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星星在天上眨着眼,月亮像个大圆盘挂在天空。
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公园散步。
公园里可热闹啦!有跳广场舞的爷爷奶奶,有玩耍的小朋友,还有卖各种小玩具的叔叔阿姨。
我开心地跑来跑去,像只快乐的小鸟。
走着走着,我看到一个卖棉花糖的小摊。
那棉花糖像一朵朵彩色的云,漂亮极了!我缠着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个。
我舔一口,甜甜的,心里美美的。
后来,我们坐在湖边的长椅上,听着青蛙“呱呱”叫,看着水里的小鱼游来游去。
风儿轻轻吹过,带来一阵花香,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觉得特别舒服。
那个夜晚,有好吃的棉花糖,有美丽的风景,还有爸爸妈妈的陪伴,我真的永远忘不了!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
有一个夜晚,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怎么也忘不掉。
那天晚上,家里停电了。
一开始我还有点害怕,黑漆漆的啥也看不见。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也不害怕了。
我们还一起玩了手影游戏,我用手做出小兔子、小狗的样子,映在墙上可好玩啦。
后来电来了,屋子里一下子亮堂堂的。
但那个停电的夜晚,在烛光下的温暖时光,我永远忘不了。
以什么让我念念不忘为题写一篇作文

以什么让我念念不忘为题写一篇作文《那片花海让我念念不忘》在我的记忆里,有一个地方总是让我念念不忘,那就是那片美丽的花海。
去年春天,爸爸妈妈带我去了一个公园。
一走进公园,我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一大片五颜六色的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好看极了。
我欢快地在花海中奔跑,闻着花香,感觉自己像一只快乐的蝴蝶。
我还看到好多小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忙着采蜜。
我躺在花海中间,望着蓝天,心里特别舒畅。
那片花海的美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怎么都忘不了。
《那次旅行让我念念不忘》在我的生活中,有一次旅行让我一直记在心里,怎么也忘不掉。
那是暑假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去了海边。
一到海边,我就看到了无边无际的大海,海浪一个接着一个地拍打着沙滩,发出“哗哗”的声音。
我迫不及待地脱掉鞋子,冲向沙滩。
沙子细细的、软软的,踩在上面特别舒服。
我还和爸爸一起堆了一个大大的沙堡,可开心啦。
到了晚上,我们围坐在沙滩上,吃着美味的烧烤,看着天上一闪一闪的星星,那种感觉真是太棒了。
这次旅行的快乐时光,让我念念不忘。
《奶奶的笑容让我念念不忘》在我的心里,有一个笑容总是让我念念不忘,那就是奶奶的笑容。
每次我去奶奶家,奶奶都会站在门口迎接我,脸上带着温暖的笑容。
那笑容就像春天的阳光,让我心里暖洋洋的。
有一次,我考试没考好,心情特别不好。
奶奶看到我不开心,拉着我的手,笑着对我说:“孩子,一次没考好没关系,下次努力就行。
”奶奶的笑容和鼓励的话,让我一下子有了信心。
奶奶的笑容充满了爱和关怀,我永远也忘不了。
《那个夜晚让我念念不忘》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夜晚特别难忘。
那天晚上,月亮特别圆,星星特别亮。
爸爸妈妈带着我去公园散步。
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了湖边。
湖水在月光的照耀下,闪着银色的光,美丽极了。
那一个忘不掉的夜晚作文初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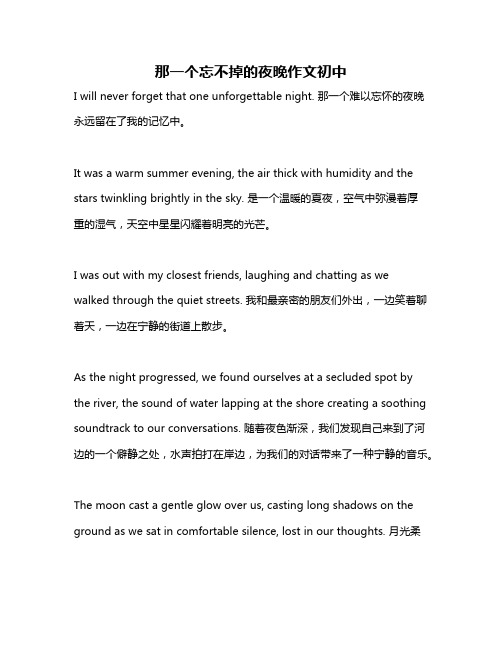
那一个忘不掉的夜晚作文初中I will never forget that one unforgettable night. 那一个难以忘怀的夜晚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It was a warm summer evening, the air thick with humidity and the stars twinkling brightly in the sky. 是一个温暖的夏夜,空气中弥漫着厚重的湿气,天空中星星闪耀着明亮的光芒。
I was out with my closest friends, laughing and chatting as we walked through the quiet streets. 我和最亲密的朋友们外出,一边笑着聊着天,一边在宁静的街道上散步。
As the night progressed, we found ourselves at a secluded spot by the river, the sound of water lapping at the shore creating a soothing soundtrack to our conversations. 随着夜色渐深,我们发现自己来到了河边的一个僻静之处,水声拍打在岸边,为我们的对话带来了一种宁静的音乐。
The moon cast a gentle glow over us, casting long shadows on the ground as we sat in comfortable silence, lost in our thoughts. 月光柔和地照耀着我们,投下长长的影子在地面上,我们坐在那里,陷入了安静的思考之中。
I remember feeling a sense of contentment and happiness, surrounded by the people who meant the most to me in the world.我记得当时感到一种满足和幸福,被那些在我生命中占据至关重要位置的人包围着。
什么令人难忘作文

什么令人难忘作文《那个夜晚令人难忘》“哎呀,这可怎么办呀!”我着急地说道。
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逛夜市。
夜市里灯火辉煌,热闹非凡,各种商品琳琅满目,还有好多好吃的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我兴奋地这儿看看,那儿瞧瞧,开心极了。
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了一个卖小饰品的摊位前。
我一下子就被那些漂亮的发夹吸引住了,眼睛都挪不开了。
“哇,这个发夹好漂亮呀!”我忍不住赞叹道。
妈妈看我这么喜欢,就说:“那给你买一个吧。
”我高兴地挑了一个最喜欢的,小心翼翼地拿在手里。
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一边走一边摆弄着我的新发夹。
突然,我发现发夹不见了!“哎呀,我的发夹呢?”我惊慌失措地叫起来。
爸爸妈妈也赶紧帮我找,可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我心里难受极了,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那可是我最喜欢的发夹呀!爸爸安慰我说:“别着急,我们再回去找找看。
”于是我们沿着刚才走过的路往回走,每一个摊位都仔细地看。
我一边走一边想:会不会是掉在路上被别人捡走了呢?要是找不到了怎么办呀?就在我万分焦急的时候,一个小女孩跑过来,手里拿着我的发夹,气喘吁吁地说:“姐姐,这是你掉的发夹吗?”我一看,正是我丢失的那个发夹,我激动地说:“是呀,谢谢你,小妹妹!”小女孩笑着说:“不用谢,我刚刚看到它掉在路上,就想着要还给失主呢。
”我心里充满了感激,这个小女孩真是太善良了。
那个夜晚,因为这个小女孩的善举,让我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善意。
这不就像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吗?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
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但却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那个夜晚真的令人难忘啊!我想,我也要像那个小女孩一样,做一个善良、有爱心的人,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更多的人。
忘不掉的那天晚上文案

1.那一个天空中繁星点点、城市中灯火通明的夜晚,那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夜晚,又是一个意义非优哉游哉的搬着一个我每天都坐的小板凳,晃晃悠悠地走了过去,这时妈妈已接好了洗脚水,用手轻轻触碰了几下,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可能只是妈妈的习惯问题而已,而现在的我明白了,这一个小如尘土的举动却饱含着妈妈大大的爱,这个举动应该是世界上所有母亲的通病吧。
2.不管在任何地点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只要猛地一回神就好像回到那个夜晚那是我至死都忘不了的夜晚明明没那么相干的几个人就因为在那个夜晚紧密相连了3.永远忘不掉那天晚上我们侃侃而谈解开心结最后在长椅上吻别我很庆幸当初你没选择我祝我们和各自的另一个幸福毕业快乐前程似锦4.忘不掉那天晚上的那些曾经我们就是两颗坠落的流星只留下瞬间的曾经火光终会燃烧殆尽最后温度回归到零5.大一结束考完最后一科那天的晚上,和室友以及对面宿舍的小姑娘聊天,听到了对面宿舍的姑娘share家境…我和老乡室友面面相觑,瑟瑟发抖。
我俩的家乡不算富裕,在读书的城市买房都很难。
而她家已经给她买了房了。
那天之后就放假了,做了一个暑假的心理建设重新回来面对富婆…可能当时觉得自己从小地方来比较自卑吧,现在慢慢发现其实这也没什么的,她人很好,我们朋友照样做。
但当时那种心情现在还记得。
6.我永远不会忘掉那个夜晚,它比我所经历的其他夜晚加在一起还要不可思议。
那是在一个裸露出大块红壤的陌生小镇。
很少的房子,几棵怪模怪样的树,一个小旅馆,墙体由片岩堆砌而成。
7.那个晚上的月亮是滇南天上的灯照着山岳丛林一片朦胧白天这里的一场捕俘战斗检阅祖国卫士的忠诚长着大胡子的傅参谋迟迟还未归来我看到月亮都在躁动。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我永远忘不掉那个夜晚
我永远不会忘掉那个夜晚,它比我所经历的其他夜晚加在一起还要不可思议。
那是在一个裸露出大块红壤的陌生小镇。
很少的房子,几棵怪模怪样的树,一个小旅馆,墙体由片岩堆砌而成。
我忘了是什么原因让自己在这个小镇停留下来。
可能是一场突发的洪水冲垮了公路,一次心血来潮的独自出游,一个互联网上的无聊约会……总之,我背着双肩包到了那儿。
背包里有一台联想笔记本、几件换洗衣裳。
小镇的夜空异常大,群星璀璨。
我看了一眼,就把脖子看扭了。
疼,很别扭的疼,整个人都感觉是长在这种“疼”上,变成了一棵歪脖子树。
我拦住一个穿花衣裳的少年,问小镇哪里有药店。
少年目光警惕,瞪着我,看到我心里都浮现出一头野兽的时候,他才把一只鸡爪般蜷缩的手缓慢地指向树下的旅馆。
是一棵歪脖子的槐树。
我在旅馆老板娘手里买到一盒跌打扭伤膏药。
不是三无产品,上面有国药准定号。
保质期已过了二年整。
我拿不准主意。
身材瘦削的老板娘穿一件灰格子高領外套,眼里有难以捉摸的光。
我问她药膏能否便宜点,一盒五十块钱太贵。
她说就这个价,这里只有鬼才会把脖子扭伤。
我苦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买下药膏。
又问她房间一晚上多少钱。
她说三十块。
我吓一跳。
有了前车之鉴,就算她说一千块,我也不会吃惊。
没想到这么便宜。
交完钱,洗过热水澡,贴上膏药,推开窗户,望远山,再听松涛,听到恍恍惚惚时候,肚子饿了。
我想去找些食物,她敲门进来,问我要不要服务。
我问她都有哪些服务。
她解下外衣,露出一对丰满乳房。
我问她多少钱。
她说,五百,全套,整晚。
她说的六个字,声调与和尚念六字真言差不多。
我动心了,犹豫,怕遇上仙人跳。
我说等会不会有男人拿着斧头闯进来吧?她露齿微笑,说小店信誉良好。
我点燃一根烟,说其实进来也没关系,别闯,男人都怕这种破门而入的
惊吓。
先敲下门,最好也不要像谢耳朵那样敲得那样急。
她哈哈大笑,说,你真逗,我喜欢谢耳朵这个梗。
我说是吗?
我不知道自己是逗,还是不逗。
现在有一个词很流行,叫逗比。
逗比牺牲自己,娱乐他人。
我没有这么高尚,我只是陈述事实。
事实与现实不一样。
乡间的夜晚,如梦似幻。
我上前抱住她裸露的肩头,去嗅她鬓发间的香味。
她刚用过潘婷洗发水。
我喜欢这种香味,比香奈儿、范哲思等香水好闻多了。
她颈脖间挂着一根镶嵌着蓝色珠子的吊坠。
肩胛骨处有一串字母与数字组合成的编码S/NEB05241560,淡青色,不是贴纸,是那种深入皮肤的文身。
我问这是什么?她的眉毛一挑,模样有点诧异,问我真想知道?我说是。
很奇怪,在看到这组编码的一刹那,我的性欲消失了。
她说,那你得加钱。
我说加多少?她伸出一根手指。
我说一百?她摇摇头,说
一千。
我又吓了一大跳。
她看出我眼里的迟疑之色,说,那咱们继续做吧。
她撩拨我,用唇齿伺候我。
她的技术不错,我没有反应,丹田处那股热的气流不知上哪了,只好双手枕头,身体放平,让各种负面情绪啃咬着脑细胞的效率慢一点。
墙壁上有一块污秽的镜子。
镜子里有我与她的裸露。
她的锁骨很漂亮,美人骨。
《续玄怪记》里有一个锁骨菩萨。
我不是胡僧。
我揽她入怀,问:“你喜欢与男人做这件事吗?”她说:“是,舒服。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捏捏她下巴。
我喜欢肉贴着肉,一个女人的肉贴着一个男人的肉,暖和,哪怕什么也不做,就这样贴着。
她理解了这点,身子蜷入我怀里,是猫科动物的那种蜷曲。
肌肤光滑,结实,掌指间有体力劳动的痕迹。
她的发丝有那么几根飘入我的鼻腔。
我打了个喷嚏,继续放平身体,什么也不想。
又痒了。
她是故意的。
她故意用手抓着几根头发来挠我的鼻腔。
我抓着她的手,亲了下,说睡吧。
她嫣然,说好啊,扯过一床被褥。
被褥结实,厚重,带着被米汤浆洗过的香味与小时候的气息。
月光在屋子里涨起来,颇有点水波潋滟的意思,远远近近有秋虫之鸣。
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
我看着隐没在暗中的她的脸庞,脑子里出现几行唐诗,可还没等我念出来,她说:“你听过食骨蠕虫吗?”心头略有不快。
她在这个时候提蠕虫实在大煞风景。
不管什么样的蠕虫,总能让我自行脑补起一幅绦虫在肚子里翻滚的画面。
幸好我不是蠕虫恐惧症患者。
她继续说:“你看《动物世界》吗?”我当然看过。
不仅看过,还特意在互联网上搜索出为《动物世界》配音的赵忠祥与饶颖女士的音频文件,认真学习过。
我握了下她的手说:“睡吧。
”
“蠕虫都是雌雄异体,可科学家2002年在灰鲸遗骨上第一次发现它时,只找到雌性,没有找到雄性。
你知道为什么吗?”她的声音在黑暗中荡漾,如神的灵运行于水面。
是的,如神的灵运行于水面。
我打了个激灵。
她不是夏娃,我也不是亚当。
她不是我肋骨的一部分。
我是嫖客,她是妓女,而且是纯粹的皮肉生意,没有执手相看泪眼,没有小红低唱我吹箫,没有红缨翠带鸾镜鸳衾棋子灯花。
一只飞蛾扑入屋内,在灯光下犹如鬼魂。
我叹口气:“我不是谢耳朵。
我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人。
”
“你说谢耳朵的时候,我想起了蠕虫。
”
“为什么?”
我不大能理解这个逻辑。
谢耳朵与蠕虫会有什么关系呢,谢耳朵那个移动数据库级别的大脑被蠕虫病毒侵入过?蠕虫与蠕虫病毒可
是两回事。
“每个雌性食骨蠕虫体内有近百只雄性个体,只是它们个头太小,要用显微镜才能发现哦。
”她被自己的笑声呛住了,我赶紧拍她的脊背。
她的脊背光滑冰凉,手指上的触感跟摸笔记本电脑差不多。
我有点恍惚,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
她的逻辑跟还没修建完工
的桥梁一样。
也许,她从谢耳朵联想到蠕虫,根本就没有动用过逻辑。
“你想想,这是真正的女王大人啊。
当女王大人表示自己好寂寞想生小虫子,她体内的男宠们一起大叫,我来我来……你再想想,当谢耳朵这样喊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多么有趣啊。
”她柔软的嘴唇贴上我的胸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