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首次核试验的文章有很多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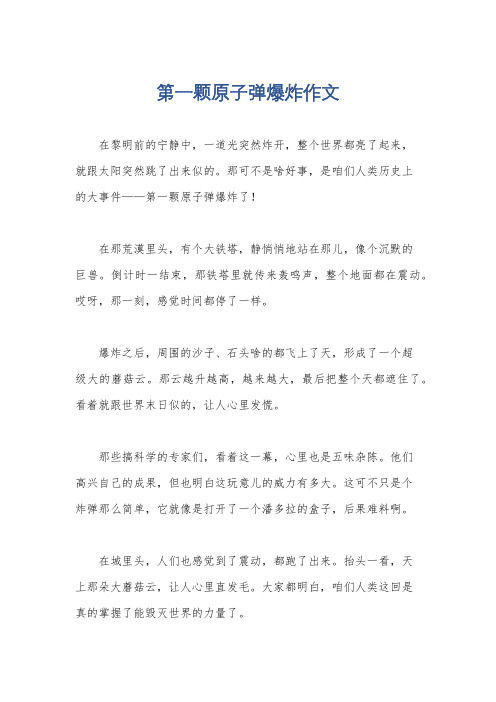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作文
在黎明前的宁静中,一道光突然炸开,整个世界都亮了起来,
就跟太阳突然跳了出来似的。
那可不是啥好事,是咱们人类历史上
的大事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
在那荒漠里头,有个大铁塔,静悄悄地站在那儿,像个沉默的
巨兽。
倒计时一结束,那铁塔里就传来轰鸣声,整个地面都在震动。
哎呀,那一刻,感觉时间都停了一样。
爆炸之后,周围的沙子、石头啥的都飞上了天,形成了一个超
级大的蘑菇云。
那云越升越高,越来越大,最后把整个天都遮住了。
看着就跟世界末日似的,让人心里发慌。
那些搞科学的专家们,看着这一幕,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他们
高兴自己的成果,但也明白这玩意儿的威力有多大。
这可不只是个
炸弹那么简单,它就像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后果难料啊。
在城里头,人们也感觉到了震动,都跑了出来。
抬头一看,天
上那朵大蘑菇云,让人心里直发毛。
大家都明白,咱们人类这回是
真的掌握了能毁灭世界的力量了。
这原子弹一炸,咱们人类就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战争都不再是以前那样了,人类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
以后的日子,咱们可得好好面对这个新玩意儿带来的所有问题和后果了。
第一颗原子弹作文

第一颗原子弹作文篇一《第一颗原子弹:震撼世界的“大炸弹”说起第一颗原子弹,那可真是个超级厉害的玩意儿。
这就像突然冒出来个超级大怪兽,一下子让全世界都惊掉了下巴。
我记得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看那种讲武器的杂志。
有一次我在爷爷的旧书堆里翻出了一本都有点破旧的军事杂志,那里面就有几页是在讲第一颗原子弹的事儿。
当时我就好奇啊,啥东西这么牛,能把人都吓得半死。
那页纸上有张模糊的照片,原子弹爆炸的时候,蘑菇云就像一个巨大的黑色怪物从地上猛地窜起来,边上的东西都被吹得乱七八糟的。
图片旁边的文字说,那时候人们看到这种场面,心里就想,这世界是不是要被这个大炸弹给整没了。
我就想象着自己站在离爆炸不太远的地方(当然这只是想象,真站那可就完蛋了),一定能感觉到地面都在剧烈摇晃,耳朵里全是“轰隆隆”的巨响,就像一万个雷一起炸了似的。
制造这第一颗原子弹的那些科学家可真是厉害得没边了。
他们得在实验室里捣鼓多少回呀,估计那些瓶瓶罐罐、各种电线设备啥的,都能堆满好几个大房子。
他们就像一群魔法师,只不过魔法变成了搞出这么一个能把天翻个底朝天的炸弹。
看那杂志上说,这原子弹背后有好多好多故事,有人在坚持研究的时候穷得叮当响,有人被敌对方派人盯着,就怕他们先搞出来。
这第一颗原子弹出现之后,整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好像一下子就变了。
各个国家看了以后,有的害怕得不行,赶紧想办法自保;有的就想,咱也得有这个厉害的东西呀,于是全世界就进入了一个疯狂搞这类超级武器的时代。
而我就坐在爷爷家的小凳子上,翻着那本杂志愣住了,满脑子都是那巨大的蘑菇云和那一声惊天动地的“轰”。
篇二《第一颗原子弹背后的趣事与惊人之处》第一颗原子弹啊,就像是个带着神秘色彩又超级疯狂的闹剧主角。
它呢,不是平白无故就冒出来的。
我有个同学他爸,那可是军事迷,有一回他给我们讲第一颗原子弹的事儿。
他说在当时搞原子弹,那些个科学家就跟住在破庙里的苦和尚似的,物资极度匮乏。
他们到处去找材料,东拼西凑的。
中国的第一原子弹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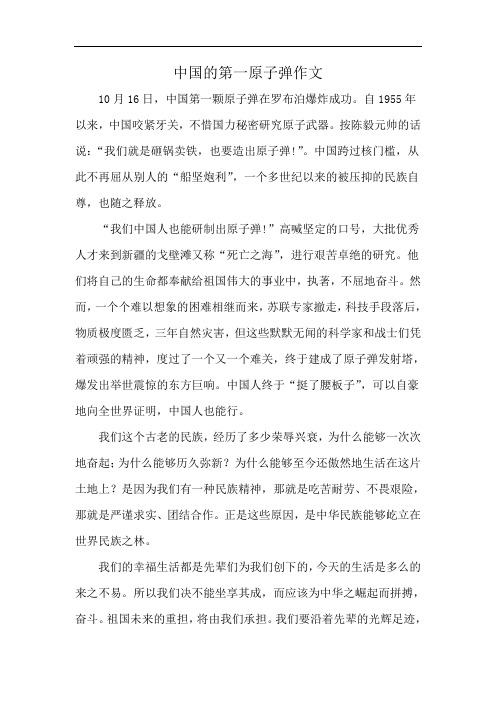
中国的第一原子弹作文
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
自1955年以来,中国咬紧牙关,不惜国力秘密研究原子武器。
按陈毅元帅的话说:“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要造出原子弹!”。
中国跨过核门槛,从此不再屈从别人的“船坚炮利”,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被压抑的民族自尊,也随之释放。
“我们中国人也能研制出原子弹!”高喊坚定的口号,大批优秀人才来到新疆的戈壁滩又称“死亡之海”,进行艰苦卓绝的研究。
他们将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祖国伟大的事业中,执著,不屈地奋斗。
然而,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相继而来,苏联专家撤走,科技手段落后,物质极度匮乏,三年自然灾害,但这些默默无闻的科学家和战士们凭着顽强的精神,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终于建成了原子弹发射塔,爆发出举世震惊的东方巨响。
中国人终于“挺了腰板子”,可以自豪地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也能行。
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经历了多少荣辱兴衰,为什么能够一次次地奋起;为什么能够历久弥新?为什么能够至今还傲然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是因为我们有一种民族精神,那就是吃苦耐劳、不畏艰险,那就是严谨求实、团结合作。
正是这些原因,是中华民族能够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的幸福生活都是先辈们为我们创下的,今天的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所以我们决不能坐享其成,而应该为中华之崛起而拼搏,奋斗。
祖国未来的重担,将由我们承担。
我们要沿着先辈的光辉足迹,
继续在神州大地上谱写壮丽的诗篇!。
两弹一星的感人小故事

两弹一星的感人小故事
有一位叫做中国核父李四光的科学家,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发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1965年中国成功进行了第一次
核试验之后,李四光深深感受到了核武器对人类的威胁和危害。
于是,他开始思考如何利用核技术造福人类。
在1970年代初期,他开始研究用核技术治疗癌症的项目,他希望利用核技术来缓解人类疾病的痛苦。
但是,他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因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基础还极其薄弱,尤其是核安全问题让很多医生和患者望而却步。
李四光不断努力,他通过合作和交流,结合中国自身医学实践和核技术探索,最终创造出了核医学的成功应用。
他发明了一种新的诊断技术——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把基础医
学和核科学融为一体,使人们对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病等重大疾病有了更准确的诊断和治疗评估。
在华夏国家医疗保险体系中,核医学已经被纳入国家医疗保障机构,成为现代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四光的功绩不仅仅是在核武器和核技术的开发,更是在为人类健康和医学进步做出的贡献。
他的精神传承至今,鼓励着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医生致力于科学研究和为人民群众的安康服务。
这则小故事告诉我们,科学技术是非常双刃的,关键在于人们如何使用它。
我们要感谢那些为人类的健康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的科学家,也要努力推动科技创新,在合理、有效的范围内使用技术,让人类早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核弹的自述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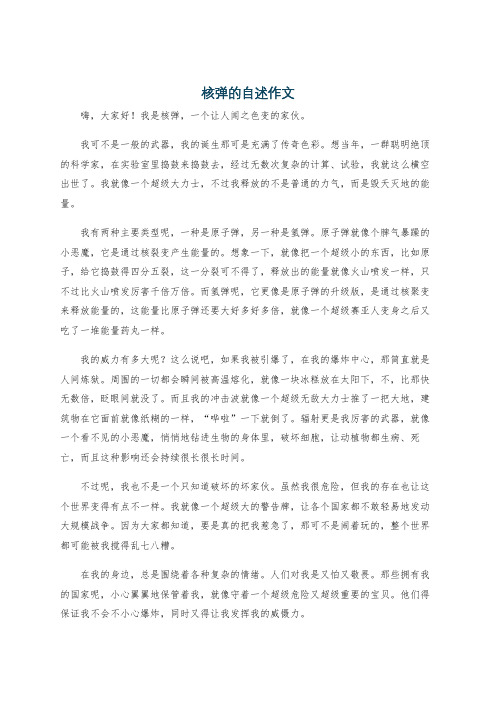
核弹的自述作文嗨,大家好!我是核弹,一个让人闻之色变的家伙。
我可不是一般的武器,我的诞生那可是充满了传奇色彩。
想当年,一群聪明绝顶的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捣鼓来捣鼓去,经过无数次复杂的计算、试验,我就这么横空出世了。
我就像一个超级大力士,不过我释放的不是普通的力气,而是毁天灭地的能量。
我有两种主要类型呢,一种是原子弹,另一种是氢弹。
原子弹就像个脾气暴躁的小恶魔,它是通过核裂变产生能量的。
想象一下,就像把一个超级小的东西,比如原子,给它捣鼓得四分五裂,这一分裂可不得了,释放出的能量就像火山喷发一样,只不过比火山喷发厉害千倍万倍。
而氢弹呢,它更像是原子弹的升级版,是通过核聚变来释放能量的,这能量比原子弹还要大好多好多倍,就像一个超级赛亚人变身之后又吃了一堆能量药丸一样。
我的威力有多大呢?这么说吧,如果我被引爆了,在我的爆炸中心,那简直就是人间炼狱。
周围的一切都会瞬间被高温熔化,就像一块冰糕放在太阳下,不,比那快无数倍,眨眼间就没了。
而且我的冲击波就像一个超级无敌大力士推了一把大地,建筑物在它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哗啦”一下就倒了。
辐射更是我厉害的武器,就像一个看不见的小恶魔,悄悄地钻进生物的身体里,破坏细胞,让动植物都生病、死亡,而且这种影响还会持续很长很长时间。
不过呢,我也不是一个只知道破坏的坏家伙。
虽然我很危险,但我的存在也让这个世界变得有点不一样。
我就像一个超级大的警告牌,让各个国家都不敢轻易地发动大规模战争。
因为大家都知道,要是真的把我惹急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整个世界都可能被我搅得乱七八糟。
在我的身边,总是围绕着各种复杂的情绪。
人们对我是又怕又敬畏。
那些拥有我的国家呢,小心翼翼地保管着我,就像守着一个超级危险又超级重要的宝贝。
他们得保证我不会不小心爆炸,同时又得让我发挥我的威慑力。
研究原子弹艰苦作文

研究原子弹艰苦作文
《原子弹背后的艰苦岁月》
嘿,您知道研究原子弹那阵子有多艰苦不?
我给您讲讲我听说的一个事儿啊。
那时候,有个科学家叫老张,为了能搞出原子弹,那真是拼了老命。
他们工作的地方在大西北,那条件,差得没法说。
住的房子破破烂烂的,风一吹,沙子直往屋里灌。
老张他们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干活儿。
有一回,老张他们要做一个实验。
那实验设备可简陋了,全靠他们自己动手改造。
老张蹲在那机器旁边,一蹲就是好几个小时,腿都麻得没知觉了。
吃的东西也不好,天天就是窝头咸菜。
可老张不在乎,心里就想着把实验做好。
有一天,老张正忙着呢,突然肚子疼得厉害。
原来是长期营养不良,胃出了毛病。
可他咬着牙,愣是坚持把工作做完才去休息。
就这么着,老张他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您瞧瞧,这就是研究原子弹的艰苦。
但也正是因为有了像老张这样不怕苦不怕累的人,咱们国家才能有自己的原子弹啊!
回过头想想,老张他们的艰苦付出,真的太了不起啦!。
中国第一课原子弹爆炸中相关作文

中国第一课原子弹爆炸中相关作文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
从此,中国步入了拥有核武器国家的行列,我们不再惧怕任何大国的核威慑。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建立强大的国防,不受帝国主义的欺负,我国于1955年开始筹建核工业。
1959年,苏联撤走了支援中国的专家,中国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工业。
1962年,我国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专门领导机构,负者原子弹的研发工作。
在大家的努力下,在那个艰难的年代,我国的核试验最终取得了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成为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我国的原子弹正式起步研制是1959年下半年,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供应,副食品短缺。
核武器研究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同样度过了每天挨饿、身体浮肿的艰苦时期。
原子弹的爆炸成功,谈何容易。
除了要突破科技领域中的无数难关,真正掌握确保原子弹起爆成功的奥秘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情况,那就是国家当时正处于经济最困难时期。
可以说中国人勒紧了裤带,把原子弹研制出来,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科学务实、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将会永放光芒。
远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百万大军在那里从事科研工作和基建工程,那里大戈壁的客观条件本身就很艰苦了,在三年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断炊的问题,更是雪上加霜。
罗布泊本来植物就很稀少,可以吃的如榆树叶、沙枣树籽,甚至骆驼草,几乎都被他们拿来充饥了。
这里我想起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的一段话:“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辛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今天的朋友们,你们可曾想到过曾经有过如此困难、如此忍饥挨饿的人把原子弹搞出来。
有了他们艰苦奋斗的闪光精神,才有我们今天的强大中国。
这难道不是奇迹吗?原子弹爆炸后,第一时间看到的能量是闪光,科学家把它叫做光辐射,有极强的亮度,但是它比起从事我国原子弹事业的科技人员的内心的闪光,也只是第二位的。
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作文

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作文
《原子弹爆炸那点事儿》
嘿,你们知道不,咱国家当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可是轰动世界的大事儿呀!我爷爷就给我讲过他那个时候的事儿。
爷爷说,那时候他还年轻呢,消息传出来的时候,他正在地里干活儿。
突然有人喊着:“原子弹爆炸啦!咱们国家成功啦!”爷爷一听,锄头都顾不上拿,就跟着大家跑起来。
到了村里的空地,大家都兴奋地议论着,一个个脸上都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爷爷说那感觉就像是过年一样,特别热闹。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原子弹爆炸意味着什么,虽然很多人也并不是特别懂那些专业的东西,但就是知道咱国家厉害了,以后不会被人欺负了。
爷爷回忆说,那几天村子里都充满了一种特别的氛围,仿佛空气都变得不一样了。
而且听说有的地方还放起了鞭炮庆祝,就好像过节似的。
爷爷感慨呀,他说他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场景。
看着爷爷那激动的样子,我也能感受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对那时候人们的重大意义。
这可是咱国家强大起来的重要标志呀!
如今,咱们国家发展得越来越好,科技也越来越先进。
回想当年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真的是特别神奇又了不起的事情。
咱可得珍惜现在的好生活,也得为国家的未来继续努力呀!哎呀,不说了,我得去奋斗啦,就像咱国家研究原子弹那样,努力向前冲!。
我国研发原子弹成功的文章

我国研发原子弹成功的文章1964年10月16日,在新疆罗布泊的上空,我国第一次将巨大的火球和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也意味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那一天,整个中国大地都洋溢着激动和喜悦,深秋的夜晚,首都长安街上蜂拥的人群,追逐着散发原子弹爆炸成功号外的大卡车,全市人民奔走相告,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广播,全世界都沉浸在一片喧哗声中。
在最近热映的《我和我的祖国》电影中,更是作为七个故事之一计入中国重大历史事件。
我国第一个原子弹爆炸成功对于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维护世界和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它在宣告着一个曾经落后的大国正在以强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之林,这是一封震惊世界的宣言书,更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
荒芜的戈壁滩上,矗立着一座巨塔,它高102米,由8647个部件构成,是当时名副其实的“中国最高塔”。
它的全部使命只是为了原子弹的试爆,就像是从事着这份事业的人们。
程开甲,中国核物理试验的开拓者之一,曾经受教于诺贝尔奖得主的玻恩教授,并与薛定谔等国际知名顶尖教授进行学术探讨。
和邓稼先、钱学森一样,程开甲最终选择回国,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南京大学。
1960年,他接到一项秘密任务,“派你造原子弹”,就这样他“消失了20年”。
当时所有和研制原子弹相关的工作和人员,都被列入机密,甚至,还有一套密语被设计出来。
原子弹因其形状,被谐音称作“老邱(球)”、“邱小姐”,复杂的导管装置被称作“小姐的头发”,支撑系统被称作“梳妆台”,装配叫“穿衣”,接雷管叫“梳辫子”……各中滋味,从来无人知晓。
研制原子弹的关键时间,是1959-1961年。
那时候,全国爆发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很多地方饿死了人。
这也影响到了核武器技术研究所,食品供应不足,电力供应不足,很多时候,靠喝水充饥,点着油灯工作。
当时的人一部分去攻克理论难关,另一部分人去进行原子弹的试验,当时最大的难关就是不知道原子弹爆炸流程,苏联专家撤走的时候,曾扬言“给你们一颗原子弹,你们也爆不响”,但我们不信这个邪,经过反复的研究,精密的计算,终于提出了原子弹塔爆方案,这是一项独立自主的,具有创新的核爆炸。
原子弹研发作文

原子弹研发哎,说起原子弹,这可真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话题。
不过,今天咱们不聊那些沉重的历史,也不谈什么政治,就说说原子弹研发背后那些有趣的小故事,让你在轻松幽默中了解这个改变世界的力量。
话说,原子弹的研发,那可是个技术活儿。
你想想,那会儿的科学家们,一个个都是穿着白大褂,戴着眼镜,手里拿着试管,看起来挺斯文的。
但实际上,他们干的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就像那个著名的曼哈顿计划,那可是集结了全世界最聪明的脑袋,就为了搞出这个大家伙。
记得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个故事,说是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正忙着调配原子弹的原料。
他一边搅和着那些危险的化学品,一边还得小心翼翼地避免自己被辐射。
突然,他发现试管里的液体开始冒泡,颜色也开始变化。
他紧张得不得了,心想:“这下完了,是不是要爆炸了?”结果,他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不小心把咖啡洒进去了。
你说这事儿逗不逗?还有一次,我听一个老科学家讲,他们当年在研发原子弹的时候,为了保密,连实验室的门都是特制的。
有一次,一个新来的助手,不知道门的机关,硬是推不开。
他急得满头大汗,最后只好用脚踹。
结果,门是开了,但他的脚也肿了好几天。
这事儿在实验室里传为笑谈,大家都说,这门比原子弹还难搞。
不过,说归说,笑归笑,原子弹的研发可不是儿戏。
那可是关乎到国家安危,世界和平的大事。
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是为了确保这个大家伙能安全、有效地发挥作用。
他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一个细节。
有一次,一个科学家在计算原子弹爆炸的威力时,不小心把一个数字算错了。
结果,整个团队都得重新来过。
那个科学家自责得不得了,好几天都没睡好觉。
后来,他终于把数字算对了,团队也松了一口气。
这事儿告诉我们,科学这东西,容不得半点马虎。
总之,原子弹的研发,是个既严肃又有趣的话题。
它让我们看到了科学家们的聪明才智,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责任和担当。
虽然原子弹的存在,给世界带来了很多争议和不安,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平,更加重视科技的力量。
亲历原子弹核爆炸试验

我 们 翻 过 了天 山 ,经 过 库 尔 勒 , 直 到 半 夜 才
参试者进入爆心执 行任 务前合 影 ( 前排 中为作 者 )
到 达基 地—— 米 兰 。 从 米 兰 到 试 验 驻 地 就 不 远 了 , ~ 到 驻地 就 受
由 著 名科 学 家 贝 时 璋 教 授 担 任 所 长 的 中 国科 院生物 物理 研 究所 ,有 一支 由 贝先生亲 自领 导 的 文 . 射生物 学研 究 队伍 ,为我 国的原 子弹事 业做 出了
一
物 回收任 务 。紧接着 进 行实验 动物 、卡车 和个 人 的
防护 用具 的洗 消处理 。我 们个 人 的清 洗 ,是在 沙漠 中用 塑料 布搭 成 的临时淋 洗 问里完 成 的,里面有 充
足 的热水 ,能 得到 充分 的洗涤 。从 爆心 带 回的放 射 性物 质会 被清 洗干净 ,以保证 参试 者 的安 全 。这 也 是我 们参 试几个 月来 唯 一洗 的一次澡 。
勺 地上 ,手 拿汽 油喷灯 用 火烤 发动机 和 水箱 ,经 过
一
个 多小时 的烘烤 汽 车才 能发 动 ,他们 必须 赶在 天
毛 前完 成全 部准备 工作 。装 满 了人 员和 参试物 资 的
结 晶 ,大 大 小小 的结 晶有 透 明的 、有带 色 的 ,一 眼
21 前 论 I NA 0 ・ 进 坛Q NI UT 1 3 AJ L N N
4 7
◆ 往 事 回 眸 ◆
望不到 边 ,可想而 知 当时爆 炸温度 之 高 ,真 开 了眼
界。
把动 物笼 子抬 上卡 车 。这是很 危 险的工作 ,但 大家
丝毫 没有 考虑 个人 安危 ,齐 心协 力 ,圆满 完成 了动
两弹一星事迹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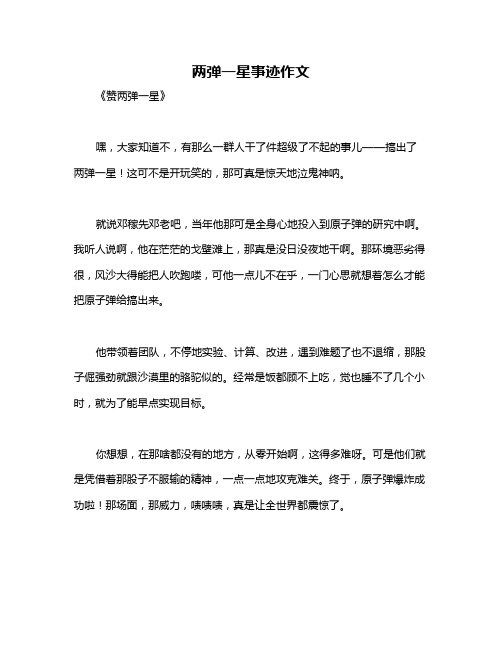
两弹一星事迹作文
《赞两弹一星》
嘿,大家知道不,有那么一群人干了件超级了不起的事儿——搞出了两弹一星!这可不是开玩笑的,那可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呐。
就说邓稼先邓老吧,当年他那可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原子弹的研究中啊。
我听人说啊,他在茫茫的戈壁滩上,那真是没日没夜地干啊。
那环境恶劣得很,风沙大得能把人吹跑喽,可他一点儿不在乎,一门心思就想着怎么才能把原子弹给搞出来。
他带领着团队,不停地实验、计算、改进,遇到难题了也不退缩,那股子倔强劲就跟沙漠里的骆驼似的。
经常是饭都顾不上吃,觉也睡不了几个小时,就为了能早点实现目标。
你想想,在那啥都没有的地方,从零开始啊,这得多难呀。
可是他们就是凭借着那股子不服输的精神,一点一点地攻克难关。
终于,原子弹爆炸成功啦!那场面,那威力,啧啧啧,真是让全世界都震惊了。
这就是咱国家的两弹一星事迹,这背后是无数像邓老这样的英雄们的付出和努力啊。
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
咱可得好好向他们学习,也为国家出一份力呀!
现在想起这些事儿,还是觉得特别震撼呢。
两弹一星,永远的传奇!。
邓稼先发明核弹的故事作文

邓稼先发明核弹的故事作文“哎呀,爸爸,快给我讲讲邓稼先爷爷的故事嘛!”我缠着爸爸说道。
爸爸笑着摸了摸我的头,开始讲述起来:“邓稼先爷爷呀,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他为了咱们国家能拥有强大的核武器,付出了太多太多……”
我静静地听着,思绪仿佛被带到了那个充满挑战与奋斗的年代。
邓稼先爷爷生活的那个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和威胁。
但是邓稼先爷爷毅然决然地投身到了核弹研究的工作中。
他和很多科学家一起,在艰苦的环境下,日夜不停地进行着研究和实验。
我仿佛看到了他们在简陋的实验室里,专注地计算着各种数据,脸上满是认真和执着。
“这个数据一定要精确,不能有一丝差错!”邓稼先爷爷严肃地对身边的同事说。
他们互相讨论,互相鼓励,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着。
那时候,条件很差,他们吃不好,睡不好,但是没有一个人抱怨,没有一个人退缩。
“为了国家,这点苦算什么!”这是他们常说的话。
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和失败,邓稼先爷爷他们终于取得了成功!当那朵巨大的蘑菇云升起的时候,邓稼先爷爷和他的同事们激动地欢呼起来。
“哇,邓稼先爷爷太厉害了!”我不禁感叹道。
爸爸点点头说:“是呀,他是我们国家的英雄。
正是因为有了像他这样的科学家,我们的国家才能越来越强大,我们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
我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也像邓稼先爷爷那样,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邓稼先爷爷的故事,就像一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我前进的道路。
我会永远记住他,记住他的奉献和付出。
两弹一星高三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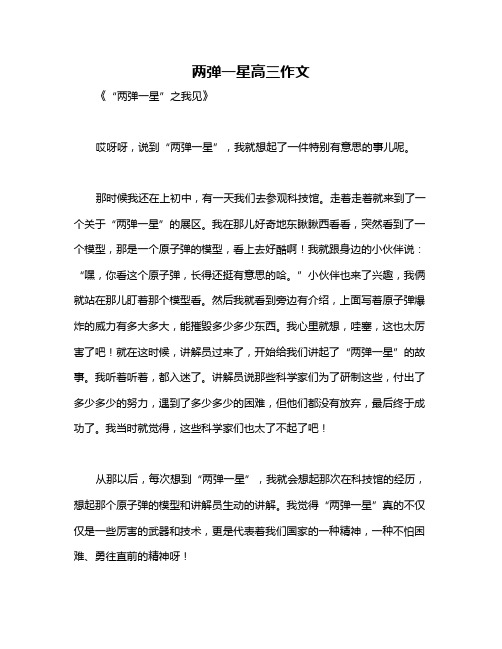
两弹一星高三作文
《“两弹一星”之我见》
哎呀呀,说到“两弹一星”,我就想起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呢。
那时候我还在上初中,有一天我们去参观科技馆。
走着走着就来到了一个关于“两弹一星”的展区。
我在那儿好奇地东瞅瞅西看看,突然看到了一个模型,那是一个原子弹的模型,看上去好酷啊!我就跟身边的小伙伴说:“嘿,你看这个原子弹,长得还挺有意思的哈。
”小伙伴也来了兴趣,我俩就站在那儿盯着那个模型看。
然后我就看到旁边有介绍,上面写着原子弹爆炸的威力有多大多大,能摧毁多少多少东西。
我心里就想,哇塞,这也太厉害了吧!就在这时候,讲解员过来了,开始给我们讲起了“两弹一星”的故事。
我听着听着,都入迷了。
讲解员说那些科学家们为了研制这些,付出了多少多少的努力,遇到了多少多少的困难,但他们都没有放弃,最后终于成功了。
我当时就觉得,这些科学家们也太了不起了吧!
从那以后,每次想到“两弹一星”,我就会想起那次在科技馆的经历,想起那个原子弹的模型和讲解员生动的讲解。
我觉得“两弹一星”真的不仅仅是一些厉害的武器和技术,更是代表着我们国家的一种精神,一种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呀!
如今我都上高三了,但是这件事还是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两弹一星”的精神也一直激励着我,让我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会想起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们,然后告诉自己,要努力,要加油,不能轻易放弃。
这就是我和“两弹一星”的故事啦,嘿嘿!。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散文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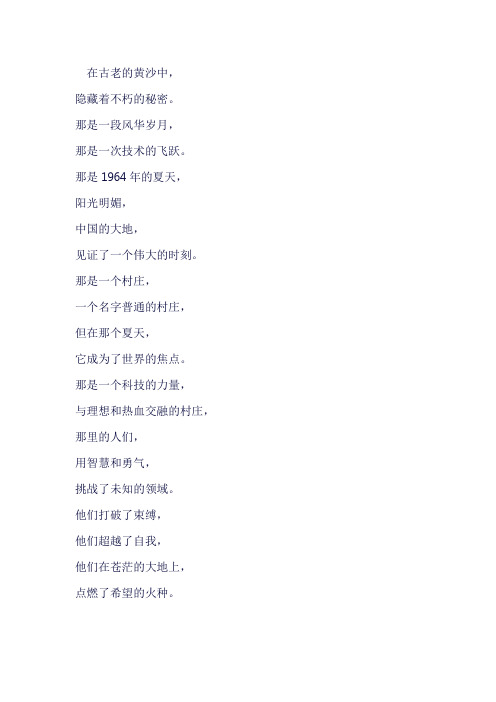
在古老的黄沙中,
隐藏着不朽的秘密。
那是一段风华岁月,
那是一次技术的飞跃。
那是1964年的夏天,
阳光明媚,
中国的大地,
见证了一个伟大的时刻。
那是一个村庄,
一个名字普通的村庄,
但在那个夏天,
它成为了世界的焦点。
那是一个科技的力量,
与理想和热血交融的村庄,那里的人们,
用智慧和勇气,
挑战了未知的领域。
他们打破了束缚,
他们超越了自我,
他们在苍茫的大地上,
点燃了希望的火种。
他们的名字,
或许已被历史遗忘,
但他们的付出,
却铭刻在了星辰中。
他们带着坚定的信念,面对困难的挑战,
他们以不屈的意志,
书写了人类的历史。
他们的努力,
换来了一个奇迹,
那是一颗原子弹,
那是一个国家的骄傲。
那是一颗蘑菇云,
它升起了在中国的天空,它象征着力量,
它象征着希望。
那是一个时代的开始,那是一个国家的崛起,那是一个民族的自信,那是一个世纪的见证。
如今,
当我们仰望星空,
当我们回望历史,
我们不禁想起那个夏天,
那个普通的村庄。
那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诞生地,那是人类科技的伟大里程碑,
那是无数无名英雄的付出,
那是永恒的纪念。
两弹一星指的作文

两弹一星指的作文“两弹一星”,这四个字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那可真是意义非凡。
说起“两弹一星”,咱得先弄明白它到底指的是啥。
简单来说,“两弹一星”指的是核弹(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
这可不是一般的东西,那是咱们国家科技实力和国防力量的重要象征。
就拿原子弹来说吧,当年为了搞出这玩意儿,那真是费了老大的劲。
在那个时候,咱们国家的条件可不咋样,要技术没技术,要设备没设备。
但是,咱们的科学家们那股子劲儿,真是让人佩服得不行。
我曾经看过一些关于那段历史的资料和纪录片,那里面的细节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比如说,那些科学家们,好多都是从国外学成归来,放弃了国外优厚的条件,一心就想着为祖国出力。
他们钻进实验室,没日没夜地干。
当时的计算工具都很简陋,很多数据都是靠算盘一点点打出来的。
我还记得有一位科学家,叫邓稼先。
他为了研究原子弹,那真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搭进去了。
他带着团队在大西北的荒漠里,风餐露宿。
那地方环境恶劣得很,吃不好睡不好,可他们谁都没有抱怨。
邓稼先经常亲自到试验现场,有时候为了获取第一手的数据,他不顾危险,离爆炸点特别近。
还有那些负责后勤保障的工作人员,也是功不可没。
他们要保障科学家们的生活物资供应,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能搞来一点好吃的,给大家改善改善伙食,那都是不容易的事儿。
再说导弹。
导弹这东西,可不像咱们平时看到的玩具火箭那么简单。
它的研制需要涉及到好多复杂的技术,什么飞行控制啦,燃料推进啦,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岔子。
咱们的科研人员从零开始,一点点摸索,一次次试验。
失败了就重新再来,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记得有一次试验,导弹升空后出现了故障,没有按照预定的轨迹飞行。
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现场的气氛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但是,科研人员们没有慌乱,迅速收集数据,分析问题,最后找出了原因,解决了难题。
最后说人造卫星。
当咱们国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的时候,那场面,真是让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两弹一星作文500字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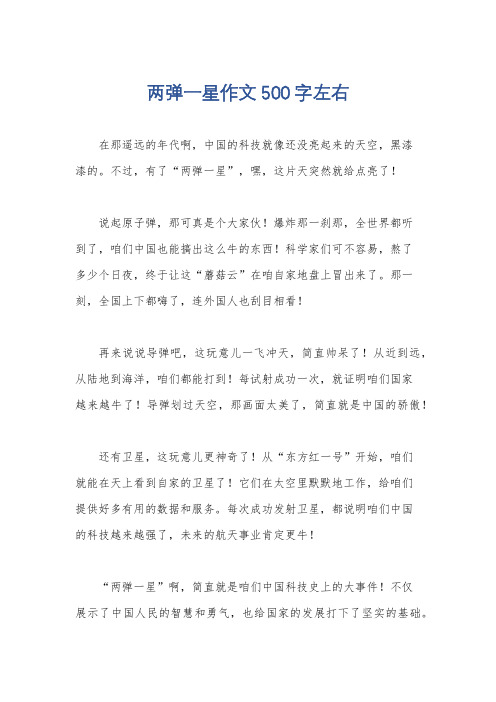
两弹一星作文500字左右
在那遥远的年代啊,中国的科技就像还没亮起来的天空,黑漆
漆的。
不过,有了“两弹一星”,嘿,这片天突然就给点亮了!
说起原子弹,那可真是个大家伙!爆炸那一刹那,全世界都听
到了,咱们中国也能搞出这么牛的东西!科学家们可不容易,熬了
多少个日夜,终于让这“蘑菇云”在咱自家地盘上冒出来了。
那一刻,全国上下都嗨了,连外国人也刮目相看!
再来说说导弹吧,这玩意儿一飞冲天,简直帅呆了!从近到远,从陆地到海洋,咱们都能打到!每试射成功一次,就证明咱们国家
越来越牛了!导弹划过天空,那画面太美了,简直就是中国的骄傲!
还有卫星,这玩意儿更神奇了!从“东方红一号”开始,咱们
就能在天上看到自家的卫星了!它们在太空里默默地工作,给咱们
提供好多有用的数据和服务。
每次成功发射卫星,都说明咱们中国
的科技越来越强了,未来的航天事业肯定更牛!
“两弹一星”啊,简直就是咱们中国科技史上的大事件!不仅
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勇气,也给国家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都是咱们中国的骄傲!咱们得铭记这段历史,为了祖国的明天继续加油干!。
中国第一颗原子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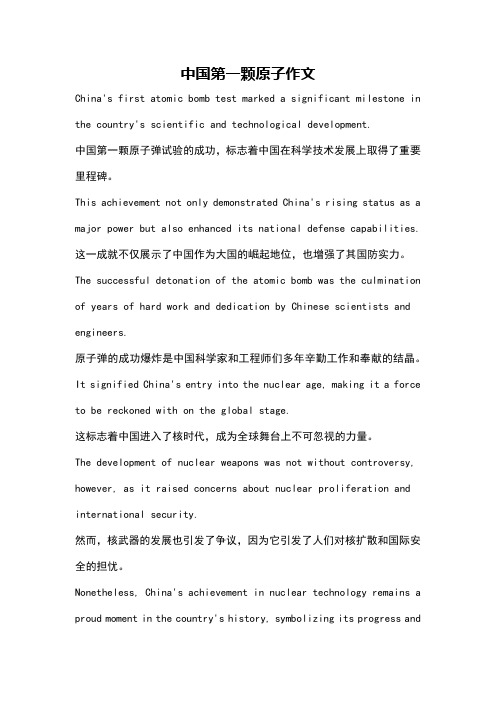
中国第一颗原子作文China's first atomic bomb test marked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in the country'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在科学技术发展上取得了重要里程碑。
This achievement not only demonstrated China's rising status as a major power but also enhanced its national defense capabilities. 这一成就不仅展示了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地位,也增强了其国防实力。
The successful detonation of the atomic bomb was the culmination of years of hard work and dedication by Chinese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原子弹的成功爆炸是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多年辛勤工作和奉献的结晶。
It signified China's entry into the nuclear age, making it 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 on the global stage.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核时代,成为全球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was not without controversy, however, as it raised concerns about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然而,核武器的发展也引发了争议,因为它引发了人们对核扩散和国际安全的担忧。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回忆首次核试验的文章有很多,其中有些文章写的真实而又精彩。
我的文笔很差,那么就凭我的记忆,来个实话实说,随便想到哪写到哪吧。
)四十四年前的10月16日,作为一名我国首次核试验的参加者,每年自己的生日可能会忘掉,但唯10.16这一天,却从来没有忘记过,我想大家都是如此吧!能亲自参加首次核试验,确实是一生中的最大荣幸。
首次核试验进场人数,控制的非常严格,要求是安岗位定人,“一个萝卜一个坑”,多一个也不准。
我们21所是“核试验基地研究所”,也是核试验场内的主力军,承担着90%以上的测试任务。
1964年初,全所有400多名技术人员,而这次进场的只有200人左右;五室(理论研究室)当时有62个人,也只批准了27人进场,连我们室的元老王懋江、蒋伯诚同志也都被留在了北京。
唯我们放射性沉降组最运气,邹德山、杨成林、朱明发、刘贵荣、王可定和高连科,六个人要全部上阵。
还记得在临出发前,我的痔疮病突然发作而不得不卧床休息,室里有一位同志开玩笑地说:“大高,看来这次任务你是参加不了啦!”但第二天我还是随队按时出发了。
首次核试验的保密之事我们是六月进场的,其实美国早在几个月前就已察觉到中国即将要进行核试验,(这些事现在都已公开了)。
我记得,那时经常有美国的间谍卫星和U-2飞机从场区上空飞过。
102米高,76吨重的大铁塔立在戈壁滩上、数百顶帐篷的突然出现、上千辆汽车及五千多人员的频繁活动,美国能不知道吗?当然,他知道归知道,保密教育还是要天天讲、天天抓。
但是,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玄乎,似乎我们一点自由都没有了。
比如,我看过公安部一同志的回忆录,他写道:“进入核试验期间,一律禁止私人通信。
”其实并非完全如此。
在场区一次大会上,张爱萍副总长就通信的保密问题做了三点指示:“一、无事不写信;二、有事少写信;三、写信不泄密。
”当然,21所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大家写信时,信封上仍以北京通县为发信地址,21所每周派通信员回北京一次送、取信件。
五室申江河指导员则建议大家写好信后,最好找别的同志帮助看看,(当然是自愿的了)“把把关”。
我记得桑凤嶠、朱明发等同志写给爱人的信都让我帮看过,看什么看,难道这些老同志还要别人把关吗?核试验前有三大核心机密:爆炸当量、试验方式及爆炸时间(即“零时”)。
试验当量,我们这些搞理论计算的早在六三年接受任务时就已知道;塔爆,已是明摆在那了。
那么最后的绝密就是“零时”。
在中央确定了大致试验时间后,我们沉降预报组,就与基地气象室预报员进入了201#地下室。
气象室在顾震潮教授带领下负责预报天气,(在同一个房间,我们列席旁听),然后我们就根据报的天气做出场区内和场区外的放射性沉降预报,最后送试委会张爱萍那里审查。
尤其是进入“零”前72小时以后,几个小时就要预报一次,那几天我们是不分昼夜连续工作,实在困了就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
除了试委会的核心成员外,在21所内,乔主任、邹进上(他参与天气预报)加上我们沉降组六个人恐怕是最早知道“零时”的人了。
由于进入了试前的紧张时刻,大家都在盼着“零时”快快到来。
那两天和其他同志相遇时,都想从我们这几个人的言语中知道何时是“零时”?可是,我们谁也不敢讲。
有一次见旁边无人,老桑对我用手画了个“?”,我也只能小声说了句“快了!”场内吃、穿、住、行的苦与乐几乎所有的回忆文章都谈到了试验场喝苦水,耐炎热,抗风沙。
从六月到十月,可以说是戈壁滩里最难熬的日子。
刚进场时,我们21所集中住在101#,在铁塔的西南约四公里处。
几十顶帐篷排列有序,像一个小村庄似的。
在远离“村”的一个角落里由五顶帐篷组成一个小院,因为住的全是女同志,所以被取名为“木兰村”;在另一个角落里,还有一个由三顶小帐篷成品字型排列的小院,因为住着的是我们五室的人。
我们理论室的人整天就是摇计算机、拉计算尺、画图、看资料,所以很多人称我们这是“夫子庙”。
我们沉降组六个人和申指导员同住一个小帐篷,中间只留下那么不到四平米的空间就是我们的“办公室”了。
七八月份,戈壁滩白天热到四十多度,连刮的风都是烫人的,尽管不断地往沙土地上洒水,但还是热的受不了。
不知谁提出的,反正大家都是在计算,干脆叫哈森和张子珍两位女同志回她们“木兰村”去算。
这一下我们男同胞可解放了,索性脱了上衣,光着膀子在帐篷里工作,真痛快!吃,就不必多说了,进过场的人都有体会。
每天就那么几样,土豆、萝卜、粉丝、蛋黄粉、花生米,连大白菜都很难见到,吃上冻猪肉已算是改善了。
我记得,桑凤嶠负责炮伞取样,爆后要乘飞机去沾染区上空寻找取样伞,他享受空军的空勤灶待遇,也只不过每顿饭多给几条罐头装的小凤尾鱼,外加一个苹果。
老桑是大连人,早吃腻了这东西,而我恰恰爱吃凤尾鱼,所以他的空勤灶大多是由我代劳了。
说到喝,所有文章都会提到那又苦、又咸、又涩嘴的孔雀河水。
进沾染区吃保健灶的,每顿早餐可得到一碗用孔雀河水冲的奶粉,那简直是比中药汤都难喝,但为了保持体力,再苦也得喝。
说句心里话,在试验场内,除了工兵团,可能就算我们21所是最苦了,知识分子要接受改造嘛。
场区内有二十多个效应单位,有的单位人家从北京带运水车来,自己到甘草泉去拉水,(我们都叫那是“甜水”!)我每次去效应单位帮忙,临走时都会给我装满一壶“甜水”,简直等于送了一瓶好酒似的。
说到“穿”,也许有人感到奇怪,与穿衣有何关系?进场时,我们一般都是身穿一套,再带一套军装以备换洗,原以为这足够了,可是后来就惨了。
这就要说到了“行”,我们五室虽然是搞理论的,但也几乎要天天跑各工号、各效应大队。
我们这个级别的技术人员,交通工具就是要靠自己到戈壁滩上去拦大卡车。
解放牌卡车大多数是矮梆的,人在上面不能站,必须坐着、蹲着或跪着,戈壁滩上那搓板路,简直能把人颠散了架。
没多久,很多同志的裤子全磨烂了,是缝没法缝,补又没有布补。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我们终于想出了办法,去医疗队找护士要医用胶布,人家也很同情我们,每次去要,是有求必应。
回来将白胶布放在裤子里面,然后从外面将磨烂部分往上一压就粘上了。
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张超所长(那时习惯称他张部长)发现我们很多人裤子的膝盖或屁股上都贴着白布,感到很奇怪。
张部长听我们一讲缘由,他即难受,又生气。
没过几天,所里就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套新的战士服。
没想到这件事被谁给捅到了基地,结果基地对21所“违反规定,擅自发放军装”作了通报批评。
张部长也是一个很倔的人,“责任由我承担,反正大家有裤子穿了!”这虽然是一件小事,我却永远忘不了。
四个月洗了一次澡从六月进场到十月下旬撤到马兰,这120多天在场区内是没有星期天的,只记得“八、一”休息一天。
大家都两个月没洗过澡了,这一天21所决定,全体人员去孔雀河洗澡。
101#距孔雀河不到十公里,十几辆大卡车,拉着我们这200多人浩浩荡荡地去了孔雀河。
不知谁选的这个位置,在河的转弯处恰好有一个几米高的大土丘,可以将男女同志隔开。
六十年代,孔雀河水的流量还是可以的,河宽处有20多米,水深不过膝,可以淌水过河;而河窄的地方只有四五米宽,这种地方可真是“水深莫测”,听说曾淹死过人。
我和罗箭、王可定曾大胆地去试探过,下去了三米多深尚未触到底。
进入九月,试验准备工作一切就绪,21所撤到了201#地区,整个场区进入待命状态。
可是不久便得知,“十、一”前肯定是不试验了,而且开始忙着发棉衣、领炉子,要大家有思想装备,有可能要在场区内过冬。
在后一段时间,每天就是开会、学习、休息。
有一天下午,呆得实在难过,201#离孔雀河又很近,我和王可定等几个人就对申指导员说:“咱们这么呆着太寂寞了,干脆大家去孔雀河边玩玩吧!”指导员担心我们去了孔雀河就要下河游泳,我们说:“现在都是穿棉衣的时候了,我们不会下去游泳的。
”指导员说:“去可以,但到时得听我的啊!”哪知一到了河边,我和罗箭、刘贵荣、王可定脱了棉衣,拿着邹德山的蚊帐就下河里去捞鱼了。
别看已是穿着棉衣的时候,可是中午的孔雀河水却一点儿也不凉。
尽管指导员在岸上一直喊着让我们快上来,我们全当没听清,就这样,我们又洗了一次澡。
再说说张爱萍副总长谈到核试验总指挥张爱萍上将,他和大家一样,无论走到哪,都是身背水壶,带着墨镜和草帽,人称这是“戈壁滩上三件宝”。
若不是在近处才能看清楚他领章那三颗星,还很难认出他就是张爱萍上将。
张爱萍经常到我们21所驻地来,有时是检查工作,有时是开大会作报告。
谈起作报告,人们自然会想起“猴子盘儿”那件事。
那是进入待命状态时,张爱萍专门来21所作动员报告。
他特别强调,各种仪器设备都调试好了,就不要轻易再动它了。
于是他就讲了个“猴子盘儿”的四川民间谚语,意思是母猴生了个小猴,喜欢地每天盘来盘去,最后给盘弄死了。
散会后各个室回去要进行讨论,四室有位同志就说:“该盘还得盘,小猴拉屎撒尿,不能不管吧?”这句话不知怎么传到张爱萍那了,结果第二天开会时,张爱萍说:“哪个说小猴拉屎撒尿不让你管了,你这不是和我抬杠吗?”全场同志听了哈哈大笑。
还有一件事,有一天,场区各大单位负责人去720#开会,散会时天已黑了。
二十多辆小车排成一长串开往201地区。
最前面的那辆车没看清路,冲到一个土坡上翻了车,结果后面的车一辆辆接着翻,有几个干部受了伤。
为此事,在一次会上,基地一位领导说要处分那位司机,还说以后绝不准再开快车了。
张爱萍马上打断了他的话,说:“就不要处分司机了,他又不是有意要翻车的。
”接着又说:“为什么不准开快车?要是汽车开得慢慢腾腾的,那以后我宁愿自己走路。
要讲辩证法嘛,该快就快,该慢就慢才对!”熟悉张爱萍的人都知道他的脾气,那是不管谁,批评起来一点面子也不留,但批评完了和没事一样。
我就想起试验后的那天夜里,指挥部突然来电话,叫乔登江马上到张爱萍那去,乔主任拉着我陪他去了。
一进指挥部张爱萍就问:“乔老爷,你报一下,现在放射性烟云已到哪啦?放射性浓度是多少?”我和乔主任马上算,然后报了一个大概数字(这东西是最难估算的)。
张爱萍从背后拿出一张纸看了一眼说:“不对!重算。
”又算了一次,还是不对,结果是挨了一顿训,我是躲在乔主任身后不敢讲话,后来总算放我们走了。
一出门,乔主任就往左走,那边是一片戈壁滩,我感到莫名其妙,便问他:“乔主任,咱还要到哪去啊?”他突然发现方向走反了。
他说:“唉!让他给训糊涂了,他拿着测得的数据让我猜,我又不是神仙。
”别看张爱萍训乔主任,可每当核试验现场遇到难题时,他还是常常想到要找咱们的乔老爷!这是第二炮兵原司令员李旭阁夫人耿素墨向我讲述的一个故事,装在我心中多年了,每每想起,感慨不已。
</p><p>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两弹一星”功臣邓稼先罹患癌症去世后,他的夫人许鹿希,一直沉浸在高贵爱情里的世家之女,无法自拔。
不仅原封不动摆放着邓稼先生前家里所有物品、书籍和纸条,任其岁月烟云褪色,尘埃落下,而且开始做一件事情,追踪当年到过核试验爆炸中心的两弹一星功臣的身体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