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文学作家传记中的“隐讳”(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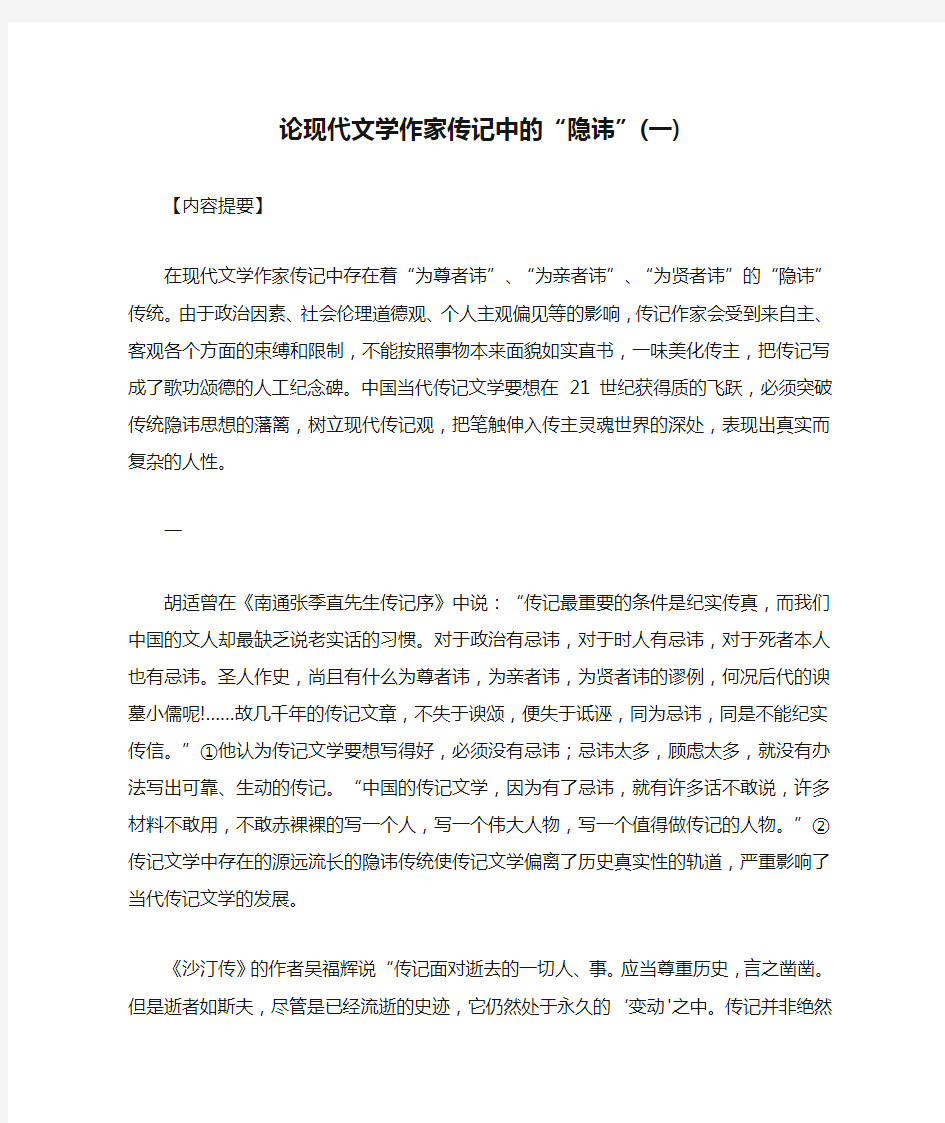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论现代文学作家传记中的“隐讳”(一)
【内容提要】
在现代文学作家传记中存在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隐讳”传统。由于政治因素、社会伦理道德观、个人主观偏见等的影响,传记作家会受到来自主、客观各个方面的束缚和限制,不能按照事物本来面貌如实直书,一味美化传主,把传记写成了歌功颂德的人工纪念碑。中国当代传记文学要想在21世纪获得质的飞跃,必须突破传统隐讳思想的藩篱,树立现代传记观,把笔触伸入传主灵魂世界的深处,表现出真实而复杂的人性。
一
胡适曾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中说:“传记最重要的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后代的谀墓小儒呢!……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同为忌讳,同是不能纪实传信。”①他认为传记文学要想写得好,必须没有忌讳;忌讳太多,顾虑太多,就没有办法写出可靠、生动的传记。“中国的传记文学,因为有了忌讳,就有许多话不敢说,许多材料不敢用,不敢赤裸裸的写一个人,写一个伟大人物,写一个值得做传记的人物。”②传记文学中存在的源远流长的隐讳传统使传记文学偏离了历史真实性的轨道,严重影响了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沙汀传》的作者吴福辉说“传记面对逝去的一切人、事。应当尊重历史,言之凿凿。但是逝者如斯夫,尽管是已经流逝的史迹,它仍然处于永久的‘变动'之中。传记并非绝然建筑在对象物的凝固不动上面的。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不习惯诉说一个鲜活的人,表面是要盖棺论定(即凝固),或许正想随心所欲地打扮历史。当然,现在多半又鉴于传主及传主的同辈人俱在,怕受多方的掣肘,‘为尊者讳',而不易发表创见。……在中国这样一种人文环境下,发表纪实性文字,说不定半空里会落下什么责难、挑剔,要说写一本见血见肉的传记,谈何容易!”③田本相在《曹禺传?后记》中也说:“本来,我国有着历史久远的史传文学传统,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史传文学却愈来愈不发达。
近几年有所发展,但有形的或无形的禁忌和框框还是太多了。即使在材料很少的情况下,写什么,怎么写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会遇到麻烦。我和一些传记文学作者私下交换意见,几乎都遇到程度不同、大小不等的麻烦和苦恼,主要是传记文学的观念不够开放。我自己虽力求摆脱困扰,但写起来也难免缩手缩脚。”④在现代文学作家传记写作过程中,由于主、客观环境的影响,传记作家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有形无形的压力和束缚,不能按照事物本来面貌如实直书,导致传记文学中隐讳现象的产生。
政治因素是传记文学中“隐讳”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影响了传记文学的客观性。中国古代史学历来有“书法不隐”的“实录”传统。班固称赞司马迁:“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⑤刘知几说:“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⑥司马迁因为在《史记》中敢于揭露现实,不为统治阶级避讳,对历史采取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而被称为良史。孔子认为“秉笔直书”、“书法不隐”是一个优秀历史学家应该具备的品格,他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但是另一方面孔子自己在写《春秋》时又使用“春秋笔法”,主张为统治阶级避讳,“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⑥。刘勰说“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⑦对于统治者或者圣贤的缺点要有所隐讳,就像农夫看见野草要把它锄掉一样,这是世代必须遵守的原则。孔子的“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⑧,形成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隐讳”
文化,导致了传记文学中“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传统。美化统治阶级,为统治者避讳作为一种伦理道德原则,成为后代史家必须遵守的教条。一方面要求秉笔直书,另一方面又要求为统治阶级隐讳,形成中国古代史学的悖论,困扰了一代又一代史学家。中国古代正史传记具有浓郁的经学倾向,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所有的学问都是用来“载道”的。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传统传记也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明确的“经世致用”目的,成为传播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工具。封建统治阶级历来重视对史传写作的控制,入传的人物受到严格限制,评价人物的尺度也以统治阶级的好恶为标准。到了隋唐,严禁私人修史写传,史官制度发展为史馆制度,在史馆制度下,史官只能秉承统治阶级意志写作,完全丧失了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于是传记中的“隐讳”现象也更加严重。刘知几指出:“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污来世”,但是他又承认这种现象有其合理性,符合儒家伦理道德,“夫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⑥。这种为传主隐讳,不惜因隐讳而模糊篡改、歪曲历史事实的传统,违背了传记真实性的原则,对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在近20年的现代文学作家传记写作中,为传主“避讳”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朱自清去清华大学任教,陈孝全的《朱自清传》上说是:“俞平伯介绍他到清华大学任教授”⑨。但俞平伯只是朱自清的北大同学,他自己都进不了清华,又怎么能够推荐比他低一级的同学进清华呢?朱自清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是胡适推荐自己进的清华大学,《朱自清传》之所以要回避胡适推荐的事实,实际上是因为政治因素的干扰而导致的对历史真相的歪曲,是一种有意或无意识的回避。陆耀东在写《冯至传》的时候,则对传主抗日期间在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骅的要求下可能加入过国民党一事直言不讳,“姚先生(冯至夫人)并未说明冯是否答应加入国民党。我以为有可能,而且可以理解,于冯至也无损”⑩。为了生存必需的经济条件和人身安全,这种选择在当时的战争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乎人情的。传记作家敢于直言,不为贤者讳,和时代的进步与社会政治气氛的宽松是分不开的。又比如郭沫若和政治的关系,已出版的几本郭沫若传揭示得都不够充分。郭沫若在中国文化学术界取得的崇高地位除了他自身的原因外,与政治因素的推动也是密不可分的。吴奚如说:“1938年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作出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人、中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11如果说政治权力在利用郭沫若的话,那么郭沫若也自愿做了政党的工具和传声筒,和前期张扬个性、崇尚自我的郭沫若相比,后期郭沫若的主体性严重失落了,没有能始终如一地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由立场和独立品格。正是这种随波逐流的性格,使他在“文革”期间写出“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12这样的丧失审美趣味的政治打油诗。但是大多数郭沫若传没有对郭沫若的精神气质与时代背景的互动以及他心理世界的发展变化进行深入挖掘,因为郭沫若的社会地位而人为美化传主形象,一味歌功颂德显然是不利于认识郭沫若的真实面貌和社会价值的。
还有一些现代文学作家传记对传主在“文革”期间的表现讳莫如深,一笔带过,对知识分子丧失自我意志的深层原因缺乏分析和批判,如田本相的《曹禺传》。作为国统区来的作家,曹禺建国后最早真诚地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严厉的反省和自我批评,1950年在《文艺报》第3期发表《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说要把“自己的作品在工农兵方向的X光线中照一照”,挖去“创作思想的脓疮”,对自己过去的创作基本上否定了。这既与他的胆小、谨慎的性格有关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他只能做出那样的选择。建国后的曹禺在对政治的妥协、顺从中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与主体意识,导致创作力的枯竭。作为“早衰的名家”,曹禺的命运不仅是一种个人命运而且是一种集体文化现象,是建国后许多知名作家的共同命运。如郭沫若、冰心、巴金、茅盾、老舍、沙汀等等,建国以后,他们的艺术生命都有一个从繁盛到枯萎的过程。“文革”期间文化的一元化、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使作家的主体意识、自由意志受到泯灭和压抑,他们的思想与创作空间越来越少。为了保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