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雪莱济慈3人关系
拜伦雪莱济慈3人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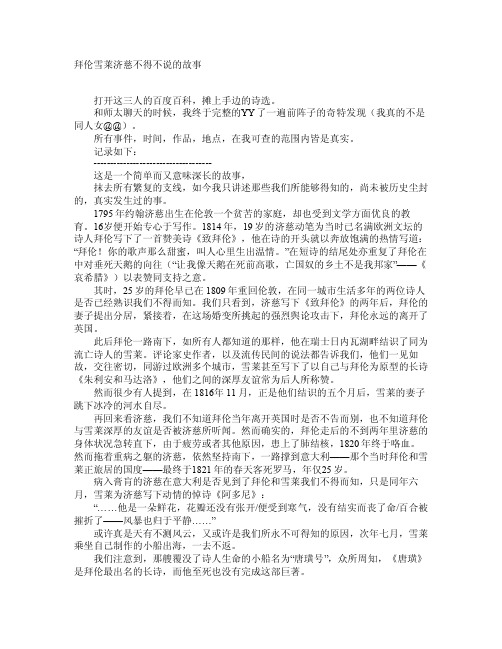
拜伦雪莱济慈不得不说的故事打开这三人的百度百科,摊上手边的诗选。
和师太聊天的时候,我终于完整的Y Y了一遍前阵子的奇特发现(我真的不是同人女@@)。
所有事件,时间,作品,地点,在我可查的范围内皆是真实。
记录如下:------------------------------------这是一个简单而又意味深长的故事,抹去所有繁复的支线,如今我只讲述那些我们所能够得知的,尚未被历史尘封的,真实发生过的事。
1795年约翰济慈出生在伦敦一个贫苦的家庭,却也受到文学方面优良的教育。
16岁便开始专心于写作。
1814年,19岁的济慈动笔为当时已名满欧洲文坛的诗人拜伦写下了一首赞美诗《致拜伦》,他在诗的开头就以奔放饱满的热情写道:“拜伦!你的歌声那么甜蜜,叫人心里生出温情。
”在短诗的结尾处亦重复了拜伦在中对垂死天鹅的向往(“让我像天鹅在死前高歌,亡国奴的乡土不是我邦家”——《哀希腊》)以表赞同支持之意。
其时,25岁的拜伦早已在1809年重回伦敦,在同一城市生活多年的两位诗人是否已经熟识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只看到,济慈写下《致拜伦》的两年后,拜伦的妻子提出分居,紧接着,在这场婚变所挑起的强烈舆论攻击下,拜伦永远的离开了英国。
此后拜伦一路南下,如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他在瑞士日内瓦湖畔结识了同为流亡诗人的雪莱。
评论家史作者,以及流传民间的说法都告诉我们,他们一见如故,交往密切,同游过欧洲多个城市,雪莱甚至写下了以自己与拜伦为原型的长诗《朱利安和马达洛》,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常为后人所称赞。
然而很少有人提到,在1816年11月,正是他们结识的五个月后,雪莱的妻子跳下冰冷的河水自尽。
济慈简介

济慈简介JohnKeats(1795~1821)英国诗人。
1795年10月29日生于伦敦。
他的父亲以经营马车行为业,生活比较富裕。
1804年父亲去世,母亲再嫁,济慈和两个弟弟由外祖母收养。
1810年母亲又病故,外祖母委托两名保护人经管他们弟兄的财产。
1811年,济慈由保护人安排离开学校,充当医生的学徒。
他对医学并不厌弃,但也喜好文学,并在中学的好友查尔斯·克拉克的鼓励之下开始写诗,模仿伊丽莎白时代诗人埃德蒙·斯宾塞。
1815年10月,济慈进入伦敦一家医院学习。
这时他已热爱写诗,深受诗人亨特和华兹华斯的影响。
1816年5月在亨特所编《检察者》杂志发表十四行诗《孤寂》。
1816年7月,通过考试获得内科医生执照,继续学习外科。
同年夏写成十四行诗《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史诗》。
10月间经克拉克介绍,与亨特相识,并与雪莱、哈兹里特、兰姆等人来往。
11月间,济慈决心从事文学创作,通知他的保护人,放弃学医。
1817年,济慈出版第一部诗集,其中大多带有模仿的痕迹,但也有佳作,如上述的读荷马史诗的十四行诗和《蟋蟀与蚱蜢》等,而《睡眠与诗》则表露了济慈的创作思想,即诗应给人们以安慰,并提高他们的思想。
诗集出版后得到好评。
4月,济慈写作长诗《恩底弥翁》,以凡人恩底弥翁和月亮女神的恋爱故事为题材,虽嫌松散,但已显出他对周围世界中的美的境界的敏感和独特的语言表达能力。
与此同时,济慈也形成了许多对哲学和艺术的观点,其中著名的有“天然接受力”的思想。
根据济慈的解释,在一个大诗人身上,对美的感受能压倒或抵消一切其他的考虑,如莎士比亚就突出地具有这种能力。
1817年冬,济慈在伦敦与华兹华斯相见。
虽然他仍然钦佩华兹华斯的诗,却不喜欢他的为人。
和亨特也渐渐疏远。
1818年3月,济慈去外地照顾患病的弟弟托姆。
这时他写成取材于薄伽丘的《十日谈》的叙事诗《伊萨贝拉》。
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强调感官享受转而强调思想深度。
拜伦、雪莱与济慈

拜伦、雪莱与济慈三位诗人的选篇都探讨了死亡、新生、爱情、自由等主题,探讨了死亡与爱情、死亡与革命、死亡与美等之间的关系。
拜伦与雪莱的激进思想,都体现了生命燃烧的一生,短短人生却留下了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激情的岁月。
1.如早年都受到主流社会的抨击,拜伦在学生时代因出版诗集《闲散的时刻》(hours of Idleness)受到攻击,后来因此事引起轰动。
最后终因离婚事件被迫离开了伦敦,到意大利定居。
雪莱则是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因印发无神论的必然性(The Necessity of Atheism)而被开除。
也发生过离婚事件,也被迫离开了英国,也到意大利定居。
2.都坚持追求自由(freedom)和英雄豪情。
1823年7月,拜伦前往希腊,支援希腊人们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斗争,死于营地,比希腊人民奉为英雄。
3.强烈的政治和抒情意识体现了诗人的英雄豪情和儿女私情的完美结合,如课文选篇中的拜伦的两首诗。
She Walks in beauty一个姑娘的美丽,会是怎么样的?用哪些形容词可以描述?tender,soft, calm, pure, dear,sweet,peace,innocent.外在的美描述哪些部位?如眼睛(eye),头发(raven tress)(色调),脸庞(色调)(face),面颊(cheek),额际(brow),微笑(smile),容颜(aspect),心灵(peace)(mind and heart)1.What is the word as the central image of the second part of thepoem?2.Would you like to analyze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part 2?3.The body narrative is apparent in this poem, so how do you thinkbody parts(what are they?) are narrated by Byron?4.除了对有形身体(body parts)的叙述,还有就是对无形的身体叙述。
正高级教师推荐--拜伦、雪莱和济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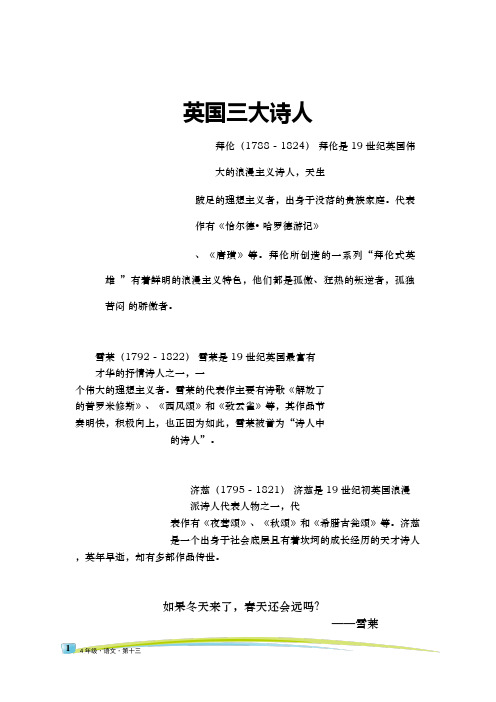
英国三大诗人拜伦(1788 - 1824)拜伦是19世纪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天生跛足的理想主义者,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
代表作有《恰尔德• 哈罗德游记》、《唐璜》等。
拜伦所创造的一系列“拜伦式英雄”有着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他们都是孤傲、狂热的叛逆者,孤独苦闷的骄傲者。
雪莱(1792 - 1822)雪莱是19世纪英国最富有才华的抒情诗人之一,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
雪莱的代表作主要有诗歌《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西风颂》和《致云雀》等,其作品节奏明快,积极向上,也正因为如此,雪莱被誉为“诗人中的诗人”。
济慈(1795 - 1821)济慈是19世纪初英国浪漫派诗人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夜莺颂》、《秋颂》和《希腊古瓮颂》等。
济慈是一个出身于社会底层且有着坎坷的成长经历的天才诗人,英年早逝,却有多部作品传世。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雪莱14年级·语文·第十三课知识链接浪漫主义的兴起与衰落19世纪20-30年代,在欧洲出现了一股狂热的文学浪潮——浪漫主义运动,我们本课所讲的拜伦、雪莱、济慈都是这一运动中的先驱。
熟悉欧洲历史的同学应该知道,此时欧洲已经经历了一场从思想到制度上全面的大解放。
发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大革命打破了欧洲大陆上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在这场大的变革之中,不可一世的路易十六成为了法国历史上第一个被送上断头台的国王。
而后来叱咤风云的军事天才拿破仑,也正是在这场大革命中崭露头角的。
然而这场大变革并没有给大多数人带来他们所渴望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尤其是拿破仑当政之后穷兵黩武,而其后的复辟王朝又逆行倒施。
种种复杂的情绪汇在了一起,诗歌就成了一个有力的表现武器。
在这样的背景下,浪漫主义运动揭开帷幕了。
在这场持续时间并不长久的文学浪潮中,诞生了一大批至今仍影响着人们的作家:德国的歌德、席勒,英国的拜伦、雪莱、济慈,法国的雨果、乔治桑、梅里美……正如拜伦、雪莱与济慈的诗歌一样,整个浪漫主义运动产生的文学作品都充满炽热的感情,这种炽热来源于人们积累已久的、深厚的感情。
浅析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语言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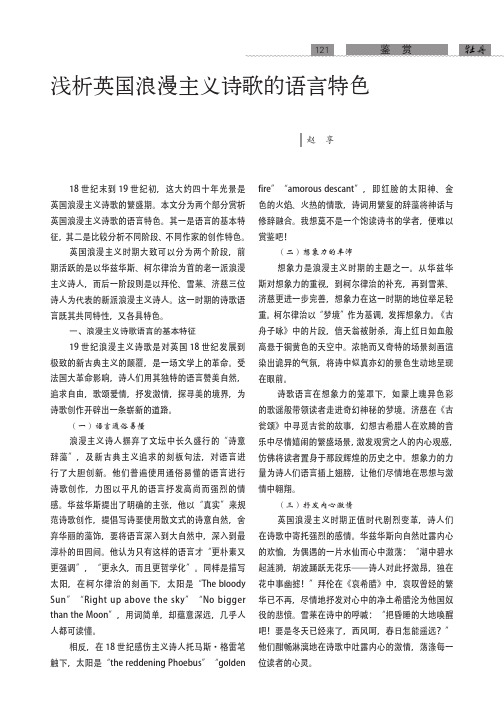
121鉴 赏浅析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语言特色赵 享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大约四十年光景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繁盛期。
本文分为两个部分赏析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语言特色。
其一是语言的基本特征,其二是比较分析不同阶段、不同作家的创作特色。
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活跃的是以华兹华斯、柯尔律治为首的老一派浪漫主义诗人,而后一阶段则是以拜伦、雪莱、济慈三位诗人为代表的新派浪漫主义诗人。
这一时期的诗歌语言既其共同特性,又各具特色。
一、浪漫主义诗歌语言的基本特征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是对英国18世纪发展到极致的新古典主义的颠覆,是一场文学上的革命。
受法国大革命影响,诗人们用其独特的语言赞美自然,追求自由,歌颂爱情,抒发激情,探寻美的境界,为诗歌创作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
(一)语言通俗易懂浪漫主义诗人摒弃了文坛中长久盛行的“诗意辞藻”,及新古典主义追求的刻板句法,对语言进行了大胆创新。
他们普遍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诗歌创作,力图以平凡的语言抒发高尚而强烈的情感。
华兹华斯提出了明确的主张,他以“真实”来规范诗歌创作,提倡写诗要使用散文式的诗意自然,舍弃华丽的藻饰,要将语言深入到大自然中,深入到最淳朴的田园间。
他认为只有这样的语言才“更朴素又更强调”,“更永久,而且更哲学化”。
同样是描写太阳,在柯尔律治的刻画下,太阳是“The bloody Sun”“Right up above the sky”“No bigger than the Moon”,用词简单,却蕴意深远,几乎人人都可读懂。
相反,在18世纪感伤主义诗人托马斯·格雷笔触下,太阳是“the reddening Phoebus”“golden fire”“amorous descant”,即红脸的太阳神、金色的火焰、火热的情歌,诗词用繁复的辞藻将神话与修辞融合。
我想莫不是一个饱读诗书的学者,便难以赏鉴吧!(二)想象力的丰沛想象力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主题之一。
情谊深笃还是一厢情愿——论拜伦和雪莱的友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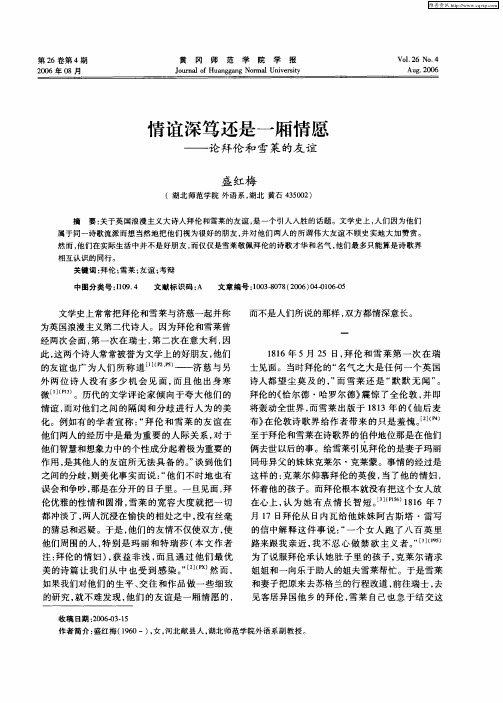
第2 6卷第 4期
20 06年 0 8月
黄
冈
师
范
学
院
学
报
Vo . 6 N . 12 o 4
Au . 00 g2 6
J un l fHu n g n oma iest o r a a g a g N r l Unv ri o y
这样 的: 克莱尔仰慕拜伦的英俊 , 当了他 的情妇 ,
怀着 他 的孩 子 。而拜 伦根 本 就没 有 把这 个女 人 放 在 心上 , 为 她 有 点 情 长 智 短 。 ] 1 1 认 E( 3 P 86年 7 月 1 7日拜 伦从 日内瓦 给 他妹 妹 阿 古斯 塔 ・ 写 雷 的信 中解 释 这 件 事 说 : 一 个 女 人 跑 了八 百 英 里 “ 路来 跟 我 亲 近 , 不 忍 心 做 禁 欲 主义 者 。 ’ 我 ”3 J ( 为 了说 服拜伦 承认 她 肚子 里 的孩 子 , 克莱 尔请 求
美 的诗 篇 让 我 们 从 中 也 受 到 感 染 。 然 而 , ”2 J ( 如 果我 们对 他们 的生 平 、 往 和 作 品 做 一 些 细致 交 的研 究 , 不难 发现 , 们 的 友谊 是 一 厢 情 愿 的 , 就 他
收 稿 日期 :0 6 31 20 - .5 0
第 4期
盛红梅 : 情谊深笃还是 一厢情愿
・0 17・
位名 满天 下 的诗人 。两 位 志趣 相 同的诗 人 在 日内 瓦 湖 畔 度 过 了三 个 月 美 好 的 日子 , 起 谈 诗 、 一 划 船、 沐浴 大 自然 的美丽 。 这 次见 面使雪 莱 对拜 伦有 了更深 的 了解 。在 此 之前 , 伦在 国 内饱受谣 言 的 困扰 , 得不 永远 拜 不 地 离 开祖 国 。雪 莱对 他 给予 了深 刻 的 同情 。在 日 内 瓦期 间雪 莱 给友 人托 马斯 ・ 夫 ・ 卡 克信 中 拉 皮 说 :拜伦 是 个 很 有 趣 的 人 , 惜 他 遭 受 最 恶 毒 、 “ 可 最粗 俗 的偏 见的奴 役 , 点 疯 疯 癫 癫 。 这 些 日子 有 ” 里他 虽 然受拜 伦 的启 发 写 了一 些 诗 , 歌 颂 他们 但 俩 新结 成 的友谊 还是 两年 后在 意 大利 见 面 的事 。 两人分 手是 在 1 1 的八 月 。整 整两 年后 , 86年 又在威 尼斯 见 面 。这 时拜 伦不 仅 承认 了他 跟 克莱
雪莱三大颂

雪莱三大颂雪莱三大颂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年8月4日—1822年7月8日),英国著名作家、浪漫主义诗人,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出色的英语诗人之一。
英国浪漫主义民主诗人、第一位社会主义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散文随笔和政论作家、改革家、柏拉图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颇深。
雪莱生于英格兰萨塞克斯郡霍舍姆附近的沃恩汉,12岁进入伊顿公学,1810年进入牛津大学,1811年3月25日由于散发《无神论的必然》,入学不足一年就被牛津大学开除。
1813年11月完成叙事长诗《麦布女王》,1818年至1819年完成了两部重要的长诗《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和《倩契》,以及其不朽的名作《西风颂》。
1822年7月8日逝世。
恩格斯称他是“天才预言家”。
1792年8月4日,佩西·比希·雪莱生于英国苏塞克斯郡霍舍姆附近的菲尔德·普莱斯一个世袭从男爵的家庭中。
父母思想都陈腐庸俗,雪莱自幼与父母不亲,后有四妹及一弟。
雪莱六岁时即被每日送往一教士处学拉丁文。
1800年,作讽刺诗《一只猫咪》,此为雪莱诗全集中所载雪莱最早的一首诗作。
1802年,入萨昂学校(Sion House Academy),该校在勃兰特福德(Brentford)附近。
1804年,雪莱被送到伊顿贵族学校,并在此度过了六年的中学生活。
伊顿公学在当时有一些在现代社会看来粗俗野蛮的规矩,比如,低年级学生就是高年级学生的“学仆”或奴隶。
每个“学仆”要替他的“宗主”铺床叠被,刷衣刷鞋,如不服从,均要接受处罚。
但身体瘦弱的雪莱却以他的激烈反抗的形式表示了他的不予服从,以至得了一个“疯子”的外号雪莱在该校近六年,处境极坏。
他在萨昂学校时即受同学辈欺侮,至伊顿更甚。
只有一个比他年幼的同学豪立戴(W.S.Halliday)同他友善,据豪立戴回忆,雪莱在伊顿确实备受贵族子弟同学辈欺凌;但雪莱学业优良,视作业和考试如同儿戏,尤其拉丁诗艺出众超群。
拜伦与雪莱的比较

在英国诗歌史上,波西·比希·雪莱是和拜 伦齐名的杰出诗人。他们的诗歌都是浪漫主
义的代表作品,却又各具特色。
拜伦出生伦敦贵族家庭,父亲在拜伦3 岁时游荡而死。母亲把对丈夫的怨恨发泄在 儿子身上。拜伦天生脚,从小养成忧郁、孤 独、反抗的性格。10岁继承爵位,成年后以 世袭议员的身份进入上议院。
他是如暴风一般轰响在19世纪初叶英国 诗坛上的巨璧。他被歌德誉为“19世纪最富 天才的诗人”,普希金奉他为“思想界的君 王”。他的诗篇洋溢着民主理想和民族解放 斗争的激情。毕生为民主自由而战,是西方 文学史上用生命去殉从理想的著名代表。
拜伦深受资产阶级英雄史的影响,加之家庭生活十分不 幸,又是天生跛足,从小比较自卑、孤僻,所以他在“辛辣 讽刺现实社会,批判邪恶如狂涛厉风”之余,往往带有一种 挥之不去的孤独和忧郁情绪,也就被称之为“忧郁的浪漫主 义诗人”。
而雪莱是在受到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在家庭生活比 较和睦且身体没有什么缺陷的情况下进行创作的,所以作品 基调以光明、乐观为主;批判揭斯誉为“天才的预言 家”,也是读者们心中的“快乐的浪漫主义诗人”。
乔治•戈登•拜伦 (1788—1824)
波西•比希•雪莱 (1792-1822)
雪莱,英国诗人,生于贵家庭。受卢梭等的影 响,他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是想,最终与保守的 家庭决裂。他以诗歌的形式抨击压迫和强权, 召唤对于现实的变革。其最优秀的作品有评论 人间事务的长诗《仙后麦布》(1813年),描写 反封建起义的幻想性抒情故事诗《伊斯兰的反 叛》(1818年),控诉曼彻斯特大屠杀的政治诗 《暴政的行列》 (1819年),支持意大利民族解 放斗争的政治诗《自由颂》(1820年),表现革 命热情及胜利信念的《西风颂》(1819年),以 及取材于古希腊神话,表现人民反暴政胜利后 瞻望空想社会主义前景的代表诗剧《解放了的 普罗米修斯》 (1819年)等。
雪莱的灵魂诗学

女性地位:雪莱的诗歌中,女性形象往往代表着对女性地位和权利的关 注和呼吁
现代意义:雪莱的诗歌中,女性形象往往代表着对现代社会中女性地位 和权利的关注和呼吁,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和价值。
07
总结与展望
总结雪莱的灵魂诗学思想
雪莱诗歌的06现代意义与
价值
雪莱诗歌中的人文精神
追求自由:雪莱诗歌中充满了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体现了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 关注社会:雪莱诗歌关注社会问题,如贫困、战争、压迫等,体现了人文精神的社会责任感。 强调人性:雪莱诗歌强调人性的尊严和价值,体现了人文精神的人文关怀。 追求真理:雪莱诗歌追求真理,反对虚假和欺骗,体现了人文精神的理性精神。
雪莱的灵魂诗学思想
雪莱的诗学理念
浪漫主义:强调情感、想 象和激情,追求自由和个 性
自然主义:强调自然与人 的和谐统一,追求自然之 美
理想主义:追求理想和真 理,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
现实主义:关注社会现实, 揭示社会矛盾和问题,追
求社会公正和进步
雪莱的诗歌创作原则
追求自由:反 对束缚,追求
心灵的自由
风格突破:雪 莱的诗歌风格 独特,既有浪 漫主义色彩, 又有现实主义 元素,突破了 传统诗歌的风 格界限。
语言创新:雪 莱的诗歌语言 优美,富有想 象力和创造力, 突破了传统诗 歌的语言表达 方式。
形式创新:雪 莱的诗歌形式 多样,包括抒 情诗、叙事诗、 哲理诗等,突 破了传统诗歌 的与评价
雪莱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浪漫主义诗歌的 代表人物之一
对后世诗人产生 了深远影响
诗歌主题广泛, 涉及爱情、自然 、社会等
三诗人之死

三诗人之死孩子们没有伙伴,出外去的时候,因为国度不同,每每受到邻近渔家的儿童们欺侮。
坐在家里,时常听见他们在外面的哭声,或则流泪回来,有时他们又表现些不好的行为,说出些不中听的话,这当然是从外边濡染来的。
因此我们便立了一个家规:没有大人同路不许他们出去。
但是这又太使他们孤苦了。
晓芙时常对我说:“我们去买匹兔子来喂罢,兔子干净,喂来也不很费事。
”五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们便走到一家养兔园去。
兔子的种类是很多的。
养兔主人说:“兔的繁殖力很大,生后六个月便要生儿,第一胎五六匹,以后每月一胎,一胎七八匹。
”我那时听了这话,很是出乎意外。
我以为这养兔的事业倒是很有利益的一项生意了。
譬如在正月里买一对满了六个月的兔儿来,养到年底就可以产出将近千匹的子孙了。
不过养兔的人又说:“出产太多了,太麻烦,每胎大概只留两匹,要杀死五六匹,——这也是一种无形的生存竞争。
假如不加屠戮时,恐怕全地球要成为兔子王国呢。
”在兔园里我们买了一只怀了孕的母兔。
但我们倒不是希望她在一年之后替我们产出千匹的子孙,我们只希望她产几匹兔子来替儿子们做做朋友罢了。
我们买的母兔是波斯种,这只是据养兔的人告诉我们的,毛是棕褐色的,和我们平常看见的山兔一样。
我们从养兔园里把它抱回寓里来,养在“玄关”里面——日本房屋的玄关就象我们说的“朝门”,大概的结构是前后两道门的进口中间的一个过道,横不过一丈,纵不过五尺。
母兔和我们同居之后,起初异常怕人,但相处一两日,也就和人亲近起来,向人依依求食了。
我们第天的清早在草原里去摘些带着露水的鲜草来喂它,晚上出游的时候,也把它带到海岸上去,任它在草原里闲散。
孩子们非常高兴;邻近的儿童们看见,也觉得非常羡慕。
但是高兴极了,他们又常起争端,因为他们对于它的态度,不能时常一致。
有时一个想作弄它,嗾使它,而别一个又要袒庇它,保护它;小小的保护者时而用出他们最后的武器来,便是放声大哭了。
相处一礼拜了,十日了,十二日了。
欢娱的五月看看便要告终,而我们的母兔娘娘还不见产生儿子。
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

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开端,是以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在一七九八年出版的《抒情歌谣集》为标志的。
华兹华斯于一八OO年在诗集再版时撰写的《序言》,成为英国浪漫主义向古典主义宣战的一篇艺术纲领。
由于他们对古典主义传统法则的反抗,宣扬浪漫主义的艺术方法,故又将湖畔派诗人称为“浪漫派的反抗”。
华兹华斯华兹华斯(1770~1850)Wordsworth,William,英国诗人。
1770年4月7日生于北部昆布兰郡科克茅斯的一个律师之家,1850年4月23日卒于里多蒙特。
8岁丧母。
5年后,父亲又离开了他。
亲友送他到家乡附近的寄宿学校读书。
1787年进剑桥大学,曾在1790年、1791年两次访问法国。
其间与法国姑娘阿内特·瓦隆恋爱,生有一女。
1795年从一位朋友那里接受了一笔遗赠年金,他的生活有了保障,也有了实现回归大自然夙愿的可能,便同妹妹多萝西移居乡间。
1797年同诗人柯尔律治相识,翌年两人共同出版《抒情歌谣集》。
1798~1799年间与柯尔律治一同到德国游历,在那里创作了《采干果》、《露斯》和组诗《露西》,并开始创作自传体长诗《序曲》。
1802年与玛丽·哈钦森结婚。
此时开始关注人类精神在与大自然交流中得到的升华,并且发现这一主题与传统的宗教观实际上并行不悖,因此重新皈依宗教。
同时,在政治上日渐保守。
华兹华斯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在1797~1807年。
随着声誉逐渐上升,他的创作逐渐走向衰退。
到了1830年,他的成就已得到普遍承认,1843年被封为英国桂冠诗人。
由于他与柯尔律治等诗人常居住在英国西北部多山的湖区,1807年10月的《爱丁堡评论》杂志称他们是湖畔派诗人。
早期诗歌《晚步》和《素描集》中,对大自然的描写基本上未超出18世纪的传统。
然而,从《抒情歌谣集》开始,一反18世纪的诗风,将一种崭新的风格带到诗歌创作中,开创了英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诗歌的新时代。
他为《抒情歌谣集》的再版所写的序言被认为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宣言。
外国文学史

外国文学史1.积极浪漫派与消极浪漫派分别是指哪几位诗人?积极:拜伦雪莱济慈消极: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2.“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的创作主张出自哪位文学家之口?华兹华斯3.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现在哪几个方面?答:(1)同情下层人民(2)提倡仁爱感化(3)坚信善必胜恶4.雨果是哪一个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答:法国浪漫主义运动领袖5.被誉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宣言是斯丹达尔的《拉辛与莎士比亚》。
6.以1830年纪事为副标题的是斯丹达尔的《红与黑》。
7.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特征(1)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2)深切的人道主义关怀8.“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家,而我不过是这位历史家的书记员”——巴尔扎克《人间喜剧》9.被誉为19世纪上半期法国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是《人间喜剧》10.贯穿狄更斯小说的思想基础是什么?人道主义是贯穿狄更斯一生创作的基本思想11.最先反映“圣诞精神”的是狄更斯的哪部作品?《圣诞故事集》12.狄更斯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是什么?《大卫•科波菲尔》13.狄更斯创作《双城记》的目的是有着借古讽今的现实意义,给英国敲警钟14.《双城记》以哪一个历史时段为背景?法国大革命15.《双城记》中人道主义思想有何独特性?有着二重性,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既反对封建贵族对农民的迫害,也反对革命开始后人民对封建贵族的专政。
狄更斯《双城记》中的梅尼特医生是人道主义的典型。
16.“勃朗特三姐妹”分别是指哪三位女性作家,其各自的代表作是什么?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米莉•勃朗特----长篇小说《呼啸山庄》安妮•勃朗特----《阿格尼斯•格雷》勃朗特三姐妹中夏洛蒂•勃朗特被誉为英国一派出色的小说家17.夏洛蒂•勃朗特笔下代表着19世纪正处于萌芽状态的欧美女性运动小说人物形象是简•爱18.《简•爱》中追求精神之爱的人物形象有哪些?简•爱、罗切斯特19.被称为英国小说家中最伟大的悲剧大师的是谁托马斯•哈代20.小说《德伯家的苔丝》是19C哪一种艺术思潮代表作?批判现实主义21.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假装笃信宗教、满口仁义道德的人物形象是谁?亚雷22.(马克思)称誉狄更斯、萨克雷、盖斯凯尔夫人等作家是现代英国“一派出色的小说家”。
简爱人物关系

简·爱人物关系简·爱(Jane Eyre):女主人公,孤儿,由其舅妈抚养。
萨拉·里德太太(Mrs. Sarah Reed):简的舅妈,住在盖茨海德府。
里德先生(Mr. Reed):简的舅舅。
伊丽莎·里德(Eliza Reed):里德太太的长女,简的表姐妹。
约翰·里德(John Reed):里德太太的儿子,简的表兄弟。
乔治安娜·里德(Georgiana Reed):里德太太的小女儿,简的表姐妹。
贝茜·李(Bessie Lee):保姆,住在盖茨海德府。
罗伯特(Robert Leaven):生活在盖茨海德府的车夫,有时会给简驾驶马车。
劳埃德先生(Mr. Lloyd):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药剂师,建议里德太太把简送到学校。
勃罗克赫斯特先生(Mr. Brocklehurst):傲慢的,虚伪的教士,担任洛伍德学校的校长和司库。
玛丽亚·谭波儿小姐(Miss Maria Temple):和蔼的洛伍德学校年轻主管,学监。
斯凯契德小姐(Miss Scatcherd):恶毒的洛伍德学校老师。
海伦·彭斯(Helen Burns):简的同学,简在洛伍德最好的朋友。
玛丽·安·威尔逊(Mary Ann Wilson):落伍德爆发后简的最好的朋友。
阿黛勒·瓦朗(Adele Varens):一个天真活泼的法国的孩子,简在桑菲尔德府做她的家庭教师。
爱丽丝·费尔法克斯夫人(Mrs. Alice Fairfax):一个寡妇,费尔法克斯桑菲尔德庄园的管家。
爱德华·费尔法克斯·罗切斯特(Edward Fairfax Rochester):男主人公,桑菲尔德庄园的主人,简的情人和最终的丈夫。
伯莎·梅森(Bertha Mason):爱德华罗切斯特的、暴力的、疯狂的、秘密的妻子,被罗切斯特藏于桑菲尔德府中。
雪莱夫人和梵高弟媳

雪莱夫人和梵高弟媳余光中1822年7月中旬,地中海的潮水将两具海难的遗体冲上沙岸。
朋友们赶来认领时,面目已经难辨,但衣服尚可指认;其中一具的口袋里有一本书,是济慈的诗集,该是雪莱无疑。
另一具是雪莱的中学同学威廉姆斯中尉。
七月八日两人驾着快艇“唐璜”,从来亨驶回雷瑞奇,在暴风雨中沉没。
拜伦、李衡、崔罗尼就在海边将亡友火化,葬在罗马的新教徒公墓。
曲终人散。
雪莱与夫人玛丽(MaryWollstonecraftShelley)所生的长子威廉,三年前已葬入那公墓,只有三岁。
一年前,济慈也在那里躺下。
不到两年之后,拜伦就死在希腊。
于是英国浪漫诗人的第二代就此落幕,留下了渐渐老去的第一代,渐渐江郎才尽。
雪莱周围的金童玉女,所谓“比萨雅集”(ThePisanCircle),当然全散了。
散是散了,但是故事还没有说完。
拜伦早已名满天下,但雪莱仍然默默无闻,诗集的销路没有一种能破百本。
当然,终有一天他也会成名,不过还要靠寥寥的知音努力:“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拜伦最识雪莱,却从不为他美言。
余下的只有李衡等几人,和一个黯然神伤的寡妇,玛丽·雪莱。
雪莱死时,还未满三十;玛丽,还未满廿五。
这么年轻的遗孀早已遍历沧桑。
她的父母都是名人,但对时人而言都离经叛道,是危险人物。
父亲高德温(WilliamGodwin)是思想家兼作家,在政治与宗教上立场激进,鼓吹法国革命与无神论,反对社会制度的束缚,对英国前后两代浪漫诗人影响巨大。
母亲瓦斯东克拉夫特(MaryWollstonecraft)乃英国女性主义的先驱,所著《女权申辩》一书析论女性不平的地位,说理清晰,兼富感性,成为经典名著,但因她特立独行,婚前与情人有一私生女,又因失恋投水获救,不见容于名教。
夫妻相爱本极幸福,不幸她在生玛丽时失血过多而死。
玛丽生在这么一个“革命之家”,一生自多波折。
十六岁她与大她五岁的雪莱私奔欧洲,等到两年后雪莱前妻投湖自尽,才成为第二位雪莱夫人。
拜伦和雪莱有怎样的关系

拜伦和雪莱有怎样的关系呃其实这两个人扯出来的一大圈名人大概和娱乐圈的周迅王菲那一圈差不多理清楚一点是这样的:先说雪莱夫妇这一边吧:Mary Shelley的妈妈是 Mary Wollstonecraft 女权主义重要奠基人爸爸是 William Godwin, utilitarianism的提出者和anarchism的支持者因为仰慕Mary的父母, Percy Shelley前来拜访,然后认识了未来妻子. 两个人恋爱时还常在教堂后的墓地里读Wollstonecraft的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而他们这个约会的墓地现在依然在伦敦保留着Mary Shelley有两个妹妹一个叫Fanny 一个叫Claire 后者在拜伦和雪莱的这个圈里比较重要然后拜伦大人Lord Byron呢,原配妻子与他不合,生了个女儿以后就带着女儿远走他分居了。
女儿名字叫Ada Lovelace,和巴贝奇先生Charles Babbage 一起设计了差分机 Differential Machine,并且甚至比巴贝奇更早一步的构想了这个机器在数学以外的领域的应用,设想了编程的未来,也因此被称作第一个女程序员。
拜伦的私人医生叫Polidori,坊间一直有传他和拜伦的暧昧,直到后来大家开始传拜伦和他姐姐的私情,人们才慢慢把焦点从同性暧昧转向姐弟恋。
然后重点来了!终于开始回到题主问题==在1816年,拜伦和他医生,雪莱夫妇以及Mary Shelley的妹妹Claire一众人前往日内瓦湖畔度假。
那年被称作无夏之年 (year without a summer) ,印尼火山导致天气反常,瑞士连日降雨低温,于是这一群人只能待在室内消遣。
Percey Shelley和Claire,也就是姐夫和小姨子有了一腿。
拜伦和他医生Polidori也一直有着一腿。
Claire因为一直对于姐姐能找诗人当伴侣心存嫉妒,然后见到拜伦遂决定要定了这个男人,于是也和拜伦有一腿(后来还给拜伦生了个女儿好像)。
拜伦式英雄(1)

拜伦式英雄拜伦式英雄(Byronichero)是指在拜伦的作品中特别是《东方叙事诗》中,塑造的一系列个人主义反叛者的形象。
他们烙刻着拜伦的思想气质个性的印记。
这些反叛者才能出众,出于个人的原因,起来反抗国家的强权,社会秩序和宗教道德,但没有明确的斗争目的;他们追求个人自由,却又常常把自己关闭在孤独和高傲中,斗争总是以失败告终。
由于这些形象具有作者本人的思想性格特征,因此被称作"拜伦式英雄"。
拜伦式英雄(Byronic Hero), 又名反英雄Anti-hero, 悲情英雄Tragic hero, 浪漫英雄Romantic hero,是指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在作品中塑造出来的一系列充满强烈的反叛热情而又孤独、忧郁的一类人物形象。
这些人物都是悲剧性的傲慢的叛逆者,他们都有非凡的才能和力量,但在腐败的社会中却无法施展。
他们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而感到痛苦,因自己的才能和情感的虚耗而感到绝望。
他们以挑战示威的态度,以异样的勇敢和热情,以不屈不挠的一直和毫不妥协的精神,或报复或反抗社会的专制与压迫。
在这些人物的身上,有诗人本人生活遭遇的明显痕迹,所以被称为 "拜伦式英雄 ""拜伦式英雄"一词最早来源于拜伦的《东方叙事诗》中,用它来描述一批侠骨柔肠的硬汉,他们有海盗、异教徒、被放逐者,这些大都是高傲、孤独、倔强的叛逆者,他们与罪恶社会势不两立,孤军奋战与命运抗争,追求自由,最后总是以失败告终。
拜伦通过他们的斗争表现出对社会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同时反映出自己的忧郁、孤独和彷徨的苦闷。
"拜伦式英雄"是指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作品中的一类人物形象。
他们高傲倔强,既不满现实,要求奋起反抗,具有叛逆的性格;但同时又显得忧郁、孤独、悲观,脱离群众,我行我素,始终找不到正确的出路。
他们的性格特征是反抗、孤傲、浪漫。
他们既不满现实,又找不到出路。
拜伦与雪莱是什么关系

拜伦与雪莱的关系在1816年,拜伦居住在瑞士,在日内瓦结识了另一个正在流亡的诗人雪莱,对英国统治者的憎恨和对诗歌的同样爱好使他们结成了密友。
拜伦和雪莱是近代世界文坛上的两个璀灿巨星,也是十九世纪英国家喻户晓的两个浪漫主义诗人。
两人都出生在英格兰群岛,在英吉利的海峡凌厉强劲的海风中吹拂长大,也因此享有在那个海洋民族所特有的独特秉性:他们热爱生命,但更酷爱那赋予生命以形貌和声音的源泉:海洋。
拜伦和雪莱两人的友谊也正是从水边开始的。
六年前,他们相识于瑞士日内瓦的莱蒙湖畔,然而在六年后,他们的人世间情缘在意大利维亚雷焦镇的地中海沙滩上结束。
雪莱逝世在大海里,而拜伦的生命最终也因为水大海的精魂所勾摄。
在海滩边的火葬仪式过去一年又八个月后,一场飘泼大雨,又结束了十九世纪英国最后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波澜壮阔的一生。
这一对受尽人间风雨的青年诗人,如同他们后来那般如日中天的文坛盛世,他们生前死后的经历也是那样的相似。
对拜伦的评价拜伦搜寻英雄,并不是之局限于地中海各国和中世纪而已,因为给拿破仑加上一件浪漫主义的外衣是不难的。
拿破仑对十九世纪时的欧洲人们思想的影响很深。
克劳泽维茨、费希特、海涅以及尼采的思想,意大利爱国者的行动,都受到了他的精神召唤。
他的灵魂在整个时代都在昂首阔步。
拜伦在希腊有着不同凡响的名誉,在他因病逝世后,希腊人们感到悲痛万分,希腊政府还宣布拜伦之死为国葬,可见拜伦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拜伦被誉为是的19世纪举世公认的浪漫主义文学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可见世人对拜伦的评价很高。
拜伦与浪漫主义拜伦在短暂的一生中,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光辉的诗作,其中最负盛名的有长篇抒情叙事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和《唐璜》等。
拜伦的这些被世人誉为抒情史诗的作品中,拜伦以积极浪漫主义的手法,将自己亲身游历欧洲各国的切身融入到作品之中,用开阔的视野来展示了辽阔雄壮的时代画卷,抒发了诗人情怀,表达了傲然不屈的斗争誓言。
拜伦的抒情史诗随着他的足迹,呈现出一幅幅动人心弦的美丽风景,拜伦将他诗人的无比热情倾注于对这些国家风光的描绘上,其目的就是为了激发这些国家人民的爱国热情,鼓励他们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夏天,与雪莱一起,邀请在英国受到迫害的李·亨特前来意大利,共同筹办文学期刊《自由人》。
7月8日,雪莱溺死于斯塔西亚湾。 拜伦火葬雪莱
济慈代表性的作品有:《恩底弥翁》(1818)、《圣阿格尼斯节前夕》(1819)等叙事诗,还有《夜莺颂》(1819)、《希腊古瓮颂》(1819)等颂歌。
拜伦和雪莱于1816年四月在瑞士日内瓦的莱蒙湖畔相识,雪莱的无神论和乐观主义对拜伦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8月,雪莱夫妇离开日内瓦。 1818年8月,雪莱来威尼斯与其相见。 秋冬之间,雪莱作《朱利安与马达洛》一诗,实际上是对拜伦提出善意的批评和规劝。从拜伦尔后的作品和实际行动来看,他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雪莱的批评。
如今我们再去那片墓地,绕过罗马最南边的城墙,可以发现墓地被石墙隔开分为两个区域,济慈被葬在老区的尽头,而雪莱则在新区的入口。至于去世时间不过相差一年的两人为何被远远隔开,或许只有那个安葬了他们的人才知道。
两年后,1824年,36岁的拜伦身染重病,死于希腊。
【天涯博客】本文地址/blogger/post_show.asp?PostID=18190562&BlogID=394620
现代的评论家多认为拜伦虽有一流的讽刺与叙事才华,但总的说来享受了与其才华不配的名誉。说他伟大,似主要不是诗文本身的缘故,因在所谓六大诗人中,他的文思较缺乏深度,用词、组句、织体的丰富性与文本的平衡感等也不如他人,后来,T·S·艾略特甚至说他对英国语言无任何贡献。其实拜伦无论在思路、意象或词语方面都曾以间接的方式仿效他所蔑视的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有时套用好友雪莱、甚至济慈的灵感,难免显出平庸。
我们注意到,那艘覆没了诗人生命的小船名为“唐璜号”,众所周知,《唐璜》是拜伦最出名的长诗,而他至死也没有完成这部巨著。
拜伦在海边火葬了挚友,又按照他遗愿将骨灰带回罗马,葬在“一处他生前认为最理想的安息场所”。
罗马,罗马正是年轻的济慈客死的异乡,而那安息场所,也正是济慈下葬的那片“非天主教徒墓地”。
拜伦雪莱天的时候,我终于完整的YY了一遍前阵子的奇特发现(我真的不是同人女@@)。
所有事件,时间,作品,地点,在我可查的范围内皆是真实。
记录如下:
------------------------------------
尽管相对欧洲历史而言,济慈的影响力不及拜伦,但说到英国诗歌史,拜伦的声望则无法与济慈相比。与雪莱比较,济慈更愿以热心而冷眼的观者姿态绘制生活的戏剧画面,对在真实的生活中扮演各种角色的真人表现出艺术家的兴趣,他并不因至上的理想而厌弃有限的世事,而是以具体人间情感证实无限的存在。济慈在1818年的一封信中指出,华兹华斯较弥尔顿“更深刻”,因为他重视灵魂在俗界的旅程,比弥尔顿更关注“人心”或“人性”,其特有的才华能帮我们“探索”人生“巨宅”中那些“漆黑的通道”,从而减轻“生死奥秘的重压”。济慈发展了有关信念,认为人间是“造就灵魂的深谷”,除此无其他途径。有评论家认为,济慈的倾向是要发掘新的永久价值,他主要不是让我们相信世间充满苦难与压迫,而是让我们鼓足勇气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世界充满欢乐、健康、自由。这些都属于他人,但只要争取,也能属于我们自己。济慈思想与艺术的精髓就是让我们有勇气相信他人是幸福的,并能为此感到由衷的喜悦。
波西·比希·雪莱(1792——1822):《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因体现其思想之精髓而在雪莱诗中占中心位置。该诗剧分四幕,写到了普罗米修斯的被缚与解放。该诗使雪莱的两大主题)——社会变革与人间情爱——交织互补,并配之以两条线索:普罗米修斯与朱庇特的善恶关系和他与亚细亚的分别与重逢。这两条线索由代表必然性和原始生命力的冥王来串连,由他来影响众神之命运,决定不同人物的胜败。这位埃斯库罗斯笔下的巨人吸引诗人,是因为他以美德抗暴,他基本代表完美人格,无私、无野心、无妒意,集人类灵智与永恒灵智为一体。雪莱写这首诗时不再过分强调外在变革,而更注重自我完善和爱的力量,不再涉及具体的政治自由,而聚焦于超然而又深厚的自由含意。因此,《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实际是理念诗,旨在展现理想生活的幻景,提供宇宙新生的启示。相对拜伦的现实革命精神而言,雪莱的革命概念更具理想色彩,因而也更彻底,是对现有世界方方面面的哲学否定。“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即是雪莱对未来美好世界必将来临的预言,发人深省。雪莱还以抒情诗著称于世,继承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兹华斯的传统,以大自然入诗,《西风颂》、《云》、《致云雀》等作品,音韵铿锵,感情真挚,闪耀着深邃的思想光辉。
对于雪莱,曾有著名评论家有所贬损,但也有人持平而论,认为弥尔顿的厚重与雪莱的“空气与火”各代表但丁的一半,而能顶其一半即是荣幸,雪莱的诗有时堪与莫扎特的音乐相比。
约翰·济慈(1795——1821):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都寿命短暂,济慈最令人叹息,享年仅26岁,却留下许多精美的诗篇,包括莎翁与但丁在内的巨笔在那样年轻时尚未写出相当水平的作品。就诗艺,有人认为他是19世纪最杰出的诗人,他不独属于浪漫主义,唯美派与颓废派都受到他的影响。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拜伦现象是19世纪西方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体现了那个不朽时代的激情,代表了它的才智、深思、狂暴和力量;他那普罗米修斯式的孤独的反抗意志,在上个世纪欧洲人的精神生活中非同凡响,以致改变着“社会结构、价值判断标准及文化面貌”。(罗素)这个独立不羁的天才,有博大的政治家的胸襟和哲人的才智。他的气质敏感而暴烈,感情深沉而细腻。但他也是个放浪形骸的公子、虚荣傲岸的爵爷和孤高悒郁的自我主义者。他崇尚伟大的精神,向往壮丽的事业,却被黑暗的时代所窒息。他的心是伤感的,他的叹息充斥了整个生涯……别的诗人编织梦想,他却曾被认为是梦想的本身,在诗、行动、人格之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生命。他融入文学但又大于文学。他说两种情感即能限定他的实质:热爱自由,痛恨虚伪(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情爱的等),但他是个复杂的矛盾集合体:生来微跛,却爱四方漫游;身为贵族,充满等级观念,却又具有平民的反抗意识;他时而阴沉、焦躁,但更多时表现出和蔼、幽默或玩世的轻松;他崇尚自由,却坚守浪漫时代之前的古旧文体;他主观自信,却富有经验式的常识;他有强烈的男权中心意识,却常陷入他所谓的“女性思维”;他痛恨战争,但热衷于“争取自由的战役”。最后,他从物质和行动上投入战争,似乎是对他超越或毁弃文学文本而去用行动创造人生文本的诠释。
济慈之后有多人将他与莎翁比较,甚至认为他是在资质、意识等方面最像莎翁的诗人。济慈曾强调,诗人应像莎翁那样有能力排除内外世界各种干扰,主动做到不急于介入作品的冲突中,保持戏剧的视角。他称华兹华斯表现出“自我的超卓”,似暗示自己更愿像莎翁那样摆脱自我人格的困扰,尽量潜入剧中人物的视角,使自我化为每一个人物。在20世纪一些现代主义批评家眼中,济慈摆脱了同时代浪漫主义诗人的那些不合现代人口味的“毛病”,其作品可算现代意义上的理想文本。今人则更看重济慈所代表的某种新人的气质:他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情感,包括疚痛、欲念、尴尬与窘迫、美感与疾病、孤独、快乐等,都有敏锐的把握,能以生动而具体的感觉表达这类痛苦和欢乐。
由拜伦、雪莱和济慈代表的第二代诗人创造了与第一代诗人不大相同的浪漫文风。尤其拜伦,基本上未公开表示过对华兹华斯或柯尔律治有何好感,至少在风格上划清界线。他并不崇拜深刻,对哲思三心二意,却更具现实的浪漫情绪和时代感;他易被读懂,引起热情的共鸣,更具普遍的影响力。拜伦是19世纪欧洲文学的奇观,在一段时间内显出叱咤风云的魅力,引起歌德、雨果、普希金,下至青年男女的喜爱,将许多文人罩入其巨影。但今天若绘制浪漫诗人的命运图表,会发现他的名声经历了最大的落差。布莱克终于被发现,迅速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的名誉一向稳步缓升,华兹华斯于20世纪初期遭过轻蔑,但二战后二人稳居经典位置,华兹华斯被大多数学者认定为最伟大的浪漫诗人;济慈的伟名从未有大的波动;雪莱创造了尖锐对立的阵营,在20世纪20年代后曾受过最严重的轻蔑,后被左派和保守派共视为伟大诗人。而拜伦则于19世纪中叶从最高处快速下滑,世纪末已有人反思拜伦现象,虽仍有慕名崇拜者,但更多的是不甚公正的贬低和漠视,只在20世纪中叶后才受到较深刻的解读和较客观的评价。
这是一个简单而又意味深长的故事,
抹去所有繁复的支线,如今我只讲述那些我们所能够得知的,尚未被历史尘封的,真实发生过的事。
1795年约翰济慈出生在伦敦一个贫苦的家庭,却也受到文学方面优良的教育。16岁便开始专心于写作。1814年,19岁的济慈动笔为当时已名满欧洲文坛的诗人拜伦写下了一首赞美诗《致拜伦》,他在诗的开头就以奔放饱满的热情写道:“拜伦!你的歌声那么甜蜜,叫人心里生出温情。”在短诗的结尾处亦重复了拜伦在中对垂死天鹅的向往(“让我像天鹅在死前高歌,亡国奴的乡土不是我邦家”——《哀希腊》)以表赞同支持之意。
其时,25岁的拜伦早已在1809年重回伦敦,在同一城市生活多年的两位诗人是否已经熟识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看到,济慈写下《致拜伦》的两年后,拜伦的妻子提出分居,紧接着,在这场婚变所挑起的强烈舆论攻击下,拜伦永远的离开了英国。
此后拜伦一路南下,如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他在瑞士日内瓦湖畔结识了同为流亡诗人的雪莱。评论家史作者,以及流传民间的说法都告诉我们,他们一见如故,交往密切,同游过欧洲多个城市,雪莱甚至写下了以自己与拜伦为原型的长诗《朱利安和马达洛》,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常为后人所称赞。
病入膏肓的济慈在意大利是否见到了拜伦和雪莱我们不得而知,只是同年六月,雪莱为济慈写下动情的悼诗《阿多尼》:
“……他是一朵鲜花,花瓣还没有张开/便受到寒气,没有结实而丧了命/百合被摧折了——风暴也归于平静……”
或许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又或许是我们所永不可得知的原因,次年七月,雪莱乘坐自己制作的小船出海,一去不返。
然而很少有人提到,在1816年11月,正是他们结识的五个月后,雪莱的妻子跳下冰冷的河水自尽。
再回来看济慈,我们不知道拜伦当年离开英国时是否不告而别,也不知道拜伦与雪莱深厚的友谊是否被济慈所听闻。然而确实的,拜伦走后的不到两年里济慈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由于疲劳或者其他原因,患上了肺结核,1820年终于咯血。然而拖着重病之躯的济慈,依然坚持南下,一路撑到意大利——那个当时拜伦和雪莱正旅居的国度——最终于1821年的春天客死罗马,年仅2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