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
以《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为题的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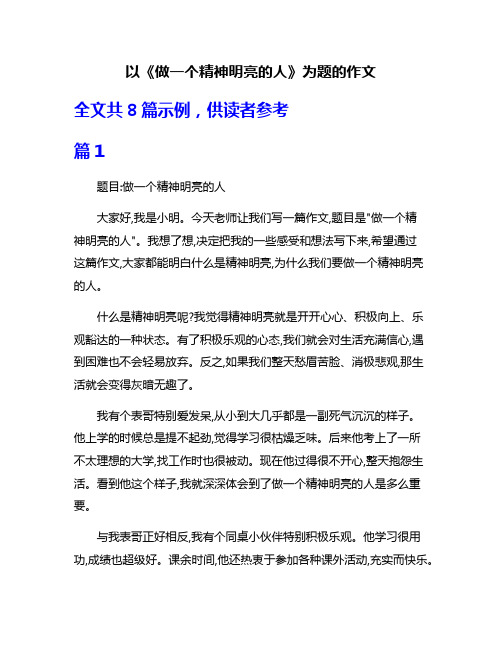
以《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为题的作文全文共8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篇1题目: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大家好,我是小明。
今天老师让我们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
我想了想,决定把我的一些感受和想法写下来,希望通过这篇作文,大家都能明白什么是精神明亮,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
什么是精神明亮呢?我觉得精神明亮就是开开心心、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的一种状态。
有了积极乐观的心态,我们就会对生活充满信心,遇到困难也不会轻易放弃。
反之,如果我们整天愁眉苦脸、消极悲观,那生活就会变得灰暗无趣了。
我有个表哥特别爱发呆,从小到大几乎都是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
他上学的时候总是提不起劲,觉得学习很枯燥乏味。
后来他考上了一所不太理想的大学,找工作时也很被动。
现在他过得很不开心,整天抱怨生活。
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就深深体会到了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是多么重要。
与我表哥正好相反,我有个同桌小伙伴特别积极乐观。
他学习很用功,成绩也超级好。
课余时间,他还热衷于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充实而快乐。
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他,因为他的精神状态一直很饱满。
他经常鼓励我们要热爱生活、热爱学习,要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待一切。
我深受他的影响,决心也要像他一样,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
除了学习好、成绩好之外,我觉得一个精神明亮的人,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生活中处处有惊喜,只要用心体会,就会发现这世界其实很美好。
每当我看到窗外阳光普照、鲜花盛开的时候,心情就会变得无比愉悦。
早上我妈妈为我做的营养早餐,让我充满了能量去学习和玩耍。
老师辛勤细致的教导,让我获益匪浅。
朋友们的友谊和关爱,温暖着我的心灵。
只要用感恩的眼光看世界,我们就会发现生活处处是幸福。
当然,生活中难免也会遇到一些挫折和不如意。
但是只要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就一定能够度过难关。
比如上学期我数学考试成绩不理想,我并没有放弃,而是更加刻苦用功,跟着老师的步骤一点一点地学习、练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学期我的数学成绩有了很大提高。
初三关于写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的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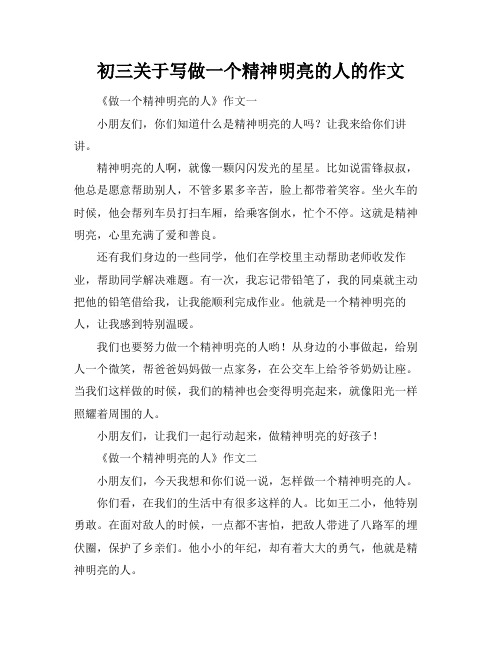
初三关于写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的作文《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作文一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什么是精神明亮的人吗?让我来给你们讲讲。
精神明亮的人啊,就像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
比如说雷锋叔叔,他总是愿意帮助别人,不管多累多辛苦,脸上都带着笑容。
坐火车的时候,他会帮列车员打扫车厢,给乘客倒水,忙个不停。
这就是精神明亮,心里充满了爱和善良。
还有我们身边的一些同学,他们在学校里主动帮助老师收发作业,帮助同学解决难题。
有一次,我忘记带铅笔了,我的同桌就主动把他的铅笔借给我,让我能顺利完成作业。
他就是一个精神明亮的人,让我感到特别温暖。
我们也要努力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哟!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给别人一个微笑,帮爸爸妈妈做一点家务,在公交车上给爷爷奶奶让座。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精神也会变得明亮起来,就像阳光一样照耀着周围的人。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做精神明亮的好孩子!《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作文二小朋友们,今天我想和你们说一说,怎样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
你们看,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
比如王二小,他特别勇敢。
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保护了乡亲们。
他小小的年纪,却有着大大的勇气,他就是精神明亮的人。
还有那些在疫情期间的医生和护士们,他们不顾自己的危险,去照顾生病的人。
每天穿着厚厚的防护服,累得满头大汗,也不抱怨。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让我们感到安心。
我们小朋友也能做精神明亮的人呢!在学校里,和同学们友好相处,不吵架、不打架。
看到地上有垃圾,主动捡起来。
在家里,听爸爸妈妈的话,不任性。
这些小小的事情,都能让我们的精神变得明亮。
只要我们心里充满阳光,多做好事,我们都能成为精神明亮的人!。
精神明亮的人摘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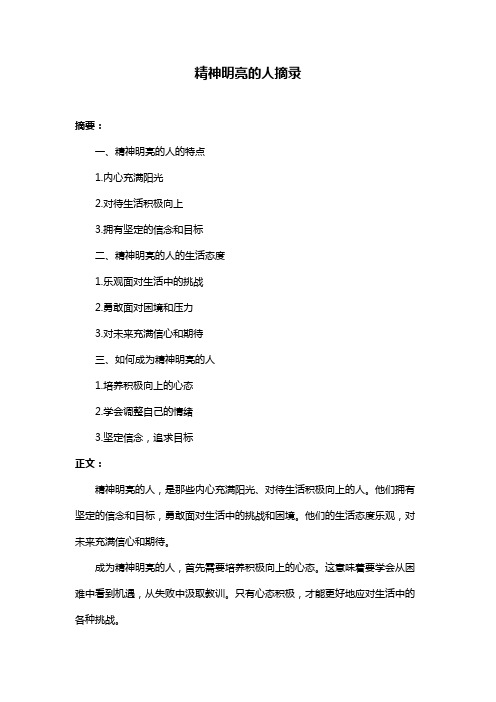
精神明亮的人摘录
摘要:
一、精神明亮的人的特点
1.内心充满阳光
2.对待生活积极向上
3.拥有坚定的信念和目标
二、精神明亮的人的生活态度
1.乐观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2.勇敢面对困境和压力
3.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
三、如何成为精神明亮的人
1.培养积极向上的心态
2.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
3.坚定信念,追求目标
正文:
精神明亮的人,是那些内心充满阳光、对待生活积极向上的人。
他们拥有坚定的信念和目标,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境。
他们的生活态度乐观,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
成为精神明亮的人,首先需要培养积极向上的心态。
这意味着要学会从困难中看到机遇,从失败中汲取教训。
只有心态积极,才能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其次,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也很重要。
生活中总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看待这些事情,以及如何调整自己的情绪。
一个精神明亮的人,会找到合适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情绪,避免让负面情绪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最后,成为精神明亮的人还需要坚定信念,追求目标。
一个有信念的人,会更有动力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会轻易放弃。
而当一个人有了明确的目标,他就会更加明确自己的人生方向,充满信心地迈向成功。
总之,成为一个精神明亮的人,需要具备积极向上的心态、勇敢面对困境和压力的能力,以及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
初三关于写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的作文

初三关于写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的作文嘿,伙计们!今天我们来聊聊如何成为一个精神明亮的人。
你知道吗,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好坏直接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如何让自己的精神焕发光彩吧!我们要保持乐观的心态。
就像那句话说的:“人生就像一面镜子,你笑它就笑,你哭它就哭。
”我们要学会看到生活中的美好,不要总是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不如意的事情上。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现实视而不见,而是要学会在困难面前保持冷静,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问题。
记住,阳光总在风雨后,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总会迎来属于我们的那片蓝天。
我们要保持好奇心。
好奇心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也是我们不断学习、成长的源泉。
我们要像孩子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勇于探索未知的领域。
不要害怕失败,因为失败是成功的垫脚石。
只有不断地尝试和摸索,我们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成功之路。
我们要学会与人沟通。
沟通是建立人际关系的桥梁,也是我们了解别人、被别人了解的重要途径。
我们要学会倾听别人的意见,尊重别人的观点,这样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和友谊。
我们也要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要把心里的话憋在肚子里,因为真诚的交流能让我们更加了解彼此,也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我们要关注身体健康。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有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更好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我们要注意饮食均衡,多吃蔬菜水果,少吃油腻食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让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还要适当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充沛的精力去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我们要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生活中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值得我们去珍惜,比如亲情、友情、爱情等。
我们要学会感恩,感谢那些在我们身边默默付出的人,感谢那些给我们带来快乐和温暖的事。
只有珍惜现在,我们才能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成为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并不是一件难事。
只要我们保持乐观的心态,保持好奇心,善于沟通,关注身体健康,珍惜身边的人和事,我们就能让自己的精神焕发光彩。
《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国旗下讲话

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早上好。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
居斯塔夫•福楼拜在给朋友的信件中写到:“我拼命工作,不接待来访,按时看日出,在寂静的书房里工作到深夜……”一位以面壁写作为誓志的世界文豪,一个如此吝惜时机的人,却每天按时看日出,把寻常的晨曦之降视若一件盛事。
为什么呢?王开岭这样回答:“这是生命健康与积极性情的标志,更是精神明亮的标志。
”你们是怎样定义“精神明亮”的呢?第一次读这个词的时候,我好像真的感受到了由衷的,潜藏在身体内的,一种豁然的明朗。
我们必须承认,人性是复杂的。
正如《罗生门》所指,门内是正义,善良,良知,道德和自我克制;门外即是邪念,自私,贪婪,堕落和无底线。
几级台阶的距离,一念之差,就是人世和地狱的模糊界限。
而我,我们,所有站在这里的人,一定都能从身体里分裂出两个对立面:这是不可否认,不可避免的。
但是我依然可以自信地,坚定地说:我的精神是明亮的。
我努力驱逐消极的情感,满怀梦想与希望,认真地过活。
这就是精神明亮。
然而有时候我会感到,我们的生命缺少热情,缺少仪式感,缺少因光线而激动的清晨。
我们行走在人间,却好像蜷缩在被子里,在昏迷,在蒙头大睡,在冷漠地打着呼噜,光线总也照不到身体和灵魂。
精神颓靡而低落,冰冷而麻木,目光困囿于脚下的磕磕绊绊,无力企盼远方的鸟语花香。
这不是年轻的生命该有的模样。
我们应该大声哭,大声笑,大踏步地向前走,勇敢地想象未来,相信未来。
恣意而张扬,清澈而烂漫。
关于这一点,我的朋友们可以为我作证。
自从我在小时候的某一刻真正地认识了自己开始:我擅长尖叫,擅长大笑,擅长自娱自乐。
事实上,我不敢想象,如果不是这样,我的生活该有多么压抑,多么沉重。
有那么多可怕的事情要背负,要担忧。
如果不是精神明亮,一个人将要把自己折磨成什么样子呢?最喜欢海子的一句诗:活在这珍贵的人间/感到自己是彻底干净的黑土块。
多么清爽,多么舒坦。
唯有轻装,才可远行。
精神明亮的人心得体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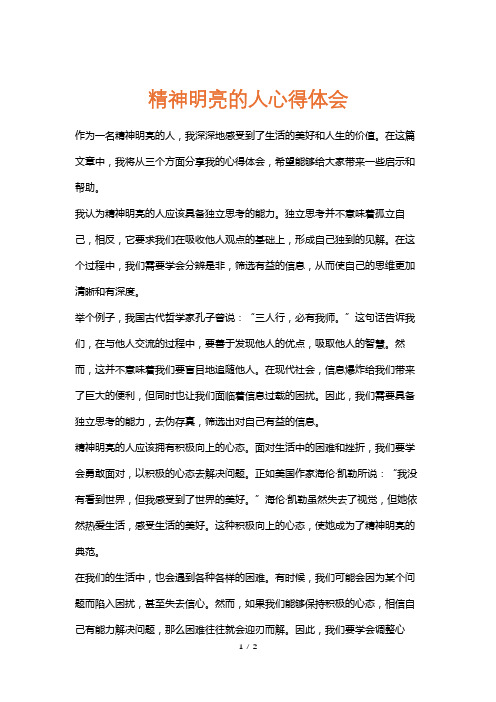
精神明亮的人心得体会作为一名精神明亮的人,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人生的价值。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从三个方面分享我的心得体会,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
我认为精神明亮的人应该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
独立思考并不意味着孤立自己,相反,它要求我们在吸收他人观点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学会分辨是非,筛选有益的信息,从而使自己的思维更加清晰和有深度。
举个例子,我国古代哲学家孔子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这句话告诉我们,在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要善于发现他人的优点,吸取他人的智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盲目地追随他人。
在现代社会,信息爆炸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但同时也让我们面临着信息过载的困扰。
因此,我们需要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去伪存真,筛选出对自己有益的信息。
精神明亮的人应该拥有积极向上的心态。
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我们要学会勇敢面对,以积极的心态去解决问题。
正如美国作家海伦·凯勒所说:“我没有看到世界,但我感受到了世界的美好。
”海伦·凯勒虽然失去了视觉,但她依然热爱生活,感受生活的美好。
这种积极向上的心态,使她成为了精神明亮的典范。
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某个问题而陷入困扰,甚至失去信心。
然而,如果我们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相信自己有能力解决问题,那么困难往往就会迎刃而解。
因此,我们要学会调整心态,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精神明亮的人应该注重个人修养。
个人修养不仅包括道德品质,还包括文化素养、心理素质等方面。
一个精神明亮的人,不仅要有高尚的品德,还要有丰富的内心世界。
提到个人修养,我想到了一个故事。
我国古代有一位名叫陈平的人,他家境贫寒,却非常好学。
有一天,他看到一位富家子弟拿着书在读,便主动上前请教。
富家子弟见到陈平衣着简陋,心生鄙夷,故意将书扔到地上。
陈平却毫不气馁,捡起书认真阅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修养并不取决于他的出身和财富,而是取决于他内心的品质和追求。
国旗下演讲稿《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

国旗下演讲稿《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的演讲题目是“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却不改其乐。
古人的物质生活如此匮乏,却依然快乐,他们到底乐在何处?在我看来,他们的快乐源自于精神的高洁与自由,因为精神丰盈明亮,他们才能安贫乐道,挣脱物质的束缚,驰骋于精神世界的快乐。
“孔颜之乐”告诉我们,只有精神饱满明亮,才会感到真正的幸福,才能成就人生理想。
苏武北海牧羊、陶潜南山采菊,伟岸信念支撑的一样是幸福的人生!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追求幸福人生,就要求我们青年人用青春的力量,勇于担当时代的责任。
用强大的毅力,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不断充实自己。
这毅力,是远航的船的风帆,有了帆,船才可以到达成功的彼岸。
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就不能甘于平庸。
周国平曾说:“一旦人不甘于被世俗生活的浪潮推着走,而总想为生活确立一个具有恒久意义的目标,他就是一个有信仰生活的人。
”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就要摆正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
在我看来,个人生命意义就是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不断认清自己,提升自己,奉献自己,同时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精神明亮是一种力量,它是刺破乌云的一道闪电,是架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一道彩虹,是升腾在灰暗心底的一轮明月。
精神的明亮,本质上是一种向上的坚强,一种牙关咬紧的优雅,一种劫波渡尽的从容。
精神明亮的人,你永远看不到他的低迷、消沉。
厚德者,载物于身,自强者,不息于行!秋天是收获的快乐,正是因为春天的播种,夏天的悉心的呵护、辛勤的劳作。
愿我们每一个学子,都能成为心中有爱、眼中放光、脸上带笑容的阳光中学生,每一天都能快乐而充实。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1-。
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初三作文600字

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初三作文600字《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作文一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可太棒啦!什么是精神明亮呢?就像太阳每天升起,照亮大地,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光明。
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呀,总是开开心心的,心里充满了正能量。
比如说雷锋叔叔,他就是一个精神明亮的人。
他总是帮助别人,不管多累多辛苦,脸上都带着笑容。
有一次,下着大雨,他看到一位大嫂带着孩子走在路上,就赶紧跑过去,把自己的雨衣给大嫂披上,还抱着孩子送他们回家。
他自己却被雨淋湿了。
雷锋叔叔这种帮助别人、快乐自己的精神,就是精神明亮的表现。
我们班也有这样精神明亮的同学。
有一次,我忘记带铅笔了,心里特别着急。
我的同桌看到了,马上递给我一支铅笔,还笑着说:“别着急,用我的!”那一刻,我觉得他的笑容就像阳光一样温暖。
小朋友们,让我们也努力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吧!多帮助别人,多给别人带来快乐,我们自己也会变得更加快乐和幸福!《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作文二小朋友们,今天我想和你们说一说,怎样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
精神明亮的人啊,就像闪闪发光的小星星。
他们总是积极向上,对生活充满了热爱。
我们学校的李老师就是这样的人。
她每天早早地来到学校,迎接我们,脸上总是挂着亲切的笑容。
不管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她都会耐心地帮助我们解决。
有一次,我考试没考好,心情特别低落。
李老师看到我,轻轻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别灰心,这次没考好,下次努力就行啦!”她的鼓励让我重新有了信心。
还有我的好朋友明明,他也是个精神明亮的孩子。
在运动会上,他参加跑步比赛,不小心摔倒了,但是他马上爬起来,继续跑,坚持到了终点。
虽然他没有拿到第一名,但是他的勇敢和坚持让大家都为他鼓掌。
小朋友们,让我们也像李老师和明明一样,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
遇到困难不害怕,总是带着微笑去面对,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
文学类: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

文学类: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特别喜欢这么一段“19世纪的一个黎明,在巴黎乡下一栋亮灯的木屋里,福楼拜在给最亲密的女友写信:我拼命工作,天天洗澡,不接待来访,不看报纸,按时看日出,我工作到深夜,窗户敞开,不穿外衣,在寂静的书房里。
”多么令人震撼。
按时看日出,把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当成一门必修课来做。
这是怎样一种情调,与对生活的热爱。
这位按时看日出的人,是位精神明亮的人。
只有精神真正明亮的人,才会以光线照见自己的生命与灵魂。
有太多精神明亮的人,有这么一位,更是我最认同的。
他就是史铁生。
《病隙碎笔》这篇文章是史铁生写于生病治疗间隙的片断随笔,没有繁琐的考证、推理或判断,也没有精彩优美的语词、段落或引文,只有作者于病痛的折磨中记录下的文字和思考,是平易的又是精辟的,是朴实无华的,又是鲜活无比的,他的精神明亮之处,体现在他对命运的态度。
“命运,就是说,这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
”他把生活比作戏剧,诠释的那么准确,“要让一出戏剧吸引人,必要有矛盾、有人物间的冲突,矛盾和冲突的前提,是人物的性格、境遇各异,乃至天壤之异”然而生活何尝不是这样呢,生活就是由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生,不同的命运来组合的。
每个人的命运不同造成了人生的差异,才显示出生活的五彩缤纷。
所以每个人的命运都不可以随意调换,也不可能千般一律。
正如他在《我与地坛》说的“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
”“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
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生活存在差别的,必须接受上帝安排的命运,不要过于埋怨上帝对自己的不公。
他的精神明亮之处,显现在他对生活的坦然豁达。
“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以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为题的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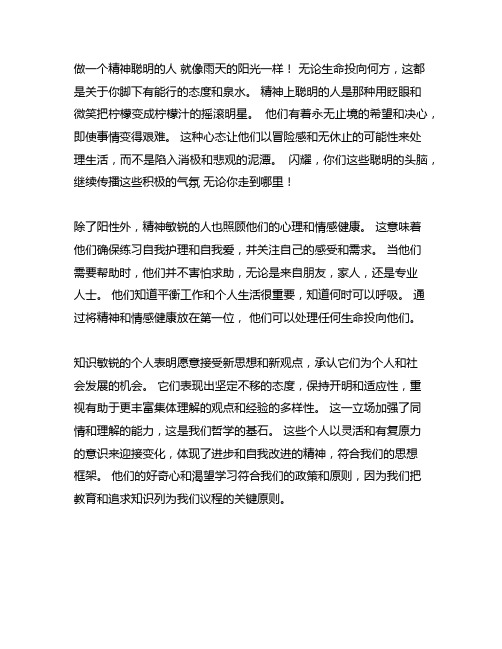
做一个精神聪明的人就像雨天的阳光一样!无论生命投向何方,这都是关于你脚下有能行的态度和泉水。
精神上聪明的人是那种用眨眼和
微笑把柠檬变成柠檬汁的摇滚明星。
他们有着永无止境的希望和决心,即使事情变得艰难。
这种心态让他们以冒险感和无休止的可能性来处
理生活,而不是陷入消极和悲观的泥潭。
闪耀,你们这些聪明的头脑,继续传播这些积极的气氛无论你走到哪里!
除了阳性外,精神敏锐的人也照顾他们的心理和情感健康。
这意味着
他们确保练习自我护理和自我爱,并关注自己的感受和需求。
当他们
需要帮助时,他们并不害怕求助,无论是来自朋友,家人,还是专业
人士。
他们知道平衡工作和个人生活很重要,知道何时可以呼吸。
通过将精神和情感健康放在第一位,他们可以处理任何生命投向他们。
知识敏锐的个人表明愿意接受新思想和新观点,承认它们为个人和社
会发展的机会。
它们表现出坚定不移的态度,保持开明和适应性,重
视有助于更丰富集体理解的观点和经验的多样性。
这一立场加强了同
情和理解的能力,这是我们哲学的基石。
这些个人以灵活和有复原力
的意识来迎接变化,体现了进步和自我改进的精神,符合我们的思想
框架。
他们的好奇心和渴望学习符合我们的政策和原则,因为我们把
教育和追求知识列为我们议程的关键原则。
《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初中作文

《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初中作文作文一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们要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
什么是精神明亮呢?就像太阳每天升起,照亮大地,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光明。
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心里总是充满着快乐和善良。
比如说,我们班的小明就是这样的人。
有一次,我不小心摔倒了,膝盖擦破了皮,疼得我直掉眼泪。
小明看到后,马上跑过来,把我扶起来,还轻轻地帮我吹伤口,安慰我说:“别害怕,一会儿就不疼啦。
”他的关心就像一束温暖的阳光,照进了我的心里。
还有一次,在公交车上,一位老奶奶上车后没有座位。
很多大人都在玩手机,没有注意到。
这时,一个小姐姐站起来,对老奶奶说:“奶奶,您坐我这儿吧。
”老奶奶笑着说谢谢,小姐姐的脸上也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小朋友们,让我们都像小明和小姐姐一样,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吧。
用我们的善良和爱心,去照亮身边的每一个人。
作文二
小朋友们,今天我想和你们说一说,怎样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
精神明亮的人呀,总是带着微笑,就像春天里盛开的花朵,让人看了心情都变好。
我的好朋友小红就是这样。
有一天,我们一起在公园里玩,看到一个小弟弟在哭。
小红走过去,蹲下来问:“小弟弟,你怎么哭啦?”小弟弟说他找不到妈妈了。
小红拉着小弟弟的手,带他去公园
的广播室,帮小弟弟找到了妈妈。
小弟弟破涕为笑,小红也笑得特别甜。
还有我们小区的王爷爷,他每天都会把小区的花园打扫得干干净净。
他说,看到大家在整洁的花园里玩耍,他就很开心。
小朋友们,让我们也做这样的人,给别人带来温暖和快乐,那我们自己也会变得精神明亮哟!。
百度搜索作文 做一个 精神明亮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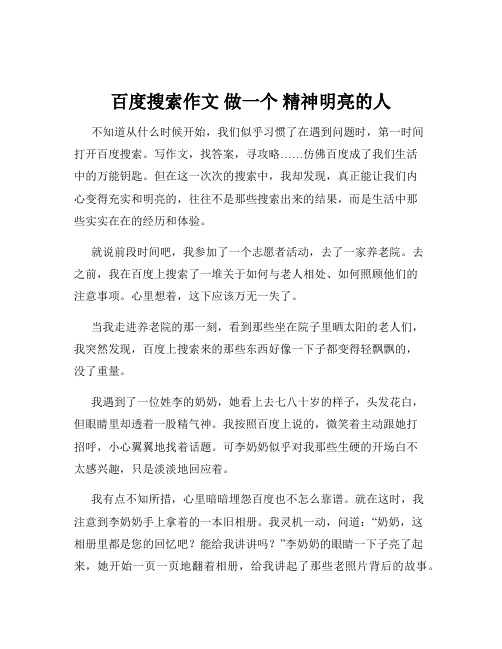
百度搜索作文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似乎习惯了在遇到问题时,第一时间打开百度搜索。
写作文,找答案,寻攻略……仿佛百度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万能钥匙。
但在这一次次的搜索中,我却发现,真正能让我们内心变得充实和明亮的,往往不是那些搜索出来的结果,而是生活中那些实实在在的经历和体验。
就说前段时间吧,我参加了一个志愿者活动,去了一家养老院。
去之前,我在百度上搜索了一堆关于如何与老人相处、如何照顾他们的注意事项。
心里想着,这下应该万无一失了。
当我走进养老院的那一刻,看到那些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的老人们,我突然发现,百度上搜索来的那些东西好像一下子都变得轻飘飘的,没了重量。
我遇到了一位姓李的奶奶,她看上去七八十岁的样子,头发花白,但眼睛里却透着一股精气神。
我按照百度上说的,微笑着主动跟她打招呼,小心翼翼地找着话题。
可李奶奶似乎对我那些生硬的开场白不太感兴趣,只是淡淡地回应着。
我有点不知所措,心里暗暗埋怨百度也不怎么靠谱。
就在这时,我注意到李奶奶手上拿着的一本旧相册。
我灵机一动,问道:“奶奶,这相册里都是您的回忆吧?能给我讲讲吗?”李奶奶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她开始一页一页地翻着相册,给我讲起了那些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原来,李奶奶年轻的时候是个舞蹈演员,照片上那些穿着漂亮舞裙的身影就是她曾经的辉煌。
她讲着讲着,脸上洋溢着自豪和幸福。
我听得入了迷,也不再去想什么百度上的技巧了,只是顺着奶奶的话,时不时地插上几句,表达我的好奇和赞叹。
聊着聊着,李奶奶突然叹了口气说:“人老了,跳不动咯。
”我连忙说:“奶奶,您在我心里永远是最美丽的舞者!”李奶奶笑了,笑得像个孩子。
那天,我陪李奶奶聊了很久很久,听她讲了好多过去的事情。
从她的青春岁月,到她的爱情故事,再到她如何含辛茹苦地把孩子养大。
我发现,她的每一个故事都那么生动,那么感人,比百度上那些干巴巴的文字要精彩得多。
离开养老院的时候,李奶奶拉着我的手说:“孩子,谢谢你,今天我很开心。
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海子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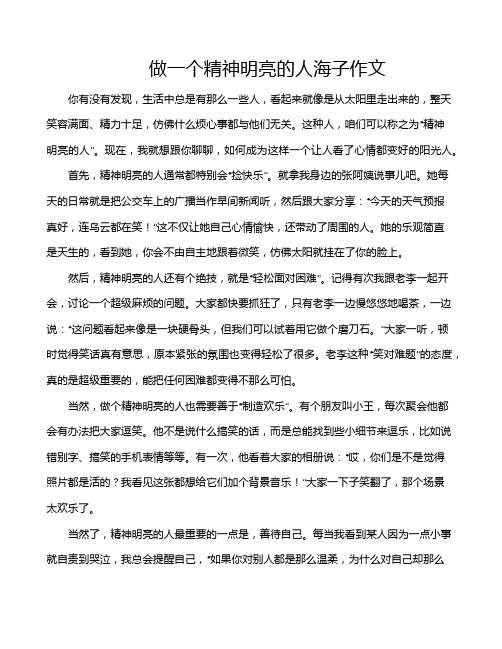
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海子作文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总是有那么一些人,看起来就像是从太阳里走出来的,整天笑容满面、精力十足,仿佛什么烦心事都与他们无关。
这种人,咱们可以称之为“精神明亮的人”。
现在,我就想跟你聊聊,如何成为这样一个让人看了心情都变好的阳光人。
首先,精神明亮的人通常都特别会“捡快乐”。
就拿我身边的张阿姨说事儿吧。
她每天的日常就是把公交车上的广播当作早间新闻听,然后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天气预报真好,连乌云都在笑!”这不仅让她自己心情愉快,还带动了周围的人。
她的乐观简直是天生的,看到她,你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微笑,仿佛太阳就挂在了你的脸上。
然后,精神明亮的人还有个绝技,就是“轻松面对困难”。
记得有次我跟老李一起开会,讨论一个超级麻烦的问题。
大家都快要抓狂了,只有老李一边慢悠悠地喝茶,一边说:“这问题看起来像是一块硬骨头,但我们可以试着用它做个磨刀石。
”大家一听,顿时觉得笑话真有意思,原本紧张的氛围也变得轻松了很多。
老李这种“笑对难题”的态度,真的是超级重要的,能把任何困难都变得不那么可怕。
当然,做个精神明亮的人也需要善于“制造欢乐”。
有个朋友叫小王,每次聚会他都会有办法把大家逗笑。
他不是说什么搞笑的话,而是总能找到些小细节来逗乐,比如说错别字、搞笑的手机表情等等。
有一次,他看着大家的相册说:“哎,你们是不是觉得照片都是活的?我看见这张都想给它们加个背景音乐!”大家一下子笑翻了,那个场景太欢乐了。
当然了,精神明亮的人最重要的一点是,善待自己。
每当我看到某人因为一点小事就自责到哭泣,我总会提醒自己,“如果你对别人都是那么温柔,为什么对自己却那么苛刻?”于是,我学会了学会放松,偶尔给自己放个假,去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比如看看搞笑电影、泡泡热水澡。
这种简单的自我关爱,真的能让人变得更快乐,更充满活力。
最后,我想说的是,精神明亮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一种选择。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决定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培训心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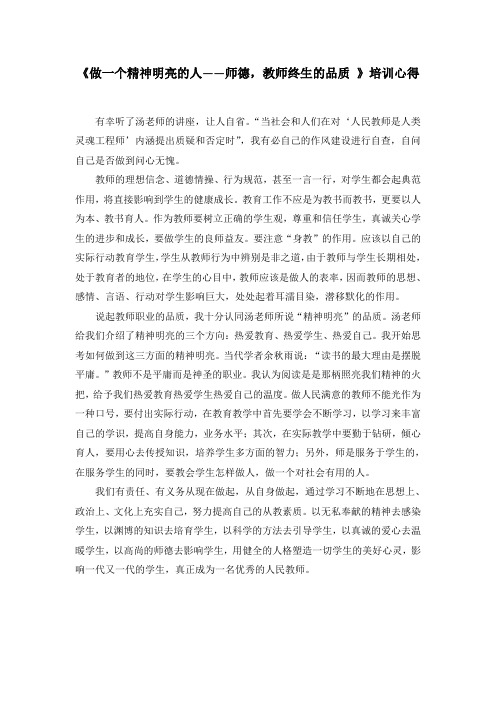
《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师德,教师终生的品质》培训心得有幸听了汤老师的讲座,让人自省。
“当社会和人们在对‘人民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内涵提出质疑和否定时”,我有必自己的作风建设进行自查,自问自己是否做到问心无愧。
教师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行为规范,甚至一言一行,对学生都会起典范作用,将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健康成长。
教育工作不应是为教书而教书,更要以人为本、教书育人。
作为教师要树立正确的学生观,尊重和信任学生,真诚关心学生的进步和成长,要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要注意“身教”的作用。
应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学生,学生从教师行为中辨别是非之道,由于教师与学生长期相处,处于教育者的地位,在学生的心目中,教师应该是做人的表率,因而教师的思想、感情、言语、行动对学生影响巨大,处处起着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作用。
说起教师职业的品质,我十分认同汤老师所说“精神明亮”的品质。
汤老师给我们介绍了精神明亮的三个方向:热爱教育、热爱学生、热爱自己。
我开始思考如何做到这三方面的精神明亮。
当代学者余秋雨说:“读书的最大理由是摆脱平庸。
”教师不是平庸而是神圣的职业。
我认为阅读是是那柄照亮我们精神的火把,给予我们热爱教育热爱学生热爱自己的温度。
做人民满意的教师不能光作为一种口号,要付出实际行动,在教育教学中首先要学会不断学习,以学习来丰富自己的学识,提高自身能力,业务水平;其次,在实际教学中要勤于钻研,倾心育人,要用心去传授知识,培养学生多方面的智力;另外,师是服务于学生的,在服务学生的同时,要教会学生怎样做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通过学习不断地在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充实自己,努力提高自己的从教素质。
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去感染学生,以渊博的知识去培育学生,以科学的方法去引导学生,以真诚的爱心去温暖学生,以高尚的师德去影响学生,用健全的人格塑造一切学生的美好心灵,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学生,真正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

93阅读广场◆主题阅读1·精神明亮精神明亮有一种巨大的能量,照亮自己,亦照亮他人。
精神明亮的人,心中有旷野,有悲悯,能从灵魂深处感到满足与沉静;精神明亮的人,能够欣赏大自然的美,感受黎明、鸟语、花香,深情地打量自己,有一颗赤子之心;精神明亮的人,灵魂始终高蹈在生活之上,在困境中不哀叹,笃定,无所畏惧。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积极昂扬地生活,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
(魏 薇)明代理学家王阳明说过:“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所谓的“心外无物”,“心”亦精神。
你的精神明亮,凡俗尘世才会被照亮;你的目光清澈,世事万千才能被洞悉。
明亮,在现代汉语中,有“亮光、正义、有希望的”几层意思,无论哪层,它都是一个指向正向价值的词,象征着勇敢、温暖、幸福、新生和告别黑暗。
而精神明亮,意味着内心有着阔远的时空格局,可以盛装对世界的悲悯、对苍生的关爱、对草木的体恤。
它喷涌出深切的激情和美德的光芒,去照亮晦暗。
那些精神明亮的人,懂得生活的真正目的——能从灵魂深处感到满足与沉静,而不是庸俗地追求物质和感官享受。
精神的明亮之光,可以是乡情、爱情、亲情,可以是格局、理想、信仰,也可以是真善美和良知。
它有时会和物质有所牵连和关涉,但它必是精神的。
今天,若从全世界挑出几个能以思想影响世界格局和转向的人物,我想,马克思必是其中之一。
马克思年轻时是富家子、人生赢家:23岁,通过答辩获博士学位;25岁,迎娶“舞会皇后”燕妮;他满腹才情,年纪轻轻被聘为《莱茵报》主编,荣华富贵,唾手可得,可谓春风得意。
然而,之后几十年,他却过着艰苦斗争、奔走逃亡的生活。
他为写《资本论》,贫穷到全家只能吃土豆、睡光板床,子女夭折后连丧葬费都是借来的。
这是马克思的选择。
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米丽宏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94作文19世纪的一个黎明,在巴黎乡下一幢亮灯的木屋里,福楼拜在给最亲密的女友写信:“我拼命工作,天天洗澡,不接待来访,不看报纸,按时看日出。
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作文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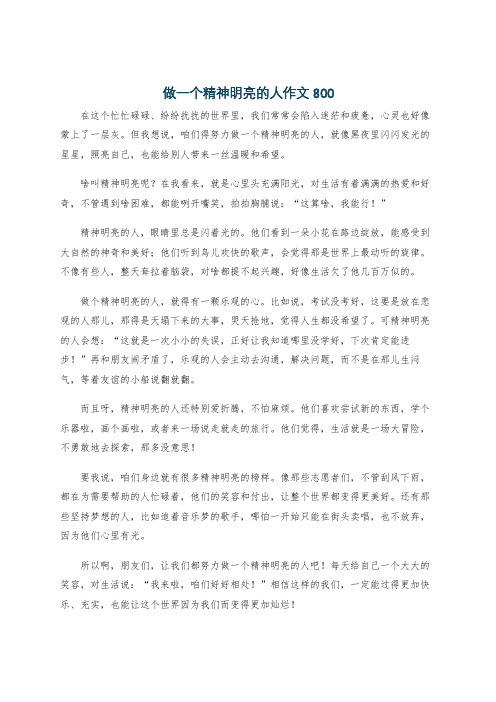
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作文800在这个忙忙碌碌、纷纷扰扰的世界里,我们常常会陷入迷茫和疲惫,心灵也好像蒙上了一层灰。
但我想说,咱们得努力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就像黑夜里闪闪发光的星星,照亮自己,也能给别人带来一丝温暖和希望。
啥叫精神明亮呢?在我看来,就是心里头充满阳光,对生活有着满满的热爱和好奇,不管遇到啥困难,都能咧开嘴笑,拍拍胸脯说:“这算啥,我能行!”精神明亮的人,眼睛里总是闪着光的。
他们看到一朵小花在路边绽放,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好;他们听到鸟儿欢快的歌声,会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动听的旋律。
不像有些人,整天耷拉着脑袋,对啥都提不起兴趣,好像生活欠了他几百万似的。
做个精神明亮的人,就得有一颗乐观的心。
比如说,考试没考好,这要是放在悲观的人那儿,那得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哭天抢地,觉得人生都没希望了。
可精神明亮的人会想:“这就是一次小小的失误,正好让我知道哪里没学好,下次肯定能进步!”再和朋友闹矛盾了,乐观的人会主动去沟通,解决问题,而不是在那儿生闷气,等着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而且呀,精神明亮的人还特别爱折腾,不怕麻烦。
他们喜欢尝试新的东西,学个乐器啦,画个画啦,或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他们觉得,生活就是一场大冒险,不勇敢地去探索,那多没意思!要我说,咱们身边就有很多精神明亮的榜样。
像那些志愿者们,不管刮风下雨,都在为需要帮助的人忙碌着,他们的笑容和付出,让整个世界都变得更美好。
还有那些坚持梦想的人,比如追着音乐梦的歌手,哪怕一开始只能在街头卖唱,也不放弃,因为他们心里有光。
所以啊,朋友们,让我们都努力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吧!每天给自己一个大大的笑容,对生活说:“我来啦,咱们好好相处!”相信这样的我们,一定能过得更加快乐、充实,也能让这个世界因为我们而变得更加灿烂!。
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读后感1500字(五篇)

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读后感1500字(五篇)(实用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文档下载后可定制修改,请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和使用,谢谢!并且,本店铺为大家提供各种类型的教育资料,如体裁作文、议论文、字数作文、记叙文、高中作文、初中作文、小学作文、祝福语、心得体会、其他范文等等,想了解不同资料格式和写法,敬请关注!Download tips: This document is carefully compiled by this editor.I hope that after you download it, it can help you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The document can be customized and modified after downloading, please adjust and use it according to actual needs, thank you!Moreover, this store provides various types of educational materials for everyone, such as genre essays, argumentative essays, word count essays, narrative essays, high school essays, middle school essays, elementary school essays, blessings, experiences, and other sample essays. If you want to learn about different data formats and writing methods, please pay attention!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读后感1500字(五篇)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
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海子作文

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海子作文当我在脑海中琢磨“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这个话题时,脑海里浮现出的画面就像是阳光下的金色麦田,散发着温暖和活力。
说实话,要是人生能像那些广告里的白衣天使一样总是光鲜亮丽,那真是太好了。
不过,我们这帮普通人可得学会怎样在平凡的生活中,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
来,听我说说这些事儿。
先讲个小故事。
那天,我跟好朋友小张一起去咖啡馆,刚进门,我们就碰到了一位看起来特别无精打采的服务员。
他的表情就像被人从床上拖出来的,笑容更像是被冬天冻僵了一样。
于是,小张这人呢,就开始发挥他的“魔力”了。
他的脸上立刻挂上了一个大大的笑容,声音也是特别亲切,“嘿,兄弟,今天这天气真不错啊!你是不是也觉得咖啡馆的温度刚刚好?”服务员抬头看看小张,似乎有点被这个笑容震惊了,嘴角渐渐露出了一点儿笑意,声音也变得有些轻松起来:“嗯,是啊,其实今天我还挺喜欢这天气的。
”看到这儿,我心里有点儿小激动,真的是,精神明亮的人,光是他们的态度,就能影响到周围的人。
小张继续跟服务员聊了几句,结果那服务员的脸上已经挂满了笑容,看起来整个人都活跃了不少。
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什么让我们成为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呢?有时候,真的是简单的微笑和热情的问候,能把别人也带上这条路。
你瞧,小张不过是用了一点儿小技巧,就让一个人变得明亮了。
说到这儿,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秘密。
我发现,跟别人说话时,尽量多用一些积极的词汇,少用那些负面的词汇。
比如,换句话说,“这事儿真让人头疼”可以改成“这事儿真是个挑战”。
这种小小的改变,能让你看起来更乐观,也能让你在别人面前显得更有活力。
有一次,我在办公室和小李聊天,他一直在抱怨工作压力太大。
我试着用了一点儿小技巧,“小李,你说这工作挑战也算一种成长的机会吧?”结果他愣了一下,笑着说:“嗯,你说得对,这样想,心情也会好一些。
”不过,这种精神明亮的状态不仅仅是对别人有效,自己也能从中受益。
当我们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琐事时,整个人的状态都会变得更好。
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作文800

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作文800在这个忙忙碌碌、纷纷扰扰的世界里,你有没有想过,要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啥叫精神明亮?可不是说脑袋会发光哈,而是说要有一颗积极向上、充满阳光、乐观豁达的心。
精神明亮的人,就像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不管周围有多黑暗,他们都能照亮自己,也能给别人带来一丝温暖和希望。
他们不会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好像全世界都欠了他们几百万似的。
就算遇到了困难,他们也会笑着说:“这算啥,都是小场面!”然后撸起袖子加油干。
你看那街边卖早点的阿姨,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起来准备,不管是寒冬还是酷暑,脸上总是带着亲切的笑容。
对她来说,能为大家提供一份美味的早餐,就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这就是精神明亮,简单而又满足。
再看看那些热爱生活的人,他们会在阳台上种满花花草草,会在周末去爬山、骑行,会在空闲时间读书、画画。
他们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充满了色彩和乐趣。
他们不会抱怨没时间、没金钱,因为他们知道,生活的美好就在身边,只要用心去感受。
相反,那些精神不明亮的人呢?总是在抱怨工作累、压力大,总是在羡慕别人的生活,却从不肯努力改变自己。
他们的世界里充满了阴霾,看不到一丝阳光。
这样的人生,多无趣啊!要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其实也不难。
要有一个好心态,学会乐观地看待问题。
别一点小事就觉得天要塌了,要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
要多和积极向上的人在一起,正所谓“近朱者赤”,他们的正能量会感染你。
还有啊,要学会发现生活中的小美好,一朵绽放的花、一个可爱的孩子的笑容、一顿美味的晚餐,都能让你的心情瞬间变好。
朋友们,让我们都努力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吧!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的路。
这样的人生,才够精彩,才够有意义!。
作为一个精神明亮的人作文科学家例子

作为一个精神明亮的人作文科学家例子《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
嘿,大家知道吗?我觉得成为一个精神明亮的人超酷的!就像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一样。
比如说牛顿,哇哦,那家伙可太牛了。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关于他的故事。
据说呀,有一天牛顿坐在苹果树下休息,你说巧不巧,突然就有个苹果掉下来了,“啪”的一下就砸在了他脑袋上。
一般人可能就哎哟一声,然后捡起苹果吃了或者扔一边去了。
但牛顿可不一般啊,他就开始琢磨了:这苹果咋就掉下来啦,咋不往天上飞呢?他就这么一思考,嘿,竟然发现了万有引力!你说神奇不神奇。
牛顿就是这样一个精神明亮的人,一个小小的苹果就能让他开启智慧的大门。
我也想成为像牛顿那样精神明亮的人呀。
我希望自己能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好奇,能从平凡的小事中找到不平凡的意义。
我要让自己的眼睛始终闪烁着光芒,去发现更多的奇妙。
以后呀,我也要多多留意身边的点点滴滴,说不定哪天我也能像牛顿似的,从一个小小的事情中找到大大的发现呢。
我要努力让自己也成为一个精神明亮的人,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和精彩呀!哈哈哈。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诚哉斯言!一个健康的社会必定是每个个体的价值得到充分尊重,理想之翼得到充分舒展的社会。王开岭的思考给我们自己的思考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教育出问题,还是会从内部出问题,根源王开岭说得很明白。教育者应精心守护“童心”这粒“花粉”,不让它“被世俗经验这匹蟑螂悄悄拖走”……
三、让“个”挺直腰杆
孩提时代“只是被视作一个‘待超越’的初始阶段,一个尚不够‘文明’的低级状态……”,学生一直被当作“不及格、非正式、未成型、待加工”的产品,也是和成人对孩童作为“个体”的忽视分不开的。非但成人之于孩童,教育者之于学生是这样,在群体生活中,整体淹没个体的现象比比皆是,并成为一种规范在人们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尊重个体的感受和价值,倾听个体发出的声音,为被噤声的个体仗义执言,这是王开岭散文随笔中振聋发聩,色彩异常亮丽的一笔。
“影响一个人终生价值观的,一定是童年的记忆和生命印象——那些最早深深感动过心灵的细节!”
捍卫童年就是营造终身的精神家园!教育是为了人的精神发展,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教育就是捍卫和留住童年,是浇水、施肥、捉虫,而非一味提剪刀对准枝和叶。成人,尤其教育工作者须从改变自身做起。“值得尊敬的成年人,一定是那种‘直至成年依然童心未泯的人’”。
故乡曾经贫穷过,如今,故乡不再一无所有;故乡曾经以窑洞为家,如今,故乡拥有窗明几净的楼房。可故乡失去的远远超过故乡所得到的。
拿着相机,我走遍故乡的角角落落,我能真切地看到往事的影子,能听到逝去的亲人的呓语。如今,围沟而住的人们早已进城的进城,到坳心平坦的地方建新居的建新居,当年人烟兴旺的地方不再有鸡鸣狗吠之声。残垣断壁里面,一孔又一孔黑魆魆的窑洞面对远方的天空瞪着大大的眼睛,荒草无孔不入,发疯似的长满老屋的角角落落。风从远方吹来,又吹向远方。作为当年联系村庄里外的洞子已垂垂老矣,又因风吹雨淋、年久失修而坍塌。惟有放牧的人偶尔赶着羊群,在提防中快步穿过,洞子和老屋一样在岁月的长河中逐渐淡出人们生活的舞台。
有人说王开岭的文字,有一种温润的金属感,有一种磁性的光芒,它敏感、深邃.明亮又干净……
作为一个思想者,他对童年的敬畏和捍卫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感染。
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必定有着睿智的眼睛,清醒的大脑,不,这还不够,还得有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王开岭就是这样一个人。
读这些文字,有如长鞭加身,芒刺在背,尤其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尤如此。学生在教育者的眼里何尝不是如此!二十多年的从教生涯中,教高中之前,我教过小学,教过初中。回想从教伊始,怀揣育人梦想,诧异并反感于那些对学生爆粗口乃至体罚的行为,心想教育怎能如此粗暴。也说教学上分层次,也说因材施教,受各种因素影响,也只是说说而已,重共性,轻个性;求大同,直至灭小异,有多少教育者肯俯下身子,倾听一个孩童的心声?管理、教学力求整体化一,用成人的思维揣度孩童的心理,用成人的规范左右孩童的行为,凡此种种,不禁又想,教育怎能这样简单和变异?
当“小”的对手被放扩为无边无际的“大”时,“小”无法不绝望,无法不崩溃。除了一遍遍地自卑、沮丧,他能怎么样呢?他能说出“国家错了”那样的话吗?他敢想象“政府应向这个人道歉”那样的事吗?能忍则忍,能屈则屈,能受则受,实在受不了就只剩一条路……
他实在太弱了。何止是“小”——简直是渺小。正是几十年藐视“人”的文化激素和凶险的政治环境,发育了这种畸型可怜的弱和唯唯诺诺。正是长期“个”的缺席和权利的严重不足值,导致了一代人根本不理会或不敢动用自己的权利。尤其一个被勒令停止尊严、含垢咀辱达37年的老人,如何在一夜间拣回久违了的尊严、拣回自己的公民资格?(《一个人的遭遇》)
我们之所以对故乡情有独钟,念念不忘,不单在于“我从哪里来”这个古老的苦苦追问,更在于“每个故乡都在沦陷,每个故乡都因整容而毁容”这个现实。“沦陷”的不仅是现实的家园,更是精神的家园,“毁”掉的不仅是故乡的“容”,更是故乡的神,是维系故乡这棵大树生命的根。
一方面,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整体化一的新农村构建使得此乡与他乡不再有形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窗明几净外难见黄昏时炊烟袅袅的温馨,整齐化一中少了曾经的乡情依依,兼之大量农村劳动力背井离乡,去远方,去大城市寻梦,产生了“留守”一词所不能完全涵盖的亲情的残缺。
他认为个体是最真实的生命单位。以对悲剧的日常感受为例,“人们总惯于以整体印象代替个体的不幸——以集合的名义遮蔽最真实的生命单位”。
感受悲剧最人道和理性的做法:寻找“现场感”!为不幸找到真实的个体归属,找到那“一个,又一个……”的载体。世界上,没有谁和谁是可以随意叠加和整合的,任何生命都唯一、绝对,其尊严、价值、命运都不可替代。生生死死只有落在具体的“个”上才有意义,整体淹没个体、羊群淹没羊的做法,实际上是对生命、对悲剧主体的粗暴和不敬,也是背叛与遗忘的开始。(《打捞悲剧中的“个”》)
美国教育家杜威也指出:“生活就是生长,所以一个人在一个阶段的生活,和另一个阶段的生活是同样真实、同样积极的,这两个阶段的生活,内容同样丰富,地位同样重要。因此,教育就是无论年龄大小,提供保证其充分生活条件的事业……”他说,“教育者要尊重未成年状态”。目前国际社会基本认同的童年概念包括:第一,必须将儿童当“人”看,即承认其独立人格。第二,必须将儿童当“儿童”看,不能将其当作“成人的预备”。第三,儿童在成长期,应尽量给其提供与之身心相适应的生活。(《向儿童学习》)
二、守护“童心”这粒“花粉”
儿童的美德和智慧,常常被大人们粗糙的双目所忽视,常常被不以为然地当废电池一样地扔进岁月的垃圾沟里。而很多时候,孩提时代在教育者那儿,只是被视作一个“待超越”的初始阶段,一个尚不够“文明”的低级状态……父母、老师、长辈都眼巴巴焦急地盼着,盼望他们尽早地摆脱这种幼小和单薄,“从生命之树进入文明社会的罐头厂”(凯斯特纳),尽早地成为和自己一样“散发着罐头味的人”……继而成为具有教育下一代资格的“大人”“成品人”。
当眼前事物与记忆完全不符,当往事的青苔被抹干净,当没有一样东西提醒你曾与之耳鬓厮磨、朝夕相处……它还能让你激动吗?还有人生地点的意义吗?”
这是《每个故乡都在消逝》中的文字。
“我总习惯性地游走于故土的塌窑烂庄之间。这里,有着太多的积淀——历史的、文化的;这里,有着太多的记忆——父辈的、儿时的。我带着女儿,一一指给她看:这是咱家的老屋,这是咱家分家之后借住的窑洞,这是你爷爷一 头一 头凿的第二处庄子,这是相宁奶奶家的高窑,这是黑黑爷爷家的窑洞院落,这是当年救了你姑姑命的老中槐,这是……如今,早已物是人非。说“物是”也不尽然。人去院空,到处荒草浸淫,墙毁窑塌,过去已不再。这块土地承载的太多太多——贫瘠、愚昧、饥饿;善良、质朴、勤劳;汗水、泪水,更不乏记忆和梦想。于是,才有《梦中的家园》五篇,给父辈作记,给儿时作记,也给这块土地作记。”
这是我的系列散文《梦中的家园》“后记”中的一段话。
每当回到故土,无论春夏秋冬,我总要走遍村庄的角角落落,尽管“人去院空,到处荒草浸淫,墙毁窑塌,过去已不再”,但诚如王开岭所言,“一井一石一树”,无不有着记忆中的蛛丝马迹,无不牵起过往的悲欢离合。“故乡”,“不仅仅是个地址和空间,它是有容颜和记忆能量、有年轮和光阴故事的”。
但愿故乡不只是用来怀念的。
其实,“故乡”的全部含义,都将落实在“地点”和它养育的内容上。简言之,“故乡”的文化任务,即演示“一方水土一方人”之逻辑,即探究一个人的身世和成长,即追溯他那些重要的生命特征和精神基因之来源、之出处。若抛开此任务,“故乡”将虚脱成一记空词、一朵谎花。
读王开岭的散文,诸如此类,总能时不时达到精神上的默契,引发情感的共鸣,他思考的维度、深度,总能给人以精神上的导引,情感上的触发和慰藉。做一个精 Nhomakorabea明亮的人
——读王开岭先生的散文随笔自选集《精神明亮的人》
宁县一中窦志宁
初识王开岭,源于《读者》——
《两千年的闪击》(2008第22期);
《生活在险境中》(2010年第2期);
《轮椅上的那个年轻人,起身走了》(2012年第12期);
《自己做主的舌头》(2012年第13期);
《一辈子就是玩》(2012第18期);
《必须的力量》(2012第19期);
《没有爱,世界会冻僵》(2012第22期);
《父与子》(2013第3期);
《一条狗的事业》(2013第8期);
《这个叫“霾”的春天》(2013第20期);
《人生的深味》(2014第3期)。
一、每个故乡都在消逝
“‘故乡’,不仅仅是个地址和空间,它是有容颜和记忆能量、有年轮和光阴故事的,它需要视觉凭证,需要岁月依据,需要细节支撑,哪怕蛛丝马迹,哪怕一井一石一树……否则,一个游子何以与眼前的景象相认?何以肯定此即梦牵魂绕的旧影?此即替自己收藏童年、见证青春的地方?
如果为了国家利益可任意贬低个体尊严,如果牺牲个体自由与权利的做法得到了宣传机器的大肆鼓吹,那么,不管该国家利益被冠以怎样的“崇高”或“伟大”,其本质都是可疑的。任何政府和部门之“权威”,惟有在代表公意时才具合法性,才配得上民间的服从。在一个靠常识维护的国家里,每一个“个人”都是唯一性资源,都拥有平等的社会席位,每个人的福祉都是国家重要的责任目标……正是基于这些同构、互动和彼此确认的关系,个人才可能成为国家的支持者,才会滋生真正的爱国者和“人民”概念。(《是“国家”错了》)
长期以来,在体制神话伦理和极端一元的意识形态下,我们一再被叮咛:个体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任何重视或放大个体的做法皆自私可耻,惟国家和集团利益至高无上,为了“大”,必须时刻准备牺牲“小”……正像“皮毛论”鼓吹的那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借助这样一句俚语性质的“真理”,作为“毛”的个体就天然披覆了一种自卑,被烙上了一记鲜红的耻字,也使得“小”在一切被誉为“大”和“皮”的权威前羞愧地低下头去,自惭形秽,无地自容。(《一个人的遭遇》)
二十多年过去了,教育还是这样的教育,学生仍是教育者眼里那样的学生,有改观,但不大,有改变的尝试,但成效尚待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