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思路与表现方法的异同
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艺术之比较

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艺术之比较作者:万江婷来源:《科技资讯》2019年第31期摘 ;要:中华民族发展至今,涌现出了无数文学家。
作为我国文坛灵魂人物的鲁迅已然形成一种文化传统,而才女张爱玲也为我国文学发展带来了诸多有名作品。
就目前来看,学界对于二者的创作艺术方面的研究数不胜数,但是将二者创作艺术进行异同比较的却是少之又少。
该文就从两位文学工匠的创作艺术形式着手,对其进行了平行比较,以求能够寻找到文化作品创作过程中的共性。
关键词:鲁迅 ;张爱玲 ;小说 ;创作艺术 ;比较中图分类号:I207.42 ;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9)11(a)-0255-02鲁迅的文学特色以及二人的写作内容都存在极大差异,鲁迅一直都是我國文学历史上的重要工匠,其文学作品也一直被广泛推崇;而张爱玲的文字学作品偏向于个人化写作,并且张爱玲还和卖国贼胡兰成有过一段爱情往事,因此其文学作品通常不会被当代文坛所接受。
大多数人认为张爱玲并不能和鲁迅相提并论。
1 ;颇具艺术特色的表现手法文学巨匠鲁迅以及张爱玲生活在我国最为黑暗的年代,两位均是对当时的社会现象予以披露的作家。
鲁迅的作品展现出的是对社会黑暗的映射以及讽刺,而张爱玲则是对人的劣根性予以揭露以及讽刺。
如果就表现手法的共性来看,二者均使用了大量讽刺内容。
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讽刺,作为新旧时代交替时期的“掘墓人”,鲁迅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讽刺社会政治环境的队伍之中,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将事实展现给人们。
可以说,讽刺艺术贯穿了鲁迅的大部分文学作品。
比如,在《孔乙己》中,主角总是说“窃书不能算偷……”这类的话,其本身就是作为一种笑料呈现在读者面前的。
鲁迅为人们展示出了下层读书人的清高、迂腐而又可悲可叹的艺术形象,其本身就是一种讽刺,在读者品汇文章的过程中,其或许会有笑意,但是其中却又掩藏着些许心酸。
由此可见,鲁迅的讽刺比较幽默,但是在语言深处却又隐藏着大量的黑暗色彩,言辞犀利,直击社会阴暗面。
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艺术之比较

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艺术之比较鲁迅与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两位杰出作家,他们在小说创作方面都有着不俗的造诣和成就。
鲁迅被誉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奠基人”,张爱玲则被誉为“中国现代派小说的代表人物”。
这两位文学巨匠的小说创作风格各有特点,在内容、形式、语言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下面将从这几个方面来比较鲁迅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艺术。
一、内容方面的比较鲁迅的小说创作内容多从中国社会和人性角度出发,关注弱势群体、贫苦百姓及其受压迫的生存状态,批判封建主义制度和文化传统。
他的小说多具有强烈的社会意味和人性关怀,例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
在创作上,鲁迅多运用夸张、讽刺、幽默的手法,以达到社会批判的效果。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内容则更多关注人物内心的情感体验和生活状态,关注女性身份和角色的转变和挣扎,对城市生活及现代文化的抨击和反思。
她的小说多情节曲折,人物复杂,多暗示和隐喻,例如《色戒》、《金锁记》等。
张爱玲多强调爱情主题,赋予女性情感世界新的表达形式,以达到文学表现的效果。
鲁迅的小说创作形式多采用简明紧凑的叙述方式,内容生动、情节明晰,多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呈现,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
鲁迅在小说中多运用对话,表达出人物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现代中国社会的深刻问题。
鲁迅多注重描写现实场景,使得小说具有更强的现实感。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形式多采用夹叙夹议的叙述方式,内容多朦胧和含蓄,不断探寻和挖掘人物内心的复杂情感和思想。
她的小说注重描写城市生活的细节,刻画出上海滩的繁华与虚荣,体现出她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和个人风格。
鲁迅的小说创作语言朴实、质朴,不太注重修辞和华丽的表达方式,更多采取白话文种的语言表现,用一种较为普遍的语言书写出普通百姓的生活与斗争,更具可读性和文学感染力。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语言华丽优美,注重修辞和韵律方面的表现。
她的小说多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学和艺术为背景,充满着精致的文化内涵。
她的小说语言流畅、娓娓动听,富有诗意和意境。
鲁迅与张爱玲

鲁迅与张爱玲————————————————————————————————作者:————————————————————————————————日期:鲁迅与张爱玲-汉语言文学鲁迅与张爱玲李丽摘要:鲁迅与张爱玲分别是20世纪20年代、40年代登峰造极的作家,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作家,但他们作品的思想内涵存在着一致性,笔者正是从这一共性出发探索共性中的个性。
由此可见,张爱玲继承并发展了鲁迅的思想,两位作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关键词:鲁迅张爱玲异同前言尽管鲁迅与张爱玲是分属于两个时代、两个阵营的作家,似乎毫不相干,然而文学界将鲁迅与张爱玲放在一起并非新鲜事,1944年,著名翻译家傅雷认为《金锁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胡兰成在《评张爱玲》中说:“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着。
”他们之间或多或少的联系,那么他们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共性与个性呢?一、从对女性命运的观照来看,礼教与自身鲁迅与张爱玲是两位极为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家,都不同程度地道出了女性生存境遇的艰难与所受的不公正待遇。
而就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探讨上,两位作家的意见并不一致,鲁迅将女性的悲剧命运归咎于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戕害,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她勤劳、善良、朴实,却在糊里糊涂中成了旧礼教的牺牲品。
使祥林嫂饱受磨难的不仅仅是生活的困苦,更重要的是受到封建礼教文化制度影响的精神摧残。
“从一而终”是祥林嫂固守的封建思想,为此被迫改嫁时她撞得头破血流,甚至到庙里捐门槛来试图解脱这个“罪孽”,让千人踩、万人踏,种种荒唐行为的背后,无不表露着那个时代的女性在长期封建礼教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自我否定的自虐倾向。
《离婚》中的爱姑不正是在封建势力的代言人“七大人”的威逼下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他的一切不公正的安排吗?而张爱玲将其归咎于女性自身对男性不自觉的依附,正如张爱玲在《谈女人》中所言:“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
叩问女性命运:从鲁迅到张爱玲

女性异化是鲁迅国民性批判与张爱玲人性批判的契合点,张爱玲对女性奴性意识的批判是对鲁迅先生国民性批判的继承和开拓,在探索女性命运问题上,张爱玲思考的深度直追鲁迅。铁屋子是鲁迅书写国人奴隶命运的隐喻,铁闺阁是对张爱玲女性奴隶命运书写的诗性概括,本文具体从鲁迅与张爱玲共同关注的女性命运入手,从二人创作主题、创作视角、创作态度三方面的异同比较来阐述张爱玲女奴历史书写对鲁迅来考察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张爱玲站在女性立场来体察女性命运。鲁迅采取社会一外向视角对女性抱以深切的同情,张爱玲采用家庭一内向视角挖掘女性奴性意识的心理痼疾。鲁迅与张爱玲都通过对男权社会的批判来观照女性奴性意识产生的根源。张爱玲是继鲁迅之后的神话消解者,本文通过鲁迅与张爱玲对男性神话、爱情神话、亲情神话的三个层面的消解来阐释张爱玲与鲁迅对造成女性异化的男权社会的批判。鲁迅与张爱玲通过女性异化的书写对女性命运作了历史性的反思,二人都写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人性缺失,共同完成了对女性异化过程的书写:在鲁迅笔下女性异化是女性泯灭妻性后仅残留下浑茫母爱的状态;女性意识丧失到张爱玲笔下已经发展到女性双重身份的失落,女性在男权重压下妻性与母性已完全丧失。鲁迅笔下女性生存困境和张爱玲笔下女性异化三重象征共同构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女性异化写真。
_荒野的呐喊_与_苍凉的手势_鲁迅与张爱玲的美学风范比较

探求!""#年第$期(新%&期・总’#(期)・文化与教育・)摘要*鲁迅“荒野的呐喊”与张爱玲“苍凉的手势”的美学风范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悲壮美”与“苍凉美”———悲剧心理的意象背景,“黑白分明”的强烈震撼与“葱绿配桃红”的参差启迪;“含泪的笑”与“无声的哭”———“大团圆”收梢的反讽。
)关键词*鲁迅;张爱玲;悲壮美;苍凉美;比较)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彭维芳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彭维芬(’%,,—),女,文学硕士,广州市轻工业中专学校高级讲师。
“荒野的呐喊”与“苍凉的手势”/广州市轻工业中专学校,广东广州#’",#")鲁迅这颗!"世纪“中国最苦痛的灵魂”,用他冷峻、辛辣、犀利的笔,揭示国民的劣根性,给世人敲响了“人性荒凉”的警钟,呼唤美好人性的回归。
鲁迅文本体现的“荒野的呐喊”,其声凄厉、惨烈,其形孤独、虚空,其情悲愤、不甘,充满斗士的不屈,英雄的刚烈,男子汉力度的“悲壮美”。
而张爱玲的故事,所有的结局定格在“苍凉的手势”,无声无息,暗淡无光。
张爱玲认为“我不喜欢壮烈。
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
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
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
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
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张爱玲《传奇》的故事,传达出“人间无爱”、“人性荒凉”,都是以“苍凉”的结局为收梢。
如果说鲁迅以其男性的强烈对照00黑白分明的“悲壮美”为风格,那么张爱玲则以其女性的深长回味00葱绿配桃红的“苍凉美”为特色。
试论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表现方法的异同

试论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表现方法的异同论文摘要:鲁迅与张爱玲是两位享有不相同成果和影响力的作家,但在小说创造范畴里他们存在着值得剖析的类似的创造宗旨或艺术办法:鲁迅站在启蒙主义视点对全体国民性加以提醒,张爱玲以启示的小说观对俗人脆弱性加以展现;鲁迅凝聚了本身的魂灵与情感却镇定地在一般人事里寻觅悲痛,张爱玲以凄凉的自个生命体会不露神色地叙说一般人的故事;鲁迅将承继传统与突破传一致致,张爱玲将中国传统与现代前锋联系;鲁迅用终身失望的抵挡影响着每一代人,张爱玲在尘俗生活中寻觅永世的意味,影响力有年代特点。
论文关键字:鲁迅张爱玲国民劣根性俗人脆弱性镇定传统现代影响力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到目前为止的最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
于青则在《张爱玲传略》里说:“若是说,鲁迅终身致力于国民性的批评,是对民族文明心思建构的一个奉献,那么,张爱玲对女性认识里‘女性原罪’认识的展露和批评,则是张爱玲对民族文明心思建构的一个弥补,是对女性认识进化和开展的一个奉献。
”咱们发现张爱玲与鲁迅在小说创造上好像的确存在着某种相关,招引着研讨者不自觉地将二人放在一同加以论说。
这篇文章试从四个方面,从二人的创造思路与表现办法上发现这两位不相同成果、不相同影响力的作家在小说创造范畴里的某些异同之处。
一、鲁迅:“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小说观与对中国全体国民劣根性的露出。
张爱玲:“给予周围的实际一个启示”的小说观与对脆弱的俗人低微生命与凄凉情感的展现张定磺说过这样一段话:“鲁迅先生站在路周围,看见咱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往来不断,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动。
从咱们的双眼,相貌,举动上,从咱们的全身上,他看出咱们的冥顽,卑鄙,丑陋和饥饿。
”但鲁迅绝不是逗留于鉴赏,而是要发掘他看到的全体中国人、中华民族病态的本源,找到彻底治好的良方。
他用那只贱卖的“金不换”做东西,成了手术台上的外科医师,他在显微镜下看清血淋淋的病变安排,并将它切除。
从呐喊到流言——鲁迅与张爱玲相同点之比较

维普资讯
国文化革命 的主将。他 不但是伟 大的文学家 , 而 且是伟刁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 家。鲁迅的骨头 是最硬的, 他没有丝毫的奴颜 和媚骨 , 这是殖 民地
之 处 ?从表 面 上 看 , 位 作 家 相 距 3 两 0年 , 张爱 玲
又不像当时其他女作家那样追 随鲁迅 , 她脱离 了 “ 五四” 新文学运动 的光照 和影 响 , 追求个人真实
学 的认 同 , 以至 于在解 放后 被 排 斥 在文 学 史之 外 。 这两 位作 家 因为 走 上 文 学 道 路 的境 遇 不 同 , 被 都
从 13 年毛泽东发表《 98 论鲁迅》 4 到 0年代初 发表《 民主主义论》 《 新 、反对党八股》 毛泽东尊鲁 ,
方向。 毛泽东的这个评价是经典性 的, ” 这就是著 名的“ 三个家” 五个最” 和“ 。很 显然 , 毛泽东是把 鲁迅作为中华 民族的精神领袖来定位的。
则“ 我以我血荐轩辕 ”东渡扶桑 , 医学救 国。而后 弃医从文 , 以文艺唤起愚弱国民的觉醒 , 发出了 自 己独特 的“ 呐喊” 。鲁迅成 了左翼 文 艺运动 的领 袖 。而张爱玲是在“ 低气 压” 的环境里 , 在上海沦 陷区狭窄的圈子里一炮走红 , 低气压”的环境 给“ 带来了一片亮色。一场震撼 民族 的解放战争在小 说中没有得到很好 的反映 , 这个身 陷孤 岛的女作 家发出了 自己内心 的对人性 、 对情欲世界 的深刻 解剖 。也正因此 , 张爱玲 的作品没有得到 主流文
伟大的寻求者 ; 于青指出鲁迅毕生致力于 国民性 的批判 , 是对民族 文化心理建构 的一个贡献。张 爱玲 对 女 性 意 识 里 “ 性 原 罪 ” 识 的 展 露 和 批 女 意 判, 则是张爱玲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补充 , 是对女性意识的进 化和发展的~个贡献; 费勇则 认为鲁迅是一位 能够承担伟大两字的作家 , 张爱 玲则是一位创造 了一种独特风格 的优秀作 家 , 在
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艺术之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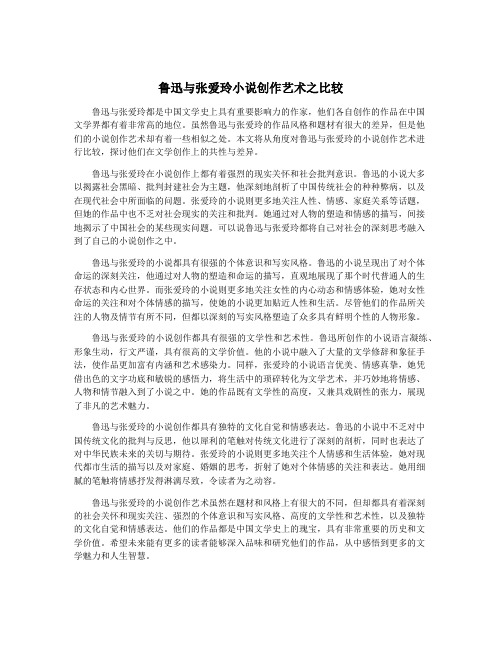
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艺术之比较鲁迅与张爱玲都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家,他们各自创作的作品在中国文学界都有着非常高的地位。
虽然鲁迅与张爱玲的作品风格和题材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们的小说创作艺术却有着一些相似之处。
本文将从角度对鲁迅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艺术进行比较,探讨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共性与差异。
鲁迅与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上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社会批判意识。
鲁迅的小说大多以揭露社会黑暗、批判封建社会为主题,他深刻地剖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种种弊病,以及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问题。
张爱玲的小说则更多地关注人性、情感、家庭关系等话题,但她的作品中也不乏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
她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和情感的描写,间接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某些现实问题。
可以说鲁迅与张爱玲都将自己对社会的深刻思考融入到了自己的小说创作之中。
鲁迅与张爱玲的小说都具有很强的个体意识和写实风格。
鲁迅的小说呈现出了对个体命运的深刻关注,他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和命运的描写,直观地展现了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
而张爱玲的小说则更多地关注女性的内心动态和情感体验,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对个体情感的描写,使她的小说更加贴近人性和生活。
尽管他们的作品所关注的人物及情节有所不同,但都以深刻的写实风格塑造了众多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
鲁迅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都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和艺术性。
鲁迅所创作的小说语言凝练、形象生动,行文严谨,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他的小说中融入了大量的文学修辞和象征手法,使作品更加富有内涵和艺术感染力。
同样,张爱玲的小说语言优美、情感真挚,她凭借出色的文字功底和敏锐的感悟力,将生活中的琐碎转化为文学艺术,并巧妙地将情感、人物和情节融入到了小说之中。
她的作品既有文学性的高度,又兼具戏剧性的张力,展现了非凡的艺术魅力。
鲁迅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都具有独特的文化自觉和情感表达。
鲁迅的小说中不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他以犀利的笔触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华民族未来的关切与期待。
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艺术之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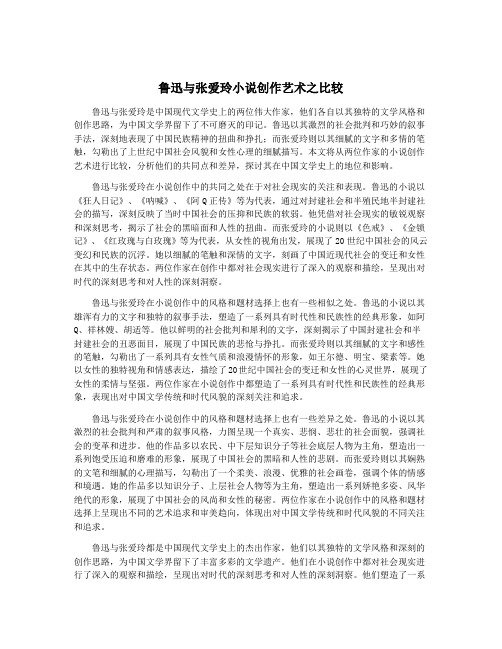
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艺术之比较鲁迅与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伟大作家,他们各自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和创作思路,为中国文学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鲁迅以其激烈的社会批判和巧妙的叙事手法,深刻地表现了中国民族精神的扭曲和挣扎;而张爱玲则以其细腻的文字和多情的笔触,勾勒出了上世纪中国社会风貌和女性心理的细腻描写。
本文将从两位作家的小说创作艺术进行比较,分析他们的共同点和差异,探讨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鲁迅与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中的共同之处在于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表现。
鲁迅的小说以《狂人日记》、《呐喊》、《阿Q正传》等为代表,通过对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描写,深刻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压抑和民族的软弱。
他凭借对社会现实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思考,揭示了社会的黑暗面和人性的扭曲。
而张爱玲的小说则以《色戒》、《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为代表,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展现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和民族的沉浮。
她以细腻的笔触和深情的文字,刻画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迁和女性在其中的生存状态。
两位作家在创作中都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描绘,呈现出对时代的深刻思考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鲁迅与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中的风格和题材选择上也有一些相似之处。
鲁迅的小说以其雄浑有力的文字和独特的叙事手法,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经典形象,如阿Q、祥林嫂、胡适等。
他以鲜明的社会批判和犀利的文字,深刻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和半封建社会的丑恶面目,展现了中国民族的悲怆与挣扎。
而张爱玲则以其细腻的文字和感性的笔触,勾勒出了一系列具有女性气质和浪漫情怀的形象,如王尔德、明宝、梁素等。
她以女性的独特视角和情感表达,描绘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女性的心灵世界,展现了女性的柔情与坚强。
两位作家在小说创作中都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经典形象,表现出对中国文学传统和时代风貌的深刻关注和追求。
鲁迅与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中的风格和题材选择上也有一些差异之处。
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艺术之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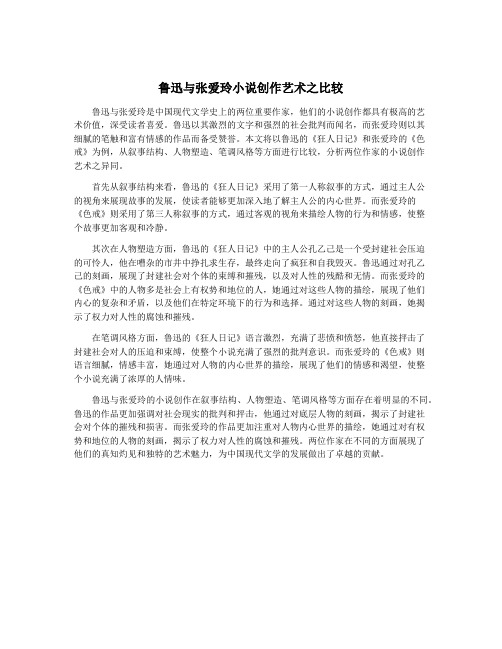
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艺术之比较鲁迅与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重要作家,他们的小说创作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深受读者喜爱。
鲁迅以其激烈的文字和强烈的社会批判而闻名,而张爱玲则以其细腻的笔触和富有情感的作品而备受赞誉。
本文将以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张爱玲的《色戒》为例,从叙事结构、人物塑造、笔调风格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两位作家的小说创作艺术之异同。
首先从叙事结构来看,鲁迅的《狂人日记》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通过主人公的视角来展现故事的发展,使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而张爱玲的《色戒》则采用了第三人称叙事的方式,通过客观的视角来描绘人物的行为和情感,使整个故事更加客观和冷静。
其次在人物塑造方面,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孔乙己是一个受封建社会压迫的可怜人,他在嘈杂的市井中挣扎求生存,最终走向了疯狂和自我毁灭。
鲁迅通过对孔乙己的刻画,展现了封建社会对个体的束缚和摧残,以及对人性的残酷和无情。
而张爱玲的《色戒》中的人物多是社会上有权势和地位的人,她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描绘,展现了他们内心的复杂和矛盾,以及他们在特定环境下的行为和选择。
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刻画,她揭示了权力对人性的腐蚀和摧残。
在笔调风格方面,鲁迅的《狂人日记》语言激烈,充满了悲愤和愤怒,他直接抨击了封建社会对人的压迫和束缚,使整个小说充满了强烈的批判意识。
而张爱玲的《色戒》则语言细腻,情感丰富,她通过对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描绘,展现了他们的情感和渴望,使整个小说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
鲁迅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笔调风格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鲁迅的作品更加强调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抨击,他通过对底层人物的刻画,揭示了封建社会对个体的摧残和损害。
而张爱玲的作品更加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绘,她通过对有权势和地位的人物的刻画,揭示了权力对人性的腐蚀和摧残。
两位作家在不同的方面展现了他们的真知灼见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艺术之比较

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艺术之比较鲁迅与张爱玲是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家,他们各自以独特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手法,产生了许多经典小说作品。
鲁迅的作品以其激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思想性著称,而张爱玲则以其细腻的笔触和对情感的深刻探索而闻名。
本文将对两位作家的小说创作艺术进行比较,探讨他们的共同之处和差异之处,以期能更加全面地理解他们各自独特的艺术魅力。
鲁迅与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中所表现的现实与意象的处理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鲁迅的小说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他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观察和批判,呈现了一幅幅残酷的人间画卷。
《鲁迅全集》中的《狂人日记》、《呐喊》、《阿Q正传》等作品,都以鲜明的现实主义笔触揭示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倒退。
而张爱玲的小说则更多地体现了她对情感和个人命运的追求和表达。
她通过细腻的笔触和独特的心理描写,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强烈内心冲突和情感挣扎的形象,将女性的柔弱和坚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张爱玲全集》中的《色戒》、《倾城之恋》等作品,无一不展现了张爱玲对情感的敏锐洞察和对人性的深刻触摸。
鲁迅与张爱玲在人物形象刻画、叙事结构和语言表达方式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鲁迅的小说以其深刻的思想渗透和对社会现实的犀利揭露而著称,他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对故事情节的安排,将社会的丑恶和人性的扭曲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张爱玲则更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绘和情感的表达,在她的小说中,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人物内心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
张爱玲的语言表达也更加细腻和优美,她善于运用比喻、隐喻和象征等修辞手法,使作品充满了诗意和韵味。
尽管鲁迅与张爱玲在小说创作艺术上存在诸多差异,但他们的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人文关怀。
鲁迅的小说是对中国封建传统和国民性格的深刻批判,他以犀利的笔触和激烈的语言,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病和人性的丑恶。
而张爱玲的小说则更多地体现了她对个人命运和情感的深刻关注,她以细腻的笔触和柔软的语言,展现了人性的柔情和深情。
乡村与城市的灵魂书写——鲁迅与张爱玲的小说比较分析

乡村与城市的灵魂书写——鲁迅与张爱玲的小说比较分析鲁迅与张爱玲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对他们进行比较,可以有很多切入的角度,这里我且从他们描写的场景来看。
鲁迅在为所不多的小说中,主要描写了农民和知识分子两类形象,他几乎没有书写城市,而是专著于农村。
鲁迅在开始《狂人日记》写作的时候,他正身处北京,此前,他从1898年离开绍兴,前往南京求学十年,后来又在日本留学七年,回国后,又先后在杭州,南京和北京等城市居住。
鲁迅当然是有城市生活和体验的。
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农村书写,这自然是和他的文学观念有关的。
他从一开始就思考国民性的揭示,而农民无疑是国民的主体,是最能体现国民性的。
鲁迅并非不熟悉小市民和新知识分子,但是他更愿意书写作为几千年奴性文化载体的农民和旧知识分子,去书写他们灵魂的创伤,试图捣毁铁屋子,因而奋力呐喊,虽然终于不免失望,于是在生与死,新与旧之间彷徨,而终于还是没有沉沦,而是一直反抗绝望。
张爱玲则是一直专注于对城市的书写,虽然后来也写了农村题材的《秧歌》和《赤地之恋》,但是显然没有对于城市的描写那样得心应手。
童年和求学的经历,特殊的家庭和亲历战争的特殊境遇,使得张爱玲的绝大多数小说描写的都是“双城记”。
她最熟悉的是身边的这些都市男女,在乱世中的各色表演。
战争背景下的都市,不是像古老的乡村那样宁静甚至凝固,而是如跳着踢踏舞一样快速旋转,人性的自私贪婪,及时作乐,醉生梦死也和乡村完全不同。
鲁迅是习惯用解剖刀去剖开仁义礼智信厚厚的屏障下的深层次的痛苦,于是有闰土的麻木,祥林搜的绝望,吕纬甫和魏连殳的忧伤,他们失去乡土,无枝可依,因而注定绝望。
而张爱玲则不如鲁迅这样忧愤深广,她让笔下的人物穿上华丽的衣袍,展示世纪末的华丽,但是那衣袍上却爬满了虱子,这华丽毕竟是转瞬即逝,是没有灵魂的空壳,于是有曹七巧的冷酷与空虚,白流苏的费尽心机的得到与失落。
鲁迅是试图立人,他要让笔下的人物明白没有灵魂的生命是算不上人的,但是终于知道这种努力的徒劳。
鲁迅和张爱玲的女权思想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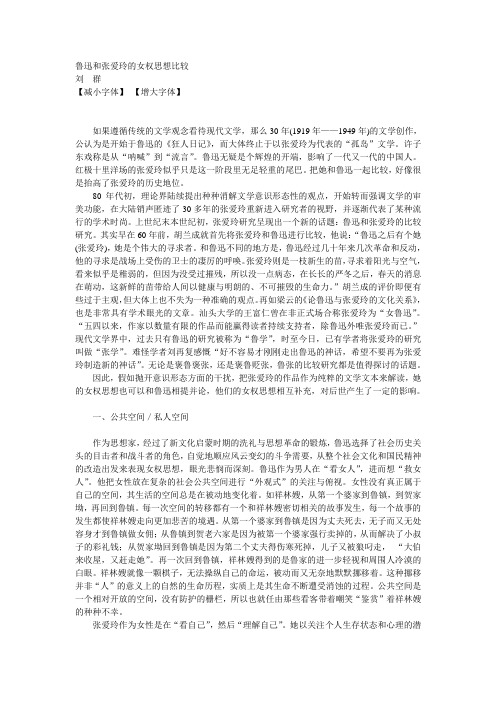
鲁迅和张爱玲的女权思想比较刘群【减小字体】【增大字体】如果遵循传统的文学观念看待现代文学,那么30年(1919年——1949年)的文学创作,公认为是开始于鲁迅的《狂人日记》,而大体终止于以张爱玲为代表的“孤岛”文学。
许子东戏称是从“呐喊”到“流言”。
鲁迅无疑是个辉煌的开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红极十里洋场的张爱玲似乎只是这一阶段里无足轻重的尾巴。
把她和鲁迅一起比较,好像很是抬高了张爱玲的历史地位。
80年代初,理论界陆续提出种种消解文学意识形态性的观点,开始转而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在大陆销声匿迹了30多年的张爱玲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逐渐代表了某种流行的学术时尚。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张爱玲研究呈现出一个新的话题:鲁迅和张爱玲的比较研究。
其实早在60年前,胡兰成就首先将张爱玲和鲁迅进行比较,他说:“鲁迅之后有个她(张爱玲),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
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受伤的卫士的凄厉的呼唤。
张爱玲则是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受过摧残,所以没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人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
”胡兰成的评价即便有些过于主观,但大体上也不失为一种准确的观点。
再如梁云的《论鲁迅与张爱玲的文化关系》,也是非常具有学术眼光的文章。
汕头大学的王富仁曾在非正式场合称张爱玲为“女鲁迅”。
“五四以来,作家以数量有限的作品而能赢得读者持续支持者,除鲁迅外唯张爱玲而已。
”现代文学界中,过去只有鲁迅的研究被称为“鲁学”,时至今日,已有学者将张爱玲的研究叫做“张学”。
难怪学者刘再复感慨“好不容易才刚刚走出鲁迅的神话,希望不要再为张爱玲制造新的神话”。
无论是褒鲁褒张,还是褒鲁贬张,鲁张的比较研究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因此,假如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干扰,把张爱玲的作品作为纯粹的文学文本来解读,她的女权思想也可以和鲁迅相提并论,他们的女权思想相互补充,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讽刺意味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论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讽刺意味李美慧 鞍山师范学院摘 要:鲁迅和张爱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唤醒民族意识和人性命运的一代作家,作为时代背景下的男性与女性的领军人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他们都挖掘深层次的民族现象,超越了文学作品的表象,运用一种独特的反讽艺术反映时代背景下受道德伦理束缚的广大中国民众的生活辛酸史,力求人们精神世界的转变,追求民族的觉醒与人性的解放。
一定的文学作品反映的是时代的产物,文学现象不仅展示作家的“显意识”,也反映了作家的“潜意识”,更反映了民族意识和人类命运的悲剧性。
关键词:反讽艺术;民族劣根性;女性意识;人性解放;悲剧意味[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40-01鲁迅在其文学创作中展现了众多带有国民劣根性的麻木的劳苦大众,他以现代幽默反讽为武器,揭露并抨击了时代背景下“吃人”的现象,以及对麻木腐朽愚昧的中国同胞的痛惜之情。
继鲁迅之后,张爱玲是一位以人性觉醒为目的的女性作家,超越了性别的差异,从女性的视角展现20世纪40年代国家、民族的衰败与人性的苍凉,她以尖锐的笔触讽刺了现代都市中人性的泯灭、扭曲以及变态心理带来的人性命运的悲剧。
1、讽刺笔法下的“人吃人”的社会现象鲁迅的文学作品中小说的讽刺意味尤为突出,他的《狂人日记》是一篇讽刺意味十足的战斗性文章,他所呈现的是一个“迫害狂”眼中的中国现状——用伦理道德来迫害人的生命。
它所侵蚀的是不仅是广大的民众,而且还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灵魂与精神。
卑微、无地位的阿Q,是一个具有欺软怕硬、以丑为美的典型形象,他是当时社会最底层民众的真实写照,作者塑造的这个形象是对社会制度的嘲讽,并寄希于民族劣根性的唤醒。
鲁迅暴露的是民族的劣根性,所讽喻的是整个封建社会,他使用辛辣讽刺的手法意在触动中国民众麻木不仁的精神世界。
但这种用笔触来治疗病态已久的精神世界 ,在某种程度上是慢性的,甚至是无效的。
鲁迅和张爱玲人性悲剧作品的异同

“ 个性” 例如 《 Q正传 》中的 “ , 阿 阿 Q 、《 ” 孔乙己》中的 “ 孔乙己” 《 、 祝 福》中的 “ 祥林嫂”等来表现现实中的
农民、知识分子、 妇女的悲剧性乃至整
了“ 救救孩子”的呼声 , 《 在 故乡》 里。
他写到. “ 这世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 j 也便成了 , 路……”矛盾在 12 年发 92 表的 《 ( 一文中说: “ 读 呐喊 》 当时亦 未必发生 r 如何明确的印象 ,只觉得受 到一种痛苦的刺激 ,犹如久处黑暗的人 骤然看到了 耀眼的阳光。 我想正是这束 ” “ 阳光”更清楚地衬托出封建家族制度下 的无边黑暗 ,这束 “ 阳光”便来 自于
目中所经历的社会和人生。 “ 早上小心
大的 不同。 鲁迅作品题材较广,视 野开 阔。 从题材的角度看 , 鲁迅的人性悲剧 作品可以分为四类,1 . 知识分 子的悲剧。 例如, 《F 日 、 《 彳人 记》 孔乙己》 伤 、《
那正常表象下传统文化吃人的本质。在 《 》 药 里, 人们争先恐后地去看革命者夏
鲁迅和张爱玲人-悲剧作品的异同 t I :
◆ 曾海燕
在中同 现代文学史 k .鲁迅和张爱 玲, 无论从哪方面看, 都是相差很大的 两位作家。这是众所周知的。 但近年来 , 却不断有人把两位作家放在一起比较。 北师大教授王复仁说: “ 在现代作家里 面,只有张爱玲可以与鲁迅媲美。 ”我以 为如果一定要作比较, 那么这主要是指 他们作品中彻底、残酷的悲观精神和对 人性扭曲、异化的沉痛刻画而言的。 可 以这样说,在现代文学史上, 他们的作
到农民、知识分子、 旧民主主义革命者、
出门. 赵贵翁的眼色便怪:是乎 i我, l f 是乎想害我 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
“ 吃人”的意象写得惊心动魄 、 毛骨悚
试论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思路与表现方法的异同

论文摘要:鲁迅与张爱玲是两位享有不同成就和影响力的作家,但在小说创作领域里他们存在着值得分析的类似的创作主旨或艺术手法:鲁迅站在启蒙主义角度对整体国民性加以揭示,张爱玲以启示的小说观对凡人软弱性加以展示;鲁迅凝聚了自身的灵魂与情感却冷静地在普通人事里寻找悲哀,张爱玲以苍凉的个人生命体验不露声色地讲述普通人的故事;鲁迅将继承传统与冲破传统统一,张爱玲将中国传统与现代先锋结合;鲁迅用一生绝望的抗争影响着每一代人,张爱玲在世俗生活中寻找永恒的意味,影响力有时代特点。
论文关键词:鲁迅张爱玲国民劣根性凡人软弱性冷静传统现代影响力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
于青则在《张爱玲传略》里说:“如果说,鲁迅毕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是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贡献,那么,张爱玲对女性意识里‘女性原罪’意识的展露和批判,则是张爱玲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补充,是对女性意识进化和发展的一个贡献。
”我们发现张爱玲与鲁迅在小说创作上似乎确实存在着某种关联,吸引着研究者不自觉地将二人放在一起加以论述。
本文试从四个方面,从二人的创作思路与表现方法上发现这两位不同成就、不同影响力的作家在小说创作领域里的某些异同之处。
一、鲁迅:“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小说观与对中国整体国民劣根性的暴露。
张爱玲:“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的小说观与对软弱的凡人卑微生命与苍凉情感的展示张定磺说过这样一段话:“鲁迅先生站在路旁边,看见我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来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动。
从我们的眼睛,面貌,举动上,从我们的全身上,他看出我们的冥顽,卑劣,丑恶和饥饿。
”但鲁迅绝不是停留于鉴赏,而是要挖掘他看到的整体中国人、中华民族病态的根源,找到根治的良方。
他用那只廉价的“金不换”做工具,成了手术台上的外科医生,他在显微镜下看清血淋淋的病变组织,并将它切除。
“男狂人”与“女疯子”--鲁迅《狂人日记》与张爱玲《金锁记》比较研究

鲁迅的《狂人日记》被公认为白话文学的开山之 作,而张爱玲的《金锁记》也被盛誉为“中国自古以来 最伟大的中篇小说。”[1]261尽管 《狂人日记》与 《金锁 记》都可以简约概括为“疯癫”的故事,然而由于两位 作者的性别不同、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作者落 笔时怀揣 的 用 意 不 同,鲜 有 学 者 将 他 们 进 行 比 较 解 读。从性别差异的角度来说,鲁迅开创了中国现代文 学中首个“男狂人”写作,而张爱玲则创造了一个极其 具有典型意义的“女疯子”形象;由于作品产生的时代 背景不同,鲁迅选择了较为开放的时间形式,张爱玲 则采用了较为闭锁的时间形式;就两位作家的思想资 源、生命经验以及创作文本时可能怀揣的小说预设来 说,《狂人日记》倾向于寻找“真的人”,而《金锁记》则 倾向于寻找“真的心”。
鲁迅小说不如张爱玲小说

2008年3月 理论学刊 Ma r.2008第3期 总第169期 T h e o r yJ o u r n a l N o.3S e r.N o.169鲁迅小说不如张爱玲小说吗?高旭东(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北京100083) 〔摘 要〕在美国的汉学界,从夏志清到王德威,都认为张爱玲是比鲁迅更为优秀的、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
本文通过对鲁迅与张爱玲小说的比较,尤其通过对夏志清有关鲁迅小说艺术批评的再审视,得出结论:张爱玲与鲁迅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作家,也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将张爱玲与鲁迅相提并论甚至以为前者创作成就超过后者,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伪命题。
〔关键词〕鲁迅;张爱玲;小说;成就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8)03-0113-05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张爱玲在中国大陆几乎已经被遗忘了。
20世纪60年代,由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爱玲的过分推崇,这个名字才又被人瞩目。
如果说,夏志清对张爱玲的推崇体现了一种矫枉过正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中国大陆频频出现张爱玲热、而鲁迅反而经常被人贬低,甚至在美国学界执中国文学研究之牛耳的王德威教授视张爱玲为超过鲁迅的现代最优秀的小说家,就不能不使人们困惑了。
笔者不禁要问:鲁迅小说真的不如张爱玲的小说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对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进行必要的学术清理。
一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可以说见解独到,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
这部小说史自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之后,既影响了国内学界对张爱玲、钱钟书等人的评价,也影响了对鲁迅小说在文学史上历史定位的重新审视。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张爱玲的专章在篇幅上有鲁迅专章的近一倍。
一个作家重要不重要,与讨论他的篇幅当然有关系,比如说写中国诗歌史,给王勃、张若虚的篇幅超过了李白和杜甫,就说明这个诗歌史明显是贬低了李白与杜甫。
绝望与反抗绝望——论张爱玲与鲁迅小说的异质性

因,即在 于二 者所持的不 同人 生哲 学:张爱玲是 绝望 ,鲁迅却是反抗 沉 重 的枷 角 劈 杀 了几 个 人 ,没 死 的 也 送 了 半 条 命 。她 知 道 她 儿
绝 望 。这 直接 源 于 两位 作 家不 同的 人 生 际遇 、 生存 环 境 和 不 同的 文 化 子 女 儿恨 毒 了她 ,她 婆 家 的人 恨她 ,她 娘 家 的人 恨 她 。 ”小说 的 选择 。
・
文 艺评 论 ・
大 众 文 艺
绝望 与反抗绝望
论张爱玲与鲁迅小说的异质性
卢志 娟 ( 包头 师 范学 院 文学 院 0 1 4 0 3 0 )
摘要 : 2 0 世 纪9 0 年代 以来,常有学者将 张爱玲与鲁迅相提并论 ,
雷就 说过 《 金锁 记 》 中 “ 有 《 狂人 日记 》 中某些 故 事 的风 味 ” 。
认 为她 对人性之 恶的揭露延续 了鲁迅 的 “ 国民性改造”的思索。读他 和 鲁 迅一 样 , 张爱 玲经 常 为其 笔 下 的人物 设 置一 个 又一 个 无法 逃 们 的 小说 会 时 时 感 受 到 黑 暗 、 虚 无 与 绝 望 。但 鲁迅 的 小说 充 满 战 斗 的 脱 的悲剧 结局 ,在 《 金 锁记 》 中 ,曹 七 巧3 0 年来 戴 着黄 金 的枷 , 激情 和力 量 ,张 爱玲 的小说 更多的却是 “ 沉 下去 ”的压抑 ,究其原 她 是 可悲 的 “ 被 吃者 ”, 同时 又是 可 怕 的 “ 吃人 者 ” , “ 她 用 那
着 “ 张 爱玲 热 ”的再 度升 温 ,张 爱玲 的文 学地 位也 越 升越 高 ,动 的苍凉 的 故事 ”中 的一个 ,是 战争 成全 了这对 自私 男女 的婚 姻 ,
辄 被 人和 鲁迅 相提 并 论 。于 青在 《 张爱 玲 传 》 中说 : “ 如果 说 , 谁 也 别指 望什 么 “ 死 生 契 阔 ,与子 成 悦 ,执 子之 手 ,与 子偕 老 ” 鲁 迅 毕生 致 力于 国 民性 的批 判 ,是 对 民族 文化 心 理建 构 的一 个 贡 的天 长地 久 ,仍 然 是冷 彻 心扉 的 绝望 … …从 这个 角 度来 看 , 张爱 献 :那 么 ,张 爱 玲 对 女 性 意 识 里 ‘ 女 性 原 罪 ’意 识 的 展 露和 批 玲 小 说 中的 这种 绝 望似 乎和 2 O 年 前鲁 迅 小说 中 的绝 望遥 相 呼应 ,
论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思路与表现方法的异同

论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思路与表现方法的异同
孟昕;熊建新
【期刊名称】《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5(021)005
【摘要】鲁迅与张爱玲是两位享有不同成就和影响力的作家,但在小说创作领域里他们存在着值得分析的类似的创作主旨或艺术手法:鲁迅站在启蒙主义角度对整体国民性加以揭示,张爱玲以启示的小说观对凡人软弱性加以展示;鲁迅凝聚了自身的灵魂与情感却冷静地在普通人事里寻找悲哀,张爱玲以苍凉的个人生命体验不露声色地讲述普通人的故事;鲁迅将继承传统与冲破传统统一,张爱玲将中国传统与现代先锋结合;鲁迅用一生绝望的抗争影响着每一代人,张爱玲在世俗生活中寻找永恒的意味,影响力有时代特点.
【总页数】4页(P13-15,49)
【作者】孟昕;熊建新
【作者单位】河北北方学院中文系,河北,张家口,075000;华北煤炭医学院,河北,唐山,063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6
【相关文献】
1.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创作的异同 [J], 喻恂
2.“娜拉走后怎样”:论张爱玲以小说创作对鲁迅思想的延展 [J], 李清宇
3.承传与拓展--张爱玲王安忆都市小说创作异同之比较 [J], 邓玉莲
4.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艺术之比较 [J], 万江婷
5.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艺术比较论 [J], 杜正香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论文摘要:鲁迅与张爱玲是两位享有不同成就和影响力的作家,但在小说创作领域里他们存在着值得分析的类似的创作主旨或艺术手法:鲁迅站在启蒙主义角度对整体国民性加以揭示,张爱玲以启示的小说观对凡人软弱性加以展示;鲁迅凝聚了自身的灵魂与情感却冷静地在普通人事里寻找悲哀,张爱玲以苍凉的个人生命体验不露声色地讲述普通人的故事;鲁迅将继承传统与冲破传统统一,张爱玲将中国传统与现代先锋结合;鲁迅用一生绝望的抗争影响着每一代人,张爱玲在世俗生活中寻找永恒的意味,影响力有时代特点。
论文关键词:鲁迅张爱玲国民劣根性凡人软弱性冷静传统现代影响力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
于青则在《张爱玲传略》里说:“如果说,鲁迅毕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是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贡献,那么,张爱玲对女性意识里‘女性原罪’意识的展露和批判,则是张爱玲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补充,是对女性意识进化和发展的一个贡献。
”我们发现张爱玲与鲁迅在小说创作上似乎确实存在着某种关联,吸引着研究者不自觉地将二人放在一起加以论述。
本文试从四个方面,从二人的创作思路与表现方法上发现这两位不同成就、不同影响力的作家在小说创作领域里的某些异同之处。
一、鲁迅:“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小说观与对中国整体国民劣根性的暴露。
张爱玲:“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的小说观与对软弱的凡人卑微生命与苍凉情感的展示张定磺说过这样一段话:“鲁迅先生站在路旁边,看见我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来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动。
从我们的眼睛,面貌,举动上,从我们的全身上,他看出我们的冥顽,卑劣,丑恶和饥饿。
”但鲁迅绝不是停留于鉴赏,而是要挖掘他看到的整体中国人、中华民族病态的根源,找到根治的良方。
他用那只廉价的“金不换”做工具,成了手术台上的外科医生,他在显微镜下看清血淋淋的病变组织,并将它切除。
而张爱玲也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她却是站在都市的公寓阳台上,去窥破都市家庭内部挣扎着的女性们的人生。
从她们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看出现代社会女人们生存的艰难与灵魂深处的怅惘、悲凉与无奈。
于是她要做女性们的心理医生,用她慈悲却含而不露的方式,坐在屋里面对病人,亲切又冷静的娓娓而谈,揭露她们自身软弱、自甘堕落造成的病态,但又安慰她们活着就必然麻烦,她用启示的办法引导女人们理解、宽容、慈悲,从烦恼中危机中寻求人生永恒的意味。
她用这种方式呼唤着、渴望着女性挣脱心灵沉重的负荷,拥有自尊优美的生活。
应该说,他们都是高明的大夫,都有一样的良苦用心,但二人采取了不同的观察角度与治疗方法,挖掘着中国男男女女的病根,他们的相似点何在,取得的效果如何呢? 鲁迅有过痛苦的家庭生活经历,少年时小康家庭没落让他体验了世态的炎凉,人情的淡薄。
中年时兄弟反目让他体会了亲情带来的残酷打击。
这些经历,让他看透了所谓礼仪之国人心的势利与险恶,个体之间灵魂的隔膜与自身内心深处的矛盾困惑,再加上对历史、对现实、对世界的透彻研究,他决心要用自己所能使用的最有效方式揭示中国人的种种病态,促其自省,从而真正排除瘤疾,使中华民族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他说:“说到‘为什么做起小说罢,我仍旧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这是鲁迅创作小说的出发点,他强调‘“人”,“国民”,才是社会与国家的主体,要改造社会必须着眼于“人”的改造,要改造“人”必须从精神与个性上“立人”,而改造国民精神,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要推文艺,所以他就拿起了文艺这一精神工具去做改造国民性的工作。
所以他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纵观鲁迅全部的小说创作,他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题材,而纵笔所至又几乎囊括了中国“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人民的不幸”。
最终以他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熟悉的一张张典型的中国面孔与灵魂,如阿Q、闰土、祥林嫂等等,让我们看到了属于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疾患和由它带来的灾难。
[!--empirenews.page--] 张爱玲也有过不幸的家庭生活,没落的封建家庭,缺少无私的亲情关怀。
从成长经历里,她看到的是现代中国社会的变形,人性的自私、空虚,生存的艰难。
她愿以文学作品探询这人生的麻烦,并从中找到“永恒的意味”。
她说“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
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末。
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
”“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
而以此给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
”“女人是最普遍,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
女人把人类飞跃天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
”作为一个女人,她尤其同情于生活在男性社会里的软弱的女性们。
生存本身是艰难的,理想的爱人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感情是渺茫不可及的。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表面或和谐或圆满或华丽的背后,是“那种不明不白,狠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然而到底还是凄凉的。
”生活在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苍白、渺小,女人们更是难以摆脱内心的恐怖与荒凉。
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女性的未来如何自己掌握?她用曹七巧、白流苏、葛薇龙等女人做代表,以否定现在生态下女性的女奴角色的方式,让我们听到了她深沉的叹息,体会了她深情的渴望,引导我们思考女性如何能挣脱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诸般枷锁的栓桔,成为自在的女性优美的生存。
[1][2][3]下一页不能否认二人的理想与追求存在博大与狭小的区别。
鲁迅将最终的目的定在中华民族的觉醒与自立上,张爱玲则要给周围普通的中国人一个生活的启示。
但是,警醒“睡在铁屋子中的人”也好,怅惘周旋于无爱的家中的女人也好,二人都是伟大的寻求者,都以自己的作品成为中国人不再麻痹的一剂良药,提醒着中国的男男女女正视眼前恐怖的生活状态,寻求一条新生之路。
二、鲁迅:表层冷静地在普通平凡的人事里寻找永久的悲哀,深层却对表现对象凝聚了自身的灵魂与情感。
张爱玲:不露声色地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却流露着以个体生命体验为背景的苍凉感受张家瑛说鲁迅先生的小说里“有的只是些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你天天在屋子里街上遇见的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自己……在这个习见的世界里,在这些熟识的人们里,要找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是很难的……然而鲁迅先生告诉我们,偏是这些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事里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
鲁迅先生并没有把这个明明白白地写出来告诉我们,他不是那种人。
但这个悲哀毕竟在那里,我们都感觉到它。
”“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
”即使是《故事新编》这样的历史小说,他也让每一个历史人物以普通人的身份面貌与表现站立在我们面前,成为千千万万小老百姓其中的一员。
鲁迅在1927年冬天的一次讲演中谈到现在的文艺创作时说“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里去!”这些都让我们看到鲁迅的创作方式,他采取了很多象征的隐晦的方式,将自己似乎深深藏了起来,但每一篇作品都可以看到背后立着的一个优患又痛苦的鲁迅的灵魂。
他从不将自己置身事外,而是参与着每一场对灵魂的审问与对病体的剖析。
《孤独者》、《在酒楼上》可以看到鲁迅灵魂深处的矛盾体在对话;《伤逝》中涓生的软弱、自私、绝望何尝不是来自鲁迅内心的叹息; 《铸剑》中冷峻的黑色人宴之敖者身上闪烁的正是鲁迅那颗高贵的反抗一切的心灵光辉。
正因为如此,鲁迅的小说如同一面具有魔力的镜子,那么有说服力地照见了历史的虚空,照见了社会的污浊,照见了国人的病变。
[!--empirenews.page--] 张爱玲说:“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
于是她冷静讲述一个个女性的故事,不用苦口婆心的说教,不用摇旗呐喊,不用哭诉愤怒,却让这“普通人中的传奇,传奇中的普通人”缓缓地流进读者心中,冲击着他们内心深处柔软的灵魂。
她似乎只是欣赏人生的舞台上表演的戏剧的观众,如此冷峻、不露声色。
她说:“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
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沉香屑—第一炉香》她又说:“胡琴晰晰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倾城之恋》她看透了人生的虚妄,也理解女性短暂的一生挣脱不了的时代、历史、生理与心理的种种束缚。
她叹息于艰难生存中的女性的妥协、苍白、畸形的追求,但是,透过那不和谐处,我们依然能领悟着张爱玲来自自身生存体验的深挚的同情与慈悲,因为那里流露的是以个体生命体验为背景的苍凉感,那也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夏志清教授早就精辟地指出:对于张爱玲,“人生的愚妄是她的题材,可是她对于一般人正当的要求(适当限度内的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宽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赞同的。
这种态度使得她的小说的内容更为丰富。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是在男人世界里索求微薄报酬的女奴,但是,这可悲可叹的故事,却穿透了历史甚至穿越了今天与明天,照见女性几千年来难以治愈的生命之伤。
在这一点上,二人有着同样的良苦用心,也取得了艺术的坚实力度,他们的作品因此而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烟消云散,而以它无穷的后劲影响着一代代读者与文学的发展。
上一页[1][2][3]下一页三、誉迅:继承发展了白.描等古典文学优良传统,成功运用象征主义等现代创作方法。
张爱玲,搜长故事的叙述等传统叙述手法,自如运用精神分析法等现代创作方法鲁迅的小说继承并发展了古典文学中的白描手法,人物形象与场景描写简炼干脆又韵味十足,这深得中国传统的审美趣味。
《故乡》中闰土的肖像,《祝福》中祥林嫂“间或一轮”的眼神,都很逼真传神。
但是,他在分析人物灵魂与揭示社会病态时,又常常采取象征主义、精神分析学等西方现代主义的各种手一法,将表层平静生活,表面伦理道德背后的恶浊不堪细腻深刻地展示给人们。
《狂人日记》《长明灯》《在酒楼上》等是象征主义成功运用的典范,《肥皂》《兄弟》《补天》等可看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被鲁迅合理地接纳和吸收。
鲁迅自己说:“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