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的优雅
《刺猬的优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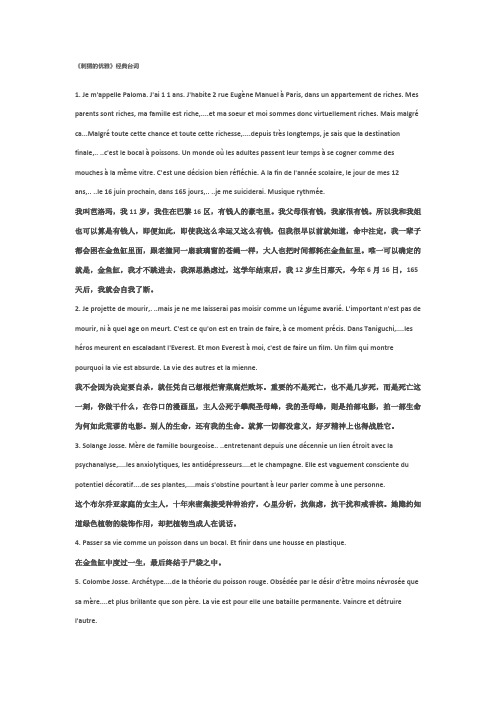
《刺猬的优雅》经典台词1. Je m'appelle Paloma. J'ai 1 1 ans. J'habite 2 rue Eugène Manuel à Paris, dans un appartement de riches. Mes parents sont riches, ma famille est riche,....et ma soeur et moi sommes donc virtuellement riches. Mais malgré ca...Malgré toute cette chance et toute cette richesse,....depuis très longtemps, je sais que la destination finale,.. ..c'est le bocal à poissons. Un monde où les adultes passent leur temps à se cogner comme des mouches à la même vitre. C'est une décision bien réfléchie. A la fin de l'année scolaire, le jour de mes 12 ans,.. ..le 16 juin prochain, dans 165 jours,.. ..je me suiciderai. Musique rythmée.我叫芭洛玛,我11岁,我住在巴黎16区,有钱人的豪宅里。
我父母很有钱,我家很有钱。
所以我和我姐也可以算是有钱人,即便如此,即使我这么幸运又这么有钱,但我很早以前就知道,命中注定,我一辈子都会困在金鱼缸里面,跟老撞同一扇玻璃窗的苍蝇一样,大人也把时间都耗在金鱼缸里。
法国女作家妙莉叶·芭贝里的小说《刺猬的优雅》的名言名句摘抄(23条)

法国⼥作家妙莉叶·芭贝⾥的⼩说《刺猬的优雅》的名⾔名句摘抄(23条)1、我相信这世上⼀定有⼀个能感受到⾃⼰的⼈,那⼈未必是恋⼈,他可能是任何⼈。
2、我们都是孤独的刺猬,只有频率相同的⼈,才能看见彼此内⼼深处不为⼈知的优雅。
3、重要的不是死亡,⽽是死亡的那⼀刻你在做什么。
4、性喜孤独,优雅的⽆以复加。
5、我们从来都是局限在⾃⼰根深蒂固的感知之中,却不能放眼看周遭的世界。
6、⼈们总梦想上天摘星,结局却和鱼缸⾥的⾦鱼⼀样。
我觉得从⼀开始就让孩⼦明⽩⼈⽣是荒谬的,事情就简单多了。
7、好些⼈不能从思考中去了解是什么能让事物拥有内在的⽣命和⽓息,⽽是把⼀⽣的时间都花在讨论⼈和物。
8、⼈们相信追逐繁星会有回报,最终却像鱼缸⾥的⾦鱼⼀般了结残⽣。
9、我们⽆法停住欲望的脚步,它赞美了我们,也谋杀了我们。
欲望!它承载了我们,也折磨了我们。
10、聪明头脑能使成功的滋味变得苦涩,⽽平庸才会让⼈⽣充满希望。
11、我们何必要在虚⽆飘渺的苍穹之中去寻找永恒呢?12、某些事情必须结束,某些事情必须开始。
13、我们规划⾃⼰的⼀⽣为的是让⾃⼰相信不存在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不想遭受苦难的⽣物。
14、播种欲望的⼈必会受到压迫。
15、成年⼈总是对死亡歇斯底⾥,把它看作是什么天⼤的事情⼀样,其实死亡是世界上最平凡的⼀件事情。
16、伟⼤的作品是⼀种直观的形式,⽽这种形式在我们⼼中产⽣了⼀种超越时间的恰当感。
17、如果你想拯救⾃⼰,还是先拯救别⼈吧,微笑或哭泣,这是命运180⼤转变。
18、⾯对曾经,该做什么,如果不在隐藏的⾳符中,追寻永远。
19、如果你想让⽣命浪费得再快⼀些,对别⼈的话漫不经⼼的程度再深⼀些,那就照看植物吧。
20、对于在欲求中迷失的⼈们来说,只要满⾜他们的基本需求即可。
21、也许吧,活着,就是要随时追捕那转瞬即逝的⽚刻时光。
22、⼀个如此否认⾃⼰⾝上善良⼀⾯的男⼈,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仿佛是⼀具⼫体了。
23、真正的坏⼈,毫⽆疑问,他们厌恶所有⼈,尤其厌恶的是他们⾃⼰。
《刺猬的优雅》影评6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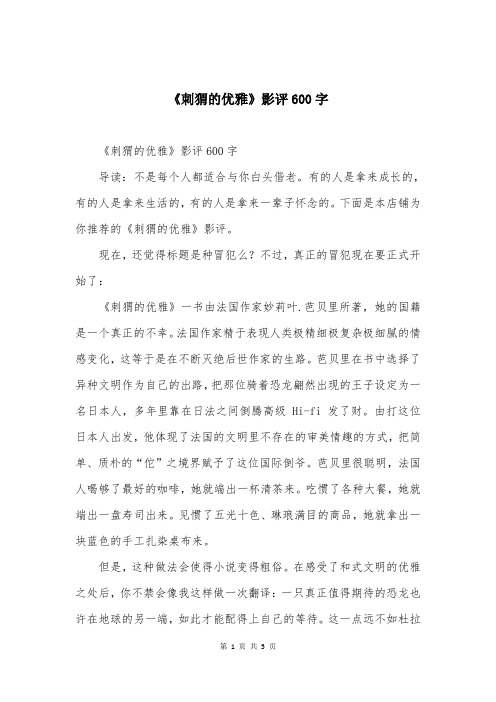
《刺猬的优雅》影评600字《刺猬的优雅》影评600字导读: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与你白头偕老。
有的人是拿来成长的,有的人是拿来生活的,有的人是拿来一辈子怀念的。
下面是本店铺为你推荐的《刺猬的优雅》影评。
现在,还觉得标题是种冒犯么?不过,真正的冒犯现在要正式开始了:《刺猬的优雅》一书由法国作家妙莉叶.芭贝里所著,她的国籍是一个真正的不幸。
法国作家精于表现人类极精细极复杂极细腻的情感变化,这等于是在不断灭绝后世作家的生路。
芭贝里在书中选择了异种文明作为自己的出路,把那位骑着恐龙翩然出现的王子设定为一名日本人,多年里靠在日法之间倒腾高级Hi-fi 发了财。
由打这位日本人出发,他体现了法国的文明里不存在的审美情趣的方式,把简单、质朴的“佗”之境界赋予了这位国际倒爷。
芭贝里很聪明,法国人喝够了最好的咖啡,她就端出一杯清茶来。
吃惯了各种大餐,她就端出一盘寿司出来。
见惯了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商品,她就拿出一块蓝色的手工扎染桌布来。
但是,这种做法会使得小说变得粗俗。
在感受了和式文明的优雅之处后,你不禁会像我这样做一次翻译:一只真正值得期待的恐龙也许在地球的另一端,如此才能配得上自己的等待。
这一点远不如杜拉斯的坦诚,《情人》里她并不讳言她爱的是中国情人带来的肉欲和现金,而不是遥远的中华文明。
恐龙从地球另一端来,带着武装到牙齿的学识和审美,这是传奇。
在增强了戏剧性的同时,却让作品变得粗俗,因为这毫无疑问的又是一次“降神”。
生活在别处的说法,如果最后要归结为异种文明,或者地理上的遥远,这和希望外星人乘坐UFO从天而降打救世人并没有任何不同。
更倒霉的是,芭贝里在避免和前人撞车的同时,选择了她自己也并不熟悉的日本文化。
在这本书里,那位从天而降,带着Hi-Fi音响而来的日本人几乎成为文艺女青年心目中的完美先生。
他做什么都是对的,都是合理的,都在美学上是超越的,都能够强烈地撞击孀居寡妇的心。
一个名字因此在我心头徘徊不去:琼瑶阿姨。
刺猬的优雅观后感

刺猬的优雅观后感刺猬,是一种生活在自然界中的小动物,它们背上布满了尖锐的刺,十分与众不同。
在我的观察中,刺猬不仅仅是一种有趣的动物,更是一种优雅的存在。
通过与刺猬的相处,我深入体会到了刺猬所展现出来的优雅与魅力。
首先,刺猬的外表给人一种独特的美感。
我们常说“外貌即气质”,刺猬的外貌正是与众不同的标志之一。
无论是那一片件互相交错的刺,还是褐色的毛发,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刺猬的刺是它们保护自己的武器,它们用这些尖锐的刺展现出自己的独特之处,即使在别的动物中也是独具一格的。
这种与众不同的外表让我产生了对刺猬优雅的看法。
其次,刺猬的生活方式也展现了它们的优雅。
刺猬大多数时间都是隐藏在树丛或灌木丛中,只有在夜晚才会出来觅食。
与其它动物相比,刺猬在生活习性上显得十分独特,它们有一种与世界保持距离的姿态。
当我在某个夜晚静静地观察刺猬时,我发现它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那样的从容与优雅。
它们爬行的身姿,蜿蜒的动作,仿佛一种流畅而舒缓的舞蹈。
刺猬不为其他动物所侵扰,它们在夜晚自由自在地觅食,展现出了一种与世无争、从容不迫的优雅。
最后,刺猬的生存智慧更是让我对它们的优雅产生了无尽的思考。
刺猬的刺虽然是它们的保护武器,但它们却并不滥用这种力量。
当遇到敌害时,刺猬会将身体蜷缩成一个团,将刺向四面八方,形成一个坚固的防御球,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这种聪明的应对方式让我不禁佩服刺猬的智慧与优雅。
刺猬用最简单的方式,达到了最有效的保护自己的目的,这种智慧也正是优雅的体现。
总的来说,刺猬的优雅不仅仅是由外表所带来的美感,更体现在它们与世界的接触方式和生存智慧上。
刺猬的存在是如此与众不同,却又能在自然界中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和优雅。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喧嚣的世界中,观察和感受刺猬的优雅,也让我重新审视了生活的本质与价值。
刺猬的优雅观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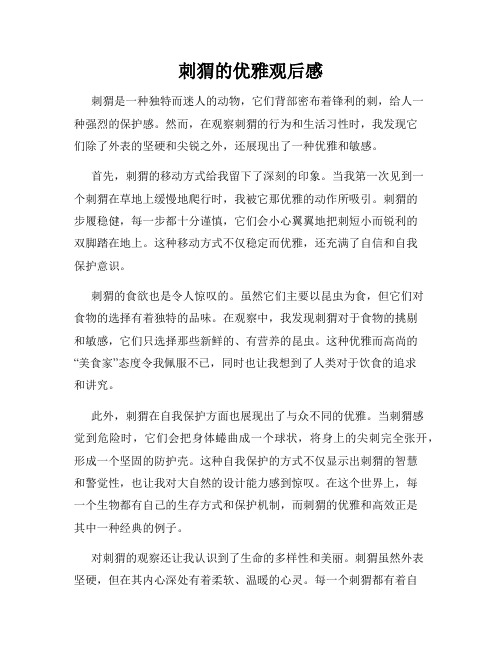
刺猬的优雅观后感刺猬是一种独特而迷人的动物,它们背部密布着锋利的刺,给人一种强烈的保护感。
然而,在观察刺猬的行为和生活习性时,我发现它们除了外表的坚硬和尖锐之外,还展现出了一种优雅和敏感。
首先,刺猬的移动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我第一次见到一个刺猬在草地上缓慢地爬行时,我被它那优雅的动作所吸引。
刺猬的步履稳健,每一步都十分谨慎,它们会小心翼翼地把刺短小而锐利的双脚踏在地上。
这种移动方式不仅稳定而优雅,还充满了自信和自我保护意识。
刺猬的食欲也是令人惊叹的。
虽然它们主要以昆虫为食,但它们对食物的选择有着独特的品味。
在观察中,我发现刺猬对于食物的挑剔和敏感,它们只选择那些新鲜的、有营养的昆虫。
这种优雅而高尚的“美食家”态度令我佩服不已,同时也让我想到了人类对于饮食的追求和讲究。
此外,刺猬在自我保护方面也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优雅。
当刺猬感觉到危险时,它们会把身体蜷曲成一个球状,将身上的尖刺完全张开,形成一个坚固的防护壳。
这种自我保护的方式不仅显示出刺猬的智慧和警觉性,也让我对大自然的设计能力感到惊叹。
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生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和保护机制,而刺猬的优雅和高效正是其中一种经典的例子。
对刺猬的观察还让我认识到了生命的多样性和美丽。
刺猬虽然外表坚硬,但在其内心深处有着柔软、温暖的心灵。
每一个刺猬都有着自己的个性和特点,有些可能更加勇敢和好奇,有些则更加内向和安静。
这种种不同的特点和性格使每一只刺猬都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也增添了自然界的丰富性和色彩。
通过观察刺猬的一系列行为和生活习性,我不禁想到:人类是否也能从刺猬身上获得一些启示呢?或许,我们可以向刺猬学习其优雅和敏感。
正如刺猬在移动过程中的谨慎和稳定,我们也可以通过平静和坚定的态度面对人生的挑战。
刺猬的饮食习惯也提醒我们要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尽管我们的饮食选择会更加复杂和多样化。
刺猬在自我保护中的智慧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即要学会保护自己,保持警觉和机智,在面对困难和威胁时有所准备。
评价《刺猬的优雅》这部电影

评价《刺猬的优雅》这部电影评价《刺猬的优雅》这部电影导读:人的一生,有许多事情,是需要放在心里慢慢回味的,过去的就莫要追悔,一切向前看吧任何打击都不足以成为你堕落的借口,即使你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你却依然可以改变自己,选择条正确的路永远走下去。
下面是小编为你推荐的评价《刺猬的优雅》这部电影。
生与死只是构建得好与坏的结果如果有一件事是穷人讨厌的,那就是其他的穷人。
在无人能看透的内心深处笑看红尘。
如果你忘记未来,你失去的就是现在。
应该抱着我们终归老去的态度去生活,那不会很美,不会很好,也不会很快乐。
对自己说重要的是现在:构建某种生命状态,就在此刻,不惜代价,竭尽全力。
未来,它的作用就是:用充满活力的真正计划来构建现在美好的生活。
当我们的情感和意志背道而弛时,意志便利用所有的智慧来达到目的。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当我们打开扇门。
我们其实就是以一种狭隘的方式改变了我们的空间艺术,就是生活,只不过是伴随着另一种节奏罢了。
当智慧本身变成了目标,表现出智慧的行为就会变得异常奇怪:智慧存在的标志并不在于智慧产生得多么巧、多么容易,而是在于晦涩不明的感情。
《刺猬的优雅》(L’elegance Du Herisson)这本书在法国很出名。
由于作者Muriel Barbery将法国典型的文艺腔体现得淋漓尽致,加上作者又是一名哲学教授,为这本比起小说更像是哲学散文的书打了不少广告,所以这本书在法国获得了书商奖,销售额可观,还被拍成了电影。
传入中国,有繁体和简体两个版本。
台湾版的封面是一张有绿色墙纸衬底的玫瑰红色沙发椅,法国的文艺帝国味道浓重。
内地版的封面奇丑,剥去封皮,全书为白色,封面印着一幅简单的画,倒是更贴近书素雅的本意。
看过法国原版的封面,白底红花,也分外有禅意。
这便应了我读这本书时,始终觉得生硬的,那点日本味道。
先更正标题,书中所提到的“刺猬”指的是一位中年门房,她是一位法国人,并非“日本的”。
刺猬的优雅观后感

刺猬的优雅观后感刺猬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生物,以其独特的外表和生活习性而闻名。
曾经有一次,我在一个公园里看到了一只可爱的刺猬,这次见到刺猬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通过观察和思考,我对刺猬的优雅之处有了更深的理解。
首先,刺猬的外表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
刺猬全身布满了尖锐的刺,这些刺可以让它们在受到威胁时迅速卷曲起来,形成一个坚固的保护壳。
这种自我保护机制展示了它的聪明和机敏,令人赞叹。
尽管刺猬看起来很尖刻,但它们却充满了可爱的气息。
它们的小眼睛透露出一种温和而聪明的光芒,使我对它们产生了亲近感。
其次,刺猬的行动也显示出它们的优雅。
我发现刺猬移动时总是小心翼翼地摇摆前爪,步伐轻盈而自信。
即使在坡道上行走,它们也能够稳定地前进,没有一点儿颤振的迹象。
刺猬总是将自己的生活环境打理得井井有条,不论是在草地上还是在林间小道上,它们都能保持整洁,展现出一种自由自在而又和谐的姿态。
此外,刺猬的食物选择也给我带来了一些思考。
它们主要以昆虫为食,这种选择反映了刺猬的智慧。
相比于植物,昆虫更容易获取,且富含蛋白质。
这种追求高质量的食物不只体现了它们的食欲,更是一种自我进化的体现。
刺猬通过选择更适合自己的食物,提高了自己的存活能力,这种智慧深深打动了我。
最后,刺猬的生活习性也令人称叹。
他们通常是夜行性的动物,这样可以避免在白天受到很多干扰。
尽管刺猬喜欢栖息在草地或树丛中,但它们能够迅速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这种适应能力十分了不起。
例如,在临近冬季时,刺猬会找到一个温暖的地方,卷曲起来进入冬眠状态,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的节约能量的方式。
总的来说,刺猬的优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它们独特的外表、机敏的反应、优美的行动和智慧的选择都让我感到非常敬佩。
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刺猬不仅展示了它们自身的美丽与优雅,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思考的角度。
我们应该学习刺猬的聪明和机敏,以及它们适应环境和保护自己的能力。
正是这种优雅的品质,使得刺猬成为了我们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
刺猬的优雅观后感

刺猬的优雅观后感刺猬是一种生活在草地和丛林中的小动物,它以它那独特的外表和行为习惯而闻名。
我最近有幸观察到了一只刺猬,它的优雅和迷人之处令我十分着迷。
在这篇观后感中,我将分享我对刺猬的观察和心得体会。
首先,刺猬的外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它的身体全身覆盖着短而尖锐的刺,像一颗颗小小的箭头,给人一种霸气和自信的感觉。
刺猬的刺并不是尖锐的,却有一种震撼和威慑力。
这些刺不仅为刺猬提供了保护,还使它能够深入潜伏在森林的浓密丛林中,不易被其他动物发现。
其次,刺猬的行动也十分令我赞叹不已。
尽管它是一种缓慢而笨拙的动物,但它却能够以其独有的方式表现出自己的优雅。
它通常会沿着固定的路线行动,径直朝着目的地前进。
它的步态虽然不快,但它却一步一步地坚定地走着。
这种坚毅和决心令我深感敬佩。
再次,刺猬的饮食习惯也是我观察到的一大亮点。
刺猬主要以昆虫和小型无脊椎动物为食,这些食物对于它们来说是主要的营养来源。
刺猬以其锋利的嘴巴和牙齿捕捉和咀嚼食物,同时它也会利用自己独特的舌头来帮助进食。
观察它们吃东西的过程,我感受到了它们对食物的热爱和专注。
刺猬会小心翼翼地咀嚼每一口食物,仿佛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感受着大自然的恩赐。
最后,刺猬的为人父母的行为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刺猬是一种为数不多野生动物中有良好亲子关系的动物之一。
雌性刺猬会为未出生的幼崽营造一个舒适而安全的巢穴,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幼崽。
在幼崽出生之后,雌猬仍会继续照顾它们,直到它们能够独立生活。
这种对亲子的呵护和关爱令我感到温馨和感动。
它们用自己的方式展现着家庭的温暖和和谐。
通过观察和体验刺猬,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自然界的奇妙和刺猬的优雅。
尽管刺猬的外貌和行为习惯看似平凡,但它却有一种独特的美和魅力。
它们的刺代表着坚韧和自信,它们的行动和食物消化方式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和专注,它们的亲子关系展现了家庭的和谐和亲密。
刺猬的优雅是一种默默无闻的美,值得我们去品味和学习。
总而言之,观察和感受刺猬的优雅是一次难忘的体验。
刺猬的优雅观后感

刺猬的优雅观后感人类与自然界的万物相互依存,每一个生命形态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和魅力。
而在我接触到刺猬的时候,我也被它们的独特魅力所吸引。
刺猬虽然外表尖刺森森,但却给人一种特别的优雅感。
下面我将分享关于刺猬的观后感。
首先令人难以忽视的是刺猬的外表。
当我第一次看到刺猬时,立刻被它们身上长满的尖刺所吸引。
这些尖刺紧密地覆盖着刺猬的背部,形成了一层天然的防御盾牌。
刺猬的尖刺可以通过肌肉的收缩和舒张来控制,不仅能够将尖刺竖立起来以威慑敌人,还可以让自己身体变得更加蓬松,增加腹部的保护。
这种身体结构的设计让我感受到刺猬的自然智慧,它们以自己特殊的方式适应了环境中的挑战,并且通过与其他生物的互动来保护自身。
刺猬的行动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它们大多数时间都在夜晚活动,寻找食物和探索领地。
尽管刺猬的视力相对较差,但它们却拥有敏锐的嗅觉和听觉。
我曾看到刺猬在灯光照耀下小心翼翼地探索周围的环境,灵活地躲避潜在的危险。
它们细小而敏捷的身躯,以及迅速卷曲成球状的技巧,给人展现了一种独特的优雅感。
刺猬在生存中也有着与众不同的饮食习惯。
它们主要以昆虫、蠕虫和一些植物为食,特别喜欢吃蚯蚓。
正是这种独特的饮食习惯,使得刺猬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控制着害虫的数量。
我惊叹于刺猬们包括食物在内的生活方式,它们以独特的、优雅的方式融入了生态系统。
与人类相比,刺猬的寿命相对较短,大约只有3-7年。
然而,我觉得刺猬们用短暂的一生展现了对生命的热爱和追求。
它们不退缩于环境中的困难和挑战,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对生态平衡的思考。
总的来说,刺猬以其外表的尖刺、行动的优雅和饮食的特殊性,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观后感。
刺猬们以独特的方式适应了自然环境的挑战,保护自己的生活。
它们是自然界中的一份子,也是我们与之共生的伙伴。
通过与刺猬们的相处,我从中学到了生命的坚韧和追求,也更加珍惜与自然界中各种生命相互的联系与共存。
这就是我对刺猬的观后感。
妙莉叶 巴贝里《刺猬的优雅(节选)》阅读训练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6~9题。
刺猬的优雅(节选)【法】妙莉叶·巴贝里①我叫勒妮①,今年五十四岁。
二十七年来,我一直在格勒内勒街七号的一栋漂亮公寓里当门房。
那是一栋配有庭院和花园的美轮美奂的住宅楼,分成八个极度奢华、住满房东、宽敞无比的公寓。
我寡居、矮小、丑陋、肥胖,脚上布满老茧,有一些早晨,我会因自己有如猛犸象一般呼吸时发出的口臭味而感到不适。
我从未上过学——不对,我拿到了小学毕业文凭;贫穷也从未远离过我,我是一个平庸而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②我和我的猫咪一起生活,那是一只肥胖慵懒的公猫,它有个特点,当它心情不好时,爪子会散发出奇臭无比的味道。
它和我一样,不大在融入同类这方面下功夫。
我冷漠绝情,然而我总是彬彬有礼,大家虽然不喜欢我,但还是容忍我,因为我很符合社会信仰所塑造出的门房形象,我是让世人共同的伟大梦想维持运转的复杂构件之一,按照这一梦想生命是有意义的,但这意义很容易被破解。
③每天早上,我都会到肉店买一片火腿或者小牛肝,再将其放到网兜里,夹在一袋面条和一把胡萝卜之间。
我得意地炫耀这些能够凸显其相当重要特点的寒酸食物,因为我是这所高档住宅中的穷人,买这些东西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他们对门房根深蒂固的看法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喂养我的猫咪列夫,它因吃了本该属于我的食物而发胖。
当它愿意享用它的猪肉和奶油通心粉时,我就能够在毫无嗅觉干扰、没人怀疑我对食物的个人偏好的情况下好好满足下自己的胃口。
④那个连着红外线装置的电铃时刻提醒着我大厅里人们的一举一动,这可以确保我像每个门房一样能够第一时间得到信息:有谁进来,有谁离开,和谁一起,在什么时候。
而我自己总是待在走廊深处的一个小房间里度过我大部分的闲暇时间,做回我自己。
我尤其怀念那些丈夫还在时的周日早上,在寂静的厨房,他喝着他的咖啡,而我则捧着我的书。
我看的书籍是关于历史、哲学、经济、政治、社会、教育、心理分析等方面的,当然还有文学。
我的猫叫列夫,因为那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名字,我的前一只猫叫唐戈,因为那是法布里斯·戴尔的姓。
电影推荐:刺猬的优雅

电影推荐:刺猬的优雅电影梗概:左岸葛内乐街七号,一栋来来往往全是高级知识分子、社会菁英的高级公寓。
其貌不扬、又矮又驼的寡妇荷妮,多年来一直是这栋高级公寓的门房。
二十七年来,当大家以为她的生活应是抹布、毛线、充斥菜味的厨房时,她也顺势以整天开著播放连续剧的电视掩人耳目,躲在密室里专注研读弗洛伊德、胡塞尔现象学、中世纪哲学……。
她保守著自己的秘密,告诉自己--我必须对我的一切缄口不言,而且绝不能把脚踩进另一个世界,小心翼翼地不和这个世界打交道……住在同栋公寓,把学习时间全用来装笨的天才儿童的芭洛玛,父亲是国会议员,嫌恶母亲与姊姊布尔乔亚式的愚蠢、市侩,从身边往来堪称优雅的大人身上,看透了生命的荒谬与空虚。
害怕自己的命运已被注定,于是秘密计划在生日当天自杀,并烧了父母的豪宅。
但她为了避免搞错为什么而死,决定不浪费剩余的七个月生命,试图寻找一个理想,明白一些事情,而刚搬进来的日本住户小津先生,是退休高级音响代理商,他的另类文化和生活态度,在这栋高级公寓掀起了大骚动。
他的细腻,识破了荷妮和芭洛玛两人刻意隐瞒的奇特生活,最后和芭洛玛联手挖掘出荷妮不为人知的过去……经典台词:(1)重要的不是死,而是我们死的那一刻在做什么。
(2)国际象棋要杀死对方才能赢,围棋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得活下去才会赢,而且还得设法让对方也活下去,生死仅仅布局好坏与否的结果,最重要的是要好好布局。
(3)米谢儿太太让我想起刺猬,浑身是刺,一座如假包换的堡垒,但我感觉她仅仅故意装得很懒散,其实内心跟刺猬一般细致,性喜孤独,优雅的无以复加(4)一切轧不过止,这就是死吗?再也看不到您爱的人,如果这就是死的话,那真的跟大家说的一样,是个悲剧。
刺猬的优雅观后感

刺猬的优雅观后感引言《刺猬的优雅》是法国作家穆里埃尔·巴雷斯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由国际著名导演孟浩然执导,并于2019年上映。
电影通过刻画现代社会的冷漠与孤独,以及普通人之间的温暖与关爱,让观众深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沟通。
观看完这部影片后,我不禁产生了一些深刻的感悟与思考。
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影片中的主人公勒庞夫人是一个自闭的老寡妇,她过着孤独而无趣的生活,除了阅读与研究,几乎没有与外界有过多的接触。
她周围的人也都是忙于自己的生活,缺少真正的沟通与关心。
正因如此,大家对周围的世界变得越来越麻木与冷漠。
这让我深思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互动。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忙于自己的生活与工作,很难有闲暇的时间与精力去关注他人。
我们愈加独立与自私,更倾向于渴望个人空间而远离别人。
然而,这种日益增长的冷漠与孤立感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深深的伤害。
我们需要仔细思考如何在现实生活中,与身边的人建立起更为深刻的联系与交流。
关爱与温暖的力量电影中,勒庞夫人邂逅了同样独居的邻居拉尼尔先生和下楼住的女仆韦若妮卡。
通过勒庞夫人对邻居们的观察,她逐渐意识到真正与他人建立联系的重要性。
她开始与邻居拉尼尔先生展开交流,然后与韦若妮卡一起参与到一个秘密的计划中。
通过这个计划,他们为小区居民带来了爱与温暖,让孤独与冷漠的环境开始变得生机勃勃。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名言:“关爱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
”电影中勒庞夫人的行动正是这个道理的最好证明。
只要我们开始关注他人,给予他人关爱和温暖,不仅能改变他人的生活,也能成为我们自己内心的滋养与宽慰。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我们不妨暂停一下脚步,与身边的人分享关爱和温暖。
寻找生活的意义影片中,勒庞夫人一直在寻找生活的意义与价值。
她对现实世界的冷漠与麻木感到失望与困惑,却又没有找到出路。
直到她邂逅了拉尼尔先生和韦若妮卡,通过与他们的交流与接触,她才逐渐找到了内心的平衡点与生活的意义。
这令我想到,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程中,我们都在寻找生活的意义。
刺猬的优雅观后感

刺猬的优雅观后感引言《刺猬》是一部由法国女作家巴尔扎克所著的小说。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生活在一个巴黎富人小区的情感麻木的保安人员,他隐藏着自己的高智商和独特的思想。
小说揭示了社会阶层差距对人们心灵自由的压抑,以及每个人追逐真实和幸福的渴望。
通过对这部作品的阅读,我深受启发,思考了人与社会以及内在矛盾的关系。
主题的思考小说以一种独特而深刻的方式探讨了人类生存的困境。
主人公雷纳尔是一个非常机智,但外表看似平凡的保安人员。
他隐藏自己的才华和独到的见解,以避免被其他人发现。
他选择用抗议的方式反抗社会的假面具,并表达他对人生的疑惑和追求真相的渴望。
小说通过雷纳尔的角度,揭示了权力与阶级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压迫。
雷纳尔通过挖掘大人物的虚伪和虚荣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抗社会的不公正。
雷纳尔的内在冲突雷纳尔对社会的腐败和虚伪感到愤怒和无奈,但他也存在内心的冲突。
他既想保护自己的内心和真实的思想,又怕被社会深深地伤害和排斥。
他选择隐藏自己的才能和智慧,避免被社会所拒绝,并保持独特的自我认同。
然而,这种隐藏并没有使他真正获得自由与幸福。
他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情感无法得到真正的表达,也无法与社会和他人建立真实的联系。
对社会的反思与批判通过雷纳尔的视角,小说对社会的虚伪和不公正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社会上的人们都穿着各自的假面具,隐藏着真实的自我。
有些人通过社会地位和财富来获得虚荣的快感,不顾他人的需求和痛苦。
小说中的贵妇人瑞尼尔小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她拥有财富和地位,但却对贫困和痛苦的人漠不关心。
小说警示了这种虚伪和自私的行为对个人和社会的巨大破坏。
追求真实与内在自由小说中的雷纳尔成为了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深深地渴望真实和自由。
他通过与一位年轻的女孩塞莉娜的互动,慢慢地打开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雷纳尔通过与塞莉娜的交流,逐渐找到了对抗虚伪和追求真实的力量。
小说以一种平淡而真实的方式展示了人类对真实和内在自由的渴望,以及追求真实所带来的幸福和满足感。
刺猬的优雅观后感

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刺猬,只不过多半不怎么优雅。
确实,在我们平常的日常中,每个人都是刺猬,对身边的人都有着防备和介意。
我们每个人也都像生活在鱼缸里,尽管衣食无忧,看似有很多的自由,然而始终被他人左右着,过着毫无意义的生活。
主人公54岁的勒妮是一个自认为相貌丑陋,能力平庸且微不足道的高档小区的门房。
她年老色衰、外貌丑陋、脾气暴躁。
和小区里的富人们格格不入,在外人看不见的时候,她是一位热衷于艺术和哲学,且有些自卑敏感、真诚善良、有着高贵典雅的公主之心的小公主。
看完这部电影,我们也许会发现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所需要的也许并不需要太多。
勒妮刚认识的新房东小津.格郎也喜欢油画,喜欢莫扎特的音乐,喜欢文学和电影。
认识格郎之前,勒妮生活的很简单,她说,:“我没有孩子, 我不看电视, 我不信上帝, 这些都是所有人为了让人生之路能够更便捷而所走的道路。
”对她来说有住的地方,有份不太忙碌的工作,可以有空闲时间看书就足够了。
她对于衣着打扮不怎么讲究,在众人眼中是个性格孤僻的不合群的普普通通的门房,但关上门,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却有着大世界,文学,音乐,哲学,她都喜欢,并用这些来充实和滋润着自己的内心。
她有一个很好的知己。
她和她唯一的好姐妹曼努埃拉一起品茶、闻香气四溢的咖啡、吃精致饼干、点心和巧克力,聊天;丈夫已经在多年前去世了,对她来说,丈夫也是可有可无的,并不是必需品。
所以,她选择一直单身。
她有陪伴着她的猫咪,还有一个小小的忘年交帕洛玛。
她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童真童趣,所以才可能和帕洛玛成为好朋友,才允许帕洛玛举着摄像机拍摄她,并且说出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
富人家的小女孩帕洛玛,并不喜欢自己的父母和姐姐,她感觉他们可耻、空虚、腐败。
她的存在就是以剧烈的形式打击他们,做坚硬的反抗。
她喜欢着他们都不喜欢的门房勒妮,巨大的年龄差也没能阻挡她们成为好朋友,忘年交。
帕洛玛是一个独立、有思想、敏锐的小孩,想追寻属于自己的漫天繁星和自由,她想要在12岁生日时自杀,但她渐渐成长了,“勒妮妈妈”用自己亲身的故事让她明白了生命的可贵,人间的值得和美好。
刺猬的优雅观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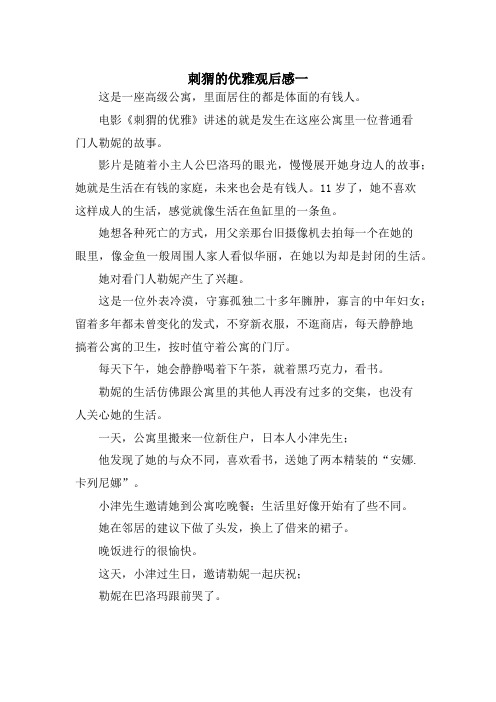
刺猬的优雅观后感一这是一座高级公寓,里面居住的都是体面的有钱人。
电影《刺猬的优雅》讲述的就是发生在这座公寓里一位普通看门人勒妮的故事。
影片是随着小主人公巴洛玛的眼光,慢慢展开她身边人的故事;她就是生活在有钱的家庭,未来也会是有钱人。
11岁了,她不喜欢这样成人的生活,感觉就像生活在鱼缸里的一条鱼。
她想各种死亡的方式,用父亲那台旧摄像机去拍每一个在她的眼里,像金鱼一般周围人家人看似华丽,在她以为却是封闭的生活。
她对看门人勒妮产生了兴趣。
这是一位外表冷漠,守寡孤独二十多年臃肿,寡言的中年妇女;留着多年都未曾变化的发式,不穿新衣服,不逛商店,每天静静地搞着公寓的卫生,按时值守着公寓的门厅。
每天下午,她会静静喝着下午茶,就着黑巧克力,看书。
勒妮的生活仿佛跟公寓里的其他人再没有过多的交集,也没有人关心她的生活。
一天,公寓里搬来一位新住户,日本人小津先生;他发现了她的与众不同,喜欢看书,送她了两本精装的“安娜.卡列尼娜”。
小津先生邀请她到公寓吃晚餐;生活里好像开始有了些不同。
她在邻居的建议下做了头发,换上了借来的裙子。
晚饭进行的很愉快。
这天,小津过生日,邀请勒妮一起庆祝;勒妮在巴洛玛跟前哭了。
她孤独了那么多年,没有人在意过她;她也习惯将自己隔绝到那个隐蔽灰暗的角落,她自觉丑陋肥胖。
巴洛玛,这个年龄很小,但是却一直想寻找自己空间的女孩子,搂着她;勒妮终于面对了自己,给小津留言,看他的邀请是否有变。
小津为勒妮送来了一身漂亮的衣服鞋子,围巾;她脱掉了多年深色的外套,跟着小津一起吃日本料理。
生活开始与过去有了不一样。
那天早晨,勒妮在马路上突然被洗衣店的面包车撞倒,永远离开了。
巴洛玛和小津先生一起收拾勒妮的遗物,一箱一箱的书籍堆在门厅;巴洛玛清晰地看见熟悉的人,那个也是她喜欢的看门人在眼前就这样死亡,对于生死,她有了与过去不同的认识:重要的不是死亡,而是死亡的那一刻,你在做什么?勒妮,您在做什么呢?您在准备去爱一个人。
刺猬的优雅书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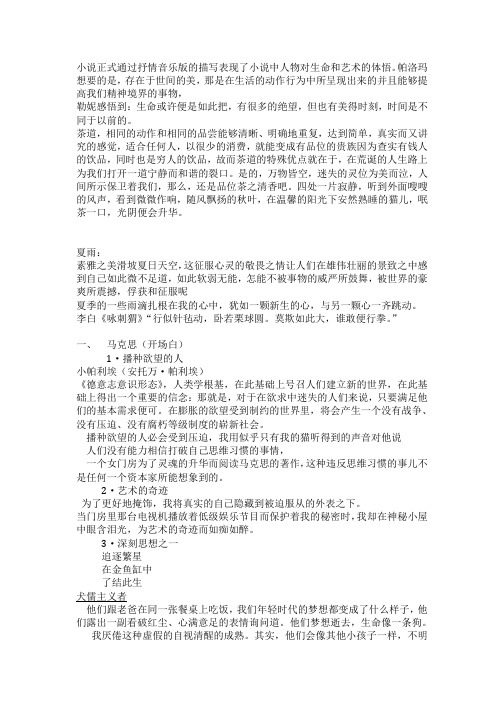
小说正式通过抒情音乐版的描写表现了小说中人物对生命和艺术的体悟。
帕洛玛想要的是,存在于世间的美,那是在生活的动作行为中所呈现出来的并且能够提高我们精神境界的事物,勒妮感悟到:生命或许便是如此把,有很多的绝望,但也有美得时刻,时间是不同于以前的。
茶道,相同的动作和相同的品尝能够清晰、明确地重复,达到简单,真实而又讲究的感觉,适合任何人,以很少的消费,就能变成有品位的贵族因为查实有钱人的饮品,同时也是穷人的饮品,故而茶道的特殊优点就在于,在荒诞的人生路上为我们打开一道宁静而和谐的裂口。
是的,万物皆空,迷失的灵位为美而泣,人间所示保卫着我们,那么,还是品位茶之清香吧。
四处一片寂静,听到外面嗖嗖的风声,看到微微作响,随风飘扬的秋叶,在温馨的阳光下安然熟睡的猫儿,呡茶一口,光阴便会升华。
夏雨:素雅之美滑坡夏日天空,这征服心灵的敬畏之情让人们在雄伟壮丽的景致之中感到自己如此微不足道,如此软弱无能,怎能不被事物的威严所鼓舞,被世界的豪爽所震撼,俘获和征服呢夏季的一些雨滴扎根在我的心中,犹如一颗新生的心,与另一颗心一齐跳动。
李白《咏刺猬》“行似针毡动,卧若栗球圆。
莫欺如此大,谁敢便行拳。
”一、马克思(开场白)1·播种欲望的人小帕利埃(安托万·帕利埃)《德意志意识形态》,人类学根基,在此基础上号召人们建立新的世界,在此基础上得出一个重要的信念:那就是,对于在欲求中迷失的人们来说,只要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便可。
在膨胀的欲望受到制约的世界里,将会产生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压迫、没有腐朽等级制度的崭新社会。
播种欲望的人必会受到压迫,我用似乎只有我的猫听得到的声音对他说人们没有能力相信打破自己思维习惯的事情,一个女门房为了灵魂的升华而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这种违反思维习惯的事儿不是任何一个资本家所能想象到的。
2·艺术的奇迹为了更好地掩饰,我将真实的自己隐藏到被迫服从的外表之下。
当门房里那台电视机播放着低级娱乐节目而保护着我的秘密时,我却在神秘小屋中眼含泪光,为艺术的奇迹而如痴如醉。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刺猬的优雅》:日常生活秩序中的生死之问请把我的宿命忘掉。
——亨利·普赛尔1、小津安二郎通往“刺猬的优雅”核心,有一条悠远的道路,就是“小津”。
“小津”在这部电影中,既是电影主角小津格郎,也是日本著名电影导演小津安二郎。
和格郎一起看着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宗方姐妹》,是荷妮一生中最温暖、甜蜜的片段,用小说中荷妮的话来说,“这是时间长河之中的时间之外”。
小津电影的出现并不偶然:没有什么比小津的电影更能展现生活的“平凡之美”了。
小津的电影总是关心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之类的“永恒的”日常生活琐事,人物举止永远具有某种安详的尊严,甚至显得拘谨;在形式上,低角度镜头永远安静而克制,构图总是平衡、严谨。
也就是说,平凡(日常)生活本身有条不紊的秩序,在小津的电影中始终占据着突出的位置——正是每个人对这种秩序的深刻经验才让小津的古板风格不流于乏味和做作。
然而,这种秩序似乎又是“为了被打破而存在”(唐纳德·里奇《小津》)。
比如在《宗方姐妹》中,父亲和节子在榻榻米上聊天,端坐的人物、日式滑门的轮廓和地板构成了一个严谨的构图;他们从容地谈论着游览寺庙时所见的日照青苔、山茶花满地的美景。
然而,和这安详的一切构成冲撞的是:节子已经知道父亲时日不多,死亡正在吞噬眼前的美好。
谈论之间,她突然低头欲泣。
她的情绪和动作冲击着表面的有序,也因为秩序之衬托而显得更加真实动人。
如果说小津电影的“平凡之美”正在于它总是能触及到严谨的(平凡的)生活表层秩序之下生命的真实跃动并加以含蓄、克制的表达的话,那么,《刺猬的优雅》同样讲述了一个关于日常生活秩序及其内在的颠覆力量的故事。
2、荷妮可是,如何理解这种日常生活秩序?在《刺猬的优雅》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打扮一新的荷妮和格郎一起出门就餐,在公寓门口正好遇见楼里的太太,她完全没有认出荷妮。
格郎说:“因为她们从来没有见过您。
”这种秩序的特征就是:它决定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看“见”什么。
没有单纯的看,在每次看中,我们的身份、利益、阶级,甚至我们的整个过去和所处的文化都“总是已经”在起作用。
“偏见”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这种秩序的表征之一。
巴黎上层社会的太太每天和楼下的门房(抽象的、功能性的一面)打招呼,但看不“见”门房身份之下的“这一个”的本性,这几乎是自然而然的。
即使在看似亲密的家庭关系中,这种秩序同样存在:父母并不了解芭洛玛,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熟悉却古怪、孤僻的孩子,并像多数家庭一样不顾其本性地安排着她的生活。
因为这种秩序的存在,荷妮是矛盾的、分裂的:她既利用这种秩序伪装、掩盖自己——使自己符合典型的又老又丑、脾气暴躁的门房形象(迎合别人的“偏见”),然而又对这种秩序感到厌恶并深陷孤独。
于是,我们看到,客厅的电视机开着,荷妮却在书籍构筑的精神密室中。
一个底层人物的精神需求在日常生活(正常秩序下的社会互动游戏)中得不到满足,那么她只能在书和艺术中寻求缓解,在无人之境独自优雅。
小津安二郎是她的安慰之一:“一个使我从生理命运的枷锁里挣脱出来的天才”。
荷妮只是渴望一件事情:那就是希望别人能让她平静地度过此生。
电影在刻画荷妮的形象时,很遗憾没有触及小说中荷妮的创伤核心——聪慧、美丽的姐姐的意外死亡,正是这个事件让她决定不让自己的聪明和优雅加入正常的社会游戏。
3、芭洛玛这种庸常的日常生活秩序,对于11岁的芭洛玛,又意味着什么呢?是死亡。
芭洛玛每周从妈妈的药盒中偷一到两颗抗抑郁药,她下定决心要在自己12岁生日时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个出生于巴黎上层社会的孩子的绝望源于:她很早就知道自己人生的终点便是金鱼缸。
“人们相信追逐繁星会有回报,而最终却像鱼缸里的金鱼一般了结残生。
”芭洛玛觉得自己无法反抗那种决定她命运的生活秩序。
在自杀之前,她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仅仅是拍一部揭示生命如此荒谬的电影。
在她敏锐地抓拍的“电影”中包括了这样的生活细节:妈妈拒绝门房进自己家门——仿佛她和门房之间真有什么界限似的,等等。
所谓荒谬,根本言之,就是我们在“天真”的生命之上妄加秩序,却最终把这一秩序当做唯一真实之物。
“实际上如果人生是荒谬的,那么价值再大的伟大成功也不比失败好到哪里。
”芭洛玛领悟到,衡量价值的现成秩序根本上是荒谬的。
一个天生聪慧的11岁女孩居然如此敏感于生活的荒谬,并承担起加缪式的自杀思考,这一定程度上也是故事原创者、法国哲学教授妙莉叶·芭贝里理想化童真的结果。
芭洛玛决定以死亡(自杀)来避免自己成为既有生活秩序的俘虏。
然而,这个故事最终关心的问题是,把自己变成不是“命中注定”的样子,或者说,超越秩序,是否真的不可能?4、小津格郎小津格郎的出现,改变了荷妮和芭洛玛的“宿命”:一个准备忍受精神分裂之苦在既有生活秩序中平静过活;另一个则准备以死亡拒绝这种秩序。
格郎是一个外来者,来自另一个文化国度。
无论是不是出于妙莉叶·芭贝里对东方-日本文化的偏爱和误读,格郎在他所迁居的那个高档公寓(一个微观的西方文化空间)中轻易地超越(克服)了其中的日常生活秩序。
这个举止优雅、待人平易的外来者轻易地洞悉了一个门房的“刺猬的优雅”。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津格郎和小津安二郎不仅是名字上的接近,格郎看待周遭人事的眼光几乎是小津安二郎的那个经典的固定低角度镜头的化身,两者相通之处在于:同一种克制、和平和通透。
小津格郎使得荷妮终于在“现实”生活中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与她的精神世界相匹配的表里如一的人。
然而,这“奇迹”很短暂,就像《宗方姐妹》中三村的意外死亡挡在了节子和田代之间,意外死亡也挡在了荷妮和格郎之间。
当荷妮在车祸现场死去时,导演给了一个荷妮似乎活着的主观视角镜头。
其中“生”的含义不仅是指荷妮最终完成了在既有生活秩序中另一个自我的“复活”,也暗示了生的奇迹将延续,在芭洛玛身上延续。
这场微妙的生死转换(欲生之人的死和欲死之人的生)在金鱼这个细节上已经预演。
芭洛玛在自杀之前把她的金鱼倒进抽水马桶冲走,但金鱼却在荷妮家的马桶中奇迹般“复活”。
荷妮死后,拿回金鱼的芭洛玛决定活下去,因为她通过荷妮和小津看到:改变秩序(奇迹)是可能的,爱是可能的。
或者说,爱本身就是一种改变秩序的力量。
爱是一个相遇-事件,它总是超越既有秩序以及被这种秩序所定义的自我。
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曾提出一种“真理伦理学”。
关于爱,他说:每一次爱的相遇,都开启不可能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the impossible ),这种可能性是真理伦理学的核心原则——对抗那种起真实内容不过是确认死亡的苟活伦理学。
对荷妮来说,小津格郎是一个全然的例外,与他的意外相遇开启了控制着特定情境的逻辑和秩序之外的可能性,打破了她基于这种秩序的日常生活惯例和幻觉,使得被压抑的东西得到表达和解放。
而对芭洛玛来说,活下去意味着“奇迹”是值得期盼的,自己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奇迹”,比如使家人从上流社会的庸俗生活秩序中解脱出来,让爱作为超越秩序的真理-事件发生。
《香水》:穿越格雷诺耶的气味乌托邦在格雷诺耶的内心宇宙里压根儿没有东西,只有东西的气味。
——帕特里克·聚斯金德1,格雷诺耶是谁?读完德国作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Patrick Süskind)的小说《香水》,主角格雷诺耶的独特形象无论如何是挥之不去的,他无疑倾注了作者巨大的想象力。
他首先是一个奴仆和国王的混合体:在现实生活中他过着最底层奴隶和虫豸般的生活,然而在另一个气味的世界里,他却是一个能识别并驱使无数种香味创造出精美香水的国王。
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魔鬼和天使的混合体,因为他既毁灭着美好的事物,也创造着美好的事物。
格雷诺耶究竟是谁?“让一巴蒂斯特一格雷诺耶,出生在世界上最臭的地方。
他在没有爱的情况下长大的,在没有温暖的人的灵魂情况下,只有依靠倔强和厌恶的力量才得以生存,身材矮小,背呈弓状,瘸腿,而且丑陋,无人与他交往,从里到外是个怪物。
”这是聚斯金德的概述。
没有亲人的爱,没有教育,没有交往,这决定了他一开始就生活在社会的象征秩序(道德、习俗、律法等观念和行为准则)之外,是一个“怪物”。
然而,格雷诺耶仍然有自己的天赋和感知这个世界的方式:超常的嗅觉。
他的整个意义世界都是由他在巴黎嗅到并记住的无数种气味构成,他把它们分门别类,形成了一座“一座日益扩大、日益美丽和内部结构日益完善的最最壮观的气味组合的堡垒”。
然而在这个城堡中,仍有一块重要的空白,那就是他自己——他本人居然没有气味。
没有体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他天生在社会象征秩序之外的生存状况的一个形象概括。
这时候,整个故事情节最重要的推动力出现了:因为他没有气味,所以他无法在自己的世界中以自己的方式确定“我是谁”这个问题,这时他不得不闯入外部世界尝试完成身份认同,于是一场离奇的冒险开始了。
当然,对常人来说,“我是谁”是不成其为问题的,因为其总是已经身在其中的社会象征秩序总是已经给出了答案。
2,香水的功能一个人从另一个人的身上能夺走什么?聚斯金德给出的答案是:香味。
18世纪的巴黎到处散发着恶臭,格雷诺耶却凭自己的嗅觉天赋从中发觉了一种格外诱人的香味——少女的体味。
“格雷诺耶认为,不占有这香味,他的生活就没有意义。
”他似乎由此找到了生活的方向。
最终,他通过收集多个少女的体香制成了世界上最美好的香水,能激起爱欲的香水。
可是他真的仅仅是为了创造世上最美的香水吗?不是的,他是给自己创造一种香味,其实也就是通过香水创造一个自我的理想形象:他渴望看到一个被所有人爱的自我形象。
“他梦寐以求的事物,即让别人爱自己。
”香水是他所能创造的最完美的面具,是欲望的对象,但不是欲望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香水及其带来的这个形象能填补那个嗅不到的、一直困扰着他的自身空白。
也就是说,当格雷诺耶嗅不到自己,进而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他就试图通过香水征服别人,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形象。
前者是现实,后者是理想(意识幻象),当两者发生短路的时候,有趣的事情总会发生。
整个故事最大的戏剧性就出现在他“成功”实现“理想”的时候。
他站在行刑台上,听到台下所有的人都在高呼,“他是无罪的”“他是天使”,看到所有的人都想亲吻他,都陷入他的香水带来的爱欲的迷狂,他拥有了他想拥有的一切。
可是就在这瞬间,突然“他觉得难以忍受,因为他本人并不爱他们,而是憎恨他们。
他突然明白了,他在爱之中永远也不能满足。
”我们可以大致这样概括:格雷诺耶的香水制造成功并发挥理想效果时,正是他寄托在香水中的“理想”被证实并不切身的时候,格雷诺耶发现实现了的“理想”和自己之间总是存在着不可克服的裂缝。
所有欲望的客体,比如格雷诺耶的香水,总是因为某种something in it more than itself(欲望的原因),而当这种客体成为现实的时候,也正是欲望的原因消失的时候,而不是欲望被满足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