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作家书写中国形象的叙事模式以严歌l苓为例
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典型的美国人》的中国叙事分析

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典型的美国人》的中国叙事分析
任碧莲(Jade Snow Wong)是一位在美国国内享有盛誉的华裔美国作家,她的作品《典型的美国人》被誉为亚裔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
这部作品以自传体的形式,描绘了作者在美国成长的经历和对美国文化的思考,通过她的叙述,读者可以感受到作为华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冲突。
本文将从中国叙事的角度对《典型的美国人》进行分析,探讨任碧莲如何以中国叙事的方式诠释自己的美国故事。
任碧莲在《典型的美国人》中以中国叙事的方式展现了对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的探索和追求。
在她的叙述中,读者可以看到她从一个羞怯、畏缩的少女逐渐成长为一个自信、坚韧的女性,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不懈奋斗,最终实现了自我梦想和人生目标。
她在书中描述了自己的学习、工作和创作历程,以及在美国社会中的奋斗和探索,展现了一个华裔女性在美国社会中追求自由和独立的励志故事。
这种对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的追求与中国叙事中对个体成长和自我价值的探索有着共通之处,体现了中国叙事在塑造自我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方面的独特魅力。
《典型的美国人》是一部充满中国叙事韵味的作品,任碧莲以中国叙事的方式诠释了自己作为华裔美国人的成长故事和文化追求。
她通过对家庭、传统和文化的珍视,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的思考,以及自我成长和追求的探索,展现了一个华裔美国人独特的生存状态和文化价值观念。
通过她的叙述,读者不仅可以感受到中国叙事在塑造文化认同和自我实现方面的独特魅力,更可以了解到华裔美国人在美国社会中的生存现状和文化困境,从而增进对美国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任碧莲的《典型的美国人》不仅是一部华裔美国人的自传故事,更是一部关于文化认同和自我实现的文化隐喻,值得我们深入品味和思考。
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典型的美国人》的中国叙事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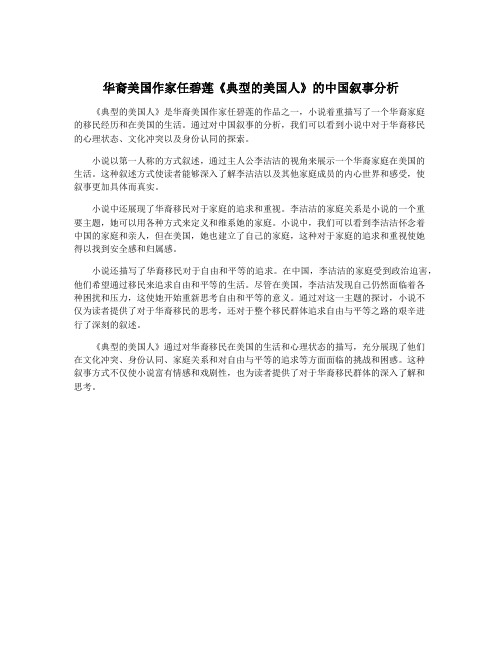
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典型的美国人》的中国叙事分析
《典型的美国人》是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的作品之一,小说着重描写了一个华裔家庭
的移民经历和在美国的生活。
通过对中国叙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对于华裔移民
的心理状态、文化冲突以及身份认同的探索。
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通过主人公李洁洁的视角来展示一个华裔家庭在美国的
生活。
这种叙述方式使读者能够深入了解李洁洁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内心世界和感受,使
叙事更加具体而真实。
小说中还展现了华裔移民对于家庭的追求和重视。
李洁洁的家庭关系是小说的一个重
要主题,她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定义和维系她的家庭。
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李洁洁怀念着
中国的家庭和亲人,但在美国,她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这种对于家庭的追求和重视使她
得以找到安全感和归属感。
小说还描写了华裔移民对于自由和平等的追求。
在中国,李洁洁的家庭受到政治迫害,他们希望通过移民来追求自由和平等的生活。
尽管在美国,李洁洁发现自己仍然面临着各
种困扰和压力,这使她开始重新思考自由和平等的意义。
通过对这一主题的探讨,小说不
仅为读者提供了对于华裔移民的思考,还对于整个移民群体追求自由与平等之路的艰辛进
行了深刻的叙述。
《典型的美国人》通过对华裔移民在美国的生活和心理状态的描写,充分展现了他们
在文化冲突、身份认同、家庭关系和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等方面面临的挑战和困惑。
这种
叙事方式不仅使小说富有情感和戏剧性,也为读者提供了对于华裔移民群体的深入了解和
思考。
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典型的美国人》的中国叙事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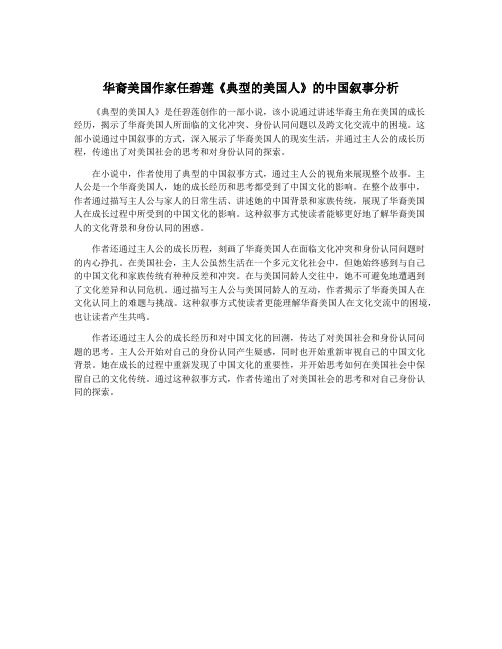
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典型的美国人》的中国叙事分析《典型的美国人》是任碧莲创作的一部小说,该小说通过讲述华裔主角在美国的成长经历,揭示了华裔美国人所面临的文化冲突、身份认同问题以及跨文化交流中的困境。
这部小说通过中国叙事的方式,深入展示了华裔美国人的现实生活,并通过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传递出了对美国社会的思考和对身份认同的探索。
在小说中,作者使用了典型的中国叙事方式,通过主人公的视角来展现整个故事。
主人公是一个华裔美国人,她的成长经历和思考都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在整个故事中,作者通过描写主人公与家人的日常生活、讲述她的中国背景和家族传统,展现了华裔美国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中国文化的影响。
这种叙事方式使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背景和身份认同的困惑。
作者还通过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刻画了华裔美国人在面临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问题时的内心挣扎。
在美国社会,主人公虽然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中,但她始终感到与自己的中国文化和家族传统有种种反差和冲突。
在与美国同龄人交往中,她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文化差异和认同危机。
通过描写主人公与美国同龄人的互动,作者揭示了华裔美国人在文化认同上的难题与挑战。
这种叙事方式使读者更能理解华裔美国人在文化交流中的困境,也让读者产生共鸣。
作者还通过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和对中国文化的回溯,传达了对美国社会和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考。
主人公开始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疑惑,同时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中国文化背景。
她在成长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了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并开始思考如何在美国社会中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
通过这种叙事方式,作者传递出了对美国社会的思考和对自己身份认同的探索。
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典型的美国人》的中国叙事分析

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典型的美国人》的中国叙事分析《典型的美国人》是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所著的小说,小说描述了海外华人的生活经历、文化背景以及与主流美国社会的交流与融合。
小说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之间,这个时期正是美国的繁荣期,也是在感情生活,政治生活等方面出现许多变化的时期。
本文将从中国叙事的角度,对小说中所呈现的精彩叙事进行分析。
小说中的中国叙事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中国籍人士的生活在美国、寻根之旅、和儿子的关系问题。
小说中最初呈现的叙事形式是关于中国籍人士在美国的生活,主要描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在经济方面的状况。
小说中所呈现的这种生活方式着重强调了“越来越不同”的生活态度,即海外华人常常体验到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难题。
小说中的华人人物,尤其是主角,对于自身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背景的融合都存在着一定的困扰和不安,这也是华人在美国生活中时时面对着的问题,对于在美国的华人来说,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是无法避免的难题。
本文认为,小说中通过对华人人物的细节描写,让读者更好地感受到了身份认同和文化融合这一方面的困难,这种细节描写让人感到文化的差异具有深刻的意义。
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寻根之旅中,小说的叙事内容体现了一个人对家乡的记忆的追溯,再加上亲情与朋友之间的纽带,人物逐渐感受到了家庭纽带的重要性以及自身身份的更深入探究。
寻根之旅是一种人性的探究,也体现了对文化差异的思考。
这一部分小说的叙事形式将人性和文化融合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使得小说更具深刻的意义。
在寻根之旅中,作者通过描述人物的思想感情展现了文化之间的差异。
例如,在叙事中让人物感受到了自然和人类的相互纠缠,从而感受到了“家”的力量和重要性,这表达了中国人对祖先乡土的强烈感情,表现出了对身份认同的追求。
最后一个部分是关于父子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一部分的中国叙事主要是围绕美国人文化和传统中国文化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父子关系的传统和现代变化展开的。
论华裔美国英语叙事文本中的中国形象

一、文本中的形象表达
在华裔美国英语叙事文本中,对中国形象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人物 形象的描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在著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喜福会》 中,母亲们虽然生活在美国,但她们身上的中国特质却格外鲜明,如传统价值观、 生活习俗等。这些人物形象的描绘不仅展现了华裔传承中华文化的真实写照,也 呈现了他们在异国他乡的生活状态。
参考内容
在西方语境的影响下,美国华裔英语文学逐渐发展壮大,并呈现出独特的中 国文化书写。自19世纪末华裔文学在美国诞生以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表 现出不同的文化内涵和特色。在华裔文学的初期,作品多以传记形式呈现,内容 主要集中在文化冲突为核心的代际冲突以及在种族歧视的美国如何奋斗并取得成 功。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华裔文学开始突破原有的模式,进入 多元化和深入探索的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华裔文学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时 期的作品不再局限于传记形式,而是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和主题来探讨华裔在美国 的生活和经历。
华裔作家开始更加中国文化的表达和传承。在他们的作品中,读者可以发现 中国文化的元素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入。这些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将中国文化、 价值观和习俗介绍给美国读者,为读者提供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人物形象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一些作 家开始将目光投向跨文化、跨族裔的主题,通过不同的人物形象展现多元文化交 融的复杂性。例如,在美籍华裔作家任璧莲的小说中,主人公往往跨越东西方文 化,体现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这种趋势的出现,反映了华裔美国人对文化多 元性的认识和追求,也进一步拓宽了华裔美国文学的表现主题。
除了人物形象,环境也是华裔美国英语叙事文本中经常出现的元素。在很多 作品中,作者会描绘中国特有的风土人情、风景名胜等。例如,在《花鼓歌》中, 作者以中国传统民间艺术花鼓为切入点,生动地描绘了中国南方水乡的风光和人 文气息。这些环境描写不仅让读者身临其境,更是传递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
小说《扶桑》“忍”之消解与重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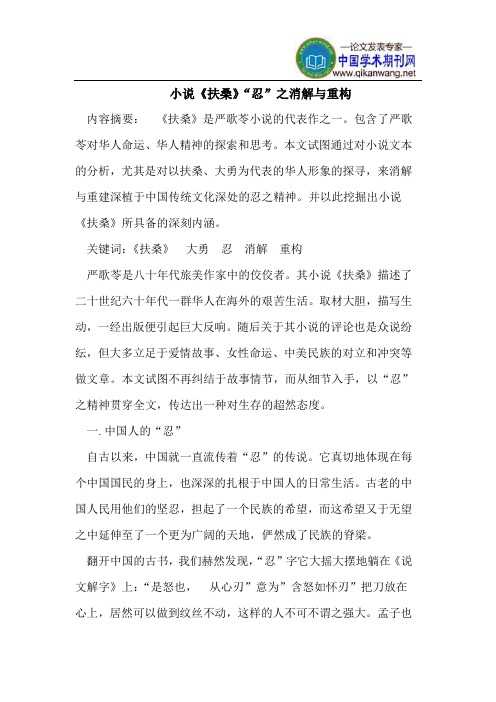
小说《扶桑》“忍”之消解与重构内容摘要:《扶桑》是严歌苓小说的代表作之一。
包含了严歌苓对华人命运、华人精神的探索和思考。
本文试图通过对小说文本的分析,尤其是对以扶桑、大勇为代表的华人形象的探寻,来消解与重建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处的忍之精神。
并以此挖掘出小说《扶桑》所具备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扶桑》大勇忍消解重构严歌苓是八十年代旅美作家中的佼佼者。
其小说《扶桑》描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群华人在海外的艰苦生活。
取材大胆,描写生动,一经出版便引起巨大反响。
随后关于其小说的评论也是众说纷纭,但大多立足于爱情故事、女性命运、中美民族的对立和冲突等做文章。
本文试图不再纠结于故事情节,而从细节入手,以“忍”之精神贯穿全文,传达出一种对生存的超然态度。
一.中国人的“忍”自古以来,中国就一直流传着“忍”的传说。
它真切地体现在每个中国国民的身上,也深深的扎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古老的中国人民用他们的坚忍,担起了一个民族的希望,而这希望又于无望之中延伸至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俨然成了民族的脊梁。
翻开中国的古书,我们赫然发现,“忍”字它大摇大摆地躺在《说文解字》上:“是怒也,从心刃”意为”含怒如怀刃”把刀放在心上,居然可以做到纹丝不动,这样的人不可不谓之强大。
孟子也在其《孟子·告子》上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明确的指出,只有能忍的人才能担起大任。
于是“忍”字,自中国古代就饱尝了诸多赞誉。
这样的赞誉,于严歌苓看来似乎也同样具备强大的魔力,虽然她极力地想展现它的落后,它的不合时宜,却又不经意地在文本中透露出对它的欣赏。
随她的眼光铺设开去,我们看到了异国的金山海岸上,那一群拖着沉重身体,挣着微薄公分的坚韧的中国工人。
他们每小时挣着八十分的工钱,他们签着一切伤亡后果自负的合约,在已经废除了奴隶制的异土上,劳动生息,繁衍生长。
“在海港之嘴广场聚集着很多的中国老单身汉,他们一辈子也没把娶老婆的钱挣够,但是再穷也不流浪,行乞。
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典型的美国人》的中国叙事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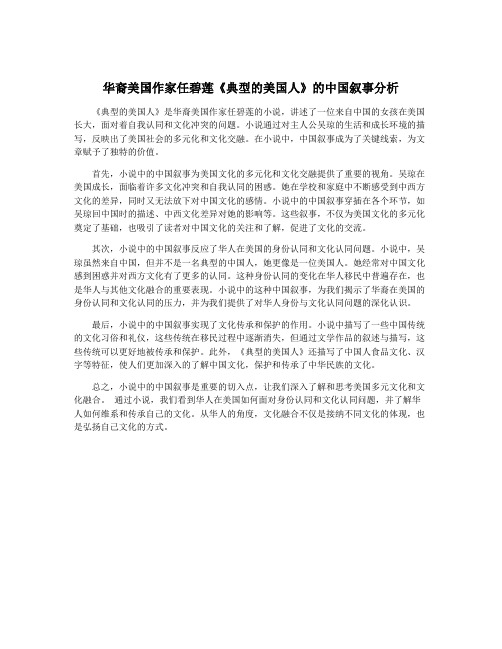
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典型的美国人》的中国叙事分析《典型的美国人》是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的小说,讲述了一位来自中国的女孩在美国长大,面对着自我认同和文化冲突的问题。
小说通过对主人公吴琼的生活和成长环境的描写,反映出了美国社会的多元化和文化交融。
在小说中,中国叙事成为了关键线索,为文章赋予了独特的价值。
首先,小说中的中国叙事为美国文化的多元化和文化交融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吴琼在美国成长,面临着许多文化冲突和自我认同的困惑。
她在学校和家庭中不断感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同时又无法放下对中国文化的感情。
小说中的中国叙事穿插在各个环节,如吴琼回中国时的描述、中西文化差异对她的影响等。
这些叙事,不仅为美国文化的多元化奠定了基础,也吸引了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和了解,促进了文化的交流。
其次,小说中的中国叙事反应了华人在美国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问题。
小说中,吴琼虽然来自中国,但并不是一名典型的中国人,她更像是一位美国人。
她经常对中国文化感到困惑并对西方文化有了更多的认同。
这种身份认同的变化在华人移民中普遍存在,也是华人与其他文化融合的重要表现。
小说中的这种中国叙事,为我们揭示了华裔在美国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压力,并为我们提供了对华人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的深化认识。
最后,小说中的中国叙事实现了文化传承和保护的作用。
小说中描写了一些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和礼仪,这些传统在移民过程中逐渐消失,但通过文学作品的叙述与描写,这些传统可以更好地被传承和保护。
此外,《典型的美国人》还描写了中国人食品文化、汉字等特征,使人们更加深入的了解中国文化,保护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总之,小说中的中国叙事是重要的切入点,让我们深入了解和思考美国多元文化和文化融合。
通过小说,我们看到华人在美国如何面对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问题,并了解华人如何维系和传承自己的文化。
从华人的角度,文化融合不仅是接纳不同文化的体现,也是弘扬自己文化的方式。
海外视角下的“中国故事”写作——海外华文作家张翎访谈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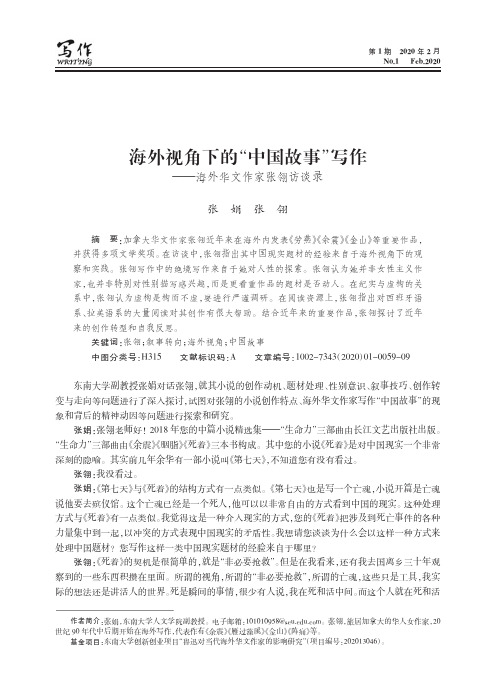
第1期2020年2月No.1Feb.2020海外视角下的“中国故事”写作—海外华文作家张翎访谈录——张娟张翎摘要:加拿大华文作家张翎近年来在海外内发表《劳燕》《余震》《金山》等重要作品,并获得多项文学奖项。
在访谈中,张翎指出其中国现实题材的经验来自于海外视角下的观察和实践。
张翎写作中的绝境写作来自于她对人性的探索。
张翎认为她并非女性主义作家,也并非特别对性别描写感兴趣,而是更看重作品的题材是否动人。
在纪实与虚构的关系中,张翎认为虚构是构而不虚,要进行严谨调研。
在阅读资源上,张翎指出对西班牙语系、拉美语系的大量阅读对其创作有很大帮助。
结合近年来的重要作品,张翎探讨了近年来的创作转型和自我反思。
关键词:张翎;叙事转向;海外视角;中国故事中图分类号:H3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343(2020)01-0059-09东南大学副教授张娟对话张翎,就其小说的创作动机、题材处理、性别意识、叙事技巧、创作转变与走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试图对张翎的小说创作特点、海外华文作家写作“中国故事”的现象和背后的精神动因等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
张娟:张翎老师好!2018年您的中篇小说精选集———“生命力”三部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生命力”三部曲由《余震》《胭脂》《死着》三本书构成。
其中您的小说《死着》是对中国现实一个非常深刻的隐喻。
其实前几年余华有一部小说叫《第七天》,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
张翎:我没看过。
张娟:《第七天》与《死着》的结构方式有一点类似。
《第七天》也是写一个亡魂,小说开篇是亡魂说他要去殡仪馆。
这个亡魂已经是一个死人,他可以以非常自由的方式看到中国的现实。
这种处理方式与《死着》有一点类似。
我觉得这是一种介入现实的方式,您的《死着》把涉及到死亡事件的各种力量集中到一起,以冲突的方式表现中国现实的矛盾性。
我想请您谈谈为什么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处理中国题材?您写作这样一类中国现实题材的经验来自于哪里?张翎:《死着》的契机是很简单的,就是“非必要抢救”。
论华裔美国英语叙事文本中的中国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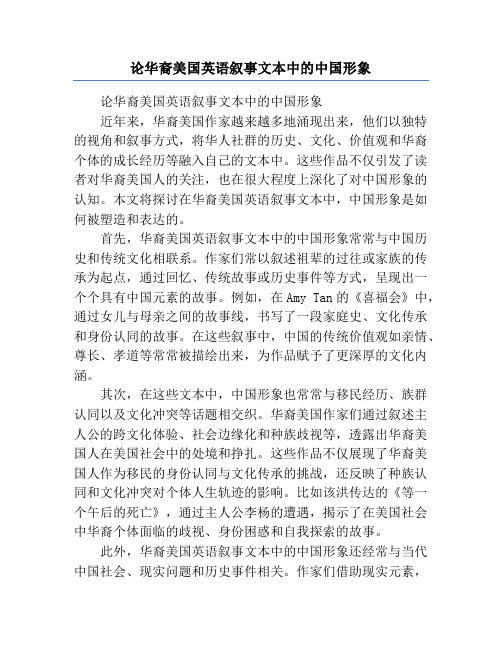
论华裔美国英语叙事文本中的中国形象论华裔美国英语叙事文本中的中国形象近年来,华裔美国作家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和叙事方式,将华人社群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和华裔个体的成长经历等融入自己的文本中。
这些作品不仅引发了读者对华裔美国人的关注,也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对中国形象的认知。
本文将探讨在华裔美国英语叙事文本中,中国形象是如何被塑造和表达的。
首先,华裔美国英语叙事文本中的中国形象常常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相联系。
作家们常以叙述祖辈的过往或家族的传承为起点,通过回忆、传统故事或历史事件等方式,呈现出一个个具有中国元素的故事。
例如,在Amy Tan的《喜福会》中,通过女儿与母亲之间的故事线,书写了一段家庭史、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的故事。
在这些叙事中,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如亲情、尊长、孝道等常常被描绘出来,为作品赋予了更深厚的文化内涵。
其次,在这些文本中,中国形象也常常与移民经历、族群认同以及文化冲突等话题相交织。
华裔美国作家们通过叙述主人公的跨文化体验、社会边缘化和种族歧视等,透露出华裔美国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处境和挣扎。
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华裔美国人作为移民的身份认同与文化传承的挑战,还反映了种族认同和文化冲突对个体人生轨迹的影响。
比如该洪传达的《等一个午后的死亡》,通过主人公李杨的遭遇,揭示了在美国社会中华裔个体面临的歧视、身份困惑和自我探索的故事。
此外,华裔美国英语叙事文本中的中国形象还经常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和历史事件相关。
作家们借助现实元素,在小说中描绘了中国的发展、社会问题和历史事件,以展示他们对中国的关注和思考。
例如,在Lisa See的《雪花秘扇》中,以妾侍角色的视角,探讨了中国的历史变迁与妇女地位的微妙变化。
这些作品不仅富含作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现实情况和历史背景。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华裔美国英语叙事文本中的中国形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论文范文:聂华苓小说的自传性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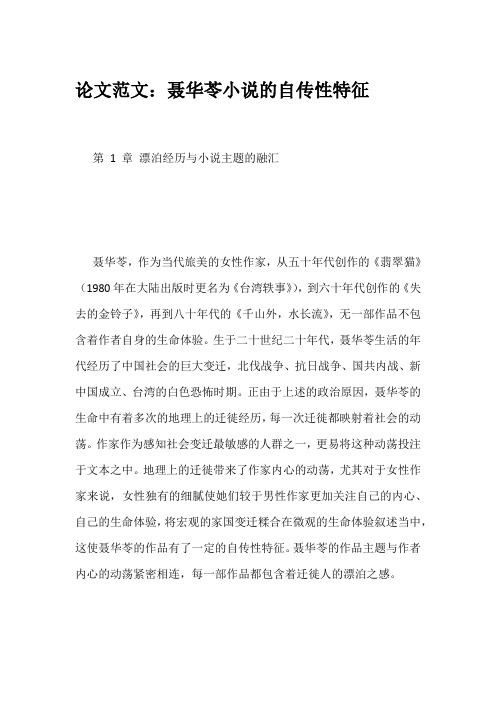
论文范文:聂华苓小说的自传性特征第1 章漂泊经历与小说主题的融汇聂华苓,作为当代旅美的女性作家,从五十年代创作的《翡翠猫》(1980年在大陆出版时更名为《台湾轶事》),到六十年代创作的《失去的金铃子》,再到八十年代的《千山外,水长流》,无一部作品不包含着作者自身的生命体验。
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聂华苓生活的年代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
正由于上述的政治原因,聂华苓的生命中有着多次的地理上的迁徙经历,每一次迁徙都映射着社会的动荡。
作家作为感知社会变迁最敏感的人群之一,更易将这种动荡投注于文本之中。
地理上的迁徙带来了作家内心的动荡,尤其对于女性作家来说,女性独有的细腻使她们较于男性作家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自己的生命体验,将宏观的家国变迁糅合在微观的生命体验叙述当中,这使聂华苓的作品有了一定的自传性特征。
聂华苓的作品主题与作者内心的动荡紧密相连,每一部作品都包含着迁徙人的漂泊之感。
1.1 聂华苓的漂泊经历在早期的人类神话当中,“家园”的原型就是伊甸园,那是美好的、让人无忧无虑的天堂。
而从亚当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时开始,人类便开始了漫长的、充满苦楚的漂泊。
对于聂华苓来说,也是如此。
远离家乡,频繁的地理变迁带来了作家的漂泊之感,聂华苓的这种漂泊体验被融会在作品之中。
一方面,作品中的漂泊主题是作者自身漂泊经历的缩影,甚或还原,另一方面,作者又将自身经历进行艺术加工,将情感外化形成文本。
漂泊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难逃的宿命,也是华文文学探讨到台港及海外华文作家时经常提到的议题。
学界公认的是,聂华苓一生经历着两次重大的迁徙,一次是从祖国大陆到台湾,另一次是从台湾到美国爱荷华。
对聂华苓漂泊经历的探讨,也常围绕上述二者,从“逃亡”“流浪”的角度展开。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除了上述两者之外,从童年时期开始,由于家庭原因,聂华苓已经经历过多次的迁徙。
童年时期的漂泊经历给作家幼小的心灵打下深刻的烙印,也影响着作家创作风格的养成。
二十世纪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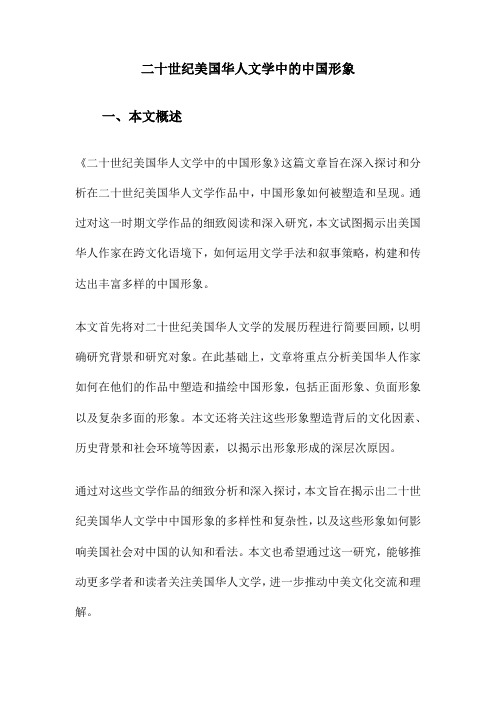
二十世纪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一、本文概述《二十世纪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这篇文章旨在深入探讨和分析在二十世纪美国华人文学作品中,中国形象如何被塑造和呈现。
通过对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细致阅读和深入研究,本文试图揭示出美国华人作家在跨文化语境下,如何运用文学手法和叙事策略,构建和传达出丰富多样的中国形象。
本文首先将对二十世纪美国华人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回顾,以明确研究背景和研究对象。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重点分析美国华人作家如何在他们的作品中塑造和描绘中国形象,包括正面形象、负面形象以及复杂多面的形象。
本文还将关注这些形象塑造背后的文化因素、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等因素,以揭示出形象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通过对这些文学作品的细致分析和深入探讨,本文旨在揭示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文学中中国形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这些形象如何影响美国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和看法。
本文也希望通过这一研究,能够推动更多学者和读者关注美国华人文学,进一步推动中美文化交流和理解。
二、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概览在美国华人文学中,中国形象呈现出丰富多元的面貌。
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华人移民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和文化冲突,也揭示了他们对于故土中国的深情厚意和复杂情感。
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形象在美国华人笔下的变迁与演变。
早期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往往与苦难和落后相关联。
这些作品多描写华人移民在美国遭遇的种族歧视、生活艰辛和文化隔阂,将中国描绘成一个贫穷、落后、需要拯救的形象。
这种描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刻板印象和偏见。
然而,随着华人移民在美国社会地位的提升和文化认同的增强,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开始发生变化。
一些作家开始从更加客观和全面的角度描绘中国,展现出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变迁和人民的生活状态。
他们试图通过文学作品打破刻板印象,向美国读者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多面的中国。
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受到了全球化、跨文化交流等因素的影响。
严歌苓:娴熟驾驭小说可读性与技巧性的作家

认识严歌苓是在南昌大学举行的“首届新移民文学国际研讨会”期间,其时是2014年11月中旬,这离我开始关注并研究她已有整十年时间。
已经功成名就、名利双收的严歌苓,看上去依然是一副清纯模样:大大的眼睛,苗条的身段,及肩的头发松松地自然披散,白白的脸庞,深蓝色的连衣裙,浅色的中长外套,全身上下散发着高雅文静的气息。
虽然早已蜚声海内外,可她依然如此安静低调,毫无霸气外露的迹象,看上去像一个好脾气的邻家大姐姐。
有着大姐姐形象的严歌苓,似乎与“强悍”二字无缘,却能纵横驰骋海外华人文坛,在文学界占据着非常强势的地位,让人不由得心生兴趣,要对其生活与创作一探究竟。
1.个人生活与创作经历才貌双全的严歌苓1958年生于上海,现为美籍华裔小说家、好莱坞编剧。
她同时用中文和英文写作,作品已被译成英、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
7岁离家,13岁参军,成为部队芭蕾舞演员。
1978年,严歌苓发表处女作童话诗《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
1970年代,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严歌苓要求到前线采访写作;1979年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写了一批叙事诗在军区报纸发表;不久被调到铁道兵严歌苓:娴熟驾驭小说可读性与技巧性的作家倪立秋作者近照004cn. All Rights Reserved.政治部担任创作员,结束了舞台生涯,正式成为一名专业作家;后来她把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体验写进小说处女作《七个战士和一个零》中。
1980年,发表电影文学剧本《心弦》,次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影片,二十余岁的严歌苓开始在文坛崛起。
第一任丈夫是李克威,据说两人1986年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写作楼相遇并结婚。
同年加入中国作协,出版长篇《绿血》。
1989年离婚,第一段婚姻只持续了大约两年时间。
1989年底赴美留学后开始向港台文学报刊投稿,获得海外九项文学大奖和两项电影奖。
在美国留学时严歌苓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就读,获艺术硕士学位(MFA–Master of Fine Arts),成为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百年建校史上首位华人校友。
论海外华人文学的形象学研究_游华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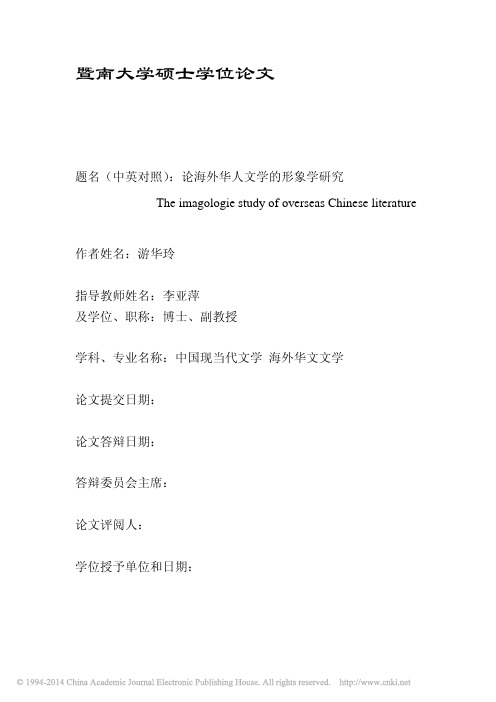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题名(中英对照):论海外华人文学的形象学研究The imagologie study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作者姓名:游华玲指导教师姓名:李亚萍及学位、职称:博士、副教授学科、专业名称: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论文提交日期:论文答辩日期:答辩委员会主席:论文评阅人:学位授予单位和日期:独创性声明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
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暨南大学 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
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签字日期:2012年06月01日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暨南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
本人授权暨南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导师签名:签字日期:2012年06月日签字日期:2012年06月日学位论文作者毕业后去向:工作单位:电话:通讯地址:中文摘要形象学是海外华人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多年来,运用形象学来研究海外华人文学的研究成果颇为可观,本文即以这些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以形象学在海外华人文学研究中的运用为本文考察的主题。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海外华人文学的形象学研究做了分析。
首先,梳理历史脉络,从形象学理论的引入,到后殖民主义形象学的主导,再到学科理论的自觉,海外华人文学的形象学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步入了成熟期。
其次,归纳了海外华人文学形象学研究中的三种形象类型,即自塑形象、异国形象和双重“他者”形象,并分析了各种形象类型研究的特点。
严歌芩书籍推荐:严歌芩的《芳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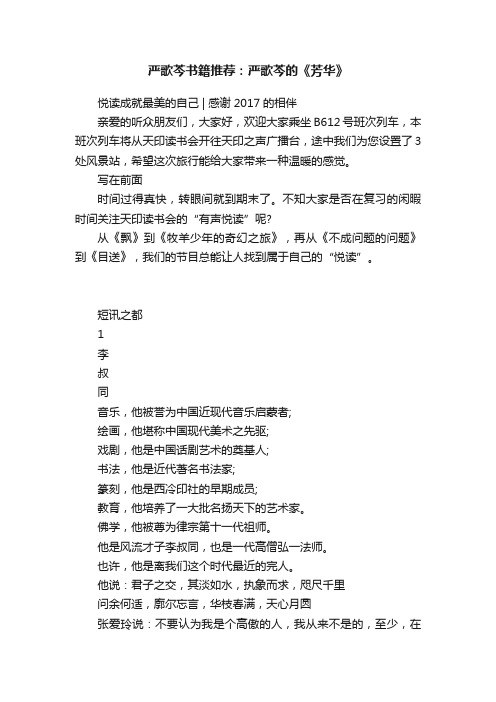
严歌芩书籍推荐:严歌芩的《芳华》悦读成就最美的自己 | 感谢2017的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乘坐B612号班次列车,本班次列车将从天印读书会开往天印之声广播台,途中我们为您设置了3处风景站,希望这次旅行能给大家带来一种温暖的感觉。
写在前面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就到期末了。
不知大家是否在复习的闲暇时间关注天印读书会的“有声悦读”呢?从《飘》到《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再从《不成问题的问题》到《目送》,我们的节目总能让人找到属于自己的“悦读”。
短讯之都1李叔同音乐,他被誉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启蒙者;绘画,他堪称中国现代美术之先驱;戏剧,他是中国话剧艺术的奠基人;书法,他是近代著名书法家;篆刻,他是西冷印社的早期成员;教育,他培养了一大批名扬天下的艺术家。
佛学,他被尊为律宗第十一代祖师。
他是风流才子李叔同,也是一代高僧弘一法师。
也许,他是离我们这个时代最近的完人。
他说: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转围墙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后人说:半世风流半世空,世间再无李叔同在我看来,他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入世的事,每一分做的彻底而不执著,如此,才能活在世间,却不属于他......历史长河里,他是文学家,他也是语言学家,又是教育家、翻译家和我们熟知的散文家,他还精通着12国语言。
他便是,季羡林老先生。
在这一条十分漫长的路上,他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
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
他说,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
他说,如果读书也能算是一个嗜好的话,我的唯一嗜好就是读书。
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
人类之所以能进步,靠的就是能读书又写书的本领。
他说有四句话影响他一生,分别是陈寅恪所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所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梁漱溟所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马寅初所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2季羡林历史长河里,他是文学家,他也是语言学家,又是教育家、翻译家和我们熟知的散文家,他还精通着12国语言。
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论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中国文化书写

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论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中国文化书写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论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中国文化书写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中一直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其独特的历史、哲学和传统艺术形成了一个丰富而多元的文化传统。
作为中国文化的先锋,美国华裔作家通过英语文学书写,将中国故事引入了西方语境。
这些作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经历,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一个窥探中国文化的窗口,并在这种交流中推动了文化的传播和理解。
本文将探讨美国华裔作家在英语文学中对中国文化的书写,并分析这种书写对跨文化交流的意义。
首先,美国华裔作家以自己独特的经历和视角书写中国文化,使其更具有地域性和个性化。
无论是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华裔,还是移民自中国的作家,他们在日常生活和文化体验中都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中国元素。
这些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将个人经历巧妙地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使作品更具有深度和真实性。
他们深入探讨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和传统价值观,揭示了中国文化所承载的丰富内涵。
通过借鉴西方文学的写作技巧,他们将中国文化与西方读者的视角相结合,使作品更具有普遍性和亲近感。
其次,美国华裔作家在英语文学中书写中国文化,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的窗口。
作为英语写作的一部分,这些作品通过西方人的视角和英语的表达方式向读者传递着中国文化的精髓。
由于英语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这些作品能够被更广泛的读者群体所接触。
通过对中国文化的书写,西方读者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
这种文化的交流与理解有助于建立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促进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共存。
最后,美国华裔作家在英语文学中书写中国文化,推动了跨文化交流的发展和文化多样性的传播。
通过他们的作品,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中得以被广泛传播和认同,使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多的关注。
这种文化交流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碰撞,促使文化的传统与创新相结合,创造出更富有活力和多样性的文化现象。
这种丰富多元的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西方文学的内涵,也拓展了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
2015高考作文素材(人物类36):严歌苓《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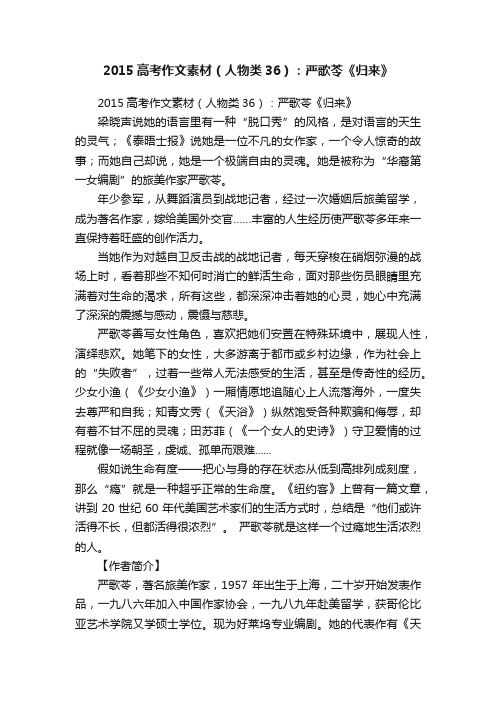
2015高考作文素材(人物类36):严歌苓《归来》2015高考作文素材(人物类36):严歌苓《归来》梁晓声说她的语言里有一种“脱口秀”的风格,是对语言的天生的灵气;《泰晤士报》说她是一位不凡的女作家,一个令人惊奇的故事;而她自己却说,她是一个极端自由的灵魂。
她是被称为“华裔第一女编剧”的旅美作家严歌苓。
年少参军,从舞蹈演员到战地记者,经过一次婚姻后旅美留学,成为著名作家,嫁给美国外交官……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严歌苓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
当她作为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地记者,每天穿梭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时,看着那些不知何时消亡的鲜活生命,面对那些伤员眼睛里充满着对生命的渴求,所有这些,都深深冲击着她的心灵,她心中充满了深深的震撼与感动,震慑与慈悲。
严歌苓善写女性角色,喜欢把她们安置在特殊环境中,展现人性,演绎悲欢。
她笔下的女性,大多游离于都市或乡村边缘,作为社会上的“失败者”,过着一些常人无法感受的生活,甚至是传奇性的经历。
少女小渔(《少女小渔》)一厢情愿地追随心上人流落海外,一度失去尊严和自我;知青文秀(《天浴》)纵然饱受各种欺骗和侮辱,却有着不甘不屈的灵魂;田苏菲(《一个女人的史诗》)守卫爱情的过程就像一场朝圣,虔诚、孤单而艰难......假如说生命有度——把心与身的存在状态从低到高排列成刻度,那么“瘾”就是一种超乎正常的生命度。
《纽约客》上曾有一篇文章,讲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艺术家们的生活方式时,总结是“他们或许活得不长,但都活得很浓烈”。
严歌苓就是这样一个过瘾地生活浓烈的人。
【作者简介】严歌苓,著名旅美作家,1957年出生于上海,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一九八六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一九八九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又学硕士学位。
现为好莱坞专业编剧。
她的代表作有《天浴》、《扶桑》、《少女小渔》、《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等,其中《天浴》由陈冲拍成电影后荣获金马奖最佳影片等七项大奖,一九九九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十大最佳影片。
严歌苓人物素材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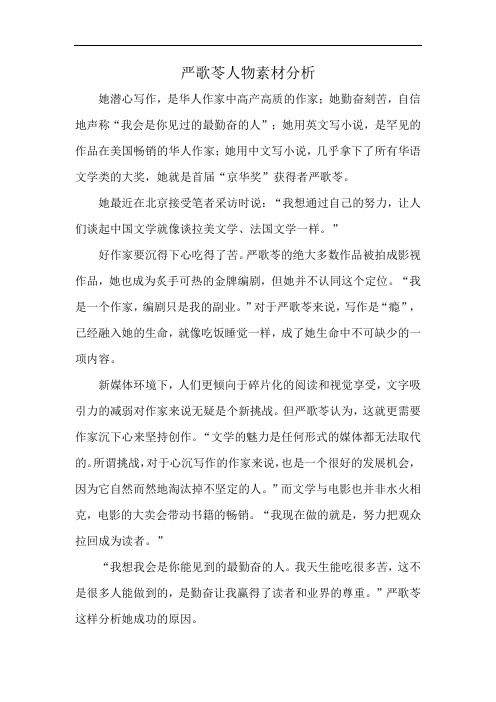
严歌苓人物素材分析
她潜心写作,是华人作家中高产高质的作家;她勤奋刻苦,自信地声称“我会是你见过的最勤奋的人”;她用英文写小说,是罕见的作品在美国畅销的华人作家;她用中文写小说,几乎拿下了所有华语文学类的大奖,她就是首届“京华奖”获得者严歌苓。
她最近在北京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人们谈起中国文学就像谈拉美文学、法国文学一样。
”
好作家要沉得下心吃得了苦。
严歌苓的绝大多数作品被拍成影视作品,她也成为炙手可热的金牌编剧,但她并不认同这个定位。
“我是一个作家,编剧只是我的副业。
”对于严歌苓来说,写作是“瘾”,已经融入她的生命,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成了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
新媒体环境下,人们更倾向于碎片化的阅读和视觉享受,文字吸引力的减弱对作家来说无疑是个新挑战。
但严歌苓认为,这就更需要作家沉下心来坚持创作。
“文学的魅力是任何形式的媒体都无法取代的。
所谓挑战,对于心沉写作的作家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因为它自然而然地淘汰掉不坚定的人。
”而文学与电影也并非水火相克,电影的大卖会带动书籍的畅销。
“我现在做的就是,努力把观众拉回成为读者。
”
“我想我会是你能见到的最勤奋的人。
我天生能吃很多苦,这不是很多人能做到的,是勤奋让我赢得了读者和业界的尊重。
”严歌苓这样分析她成功的原因。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海外华人作家书写中国形象的叙事模式以严歌苓为例[内容摘要]海外华人写作中始终有着浓厚的家国关怀,这既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也是海外华人作家在特殊的文化境遇中做出的文化选择。
而不同的文化身份使得海外华人作家在书写中国形象时有着不同的切入角度和书写模式。
严歌苓作为优秀的华人作家,以历史记忆对中国形象进行了阐释。
[关键词]中国形象;历史记忆;王德威在《想象中国的方法》一书的序言中,这样讲到:“由涕泪飘零到嬉笑怒骂,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之命运,看似无甚枚关,却每有若合符节之处。
在泪与笑之间,小说曾负载着革命与建国等使命,也绝不轻忽风花雪月、饮食男女的重要。
小说的天地兼容并蓄,众生喧哗。
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
”尽管中国形象确实是一个具有多重的矛盾和歧义丛生的概念,但就文学而言,一直都充当这一形象的实践与阐释。
中国文学中一直就有一种极其浓郁的家国关怀,尤其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路途,在强烈的向往与焦虑之中,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书写了自己心中的中国形象:梁启超的理想是一个“少年中国”,在胡适的眼中,古老的中国仿佛是一个沉睡了太久太久的“睡美人”,只有来自西方文明的神奇的一吻方可将其唤醒,而在鲁迅看来,中国是一个无比郁闷的“铁屋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奋力将其摧毁。
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写作者都会在这一维度上留下自己的发言。
“如果从形态的角度来看,所谓文化有两个层次,其一是指精神文化,亦即哲学、宗教、艺术所体现的某种精神意识;其二是指社会文化,亦即某一民族的历史中具体的生活方式、行为结构、社会组织、实用技术、民俗习惯、礼制宗法等,。
不难发现,在对中国形象的呈现中,这种种的文化质素都可以包括在内,正是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形象成为从文化和审美两个层而上理解文学时的一个交汇之处。
海外华人作家,作为在异乡的漂泊者,始终都与身处的社会、文化存在着隔阂与疏离,转身注视曾经的祖国,在时间与空间的重重阻隔之下,也有了别样的出口。
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境遇中,海外华人作家在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上必然有其独到的切入点。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从文本中的中国形象入手,来考察海外华人写作的种种文化心理机制的可能。
本文正是通过对严歌苓这位海外华人作家的典型文本的细读和分析,梳理出在其小说文本中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形象,并通过对其人生遭际和文化心理的把握,力图窥一斑而见全豹,寻找到海外华人作家在书写中国形象时的主要叙事模式。
严歌苓是一位“旅美作家”,她有着长久的大陆成长经历,很小时就作为文艺兵在部队里生活,对那个时代显性的和隐性的规则都有着切实的体会,自九十年代去美国读书生活,可以说,不同的的生活和文化给了她很大的震动,使她的写作在原本就敏感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严歌苓小说中的“中国形象”应该说是在她旅美以后的作品中才清晰起来的,也许只有处身于国外,才会有更多的心志和精力为自己身后的国家所吸引,而在这样的一种迁徙之后,严歌菩在其小说文本中呈现出的“中国形象”更多的具有“历史记忆”的特征。
《人寰》是严歌苓在美国的文化语境中对中国的历史、政治及身在其中的中国人的情感、命运的言说。
小说以一种极富意味的形式展开。
“我”是一个四十五岁的中国女博士,而临毕业,急需工作,和系里的舒茨教授陷入了一场感情纠葛,同时对多年前的记忆耿耿于怀,不能释然。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成就了“我”对“你”的诉说。
我们只知道“你”是一位心理医生。
可以说,心理医生与对心理医生的需要都是美国特色的,由此,这种诉说在文化上转化成了对于美国语境的言说,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的差异中,我们所惯常熟悉的故事才呈现出了别样的意味。
在《人寰》中,故事始终是在多个不同的层而上展开,在纵向上,有对现实境况的书写和对历史遭遇的回忆,在表达方式上,“我”是以英语和汉语两种不同的语言诉说出了不同的故事,即便是涉及到的人,也存在着“我”和父辈两代人的悲欢。
这层层的交错和纠集使小说显得有点扑朔迷离,叙述者在两种文化之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真实与向往之间,呈现出了惆怅和苦涩相间的“中国形象”。
而这种“Talk out”的叙述方式并没有赋予小说文本以行云流水般的流畅,我们从中感觉到了更多的是叙述者而对一种异质文化的为难和突破文化障碍的努力。
“我得先形容这个人。
他是我爸爸的朋友。
我们都这样说:领导。
没有老板,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雇佣关系。
有主人,没有仆人,主人是工人,农民,士兵。
这些词在我们那时的中国是集合名词,具有高度象征性,无法单数或复数。
是我们城市博物馆门口举着榔头、镰刀、步枪的大于真人数倍的两男一女铜塑。
后来一天,三个人变成了四个人,添出一个戴宽边眼镜的男人,手里托一个人造卫星。
这个人也是国家社会的主人,同前而那两男一女一同跨出一个大弓箭步,鼓着和平鸽式的圆饱的胸脯。
这个人是:革命的知识分子。
就是我爸爸的这个朋友。
这样的一种叙述方式在《人寰》中是随处可见的。
因为而对的是对中国的文化历史背景并不熟悉的听众,伴随叙述的是更多的解释,正是在这种解释中,许多从前视为平常的、理所当然的事情也呈现一种略显突兀的特质。
不是太长的一段话中,不得不就“朋友”、“领导”、“主人”做出解释,而在这样的叙述中,简单的事实也有了丰富的涵义。
《人寰》中诸如此类的解释比比皆是。
诉说更多地成为了一种自我辨析,成为了事实和记忆在两种文化中的转换。
“我爸爸的朋友”贺一骑是小说中的中心人物,他和“我”以及和“我爸爸”的关系构成了书写的重点,也正是对于这两种关系的处理凸现出了这样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人格的多而性,映现出了历史和政治风潮在一个个人身上烙下的印记。
这个从前的小乞丐在参加革命后凭借一篇小说《紫愧》获得了文名,小说中的故事是很感人的,其真实性却是极其可疑的。
尽管如此,贺一骑仍不失为一个正直的人,他和“我”父亲相识之时是一个特殊的时刻。
天真的富有文人气的父亲写了一篇可能招致祸端的文章,是蒙受了贺一骑的关照才逃脱了政治上的厄运,这种关照却以父亲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的付出作为代价。
即便是借助政治上的形势,懦弱的父亲跳上台去打了贺一骑一个耳光,却又陷入了对于“背叛”的内疚。
在长久的自我惩罚之后,父亲终于还是不顾妻子和女儿的反对和蔑视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宿命中,听从贺一骑的安排,为他付出了自己最后的时光。
“我”和贺一骑的感情也是小说书写的重点。
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个少女的相互吸引与爱恋。
但严歌苓并没有写就一个中国版本的《洛丽塔》,因为在单纯的感情之外有着如此多的内容。
在长久的浓厚的政治的浸淫中,原本单纯的小女孩也会在情感中搀杂进不无悲凉的因素。
尽管,这样一种解释很有可能是在“我”经历了许多事之后,同时也存在着对自己少女时期的情欲的遮挡心理的解释,可能选择这样的一种解释本身就说明了曾经的生命的灰暗。
对于历史的记忆,甚至一直都影响着“我”的现实生活。
“我”和舒茨教授,不是没有一点真心的,但“我”对于这段感情的开始难以释然。
权力和强迫是无法忽视的,“我”决心逃脱这样一种宿命。
当“我”用英语,这种年轻的语言说出了隐藏在心中的秘密之后,终于有力量逃脱那“主宰、恩典”和“给予、收回”。
“我”在“争取从此做一个正常的人”。
不难看出,在《人寰》中,有关中国形象的呈现是在历史记忆的书写中展开的。
沉重的灰暗的记忆在另外的语言的诉说中得到缓释,中国形象在文化的差异中得以展示。
严歌苓以这样一种方式抒写了她在生活中的经验和身处异国对于中国文化的反思。
杰姆逊曾说“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是那些看起来好象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严歌苓对于“中国形象”的书写,无疑是印证了这一点。
在凭借《扶桑》一举成名之后,严歌苓成为了当代美国的畅销作家。
即便是因为华人身份,她在美国与主流的社会曾存在过一定的隔阂,但其成长经历和最终的成功也说明了严歌苓在美国的文化和现实生活中己经取得了一定的位置。
她的写作更多的是而对美国受众,由于真正的中国生活经验的阀如,严歌苓小说文本中的“中国形象”更多的是一种“历史记忆”。
在这其中,既有她成长中从长辈接受来的传说和印象,也不无对美国人对于中国的神秘想象的某种程度上的迎合。
毕竞,在自我身份的界定上,严歌苓始终认为自己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如果我们对严歌苓小说中的“中国形象”的认识仅只于此,又是远远不够的。
尽管她生于中国长于美国,对于美国的文化价值社会规范有着相当多的认同,中国却始终是她精神上的故乡,小说讲述了中国妓女扶桑,在一个世纪前的美国旧金山,与白人贵族少年的凄美爱情。
扶桑在20岁时被拐卖到旧金山,并与已经成了江洋大盗的“丈夫”相遇,彼此不知情。
最终“丈夫”为了维护“妓女”的尊严,甘心为警方所俘,俩人在死刑场上举行了婚礼。
其间,她与贵族少年的爱情断断续续,重生的美丽在烧杀抢掠和命运飘摇中一次次惨烈地展露……“个人、自我和情感是传统民族志架构难以反映的论题。
而对实验民族志来说,探究这些论题可以使我们进入文化差异的最深层而。
文化差异根植于情感当中,也根植于不同民族对个人和社会关系的本质思考之中。
”“没有对情感和经验的文化差异和表现形式进行细致的考察,我们就无法直接领悟它们的本质,更无法将进行建构的过程中,最终在情感的层而上肯定了中国的文化价值,使她的小说文本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实验民族志的功能。
以上,我以严歌苓的小说文本作为分析的对象,对其中映现出的中国形象做了描述,并以历史记忆和神话想象概括了两种书写中国形象的不同方式。
事实上,这两位作家并不是孤立的。
我们可以说,在严歌苓的背后,有客居英国的张戎和虹影,她们更具自传性质的书写方式,使历史记忆的特征愈发明显,在《鸿》和《饥饿的女儿》中,对于一个过去的疯狂和贫瘩的时代有着更直白的叙述一书中,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移民作家和华裔作家由于不同的生活体验、文化积淀,使他们在体现自己的家国关怀时有了不同的角度和关注焦点,而这一切,集中地体现在了他们所塑造出来的中国形象上。
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如何书写出一个更为全而、立体和丰满的“中国形象’是当代海外华人作家无法回避的历史责任。
应该说,无论是采用历史记忆还是叫话想象的书写方式,都对中国形象有着进构的作用。
历史记忆注重对历史的还原,在严肃的诉说中更具有心理的深度,尤翼是几位移民作家在其小说文本中多半会袋个人的生存记忆与时代相重合,使得个付的诉说转化为对国家和民族的慨叹,最丝获得了对人性思考的广度与深度。
华人与白人的冲突,在文化学和历史学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全球化是现代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走势,而一旦真的有朝一日“天下大同”郎鸟托邦成为现实,如何体现文化的差异将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
在这样的文化垮越中,对于中国形象的阐释成为保存中国夕化特质的重要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