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舞蹈的现实价值【论当代女性文学“身体叙事”的价值】
舞蹈创作中的文学艺术表现手法

舞蹈创作中的文学艺术表现手法一、舞蹈创作中的叙事手法在舞蹈创作中,叙事手法是舞者们常常采用的表现手法之一。
通过音乐、舞蹈动作、舞台布景等多种元素的结合,舞者们可以展现出不同的情节和故事情感。
这种叙事手法往往与文学创作中的叙事手法相似,通过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塑造、时间、空间等元素的安排,来表达出舞者们想要呈现的主题和情感。
叙事舞蹈作品中的情感表达通常更加直观、贴近观众的情感共鸣,舞者们通过具象的舞蹈动作和形象的呈现,将叙事中的情感表达得更加深刻。
叙事舞蹈作品也对编舞者和舞者的技巧要求更高,需要他们对情节的把握和舞蹈技巧的运用有更高的要求,以表达出故事情节所要传达的内涵。
二、舞蹈创作中的象征手法象征手法在文学创作中常常被运用,而在舞蹈中同样缺不可少。
通过具体的动作、姿势和舞蹈动作的联想,舞者们可以用舞蹈形式来表达出抽象的概念和情感。
这种象征手法使得舞蹈作品可以有更加深刻、抽象的表现形式,而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情节和故事。
象征主题的舞蹈作品常常更加适合展现抽象的主题和情感,舞者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动作和表情来传达出一种抽象的内涵,使得观众在观赏舞蹈作品的时候更加有自由的想象空间。
通过对象征手法的运用,舞者们可以将舞蹈作品的内涵和情感传达的更加丰富和深刻。
三、舞蹈创作中的对话手法对话手法是一种舞者之间或舞者与观众之间通过语言或者动作进行交流的一种表演形式。
在舞蹈创作中,对话手法常常会与舞蹈动作和舞台布景相结合,以呈现出一种更加立体的表达形式。
这种对话手法使得舞蹈作品的表达形式更加多样化,也更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
对话手法在舞蹈创作中可以体现出舞者们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也可以体现出舞者与观众之间的沟通和情感的传递。
这种对话手法的运用使得舞蹈作品更富有情感和故事性,也更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和情感共鸣。
意象手法的运用使得舞蹈作品更具有审美性和艺术性,也更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和情感共鸣。
舞者们可以通过对意象的选择和表达,使得舞蹈作品更加丰富和深刻,也更富有艺术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的女性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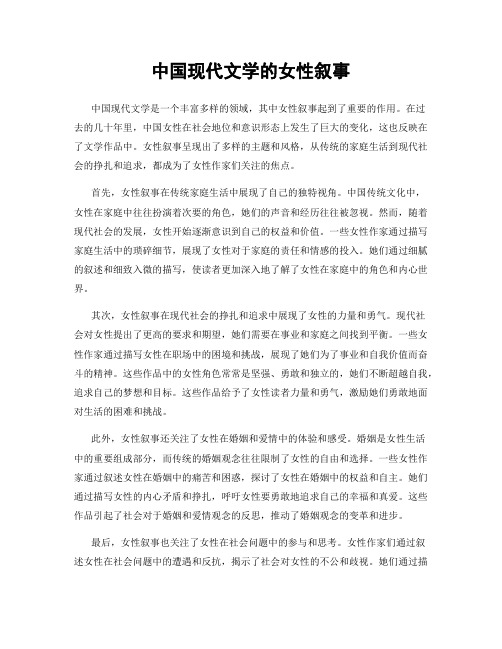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的女性叙事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丰富多样的领域,其中女性叙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女性在社会地位和意识形态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反映在了文学作品中。
女性叙事呈现出了多样的主题和风格,从传统的家庭生活到现代社会的挣扎和追求,都成为了女性作家们关注的焦点。
首先,女性叙事在传统家庭生活中展现了自己的独特视角。
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在家庭中往往扮演着次要的角色,她们的声音和经历往往被忽视。
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女性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权益和价值。
一些女性作家通过描写家庭生活中的琐碎细节,展现了女性对于家庭的责任和情感的投入。
她们通过细腻的叙述和细致入微的描写,使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内心世界。
其次,女性叙事在现代社会的挣扎和追求中展现了女性的力量和勇气。
现代社会对女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她们需要在事业和家庭之间找到平衡。
一些女性作家通过描写女性在职场中的困境和挑战,展现了她们为了事业和自我价值而奋斗的精神。
这些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常常是坚强、勇敢和独立的,她们不断超越自我,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这些作品给予了女性读者力量和勇气,激励她们勇敢地面对生活的困难和挑战。
此外,女性叙事还关注了女性在婚姻和爱情中的体验和感受。
婚姻是女性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传统的婚姻观念往往限制了女性的自由和选择。
一些女性作家通过叙述女性在婚姻中的痛苦和困惑,探讨了女性在婚姻中的权益和自主。
她们通过描写女性的内心矛盾和挣扎,呼吁女性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真爱。
这些作品引起了社会对于婚姻和爱情观念的反思,推动了婚姻观念的变革和进步。
最后,女性叙事也关注了女性在社会问题中的参与和思考。
女性作家们通过叙述女性在社会问题中的遭遇和反抗,揭示了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和歧视。
她们通过描写女性在社会问题中的角色和经历,呼吁社会对女性的关注和尊重。
这些作品使人们意识到女性在社会进步和改革中所起到的作用和价值,促进了性别平等的发展。
身体叙事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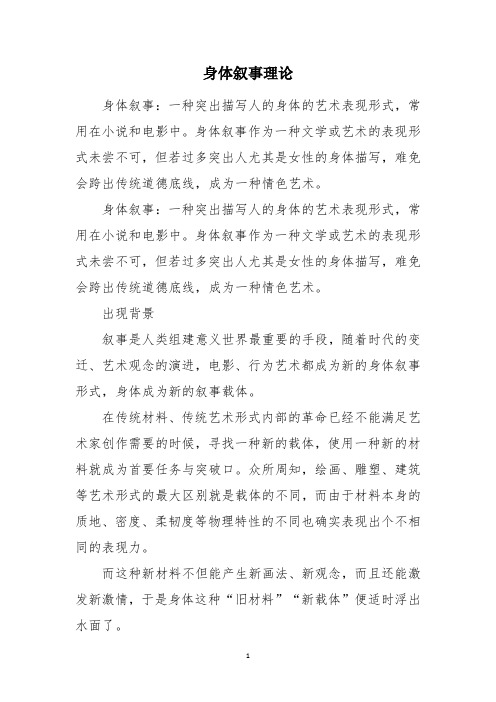
身体叙事理论身体叙事:一种突出描写人的身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常用在小说和电影中。
身体叙事作为一种文学或艺术的表现形式未尝不可,但若过多突出人尤其是女性的身体描写,难免会跨出传统道德底线,成为一种情色艺术。
身体叙事:一种突出描写人的身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常用在小说和电影中。
身体叙事作为一种文学或艺术的表现形式未尝不可,但若过多突出人尤其是女性的身体描写,难免会跨出传统道德底线,成为一种情色艺术。
出现背景叙事是人类组建意义世界最重要的手段,随着时代的变迁、艺术观念的演进,电影、行为艺术都成为新的身体叙事形式,身体成为新的叙事载体。
在传统材料、传统艺术形式内部的革命已经不能满足艺术家创作需要的时候,寻找一种新的载体,使用一种新的材料就成为首要任务与突破口。
众所周知,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形式的最大区别就是载体的不同,而由于材料本身的质地、密度、柔韧度等物理特性的不同也确实表现出个不相同的表现力。
而这种新材料不但能产生新画法、新观念,而且还能激发新激情,于是身体这种“旧材料”“新载体”便适时浮出水面了。
具备条件作为一个隐讳的名词,身体与肉体(flesh)、裸体(nude)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
肉体是身体最粗浅的层面,从生理学角度而言,它代表的是无色情、无感官肉欲的医学和解剖学的对象。
裸体给人的模糊印象并不是蜷缩和无助的躯体,而是一种平衡、丰饶和自信的躯体:重构的躯体。
行为中的身体多为裸体,而裸体诉说的是被剥光了衣服,暗指绝大多数人都会感到的“被看”的、窘迫的状况,也是人最本真、最自然、最未被物质世界污染的状态,当然更是人在被动情景中直视自身、审查自身的契机。
同时,身体又集合了社会观念的诸种因素:艺术、政治、人性、道德、甚至宗教都被整一性地思考。
它连接了社会的道德标准和公众的审美习惯,又反映了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原则,同时还刺激着政府的法规政策和社会禁忌。
双重身份在叙事过程中,身体是行动的主体也是叙事的主体。
它是展现行为的载体,也是叙事的承担者。
现实题材舞蹈叙事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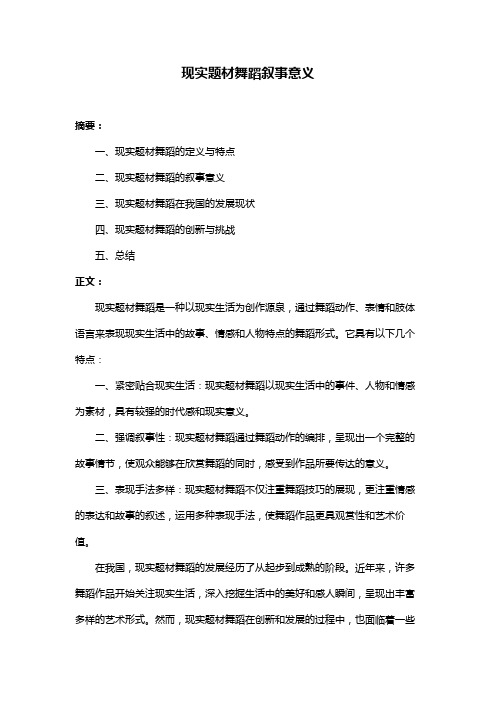
现实题材舞蹈叙事意义摘要:一、现实题材舞蹈的定义与特点二、现实题材舞蹈的叙事意义三、现实题材舞蹈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四、现实题材舞蹈的创新与挑战五、总结正文:现实题材舞蹈是一种以现实生活为创作源泉,通过舞蹈动作、表情和肢体语言来表现现实生活中的故事、情感和人物特点的舞蹈形式。
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紧密贴合现实生活:现实题材舞蹈以现实生活中的事件、人物和情感为素材,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
二、强调叙事性:现实题材舞蹈通过舞蹈动作的编排,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使观众能够在欣赏舞蹈的同时,感受到作品所要传达的意义。
三、表现手法多样:现实题材舞蹈不仅注重舞蹈技巧的展现,更注重情感的表达和故事的叙述,运用多种表现手法,使舞蹈作品更具观赏性和艺术价值。
在我国,现实题材舞蹈的发展经历了从起步到成熟的阶段。
近年来,许多舞蹈作品开始关注现实生活,深入挖掘生活中的美好和感人瞬间,呈现出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
然而,现实题材舞蹈在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首先,现实题材舞蹈的创作难度较大。
舞者需要在掌握舞蹈技巧的基础上,深刻理解作品的主题和情感,将生活中的细节融入舞蹈动作中,使作品更具真实感和感染力。
其次,现实题材舞蹈的审美需求多样化。
观众对于现实题材舞蹈的期待不断提高,既要看到舞蹈作品的创新和突破,又要体现出舞蹈艺术的价值。
如何在满足观众审美需求的同时,保持现实题材舞蹈的独特性和深刻性,是创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面对挑战,现实题材舞蹈创作者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深入生活、挖掘题材,以更具时代特色和艺术价值的作品回馈观众。
总之,现实题材舞蹈作为一种具有强烈叙事意义的艺术形式,在我国舞蹈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论90年代女性“身体叙事”小说的身体意象

论90年代女性“身体叙事”小说的身体意象作者:薛国栋来源:《陕西教育·高教版》2009年第05期9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了一种抢眼且颇具争议的文学现象——“身体叙事”。
在女性作家笔下“身体”成为了她们向男权文化宣战的一支鲜明旗帜。
她们把长期受压抑,受限制的“身体”当作了新的写作对象和手段,以身体来叙事,将叙事的笔触延伸到了长期以来禁锢的叙事禁区——身体以及与身体有关的感官体验。
女性话语下的身体意象什么是女性话语呢?笔者认为女性话语就是指以女性自己的立场关注女性的存在和发展的话语。
中国女性作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情景下,从陈染、林白的私人化书写到卫慧、棉棉的享受身体现象的出现,再到目前木子美、竹影清瞳等通过网络媒体将其游戏一样的展示,她们分别将为身体意象同精神,欲望,消费,物质联系在了一起。
1.陈染、林白的“灵与肉”的融合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的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私人写作”,从深度上和规模上都比80年代前进了一步,她们开始把男性在创作的文本中放逐到女性意识所支配下,只写女性个人经验生活以及个人相关的身体、欲望,力图通过女人自己的目光,自己认识自己的躯体,将身体,性,女性体验,自我经历坦诚的放在阅读的文本中。
陈染、林白的私人写作是精神的自由表达,体现了“灵与肉”的融合。
作者并不把身体展示当作目的而是把身体描写当作反抗男权文化的一种意识手段,精神仍是她们创作的主题。
陈染的作品常选用“镜子”来使女性自己认知自己,来逃离男性的视角。
《无处告别》中,男性眼里,瘦骨伶仃的黛二小姐,则在镜前看到了美:“她把手在自己弱不禁风的躯体上抚摸一下,一根根肋骨犹如绷紧的琴弦,身上除了骨架上一层很薄的脂肪……然后一双饱满的乳房却在黛二小姐瘦骨伶仃的胸前绽开。
”这种带有诗意化的描述,从而也使读者感觉到了女性身体那种独特的美,更凸显出了对男权文化的反叛。
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中,讲述了一个女人的内心生活,多米是一个逃避生活的女人,但又同时挚爱生活。
中国当代舞蹈作品的多视角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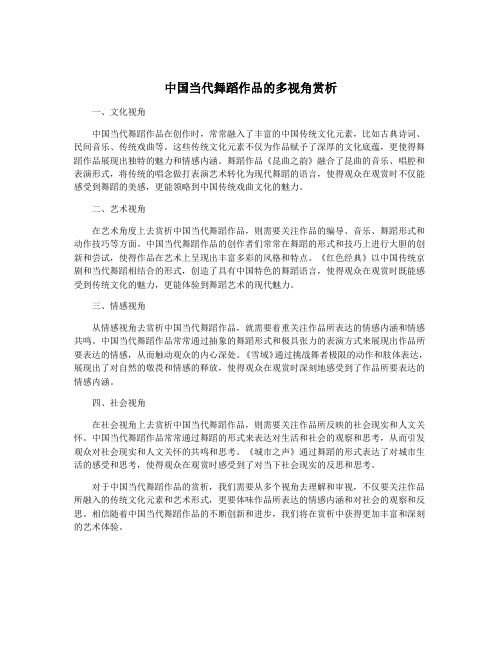
中国当代舞蹈作品的多视角赏析一、文化视角中国当代舞蹈作品在创作时,常常融入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比如古典诗词、民间音乐、传统戏曲等。
这些传统文化元素不仅为作品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更使得舞蹈作品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和情感内涵。
舞蹈作品《昆曲之韵》融合了昆曲的音乐、唱腔和表演形式,将传统的唱念做打表演艺术转化为现代舞蹈的语言,使得观众在观赏时不仅能感受到舞蹈的美感,更能领略到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二、艺术视角在艺术角度上去赏析中国当代舞蹈作品,则需要关注作品的编导、音乐、舞蹈形式和动作技巧等方面。
中国当代舞蹈作品的创作者们常常在舞蹈的形式和技巧上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尝试,使得作品在艺术上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风格和特点。
《红色经典》以中国传统京剧和当代舞蹈相结合的形式,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舞蹈语言,使得观众在观赏时既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更能体验到舞蹈艺术的现代魅力。
三、情感视角从情感视角去赏析中国当代舞蹈作品,就需要着重关注作品所表达的情感内涵和情感共鸣。
中国当代舞蹈作品常常通过抽象的舞蹈形式和极具张力的表演方式来展现出作品所要表达的情感,从而触动观众的内心深处。
《雪域》通过挑战舞者极限的动作和肢体表达,展现出了对自然的敬畏和情感的释放,使得观众在观赏时深刻地感受到了作品所要表达的情感内涵。
四、社会视角在社会视角上去赏析中国当代舞蹈作品,则需要关注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和人文关怀。
中国当代舞蹈作品常常通过舞蹈的形式来表达对生活和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从而引发观众对社会现实和人文关怀的共鸣和思考。
《城市之声》通过舞蹈的形式表达了对城市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使得观众在观赏时感受到了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反思和思考。
对于中国当代舞蹈作品的赏析,我们需要从多个视角去理解和审视,不仅要关注作品所融入的传统文化元素和艺术形式,更要体味作品所表达的情感内涵和对社会的观察和反思。
相信随着中国当代舞蹈作品的不断创新和进步,我们将在赏析中获得更加丰富和深刻的艺术体验。
身体书写的文化——当代舞剧创作走向

身体书写的文化——当代舞剧创作走向陈雪飞【摘要】Where am Ⅰ from? Where will Ⅰ fly? This is the ultimate question the dance drama Peacock on the theme of life, and is the question of present creation trend of Chinese dance drama. As an independent style, the "new dance drama" constitutes China' s new theatric art together with the new opera and the new modern drama. From the new carrier of cultural enlightenment, the revolutionary art, the aesthetic carrier to the cultural and economic carrier, the dance drama experiences the development from the combination with the national aesthetic, highlighting the mod-ern connotation with humanistic care to a win-win of art and commerce. It i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ance drama to pursue the noumenon of ar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art and commerce is the trend.%"我" 从哪里来? 要飞向哪里去? 是舞剧《孔雀》关于生命主题的终极之问, 也是现阶段中国舞剧创作走向之问. 作为独立文体的 "新舞剧" 与新歌剧、新话剧构成中国新演剧, 从文化启蒙新载体到革命文艺载体, 再到审美载体和文化经济载体, 舞剧艺术经历了与民族审美融合、以人性关怀彰显现代内涵和力求艺术与商业双赢的发展. 舞剧艺术可以概括为: 对艺术本体的追求是其发展的核心动力, 商业与艺术的融合也一定是大势所趋.【期刊名称】《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年(卷),期】2015(013)001【总页数】8页(P69-75,83)【关键词】民族;舞剧;创作审美;艺术【作者】陈雪飞【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金华 32100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J723“我”从哪里来?要飞向哪里去?是舞剧《孔雀》关于爱和生命主题的终极之问,此问也是现阶段中国舞剧创作走向之问,更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文化命题。
现代舞蹈的身体语言与情感表达

现代舞蹈的身体语言与情感表达现代舞蹈作为一种独特的舞蹈形式,强调个体表达和情感传达,其身体语言和情感表达特点立足于当代社会背景下的审美需求与艺术表现。
本文将探讨现代舞蹈中的身体语言与情感表达,并思考其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一、身体语言的多样性1. 舞者身体的动态美感现代舞蹈舞者在舞台上用自由的身体动作展现出独特的美感。
舞者的肢体舞动、肌肉线条等元素,都构成了他们个体身体美的表达。
灵活的身姿、独特的身体扭曲和肢体的伸展,展示了身体语言的多样性。
2. 动作的创新与变异现代舞蹈强调对动作的创新和变异,舞者可以依照自己的感受和主题要求,将经典舞蹈动作进行改编和重新解释。
他们通过身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独特审美观和情感体验,从而赋予舞蹈以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3. 肢体表达的自由性在现代舞蹈中,肢体的表达并不受束缚于固定的技法和形式,而是注重身体的自由性。
舞蹈家不再局限于特定的舞蹈语汇,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艺术创作需求,通过个体的身体动作来与观众建立情感联系。
二、情感表达的方式现代舞蹈注重舞者内心情感的表达,舞者可以通过身体动作展示出对内心情感状态的理解和描绘。
他们可以通过情感的内省,用舞蹈将自己的情感状态直观地呈现给观众,使观众能够与舞者建立起情感共鸣。
2. 舞蹈作品的主题情感表达现代舞蹈作品通常都有明确的主题和情感目标。
舞者通过自己的身体语言和技巧,将主题所代表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比如,当一位舞者通过身体的姿势、肢体动作等来表达悲伤和绝望时,观众能够感受到舞蹈作品传递出的深深的情感内涵。
3. 观众情感的激发与共鸣现代舞蹈通过舞蹈作品中独特的身体语言和情感表达,可以激发观众自身情感的共鸣,让他们在观看舞蹈的过程中产生共鸣和情感共振。
观众可以通过对舞者舞蹈动作和姿态的理解和感受,善于用自己的情感冲击来理解舞者所传递的情感信息。
三、现代舞蹈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1. 艺术价值的突显现代舞蹈将身体语言和情感表达融为一体,使舞蹈艺术更加丰富和多元化。
文学作品与舞蹈艺术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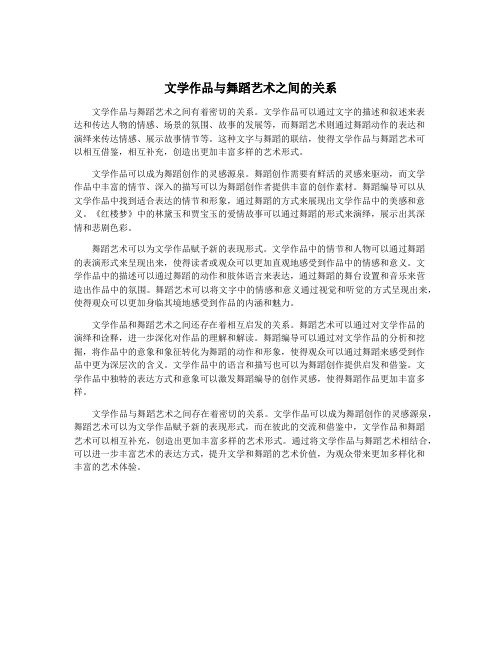
文学作品与舞蹈艺术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与舞蹈艺术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学作品可以通过文字的描述和叙述来表达和传达人物的情感、场景的氛围、故事的发展等,而舞蹈艺术则通过舞蹈动作的表达和演绎来传达情感、展示故事情节等。
这种文字与舞蹈的联结,使得文学作品与舞蹈艺术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创造出更加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
文学作品可以成为舞蹈创作的灵感源泉。
舞蹈创作需要有鲜活的灵感来驱动,而文学作品中丰富的情节、深入的描写可以为舞蹈创作者提供丰富的创作素材。
舞蹈编导可以从文学作品中找到适合表达的情节和形象,通过舞蹈的方式来展现出文学作品中的美感和意义。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故事可以通过舞蹈的形式来演绎,展示出其深情和悲剧色彩。
舞蹈艺术可以为文学作品赋予新的表现形式。
文学作品中的情节和人物可以通过舞蹈的表演形式来呈现出来,使得读者或观众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作品中的情感和意义。
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可以通过舞蹈的动作和肢体语言来表达,通过舞蹈的舞台设置和音乐来营造出作品中的氛围。
舞蹈艺术可以将文字中的情感和意义通过视觉和听觉的方式呈现出来,使得观众可以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作品的内涵和魅力。
文学作品和舞蹈艺术之间还存在着相互启发的关系。
舞蹈艺术可以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演绎和诠释,进一步深化对作品的理解和解读。
舞蹈编导可以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和挖掘,将作品中的意象和象征转化为舞蹈的动作和形象,使得观众可以通过舞蹈来感受到作品中更为深层次的含义。
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和描写也可以为舞蹈创作提供启发和借鉴。
文学作品中独特的表达方式和意象可以激发舞蹈编导的创作灵感,使得舞蹈作品更加丰富多样。
文学作品与舞蹈艺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文学作品可以成为舞蹈创作的灵感源泉,舞蹈艺术可以为文学作品赋予新的表现形式,而在彼此的交流和借鉴中,文学作品和舞蹈艺术可以相互补充,创造出更加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
通过将文学作品与舞蹈艺术相结合,可以进一步丰富艺术的表达方式,提升文学和舞蹈的艺术价值,为观众带来更加多样化和丰富的艺术体验。
《2024年舞剧叙事性研究》范文

《舞剧叙事性研究》篇一一、引言舞剧作为综合了舞蹈、音乐、戏剧、美术等多种艺术形式的表演艺术,其叙事性在表达故事、传达情感、塑造人物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
本文旨在通过对舞剧叙事性的研究,探讨其表达方式、特点及价值,以期为舞剧创作和欣赏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二、舞剧叙事性的表达方式1. 舞蹈语言:舞蹈是舞剧叙事的核心,通过动作、姿态、节奏等元素,将故事情节、人物性格、情感变化等表现出来。
舞蹈语言的运用要符合剧情需要,具有表现力和感染力。
2. 音乐与音响:音乐和音响在舞剧中起着烘托气氛、推动剧情、刻画人物等作用。
通过音乐的旋律、节奏、音色等元素,以及音响的配合,使观众更好地理解剧情和人物。
3. 舞台美术:舞台美术包括布景、灯光、服装、道具等元素,为舞剧提供了表演的场景和空间。
舞台美术的设计要符合剧情需要,为观众营造出适合故事发展的环境。
4. 戏剧结构:戏剧结构是舞剧叙事的基础,通过合理的情节安排、矛盾冲突、高潮悬念等手法,使故事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舞剧叙事性的特点1. 抽象性与具象性的结合:舞剧通过舞蹈、音乐、舞台美术等手段,将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转化为抽象的艺术形象,使观众在观赏过程中产生共鸣和联想。
2. 时间与空间的综合性:舞剧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通过舞蹈、音乐、布景等元素的综合运用,展现出丰富的时间和空间变化,使观众感受到剧情的紧凑和丰富。
3. 情感表达的深刻性:舞剧通过舞蹈、音乐等手段,将人物的情感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使观众在观赏过程中感受到情感的共鸣和震撼。
四、舞剧叙事性的价值1. 艺术价值的提升:舞剧叙事性的表达方式多样,使舞剧成为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艺术形式。
通过研究舞剧叙事性,可以更好地理解舞剧的艺术价值和美学特征。
2. 文化传承的功能:舞剧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形式,可以承载和传承一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化传统。
通过舞剧叙事性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和传承一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化。
3. 观众审美的满足:舞剧叙事性的表达方式可以使观众在观赏过程中得到美的享受和情感的满足。
《2024年舞剧叙事性研究》范文

《舞剧叙事性研究》篇一一、引言舞剧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以舞蹈为主要表现手段,通过音乐、服装、舞台布景等元素的配合,将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以及情感表达以动态的形式展现出来。
叙事性作为舞剧的重要特征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文将就舞剧叙事性的概念、特点、研究方法及价值进行深入研究。
二、舞剧叙事性的概念及特点1. 概念:舞剧叙事性是指通过舞蹈语言、音乐、服装、舞台布景等元素,将故事情节、人物关系以及情感变化以动态的形式呈现出来,使观众能够理解并感受到故事内容的过程。
2. 特点:(1)综合性:舞剧叙事性需要综合运用舞蹈、音乐、服装、舞台布景等多种艺术手段,以实现故事的完整呈现。
(2)动态性:舞剧叙事性以动态的形式展现故事情节,通过舞蹈动作的变化、音乐节奏的转换等手段,使故事情节得以发展。
(3)情感性:舞剧叙事性注重情感表达,通过舞蹈动作、音乐以及舞台布景等手段,使观众能够感受到故事中人物的情感变化。
三、舞剧叙事性的研究方法1. 文本分析法:通过对舞剧剧本、舞蹈动作、音乐等元素的深入分析,了解舞剧的叙事结构、人物形象以及情感表达。
2. 观演法:通过观看舞剧表演,了解舞剧的舞台布景、灯光效果以及观众的反应,从而对舞剧叙事性进行深入研究。
3. 跨学科研究法:结合舞蹈学、戏剧学、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舞剧叙事性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
四、舞剧叙事性的价值1. 文化传承:舞剧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能够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使观众在欣赏舞剧的过程中了解不同文化的特点和价值。
2. 情感表达:舞剧叙事性注重情感表达,能够使观众感受到故事中人物的情感变化,从而产生共鸣和情感共鸣。
3. 艺术审美:舞剧以舞蹈为主要表现手段,通过音乐、服装、舞台布景等元素的配合,使观众在欣赏过程中获得美的享受和审美体验。
4. 创新性:舞剧叙事性具有创新性,通过运用新的舞蹈语言、音乐以及舞台布景等手段,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艺术体验。
五、舞剧叙事性的实例分析以某部具有代表性的舞剧为例,从剧本结构、舞蹈动作、音乐以及舞台布景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其叙事性的特点及表现手法。
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躯体化”文本叙事范式的审美流变

绎的 “ 前身体 写 作 ” 虽 说 在 身体 写 作 上做 出 了
自己的 独到 贡献 而又 显 露 出 无 法 弥 补 的先 天 缺
陷 ;卫 慧 、棉 棉 所 扮 演 的 “ 身体 写 作 ” 却 使 后 女性 主题 的欲 望 化 舞 蹈 得 以 复 杂 化 彰 显 ;王 安
忆对 于母 系重 塑 有 着 理性 的掌 控 ;赵玫 、蒋 韵 以性灵 突显 的 方式 挖 掘 女 性 历 史 模 本 ;张 洁对
21 00年第 2期 ( 总第 3 ) 9期
21 00年 4月
广 州 广播 电视 大 学 学 报
J U N L O U NG H U O E N V R I Y O R A F G A Z O P N U I E ST
Vo.1 . 1 O No 2 Ap . 01 r2 0
“ 隐私 窥探 ” 等文本 模式 正渐趋 演绎 为众 多女 性
作家 群体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的创 作姿态 、叙 写策 略和审美 品位 。
一
诸 多女性作 家 及 其 文 学 作 品 皆 闪 亮 登 场 、争 奇
斗妍 、绚 丽多姿 而 争 相 张扬 为 世 纪 之 交 文 苑 笔 触 的一道 独 特 的 艺 术 景 观 。为此 ,新 生 代 女 性 在九 十年代 的写作 向 度 的获 取 既 与 中 国女 性 在 历史 、现实 中的处 境 密切 相 关 又是 承受 西 方 女 性 主义理 论所 浸 染 的生 命 结 晶。然 则 女 性 自身 的书写 主 要 包 括 以 一 种 前 所 未 有 的笔 触 体 认 、 描绘 、讴 歌女性 的 生 命 本 体 或 希 冀 从 岁 月 的 痛 苦深 渊 中重 新 打 捞 起 女 性 的深 层 生 命 体 验 以及 试 图在 既往 的 以男 性 为 中心 的 阳 刚谱 系 之 外 抒 发女性 的生 命 感 喟 。诸 如林 白、陈 染 、海 男 演
《2024年舞剧叙事性研究》范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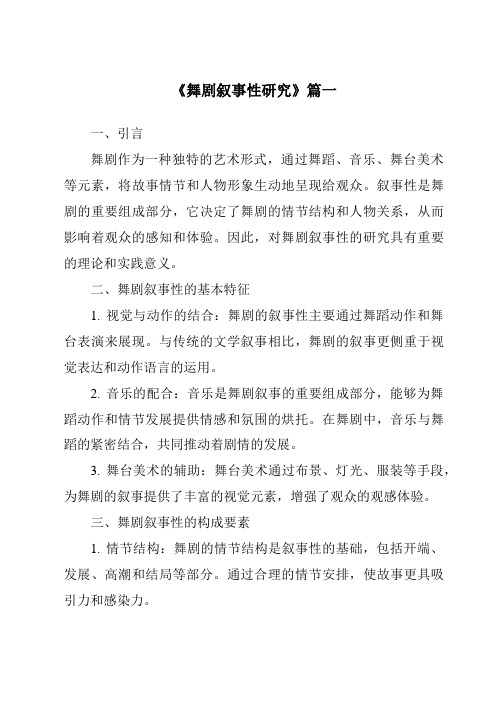
《舞剧叙事性研究》篇一一、引言舞剧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通过舞蹈、音乐、舞台美术等元素,将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生动地呈现给观众。
叙事性是舞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决定了舞剧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关系,从而影响着观众的感知和体验。
因此,对舞剧叙事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舞剧叙事性的基本特征1. 视觉与动作的结合:舞剧的叙事性主要通过舞蹈动作和舞台表演来展现。
与传统的文学叙事相比,舞剧的叙事更侧重于视觉表达和动作语言的运用。
2. 音乐的配合:音乐是舞剧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舞蹈动作和情节发展提供情感和氛围的烘托。
在舞剧中,音乐与舞蹈的紧密结合,共同推动着剧情的发展。
3. 舞台美术的辅助:舞台美术通过布景、灯光、服装等手段,为舞剧的叙事提供了丰富的视觉元素,增强了观众的观感体验。
三、舞剧叙事性的构成要素1. 情节结构:舞剧的情节结构是叙事性的基础,包括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等部分。
通过合理的情节安排,使故事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2. 人物形象:人物形象是舞剧叙事的核心,通过舞蹈动作、音乐和舞台美术等手段,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性格特点。
3. 舞蹈语言:舞蹈语言是舞剧叙事的主要手段,通过不同的舞蹈动作、技巧和编排,传达出不同的情感和意境。
四、舞剧叙事性的表现手法1. 运用多媒体手段:现代舞剧常运用多媒体手段,如投影、灯光等,增强舞台效果,使叙事更加生动形象。
2. 融合其他艺术形式:舞剧可以与其他艺术形式如戏剧、音乐等相结合,共同构建一个完整的叙事体系。
3. 创新编排手法:通过独特的舞蹈编排和动作设计,使舞剧的叙事更加丰富多样,增强观众的观感体验。
五、舞剧叙事性的实例分析以某部具有代表性的舞剧为例,分析其叙事性的表现手法和特点。
具体包括剧情简介、人物形象、舞蹈动作、音乐和舞台美术等方面的分析,探讨其如何通过这些元素构建一个完整的叙事体系。
六、舞剧叙事性的发展趋势与挑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众需求的多样化,舞剧的叙事性也在不断发展和创新。
舞蹈创作与文学作品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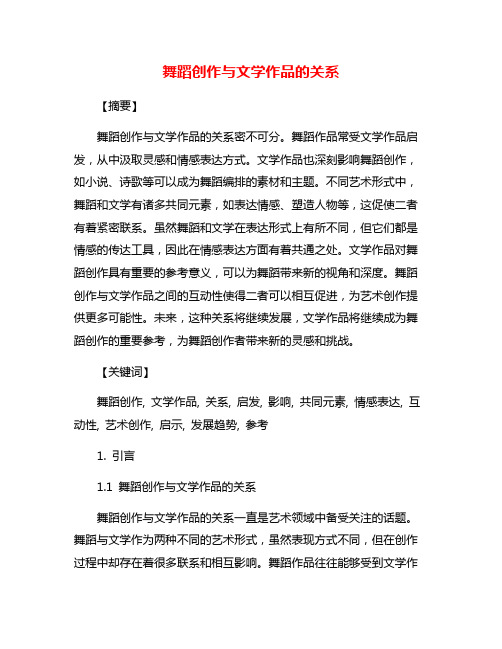
舞蹈创作与文学作品的关系【摘要】舞蹈创作与文学作品的关系密不可分。
舞蹈作品常受文学作品启发,从中汲取灵感和情感表达方式。
文学作品也深刻影响舞蹈创作,如小说、诗歌等可以成为舞蹈编排的素材和主题。
不同艺术形式中,舞蹈和文学有诸多共同元素,如表达情感、塑造人物等,这促使二者有着紧密联系。
虽然舞蹈和文学在表达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情感的传达工具,因此在情感表达方面有着共通之处。
文学作品对舞蹈创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可以为舞蹈带来新的视角和深度。
舞蹈创作与文学作品之间的互动性使得二者可以相互促进,为艺术创作提供更多可能性。
未来,这种关系将继续发展,文学作品将继续成为舞蹈创作的重要参考,为舞蹈创作者带来新的灵感和挑战。
【关键词】舞蹈创作, 文学作品, 关系, 启发, 影响, 共同元素, 情感表达, 互动性, 艺术创作, 启示, 发展趋势, 参考1. 引言1.1 舞蹈创作与文学作品的关系舞蹈创作与文学作品的关系一直是艺术领域中备受关注的话题。
舞蹈与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虽然表现方式不同,但在创作过程中却存在着很多联系和相互影响。
舞蹈作品往往能够受到文学作品的启发,从中汲取灵感和情感,为舞蹈创作注入新的元素和意义。
文学作品也可以影响舞蹈创作的方向和主题,启发舞者们表达更加深刻的情感和观念。
舞蹈和文学在情感表达、意义传达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元素,如节奏、情绪、人物塑造等,这种共通点为两者之间的互相借鉴和交流提供了基础。
舞蹈作品和文学作品的情感表达方式也有所不同,舞蹈更加直观感性,而文学更加抽象理性,但二者都是通过情感来引发观众的共鸣和思考。
舞蹈创作与文学作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二者之间的互动性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无限可能。
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探讨舞蹈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为艺术创作带来更多的新思维和创意。
2. 正文2.1 舞蹈作品如何受文学作品启发文学作品是人类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情感经常会激发舞蹈创作者的灵感,影响他们的作品创作。
行为艺术中的身体叙事详细内容

行为艺术中的身体叙事详细内容【摘要】行为艺术是一种以身体行动为媒介的艺术形式,身体叙事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通过身体的动作、姿势和表情等,艺术家能够传达丰富的情感和意义。
身体叙事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表现,例如舞蹈、肢体语言等。
在行为艺术中,身体叙事不仅是一种表达方式,更是一种符号,具有深刻的意义和隐喻。
观众在面对身体叙事时,会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和体验,这种互动与交流是行为艺术的独特魅力所在。
身体叙事在行为艺术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其丰富的表现形式和深刻的意义给艺术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
未来,随着人们对身体表达和情感交流的需求不断增长,身体叙事在行为艺术中的价值将会得到更多的肯定与发展。
【关键词】行为艺术,身体叙事,角色,表现形式,情感表达,符号意义,观众体验,价值,未来发展,总结。
1. 引言1.1 行为艺术的定义行为艺术是一种当代艺术形式,强调艺术家以行动方式创作并呈现作品,其中艺术家的身体是最重要的媒介。
行为艺术作品常常通过身体动作、表情、声音等方式来传达艺术家的思想、情感和观念,以及与观众产生直接而真实的互动。
行为艺术通常是一种即兴的、非传统的、非商业性的艺术形式,强调体验和过程而非产物和结果。
通过行为艺术,艺术家可以挑战传统的艺术观念和边界,以身体和行动作为创作的核心,从而打破观众与作品之间的距离,创造出更加直接和深刻的艺术体验。
在行为艺术中,身体不仅是艺术家的工具,也是作品本身的主题和表达方式,通过身体的动作和姿态来传达情感、观念和意义。
行为艺术的定义是多元且开放的,可以包括各种形式和内容的行为实践,但其中身体作为媒介和表现形式的特点是其最为核心和重要的特征。
1.2 身体叙事的重要性身体叙事在行为艺术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是艺术家通过身体语言和姿态来传达情感和意义的主要手段。
身体叙事能够深刻地触动观众的内心,激发情感共鸣,拉近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使观众更加投入到艺术作品中。
通过身体叙事,艺术家能够表达出自己的内心情感和思想,将观众带入到一个全新的情感体验中。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叙事视角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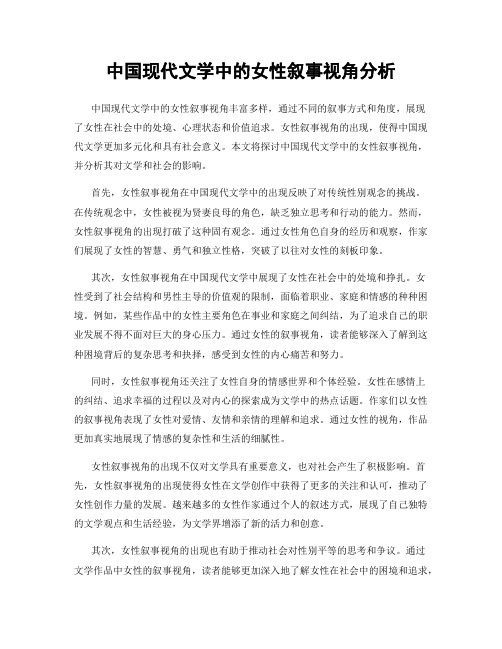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叙事视角分析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叙事视角丰富多样,通过不同的叙事方式和角度,展现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处境、心理状态和价值追求。
女性叙事视角的出现,使得中国现代文学更加多元化和具有社会意义。
本文将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叙事视角,并分析其对文学和社会的影响。
首先,女性叙事视角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出现反映了对传统性别观念的挑战。
在传统观念中,女性被视为贤妻良母的角色,缺乏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
然而,女性叙事视角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固有观念。
通过女性角色自身的经历和观察,作家们展现了女性的智慧、勇气和独立性格,突破了以往对女性的刻板印象。
其次,女性叙事视角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展现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处境和挣扎。
女性受到了社会结构和男性主导的价值观的限制,面临着职业、家庭和情感的种种困境。
例如,某些作品中的女性主要角色在事业和家庭之间纠结,为了追求自己的职业发展不得不面对巨大的身心压力。
通过女性的叙事视角,读者能够深入了解到这种困境背后的复杂思考和抉择,感受到女性的内心痛苦和努力。
同时,女性叙事视角还关注了女性自身的情感世界和个体经验。
女性在感情上的纠结、追求幸福的过程以及对内心的探索成为文学中的热点话题。
作家们以女性的叙事视角表现了女性对爱情、友情和亲情的理解和追求。
通过女性的视角,作品更加真实地展现了情感的复杂性和生活的细腻性。
女性叙事视角的出现不仅对文学具有重要意义,也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
首先,女性叙事视角的出现使得女性在文学创作中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推动了女性创作力量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通过个人的叙述方式,展现了自己独特的文学观点和生活经验,为文学界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创意。
其次,女性叙事视角的出现也有助于推动社会对性别平等的思考和争议。
通过文学作品中女性的叙事视角,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女性在社会中的困境和追求,从而增加对性别平等的关注和思考。
这种关注对于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女性权益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舞蹈编导毕业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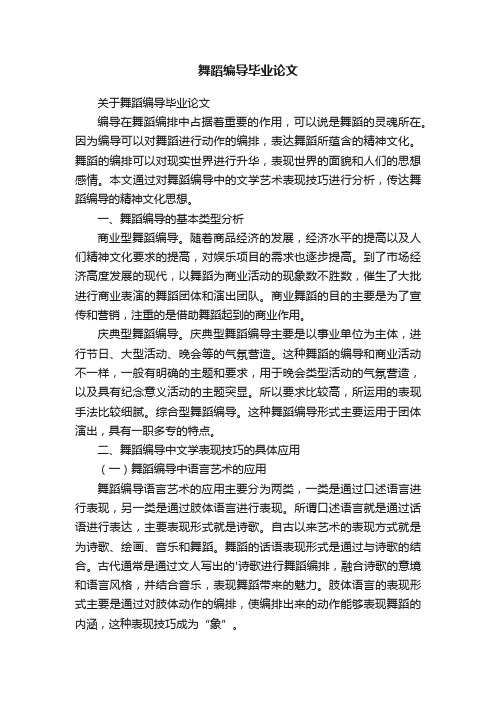
舞蹈编导毕业论文关于舞蹈编导毕业论文编导在舞蹈编排中占据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舞蹈的灵魂所在。
因为编导可以对舞蹈进行动作的编排,表达舞蹈所蕴含的精神文化。
舞蹈的编排可以对现实世界进行升华,表现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思想感情。
本文通过对舞蹈编导中的文学艺术表现技巧进行分析,传达舞蹈编导的精神文化思想。
一、舞蹈编导的基本类型分析商业型舞蹈编导。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精神文化要求的提高,对娱乐项目的需求也逐步提高。
到了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以舞蹈为商业活动的现象数不胜数,催生了大批进行商业表演的舞蹈团体和演出团队。
商业舞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宣传和营销,注重的是借助舞蹈起到的商业作用。
庆典型舞蹈编导。
庆典型舞蹈编导主要是以事业单位为主体,进行节日、大型活动、晚会等的气氛营造。
这种舞蹈的编导和商业活动不一样,一般有明确的主题和要求,用于晚会类型活动的气氛营造,以及具有纪念意义活动的主题突显。
所以要求比较高,所运用的表现手法比较细腻。
综合型舞蹈编导。
这种舞蹈编导形式主要运用于团体演出,具有一职多专的特点。
二、舞蹈编导中文学表现技巧的具体应用(一)舞蹈编导中语言艺术的应用舞蹈编导语言艺术的应用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口述语言进行表现,另一类是通过肢体语言进行表现。
所谓口述语言就是通过话语进行表达,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诗歌。
自古以来艺术的表现方式就是为诗歌、绘画、音乐和舞蹈。
舞蹈的话语表现形式是通过与诗歌的结合。
古代通常是通过文人写出的'诗歌进行舞蹈编排,融合诗歌的意境和语言风格,并结合音乐,表现舞蹈带来的魅力。
肢体语言的表现形式主要是通过对肢体动作的编排,使编排出来的动作能够表现舞蹈的内涵,这种表现技巧成为“象”。
(二)舞蹈编排中抒情和叙事的应用对舞蹈的概念分类可以从本质及形式来说,前者将舞蹈归为抒情的艺术,后者则归为对比拟和象征手法的利用。
优美的肢体动作可以将舞蹈编导所赋予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叙事性舞蹈研究

DANCE FASHION 2021观点DANCE FASHION 叙事性舞蹈是叙述某一特定情节的舞蹈,就是人们常说的情节舞,甚至可以描述为舞蹈小品和哑剧舞等。
叙事性舞蹈中心思想是经过提炼核心事件,表述典型的人物、情节及事件,通常是表明一种思想倾向、表彰一种高尚情操、宣扬一种人物关系或鞭挞某种丑恶现象,使观赏者从中获得教义,有所启发。
叙事舞蹈概念在现阶段不够完备,根据塑造舞者人物形象及反映现实生活进行划分,可以分为抒情性舞蹈、叙事性舞蹈和戏剧性舞蹈三类。
其中抒情性舞蹈是指借助舞蹈肢体语言传达编导思想情感的舞蹈;叙事性舞蹈具有一定故事情节,是诉说事件表述现象的小型舞蹈作品;戏剧性舞蹈是指舞剧,与叙事性舞蹈最大的区别在于篇幅长度。
1.叙事结构方式叙事作品的叙述方法从不同角度有多种划分方法,最常用的是按叙述先后顺序,即时间向度上的划分,一般分为顺叙、倒叙、插叙、补叙和分叙五种。
1.1顺叙顺叙是根据故事情节,按照时间发展顺序进行叙事,从头到尾讲述一个完整故事,使人物形象根据情节发展变化而变化。
一般在顺叙结构中,有交代时间、地点、人物及事件起因、经过、高潮和结果,具有较强的逻辑连贯性,使舞蹈叙事层次更加分明,是最简单自然的表现手法。
例如舞蹈《鸡毛信》,整支舞蹈紧紧围绕“送”鸡毛信的中心展开,细致描述出身处那个年代下不同角色的人们为了将鸡毛信送出的艰难经过,所谓“人在情报在,人亡情报转”,送信件的同志们甚至不知道对方姓名,仅通过代号和名称交流,但都有在中转途中不论遇到任何困难,都要把信送到的决心。
1.2倒叙倒叙是指根据故事情节,将作品中的重要部分、最能表达作品中心思想的一部分或事件结局放在作品最前面进行叙述,随之再完整叙述事件起因和经过。
这种叙事结构会直击观众内心,在大致了解作品后,对作品的细枝末节有一种沉重感。
例如群舞《汉宫秋月》,作品以一位老宫女的视角入手,讲述其在深宫中凄惨的人生经历。
随着音乐响起,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宫女出现在舞台上,通过新入宫宫女的欢喜引出自己酸甜苦辣的人生。
现实题材舞蹈叙事意义

现实题材舞蹈叙事意义摘要:一、引言1.现实题材舞蹈的兴起2.舞蹈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二、现实题材舞蹈的特点1.表现形式的多样性2.反映社会现象的深刻性3.艺术性与大众性的结合三、现实题材舞蹈的叙事意义1.传达社会价值观2.引发观众共鸣3.促进文化交流与理解四、现实题材舞蹈的创作与实践1.创作者的关注点2.表现手法与技巧的创新3.成功案例分析五、我国现实题材舞蹈的发展现状1.政策支持与市场需求2.舞蹈团的积极探索3.观众反馈与评价六、现实题材舞蹈的未来展望1.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2.舞蹈技术的进一步突破3.更加广泛的国际交流正文:现实题材舞蹈近年来在我国逐渐兴起,成为舞蹈界的一大趋势。
它以现实生活为创作源泉,通过舞者的身体语言,展现出生活的点滴、社会的风貌。
现实题材舞蹈不仅具有艺术价值,更具有强烈的叙事意义。
一、引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现实题材舞蹈应运而生,它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反映了现实生活,让观众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生活的温度。
现实题材舞蹈作品的涌现,体现了舞蹈与现实的紧密联系。
二、现实题材舞蹈的特点现实题材舞蹈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表现形式多样。
现实题材舞蹈不仅局限于舞台表演,还可以通过录像、户外表演等多种形式呈现。
其次,反映社会现象深刻。
现实题材舞蹈以小见大,从生活中的细节入手,展现出社会的全貌。
最后,艺术性与大众性的结合。
现实题材舞蹈既注重艺术表达,又兼顾观众需求,使得作品既具有艺术价值,又易懂易记。
三、现实题材舞蹈的叙事意义现实题材舞蹈的叙事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传达社会价值观。
现实题材舞蹈以富有感染力的方式传递了正能量,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次,引发观众共鸣。
现实题材舞蹈作品往往聚焦于人民群众的生活,使观众在欣赏过程中产生共鸣。
最后,促进文化交流与理解。
现实题材舞蹈作品展现了我国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助于增进国内外观众对我国文化的了解。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以陈染、林白、海男、卫慧等为代表的女作家借助哲学界进步的身体观和西方女性主义思想资源、开始了“身体叙事”的写作热潮,她们从身体、自我、欲望、潜意识等人的本体范畴出发,试图摆脱男权文化意识形态的束缚与遮蔽,塑造真实的女性形象,认识自我,创造自我,构建女性自己的历史。
这与“五四”女性作家的文化努力相衔接。
当代女作家的“身体叙事”由于书写身体、欲望等女性生命特点,被男权文化诟病是意料中事。
还因其在这个传媒时代、消费时代成为被消费和被欣赏的对象,而未得到评论界的充分肯定。
其实,被看是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被设定了的境遇,如果女性怕被窥视而不写作,而放弃自我认识、自我创造,难道不是更深地中了男权文化的套?如果我们放弃了男权文化意识形成的具有性别歧视的“男性阅读”视角,如果我们能超越男权文化意识在心灵深处设置的障碍,那么就不会忽视“身体叙事”文本中的女性声音和女性作家们为认识自我、创自我造所做出的努力。
一、发现被千年历史遮蔽的自我
人类自我认识的天性被许多哲学家认为是人类之所以伟大的真正核心。
人类文化历史就是伴随着人类对自我形象的解释而发展起来的。
但是在父权制的象征秩序规约下,人类文化只表达了对一个性别的认知,自我的概念都是以男性为楷模的,任何关于女性的知识都是在男权文化的性别歧视视角下形成的。
女性在男权文化中一直处于缺席、沉默的境遇,是文化被动的接受者,是被设计、被异化的他者。
女性该从哪里开始寻找自我的真相?也许用身体去感知,用身体去发现是唯一的路径。
当代女性文学“身体叙事”对自我的发现集中体现为从身体的感知
中确认女性真我、从身体欲望中生发对女性生命意识的体察和肯定、从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中发现女性的内在匮乏。
首先,“身体叙事” 文本中有回忆式的对女性身体成长的描写,女孩对自己躯体的凝视与抚摸被描写为对女性自我的物质实体的体察与确认。
女性作家认为对躯体的感知是真我的来源处。
陈染在《私人生活》中,叙述了带有自传色彩的主人公倪拗拗的身体成长过程。
倪拗拗是一个不合群的敏感女孩,她关注自我躯体,给胳膊取名叫“不小姐” ,
腿叫“是小姐”,食指叫“筷子小姐” ,常与它们交谈。
倪拗拗凝视着躯体的茁壮成长,逐渐形成了自我意识和坚实可触的自我形象。
由于倪拗拗的卓尔不群的女性自我意识的显现,小小年纪,却引起男老师T 对她的怪异行为——打击她、排斥她又被她吸引。
倪拗拗通过对躯体的感知从而在心理上形成的坚实的自我形象,其力量足以与父亲、男老师T 所代表的压制性力量相抗衡,特别是与男老师T 的较量中,不但没有被毁灭,反而取得了胜利。
在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中,主人公多米从五岁开始自慰,五岁的多米是凭着本能,抚摸自己的身体,用身体的快慰抵御这个无爱的、孤独的、黑暗的恐怖世界。
这种不依赖别人而获得的自我身体的快慰,让多米发现身体的快乐可以与他人无关,可以与男人无关。
身体的自我所属感和身体快乐的自足性让年幼的多米勇敢无畏,这是后来的多米形成坚强独立的精神自我的物质前提。
“身体叙事”文本中还有对美丽女人身体的凝视,例如《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对美丽女子姚琼的迷恋,对往昔美丽女子朱凉的神秘幻影的向往。
在海男的
《花纹》中,用“花纹”象征女性躯体和生命体验、创伤、时间在女性身体、心灵上留下的印记,并加以凝视。
对魅力女性身体的凝视、向往和将女性身体、心灵的成长诗化,这些都是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对女性身份的确认和对自我之美的认知。
“在心理学意义上,’自我’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躯体的五官四肢无疑是认识’自我’的素材。
婴儿逐步了解到五官四肢的归属,了解到自己对于五官四肢的支配权,最终确认躯体与自我的统一。
”而男权社会恰恰就是通过剥夺女性的身体所属权来压
制女性的自我意识,从而压制女性的生命活力、创造力,扼杀女性的言论与思想,女性的自我还未形成过。
女性作家们的“身体叙事”正是在寻找自我的物质实体以及建立在这个物质实体上女性真我。
通过对身体的感知而发现的女性自我无疑抵御了被男权文化的性别歧视污染了的女性知识,让女性自我的意识从女性的自然身体的私有感中生长起来,这是女性的人性基础,是女性成长的起点。
其次,“身体叙事”的作家们从对身体自然欲望的体察中生发了女性生命意识,并将生命意识的表达集中在对女性主体意识的构建、对个体生存方式的思考和对女性欲望的肯定。
对女性欲望的肯定是女性生命意识表达中最具先锋气质的内容,因为这直接冲击着男权社会的性别秩序,男权社会的性别秩序就是建立在对女性身体施以禁锢、惩罚而致使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蒙昧与自闭之上的。
在《上海宝贝》中,卫慧充分肯定了主人公倪可的生命欲望,将女性的种种欲望一一渴望名声渴望成功以及对性满足的渴望,真真切切地描写出来,第一次让女性的生命意识飞扬起来。
倪可有生活理想,写作是她的存在方式,梦想可以获得事业的成功,生命可以像烟花般绚烂。
倪可徘徊在心灵男友天天和性爱情人马克之间,过着灵肉分离的痛苦生活,但她并不否定这种生活,尤其是与马克的情欲关系。
性欲是她生命的原欲,使她显得生气勃勃。
在卫慧看来,倪可对性爱的追求是女性对自身作为生命存在的一种确认或体察,是女性对完整生活和完整的主体的追求。
卫慧在表现女性生命意识时,并不以批判男权社会为前提,而是迎着男权社会的欲望, 勇敢地将被男权社会遮蔽了的女性真实的生命形态呈现出来,用女性欲望与之相抗衡。
卫慧笔下的女性形象不再是匍匐在男权之下任人摆布的可怜女人,在男女生命形态相映成趣的性别场景中,将女性人物放在生活的主动者、强者的位置上卫慧以自
己为原型,塑造了有血有肉、彰显着生命意识、充满女性生命力与性魅力、自在坦荡的强美型女性形象。
完全冲破了历史文化的虚假怪圈,打破了男权社会主流文学中刻板的女性印象,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性别角色定型观念。
卫慧的《上海宝贝》一出现便遭到评论界狂轰滥炸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中国人害怕真实,这是中国国民劣根性的表现。
一个男权的社会,尤其怕看见真实的女性生命。
卫慧的“身体叙事”表达的是女性生命意识的自觉,是女性对自我真身的发现,是向男权文化的迷雾洒下的一抹耀眼的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