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智:中国哲学家论死亡
段德智|西方主体性思想虽面临一系列棘手难题,但永远不会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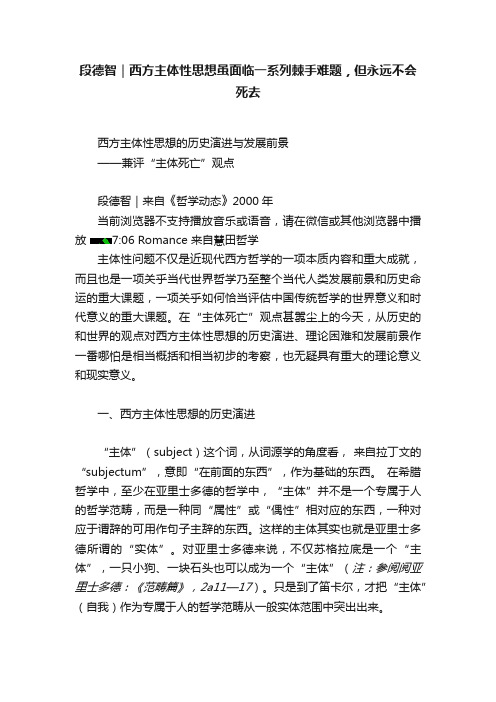
段德智|西方主体性思想虽面临一系列棘手难题,但永远不会死去西方主体性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发展前景——兼评“主体死亡”观点段德智|来自《哲学动态》2000年当前浏览器不支持播放音乐或语音,请在微信或其他浏览器中播放7:06 Romance 来自慧田哲学主体性问题不仅是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一项本质内容和重大成就,而且也是一项关乎当代世界哲学乃至整个当代人类发展前景和历史命运的重大课题,一项关乎如何恰当评估中国传统哲学的世界意义和时代意义的重大课题。
在“主体死亡”观点甚嚣尘上的今天,从历史的和世界的观点对西方主体性思想的历史演进、理论困难和发展前景作一番哪怕是相当概括和相当初步的考察,也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西方主体性思想的历史演进“主体”(subject)这个词,从词源学的角度看,来自拉丁文的“subjectum”,意即“在前面的东西”,作为基础的东西。
在希腊哲学中,至少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主体”并不是一个专属于人的哲学范畴,而是一种同“属性”或“偶性”相对应的东西,一种对应于谓辞的可用作句子主辞的东西。
这样的主体其实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实体”。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不仅苏格拉底是一个“主体”,一只小狗、一块石头也可以成为一个“主体”(注:参阅阅亚里士多德:《范畴篇》,2a11—17)。
只是到了笛卡尔,才把“主体”(自我)作为专属于人的哲学范畴从一般实体范围中突出出来。
在笛卡尔看来,所谓“主体”就是指自我、灵魂或心灵。
自我、灵魂或心灵虽然与物体同为实体,但却与后者有本质的不同。
物体的本质是广延,而自我、灵魂或心灵的本质则是思想。
自我不仅与物质实体有本质的区别,而且也不来源于物质实体。
它是一种独立自在的精神实体。
笛卡尔的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即是谓此(注:参阅笛卡尔:《方法谈》“第四部”,《形而上学的沉思》之“沉思第二”)。
这就把人的主体性问题鲜明地提了出来。
但是,由于笛卡尔是在心物二元论或身心二元论的理论框架内提出他的主体性理论的,因此,在他那里,人的主体性概念本身除了“自在”之外不可能有更进一步的或更深一层的涵义。
《伊凡·伊里奇之死》与《墙》——海德格尔与萨特的死亡观差异探究

‘伊凡㊃伊里奇之死“与‘墙“海德格尔与萨特的死亡观差异探究刘家玉㊀陈国雄摘要:托尔斯泰的‘伊凡㊃伊里奇之死“直接影响了海德格尔死亡观的建构,而‘墙“则是萨特死亡观生动的文学表达㊂死亡与生存意义的关系,是萨特与海德格尔死亡哲学中对立最突出的部分㊂海德格尔认为,死亡之作为 悬临 ,使人产生 畏 这种最本真的情态,由此人才得以 向死而在 ;萨特在‘墙“中回击了海德格尔 死亡具有本己性和不可通约性 这一论断,并表达了 死亡是荒诞的 观点㊂海德格尔与萨特死亡观差异的核心是:海德格尔力图在存在本体论的建构层面上理解死亡,而萨特直接从现实的㊁有意识生存出发考虑死亡问题㊂二者死亡观的差异,构成了存在论哲学中一种独特的张力㊂一方面揭示了存在论内部思想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极大推动了死亡哲学在现代哲学语境下的进一步发展㊂关键词:海德格尔;萨特;‘伊凡㊃伊里奇之死“;‘墙“;死亡观中图分类号:B516.54;B565.53㊀㊀㊀㊀文献标识码:A㊀㊀㊀㊀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2-0153-04㊀㊀死亡是哲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其不仅是人类思维和想象的形而上建构,更与每个个体的现实人生有着深刻的关联㊂段德智先生这样评价死亡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从越来越深的层面上猜度死亡的历史㊂ [1]而对于死亡的理解,往往是最能体现不同哲学家㊁哲学流派思想特点的因素㊂随着神学世界观的解构和现代哲学的兴起,哲学对死亡的理解愈发深入,在这之中,存在主义是现代哲学中对死亡问题探讨较多的一派,并且,其代表思想家的死亡观都与文学作品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伊凡㊃伊里奇之死“直接影响了海德格尔死亡观的建构,而‘墙“则是萨特死亡观生动的文学表达㊂一㊁本己之死与荒诞之死在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中,死亡的本己性问题首当其冲㊂他人之死和个体自身之死,这两种意义完全不同的死亡,在此前的思想史讨论中,没有被严格地区分开㊂在他看来,死亡是一个没有被完全澄清的概念㊂人可能见证过死亡,但是人永远不可能把死亡作为一种经历,因为死亡本身就是人 能经验 之可能性的消亡㊂所以,我们对于死亡始终只是 在傍 ㊂ 海德格尔对死亡的 事件性 的消解,可以浓缩为这样一个基本思想:死亡不可能作为一种对象性的事件被经验㊂ [2]然而,死亡固然不可被经验,但是由于死亡这种 只属于个体本身 的专属性,能够帮助沉浸日常生活的现代人排除外界的搅扰,获得关注自身存在的机会㊂从而由关注 死 ,带给 生 丰富的意义㊂死亡的个体性是开启死之启示的一把钥匙,人必须把死作为自己 最本己的和无可关联的可能性 来把握,把死当做自己的死来拥有,才能把 生 的意义发掘出来㊂托尔斯泰的小说‘伊凡㊃伊里奇之死“,就是对海德格尔死亡观的最佳注解㊂从形式方面看,小说采用倒叙的叙事手法,表现了文本在形式方面对死亡之本己性的强调㊂作者把处于故事内时间最末端的葬礼提到开篇处的叙事安排,既突出了小说的死亡主题,又是对每一位读者的警示,他提醒世人:重新反思死亡㊁真诚地面对死亡㊂从内容方面看,在小说的第一章中,伊凡之死作为一个冷冰冰的事实,赫然横在开头,强调了身边人对伊凡之死冷淡㊁漠然的态度㊂文中对伊凡的亲友对待其死亡的态度有这样的描写: 怎么?他死了;可是你瞧,我却没死 每个人都这样想,或这样的感觉㊂伊凡伊里奇的一些熟人,也就是所谓的朋友们,这时都不由得想到㊂ [3]联系后文伊凡在面对自己死亡时的态度,不难发现,这是海德格尔哲学中死亡个体性的文学预演㊂这段叙述表达的不止是旁人对伊凡之死的态度,而且也是对死亡本身的态度㊂这种庆幸,正是对个体死亡的闪躲㊂这种把死亡看作 他人之事 的倾向,暗含着对自己将来之死亡,即对死亡本己性的回避㊂海德格尔把这提炼为: 死亡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 ㊂在伊凡的朋友伊凡内奇探视伊凡遗351体时,又有了如下描写: 那神态还在责备活人或者提醒他们什么事㊂ 实际上,伊凡的遗容所要提醒生者的事,正是海德格尔的死亡的个体性想要给予世人的警示:死亡是人最本己的,无可关联的可能性,要把死亡作为自己的死亡看待,面对有限的㊁本真的自己,从死中,求解生的意义㊂ 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只有把我的死亡带给我自己,本真的存在对我才有可能㊂ [4]与海德格尔不同,萨特认为荒诞性才是死亡的基本性质㊂他把死亡看作是一个外在于个体存在的㊁与人的生存结构没有任何联系的偶然事实㊂死亡具有彻底的荒诞性,它丝毫不可被等待㊁被预测,也就无法真正对人生产生任何影响㊂在小说‘墙“中,萨特通过巧妙的情节设计,把死亡之荒诞,刻画得入木三分㊂相比‘伊凡㊃伊里奇之死“,承载了表达萨特个人死亡哲学重任的‘墙“,在视角选择上带有更强的目的性㊂‘墙“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是萨特基于其哲学基础和写作目的的必然结果㊂他与海德格尔最大的不同,就是把 以此在为基础 改进成了 以意识为基础 ㊂换句话说,萨特的 自为存在 与海德格尔的 此在 最大的区别,就是把自为严格限定在 人的意识 这一范围之内,意识使人的存在具备了本体的意义㊂可以说,二者对死亡看法的根本不同,是由各自哲学基础的差异决定的㊂因此,‘墙“的叙事建构在自为存在的意识范围内部,即主人公伊比埃塔在特定时空内的所见所闻所想之中㊂这种处理使小说得以立足于具体的人生处境中㊁从多方位展现出了作为个体的现代人面对死亡时最真切的感受,表达了站在其时代最前沿的㊁对死亡哲学的深沉思考㊂一般来说,思想性较强的文学作品,往往不以情节见长,而萨特以其巧思有力地打破了这一成见㊂不读到小说的最后,大多数读者都会理所应当地认为,‘墙“是一部意在描绘在可预计死亡之前,个体真实的身心状态的小说㊂但是,萨特的妙思在小说的尾声处掀起了真正的高潮㊂本应躲在藏身处的格里斯鬼使神差地跑到了墓地去,被伊比埃塔的玩笑骗到墓地的长枪党人在那里打死了他,预想中对敌人的嘲弄㊁勇敢的赴死变成了事实上的背叛㊂求生的格里斯死在乱枪下,求死的伊比埃塔却捡回了性命㊂在‘墙“中,把文学作品的主旨升华到其哲学高度的,正是结尾处这一出人意料的转折㊂这一反转设计可谓神来之笔,把死亡的荒诞性表现得极其透彻而富有真实感㊂一方面,萨特用 格里斯确实替代了伊比埃塔去死 这一事实,回击了海德格尔 死亡具有本己性和不可通约性 这一论断㊂另一方面,这一出人意料的结局印证了萨特对死亡的理解,即 死亡是荒诞的 ㊂二㊁意义的开显与意义的取消死亡与生存意义的关系,是萨特与海德格尔死亡哲学中对立最突出的部分㊂海德格尔认为,死亡之作为 悬临 ,使人产生 畏 这种最本真的情态,由此人才得以 向死而在 ,脱离人群,站在个体的角度筹划自身㊂使得生之意义,在死的限定下,得以敞开和澄明㊂在‘伊凡㊃伊里奇之死“中,海德格尔的这一思索,是由病床上濒死的伊凡对自己一生的反省而开显出来的㊂患病后的伊凡对死亡的态度,以第七节受到盖拉西姆的启示为分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㊂第四到第六节是伊凡的顽抗阶段,第八到第十二节结束是反思阶段㊂第七节中,伊凡通过与仆人盖拉西姆的接触,感受到他身上一种自然的㊁本真的,向死而生的人生态度㊂由此开始,伊凡对死亡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他不再通过非本真的 操劳 与 操持 来逃避死亡,而开始了对自己人生㊁对死亡的思索㊂随着他生命力的日渐垂危,他对死亡的思考,也变得越来越深入㊂概括来说,伊凡反思死亡的核心在于两点,第一, 之前的生活到底哪里过得不对头? 第二, 应该怎样过才算 对头 ? 当然,托尔斯泰只是 现代之死 的预言家,对这一 不对头 的原因,在小说中留下了悬念㊂这一问题在近半世纪后,由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给出了明确回答:首先,伊凡生病前的生活,长期处于日常的 沉沦 状态,本真的生存状况受到了遮蔽,不曾在 畏 的情绪中,面对过 死 这种可能性;其次,伊凡应该先行到死㊁向死而在,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就是: 带到主要不依靠操持而是去作为此在自己存在之前的可能性之前,而这个自己就在热情的㊁解脱了常人幻想的㊁实际的㊁确知它自己而又畏着的向死的自由之中㊂ [5]305就情节来说,患病前的伊凡,以 维持快乐和体面 为信条,他没有想过,这种虚浮的快乐与他人眼中的体面,与自己的存在的意义其实毫不相关㊂在他患病前,他从未从迷梦中醒来,倾听一次自己内心的倾诉㊂这足以解释垂死时的伊凡为什么产生了 所以那些美好的日子现在看来一点也不美好,只有童年除外 这样的困惑㊂随着人的成长,操劳㊁操持活动的增加,人越来越远离本真的自我存在,迷失在滚滚而来的 日常生活 中㊂而这种 日常生活 对死亡之本己性的遮蔽,使得只有借死亡之畏才可得以澄明的本真生存意义愈发模糊不清㊂而伊凡在反思中感到痛苦㊁无助的真正原因,正是过了一辈子这种 不向死而生 的糊涂生活,才让自己在临终时丝毫感451受不到生活的意义㊂而萨特的反对海德格尔把生存意义与死亡相结合的观点,他认为死并不能从外部赋予生命以任何意义㊂段德智先生在‘死亡哲学“一书中,把萨特这一说法解析为两个前后联系的部分:首先,死亡是自为存在的毁灭,而自为存在是生命意义的赋予者,所以死亡是生命意义赋予者的取消㊂其次,因为自为存在自主筹划自身的意义,而这种筹划要求一种 后来的存在 ㊂死亡恰好取消了自为成为这一 后来 的可能性,故死是人全部意义的筹划的毁灭和生命意义的取消㊂二者死亡观的对立鲜活地在不同文本中得到了反映,与‘伊凡㊃伊里奇之死“中,伊凡在临死前对人生意义的恍然大悟产生强烈对比的是,萨特笔下的伊比埃塔在临死前落入了形存神灭的麻木不仁中,甚至连爱情㊁友谊㊁爱国这些曾经在伊比埃塔的生命中长期留存的价值追求,也顿时显得黯淡无光㊂在‘墙“中,萨特对死亡的这种理解,主要通过主人公伊比埃塔的心理独白得到反复的展现㊂在文中,面对来看望死刑犯的医生时,对主人公有以下心理描写: 我们三人都在看着他,因为他是个活人㊂他做出活人的动作,有着活人的忧虑,在这个地窖里像个活人一样冻得发抖;他有一副营养良好,听从自己指挥的躯体,我们这几个人却不大感觉得到自己的躯体了㊂ 他蜷着腿,支配着自己的肌肉,并且他可以想明天的事㊂ 为什么活生生的人会把自己当作死人看待呢?这是因为在可见的死亡面前,已经被剥夺了自己作为自为存在,即自身存在意义赋予者的权利㊂因为意义赋予者即将毁灭,所以生命所包含的各种意义,甚至包括支配躯体㊁感知寒冷等纯粹的生理意义,也被眼前的死亡一并剥夺㊂另外,对 死亡通过阻碍自为存在通向未来而取消所有意义 这一论述,小说中也使用了大量笔墨加以对象化展现㊂伊比埃塔被宣判死刑后,往昔他所珍视的,多彩的生活体验㊁乃至于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再也不能在他心中激起一丝波澜㊂在萨特的死亡观中,伊比埃塔此刻对一切漠然的态度不难理解㊂因为自为存在一切的存在意义都依赖于 后来的存在 ,死亡如同一堵墙一般,隔断了伊比埃塔通往存在之 后来 的道路㊂因此,自为存在无法展开进一步自我筹划,也就不能赋予其即将毁灭的生命任何意义㊂三㊁ 向死自由 的叛徒与 绝对自由 的英雄在‘存在与时间“的论述中,死亡与自由具有天然的血肉联系㊂可以说,海德格尔前期的自由观,就是直接从其死亡哲学中导引出来的,即人的自由其实是一种 向死的自由 ㊂具体来说, 向死而在 者先行到死亡之中,以死亡为其存在方式,此在立足于这种本真状态展开的自我筹划,就能把死亡作为最本己的可能性自己承担起来㊂这种意义上此在的谋划被海德格尔称为 决心 ㊂此在的自由,就寓于这种决心之中㊂因为此在在这时能够 面对着自己的死亡,凭自己的良心自己选择自己,自己筹划自己,自己把自己的可能性开展出去㊂ [5]306其自由观念,依赖于 向死而在 这一过程,是由此在的死亡之 悬临 而派生出的一种可能性,通过此在在进入本真状态后的朝向有限性的自我筹划开展出来㊂这种对死亡与自由关系的思考,在托尔斯泰对伊凡人生态度㊁人生选择的表现中,得到了充分的文学化展现㊂‘伊凡㊃伊里奇之死“的第二节是对伊凡的生平的记述,此节的开头处这样写道: 伊凡㊃伊里奇过去的生活经历是最普通㊁最平常,但也是最可怕的㊂ 这段话极富深意,至少包含着两个矛盾㊂首先, 最简单㊁最平常的 人生,不应该是 最可怕 的;其次,伊凡从小就是家里的佼佼者,长大后成为了事业上较为成功的上流人物,并且经历过仕途的坎坷起伏,其身世并不简单㊁平常,也谈不上可怕㊂实际上,这种矛盾的表述恰好表达了托尔斯泰关于人生与众不同的看法:首先,极其普通㊁平常的人生,就是极其可怕的;其次,人生过得到底如何,并不由他人的评价决定,而是取决于个体本身对待人生的态度㊂这两点在海德格尔 向死的自由 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㊂这里的 普通 和 简单 ,并非是对人生丰富性的规定,而是着眼于个体对待自己人生的态度,即人是否能怀揣着一种本真的态度,自主地选择㊁筹划自己的人生,以此免于在 常人 中遗忘掉自己的存在整体㊂ 常人 是海德格尔用来区别 能死者 的概念,主要指一类退到自己以外的世界及其他同类此在构成的此在集合中的此在,他们以牺牲存在的完整性为代价,长期处于非本真的状态以免受 畏 的侵扰㊂换句话说,常人就是那些不愿意承担起自己的死亡㊁无法展开本真的自我筹划的人㊂托尔斯泰之所谓 极其简单,普通的人生, 实际上就是指这种 常人 的人生㊂伊凡正是这样一位为了逃避 畏 的侵扰,而牺牲自由逃遁到群体中的 常人 ㊂相较于海德格尔,自由在萨特存在论哲学中,拥有更彻底的意味和更本体的地位㊂萨特哲学的中心思想之一,就是 人是虚无而自由的存在㊂ 这种观点把人的自由看作是绝对的㊁无条件的㊂在死亡观中,这种自由表现为:与死亡毫不相干㊂萨特认为,人即使在极端受限的情551景中,在被步步逼近的死亡抹杀掉一切生命意义的条件下,人的自由选择仍然丝毫无法被动摇㊂小说‘墙“的主人公伊比埃塔的言行,正是萨特这种论述的对象化,是一位 存在主义自由英雄 ㊂在小说的结尾处,长枪党徒们让主人公出卖战友,以换取活命的机会㊂由此引出了文本中最精彩的一段心理描写: 我在这里,我可以出卖格里斯来换取自己一条命㊂可我拒绝这样做㊂我觉得这有一点可笑,因为这是顽固㊂我想: 难道就应该顽固? 出卖或者就义,面对看似非此即彼的两种必然选择,伊比埃塔都不屑一顾㊂在其心理活动中,彻底地体现着自为存在的自由选择本质:否定一切既定现成,朝向自己所不是去选择自己㊂出卖战友根本不被他纳入考虑,而选择英勇就义,成为一个 世俗的英雄 也不被伊比埃塔所接受㊂他大胆地开辟出了第三条道路:通过戏弄长枪党人,自主地把未来引向未知㊂伊比埃塔把这一荒唐选择解释为 顽固 ,其实这一连生死都不屑的 顽固 ,就是人对自由的坚持㊂在‘墙“中,萨特让我们领会到,人的绝对自由,不但不会在死亡的威胁下有所折损,而且会在所有希望之火都被死亡所浇灭的至暗时刻,放射出无比耀眼的英雄主义光芒㊂结语结合两个小说文本以及两位哲学家死亡观的对照阐述,以及以上三个层面的对比,可以看出,海德格尔与萨特死亡观歧见的核心在于:海德格尔力图在存在本体论的建构层面上理解死亡㊂所以在他看来,死亡对人生意义重大,他从本真性的启示㊁生存意义的揭示㊁自由感的源泉等角度,在此在本真在世结构中赋予了死亡不可或缺的地位㊂而萨特直接从现实的㊁有意识生存出发考虑死亡问题,所以在他的小说中,他把死亡表述为彻底荒诞的㊁取消人生一切价值和意义的㊁阻碍自为向前 去存在 的 墙 ㊂二者死亡观的歧见,构成了存在论哲学中一种独特的张力㊂一方面揭示了存在论内部思想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极大推动了死亡哲学在现代哲学语境下的进一步发展㊂这为后世人们思考死亡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㊂参考文献:[1]段德志.西方死亡哲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余平.论海德格尔的死亡本体论及其阐释学意义[J ].哲学研究,1995(11).[3]托尔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M ].许海燕,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7:183.[4]巴雷特.非理性的人[M ].段德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298.[5]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作者简介:刘家玉(1994 ),男,汉族,云南昆明人,单位为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方向为西方现代哲学㊁西方文论㊂陈国雄(1977 ),男,汉族,湖南新化人,哲学博士,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㊁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环境美学㊂(责任编辑:董惠安)651。
先秦诸子对死亡的理解

先秦诸子对死亡的理解
先秦时期是中国哲学的重要阶段,诸子百家对生死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儒家、道家、法家、墨家是我国春秋至秦、西汉初期的重要的哲学思想流派,其中儒家、道家和墨家对生死问题有着较为系统的思考。
儒家认为,人的生命是由天地之气所构成的,死亡则是天地之气消散的结果。
因此,儒家强调“尽人事,听天命”,即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尽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接受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命运。
道家则认为,生与死是自然循环的一部分,人应该顺应自然规律,不要过度追求生命或抗拒死亡。
庄子提出了“全生”、“保身”、“逍遥”的生命观和超越、达观的死亡观。
墨家则主张“非攻”、“兼爱”,反对战争和暴力,认为生命的存在应该为了实现和平与公正。
因此,在墨家看来,生死问题应该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下来看待,个人的生命价值应该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相统一。
中国哲学中的生命观与死亡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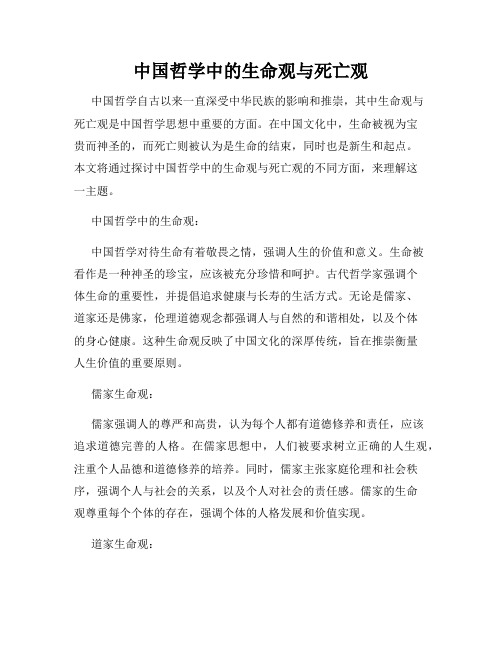
中国哲学中的生命观与死亡观中国哲学自古以来一直深受中华民族的影响和推崇,其中生命观与死亡观是中国哲学思想中重要的方面。
在中国文化中,生命被视为宝贵而神圣的,而死亡则被认为是生命的结束,同时也是新生和起点。
本文将通过探讨中国哲学中的生命观与死亡观的不同方面,来理解这一主题。
中国哲学中的生命观:中国哲学对待生命有着敬畏之情,强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生命被看作是一种神圣的珍宝,应该被充分珍惜和呵护。
古代哲学家强调个体生命的重要性,并提倡追求健康与长寿的生活方式。
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伦理道德观念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个体的身心健康。
这种生命观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深厚传统,旨在推崇衡量人生价值的重要原则。
儒家生命观:儒家强调人的尊严和高贵,认为每个人都有道德修养和责任,应该追求道德完善的人格。
在儒家思想中,人们被要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注重个人品德和道德修养的培养。
同时,儒家主张家庭伦理和社会秩序,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
儒家的生命观尊重每个个体的存在,强调个体的人格发展和价值实现。
道家生命观:道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注重个体的自我体验和理解。
道家认为,人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追求内心的平静与和谐。
在道家思想中,个体生命被视为宇宙的一部分,起伏变化的生命体验与自然的无常相呼应。
道家的生命观强调个体对自身的认知和修养,追求自身的内在道德和精神的成长。
佛家生命观:佛家强调生命的无常和轮回,认为生死是一个永恒的循环。
佛家生命观中,生死被看作是一个过程,个体生命的终结只是开始。
佛家鼓励人们超越尘世的束缚,解脱自己,达到灵性和智慧的觉醒。
佛家的生命观强调个体对自身的忏悔和反思,追求在生命中达到照亮自己和他人的境界。
中国哲学中的死亡观:中国哲学中的死亡观与生命观相辅相成,死亡被看作是生命的一部分,是必然的命运。
中国哲学中的死亡观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和解释,每个哲学流派都有其特定的理解和表达方式。
当代中国_主体性哲学_的出场

主体性哲学与希望人学 笔谈读段德智教授的 主体生成论 对 主体死亡论 之超越当代中国 主体性哲学 的出场吴根友,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主体性 问题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也是现代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然而从整体上看,现代中国有关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囿于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缺乏中国哲学的自身特色。
少数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将明清之际看作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发端点,在中西对比的宏观视野里论述了中国现代主体性的自身特点,如相对于西方走出中世纪反对 宗教异化 的现象,中国社会则反对 伦理异化 ;相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 顺产 而言,中国近代社会是 难产 [1]24。
然而,这一即哲学史讲哲学的思路本身虽然是哲学创造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并不是哲学创造的突出表现,尤其不是其主要的表现。
当代中国蓬蓬勃勃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本身,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主体性哲学。
依笔者对当代中国哲学界的粗浅了解而言,认为段德智教授的 主体生成论 对 主体死亡论 之超越 (下文简称 主体生成论 )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本这样性质的著作。
该书通过对西方主体性哲学历史的回顾、分析与批判,灵活而又娴熟地运用了马克思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思想精神,针对现代西方 主体死亡论 的主流思想,创造性提出了 主体生成论 的新命题;而且,在吸收了西方基督宗教哲学合理内核的新视野里,提出了希望人学的新人学理想。
由于笔者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对于西方哲学以及西方哲学中主体性问题的论述,知之甚少,更谈不上系统。
因此对于此书在西方哲学领域里的成就与得失没有评价能力。
而有关本书对于主体性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序 文中已经作了非常精辟的概括。
杨先生认为,该书从历史时性与共时性两个维度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并高度肯定这是一部 极富特色和创见的、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著作 [2]杨祖陶序3-5。
在此,笔者只想就 主体生成论 命题的提出与 希望人学 的理论设想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创新的价值与意义,谈一点个人的感想。
死亡观.doc

死亡观种种乘此机会,不妨对哲学史上的死亡观作一简略的回顾。
哲学和诗不同。
诗人往往直抒死亡之悲哀,发出“浮生若梦”、“人生几何”的感叹。
哲学家却不能满足于悲叹一番,对于他来说,要排除死亡的困扰,不能靠抒情,而要靠智慧。
所以,凡是对死亡问题进行思考的哲学家,无不试图规划出一种足以排除此种困扰的理智态度。
大体而论,有以下几种死亡观:一、功利主义的入世论。
这是一种最明智的态度:死亡既然是不可避免的,就不必去考虑,重要的是好好地活着,实现人生在世的价值。
例如,伊壁鸠鲁说:“死对于我们无干,因为凡是消散了的就没有感觉,而凡无感觉的就是与我们无干的。
”“贤者既不厌恶生存,也不畏惧死亡,既不把生存看成坏事,也不把死亡看成灾难。
”应当从对不死的渴望中解放出来,以求避免痛苦和恐惧,享受人生的快乐--肉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平静。
斯宾诺莎说:“自由人,亦即依理性的指导而生活的人,他不受畏死的恐惧情绪所支配,而直接地要求善,换言之,他要求根据寻求自己的利益的原则,去行动、生活,并保持自己的存在。
所以他绝少想到死,而他的智慧乃是生的沉思”,“而不是死的默念”。
中国儒家尽人事而听天命的态度亦属此种类型,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就是教导人只须关心生,不必考虑死。
总之,重生轻死,乐生安死,这种现实的理智的态度为多数哲学家所倡导,并为一般人易于接受。
二、自然主义的超脱论。
这种观点以中国的庄子为典型代表,他主张:“齐生死”,“不知说(悦)生,不如恶死”,“无古今而后入于不死不生”。
生死都是自然变化,一个人只要把自己和自然融为一体,超越人世古今之变,就可以齐生死,不再恋生患死了。
超脱论与入世论都主张安死,但根据不同。
入世论之安死出于一种理智的态度:死是不可避免的,想也没用,所以不必去想,把心思用在现实的人生上。
它教人安于人生的有限,把小我化入宇宙的大我,达于无限。
所以,超脱论安死而不乐生,对人生持一种淡泊无为的立场。
三、神秘主义的不朽论。
苏童小说中死亡书写

两南人宁:硕十学何论文
Abstract
psychoIogy.They are deVoting oneself to the others,committing suicide and redemption.
When claSsi匆ing,we analyze the text at the s锄e time,so it mal(es the argumentation
ret啪in but also mll of predestination.It likes that,death is the only home of
such a
noisy society.The death is cl嬲si6ed into types according to dif.fcrent ways觚d
lV
两南人学硕十学何论文
绪论
绪论
苏童,苏州人,原名章忠贵,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小时候因生病休学 在家,正是从那个时候受其二姐的感染喜欢上了文学,读过很多文学名著并受益 于此“培养了某种幻想精神"。他从高中时代起就开始写小说,但一直都未被发表, 直到1983年短篇小说《第八个是铜像》发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相继发表了如
Su Tong h嬲suffered f.rom pain,survived丘Dm death,锄d aRer tlIe“WEN GE”,he
托alizes the bare h啪anit)r锄d the absurd society.Funhe咖ore,he grows up in south
part of China whe心is gloomy觚d h啪id,that foms his temper锄e眦.Such rich
主体生成论的意义-2019年文档

主体生成论的意义作为主体的人和人的主体性是哲学常提常新的话题。
自近代以降,尤其是自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标志的主体性原则得以确立以来,这个话题更是成为几乎所有哲学体系围之旋转的枢纽。
然而,“主体死亡论”哲学的出现对主体性哲学提出了严峻挑战。
如何回应这种挑战,如何在“主体死亡论”的背景下重建主体性哲学,成为现代哲学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
段德智教授的《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这部著作以严密的逻辑、清新的笔调、丰富的内容,为我们展示出一个“希望人学”的哲学体系,提出了诸多极富独创性的真知灼见。
限于篇幅,我只谈使我感触最深的两点:1.作者强调主体是“生成着的”主体,或者说,强调主体的“生成性”。
一方面,人的主体性不是现成的东西,或者说,人不是天生的主体。
“人的根本特征在于他始终是一种‘未完成的动物,,是一种逐步‘生成’自己的动物。
人的本质的变动性和生成性乃人之区别于天使,特别是人区别于上帝的根本性内容”。
另一方面,人的主体化过程也是一个永恒的过程,是一个未完成的、并且永远不可能完成的过程。
段德智教授以此把作为主体的人与神和动物区别开来,把它视为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特征。
对于前一点,相信大多数人容易接受。
人之成为人,主体之成为主体,有一个进化的过程,这在今天已几乎成为常识。
但对于后一点,可能就不那么容易被人接受了。
人是一种有理想的动物,在人类的历史上,诸多伟大的思想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又一幅人类未来的美好蓝图,而且都坚信那是必然实现的。
即便是我们自己,也是唱着“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长大的。
而段德智教授断言:“我们所谓人的主体性的未来之维,作为未来之维,是永远处于我们前面的东西,是我们永远要为之奋斗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出来的东西。
也就是说,人的主体性的未来之维并不是某种僵硬的、固定不变的东西,既不是任何一个确定不变的偶像,也不是任何一个确定不变的社会模式。
作为主体的人的未来之维是那种永远变动不居的,从而能够永远处于我们前面的东西”。
死亡哲学资料

1. 伊壁鸠鲁则根本不承认死亡,他说:“最可怕的恶是死,但死却与我们毫无关系,因为我们活着的时候,死亡还不存在;当死亡来到的时候,我们又已经不存在了。
”但他却没想到死亡却是给活着的人留下了巨大的悲伤和痛苦。
死人当然不知道,并且也不在乎了,而活着的人则因为死亡而意识到了它的可怕。
其实,人不是对于自己,而是对于旁观者才死的。
珍爱生命,要学会善待自己,学会放飞自己,让自己更贴近自然。
生活中有许多有趣的事,生命中有许多美好的东西,我们完全可以去尝试着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踢踢球、上上网,与朋友去郊游,去大海里游泳,去小溪边钓鱼,去看看喜剧片,去爬喜欢的山,去看看飞瀑,去听听涛声……那么多的事等着我们去做,那么多的开心需要我们参与。
我们奔跑,我们跳跃,我们欢笑,我们歌唱,这一份美好,皆因有了生命。
珍爱生命,要让自己的生命有所价值。
充实自己、提高自己,为了人生的充实,为了生命的完美,你没有理由不努力,让生命因奋斗而精彩。
珍爱生命,还要学会以一颗平常心对待生活,适时调整自己的心态,平静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要相信,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
生命是珍贵的,是金钱换不来的。
让我们一起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心理和生理的健康,珍爱我们的生命吧!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首小诗踏上人生之路吧! 珍爱生命,世界因你精彩!!、死并非生的对立,有时候生只是死的另一种形式(尼采)2、人从来不曾经历过死亡,所以这一刻活着即是永恒(维特根斯坦)3、财富的意义在于更好的完成义务,而不是逃避义务(卢梭)4、忍耐是出于对行为一般性准则的是适宜考察(亚当·斯密)5、人类本能的自然倾向自动产生所有惩罚的政治目的(亚当·斯密)6、政治和强权结合是必要的(帕斯卡尔)7、语言是世界的边缘(某位天才说的)……全球化是人类大尺度上的历史进程。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从前的哲学面临两种死亡抉择:一是在哲学家手里曲高和寡地死亡——彻底的死亡。
二是随社会进步在人的社会主体性关系的全面复苏中死亡——涅槃再生式的死亡。
“未知生,焉知死”与“未知死,焉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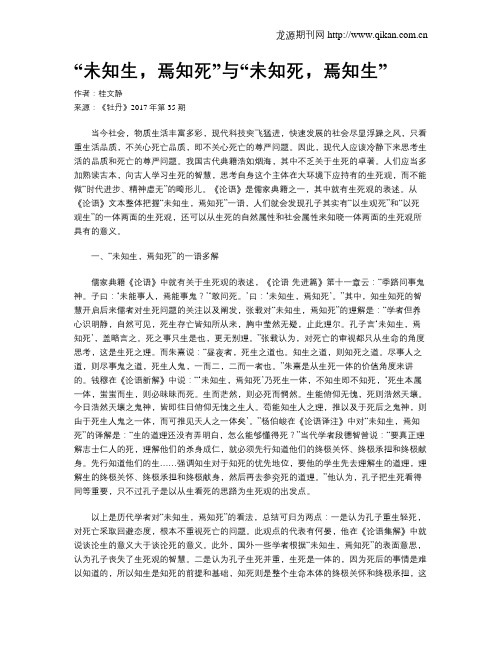
“未知生,焉知死”与“未知死,焉知生”作者:桂文静来源:《牡丹》2017年第35期当今社会,物质生活丰富多彩,现代科技突飞猛进,快速发展的社会尽显浮躁之风,只看重生活品质,不关心死亡品质,即不关心死亡的尊严问题。
因此,现代人应该冷静下来思考生活的品质和死亡的尊严问题。
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其中不乏关于生死的卓著。
人们应当多加熟读古本,向古人学习生死的智慧,思考自身这个主体在大环境下应持有的生死观,而不能做“时代进步、精神虚无”的畸形儿。
《论语》是儒家典籍之一,其中就有生死观的表述。
从《论语》文本整体把握“未知生,焉知死”一语,人们就会发现孔子其实有“以生观死”和“以死观生”的一体两面的生死观,还可以从生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来知晓一体两面的生死观所具有的意义。
一、“未知生,焉知死”的一语多解儒家典籍《论语》中就有关于生死观的表述,《论语·先进篇》第十一章云:“季路问事鬼神。
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
’曰:‘未知生,焉知死’。
”其中,知生知死的智慧开启后来儒者对生死问题的关注以及阐发,张载对“未知生,焉知死”的理解是:“学者但养心识明静,自然可见,死生存亡皆知所从来,胸中莹然无疑,止此理尔。
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盖略言之。
死之事只生是也,更无别理。
”张载认为,对死亡的审视都只从生命的角度思考,这是生死之理。
而朱熹说:“昼夜者,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
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朱熹是从生死一体的价值角度来讲的。
钱穆在《论语新解》中说:“‘未知生,焉知死’乃死生一体,不知生即不知死,‘死生本属一体,蚩蚩而生,则必昧昧而死。
生而茫然,则必死而惘然。
生能俯仰无愧,死则浩然天壤。
今日浩然天壤之鬼神,皆即往日俯仰无愧之生人。
苟能知生人之理,推以及于死后之鬼神,则由于死生人鬼之一体,而可推见天人之一体矣’。
”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对“未知生,焉知死”的译解是:“生的道理还没有弄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当代学者段德智曾说:“要真正理解志士仁人的死,理解他们的杀身成仁,就必须先行知道他们的终极关怀、终极承担和终极献身。
从死亡教育到临终关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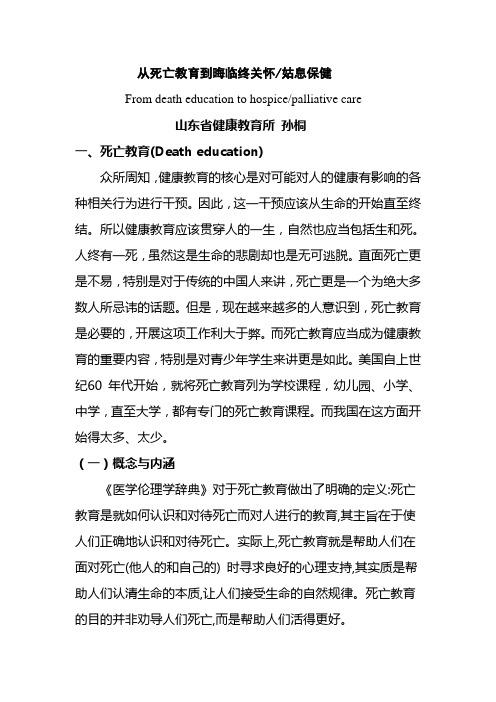
从死亡教育到晦临终关怀/姑息保健From death education to hospice/palliative care山东省健康教育所孙桐一、死亡教育(Death education)众所周知,健康教育的核心是对可能对人的健康有影响的各种相关行为进行干预。
因此,这一干预应该从生命的开始直至终结。
所以健康教育应该贯穿人的一生,自然也应当包括生和死。
人终有一死,虽然这是生命的悲剧却也是无可逃脱。
直面死亡更是不易,特别是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讲,死亡更是一个为绝大多数人所忌讳的话题。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死亡教育是必要的,开展这项工作利大于弊。
而死亡教育应当成为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对青少年学生来讲更是如此。
美国自上世纪60 年代开始,就将死亡教育列为学校课程,幼儿园、小学、中学,直至大学,都有专门的死亡教育课程。
而我国在这方面开始得太多、太少。
(一)概念与内涵《医学伦理学辞典》对于死亡教育做出了明确的定义:死亡教育是就如何认识和对待死亡而对人进行的教育,其主旨在于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死亡。
实际上,死亡教育就是帮助人们在面对死亡(他人的和自己的) 时寻求良好的心理支持,其实质是帮助人们认清生命的本质,让人们接受生命的自然规律。
死亡教育的目的并非劝导人们死亡,而是帮助人们活得更好。
(二)目的、意义与作用死亡教育不仅让人们懂得如何活得健康、活得有价值、活得无痛苦,而且还要死得有尊严。
它会使人们增强维护健康的责任感和自觉性,提高健康素养和技能,自觉采纳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更加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它既强化人们的权利意识,又有利于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
通过死亡教育,使人们认识到死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死亡教育是破除迷信和提高素养的教育,是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生观教育的组成部分。
使医学生明确死亡的本质、伦理道德,掌握有关死亡的各种知识及应对方法,使其在今后的工作中对死亡和濒死的恐惧程度降低或消失,并能够积极采取各种调适技能满足临终者及其家属的身心需要。
对死亡现象的宗教学思考

对死亡现象的宗教学思考选择字号:大中小本文共阅读2932 次更新时间:2009-03-08 09:48:37进入专题:死亡现象宗教学[3]罗素也曾经把“对死亡的恐惧”理解为“宗教的基础”,强调指出:“整个宗教的基础是恐惧――对神秘的恐惧,对失败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
”(罗素.一个自由人的崇拜[M].胡品清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59.)可以说,死亡问题或人的不死(不朽)问题,是任何宗教产生和发展的基础,离开了死亡问题或人的不死问题,对于任何重大的宗教现象,都是不可能作出合理的说明的。
[3]●段德智(进入专栏)正如“死亡是给予哲学灵感的守护神”(叔本华语)一样,死亡也是给予宗教和宗教学灵感的守护神。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学的奠基人迈克斯•缪勒在谈到宗教的起源和发展时,曾经强调指出:“无论人们在别的问题上有什么相反的说法,人们对那些因死亡而暂时离开人世的人们的思考和情感,都构成了最早的和最重要的宗教因素。
而且,相信来世、想象来世、希望在来世再见面的信仰也构成了宗教的因素。
这种信仰不仅以其不抗拒的力量成为我们祖先的真理,而且至今仍起着很大的作用。
”[1]几年之后,恩格斯在谈到宗教的起源和发展时,也强调指出:是人的不死的观念,确切地说,是人的灵魂不死的观念,“通过自然力的人格化,产生了最初的神。
随着各种宗教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神越来越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通过智力发展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
”[2]可以说,死亡问题或人的不死(不朽)问题,是任何宗教产生和发展的基础,离开了死亡问题或人的不死问题,对于任何重大的宗教现象,都是不可能作出合理的说明的。
[3]虽然死亡问题构成了任何一种宗教的核心和基础(弗雷泽语),但是,不同的宗教对死亡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对达到人的不朽的途径也多所区别。
因此,为了比较全面地了解对死亡现象的宗教或宗教学思考,比较具体比较深入地考察一下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宗教是必要的。
儒家思想中的死亡观与生命态度

傅佩荣儒家思想直接谈及死亡的地方并不多;不过,从他们对生命的态度反映出死亡看法的倒有不少。
我们就由这个角度来看看儒家的死亡观。
第一,儒家认为死亡是自然生命的结束,人既然出生,就无法避免老、病、死,死亡是极其自然的现象,因此在《论语颜渊》中即有”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之言,也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话。
死亡既非人力所能左右,是自然的结果,所以儒家认为人对死亡毋须过分悲叹。
价值生命的完成不过,儒家认为人活在这世上,除了”自然生命”之外,还有”价值生命”需完成,人必须藉自然生命以实现其价值生命,因此人必须珍惜生命。
所以,当颜渊死时,孔子在《论语雍也》中以”不幸”二字来形容,并为他痛哭。
这不仅出自深刻的师生情谊,也出自对”道统”恐怕失传的忧念,颜渊的自然生命太短促,无法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生命,在孔子看来是极为可惜的一件事。
因此,儒家认为君子应当善自惜生。
在《论语述而》中,孔子就曾劝诫子路不可”暴虎凭河,死而无悔”,在〈宪问〉中,亦批评”若匹夫匹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
在他看来,为血气之勇或小信小义而轻易牺牲生命,都是很不值得的。
在《孟子尽心篇上》也劝人不要”立乎岩墙之下”,从事不必要的冒险。
所以,尽管管仲变节改事齐桓公,孔子仍对他赞誉有加,因为他对社会国家尽上了责任,完成了自我的价值生命。
基于同一理由,儒家并不认为长命是一件好事。
孔子就曾在论语宪问篇中说他的朋友原壤”幼而不逊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
”如果一个人只有自然生命,活得很老,却无法完成自我人格与价值生命,则不如不活;自然生命绝非人一生的目的所在。
自然生命的結束第二、儒家认为死亡是自然生命的結束。
儒家一方面相信死亡与命运有关,另一方而相信死亡与使命有关。
所谓使命,即是人对于自己之所以成为一个人的自觉:人要知道自己为何而生、为何而死;知道为何而生为何而死,就可以选择某一理想,以成全其价值生命。
当人一旦对死亡采取主动态度,就不再被动的被死亡攫获,生命向度遂豁然开朗。
古今名人对生死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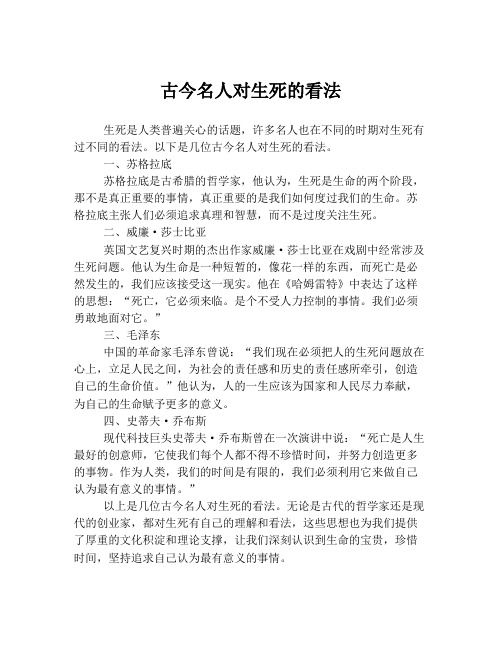
古今名人对生死的看法
生死是人类普遍关心的话题,许多名人也在不同的时期对生死有过不同的看法。
以下是几位古今名人对生死的看法。
一、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他认为,生死是生命的两个阶段,那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度过我们的生命。
苏格拉底主张人们必须追求真理和智慧,而不是过度关注生死。
二、威廉·莎士比亚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作家威廉·莎士比亚在戏剧中经常涉及生死问题。
他认为生命是一种短暂的,像花一样的东西,而死亡是必然发生的,我们应该接受这一现实。
他在《哈姆雷特》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死亡,它必须来临。
是个不受人力控制的事情。
我们必须勇敢地面对它。
”
三、毛泽东
中国的革命家毛泽东曾说:“我们现在必须把人的生死问题放在心上,立足人民之间,为社会的责任感和历史的责任感所牵引,创造自己的生命价值。
”他认为,人的一生应该为国家和人民尽力奉献,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更多的意义。
四、史蒂夫·乔布斯
现代科技巨头史蒂夫·乔布斯曾在一次演讲中说:“死亡是人生最好的创意师,它使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珍惜时间,并努力创造更多的事物。
作为人类,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必须利用它来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
”
以上是几位古今名人对生死的看法。
无论是古代的哲学家还是现代的创业家,都对生死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这些思想也为我们提供了厚重的文化积淀和理论支撑,让我们深刻认识到生命的宝贵,珍惜时间,坚持追求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
段德智:中国哲学家论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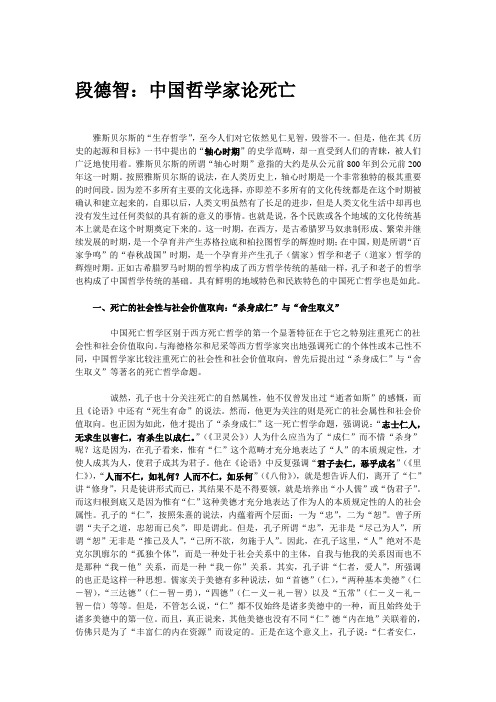
段德智:中国哲学家论死亡雅斯贝尔斯的“生存哲学”,至今人们对它依然见仁见智,毁誉不一。
但是,他在其《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一书中提出的“轴心时期”的史学范畴,却一直受到人们的青睐,被人们广泛地使用着。
雅斯贝尔斯的所谓“轴心时期”意指的大约是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一时期。
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在人类历史上,轴心时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极其重要的时间段。
因为差不多所有主要的文化选择,亦即差不多所有的文化传统都是在这个时期被确认和建立起来的,自那以后,人类文明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人类文化生活中却再也没有发生过任何类似的具有新的意义的事情。
也就是说,各个民族或各个地域的文化传统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时期奠定下来的。
这一时期,在西方,是古希腊罗马奴隶制形成、繁荣并继续发展的时期,是一个孕育并产生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哲学的辉煌时期;在中国,则是所谓“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孕育并产生孔子(儒家)哲学和老子(道家)哲学的辉煌时期。
正如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构成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基础一样,孔子和老子的哲学也构成了中国哲学传统的基础。
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中国死亡哲学也是如此。
一、死亡的社会性与社会价值取向:“杀身成仁”与“舍生取义”中国死亡哲学区别于西方死亡哲学的第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它之特别注重死亡的社会性和社会价值取向。
与海德格尔和尼采等西方哲学家突出地强调死亡的个体性或本己性不同,中国哲学家比较注重死亡的社会性和社会价值取向,曾先后提出过“杀身成仁”与“舍生取义”等著名的死亡哲学命题。
诚然,孔子也十分关注死亡的自然属性,他不仅曾发出过“逝者如斯”的感慨,而且《论语》中还有“死生有命”的说法。
然而,他更为关注的则是死亡的社会属性和社会价值取向。
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提出了“杀身成仁”这一死亡哲学命题,强调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
”(《卫灵公》)人为什么应当为了“成仁”而不惜“杀身”呢?这是因为,在孔子看来,惟有“仁”这个范畴才充分地表达了“人”的本质规定性,才使人成其为人,使君子成其为君子。
主体性的死亡段德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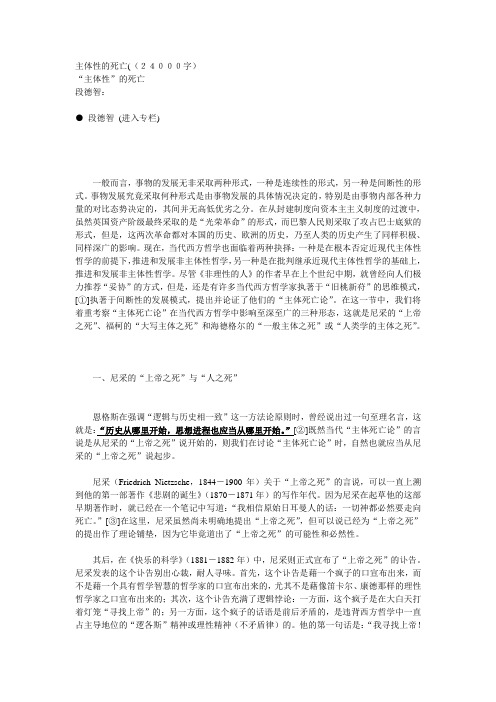
主体性的死亡((24000字)“主体性”的死亡段德智:●段德智(进入专栏)一般而言,事物的发展无非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连续性的形式,另一种是间断性的形式。
事物发展究竟采取何种形式是由事物发展的具体情况决定的,特别是由事物内部各种力量的对比态势决定的,其间并无高低优劣之分。
在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主义制度的过渡中,虽然英国资产阶级最终采取的是“光荣革命”的形式,而巴黎人民则采取了攻占巴士底狱的形式,但是,这两次革命都对本国的历史、欧洲的历史,乃至人类的历史产生了同样积极、同样深广的影响。
现在,当代西方哲学也面临着两种抉择:一种是在根本否定近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前提下,推进和发展非主体性哲学,另一种是在批判继承近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基础上,推进和发展非主体性哲学。
尽管《非理性的人》的作者早在上个世纪中期,就曾经向人们极力推荐“妥协”的方式,但是,还是有许多当代西方哲学家执著于“旧桃新苻”的思维模式,[①]执著于间断性的发展模式,提出并论证了他们的“主体死亡论”。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着重考察“主体死亡论”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影响至深至广的三种形态,这就是尼采的“上帝之死”、福柯的“大写主体之死”和海德格尔的“一般主体之死”或“人类学的主体之死”。
一、尼采的“上帝之死”与“人之死”恩格斯在强调“逻辑与历史相一致”这一方法论原则时,曾经说出过一句至理名言,这就是:“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②]既然当代“主体死亡论”的言说是从尼采的“上帝之死”说开始的,则我们在讨论“主体死亡论”时,自然也就应当从尼采的“上帝之死”说起步。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年)关于“上帝之死”的言说,可以一直上溯到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1870-1871年)的写作年代。
因为尼采在起草他的这部早期著作时,就已经在一个笔记中写道:“我相信原始日耳曼人的话:一切神都必然要走向死亡。
”[③]在这里,尼采虽然尚未明确地提出“上帝之死”,但可以说已经为“上帝之死”的提出作了理论铺垫,因为它毕竟道出了“上帝之死”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思索死亡的特殊角度——评《死亡哲学》

作者: 陶佳珞;昌切
出版物刊名: 江汉论坛
页码: 80-80页
主题词: 死亡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西方哲学史;西方人本主义;基本原理;系统考察;人生哲学;对立统一规律;出版社;角度
摘要: <正> 严格地说,新近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死亡哲学》(段德智著)是一部西方死亡哲学史。
作者的思索角度无疑是特殊的。
说其特殊,主要是相对过去和国外而言,因为我们还不曾见到有人象他那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系统考察和整理整个两方死亡哲学史,从而初步也是比较完整地建立了作者个人或中国的死亡哲学观和西方死亡哲学史体系,为我国继续深入研究西方人本主义哲。
面向死亡的_哲学之安慰_读_西方死亡哲学_

第60卷 第3期2007年5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Wuha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y Sciences)V ol.60.No.3May2007.413~414收稿日期:2006 02 23面向死亡的 哲学之安慰!!!读∀西方死亡哲学#王 成 军(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作者简介]王成军(1978 ),男,湖北荆门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世纪哲学及宗教学原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B503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671 881X(2007)03 0413 02如果说哲学是爱智慧,那么,人类以哲学的方式所能达致的最大的智慧,莫过于对 死亡的洞悉。
与死亡本身的 不可避免性与 终极性一样,哲学思辨与死亡问题之间的紧密关系也是不可避免的、终极性的。
谈哲学的人如果不谈论死亡,大概相当于搞艺术的人不谈论美。
按照柏拉图的说法, 哲学就是死亡的练习。
(∀斐多篇#)这实在是一句极其明白又深不可测的格言。
恩格斯曾断言,直立行走是从猿到人的一大飞跃,这话不无道理。
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正是死亡塑造了人本身!!!正是人类最本底的死亡意识与存在冲动,让人从与自然同一的物理性存在样态中逃离出来,开始具有理性,具有精神存在的维度。
成为人便意味着 向死而在,意味着在死亡与虚无所带来的巨大的恐惧之阴影下筹划自己的生存,这种能力让人类获得了 万物之灵长的尊贵地位,也让每个个体的人获得了无上的尊严与价值。
哲学作为人学,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制高点,如果没有把 死亡作为自己的 最高问题,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虽然大多数哲学史家倾向于把 存在问题当作西方哲学的主要线索。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我们会发现,大哲学家们对存在问题的关切,无不是以畏死的焦虑为前提的,无不是从 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这一赫拉克利特式的命题出发的。
从我们所知的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一直到当代的德里达等后现代思想家,他们全部的哲学,无不是与死亡问题紧密相关的。
要正确看待“死亡”问题——武汉大学师生对《死亡哲学》一书的读后反映

作者: 王琴梅
出版物刊名: 湖北社会科学
页码: 46-47页
主题词: 死亡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武汉大学哲学系;死亡问题;读后;人生观;正确看待;价值观;哲学界;视角
摘要: <正> 由武汉大学哲学系段德智教授著述、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死亡哲学》,是从崭新的视角——死亡哲学的角度来探讨人生堂奥的一部开拓之作。
该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
我们搜集了武汉大学部分教师和学生的读后反应,现综述如下: 哲学系李维武博士说:《死亡哲学》的一个很大特点与优点,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作了比较深入和系统的阐发。
马克思主义有没有自己的死亡哲学?对于这个当代国际哲学界争议甚大的问题,该书作了肯定的回答。
该书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是马克恩主义哲。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段德智:中国哲学家论死亡雅斯贝尔斯的“生存哲学”,至今人们对它依然见仁见智,毁誉不一。
但是,他在其《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一书中提出的“轴心时期”的史学范畴,却一直受到人们的青睐,被人们广泛地使用着。
雅斯贝尔斯的所谓“轴心时期”意指的大约是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一时期。
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在人类历史上,轴心时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极其重要的时间段。
因为差不多所有主要的文化选择,亦即差不多所有的文化传统都是在这个时期被确认和建立起来的,自那以后,人类文明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人类文化生活中却再也没有发生过任何类似的具有新的意义的事情。
也就是说,各个民族或各个地域的文化传统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时期奠定下来的。
这一时期,在西方,是古希腊罗马奴隶制形成、繁荣并继续发展的时期,是一个孕育并产生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哲学的辉煌时期;在中国,则是所谓“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孕育并产生孔子(儒家)哲学和老子(道家)哲学的辉煌时期。
正如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构成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基础一样,孔子和老子的哲学也构成了中国哲学传统的基础。
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中国死亡哲学也是如此。
一、死亡的社会性与社会价值取向:“杀身成仁”与“舍生取义”中国死亡哲学区别于西方死亡哲学的第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它之特别注重死亡的社会性和社会价值取向。
与海德格尔和尼采等西方哲学家突出地强调死亡的个体性或本己性不同,中国哲学家比较注重死亡的社会性和社会价值取向,曾先后提出过“杀身成仁”与“舍生取义”等著名的死亡哲学命题。
诚然,孔子也十分关注死亡的自然属性,他不仅曾发出过“逝者如斯”的感慨,而且《论语》中还有“死生有命”的说法。
然而,他更为关注的则是死亡的社会属性和社会价值取向。
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提出了“杀身成仁”这一死亡哲学命题,强调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
”(《卫灵公》)人为什么应当为了“成仁”而不惜“杀身”呢?这是因为,在孔子看来,惟有“仁”这个范畴才充分地表达了“人”的本质规定性,才使人成其为人,使君子成其为君子。
他在《论语》中反复强调“君子去仁,恶乎成名”(《里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就是想告诉人们,离开了“仁”讲“修身”,只是徒讲形式而已,其结果不是不得要领,就是培养出“小人儒”或“伪君子”。
而这归根到底又是因为惟有“仁”这种美德才充分地表达了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的人的社会属性。
孔子的“仁”,按照朱熹的说法,内蕴着两个层面:一为“忠”,二为“恕”。
曾子所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即是谓此。
但是,孔子所谓“忠”,无非是“尽己为人”,所谓“恕”无非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因此,在孔子这里,“人”绝对不是克尔凯廓尔的“孤独个体”,而是一种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主体,自我与他我的关系因而也不是那种“我-他”关系,而是一种“我-你”关系。
其实,孔子讲“仁者,爱人”,所强调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思想。
儒家关于美德有多种说法,如“首德”(仁),“两种基本美德”(仁-智),“三达德”(仁-智-勇),“四德”(仁-义-礼-智)以及“五常”(仁-义-礼-智-信)等等。
但是,不管怎么说,“仁”都不仅始终是诸多美德中的一种,而且始终处于诸多美德中的第一位。
而且,真正说来,其他美德也没有不同“仁”德“内在地”关联着的,仿佛只是为了“丰富仁的内在资源”而设定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说:“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里仁》)“同理,勇也不仅是血气之勇,而且也是一种道德上的勇气;义也不仅是一种法律上的公正,而且也是一种人道上的公正;礼不仅是恪守祭祀仪式,而且也是伦理行为方面的彬彬有礼,而信则基本上是人际交往中的可信赖性。
”[1]而这正是孔子把“践仁”作为君子终极承担和终极献身,宣称“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的根本缘由,这也正是孔子宣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根本缘由。
不难看出,孔子所赞赏的这种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乃至身家性命的仁者风骨正是基于他对人生和死亡的社会属性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深刻体悟之上的。
与孔子讲“杀身成仁”不同,孟子则强调“舍生取义”。
孟子并不轻生,他在《尽心章句上》中曾强调说:“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在《离娄章句下》中更进一步强调说:“可以死,可以不死,死伤勇”,以为在可以不死的情况下随意死去便有失“大勇”。
在他看来,人之欲求生,一如口之欲求美味、目之欲求美色、耳之欲求好听的声音、鼻子欲求芳香的气味、四肢欲求舒适安逸的环境一样,都是人之本性之所好,无可非议。
问题在于:在人的欲求对象中,究竟有无高于“生”的东西。
孟子认为,义就是高于“生”的东西,是比生更值得欲求的东西。
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他提出了“舍生取义”的死亡哲学命题,宣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告子上》)这样,孟子就把“义”提升到了生死抉择至上标准和唯一准绳的高度。
孟子的“舍生取义”虽然有别于孔子的“杀身成仁”,但却不是同后者相对立的东西。
“义”,从字面上看来,虽然无非是礼仪、适宜、道理诸义,但在孟子这里所要表达的却是“仁”的一个更深层面的内容。
孟子曾尖锐地批评告子的“仁内义外”的观点,说告子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义”(所谓“告子未尝知义”),并在事实上提出了“义因仁果”“仁由义生”的说法。
这是因为,在孟子看来,“义”不仅不是外在于人之本心的东西,反而恰恰是内在于人之本心且是使人之本心成为人之本心的东西。
孟子认为,“凡同类者”,其本性也都相同,人这个类也是如此。
人这个类的本性即在于“义”,从而人之能否成圣成贤,关键也正在于能否得到这个“义”。
他解释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
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
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耳。
”(《告子上》)这就把“义”看成了“人同此心”之心,看成了人的本质规定性,并使之获得了终极实在的本体论意义。
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孟子突出地强调了“义”在“仁”的生成过程中的能动性品格和内驱力地位。
孟子不仅同孔子一样,认为君子和圣贤必须具有仁德,而且还进一步深层次地探讨了仁德的成因问题。
在孟子看来,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具有“仁”德,首先就在于他具有“恻隐之心”,然而,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虽然同“仁德”有关,但毕竟还称不上“仁德”,只能说是“仁端”,为要从“仁端”达到“仁德”,就需要对“恻隐之心”(即“仁端”)加以扩充、培植。
孟子常把这一培植的过程称作“尽心”“知性”或“存心”“养性”,或曰“养浩然之气”。
但是,“尽心”“知性”也好,“存心”“养性”也好,“养浩然之气”也好,归根到底,用孟子的话说,是一个“集义所生”的过程,离开了“集义”,便既无所谓“尽心”“知性”、“存心”“养性”,也无所谓“养浩然之气”。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提出了“居仁由义”的修养理路,强调:“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
”(《离娄章句上》)由此看来,孟子的“舍生取义”与孔子的“杀身成仁”虽然从表面看来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都是以强调死亡的社会性为鹄的的。
诚然,儒家的死亡哲学在随后的发展中,又新增了不少内容,但孔孟的“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一直构成儒家死亡哲学的基本格调。
朱熹继孔孟之后,明确地赋予“仁”以哲学本体论地位,强调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
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避之,则曰仁而已矣。
”又说:“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用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
”而且,在朱熹看来,这也正是孔子之所以强调“杀身成仁”的理据。
因为,“‘杀身成仁’,则以欲甚于生,恶甚于死,为能不害乎此心也。
”(朱熹:《仁说》)与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则更进一步用“公私”、“义利”和“经世”“出世”作为“判教”的尺度,强调说:“某尝以义利二字判儒释,又曰公私,其实即义利也。
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间,灵于万物,贵于万物,与天地并而为三极。
……其教之所从立者如此,故曰义、曰公。
释氏以人生天地间,有生死,有轮回,有烦恼,以为甚苦,而求所以免之。
……故其言曰:‘生死事大。
’……其教之所从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
惟义惟公,故经世;惟利惟私,故出世。
”[2]他又批评释家说:“释氏立教,本欲脱离生死,惟主于成其私耳,此其病根也。
”[3]正因为如此,他多次针对释家的死亡观明确地强调说:“凡欲学者,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
今所学果为何事?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
”[4]“身或不寿,此心实寿”,“或为国死事,杀身成仁,亦为考终命。
”[5]从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到陆九渊的“惟义惟公”和“为国死事”,所强调的显然都是死亡的社会性和社会价值。
当代新儒家梁漱溟(1893-1988年)一生倡导“以身殉道”,即便80岁高龄,在“文化大革命”中身处逆境的情况下,面对一些人的政治淫威,拍案而起,为捍卫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发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战斗呐喊,并决意把他“个人的安危,付之于天”,所承继的正是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传统和凛然正气。
二、死亡的终极性和非终极性:“死而不朽”与“死而不亡”中国哲学家既然特别注重死亡的社会性和社会价值取向,也就势必会特别注重死亡的终极性和非终极性,亦即人生的有限性和无限性,从而提出“死而不朽”和“死而不亡”的死亡哲学论断。
中国哲学家虽然看重人的寿命,但还是清醒地意识到了死亡的终极性。
《论语•泰伯》中有曾子的两段话是颇耐人寻味的。
一段是曾子在谈到儒士应当具有的“弘大刚毅”品格时讲的。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另一段话则是在曾子临终时对他的弟子讲的。
曾子说:“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曾子的这两段话,前一段讲的是人的精神层面的终极性,后一段讲的是人的身体方面的终极性,所关涉的都是人生的有限性和死亡的终极性。
然而,中国哲学家也并不因此而否认人生的无限性和死亡的非终极性。
因为,无论是“死而后已”,还是“吾知免夫”,都只是就志士仁人生前“自强不息”的“践仁”活动而言的,而不是就他们的生存价值而言的。
而如果从后一个层面看,则中国哲学家显然是特别在乎人生的无限性和死亡的非终极性的。
程子在解释曾子的这些话时,曾经说道:“君子曰终(停止),小人曰死(绝灭)”。
这就清楚不过地说明,中国哲学家在意识到死亡的终极性或人生的有限性的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了死亡的非终极性或人生的无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