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在中国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

代教育 的起 步与发展 。传教 士最初办教会 学校主要 这 使得西方传教士活动处 于多层色彩 的笼罩 下而变 集 中在 开放 的 五个通 商 口岸 、 港和 澳 门 , 17 得 愈加特殊 。 香 从 85 一方面我们应看到传教士传教是 随着西
年起 , 教会学校急 剧发展。 19 , 到 89年 教会学校达到 方 的殖 民主义 、 帝国主义的对外扩 张 , 随着血与火 伴 约 1 6 ,学生人数 增加 到三 万多人 。到 1 0 7 6所 9 0年 传播开来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正视西方传教士是近 后, 教会 学校 迅速发 展 , 表是 1 1 下 9 9年新 教传 教士 代 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 给封闭的 中国带来 了西 学校 和招生人数 , 中可看 出教会学 校在 中国教育 方先进的政治制度 与先进文化 , 从 也把中 国的文化传播 中所 占的份量 。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正视西方传教士是近后教会学校迅速发展下表是1919年新教传教士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给封闭的中国带来了西学校和招生人数从中可看出教会学校在中国教育方先进的政治制度与先进文化也把中国的文化传播中所占的份量
历 ・0 史x■ 臻p ? 蹲 凝
西方传教士⑧ 中闽
口 李 芸 尹 国安
兴办慈善事业。传 教士兴办慈 善事业主要有行
10 年 《 丑 条约 》 91 辛 的签 订打 击 了中 国 的顽 固 医事业 、 慈幼事业与赈济救灾事业 等。 教会慈幼事业
守 旧势 力 , 西方传 教士进一步深入 内地传 教。 人们对 包括育 婴堂 、 孤儿 院 、 童学 校 、 哑学 校 等慈幼机 肓 聋 宗教的态 度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由敌 视发 展为 承认乃 至认 同 , 信仰基 关 , 教士还经常地从事有计 划 、 组织的赈济救灾 传 有 督 教的人数也迅速增加 。 二 、西方传教士在 中国进行 了哪些活动 动, 目的在于 使中 国基 督教化 , 中国人 民了解 、 使 认 工作 , 12 如 9 0年 , 华北 5省发生 大旱灾 , 正定天主教
美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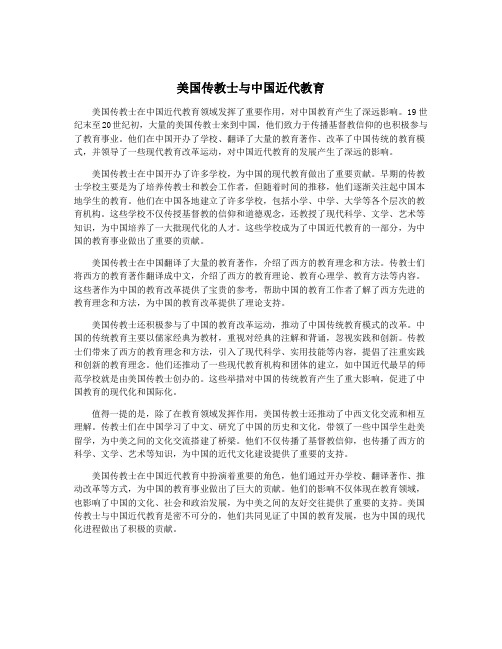
美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美国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教育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量的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致力于传播基督教信仰的也积极参与了教育事业。
他们在中国开办了学校、翻译了大量的教育著作、改革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并领导了一些现代教育改革运动,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许多学校,为中国的现代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期的传教士学校主要是为了培养传教士和教会工作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关注起中国本地学生的教育。
他们在中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等各个层次的教育机构。
这些学校不仅传授基督教的信仰和道德观念,还教授了现代科学、文学、艺术等知识,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现代化的人才。
这些学校成为了中国近代教育的一部分,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翻译了大量的教育著作,介绍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传教士们将西方的教育著作翻译成中文,介绍了西方的教育理论、教育心理学、教育方法等内容。
这些著作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帮助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了解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
美国传教士还积极参与了中国的教育改革运动,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模式的改革。
中国的传统教育主要以儒家经典为教材,重视对经典的注解和背诵,忽视实践和创新。
传教士们带来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引入了现代科学、实用技能等内容,提倡了注重实践和创新的教育理念。
他们还推动了一些现代教育机构和团体的建立,如中国近代最早的师范学校就是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
这些举措对中国的传统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在教育领域发挥作用,美国传教士还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
传教士们在中国学习了中文、研究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带领了一些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为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
浅议早期来华传教士的不同传教策略

浅议早期来华传教士的不同传教策略早期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中采取了不同的传教策略,这些策略反映了传教士们在与中国文化和宗教相遇时的不同态度和方法。
本文将从文化交流、语言翻译、教育传道等方面,浅议早期来华传教士的不同传教策略。
一、文化交流早期来华传教士在进行传教活动时,面对中国文化和宗教传统,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来与当地人进行文化交流。
有些传教士采取了封闭式的策略,将传教士居住在传教区内,与当地人保持距离,不愿意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传统。
这种策略导致传教士与当地人之间的隔阂加大,很难取得他们的信任和认可。
而另一些传教士则采取了开放式的策略,他们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尊重中国传统,与当地人建立友好关系。
这种策略使得传教士更容易接近当地人,获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也更有可能将基督教传入中国。
二、语言翻译在早期来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中,语言翻译是一项关键工作。
一些传教士并没有重视学习中文,甚至使用殖民者的语言进行传教活动,这使得他们与当地人之间存在沟通障碍,难以进行有效的传教工作。
这种传教策略往往导致传教士无法深入中国内地,只能在一些外国殖民地地区传播基督教。
而另一些传教士则重视学习中文,积极进行语言翻译工作。
他们致力于将圣经等基督教经典翻译成中文,以便更好地传播基督教思想。
这种传教策略大大提高了传教士与当地人之间的沟通效率,也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教育传道早期来华传教士在传教活动中以教育为手段进行传道,也是一种重要的传教策略。
有些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学校,积极进行教育工作,以此来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的思想和价值观。
这种教育传道的策略不仅可以培养更多的基督徒,而且也能够提高中国人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为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传播打下良好的基础。
另一些传教士则采取了巡回传道的策略,他们走村串巷,挨家挨户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的思想和教义。
这种策略是最直接、最贴近中国人群的传教方式,能够更好地与普通百姓进行沟通,引导他们接受基督教的信仰。
【历史典故】回看历史: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13所名牌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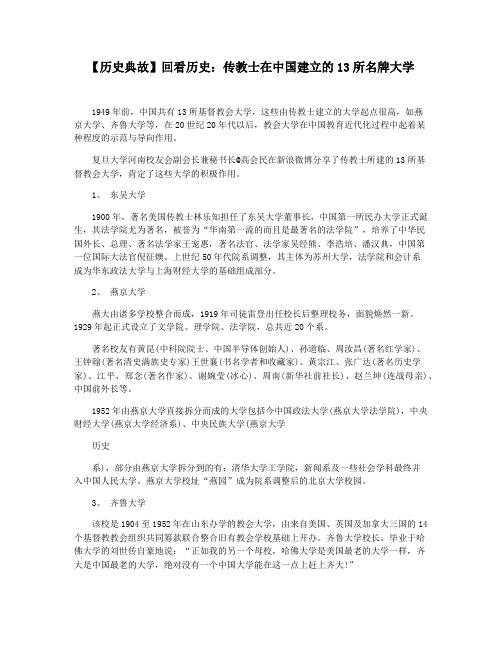
【历史典故】回看历史: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13所名牌大学1949年前,中国共有13所基督教会大学,这些由传教士建立的大学起点很高,如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
复旦大学河南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高会民在新浪微博分享了传教士所建的13所基督教会大学,肯定了这些大学的积极作用。
1、东吴大学1900年,著名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担任了东吴大学董事长,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正式诞生,其法学院尤为著名,被誉为“华南第一流的而且是最著名的法学院”,培养了中华民国外长、总理、著名法学家王宠惠,著名法官、法学家吴经熊、李浩培、潘汉典,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倪征燠。
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其主体为苏州大学,法学院和会计系成为华东政法大学与上海财经大学的基础组成部分。
2、燕京大学燕大由诸多学校整合而成,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后整理校务,面貌焕然一新。
1929年起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总共近20个系。
著名校友有黄昆(中科院院士、中国半导体创始人)、孙道临、周汝昌(著名红学家)、王钟翰(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王世襄(书名学者和收藏家)、黄宗江、张广达(著名历史学家)、江平、郑念(著名作家)、谢婉莹(冰心)、周南(新华社前社长)、赵兰坤(连战母亲)、中国前外长等。
1952年由燕京大学直接拆分而成的大学包括今中国政法大学(燕京大学法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燕京大学经济系)、中央民族大学(燕京大学历史系),部分由燕京大学拆分到的有:清华大学工学院,新闻系及一些社会学科最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
燕京大学校址“燕园”成为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校园。
3、齐鲁大学该校是1904至1952年在山东办学的教会大学,由来自美国、英国及加拿大三国的14个基督教教会组织共同筹款联合整合旧有教会学校基础上开办。
齐鲁大学校长、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刘世传自豪地说:“正如我的另一个母校,哈佛大学是美国最老的大学一样,齐大是中国最老的大学,绝对没有一个中国大学能在这一点上赶上齐大!”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齐鲁大学被解体,相关院系并入不同的大学,如药学系并入今中国药科大学,理学院中的生物、物理和化学三系并入今山东师范大学。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13所教会大学和其它教会大学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13所教会大学和其它教会大学(如:天主教辅仁大学、天主教耶稣会震旦大学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中国共有13所基督教教会大学,分别是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齐鲁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cheeloo)、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之江大学Hangchou Christian College、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金陵女子文理学院Ginling College、、沪江大学Shanghai University、华中大学Huachung University、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华南女子文理学院Hwa Nan College华西协和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等。
虽然数量不多,但起点很高。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
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
由此可见,教会大学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它们为中国高等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外,中国教会大学还包括南京:金陵神学院,上海:震旦大学(Aurora University)为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上海创办的著名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著名高校。
以及徐汇神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天主教辅仁大学,天津:天津工商学院,长沙:湘雅医学院等。
当年(新中国成立前)沪上七大私立名校(大学):圣约翰(教会大学)、震旦(教会大学)、复旦、光华(圣约翰分离的教会大学)、大夏、大同、沪江(教会大学)。
传教士来到中国的起因

当西方传教士空洞的教 义宣传屡遭碰壁时,满足 乡土民众基本物质生活需 要的间接布道活动就成 为他们打开民众入教潮 流的简洁而有效的途径。
3.促进文化交流
部分传教士向中国介绍了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并把 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并取得了中国官员和士大夫的信任和支持。
美国传教士
狄考文 (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 1908) 美国宾夕法尼亚人。基督教北长 老会传教士。 1863年底来华, 1864年1 月到登州传教, 开办蒙养学堂。该学堂 1876年改称文会馆,由小学升为中学, 1881年开设大学预科,1904年迁潍县, 与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办的广德书院大学 部合并,改称广文学堂(后成为齐鲁大学 一部分)。他多次利用回国休假机会为文 会馆募集资金和实验设备。1880年获汉 诺威大学荣誉神学博士学位。1888年获 伍士德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890年 基督教来华传教士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推选他为“中华教育会”首任会长。
德国传教士
邓玉函,(Johann Schreck, 1576年-1630年5月11日),天 主教耶稣会德国传教士。生于 康斯坦茨。1618年4月16日,随 金尼阁在里斯本启程赴东方。 1619年7月22日抵达澳门。同行 的传教士还有汤若望、罗雅谷、 傅泛际。1621年到杭州传教。 1623年到达北京。1629年,经 徐光启推荐在历局任职,1630 年病逝于北京,享年55岁。埋 葬在北京滕公栅栏。著有《远 西奇器图说》。他第一个把天 文望远镜带进中国。他还是伽 利略的朋友。
4.为欧洲殖民者的侵略活动服务
认真
听讲
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士是跟随殖民者之后来到中国进行 宗教活动的.他们当中,有人以传教作掩护,在中国测 绘地图,搜集情报,为欧洲殖民者的侵略活动服务。
清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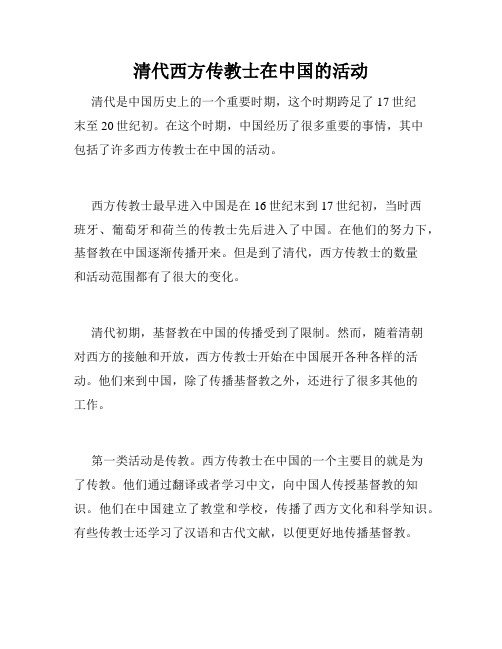
清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跨足了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
在这个时期,中国经历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其中包括了许多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
西方传教士最早进入中国是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当时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的传教士先后进入了中国。
在他们的努力下,基督教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
但是到了清代,西方传教士的数量和活动范围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清代初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受到了限制。
然而,随着清朝对西方的接触和开放,西方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展开各种各样的活动。
他们来到中国,除了传播基督教之外,还进行了很多其他的工作。
第一类活动是传教。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传教。
他们通过翻译或者学习中文,向中国人传授基督教的知识。
他们在中国建立了教堂和学校,传播了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
有些传教士还学习了汉语和古代文献,以便更好地传播基督教。
第二类活动是医疗和救济。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另一个重要活动是医疗和救济。
在当时,中国许多地方的医疗条件都比较落后,而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先进的医学知识和医疗设备能够对当地人的健康状况起到很大的帮助。
很多传教士都在中国建立了医院和救济站,为当地人提供医疗服务和援助。
第三类活动是研究和教育。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另一个重要活动是研究和教育。
他们学习了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文献,研究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提供了很多的数据和信息。
同时,他们还在中国建立了学校和大学,推广西方的教育理念和先进的教学方法。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受到了中国政府的一定程度的限制和压制。
但是,他们的工作还是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他们的医疗、教育和救助活动帮助了中国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促进了中国的社会进步。
他们学习中国的文献和研究中国史、文化等方面,也为西方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总之,西方传教士在清代中国的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涉及到很多方面,包括宗教、文化、医学、教育、社会等。
鸦片战争时期外国传教士在华活动

鸦片战争时期传教士在中国的文化活动及其产生的积极作用对外汉语121班徐嘉莹 2012212680内容提要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是近代史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列强获得了传教权。
西方传教士涉足香港和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东南沿海城市,为了传播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对近代中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关键词传教士文化活动进步鸦片战争时期,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尤其是中法《黄埔条约》其中一条要求允许传教士在通商口岸传教,法国人可以在五口建造教堂、坟地,清政府有保护教堂的义务。
英、美等各国传教士纷纷涉足东南沿海,从传教的目的出发,想要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1.创办报刊、杂志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报刊的目的,是企图用“文字播道”的方法来宣传基督教,为殖民侵略服务。
用文字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文化观念。
在传教士看来,“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只要控制住在中国出版的“主要的报纸”和“主要的杂志”,“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脊梁骨”。
○1因此这些报纸的内容除宣传基督教外,还有干涉中国政治,搜集中国情报,为殖民侵略服务的作用。
但是,由于传教士把介绍西学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因此, 这些报刊杂志客观上在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
大多数报刊都介绍了大量的有关政治、历史、地理、天文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
如《格致汇编》、《万国公报》等。
《万国公报》还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介绍马克思及其《资本论》的刊物。
“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指社会主义)之一派,为德人之马客偲(马克思)主于资本者也。
”○2西方传教士对西方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介绍,客观上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加深了他们对西方的认识,了解了一些时事,学习到了新事物,推动了他们向西方学习的步伐,促进他们的觉醒。
清初传教士白晋在华活动及其贡献

清初传教士白晋在华活动及其贡献清初传教士白晋是西方文化传播的先驱之一,他为中国的近代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白晋自1689年来华一直到1721年去世,他在中国的活动期间,不仅学习了中文、学习了中国文化,更通过自己的教育方法和译著等文化输出,对当时中国的文化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本文将从他的生平经历、传教活动、学术贡献等多个方面来探讨白晋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交流的重要贡献。
一、生平经历白晋生于荷兰的代尔夫特市,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孩子。
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关注。
后来,他希望能在传教行业中发挥自己的天赋和使命,并来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学习神学。
1692年他按照浸信会的准则受洗。
从那时起,他进一步学习了拉丁语并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
白晋出发前往中国的时候,他携带了一部分牛津词典,这个细节非常有意义。
因为下面我们要提到的词典是他进行中西方文化对接的重要材料之一,证明了白晋对中国教育的深刻研究和投入。
乘坐葡萄牙船只来到中国之后,白晋开始了他的中国传教生涯。
在这时期,欧洲人在中国是非常稀少的,目睹清朝的盛衰,白晋开始体悟到中国的文化体系,进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
二、传教活动白晋到达中国后,他开始讲授西方基督宗教,并将其翻译成中文来传播。
在翻译基督宗教的时候,他也不忘将欧洲的科学知识带给了中国人。
他的传教活动非常成功,不仅有很多中国人前来听他的讲座,还被派往多个省份,继续传教。
在白晋的传教工作中,他注重文化的融合,希望帮助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体制实现现代化和欧洲化。
他也推广了修建和经营学校,以更好地推广西方文化。
1. 白晋首先到达中国的地方是南京。
他在南京的主要工作是改善当地的福音会会堂,让它能够适应基督教的礼仪。
2. 在福州传教期间,白晋展开了大规模的传教活动,收容了大量规模庞大的信徒,建立了一群基督教的教育班级。
他还撰写了一些中国文化的经典著作,翻译了宽敞的基督教经典。
3. 在南京时期,白晋发掘了许多中国古代图书,从中发现了许多与希腊文化贯穿的主题和像和荒谬的。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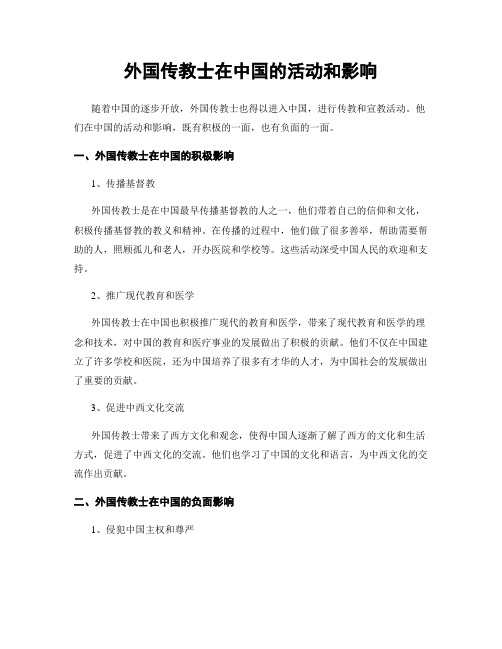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随着中国的逐步开放,外国传教士也得以进入中国,进行传教和宣教活动。
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负面的一面。
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积极影响1、传播基督教外国传教士是在中国最早传播基督教的人之一,他们带着自己的信仰和文化,积极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和精神。
在传播的过程中,他们做了很多善举,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照顾孤儿和老人,开办医院和学校等。
这些活动深受中国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2、推广现代教育和医学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也积极推广现代的教育和医学,带来了现代教育和医学的理念和技术,对中国的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们不仅在中国建立了许多学校和医院,还为中国培养了很多有才华的人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外国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文化和观念,使得中国人逐渐了解了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他们也学习了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贡献。
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负面影响1、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曾经对中国的主权和尊严进行了侵犯,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持批判态度,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进行干涉,给中国的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和压力。
2、带来了外来宗教和文化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带来了外来的宗教和文化,使得中国的文化受到冲击和侵蚀。
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信仰进行抨击和否定,使得中国的文化传承遭到阻碍和破坏,给中国的文化带来了一定的损失和冲击。
3、在中国传播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思想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也传播了一些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思想,损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和自信心,甚至引起了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
三、结语总的来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是一个双刃剑,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我们应该客观看待他们的活动和影响,既要肯定他们的贡献和努力,也要警惕他们的不良影响和负面作用。
希望未来外国传教士能够更好的融入中国的社会,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多的贡献。
【清朝历史】清朝传教士是如何在中国传教的

【清朝历史】清朝传教士是如何在中国传教的?1644年,清王朝开始了对中国的统治。
鉴于自己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以在政治上尽量保存明代章法,以巩固其统治。
在顺康时期,教士活动自由,传教事业发展迅速。
最初,一般东来教士均属耶稣会派,意见比较一致,且东方传教权受葡萄牙一国保护。
罗马教廷也因东方教区初辟,对于教士传教方法任其自由,不予干涉。
到17世纪中叶,这种局面逐渐变化。
葡萄牙势力日趋衰落,不能独霸东方传教保护权,因而在中国除了耶稣会派,又出现了西班牙多明我派和巴黎外方传教会等派别。
积久,各派意见渐歧,纷争渐起。
17世纪中叶,法兰西崛起欧洲,与各国互争雌雄。
罗马教廷也欲借助法国势力,消弱葡萄牙独霸东方传教的地位。
1658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委派法国耶稣会教士巴流和另一教士兰贝尔特为专使,东来督察安南教务,并管理中国长江以南数处教会事业。
1660年,又派一名叫吉突兰的教士为专使。
督察南京教务,并管理朝鲜及中国北部数处教会事务,以扩大教廷的监督权。
但是葡萄牙人坚决反对教廷专使插手中国教务,双方矛盾发展。
1690年,教廷为了缓和矛盾,在中国境内划出南京、北京、澳门三大主教区,归葡人管理。
而葡人竟将中国各省尽数划归三大教区之内,致使教廷派来的专使、主教无插足之地。
对此,教廷深为不满。
1699年,教廷派出大批传教士为特使、主教来华,并明令葡人缩小其教区,而另辟八个主教区,归教廷直接管辖。
每一教区由教廷派遣一副主教,负责巡查监督中国教会。
为防止在华教士反对,教廷又专门发下通知说,必须服从教廷所派主教的管理,教中仪式亦须遵守教廷颁布的命令执行。
通过派遣专使、主教,教廷在东方布道事业中的统治权日渐增强。
正当罗马教廷开始着手削弱葡萄牙的东方保教权时,在华各派传教士,对中国的祭天、祭孔、拜祖等习尚风俗展开争论:一派认为中国教徒祭祖、祀孔崇拜偶像,触犯天主教十戒之一,教会决不容许;一派认为,凡中国习俗,与教仪并无大冲突者,均应不在禁止之例。
当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做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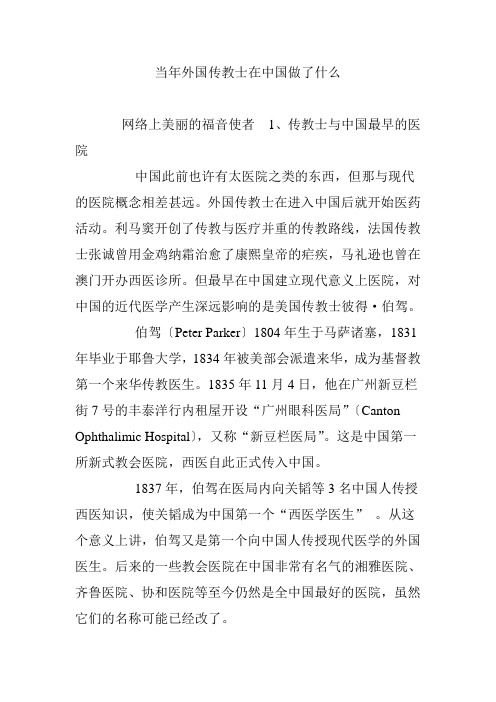
当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做了什么网络上美丽的福音使者1、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
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
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在澳门开办西医诊所。
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
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
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学医生”。
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学的外国医生。
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的湘雅医院、齐鲁医院、协和医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2、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
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3、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中国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
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科学发展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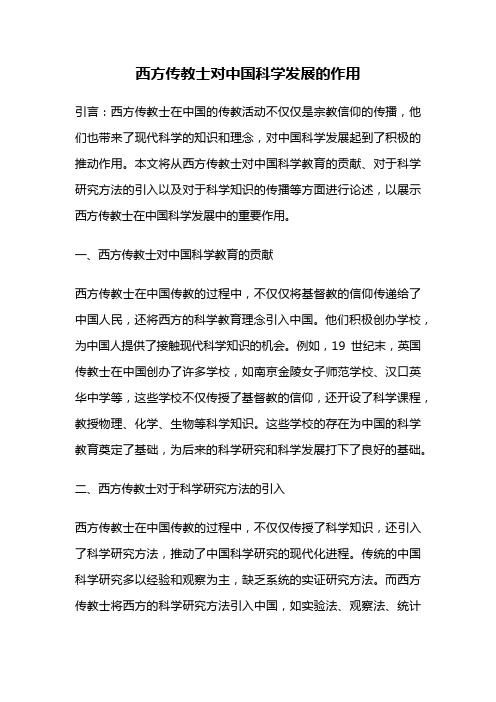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科学发展的作用引言: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传播,他们也带来了现代科学的知识和理念,对中国科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文将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科学教育的贡献、对于科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对于科学知识的传播等方面进行论述,以展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科学教育的贡献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不仅仅将基督教的信仰传递给了中国人民,还将西方的科学教育理念引入中国。
他们积极创办学校,为中国人提供了接触现代科学知识的机会。
例如,19世纪末,英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许多学校,如南京金陵女子师范学校、汉口英华中学等,这些学校不仅传授了基督教的信仰,还开设了科学课程,教授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知识。
这些学校的存在为中国的科学教育奠定了基础,为后来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西方传教士对于科学研究方法的引入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不仅仅传授了科学知识,还引入了科学研究方法,推动了中国科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
传统的中国科学研究多以经验和观察为主,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方法。
而西方传教士将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引入中国,如实验法、观察法、统计法等,为中国科学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例如,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马卡蒂在中国开展了地球物理研究,他运用了现代地质学的研究方法,系统地进行了地质调查和地震观测,为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西方传教士对于科学知识的传播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积极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知识,推动了中国科学知识的更新和发展。
他们将西方的科学书籍、期刊、研究报告等带入中国,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了解西方科学的窗口。
例如,19世纪末,英国传教士麦克尔在中国翻译了许多西方科学书籍,如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通过翻译和出版,将这些重要的科学著作介绍给了中国学者,为中国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西方传教士在华贡献

西方传教士在华的历史贡献靠着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的爱以及他们的牺牲,使得福音在中国传开。
在官方舆论主导了这样一种一面倒的认识之后,对在华西方传教士做任何正面的评价是十分艰难的。
然而,我们必须要还历史一个公道,否则我们有负于历史。
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在向中国学生学者传福音时,一个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干了那么多坏事,我们为什么还要信他们的宗教?”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就是因为生在“新中国”的这一代知识份子,在国内所接触到的有关在华西方传教士的资料都是负面的。
比如,在华西方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马前卒”,是“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而基督教则是“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药”。
就如去年10月1日罗马教廷将一百二十名在中国的天主教的“殉道者”,册封为“圣徒”之后,《人民日报》就刊登文章,指名道姓地抨击那些所谓的“圣者”,说他们有的是“作为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工具的外国传教士”,有的是“作为那些劣迹斑斑的外国传教士的帮凶和追随者的中国教徒”,还有的是“在由于外国传教士凭藉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横行乡里,欺凌百姓,激起人民反抗中死于非命,而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殉难者和殖民地教会势力的牺牲品的中国教徒”(见《揭开所谓“圣人”的面目》,署名为“史岩”,《人民日报》2000年10月3日)。
这篇文章虽然是针对天主教传教士的,但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的宣教士并无明显的差别,一言以蔽之,都是“一丘之貉”。
在官方舆论主导了这样一种一面倒的认识之后,对在华西方传教士做任何正面的评价是十分艰难的。
然而,我们必须要还历史一个公道,否则我们无论是作为基督徒,或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学人,都会感到有负于历史,有负于前人和后人,也有负于自己的良心。
在这里,我完全无意于美化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全部行为。
西方传教士和我们一样是普通人,也会有普通人有的弱点和局限。
传教士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上的作用

传教士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上的作用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活动,作为西方殖民者对华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辅助手段,在加剧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又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具有两重性。
客观上,对介绍西方近代文明,促进中国封建社会机体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
从这一方面来说,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义是传播西方科学文化,酝酿和促进近代中国新闻、出版、教育等项事业以及资产阶级先进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之一,具有推动中国近代化运动和促进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作用。
一、创办报刊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始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文化活动,应首推办报。
早在1815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就在马六甲编辑出版了一份名为《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期刊,这是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第一份中文期刊。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停刊以后,基督教传教士又陆续在南洋、香港、澳门和广州等地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文报刊。
如《东西洋每月统纪传》、《天下新闻》、《各国消息》等。
其中,德国传教士郭实猎于1833年7月在广州编辑出版的《东西洋每月统纪传》,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
在这一时期,传教士还创办了一些以外商、传教士、外交官员为对象的外文报刊,其中以美国传教士俾治文编辑出版的《中国丛报》影响最大。
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的办报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十九世纪四十到九十年代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他们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其中大部分是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的名义创办的。
”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报刊的目的,是企图用“文字播道”的方法来宣传基督教,以实现“中华归主”和为殖民侵略服务。
因此这些报纸除宣传基督教外,:还起着干涉中国政治,搜集中国情报,为殖民侵略服务的作用。
但是,由于传教士把介绍西学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因而在客观上,这些报刊杂志在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沟通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
十九世纪德国传教士开始来华

十九世纪,德国传教士开始来华。
第一个来华的德国传教士是郭实腊,他决心为德国教会开辟中国教区。
传教士在中国主要从事布道、建立传教站、创办学校和举行医疗卫生事业等活动。
他们积极编撰文章,讲解教义,同时介绍西方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并钻研中国思想文化,介绍到本国。
郭实腊原名卡尔‧古茨拉夫(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1803—1851年,中文名郭实腊,又译为郭实猎、郭士立等),德国人,出生于普鲁士,18岁进入柏林教会学校学习,1823年入荷兰布道会,欲到中国传教,未获批准,遂脱离布道会,转为伦敦布道会服务。
1831和1832年他三次探察中国沿海地区,收集军事情报,绘制航海地图。
郭实腊的三次探察活动公布后,震动了对中国感兴趣的欧美商人、政客及传教士。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按照郭实腊的建议贿赂中国官员,顺利地扩大了对华输入鸦片。
郭实腊以“归化华人”身份进入广州,穿中国服饰,取中国名字,讲汉语。
1833年8月1日,郭实腊在广州创办了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这是创建于中国境内的第一家中文近代报刊,也是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份报刊。
花之安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年),生于德国科堡,19岁考入德国巴门神学院。
1864年加入礼贤会,受委牧师之职,并被派往中国。
1865年抵达香港,学习中国语言文字。
不久,入粤东内地宣传福音,并开办学校和医院,因在眼科手术上颇有成就,被当地人称为“圣手”。
他潜心研究中国典籍,著书立说,第一部中文著作是《西国学校》,介绍西方教育制度。
他也用德文写作并出版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著述。
1883年,花之安移居香港,继续从事传教活动。
1885年,迁居上海,参加了“广学会”的筹办工作,并成为《万国公报》主要撰稿人之一。
1898年,因德国在青岛建立殖民地,花之安被委派到那里建立传教点。
但他刚抵达不久就生病故世,被安葬在青岛。
对传教士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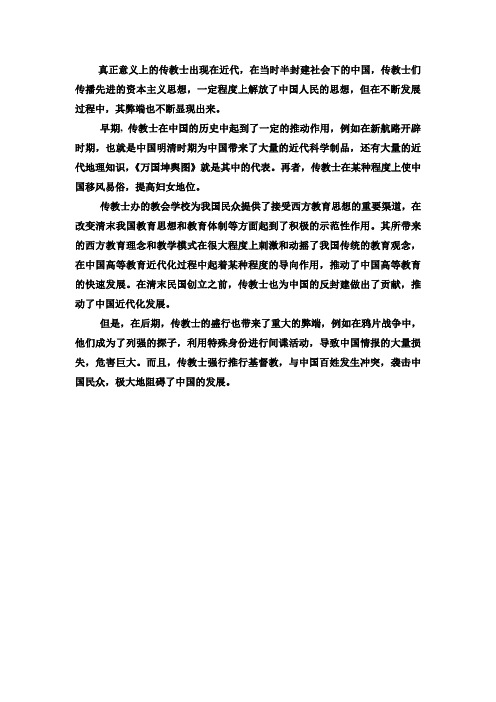
真正意义上的传教士出现在近代,在当时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传教士们传播先进的资本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思想,但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其弊端也不断显现出来。
早期, 传教士在中国的历史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例如在新航路开辟时期,也就是中国明清时期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近代科学制品,还有大量的近代地理知识,《万国坤舆图》就是其中的代表。
再者,传教士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移风易俗,提高妇女地位。
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为我国民众提供了接受西方教育思想的重要渠道,在改变清末我国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示范性作用。
其所带来的西方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刺激和动摇了我国传统的教育观念,在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导向作用,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
在清末民国创立之前,传教士也为中国的反封建做出了贡献,推动了中国近代化发展。
但是,在后期,传教士的盛行也带来了重大的弊端,例如在鸦片战争中,他们成为了列强的探子,利用特殊身份进行间谍活动,导致中国情报的大量损失,危害巨大。
而且,传教士强行推行基督教,与中国百姓发生冲突,袭击中国民众,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传教士在中国

传教士在中国请选中您要保存的内容,粘贴到此文本框本文出自《腾云》044期。
推荐人:苗曦四川日报区域中心副主任推荐语:如果说300多年前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全球化浪潮,甚至已有了全球贸易网络的雏形,那么当时前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们,比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无疑都是最早的全球化信使,而这批全球化“先行者”之所以能在中国立住脚,和当时的中国最高统治者对西方文明持相对宽容和学习的态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历史证明,当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心态更加包容和自信时,与外来文化的融合总会带来很多奇妙的产物。
以文治武功著称的康熙就是一个科技爱好者,尤其对传教士们带来的西洋乐器、机械玩具和各种西方科技知识充满热情。
比利时人南怀仁曾记述,朝鲜人曾向康熙进献活海豹,康熙询问他欧洲何书中记载了这种“鱼”。
南怀仁深得康熙信任,后来得以执掌钦天监,当上国家天文台台长,1688年死后也尽享哀荣,以国家之礼厚葬。
4年后,康熙甚至下保教令,宣布信奉天主教合法,以至于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
虽然大门打开了一道细缝,但仅仅依靠难以捉摸的皇帝个人爱好来推动与西方的交流并不靠谱,需要理性缜密的制度设计与民众的启蒙。
事实上此后清廷也不断在开放和封闭之间反复摇摆,既未能形成自上而下的思想启蒙,也没能融入当时的世界贸易与货币体系。
而这一年的世界却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688年开始,中国距离外面的世界反而越发遥远。
300多年后,采取开放政策的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者,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甚至都这样吓唬美国的CEO们:“想想亚洲、拉美、东欧吧,那里的人聪明、反应快又廉价,而且离你们这么近,他们是你们最可怕的噩梦。
”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物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已成为今天全球化的新驱动力,如何实现经济和市场全球化之后的新制度建设、新文明培育、新文化输送正成为中国下一个全球化课题。
文章内容传教士在中国文/[美]小约翰·威尔斯译/文昊1688年3月11日,北京西北角的中国人围在街边看一支送葬队伍走过。
[讲解]传教士在中国
![[讲解]传教士在中国](https://img.taocdn.com/s3/m/a875a61a854769eae009581b6bd97f192279bfec.png)
聖經翻譯的把關人富善
富善夫婦及兒女
富善牧師夫婦於1865年1月24日由紐約啟程,繞行大半個地球歷時六個月,才到達目的地中國上海。在上海稍事休息後再經天津抵達北京長駐,由差會安排宣教任務。
宣教士離鄉別井來到完全陌生的異文化地域,展開宣教聖工之前,當務之急,首重學習當地語文,否則一籌莫展。富善在求學期間已顯出對語文甚有深厚天賦恩賜之神速,實在令人驚異。初抵北京,為了與中國人打成一片,秉承入鄉隨俗;留長辮、穿長衫、予人有親切感。此舉除方便宣教外,對於學習中國語文亦產生事半功倍之效。1891年富善累積了豐富中文知識,出版了一本《中英袖珍字典》,內裏包括10,400個漢字。另外又出版了一本《官話特性研究》,更包
外出宣教
乡村小学
圣经翻译委员会
1890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全国会议,通过一项决议,由新教各宗派联合组成一个翻译班子,分成三组,分别负责文理、浅文理和白话文三种译本。经过28年的努力,在1919年出版,其中以白话文版的“国语和合本译本”最受欢迎,经过80个春秋,这部译本在中国仍广为使用,但分称“上帝”和“神”两种版本。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传教士在中国请选中您要保存的内容,粘贴到此文本框本文出自《腾云》044期。
推荐人:苗曦四川日报区域中心副主任推荐语:如果说300多年前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全球化浪潮,甚至已有了全球贸易网络的雏形,那么当时前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们,比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无疑都是最早的全球化信使,而这批全球化“先行者”之所以能在中国立住脚,和当时的中国最高统治者对西方文明持相对宽容和学习的态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历史证明,当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心态更加包容和自信时,与外来文化的融合总会带来很多奇妙的产物。
以文治武功著称的康熙就是一个科技爱好者,尤其对传教士们带来的西洋乐器、机械玩具和各种西方科技知识充满热情。
比利时人南怀仁曾记述,朝鲜人曾向康熙进献活海豹,康熙询问他欧洲何书中记载了这种“鱼”。
南怀仁深得康熙信任,后来得以执掌钦天监,当上国家天文台台长,1688年死后也尽享哀荣,以国家之礼厚葬。
4年后,康熙甚至下保教令,宣布信奉天主教合法,以至于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
虽然大门打开了一道细缝,但仅仅依靠难以捉摸的皇帝个人爱好来推动与西方的交流并不靠谱,需要理性缜密的制度设计与民众的启蒙。
事实上此后清廷也不断在开放和封闭之间反复摇摆,既未能形成自上而下的思想启蒙,也没能融入当时的世界贸易与货币体系。
而这一年的世界却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688年开始,中国距离外面的世界反而越发遥远。
300多年后,采取开放政策的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者,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甚至都这样吓唬美国的CEO们:“想想亚洲、拉美、东欧吧,那里的人聪明、反应快又廉价,而且离你们这么近,他们是你们最可怕的噩梦。
”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物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已成为今天全球化的新驱动力,如何实现经济和市场全球化之后的新制度建设、新文明培育、新文化输送正成为中国下一个全球化课题。
文章内容传教士在中国文/[美]小约翰·威尔斯译/文昊1688年3月11日,北京西北角的中国人围在街边看一支送葬队伍走过。
送葬的队伍里有一群人扛着铭板,上面有亮金的大字,写着死者的名讳和官衔:南怀仁,钦天监监正。
之后再跟着大队旌旗和一具大十字架,走在左右两列神情肃穆的华人基督教信徒当中。
死者遗像旁有皇帝亲撰的圣旨,写在一面大黄锦缎上面。
这位南怀仁,原名费迪南德·费比斯特,是比利时佛兰德来的传教士。
南怀仁是马泰罗·里奇(利玛窦)、约翰·亚当·沙尔·冯·贝尔(汤若望,1591-1666)之后到中国的传教士中杰出的一位。
三人都极擅长糅合科学、技术、俗家知识的巧劲儿,争取在中国皇帝面前有好的表现,进而为基督传教士在中国境内活动开拓出隐忍默许的空间。
康熙对耶稣会、对传教士的学问和技术真的很感兴趣,也是个人的兴趣。
传教士常在拂晓骑马到郊区的宫里教皇帝天文、物理、数学。
传教士先前就当过葡萄牙、荷兰特使的通译,现在则必须参与清廷和俄罗斯的议约。
传教士讨厌这些不堪的俗务,觉得和自己传教的使命有冲突,但1668年起传教士重新打入清廷,在其他省份为传教士打开了传教之路。
最后终于在1692年,由康熙皇帝下诏(康熙保教令),宣布天主教不违背中国社会的善良风俗及文化传统,大清子民可以合法信奉。
1688年3月跪在南怀仁墓前的传教士,有五位是新来的法国人。
他们到北京时,传教士在中国朝廷的最后一位开路先锋也正好去世。
1688年的头几个月就成了转折点。
直到这时,传教士派到中国的人都是欧洲的天主教徒,但都得听葡萄牙国王的号令行事,因为葡萄牙国王依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订的条约,由葡萄牙和西班牙二分天下,而将亚洲的天主教传教划为自己的保护区。
这几位法国教士虽然是注入了新鲜血液和人力,但也对葡萄牙的独大地位形成挑战。
而他们的学问和文采,在天主教到底该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老论战中,日后也会引发新的转折。
耶稣会从利玛窦开始和中国进行文化交流,为我们点出了现代世界早期全球互动的一些现象。
欧洲航海路线愈伸愈远的网,带他们遇见了一个个前所未知的民族;这些民族有许多被欧洲人硬塞进了他们先入为主的人种划分法。
但他们的中国经验,都放不进他们依欧洲、地中海历史所得来的划分法。
中国的文人官僚体制不以上帝或众神为道德的指导,而是古圣先贤;中国的秩序、富庶、繁华,在欧洲先前的异族见闻录里都找不到先例。
利玛窦深感他的中国文人朋友学识之丰富、道德之严正——他的中国文人朋友对他的感觉也一样——以致认为中国的精英传统和基督信仰大部分应该是相容的,不必作大变动。
尤其是儒家,可以视作中国俗家或民间传统之大成,像圣保罗将早期基督信仰连上了希腊文化;也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以天主教的热忱,赞叹希腊、罗马文化且辛勤研究一般,利玛窦他们浸染的就是这样的文化。
法国人为了扩大他们在中国传教的队伍,很快就拟订计划,要派一队法籍的传教士到中国来。
这些教士绝对独立。
为了拉高他们在北京的人气,选择的标准也以数学、天文及相关领域为优先。
此外,法国人还利用那时候公众对资料、地图的极大兴趣,说他们派的教士是到中国去为法国科学院作科学观测,搜集地理和天文资料。
康熙很高兴有传教士来了,懂数学、天文,还带来科学书籍和仪器,便召他们进京。
出现在南怀仁葬礼上的就是这五位法籍传教士。
其中一位叫让·弗朗西斯·热尔比隆(张诚),负责的是搜集地理资料,未几就有机会恣意驰骋他的想象。
那时,一批高官由索额图和皇帝的舅舅佟国维带领,即将出发去和俄国使节见面;俄国使节前一年冬天就已经在色楞格斯克等候了。
先前挡在清廷和俄国人间的语言障碍,现在俄国人找到解决办法了。
俄国使节现在一定带一位波兰秘书随行,他可以把俄国这边讲的每一句话译成拉丁文,再由北京这边的传教士把拉丁文译成汉语或满语。
这样一来,就势必需要两位传教士跟着去了。
其中一位是托马斯·佩雷尔(徐日昇),他在北京已经待了15年,因为教皇帝西洋音乐而特获宠信。
雀屏中选的另一位,就是热尔比隆。
1688年5月30日大清早,热尔比隆来中国还不到一年,到北京也不过四个月,就加入了清廷这支七八十名官员加千名骑士的壮观队伍,从北京出发往北去,还有皇帝的“太子”送行。
而在一路四个月穿越北亚草原的旅程里,热尔比隆这位法国科学院派出来的科学研究员,秉承仔细观察的精神,致力于扩充人类的知识;每天都详细记下一行人走的距离和方向、田野的自然景观、动植物,还有风土人情。
这样的冒险很难得,有幸一瞥宫中辉煌很刺激,搜集到的资料科学院也一定很高兴。
但传教士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历尽千辛万苦到远地来的目的,是拯救灵魂。
赢得清廷的宠信,是传教大业安全地持续的保障,但成果好像来得好慢。
虽然清廷的政策相当仁慈,但他们太容易因外国人的身份而遭猜忌,很可能还没学会语言、还没同化去和当地人沟通,就壮志未酬身亡。
只是,教会后来的想法还是渐渐转弯,朝培养本土传教士的路走。
因此,1688年8月1日,三位华人——刘蕴德、万其渊、吴历——在澳门一处教堂里,跪在雷戈里奥(罗文藻)主教(1616-1691,中国首任主教,第一位中国籍主教)面前祝圣,成为传教士。
吴历是传教士梦寐以求的最好信徒,以诗画技艺在创意、鉴赏都最超拔的精英圈里备受赞赏。
他是推动清初伦理、学术追求蓬勃发展的一员。
他觉得基督信仰和他追求的儒道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相辅相成。
这跟传教士从利玛窦开始的说法一样。
吴历生于1632年,清初循科考求仕进的路比较狭窄,他真正的兴趣在诗画,17世纪60年代已经和当时最有名的大师时有往来了。
17世纪70年代,吴历打入一批文人圈子,他们都是走过明末清初乱世的人。
吴历交往的人里,也有地方上钻研儒家经典和教诲的学者。
但社会和谐、世界大同的乌托邦理想,和现下污浊的尘世距离未免太大;朝代治乱兴亡的老套故事,误解和欺瞒也实在太多。
这样的人要的是“一主”,可以让他追随、礼拜,这样的人要的是了解世界起源和本质的新道路。
许多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从儒家转向了佛教,或从佛教转向儒家,要不就是祭出某个中国的民间信仰和英雄崇拜。
吴历则和一小撮人一起在1679年做出惊人之举,转进一个显然是异己的宗教。
传教士曾冒险朝中国文化靠拢。
有些批评他们的人还认定耶稣会教出来的基督信徒,根本不懂上帝之子受难而后复生演的是哪一幕惊天动地的情节,上帝之子又赐予每一位罪人以怎样的救赎。
只是,看看吴历诗里的基督信仰,这样的指责就无立足之地了:“我本性即与天道接近,吟完新诗总能专心致志。
死之前,谁相信天国的喜乐;死后,方才憬悟地狱之火是真。
浮生功名如鹅爪留痕在雪上;这副肉身一生碌碌,如同马蹄下的尘土。
更有甚者,光阴逝去催人如斯;且谨慎渡过河中浅滩,朝向本源而去。
”传教士不惜一切要改变中国。
许多中国人敬重他们,有些中国人皈依他们。
中国的历法专家看出传教士技高一筹,甘心沿用他们的算法。
许多中国画家也把西方的透视法和明暗法学了去用,虽然那些对自己的才艺最为自信、对中国文化颇为自负者不在其列。
不过,西洋传教士所带来的宗教和文化冲击,程度和幅度还是相当有限。
吴历皈依,并没有带动起多大的入教热潮。
利玛窦是凑巧碰上中国文化特别开通,对固有思想有很深质疑的时代。
但到了1688年,中国文人心里的挣扎大部分都已化解,而且没靠一丁点儿洋教帮忙。
中国文化一直在变、一直在反省,但没有对新奇贪得无厌的追求,没有“古今”的原则之争,而且一直这样到1900年左右。
中国虽然有很庞大的出版业,但出版的东西绝少勾画得出世界全面的景象,能将外来行商、教士出身的遥远地方和中国连起来。
但在1688年后的欧洲出版业,倒是有一股中国热在1700年左右达到鼎沸,直到18世纪历久不衰。
1687年,欧洲知识界因为巴黎出版了一本新书——《孔夫子的中国哲学》,而有了进入中国儒家学说核心的门路。
《孔夫子的中国哲学》这部巨著将四书完整译成法文。
中国人认为四书记的是孔子和他的弟子的教诲,演为后世新儒家学说的核心。
书中也附了孔子的生平简介,中国3000多年的历代年表就占了100多页。
《孔夫子的中国哲学》的前言是一篇重要的宣言,说明耶稣会从利玛窦起是以怎样的角色去看待儒家的文化传统的。
前言里说四书里有几段文字,好像认为“天”是有意识的,会照顾世人,会在人心里注入道德良心。
还有一小部分的段落提到“上帝”,看来也很像在暗指“唯一的神”。
但宋朝的新儒学者写评注时,则推演出一套有机的理学观。
这一路线原本也是中国文化很早就有的一种强势传统,主张“上帝”不过是“天”的同义词;而“天”指的则是宇宙运行的秩序,自行运转,不需要超自然的神去建立秩序或作为膜拜的对象。
晚明对宋朝理学的批评给了利玛窦不少启示,因此强调这些文句闪烁着中国古代上帝认识论的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