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宫秋
《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原文及鉴赏

《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原文及鉴赏(最新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文档下载后可定制修改,请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和使用,谢谢!并且,本店铺为大家提供各种类型的经典范文,如诗歌散文、原文赏析、读书笔记、经典名著、古典文学、网络文学、经典语录、童话故事、心得体会、其他范文等等,想了解不同范文格式和写法,敬请关注!Download tips: This document is carefully compiled by this editor.I hope that after you download it, it can help you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The document can be customized and modified after downloading, please adjust and use it according to actual needs, thank you!In addition, this shop provides you with various types of classic sample essays, such as poetry and prose, original text appreciation, reading notes, classic works, classical literature, online literature, classic quotations, fairy tales, experience, other sample essays, etc.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difference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the format and writing of the sample essay!《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原文及鉴赏【导语】:【仙吕点绛唇】车碾残花,玉人月下吹箫罢;未遇宫娃,是几度添白发! 【混江龙】料必他珠帘不挂,望昭阳一步一天涯; 疑了些无风竹影,恨了些有月窗纱。
汉宫秋主要内容

汉宫秋主要内容
1. 汉宫秋的概述
汉宫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著名的节气之一,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
日为汉宫秋。
在这一天,人们通常会赏月、吃月饼、赏桂花等,这些
活动都是与汉宫秋有着密切的关联。
2. 汉宫秋的起源与历史
汉宫秋的起源可追溯到唐朝时期,当时,汉武帝坚持从京城派遣官员
前往长安和咸阳,检查和管理农业生产。
此外,他还提倡峨眉山和华
山等地的民间传统文化和艺术。
3. 汉宫秋的习俗与文化
汉宫秋节日的习俗非常丰富多彩,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赏月和吃月饼。
此外,人们还会在这一天贴桂花,体验中秋节的神秘气氛。
4. 汉宫秋的意义与诠释
汉宫秋象征着中秋节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一个重要节日,汉宫秋饱含着人们对于家庭团圆的期望和对于美好生
活的追求。
5. 汉宫秋的现代传承与发展
在现代社会中,汉宫秋的传承和发展已经逐渐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人们通过各种形式来庆祝和纪念这一节日,以此传承和继承汉宫秋的
文化传统和精神价值。
通过对汉宫秋的整体介绍,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这一传统文化
节日的内涵和意义。
汉宫秋作为中秋节的文化衍生,不仅仅是一种传
统习俗,更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在今
后的日子里,人们需要更好地传承和发扬这一文化节日,使之更好地
服务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赏析元曲:关汉卿《汉宫秋》

赏析元曲:关汉卿《汉宫秋》北宋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开篇便以“人中有丘壑,然后有词章。
若夫《典论》之类,岂足多数哉?然千古秀才,终难当《王右军》之赋;何者?其人可访。
乃关、应两人丹青逼真画面呢。
“哀号摧肝肺,万里驱曹军。
”这首《王右军之赋》,以其悲壮的氛围和磅礴的笔墨,让这首文章成为了一首不可磨灭的传世名篇。
《汉宫秋》是由元代文学家关汉卿所创作的一首琵琶曲。
此篇词章以叙述了北汉宫的秋天景色为中心,笔者在此文章中试图通过笔墨的运用,展现出中国古代文学的多样性及其内涵。
《汉宫秋》一文选取的是嫦娥奔月的传说做題材,通過對於主人公唐明皇的描寫,以及描述她思念夫君,无法入眠的画面描写,以及形容被巍巍高山以及闻名世界的长城所穿插等等。
以至于这篇曲子在历史上被赋予了“场面大、手笔大”的特点。
首先,《汉宫秋》采用了华丽的辞藻和声韵来体现整篇曲子的气氛。
比如“山原旦春晚充夜,半殿仙姬散珠簪。
“这一段词句之间所运用的平仄抑扬使得词章的节奏感大幅度加强。
再如“高木无阴,外有长城万里闻名,有你的这里都不重,可是我心中的你一点也返不起。
”在这里作者通过对于唐明皇思念夫君以及失眠这个状态的形容使得读者感到阵阵心酸。
同时,有一定声韵的使用,使得这篇曲子更具空灵的美感。
其次,《汉宫秋》在描写场景时采用了大量形象生动的描写手法。
例如,“秋月寒于故国月”一句通过对比形象来表达主人公思乡之情。
又如“夜深不吟、宫关锁”一句,通过夜深和锁门的描写,使得整个宫殿显露出荒凉的氛围。
这些描写手法不仅增添了曲子的层次感,也更好地展示了元曲的独特魅力。
最后,关汉卿在《汉宫秋》中巧妙地运用了对比和对景来表达主题。
比如通过对比夫君与长城的形象,一方面表达出主人公对夫君的思念之情,另一方面也展现了长城宏伟壮观的景色。
同时,他还通过对夜晚和白天的描写、对山原和玉楼的对称等手法来体现曲子的悬念性和层次感。
综上所述,关汉卿的《汉宫秋》是一首情感丰富、意境独特的元曲。
汉宫秋名句

汉宫秋名句汉宫秋,是指汉代宫廷的秋季景色。
秋季的汉宫,金黄的叶子覆盖了整个宫廷,红霞映照下的建筑更添一层秋意。
汉宫秋的景色,给人以宁静、深邃、悠远之感,同时也蕴含着凄美、寂寥、离愁之意。
下面是一些与汉宫秋相关的名句,用以形容汉宫秋的幽静与美丽。
1. “秋思悠悠,汉宫萧索。
” 这句诗出自杜牧的《秋思》,表达了对汉宫秋景的思念之情。
汉宫秋景荒凉萧索,让人想起往事,引发了对过去的怀念和离散之情。
2. “汉宫秋月下,寂寞断人肠。
” 杜甫的这首《月夜忆舍弟》描述了汉宫秋夜的寂寥与离愁。
在月色的照耀下,一片宁静的汉宫显得愈发空寂,让人心生感伤之情。
3.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 (纳兰性德《浣溪沙·银烛秋光冷画屏》)这句词描述了汉宫秋夜的凄美景象。
宫廷里的烛光照耀下的画屏显得冷冷清清,而纱帘轻拂下扑飞的萤火虫更增添了一层独特的幽静氛围。
4. “飒飒寒花开,碧水寒山倒影来。
” (王之涣《登鹳雀楼》)这句诗描绘了汉宫秋日的冷寂景致。
汉宫的花开寥落,碧水又映照着寒山的倒影,呈现出一幅萧瑟而美丽的画卷。
5. “荒梗残灯夜气寒,千年古殿足泪干。
” 这是白居易的《宫词》中的一句诗句。
汉宫秋夜里一片荒凉,弥漫着寒意。
千年古殿承载了太多的宫廷往事,历史的痕迹在这里显得尤为清晰,人们思绪万千,情感沉淀。
6. “秋天的汉宫,是岁月的过客。
” 这句话引用了一种旁观者的视角,描述了汉宫秋景的短暂与变幻。
秋天的汉宫象征了兴盛之后的衰退,正如同岁月的无情,过去的辉煌只是短暂的停留。
汉宫秋的景色充满了沧桑和哀愁,将人们带入了历史的长河。
汉宫作为古代帝王的居所,无论是辉煌繁华的宫殿,还是寂寥凄美的遗址,都沉淀着无数的历史和文化。
正因为汉宫秋的幽静与美丽,才引起了文人雅士的无限悲叹和缠绵情思。
马致远《汉宫秋》名词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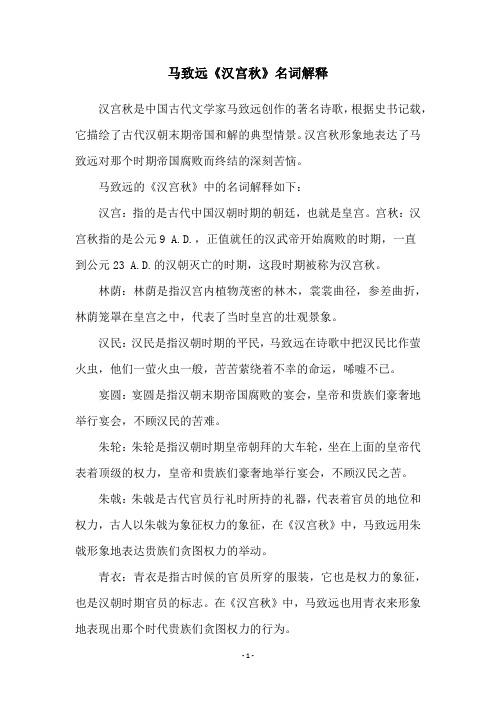
马致远《汉宫秋》名词解释汉宫秋是中国古代文学家马致远创作的著名诗歌,根据史书记载,它描绘了古代汉朝末期帝国和解的典型情景。
汉宫秋形象地表达了马致远对那个时期帝国腐败而终结的深刻苦恼。
马致远的《汉宫秋》中的名词解释如下:汉宫:指的是古代中国汉朝时期的朝廷,也就是皇宫。
宫秋:汉宫秋指的是公元9 A.D.,正值就任的汉武帝开始腐败的时期,一直到公元23 A.D.的汉朝灭亡的时期,这段时期被称为汉宫秋。
林荫:林荫是指汉宫内植物茂密的林木,裳裳曲径,参差曲折,林荫笼罩在皇宫之中,代表了当时皇宫的壮观景象。
汉民:汉民是指汉朝时期的平民,马致远在诗歌中把汉民比作萤火虫,他们一萤火虫一般,苦苦萦绕着不幸的命运,唏嘘不已。
宴圆:宴圆是指汉朝末期帝国腐败的宴会,皇帝和贵族们豪奢地举行宴会,不顾汉民的苦难。
朱轮:朱轮是指汉朝时期皇帝朝拜的大车轮,坐在上面的皇帝代表着顶级的权力,皇帝和贵族们豪奢地举行宴会,不顾汉民之苦。
朱戟:朱戟是古代官员行礼时所持的礼器,代表着官员的地位和权力,古人以朱戟为象征权力的象征,在《汉宫秋》中,马致远用朱戟形象地表达贵族们贪图权力的举动。
青衣:青衣是指古时候的官员所穿的服装,它也是权力的象征,也是汉朝时期官员的标志。
在《汉宫秋》中,马致远也用青衣来形象地表现出那个时代贵族们贪图权力的行为。
汉宫秋是古代汉朝时期最著名的一部诗歌,马致远细致而激烈地描写了当时汉朝统治者腐败暴虐的情景,以及他们深深地苦苦萦绕着不幸的命运。
他在《汉宫秋》中使用的名词也是这一背景下的写照。
朱轮、朱戟、青衣等名词不仅仅是文字,更代表了古代那个时期分层社会中贵族们腐败和权力的象征,更是古人对贪婪和邪恶的深刻批判。
“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全诗翻译赏析

“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
”全诗翻译赏析“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
”这两句隐寓着对秦汉王朝的凭吊之意——旧日的秦苑汉宫,而今在这秋天日暮时分,绿芜遍地,黄叶满林,唯有鸟儿在杂草丛生中栖息,秋蝉在树枝上鸣叫。
虫鸟不知兴亡,人有兴亡之叹,景物的描绘,表达了诗人吊古伤今的深沉感情。
出自许浑《咸阳城东楼》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
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
注“溪云”句:溪,指磻溪;阁,指慈福寺。
此句下作者自注:“南近磻溪,西对慈福寺阁。
”“鸟下”二句:夕照下,飞鸟下落至长着绿草的秦苑中,秋蝉也在挂着黄叶的汉宫中鸣叫着。
当年:一作“前朝”。
行人:过客。
泛指古往今来征人游子,也包括作者在内。
芜:杂草丛生。
苑:养禽兽植树木的处所。
这里指秦统治者打猎游乐的禁苑。
参考译文登上百尺高楼,引我万里乡愁。
芦苇杨柳丛生,好似家乡沙洲。
乌云刚刚浮起在溪水边上,夕阳已经沉落楼阁后面。
山雨即将来临,满楼风声飒飒。
秦汉宫苑,一片荒凉。
鸟儿落入乱草之中,秋蝉鸣叫枯黄夜间。
行人莫问当年繁华盛事,都城依旧,只见渭水不停东流。
赏析《咸阳城东楼》是唐代诗人许浑的作品。
此诗大约是许浑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任监察御史的时候所写。
此时大唐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政治非常腐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一个秋天的傍晚,诗人登上咸阳古城楼观赏风景,即兴写下了这首七律.此诗用云、日、风、雨层层推进,又以绿芜、黄叶来渲染,勾勒出一个萧条凄凉的意境,借秦苑、汉宫的荒废,抒发了对家国衰败的无限感慨。
全诗情景交融,景中寓情,诗人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赋予抽象的感情以形体,在呈现自然之景的同时又体现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
景别致而凄美,情愁苦而悲怆,意蕴藉而苍凉,境雄阔而高远,神完气足,为唐人登临诗篇之佳作。
此诗首联扣题,抒情写景。
“蒹葭”,暗用《诗经·国风·秦风·蒹葭》的诗意,表思念心绪。
汉宫秋译文及赏析

汉宫秋译文及赏析《汉宫秋》译文及赏析秋色渐浓,古老的汉宫流转着一片沉静与寂寥。
在这个世界的转瞬之间,人们不禁想起过往的辉煌与荣耀。
下面为大家带来《汉宫秋》的译文及赏析,让我们一起领略这首诗的内涵与魅力。
秋色浓,汉宫寂寂。
古老的汉宫,注定了沉静而寂寥的命运。
秋意渐浓,让这座宫殿更显凄美。
夜半歌声起,楚河汉界虚。
在深夜里,歌声悠扬起来,汉宫中回荡着美妙的曲调。
楚河与汉界,虚幻而遥远,仿佛将这首歌带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乱云飞渡仍从容,水云间不胜嗟。
乌云飞渡的场景展现了澎湃而奔腾的气势。
而汉宫之上,云雾弥漫,仿佛为这殿宇增添了一丝神秘与无尽的遐思。
双双翠影任斜阳,风雨雷霆无法阻。
殿宇中的树影斜射进来,犹如抚慰了这座古老宫殿的心灵。
无论是风雨雷霆,都不能阻挡它的存在与闪耀。
铁马冰河铺寒尽,金人玉树诉往昔。
冰冷的铁马穿越了漫长岁月的洗礼,寒冷之感逐渐消散。
金人与玉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诉说着昔日的辉煌与兴盛。
沧海月明珠有泪,长安花落音如泣。
千变万化的沧海也不能改变它的月光之美,柔美的泪水滑落在海面上,仿佛长安的花朵也随着阳光的消逝而凋谢,发出悲恸的哭泣声。
空山百鸟散还合,万径人踪绝复连。
空山中的百鸟飞散,又再次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新的群体。
曾经稀稀拉拉的小径上再次出现了繁忙的人踪,仿佛时间从未停滞,一切继续着。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
谁会想到,西风虽然阴凉,却也带来了美丽与凄凉的感触。
黄叶依然纷纷落下,轻敲着疏窗,为寂寞与孤独增添了些许凄美。
相思枫叶丹,思念似火焚。
飘落的枫叶如同火焰般的红,让人有种无法言喻的思念之情,仿佛内心被燃烧着,难以平息。
几回魂梦与君谈,明月皎如旧。
几次魂梦中与心上人相聚,共度幽会。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仿佛昔日的美好时光重现眼前。
汉宫秋,凄凉寂静。
在这个秋季的汉宫里,寒意袭人,一片寂静与孤寂。
岁月的洗礼,将这里的荣耀与辉煌抹去,让人们不禁沉思回忆。
以上即为《汉宫秋》的译文及赏析。
此诗以凄美的笔触,描绘了古老宫殿的辉煌与凋谢,表达了对兴盛时光的思念与感慨。
元杂剧《汉宫秋》赏析

元杂剧《汉宫秋》赏析
《汉宫秋》是元代马致远创作的一部历史剧,是元朝四大悲剧之一。
全名《破幽梦孤雁汉宫秋》。
全剧四折一楔子,取王昭君出塞的故事,非正史。
主要内容写的是西汉元帝受匈奴威胁,被迫送爱妃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
事实上,正史上王昭君出塞不是受匈奴威胁,当时汉强匈奴弱。
史书记载昭君出塞最早见于《汉书·元帝纪》和《匈奴传》,大致情节是:西汉竟宁元年,元帝以宫人王嫱赐呼韩耶单于为阏氏;昭君入匈奴,生二子;呼韩耶死,从成帝敕令,复为后单于阏氏。
而《汉宫秋》将其戏剧化处理,表达出的意味便截然不同。
元曲 汉宫秋原文及译文

元曲汉宫秋原文及译文
一、原文
汉宫秋
作者:马致远
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空馀床。
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
也还记得当日音容相貌,
怎禁得银灯半掩黄昏晓。
愁来正欲和衣睡,一思想起泪沾襟。
数拍阑干,凭阑万绪,听画檐铁马声敲。
故园三径吐幽兰,十二钗鸾独掩妆。
几回廊,几回小院想。
雨过也梨花欲谢恐春寒。
二、译文
美人还在的时候,满堂都飘着花香;美人一离开之后,就只剩下空空的床了。
结满了蛛丝的梁上,绿色的纱窗现在又糊上了。
还记得美人的音容笑貌,禁不住银灯半掩,在夜半黄昏的景象中思念起她来而泪满衣襟。
听到画檐铁马声敲,引起我万种愁绪。
故园三径吐幽兰,十二钗鸾独掩妆。
几回在回廊、小院漫步思考。
雨过也梨花落了,因为春寒恐怕它凋谢了。
汉宫秋讲的是什么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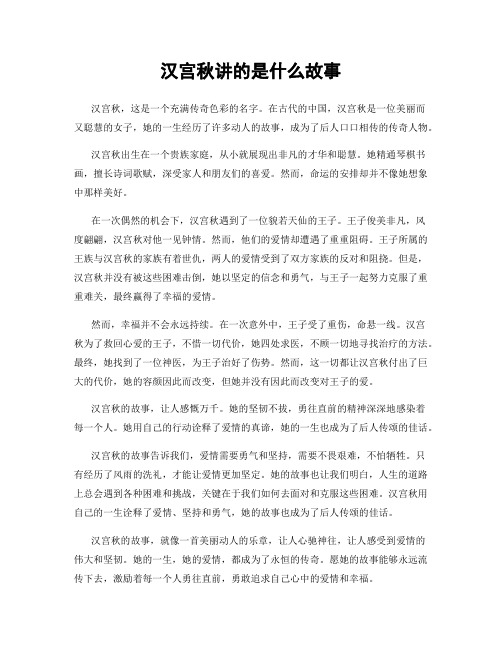
汉宫秋讲的是什么故事汉宫秋,这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名字。
在古代的中国,汉宫秋是一位美丽而又聪慧的女子,她的一生经历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成为了后人口口相传的传奇人物。
汉宫秋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才华和聪慧。
她精通琴棋书画,擅长诗词歌赋,深受家人和朋友们的喜爱。
然而,命运的安排却并不像她想象中那样美好。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汉宫秋遇到了一位貌若天仙的王子。
王子俊美非凡,风度翩翩,汉宫秋对他一见钟情。
然而,他们的爱情却遭遇了重重阻碍。
王子所属的王族与汉宫秋的家族有着世仇,两人的爱情受到了双方家族的反对和阻挠。
但是,汉宫秋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击倒,她以坚定的信念和勇气,与王子一起努力克服了重重难关,最终赢得了幸福的爱情。
然而,幸福并不会永远持续。
在一次意外中,王子受了重伤,命悬一线。
汉宫秋为了救回心爱的王子,不惜一切代价,她四处求医,不顾一切地寻找治疗的方法。
最终,她找到了一位神医,为王子治好了伤势。
然而,这一切都让汉宫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她的容颜因此而改变,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对王子的爱。
汉宫秋的故事,让人感慨万千。
她的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人。
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爱情的真谛,她的一生也成为了后人传颂的佳话。
汉宫秋的故事告诉我们,爱情需要勇气和坚持,需要不畏艰难,不怕牺牲。
只有经历了风雨的洗礼,才能让爱情更加坚定。
她的故事也让我们明白,人生的道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面对和克服这些困难。
汉宫秋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爱情、坚持和勇气,她的故事也成为了后人传颂的佳话。
汉宫秋的故事,就像一首美丽动人的乐章,让人心驰神往,让人感受到爱情的伟大和坚韧。
她的一生,她的爱情,都成为了永恒的传奇。
愿她的故事能够永远流传下去,激励着每一个人勇往直前,勇敢追求自己心中的爱情和幸福。
关于汉宫秋的23个诗句

关于汉宫秋的23个诗句1.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
——许浑《咸阳城东楼》2.山色遥连秦树晚,砧声近报汉宫秋。
——韩翃《同题仙游观》3.春陌露草悲铜驼,汉宫秋吹惊纨罗。
——李新《感歌行》4.微雨点月汉宫秋,水殿疏萤黑处流。
——宋白《宫词·微雨点月汉宫秋》5.诗人新谱"汉宫秋",马上琵琶泪不流。
——老舍《内蒙即景·六》6.独存汉宫秋,西风乱葱翠。
——魏学洢《重过蒋氏莲雪居用昌谷韵》7.汉宫秋湛仙人掌,沆瀣文园好自攀。
——王世贞《寄吴舍人明卿》8.扇恩已尽汉宫秋,空忆金鞍远玉楼。
——吴惟信《次王汉和见寄韵》9.惟馀天上月,还似汉宫秋。
——郑珞《明妃怨》10.金母云軿宴紫楼,露寒仙掌汉宫秋。
——周密《小游仙七首其一》11.木落汉宫秋,寒虫苦悲咽。
——程诰《过未央宫遗址》12.春明一杯酒,老尽汉宫秋。
——黄辉《别汝钝二首·暂住依黄菊》13.歌残鸿鹄汉宫秋,四老曾随鹤驾游。
——黄佐《咏四皓》14.玉辇已随边地草,青山依旧汉宫秋。
——张宁《感事二首·其二》15.月沈湘浦冷,花谢汉宫秋。
——石文德《句》16.独有穹庐深夜月,清光不异汉宫秋。
——王筠《明妃怨》17.向前儿女恨,肠断汉宫秋。
——陈敬翁《月下琵琶》18.黄发锦衣篱畔立,汉宫秋色在山家。
——方鹤斋《老少年》19.多君开手抚玉轸,凄清弹出《汉宫秋》。
——吕师濂《听蓼庵处士弹汉宫秋》20.钟磬半沉萧寺月,烟霞深锁汉宫秋。
——李云龙《行经罗浮》21.西风摇落汉宫秋,玉署凉生景转幽。
——李学一《翰直闻蝉》22.两岸新蝉啼不住,隔林遥送汉宫秋。
——李廷机《雨霁闻蝉》23.山半惟存神宇旧,汾阴不似汉宫秋。
——孙珫《谒禹宫》。
汉宫秋原文及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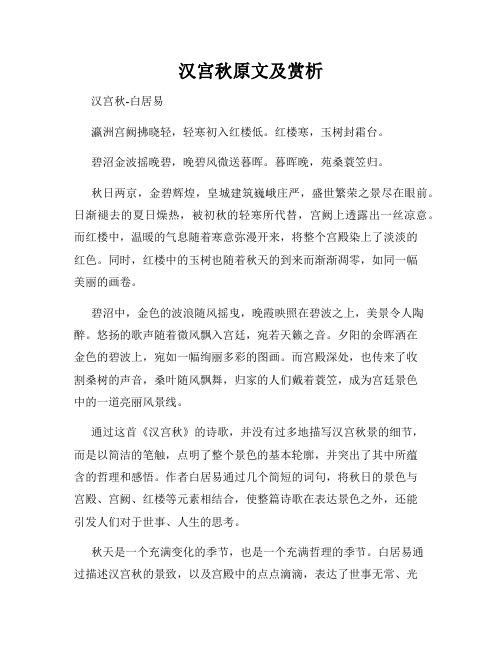
汉宫秋原文及赏析汉宫秋-白居易瀛洲宫阙拂晓轻,轻寒初入红楼低。
红楼寒,玉树封霜台。
碧沼金波摇晚碧,晚碧风微送暮晖。
暮晖晚,苑桑蓑笠归。
秋日两京,金碧辉煌,皇城建筑巍峨庄严,盛世繁荣之景尽在眼前。
日渐褪去的夏日燥热,被初秋的轻寒所代替,宫阙上透露出一丝凉意。
而红楼中,温暖的气息随着寒意弥漫开来,将整个宫殿染上了淡淡的红色。
同时,红楼中的玉树也随着秋天的到来而渐渐凋零,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
碧沼中,金色的波浪随风摇曳,晚霞映照在碧波之上,美景令人陶醉。
悠扬的歌声随着微风飘入宫廷,宛若天籁之音。
夕阳的余晖洒在金色的碧波上,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图画。
而宫殿深处,也传来了收割桑树的声音,桑叶随风飘舞,归家的人们戴着蓑笠,成为宫廷景色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通过这首《汉宫秋》的诗歌,并没有过多地描写汉宫秋景的细节,而是以简洁的笔触,点明了整个景色的基本轮廓,并突出了其中所蕴含的哲理和感悟。
作者白居易通过几个简短的词句,将秋日的景色与宫殿、宫阙、红楼等元素相结合,使整篇诗歌在表达景色之外,还能引发人们对于世事、人生的思考。
秋天是一个充满变化的季节,也是一个充满哲理的季节。
白居易通过描述汉宫秋的景致,以及宫殿中的点点滴滴,表达了世事无常、光阴荏苒的哲理。
无论是宫阙拂晓轻,寒意渐渐浸润红楼,还是细腻描绘的碧波金波和苑桑蓑笠归的场景,都传达出了时光流转、万物皆生的生命之美。
同时,这首诗描绘了宫殿中的繁荣景象,一片金碧辉煌。
这种盛世繁荣的景象,也隐喻了诗人对于时局的观察。
白居易所处的时代,正是唐朝盛世的黄金时期,政治稳定、社会繁荣。
通过描绘瀛洲宫阙、红楼这些华丽壮观的建筑,诗人向读者展现了盛世之景,寄托出对黄金时代的向往和眷恋之情。
总的来说,这首《汉宫秋》描绘了一个充满美丽景色和哲理的汉宫秋景。
诗人以简洁的语言,将景色、人物和时局相结合,一幅美丽的图景在读者面前展开。
不仅仅是描绘了秋日的美丽,更是折射出社会的繁荣和生命的哲理,给人以启迪和思考。
《汉宫秋》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汉宫秋》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最新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文档下载后可定制修改,请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和使用,谢谢!并且,本店铺为大家提供各种类型的经典范文,如诗歌散文、原文赏析、读书笔记、经典名著、古典文学、网络文学、经典语录、童话故事、心得体会、其他范文等等,想了解不同范文格式和写法,敬请关注!Download tips: This document is carefully compiled by this editor.I hope that after you download it, it can help you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The document can be customized and modified after downloading, please adjust and use it according to actual needs, thank you!In addition, this shop provides you with various types of classic sample essays, such as poetry and prose, original text appreciation, reading notes, classic works, classical literature, online literature, classic quotations, fairy tales, experience, other sample essays, etc.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difference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the format and writing of the sample essay!《汉宫秋》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导语】:《汉宫秋》是马致远的代表作。
马致远《汉宫秋》主要内容赏析

马致远《汉宫秋》主要内容赏析(最新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文档下载后可定制修改,请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和使用,谢谢!并且,本店铺为大家提供各种类型的经典范文,如诗歌散文、原文赏析、读书笔记、经典名著、古典文学、网络文学、经典语录、童话故事、心得体会、其他范文等等,想了解不同范文格式和写法,敬请关注!Download tips: This document is carefully compiled by this editor.I hope that after you download it, it can help you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The document can be customized and modified after downloading, please adjust and use it according to actual needs, thank you!In addition, this shop provides you with various types of classic sample essays, such as poetry and prose, original text appreciation, reading notes, classic works, classical literature, online literature, classic quotations, fairy tales, experience, other sample essays, etc.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difference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the format and writing of the sample essay!马致远《汉宫秋》主要内容赏析【导语】:《汉宫秋》全名《破幽梦孤雁汉宫秋》。
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全诗翻译赏析及作者出处

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
全诗翻译赏析及
作者出处
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
这句话是什幺意思?出自哪首诗?作者是谁?下面小编为同学们整理出这首古诗词的全文全文翻译及全文赏析,提供给同学们。
希望能对同学的古诗词的学习与提高有所帮助。
1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
出自唐代许浑的《咸阳城东楼/咸阳城西楼晚眺/西门》
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沉通:沈)
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
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
1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赏析人首联扣题,抒情写景:“高楼”,指咸阳城西楼,咸阳旧城在西安市西北,汉时称长安,秦汉两朝在此建都。
隋朝时向东南移二十城建新城,即唐京师长安。
咸阳旧城隔渭水与长安相望;“蒹葭”,即芦荻(蒹,荻;葭,芦),暗用《诗经·国风·秦风·蒹葭》的诗意,表思念心绪;“汀洲”,水边之地为汀、水中之地为洲,这里指代诗人在江南
的故乡。
诗人一登上咸阳高高的城楼,向南望去,远处烟笼蒹葭,雾罩杨柳,很像长江中的汀洲。
诗人游宦长安,远离家乡,一旦登临,思乡之情涌上心头。
蒹葭杨柳,居然略类江南。
万里之愁,正以乡思为始:“一上”表明触发
诗人情感时间之短瞬,“万里”则极言愁思空间之迢遥广大,一个“愁”字,奠定了全诗的基调。
笔触低沉,景致凄迷,触景生情,苍凉伤感的情怀落笔即出,意远而势雄。
《汉宫秋》诗文解析

《汉宫秋》诗文解析汉宫秋,历史长河中的黄金时代,一个极富诗意的时刻。
这首诗《汉宫秋》以华丽的词藻和独特的意境,描绘了富丽堂皇的汉宫秋景,表达了作者对美好时光的向往和追忆。
通过深入解析诗中的意象、用词和结构,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这首诗。
诗的开头,“天而高,山而遥”描绘了壮丽的天空和遥远的群山。
这种辽阔和高远的感觉犹如触摸到了苍穹之上的星辰,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
接着,诗人运用对比手法,“露气斜,诗兴要饶炉火炕姑酌酒途中嘲”,将天空与地面的景色相互映照,以展现出温暖和诗意交织的景象。
诗的下一节,作者以优美的描写,将我们带入了汉宫的神秘内部。
“明月白鹤门”,映衬出明亮如镜的月光和翩跹起舞的白鹤,以及宏伟的门楼。
这种写景手法使我们仿佛亲身置身于汉宫壮丽的景致之中。
而“宝浴夜桃红”则展现了盛世繁华的景象,用丰盈的桃花来形容皇宫的辉煌和美丽。
接下来的诗句中,作者用纤细的笔触勾勒出了汉宫内宫女们的婀娜妆容。
“罗新纱舞来”,以娇美的纱舞来描绘宫女的轻盈舞姿,这种优雅和娴静的描写方式使我们能够感受到古代宫廷女子的独特魅力。
随后,诗人又刻画了明媚的红颜与秋水相映,“倚栏语销,低纱歌送”,给人一种浓郁的诗意和情感。
在诗的结尾部分,“关山玉漏远”,借景写人,以远处的关山和悠远的玉漏来暗示岁月的流逝和光阴的逝去。
这种对时光流转的描绘,增添了诗的深邃和哲理。
最后一句“且乐今宵花月下,共留明朝醉翰墨”,表达了作者对当下美好时光的珍惜和希望能与爱人共享此刻。
通过对《汉宫秋》这首诗的解析,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运用了丰富的意象和描写技巧,使诗中的景色更加生动鲜明。
从描绘天空、山川到描写宫廷、宫女,再到写情写意,每一个环节都构成了一幅画卷,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考空间。
这首诗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法,将我们带入唐代的汉宫,感受其中的优雅与华丽。
正是因为《汉宫秋》这首诗的高度诗意和艺术性,它一直以来都被誉为唐代诗歌的经典之作。
阅读这首诗,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古代宫廷文化的瑰丽,也能够思考人生的短暂和岁月的流转。
汉宫秋赏析

汉宫秋赏析
《汉宫秋》主要描写了汉元帝对王昭君的爱情,同时,又写出了王昭君对祖国的感情,并把这两方面的描写交织在一起。
表达了作者对封建统治者昏庸、腐败、无能、荒淫、自大的揭露,也表达了对伟大爱国者王昭君的赞美。
《汉宫秋》用历史故事作了形象的比喻,把一个宫廷乃至一个国家比作一艘船,把皇帝比作船长,把朝中大臣比作船员,把辅国机构比作船舵,把国家比作一艘船,通过这样的比喻,生动地表现了封建社会中皇权和妃权之间的矛盾,表现了作者对于皇权的否定。
马致远的《汉宫秋》以《汉书·元帝纪》中的记载为基本情节,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环境的渲染方面,采用了漫画式的笔法,往往通过寥寥数语,用夸张的修辞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勾勒出活灵活现的戏剧性效果。
在戏剧冲突方面,《汉宫秋》主要围绕汉元帝、王昭君和文武官僚展开,以汉元帝和王昭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塑造了一组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构造了一系列矛盾冲突。
在语言特色方面,马致远的《汉宫秋》主要采用清丽峭拔的词风,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时代特征。
同时,剧本的主旨也通过优美的文词和动人的曲辞传达出来,表现了作者在戏剧创作中高超的艺术修养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总的来说,马致远的《汉宫秋》是一部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的戏剧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国戏曲史上的经典之作。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摘要:《汉宫秋》是以汉元帝为爱情主人公的末本戏。
君王以爱情主人公的面目出现,突破了传统封建道德观念中君王以刑政教化为重的那个严肃、无情形象的禁锢。
同时,渴望安定和平、幸福生活的生存意识的彰显以及戏剧中“情”的诗化处理方式都增添了《汉宫秋》的魅力。
关键词:《汉宫秋》汉元帝生存意识诗化方式《汉宫秋》是“元曲四大家”之一马致远的代表作。
明人臧晋叔把它列在《元曲选》之首,清人焦循《剧说》更推崇其为“绝调”。
《汉宫秋》是一个末本戏,以汉元帝为主唱,他是一个从被蒙蔽到发现真相,处于难堪境地后更加凄怆孤独的人物。
但是,他的妥协决不仅仅是因为他软弱个性等个人因素,使元帝陷入困境的也不仅仅是番王。
实际上,作者的创作意图从未把批判的矛头鲜明地指向胡、汉中的哪一家,而是将《汉宫秋》作为命运人生观的一种文学图式,着意表现了一种困境,一种不可逆转的沮势,与一种兴衰不定、生死无常的幻灭感。
在传统的阅读中存在两大误区:一是过分强调王昭君形象的历史内涵;二是走进了民族矛盾的犄角,从而使对作家、作品的研究陷入了矛盾、尴尬的境地。
笔者以为《汉宫秋》艺术魅力不仅在于它本身所能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意蕴阐释,还在于作者对帝王形象的人性解读以及生存意识的觉醒上。
另外,作者对戏剧“情”的诗化处理方式也增添了《汉宫秋》的魅力。
一、帝王形象的解禁汉元帝,这位自诩“嗣传十叶继炎刘,独掌乾坤四百州”的堂堂汉室之胄,自以为外有安邦之武将,内有定国之文臣,四境太平,天下无忧,又有昭君这样的佳人相伴,该是何等的舒心惬意!可一旦呼韩邪单于来犯,满朝文武都成了“忘恩咬主贼禽兽”,“满朝中都作了毛延寿”,这才深切地感到原来自己“空掌着文武三千万,中原四百州”,帝王的荣光威严和不可一世之尊在刹那间崩塌下来。
当他仅想做个怜香惜玉的情种,仅想和昭君做对小家子平民夫妻也不能时,这种原有的尊贵无比、美满无边的帝王感觉就破灭得更彻底,由此带来的惶恐、悲伤、凄怆就更强烈。
正像原本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突然变得阴郁愁苦、忧心忡忡。
汉元帝也有相似的悲剧领悟。
当其独恋椒房旧纱窗,幻听到孤雁哀鸣,“丧失”的感觉就更深入骨髓了。
这种“丧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指失其所爱;另一方面则是原来自足平衡的心理世界的丧失。
作为帝王都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无法抗拒命运对人的播弄,无可奈何的他意识到了为人的悲哀,领悟到了尊贵繁华的帝王事业的虚假。
帝王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历来被看作是儒家思想最有力的贯彻者和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强调“三纲五常”,强调以理统情。
而在《汉宫秋》中,作者大胆地突破了世俗观念中对帝王的敬畏心理,不仅把帝王搬上戏剧的舞台,而且还把他塑造成一个柔情无限的爱情主人公形象。
张燕瑾先生说:“在剧作家的艺术构思中,刻画昭君却是为塑造汉元帝形象服务的。
人们有时错把昭君当成戏的主人公,那是用感情倾向代替了对作品的实际分析。
”[1]此言切中肯綮。
一则元曲“四大套”的独特体制,只能有一个主角一唱到底。
基于这一点,作为《汉宫秋》主唱的汉元帝也就成了帝、妃爱情的中心人物,而王昭君则是爱情的呼应者。
二则从旦角和末角所占的戏份来看,马致远对王昭君正面描写极少,而汉元帝的戏差不多占到了全戏的三分之二。
实则昭君跳黑水的殉情、两民族交好作为双方冲突的最后结束,着墨并不多,前两折刻画她的形象时,也多是作为表现汉元帝对她痴情的背景来写,主角仍是汉元帝。
三则从人物形象刻画的精细程度上看,作者在剧中并没有深入挖掘昭君的内心世界,而昭君被迫和番后汉元帝的愁肠百结、睹物思人的心理活动则是主要刻画之处。
综合以上三点可知,汉元帝是爱情的主人公并且是马致远重点描写的对象。
汉元帝作为全戏的主角,他非维护封建制度的“伪君子”,而是一位对情有着诚挚追求的人。
把《汉宫秋》看作是具有绝对寓托的作品,认为帝、妃之间的爱情只不过是表达作品寓意载体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别林斯基曾说:“悲剧作家想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表现他笔下的主人公:历史赋予他历史环境,如果这一环境的历史人物不符合悲剧作家的标准,他就有充分的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思改变这个人物。
”[2]《汉宫秋》是文学作品,非是对历史的复原,作者只是借古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表达他的思想愿望和审美趣味。
另外,帝、妃作为人,同样有着对爱情的渴求。
《礼记·礼运》:“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3]明人张琦在《衡曲尘谭·情痴寤言》中进一步阐释情爱:“人,情种也;人而无情,不至于人矣,曷望其至人乎?情之为物也,役耳目,易神理……生可以生,死可以死,死可以生,生可以死,死又可以不死,生有可以望生,远远近近,悠悠漾漾,杳弗知其所之。
”[4]剧中的汉元帝善良多情,他惊艳于昭君姿色,沉溺爱河而难以自拔。
在他眼中,昭君“诸余可爱,所事儿相投……体态是二十年挑剔就的温柔,姻缘是五百载该拨下的配偶,脸儿有一千般说不尽的风流。
”(第二折,[梁州第七])第二折中汉元帝的表现俨然为普通人中一痴情男子。
即使如此,帝、妃恋还没有达到炽烈的程度,三折、四折随着对汉元帝内心活动的逐步展现,戏剧才真正地表现了帝、妃之间纯真、热烈的爱情。
第三折为表达汉元帝对昭君生离死别、情意缠绵的复杂情感,作者集中运用了[新水令]、[驻马听]等十只曲子,层层推进的情感抒发把戏剧推向了高潮。
第四折又尽是元帝在秋夜雁声中对王昭君的思念。
那一句句撕心裂肺表达相思之痛的唱词和说白更加突出了汉元帝“情种”的形象。
可以说,这里的汉元帝可与古今文学作品中任何一个痴情男女相媲美。
帝王以爱情主人公的面目出现并表现的如此深挚多情,《汉宫秋》突破了传统封建道德观念中君王以刑政教化为重的那个严肃、无情形象的禁锢。
、二、和亲背后的人性关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是蒙古贵族特权统治赖以维持的基石。
早在忽必烈统治后期就把全国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等,南人即原南宋统治区域的汉人。
元朝法律规定:“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
”“如有违犯之人,严行断罪”(《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四·斗殴》),“诸蒙古人居官犯法,论罪既定,必则蒙古官断之,行杖亦如之。
”(《元史》卷一〇二《刑法志一·职制》)。
类似带有民族歧视性质的法律不胜枚举。
汉族人民无论在法律、赋役、选举、任官等方面都受到不平等的对待。
但仔细欣赏《汉宫秋》我们就会发现,民族矛盾在其中不过是一个淡淡的折光而已。
马致远在剧中只是把它作为故事的背景来写,并且在剧的结尾也调和了这个矛盾。
实际上,从剧中所反映的汉、匈两民族对待战争的态度中也可看出他们要求民族和平相处的意愿。
且看匈奴主的想法。
他在楔子中自道:“今众部落立我为呼韩邪单于,实是汉朝外甥……昨曾遣使进贡,欲请公主,未知汉帝肯寻盟约否?”第二折开场说白中也说:“想汉家宫中,无边宫女,就与俺一个,打甚不紧?直将使臣赶回。
我欲待起兵南侵,又恐失了数年和好;且看事势如何,别做道理。
”第四折昭君死前又言:“昭君封为宁胡阏氏,坐我正宫。
两国息兵,多少是好。
”“我想来,人也是死了,枉与汉朝结下这般仇隙,都是毛延寿那厮搬弄出来的。
把都儿,将毛延寿拿下,解送汉朝处置。
我依旧与汉朝结合,永为甥舅,却不是好?”([收江南])从匈奴主呼韩邪单于的说白可知,匈奴始终是希望和汉朝永远息兵交好的,即使在王昭君死后也未改其初衷。
汉朝在昭君事件后也同样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
民众饱受了战争状态下妻离子散、亲人惨遭杀戮的痛苦,帝、妃爱情只不过是民族矛盾下无数个爱情悲剧的缩影。
爱情是人生存的最基本的感情,权力至高无上的皇帝爱情得不到满足,甚至遭到外力扼杀的人生遭际更能隐喻民族矛盾下芸芸众生的生存困境和悲哀。
显然,马致远写这个剧的目的,并不是要恢复历史上昭君和亲的目的,而是要通过帝妃爱情悲剧婉转表达更容易遭到战乱之苦的普通民众对安定和平、幸福生活的深情呼唤。
这是一种超越了民族偏见、超越了民族对立的一种伟大的反映民众普遍生存需求的意识。
三、“情”的诗化处理《汉宫秋》以其诗一般的语言赢得了古今观众的喜爱,并且被冠以“诗剧”的荣誉称号。
它的“诗剧”特征不仅表现在语言的凝练性以及富有节奏和韵律上,还表现在“情”的处理方式上。
首先,戏剧的命名具有诗意和高度概括性。
《汉宫秋》全名《破幽梦孤雁汉宫秋》,这一题目给人以诗意的想象。
“幽梦”多表现相思之情。
相对于大雁生活的群体性,“孤雁”蕴涵的是对伴侣的渴望,以“孤雁”称人,渲染了一种孤苦哀婉的情调。
“幽梦”与“孤雁”合用,象征性地表达了爱情的失意,而“秋”却进一步奠定了其悲的基调。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柳永《雨霖铃》),秋有凄凉、肃杀的象征意味。
“汉宫”则是对爱情主人公身份的暗示。
《破幽梦孤雁汉宫秋》以其八个字就凝练地概括了汉元帝和王昭君之间的悲剧爱情,表达了爱情得不到满足的酸楚和凄凉。
其次,重抒情而轻叙事的诗性特征。
《汉宫秋》中有王昭君与毛延寿之间、汉元帝与满朝文武的臣子之间、匈奴与汉朝之间等各个方面错杂的矛盾冲突。
然而作者把这些冲突压在两折内叙述,如王昭君与毛延寿、元帝与毛延寿的矛盾冲突都用一两句道白一带而过,毛的索贿、点破美人图等也都在暗场上处理等,但却用长达两折的篇幅让汉元帝抒发他失去昭君的痛苦心情。
由此可见,前两折的的各个矛盾冲突并不是作者要表现的重点,它们只是作为汉元帝与王昭君爱情悲剧的背景出现的。
张先生认为:“注重抒发有代表性的情绪,却不专力于对人物形象进行个性化的描绘,这就决定了马致远的剧作重在抒情,而不重视戏的矛盾冲突和故事情节……他是把冲突和情节的安排处理,为戏剧主人公的抒情服务,甚至情节结构有所疏漏亦所不顾。
”[5]这与诗歌重抒情而轻叙事的特点相暗合。
再次,在表达元帝对昭君的思念之情上,作者借用了虚实结合、意象、意境等多种诗歌创作手法。
如第三折写灞桥伤别,是全剧的高潮,其中[梅花酒]与[收江南]二曲把情和景、实感与幻觉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把元帝生离死别的感情写的淋漓尽致。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称其:“真所谓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者。
”[6]情、景、事交融,为历代评论家所赞赏。
第四折借孤雁悲鸣写形神凄怆的汉元帝对昭君的思念。
昭君去后元帝空对着美人图孤寂难眠,孤雁的凄厉哀鸣更增添了元帝痛苦的离情,并引发了元帝无限哀怨的心灵独白。
惨淡凄凉的相思之痛呼之欲出,凄厉之景如在目前,情景相称,充满着浓烈的诗意。
王国维曾说:“元剧之最佳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
”[7]《汉宫秋》成功的意境营造,是它在元杂剧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昭君和番事件的诗话处理是《汉宫秋》成为“诗剧”的必要准备。
昭君在民族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情愿和番以息刀兵,其中道出自己的真心:“但妾与陛下闱房之情,怎生抛舍也!”(第二折,[哭皇天])、“妾身这一去,虽为国家大计,怎奈舍不得陛下!”(第二折,[二煞]),其中充盈的是昭君对元帝浓重的依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