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何转换职业生涯访美国前国务卿赖斯
美国总统布什正式提名赖斯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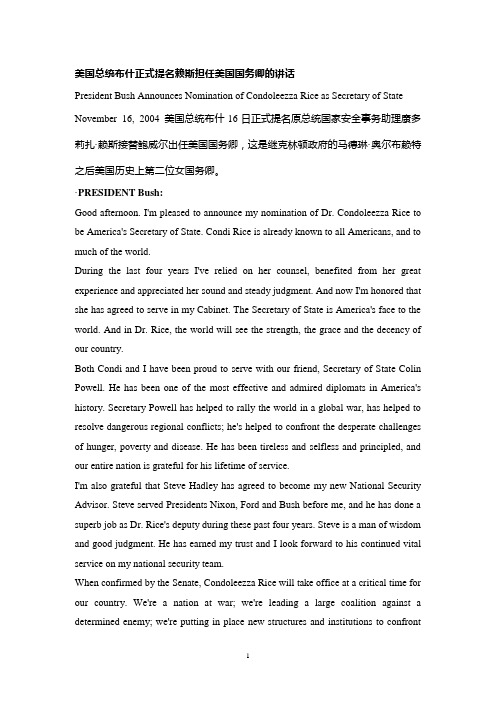
美国总统布什正式提名赖斯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讲话President Bush Announces Nomination of Condoleezza Rice as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16, 2004 美国总统布什16日正式提名原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国务卿,这是继克林顿政府的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之后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国务卿。
·PRESIDENT Bush:Good afternoon. I'm pleased to announce my nomination of Dr. Condoleezza Rice to be America's Secretary of State. Condi Rice is already known to all Americans, and to much of the world.During the last four years I've relied on her counsel, benefited from her great experience and appreciated her sound and steady judgment. And now I'm honored that she has agreed to serve in my Cabinet. The Secretary of State is America's face to the world. And in Dr. Rice, the world will see the strength, the grace and the decency of our country.Both Condi and I have been proud to serve with our friend, Secretary of State Colin Powell. He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and admired diplomats in America's history. Secretary Powell has helped to rally the world in a global war, has helped to resolve dangerous regional conflicts; he's helped to confront the desperate challenges of hunger, poverty and disease. He has been tireless and selfless and principled, and our entire nation is grateful for his lifetime of service.I'm also grateful that Steve Hadley has agreed to become my new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Steve served Presidents Nixon, Ford and Bush before me, and he has done a superb job as Dr. Rice's deputy during these past four years. Steve is a man of wisdom and good judgment. He has earned my trust and I look forward to his continued vital service on my national security team.When confirmed by the Senate, Condoleezza Rice will take office at a critical time for our country. We're a nation at war; we're leading a large coalition against a determined enemy; we're putting in place new structures and institutions to confront outlaw regimes, to oppose proliferation of dangerous weapons and materials, and to break up terror networks.The United States has undertaken a great calling of history to aid the forces of reform and freedom in the broader Middle East so that that region can grow in hope, instead of growing in anger. We're pursuing a positive direction to resolve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an approach that honors the peaceful aspirations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through a democratic state, and an approach that will ensure the security of our good friend, Israel.Meeting all of these objectives will require wise and skillful leadership at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Condi Rice is the right person for that challenge. She's a recognized expert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 distinguished teacher and academic leader, and a public servant with years of White House experience. She displays a commitment to excellence in every aspect of her life, from shaping our strategy in the war on terror, to coordinating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cross the government, to performing classical music on stage. Above all, Dr. Rice has a deep, abiding belief in the value and power of liberty, because she has seen freedom denied and freedom reborn.As a girl in the segregated South, Dr. Rice saw the promise of America violated by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by the violence that comes from hate. But she was taught by her mother, Angelina, and her father, the Reverend John Rice, that human dignity is the gift of God, and that the ideals of America would overcome oppression. That early wisdom has guided her through life, and that truth has guided our nation to a better day.I know that the Reverend and Mrs. Rice would be filled with pride to see the daughter they raised in Birmingham, Alabama, chosen for the office first held by Thomas Jefferson. Something tells me, however, they would not be surprised. (Laughter.)As many of you know, Condi's true ambition is beyond my power to grant. (Laughter.) She would really like to be the commissioner of the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I'm glad she's put those plans on hold once again. The nation needs her. I urge the Senate to promptly confirm Condoleezza Rice as America's 66th Secretary of State. Congratulations. (Applause.)DR. RICE:Thank you. Thank you, Mr. President. It has been an honor and a privilege to work for you these past four years, in times of crisis, decision and opportunity for our nation. Under your leadership, America is fighting and winning the war on terror. You have marshaled great coalitions that have liberated millions from tyranny, coalitions that are now helping the Iraqi and Afghan people build democracies in the heart of the Muslim world. And you have worked to widen the circle of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in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I look forward,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Senate, to pursuing your hopeful and ambitious agenda as Secretary of State. Mr. President, it is an honor to be asked to serve your administration and my country once again.And it is humbling to imagine succeeding my dear friend and mentor, Colin Powell. He is one of the finest public servants our nation has ever produced. Colin Powell has been a great and inspirational Secretary of State. It was my honor to serve alongside him, and he will be missed.It will, of course, be hard to leave the White House, and especially to leave behind the terrific NSC staff who have served their President and their country so ably in this most challenging of times. Yet, I can leave confident in the knowledge that they will be led by the consummate professional, a man I know and admire, my colleague and friend, Steve Hadley.Finally, let me say that in my 25 years of experience in foreign affairs, both in and out of government, I have come to know the men and women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I have the utmost admiration and respect for their skill, their professionalism and their dedication. If I am confirmed by the Senate,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the great people of the Foreign Service and the Civil Service. And one of my highest priorities as Secretary will be to ensure that they have all the tools necessary to carry American diplomacy forward in the 21st century.Mr. President, thank you again for this great opportunity, and for your continued confidence in me.鲍威尔在北京就美中关系发表讲话并回答提问PRESS BRIEFING BY SECRETARY OF STATE COLIN L. POWELLChina World HotelBeijing, ChinaOctober 25, 2004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于10月25日在北京中国大饭店(China World Hotel)举行记者会,强调了中美关系的全面性和复杂性。
美国国务卿赖斯地成长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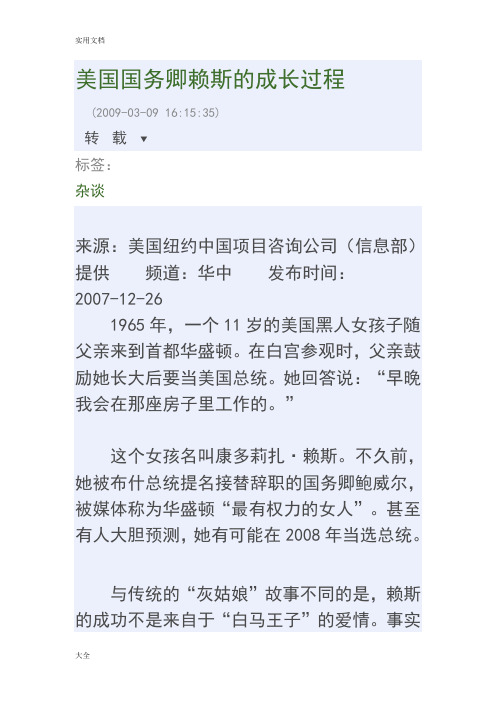
美国国务卿赖斯的成长过程(2009-03-09 16:15:35)转载▼标签:杂谈来源:美国纽约中国项目咨询公司(信息部)提供频道:华中发布时间:2007-12-261965年,一个11岁的美国黑人女孩子随父亲来到首都华盛顿。
在白宫参观时,父亲鼓励她长大后要当美国总统。
她回答说:“早晚我会在那座房子里工作的。
”这个女孩名叫康多莉扎·赖斯。
不久前,她被布什总统提名接替辞职的国务卿鲍威尔,被媒体称为华盛顿“最有权力的女人”。
甚至有人大胆预测,她有可能在2008年当选总统。
与传统的“灰姑娘”故事不同的是,赖斯的成功不是来自于“白马王子”的爱情。
事实上,她至今还是一个待字闺中的单身女人。
她的成功完全是靠她的奋斗。
在种族歧视中长大1954年11月14日,赖斯出生于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
虽然当地种族隔离盛行,但她并没有像大多数黑人那样受到种族歧视的伤害。
赖斯的父亲在取得神学硕士学位后,接管了由其父亲创立的教堂,后来他担任了丹佛大学副校长。
到赖斯出生时,这个黑人家族已有了比较高的社会地位。
赖斯小时候是个“神童”。
她从小就跟着当小学音乐教师的母亲学弹钢琴,4岁时就开了第一个独奏音乐会。
她的学习也很出色,跳了两次级。
赖斯家相信一条严酷的真理:只有当孩子们做得比白人孩子高出两倍,他们才能平等;高出三倍,才能超过对方。
但这位“神童”在学业上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过几次挫折。
1969年,她随父亲迁居丹佛后,第一次在学习上遇到了困难。
学校的顾问对赖斯的父母说,赖斯“不是一块上大学的料”。
赖斯惊呆了,但她还是以“加倍地好”为目标继续努力。
后来,她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还把网球和花样滑冰玩得很出色。
赖斯16岁进入丹佛大学音乐学院学习钢琴,梦想成为职业钢琴家。
但是,在著名的阿斯本音乐节上,她受了打击。
“我碰到了一些11岁的孩子们,他们只看一眼就能演奏那些我要练一年才能弹好的曲子,”她说,“我想我不可能有在卡内基大厅演奏的那一天了。
美国国务卿赖斯的成长过程

美国国务卿赖斯的成长过程(2009-03-09 16:15:35)转载▼标签:杂谈来源:美国纽约中国项目咨询公司(信息部)提供频道:华中发布时间:2007-12-26 1965年,一个11岁的美国黑人女孩子随父亲来到首都华盛顿。
在白宫参观时,父亲鼓励她长大后要当美国总统。
她回答说:“早晚我会在那座房子里工作的。
”这个女孩名叫康多莉扎·赖斯。
不久前,她被布什总统提名接替辞职的国务卿鲍威尔,被媒体称为华盛顿“最有权力的女人”。
甚至有人大胆预测,她有可能在2008年当选总统。
与传统的“灰姑娘”故事不同的是,赖斯的成功不是来自于“白马王子”的爱情。
事实上,她至今还是一个待字闺中的单身女人。
她的成功完全是靠她的奋斗。
在种族歧视中长大1954年11月14日,赖斯出生于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
虽然当地种族隔离盛行,但她并没有像大多数黑人那样受到种族歧视的伤害。
赖斯的父亲在取得神学硕士学位后,接管了由其父亲创立的教堂,后来他担任了丹佛大学副校长。
到赖斯出生时,这个黑人家族已有了比较高的社会地位。
赖斯小时候是个“神童”。
她从小就跟着当小学音乐教师的母亲学弹钢琴,4岁时就开了第一个独奏音乐会。
她的学习也很出色,跳了两次级。
赖斯家相信一条严酷的真理:只有当孩子们做得比白人孩子高出两倍,他们才能平等;高出三倍,才能超过对方。
但这位“神童”在学业上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过几次挫折。
1969年,她随父亲迁居丹佛后,第一次在学习上遇到了困难。
学校的顾问对赖斯的父母说,赖斯“不是一块上大学的料”。
赖斯惊呆了,但她还是以“加倍地好”为目标继续努力。
后来,她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还把网球和花样滑冰玩得很出色。
赖斯16岁进入丹佛大学音乐学院学习钢琴,梦想成为职业钢琴家。
但是,在著名的阿斯本音乐节上,她受了打击。
“我碰到了一些11岁的孩子们,他们只看一眼就能演奏那些我要练一年才能弹好的曲子,”她说,“我想我不可能有在卡内基大厅演奏的那一天了。
2012年高中语文优秀课外阅读材料(三) 那些“不婚”的领导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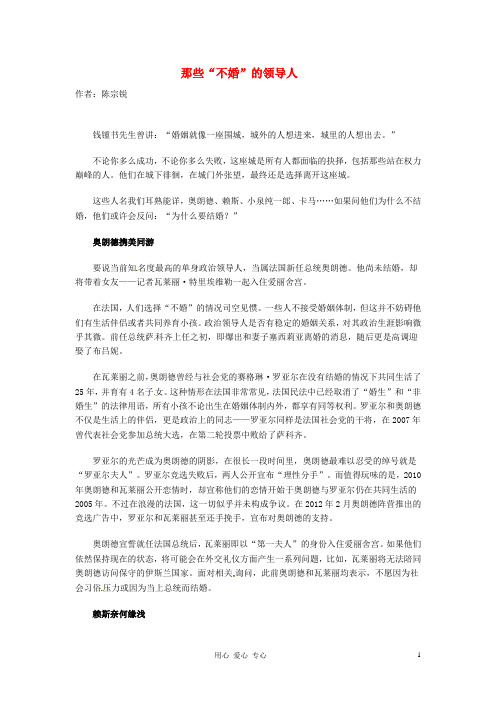
那些“不婚”的领导人作者:陈宗锐钱锺书先生曾讲:“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
”不论你多么成功,不论你多么失败,这座城是所有人都面临的抉择,包括那些站在权力巅峰的人。
他们在城下徘徊,在城门外张望,最终还是选择离开这座城。
这些人名我们耳熟能详,奥朗德、赖斯、小泉纯一郎、卡马……如果问他们为什么不结婚,他们或许会反问:“为什么要结婚?”奥朗德携美同游要说当前知名度最高的单身政治领导人,当属法国新任总统奥朗德。
他尚未结婚,却将带着女友——记者瓦莱丽·特里埃维勒一起入住爱丽舍宫。
在法国,人们选择“不婚”的情况司空见惯。
一些人不接受婚姻体制,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有生活伴侣或者共同养育小孩。
政治领导人是否有稳定的婚姻关系,对其政治生涯影响微乎其微。
前任总统萨科齐上任之初,即爆出和妻子塞西莉亚离婚的消息,随后更是高调迎娶了布吕妮。
在瓦莱丽之前,奥朗德曾经与社会党的赛格琳·罗亚尔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共同生活了25年,并育有4名子女。
这种情形在法国非常常见,法国民法中已经取消了“婚生”和“非婚生”的法律用语,所有小孩不论出生在婚姻体制内外,都享有同等权利。
罗亚尔和奥朗德不仅是生活上的伴侣,更是政治上的同志——罗亚尔同样是法国社会党的干将,在2007年曾代表社会党参加总统大选,在第二轮投票中败给了萨科齐。
罗亚尔的光芒成为奥朗德的阴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奥朗德最难以忍受的绰号就是“罗亚尔夫人”。
罗亚尔竞选失败后,两人公开宣布“理性分手”。
而值得玩味的是,2010年奥朗德和瓦莱丽公开恋情时,却宣称他们的恋情开始于奥朗德与罗亚尔仍在共同生活的2005年。
不过在浪漫的法国,这一切似乎并未构成争议。
在2012年2月奥朗德阵营推出的竞选广告中,罗亚尔和瓦莱丽甚至还手挽手,宣布对奥朗德的支持。
奥朗德宣誓就任法国总统后,瓦莱丽即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入住爱丽舍宫。
如果他们依然保持现在的状态,将可能会在外交礼仪方面产生一系列问题,比如,瓦莱丽将无法陪同奥朗德访问保守的伊斯兰国家。
职业生涯规划(土木工程系道桥专业)

4、济南-广州(2110公里,济南-荷泽-商丘-阜阳-六安-安庆-景德镇-鹰潭-南城-瑞金-河源-广州)
5、大庆-广州(3550公里,大庆-松原-双辽-通辽-赤峰-承德-北京-霸州-衡水-濮阳-开封-周口-麻城-黄石-吉安-赣州-龙南-连平-广州)
在此基础上,中国将再用十二年时间打造总规模8.5万公里以上的国家高速公路网。总的目标是,到2010年使高速公路网达到6.5万公里,到2020年达到8.5万公里。新路网由7条首都放射线、9条南北纵向线和18条东西横向线组成,简称为“7918网”,将把我国人口超过20万的城市全部用高速公路连接起来,覆盖10亿人口。工程总投资超过2.2万亿元,对国民经济的推动力将超过6万亿元以上
B. 职业价值观——努力追求的是什么?
我的人才素质测评报告结果显示,注重关系和追求成就得分较高(9分),工作条件和追求独立得分较低(6分)。这也基本上与本人相符,我的具体情况是:希望在工作中能够与同事相处和谐,并且与上下级相处融洽,并且希望能够通过工作接触到不同类型、群体、层次的人,从而学到不同的东西,来修饰提高完善自己。我一直“”希望在学习工作中,有比较好的培训机会,从而能够更好的提高自己,人生就是不断地充实的过程,尽管我比较崇尚独立,但在崇尚独立测评项中分数较低。今后,在日常学习中还需要多多注重自己的创新、及自主性的提高,能够独立进行决策,进一步完善了个人的综合素质培养。
兴趣太广, 对自己过于严格完美的要求,往往会使自己变得紧张、焦虑、害怕尝试。而且这种信念放大了自己暂时的落后,影响自己的信心。要相信,人无完人,与过去相比自己能不断提高、充实、进步,就应该感到欣慰了;另外只有开始做了,并且做成功了,才会一步步树立自己的信心
琴童改行成国务卿

EH!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从政坛卸任后,重新回到斯坦福大学做学院教授,经常有大学生慕名而来,询问这位身为美国第一位黑人女国务卿成功之路,她回答是淡定的,“从一个失败改行的钢琴学生开始”。
不知道中国3000万每天被打骂的钢琴学童和他们的父母,听了她的话作何感想。
赖斯从小被视为钢琴天才和学霸,15岁上丹佛大学的音乐学院,主修钢琴。
大二夏天,参加阿斯宾音乐节,在那里.她意识到自己只是个好的音乐演奏者,缺乏成为伟大演奏家的天才和悟性,由此,她决定不再追求职业钢琴演奏生涯。
赖斯的转折并不奇怪,钢琴学童跟钢琴演奏家的比例是25万比1,这是《时代》杂志做过的调研,25万个学生里出一个职业钢琴演奏家,可以靠开音乐会谋生。
赖斯这样早慧的神童知琴童改行成国务卿O〔美」凌岚难而退.她的兴趣转向国际政治。
赖斯在钢琴生涯上的挫折,被国际政治专业上遇到恩师的幸运完全抵消:她遇到约瑟夫•考贝尔,流亡美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家,国际政治界的大师。
现在,丹佛大学已经有了国际关系学院,以他的名字命名,这是后话。
考贝尔教授一辈子培养了两个女国务卿,赖斯是第二个,第一个是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奥尔布赖特是他的女儿。
阿拉巴马来的钢琴小天才,偶尔走进东欧知识分子教授讲的国际关系课,“那一课讲斯大林,我一听就迷上了,之前,从来没有关心过外交政策。
”这是《赖斯传》里写的,她的人生道路从此改写,赖斯在圣母大学读完硕士,再次回到考贝尔身边读博士。
与如今的钢琴教育大国相比,赖斯终身热爱钢琴艺术,没有拿过牛哄哄的奖,她不是中国钢琴产业教育链盛产的钢琴神童,你想啊,一个阿拉巴马小城牧师的女儿,没有多少钱可以砸可以投资,大学就近读的是后来父亲任副院长的丹佛大学,也是教工子弟不用交学费的缘故。
赖斯学钢琴,纯粹出于个人兴趣,所以,在她开阔眼界看到真正的音乐天才后,对自己的钢琴职业前途,也能做出清醒的判断,否定自己是不世出天才。
中国是钢琴教育大国,家长逼孩子学琴、考级、参加钢琴比赛,是持续二十年的时髦,像赖斯那样知难而退,改弦易辙的钢琴学生,估•不太多。
励志故事:真正的女强人—美国国务卿赖斯

励志故事:真正的女强人—美国国务卿赖斯提起赖斯,人们就会想到小布什和老布什。
布什曾开玩笑说,赖斯就像“妈妈”,什么都管。
在美国,从来没有一个黑人妇女能掌控如此大的权力。
下面店铺为大家带来双语励志故事:真正的女强人—美国国务卿赖斯,欢迎大家阅读!The Moscow News wasn't sure what to make Condoleezza Rice when the 34-year-old Stanford University professor came to town in 1988 to inaugurate1 a series of seminars2 at the U.S. ambassador's3 residence. She spoke of arms control policy and of a coming summit4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writer could not quite get past the notion5 of a young black woman as an expert on Soviet affairs.“ The men... couldn't help wondering: ‘ She should be busy cooking and driving her admirers mad. But instead she aptly6 juggles7 numbers of missiles and tanks, names of marshals8 and dates of summits,’ ” the paper wrote.It would be neither the first nor the last time that Rice, President-elect George W. Bush's choice to head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ould exceed expectations.“ I've seen it happen time and time again,” said Michael McFaul, a Democrat who advised Al Gore's campaign but is close to Rice. “ Foreign policy is dominated by bald9, graying white men and they're not used to someone like Condi Rice.”Indeed, Rice, 46, bears little outward10 resemblance11 to Henry Kissinger, the quintessential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but friends and colleagues say she is among of the smartest, most articulate12 and charming people they know.A steely13 manager, she also is a concert pianist and maniacal14 sports fan, half-joking that the only job she would rather have is commissionerof the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Philosophically, she is quite conservative. Rice argues against humanitarian15 miss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d for a hard line on Russia and putting U.S. strategic interests at the center of all decision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a Repulican administration should refocus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national interest,” Rice wrote this year in Foreign Affairs magazine. “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doing something tha t benefits all humanity,but that is,in a sense,a second-order effect.”An expert on the Soviet Union, Rice was plucked16 from academia in 1989 by Brent Scowcroft to serve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f former President George Bush, where she helped shape U.S. policy during the tumultuous17 time of the Soviet Union's collapse18.She was responsible for a part of the world that was exploding, giving her unusual access19 to the President. They would develop a friendship that, nearly a decade later, would lead Rice to his son.She first met George W. Bush in 1995 when she happened to be in Texas visiting his father. They talked mostly about their shared passion· · sports. Bush, in his first year as Texas governor, had neither foreign policy nor the presidency on his mind.But by August 1998, when they were together again at the Bush family house in Kennebunkport, Maine, that had changed.“ In between tennis games and going out on the boat and sitting out on the back porch we would have conversations about wha t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would face the next president,” Rice said last week in an interview.As Rice ran on the treadmill20 and Bush worked out on a glider21, the college professor began a two-year tutorial22 of her most important student yet. Bush hassaid that he likes Rice because she explains issues in a way he can understand.When George Bush was elected president in 1988, Scowcroft becam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and recruited23 Rice, who had impressed him with her knowledge of arms control.She was never a top tier policy aide in the White House, but her timing was perfect.The Berlin Wall collapsed, the Soviet Union was crumbling, and she was part of team that developed U.S.policy.Burned out24 after two years in Washington,she returned to Stanford.Within a year, she was elevated25 to provost26 the No.2 job at Stanford although she never been a department head or dean.Now, as Rice becomes the first woman to head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here's some concern that she was too far removed from international affairs as she was focused on university affairs. “ One critique27 you'll hear is that the Russia she knows is the Soviet Union of 10 or 12 years ago,” said Andrew Kuchins, who worked with Rice at Stanford and is now at the Carnegie Endowment28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even if she is an expert on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what about the Middle East,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Rice responds that every scholar has to specialize in something.Another challenge: Making her voice heard above Colin Powell, nominated to b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Vice President-elect Chency, strong personalities who might wind up29 battling one another.Kuchins is betting she will exceed expectations again. “ She's a strong personality and she should never be underes timated,” he said. “ Whether she's sitting in a room with Dick Cheney or Colin Powell, Condi will her own.”1988年,34岁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康多莉扎.赖斯来到莫斯科主持召开在美国大使官邸举行的系列研讨会时,《莫斯科新闻》还不知道她是何许人也。
美国国务卿赖斯简历(叙述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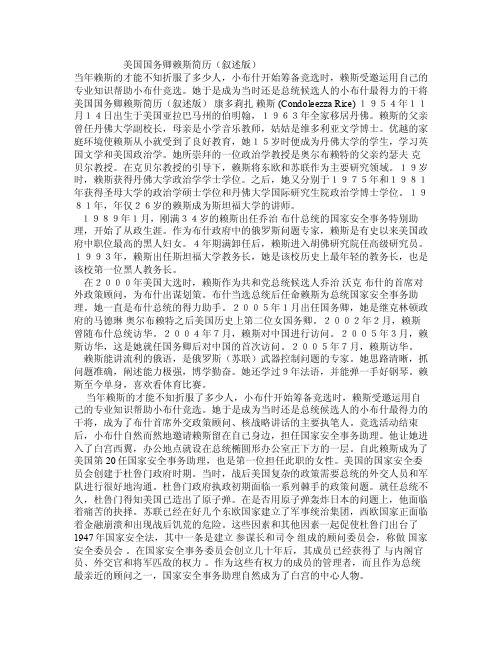
美国国务卿赖斯简历(叙述版)当年赖斯的才能不知折服了多少人,小布什开始筹备竞选时,赖斯受邀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小布什竞选。
她于是成为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小布什最得力的干将美国国务卿赖斯简历(叙述版)康多莉扎赖斯(Co ndo lee zza Ri ce)1954年11月14日出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1963年全家移居丹佛。
赖斯的父亲曾任丹佛大学副校长,母亲是小学音乐教师,姑姑是维多利亚文学博士。
优越的家庭环境使赖斯从小就受到了良好教育,她15岁时便成为丹佛大学的学生,学习英国文学和美国政治学。
她所崇拜的一位政治学教授是奥尔布赖特的父亲约瑟夫克贝尔教授。
在克贝尔教授的引导下,赖斯将东欧和苏联作为主要研究领域。
19岁时,赖斯获得丹佛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
之后,她又分别于1975年和1981年获得圣母大学的政治学硕士学位和丹佛大学国际研究生院政治学博士学位。
1981年,年仅26岁的赖斯成为斯坦福大学的讲师。
1989年1月,刚满34岁的赖斯出任乔治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开始了从政生涯。
作为布什政府中的俄罗斯问题专家,赖斯是有史以来美国政府中职位最高的黑人妇女。
4年期满卸任后,赖斯进入胡佛研究院任高级研究员。
1993年,赖斯出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她是该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教务长,也是该校第一位黑人教务长。
在2000年美国大选时,赖斯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乔治沃克布什的首席对外政策顾问,为布什出谋划策。
【2018最新】美国赖斯简介-实用word文档 (8页)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整理,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或侵权请及时联系,本司将立即删除!==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方便编辑和修改! ==美国赖斯简介篇一:美国国务卿赖斯简历康多莉扎·赖斯 (Condoleezza Rice) 1954年11月14日出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1963年全家移居丹佛。
赖斯的父亲曾任丹佛大学副校长,母亲是小学音乐教师,姑姑是维多利亚文学博士。
优越的家庭环境使赖斯从小就受到了良好教育,她15岁时便成为丹佛大学的学生,学习英国文学和美国政治学。
她所崇拜的一位政治学教授是奥尔布赖特的父亲约瑟夫·克贝尔教授。
在克贝尔教授的引导下,赖斯将东欧和苏联作为主要研究领域。
19岁时,赖斯获得丹佛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
之后,她又分别于1975年和1981年获得圣母大学的政治学硕士学位和丹佛大学国际研究生院政治学博士学位。
1981年,年仅26岁的赖斯成为斯坦福大学的讲师。
1989年1月,刚满34岁的赖斯出任乔治·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开始了从政生涯。
作为布什政府中的俄罗斯问题专家,赖斯是有史以来美国政府中职位最高的黑人妇女。
4年期满卸任后,赖斯进入胡佛研究院任高级研究员。
1993年,赖斯出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她是该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教务长,也是该校第一位黑人教务长。
在2000年美国大选时,赖斯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乔治·沃克·布什的首席对外政策顾问,为布什出谋划策。
布什当选总统后任命赖斯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她一直是布什总统的得力助手。
2005年1月出任国务卿,她是继克林顿政府的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之后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国务卿。
2002年2月,赖斯曾随布什总统访华。
2004年7月,赖斯对中国进行访问。
2005年3月,赖斯访华,这是她就任国务卿后对中国的首次访问。
2005年7月,赖斯访华。
赖斯能讲流利的俄语,是俄罗斯(苏联)武器控制问题的专家。
康多莉扎·赖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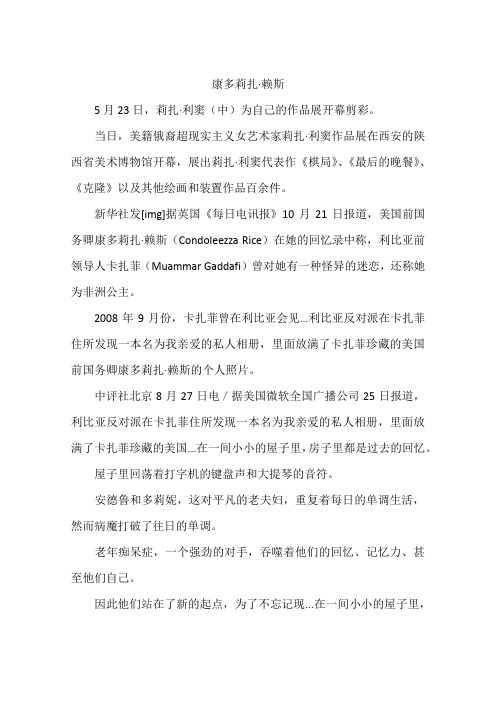
康多莉扎·赖斯5月23日,莉扎·利窦(中)为自己的作品展开幕剪彩。
当日,美籍俄裔超现实主义女艺术家莉扎·利窦作品展在西安的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开幕,展出莉扎·利窦代表作《棋局》、《最后的晚餐》、《克隆》以及其他绘画和装置作品百余件。
新华社发[img]据英国《每日电讯报》10月21日报道,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在她的回忆录中称,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Muammar Gaddafi)曾对她有一种怪异的迷恋,还称她为非洲公主。
2008年9月份,卡扎菲曾在利比亚会见...利比亚反对派在卡扎菲住所发现一本名为我亲爱的私人相册,里面放满了卡扎菲珍藏的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的个人照片。
中评社北京8月27日电/据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25日报道,利比亚反对派在卡扎菲住所发现一本名为我亲爱的私人相册,里面放满了卡扎菲珍藏的美国...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房子里都是过去的回忆。
屋子里回荡着打字机的键盘声和大提琴的音符。
安德鲁和多莉妮,这对平凡的老夫妇,重复着每日的单调生活,然而病魔打破了往日的单调。
老年痴呆症,一个强劲的对手,吞噬着他们的回忆、记忆力、甚至他们自己。
因此他们站在了新的起点,为了不忘记现...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房子里都是过去的回忆。
屋子里回荡着打字机的键盘声和大提琴的音符。
安德鲁和多莉妮,这对平凡的老夫妇,重复着每日的单调生活,然而病魔打破了往日的单调。
老年痴呆症,一个强劲的对手,吞噬着他们的回忆、记忆力、甚至他们自己。
因此他们站在了新的起点,为了不忘记现...据英国《每日电讯报》10月21日报道,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在她的回忆录中称,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Muammar Gaddafi)曾对她有一种怪异的迷恋,还称她为非洲公主。
2008年9月份,卡扎菲曾在利比亚会...据外媒报道,曾经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康多莉扎·赖斯日前透露,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她曾打电话给小布什,要求其不要回到华盛顿,之后就挂断了电话。
哈佛商业评论案例点评3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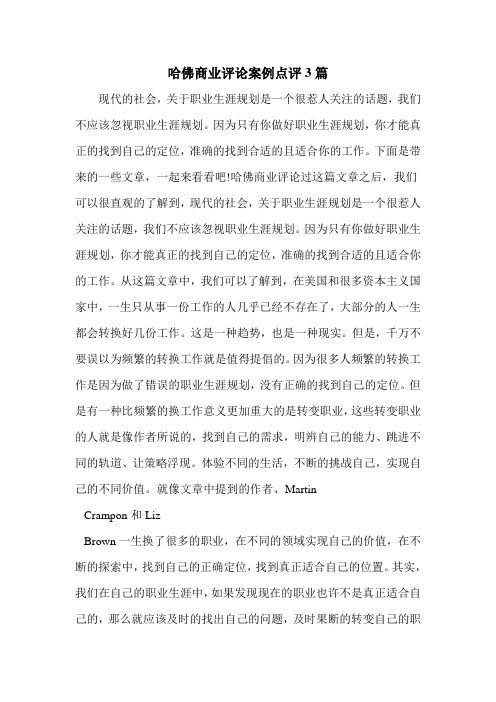
哈佛商业评论案例点评3篇现代的社会,关于职业生涯规划是一个很惹人关注的话题,我们不应该忽视职业生涯规划。
因为只有你做好职业生涯规划,你才能真正的找到自己的定位,准确的找到合适的且适合你的工作。
下面是带来的一些文章,一起来看看吧!哈佛商业评论过这篇文章之后,我们可以很直观的了解到,现代的社会,关于职业生涯规划是一个很惹人关注的话题,我们不应该忽视职业生涯规划。
因为只有你做好职业生涯规划,你才能真正的找到自己的定位,准确的找到合适的且适合你的工作。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美国和很多资本主义国家中,一生只从事一份工作的人几乎已经不存在了,大部分的人一生都会转换好几份工作。
这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现实。
但是,千万不要误以为频繁的转换工作就是值得提倡的。
因为很多人频繁的转换工作是因为做了错误的职业生涯规划,没有正确的找到自己的定位。
但是有一种比频繁的换工作意义更加重大的是转变职业,这些转变职业的人就是像作者所说的,找到自己的需求,明辨自己的能力、跳进不同的轨道、让策略浮现。
体验不同的生活,不断的挑战自己,实现自己的不同价值。
就像文章中提到的作者、MartinCrampon和LizBrown一生换了很多的职业,在不同的领域实现自己的价值,在不断的探索中,找到自己的正确定位,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位置。
其实,我们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如果发现现在的职业也许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那么就应该及时的找出自己的问题,及时果断的转变自己的职业,这是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这样才能更好的贡献自己的价值。
就像以前看过一篇文章,是关于美国前国务卿赖斯。
她的一生转变几次职业。
她说,“我坚信,人不应沉湎于过去。
无论你以前当过什么,都不要老想着回到以前的那个自己。
转变也许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更加完美的自己。
”那么,如何转变呢?首先,必须确定志向,志向是事业成功的基本前提,没有志向,事业的成功也就无从谈起。
俗话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高考优秀作文素材:自知之明

高考优秀作文素材:自知之明【#高考# 导语】只有真正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避己所短,扬己所长,才能对自己的人生坐标进行准确定位。
当你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时,也就是进步的开始。
整理“高考优秀作文素材:自知之明”,以供大家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感谢大家的阅读与支持!1.高考优秀作文素材:自知之明中国有句古话:“人贵有自知之明。
”所谓“自知”是指自己了解自己。
不会因为别人的安排而失去自己人生的方向,不会由于命运的打击而抹杀自己的闪光,更不会得意于一些井底之蛙的宠爱而放浪形骸……自知才能为自己即将要走的路正确定位,找准自己应该努力的方向。
美国历第一位女国务卿赖斯正是因为自知,才成就了她辉煌的人生。
在二十岁之前,赖斯一直梦想着成为舞台上一位众星捧月的钢琴家。
她刻苦地训练,直到一个11岁的小孩出现在她面前。
那个小孩可以把赖斯当时会的曲子全部弹下来,而且弹得声情并茂。
她毅然地改修了律师专业,与生俱来的口才,思维敏捷的天赋,使她很快进入了美国政界,打拼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赖斯了解自己,有选择的勇气,于是她的才华得以施展,而她也因为自知而创造了美国历史,创造了辉煌人生。
自知才能支撑着我们在追求梦想的旅途中忍受质疑和嘲笑。
哪怕遍体鳞伤,也要活得漂亮。
“我的存在就是让全世界都皱眉!”韩寒自信得过分,自恋得过火,不过他的自知又让人佩服。
他的存在确让世界_皱眉,最起码是中国舆论。
他的成名曾引发了全社会对培养专才还是全才的热议。
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他放荡不羁,却又忧郁伤感。
不管命运给他以多大的舆论冲击,他只是安静地反驳,不大肆澄清,也不轻言放弃,因为他始终明白自己的重量,并一直对自己抱有信心。
自知让他面对外界的重压依然对自己的灵魂不离不弃。
2.高考优秀作文素材:自知之明人生之路千万条,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路?毋庸置疑,一个具有自知之明的人选择的道路,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牛顿是英国十七世纪家喻户晓的物理学巨人、科学界高峰,但是人们只看到他卓越的成就,殊不知,牛顿起初潜心钻研化学,却毫无建树。
赖斯善于总结的名人例子

赖斯善于总结的名人例子赖斯1954 年11月14日出生在美囯伯明翰。
胒称康迪。
祖父是棉农。
后上大学成了牧师。
并在伯明翰建立一所教堂。
她父亲约翰·赖斯,在取得神学硕士学位后,掌管了这个教堂,到赖斯出生时他们这个黑人家庭已経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
当时伯明翰种族主义十分严重。
该市只有白人孩子能上的学校、白人进的影院、图书舘……。
而且黑人家庭还会遭到枪弹袭击。
她在家人保护教育下得以顺利成长。
她家坚伩一条:黑人孩子只有做得比白人孩子优秀两倍,他们才能平等。
优秀三倍才能超过对方。
父母告诉她:"因肤色妳可能在餐舘中买不到一个汉堡包,但如果努力,你就可能当上美国总统。
" 她坚伩父母的判断。
她为加倍的好,非常努力,她学习优秀。
一年级、七年级康迪都跳级了。
她家从各方面保证孩子们不受种族主义伤害。
他父亲宁愿他们回家上厕所,也不让使用种族隔离的公共设施。
赖斯这样回忆童年的経历:伯明翰光怪陆离,种族隔离无以复加,但黑人社区建立了自已的世界。
我上过芭蕾舞课、礼仪课、学过法语。
直到1964她父亲在斯蒂尔曼学院找到工作。
后又被丹佛大学录用,全家迁到丹佛,才彻底离开了种族歧视严重的南方。
她父亲后任丹佛大学副校长。
妈妈为钢琴教师,姑姑是文学博士。
此时她13岁;第一次进入取消种族隔离的学校——圣玛丽学院。
大学,毕业……康多莉扎,是母亲起的名字。
来源于意大利文,是 "弹奏得很甜美 " 的意思。
自小就跟母亲学钢琴,幼年就接受良好的音乐教育,四岁时康迪开了第一个独奏会。
母亲计划是赖斯成为职业钢琴家。
在黑;白键盘上奏响人生的精彩乐章。
她日夜刻苦练习,演奏,终于获得美国青少年钢琴大赛第一名。
15岁进入丹佛大学拉蒙特音乐学院学习钢琴演奏。
人们似乎看到一颗钢琴演奏的新星正冉冉升起。
但在大学二三年级间她参加了亚斯平音乐节,遇到了残酷的竞争。
赖斯说;"我碰到11岁的孩子,他们只看一眼就能演奏我要练一年才能弹好的曲子,我想我不可能有在卡内基大厅演奏的机会了。
美国国务卿赖斯的励志故事及感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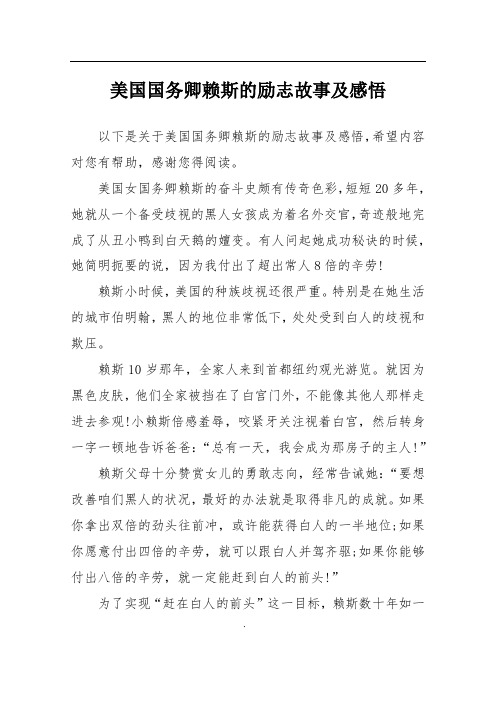
美国国务卿赖斯的励志故事及感悟以下是关于美国国务卿赖斯的励志故事及感悟,希望内容对您有帮助,感谢您得阅读。
美国女国务卿赖斯的奋斗史颇有传奇色彩,短短20多年,她就从一个备受歧视的黑人女孩成为着名外交官,奇迹般地完成了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嬗变。
有人问起她成功秘诀的时候,她简明扼要的说,因为我付出了超出常人8倍的辛劳!赖斯小时候,美国的种族歧视还很严重。
特别是在她生活的城市伯明翰,黑人的地位非常低下,处处受到白人的歧视和欺压。
赖斯10岁那年,全家人来到首都纽约观光游览。
就因为黑色皮肤,他们全家被挡在了白宫门外,不能像其他人那样走进去参观!小赖斯倍感羞辱,咬紧牙关注视着白宫,然后转身一字一顿地告诉爸爸:“总有一天,我会成为那房子的主人!”赖斯父母十分赞赏女儿的勇敢志向,经常告诫她:“要想改善咱们黑人的状况,最好的办法就是取得非凡的成就。
如果你拿出双倍的劲头往前冲,或许能获得白人的一半地位;如果你愿意付出四倍的辛劳,就可以跟白人并驾齐驱;如果你能够付出八倍的辛劳,就一定能赶到白人的前头!”为了实现“赶在白人的前头”这一目标,赖斯数十年如一日,以超出他人8倍的辛劳辛劳发奋学习,积累知识,增长才干。
普通美国白人只会讲英语,她则除母语外还精通俄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白人大多只是在一般大学学习,她则考进了美国名校丹佛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普通美国白人26岁可能研究生还没读完,她已经是斯坦福大学最年轻的女教授,随后还出任了这所大学最年轻的教务长。
普通美国白人大多不会弹钢琴,可她不仅精于此道,而且还曾获得美国青少年钢琴大赛第一名;此外,赖斯还用心学习了网球、花样滑冰、芭蕾舞、礼仪训练等,并获得过美国青少年钢琴大赛第一名。
凡是白人能做的,她都要尽力去做;白人做不到的,她也要努力做到。
最重要的是,普通美国白人可能只知道遥远的俄罗斯是一个寒冷的国家,她却是美国国内数一数二的俄罗斯武器控制问题的权威。
天道酬勤,“8倍的辛劳”带来了“8倍的成就”,她终于脱颖而出,一飞冲天。
赖斯演讲稿三篇范文

赖斯演讲稿三篇范文中国终将走向民主日前,美国国务卿莱斯在旧金山的共和俱乐部发表演讲。
莱斯说,民主之路绝非一帆风顺,民主制度也并非尽善尽美,但民主确是尊重人性和自由的机制。
她说,为世界自由事业开辟前进的道路,美利坚义不容辞。
莱斯强调,民主不同于专制,不需要强加于人。
“我们相信——我们坚信——中国不会永远成为(民主的)例外”。
以下是演讲全文,由中国信息中心翻译。
谢谢。
谢谢大家。
回家的感觉真好。
罗斯(Rose),谢谢你热忱的介绍。
谢谢你邀请我来到这里同湾区的众多朋友和同事们交流。
我并且要感谢俱乐部的主席,我的好朋友葛洛丽雅达菲(Gloria Duffy),葛洛丽雅致力于国际事务几近二十年。
葛洛丽雅,谢谢你对共和俱乐部(Commonwealth Club)的卓越领导。
重回加州的感觉实在美妙。
加州让我魂牵梦萦的不仅是气候、美酒和佳肴,更在于她的风土和人民。
来到旧金山我感到特别高兴,(赖斯1993年至1999这座城市令我回想起自己在斯坦福的学院生活。
年曾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
译者注。
)旧金山还是国际政治史上的一座重要城市。
60年前,世界各国在这里缔结了联合国XX,人类历史的全新纪元由此展开。
20年前,在旧金山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又帮助终结了那个旧时代。
当时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chulz)也是在共和俱乐部提出了瓦解苏联的战略,这就是后来里根主义的雏形。
里根主义简单而卓有成效。
舒尔茨国务卿说,民主浪潮正席卷全球,美利坚将不遗余力地保障并推进世界各国的民主化进程。
此后仅四年,柏林墙坍塌了,黎明的曙光乍现。
苏联的崩溃根本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
对一些人来讲,这意味着俄罗斯和东欧获得了解放;但另一方面,脆弱而稳定的国际关系由此结束。
先是巴尔干的种族清洗,随后是中非的战乱和屠戮,接着邪恶的宗教狂热分子在阿富汗攫取了政权并展开血腥的屠戮。
紧跟着是发生在那个温暖九月早上的袭击事件。
整个世界都蒙上了恐怖阴影。
也是在这一天,美利坚意识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同世界其它区域的民主成败息息相关。
赖斯

赖斯百科名片康多莉扎〃赖斯 (Condoleezza Rice) 赖斯的父亲曾任丹佛大学副校长,母亲是小学音乐教师,姑姑是维多利亚文学博士。
优越的家庭环境使赖斯从小就受到了良好教育,她15岁时便成为丹佛大学的学生,学习英国文学和美国政治学。
2005年1月出任国务卿,她是继克林顿政府的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之后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国务卿。
赖斯能讲流利的俄语,是俄罗斯(苏联)武器控制问题的专家。
她还学过9年法语,并能弹一手好钢琴。
赖斯至今单身,喜欢看体育比赛。
天才儿童黑人骄傲赖斯家相信这样一条严峻的真理:黑人的孩子只有做得比白人孩子优秀两倍,他们才能平等;优秀三倍,才能超过对方。
父母告诉康迪,在伯明翰以外有更多的机会,如果她勤奋学习,力争上游,就会得到回报。
‚你可能在餐馆里买不到一个汉堡包,但也有可能当上总统。
‛进入学校后,康迪学习十分出色,一年级和七年级都跳级了。
回忆起自己童年的经历时,赖斯说:‚伯明翰光怪陆离,种族隔离无以复加,但黑人社区建立了自己的世界。
我上过芭蕾舞课,学过法语,还上过礼仪课。
‛康迪的外祖父母从各方面保证孩子们不受种族主义的伤害。
康迪的舅舅回忆说,他父亲宁愿他们回家上厕所也不让使用种族隔离的公共设施,‚实际上,我一生从未坐过种族隔离的公共汽车。
‛然而到1963年,伯明翰却成了暴力和民权运动的大熔炉,广大黑人成了种族思想根深蒂固的伯明翰警察当局的打击目标。
赖斯的父亲和大部分黑人不得不自我武装起来,防止有暴力倾向的白人进入黑人社区。
1965年,11岁的赖斯跟随父母到了首都华盛顿。
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散步,最后在白宫大门前停下来,因为肤色,他们不能进去参观。
他们看这那座举世瞩目的建筑物徘徊良久,最后,赖斯转过身平静地告诉父亲:‚我现在因为肤色而被禁止进入,但总有一天,我会在那间屋里。
‛1969年,父亲在丹佛大学谋得教职,全家随之迁居丹佛,彻底走出了种族歧视严重的南方。
康迪进入圣玛丽学校读书,这年她13岁,第一次进入了不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
国务卿赖斯就职演讲

as we work for a more just economic order, we must also work to promote a freer andmore democratic world – a world that will one day include a democratic cuba, ademocratic burma, and a fully democratic middle east. 当我们要想建立一个公平的经济秩序,同时我们也必须得努力去营造一个更自由、更民主的世界,这个世界将包含一个民主的古巴、缅甸和完全民主的中东。
now, this emphasis on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 is controversial, i admit,and some would say, “well, we’ve actually made the situation worse.”如今中东的民主已经变得有争议了,我承认这一点。
因此可能就会有人说:好吧,我们让情况变得更糟了。
而我不禁想反问他们:比什么更糟了?worse than when the syrian army occupied lebanon for nearly 30 years? worse thanwhen the palestinian people could not hold their leaders accountable, and watchedas a chance for peace was squandered and evaporated into the second intifada?比叙利亚军队侵占黎巴嫩将近30年更糟糕吗?能比巴勒斯坦人民再也不相信他们的政府且眼睁睁地看着和平的机会被浪费了并再次进入混乱更糟嘛?worse than the tyranny of saddam hussein at the heart of the middle east, whoterrified his neighbors and whose legacy is the bodies of 300,000 innocent peoplethat he left in unmarked mass graves?能比萨达姆侯赛因在中东的暴行,如恐吓其邻国,它的遗产是那无名坟冢中的三十万具无辜的尸体,能比这更糟糕么?or worse perhaps than the false stability which masked a freedom gap, spawnedhopelessness, and fed hatreds so deep that 19 men found cause to fly airplanes intoamerican cities on a fine september morning?或者是这虚假的稳定掩饰了自由的鸿沟,给人们带来无望,同时带来的仇恨之深以至于19个人在一个美好的九月的早晨空袭了美国城市,能比这更糟嘛?no,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ast order in the middle east is nothing to extol,but it does not make the challenges of the present less difficult. even when youcherish democratic ideals, it is never easy to turn them into effective democraticinstitutions. this process will take decades, and it will be driven, as it shouldbe, and as it only can be, by courageous leaders and citizens in the region.没有,女士们先生们,中东过去的秩序并不值得赞扬,但其现今所面临的挑战也并不因此而减轻,把民主制度付诸行动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政治人物赖斯

11、强硬作风导致工作的不足
赖斯是一个女强人,但也不是 一个可以面面俱到的超人,在起初 对待恐怖主义事件中就体现出她对 恐怖主义威胁估计的失误。在她上 任之后,反恐问题她都倚重自己的 副手蒂夫· 哈德利,自己就有更多 时间关注于自己熟悉看重的领域。 在布什上台头两个月里,赖斯领导 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伊拉克问题、 尤其是解决萨达姆政权问题为新政 府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 ,其他一切事物都是次要的。
12、处理中国问题
炒作中国问题: 在竞选中,赖斯与小布什都一再强调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 争者,而不是战略合作伙伴,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政策, 这成为当时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他们抨击克林顿政府对华 政策是摇摆的,错误的,赖斯主张美国要尽一切可能促进中 国的政治变化,与中国进行贸易将促进中国的经济对外开放 ,有利世界经济。受到赖斯影响,布什发表的演讲、接受采 访,三句不离中国问题,在台湾问题上,布什说:“我们期 待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争端能够和平解决,美国奉行一个中 国政策,但是也遵行台湾关系法,必要时协助台湾自卫。” 参加电视辩论前,赖斯精心协助指导布什,提到中国问题 将是这次辩论的重点,并且支持中国加入WTO,在处理与中 国关系中,即和平对待,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又把中国看成 新的战略竞争者,支持太独,这样强硬的外交态度为他拉了 不少选票。
母亲的影响:赖斯曾评价说:“母亲是
一位优雅美丽的女人,她喜欢穿的雅致大 方。”母亲从小就把她打扮的很漂亮很清 爽,又重视对她礼仪方面的教育,所以赖 斯担任首席外交官之后,十分重视个人仪 表的赖斯的穿着打扮总是看起来优雅得体 。
4、人生的转折点
从音乐到政治的跨度
从小赖斯就希望当一个音乐钢琴演奏家,并且在10岁 那年成为南方音乐学校的第一位黑人学生,不仅学习钢琴 ,还学习小提琴、长笛等。在赖斯13岁那年进入了丹佛市 最著名的私立女子学校圣玛丽学校读书,15岁那年提前 学完了高中课程,16岁她进入了丹佛大学拉蒙特音乐学 院主修钢琴演奏。 在音乐学院学习过程中她发现,许多年纪比她小多了 的天才音乐神童,读一遍谱就能熟练演奏她练习了几个月 的曲子,于是她决定换一个专业,从新选择人生起跑线。 大三,她遇到了改变她一生的老师,主讲国际关系的 教授科贝尔,他讲的“斯大林时代与政治”的讲座深深吸 引了赖斯,于是,赖斯开始了她学习国际政治的道路,主 修当时最热门的苏联问题。
我给赖斯当保镖

当天 晚 上 。 斯把 我 叫 到 她 的 赖
被聘为赖斯保镖
2( 年 3月 的 一 天 . 两 位 政 05 } 有
府 官 员 模 样 的 人找 到 我 。来 人 自称
维普资讯
新 闻 ・新知 ・新பைடு நூலகம்生 活 ・新 境 界
一 一 一 一 - - - _ 一 - - - _ _ _ 一 ● _ _ _ _ 一 _ - _ _ 一 _ - - - 一 _ _ 一 - 一 _ 一 _ 一 - - - - _ 一 - - - 一 - - 一 - - - - - 一 - - - - _ 一 - ● - -
教赖斯练太极
21 (5年 8月底 , 第 一 次 随 赖 0 我
斯 出 国访 问 , 目 的地 是 德 国柏 林 。 她 乘 坐 的 是 美 国 空 军 一 架 波 音 专 机 。我 们 先 是 直 飞柏 林 机 场 , 后 然
从 机 场 乘车 前往 德 国 总理 府 。 会 谈 结 束 后 , 斯 直 接 前 往 洲 赖
他 们 对 我 的 表 现 很 满 意 。 此
房 间 , : 丁 先 生 . 今 天 的 表 现 说 “ 你 很 勇 敢 ,很 机 智 , 我 一 定 要 奖 励
后 . 接 受 了 一 系 列 培 训 。2 0 我 0 5年
8月 .我 正 式 成 为 一 名 保镖 ,月薪
1 0 0美 元 。 5O
你 。” 这 样 , 成 了赣 斯 的近 身保 就 我 镖 , 常离 她 只 有 一两 米 远 。事 后 , 经 上 司 不 光 奖 勋 了 我 1万 美 元 . 还把
道路桥梁职业生涯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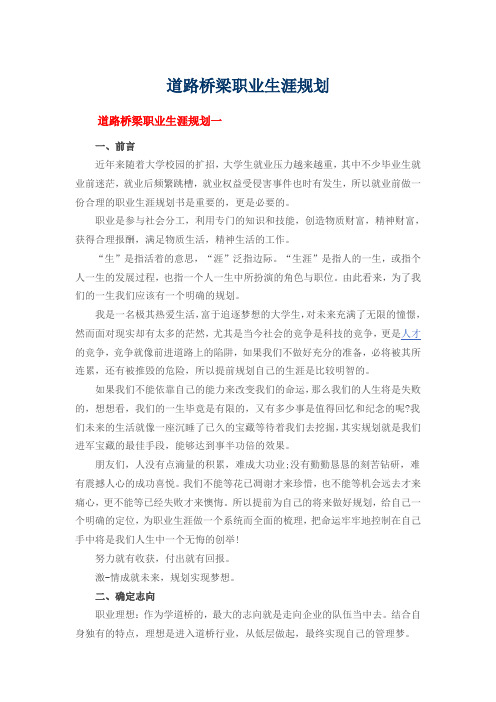
道路桥梁职业生涯规划道路桥梁职业生涯规划一一、前言近年来随着大学校园的扩招,大学生就业压力越来越重,其中不少毕业生就业前迷茫,就业后频繁跳槽,就业权益受侵害事件也时有发生,所以就业前做一份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书是重要的,更是必要的。
职业是参与社会分工,利用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获得合理报酬,满足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工作。
“生”是指活着的意思,“涯”泛指边际。
“生涯”是指人的一生,或指个人一生的发展过程,也指一个人一生中所扮演的角色与职位。
由此看来,为了我们的一生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规划。
我是一名极其热爱生活,富于追逐梦想的大学生,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憧憬,的竞争,竞争就像前进道路上的陷阱,如果我们不做好充分的准备,必将被其所连累,还有被推毁的危险,所以提前规划自己的生涯是比较明智的。
如果我们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来改变我们的命运,那么我们的人生将是失败的,想想看,我们的一生毕竟是有限的,又有多少事是值得回忆和纪念的呢?我们未来的生活就像一座沉睡了已久的宝藏等待着我们去挖掘,其实规划就是我们进军宝藏的最佳手段,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朋友们,人没有点滴量的积累,难成大功业;没有勤勤恳恳的刻苦钻研,难有震撼人心的成功喜悦。
我们不能等花已凋谢才来珍惜,也不能等机会远去才来痛心,更不能等已经失败才来懊悔。
所以提前为自己的将来做好规划,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为职业生涯做一个系统而全面的梳理,把命运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将是我们人生中一个无悔的创举!努力就有收获,付出就有回报。
激-情成就未来,规划实现梦想。
二、确定志向职业理想:作为学道桥的,最大的志向就是走向企业的队伍当中去。
结合自身独有的特点,理想是进入道桥行业,从低层做起,最终实现自己的管理梦。
人生理想:最大程度的实现自我价值,最终成为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高素质复合性人才。
三、自我剖析1)兴趣爱好:还有上网,喜欢社交、娱乐2)人格描述:·看问题有很强的批判性,通常持怀疑态度,需要时常的换位 1思考,更广泛的收集信息,并理智的评估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可能后果。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我如何转换职业生涯——访美国前国务卿赖斯采访者:凯瑟琳•贝尔(Katherine Bell)凭借不畏失败的勇气与毅力,赖斯(Rice)在艰难时期登上了权力巅峰,尽管批评家们认为她并不具备必要的经验。
35岁时,她出任老布什总统的苏联事务顾问。
1993年,在斯坦福大学深陷预算危机之际,她临危受命,成为该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教务长。
2001年,她被小布什总统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家安全顾问。
在经过八年的华盛顿政治生涯后,赖斯重返斯坦福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并任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
编者注:本次采访的精选内容刊登于哈佛《商业评论》杂志2010年3月号。
《哈佛商业评论》:时隔8年您又回到斯坦福大学,有何感受?赖斯:感觉好极了。
从某些方面来看,我觉得自己仿佛从未离开过斯坦福。
我早在1981年就开始在斯坦福任教了,所以现在可以说是回家了。
这次我是在商学院教书,以前我还没在商学院教过书,但是我熟悉教书,也熟悉斯坦福,还熟悉斯坦福的体育运动。
所以,再转回以前的角色,对我来说没什么困难。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离开政界。
您的职业生涯有过数次跨界的重大变动。
您是如何完成这些转变的?我坚信,人不应沉湎于过去。
无论你以前当过什么,都不要老想着回到以前的那个自己。
比如,我会告诉自己,我不是苏联事务前特别助理,而是新任教务长。
我不是前教务长,而是新任国家安全顾问。
现在,我也不想顶着前国务卿的名号。
我觉得,要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就更容易适应新环境。
你必须忘却以前的工作环境,转而适应新环境。
但是,在这些角色之间来回转换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你会带来一些新技能和看问题的新角度。
您从学术生涯中获得的哪些知识对于您在国务院的工作最有助益?我觉得有一点必须牢记:大多数组织都不想变革。
它们已经体制化了,它们有一套自己的传统、规范和专长,很难改变。
我在学术领域所做的许多研究都证明,组织通常在遭遇挫折后才进行变革。
成功时,很难让它们变革。
而一旦发现不得不变革,往往为时已晚。
所以问题是,你如何让一个比较成功的组织去应对新挑战。
我对组织发展的研究,对于我领导国务院步入后“9·11”时代的世界大有帮助。
我觉得三件事情很有帮助。
首先,你必须描述组织过去是怎么成功应对变革和困境的。
于是,我在国务院就大谈它在二战后是怎么做的,又是怎么为成功结束冷战铺路的。
其次,如果你能在组织中找到符合变革方向的非主流言论,那会很有帮助。
我在国务院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让它更多地走出去,减少在伦敦、巴黎等首府做政治报告的人,增加派往喀布尔、巴格达军事基地考察、合作的人,还有在危地马拉高地、莫桑比克艾滋病诊所为那里的援助人员提供支持的人。
我发现,国务院实际上历来就有人在贝鲁特、哥伦比亚和叙利亚等地的艰苦条件下工作。
我们可以把这些经历端出来说,以前的国务院官员们也做过这些事情。
我还会密切关注我们在奖励什么行为。
如果你说组织应该做x,可你实际却在奖励y,那么人们就会接受这样的信号。
国务院大概有30个左右的奖项是为政治报告所设的,但是为民事/军事合作设的奖项一个也没有,为支持人权所设的奖项也很少。
我们所奖励的行为与我们所倡导的国务院的发展方向完全背道而驰。
最后,你还必须要看有没有一些障碍在阻止人们做正确的事。
在优秀的组织里——国务院当然是一个优秀的组织——人们大多想做正确的事,我认为在斯坦福也是这样,人们不想当绊脚石,但是有时候会有一些障碍让他们很难去做正确的事。
例如,在国务院,我需要阿拉伯事务发言人到巴格达这样的地方去,这就要求他们走出开罗。
但是如果他们离开开罗,他们的家人就得千里迢迢搬回美国。
所以,我们得想办法让他们在巴格达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家人仍能留在开罗。
当您从国家安全局调任国务院时,您曾说过,与参谋职位相比,您更喜欢直接主事。
现在回顾那段日子,您还是这样想吗?我喜欢在白宫的日子。
我离总统只有几步之遥,我每天可以看到他六七次。
我崇拜他,喜欢与他那样近距离地共事。
但在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时,我更像是通过遥控来影响外交政策。
“我们能否让国防部长做这个,让国务卿做那个?”所以,你说的对,权衡下来,我更喜欢出任国务卿。
有人评价您的管理风格是强调制度、等级有序。
您如何评价自己的风格?这些年来,您的风格有什么变化吗?我不认为自己有很强的等级观念。
例如,我的办公室大门向几位助理国务卿敞开。
他们并不需要通过任何人来见我,因为他们是我手下的事务主管,他们是那些必须做实事的人,我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这些人得到了充分授权。
但我不认为国务院的每个人都应该对外阐述美国政策。
那会引起混乱。
在我第一次当教务长之前,我连系主任都没当过,更别提当院长了。
起初,我都不知道如何授权,总是想去把别人的活儿都干了。
后来我认识到,这样下去会让自己抓狂,而且那些有能力的人在自己手下也会干不长。
从那以后,我觉得自己在授权方面有所进步。
当您成为斯坦福大学的教务长,也就是一家年预算支出近20亿美元组织的首席运营官时,您并没有管理经验。
您是如何边干边学,又是如何与那些觉得您自不量力的人相处的?还有如何与那些认为自己才应该担任教务长的人相处吧?其实,我的一个优势就是:我很清楚我的工作重心应放在何处。
我是93年出任教务长的,斯坦福大学当时深陷经济困境——我们仍有1.57亿美元的地震损失无法填补。
我知道自己的首要任务是稳定预算和重建校园。
于是,我就全力以赴先解决这个问题。
我很快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其实没那么复杂,不过你得做一些艰难的决定,在做决定时要讲究策略,你不能没钱还乱花。
当时,我刚走出华盛顿,头上还顶着冷战后苏联专家的光环,真有点放不下架子。
我让周围一些我能信任、我觉得能帮上忙的人来协助我工作。
在教师队伍中我有一些认识多年的朋友,能做我的耳目,告诉我真实情况如何,我的决定又引起了多大的动荡。
您是否觉得有压力,必须向别人证明自己有多强悍?在第一年里,不仅仅是“证明”,而是“的的确确”必须要强悍。
我原本对人非常尖刻。
但我从课堂上学到,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打击别人,因为这样会让人家不敢做声,全班都会噤若寒蝉。
身为一名管理者,我不得不补上这一课。
众所周知,您和布什总统的关系非常密切。
这种密切关系显然会有一些好处。
那您觉得是否也有一些不利之处呢?跟上司关系密切,这事可能会挺复杂。
首先,好处要明显多于坏处。
当你在与俄罗斯外长磋商时,你最不希望自己是孤立无援的,而俄方也不确定你是否能代表总统本人。
但是,当我转到国务院工作时,就非常有必要保持一个独立的声音,而不是成为总统的传声筒。
另外一个不利之处是,你必须牢记他不只是你的朋友,他还是总统。
您的业余活动,比如弹钢琴、看体育比赛、做运动,这些对您来说很重要,那么这些活动对您的工作有没有影响?竞技滑冰、钢琴演奏都需要刻苦训练、严守规则,这样的精神几乎适用于任何工作,因为你必须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想方设法完成任务,即使失败也要继续前行。
但是,从事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平衡我的生活。
我不是一个工作狂。
我知道许多人不相信这一点,但我的确不是工作狂。
我对许多事情的热爱要超过对工作的热爱。
我听到有传言说,您职业生涯的下一个重大行动是想成为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总裁。
我以前是有这样的想法。
但我告诉现任联盟总裁罗杰·古德尔(Roger Goodell),当我在和俄罗斯、朝鲜政界周旋的那会儿,觉得他那份工作看上去很不错。
但现在我到了斯坦福,加利福尼亚的北部,就不再觉得那份工作有多好了。
不过,我还是挺喜欢做体育管理的,我觉得那会有很多乐趣。
您这一路走来遇到了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导师和支持者。
其中多少是运气成分,多少是刻意为之?两者兼而有之吧。
我很幸运有些人走进了我的生活,但我也会时不时地主动寻找那些跟我想做的事情相类似的人。
我不是一个腼腆的人,我会主动打电话跟别人说,你愿不愿意抽几分钟时间跟我谈谈。
比如说,我还是一个年轻教授的时候,我曾打电话约见教务长。
没人打电话给教务长,但我打了,他也见了我。
当然,你要凭自己的真本事,但是有人支持你总没坏处。
人们经常评论说,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充满着信心。
在您的内心,是否也像您对外表现得那样信心十足呢?我基本上是一个充满信心的人。
这种信心源于充足的准备,一流的实力。
我的信心还跟我小时候就总是身处必须表现自己的场合有关。
钢琴比赛、钢琴独奏、滑冰,这些我原本都做得不大好,但我还是尽力尝试。
还有一点可能也非常重要,我在事情还没有结束前不会去想失败的事,到事情结束后,我才会想,哎呀,这件事本可能会是怎样的一个糟糕结果。
不要过多地去想负面的东西,别老是想事情会变得如何如何糟糕。
那您又是怎么面对失败结局的呢?我曾经是个糟糕的花样滑冰选手,这段经历让我学会了怎样面对失败。
你第二天还是必须爬起来,重振精神,继续滑下去。
回顾您的职业生涯,什么失误让你最感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