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 迟桂花及赏析
郁达夫后期小说中的道家文化解读——以《迟桂花》为中心

现当代文学郁达夫后期小说中的道家文化解读——以《迟桂花》为中心文/刘奕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传统文化紧密相关,道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地影响了一大批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郁达夫也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迟桂花》是郁达夫后期小说中的杰作,显示了郁达夫小说创作向传统文化的回归。
为此,本文拟作一次小小的尝试,通过全面解读《迟桂花》来考察郁达夫后期小说中的道家文化意蕴及其相应的审美观念和文化心态。
关键词:《迟桂花》;道家文化;审美观念;文化心态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是在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中国现代文学也是在学习和借鉴外国进步文学中发展成熟起来的,但是它同民族文化传统之间有着更为深刻的联系。
”[1]3道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大批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
“他们对道家文化贬抑者有之,批判者有之,重新诠释者有之,默默吸收者亦有之。
尽管道家文化有着不少的消极面,但它确实给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带来了丰富的智慧和独特的魅力、丰富了剧烈变动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精神素养和艺术表现形式,以其自身文化品格的柔韧性和弹性使中国的现代文学文化熠熠生辉。
”[2]1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多作家都与道家文化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郁达夫也是其中的代表之一,郁达夫的小说大部分创作于二十世纪20—30年代。
30年代后他的小说创作发生转向。
有学者提到,1932年后,郁达夫在好些文章中以道家的隐士姿态出现,以写读书游记自娱。
[3]80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郁达夫小说创作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
《迟桂花》是郁达夫后期小说的典型代表,被郁达夫誉为“自己作品中的杰作”。
[4]54表现出了鲜明的道家文化意蕴及其相应的审美观念和文化心态。
一、崇尚自然的审美观念“自然”,是道家哲学体系和审美观念的核心。
《老子》中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庄子继承老子思想提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观点。
叙事聚焦:郁达夫的《迟桂花》解读

牡 丹 江 师 范 学 院 学报 ( 哲社版)
J o u r n a l o f Mu d a n j i a n g No r ma l Un i v e r s i t y
NO . 2. 2 O 1 4 To t a l NO .1 8 0
叙事 聚焦 : 郁达夫的《 迟 桂花 》 解读
蒋 玲 凤
( 华 侨 大 学 文学 院 , 福建 泉州 3 6 2 0 2 1 )
[ 摘 要 ] 在 郁 达 夫 的 小 说《 迟桂花 》 中, 作者 一 改大胆暴 露, 零 余 者 形 象 的写 法 , 在 淳 朴 静 美 的境 界 中 荡 涤 自 己 内心 的躁 动 , 发 出 了对 人 间真 情 的 呼 唤 。作 品 中 不 自觉地 运 用 了叙 事 聚 焦 , 主 要 是 运 用 内聚 焦 的形
绘上 。
得见 的 , 只是 些 青 葱 的 山 , 和如 云 的树 , 在 这 些 绿 树 丛
中, 又是 些 这 儿 几 点 , 那 儿 一 簇 的 屋 瓦 与 白墙 ”, [ 2 ] 1 到 了翁 则 生 的家 中 , “ 我” 立 在 他 们 家 的空 地 里 , “ 前 山
后 山的山景 , 是依 旧历历 可见 的。屋前屋 后 , 一 段 一 段 的 山坡 上 , 都 长着些不 知名 的杂树 , 三 株 两 株 夹 在
适 应 其 自身 的 经 验 现 实 。由 此 可 知 , 作 者笔 下 的 这 些
景物其实是 真实 的 , 反映 出“ 我” 实 际 感 受 的 风 景 描
写。
概念 : 聚焦 主 体 ( 聚焦 者 ) 和聚焦客体( 聚焦 对 象 ) 。 “ 聚焦 对 象 它 不 一 定 是 人 物 。客 观 对 象 、 风景 、 事件, 总之所有 成分 都可 被 聚焦 , 或 者 由 外 在 式 聚 焦 者 进 行, 或 者 由人 物 聚焦 者 进 行 ” [ 1 ] 】 ”。 朋 友 翁 则 生 邀 请 我 参 加 他 的婚 礼 。初 人 翁 家 山 ,
情谊文章 久若迟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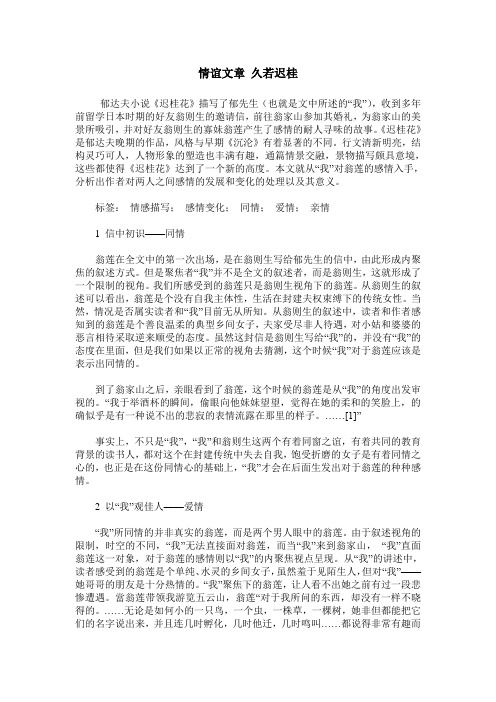
情谊文章久若迟桂郁达夫小说《迟桂花》描写了郁先生(也就是文中所述的“我”),收到多年前留学日本时期的好友翁则生的邀请信,前往翁家山参加其婚礼,为翁家山的美景所吸引,并对好友翁则生的寡妹翁莲产生了感情的耐人寻味的故事。
《迟桂花》是郁达夫晚期的作品,风格与早期《沉沦》有着显著的不同。
行文清新明亮,结构灵巧可人,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丰满有趣,通篇情景交融,景物描写颇具意境,这些都使得《迟桂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本文就从“我”对翁莲的感情入手,分析出作者对两人之间感情的发展和变化的处理以及其意义。
标签:情感描写;感情变化;同情;爱情;亲情1 信中初识——同情翁莲在全文中的第一次出场,是在翁则生写给郁先生的信中,由此形成内聚焦的叙述方式。
但是聚焦者“我”并不是全文的叙述者,而是翁则生,这就形成了一个限制的视角。
我们所感受到的翁莲只是翁则生视角下的翁莲。
从翁则生的叙述可以看出,翁莲是个没有自我主体性,生活在封建夫权束缚下的传统女性。
当然,情况是否属实读者和“我”目前无从所知。
从翁则生的叙述中,读者和作者感知到的翁莲是个善良温柔的典型乡间女子,夫家受尽非人待遇,对小姑和婆婆的恶言相待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
虽然这封信是翁则生写给“我”的,并没有“我”的态度在里面,但是我们如果以正常的视角去猜测,这个时候“我”对于翁莲应该是表示出同情的。
到了翁家山之后,亲眼看到了翁莲,这个时候的翁莲是从“我”的角度出发审视的。
“我于举酒杯的瞬间,偷眼向他妹妹望望,觉得在她的柔和的笑脸上,的确似乎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寂的表情流露在那里的样子。
……[1]”事实上,不只是“我”,“我”和翁则生这两个有着同窗之谊,有着共同的教育背景的读书人,都对这个在封建传统中失去自我,饱受折磨的女子是有着同情之心的,也正是在这份同情心的基础上,“我”才会在后面生发出对于翁莲的种种感情。
2 以“我”观佳人——爱情“我”所同情的并非真实的翁莲,而是两个男人眼中的翁莲。
郁达夫小说《迟桂花》解读

人间真情的呼唤——郁达夫小说《迟桂花》解读摘要:《迟桂花》是郁达夫后期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体现了与前期作品不同的思想情感。
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小说中主要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小说设置的叙事结构进行详细分析和解读,可以看出,小说主要表现的是作者在人生困境中对人间亲情和友情的真切呼唤。
关键词:现代文学;郁达夫;迟桂花;思想;解读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坛的著名作家,他开创了自叙传式的抒情体小说,在五四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以《沉沦》为代表的前期小说塑造了一系列“零余者”的形象,敢于毫无遮掩的暴露自我,“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
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
”[1]但30年代以后,进入中年的郁达夫,其小说无论是在风格上还是思想内容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迟桂花》就是这一时期的小说代表作之一,作者一改大胆的暴露,零余者形象的写法,在淳朴静美的境界中荡涤自己内心的躁动,发出了对人间真情的呼唤。
虽然《迟桂花》发表后的影响并没有《沉沦》等作品那样大,但却“是小说家融合心灵的体验、诗意的感悟和自由的想象而写成的一部抒情小说杰作。
”[2]其所具有的思想意蕴更为深厚,在艺术表现上也更为成熟。
要想把握小说丰厚的内在意蕴,就必须结合作品对主要人物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作品内在的叙事结构进行详细梳理和分析,通过文本细读我们自然就能感受到其内在的真意。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或隐或显地包含着作者的某种思想情感,对于小说而言,作者通常是不会站出来直接言说的,思想情感的表现比较隐蔽。
在小说中,作者的观点是通过小说的叙述者或小说中的人物来传达的。
换句话说,小说的叙述者或人物就是起到传达作者观点的功能的。
同时,小说作为一种叙事作品是有情节的,自然也就内含着一个叙事结构或称话语结构。
不同的叙事结构隐含着不同的意义,其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也就不一样。
迟桂花

郁达夫的早期代表作《沉沦》以强烈的感伤和抒情色彩著名,并因其带有作者自我经历的影子,被称作是“自叙传小说”。《迟桂花》创作于1932年,算是郁达夫的晚期作品,与《沉沦》相比,它的思想和艺术特点有了明显的改变。
作品的最大艺术特点是散文化的叙事风格和内敛却又强烈的感情色彩。郁达夫的作品一向不以情节复杂取胜,本篇也不例外。它的故事相当单纯,表达也如同生活本身一样的质朴自然,语言则体现出散文般的清新和流畅。最能吸引和感染读者的,是作者无处不在却又相当内敛的真挚感情。作品一开端,“郁先生”收到信,准备到翁家山去,就投射进很强的感情色彩,此后故事的发展,直到小说结束,都笼罩在主人公的情感氛围里。比较《沉沦》,《迟桂花》的感情表达显得相当舒缓柔和。它没有了青年人的峻急,呈现的是中年人的沉静和淡泊。正是这种情绪,使人不知不觉地被打动,被迷醉。
莲是作品最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她是一个农村青年妇女,美丽善良,性格率真,尽管遭受了生活的挫折,却依然保持着天真活泼的性格。正是她的美丽、沉静和乐观,给予了叙述者“郁先生”强烈的精神愉悦,使他被燃起的欲望得到净化,心灵也融化为澄静大自然中一部分。作品将莲的形象和迟桂花时时相映衬,又把她的性格气质放在翁家山的大自然世界中,仿佛她不只是一个具体的人,同时也成为了大自然美和宁静的化身,是一枝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迟桂花”。
作品的另一艺术特点是情和景巧妙的融合。作品的感情色彩并不是突兀而至,而是融合在美丽的山水风景中,自然地流淌出来。作品在写景方面用力甚勤,取得的效果也特别好。如作品写翁家山的景致,就分别从暮时、月下和清晨三个时辰来写,可以说是各具情趣,充分渲染出了山村的恬静和安宁。而且,作者在描绘大自然的种种景致时,并不是纯客观地描写,而是同时糅杂以人物真切的心理感受,将这种主观情绪投射在客观景物上,从而产生了特殊的艺术效果。如作品对最主要的象征景物——迟桂花的描写,就时时见出真情,使读者在阅读这些片段时,不知不觉地融入到了桂花香的世界中。
百看不厌 回味无穷——郁达夫《迟桂花》浅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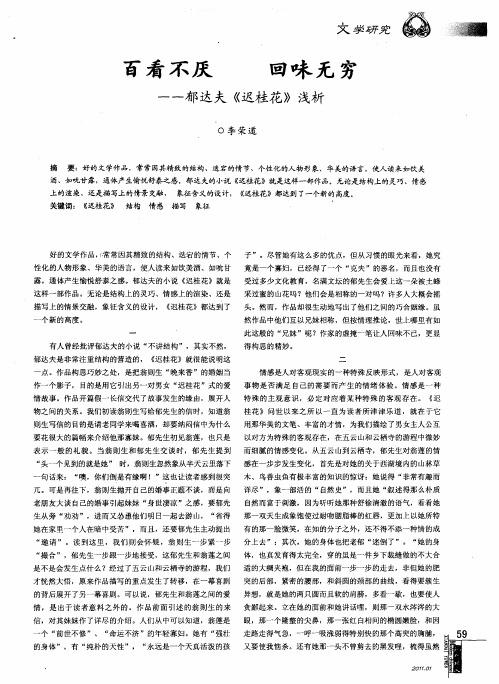
个新的高度。
然 作 品 中他 们 互 以兄妹 相 称 ,但 按 情 理推 论 ,世 上哪 里 有 如 此 这 般 的 “ 妹 ”呢 ?作 家 的虚 掩 一 笔让 人 回 味 不 已 ,更 显 兄
有人 曾经批评郁达夫的小说 “ 不讲 结构 ”,其实不然, 郁达夫是非常注重结构的营造的, 《 迟桂花》就很能说明这
信 ,对 其 妹 妹 作 了详 尽 的 介 绍 。人 们 从 中 可 以知 道 ,翁 莲 是 眼 ,那 一 个 隆 整 的尖 鼻 ,那 一 张 红 白相 问 的椭 圆嫩脸 ,和 因
一
个 “ 前世不修”、 “ 命运不济 ”的年轻寡妇 。她有 “ 强壮 走路走得气急,一呼一吸涨弱得特别快的那个高突的胸脯 ,
的 身体 ” ,有 “ 纯朴 的天 性 ” , “ 远是 一 个 天 真 活泼 的 孩 又要 使 我 恼 杀 。还 有 她 那一 头 不 曾剪 去 的 黑 发哩 ,梳得 虽 然 永
于是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草木 很多 的这深 山顶上,这也起 了一层 白茫茫的透 明
雾 障。一种空 山秋 夜的沉默的感觉 ,处 处在高压着人 ,使 人肃 然会起一种畏 敬之 思。 ”这 是月光下的翁家 山。除此 之外 ,作者还 写了屋前屋后 的翁 家山 以及翁家 山的清 晓和 翁家 山的早晨 。这些 自然景色 的描写,有颜色 、有光 线、
一
句话来 : “ 噢,你们倒是有缘啊 !”这也让读者感到很突 木、鸟兽虫鱼有极丰富的知识的惊 讶:她说得 “ 非常有趣而
详 尽 ” ,象 一 部 活 的 “ 自然 史 ” ,而 且她 “ 叙述 得 那 么 朴质
兀。可是再往下,翁则生抛开 自己的婚事正题不谈,而是 向 老朋友大谈 自己的婚事引起妹妹 “ 身世凄凉”之感,要郁先
迟桂花 郁达夫

3 Leabharlann 简繁地当的描写与处理1) 对莲的笑的描写,见P73P77P80P82. 2)为突出重点的省写了许多情节,如P82P83. 3)有些重点故意省写,有些细节却毫不放松. 如: (1)P83写手杖. (2)对迟桂花的反复描写.
4) P68-P69对莲身世的描写与P68-P69对莲哭的 描写对照. 5)质朴自然固是本文的优点,但, 它并不是凭直觉 写成,实际上还是结合着理性的思考的.
迟桂花
郁达夫
一 简介与简评
1 <迟桂花>是郁达夫于1932年创作地一部 短篇小说.反映了他后期小说创作在艺术上 的成熟程度. 2 <迟桂花>不仅传达出”人性返归自然” 及心灵净化的主旨,而且完成了从感伤美向 宁静美的转化,由直抒胸臆的方式向诗的意 境的营造的转化.
二
B 在自然景物的描写中,情景交融,构造出意境.
2 诗的结构 <迟桂花>着重以主人公的情感起伏发展为主 线组织篇章,贯穿全篇的或明或暗,或高或底,起 伏有致的情调构成了作品诗一般的抒情结构.
三 质朴自然的美学追求在文中的体现 1 P78写的自然优美的情韵. 2 P68P75写的天真自然的美好状态.
四
课后作业:
比较阅读<迟桂花>与<春风沉醉的晚上>, 思考二者郁翁兄妹与贫民窟青年男女的个 性与共性.
<迟桂花>的诗意美
1 诗化的人物 翁则生:内心安宁,新境平静,与世无争 “我”:遁世的隐逸倾向,向往田园山林 翁莲:健康纯朴,自然真率,散发着迟桂花的芳香 2 诗的意境 意境是一种主客观统一,物我无间的艺术境界. 构成<迟桂花>意境的两种方式: A 在对日常生活的抒写中,情与事水乳交融构造 出意境
迟桂花读书笔记摘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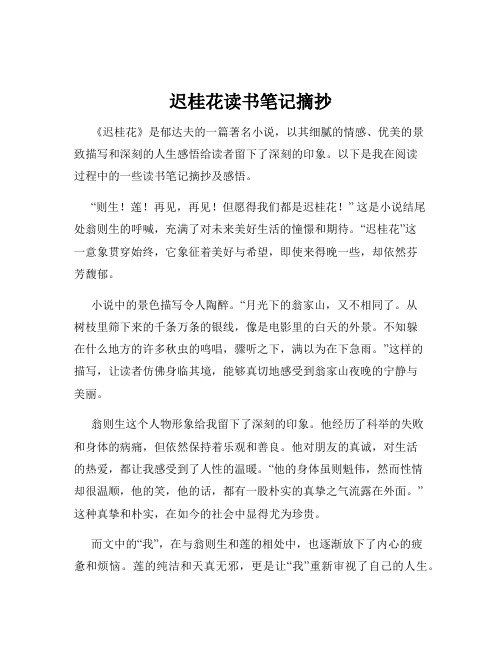
迟桂花读书笔记摘抄《迟桂花》是郁达夫的一篇著名小说,以其细腻的情感、优美的景致描写和深刻的人生感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下是我在阅读过程中的一些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
“则生!莲!再见,再见!但愿得我们都是迟桂花!” 这是小说结尾处翁则生的呼喊,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期待。
“迟桂花”这一意象贯穿始终,它象征着美好与希望,即使来得晚一些,却依然芬芳馥郁。
小说中的景色描写令人陶醉。
“月光下的翁家山,又不相同了。
从树枝里筛下来的千条万条的银线,像是电影里的白天的外景。
不知躲在什么地方的许多秋虫的鸣唱,骤听之下,满以为在下急雨。
”这样的描写,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翁家山夜晚的宁静与美丽。
翁则生这个人物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经历了科举的失败和身体的病痛,但依然保持着乐观和善良。
他对朋友的真诚,对生活的热爱,都让我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
“他的身体虽则魁伟,然而性情却很温顺,他的笑,他的话,都有一股朴实的真挚之气流露在外面。
”这种真挚和朴实,在如今的社会中显得尤为珍贵。
而文中的“我”,在与翁则生和莲的相处中,也逐渐放下了内心的疲惫和烦恼。
莲的纯洁和天真无邪,更是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人生。
“她的身体,也真发育得太完全,穿的虽是一件乡下裁缝做的不大合式的大绸夹袍,但在我的面前一步一步的走去,非但她的肥突的后部,紧密的腰部,和斜圆的胫部的曲线,看得要簇生异想,就是她的两只圆而且软的肩膊,多看一歇,也要使人贪鄙起来。
”这段对莲的描写,不仅展现了莲的青春美丽,也反映了“我”内心深处的波动。
文中对于亲情和友情的描绘也十分动人。
翁则生和他妹妹之间深厚的感情,以及“我”与翁则生之间多年不变的友谊,都让我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真挚情感的力量。
“桂花开得愈迟愈好,因为开得迟,所以经得日子久。
” 这句话富有哲理,让我明白,美好的事物不一定要急于一时,只要能够持久,晚一点到来又何妨?人生中的许多美好,或许都需要我们耐心等待,用心去感受。
郁达夫小说《迟桂花》解读

人间真情的呼唤——郁达夫小说《迟桂花》解读摘要:《迟桂花》是郁达夫后期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体现了与前期作品不同的思想情感。
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小说中主要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小说设置的叙事结构进行详细分析和解读,可以看出,小说主要表现的是作者在人生困境中对人间亲情和友情的真切呼唤。
关键词:现代文学;郁达夫;迟桂花;思想;解读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坛的著名作家,他开创了自叙传式的抒情体小说,在五四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以《沉沦》为代表的前期小说塑造了一系列“零余者”的形象,敢于毫无遮掩的暴露自我,“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
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
”[1]但30年代以后,进入中年的郁达夫,其小说无论是在风格上还是思想内容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迟桂花》就是这一时期的小说代表作之一,作者一改大胆的暴露,零余者形象的写法,在淳朴静美的境界中荡涤自己内心的躁动,发出了对人间真情的呼唤。
虽然《迟桂花》发表后的影响并没有《沉沦》等作品那样大,但却“是小说家融合心灵的体验、诗意的感悟和自由的想象而写成的一部抒情小说杰作。
”[2]其所具有的思想意蕴更为深厚,在艺术表现上也更为成熟。
要想把握小说丰厚的内在意蕴,就必须结合作品对主要人物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作品内在的叙事结构进行详细梳理和分析,通过文本细读我们自然就能感受到其内在的真意。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或隐或显地包含着作者的某种思想情感,对于小说而言,作者通常是不会站出来直接言说的,思想情感的表现比较隐蔽。
在小说中,作者的观点是通过小说的叙述者或小说中的人物来传达的。
换句话说,小说的叙述者或人物就是起到传达作者观点的功能的。
同时,小说作为一种叙事作品是有情节的,自然也就内含着一个叙事结构或称话语结构。
不同的叙事结构隐含着不同的意义,其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也就不一样。
郁达夫的《迟桂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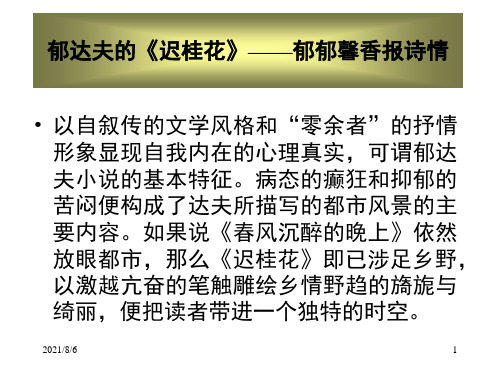
2021/8/6
8
郁达夫的《迟桂花》——郁郁馨香报诗情
• …她的眼里却无丝毫羞惧兴奋的痕迹出现,她的微笑,还依旧同平
时一点也没有什么笑容一样。看了我这一种奇怪的形状,她过了一 歇,反又自然的问我说:“你究竟在那里想什么?”
• ……
• “我……我在这儿想你!”
• “是在想我的将来如何的和他们同住么?”
2021/8/6
1
郁达夫的《迟桂花》——郁郁馨香报诗情
• 造境抒情,这是《迟桂花》迥异与郁达夫其他小 说的构思脉绪。翁家山即是《迟桂花》借以传情 达意的实境。
• 烟霞夕景:青葱的山黛,如云的树,掩映着一簇 屋瓦与白墙;最令人心弛神往、意绪翩然的是空 气中满含着的桂花清香;再加上晚钟锤击的幽幽 声浪,构成了一幅凄清、静穆的诗意情境。—— 有别于都市的喧嚣与嘈杂——走出喧嚣感受到自 然的温馨后留下的心灵的震动。
郁达夫的《迟桂花》——郁郁馨香报诗情
• 以自叙传的文学风格和“零余者”的抒情 形象显现自我内在的心理真实,可谓郁达 夫小说的基本特征。病态的癫狂和抑郁的 苦闷便构成了达夫所描写的都市风景的主 要内容。如果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依然 放眼都市,那么《迟桂花》即已涉足乡野, 以激越亢奋的笔触雕绘乡情野趋的旖旎与 绮丽,便把读者带进一个独特的时空。
丽自然,内在的玲珑剔透、静穆幽远,与迟桂花的馥郁芳香一起, 便从形与质上构成了这幅山水画的整体框架。其意境见出清空入禅 的绝妙,然而郁桂飘香又点化了意境的静穆,予人以清鲜的风采和 鲜活的生命气息。格调静美情境婉丽。在这里,再也体味不到咀嚼 未熟橄榄的苦涩,再也不见作者自身放荡而自卑、愤世又沉痛的心
理潜影。
2021/8/6
2
郁达夫的《迟桂花》——郁郁馨香报诗情
《迟桂花》的叙事艺术

浅谈《迟桂花》的叙事艺术摘要小说《迟桂花》是郁达夫后期的作品,小说以其清新、淡雅、意蕴悠远为读者所喜爱。
一部优秀的小说必然有高超的叙事艺术才能带给读者最美好的情感体验与审美愉悦,作者运用第一人称的视角综合多种叙事手法给读者持久绵长的情感冲击和意蕴回味。
关键词叙事技巧情感体验审美愉悦一部优秀的小说应该是通过巧妙的故事情节塑造具备鲜明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从而或反映一个时期的社会风貌或揭露一些社会现实,给读者以启迪或者是美的享受。
小说一开始用一封信交代了故事的背景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接着向我们讲述了老郁参加朋友婚礼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
一、篇章结构分析一部小说的篇章结构主要包括小说的叙述视角和情节的重心以及小说的叙事顺序。
小说以第一人称来叙述,当然第一人称在这中间发生了变化,由于小说以一封信开头,信中的“我”是翁则生,而到后来的“我”是老郁。
郁达夫是主张小说是作者自己的”自叙传”,并且郁达夫善于暴露人性中遭人非议的地方,所以选择第一人称是郁达夫的个人特点同时也便于作者的叙述,作品中流露的主观抒情性和散文化的结构以及个性化的自然风景描写都是作者运用第一人称叙事的结果。
第一人称写作的优势还在于它的真实和未知,作品中的“我”和现实中的读者永远不会知道故事会怎么发展,读者只有跟着“我”的主观情感去感受去猜测,这样就增强了小说的故事性和真实性。
虽然这篇小说的故事性并不是很强,但是读者可以跟随“我”一起做情感的审美体验。
整部作品中的“我”首先是受到远方朋友的邀请去参加婚礼,接着是在去朋友家的路上感受美好的自然风光,在到了朋友家与久别的老友重逢叙旧并且收到了十分热情地招待,还有天真灿漫的翁莲相陪一起游玩五云山,不得不说读者跟随“我”进行了一次愉快浪漫的经历。
作品中的两个“我”非同一个人,但是作者的转换却非常自然流畅。
作者以一封信作为开头不露痕迹的交代了故事的背景和人物关系,接着作者说明是“我”收到朋友的来信,作者在这部分运用了倒序的手法(看信的内容很显然是在收到信之后的行为)。
缘情赋形 意境幽远——郁达夫《迟桂花》浅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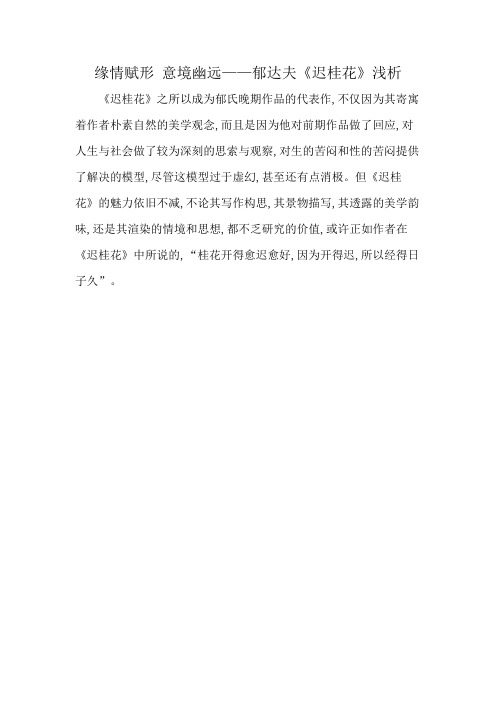
缘情赋形意境幽远——郁达夫《迟桂花》浅析
《迟桂花》之所以成为郁氏晚期作品的代表作,不仅因为其寄寓着作者朴素自然的美学观念,而且是因为他对前期作品做了回应,对人生与社会做了较为深刻的思索与观察,对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提供了解决的模型,尽管这模型过于虚幻,甚至还有点消极。
但《迟桂花》的魅力依旧不减,不论其写作构思,其景物描写,其透露的美学韵味,还是其渲染的情境和思想,都不乏研究的价值,或许正如作者在《迟桂花》中所说的,“桂花开得愈迟愈好,因为开得迟,所以经得日子久”。
论郁达夫《迟桂花》的美学意蕴

论郁达夫《迟桂花》的美学意蕴1.引言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之一,他的作品《迟桂花》被誉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迟桂花》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意义,吸引了无数读者的注目,是一篇值得深入研究的优秀作品。
本文旨在通过对《迟桂花》的分析,探讨其美学意蕴,旨在帮助读者深入了解这篇杰出的文学作品。
2.文学形式上的美学意蕴《迟桂花》是一篇充满了语言美的散文,它充分利用了汉语语言的多元性和表现力,使得作品在形式上呈现出了极大的美学价值。
首先,文章的语言优美流畅,从语言结构到句式运用都非常精妙。
例如文章开头的一段:夜静若水。
这一句中的“静”、“若”、“水”等词汇都是非常典雅的,通过一个简洁的描写,让人产生强烈的美感。
其次,《迟桂花》在描写上也非常独特。
作者通过借景抒情的手法,将一个美丽的桂花的故事融入到一段人物事迹中,达到了表现感情的目的。
例如一段描写:桂花,从来都是它,也只有它最美。
它那又香又娇艳的芳姿,几乎没有人不爱。
迟桂花比普通桂花更加美丽,但它需要很长时间的候,才能在人们的世界里盛放。
这个描写自然流畅,不刻意张扬,但有强烈的感染力。
阐发了作者对迟桂花的深情厚意。
3.哲学意蕴的美学意蕴《迟桂花》除了在形式上具有美学意蕴外,在哲学上也充满了美学意义。
文章的核心思想是“不急不暴不狂”,作者通篇倡导的是一种谦虚、平和的处世哲学。
文章中提到的“迟桂花”,就给了人们一个非常好的象征:它是一种不着急的生命方式,虽然时间很长,但一定会盛开,并留下永恒的美好。
作者在《迟桂花》中的哲学思想,也激发了读者对人生哲学的感悟。
在生活中,人们应该像迟桂花一样,不要急躁,要耐心等待,只有这样,才能欣赏到生活的美好。
4.文化意蕴的美学意蕴《迟桂花》是一篇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的散文,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文章中的文化元素丰富,既有桂花这一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也有儒家思想对作者写作的影响。
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作者在描写桂花时也特别注重“君子之交淡如水”这一词的象征意义,让读者理解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的理念:就是要淡然处之,明白自己的位置,遵循自己的道德准则。
关于《迟桂花》的解读

关于《迟桂花》的解读春节假期,大凡上班族较平时都有了充裕的时间,恰逢是岁“过年”又踩上六九的尾巴,气温日渐趋暖,笔者心里也就油然萌生出读书、写作的莫名冲动。
郁达夫先生的短篇小说集非常有名,一直在我的读书、写作计划中,今日有闲,笔者欣欣然捧读起了小说《迟桂花》。
《迟桂花》以翁则生写给同窗好友老郁的一封情真意切长信开启,一信一章,在区区数章的短篇小说中实属罕见。
信中回顾了两人在东京留学时点点滴滴的美好往事,以及翁则生归国后自己及寡居妹妹翁莲近年的境遇状况。
通篇书信文笔优美,文风简练,让人读之如痴如醉,同时翁则生还在信中向老郁发出了参加其婚礼的邀约。
老郁收到信后感慨万千,次日便前往翁家山与老同学相聚,其间一并见到了新寡而被迫回娘家的翁莲。
细心敏锐的哥哥,生怕自己结婚,给妹妹造成触景生情的伤害,便请求老郁陪翁莲到五云山游玩。
老郁在陪翁莲爬山时,一度因痴迷其举止、体态而陷入了对翁莲的幻想中,以致产生丝丝邪念,不过老郁终究在山光水色洗礼下,被翁莲纯朴直率的天性所唤醒,改弦更张,升华了自己的思想,净化了自己的灵魂。
《迟桂花》大量釆用内心独白式手法,有效切换运用抒情与描写,构成了错落有致,感情真挚的绝佳文韵;景物描写清新舒适,人物刻画旖旎绝伦,二者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情节更如行云流水般,情景交融,形成了人物为景而生,反之景又掩映人物的鲜有笔触,尤其值得一提是,书中山中庙、云中雾的铺陈表现,更是美轮美奂,美不胜收。
郁达夫先生的作品惯以第一人称“我”来入笔,《迟桂花》第一章“我”为翁则生,余后又为老郁。
此种手法,笔者肤浅觉得读起来很容易让人产生代入感,能激发起读者浓厚的兴趣,产生迫切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的强烈念头;另一层意义所在,更是营造出了小说中呈现两位叙述者声音的别样氛围,不是回声,犹胜回声,在字里行间行文处游走运旋,浑然一体。
小说通篇,对其它事物并没有过多着墨,而是向我们展示了一位淳朴自然,儿童般活泼天真,又极具原始美的女性形象。
《迟桂花》赏析

《迟桂花》赏析读罢,被文章中的莲儿的单纯感动,也被作者对莲儿的单纯的喜欢的感情所感动。
在这样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人都变得复杂,感情也变得虚假。
我们很难分辨孰真孰假,也很难被感动。
说到文章中的这样的经历更是稀罕。
文章题为迟桂花,迟桂花在文中多次出现,是这篇文章的线索,也是意象。
迟桂花代表着莲儿,迟开的桂花,就像她28岁的姑娘,愈发芬芳和迷人。
她的天真和单纯也像极了迟桂花的清新,令人喜欢、陶醉和惊讶。
莲儿是害羞的,文中多次提到她脸红。
初次见面时,“脸上却涨起了一层红晕”,问了一句话后,“她脸上又红了一红”,当哥哥问她,和郁先生相比哪个年龄大时,“面色又涨红了”,她喊作者大哥,听到应声后,“涨红了脸”。
莲儿是美丽的,不是柔弱的女性的那种美,而是山里姑娘的健康的壮实的美。
“身体强健,两颊微红”“红红的双颊,挺突的胸脯,和肥圆的肩臂”“她那一双天生成像饱使过耐吻胭脂棒般的红唇”“肥突的后部,紧密的腰部,和斜圆的胫部曲线”“两只圆而且软的肩膊”“一双水汪汪的大眼,那一个隆正的尖鼻,那一张红白相间的椭圆的嫩脸”“一头不曾剪去的黑发”都表现出莲儿康健自然纯朴的美。
文中则生形容迟桂花“因为开得迟,所以日子经得久”,后来在婚礼上作者把这话用来祝福这对新人,愿他们像迟开的桂花长长久久,还开玩笑说“大约明年来的时候,在这两株迟桂花中间,总已经有一株早桂花发出来了”。
表达了美好的祝愿。
迟桂花代表着一种沉静自得的安然之美,也体现为一种顽强生命的意志力。
作者对“迟桂花”的歌颂,着意于对人、对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品格的歌颂。
文中翁家的人,从年迈的母亲到好友和他妹妹,都是平和安分勤劳的人,正是迟桂花的精神所在。
这篇文章的故事情节很简单,就是讲述了“我”应当年同窗好友翁则生之邀去参见他的婚礼,并同其妹翁莲同游五云山这一过程,文章的感人之处在于其中细腻的情感。
文风清淡,笔墨轻松,表达出来的感情却是内敛而强烈的。
文中有亲情,老母对儿子的爱,哥哥对妹妹的关爱。
浅析郁达夫小说《迟桂花》中的迟桂意象

浅析郁达夫小说《迟桂花》中的迟桂意象浅析《迟桂花》中的迟桂意象摘要:《迟桂花》是郁达夫其后期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与其前期作品相比体现出了不同的艺术风格。
小说主要表现的是作者在人生困境中对人间亲情和友情的真切呼唤,就像它的题目一样,显得芬芳馥郁。
小说中多次写到桂花,表现了老郁和翁则生、翁莲的友情就如那迟开的桂花,馥郁持久,同时,也寓意着一种自然美好的生活境界。
迟桂花开得迟,因而开放时间更持久,香味更芬芳。
迟桂花具有清香、朴素、耐久的品性。
以此看出,迟桂花是富于多层意境的,有自然之桂、人物之桂、人生之桂。
关键词:郁达夫迟桂花意象郁达夫是我国著名的现代作家、诗人,他热情敏感,小说充满着诗情画意。
《迟桂花》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
文中的翁则莲就如一株迟桂花,开放在翁家山大自然的世界中,以她独特顽强的性格展现出非一般的自然之美,不时散发出一阵阵沁人心脾的清香。
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作者将感情揉进了桂花中,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愿望融进大自然。
所以在作品中,迟桂花既代表着一种沉静自得的安然之美,也体现为一种顽强生命的意志力。
本文将试从自然之桂、人物之桂和人生之桂对《迟桂花》进行解读。
一、自然之桂自然是指具有无穷多样性的一切存在物,非人为的或不做作,不拘束,不呆板,非勉强的特性。
迟桂花的特点是耐寒,花香浓,持续时间长。
作者在小说中用了很多笔墨来描述他对迟桂花的喜爱之情。
在正文的开始,作者首先接触到的就是翁家山的迟桂花。
老郁接受好友翁则生的邀请,前往翁则生家。
在路上,途经烟霞洞时,远远就闻到迟桂花的“说不出的撩人的桂花香气[1]”。
“我看见了东天的已经满过半弓的月亮,心里正在羡慕翁则生她们老家的处地深幽,而从背后又吹来了一阵微风,里面竟含满着一种说不出的撩人的桂花香气。
[2]”“原来这儿到这时候还有桂花?[3]”寥寥数笔,不仅写出了迟桂花的幽香,还勾勒出了迟桂花生长环境的僻静、清幽。
环境的僻静,承载着作者内心的细腻,对自然的观感,以及对朋友生活的关怀。
郁达夫《迟桂花》阅读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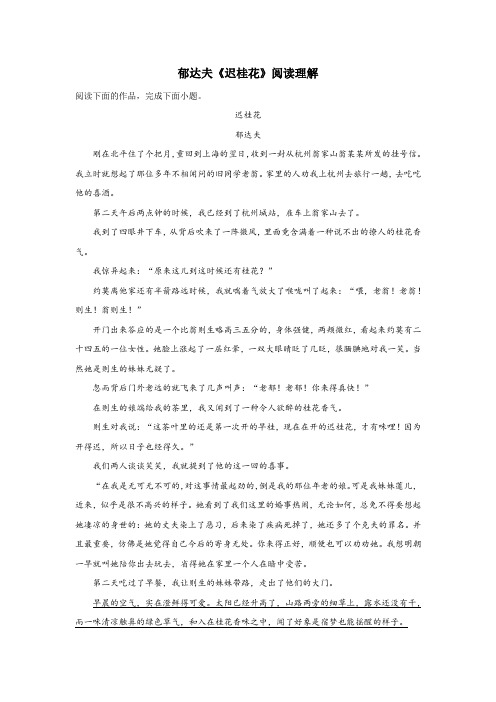
郁达夫《迟桂花》阅读理解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下面小题。
迟桂花郁达夫刚在北平住了个把月,重回到上海的翌日,收到一封从杭州翁家山翁某某所发的挂号信。
我立时就想起了那位多年不相闻问的旧同学老翁。
家里的人劝我上杭州去旅行一趟,去吃吃他的喜酒。
第二天午后两点钟的时候,我已经到了杭州城站,雇车上翁家山去了。
我到了四眼井下车,从背后吹来了一阵微风,里面竟含满着一种说不出的撩人的桂花香气。
我惊异起来:“原来这儿到这时候还有桂花?”约莫离他家还有半箭路远时候,我就喘着气放大了喉咙叫了起来:“喂,老翁!老翁!则生!翁则生!”开门出来答应的是一个比翁则生略高三五分的,身体强健,两颊微红,看起来约莫有二十四五的一位女性。
她脸上涨起了一层红晕,一双大眼睛眨了几眨,很腼腆地对我一笑。
当然她是则生的妹妹无疑了。
忽而背后门外老远的就飞来了几声叫声:“老郁!老郁!你来得真快!”在则生的娘端给我的茶里,我又闻到了一种令人欲醉的桂花香气。
则生对我说:“这茶叶里的还是第一次开的早桂,现在在开的迟桂花,才有味哩!因为开得迟,所以日子也经得久。
”我们两人谈谈笑笑,我就提到了他的这一回的喜事。
“在我是无可无不可的,对这事情最起劲的,倒是我的那位年老的娘。
可是我妹妹莲儿,近来,似乎是很不高兴的样子。
她看到了我们这里的婚事热闹,无论如何,总免不得要想起她凄凉的身世的:她的丈夫染上了恶习,后来染了疾病死掉了,她还多了个克夫的罪名。
并且最重要,仿佛是她觉得自己今后的寄身无处。
你来得正好,顺便也可以劝劝她。
我想明朝一早就叫她陪你出去玩去,省得她在家里一个人在暗中受苦。
第二天吃过了早餐,我让则生的妹妹带路,走出了他们的大门。
早晨的空气,实在澄鲜得可爱。
太阳已经升高了,山路两旁的细草上,露水还没有干,而一味清凉触鼻的绿色草气,和入在桂花香味之中,闻了好象是宿梦也能摇醒的样子。
因为今天有一天的时间,可以供我们消磨,所以我就走得特别的慢。
这里看看,那里看看的看个不住。
桂花开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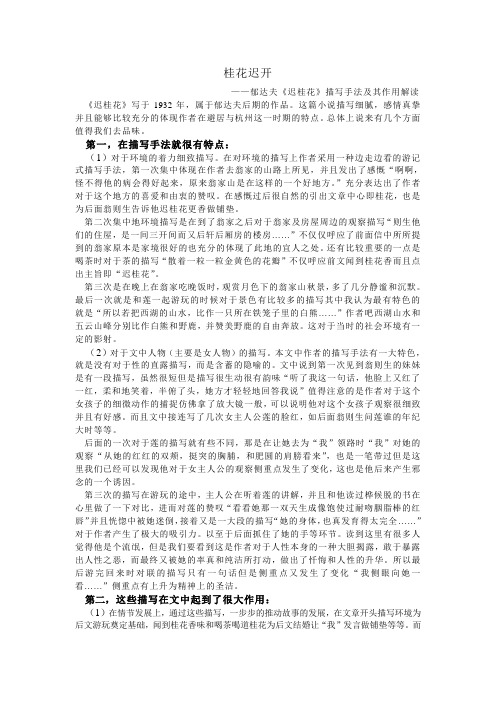
桂花迟开——郁达夫《迟桂花》描写手法及其作用解读《迟桂花》写于1932年,属于郁达夫后期的作品。
这篇小说描写细腻,感情真挚并且能够比较充分的体现作者在避居与杭州这一时期的特点。
总体上说来有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去品味。
第一,在描写手法就很有特点:(1)对于环境的着力细致描写。
在对环境的描写上作者采用一种边走边看的游记式描写手法,第一次集中体现在作者去翁家的山路上所见,并且发出了感慨“啊啊,怪不得他的病会得好起来,原来翁家山是在这样的一个好地方。
”充分表达出了作者对于这个地方的喜爱和由衷的赞叹。
在感慨过后很自然的引出文章中心即桂花,也是为后面翁则生告诉他迟桂花更香做铺垫。
第二次集中地环境描写是在到了翁家之后对于翁家及房屋周边的观察描写“则生他们的住屋,是一间三开间而又后轩后厢房的楼房……”不仅仅呼应了前面信中所所提到的翁家原本是家境很好的也充分的体现了此地的宜人之处。
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喝茶时对于茶的描写“散着一粒一粒金黄色的花瓣”不仅呼应前文闻到桂花香而且点出主旨即“迟桂花”。
第三次是在晚上在翁家吃晚饭时,观赏月色下的翁家山秋景,多了几分静谧和沉默。
最后一次就是和莲一起游玩的时候对于景色有比较多的描写其中我认为最有特色的就是“所以若把西湖的山水,比作一只所在铁笼子里的白熊……”作者吧西湖山水和五云山峰分别比作白熊和野鹿,并赞美野鹿的自由奔放。
这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一定的影射。
(2)对于文中人物(主要是女人物)的描写。
本文中作者的描写手法有一大特色,就是没有对于性的直露描写,而是含蓄的隐喻的。
文中说到第一次见到翁则生的妹妹是有一段描写,虽然很短但是描写很生动很有韵味“听了我这一句话,他脸上又红了一红,柔和地笑着,半俯了头,她方才轻轻地回答我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于这个女孩子的细微动作的捕捉仿佛拿了放大镜一般,可以说明他对这个女孩子观察很细致并且有好感。
而且文中接连写了几次女主人公莲的脸红,如后面翁则生问莲谁的年纪大时等等。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迟桂花】××兄: 突然间接着我这一封信,你或者会惊异起来,或者你简直会想不出这发信的翁某是什么人。
但仔细一想,你也不在做官,而你的境遇,也未见得比我的好几多倍,所以将我忘了的这一回事,或者是还不至于的。
因为这除非是要贵人或境遇很好的人才做得出来的事情。
前两礼拜为了采办结婚的衣服家具之类,才下山去。
有好久不上城里去了,偶尔去城里一看,真是象丁令威的化鹤归来,触眼新奇,宛如隔世重生的人。
在一家书铺门口走过,一抬头就看见了几册关于你的传记评论之类的书。
再踏进去一问,才知道你的著作竟积成了八九册之多了。
将所有的你的和关于你的书全买将回来一读,仿佛是又接见了十余年不见的你那副音容笑语的样子。
我忍不住了,一遍两遍的尽在翻读,愈读愈想和你通一次信,见一次面。
但因这许多年数的不看报,不识世务,不亲笔砚的缘故,终于下了好几次决心。
而仍不敢把这心愿来实现。
现在好了,关于我的一切结婚的事情的准备,也已经料理到了十之七八,而我那年老的娘,又在打算着于明天一侵早就进城去,早就上床去躺下了。
我那可怜的寡妹,也因为白天操劳过了度,这时候似乎也已经坠入了梦乡,所以我可以静静儿的来练这久未写作的笔,实现我这已经怀念了有半个多月的心愿了。
提笔写将下来,到了这里,我真不知将如何的从头写起。
和你相别以后,不通闻问的年数,隔得这么的多,读了你的著作以后,心里头触起的感觉情绪,又这么的复杂;现在当这一刻的中间,汹涌盘旋在我脑里想和你谈谈的话,的确,不止象一部二十四史那么的繁而且乱,简直是同将要爆发的火山内层那么的热而且烈,急遽寻不出一个头来。
我们自从房州海岸别来,到现在总也约莫有十多年光景了吧!我还记得那一天晴冬的早晨,你一个人立在寒风里送我上车回东京去的情形。
你那篇《南迁》的主人公,写的是不是我?我自从那一年后,竟为这胸腔的恶病所压倒,与你再见一次面和通一封信的机会也没有,就此回国了。
学校当然是中途退了学,连生存的希望都没有了的时候,哪里还顾得将来的立身处世?哪里还顾得身外的学艺修能?到这时候为止的我的少年豪气,我的绝大雄心,是你所晓得的。
同级同乡的同学,只有你和我往来得最亲密。
在同一公寓里同住得最长久的,也只有你一个人;时常劝我少用些功,多保养身体,预备将来为国家为人类致大用的,也就是你。
每于风和日朗的晴天,拉我上多摩川上井之头公园及武藏野等近郊去散步闲游的,除你以外,更没有别的人了。
那几年高等学校时代的愉快的生活,我现在只教一闭上眼,还历历透视得出来。
看了你的许多初期的作品,这记忆更加新鲜了。
我的所以愈读你的作品,愈想和你通一次信者,原因也就在这些过去的往事的追怀。
这些都是你和我两人所共有的过去,我写也没有写得你那么好,就是不写你总也还记得的,所以我不想再说。
我打算详详细细向你来作一个报告的,就是从那年冬天回故乡以后的十几年光景的山居养病的生活情形。
那一年冬天咯了血,和你一道上房州去避寒,在不意之中,又遇见了那个肺病少女——是真砂子罢?连她的名字我都忘了——无端惹起了那一场害人害己的恋爱事件。
你送我回东京之后,住了一个多礼拜,我就回国来了。
我们的老家在离城市有二十来里地的翁家山上,你是晓得的。
回家住下,我自己对我的病,倒也没什么惊奇骇异的地方,可是我痰里的血丝,脸上苍白的,和身体的瘦削,却把我那已经守了好几年寡的老母急坏了,因为我那短命的父亲,也是患这同样的病而死去的。
于是她就四处的去求神拜佛,采药求医,急得连粗茶淡饭都无心食用,头上的白发,也似乎一天一天的加多起来了。
我哩!恋爱已经失败了,学业也已辍了,对于此生,原已没有多大的野心,所以就落得去由她摆布,积极地虽尽不得孝,便消极地尽了我的顺。
初回家的一年中间,我简直门外也不出一步,各色各样的奇形的草药和各色各样的异味的单方,差不多都尝了一个遍。
但是怪得很,连我自己都满以为没有希望的这致命的病症,一到了回国后经过的第二个夏天,竟似乎有神助似地忽然减轻了,夜热也不再发,盗汗也居然止住,痰里的血丝早就没有了。
我的娘的喜欢,当然是不必说,就是在家里替我煮药缝衣,代我操作一切的我那位妹妹,也同春天的天气一样,时时展开了她的愁眉,露出了她那副特有的真真是讨人欢喜的笑容。
到了初夏,我药也已经不服,有兴致的时候,居然也能够和她们一道上山前山后去采采茶,摘摘菜,帮她们去服一点小小的劳役了。
是在这一年的——回家后第三年的——秋天,在我们家里,同时候发生了两件似喜而又可悲,说悲却也可喜的悲喜剧。
第一,就是我那妹妹的出嫁,第二,就是我定在城里的那家婚约的解除。
妹妹那年十九岁了,男家是只隔一支山岭的一家乡下的富家。
他们来说亲的时候,原是因为我们祖上是世代读书的,总算是来和诗礼人来攀婚的意思。
定亲已经定过了四五年了,起初我娘却嫌妹年纪太小,不肯马上准他们来迎娶,后来就因为我的病,一搁就又搁起了两三年。
到了这一回,我的病总算已经恢复,而妹妹却早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
男家来一说,我娘也就应允了他们。
也算完了她自己的一件心事。
至于我的这家亲事呢,却是我父亲在死的前一年为我定下的,女家是城里的一家相当有名的旧家。
那时候我的年纪虽还很小,而我们家里的不动产却着实还有一点可观。
并且我又是一个女子,将来家里要培植我读书处世是无疑的,所以那一家旧家居然也应允了我的婚事。
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门亲事,当然是我们去竭力高攀的,因为杭州人家的习俗,是吃粥的人家的女儿,非要去嫁吃饭的人家不可的。
还有乡下姑姑,嫁往城里,倒是常事,城里的千金小姐,却不大会下嫁到乡下来的,所以当时的这个婚约,起初在根本上就有点儿不对。
后来经我父亲的一死,我们家里,丧葬费用,就用去不少。
嗣后年复一年,母子三人,只吃着家里的死饭。
亲族戚属,少不得又要对我们孤儿寡妇,时时加以一点剥削。
母亲又忠厚无用,在出卖田地山场的时候,也不晓得市价的的高低,大抵是任凭族人在勾搭。
就因这种种关系的结果,到我考取了官费,上日本去留学的那一年,我们这一家世代读书的翁家山上的旧家,已经只剩得一点仅能维护衣食的住屋山场和几块荒田了。
当我初次出国的时候,承蒙他们不弃,我那未来的亲家,还送了我些赆仪路费。
后来由于寒假暑假回国的期间,也曾央原媒来催过完姻。
可是接着就是我那致命的病症的发生,与我的学业的中辍,于是两三年中,他们和我们的中间,便自然而然的断绝了交往。
到了这一年的晚秋,当我那妹妹嫁后不久的时候,女家忽而又央了原媒来对母亲说:“你们的大少爷,有病在身,婚娶的事情,当然是不大相宜的,而他家的小姐,也已经下了绝大的决心,立志终身不嫁了,所以这一个婚约,还是解除了的好。
”说着就打开包裹,将我们传红时候交去的金玉如意,红绿帖子等,拿了出来,退还了母亲。
我那忠厚老实的娘,人虽则无用,但面子却是死要的,一听了媒人的这一番说话,目瞪口僵,立时就滚下几颗眼泪来。
幸亏我在旁边,做好做歹的对娘劝慰了好久,她才含着眼泪,将女家的回礼及八字全帖等检出,交还了原媒。
媒人去后,她又上山后我父亲的坟边去大哭一场。
直到傍晚,我和同族邻人等一道去拉她回来,她在路上,还流着满脸的眼泪鼻涕,在很伤心地呜咽。
这一出赖婚的怪剧,在我只有高兴,本来是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由头脑很旧的她看来,却似乎是翁家世代的颜面家声都被他们剥尽了。
自此以后,一直下来,将近十年,我和她母子二人,就日日的寡言少笑,相对茕茕,直到前年的冬天,我那妹夫死去,寡妹回来为止,两人所过的,都是些在炼狱里似的沉闷的日子。
说起我那寡妹,她真也是前世不修。
人虽则很长大,身体虽则很强壮,但她的天性,却永远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孩子。
嫁过去那一年,来回郎的时候,她还是笑嘻嘻地如同上城里去了一趟回来了的样子,但双满月之后,到年下边回来的时候,从来不晓得悲泣的她,竟对我母亲掉起眼泪来了。
她们夫家的公公虽则还好,但婆婆的繁言吝啬,小姑的刻薄尖酸和男人的放荡凶暴,使她一天到晚不到一刻安闲自在的生活。
工作操劳本系是她在家里的时候所惯习的,倒并不以为苦,所最难受的,却是多用一枝火柴,也要受婆婆责备的那一种俭约到不可思议的生活状态。
还有两位小姑,左一句尖话,右一句毒语,仿佛从前我娘的不准他们早来迎娶,致使她们的哥哥染上游荡的恶习,在外面养起了女人这一件事情,完全是妹妹的罪恶。
结婚之后,新郎的恶习,仍旧改不过来,反而是在城里他那旧情人家里过的日子多,在新房里过的日子少。
这一笔帐,当然又要写在我妹妹的身上。
婆婆说她不会侍奉男人,小姑们说她不会劝,不会骗。
有时候公公看得难受,替她申辩一声,婆婆就尖着喉咙,要骂上公公的脸去;“你这老东西!脸要不要,脸要不要,你这扒灰老!”因为那妹夫,过的是这一种不自然的生活,所以前年夏天,就染了急病死掉了,于是我那妹妹又多了个克夫的罪名。
妹妹年轻守寡,公公少不得总要对她客气一点,婆婆在这里就算抓住了扒灰的证据,三日一场吵,五日一场闹,还是小事,有几次在半夜里,两老夫妇还会大哭大骂的喧闹起来。
我妹妹于有一回被骂被逼得特别厉害的争吵之后,就很坚决地搬回到了家里来住了。
自从她回来之后,我的娘非但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帮手,就是我们家里的沉闷的空气,也缓和了许多。
这就是和你别后,十几年来,我在家里所过的生活的大概。
平时非但不上城里去走走,当风雪盈途的冬季,我和我娘简直有好几个月不出门外的时候。
我妹妹回来之后,生活又约略变过了。
多年不做的焙茶事业,去年也竟出产了一二百斤。
我的身体,经了十几年的静养,似乎也有一点把握了。
从今年起,我并且在山上的晏公祠里参加入了一个训蒙的小学,居然也做了一位小学教师。
但人生是动不得的,稍稍一动,就如滚石下山,变化便要接连不断的簇生出来。
我因为在教教书,而家里头又勉强地干起了一点事业,今年夏季居然又有人来同我议婚了。
新娘是近邻乡村里的一位老处女,今年二十七岁,家里虽称不得富有,可也是小康之家。
这位新娘,因为从小就读了些书,曾在城里进过学堂,相貌也还过得去——好几年前,我曾经在一处市场上看见过她一眼的——故而高不凑,低不就,等闲便度过了她的锦样的青春。
我在教书的学校里的那位名誉校长——也是我们的同族——本来和她是旧亲,所以这位校长就在中间做了个传红线的冰人。
我独居已经惯了,并且身体也不见得分外强健,若一结婚,难保得旧病的不会复发,故而对这门亲事,当初是断然拒绝了的。
可是我那年老的母亲,却仍是雄心未死,还在想我结一头亲,生下几个玉树芝兰来,好重振重振我们的这已经坠落了很久的家声,于是这亲事又同当年生病的时候服草药一样,勉强地被压上我的身上来了。
我哩,本来也已经入了中年了,百事原都看得很穿,又加以这十几年的疏散和无为,觉得在这世上任你什么也没甚大不了的事情,落得随随便便的过去,横竖是来日也无多了。
只教我母亲喜欢的话,那就是我稍稍牺牲一点意见也使得。
于是这婚议,就在很短的时间里,成熟得妥妥贴贴,现在连迎娶的日期也已经拣好了,是旧年九月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