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汉家寨原文及教案
《汉家寨》教案 (人教版高一选修)共3篇

《汉家寨》教案 (人教版高一选修)共3篇《汉家寨》教案 (人教版高一选修)1《汉家寨》教案 (人教版高一选修)一、教材分析人教版高一选修课程中的《汉家寨》是一篇由龙应台所写的散文,通过讲述作者在回到祖籍——重庆的过程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将一幅中国山村的风情展现在读者面前。
文章巧妙地运用语言艺术手法,既形象地揭示了中国乡村的生活现状,也表达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二、教学目标1.了解中国山村的自然地理环境,并能通过图片、地图等形式理解山区的发展状况。
2.理解并掌握散文的写作技巧及文学作品的语言魅力,提高语感和写作素养。
3.在理解文章的内容的基础上,学生了解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历程,树立爱国主义情感。
4.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思考、讨论和创新探究,提高综合能力。
三、教学内容及设计1.导入通过放映图片、介绍地理环境和当地发展现状,在学生的认知上打下基础与简单了解,激发学生的兴趣。
在导入环节中,可以让学生自己说说对于“山区人民”的印象,激起他们对于所学内容的兴趣与思考。
2.教学重点重点讲解文章的结构,表达技巧和语言风格,使学生能够理解并感受到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
3.教学难点让学生从固有的思维模式中摆脱出来,通过全面了解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社会经济现状,以全新的视角和思想探究中国乡村现状和文化传承问题。
4.讲解与讨论带领学生字词语义研究,探究写作技巧和意义。
重点讲述为什么文章采取叙事的手法来表达作者的思想。
结合文中的语言,引导学生分析文章中的内容,加深对于乡村的认识。
5.归纳总结对已有的内容进行复述,加深学生对于散文语言与内容的印象,整合学生的知识结构。
四、教学方式1.情境模拟通过模拟当地的生活场景与文化环境,帮助学生感知文章中的人文环境,并加强学生的语感与文学修养。
2.分组讨论分组讨论的方式,让每一个小组针对不同的策略,结合所学知识和个人素养,加深对于文章内容和意义的理解。
3.自主研究让学生自己进行阅读和研究,让学生在研究中体会、继承和发展中国民族文化的内涵。
《汉家寨》公开课教案

《汉家寨》
授课人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品味庄重、冷峻的语言风格,理解文章内容
过程与方法
学会阅读,通过阅读体会作者寄托的情感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领悟作者颂扬的“坚守”精神,思考“坚守”的现实意义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探讨、来自解“坚守”精神的意义,挖掘作品丰富的内涵
教学难点
联系作者自身际遇与写作背景体会作品深层意蕴
教
学
过
程
一、初读课文
(1)划一划:收集有关汉家寨的信息(如地理位置、居民、历史、环境等)。
(2)圈一圈:作者在旅途中的感受。
二、再读课文
(1)在如此一处绝地中作者见到了谁?他们有什么特点?
(2)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居然还有人居住,作者的感受又是怎样的?在文中划出。
(3)你认为他们在坚守什么?
三、深入阅读
(1)作者介绍
(2)联系作者背景,回味揣摩语句,你是否能够理解作者的“坚守”情怀?
四、拓展阅读
韩东《山民》
思考:为什么写作题材基本一致,作者的角度和观点却大不相同呢?
五、结束语
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汉家寨》的“坚守”精神有什么现实意义?
板书设计
汉家寨
张承志
地理意义上:绝地
文学意义上:坚守
《汉家寨》教案
2024年《汉家寨》教案(教师中心稿)教案教学设计

2024年《汉家寨》教案(教师中心稿)教案教学设计1.1 设计意图1.1.1 通过引入《汉家寨》这篇课文,激发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兴趣,培养他们的文学素养。
1.1.2 引导学生了解课文背景,为后续的学习打下基础。
1.1.3 营造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使学生在轻松中学习,提高学习效果。
二、知识点讲解2.1 课文内容分析2.1.1 概括课文主要内容,帮助学生理清思路。
2.1.2 分析课文主题,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作品。
2.1.3 讲解重点词语和句式,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三、教学内容3.1 课文朗读与理解3.1.1 组织学生朗读课文,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3.1.2 引导学生概括段落大意,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
3.1.3 分析课文中的修辞手法,提升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
四、教学目标4.1 知识与技能目标4.1.1 学生能够理解课文内容,掌握相关知识点。
4.1.2 学生能够流利朗读课文,提高阅读能力。
4.1.3 学生能够运用课文中的词语和句式进行表达。
五、教学难点与重点5.1 教学难点5.1.1 课文中的生僻词语和句式的理解与运用。
5.1.2 课文中蕴含的深层次含义的把握。
5.1.3 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鉴赏能力的培养。
5.2 教学重点5.2.1 学生能够理解并掌握课文内容。
5.2.2 学生能够运用课文中的知识点进行表达。
5.2.3 学生能够提高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鉴赏能力。
六、教具与学具准备6.1 教具准备6.1.1 教学PPT,包含课文内容、知识点讲解、教学过程等。
6.1.2 课文原文,方便学生查阅和朗读。
6.1.3 相关文学作品的资料,用于拓展学生的视野。
6.2 学具准备6.2.1 笔记本,用于学生记录知识点和课堂笔记。
6.2.2 笔,用于学生做笔记和回答问题。
6.2.3 课文原文,方便学生阅读和理解。
七、教学过程7.1 课堂导入7.1.1 教师通过引入相关话题,激发学生的兴趣。
7.1.2 学生分享他们对相关话题的了解和看法。
2024年《汉家寨》教案(教师中心稿)教案教学设计

2024年《汉家寨》教案(教师中心稿)教学设计一、教学目标1. 知识与技能:(1)让学生掌握《汉家寨》的基本情节、人物关系和文学特点。
(2)培养学生分析、评价文学作品的能力。
(3)提高学生对汉语语言表达的掌握程度。
2. 过程与方法:(1)通过自主学习、合作探讨的方式,深入理解课文内容。
(2)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探讨作品的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
(3)培养学生阅读名著的兴趣和习惯。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1)感受作品中所表现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
(2)领悟作品中的人物情感,培养学生的同理心和人文关怀。
(3)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高道德素养。
二、教学内容1. 课文简介:《汉家寨》是当代作家阿来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汉家寨寨主杨大头一家三代人坚守寨子,维护民族尊严的故事。
2. 教学重点:分析作品的人物形象、情节安排和主题思想。
3. 教学难点:深入理解作品中的人物内心世界和民族精神。
三、教学过程1. 导入新课:简要介绍《汉家寨》的作者阿来及其作品特点,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2. 自主学习:让学生自主阅读课文,了解故事情节,把握人物关系。
3. 合作探讨:分组讨论,分析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形象、情节安排和主题思想。
4. 课堂讲解:针对学生的讨论结果,进行讲解,解答学生的疑问。
5. 案例分析: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段落,深入剖析作品的艺术特色和人物内心世界。
6. 情感体验: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谈谈对作品中人物情感的理解和感悟。
7. 课堂小结:总结本节课的学习内容,强调作品的主题思想和价值观念。
四、作业布置1. 请学生写一篇关于《汉家寨》的人物分析文章。
2. 选择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段落,进行详细的文本解读。
3. 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谈谈对作品中人物情感的理解和感悟。
五、教学反思六、教学策略1. 互动式教学:通过提问、讨论等方式,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
2. 情境教学:创设情境,让学生身临其境,更好地感受作品中的情感氛围。
2024年汉家寨公开课教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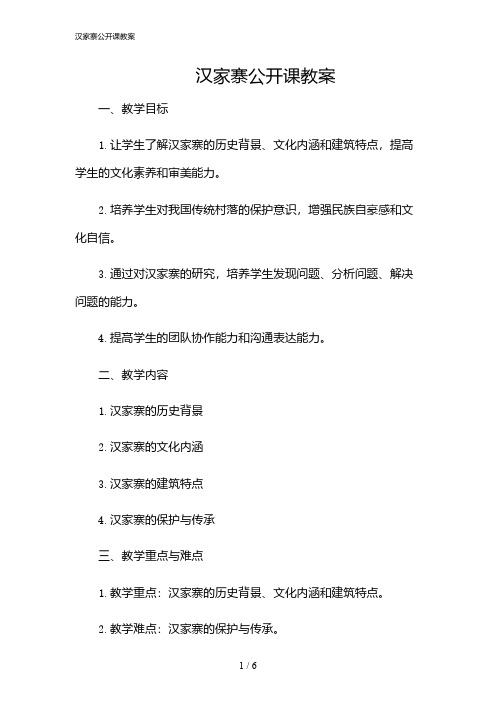
汉家寨公开课教案一、教学目标1.让学生了解汉家寨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和建筑特点,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
2.培养学生对我国传统村落的保护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3.通过对汉家寨的研究,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提高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沟通表达能力。
二、教学内容1.汉家寨的历史背景2.汉家寨的文化内涵3.汉家寨的建筑特点4.汉家寨的保护与传承三、教学重点与难点1.教学重点:汉家寨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和建筑特点。
2.教学难点:汉家寨的保护与传承。
四、教学过程1.导入新课利用多媒体展示汉家寨的图片,引导学生关注传统村落的保护与传承。
2.讲解汉家寨的历史背景(1)地理位置(2)历史沿革(3)重要历史事件3.讲解汉家寨的文化内涵(1)传统节日(2)民间信仰(3)非物质文化遗产4.讲解汉家寨的建筑特点(1)建筑风格(2)建筑布局(3)建筑技艺5.讲解汉家寨的保护与传承(1)保护现状(2)保护措施(3)传承与发展6.分组讨论学生分组讨论汉家寨的保护与传承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7.总结与拓展教师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布置课后作业,鼓励学生深入研究汉家寨的相关问题。
五、教学评价1.学生对汉家寨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和建筑特点的了解程度。
2.学生对汉家寨保护与传承的认识和参与度。
3.学生在讨论中的表现,如问题分析、解决方案等。
4.课后作业的完成情况。
六、教学资源1.多媒体课件2.图片、视频等素材3.相关书籍和文献4.网络资源七、教学建议1.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引导学生关注现实问题。
2.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沟通表达能力。
3.课后作业要注重拓展性和实践性,鼓励学生深入研究。
4.加强对汉家寨保护与传承的宣传,提高学生的保护意识。
5.结合其他学科知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汉家寨的保护与传承汉家寨的保护与传承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议题,涉及到文化、历史、建筑、社会和经济等多个方面。
2024年度《汉家寨》教案

03
对汉家寨人民的坚韧和顽强生命力的赞美,以及对汉家寨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的思考。
8
写作风格及特点
1
朴实自然的语言风格
作者运用朴实自然的语言,将汉家寨的风土人情 娓娓道来,使读者仿佛置身于汉家寨之中。
2
生动形象的描绘手法
作者通过生动的描绘手法,将汉家寨的自然景观 和人文景观呈现在读者眼前,使读者对汉家寨有 更深入的了解。
象征手法
运用象征手法,赋予人物更深层的 含义,如老人和小女孩分别象征着 汉家寨的历史和文化、未来和希望 。
14
04
环境描写及其作用
2024/3/23
15
自然环境描写技巧
细腻入微的描绘
通过对自然元素如地貌、气候、 植被的细致刻画,营造出汉家寨
独特的自然环境氛围。
感官体验的调动
运用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 官描写,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
“我”与小女孩
短暂相遇的陌生人,小女 孩的纯真和生机触动了“ 我”的内心。
13
人物塑造手法探讨
描写手法
通过外貌、动作、语言等描写手 法,生动地刻画出人物的性格特
点和内心世界。
2024/3/23
对比手法
通过人物之间的对比,突出各自的 特点和象征意义,如老人与小女孩 的对比,体现了汉家寨的历史与未 来。
情感真挚的表达方式
3
作者在文章中表达了对汉家寨人民的深厚感情, 对汉家寨文化的热爱和尊重,这种情感真挚的表 达方式深深地打动了读者。
2024/3/23
9
主题思想阐释
2024/3/23
对生命力的赞美
文章通过描绘汉家寨人民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顽强生存的场景, 赞美了人类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汉家寨 教案教学设计

《汉家寨》教案教学设计一、教学目标1. 知识与技能:(1)让学生了解《汉家寨》的故事情节,理解其中的寓意和深层含义。
(2)通过分析作品中的形象刻画,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
(3)引导学生掌握作品中的成语、俗语及地域文化特色。
2. 过程与方法:(1)采用问题驱动法,引导学生主动探讨作品中的主题思想。
(2)运用案例分析法,让学生通过分析具体情节,理解作者的写作手法。
(3)采用小组讨论法,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的能力,提高口头表达能力。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1)培养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传承意识。
(2)通过作品中所展现的人物精神风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3)激发学生对家乡、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二、教学内容1. 课文讲解:详细讲解《汉家寨》的故事情节,分析作品中的线索设置、人物刻画、环境描写等。
3. 写作手法分析:分析作品中的修辞手法、象征意义、成语、俗语等,帮助学生提高写作水平。
4. 文化内涵讲解:讲解作品中所涉及的地域文化、民俗风情,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三、教学重点与难点1. 教学重点:(1)掌握《汉家寨》的故事情节,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
(2)分析作品中的写作手法,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3)了解作品中的传统文化内涵,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
2. 教学难点:(1)深入理解作品中的象征意义和深层含义。
(2)运用写作手法分析具体情节,领会作者的用意。
四、教学过程1. 导入新课:简要介绍《汉家寨》的作者及作品背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 课文讲解:详细讲解课文内容,分析作品中的情节设置、人物刻画等。
3. 主题探讨:引导学生从作品中发现主题思想,让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
4. 写作手法分析:分析作品中的写作手法,让学生学会欣赏文学作品。
5. 文化内涵讲解:讲解作品中的地域文化、民俗风情,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五、课后作业2. 分析《汉家寨》中的一个写作手法,并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进行运用。
《汉家寨》教学设计(辽宁省省级优课)语文教案

《汉家寨》教学设计(辽宁省省级优课)语文教案第一章:教学目标与内容1.1 教学目标了解作品背景,把握作品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内涵。
分析作品中的主题思想,探讨作者的表达意图。
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写作能力。
1.2 教学内容作品背景介绍:《汉家寨》是辽宁省作家金宇辉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汉族与满族文化交流和冲突的故事。
作品主题分析:通过分析作品中的情节、人物形象和象征意义,探讨作品所反映的文化认同、民族关系和个体命运等主题。
文学鉴赏与批判性思维:引导学生从文学角度欣赏作品,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综合素养培养:通过小组讨论、写作练习等形式,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第二章:教学重点与难点2.1 教学重点作品背景与文化内涵的理解。
作品主题思想的分析和探讨。
文学鉴赏方法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学生的阅读兴趣和写作能力的提高。
2.2 教学难点作品中的象征意义和深层含义的解读。
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和学生独立思考的引导。
学生写作能力的提升和个性化表达的指导。
第三章:教学方法与手段3.1 教学方法讲授与讨论相结合:教师引导学生了解作品背景,分析作品主题,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和分享。
阅读与写作相结合:鼓励学生进行阅读思考,通过写作练习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
案例分析与实地考察相结合:选取相关案例进行分析,组织实地考察活动,增强学生对文化内涵的理解。
3.2 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利用多媒体课件和教学资源,提供丰富的视觉和听觉材料,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线学习平台:利用在线学习平台,提供相关阅读材料、讨论区和作业提交功能,方便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和交流。
写作评价工具:使用写作评价工具,给予学生及时的反馈和指导,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第四章:教学安排与评价4.1 教学安排课时安排:本章节共计10课时,每课时45分钟。
教学步骤:作品背景介绍(2课时)、作品主题分析(4课时)、文学鉴赏与批判性思维(2课时)、综合素养培养(2课时)。
2024年《汉家寨》教案(教师中心稿)教案教学设计

2024年《汉家寨》教案(教师中心稿)教案教学设计第一章:课程介绍1.1 课程背景《汉家寨》是一部描绘中国西北汉人村落生活的长篇小说,作者是中国著名作家贾平凹。
通过讲述寨子里的人物故事,揭示了汉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以及人们在变革中的困惑和挣扎。
1.2 教学目标1.2.1 知识目标让学生了解《汉家寨》的作者、作品背景及主要人物。
1.2.2 能力目标培养学生分析小说人物形象、理解小说主题的能力。
1.2.3 情感目标引导学生关注农村生活,体会汉人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民族自豪感。
1.3 教学内容本章主要介绍《汉家寨》的作者、作品背景、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
通过阅读选段,使学生对小说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第二章:人物形象分析2.1 人物形象概述本章重点分析《汉家寨》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包括寨子里的老人、青年和儿童。
分析他们的性格特点、命运走向以及他们在小说中的作用。
2.2 人物形象分析2.2.1 老人形象分析老人形象的沧桑与坚守,以及他们在传承汉人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2.2.2 青年形象探讨青年形象在追求现代文明过程中的矛盾与挣扎,以及他们在小说中的成长与转变。
2.2.3 儿童形象关注儿童形象的天真与纯朴,以及他们在汉家寨未来的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第三章:主题理解3.1 小说主题概述本章旨在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汉家寨》的主题,探讨作品所反映的汉人村落生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3.2 主题分析3.2.1 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分析小说中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对人物命运的影响。
3.2.2 文化传承与断裂探讨汉家寨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文化传承与断裂的问题,以及作品对此的思考。
3.2.3 人性的坚守与挣扎通过分析人物形象,引导学生关注人性在困境中的坚守与挣扎,以及作品对人性的揭示。
第四章:教学实践与拓展4.1 课堂讨论组织学生就小说中的某一人物、情节或主题进行讨论,分享自己的看法和感受。
汉家寨教案(王小敏)

《汉家寨》教案王小敏●教学目标1.知识目标:(1)整体感知文章,梳理文章的结构层次,概括主要内容;(2)探索文章在写景叙事、抒情写意中传达出的地域文化象征、个体生命象征意义;(3)通过阅读使学生感知文章形象化、有张力的语言特色。
2.能力目标:(1)通过阅读分析培养学生的感悟及表达能力;(2)引发学生对问题进行自主探究,培养其自主探究及创新能力。
3.情感目标:(1)理解文章“坚守”的内涵,明确这种精神对人生的意义及价值,进一步感受张承志散文的精神魅力。
●教学难点、重点(1)引导学生理解“坚守”的内涵,并帮助学生将“坚守”的精神内化。
●教学过程1.导入:通过《管子.自然》中、郑悉予的《错误》及余秋雨的《道士塔》来引入,介绍本文的出自张承志的散文集《荒芜英雄路》。
2.整体感知:(1)划分文章段落,理清行文线索:走近汉家寨(1-6段)走进汉家寨(7-30段)离开汉家寨(31-36段)3.阅读分析:(1)第一部分(1-6段):问题:作者为什么不开篇就写身在汉家寨,而是要用大量的篇幅来写“走近”的过程,这样写的用意何在?这一部分主要写了汉家寨所处的残酷的地理环境和恶劣的自然条件,可通过抓住“我在曝晒中晕眩了,怔怔地觉得马的脚踝早已被那些尖利的石刃割破了”及“我觉得自己渺小得连悲哀都是徒劳”等作者主观感受的语句,帮助学生感受汉家寨生存环境的恶劣。
引导学生立足文章本身,用文中出现的一些点型的词汇来概括“汉家寨”环境的恶劣,如:空寂、苍凉、荒芜、残酷等。
这种残酷的地理环境和恶劣的自然条件为下文突出“坚守”精神做了铺垫和伏笔。
(2)第二部分(7-30段)示范朗读:“汉家寨只是几间破泥屋,它坐落在新疆吐鲁番北、天山以南的一片铁灰色的砾石戈壁正中。
无植被的枯山像铁渣堆一样,在三个方向汇指着它——三道裸山之间,是三条巨流般的黑戈壁,寸草不生,平平地铺向三个可怕的远方。
因此,地图上又标着另一个地名叫三岔口;这个地点在以后我的生涯中总是被我反复回忆,咀嚼吟味,我总是无法忘记它。
【高二】《汉家寨》教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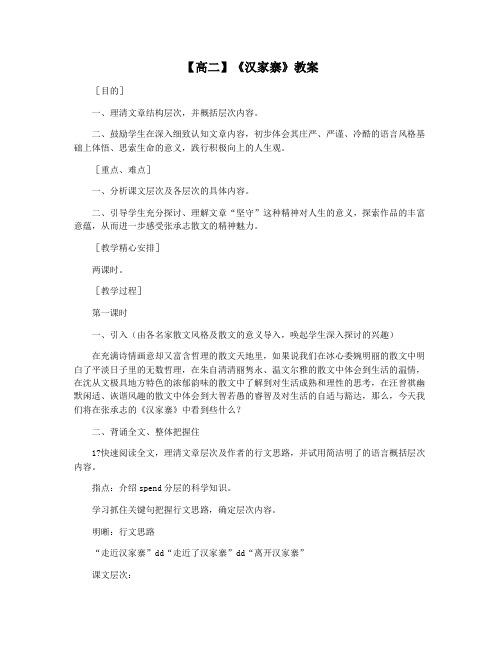
【高二】《汉家寨》教案[目的]一、理清文章结构层次,并概括层次内容。
二、鼓励学生在深入细致认知文章内容,初步体会其庄严、严谨、冷酷的语言风格基础上体悟、思索生命的意义,践行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重点、难点]一、分析课文层次及各层次的具体内容。
二、引导学生充分探讨、理解文章“坚守”这种精神对人生的意义,探索作品的丰富意蕴,从而进一步感受张承志散文的精神魅力。
[教学精心安排]两课时。
[教学过程]第一课时一、引入(由各名家散文风格及散文的意义导入,唤起学生深入探讨的兴趣)在充满诗情画意却又富含哲理的散文天地里,如果说我们在冰心委婉明丽的散文中明白了平淡日子里的无数哲理,在朱自清清丽隽永、温文尔雅的散文中体会到生活的温情,在沈从文极具地方特色的浓郁韵味的散文中了解到对生活成熟和理性的思考,在汪曾祺幽默闲适、诙谐风趣的散文中体会到大智若愚的睿智及对生活的自适与豁达,那么,今天我们将在张承志的《汉家寨》中看到些什么?二、背诵全文、整体把握住1?快速阅读全文,理清文章层次及作者的行文思路,并试用简洁明了的语言概括层次内容。
指点:介绍spend分层的科学知识。
学习抓住关键句把握行文思路,确定层次内容。
明晰:行文思路“走近汉家寨”dd“走近了汉家寨”dd“离开汉家寨”课文层次:(1)“走近汉家寨”,主要写汉家寨地处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dd空寂、苍凉、荒芜、残酷。
(可以通过把握住“我在暴晒中眩晕了,怔怔地真的马的脚踝早已被那些锋利的石刃割伤了”及“我真的自己可悲得没了可悲都就是徒劳”等作者主观体会的语句,体会汉家寨生存环境的严酷。
)(2)“走近了汉家寨”,主要写了在汉家寨的所见所感dd神秘、隔绝、真实、坚忍。
(可以通过“猛然间深感所谓‘大漠孤烟直’并没写下一种残暴”“在那块绝地里,他们究竟怎样存活下来,种什么,喝什么,至今仍就是一个谜”及“但是这不是幻觉也不是神话”“从宋至今,汉家寨至少已经固守着存活了一千多年了”去鼓励学生初步体会汉家寨所彰显出的“固守”精神。
《汉家寨》教学设计(辽宁省省级优课)语文教案

《汉家寨》教学设计(辽宁省省级优课)语文教案第一章:教学目标1.1 知识与技能:1. 能够理解课文《汉家寨》的基本内容,把握作者的写作背景及创作意图。
2. 能够分析课文中的修辞手法及表现手法,提高阅读理解能力。
3. 能够运用课文中的词语和句式进行口语表达和写作。
1.2 过程与方法:1. 通过自主学习、合作学习、讨论交流等方法,提高学生的阅读和分析能力。
2. 学会欣赏文学作品,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和审美情趣。
1.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1. 培养学生热爱家乡、传承中华文化的情感。
2. 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提高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第二章:教学内容2.1 课文简介:《汉家寨》是当代作家阿来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以作者童年时在汉家寨的生活为背景,描述了汉家寨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和村民的生活状态。
文章展现了汉家寨人民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表达了作者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民族文化的传承。
2.2 教学重点:1. 理解课文《汉家寨》的基本内容,把握作者的写作背景及创作意图。
2. 分析课文中的修辞手法及表现手法,提高阅读理解能力。
2.3 教学难点:1. 领会课文中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和作者的情感态度。
2. 运用课文中的词语和句式进行口语表达和写作。
第三章:教学过程3.1 导入新课:1. 教师简要介绍课文《汉家寨》的作者阿来及其创作背景。
2. 提问:同学们对家乡有什么印象?家乡有哪些特点和习俗?3.2 自主学习:1. 学生自主阅读课文,理解课文基本内容。
2. 学生通过课文注释和查阅相关资料,了解课文中的生僻词语和句式。
3.3 合作学习:1. 学生分组讨论,分析课文中的修辞手法及表现手法。
3.4 课堂讲解:1. 教师针对课文内容进行详细讲解,解答学生疑问。
2. 教师引导学生深入分析课文中所展现的汉家寨的风土人情和村民的生活状态。
3.5 情感体验:1. 教师引导学生感受作者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民族文化的传承。
2. 学生分享自己的家乡故事,感受家乡的美好。
《汉家寨》优秀教案

01课程介绍与目标Chapter《汉家寨》背景及作者简介0102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030201教学目标与要求课程安排与时间第二课时第一课时深入解读文本,探讨散文的特点和写作技巧,培养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第三课时02文本解读与赏析Chapter文章结构与写作特点以游踪为线索,展现汉家寨所处的环境和背景采用对比手法,突出汉家寨的孤独和坚守融入历史和文化元素,丰富文章内涵关键人物形象塑造及其特点老人形象小女孩形象描绘手法与意境营造运用生动的描绘手法,展现汉家寨的荒凉与壮美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汉家寨所处的荒凉环境和自然风光的壮美,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借助象征手法,表达作者对坚守精神的赞美作者通过对老人和小女孩形象的塑造,以及他们坚守在汉家寨的行为,表达了作者对坚守精神的赞美和敬意。
营造苍凉、凝重的意境,引发读者对历史的思考作者通过描绘汉家寨的荒凉和孤独,营造出一种苍凉、凝重的意境,引发读者对历史、文化和坚守精神的思考。
03主题思想探讨与价值体现Chapter民族精神传承与弘扬忠勇精神爱国情怀坚韧不拔地域文化特色展示自然环境描绘汉家寨所处的独特自然环境,展示西北地区苍凉、辽阔的地域风貌。
民俗风情通过介绍汉家寨人的生活方式、习俗等,展现西北地区丰富多样的民俗文化。
历史遗迹提及汉家寨的历史背景和遗迹,引导读者关注西北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传承文化传承和弘扬本民族文化,是每一个民族成员的责任和使命。
坚守信仰在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坚守信仰、保持精神追求对于个人和民族至关重要。
应对挑战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应发扬汉家寨人坚韧不拔的精神,积极应对并寻求解决方案。
现代社会意义及启示04知识拓展与延伸阅读建议Chapter相关历史背景知识补充汉朝的兴衰历程01汉武帝与匈奴的战争02古代边塞诗的特点03同类题材作品推荐及比较阅读《出塞》、《从军行》等边塞诗《史记》、《汉书》等历史典籍跨学科领域知识链接地理学社会学文学理论05互动环节与课堂活动设计Chapter01分组并确定小组长,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参与讨论。
《汉家寨》教案

《汉家寨》教案教学目标1、体会文章具有强烈抒情性和厚重感的语言。
2、分析文章精彩的景物描写和人物描写。
3、分析汉家寨人的“坚守”和作者的“坚守”,把握文章“坚守”的内涵。
教学难点探讨“坚守”的意义教学步骤第一课时一、导入新课(展示沙漠、戈壁滩的图片)这些沙漠、戈壁滩给你们什么样的感觉?——荒凉、恐怖、绝望等。
那么如果让你住在茫茫的戈壁滩呢?一年、两年、一辈子呢?今天我们就追随作者张承志的脚步,走进处于茫茫戈壁滩之中的汉家寨。
二、初读课文,划分层次,理清课文思路。
以作者的行踪为线索分为三个部分:1-6 走近汉家寨6-30走进汉家寨31-36离开汉家寨三、鉴赏课文1、作者走近汉家寨的过程中,看到了怎样的景象?这些景象有怎样的特点?作者有怎样的感受?景象:三百里空山绝谷、铁色戈壁、碧绿色的草、酥碎的红石、淡红色的焦土(单纯单调的色彩)、刀割般的风蚀痕迹、狞恶的尖石棱等。
通过跟北麓的对比,突显生存环境的恶劣。
特点:死寂、空旷宁寂、雄大磅礴、苍凉感觉:恐怖、茫然、渺小、悲哀,刻骨铭心的震撼或是这部分给你怎样的感受,结合课文谈谈2、第7自然段说“大漠孤烟直”没有写出的残酷,是怎样一种残酷?地理位置和环境:比喻一枚被人丢弃的棋子、一粒生锈的弹丸孤独、荒僻的绝地生活的人:从作者与老小二人的互动来看——木讷、呆滞、迟钝、不想说话、失去说话的欲望,近乎静态,说明汉家寨的荒僻、与世隔绝;汉人服色(千年前到此繁衍,却仍是汉族人服装的式样,没有被少数民族同化——“确实叫汉家寨“)在这样一块绝地,连种什么、吃什么都是一个谜,汉家寨人仍顽强生存,并保留汉人的服色,靠的是——坚守。
四、读汉家寨的人——小女孩1、眼睛黑亮的眼睛“不眨眼地盯着我”、“盯住我不眨眼睛“、“凝视着我”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小女孩儿盯着外来人——对陌生人好奇,对外面世界的好奇与向往,充满希望。
天真、纯净的眼神,引发作者的疼惜,“总觉得那便是我女儿的眼睛”。
2、红花棉袄红色代表——温暖、希望、美好、幸福红色与死寂、苍茫的戈壁形成鲜明的对比,是绝望的戈壁中唯一一抹亮色,那么醒目和令人震撼。
2024年《汉家寨》教案(教师中心稿)教案教学设计

一、教案基本信息2024年《汉家寨》教案(教师中心稿)教案教学设计文学作品:《汉家寨》作者:阿来教学目标:1. 理解《汉家寨》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
2. 分析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和文学特色。
3. 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教学重点:1. 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的理解。
2. 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和文学特色的分析。
教学难点:1. 作品中的深层主题和象征意义的解读。
2. 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教学准备:1. 教师手册和教科书。
2. 相关的研究资料和参考书籍。
3. 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过程:1. 导入:介绍作者阿来及其作品《汉家寨》。
2. 阅读理解:学生自主阅读《汉家寨》,理解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
3. 讨论分析:学生分组讨论,分析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和文学特色。
4. 深入解读:教师引导学生深入解读作品中的深层主题和象征意义。
5. 文学鉴赏:学生进行文学鉴赏,分析作品的文学特色和艺术表现手法。
6. 批判性思维:学生进行批判性思维训练,对作品进行评价和解读。
7. 总结反思:学生总结学习收获,教师进行教学反思。
二、教学方法1. 阅读理解:学生自主阅读,提高阅读理解能力。
2. 小组讨论:学生分组讨论,培养合作和沟通能力。
3. 教师引导:教师引导学生深入解读和批判性思维,提供指导和支持。
4. 多媒体教学: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丰富教学手段和资源。
三、教学评价1. 课堂参与度: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和表现,评估学生的学习态度和积极性。
2. 阅读理解测试:进行阅读理解测试,评估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3. 小组讨论评价:评估学生在小组讨论中的表现和合作能力。
4. 学生总结反思:评估学生的学习收获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四、教学内容第一节:作者阿来及作品《汉家寨》介绍1. 介绍作者阿来的背景和作品《汉家寨》的背景。
2. 分析作品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
第二节: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理解1. 学生自主阅读《汉家寨》,理解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
《汉家寨》教学设计(辽宁省省级优课)语文教案

《汉家寨》教学设计(辽宁省省级优课)语文教案第一章:教学目标1.1 知识与技能:理解课文《汉家寨》的基本情节和人物关系。
分析作品中的象征意义和深层含义。
掌握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
1.2 过程与方法:通过阅读和讨论,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运用文本细读和比较阅读的方法,深入探讨作品的细节和主题。
1.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培养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尊重。
引导学生思考个人与家族、民族文化的关系,培养爱国情怀。
第二章:教学内容2.1 课文内容概述:简要介绍《汉家寨》的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
分析作品中的重要事件和冲突,以及它们对人物命运的影响。
2.2 象征意义解读:分析作品中的象征元素,如汉家寨的象征意义,以及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探讨作品中的其他象征物和象征动作,如寨旗、守望等,以及它们所传达的主题。
第三章:教学重点与难点3.1 教学重点:理解课文《汉家寨》的情节和人物关系。
分析作品中的象征意义和深层含义。
3.2 教学难点:解读作品中的象征元素和文化背景知识。
深入理解作品所传达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承。
第四章:教学方法与手段4.1 教学方法:采用问题驱动法和讨论法,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和探索。
运用案例分析和比较阅读法,帮助学生深入理解作品。
4.2 教学手段:使用多媒体课件和教学资源,提供丰富的视觉和文化背景信息。
开展小组讨论和角色扮演活动,激发学生的参与和创造力。
第五章:教学评价5.1 过程性评价:通过课堂讨论、提问和小组活动,评估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程度和表现,以及他们的思考和表达能力。
5.2 终结性评价:布置课后作业,如作文或研究报告,让学生进一步深入思考作品的主题和意义。
进行期末考试,评估学生对整个课程内容的学习效果和掌握程度。
第六章:教学步骤设计6.1 引入新课:通过展示汉家寨的图片和介绍其地理位置,引发学生对课文的好奇心。
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一个偏远的小寨子会成为文学作品的主题?6.2 自主学习:学生自主阅读课文《汉家寨》,理解基本情节和人物关系。
汉家寨高三上册语文教案

汉家寨高三上册语文教案(实用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文档下载后可定制修改,请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和使用,谢谢!并且,本店铺为大家提供各种类型的实用范文,如演讲致辞、合同协议、条据文书、策划方案、总结报告、简历模板、心得体会、工作材料、教学资料、其他范文等等,想了解不同范文格式和写法,敬请关注!Download tips: This document is carefully compiled by this editor.I hope that after you download it, it can help you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The document can be customized and modified after downloading, please adjust and use it according to actual needs, thank you!In addition, this store provides various types of practical sample essays, such as speeches, contracts, agreements, documents, planning plans, summary reports, resume templates, experience, work materials, teaching materials, other sample essays, etc.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t formats and writing methods of the model essay!汉家寨高三上册语文教案《汉家寨》用苍凉而又饱含情感的笔调勾勒出一幅汉家寨人在粗犷、荒凉、孤独无援的“绝地”中顽强“坚守”的画卷,展示了人类强大的生存毅力,那就是坚守。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教案’汉家寨原文及教案一、《汉家寨》是一篇诗意盎然的。
用墨如泼地描写环境,惜墨如金地描写人物--而深刻的主题便蕴含在描写之中,在言外,耐人咀嚼。
遗憾的是,却有不少中学生读者对如此美文妄加褒贬。
有的说:作者被洗脑了,写出这篇荒诞的作品,用混乱的视象与病态的想象,充斥读者理性的头脑。
有的说:景物描写所用篇幅太多了,作者似乎在卖弄自己的文采,故意写得极晦涩。
对这篇散文的阅读,将使慧心犹在的学子明白:一篇有诗意的散文,才是上乘的散文;一个品得出诗意的读者,才是有品位的读者。
二、这篇散文主题深刻,足以振聋发聩,惊世警人。
"坚守"的主题,绝不仅仅局限于汉家寨于不毛之地中坚守着生存,其实,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可见:有人在物欲横流中坚守着清贫,有人在庸俗泛滥中坚守着高雅,有人在寂寞孤独中坚守着理想,有人在"游戏人生"中坚守着作为,有人在"众人皆醉"中坚守着"独醒",有人在急功近利中坚守着"治本",有人在"全盘西化"中坚守着民族精华…对这篇散文的学习,将使良心未泯的学子思考与选择正确的"坚守",从而使自己的人生光彩照人。
那是大风景和大地貌荟集的一个点。
我从天山大坂上下来,心被四野的宁寂--那充斥天宇六合的恐怖一样的死寂包裹着,听着马蹄声单调地试探着和这静默碰击,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若是没有这匹马弄出的蹄音,或许还好受些。
300里空山绝谷,一路单骑,我回想着不觉一阵阵阴凉袭向周身。
那种山野之静是永恒的;一旦你被它收容过,有生残年便再也无法离开它了。
无论后来我走到哪里,总是两眼幻视、满心幻觉,天涯何处都像是那个铁色戈壁,都那么空旷宁寂、四顾无援。
我只有凭着一种茫然的感觉,任那匹伊犁马负着我,一步步远离了背后的雄伟天山。
和北麓的蓝松嫩草判若两地--天山南麓是大地被烤伤的一块皮肤。
除开一种语叫uga的毒草是碧绿色以外,岩石是酥碎的红石,土壤是淡红色的焦土。
山坳折皱之间,风蚀的痕迹像刀割一样清晰,狞恶的尖石棱一浪浪堆起,布满着正对太阳的一面山坡。
马在这种血一样的碎石中谨慎地选择着落蹄之地,我在曝晒中晕眩了,怔怔地觉得马的脚踝早已被那些尖利的石刃割破了。
然而,亲眼看着大地倾斜,亲眼看着从高山牧场向不毛之地的一步步一分分的憔悴衰老,心中感受是奇异的。
这就是地理,我默想。
前方蜃气溟蒙处是海拔负154米的吐鲁番盆地最低处的艾丁湖。
那湖早在万年之前就被烤干了,我想。
背后却是天山;冰峰泉水,松林牧场都远远地离我去了。
一切只有大地的倾斜;左右一望,只见大地斜斜地延伸。
嶙峋石头,焦渴土壤,连同我的坐骑和我自己,都在向前方向深处斜斜地倾斜。
--那时,我独自一人,八面十方数百里内只有我一人单骑,向导已经返回了。
在那种过于雄大磅礴的荒凉自然之中,我觉得自己渺小得连悲哀都是徒劳。
就这样,走近了汉家寨。
仅仅有一炷烟在怅怅升起,猛然间感到所谓"大漠孤烟直"并没有写出一种残酷。
汉家寨只是几间破泥屋,它坐落在吐鲁番北、天山以南的一片铁灰色的砾石戈壁正中。
无植被的枯山像铁渣堆一样,在三个方向汇指着它--三道裸山之间,是三条巨流般的黑戈壁,寸草不生,平平地铺向三个可怕的远方。
因此,地图上又标着另一个地名叫三岔口;这个地点在以后我的生涯中总是被我反复回忆,咀嚼吟味,我总是无法忘记它。
仿佛它是我人生的答案。
我走进汉家寨时,天色昏暮了。
太阳仍在肆虐,阳光射入眼帘时,一瞬间觉得疼痛。
可是,那种将结束的白炽已经变了,汉家寨日落前的炫目白昼中已经有一种寒气存在。
几间破泥屋里,看来住着几户人。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了这样一个地名。
的汉语地名大多起源久远,汉代以来这里便有中原人屯垦生息,唐宋时又设府置县,使无望的甘陕移民迁到了这种异域。
真是异域--三道巨大空茫的戈壁滩一望无尽,前是无人烟的盐碱低地,后是无植被的红石高山,汉家寨,如一枚被人丢弃的棋子,如一粒生锈的弹丸,孤零零地存在于这巨大得恐怖的大自然中。
三个方向都像可怕的暗示。
我只敢张望,再也不敢朝那些入口催动一下马蹄了。
独自伫立在汉家寨下午的阳光里,我看见自己的影子一直拖向地平线,又黑又长。
三面平坦坦的铁色砾石滩上,都反射着灼烫的亮光,像热带的海面。
默立久了,突然意识到什么。
转过头来,左右两座泥屋门口,各有一个人在盯着我。
一个是位老汉,一个是七八岁的小女孩。
他们痴痴盯着我。
我猜他们已经好久没有见过外来人了。
老少两人都是汉人服饰;一瞬间我明白了,这地方确实叫做汉家寨。
我想了想,指着一道戈壁问道:--它通到哪里﹖老人摇摇头。
女孩不眨眼地盯着我。
我又指着另一道:--这条路呢﹖老人只微微摇了一下头,便不动了。
女孩还是那么盯住我不眨眼睛。
犹豫了一下,我费劲地指向最后一条戈壁滩。
太阳正向那里滑下,白炽得令人无法瞭望。
地平线上铁色熔成银色,闪烁着数不清的亮点。
我刚刚指着,还没有开口,那老移民突然钻进了泥屋。
我呆呆地举着手站在原地。
那小姑娘一动不动,她一直凝视着我,不知是为了什么。
这女孩穿一件破红花棉袄,污黑的棉絮露在肩上襟上。
她的眼睛黑亮--好多年以后,我总觉得那便是我女儿的眼睛。
在那块绝地里,他们究竟怎样生存下来,种什么,吃什么,至今仍是一个谜。
但是这不是幻觉也不是神话。
汉家寨可以在任何一张好一点的地图上找到。
《宋史·高昌传》据使臣王延德旅行记,有"又两日至汉家砦"之语。
砦就是寨,都是人坚守的地方。
从宋至今,汉家寨至少已经坚守着生存了一千多年了。
独自面对着那三面绝境,我心里想:这里一定还是有一口食可觅,人一定还是能找到一种生存下去的手段。
次日下午,我离开了汉家寨,继续向吐鲁番盆地前行。
大地倾斜得更急剧了;笔直的斜面上,几百里铺伸的黑砾石齐齐地晃闪着白光。
回首天山,整个南麓都浮升出来了,峥嵘嶙峋,难以言状。
俯瞰前方的吐鲁番,蜃气中已经隐约现出了绿洲的轮廓。
在如此悲凉严峻的风景中上路,心中涌起一股决绝的气概。
我走下第一道坡坎时,回转身来想再看看汉家寨。
它已经被起伏的戈壁滩遮住了一半,只露出泥屋的屋顶窗洞。
那无言的老人再也没有出现。
我等了一会儿,最后遗憾地离开了。
千年以来,人为着让生命存活曾忍受了多少辛苦,像我这样的人是无法揣测的。
我只是隐隐感到了人的坚守,感到了那坚守如这风景一般苍凉广阔。
走过-个转弯处--我知道再也不会有和汉家寨重逢的日子--我激动地勒转马缰。
遥遥地,我看见了那堆泥屋的黄褐中,有一个小巧的红艳身影,是那小女孩的破红棉袄。
那时的天山已经完全升起于北方,横挡住大陆,冰峰和干沟裸谷相衬映,向着我倾泻般伸延的,是汉家寨那三岔戈壁的万吨铁石。
我强忍住心中的激动,继续着我的长旅。
从那一日我永别了汉家寨。
也是从那一日起,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在不知不觉之间,坚守着什么。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只觉得它与汉家寨这地名天衣无缝。
在美国,在日本,我总是倔强地回忆着汉家寨,仔细想着每一个细节。
直至南麓天山在阳光照耀下的、伤痕累累的山体都清晰地重现,直至大陆的倾斜面、吐鲁番低地的白色蜃气,以及每一块灼烫的砾石都逼真地重现,直至当年走过汉家寨戈壁时有过的那种空山绝谷的难言感受充盈在心底胸间。
(选自《荒芜英雄路》)《汉家寨》教案教学目的:1、阅读课文,了解汉家寨荒凉、死寂的环境特征。
2、体会作者内心的细腻感受,理解作者所颂扬的"坚守"的精神。
3、感受作者独特的写作特点。
教学重点:1、掌握作者的个性化语言及写作特点。
2、把握文中流露出来的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难点:景物描写在文中的作用;作者思想感情的把握。
教法:讲读法教学过程:一、导入新课从《道士塔》中我们感受到的是敦煌艺术瑰宝留给世人的历史反思以及她带给我们的深厚浓郁的文化气息和心灵震撼。
今天,让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另一种亘古而新奇的"艺术"--大自然和人类 __完美结合。
让我们一起走进汉家寨--一个几乎被人类文明遗忘的、有着最古老的人类精神的家园。
(投影出示:教学目标)(音乐起)二、讲授新课(一)整体感知1、课题、作者简介(出示投影)张承志,青年作家、学者,1948年生于北京,原籍山东济南。
华附中毕业到内蒙古乌珠穆沁旗插队4年。
1978年开始笔耕。
现为自由的职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曾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现为已出版著作30余种,代表作有:小说集《张承志集》、《清洁的精神》、诗集《神云的诗篇》、文集《张承志作品集》以及《心灵史》。
流传较广的有中篇小说《黑骏马》、《春天》、《北方的河》和长篇小说《金牧场》。
2、疏通生字词。
(投影)褶(zhé)皱曝(pù)晒脚踝(huái)晕眩(yùn)(xuán)俯瞰(kàn)咀嚼(jǔ)(jué)白炽(chì)六合:指上下和东西南北四方,泛指天下或宇宙。
伫立:长时间地站立。
荟集:聚集。
峥嵘:高峻。
嶙峋:形容山石突兀、重叠。
俯瞰:俯视,从高处往下看。
决绝:非常坚决。
3、学生阅读全文,谈谈对本文的总体感受。
①语言特点:骨健瘦硬,气概充盈,体态阔大。
②环境描写:客观冷静,描写细腻,寓情于景。
(二)逐层分析,全文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到"走近了汉家寨"。
写走近汉家寨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和内心感受。
所见:铁色戈壁红石焦土所闻:单调的马蹄声感受:"我觉得自己渺小得连悲哀都是徒劳"。
▲教师评析:作者通过对一路行来所见到的自然景观的客观描述,创造了一种奇异的视觉效果,向读者传达了一种苍凉、广袤、寂寞无边、慷慨悲凉的情绪。
为下文作者的反思张本。
第二部分:从"仅仅有一柱烟…"到"…找到一种生存下去的手段"。
写走进汉家寨的所见所思。
所见:大漠孤烟:"怅怅""异域"景物黑戈壁:"可怕"" 内容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