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二午睡时刻 加西亚马尔克斯
礼拜二午睡时刻马尔克斯

业余爱好? 卡为长什大洛么后要你斯听就妈会·森养 神妈开的始不父特话懂教从诺得,道这,父德段之层话你过面是;评教判个不卡啥严洛,斯样师·森人之特儿惰诺。呀没有?走
长为神大什维父后么持吁我我一了开跑家一始得人正明比口的白别道气人生,。快活责“备。您他从的来母没亲有没想有过尽要责把任他。引梁上上正君道子
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 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 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是《百年孤独》的开头。短短的一 句话,实际上容纳了未来、过去和现在三 个时间层面,而作家显然隐匿在“现在” 的叙事角度。这个开头,以其采用了从未 来回忆过去的倒叙手法,被后人津津乐道, 并称之为经典式开头。
✓ 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
✓ 1947年入波哥大大学攻读法律,并开始文学创作。 1948年因哥伦比亚内战中途辍学。不久他进入报界, 任《观察家报》记者。1955年,他因连载文章揭露被 政府美化了的海难而被迫离开哥伦比亚,任《观察家 报》驻欧洲记者。1960年,任古巴拉丁通讯社记者。 1961年至1967年,他移居墨西哥,从事文学、新闻和 电影工作。之后他主要居住在墨西哥和欧洲,继续其 文学创作。1975年,他为抗议智利政变举行文学罢工, 搁笔5年。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并任法国西班 牙语文化交流委员会主席。1982年,哥伦比亚地震, 他回到祖国。1999年得淋巴癌,此后文学产量遽减, 2006年1月宣布封笔。
主要作品:
1967年——《百年孤独》 1975年——《家长的没落》 1985年——《霍乱时期的爱情》
1972年获拉美文学最高奖──委内瑞拉 加列戈斯文学奖,1982年凭借《百年 孤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百年孤独》是马尔克斯花了18年时间创作的代
课件6:第13课 礼拜二午睡时刻

3.找出母亲克制自己情绪的语句,体会作者节制的叙事方式。 ①她一直是直挺挺地背靠着椅子,两手按着膝盖上的一个皮包,她 脸上露出那种安贫若素的人惯有的镇定安详的神情。 用坚强克制悲伤。 ②“拖鞋穿上!” “梳梳头!” “你要有什么事,现在赶快做好!往后渴死了,你也别喝水。尤其 不许哭。” (分析三个感叹号的作用) 临近小镇,心中悲痛又矛盾,用命令的口吻克制自己的脆弱,所以 在语调上显得特别强硬。
7.巧妙的悬念设置:文中被打死的人(母亲的儿子、拳击手)是否 真的是小偷?
对于这个问题,文章一直没有明确地回答,但从母亲的陈述、事件 的回放以及神父的尴尬来看,我们可以很明确地判断出那只是一个 饥寒交迫的过路人。
主旨归纳
文章通过叙述一位母亲带着年幼的女儿去祭拜被误当“小偷”而打 死的儿子的经过,向人们展示了母爱的执著、博大与神父的宽容、 关爱,揭示人性中固有的真善美。
导语设计
法国谚语说“女人固然是脆弱的,母亲却是坚强的。”今天我们要 学的马尔克斯的《礼拜二午睡时刻》正如一部短小的黑白电影,在 平静的、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展现了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
初读文本
用简练的语言概括小说叙述了一个什么故事 。
讲述了一位母亲带着年幼的女儿(人)在礼拜二午睡时刻(时)来 到一个小镇(地)去祭奠被当“小偷”打死的儿子(事)的故事。
③找到神父之后的一番对话 以执拗克制激动 ④母亲是如何重复地说自己是小偷的母亲的?请说说她说这些话 的神态。 以平静克制痛苦 ⑤母亲是如何神色自如的回忆儿子的? 好人、听话、吃苦 以回忆克制痛苦
语文《礼拜二午睡时刻》课件(新人教版选修《外国小)

目录
• 作者介绍 • 作品背景 • 故事梗概 • 语言特色 • 人物形象 • 作品评价
01
作者介绍
Chapter
作者生平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José de la Concordia García Márquez):1927年出生于哥伦比 亚,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 他的童年经历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他 曾在巴黎大学学习法律,但很快就转向了文学创作。
对世界文学的影响
该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成为世界 文学的一部分,为全球读者提供了了 解拉丁美洲文化和历史的窗口。
03
故事梗概
Chapter
故事情节
故事发生在一个炎热的礼拜二午后,一位母亲带着自己的儿子去寻找儿子的父亲。 母亲一路上经历了种种艰辛,最终找到了儿子的父亲,却发现他已经去世了。
母亲和儿子在处理父亲后事的过程中,逐渐理解he Autumn of the Patriarch):这部作 品也是马尔克斯的经典之作,讲述了 一位独裁者的故事。
文学风格
魔幻现实主义
马尔克斯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 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充满了 奇幻和神秘的元素,通过这些元
素来反映现实生活。
叙事技巧
马尔克斯的叙事技巧非常出色,他 善于运用倒叙、闪回等手法来讲述 故事,使得故事更加引人入胜。
03
他作为被枪决的罪 犯的家属,承受着 巨大的痛苦和压力 。
04
他的生活状况和心 理状态反映了当时 社会的冷漠和无情 。
人物关系分析
母亲与女儿的关系
母亲是女儿的引路人,她用自己的行 动和言语教育女儿如何面对生活中的
困难和挫折。
《礼拜二午睡时刻》

“拖鞋穿上!” “梳梳头!” “你要有什么事,现在赶快做
好!往后渴死了,你也别喝水。尤 其不许哭。”
“拖鞋穿上!” “梳梳头!” “你要有什么事,现在赶快做 好!往后渴死了,你也别喝水。尤 其不许哭。”
• 以命令克制脆弱
• 用坚强克制悲伤 • 以命令克制脆弱 • 以执拗克制激动
• 要求:贴近原文的叙述风格“含蓄简单”。 • 字数不得多于100字
• 2、课外赏析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桔 子》。
• 体会如出一辙的叙事风格和细节描写。
读一读 品一品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
洪汉友
加西亚·马尔克斯 (1928一 )哥伦比 亚魔幻现实主义作家, 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 奖。长篇小说代表作 《百年孤独》(被誉为 “再现拉丁美洲历史 社会图景的鸿篇巨 著”。 )
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一 )
•
早期的“魔幻现实主义”主要表现为对美洲印第安
人或黑人神话传说的发掘,代表作是危地马拉作家阿斯
写作艺术
• 情感的处理——节制含蓄胜于放纵
比较阅读
• (1) “把鞋穿上!”她对小女孩说。……妈妈递给她一把梳 子。“梳梳头!”妈妈说。……“你要是还有什么事,现在赶 快做好!”女人说,“往后就是渴死了,你也别喝水。尤其不 许哭。”
•
(原文)
•
“把鞋穿上!”她对小女孩(粗声地)说。……妈妈递给
她一把梳子。“梳梳头!”妈妈(严厉地)说。……“你要是
• 1-14 小说开端 祭拜途中
• 15-55小说发展 与神父交谈
• 56-67小说高潮 准备去祭拜
母亲形象分析
• 手法:神态、外貌、语言、动作细节的刻画
• 性格:贫穷、苦难、坚强、伟大、镇定
课件1:第13课 礼拜二午睡时刻

[曲终收拨当心划,四弦一声如裂帛] 终于把我拉扯大了。即将离开父母的我有些悲伤
的感觉。爸妈老了,我发现了他们鬓上的白丝;爸妈笑 了,我看到了他们满足的欣慰的目光。我突然哭了,爸 妈的爱和他们的言传身教早已铭刻我心。最后,爸爸 说:“孩子,以后的路只能自己去走了,自己好好把握 啊!” [座中泣下谁最多,掌上明珠双眸湿]
3.小说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写母女俩未祭拜之前的 火车行程,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提示:文章中真正的情节未开始之前,用不小的篇幅 来写母女俩的火车生活,一是更加充分地展示人物的 性格特点,使母亲的形象更加丰满、完整,二是为全 文营造了一种压抑的氛围,使小说的主题更加鲜明。
4.母爱是人类伟大的情感,《礼拜二午睡时刻》怎样 含蓄地表现了这种感情? 提示:我们常说:爱,不需要理由。这只是在一般情况 下。在特殊情况下,爱,的确是需要理由的。本文中, 母爱因为儿子可能有的“污点”而失去正常表达的 可能,情感的洪流必须寻求其他的途径才能传达出来。 初次出场的母亲的状况显然不是很好,但她却是坚强 的。她的坚强体现在对女儿的态度上近乎粗暴。在 神父那里,她更表现出不近人情的“固执”和“执 拗”。
我要感谢父亲母亲的教导,他们是最普通的父母, 却是我永远敬仰的明星。他们为我照亮了前方的路,引 导我走向光明的未来。
文本图解
礼拜二午睡时刻
礼拜二午睡时刻4.8

这位母亲深爱着自己的儿子: 她顶着世俗的压力来为儿子扫墓, 而且这是个很少人会来的地方(锈 迹斑斑的钥匙可以看出来) ; 她认为儿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他很听我的话”“每吃一口 饭……那个样子”) 。
环境
小说开篇的景物描写有什么作用
•小说开篇的景物描写灰暗压抑, 是因为人物内心的悲痛和忧伤决定 了她们眼中不可能有可爱美丽的风 景,暗合了文中人物悲痛的心情。 预示了与小说情节相关的肃穆氛围。
母亲之所以能保持神态上的平静,
关键是源于性格上的坚强,更进一 步说是对这个社会现实的抗议。
母亲:
慈爱,自尊,坚强,面对苦难的生 活,拥有一种宽厚无比的忍受能力 与有力的抗争精神。
神父为什么会“刷的一下子红了脸”甚至
“头上开始冒汗”?
•在博大无边的母爱面前,神父为 自己以普通人的眼光、普通人的道 德评判标准来看待“小偷”而紧张、 惭愧不安,同时也有对这位母亲的 敬佩。
对车厢的描写是为了说明什么?
说明了母女生活条件的拮据
小镇有什么特点?这一环境描写有
什么作用?
困、静、热、闷,是个 沉静的场景。映衬出这 对母女在这一时刻来到 这个小镇的突兀。同时 也对照衬托出这位母亲 的伟大,坚强,充满爱 的力量。
59段的环境描写有什么作用?
烘托出母亲将面临的屈辱景 况——自以为有着道德优势的 人们的道德谴责。而母亲后来 的行为使毫无畏惧的母爱跨越 了道德界限,感动世人。
找出神父几次劝阻母亲去墓地的话语并结 合背景加以分析: A“天太热了,你们可以等到太阳落山呢?” (背景:神父透过纱窗望了望万里无云的明 朗的天空) 明确:普通问候 B“等一会走吧” ——(背景:在临街的大 门打开之前。。。神父一看大街上乱哄哄的 反常样子,心里顿时就明白了。他悄悄地把 大门关上。) 明确:关切的劝阻 C“等到太阳落山再去吧!”
人教版外国小说选修之《礼拜二午睡时刻》

马尔克斯显然不想煽情,只是想克 制地叙述一件本身无需渲染就令人震 撼的事情,也许对这样的一位母亲煽 情只是一种罪恶。但是,从她简单的 言行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这个妇女 内心隐藏的悲痛是多么刻骨铭心。也 许你可以隐隐感觉到,这个妇女表面 上平静得就像大地,但是内心却犹如 地底下的熔岩,奔突激荡。镇静的背 后隐藏着无比的悲痛和宽广的爱。
表现得不近人情的“固执”和“执拗”。 她的反常的“平静”“温和”“不动声色” 的声音中压抑的是对一个被当作“小偷”打 死的儿子的爱。
母亲之所以能保持神态上的平静,关键 是源于性格上的坚强,更进一步说是对 这个社会现实的抗议。
慈力 的抗争精神。
• 镇子有可能完全一模一样吗?为什么这么写?
• 表现环境的沉闷与压抑 • 把现实投放到虚幻的环境和气氛中,给以客观、 详尽的描绘,使现实披上一层光怪陆离的魔幻的 外衣。这种把现实与幻景溶为一体的创作方法, 拉丁美洲的评论家称它为“魔幻现实主义”。
2.按“开端”“发展”“高潮”给课 文分段:
一、开端 (1-14 ) 祭拜途中 二、发展 (15-58) 与神父交谈 三、高潮 (59-70) 准备去祭拜
巴尔扎克曾说:“母亲的心是一个深渊,在 她的最深处你总会得到宽恕。”神父在这坚强隐 忍的母亲面前也汗颜了,母亲战胜了道德,这种 感情超越时空,一个被人唾弃的小偷,在他的母
亲那找到了尊严,只有漫无边际的母爱才使她 面对道德舆论的时候依然一如既往的表现自己 的母爱。
• “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上正道吗?”
马尔克斯作品的主 要特色是幻想与现 实的巧妙结合,以 此来反映社会现实 生活,审视人生和 世界。这种把现实 与幻景溶为一体的 创作方法,被称为 “魔幻现实主义”。
主要作品 1967年 - 《百年孤独》(被誉为
高三语文《礼拜二午睡时刻》(课件)

加西亚· 马尔克斯(1928一)哥伦比亚魔幻
现实主义作家,记者。是父亲的非婚子,从小在外祖 父家中长大。 13岁时,他迁居首都波哥大,就读于教 会学校。18岁进国立波哥大大学攻读法律,并加入自 由党。1948年,哥伦比亚发生内战,马尔克斯中途辍 学。不久,他进入报界,任《观察家报》记者,同时 从事文学创作。1954年起,任该报驻欧洲记者。 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和哥伦比亚语言科学院名 誉院士称号。 马尔克斯作品的主要特色是幻想与现实的巧妙结合, 以此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审视人生和世界。这种把 现实与幻景溶为一体的创作方法,被称为“魔幻现实 主义”。
3、分析结尾的作用? 这样写是为了突现作品的 主题—人类伟大的情感— 母爱。小说以母女俩直接 走向墓地为结尾更突出了 这位母亲的从容坦然,表 现出其强忍着丧子的巨大 悲痛,以超常的勇气直面 人生,直面生存现实。
小结:
在这篇小说里,情感是一条潜伏的线
索。情感动力驱动着情节的发展。上 面的细节都在暗示着母亲内心难以忍 受的痛苦。读完作品后的我们能够感 到,一定得是“午睡时刻”才能带来 如此强烈而震慑的情感力量。
马尔卡斯的重要作品 有长篇小说代表作《百年 孤独》(被誉为“再现拉丁 美洲历史社会图景的鸿篇 巨著”。 )《家长的没落》 《霍乱时期的爱情》等, 中篇小说《枯枝败叶》 《恶时辰》等,短篇小说 集《蓝宝石般的眼睛》 《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等, 电影文学剧本《绑架》等。
[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 布恩 地亚上校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 个下午。] 这是《百年孤独》的开头。这个开头,以 其采用了从将来回忆过去的倒叙手法,被后人津 津乐道,并被称之为经典式开头。这的确是经典 式杰作,但是其功力不在于新颖的倒叙结构,而 在于它以经典的手法呈示了人生的经典经验。当 人们面对死神的时候,脑海里究竟会想起些什么? 不错,是有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留连。但是 恐怕更多的是对人生旅程的追忆。加西亚· 马尔克 斯的经典开头告诉我们,面对死亡,人最容易走 进自己的记忆深处,人生过程中那些看似平常的 事物和经历在远处熠熠闪光。正是这些事物和经 历,组成了荒诞不经的人生之梦。加西亚· 马尔克 斯从“冰块”开始把人们带进了梦幻人生和魔幻 之旅。
大爱无声——小说《礼拜二午睡时刻》赏析

社会日新月异,人们的认知也随之出现多样化的趋势,特别是在校的中学生。
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成长过程中得到亲人太多的关爱,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他们的心理和生理尚未成熟,却喜欢标新立异;他们喜欢新鲜事物,喜欢广泛接触社会,但有时却不能明辨是非;他们的情绪易波动,很不稳定……这时如果不对他们加以引导,培养其积极健康的情感,后果将不堪设想。
语文教学承担着教书育人的重任,应是培养积极健康情感的主阵地,更何况“情感、态度、价值观”是新课标中特别强调的三维教学目标。
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应加强情感教学,加强对学生积极健康情感的培养。
为把这一目标落实到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如何对教材中的情感教育材料进行恰当的分析,让学生充分领悟并接受其中的感情,并在生活实际中真正受益,这是语文教师应该好好思索的问题。
加西亚·马尔克斯《礼拜二午睡时刻》这篇小说无疑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情感教育的素材。
《礼拜二午睡时刻》讲述的是有关母爱的故事。
话题虽然常见,但作者跳出了前人窠臼,对母爱进行了“冷处理”,在一种看似“平静”的基调中写出了母爱的伟大。
母爱是人间大爱,是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的必不可少的素材,因为“教育的起源和亲情具有天然的关系,这既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特性,也是我国特有的文化和伦理传统使然。
亲情是最质朴、最厚重也是最具有分量的一种情感。
在人类的精神家园里,亲情永远是最能让人感到温馨的花朵;在文学艺术的长廊中,亲情永远是最能触动心灵的题材”(《情感教育与人的和谐发展》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刘晓伟)。
如何让学生深入领悟小说情感,把握“亲情”内蕴,笔者试着对这篇小说的情感处理艺术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分析,主要是以下这三个方面:一、时间推进悬念悬念是艺术创作中造成受众某种急切期待和热烈关切的心理状态的一种手法。
任何题材的中篇故事一般都含有悬念因素,无论是侦破、警匪、探险、武侠、公案或者是伦理道德、婚丧嫁娶,或是感情纠葛。
在故事进程中,悬念设置是否得当,是否巧妙,其作品的魅力是不一样的。
礼拜二午睡时刻

1978年 - 《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纯真的 埃伦蒂拉和残忍的祖母》 1981年 - 《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
1985年 - 《霍乱时期的爱情故事》
1989年 - 《迷宫里的将军》
1992年 - 《奇怪的朝圣者》
1994年 - 《关于爱和其它恶魔》
1996年 - 《绑架》
―魔幻现实主义”
―午睡时刻” ? ―睡意朦胧” 人性处于休眠状态
《礼拜二午睡时刻》
礼拜二?
能从文中看出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吗?
似乎以情感见长的作品总是不甚强调时代特色,因 为作为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情感是最容易获得人类认同 的。 以马尔克思为代表的拉美文学对世界文学尤其是 “文革”后的中国大陆文学有很大启发,一些叙事作品中 蕴涵的时空观念的变革,则被余华、苏童等“先锋小说”
一望无际、两边对称的香蕉林带
海风消失得无影无踪 令人窒息的煤烟气 和铁路平行的狭窄的小道 光秃秃的空地 相居民相混的兵营 住宅的阳台掩映在沾满尘土的棕榈树和玫瑰丛之间 关不上的窗户 简陋的三等车厢 荒凉的车站 车厢外面的香樵林里笼罩着一片神秘的静谧,树阴下显得十分洁 净 两个一模一样的小镇 枯萎的鲜花 贫瘠龟裂的土地 荒凉的旷野 比前面几个更凄凉的小镇 一股又干又热的风 镇上的居民都困乏得睡午觉去了。 有些住房里面太热,居民就在院子里吃午饭,还有些人把凳子靠在 杏树阴下,坐在街上睡午觉。
跨越道德界限,超越种族、地域和时代的阻隔,作用于每
一个读者的神经,使我们感受到那份平凡的心动。
作品同时又揭示了社会混沌和人们蒙昧、冷漠的现象。人 们不明真相、冷漠无情,对个体的死亡不以为然,还自以 为有着道德上的优势。
加西亚 马尔克斯《礼拜二午睡时刻》阅读训练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本,完成6~9题。
礼拜二午睡时刻【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火车刚从震得发颤的橘红色岩石的隧道里开出来。
就进入一望无际、两边对称的香蕉林带。
不时从车窗里吹进一股令人窒息的煤烟气。
这时候正是上午十一点,天气还不太热。
她们是这节简陋的三等车厢里仅有的两名乘客。
小女孩把她们仅有的随身物件——一个塑料食品袋和一束用报纸裹着的鲜花——放在座位上,坐到对面离窗较远的位子上,和母亲正好脸对脸。
母女二人都穿着褴褛的丧服。
女人的眼皮上青筋暴露,身材矮小孱弱。
她一直直挺挺地背靠着椅子,脸上露出那种安贫若素的人惯有的镇定安详。
十二点,天气热起来了。
火车慢腾腾地行驶着。
“梳梳头!”女人说。
小女孩正在梳头的时候,火车的汽笛响了。
女人擦干脖子上的汗水,又用手指抹去脸上的油污。
火车已经开进一个镇子。
“你要是还有什么事,现在赶紧做。
”女人说,“接下来就算渴死了,到哪儿也别喝水。
尤其不许。
”女孩点点头。
这时候,从车窗里已经可以望得见小镇的全貌。
这是八月的一个礼拜二,小镇上阳光灿烂。
小女孩用报纸把鲜花包好,目不转睛地揪着母亲,母亲也用温和的目光看了她一眼。
小镇热得像蒸笼。
镇上的居民都困乏得睡午觉去了,只有车站对面的旅店、酒馆、台球厅以及电报局还在营业。
母女俩下了车,沿着巴旦杏树荫悄悄地走进小镇,尽量不去惊扰别人午睡。
她们径直朝神父的住处走去。
女人用手指甲划了划纱窗,又去叫门。
过了一会儿,有人小心翼翼地问:“谁啊?”“我要找神父。
”地说。
“神父正在睡觉。
”“我有急事。
”女人坚持道。
她的声调很平静,又很执拗。
大门悄悄地打开了一条缝。
“请进吧。
”她们走进一间客厅。
开门的那个又矮又胖的中年妇女把她们引到一条木头长凳前,让她们坐下。
小女孩坐下了,母亲愣愣地站在那里。
除了电风扇的嗡嗡声外,听不到一点儿其他声音。
开门的那个女人从客厅深处的门里走出来。
“他叫你们三点以后再来。
”她把声音压得很低,“他才躺下五分钟。
”“火车三点半就要开了。
课件5:第13课 礼拜二午睡时刻

人物形象
神父—— 善良,富有同情心,能理解人。 ——神父从最初的冷漠到为不知死者姓名而感到 羞耻,到开始怀疑上帝的意志;神父的“道德判 断者”角色可能使小镇上的人也从昏睡的礼拜二 午睡时刻醒来。
礼拜二午睡时刻
马尔克斯
加西亚·马尔克斯
背景知识
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一 )哥伦比亚 魔幻现实主义作家, 1982年获诺贝 尔文学奖。 马尔卡斯的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代表 作《百年孤独》(被誉为“再现拉丁 美洲历史社会图景的鸿篇巨著”。 )
背景知识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20世纪50年代崛起于现代拉丁美洲文坛、富有撼动世界的轰动效 应的现代派文学重要流派。至今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广泛的影响。 魔幻现实主义植根于拉美黑暗统治的现实生活,融汇、吸纳古印 第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的有益经验,将幻象与 现实、神话与现实交融,大胆借鉴象征、寓意、意识流等西方现 代派文学的表现技巧、手法,以鲜明独异的拉美地域色彩为特征。
人物形象
母亲——小偷儿子 母亲:慈爱,自尊,坚强,面对苦难的生活,。
人物形象
神父—— 找出神父几次劝阻母亲去墓地的话语并结合背景加以分析。 ①“天太热了,”“你们可以等到太阳落山嘛!” (背景:神父透过纱窗望了望万里无云的明朗的天空) 普通问候
人物形象
人物环境
小镇上的人是些怎样的人,他们的生活状况如何? 贫穷、冷漠、蒙昧、 混沌。
人物环境
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状况正是如此。殖民者飓 风般的掠夺和政权的反复更使这些国家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人 民除了经受着贫穷之外,个体生命也没有丝毫的保障,普通民众 对个体的生命的死亡不以为然。 在这样的混沌蒙昧、冷漠的背景之下,作者让一个有着生命的尊 严的、敢于直面苦难的母亲走入了人们的视线,以一个有着尊严 的生命的个体来警醒世人。在母亲的精神的感召之下,他们的生 活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
礼拜二午睡时刻课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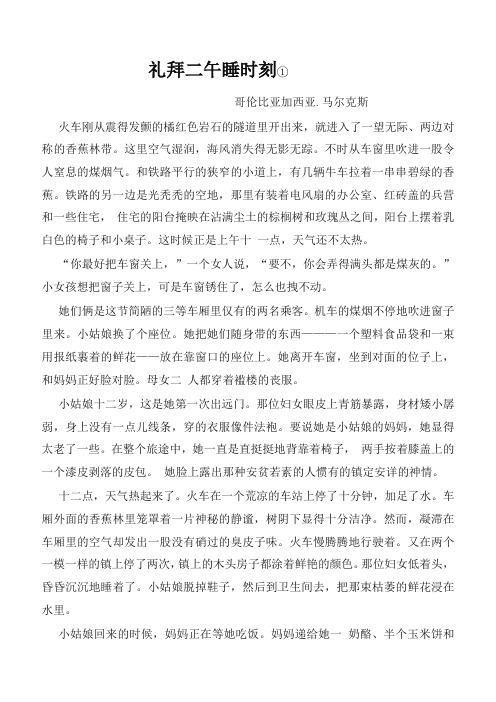
礼拜二午睡时刻①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火车刚从震得发颤的橘红色岩石的隧道里开出来,就进入了一望无际、两边对称的香蕉林带。
这里空气湿润,海风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时从车窗里吹进一股令人窒息的煤烟气。
和铁路平行的狭窄的小道上,有几辆牛车拉着一串串碧绿的香蕉。
铁路的另一边是光秃秃的空地,那里有装着电风扇的办公室、红砖盖的兵营和一些住宅,住宅的阳台掩映在沾满尘土的棕榈树和玫瑰丛之间,阳台上摆着乳白色的椅子和小桌子。
这时候正是上午十一点,天气还不太热。
“你最好把车窗关上,”一个女人说,“要不,你会弄得满头都是煤灰的。
” 小女孩想把窗子关上,可是车窗锈住了,怎么也拽不动。
她们俩是这节简陋的三等车厢里仅有的两名乘客。
机车的煤烟不停地吹进窗子里来。
小姑娘换了个座位。
她把她们随身带的东西———一个塑料食品袋和一束用报纸裹着的鲜花——放在靠窗口的座位上。
她离开车窗,坐到对面的位子上,和妈妈正好脸对脸。
母女二人都穿着褴楼的丧服。
小姑娘十二岁,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
那位妇女眼皮上青筋暴露,身材矮小孱弱,身上没有一点儿线条,穿的衣服像件法袍。
要说她是小姑娘的妈妈,她显得太老了一些。
在整个旅途中,她一直是直挺挺地背靠着椅子,两手按着膝盖上的一个漆皮剥落的皮包。
她脸上露出那种安贫若素的人惯有的镇定安详的神情。
十二点,天气热起来了。
火车在一个荒凉的车站上停了十分钟,加足了水。
车厢外面的香蕉林里笼罩着一片神秘的静谧,树阴下显得十分洁净。
然而,凝滞在车厢里的空气却发出一股没有硝过的臭皮子味。
火车慢腾腾地行驶着。
又在两个一模一样的镇上停了两次,镇上的木头房子都涂着鲜艳的颜色。
那位妇女低着头,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小姑娘脱掉鞋子,然后到卫生间去,把那束枯萎的鲜花浸在水里。
小姑娘回来的时候,妈妈正在等她吃饭。
妈妈递给她一奶酪、半个玉米饼和几块甜饼干,又从塑料袋里给自己拿出来一份。
吃饭的时候,火车徐徐穿过一座铁桥,又经过了一个镇子。
这个镇子也和前两个镇子一模一样,只是在镇子的广场上麇集着一一群人。
礼拜二午睡时刻精品课件

他们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但望这红白的花,却还 能明白看见。花也不很多,圆圆的排成一个圈,不很精神, 倒也整齐。华大妈忙看他儿子和别人的坟,却只有不怕冷 的几点青。
"瑜儿,他们都冤枉了你,你还是忘不了,伤心不过, 今天特意显点灵,要我知道么?"他四面一看,只见一只 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便接着说,"我知道了。 瑜儿——"
节 制 胜
例②:“拖鞋穿上!〞 ……“梳梳头!〞…于…“你要
有什么事,如今赶快做好!往后渴死了,你也放别喝水。
尤其不许哭。〞
纵
以执拗抑制冲动
例③:找到神父之后的一番对话
以平静抑制愤怒
例④:母亲重复地说自己是小偷的母亲时的语调和神
马尔克斯显然不想煽情,只是想抑制地表达一件 本身无需渲染就令人震撼的事情,也许对这样的一位 母亲煽情只是一种罪恶。
神父: 仁慈,富有同情心,能理解源于贫困,并
且从这贫困里锻造出来的自尊的高贵。
环境描写及其作用:
• 1、第一部分,自然环境:以凄凉之景衬悲哀之 情。
• 2、“在临街的大门翻开之前〞段,人文环境: 看似平静的小镇其实暗波涌动,看似镇定的母亲 其实内心悲哀异常;有力地衬托出母亲的形象--自尊、坚强以及面对苦难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伟 大的承受力。
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也是半白头发,褴褛的衣裙; 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篮,外挂一串纸锭,三步一歇的走。 突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 现出些羞涩。
那坟与小栓的坟,一字儿排着,中间只隔一条小路。 华大妈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饭,立着哭了一通,化过纸 锭;心里暗暗地想,"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那老女人彷 徨观望了很久。
那老女人叹一口气,无精打采的收起饭菜;又迟疑 了一刻,终于渐渐地走了。嘴里自言自语的说,"这 是怎么一回事呢?……"
礼拜二的午睡时刻

礼拜二午睡时刻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哥伦比亚】加西亚·
一个女人带着女儿去一个小镇的公墓扫墓
枯萎的鲜花
小偷
儿子
妇人固执地说。她的声调很平静 又很执拗 妇人固执地说。她的声调很平静,又很执拗 固执地说 平静, 她的回答很简短 口气很坚决 她的回答很简短,口气很坚决 简短, 声音还是那么温和 流露出各种各样的复杂表情 声音还是那么温和,流露出各种各样的复杂表情 温和, 女人不动声色的说, 我是他母亲。 女人不动声色的说,“我是他母亲。” 不动声色的说 忍住悲痛, 忍住悲痛,两眼直直盯着神父 悲痛 她毫不迟疑地、详尽准确地作了回答 毫不迟疑地 详尽准确地作了回答 看到她们根本没有要哭 看到她们根本没有要哭的意思 没有要哭的意思 那个女人神色自如 那个女人神色自如地继续说 神色自如地继续说 好像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直到这个时候,那个女人好像还不知道 直到这个时候,那个女人好像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从小女孩的手里把鲜花夺过去,就向大门走去 从小女孩的手里把鲜花夺过去, 挽着小姑娘的手朝大街走去 挽着小姑娘的手朝大街走去
固执 平静 执拗 简短 坚决 温和 不动声色 毫不迟疑 详尽准确 神色自如
枯萎的鲜花
简陋的三等车厢 一个塑料食品袋 褴褛的丧服
小偷
爱与剥落的皮包
一个女人带着女儿去一个小镇的公墓扫墓
小偷
儿子
如果儿子不是小偷, 如果儿子不是小偷,却…… 如果儿子是小偷,却是因为…… 如果儿子是小偷,却是因为……
哎!上帝的意志是难以捉摸的
?
贫困 混乱 蒙昧 冷漠
人性的高贵就是在这样 悲剧、荒唐的社会生活 悲剧、 保持应有的爱与尊严
1967年 1967年 - 《百年孤独》 百年孤独》 1975年 家长的没落》 1975年 - 《家长的没落》 1970年 落难海员的故事》 1970年 - 《落难海员的故事》 1978年 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纯 1978年 - 《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纯 真的埃伦蒂拉和残忍的祖母》 真的埃伦蒂拉和残忍的祖母》 1981年 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 1981年 - 《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
《礼拜二午睡时刻》

1、 加西亚· 马尔克斯
(1928一 )哥伦比亚魔幻 现实主义作家, 1982年获 诺贝尔文学奖和哥伦比亚语 言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马 尔克斯作品的主要特色是幻 想与现实的巧妙结合,以此 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审视 人生和世界。这种把现实与 幻景溶为一体的创作方法, 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 加西亚· 马尔克斯(1928一
)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是 20 世纪 50 年代崛 起于现代拉丁美洲文坛、富有撼动世界的 轰动效应的现代派文学重要流派。至今在 世界文坛上有着广泛的影响。魔幻现实主 义植根于拉美寡头黑暗统治的现实生活中, 融汇、吸纳古印第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 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有益经验,将幻象与 现实、神话与现实水乳交融,大胆借鉴象 征、寓意、意识流等西方现代派文学各种 表现技巧、手法,以鲜明独异的拉美地域 色彩为特征。代表作品有马尔克斯的《百 年 孤 独 》 等 。
3、请同学们思考作者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该 文得到这么高的评价? (表现了情感与道德的纠结,显示了爱的情感 力量 ,像母爱的伟大执着,神父的宽容,人类 悲悯的情感等。)
正 音:
窒( zhì )息 拽( zhuài ) 褴褛( lán )( lǚ ) 孱( chán )弱 麇( qún )集 龟( jūn )裂 趿( tā )拉 拗
小结:
在这篇小说里,情感是一条 潜伏的线索。情感动力驱动 着情节的发展。上面的细节 都在暗示着母亲内心难以忍 受的痛苦。读完作品后的我 们能够感到,一定得是“午 睡时刻”才能带来如此强烈 而震慑的情感力量。
三、探究学习
1、探究作品的情感与思想的蕴涵及社会价值 问:小说中,作家描写了死去的“小偷”的母亲在 世人面前的镇静以及神父在这位母亲面前的不安。这种 镇静与不安的“倒错”,说明了什么? 小结:巴尔扎克曾说:“母亲的心是一个深渊,在 她的最深处你总会得到宽恕。”神父在这位坚强隐忍 的母亲面前也汗颜了,母亲战胜了道德,这种感情超 越时空,一个被人唾弃的小偷,在他的母亲那找到了 尊严,只有漫无边际的母爱才使她面对道德舆论的时 候依然一如既往的表现自己的母爱。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礼拜二午睡时刻加西亚·马尔克斯火车刚从震得发颤的橘红色岩石的隧道里开出来,就进入了一望无际、两边对称的香蕉林带。
这里空气湿润,海风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时从车窗里吹进一股令人窒息得煤烟气。
和铁路平行的狭窄的小道上,有几辆牛车拉着一串串碧绿的香蕉。
铁路的另一边是光秃秃的空地,那里有装着电风扇的办公室、红砖盖的兵营和一些住宅,住宅的阳台掩映在沾满尘土的棕榈树和玫瑰丛之间,阳台上摆着乳白色的椅子和小桌子。
这时候正是上午十一点,天气还不太热。
“你最好把车窗关上,”一个女人说。
“要不,你会弄得满头都是煤灰的。
”小女孩想把窗子关上,可是车窗锈住了,怎幺也拽不动。
她们是这节简陋的三等车厢里仅有的两名乘客。
机车的煤烟不停地吹进窗子来。
小姑娘换了个座位。
她把她们随身带的东西——一个塑料食品袋和一束用报纸裹着的鲜花——放在靠窗口的座位上。
她离开车窗,坐到对面的位子上,和妈妈正好脸对脸。
母女二人都穿著褴褛的丧服。
小姑娘十二岁,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
那位妇女眼皮上青筋暴露,身材矮小孱弱,身上没有一点儿线条,穿的衣服像件法袍。
要说她是小姑娘的妈妈,她显得太老了一些。
在整个旅途中,她一直是直挺挺地背靠着椅子,两手按着膝盖上的一个漆皮剥落的皮包。
她脸上露出那种安贫若素的人惯有的镇定安详的神情。
十二点,天气热起来了。
火车在一个荒凉的车站上停了十分钟,加足了水。
车厢外面的香蕉林里笼罩着一片神秘的静谧,树荫下显得十分洁净。
然而,凝滞在车厢里的空气却发出一股没有硝过的臭皮子味。
火车慢腾腾地行驶着。
又在两个一模一样的镇上停了两次,镇上的木头房子都涂着鲜艳的颜色。
那位妇女低着头,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小姑娘脱掉鞋子,然后到卫生间去,把那束枯萎的鲜花浸在水里。
小姑娘回来的时候,妈妈正在等她吃饭。
妈妈递给她一片奶酪、半个玉米饼和几块甜饼干,又从塑料袋里给自己拿出来一份。
吃饭的时候,火车徐徐穿过一座铁桥,又经过了一个镇子。
这个镇子也和前两个镇子一模一样,只是在镇子的广场麇集着一群人。
在炎炎的烈日下,乐队正在演奏一支欢快的曲子。
镇子的另一端,是一片贫瘠龟裂的土地。
这里再也看不到香蕉林了。
那位妇女停下来不吃了。
“把鞋穿上!”她对小女孩说。
小姑娘向窗外张望了一下。
映入她眼帘的还是那片荒凉的旷野。
从这里起,火车又开始加快速度。
她把剩下的饼干塞进袋子里,连忙穿上鞋。
妈妈递给她一把梳子。
“梳梳头!”妈妈说。
小姑娘正在梳头的时候,火车的汽笛响了。
那个女人擦干脖子上的汗水,又用手抹去脸上的油污。
小姑娘刚梳完头,火车已经开进一个镇子。
这个镇子比前面几个要大一些,然而也更凄凉。
“你要是还有什幺事,现在赶快做好!”女人说。
“往后就是渴死了,你也别喝水。
尤其不许哭。
”女孩子点点头。
窗外吹进一股又干又热的风,夹带着火车的汽笛声和破旧车厢的哐当哐当声。
女人把装着吃剩下来的食物的塑料袋卷起来,放进皮包里。
这时候,从车窗里已经可以望见这个小镇的全貌。
这是八月的一个礼拜二,小镇上阳光灿烂。
小女孩用湿漉漉的报纸把鲜花包好,稍微离开窗子远一些,目不转睛地瞅着母亲。
她母亲也用慈祥的目光看了她一眼。
汽笛响过后,火车减低了速度。
不一会儿就停了下来。
车站上空无一人。
在大街对面杏树荫下的便道上,只有弹子房还开着门。
小镇热得像个蒸笼。
母女俩下了车,走过荒凉的车站,车站地上墁的花砖已经被野草挤得开始裂开。
她俩横穿过马路,走到树荫下的便道上。
快两点了。
在这个时候,镇上的居民都困乏得睡午觉去了。
从十一点起,商店、公共机关、学校就关了门,要等到将近四点钟火车返回的时候才开门。
只有车站对面的旅店和旅店附设的酒馆和弹子房以及广场一边的电话局还在营业。
这里的房子大多是按照香蕉公司的式样盖的,门从里面关,百叶窗开得很低。
有些住房里面太热,居民就在院子里吃午饭。
还有些人把凳子靠在杏树荫下,坐在街上睡午觉。
母女俩沿着杏树荫悄悄地走进小镇,尽量不去惊扰别人的午睡。
她们径直朝神父家走去。
母亲用手指甲敲了敲纱门,等了一会儿又去叫门。
屋子里电风扇嗡嗡作响,听不见脚步声。
又过了一会儿,只听见大门轻轻地吱扭一声,在离纱门不远的地方有人细声慢语地问:“谁啊?”母亲透过纱门朝里张望了一眼,想看看是谁。
“我要找神父,”她说。
“神父在睡觉呢!”“我有急事,”妇女固执地说。
她的声调很平静,又很执拗。
大门悄悄地打开了一条缝,一个又矮又胖的中年妇女探身出来。
她肤色苍白,头发是铁青色的,戴着一副厚厚的眼睛,眼睛显得特别小。
“请进来吧!”她一面说着,一面把门打开。
她们走进一间花香袭人的客厅。
开门的那个妇女把她们引到一条木头长椅前,用手指了指,让她们坐下。
小女孩坐了下去,她母亲愣愣地站在那里,两只手紧紧抓住皮包。
除了电风扇的嗡嗡声外,听不到一点其他的声音。
开门的那位妇女从客厅深处的门里走出来。
“他叫你们三点钟以后再来,”她把声音压得低低地说。
“他才躺下五分钟。
”“火车三点半就要开了,”母亲说她的回答很简短,口气很坚决,不过声音还是那么温和,流露出各种各样的复杂感情。
开门的女人第一次露出笑容。
“那好吧!”她说。
客厅深入的门又关上的时候,来访的女人坐到她女儿身边。
这间窄小的客厅虽然简陋,但是很整洁。
一道木栏杆把屋子隔成两半儿。
栏杆里边有一张简朴的办公桌,上面铺着一块用胶布做的桌布。
桌上有一台老式的打字机,旁边放着一瓶花。
桌子后面是教区的档案。
看得出这间办公室是一位单身妇女给收拾的。
房间深处的门开了。
神父用手帕揩拭着眼睛,从里面走出来。
他一戴上眼睛,马上可以看出他是那位开门的妇女的哥哥。
“你有什么事?”他问。
“我要借用一下公墓的钥匙。
”女人说。
女孩子坐在那里,把那束鲜花放在膝盖上,两只脚交叉着伸在椅子底下。
神父瞅了女孩一眼,又看了看那个女人,然后又透过纱窗望了望万里无云的明朗的天空。
“天太热了,”他说。
“你们可以等到太阳落山嘛!”女人默默地摇了摇头。
神父从栏杆里面走出来,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皮面笔记本、一支蘸水钢笔和一瓶墨水,然后坐在桌子旁边。
他的头已经谢顶了,两手却是毛茸茸的。
“你们想去看哪一座墓?”他问道。
“卡络斯·森特诺的墓。
”女人回答说。
“谁?”“卡络斯·森特诺。
”女人重复了一遍。
神父还是听不明白。
“就是上礼拜在这儿被人打死的那个小偷,”女人不动声色地说,“我是他母亲。
”神父打量了她一眼。
那个女人忍住悲痛,两眼直直地盯住神父。
神父的脸刷地一下子红了。
他低下头,准备填一张表。
一边填表一边询问那个女人地姓名、住址等情况,她毫不迟疑地、详尽准确地做了回答,仿佛是在念一份写好的材料。
神父头上开始冒汗了。
女孩子解开左脚上的鞋扣,把鞋褪下一半,用脚后跟踩在鞋后帮上。
然后把右脚的鞋扣解开,也用脚趿拉着鞋。
事情发生在上礼拜一临晨三点钟,离开这里几条街的地方。
寡妇雷薇卡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一所堆满东西的房子里。
那一天,在细雨的淅沥声中雷薇卡太太听见有人从外边撬临街的门。
她慌忙起来,摸着黑从衣箱里拿出一支老式手枪。
这支枪自从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那时候起就没有人用过。
雷薇卡太太没有开灯,就朝大厅走去。
她不是凭门锁的响声来辨认方向的。
二十八年的独身生活在她身上产生的恐惧感使她不但能够想象出门在哪里,而且能够准确地知道门锁的高度。
她两手举起枪,闭上眼睛,猛一扣扳机。
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打枪。
枪响之后,周围立刻又寂然无声了,只有细雨落在锌皮屋顶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
她随即听到在门廊的水泥地上响起了金属的碰击声和一个低哑的、有气无力的、极度疲惫的呻吟声:“哎呦,我的妈!”清晨,在雷薇卡太太家的门前倒卧着一具男尸。
死者的鼻子被打得粉碎,他穿着一件花条的法兰绒上衣,一条普通的裤子,腰中没有系皮带,而是系着一根麻绳,光着脚。
镇上没有人认识他是谁。
“这么说他叫卡络斯·森特诺。
”神父填完表,嘴里咕咕哝哝地说。
“卡络斯·森特诺,”那个女人说,“是我的独生子。
”神父又走到柜子跟前。
在柜子里钉子上挂着两把大钥匙,上面长满了锈。
在小女孩的想象中公墓的钥匙就是这个样子;女孩子的妈妈在小的时候也这么想过。
神父本人大概也曾经设想过圣彼得的钥匙就是这么个样子。
神父把钥匙摘下来,放在栏杆上那本打开的笔记本上,用食指指着写了字的那一页上的一处地方,眼睛瞧着那个女人,说:“在这儿签个字吧!”女人把皮包夹在腋下,胡乱地签上了自己地名字。
小姑娘拿起鲜花,趿拉着鞋走到栏杆前,两眼凝视着妈妈。
神父吁了一口气。
“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上正道吗?”女人签字回答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神父看看那个女人,又看看那个孩子。
看到她们根本没有要哭的意思,感到颇为惊异。
那个女人还是神色自如的继续说:“我告诉过他不要偷人家的东西吃,他很听我的话。
过去他当拳击手,有时候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
”“他没有办法,把牙全部拔掉了。
”女孩子插嘴说。
“是的,”母亲证实说,“那时候,我每吃一口饭,都好像看到礼拜六晚上她们打我儿子时的那个样子。
”“哎!上帝的意志是难以捉摸的,”神父说。
神父本人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一则是因为人生经验已经多少把他变成一个怀疑主义者了,再则是因为天气实在太热。
神父叮嘱她们把头包好,免得中暑。
他连连打着哈欠,几乎就要睡着了。
他睡意朦胧地指点母女俩怎样才能找到卡络斯·森特诺的墓地。
还说回来的时候不要叫门,把钥匙从门缝下塞进来就行了。
要是对教堂有什么施舍,也放在那里。
那个女人注意地谛听着神父的讲话,然后向他道了谢,脸上没有丝毫的笑容。
在临街的大门打开之前,神父就觉察到有人把鼻子贴在纱门上往里瞧。
那是一群孩子。
大门敞开后,孩子们立刻一哄而散。
在这个钟点,大街上通常是没有人的。
可是现在不光是孩子们在街上,在杏树下面还聚集着一群群的大人。
神父一看大街上乱哄哄的反常样子,心里顿时就明白了。
他悄悄地把大门关上。
“等一会儿走吧,”他说。
说话的时候,他没有看那个女人。
神父的妹妹从里面的门里出来。
她在睡衣外面又披上了一件黑色的上衣,头发散披在肩上。
她一声不响的瞅了瞅神父。
“怎么样?”他问。
“人们都知道了。
”神父的妹妹喃喃地说。
“那最好还是从院子的门出去。
”神父说。
“那也一样,”他妹妹说,“窗子外面净是人!”直到这个时候,那个女人好像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她透过纱门朝大街上看了看,然后从小女孩的手里把鲜花夺过去,就向大门走去。
女孩子跟在她的后面。
“等到太阳落山再去吧!”神父说。
“会把你们晒坏的,”神父的妹妹在客厅深处一动也不动地说。
“等一等,我借给你们一把阳伞。
”“谢谢!”那个妇女回答说。
“我们这样很好。
”她挽着小姑娘的手朝大街走去。
读《礼拜二午睡时刻》后记:琴剑斋主人学生集体全文朗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礼拜二午睡时刻》一文,我在黑板上写下:母亲最后为什么不顾神父的善意,坚持从大门出去,坚持面对可能让她遭受屈辱的围观人群?因为在母亲心中,她对儿子的爱光明正大,母爱从来不需在阳光下躲闪,也是母爱让她勇敢,不惧怕那些自以为有着道德优越感的人们投来的异样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