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中的史实性与符号性及在当代的衍变
《故事新编》 知识清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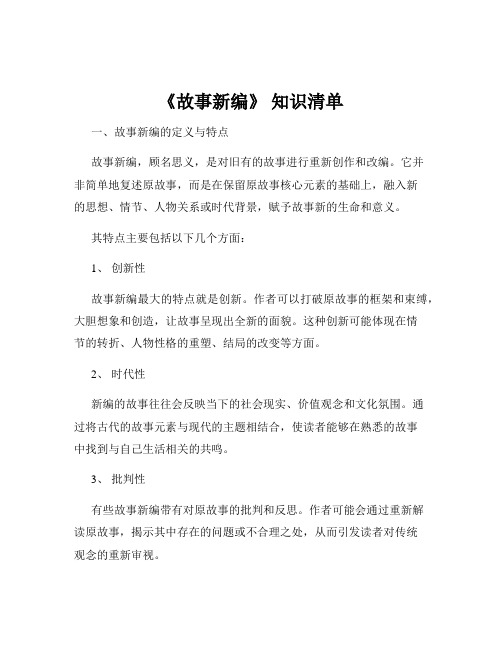
《故事新编》知识清单一、故事新编的定义与特点故事新编,顾名思义,是对旧有的故事进行重新创作和改编。
它并非简单地复述原故事,而是在保留原故事核心元素的基础上,融入新的思想、情节、人物关系或时代背景,赋予故事新的生命和意义。
其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创新性故事新编最大的特点就是创新。
作者可以打破原故事的框架和束缚,大胆想象和创造,让故事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这种创新可能体现在情节的转折、人物性格的重塑、结局的改变等方面。
2、时代性新编的故事往往会反映当下的社会现实、价值观念和文化氛围。
通过将古代的故事元素与现代的主题相结合,使读者能够在熟悉的故事中找到与自己生活相关的共鸣。
3、批判性有些故事新编带有对原故事的批判和反思。
作者可能会通过重新解读原故事,揭示其中存在的问题或不合理之处,从而引发读者对传统观念的重新审视。
4、趣味性由于故事新编充满了新奇和变化,往往能够吸引读者的兴趣,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阅读体验。
二、故事新编的常见类型1、古代神话传说新编例如,对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神话故事进行重新演绎,赋予神话人物新的性格和使命,或者将神话故事的背景设定在现代社会。
2、历史故事新编以历史事件和人物为蓝本,重新构建情节和人物关系。
比如,对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进行全新的解读,或者假设秦始皇穿越到现代会发生什么。
3、经典文学作品新编像《红楼梦》《西游记》等经典文学作品,作者可以选取其中的某个片段或人物,进行二次创作。
比如,想象林黛玉在现代职场中的遭遇。
4、民间故事新编民间故事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其进行新编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民间文化。
比如,将牛郎织女的故事改编成一个关于爱情与选择的现代故事。
三、故事新编的创作方法1、保留核心元素在进行故事新编时,首先要明确原故事中的核心元素,如主要人物、关键情节、主题思想等,并在新的创作中予以保留。
这些核心元素是故事的灵魂,失去它们就可能使新编的故事失去原有的魅力。
2、改变视角尝试从不同的人物视角来讲述故事,或者采用全知全能的视角来展现更丰富的情节。
《故事新编》: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梦幻

《故 事 新 编 : 史 与 现 实 交 织 的 梦 幻 历
。吴 小 东
摘 要:梦幻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 故事新编 采用了 “ 只取一点 因由,随意点染’ ’的方法,用丰富的想象力 将历史与现实交织在一起 ,显示 了鲁迅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文学要求。
文 学 审美 精 神 的灵 魂 。
在 一起 , 创 造 了 既有 梦 幻 感 义 有 真 实 性 的 艺 术 世 界 。在
《 事 新编 ・ 言》 中 , 鲁迅 论述 了 自己创 作 历 史小 说 的方 注 释 : 故 序
法 是 “ 事 有 时 也有 一 点 旧书 上 的根 据 ,有 时 却不 过 信 口开 叙 一 合 。 如 《 攻 》取 材 于战 国时 的思 想 家墨 子 的事 迹 ,他 主 张 非 族 面 对 日本 的 入 侵 ,社 会 中 充斥 了 虚 浮 的风 气 ,鲁 迅 说 :
了大 王 ,实 现 了复仇 。 《 非攻 》塑 造 了思想 家 墨子 的形象 , 行一 致 的 实干 家 。 《 水 》描 写 了古 代 的 治水 英雄 禹 ,讽刺 理 了文 化 山 上的 学 者和 水 利局 里 的 大 员们 。 《 薇 》刻 画 了伯 采 夷和 叔齐 这 两 个 人物 ,他 们 饿 死在 首阳 山 ,是 作 为吃 人 的正 了道 家 自然 无 为 思想 谬 误 的一 面 ,揭 示 它 违反 了人 类 社 会在 大 员们 吃 的是 面 包 ,讲 的是奇 异 食 品博 览会 和 莎 士 比亚 ,小 虚 构 叙事 和奇 思 异 想方 面 所 体现 出的天 才 的 想象 力 ,构 成 了
在 《 故事 新 编 》 中 ,作者 将 幻想 的与 现 实 的、 想象 的 与
的 、形象 的与 理 论 的等 等 ,各 种不 同的 因 素都 创造 性 地 融合
毕业论文论鲁迅故事新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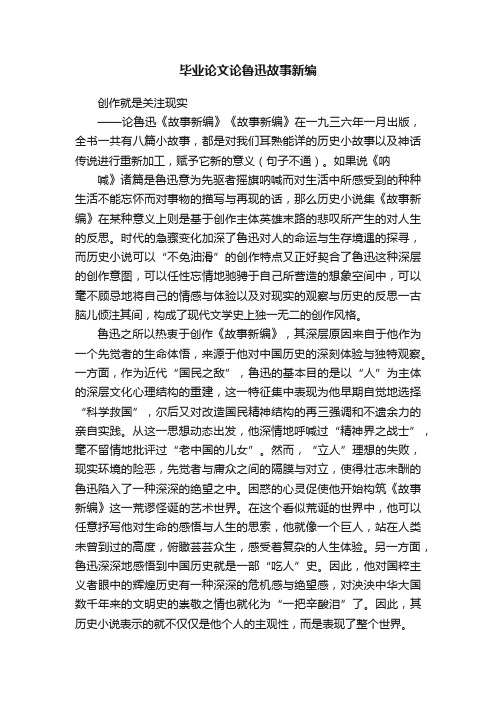
毕业论文论鲁迅故事新编创作就是关注现实——论鲁迅《故事新编》《故事新编》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出版,全书一共有八篇小故事,都是对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小故事以及神话传说进行重新加工,赋予它新的意义(句子不通)。
如果说《呐喊》诸篇是鲁迅意为先驱者摇旗呐喊而对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种种生活不能忘怀而对事物的描写与再现的话,那么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基于创作主体英雄末路的悲叹所产生的对人生的反思。
时代的急骤变化加深了鲁迅对人的命运与生存境遇的探寻,而历史小说可以“不免油滑”的创作特点又正好契合了鲁迅这种深层的创作意图,可以任性忘情地驰骋于自己所营造的想象空间中,可以毫不顾忌地将自己的情感与体验以及对现实的观察与历史的反思一古脑儿倾注其间,构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创作风格。
鲁迅之所以热衷于创作《故事新编》,其深层原因来自于他作为一个先觉者的生命体悟,来源于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体验与独特观察。
一方面,作为近代“国民之敌”,鲁迅的基本目的是以“人”为主体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重建,这一特征集中表现为他早期自觉地选择“科学救国”,尔后又对改造国民精神结构的再三强调和不遗余力的亲自实践。
从这一思想动态出发,他深情地呼喊过“精神界之战士”,毫不留情地批评过“老中国的儿女”。
然而,“立人”理想的失败,现实环境的险恶,先觉者与庸众之间的隔膜与对立,使得壮志未酬的鲁迅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绝望之中。
困惑的心灵促使他开始构筑《故事新编》这一荒谬怪诞的艺术世界。
在这个看似荒诞的世界中,他可以任意抒写他对生命的感悟与人生的思索,他就像一个巨人,站在人类未曾到过的高度,俯瞰芸芸众生,感受着复杂的人生体验。
另一方面,鲁迅深深地感悟到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吃人”史。
因此,他对国粹主义者眼中的辉煌历史有一种深深的危机感与绝望感,对泱泱中华大国数千年来的文明史的崇敬之情也就化为“一把辛酸泪”了。
因此,其历史小说表示的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主观性,而是表现了整个世界。
论《故事新编》的历史文化态度

论《故事新编》的历史文化态度作为鲁迅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颇有意味地选择了“历史事件”作为题材,进行“演义”:在《呐喊》和《彷徨》中,鲁迅给我们展现的都是近现代中国的形形色色——不论人物,还是事件,都取材于身边现实生活的“一手资料”;而《故事新编》则不同,虽然考据者们纷纷指出各种细节的现实来处,但无法否认的是,它已从前期的现实题材的描摹变为“历史”事件的“重写”。
既然是重写,必然伴随着作者的选择与建构,而在这些行为的背后,体现的是重写者对其重写对象的心理态度、情感倾向。
那么,理解《故事新编》的历史文化态度,是我们解读《故事新编》的一项基础工作,是研究《故事新编》的一把重要钥匙。
同时,《故事新编》备受关注和颇受争议的、时而宏大壮丽、慷慨激昂,时而又古今杂糅、油滑不恭的书写笔调,呈现出的也正是《故事新编》历史文化态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从鲁迅对历史的态度入手,把《故事新编》放入鲁迅的整个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之中阐释,《故事新编》研究中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才能得到回答。
一、鲁迅对历史的钟情与对历史话语的不满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家,据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连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第110页。
从远古到晚近,一整套体例严整的钦定官史和各路旁逸斜出的野史笔记,都显示着这个古老民族历史学的发达和对历史浓厚的探究兴趣。
“今夕的对立和互补,是贯串中国文化始终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9页。
在中国的传统文人心中,历史从来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国之利器。
近代以来,朴学日兴,而浙东犹盛,“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⑨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523、1页。
从小就在这样文化氛围下长大的鲁迅,对历史可谓情有独钟,我们留心鲁迅的阅读史,会见到,他从六岁起便熟读《鉴略》,并且直到去世前后,所购置的《四部丛书》正续编、《二十五史》还不断送到,参见许广平:《研究鲁迅文学遗产的几个问题》,《十年携手共艰危》,河北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127页。
《故事新编》的现代意义——以《理水》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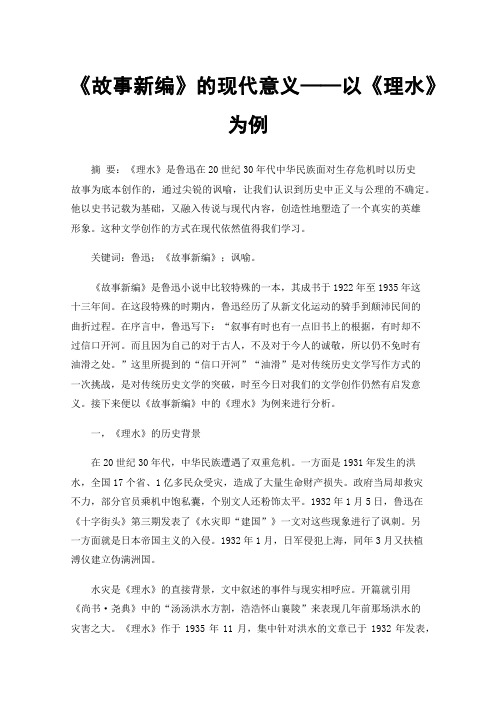
《故事新编》的现代意义——以《理水》为例摘要:《理水》是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面对生存危机时以历史故事为底本创作的,通过尖锐的讽喻,让我们认识到历史中正义与公理的不确定。
他以史书记载为基础,又融入传说与现代内容,创造性地塑造了一个真实的英雄形象。
这种文学创作的方式在现代依然值得我们学习。
关键词:鲁迅;《故事新编》;讽喻。
《故事新编》是鲁迅小说中比较特殊的一本,其成书于1922年至1935年这十三年间。
在这段特殊的时期内,鲁迅经历了从新文化运动的骑手到颠沛民间的曲折过程。
在序言中,鲁迅写下:“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
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
”这里所提到的“信口开河”“油滑”是对传统历史文学写作方式的一次挑战,是对传统历史文学的突破,时至今日对我们的文学创作仍然有启发意义。
接下来便以《故事新编》中的《理水》为例来进行分析。
一,《理水》的历史背景在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遭遇了双重危机。
一方面是1931年发生的洪水,全国17个省、1亿多民众受灾,造成了大量生命财产损失。
政府当局却救灾不力,部分官员乘机中饱私囊,个别文人还粉饰太平。
1932年1月5日,鲁迅在《十字街头》第三期发表了《水灾即“建国”》一文对这些现象进行了讽刺。
另一方面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
1932年1月,日军侵犯上海,同年3月又扶植溥仪建立伪满洲国。
水灾是《理水》的直接背景,文中叙述的事件与现实相呼应。
开篇就引用《尚书·尧典》中的“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来表现几年前那场洪水的灾害之大。
《理水》作于1935年11月,集中针对洪水的文章已于1932年发表,而《理水》其实更对应日本入侵,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之际,来势汹汹的洪灾正是对侵略者的隐喻。
接下来“只在文化山上,还聚集着许多学者,他们的食粮,是都从奇肱国用飞车运来的,因此不怕缺乏,因此也能够研究学问。
《故事新编》的文类性质、创作方法、意义与文学本体阐释

《故事新编》的文类性质、创作方法、意义与文学本体阐释赵井春【摘要】本文从素材与题材的性质区别、创作方法的具体表现手段与“油滑”的关系、文本单义与复义阐释方法的差异等多个视角,对《故事新编》的文类性质、创作方法和意义阐释提出了新的看法,并以《奔月》为案例,提出了《新编》回归文学本体阐释的新思路.【期刊名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年(卷),期】2013(000)002【总页数】7页(P53-59)【关键词】《故事新编》;文类性质;创作方法;本体解释【作者】赵井春【作者单位】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贵州遵义563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10.97鲁迅《故事新编》(以下简称《新编》)的文类性质、创作方法、意义阐释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和分歧[1]。
20世纪90年代,在文体论、新批评、巴赫金文化诗学、后现代主义思想影响下,《新编》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开拓和挖掘,其成果已在苏懿等撰写的《近十年<故事新编>研究综述》[2]和姜振昌等撰写的《新世纪鲁迅研究综述》[3]得到较为全面的反映,但学界认识分歧依然很大。
本文试图从素材与题材的性质区别、创作方法的具体表现手段与“油滑”的关系、文本单义与复义阐释方法的差异等角度,对以上争论的基本问题进行梳理。
一、《新编》文类的性质问题在《新编》诸争论中,文类的性质是首要的、最重要的问题。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就有“历史小说”论、“新的历史小说”论、“讽刺小说”论、“寓言式的短篇小说”论、“以‘故事’形式写出的杂文”论等争论[1]。
九十年代之后,文类问题还在争论,但有所发展,代表性的有“新历史小说”论、“文化寓言”论和“后现代主义边缘文本”论。
“新历史小说”论以姜振昌为代表,认为“新历史小说就是杂文化与历史小说的结合”[5]。
“文化寓言”体论以孙刚为代表,他认为《新编》各叙事文本共生着“三种异质性文本”,即它是由历史文本、自传性文本和现实性文本的结合体,这三个文本统一于文化的寓义中,它以“寓言”的方式呈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世界[6]。
从鲁迅的故事新编中看 他的人事态度和现实主义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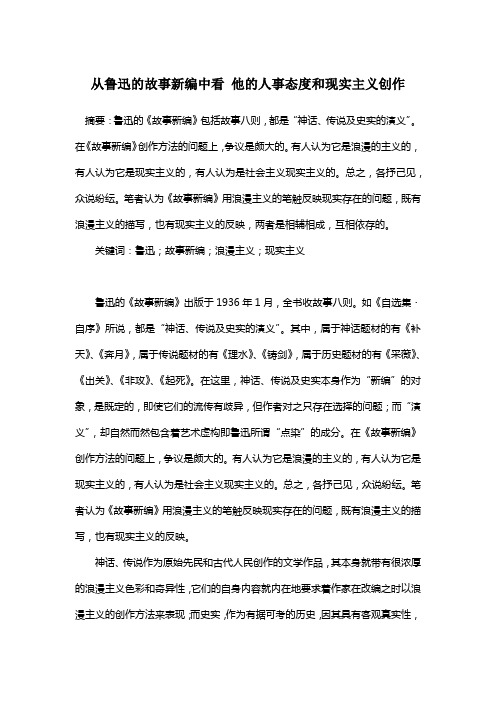
从鲁迅的故事新编中看他的人事态度和现实主义创作摘要:鲁迅的《故事新编》包括故事八则,都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
在《故事新编》创作方法的问题上,争议是颇大的。
有人认为它是浪漫的主义的,有人认为它是现实主义的,有人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总之,各抒己见,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故事新编》用浪漫主义的笔触反映现实存在的问题,既有浪漫主义的描写,也有现实主义的反映,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
关键词:鲁迅;故事新编;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鲁迅的《故事新编》出版于1936年1月,全书收故事八则。
如《自选集・自序》所说,都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
其中,属于神话题材的有《补天》、《奔月》,属于传说题材的有《理水》、《铸剑》,属于历史题材的有《采薇》、《出关》、《非攻》、《起死》。
在这里,神话、传说及史实本身作为“新编”的对象,是既定的,即使它们的流传有歧异,但作者对之只存在选择的问题;而“演义”,却自然而然包含着艺术虚构即鲁迅所谓“点染”的成分。
在《故事新编》创作方法的问题上,争议是颇大的。
有人认为它是浪漫的主义的,有人认为它是现实主义的,有人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总之,各抒己见,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故事新编》用浪漫主义的笔触反映现实存在的问题,既有浪漫主义的描写,也有现实主义的反映。
神话、传说作为原始先民和古代人民创作的文学作品,其本身就带有很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奇异性,它们的自身内容就内在地要求着作家在改编之时以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表现;而史实,作为有据可考的历史,因其具有客观真实性,先天地倾向于现实主义,但由于作家在改编它们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原则和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导向现实主义,又可以导向浪漫主义。
《故事新编》从开手创作到结集成书,前后经过13年。
鲁迅在回顾小说创作的时候,曾经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明其艺术概括的手段是:“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
古今杂糅手法在当代电影中的现代变异——《故事新编》与中国当代

第20卷第1期Vol.20No.1荆㊀楚㊀学㊀刊AcademicJournalofJingchu2019年2月Feb.2019收稿日期:2018-12-26基金项目:荆楚理工学院2015年科研项目 鲁迅历史小说的当代传承与革新 (SK201514)作者简介:聂俊(1980-)ꎬ男ꎬ湖北荆门人ꎬ荆楚理工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ꎬ文学硕士ꎮ主要研究方向:影视文学㊁现当代小说㊁影视传媒ꎮ古今杂糅手法在当代电影中的现代变异«故事新编»与中国当代穿越电影之比较聂㊀俊(荆楚理工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ꎬ湖北荆门㊀448000)摘要:鲁迅作为文体家㊁小说家ꎬ在其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开创了 故事新编 体与 油滑 艺术ꎬ其核心为后现代主义的戏仿㊁拼贴等艺术手法ꎬ具体到技术层面则主要为古今杂糅ꎬ其作为戏仿的艺术表现形式延续到当代ꎬ对穿越电影产生了不小影响ꎬ但同时在当代大众传播与消费文化的背景之下也已发生了现代变异ꎮ古今杂糅㊁时空并存的构建已由间接性的文字媒介转变成了更为直观的视听语言 镜头组接㊁场景设计㊁服装与道具等ꎻ古今叙事时空界限不明的杂糅转变成了叙事时空界限分明的 穿越 ꎻ借古讽今㊁针砭时弊的现实关怀ꎬ伴有自我灭亡的绝望反抗㊁启蒙者悲凉孤独的切身体验也转变为娱乐至上直至后来对爱情㊁人生与人性的思考ꎮ这些变异与创新正是在继承«故事新编»古今杂糅手法的基础上ꎬ为更适应电影这一视听艺术形式与当代社会现实而进行的革新ꎮ关键词:古今杂糅ꎻ时空并存ꎻ«故事新编»ꎻ穿越电影中图分类号:J905㊀㊀文献标志码:A㊀㊀文章编号:1672-0768(2019)01-0045-06㊀㊀伴随着新世纪以来网络的兴起与发展ꎬ当代小说创作㊁影视创作兴起了一股穿越热潮ꎬ引起众多关注ꎬ穿越往往被看成一种新的创作手法与潮流ꎮ其实不然ꎬ作为小说㊁影视的创作手法早已有之ꎬ只不过当时并没有形成一股热潮ꎬ也还未出现 穿越 一词ꎬ往往是以 古今杂糅 来指称ꎬ或是称之为科幻小说㊁科幻电影ꎮ前者如刘慈欣的«时间移民»ꎬ后者如«古今大战秦俑情»等ꎮ此类小说或影视剧如追根溯源ꎬ可一直上溯到鲁迅«故事新编»中的戏仿㊁拼贴等后现代艺术手法ꎬ具体到文本叙述的技术层面则为古今杂糅ꎬ只不过这一手法在当代小说㊁影视作品的运用中已与«故事新编»大不相同ꎬ甚至已经出现明显的现代变异ꎮ一㊁戏仿㊁拼贴与古今杂糅戏仿(Parody)最初是语言学上的一种修辞方式ꎬ近代以来ꎬ被引入小说㊁诗歌等文学创作领域ꎬ逐渐从一个局部技巧发展为一种成熟的文学体式ꎮ戏仿通常指作家㊁艺术家在创作时刻意模仿业已存在的话语方式㊁经典模式㊁文学范式ꎬ将其置于不适宜甚至相反的语境中ꎬ以达到对模仿对象进行讽刺㊁曲解或者颠覆的目的[1]ꎮ拼贴 (collage)一词源于绘画ꎬ指 将不同内容或不同质地的材料碎片(如报纸㊁画报㊁布头㊁铁屑㊁木片㊁线绳等)拼接粘贴在一起的构图方法 [2]ꎬ后被借用到文学创作中ꎬ成为现代主义派别使用的一种写作技法ꎬ并成为随后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普遍采用的一种叙事策略[3]ꎮ 总体上说ꎬ拼贴指并置那些相异特征的元素 ꎬ 即把不同元素的碎片黏合在一起 [4]ꎮ当戏仿中的刻意模仿是模仿具有相异特征的元素并将其并置于同一叙事文本时ꎬ就在戏仿的同时形成拼贴ꎬ成为戏仿的一种 极端化 表现形式ꎻ而在并置相异特征元素的拼贴过程中ꎬ有意54的㊁目的明确的对传统小说形式㊁题材乃至经典文本本身进行戏谑性拼贴则在拼贴的同时完成戏仿ꎬ即有意的拼贴可能成为戏仿ꎮ鲁迅的«故事新编»就存在大量的有意拼贴与戏仿ꎬ具体而言ꎬ主要是文本叙述过程中的古今杂糅ꎮ博考文献的史实典籍㊁今人今事的踪迹ꎬ生僻拗口的古语㊁通熟易懂的现代白话等古今异质元素被戏谑性模仿㊁并置拼贴于同一叙述文本之中ꎬ构成了«故事新编»古今杂糅㊁时空并存的叙事时空ꎮ二㊁«故事新编»中古今杂糅㊁时空并存的叙事时空在«故事新编»中ꎬ两种叙事时空并存于同一叙事文本之中ꎬ一为古代ꎬ一为现代ꎮ古代叙事时空主要由素材来源与文本中的叙事语言营造而成ꎮ«故事新编»中的八篇是 神话㊁传说及史实的演义 [5]469ꎬ全部都取材于古代ꎮ «补天»和«奔月»是演述我们祖先关于太古的神话:人的创造㊁天的修补和嫦娥的奔月ꎮ«理水»所演义的是关于古皇帝 禹 的传说ꎻ«采薇»是关于殷末周初伯夷叔齐的传说ꎻ«铸剑»是一个报仇故事的传说ꎬ时间约在东周ꎻ«出关»是关于老子的传说ꎬ因为采取了 孔子问礼于老子 的说法ꎬ所以传说的时间也在东周ꎻ«非攻»是关于墨子的传说ꎻ«起死»是关于庄子的传说ꎬ传说中的故事均出在战国ꎮ [6]152无论是神话传说ꎬ还是历史事实ꎬ经过长期的文化积淀ꎬ已成为一种经典并融入民族文化之中ꎬ此类素材已自带历史语境ꎬ而由此创作的作品自然不可避免的具有古代叙事时空特点ꎮ此外ꎬ«故事新编»的语言同样也构建了古代叙事时空ꎬ无论是叙述语言ꎬ还是人物语言ꎬ所涉 古 语众多ꎮ前者有 奇肱国 [7]33㊁ 简放 [7]37㊁ 启节 [7]37㊁ 天道无亲ꎬ常与善人 [7]64 圣人之道ꎬ为而不争 [7]108等ꎬ后者有 裸裎淫佚ꎬ失德蔑礼败度ꎬ禽兽行ꎮ国有常刑ꎬ惟禁! [7]12 即以其人之道ꎬ反诸其人之身 ꎮ [7]25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ꎬ可谓孝矣ꎮ [7]45 道可道ꎬ非常道ꎻ名可名ꎬ非常名ꎮ无名ꎬ天地之始ꎻ有名ꎬ万物之母ꎮ [7]107等ꎬ无论是叙述语言ꎬ还是人物语言都将文本叙事引入了特定的历史语境ꎬ并与自带历史语境的素材来源共同构建了 古代 的叙事时空ꎮ但在«故事新编»中ꎬ古代叙事时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ꎬ而是与 现代 的叙事时空同时并存㊁相互依存的ꎮ«故事新编»中现代叙事时空主要由以现代白话为主的叙述语言构建而成ꎮ«补天»中的 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ꎬ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ꎻ那一边ꎬ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ꎮ然而伊并不理会谁是下去ꎬ和谁是上来ꎮ地上都嫩绿了ꎬ便是不很换叶的松柏也显得格外的娇嫩ꎮ桃红和青白色的斗大的杂花ꎬ在眼前还分明ꎬ到远处可就成为斑斓的烟霭了ꎮ [7]5这一段文字乃是第三人称的叙述者语言ꎬ带有明显的现代浪漫主义色彩ꎬ采用的是现代白话ꎬ属于现代语言系统ꎮ此类叙述者语言其余七篇同样存在ꎬ甚至是对古籍的直译铺排ꎬ«铸剑»的出典 原文大约二三百字ꎬ我是只给铺排ꎬ没有改动 [8]30ꎮ 听哪! 她严肃地说ꎬ 你的父亲原是一个铸剑的名工ꎬ天下第一ꎮ 眉间尺凝神细视ꎬ这才仿佛看见长五尺余ꎬ却并不见得怎样锋利ꎬ剑口反而有些浑圆ꎬ正如一片韭叶ꎮ [7]82-84这一部分基本就是对古籍«列异传»中«三王冢»[9]248-249的直译与铺排ꎮ前文所举叙述语言中的 古 语同样也是融入了现代白话为主的叙述语言ꎬ两者合二为一ꎮ如 他们的食粮ꎬ是都从奇肱国用飞车运来的 [7]33ꎬ 这才传来了新闻ꎬ说禹是确有这么一个人的ꎬ正是鲧的儿子ꎬ也确是简放了水利大臣ꎬ三年之前ꎬ已从冀州启节ꎬ不久就要到这里了 [7]37ꎬ 况且 天道无亲ꎬ常与善人 ꎬ或者竟会有苍术和茯苓之类也说不定ꎮ [7]64 各人想着自己的事ꎬ待到讲到 圣人之道ꎬ为而不争 ꎬ住了口了ꎬ还是谁也不动弹ꎮ [7]108通观此类叙述语言ꎬ整体上为现代语言系统ꎬ但众多 古 语杂糅其中ꎬ从而形成了古今杂糅的叙述语言ꎮ而就人物语言来看ꎬ虽 古 语众多ꎬ但现代语言也不少ꎮ综观而言ꎬ«故事新编»中的人物语言可分为两类:现代语言与古代文言ꎮ«补天»中有一段对话:㊀㊀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 伊顺便的问ꎮ呜呼ꎬ天降丧ꎮ 那一个便凄凉可怜的说ꎬ 颛顼不道ꎬ抗我后ꎬ我后躬行天讨ꎬ战于郊ꎬ天不祐德ꎬ我师反走ꎬ什么? 伊向来没有听过这类话ꎬ非常诧异了ꎮ我师反走ꎬ我后爰以厥首触不周之山ꎬ64折天柱ꎬ绝地维ꎬ我后亦殂落ꎮ呜呼ꎬ是实惟够了够了ꎬ我不懂你的意思ꎮ 伊转过脸去了ꎬ却又看见一个高兴而且骄傲的脸ꎬ也多用铁片包了全身的ꎮ那是怎么一回事呢? 伊到此时才知道这些小东西竟会变这么花样不同的脸ꎬ所以也想问出别样的可懂的答话来ꎮ人心不古ꎬ康回实有豕心ꎬ觑天位ꎬ我后躬行天讨ꎬ战于郊ꎬ天实祐德ꎬ我师攻战无敌ꎬ殛康回于不周之山ꎮ什么? 伊大约仍然没有懂ꎮ[7]10女娲和士兵的语言显然属于两个异质的语言系统ꎬ前者为现代口语ꎬ后者为文言古语ꎬ其语体内涵截然不同ꎬ却并存于同一叙事时空ꎬ从而形成了古今杂糅ꎬ时空并存的特点ꎮ«故事新编»以素材来源与叙事语言为媒介共同创造了一个古代与现代并存的艺术世界ꎬ从而开创了 古 今 杂糅的叙事共同体这一独特的小说样式ꎮ当代小说中的新历史小说㊁穿越小说甚至科幻小说无不受此影响ꎬ 古 今 杂糅的艺术手法不仅影响到小说创作ꎬ甚至延伸到了视听艺术 电影的创作ꎬ尤其是穿越题材的电影ꎬ但已发生现代变异ꎮ三㊁中国当代穿越电影对«故事新编»的继承与变革中国最早的穿越电影是1989年的«古今大战秦俑情»ꎬ此后伴随着大众传播与消费文化的到来以及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ꎬ穿越电影迅速兴起ꎬ成为一种热潮ꎮ对穿越电影进行文本细读ꎬ不难发现ꎬ当代穿越电影似乎继承了«故事新编»中戏仿㊁拼贴尤其是古今杂糅的艺术基因ꎮ鲁迅作为20世纪30年代的启蒙者ꎬ感受到了启蒙者的孤独悲凉以及存在世界的荒诞虚无ꎬ因而将此种主体经验通过«故事新编»中的戏仿㊁拼贴以及古今杂糅艺术手法表达出来ꎬ构成了对经典㊁崇高的颠覆与消解ꎮ中国当代穿越电影流行于大众传播与消费文化时代ꎬ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ꎬ精英传播时代的传播主体 引导者已不存在ꎬ其传播主体已位移于普通大众ꎬ精英文化也已让位于消费文化ꎬ文化已降为消费的对象ꎬ其主要功能已不再是思想引导ꎬ而是消费娱乐ꎮ无论是传播ꎬ还是文化ꎬ其所具有的崇高与神圣在这一时代都已被颠覆与消解了ꎮ与此伴随的中国当代穿越电影则在艺术手法上继承了«故事新编»中戏仿㊁拼贴尤其是古今杂糅的艺术基因ꎬ但同时也有与这一时代相适应的变革与创新ꎮ具体而言ꎬ中国当代穿越电影对«故事新编»的继承主要体现在叙事时空的设置上ꎬ«故事新编»为古今杂糅㊁时空并存ꎬ而在穿越电影中同样涉及古代与现代两个时空ꎬ两者同样并存ꎮ其时空转换通常是通过 穿越 而实现ꎬ或是回到过去ꎬ或是走入当下ꎬ或是迈向未来ꎬ或是将其综合运用ꎮ 回到过去 即主角由当代现实穿越到已经流逝的时空ꎬ或为历史的古代ꎬ或为记忆中的当代ꎻ 走入当下 即主角由历史古代穿越到当代现实社会ꎻ 迈向未来 即主角由当代现实穿越到目前还未知的未来时空ꎮ«故事新编»往往通过自带语境的素材㊁自带语系的语言将古今两个时空的人物㊁事件进行创新性的戏说仿制ꎬ拼贴在同一文本之中ꎬ而穿越电影同样也在其叙事过程中将古今不同时空的人㊁事通过戏说仿制ꎬ拼贴在同一叙事文本之中ꎬ只不过其具体实现的主要媒介已不再是素材来源与语言ꎬ而是影视作品中独有的视听手段ꎮ电影是视听艺术ꎬ其叙事媒介主要为镜头㊁画面与声音ꎬ因此穿越电影往往通过镜头组接㊁画面造型与配音在电影中营造出逼真的时空穿越情节ꎬ直接作用于观众的视觉与听觉ꎬ相较于小说而言ꎬ更为直接㊁逼真ꎮ在具体的文本叙事中ꎬ此类电影中的穿越往往是因某一偶然事件(古建筑中的奇遇㊁旅途中飞机失事㊁电梯失事㊁车祸㊁梦境㊁许愿等)[10]的触发或长生㊁转世而引起ꎮ早期穿越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中的主角蒙天放与韩冬儿本为秦朝时的男女ꎬ前者因救秦始皇而被封官赐剑ꎬ后者乃为准备东渡蓬莱寻取长生仙药的征召童女ꎬ两人因互相爱慕㊁偷尝禁果ꎬ最终被秦始皇赐死ꎮ蒙天放被泥封为俑ꎬ置于皇陵ꎬ但因其服下了金丹而长生不老ꎬ直至20世纪30年代飞机失事坠入秦始皇陵ꎬ沉睡地下两千多年的蒙天放也随之复苏ꎮ韩冬儿则自投窑炉ꎬ殉情而死ꎬ但也并未消逝ꎬ而是转世成为20世纪30年代的三流影星朱莉莉ꎬ甚至直至20世纪90年代ꎬ长生不老的蒙天放又遇到了朱莉莉轮回转世的日本女郎山口靖子ꎮ蒙天放是因长生而从秦朝穿越到现代ꎬ冬儿则是转世从秦朝穿越到现代[11]ꎮ74无论是长生ꎬ还是转世ꎬ两人的穿越在电影叙事中主要依靠是电影中的叙事语言即视听语言 镜头剪辑㊁画面造型与声音设计ꎬ而不再是小说中的叙事语言 文字ꎬ具体到电影这一叙事文本来说ꎬ其时空转换叙事主要是通过镜头组接实现的ꎮ«古今大战秦俑情»所涉时空主要有三ꎬ一为秦朝ꎬ一为20世纪30年代ꎬ一为20世纪90年代ꎮ在秦朝与20世纪30年代这两个时空的转换过程中ꎬ叙事文本采用黑场来组接前后两个镜头ꎬ前一个镜头是身穿古代铠甲的蒙天放被泥封为俑ꎬ后一个镜头是具有现代气息的飞机迎面而来并配以字幕说明ꎮ而在20世纪30年代与20世纪90年代之间的时空转换中ꎬ则采用了天空的空镜头来进行衔接ꎬ之前是蒙天放战胜盗墓贼从陵墓中爬出走入一片烟雾缥缈之中ꎬ之后则是迎面而来的旅游团汽车驶入博物馆ꎮ综观而言ꎬ三个叙事时空并存于同一叙事文本之中ꎬ尤其是在第二个叙事时空中更能体现出叙事文本中的古今杂糅㊁时空并存ꎮ在20世纪30年代ꎬ秦朝时的蒙天放从沉睡中醒来穿越到现代ꎬ但其思想㊁习惯㊁语言仍停留在古代ꎬ身着古代铠甲㊁手持古剑㊁语用古语ꎬ似乎仍停留在秦朝这一历史时空ꎬ但在现代叙事时空ꎬ飞机㊁汽车㊁照相机㊁貂皮大衣㊁手枪无不体现现代气息ꎬ因而叙事文本构建出一个古今杂糅㊁时空并存的叙事时空ꎮ但从叙事顺序来说ꎬ«古今大战秦俑情»采用的是单一方向的叙事ꎬ从先秦时期的秦朝到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再到20世纪90年代ꎬ这一叙事顺序完全是按照历史的时间顺序来进行的ꎬ仅仅只有最后蒙天放的回忆才在古代与现代的时空中进行交叉叙事ꎬ因而从整体上看ꎬ«古今大战秦俑情»虽有时空并存ꎬ但并不突出ꎮ相比之下ꎬ2005年上映的电影«神话»则更能体现出古今杂糅㊁时空并存ꎮ在«神话»中ꎬ梦境与现实交替显现㊁古代与现代两个时空并存㊁交替叙事ꎮ«神话»的古今时空并存叙事同样不以文字为媒介ꎬ而是以电影的视听语言为媒介ꎬ只不过在古今两个时空转换的镜头组接中采用的是梦境这一手法ꎬ但在具体的时空构建之中就不得不依靠视听语言的另外两个元素 画面造型与声音设计ꎮ画面造型主要包括场景设计㊁构图㊁光影与色彩等内容ꎬ而与具体时空构建密切相关的则是场景设计ꎮ 场景设计构成了观众对整部影片最重要的视觉印象ꎬ因为它必须一秒钟带领观众来到电影的世界中 [12]114ꎬ也即电影中的叙事时空ꎮ具体而言ꎬ场景设计主要涉及环境㊁服装与道具ꎮ不同的环境将会把观众引入不同的叙事时空ꎬ如宫殿㊁皇宫将观众引入古代叙事时空ꎬ高楼大厦㊁咖啡厅等现代元素将观众引入现代叙事时空ꎮ电影«神话»的文本叙事不断在山川古道㊁现代化船屋㊁古代陵墓㊁河流等环境中转换ꎬ构建古代与现代两个叙事时空ꎬ并存于同一叙事文本ꎬ并不断在梦境与现实中交替叙事ꎬ直至片尾ꎬ在古墓中与等待千年的玉漱公主相见ꎬ两个叙事时空才最终交汇ꎬ融为一体ꎬ构成整个文本的叙事空间ꎮ但环境还不能独立构建电影的叙事时空ꎬ还需与服装㊁道具共同配合完成ꎮ服装 作为一种视觉语言 [12]120往往 显示影片中特定的年代㊁民族㊁地区和情境 [12]120ꎬ而 道具是和电影场景㊁剧情㊁人物相关联的一切物件的总称 [12]126ꎬ通常 能体现场景环境气氛㊁地区和时代特色 [12]126ꎬ从而与环境㊁服装相互配合㊁三位一体共同构建电影中的叙事空间ꎮ«神话»中的叙事空间主要有二ꎬ古代秦朝与现代21世纪ꎮ前者的环境㊁服装㊁道具充满古意ꎬ山川古道㊁马车㊁秦将铠甲㊁飘逸的公主服㊁红缨头盔㊁青铜古剑㊁军中旌旗等古代元素共同营造出古代叙事时空ꎻ后者的环境㊁服装㊁道具现代气息浓郁ꎬ现代船屋㊁电脑电视㊁篮球㊁高尔夫㊁风衣㊁鸭舌帽则构建出现代叙事时空ꎮ梦中的古代叙事时空与现实的叙事时空在片尾的古墓之中融为一体ꎬ古人㊁今人并置拼贴共同显现ꎬ古今时空并存于世ꎬ从而共同构成文本的叙事时空ꎮ四、古今并存叙事时空的深层内涵无论是鲁迅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ꎬ还是中国的当代穿越电影ꎬ都通过各自的叙事语言或媒介构建了古今两种时空ꎮ在这两种叙事文本之中ꎬ同样两种时空并存ꎬ但具体比较ꎬ又各具特点ꎮ在鲁迅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中ꎬ古今两个时空无明显界限ꎬ而是杂糅融合为一体ꎬ或古人说今语ꎬ或文言白话杂糅ꎬ其原因在于鲁迅 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ꎬ来做短篇小说 [7]1ꎬ其直接目的在于以古讽今㊁批判国民劣根性ꎬ讽刺社会时局ꎬ如«奔月»中对高长虹事件的影射[7]30ꎬ«理水»对北平文教界建议定 文化城 的讽刺[7]49-50ꎻ或是反叛 旧道 传统ꎬ«补天» 消解了神话中神的神性 [13]ꎬ«奔月»«理水»«铸剑» 淡化了传说中84英雄的非凡性 [13]ꎬ«采薇»«出关»«非攻»«起死»颠覆了现实中的正统性[13]ꎬ而更为深层的目的在于批判的同时努力建构ꎮ在反叛传统㊁颠覆正统㊁消解神性的同时ꎬ对神话㊁历史㊁传说中的英雄人物㊁古圣先贤进行价值重估㊁再造ꎬ最终实现破而后立㊁启蒙大众㊁改造国民性的理念ꎬ有着深刻的人文关怀与批判精神ꎻ以古今杂糅的拼贴㊁戏仿等荒诞的形式和内容构成了对叙述文本中操用现代白话的古人与现代白话的原本发出者的双面讽刺ꎬ同时表现了 以天下为沉浊ꎬ不可与庄语 的荒诞现实ꎬ传达出内心日益加重的孤独悲凉与荒诞感ꎮ«补天»中满口仁义道德的 小东西 们破坏了天地ꎬ女娲累死在修补天地的艰辛劳动中ꎬ 小东西 们却攻伐抢掠ꎻ«采薇»«起死»«出关»把伯夷㊁叔齐㊁庄子㊁老子等传统文化代表与现代日常世俗生活拼贴并置ꎬ由此揭示传统文化的荒诞性和不合理性ꎻ«奔月»承接神话㊁续写了羿射日后的日常生活ꎬ善射的英雄失去了表演舞台ꎬ昔日英雄受到邻居老太太的嘲笑㊁弟子的背叛和妻子的离弃ꎬ从而陷入孤独㊁困顿的境地ꎬ神话英雄被世俗消解ꎬ理想只能尘封[14]ꎮ鲁迅深刻认识到: 启蒙者面对的中国现实就像后羿面对的世俗世界ꎬ战斗与反抗是没有意义的ꎬ现实的琐碎和平庸最终反射出英雄存在的荒诞ꎮ [14] «理水»中的大禹为民除水害三过家门而不入ꎬ当其艰苦劳作时ꎬ被周围的人讥笑ꎻ当治水成功时ꎬ这些人却对他阿谀奉承ꎬ治水的英雄最终在一片叫好声中被同化ꎮ [14] 做起祭祀和法事来ꎬ是阔绰的ꎻ衣服很随便ꎬ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ꎬ是要漂亮的ꎮ [7]48这些奋斗者㊁战斗者的价值就这样被颠覆与消解了ꎮ«故事新编»对神话历史进行 古今杂糅 的戏仿㊁拼贴是20世纪30年代启蒙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现实社会的讽喻ꎬ传达出启蒙者身处其中的孤独与绝望以及反抗绝望的战斗精神ꎮ[14]中国当代早期穿越电影则与此相异ꎬ虽有古今杂糅的异质拼贴㊁时空并存ꎬ但已发生现代变异ꎮ早期穿越电影偏爱历史穿越ꎬ即从当代回到古代或从古代穿越到当代ꎬ其叙事模式也大多是借用现代知识在历史时空中领先一步ꎬ或是利用古代能力在当代时空成就人生ꎬ或收获爱情ꎬ或成就事业ꎬ或改变地位ꎮ这一叙事模式的目的无外乎现实中的心理缺憾在电影这一虚构的叙事文本中获得心理补偿ꎮ在现实生活中ꎬ任何人都或多或少存在遗憾ꎬ或爱情或事业ꎬ或金钱或地位ꎬ总认为 失去的 和 得不到的 是最好的ꎬ人们往往无力改变既成事实ꎬ只能正视与接受ꎬ而这些现实中的心理缺憾却能在虚构的艺术世界里实现ꎬ以此获得心理上的满足ꎬ弥补现实缺憾ꎮ正是如此ꎬ穿越电影才会引起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的内心共鸣ꎬ从而流行热播ꎮ与此同时ꎬ穿越电影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推动下ꎬ良莠不齐的跟风之作大量出现ꎬ商品化㊁娱乐化日趋突显ꎬ历史㊁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等都已成为娱乐对象ꎮ«大话西游»中 孙悟空要杀师父唐三藏 ㊁孙悟空与铁扇公主有私情 ㊁ 孙悟空与白骨精结婚生子 以及 同为一体的青霞㊁紫霞二仙子反目成仇 等一系列情节有违伦理道德ꎬ经典名著«西游记»被颠覆得支离破碎㊁面目全非ꎬ善恶美丑㊁正邪之分被颠覆了ꎬ尊师重道㊁兄弟相亲等传统美德被消解了[15]ꎮ或许ꎬ在穿越电影看来ꎬ尽善尽美和秩序规范都是无足轻重的ꎬ只需获得商业成功㊁娱乐大众即可ꎮ但自从2011年国家广电总局颁布限令遏制 穿越 风之后ꎬ这一现象有所转变ꎬ出现了更多的现代穿越电影ꎬ此类穿越电影所涉时空并不涉及古代的历史时空ꎬ而是穿越到主角自己曾经的青春年代或自己的未来ꎬ或是对自己的青春梦想重做一次选择ꎬ或是对成长人生的反思ꎬ涉及爱情㊁亲情㊁友情ꎬ人心与人性ꎮ«夏洛特烦恼»中的夏洛特在梦中重回高中时代后所获得的成功与再次人生选择[16]ꎻ«重返20岁»中年过七旬的沈梦君因照相变回20岁后在当代社会中进行又一次的人生选择[17]ꎻ«乘风破浪»中的徐太浪因车祸重回父亲的生活年代后对父亲的理解[18]ꎻ«解忧杂货店»中身处人生迷途的三个年轻人通过 穿越 时光隧道的写信咨询与回信答疑这一过程寻找到了人生方向ꎬ做出了人生选择[19]ꎻ«给19岁的我自己»中暗恋莫晓枫10年的阳艺雪通过莫晓枫留给自己的遗物 装满书信的 神秘木盒 与过去时空连接ꎬ不断地与19岁的自己鸿雁传书ꎬ追回错失的爱情[20]ꎻ«超时空同居»中2018年的谷小焦与1999年的陆鸣两人时空重叠ꎬ意外住在同一个房间㊁并为赚钱共商大计ꎬ逐渐日久生情ꎬ最终ꎬ外在 拜金 实则纯真善良的谷小焦选择了一无所有㊁同甘共苦的纯真男孩陆鸣ꎬ而怀才不遇㊁清贫如洗的陆鸣也最终战胜了曾走上错误人94。
解读鲁迅故事新编的书

解读鲁迅故事新编的书(实用版3篇)目录(篇1)一、鲁迅及其作品概述1.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作品以描写社会现实和人民疾苦为主。
2.《故事新编》是鲁迅的一部小说集,通过虚构的故事来反映现实社会中的问题。
3.《故事新编》中的故事风格各异,包括科幻、神话、讽刺等,展现出鲁迅独特的创作才华。
二、新编的特点和价值1.《故事新编》中的故事以现代视角重新诠释经典作品,赋予了新的意义。
2.鲁迅通过虚构的故事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批判,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3.《故事新编》中的故事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展现了鲁迅独特的文学风格。
三、故事分析1.《出关》中,鲁迅描写了老子与孔子的对话,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思想矛盾。
2.《在酒楼上》中,鲁迅描写了他在酒楼上回忆过去的场景,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现实的无奈。
3.《铸剑》中,鲁迅通过一个古代复仇故事,表达了对社会不公的批判和对正义的追求。
正文(篇1)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以描写社会现实和人民疾苦为主。
《故事新编》是鲁迅的一部小说集,其中的故事以现代视角重新诠释了经典作品,赋予了新的意义。
通过虚构的故事来反映现实社会中的问题,展现出鲁迅独特的创作才华。
在新编的特点和价值方面,《故事新编》中的故事以现代视角重新诠释了经典作品,赋予了新的意义。
鲁迅通过虚构的故事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批判,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同时,《故事新编》中的故事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展现了鲁迅独特的文学风格。
在故事分析方面,《出关》中,鲁迅描写了老子与孔子的对话,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思想矛盾。
《在酒楼上》中,鲁迅描写了他在酒楼上回忆过去的场景,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现实的无奈。
目录(篇2)一、鲁迅与《故事新编》1.鲁迅与《故事新编》的背景介绍:《故事新编》是鲁迅先生的一部小说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于2006年。
2.鲁迅与《故事新编》的主要内容:《故事新编》收录了鲁迅先生八篇以古代神话和传说为题材的小说,包括《补天》、《奔月》、《铸剑》、《出关》、《理水》、《采薇》、《起死》、《奔月》和《铸剑》。
论《故事新编》的后现代主义研究

on
ofOld Stories
has
on
and criticism.Looking back
many
fruitful results.and has not
many aspects.With the
deepening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o
and
the West,the researcher’S theoretical vision has been expanded,and tried
与历史小说的合集川21和“新历史小说"口1等等;对“油滑”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在探讨文本的创作手法的过程中,逐步摆脱“现实主义”的单一性,而注意到了文 本创作上的多样性与多元化特色。总而言之,研究者围绕《故事新编》的文类归属、 创作手法,以及对“油滑"的评价等方面展开的争鸣,不仅拓展了《故事新编》研 究的广度和深度,而且丰富了《故事新编》的研究史。而更重要的是,这种莫衷一 是的争鸣现象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融洽的研究氛围与开放的研究思路,有效地引导 研究者从多种角度审视文本,并积极回应关于《故事新编》的文类归属、创作手法 等诸多方面的争议。毫无疑问,研究者对这些争议的回应构成了《故事新编》研究 史中的主要内容。而《故事新编》的后现代主义研究有幸成为其中的重要分支。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于上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90年代风靡我国文化界及文 学理论界,受到先锋评论家的青睐,并逐步应用到文本研究和阐释实践之中,为解 读文本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视角。而《故事新编》只是研究者应用后现代主 义文学理论进行解读实践的对象性文本之一。
《故事新编》基因变异原因探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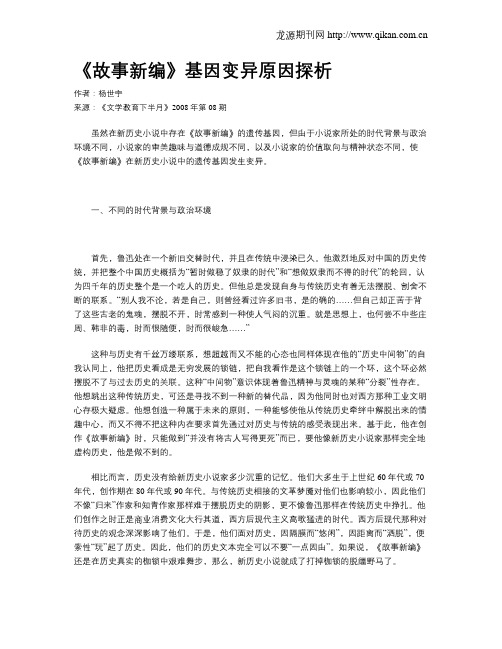
《故事新编》基因变异原因探析作者:杨世宇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08年第08期虽然在新历史小说中存在《故事新编》的遗传基因,但由于小说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政治环境不同,小说家的审美趣味与道德成规不同,以及小说家的价值取向与精神状态不同,使《故事新编》在新历史小说中的遗传基因发生变异。
一、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政治环境首先,鲁迅处在一个新旧交替时代,并且在传统中浸染已久。
他激烈地反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并把整个中国历史概括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轮回,认为四千年的历史整个是一个吃人的历史。
但他总是发现自身与传统历史有着无法摆脱、割舍不断的联系。
“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
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这种与历史有千丝万缕联系,想超越而又不能的心态也同样体现在他的“历史中间物”的自我认同上,他把历史看成是无穷发展的锁链,把自我看作是这个锁链上的一个环,这个环必然摆脱不了与过去历史的关联。
这种“中间物”意识体现着鲁迅精神与灵魂的某种“分裂”性存在。
他想跳出这种传统历史,可还是寻找不到一种新的替代品,因为他同时也对西方那种工业文明心存极大疑虑。
他想创造一种属于未来的原则,一种能够使他从传统历史牵绊中解脱出来的情趣中心,而又不得不把这种内在要求首先通过对历史与传统的感受表现出来。
基于此,他在创作《故事新编》时,只能做到“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而已,要他像新历史小说家那样完全地虚构历史,他是做不到的。
相比而言,历史没有给新历史小说家多少沉重的记忆。
他们大多生于上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创作期在80年代或90年代。
与传统历史相接的文革梦魇对他们也影响较小,因此他们不像“归来”作家和知青作家那样难于摆脱历史的阴影,更不像鲁迅那样在传统历史中挣扎。
他们创作之时正是商业消费文化大行其道,西方后现代主义高歌猛进的时代。
新世纪《故事新编》研究述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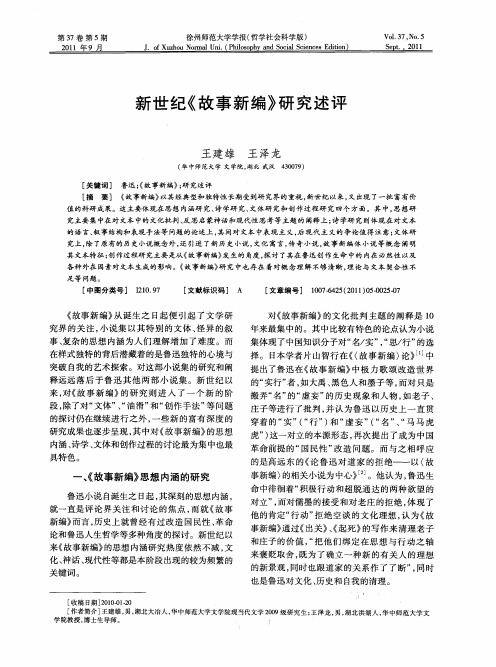
究主要 集 中在 对文本 中的文化批判、 思启蒙神话 和现代性 思考等主题 的阐释上 ; 学研 究则体现在 对文本 反 诗 的语言、 叙事 结构和表现手 法等 问题 的论 述上 , 间对 文本 中表现 主义 , 现代主 义的争论值 得注 意; 其 后 文体研
关 系 的变 化上 都可 见 出一个 很 明显 的神话 消失 的
过 程 。这 种神 话 的 消解 与 “ 四” 五 神话 性 的消 解 具 有 同步 性 。 同时 , 迅 对 自我 及 知识 分 子 的理 鲁
的终结和现代性 的开端 。因此宫爱玲提 出《 故事 新编 》 貌 似 游 戏 之笔 的 ‘ 滑 ’ 最 大 的现 实 中“ 油 是
命 中徘 徊着 “ 积极 行 动 和 超脱 通 达 的 两种 欲 望 的 对 立 ” 而对儒 墨 的接受 和 对 老庄 的拒 绝 , 现 了 , 体 他 的肯 定 “ 动 ” 绝 空 谈 的文 化 理 想 , 为 《 行 拒 认 故
鲁迅小说 自 诞生之 日 , 起 其深刻的思想 内涵 , 就一 直是 评 论 界 关 注 和讨 论 的 焦 点 , 就 《 事 而 故 新编》 而言, 历史上就 曾经有过改造 国民性 、 革命 论和 鲁迅 人生 哲学 等多 种角 度 的探 讨 。新世 纪 以
的心态 , 自我 解构 、 自我消解 的做 法 为这种 探 讨增
添 了不少 难度 。
关 于现代 文 学 的 “ 现代 性 ” 的研 究 依 然 方 兴 未艾 , 是研 究 《 也 故事 新 编 》 的一 个重 要 视 角 。宫
杨 泉 则认 为 , 文本 在消解 、 判 历史 的 同时也 批
浅谈鲁迅《故事新编》的艺术手法

浅谈鲁迅《故事新编》的艺术手法浅谈鲁迅《故事新编》的艺术手法摘要:《故事新编》逆时序的运用使文章在平铺直叙中顿生波澜,跌宕而浑然一体。
逆时序造成的时间空白,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的交互使用使历史故事更加地贴近现实生活,“油滑”也起了推手的作用,使《故事新编》这本历史小说超越了时代的局限而越显真实。
鲁迅艺术手法的高超从此处可见一斑。
关键词:《故事新编》艺术手法逆时序圆形人物扁形人物鲁迅毫无疑问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不仅仅是因为他对于国民性及其他问题的深刻批判与细致思考,还在于他对文学有巨大贡献。
在倡导使用白话文功绩的同时,他留给我们更多的是他的作品和精神。
从他的作品中,我们首先应当看到他高超的艺术手法。
本文仅从逆时序与人物塑造上浅谈《故事新编》中鲁迅的艺术手法。
一、从逆时序的使用看《故事新编》的艺术手法“时序”这一术语是在杰拉尔?日奈特的《叙事文的时况》一文中第一次被提出来的。
他说:“叙事作品是一个具有双重时间性的序列……所讲述的事情的时况和叙述的时况(所指的时况和能指的时况)。
这个二元性不仅可以造成时况上的扭曲……叙事作品的功能之一即是把一个时况兑现到另一个时况中。
”故事时序和叙事文时序之间各种形式的不协调称为逆时序。
逆时序的使用在《故事新编》中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手法,八篇文章中运用各有差异,总的说来,前面三篇可以代表整本书的此种用法,因此只详说前三篇。
1.《补天》中的逆时序状况《补天》中的时序或第一叙事文,以女娲做事发展的先后为准,即:A1:醒来;B2:造人;C3:补天;D4:死去;是A1―B2―C3―D4的顺序(英文字母表示文本中事件的发生顺序,阿拉伯数字表示故事发生因果关系的顺序)。
而在B2与C3之间有一段与A1到D4发展相反的叙述,是一段追述,这些事件是A4’:看到洪水中的人;B1’:战争;C2’:不周山倒;D3’:天裂;C(3)5:补天。
按故事发生的先后,即故事时序是:B1’―C2’―D3’―A4’― C(3)5,而在文本中呈现的顺序,即叙事文时序是:A4’―B1’ ―C2’―D3’ ―C(3)5。
鲁迅《故事新编》原型人物的重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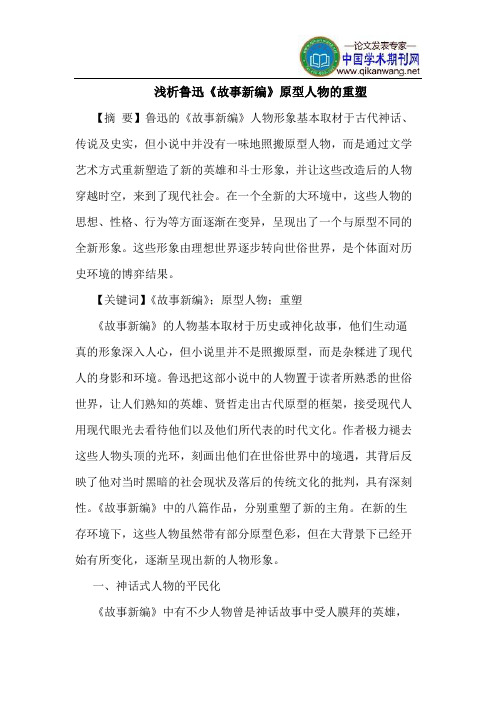
浅析鲁迅《故事新编》原型人物的重塑【摘要】鲁迅的《故事新编》人物形象基本取材于古代神话、传说及史实,但小说中并没有一味地照搬原型人物,而是通过文学艺术方式重新塑造了新的英雄和斗士形象,并让这些改造后的人物穿越时空,来到了现代社会。
在一个全新的大环境中,这些人物的思想、性格、行为等方面逐渐在变异,呈现出了一个与原型不同的全新形象。
这些形象由理想世界逐步转向世俗世界,是个体面对历史环境的博弈结果。
【关键词】《故事新编》;原型人物;重塑《故事新编》的人物基本取材于历史或神化故事,他们生动逼真的形象深入人心,但小说里并不是照搬原型,而是杂糅进了现代人的身影和环境。
鲁迅把这部小说中的人物置于读者所熟悉的世俗世界,让人们熟知的英雄、贤哲走出古代原型的框架,接受现代人用现代眼光去看待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时代文化。
作者极力褪去这些人物头顶的光环,刻画出他们在世俗世界中的境遇,其背后反映了他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状及落后的传统文化的批判,具有深刻性。
《故事新编》中的八篇作品,分别重塑了新的主角。
在新的生存环境下,这些人物虽然带有部分原型色彩,但在大背景下已经开始有所变化,逐渐呈现出新的人物形象。
一、神话式人物的平民化《故事新编》中有不少人物曾是神话故事中受人膜拜的英雄,如始祖英雄女娲、射日英雄后羿。
但在这里,他们原型人物中的神性在渐渐消失,成为芸芸众生中的凡夫俗子,为着生计奔波。
他们的神话色彩在被世俗消磨,甚至完全消失。
在新的生存困境和社会大背景下,这些神话式的人物呈现平民化的趋势。
《奔月》中的后羿曾是万古传颂的射日英雄,但他现在每天为生计劳碌奔波,陷于无聊的生活琐事中,逐渐失去他神性的光环。
一方面由于射法太高,像样的猎物都被他打光了,每天只能打到乌鸦,另一方面,他每天都要回去处处观察嫦娥的脸色讨她欢心,内心充满愧疚和不安。
他还遭到徒弟逢蒙的背叛,被老太太误认作骗子。
后羿对世俗物质方面的无知让他成为被世人嘲弄的对象。
浅谈鲁迅先生《故事新编》的叙事策略

《浅谈鲁迅先生《故事新编》的叙事策略》摘要:通过对《故事新编》叙事策略的分析能够更好的走进鲁迅先生的心灵体验,深刻体会这部作品的思想内涵,但是鲁迅先生的荒诞性叙事是基于现实基础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叙事和创作,仅仅是在叙事上体现荒诞性,进而让故事的呈现区别于传统叙事,鲁迅先生在创作这部作品当中进行个性化的情境设置,最终使得这部作品独具匠心和特色鲜明,更成为小说创作和小说创新的典型实例摘要:《故事新编》是鲁迅先生创作的一部小说集,作品的题材是神话故事,而且创作风格与其之前的作品存在极大的差异,运用了大量创造性和想象性的叙事方法,有效运用虚构手段批判和消解历史以及文化环境。
通过对《故事新编》叙事策略的分析能够更好的走进鲁迅先生的心灵体验,深刻体会这部作品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鲁迅;故事新编;叙事策略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意在对中国历史遗迹文化进行解构,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和历史哲学意识,也让读者能够在轻松欢快的阅读过程中有所收获和深思。
这部小说集在叙事方面有鲜明的特色,尤其是突破了传统的叙事方法,对情节、人物等进行特殊化的设定,最后再采用近似荒诞的创作手法深刻地揭露批判社会现实,其中的叙事策略值得人深思和探究。
一、叙事的荒诞性《故事新编》是鲁迅先生创作的大胆突破以往创作风格的短篇小说集,可以说这部作品的创作风格与以往创作差异十分明显,这部作品更多地采用幽默诙谐的语言将作者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让我们能够从中看到鲁迅先生的生命之旅和心灵体验。
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这部小说集的叙事具有荒诞性的特征,也使得叙事更加轻松诙谐。
我们通过阅读鲁迅先生的这部作品可以清晰地看到,这部小说集当中的大部分故事都取材于古代神话或者历史传说,这样的取材也为荒诞性的叙事打下了基础。
古代神话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在于故事的荒诞性,虽然荒诞但却都来源于古代质朴人民美好的愿望,是最为朴实无华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而这些美好的愿望往往是没有逻辑的,即便存在一定逻辑,但大多逻辑混乱,其中叙述的故事以及混乱逻辑更让这部作品显示出浓重的浪漫色彩,更加引人入胜。
历史与故事的二元运动关系——兼论《故事新编》的“历史编纂”特征

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Old Tales Retold)是由鲁迅不同时期创作的短篇故事结集而成的作品集,贯穿了鲁迅由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
《故事新编》历来受到国内评论家的重视,所采用的批评视角也十分多样,包括叙事学研究、修辞学批评、手稿研究、意象研究、戏仿研究、原型批评研究等等,但对《故事新编》与历史哲学,尤其是二十世纪中后期历史哲学之间的共鸣则理解不足,大都将其简单化为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文本案例,或是将其视为历史小说①(Historical Novel)的一个新脉络,亦或是将其置于“正史”与“野史”的二元对立思想之中,既没有深入到二十世纪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脉络之中,也将意蕴更为丰富的“故事(tale)”简化为小说,这都消解了《故事新编》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哲学思考。
二十世纪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肇始于海登·怀特,经过安克斯密特(F.R.Ankersmit)、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以及詹金斯(Keith.Jenkins)的梳理,已经蔚然成风,成为研究历史叙事学乃至于现代历史哲学中不可回避的一支。
在此背景下,约瑟夫·马里(Joseph Mali)与琳达·哈琴各自在历史与神话的关系问题上以及历史编纂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上进行了深入拓展。
由于海登·怀特将弗莱所提出的四种编织情节的模式——罗曼司、悲剧、喜剧和讽刺文学②——引入历史叙事的范畴,使得我们能够在文学与史学相互缠绕的前提下,对文学作品中的历史观念进行解读。
而张隆溪对历史和虚构性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核心也是基于对“Histoire”词源学考察,指出“该词同时指向了历史与故事”[1],点明了西方史学对叙事、历史与文学之间缠绕的根源。
因此,在历史哲学视域下对《故事新编》的研究,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作为文学作品,该书具有怎样的历史哲学思考?该书在哪些层面上与历史哲学发生了紧密联系?因此,本文将基于二十世纪历史哲学的再思考③,对《故事新编》中的两种重要维度即“故事”一词中所蕴含的丰富意蕴和“编”之中容纳的“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的再创作进行分析,从而探究在“新编”的过程中所表达出的全新的文学与史学内涵。
浅论《故事新编》的历史书写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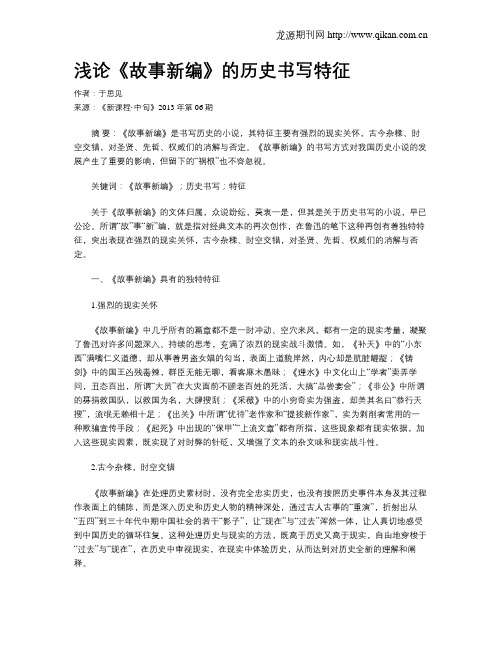
浅论《故事新编》的历史书写特征作者:于思见来源:《新课程·中旬》2013年第06期摘要:《故事新编》是书写历史的小说,其特征主要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古今杂糅、时空交错,对圣贤、先哲、权威们的消解与否定。
《故事新编》的书写方式对我国历史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留下的“祸根”也不容忽视。
关键词:《故事新编》;历史书写;特征关于《故事新编》的文体归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其是关于历史书写的小说,早已公论。
所谓“故”事“新”编,就是指对经典文本的再次创作,在鲁迅的笔下这种再创有着独特特征,突出表现在强烈的现实关怀,古今杂糅、时空交错,对圣贤、先哲、权威们的消解与否定。
一、《故事新编》具有的独特特征1.强烈的现实关怀《故事新编》中几乎所有的篇章都不是一时冲动、空穴来风,都有一定的现实考量,凝聚了鲁迅对许多问题深入、持续的思考,充满了浓烈的现实战斗激情。
如,《补天》中的“小东西”满嘴仁义道德,却从事着男盗女娼的勾当,表面上道貌岸然,内心却是肮脏龌龊;《铸剑》中的国王凶残毒辣,群臣无能无聊,看客麻木愚昧;《理水》中文化山上“学者”卖弄学问,丑态百出,所谓“大员”在大灾面前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大搞“品尝宴会”;《非公》中所谓的募捐救国队,以救国为名,大肆搜刮;《采薇》中的小穷奇实为强盗,却美其名曰“恭行天搜”,流氓无赖相十足;《出关》中所谓“优待”老作家和“提拔新作家”,实为剥削者常用的一种欺骗宣传手段;《起死》中出现的“保甲”“上流文章”都有所指,这些现象都有现实依据,加入这些现实因素,既实现了对时弊的针砭,又增强了文本的杂文味和现实战斗性。
2.古今杂糅,时空交错《故事新编》在处理历史素材时,没有完全忠实历史,也没有按照历史事件本身及其过程作表面上的铺陈,而是深入历史和历史人物的精神深处,通过古人古事的“重演”,折射出从“五四”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若干“影子”,让“现在”与“过去”浑然一体,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历史的循环往复。
浅析《故事新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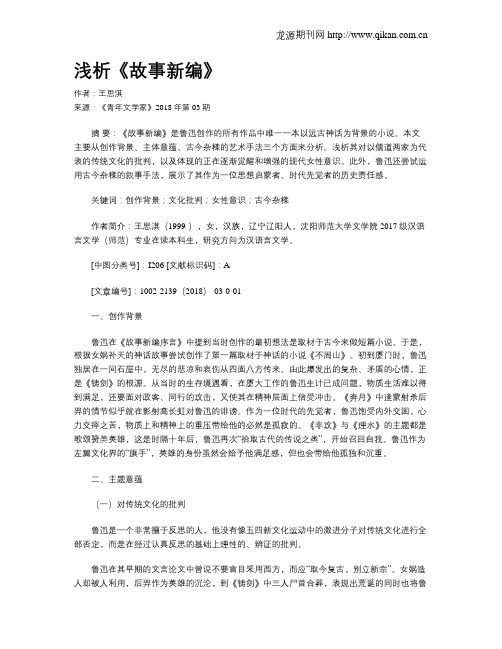
浅析《故事新编》作者:王思淇来源:《青年文学家》2018年第03期摘要:《故事新编》是鲁迅创作的所有作品中唯一一本以远古神话为背景的小说。
本文主要从创作背景、主体意蕴、古今杂糅的艺术手法三个方面来分析。
浅析其对以儒道两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批判,以及体现的正在逐渐觉醒和增强的现代女性意识。
此外,鲁迅还尝试运用古今杂糅的叙事手法,展示了其作为一位思想启蒙者、时代先觉者的历史责任感。
关键词:创作背景;文化批判;女性意识;古今杂糅作者简介:王思淇(1999-),女,汉族,辽宁辽阳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2017级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3-0-01一、创作背景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提到当时创作的最初想法是取材于古今来做短篇小说。
于是,根据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尝试创作了第一篇取材于神话的小说《不周山》。
初到厦门时,鲁迅独居在一间石屋中,无尽的悲凉和哀伤从四面八方传来。
由此爆发出的复杂、矛盾的心情,正是《铸剑》的根源。
从当时的生存境遇看,在厦大工作的鲁迅生计已成问题,物质生活难以得到满足,还要面对政客、同行的攻击,又使其在精神层面上倍受冲击。
《奔月》中逢蒙射杀后羿的情节似乎就在影射高长虹对鲁迅的诽谤。
作为一位时代的先觉者,鲁迅饱受内外交困,心力交瘁之苦,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重压带给他的必然是孤寂的。
《非攻》与《理水》的主题都是歌颂赞美英雄,这是时隔十年后,鲁迅再次“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开始召回自我。
鲁迅作为左翼文化界的“旗手”,英雄的身份虽然会给予他满足感,但也会带给他孤独和沉重。
二、主题意蕴(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鲁迅是一个非常擅于反思的人,他没有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分子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部否定,而是在经过认真反思的基础上理性的、辨证的批判。
鲁迅在其早期的文言论文中曾说不要盲目采用西方,而应“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历史的舞台现实的世界__--__《故事新编》的创作问题

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以缀合,抒写,只有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
”①于是,鲁迅根据史的一些片段,随意点染,甚至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在小说中增加了许多现代语言,比如《理水》中的“古貌林”、“好杜有图”、“O.K”等,尽管如此,鲁迅笔下的人物,不论是神话传说中的女娲、羿、禹、眉间尺、黑衣人还是史书上的老子、孔子、墨子、庄子、伯夷、叔齐等,都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这是因为作者没有改变历史的根本精神意图,只是把他们置于不同的联系当中,展现出他们的一些侧面,从而使我们对他们产生了新的印象,改变了对他们的固有感受和理解。
他们和古籍记载仍是同样一个人物,只是有具有了更丰富的生命内涵。
《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园地里开的一朵“独特”的鲜花,它在历史小说发展史上开创了崭新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
历史与现实,由于事实上的惊人相似,而有了艺术上的可倒错性。
鲁迅凭借一个艺术家的敏锐感觉,在中华思想文化的源头发现了古代文学中特有的民族特质,糅合以现代精神,脱胎换骨般创作出新的小说形式,开创了历史小说幽默、讽刺、“油滑0.韵艺术风格。
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渗透着强烈的生命意识,一改传统历史小说中平铺直叙的讲述方式,代之以富于冲突、张力的表现形式,给予了历史小说新的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
第三节:“油滑”新解“油滑”问题历来是研究《故事新编》的重点,也是难点。
甚至可以说“油滑”问题是《故事新编》的“难点”中最难研究的一个。
因为对于许多业已形成的美学标准和规范而言,油滑并不符合传统的审美方式,而是凭着自身独有的文学趣味,建立起独特的艺术风格。
对于“油滑”问题,鲁迅认为“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
然而在接下来的13年,鲁迅并未改变油滑的写法,并且明确地说:“此后还想保持此种油腔滑调”@。
正是鲁迅这种几乎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引起今后的“油滑”之争:有一种观点基本否定“油滑”。
这类观点的创始人是雨霭子,他于1936年发表《读后漫谈((故事新编)鲁迅著》一文,认为“油滑之处~‘未能尽善尽美,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把‘小说’的意味损失了,成了一篇杂感”。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故事新编”中的史实性与符号性及在当代的衍变作者简介:项黎栋,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初阳学院。
摘要:鲁迅的《故事新编》作为古代与现代的共通体,有不同程度的历史“史诗性”与“符号性”的结合,这既是历史小说创作的必然和必要,也在两者的侧重选择上使创作者的表意更加深化。
这种历史小说创作背后体现的是作家主体情感宣泄,和文化失望从而寻找依托这两方面的诉求。
但是鲁迅创设的这一文学样式在当代小说中的发展却值得关注,除掉一直以来这类小说创作与政治若即若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作家文化忧患意识的背后,游戏历史的虚无主义倾向的出现。
关键词:史实性;符号性;故事新编;历史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1-0000-01
普罗汉诺夫曾说:“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
于小说这一艺术样式来看,评价得很是恰当。
但是如果将小说限定上“历史”之名,则要求作家在创作中需要依仗一些史实“镣铐”来“跳舞”。
那么,是就历史说历史还是借历史而言其他,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传统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的流变问题,以及作家创作过程中对待历史的“史实性”和“符号性”偏倚问题。
本文想以现代文学特别是历史小说样式探索者鲁迅的《故事新编》为例,分析作家回归历史的创作背后的原因及正视新历史小说发展到当代的一些偏颇之处。
一、鲁迅《故事新编》“史实性”与“符号性”的偏倚
现代历史小说发端于“五四”运动,受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思潮的影响,鲁迅在内的一批作家群体或多或少出现了唯意志论的倾向,反映到历史小说创作上,他们抛却原有的“再现原则”,着眼于古,立意于今,借助原有的历史题材来抒写主体意识和时代精神,化身为关照历史的现实战斗武器。
鲁迅的《故事新编》共收录8篇“新编故事”,分别是《补天》、《奔月》、《理水》、《采薇》、《铸剑》、《出关》、《非攻》和《起死》。
他在序言中称自己的写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
细读文本并结合其写作的时下背景,我们不难发现新编故事中鲁迅对历史“史实性”和“符号性”的取舍。
最早成文的《不周山》(后更名为《补天》)取材神话“女娲造人”及“女娲补天”,从人物设置和情节安排上看“史实性”成分偏多,但鲁迅也新编了女娲在造人过程中的心理变化:“这诧异使伊喜欢”、“于是第一次自己也笑得合不上嘴唇来”、“伊在长久的欢喜中,早已带着疲乏了”、“自己觉得无所谓了,而且不耐烦”、“总觉得左右不如愿了,便焦躁地伸开手去”。
新编的结尾表现了荒诞背后的悲凉感,女娲造了人,人却连她的尸体都要利用,“符号性”突出。
《奔月》和《理水》两篇,分别取材于“后羿射日”和“大禹治水”的神话,新编在故事侧重表达的转移和主体精神的传达。
原有故事只占小部分,甚至英雄曾经的功绩被人遗忘和消解,“符号性”在此彰显,鲁迅从两个角度探讨了“以后”的问题:后羿面
临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尴尬,纠缠于琐事之中使其内在精神平庸;大禹不仅沦为“被看”,还被用作为统治工具。
《非攻》的新编与这两篇很相似,也是探讨先驱者的命运问题,在后半部分将原有故事颠覆。
《采薇》、《出关》、《起死》三篇属于同类型的新编,将往哲先贤放置于一个荒诞的情境中进行审视,原有故事主干精简,通过对历史再创作来体现自身对中国传统儒家、道家等思想现实意义的怀疑,“符号性”创作明显。
《铸剑》取材曹丕《列异传》中的眉间尺复仇传说,就历史小说的创作上来看可算是8篇中“符号性”成分最多,文学性的描写最为出彩,让人看了有惊心动魄之感,表达了他想要复仇但是又清楚明白在中国社会复仇这一行为的无用、无效的可悲。
史实是历史的平面状态;符号则是其立体状态。
由此可知,历史的“史实性”与“符号性”在小说创作中的结合是鲁迅《故事新编》的必然,这也使新编的故事不仅仅是情节上的引人入胜,更能在读后引人去思考此中深意,这样的历史小说创作才有持久的生命力。
二、创作主体回归历史背后的诉求
通过上文对《故事新编》8篇文章的简析可知,鲁迅不只是对原有的神话或者传说进行了文学性的想象和改编,更是有“言外之意”蕴含其中。
对读鲁迅的历史小说和受其影响、后期写作新历史小说的作家,我们可以挖掘作家主体回归历史进行小说创作背后的原因及对待历史的价值取向。
诚如鲁迅自己所说,他之所以开始写小说,是抱着一种“启蒙主义”,以为必需“为人生”。
[1]这种文学主张,对照历史小说的创作来看,作者是借历史人物和事件建构一个新的舞台,从精神层面寻找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
比如,故事新编的后几篇主要成文于1926年后,鲁迅从北平到了厦门,到了广东,又到上海,到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成立。
在这期间,他愤恨于顾颉刚,这在《故事新编》中多次出现。
如《理水》中,“‘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
”、“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鸟头先生,您不要和他去辩论了’”等,这个有口吃的学者和“鸟头先生”就是指将鲁迅的碑文拓片充公、又率众将他排挤出去的顾颉刚。
但是鲁迅除了有这样的感性的情绪宣泄之外,还有深层的理性的情绪宣泄,即对待历史的“符号性”所映射出来的彻底的怀疑主义精神,怀疑先驱者的命运,怀疑儒家、道家哲学的现实之用,怀疑他所坚持的复仇的最终效用等等,将一种思考背后的无尽悲凉通过历史张力升华。
另一用于解释作家进行历史小说创作的原因可以归于精神、思想立足点的缺失和动摇。
即奔忙于文化失范状态下的作家主体渴望一种深层的精神依托来安身立命,从传统中、古典中寻找思维依据和文化依托。
[2]鲁迅虽然竭力批判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但是对新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接受程度又不足以使其认为可作新的并且牢固的文化立足点,在这一时期不免会出现精神寄托真空的短暂状态,而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注入的一种彻底的怀疑
主义精神确是将他丰富、悲凉、痛苦的生命体验融入其中,而且是一种既怀疑外部环境,又怀疑内在想法的彻底怀疑和由此产生的落空。
三、当代新历史小说发展的偏颇
新历史小说不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为框架来构筑故事情节,而只是把小说人物活动的时空前移到历史中,表现的仍是现代的人生世相和思想感情。
[3]从这个一般定义可知,新历史小说与鲁迅《故事新编》式的背后诉求有一定的传承性,但是仔细比较二者,还是可以发现新历史小说特别是发展到当代,已经出现不少偏颇之处。
其中最突出的也是在创作上最重要的一点是,作家对历史的态度的差异。
先锋派作家为代表的作家群体将历史视为可以任意游戏的不确定的“他者”。
在这一点上,当代许多新历史小说家与西方小说家观点较为接近,认为历史小说是可以随意的,用席勒在《论悲剧艺术》中的说辞就是“严格遵从历史真实性,往往损害诗意真实性。
”另外,他们还把历史比喻为“不过是挂小说的一根钉子”、“不妨把它当成一个孩子任意摆布”。
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背后,隐含的是作家在进行历史小说创作时的消费历史主义,即认为对历史不必认真或认真不得。
由这种游戏历史的精神所导向出来的新历史小说有一个趋势是,作家的小说中剥去了传统历史观中的合理内核,而将民族文化中的劣根性成分做不适当地放大化地艺术处理。
比如,冯骥才的《神鞭》和《三寸
金莲》,刘恒的《冬之门》和孙方友的《绑票》等。
除此之外,部分作家将新历史小说视为摆脱现实迷惘的一种选择,在创作过程中抛弃了对历史本质的追问而纯粹地将历史变为世俗化、通俗化两者的演义形式。
项目名称:本文为“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注解:
[1] 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2] 刘忠《20世纪中国文学主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00-201页。
[3] 安德烈·莫洛娅著,李桅译,《三仲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