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明背景下一个性别的整体坠落_论张爱玲小说文本中对男性形象的否定
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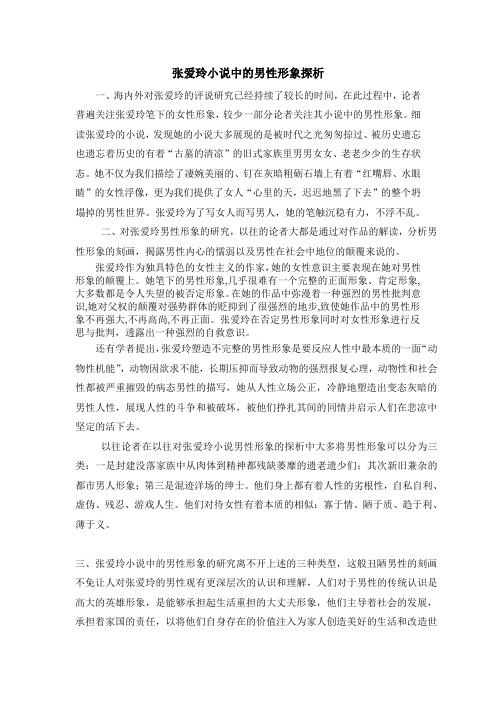
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探析一、海内外对张爱玲的评说研究已经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在此过程中,论者普遍关注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较少一部分论者关注其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细读张爱玲的小说,发现她的小说大多展现的是被时代之光匆匆掠过、被历史遗忘也遗忘着历史的有着“古墓的清凉”的旧式家族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生存状态。
她不仅为我们描绘了凄婉美丽的、钉在灰暗粗砺石墙上有着“红嘴唇、水眼睛”的女性浮像,更为我们提供了女人“心里的天,迟迟地黑了下去”的整个坍塌掉的男性世界。
张爱玲为了写女人而写男人,她的笔触沉稳有力,不浮不乱。
二、对张爱玲男性形象的研究,以往的论者大都是通过对作品的解读,分析男性形象的刻画,揭露男性内心的懦弱以及男性在社会中地位的颠覆来说的。
张爱玲作为独具特色的女性主义的作家,她的女性意识主要表现在她对男性形象的颠覆上。
她笔下的男性形象,几乎很难有一个完整的正面形象、肯定形象,大多数都是令人失望的被否定形象。
在她的作品中弥漫着一种强烈的男性批判意识,她对父权的颠覆对强势群体的贬抑到了很强烈的地步,致使她作品中的男性形象不再强大,不再高尚,不再正面。
张爱玲在否定男性形象同时对女性形象进行反思与批判,透露出一种强烈的自救意识。
还有学者提出,张爱玲塑造不完整的男性形象是要反应人性中最本质的一面“动物性机能”,动物因欲求不能,长期压抑而导致动物的强烈报复心理,动物性和社会性都被严重摧毁的病态男性的描写,她从人性立场公正,冷静地塑造出变态灰暗的男性人性,展现人性的斗争和被破坏,被他们挣扎其间的同情并启示人们在悲凉中坚定的活下去。
以往论者在以往对张爱玲小说男性形象的探析中大多将男性形象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封建没落家族中从肉体到精神都残缺萎靡的遗老遗少们;其次新旧兼杂的都市男人形象;第三是混迹洋场的绅士。
他们身上都有着人性的劣根性,自私自利、虚伪、残忍、游戏人生。
他们对待女性有着本质的相似:寡于情、陋于质、趋于利、薄于义。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及其男性观

中文摘要纵观对张爱玲的研究,其小说中的女性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而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却很少受到研究者关注。
本文以张爱玲小说中男性形象分析为切入点来论述张爱玲小说的男性书写以及男性观。
在小说中,张爱玲采用女性主体叙事方式来表现男性、审视男性、颠覆男性,为我们塑造了一群自私、阴郁、猥琐的男性形象。
本文第一部分即根据张爱玲所采用的贬异书写策略和两性参差对照的书写策略,将其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分为四种类型加以分析。
第二部分从男性阳刚性征、爱情理想与责任担当三方面来揭示张爱玲迥异于传统的男性观。
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已不再具有男性的阳刚性征,人类所特有的情感与责任在他们身上也消失殆尽。
第三部分则对张爱玲这种男性观所产生的原因进行挖掘,指出张爱玲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及个人生活经历对其男性观形成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最后指出张爱玲迥异于传统的男性观的重大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张爱玲;男性书写;男性观AbstractReview the search to Zhang AiLing, the female in her novel has been the point and hot spot of search.,however,the male image in the novel is seldom paid attention by the researcher. This text takes the male image analysis in the novel of Zhang AiLing as to correspond dot to discuss Zhang Ailing's male write and male view.In the novel ,Zhang Ailing express men, examine men and subversion men through adopt the narrative way of make women as master and depicted a huge number of Selfish cheerless and obscene men for us. I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thesis,we can classify and an analyze the male image according the strategies of devaluate difference write and both sexes comparison write what had been adoptted by Zhang AiLing. In the second part we point out the untraditional look towards the man of Zhang AiLing from these aspects that include virility ,love and responsibility. The men writing by Zhang Ailing have lost the virility,Emotion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third part, we analyze the source of Zhang A iling’s such look towards men and point out the reason what Zhang’s such look towards men is the Live antecedents,personal experience and Community, cultural back ground of the writer in those days.Finally point out the great significance and worth of Zhang A iling’s such look towards men.Keyword:Zhang Ailing;depiction of man;Zhang’s look towards men目录前言 (1)一、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书写 (2)(一)寡廉鲜耻、不务正业的遗老遗少形象 (3)(二)虚伪自私、人格分裂的假绅士形象 (4)(三)风流倜傥、迷失自我的洋场浪子形象 (6)(四)其他庸俗丑陋的都市男性形象 (8)二、张爱玲男性观的体现 (10)(一)对传统男性阳刚性征的阉割 (10)(二)对传统男性爱情理想的质疑 (11)(三)对传统男性责任担当的反思 (12)三、张爱玲男性观形成的原因 (16)(一)个人生活经历 (16)(二)社会历史文化 (18)结语 (20)参考文献 (21)致谢 (22)前言自四十年代轰动文坛以来,张爱玲的传奇作品与身世就一直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
张爱玲小说中男性“异化”形象的解读.d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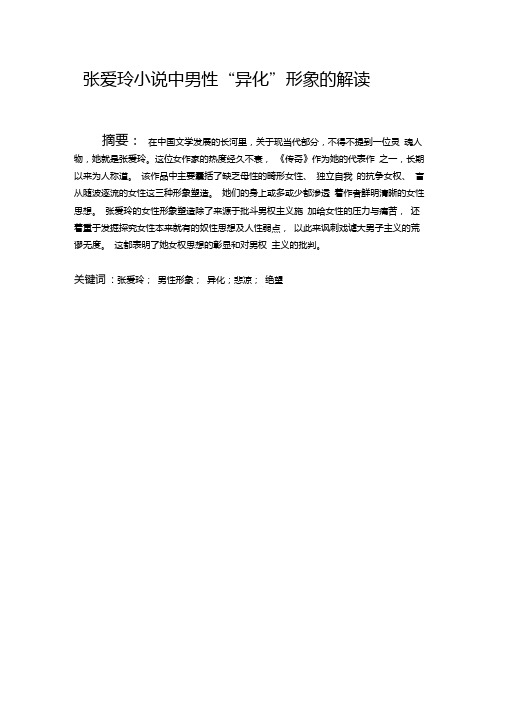
张爱玲小说中男性“异化”形象的解读摘要:在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河里,关于现当代部分,不得不提到一位灵魂人物,她就是张爱玲。
这位女作家的热度经久不衰,《传奇》作为她的代表作之一,长期以来为人称道。
该作品中主要囊括了缺乏母性的畸形女性、独立自我的抗争女权、盲从随波逐流的女性这三种形象塑造。
她们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渗透着作者鲜明清晰的女性思想。
张爱玲的女性形象塑造除了来源于批斗男权主义施加给女性的压力与痛苦,还着重于发掘探究女性本来就有的奴性思想及人性弱点,以此来讽刺戏谑大男子主义的荒谬无度。
这都表明了她女权思想的彰显和对男权主义的批判。
关键词: 张爱玲;男性形象;异化;悲凉;绝望目录一、前言二、张爱玲小说中男性“异化”的书写(一)“大观园”的无能子弟如《倾城之恋》中的白三爷、白四爷,《小艾》中的席五老爷,《花凋》中的郑先生。
(二)空虚寂寞的病态者如《金锁记》中的姜三爷和姜二爷,《琉璃瓦》中的姚先生三、溯源张爱玲小说中男性“异化”的原因(一)时代背景的局限(二)作者的悲剧观四、张爱玲小中说男性“异化”的文化意义五、小结六、参考文献、尸■、■刖言张爱玲小说的时间跨度始于清朝末年,止于刚解放的时代。
深刻的反映出了当时的时代特性、当时背景下人物的劣根性及所处境地,特别是对男权社会的挑战。
美国的相关学者约翰逊提出过这样的观点:“父权社会,就是以男权为主的社会,男性对这个社会享有不可侵犯的主导权,处于该社会的核心地位。
”我国千百年来的父权制度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在我国,历来以男性为主,大男子主义思想统治着国家。
男性也自然成为了以往书籍著作中绝对出挑的主要人物,并且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威性,因而也决定着文学作品史的总体走向。
张爱玲笔下塑造的男性形象也是丰富多彩的,具体包括家道中落的老爷少爷们、新旧思想并存充满自我矛盾的城市男性、来往于洋人聚集场所的绅士们。
这些形象都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冷漠,表里不一,贪婪,玩弄人生。
在对女性的态度上从根本上看也是一样的,一副薄情寡义,趋炎附势的小人嘴脸。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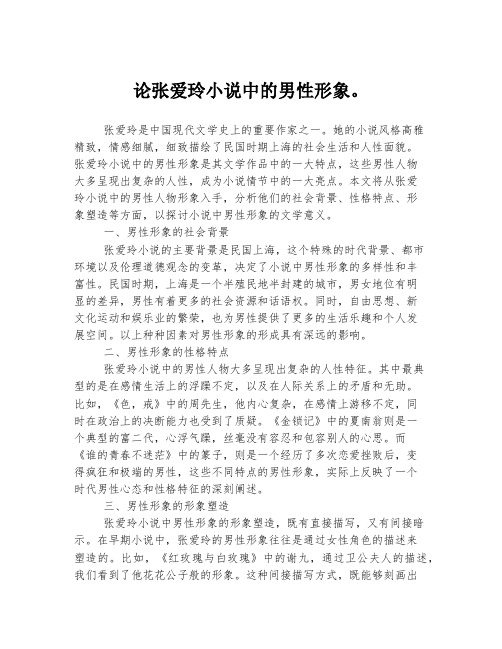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
她的小说风格高雅精致,情感细腻,细致描绘了民国时期上海的社会生活和人性面貌。
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是其文学作品中的一大特点,这些男性人物大多呈现出复杂的人性,成为小说情节中的一大亮点。
本文将从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形象入手,分析他们的社会背景、性格特点、形象塑造等方面,以探讨小说中男性形象的文学意义。
一、男性形象的社会背景张爱玲小说的主要背景是民国上海,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都市环境以及伦理道德观念的变革,决定了小说中男性形象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民国时期,上海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男女地位有明显的差异,男性有着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话语权。
同时,自由思想、新文化运动和娱乐业的繁荣,也为男性提供了更多的生活乐趣和个人发展空间。
以上种种因素对男性形象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男性形象的性格特点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大多呈现出复杂的人性特征。
其中最典型的是在感情生活上的浮躁不定,以及在人际关系上的矛盾和无助。
比如,《色,戒》中的周先生,他内心复杂,在感情上游移不定,同时在政治上的决断能力也受到了质疑。
《金锁记》中的夏南翁则是一个典型的富二代,心浮气躁,丝毫没有容忍和包容别人的心思。
而《谁的青春不迷茫》中的篆子,则是一个经历了多次恋爱挫败后,变得疯狂和极端的男性,这些不同特点的男性形象,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男性心态和性格特征的深刻阐述。
三、男性形象的形象塑造张爱玲小说中男性形象的形象塑造,既有直接描写,又有间接暗示。
在早期小说中,张爱玲的男性形象往往是通过女性角色的描述来塑造的。
比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谢九,通过卫公夫人的描述,我们看到了他花花公子般的形象。
这种间接描写方式,既能够刻画出男性人物的外表特征,增强形象的真实感,又能够反映出女性视角的情感体验。
而在后期小说中,张爱玲则更多地采用了直接描写的方式,来塑造男性形象。
例如,《色,戒》中的周先生,他的形象完全通过自身的行为举止,细节刻画和心理独白来展现。
论张爱玲小说里的男性形象的性别弱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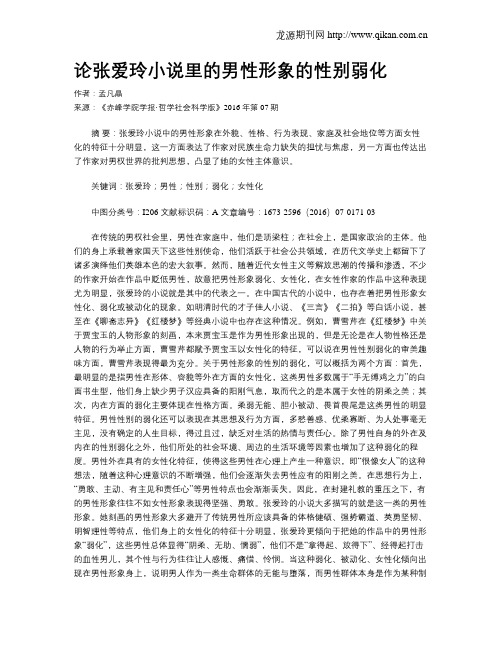
论张爱玲小说里的男性形象的性别弱化作者:孟凡晶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07期摘要: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在外貌、性格、行为表现、家庭及社会地位等方面女性化的特征十分明显,这一方面表达了作家对民族生命力缺失的担忧与焦虑,另一方面也传达出了作家对男权世界的批判思想,凸显了她的女性主体意识。
关键词:张爱玲;男性;性别;弱化;女性化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7-0171-03在传统的男权社会里,男性在家庭中,他们是顶梁柱;在社会上,是国家政治的主体。
他们的身上承载着家国天下这些性别使命,他们活跃于社会公共领域,在历代文学史上都留下了诸多演绎他们英雄本色的宏大叙事。
然而,随着近代女性主义等解放思潮的传播和渗透,不少的作家开始在作品中贬低男性,故意把男性形象弱化、女性化,在女性作家的作品中这种表现尤为明显,张爱玲的小说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在中国古代的小说中,也存在着把男性形象女性化、弱化或被动化的现象。
如明清时代的才子佳人小说、《三言》《二拍》等白话小说,甚至在《聊斋志异》《红楼梦》等经典小说中也存在这种情况。
例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关于贾宝玉的人物形象的刻画,本来贾宝玉是作为男性形象出现的,但是无论是在人物性格还是人物的行为举止方面,曹雪芹都赋予贾宝玉以女性化的特征,可以说在男性性别弱化的审美趣味方面,曹雪芹表现得最为充分。
关于男性形象的性别的弱化,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首先,最明显的是指男性在形体、容貌等外在方面的女性化,这类男性多数属于“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型,他们身上缺少男子汉应具备的阳刚气息,取而代之的是本属于女性的阴柔之美;其次,内在方面的弱化主要体现在性格方面。
柔弱无能、胆小被动、畏首畏尾是这类男性的明显特征。
男性性别的弱化还可以表现在其思想及行为方面,多愁善感、优柔寡断、为人处事毫无主见,没有确定的人生目标,得过且过,缺乏对生活的热情与责任心。
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分析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ofHeilongjiangCollegeofEducation
doi:10.3969/j.issn.10017836.2019.02.038
Feb.2019 Vol.38No.2
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分析
李雪芳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广安 638000)
关键词:男性形象;张爱玲;精神残障;猥琐;自私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解放是启蒙先驱们的根本意愿,而女 性的觉醒作为个人觉醒的副产品也悄然临世。张爱玲作为 一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都市女性,她成长在男权文化家 庭里,因此,她经济不独立,同时也没有独立的价值体系,但 是她又接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洗礼。因此,她更深刻地 认识到女性的人生悲剧,所以在她的小说里总是在诉说一些 发生在旧式家庭里的琐碎的婚恋小故事,塑造出众多典型的 女性人物形象,并将她们真实的生存困境深刻地揭示出来。 纵观张爱玲的小说,她为了突出女性主体地位这一主题,她 笔下的男性颠覆了传统观念中坚强、勇敢、刚毅的形象,都是 虚伪、自私、猥琐的形象,他们大多是身体残缺或精神残损, 或是在权威家 庭 中 缺 席,或 是 在 家 庭 和 社 会 中 处 于 劣 势 状 态。尽管她在书写男性形象方面带有个人主观色彩,但目的 并不是为表达个人哀怨。在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长 期影响下,大都市中的人难免会异化变质,为了生存,不惜出 卖了尊严、人格、灵魂,甚至出卖亲情。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 象否定与消解了传统男权的中心地位,这样的男性无法承担 起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进而也反映出张爱玲的女性主体意识 非常强烈。
张爱玲在书写像《怨女》中的姚二爷、《金锁记》中的姜 二爷等一群身体残疾的男性形象时,直接通过矮化其身体使 传统的男性形象彻底被颠覆,男性主体地位被削弱,由此凸 显出创作主题———女性主体意识。除此之外,张爱玲还从角 色、地位、性情等几个方面对比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主要运 用的书写策略就是两性参差对照,通过大量的对比丑化了男 性,并将他们置放于小说的文本边缘,男性主体地位从根本 上被削弱,突出其在失去男性权威的环境中所裸露的丑陋与
从张爱玲小说的男女形象对比看张爱玲的女性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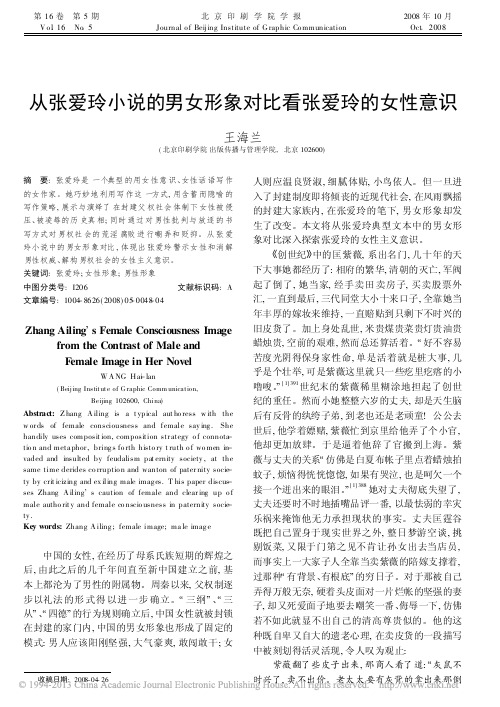
第16卷 第5期V o l 116 No 15北京印刷学院学报Journal o f Beijing Institute of G raphic Co mmunication 2008年10月Oct 12008收稿日期:2008-04-26从张爱玲小说的男女形象对比看张爱玲的女性意识王海兰(北京印刷学院出版传播与管理学院,北京102600)摘 要:张爱玲是一个典型的用女性意识、女性话语写作的女作家。
她巧妙地利用写作这一方式,用含蓄而隐喻的写作策略,展示与演绎了在封建父权社会体制下女性被侵压、被凌辱的历史真相;同时通过对男性批判与放逐的书写方式对男权社会的荒淫腐败进行嘲弄和贬抑。
从张爱玲小说中的男女形象对比,体现出张爱玲警示女性和消解男性权威、解构男权社会的女性主义意识。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形象;男性形象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626(2008)05-0048-04Zhang Ailing .s Female Consciousness Imagefrom the Contrast of Male and Female Image in Her NovelW A NG Ha-i lan(Beijing Ins titute of Graphic Comm unication,Beijing 102600,China)Abstract:Z hang A iling is a t ypical aut ho ress w ith the w or ds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and female say ing.She handily uses composit ion,composition str ategy o f connota -tio n and meta phor ,bring s fo rth histo ry t ruth o f wo men in -vaded and insulted by feudalism pat ernity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derides co rruptio n and wanton of pater nity socie -ty by crit icizing and ex iling male imag es.T his paper discus -ses Zhang A iling .s caution of female and clear ing up o f male autho rit y and female co nscio usness in paternity socie -ty.Key words:Zhang A iling ;female image;ma le imag e中国的女性,在经历了母系氏族短期的辉煌之后,由此之后的几千年间直至新中国建立之前,基本上都沦为了男性的附属物。
论张爱玲小说里的男性形象的性别弱化

Vol.37No.7Jul.2016第37卷第7期2016年7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 (S oc.S ci )论张爱玲小说里的男性形象的性别弱化孟凡晶(东北师范大学,吉林长春130024)摘要: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在外貌、性格、行为表现、家庭及社会地位等方面女性化的特征十分明显,这一方面表达了作家对民族生命力缺失的担忧与焦虑,另一方面也传达出了作家对男权世界的批判思想,凸显了她的女性主体意识。
关键词:张爱玲;男性;性别;弱化;女性化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7-0171-03在传统的男权社会里,男性在家庭中,他们是顶梁柱;在社会上,是国家政治的主体。
他们的身上承载着家国天下这些性别使命,他们活跃于社会公共领域,在历代文学史上都留下了诸多演绎他们英雄本色的宏大叙事。
然而,随着近代女性主义等解放思潮的传播和渗透,不少的作家开始在作品中贬低男性,故意把男性形象弱化、女性化,在女性作家的作品中这种表现尤为明显,张爱玲的小说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在中国古代的小说中,也存在着把男性形象女性化、弱化或被动化的现象。
如明清时代的才子佳人小说、《三言》《二拍》等白话小说,甚至在《聊斋志异》《红楼梦》等经典小说中也存在这种情况。
例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关于贾宝玉的人物形象的刻画,本来贾宝玉是作为男性形象出现的,但是无论是在人物性格还是人物的行为举止方面,曹雪芹都赋予贾宝玉以女性化的特征,可以说在男性性别弱化的审美趣味方面,曹雪芹表现得最为充分。
关于男性形象的性别的弱化,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首先,最明显的是指男性在形体、容貌等外在方面的女性化,这类男性多数属于“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型,他们身上缺少男子汉应具备的阳刚气息,取而代之的是本属于女性的阴柔之美;其次,内在方面的弱化主要体现在性格方面。
否定与颠覆——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书写

2 0 血 09
传 庆 的还有 大量 的镜 子意 象 , 象征 着在 传 庆 的生 命
态 势 中 , 和碎 是他 最 主要 的人 生体 验 , 这 种 透 凉 而
故事 , 见在 早 期创作 中张爱 玲就 关 注这 类 无所 事 可 事 的男人 , 为她 比较 喜 欢和 擅长 塑 造 的一 类 男人 成
把 对母 亲 的不满迁 怒 于儿 子 , 由此 形成 传 庆 的心理 扭 曲 与变形 。在冰 冷 的家 里享 受 不到父 爱 , 以幻 所 想 自己是言 子夜 的儿 子 ,想像 着 自己 是言 丹朱 , 对 丹朱 也 是复 杂 的 心态 : 慕 、 忌 、 欢 、 恶 … … 羡 妒 喜 憎
但传庆 背后隐隐 有着的入 影就是其 父 。 聂传庆 阴翳 、 卑微 的个性 特点 的形成和 其父有着 不解之缘 。这个 “ 外面 罩 着一 件 油渍 斑斑 的雪青 软 缎 小背 心 ” 的 u 封建遗 少只会成天躺在 烟铺上 , 儿子 似理 非理 , 对 若
理 也是非打 即 骂 ,他父 亲在烟 炕 上翻 过 身来 , “ 捏着
的情境 。 《 莉香 片》 茉 中着 笔最多 的 虽然是 儿子 聂传 庆 ,
面, 还是在 表现 和移情 这一 角度 , 都深得 推 敲 , 值得
玩味 。在她 作品 中 , 出现 了大 量类 型 的男人 。 亲 、 父
丈夫 ( 人或 情 人 ) 儿子 、 恋 、 兄弟 、 友 ; 朋 亲情 、 情 、 爱 友情 , 人类 的关 系和情 感被张 爱玲撕 裂 , 温情 不 再 ,
颠覆 了男性 的传统意 蕴。同时肯定 了女性 的 自我存在 价值 , 确立 了女性 的主体地 位 , 凸显 出作 家特 有的价值
判 断标准和对人性 深邃 的体悟能 力。 关键词 : 张爱玲 ; 小说研 究 ; 男性 形 象; 否定与颠覆
论奥斯丁和张爱玲小说中父亲形象的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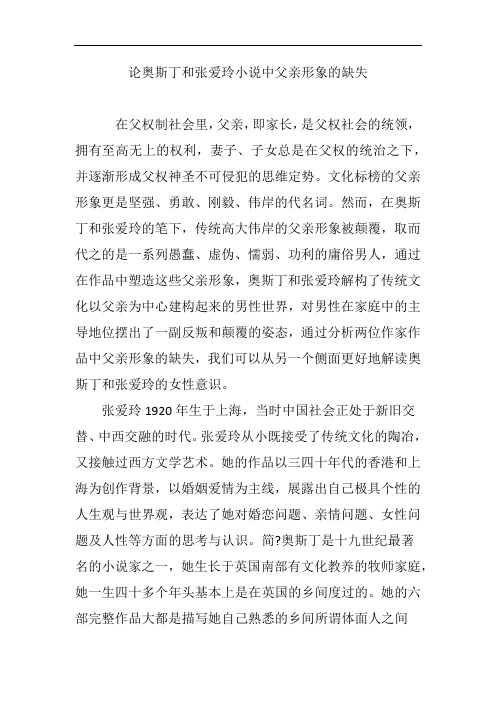
论奥斯丁和张爱玲小说中父亲形象的缺失在父权制社会里,父亲,即家长,是父权社会的统领,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妻子、子女总是在父权的统治之下,并逐渐形成父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思维定势。
文化标榜的父亲形象更是坚强、勇敢、刚毅、伟岸的代名词。
然而,在奥斯丁和张爱玲的笔下,传统高大伟岸的父亲形象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愚蠢、虚伪、懦弱、功利的庸俗男人,通过在作品中塑造这些父亲形象,奥斯丁和张爱玲解构了传统文化以父亲为中心建构起来的男性世界,对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摆出了一副反叛和颠覆的姿态,通过分析两位作家作品中父亲形象的缺失,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更好地解读奥斯丁和张爱玲的女性意识。
张爱玲1920年生于上海,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中西交融的时代。
张爱玲从小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的陶冶,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
她的作品以三四十年代的香港和上海为创作背景,以婚姻爱情为主线,展露出自己极具个性的人生观与世界观,表达了她对婚恋问题、亲情问题、女性问题及人性等方面的思考与认识。
简?奥斯丁是十九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她生长于英国南部有文化教养的牧师家庭,她一生四十多个年头基本上是在英国的乡间度过的。
她的六部完整作品大都是描写她自己熟悉的乡间所谓体面人之间的生活与交往。
细读两位作家的作品不难发现,尽管她们在生活时代、文化背景、家庭背景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她们的作品都无一例外地塑造了一系列委琐、粗暴、世故、虚荣、自私、不负责任、甚至是卑怯的父亲形象,解构了传统文化以父亲为中心建构起来的男性世界。
这种叛逆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位女作家强烈的女性意识。
在简?奥斯丁的所有作品中,父亲形象不是缺位就是形同虚设,这种父权的缺失往往使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鲜明、突出。
以《傲慢与偏见》为例,在这部小说里,奥斯丁塑造了班纳特先生这样一个失败的父亲形象:他虽为一家之主,但却玩世不恭,缺乏对家庭的责任感。
作为丈夫,他听任妻子的喜怒无常和浅薄无知,对妻子插科打诨,当着女儿的面对妻子揶揄嘲讽,从中寻找乐趣。
浅析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的男性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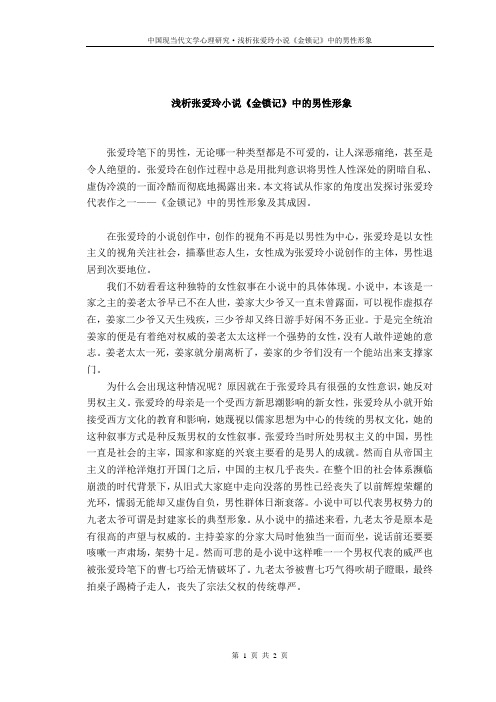
浅析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的男性形象张爱玲笔下的男性,无论哪一种类型都是不可爱的,让人深恶痛绝,甚至是令人绝望的。
张爱玲在创作过程中总是用批判意识将男性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冷漠的一面冷酷而彻底地揭露出来。
本文将试从作家的角度出发探讨张爱玲代表作之一——《金锁记》中的男性形象及其成因。
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创作的视角不再是以男性为中心,张爱玲是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关注社会,描摹世态人生,女性成为张爱玲小说创作的主体,男性退居到次要地位。
我们不妨看看这种独特的女性叙事在小说中的具体体现。
小说中,本该是一家之主的姜老太爷早已不在人世,姜家大少爷又一直未曾露面,可以视作虚拟存在,姜家二少爷又天生残疾,三少爷却又终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于是完全统治姜家的便是有着绝对权威的姜老太太这样一个强势的女性,没有人敢件逆她的意志。
姜老太太一死,姜家就分崩离析了,姜家的少爷们没有一个能站出来支撑家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就在于张爱玲具有很强的女性意识,她反对男权主义。
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受西方新思潮影响的新女性,张爱玲从小就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教育和影响,她蔑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传统的男权文化,她的这种叙事方式是种反叛男权的女性叙事。
张爱玲当时所处男权主义的中国,男性一直是社会的主宰,国家和家庭的兴衰主要看的是男人的成就。
然而自从帝国主主义的洋枪洋炮打开国门之后,中国的主权几乎丧失。
在整个旧的社会体系濒临崩溃的时代背景下,从旧式大家庭中走向没落的男性已经丧失了以前辉煌荣耀的光环,懦弱无能却又虚伪自负,男性群体日渐衰落。
小说中可以代表男权势力的九老太爷可谓是封建家长的典型形象。
从小说中的描述来看,九老太爷是原本是有很高的声望与权威的。
主持姜家的分家大局时他独当一面而坐,说话前还要要咳嗽一声肃场,架势十足。
然而可悲的是小说中这样唯一一个男权代表的威严也被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给无情破坏了。
九老太爷被曹七巧气得吹胡子瞪眼,最终拍桌子踢椅子走人,丧失了宗法父权的传统尊严。
关于张爱玲的小说学术论文

关于张爱玲的小说学术论文张爱玲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她对于中国文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是店铺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张爱玲的学术论文,仅供参考!张爱玲的学术论文篇一:《我眼中的张爱玲》【摘要】初读张爱玲,我被她特有的阴冷、悲情、残酷的调子所吸引。
看着她的作品,总是让你觉得浑身上下包括牙缝里都嘶流嘶流地穿着冷风,有时整个心都凉透了,还变幻着红黄绿紫的颜色。
她把人看得一丝不挂,她对人物描写的句子,字字直往你心里钻,对人性的解读和对事物的敏锐眼光令我折服。
可是,她对自己爱情的追求和付出却与她去塑造笔下人物的态度截然相反,她心中诚然一切却义无反顾,难道那些人物是她的影子,还是她是那些人物的影子?【关键词】张爱玲;冷色性格;暖色爱情一、冷色性格张爱玲,从来就是个矛盾。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伦经李鸿章引荐与其女儿结婚,所以爱玲属于正宗的名门之后,可见不免骨子里有骄纵傲慢的贵族习气。
这样大的家庭背景下,张佩伦之子即张爱玲之父便被熏陶出典型的遗少作风,染有弄风捧月之旧习气,更发展其性情暴戾等恶习。
而张爱玲的母亲,是清末南京黄军门的女儿,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而又清丽孤傲的漂亮女子。
旧习气与西洋化显然是格格不入。
这样的一对夫妇,又给这个复杂的家庭关系增添了另一种叛逆的格调。
家庭对一个孩子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觉得母亲对爱玲的西式教育给了她对艺术的鉴赏力、女性思想的开放性和广阔的胸襟,可是我们始终是中国人,千年的封建思想是植根在每一人心的刺,很多人早已习惯,本来爱玲已经发现了刺,可是当她的父母离婚,愁锁深闺的她即使觉得疼,也无法拔除,只有忍着痛,揭开人世间的面目,个中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逐渐清晰可见。
她从来就是有大志的,也许生活的郁闷也只能给她这样的期许。
特有的才情和早熟令她在学校中脱颖而出。
她说:“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
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张爱玲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分析

目录摘要 (2)Abstract ...............................................................................................................................................一、张爱玲的创作心态对男性形象塑造的影响 (4)(一)悲观的人生态度对男性形象塑造的影响 (4)(二)蔑视传统男权文化对男性形象塑造的影响 (4)(三)非自觉的女性意识对男性形象塑造的影响 (5)二、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剖析 (5)(一)精神空虚、放浪形骸的没落男性形象 (5)(二)乱世中的浮华浪子男性形象。
(6)(三)在生活中颓败灰暗的男性形象 (7)(四)专制家庭挤压下的病态男人形象 (8)三、结论 (9)参考文献 (10)摘要在张爱玲的小说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形形色色的市井男女,勾绘出一幅幅旧中国的风情画。
然而,由于作家对世界的敌意及对人与事的否定情绪,决定了张爱玲对人性和爱的彻底悲观,因此,她的创作总是弥漫着苍凉的情调。
由于作家对男性文化的蔑视,作家不惜以弱化甚至是病态化的手法塑造起笔下的整个的男性世界。
于是,精神空虚、放浪形骸、乱世中的浮华浪子、生活中颓败灰暗、专制家庭挤压下的病态成为张爱玲作品中塑造的男性形象。
张爱玲的小说,用苍凉的笔调剖析了男性的阴暗无耻。
她对于人物和社会的解剖直接、细微甚至鲜血淋漓。
她从人性立场公正、冷静地塑造出贴近内心的男性形象,一点一滴写他们的失衡的人性,展现他们人性的斗争和被破坏,对他们挣扎其间的酸楚寄予深厚的同情。
关键词:张爱玲;男性;悲观;塑造AbstractIn Zhang Ailing's novel work, has successfully portrayed one group of marketplace men and women of all forms, outlines an old China's character and style picture.However, as a result of the writer to the world hostility and to the human and the matter negative mood, had decided Zhang Ailing and loves thoroughly to the human nature pessimistic, therefore, her creation is always filling the air the desolate affective tone.Under because the writer to masculine cultural despising, the writer does not hesitate to attenuate even is the morbid state technique mold begins a stroke the entire masculine world.Therefore, the spirit void, abandons oneself to Bohemianism, in the tumultuous times ostentatious prodigal son, the life decadent gloomy, under the despotic family extrusion morbid state becomes the masculine image which in the Zhang Ailing work molds.Zhang Ailing's novel, analyzed masculinely with the desolate writing style gloomy shameless.She regarding character and society's dissection direct, slight even dripping with blood.She from the human nature standpoint fair, molds the drawing close to innermost feelings calmly the masculine image, writes their unbalanced human nature bit by bit, unfolds their human nature struggle and is destroyed during, struggles to them to place the deep sympathy grieved.Key words:Zhang Ailing; Male; Pessimistic; Mold张爱玲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分析一、张爱玲的创作心态对男性形象塑造的影响(一)悲观的人生态度对男性形象塑造的影响对世界的敌意及对人与事的否定情绪,决定了张爱玲对人性和爱的彻底悲观,因此,她的创作总是弥漫着苍凉的情调。
浅析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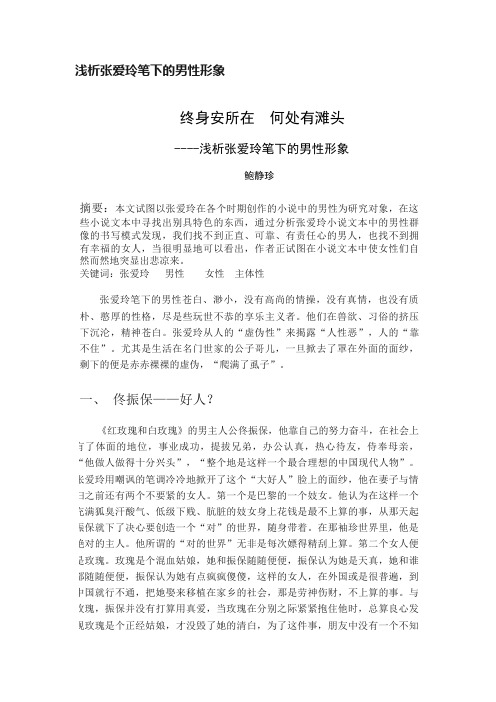
浅析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终身安所在何处有滩头----浅析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鲍静珍摘要:本文试图以张爱玲在各个时期创作的小说中的男性为研究对象,在这些小说文本中寻找出别具特色的东西,通过分析张爱玲小说文本中的男性群像的书写模式发现,我们找不到正直、可靠、有责任心的男人,也找不到拥有幸福的女人,当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作者正试图在小说文本中使女性们自然而然地突显出悲凉来。
关键词:张爱玲男性女性主体性张爱玲笔下的男性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真情,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
他们在兽欲、习俗的挤压下沉沦,精神苍白。
张爱玲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
尤其是生活在名门世家的公子哥儿,一旦掀去了罩在外面的面纱,剩下的便是赤赤裸裸的虚伪,“爬满了虱子”。
一、佟振保——好人?《红玫瑰和白玫瑰》的男主人公佟振保,他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在社会上有了体面的地位,事业成功,提拔兄弟,办公认真,热心待友,侍奉母亲,“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
张爱玲用嘲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大好人”脸上的面纱,他在妻子与情妇之前还有两个不要紧的女人。
第一个是巴黎的一个妓女。
他认为在这样一个充满狐臭汗酸气、低级下贱、肮脏的妓女身上花钱是最不上算的事,从那天起振保就下了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随身带着。
在那袖珍世界里,他是绝对的主人。
他所谓的“对的世界”无非是每次嫖得精刮上算。
第二个女人便是玫瑰。
玫瑰是个混血姑娘,她和振保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是天真,她和谁都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有点疯疯傻傻,这样的女人,在外国或是很普遍,到中国就行不通,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
与玫瑰,振保并没有打算用真爱,当玫瑰在分别之际紧紧抱住他时,总算良心发现玫瑰是个正经姑娘,才没毁了她的清白,为了这件事,朋友中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
浅谈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浅谈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摘要】张爱玲以其独特的风姿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她笔下多有苍凉的世态,展露一种穿透黑暗后的清醒。
细品其作品,其里的男性形象都带着一种“丑陋”。
本文将以张爱玲作品中具体人物为例,对其笔下的男性形象进行分析,还原张爱玲眼中的“男性形象”。
【关键词】张爱玲;男性形象;悲悯情怀张爱玲一直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特别的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她笔下的故事总是带着一种厚重的苍凉,用她犀利敏感的笔触展现给一段段新旧交替时期的悲欢离合,塑造了各色各异的人物形象。
而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出现的男性角色都带着一种“丑陋”,与以往固有的威严、勇猛的男性角色对立。
一、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张爱玲出生于1920年,正是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
她的作品也主要以30与40年代的沪港洋场为创作背景,以旧时女性、两性关系和婚假迎娶为主要切入点,力求对人物有一个细致的描绘。
张爱玲在小说中塑造了60多位身份各异的男性,他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丈夫、父亲、儿子等等。
(一)缺失的夫爱文学的主题永远离不开两性之爱,张爱玲故事里男人们都不是坚贞爱情的守卫者,而是这场战争里的逃兵。
他们贪慕刺激的激情却不愿负起责任,视婚姻于形式。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就是鲜明的例子,勾引了不用对她负责任的有夫之妇娇蕊,与她偷情,却在娇蕊想要舍弃丈夫与他在一起时落荒而逃。
随后他又娶了烟鹂,却把她置于妻子这个位置上的摆设,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与他偷情的娇蕊。
(二)异化的父爱在以往的小说中,父亲总是权威的象征。
他们或者是高大威武的保护者,或者是温暖、粗中有细的守护者。
而张爱玲站在人性的层面上,对传统的父亲形象进行了颠覆,他们不再是受到尊敬和仰视的“太阳”,只是市井中自私、无能的凡人。
《金锁记》中姜家二少爷生来就有软骨病,只得终生躺在床上,这是肢体残疾的父亲。
《花雕》中的封建遗少郑先生,眼中只有金钱,他的子女受尽伤害,甚至在女儿不幸患病之后也不愿拿出钱来治病,这是自私的父亲。
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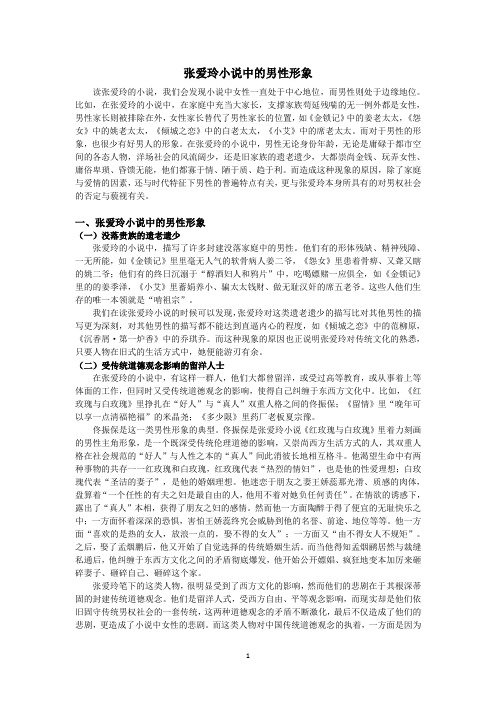
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会发现小说中女性一直处于中心地位,而男性则处于边缘地位。
比如,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在家庭中充当大家长,支撑家族苟延残喘的无一例外都是女性,男性家长则被排除在外,女性家长替代了男性家长的位置,如《金锁记》中的姜老太太,《怨女》中的姚老太太,《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小艾》中的席老太太。
而对于男性的形象,也很少有好男人的形象。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男性无论身份年龄,无论是庸碌于都市空间的各态人物,洋场社会的风流阔少,还是旧家族的遗老遗少,大都崇尚金钱、玩弄女性、庸俗卑琐、昏馈无能,他们都寡于情、陋于质、趋于利。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家庭与爱情的因素,还与时代特征下男性的普遍特点有关,更与张爱玲本身所具有的对男权社会的否定与藐视有关。
一、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一)没落贵族的遗老遗少张爱玲的小说中,描写了许多封建没落家庭中的男性。
他们有的形体残缺、精神残障、一无所能,如《金锁记》里里毫无人气的软骨病人姜二爷,《怨女》里患着骨痹、又聋又瞎的姚二爷;他们有的终日沉溺于“醇酒妇人和鸦片”中,吃喝嫖赌一应俱全,如《金锁记》里的的姜季泽,《小艾》里蓄娟养小、骗太太钱财、做无耻汉奸的席五老爷。
这些人他们生存的唯一本领就是“啃祖宗”。
我们在读张爱玲小说的时候可以发现,张爱玲对这类遗老遗少的描写比对其他男性的描写更为深刻,对其他男性的描写都不能达到直逼内心的程度,如《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乔琪乔。
而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正说明张爱玲对传统文化的熟悉,只要人物在旧式的生活方式中,她便能游刃有余。
(二)受传统道德观念影响的留洋人士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大都曾留洋,或受过高等教育,或从事着上等体面的工作,但同时又受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使得自己纠缠于东西方文化中。
比如,《红玫瑰与白玫瑰》里挣扎在“好人”与“真人”双重人格之间的佟振保;《留情》里“晚年可以享一点清福艳福”的米晶尧;《多少限》里药厂老板夏宗豫。
失去信任的残疾亚当_张爱玲在小说中对男性形象的颠覆

总23卷 专辑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232002年8月 Journal of S 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Philos ophy and S ocial SciencesAug.2002失去信任的残疾亚当———张爱玲在小说中对男性形象的颠覆余 平(川北教育学院,四川遂宁629000) 收稿日期:2002-05-30 作者简介:余平,川北教育学院教师。
摘要:20世纪初中国文学中的女性主体意识已初步觉醒。
张爱玲作为独具特色的女性主义作家,她的女性意识主要表现在对男性形象的颠覆上。
在否定男性形象的同时,她又对女性形象进行了独特的反思与批判,透露出一种强烈的自救意识。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主体意识;颠覆;批判意识;自救意识中图分类号:I20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2)ZK 3—0005—05 正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女性的主体意识在中国文化的承传中已经失落了几千年,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更是缺席了几千年。
20世纪以来,丁玲、萧红、张爱玲、苏青等正力图使缺失的女性主体意识得到回归,女性文学在浩瀚的历史中也想寻到她应有的位置。
在众多中国现代女性主义作家中,张爱玲的女性主体意识可以说是自然流露在她的文本之中,她在创作上的“母题”始终是深切的女性关怀。
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女性视点,用以解构文学中的男性主义文化中心的存在和整个男权社会的不公正的权力。
(一)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个创作活动,较早涉及到女性题材、女性写作的有著名的女作家冰心、丁玲等人。
但冰心的贤妻良母式的创作模式与丁玲、张爱玲等人有很大的区别。
冰心还是主要以男性对女性的传统要求来书写女性。
在她笔下,女人更接近于上帝,她们只是用来拯救男人的工具,仅仅是母亲而不是女人。
“她们都回避着她们自己———或她们自己的舒适或自我愿意”[1](p.25),即她们的主要行为都是向男性奉献或牺牲,而“这种献祭注定她走向死亡”[1](p.25)。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旧文明背景下一个性别的整体坠落———论张爱玲小说文本中对男性形象的否定□王艳玲(吉林大学文学院,长春130021)关键词:张爱玲男性形象否定旧文明摘要: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一举颠覆了传统文化赋予男性的内涵,他们无一例外地丑陋不堪、自私、无能,男权社会给予他们的强健体魄和坚强意志在这里荡然无存。
张爱玲用一贯的冷笔调对男性的偶像地位无情地进行了颠覆和解构,使其处在一个被鞭挞、被扭曲甚至缺席的尴尬地位,从而使小说文本中一个性别整体上从完美坠落到毁灭,张爱玲借此表达了自己内心对封建旧文明的绝望和批判。
美国社会学家约翰逊说:“所谓男权社会,就是男性中心主义社会,指一个社会由男性统治,是认同男性的,以男性为中心的。
”①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男性始终是社会的核心,是力量和兴旺的象征。
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支配权。
通常在男权文化影响下的文学作品中,男性的主体地位牢不可破,男性始终是文学作品中的主角,是决定文本走向的主体。
文学舞台上,男性被塑造成力量和美的化身,上演着一幕幕或悲壮或刚烈的激动人心的英雄史诗。
男性是一切褒义词的化身,是君临女性世界的君王,女人只能对其绝对服从。
可以说,千百年来,男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至关重要,男权的审美价值标准根深蒂固地扎根在文学的土壤之中。
然而,出现在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却一举颠覆了传统文化赋予男性的内涵,他们无一例外地丑陋不堪、自私、无能。
男权社会给予他们的强健体魄和坚强意志在这里荡然无存,男性特征普遍逐渐委顿,精神生命相继死亡。
出现在张爱玲小说文本中的男性形象只不过是一具具行走在现实社会的无精神无灵魂的肉体空壳。
张爱玲用一贯的冷笔调对男性的偶像地位无情地进行了颠覆和解构,使其处在一个被鞭挞、被扭曲甚至缺席的尴尬地位,从而使小说文本中一个性别整体上从完美坠落到毁灭。
人类可以和大自然其他生物一起并存于天地间,无非是仰赖物质和精神。
精神是人类作为灵长动物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标志,而物质即人类的肉体乃是精神的承载体,精神不在,人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肉体出了问题,精神便无从依附。
然而在张爱玲的小说文本中,众多的男性形象从身体到精神全部都被作家否定得干净彻底,毫无怜惜之情,他们要么身体废残,要么精神洞空,是一群贴附在社会肌体上的寄生虫,软脊椎动物。
他们颓废淫逸、自私软弱,没有理想,没有激情。
生下来就是软骨症,天生一副残废畸形的人体。
“身上的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麻,摸上去那感觉”②,“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
”③已经彻底沦为一具没有生命的“孩尸”。
姜家三少爷姜季泽是这个家庭里唯一有男人气息的一个,身体结实,红扑大脸,然而却游手好闲,好逸恶劳,只追求个人享受,浑身透着自私和无情,抽大烟,玩女人,赌钱,几乎五毒俱全。
当对七巧施行骗术被识破后,竟毫无半点羞愧,反骂七巧是疯子。
并为了报复七巧,领七巧的儿子逛窑子,吸大烟。
也正是因为他的欺骗,使七巧再也不相信爱情,甚至丧失了爱与被爱的能力,心理变态,灵魂扭曲。
七巧的儿子长白,浑浑噩噩,没有理想和追求,缺乏道德感,只知道吃喝玩乐,是一具行尸走肉。
他“是个瘦小白皙的年轻人,背有点驼,戴着金丝眼镜,有着工细的五官,时常茫然地微笑着”④。
正值上学年纪,却不爱读书,每天无所事事,小小年纪就抽大烟,赌钱,捧女戏子,逛窑子,任凭日子如流水一样淌过,从没打算过将来和人生,就这样任由生命和时光空耗着,一点点地走向没有光的所在。
《怨女》里的姚家二爷的外在形象在张爱玲的文本中更加清晰具体,丑陋不堪:“前鸡胸后驼背,张着嘴,像有气喘病,要不然也还五官端正,苍白的长长的脸,不过人缩成一团,一张脸显得太大,眼睛倒也看不大出,眯缝着一双吊梢眼,时而眨巴眨巴向上瞄着,可以瞥见两眼空空”⑤,出门需要佣人抱着背着。
《花凋》中的郑先生在张爱玲的笔下颇具讽刺和嘲弄意味。
郑先生是个封建遗少,醉生梦死,风流成性,“长的像广告画上喝乐口福抽香烟的标准上海青年绅士,圆脸,眉目开展,嘴角向上兜着,穿上短裤子筅0812010.6就变成了吃婴儿药片的小男孩,加上两撇八字须就代表了即时进补的老太爷,胡子一白就可以权充圣诞老人……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
他是酒缸里泡着的孩尸”⑥。
显而易见,张爱玲笔下的这类男人,是旧时代封建古墓里的一具具僵尸,不合时宜,被时代的车轮远远地甩在后面,成为社会的渣滓和绊脚石。
他们虽也在现实中扮演男人应该扮演的角色,但因了身体或精神的缺席,常常变得有名无实,充其量只是虚飘飘的一个符号、一个称谓、一张遗照而已。
这些人本应该是乱世中的支撑和希望所在,但在张爱玲的文本中,却都颓废、软弱无力,靠在糟腐的封建温床上,慵懒地打着哈欠,如同肮脏的蛀虫。
精神力量的缺失,身体的废残,最终使这些男性走向作者为他们设定好的终极命运,“一级一级,通向没有光的所在。
”张爱玲笔下另一类男人与此不同,他们受过西式的教育,貌似追求自由,思想解放,实则是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好色,自私,薄情。
这一类男性因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之前述,沉重压抑稍浅,偶尔会有一点真情和生命灵光闪耀,但因生长于中西文化夹缝中,处境尴尬,无认同感和归属感,内心常处于两种文化的纠结状态。
他们穿西装,打领带,喝咖啡,外表西化,实则思想和观念依然浸泡在中国传统的旧文明旧道德的体液中,现代其外,陈腐其内。
《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是一个私生子,从小跟随母亲在英国长大,父爱缺失,脾气古怪,吃喝嫖赌样样精通。
因自身继承遗产前后所受到的待遇冰火两重天,使其认识到人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受金钱支配的,真情是虚幻的,所以更加地玩世不恭,放浪形骸,和白流苏之间更是调情大于真情。
对待情感、婚姻,他更是精打细算,绝对不能让自己吃一点亏。
“质朴的生活逼迫了他们,一对自私的人才能结合”⑦。
然而和流苏结婚后的范柳原,“再也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⑧。
可见,他的花心从来没变,倾尽所恋,到头来也不过只是一座无爱的空城。
如果说范柳原在追猎女性的过程中,还曾有真情的倏忽闪现,那么《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乔琪乔就完全呈现出了人性中自私、无情的丑陋和虚伪,他和葛薇龙的婚姻更为肮脏堕落,完全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
而他则以寄生贵妇、靠女人“弄钱”为其享乐的来源,并恬不知耻地声称自己是“招驸马的材料”。
是畸形社会里金钱关系下以女性供养自己的丑陋男人形象的代表。
这些男人外表健康,有所谓的追求和理想,是最合乎理想的现实中的人,但他们内心仓皇,驻足新旧之交,对自己,对他人,对现实环境都不能做出明晰的判断和选择,既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也不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对现实和未来都既无能又无力。
在巨大的传统习惯下最终还是使自己成为了因因相袭的旧文化链条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卒。
张爱玲冷静地剖析他们的肌体和灵魂,裸露出他们的自私和无能,否定了他们在社会上作为男人存在的价值,可谓意味深长。
张爱玲活跃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沪港文坛,此时正值西方先锋文学席卷中国文坛之际。
在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下,审父作为一种母题在先锋文学中成为作家言说不尽的普遍情结。
精神分析学认为,父亲不仅代表了一个男人在家庭血缘中的位置,而且还意味着他在社会中拥有的一切特权,这些特权对子辈造成了无法言说的压抑和痛苦。
也就是说,父亲代表着传统,是权威和力量的象征,在这种权威和力量笼罩下的子辈们感到压抑和无奈。
父亲具有了某种文化的隐喻色彩,从这一角度分析,“审父”成为摆脱桎梏的子辈们必然之举,实际上,他的深层心理动机是对现有文化秩序的不满和对抗。
先锋作家在文本中发泄着对父辈的极度不满,他们透过非理性哲学这面多棱镜折射出父辈的真实形象,发现了父亲丑陋和衰颓的生存光景,先锋作家以非常规的手法扭曲地呈现父辈们的生存本相,从人本认知的角度掀开了父亲头上神圣、温情的面纱,揭示了父辈身上“恶”的基因和对子辈的无情戕害。
中国的文化先驱们在这种外来文化的启发和观照下,敏锐地发现封建父权和整个封建文化制度的内在血缘联系,对封建父权进行了彻底而坚决的批判,进入了“审父”的文化前沿。
在觉醒之后的创作意图和张爱玲此期创作中对父亲这一男性形象的否定不期而遇,不谋而合。
张爱玲笔下的父亲,是其文本中男性形象的重头戏,张爱玲如常一样将其设置在中国家族传统的宗法制度中,在日常琐碎的叙事中,深入到父亲这个形象的细微深处,一点点地将其自私、残忍、无能、堕落、陈腐、责任感缺失的人性撕裂开,呈现出本质的真实和丑陋,从而毫不留情地将其从高不可攀的神权地位上拉下来,废弃在时代的垃圾桶内,从而完成了对男性形象的最后否定。
《花凋》中的郑先生,是一位自私冷酷、缺乏家庭责任感和男人义务感的父亲。
川嫦是他的女儿,得了肺病,需要钱买药买营养品,他无情地说:“我花钱可得花的高兴,苦着脸子花在医药上,够多冤!……做老子的一个姨太太也养不起,她吃苹果!”⑨可是,川嫦死了,他却舍得花钱给她立了一个漂亮的墓碑,碑上刻满了圣洁的天使,题着“爱女郑川嫦之墓”,表现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慈父的好心肠。
对此,张爱玲断然0822010.6地否定:“全然不是这回事。
”⑩《多少恨》中的虞老先生,自私势利,穷困落魄:“鼻子也钩了,眼睛也黄了,抖抖呵呵的袍子上罩着件旧马裤呢大衣。
”輥輯訛就是这样一个外表邋遢内心肮脏的父亲,年轻时狠心抛弃了妻女,年老落魄时却死皮赖脸地粘上了已自立的女儿,拿着女儿的钱吃喝嫖赌,甚至为了自己的生存、利益,恬不知耻地劝女儿给人做姨太太。
此外还有《茉莉香片》中残暴的父亲聂介臣,《琉璃瓦》中用女儿婚姻做利益筹码的父亲姚先生,等等,等等,在张爱玲的笔下全部都还原成了日常形态,彰显了人性的苍凉和无奈。
对父权人性丑恶的揭露,古已有之,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这样一幅画面: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
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
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
”于是遂得脱。
輥輰訛对汉高祖刘邦的刻画,司马迁冷静而不留情面,刘邦是父亲,但面对项羽的追击,竟为了自己逃命,狠心将儿女推堕车下。
这样的行为连普通人都为之不齿,更何况是一代君王!将君权的大旗从神坛上扯下,揭露了刘邦人性中自私无情的一面。
如果说司马迁处于黑暗的封建社会,自身遭遇坎坷,看透了世态炎凉、统治者人性的丑陋和残忍,和中国进步作家一样,揭露父亲形象的自私丑陋是出于政治上的自觉,那么张爱玲则是怀着冷静而不无凄恻的感情来审视和表现这一切的。
她无意对男权进行批判与声讨,她文本中对男性形象的否定只是感到了来自于其“思想中惘惘的威胁”,是对封建制度下文化的绝望和无力。
自从人类社会有文明以来,男性一直是社会权力的化身,社会是男权社会,话语是男性话语,文化是建立在男性符码之上的,东西方如此,新旧没有变更。
